David Myers 社會心理學 v8
| Site: | CLASE CHINO |
| Course: | BUSINESS BOOKS |
| Book: | David Myers 社會心理學 v8 |
| Printed by: | Guest user |
| Date: | Saturday, 29 November 2025, 3:24 AM |
Table of contents
- 社會心理學(第8版)(認識自我、群體及社會,更有效地影響他人及社會,抵制不良群體及社會影響的科學指導性書籍!)
- 目錄
- 中譯版序言
- 前言
- 作者簡介
- 第1章 社會心理學導論
- 第一編 社會思維
- 第2章 社會中的自我
- 第3章 社會信念與判斷
- 第4章 行為和態度
- 第二編 社會影響
- 第5章 基因、文化和性別
- 第6章 從眾
- 第7章 說服
- 第8章 群體影響
- 第三編 社會關係
- 第9章 偏見:不喜歡他人
- 第10章 攻擊行為:傷害他人
- 第11章 吸引和親密:喜歡他人和愛他人
- 第12章 利他:幫助他人
- 第13章 衝突與和解
- 第四編 應用社會心理學
- 第14章 社會心理學在臨床領域中的應用
- 第15章 社會心理學在司法領域中的應用
- 第16章 社會心理學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 專業術語表
- 參考文獻

中譯版序言
為什麼常常有一些最精明能幹的企業家會犯下極其簡單愚蠢的決策錯誤?為什麼有些人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他人? 為什麼有人遇難時,圍觀的人越多,幫忙的人卻越少?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社會心理學所要探討的基本課題。因此,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就是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換句話 說,社會心理學是研究我們如何創造和改變環境,環境又如何反過來塑造我們的性格、影響我們的行為的科學。
不瞭解社會心理學的人往往會產生誤解,認為它就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學科。但確切來講,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是我們每 個人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不可否認,所有的社會問題,例如權力鬥爭、政治腐敗、經濟蕭條、惡性競爭等等都包含著社會心理因素,但社會心理學更關注每個人在這種社 會環境下怎樣思考、感受和行動。
還有一種誤解是把社會心理學理解為一門應用學科。而實際上,它也是一門基礎學科。心理學家們遵循實證研究證偽 的原則,不斷排除各種可能的假設,同時,採用大量的科學研究方法(如實驗室觀察與模擬,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等),對思維、歸因、決策、成見、從眾、團體動力、 友誼等基本心理過程進行研究。
我從1994年開始相繼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和加州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發現了一本很好的教科書,就是這本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在美國,如果一本心理學教科書能夠再版3次以上的話,這本書就堪稱經典教材了。戴維·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在過去的20年中連續再 版8次,有700多所大學或學院的心理學系採用這本書作為社會心理學課程的主講教材,由此我們便不難想像這本教材是如何的出類拔萃了。
戴維·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之所以能在同類書籍中脫穎而出、獨佔鰲頭,是由該書的許多特點決定的。首先,這 本書討論的研究對象是我們很多人都感興趣的問題,這就向人們昭示了社會心理學一定是一門涉及面很寬泛的學科。在具體敘述中,作者不僅觀照的問題廣,對每一問題 的分析還能兼顧到不同的意見。這本教科書是少數幾本真正把各個學科的相關論述與社會心理科學的有關理論和發現結合起來的論著,即使是沒有心理學背景的讀者也會 發現這本書的內容和描述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社會心理學》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其對科學方法的堅持和表述思維的嚴謹性,從而將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的優勢 發揮得淋漓盡致。比起其他由社會學家和科普專家所著的同類書籍,這本書的材料大都建立在實驗社會心理學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它的每一個觀點都有很嚴格的證據支 持。這種崇尚實證、言而有據的表達風格是本書在美國心理學的教學人員中備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書與其他教科書的另一個有別之處,就是它豐富多彩的插圖和插話。戴維·邁爾斯的這本教材已經出到了第8版, 大家公認版版優秀,越出越精。在對插圖和插話這些細微處的精心安排上,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編寫過程中所下的磨劍20年、滴水穿石的工夫,還可以感受到一位老學 者對自己專業的滿腔熱愛和專注。2005年年初,他和妻子還將其稿費中的100萬美元捐贈給美國心理協會(APS),以建立專門用於心理學教學和普及工作的基 金會。邁爾斯本人也曾榮獲著名的奧爾波特獎,以表彰他在社會心理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當中的突出貢獻。他獲此殊榮,應該說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正所謂實至而名歸。
我在美國的大學教授社會心理學,使用的一直就是戴維·邁爾斯的這本教材。隨著版本的更新,我能不斷領略作者修 改增訂的精妙所在,並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該書將基礎研究與實踐應用完美結合的風格。戴維·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已經成為這方面教材的一個典範,是美國心理學 教科書市場上評價同類教材的一個標尺,因此我很高興向國內的同行推薦這本書。我相信我們的讀者拿到這本書後,也會和我一樣捧讀再三,不忍釋卷。
彭凱平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教授
前言
當我最初應邀撰寫本書時,我立刻想到此書應該具有堅實的科學性和溫暖的人性,具有事實精確性和智力啟發性。它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揭示社會心理學——提供重要社會現象的實時概要,也包括科學家是怎樣發現和解釋這些現象的。它應該是相當全面的,但也會激發學生的思考——促使他們去探索,去分析,並把這些規則同日常生活聯繫起來。
如何選擇材料來對一個學科做相當全面的介紹——既要足夠長以便容納豐富的敘述,也要足夠清晰以使要點不至於被淹沒其中。我一直努力使我所呈現的理論和研究結果既不會對本科生來說過於深奧,也不會和單純的社會學或心理學課程重複。相反我注重那些能使社會心理學融合到自由藝術的知識傳統中的材料。通過傳授名著、哲學和科學,自由主義的教育理念拓展了我們的思維和覺知,並把我們從現存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社會心理學能夠達到這些目標。很多社會心理學的本科生並不主修心理學,實際上所有人都將從事其他職業。這本書把重點放在和人類有關的重要話題上,這樣既可以為心理學專業的學生提供基本知識,同時也能激發所有學生的興趣,並對他們有所裨益。
社會心理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盛宴。在整個有記載的歷史中,對人類社會行為的科學研究僅有100多年,也就是剛過去的那個世紀。考慮到我們起步較晚,我們的研究成果還是喜人的。我們已經在解釋信念與錯覺、愛與恨、從眾和獨立這些心理現象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知識。
人類行為的很多方面仍然是個謎,但社會心理學能就一些人們比較感興趣的問題做出部分解答。
當人們第一次採取新的態度時,他們的行為會有所改變嗎?如果有,我們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說服他們?
是什麼導致了人們有時彼此傷害,有時又互相幫助?
是什麼引發了社會衝突,如何才能把握緊的拳頭變成援助的雙手?
我的使命在前文中已經提到,就是通過回答這些問題,拓展我們對自身的理解,並使我們對那些作用於我們身上的社會力量更加敏感。
本書結構
本書開篇以單獨的一章介紹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這一章隨後告誡學生如何才能使研究結果顯而易見(一旦你瞭解了它們),以及社會心理學家如何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滲透到學科領域當中。另外,本書新增加了一個部分“社會心理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它介紹了一些令人興奮的話題:我們如何構築社會現實、社會直覺、社會影響、個人態度和性格傾向,生理行為以及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這樣安排章節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在學習後面的章節之前有一個充分的知識準備。
本書在隨後的部分將圍繞社會心理學的定義展開:社會心理學是對人們的思維方式(第一編)、社會影響(第二編)、人際關係(第三編)以及社會心理學原理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第四編)的科學研究。
第一編 探討社會思維——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它可以評價我們的印象、直覺和解釋的準確性。
第二編 探討社會影響。通過理解態度的文化因素和學習從眾、說服以及群體影響的本質,我們能更好地認識到作用在我們身上的微妙的社會力量。
第三編 分析消極和積極的社會關係的態度和行為表現:從偏見到攻擊,從吸引到互助。這一部分還將同時探討衝突與和解的動力學。
第四編 分析如何將我們在前面章節中學習到的概念應用到社會生活中。社會心理學的應用貫穿於全書的各個章節,但主要集中在第14章(社會心理學在臨床領域中的應用),第15章(社會心理學在司法領域中的應用),以及第16章(社會心理學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本版和以前的版本一樣強調多元文化的觀點,這一點可以在第6章的對待文化的影響中看到,這種強調多元文化的觀點貫穿於全書,包括了各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所有作者都是其所處文化的產物,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我通過閱讀全球的社會心理學著作,與各個國家的研究者通信往來,到國外旅遊等方式,努力向全世界的讀者展現一個社會心理學的世界。本書的重點仍然是以縝密的實驗研究揭示出社會思維、社會影響和社會關係的基本原理。當然也希望能拓展我們對整個人類的覺知,我想以跨民族的角度來闡述這些原理。
為了便於讀者閱讀,我把每一章分成三到四節。每章以預覽開頭,以概要結尾,以便於讀者掌握各章節的結構及核心概念。
我一直堅信梭羅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用通俗的語言輕鬆而自然地加以表達”,所以我一直努力構思,以期出版一本儘可能有吸引力的並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
第8版特色
第8版提供了
當前的研究 :500多處新的引用和舉例以及很多新的數據圖表對本書進行了徹底的更新,使其能一直保持前沿性。
研究背後的故事 :這一專題使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瞭解研究者,能更好地瞭解當代的、前沿的和傳統研究背後的思想火花。
聚焦 :這一專欄用於探討當前發生的事件和社會心理學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心理學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聯繫社會 :位於每章的最後,這部分把整章的內容連貫起來並鼓勵讀者進行批判性思考。
個人後記 :每章都有一個對本章某個重要話題的闡述,隨後會提出“你的觀點如何?”以此來激發讀者把社會心理學的思想應用到其日常生活中。
致謝
雖然本書的封面只寫了一個人的名字,但事實上它卻是由眾多學者組成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雖然他們任何人都無須為我所寫的東西負責,可能也沒人會完全同意我說的每句話,但他們的建議使得這本書更加完善。
尤其要感謝的是滑鐵盧大學的Steven Spencer對第9章(偏見)所做的貢獻。他以自己在刻板和偏見方面廣博的知識對該章內容做了更新和修訂。
這個版本還保留了顧問和評論者對前7版提出的改進意見。因此我對以下尊敬的同事表示感謝:
Mike Aamodt,Radord University
Robert Arkin,Ohio State University
Susan Beers,Sweet Briar College
George Bishop,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alen V. Bodenhause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artin Bolt,Calvin College
Amy Bradfield,Iowa State University
Dorothea Braginsky,Fairfield University
Fred B. Bryant,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Shawn Meghan Burn,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David Buss,University of Texas
Thomas Cafferty,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Jerome M. Chertkoff,Indiana University
Russell Clark,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iana I. Cordova,Yale University
Karen A. Couture,New Hampshire College
Cynthia Crown,Xavier University
Jack Croxt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Fredonia
Anthony Doob,University of Toronto
Philip Finney,Southea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Carie Forden,Clarion University
Kenneth Foster,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ennis Fox,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Springfield
Carrie B. Fried,Winona State University
William Froming,Pacific Graduate School of Psychology
Stephen Fugita,Santa Clara University
David A. Gershaw,Arizona Western College
Mary Alice Gordon,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Ranald Hansen,Oakland University
Allen Hart,Amherst College
Elaine Hatfield,University of Hawaii
James L. Hilton,University of Michigan
Bert Hodges,Gordon College
William Icke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Marita Inglehart,University of Michigan
Chester Insko,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Jonathan Iuzzini,Texas A&M University
Meighan Johnson,Shorter College
Edward Jones,Princeton University [deceased]
Judi Jones,Georgia Southern College
Martin Kaplan,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Timothy J. Kasser,Knox College
Janice Kelly,Purdue University
Douglas Kenrick,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orbert Kerr,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Charles Kiesler,University of Missouri
Marjorie Krebs,Gannon University
Travis Langley,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
Helen E. Linkey,Marshall University
Diane Martichuski,University of Colorado
John W. McHoskey,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Daniel N. McIntosh,University of Denver
Annie McManus,Parkland College
David McMillen,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Robert Millard,Vassar College
Arthur Miller,Miami University
Teru Morton,Vanderbilt University
Todd D. Nelson,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K. Paul Nesselroade,Jr.,Simpson College
Darren Newts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Stuart Oskamp,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Chris O'Sullivan,Bucknell University
Ellen E. Pastorino,Valencia Community College
Sandra Sims Patterson,Spelman College
Paul Paulu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Scott Plous,Wesleyan University
Nicholas Reuterman,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Edwardsville
Robert D. Ridge,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Nicole Schnopp-Wyatt,Pikeville College
Wesley Schultz,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San Marcos
Vann Scott,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
Linda Silk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Lowell
Royce Singleton,Jr.,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Stephen Slane,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Christine M. Smith,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Richard A. Smith,University of Kentucky
Mark Snyd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heldon Solomon,Skidmore College
Matthew Spackman,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Garold Stasser,Miami University
Charles Stangor,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Homer Stavely,Keene State College
JoNell Strough,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Eric Sykes,Indiana University Kokomo
Elizabeth Tanke,University of Santa Clara
William Titus,Arkansas Tech University
Tom Tyler,New York University
Rhoda Unger,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Billy Van Jones,Abilene Christian College
Mary Stewart Van Leeuwen,Eastern College
Ann L. Weber,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Asheville
Daniel M. Wegner,Harvard University
Gary Wells,Iowa State University
Bernard Whitley,Ball State University
Kipling Williams,Purdue University
Midge Wilson,DePaul University
我在創作第8版之前給一些教師以電子郵件的形式發了一份調查問卷,他們對第7版的反饋意見使我受益匪淺。在此我也要對下面這些第7版的評論者表示誠摯的謝意,他們真誠的建議幫助我完成了這個新版本:
Charles Daniel Batson,University of Kansas
Jonathon D. Brow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vid Dunning,Cornell University
Alice H. Eagly,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eandre Fabrigar,Queen's University
Tom Gilovich,Cornell University
Tim Kasser,Knox College
Norbert L. Kerr,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C.R. Snyder,University of Kansas
Mike Wessells,Randolph-Macon College
最後,還有一些教師、學者對某些新章節進行了評論,使我儘可能地少出錯誤甚至不出錯誤,並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和鼓勵):
Steve Baumgardner,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Timothy C. Brock,Ohio State University
Deana Julka,University of Portland
Joachim Krueger,Brown University
Maurice J. Levesque,Elon University
Terry F. Pettijohn,Mercyhurst College
Carolyn Whitney,Saint Michael's University
我對這些同事表示感謝。
密歇根的霍普學院為這些版本的成功創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這裡的人文環境使得創作《社會心理學》變成了一種樂趣。凱西·亞當姆斯基(Kathy Adamski)再次給予我強有力的支持並做了祕書工作。布蘭迪·賽勒(Brandi Siler)和斯泰西·佐克(Stacey Zokoe)負責取送和影印文章,正是這些文章使這一最新版本得以更新。凱瑟琳·布朗森(Kathryn Brownson)做資料調研,編輯整理書稿,控制論文流程,校對紙樣,設計美工,並做了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總之,她促成了此書的產生面世。
如果沒有McGraw-Hill出版公司尼爾森·布萊科(Nelson Black)的鼓勵,我可能永遠都寫不成此書。艾利森·彌爾斯卡特(Alison Meersschaert)對第一版本的格式給予了指導和鼓勵。高級策劃編輯麗貝卡·霍普(Rebecca Hope)和邁克·休格曼(Mike Sugarman),以及開發和新媒體部(Development and New Media)的主任朱迪思·克羅姆(Judith Kromm)都參與構想並製作了第8版教材和教學輔助材料。編輯安·格林博格(Ann Greenberge)懷著巨大的熱情和創造力,和我緊密合作,共同構思以全新的圖表方式來呈現研究結果和概念。編輯協調人凱特·茹斯里奧(Kate Russillo)找來了評論家,製作了補充材料,並設計組織了書後的術語表。高級項目經理瑞布卡·羅德布盧克(Rebecca Nordbrock)對手稿轉化為成書的加工過程進行了耐心的指導,其間編輯勞瑞·麥克吉(Laurie McGee)也做了一些精細調整的輔助工作。
得知很多人說本書的補充材料使其教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此我還要向馬丁·博爾特(Martin Bolt,Calvin College)表示感謝。他不僅撰寫了學習指南,還以眾多現成的示範活動拓展了廣泛的教學資源。
喬恩·米勒(Jon Mueller,North Central College)作為新教學資源的作者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這使我們感到十分榮幸。他將不斷積累的資源放到專門為社會心理學教學提供的在線資源中,並每月用目錄服務器(Listserv)向社會心理學教員提供資源(參見jonathan.mueller.faculty.noctrl.edu/crow)。
新加入我們隊伍的還有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學(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的克里斯廷·安西斯(Kristine Anthis)。我同樣要向她表示敬意,她為我們廣泛的考試資源進行了精心的專業製作、擴充並更新。我還要感謝佛羅里達亞特蘭大大學的瑪莎·休伯茨(Martha Hubertz),在線學習中供學生練習用的題目都是由他設計的。同時也要感謝馬裡恩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特里·佩蒂約翰(Terry Pettijohn)為我們在線學習中心設計的互動“情境”。
我對所有支持我的人深表感激。正是和這樣一些人一起工作才使得該書的創作成為一種刺激而令人愉悅的經歷。
戴維·邁爾斯
david.myers.org
作者簡介
自從獲得愛荷華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戴維·邁爾斯就在密歇根的霍普學院工作,成為那裡的John Dirk Werkman心理學教授,並且開設了多門社會心理學的課程。霍普學院的學生邀請他在畢業典禮上發言並評選他為“最傑出的教授”。
邁爾斯曾在30多種科學書籍和期刊上發表過多篇論文,包括《科學》、《美國科學家》、《心理科學》和《美國心理學家》等。除了學術著作和教科書,同時他還致力於把心理科學介紹給廣大民眾。他在許多雜誌上發表過科普類文章,如《今日教育》和《科學美國人》。
他撰寫的《心理學》(本書由著名心理學家黃希庭教授組織翻譯並審校,將於2006年出版,敬請期待)是當今最暢銷的心理學導論性教材,600多萬學生在用它來學習心理學。同樣,這本《社會心理學》在過去的10年中佔了將近30%的市場份額(社會心理學類書籍)。正如他在《心理學》第7版前言中所寫的,“我希望以一種充滿熱情的、富有個性的方式來講述心理學,而不僅僅用一種嚴謹的科學方式 ”。這應該就是他的教材如此受歡迎的祕訣吧。
戴維·邁爾斯還是城市人際關係委員會的主席,幫助創建了一個快速發展的協助中心,以扶助貧困家庭,同時他還去過數以百計的大學和社區做演講。憑藉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他還寫了有關聽力喪失的一些文章和一本書(《無聲的世界》),而且他還倡導在美國進行一場助聽技術革命(hearingloop.org)。
他常年騎自行車上下班,每天都去打籃球。邁爾斯夫婦共同育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第1章
社會心理學導論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問題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觀點
社會心理學與相關學科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與人格心理學
解釋的不同層面
社會心理學與人類價值觀
價值觀直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價值觀間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我早就知道了:社會心理學不過是常識而已嗎
研究方法:我們如何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
假設的形成與驗證
相關研究:探尋自然關係
實驗研究:探尋因果關係
從實驗室推廣至生活
個人後記: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們的生活由無數不可見的細線串連在一起。”
——赫爾曼·梅爾維爾
很 久以前有一個人,他的第二個妻子非常愛慕虛榮而且還很自私。這個女人有兩個同樣愛慕虛榮且自私的女兒。但這個男人的親生女兒卻是個可愛又善良的姑娘。我們都知道,她就是灰姑娘。而灰姑娘從一開始就知道,她最好是照著吩咐做,默默忍受責罵,少去招惹她那兩個虛榮自負的姐姐。
到後來,多虧仙女的幫助,灰姑娘才得以脫離困境,前去參加一個隆重的舞會,恰恰是在舞會上,灰姑娘引起了英俊王子的注意。再後來,那個墜入愛河的王子在灰姑娘破破爛爛的房間裡見到了這個非常不起眼的心上人時,竟然未能馬上認出她。
不可思議吧?這個童話故事讓我們不得不承認情境 所具有的魔力。當盛氣凌人的繼母在場時,溫順而不起眼的灰姑娘在這個情境中扮演的角色,與王子在舞會上遇到的美麗出眾的灰姑娘可謂判若兩人。家裡的灰姑娘戰戰兢兢,而舞會上的灰姑娘神采奕奕,舉手投足、一顰一笑自然大方。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
讓法國哲學家兼小說家薩特(Jean-Paul Sartre,1946)接受灰姑娘故事中的這個假定應該不成問題。他相信,我們人類“首先是情境中的生物”,“因為情境塑造了我們,決定我們未來的諸多可能性,我們便不可能獨立於它而存在。”(pp.59-60,轉述)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是一門研究我們周圍情境的力量的科學,尤其關注我們是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的。更確切地說,社會心理學是一門就人們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響他人,又如何互相關聯的種種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學科 。它通過提出那些激起我們所有人濃厚興趣的問題來達到這個目的(圖1-1)。

圖1-1 社會心理學是……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問題
我們的社交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之中 ?就像在後面的章節中會看到的那樣,我們的社會行為並不僅僅取決於客觀情境,還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其進行主觀建構。婚姻幸福的伴侶會把對方刻薄的言辭(“你就不能把它放回原來的地方嗎?”)歸結於某些外部因素(“他今天一定過得不怎麼樣!”)。婚姻不幸的伴侶則會把同樣的言辭歸咎於對方的品性問題(“他總是那麼惡狠狠的!”),這樣一來就不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僅如此,由於一方預期可能會聽到對方充滿挑釁的言語,他們很可能自己也變得暴躁起來,這樣便激起了他們所預期的對方的憤怒。
就像我們還會看到的那樣,人們總是預期教授的孩子肯定很聰明;富有魅力的人總是很熱情;競爭對手總是不斷製造麻煩,這些預期十有八九就會變成現實。社交信念同樣也可以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別人對我們的偏見或許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的行為。舉例來說,或許有人把你的靦腆錯認為不友善,故而怠慢冷落了你;這樣的舉動又惹得你對此人橫加指摘;這樣一來,你的言行便最終成為證實你確實“懷有敵意”的證據。
如果要求你聽命行事,你會以殘忍的方式行動嗎 ?納粹德國究竟是如何構想並最終實施了那場對600萬猶太人不可思議的大屠殺?這些惡行可以部分歸咎於只是千萬人奉命行事所致。他們把囚徒塞上火車,趕至擁擠的淋浴室,再用毒氣毒死。人們怎麼會採取這樣可怖的行徑?這些人還正常嗎?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74)想一探究竟。因此,他創設了這樣一種情境,在該情境中,要求實驗者對一個學習一系列詞語有困難的人不斷施加高壓電擊。就像我們將在第6章中看到的那樣,實驗結果令人頗為不安:將近2/3的實驗者完全服從了指令。
助人?還是助己 ?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一條街上,一袋袋現鈔從運鈔車上滾下來,沿路撒下了200萬美元。有些車主停下來幫著撿回了10萬美元。從沒有返還的數額來看,更多的人停下來幫了自己一把。隨後當在舊金山和多倫多發生了類似的意外時,結局是類似的:大多數錢進了路人的腰包(Bowen,1988)。在其他的事件中同樣發現人們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佔為己有——在1969年蒙特利爾的警察罷工期間;在1992年洛杉磯警察袖手旁觀的騷亂中;在2003年的巴格達,在那段介於薩達姆·侯賽因統治的終結與進駐、部署新軍警之間的無警狀態中。每一次,數以千計的“強盜們”都會進駐大大小小的建築物,高高興興地把錢財物品洗劫一空。
究竟什麼情境會讓人們變得樂於助人或貪婪?是否某些文化背景——或許是小城鎮和小村落——能更好地培養人類樂於助人的品質?
這些問題被一條共同的細線串連起來:它們都是關於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影響彼此的。而這同樣也是社會心理學關注的問題。社會心理學家所研究的便是態度與信念,從眾與獨立,愛與恨。
社會心理學仍舊是一門新興的學科。我們不斷提醒人們這一點,部分也是為自己對這門學科的一些問題還無法給予完整的回答尋找託詞。但它的確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第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不過是在80年前才被公之於眾(1924)。直到20世紀30年代,社會心理學才有了現在的雛形。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心理學家在研究說服與士兵士氣之間關係方面的卓越貢獻,社會心理學才開始成為像現在這樣一門生機勃勃的學科。
社會心理學中的重要觀點
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課題是什麼——它包羅萬象的籮筐裡究竟都裝了些什麼?這一學科的諸多領域,數以萬計的研究結果,數以千計的研究者得到的結論,數以百計的理論家提出的真知灼見都可以被濃縮為幾個核心觀點。生物學為我們提供了諸如自然選擇和進化論這樣的原則,社會學給我們構築了諸如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這樣的概念。音樂則賦予我們諸如節奏、旋律以及和聲這樣的理念。
在“社會心理學的重要觀點是什麼”的列表上究竟有些什麼?當你早已經遺忘了絕大部分的細節內容時,什麼主題,或是什麼樣的基本原則還值得你去記憶?我這張短短的“我們永遠不該遺忘的重要觀點”列表上包括下面這些內容,而我們會在以後章節中對它們逐一解讀(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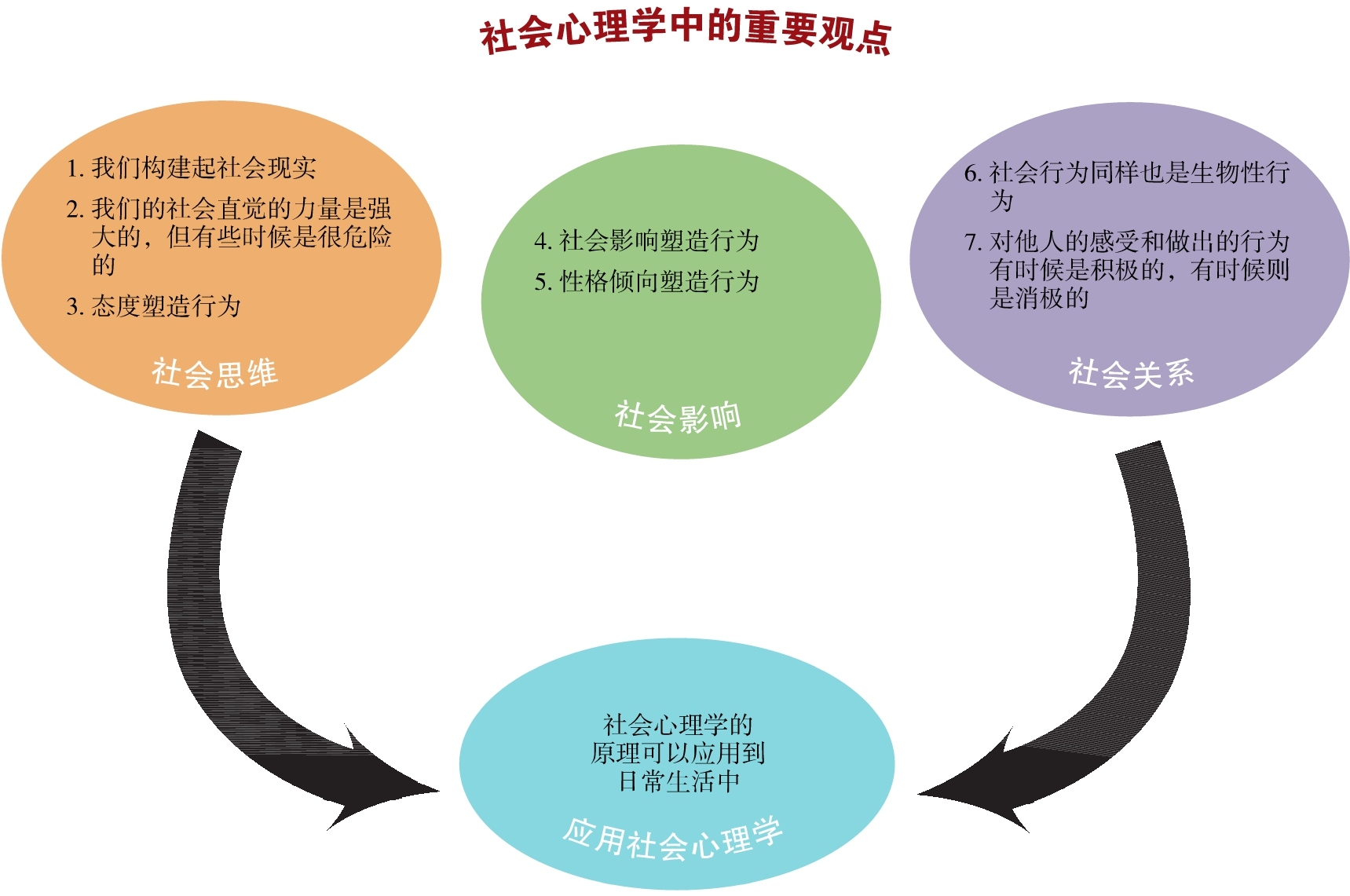
圖1-2 社會心理學中的一些重要觀點
我們構建起社會現實
我們人類總是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衝動,想要解釋行為,對其歸因,以使其變得次序井然,具有可預見性,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你我對於類似的情境卻可能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反應,這是因為我們的想法 不同。我們對朋友的責難做何反應,取決於我們對其所做的解釋,取決於我們是把它歸咎於朋友的敵意行為,還是歸結於他糟糕的心情。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們都是天生的科學家。我們解釋著他人的行為,通常足夠快也足夠準確,以適應我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當他人的行為具有一致性而且與眾不同時,我們會把其行為歸因於他們的人格。例如,如果你發現一個人說話總是對人冷嘲熱諷,你可能就會推斷此人秉性不良,然後便設法儘量避免與他的接觸。
我們對自己的信念也同樣重要。我們是否對自己的前途抱有樂觀的態度?我們是否認為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我們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還是矮人一頭?我們如何構建這個世界、如何構建我們自己是極其重要的。
我們的社會直覺的力量是強大的,但有些時候是很危險的
我們的直覺影響我們的恐懼心理(飛行是否危險?)、印象(我能否信任他?)以及人際關係(她是否喜歡我?)。直覺會影響危機時刻中的總統,牌桌上的賭徒,裁定罪行的陪審團和評估應聘者的人事主管。這樣的直覺隨處可見。
事實上,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揭示了一個令人驚歎的無意識心靈——一個由直覺在幕後操縱著的心靈——這是一個弗洛伊德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的心靈。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之前,思維不是在舞臺上進行的,而是在臺下進行的,在我們目光所不及的地方。正像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有關“自動加工過程”,“內隱記憶”,“啟發式思維”,“即時特徵推論”的研究,即時情緒和非言語交流都體現了我們的直覺能力。思維、記憶和態度都是同時在兩個水平上運行的:一個是有意識和有意圖的;另一個是無意識和自動的。今天的學者把它稱為“雙重加工”。我們的所知比我們知道自己所知的還要多。
所以,直覺的力量是強大的。在我們的意識之外,思維在幕後工作,但其結果卻時不時顯示在屏幕上。但直覺有時也是危險的。舉例來說:在現實生活中駕駛汽車時,我們判斷事物發生的可能性取決於進入我們腦海中例子的可利用程度,這一過程大多數時候是自動完成的。特別是在“9·11”之後,我們總能很輕易想起飛機失事的鏡頭。如此一來,許多人對於飛行的恐懼遠遠超過了駕駛汽車的恐懼,而且許多人會為避免飛行的危險而長距離地駕車。事實上,相比駕車出行而言,飛行的安全程度是前者的3倍(每公里)。
我們對自己的直覺甚至也時常出錯。在直覺上我們太過相信自己的記憶力。我們會錯誤地解讀自己的心理;在實驗中,我們拒絕承認受到某些事物的影響,但實際上它們確實影響了我們。我們錯誤地預測自己的感覺——如果我們現在失業了或失戀了,一年之後我們的感覺會有多麼糟糕;如果我們現在贏得了國家彩票,一年之後我們的感覺會有多麼良好。我們還常常錯估自己的未來——在買衣服時,年近中年的人仍然會買緊身裝(“我估計會瘦幾磅”);很少有人會更現實地說:“我最好還是買些寬鬆點的,因為我這個年齡的人體重傾向往上走。”
因此,我們的社會直覺不僅因其難以言喻的影響力,也因其棘手的危險性而值得引起我們注意。我們的生活既可能得益於隱祕的直覺思維,也可能會為其可預計的錯誤所困擾。社會心理學家在瞭解直覺思維益處的同時,也不忘警告我們它可能會帶來的危害,旨在完善我們的思維方式。在多數情境中,“快捷省力”的速食型判斷方式足以適應我們的需要。但在另一些情境中,當準確性變得很重要時——正如當我們需要適時地表現出恐懼,合理使用我們的資源時——我們最好用批判性的思維來抑制直覺衝動。
社會影響塑造行為
正如亞里士多德很早就觀察到的那樣,我們是社會的動物。我們所說所想均學自他人。我們渴望彼此之間建立關聯,渴望歸屬感,渴望獲得他人良好的評價。馬蒂亞斯·梅爾和詹姆斯·彭尼貝克(Mehl & Pennebaker,2003)對得克薩斯大學學生的社會行為做了量化研究,他們讓學生帶上迷你卡帶錄音機和麥克風,在非睡眠時間裡,由電腦控制的錄音機每隔12分鐘錄音30秒。儘管研究的時間段只限制在非週末的時間(包括上課時間),研究結果發現幾乎30%的時間是花在交談上。可以說關係對人類非常重要。
作為社會性動物,我們會對周圍環境做出反應。有些時候,某個社會情境所具有的影響力會引發我們做出背離自己態度的舉動。事實上,強有力的惡意情境有時會壓倒善意,使得人們附和謬誤,屈從殘暴。在納粹的淫威之下,許多看上去正直的人們變成了大屠殺的工具。另外一些情境則可能會引發高尚的行為和極大的熱情。在“9·11”災難之後,捐贈的食品和衣物,以及來自熱心志願者的服務紛紛湧向了紐約。
2003年人們對伊拉克戰爭態度的巨大差異也明顯反映出情境所具有的力量。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和以色列人極力贊成對伊宣戰。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當中,反對戰爭的佔絕對優勢。如果告訴我你生活在哪裡,那麼我會對你對戰爭的態度做出一個合理的猜測(如果告訴我你的受教育水平和你所接觸的媒體,那麼我對你的對戰爭態度的猜測會更有信心)。無論歷史最終對這場戰爭作出何種評價,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們所處的情境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的文化有助於定義我們的情境。我們對機敏、坦誠和著裝的標準隨著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你把女性美定義為苗條或是豐滿同樣取決於你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哪個地方,生活在哪個年代。你把社會公正定義為平等(所有人的所得是相同的)或是公平(多勞多得),同樣取決於你的社會意識形態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所影響。你是侃侃而談還是沉默寡言,不修邊幅還是一板一眼,部分源於你的文化或種族。你是更關注自己——個人的需要、願望和道德——還是更關注你的家庭、部族和公共團體,取決於你在多大程度上是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產物。的確,外在的社會影響力塑造著我們的態度和行為。
個人態度和性格傾向塑造行為
內在的影響力同樣也很重要。我們並非是被動的牆頭草,只能隨社會上吹的東南西北風擺動。內在態度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的政治態度左右我們的投票行為。我們對吸菸的態度會影響自己屈從同伴壓力而吸菸的可能性。我們對弱勢群體的態度會影響我們對該群體的支持程度(我們將會看到,態度同樣依附於行為,它可能使我們對那些投入滿腔熱血或備受折磨的事物更為堅信)。
性格傾向同樣也會影響行為。面對同樣的情境,不同的人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當從數十年的政治監禁中重獲自由時,有些人滿腹怨恨並尋求復仇,而也有些人,就如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一笑泯恩仇,轉而站出來幫助國家統一。
當我們感覺自己處處受制於世俗的種種壓力時,或許我們可以選擇多種不同的方式來重獲自由。那些少數群體有時甚至會反對或偏離主流。作為社會個體,我們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同樣也是社會的創造者。待別人多一份溫情,他們便也會顯得更可親可愛。至少我們的世界建立在情境與人的交互作用中。
社會行為同樣也是生物性行為
21世紀初期的社會心理學正在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到社會行為的生物基礎上。儘管如何看待情境十分重要,但在此之下,我們的種種想法卻不免隱含生物性的智慧。任何一個上過心理學入門課程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先天與後天共同作用的產物。就像一塊土地的大小取決於它的長度與寬度一樣,生物性與生活經驗造就了我們。進化論心理學家 提醒我們(見第5章),我們從遺傳得來的天性預先就已經設定,這使我們會做出那些有助於我們祖先繁衍生息的行為。我們祖先的某些特徵使得他們的血脈得以延續(其後代無疑也保留了同樣的特徵),而我們正遺傳了他們的基因。這樣一來,進化論心理學家所追問的便是,在求偶與交配,憎惡與傷害,關愛與分享中,自然選擇又是如何為我們的行為與反應寫下了腳本。自然同樣賦予了我們學習和適應的巨大能力。相對於社會環境而言,我們是敏感且反應靈敏的。
如果每一個心理反應(每一縷思緒,每一種感情)都同時伴有一個生理反應,那麼我們就可以探究社會行為背後的神經生物基礎。大腦的哪些區域可以使我們體驗到愛與憎,友善與暴力,知覺和信念?大腦、心靈和行為是如何共同作用成為一個相互協調的工作系統?大腦反應的時間進程怎樣揭示我們加工信息的過程?這些正是“社會認知神經科學”所關注的問題(Ochsner & Lieberman,2001)。
社會神經學家 並不寄希望於把諸如幫助與傷害這樣複雜的社會行為拆解成簡單的神經或分子水平。但要了解愛與恨,我們必須考慮皮下(生物的)與皮間(社會的)的影響。應激激素影響我們的感受與行動,社會排斥會令我們的血壓升高,而社會支持卻會增強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統。心與身是統一體。我們是生物、心理與社會的產物。
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可以應用到日常生活和其他學科領域中
社會心理學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包括你的信念,你的態度,你的人際關係。如此說來,它便具有了闡釋你生活的潛力,讓那些指引你所思所想的微妙力量暴露在眼前。你還會看到,它會給你提供許多理念,而它們會讓你知道如何能夠更好地瞭解自己,如何贏得朋友,如何影響他人,如何化干戈為玉帛。
學者們同樣把從社會心理學中得到的真知灼見應用到其他的學科領域。社會思維、社會影響和社會關係的原理對人類的健康福利,對司法程序和法庭上的司法決策,對鼓勵那些能夠引發人類適應未來社會環境的行為也有諸多可借鑑之處。
但是,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其他領域有何區別?社會心理學家是否會受自己價值觀的影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與策略是怎樣的,我們又該如何把它們應用到日常生活中?這些將是本章所關注的問題。
社會心理學與相關學科
社會心理學家對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以及人們之間的關係具有濃厚的興趣。而社會學家與人格心理學家也不例外。社會心理學與它們相比,區別又在何處?社會心理學家從進化生物學與神經科學的“蛛絲馬跡”裡又會獲得什麼啟示?
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對人類在團體中表現出的各種行為具有同樣的興趣。多數社會學家研究團體 ——從小團體到大團體(社會與其發展趨勢);而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的是個體 ——個體在某個特定時間對他人的看法,個體之間的互相影響及其關係。這些研究既包括團體對個體的影響,也包括個體對團體的影響。
舉幾個例子:在親密關係的研究中,社會學家可能會關注婚姻關係、離婚以及同居比例;而社會心理學家感興趣的可能是一個個體如何被另一個個體吸引。社會學家可能會調查中產階層與低收入階層在種族觀念上的差別;而社會心理學家則會研究種族觀念如何在個體中得以發展。
儘管社會學家與社會心理學家會運用一些相同的研究方法,但社會心理學家更多依賴於可對某種因素進行操縱的實驗方法,例如有無同伴影響這個因素,以期檢驗某種因素所起的作用。而社會學家所研究的因素,諸如社會經濟地位,則常常很難操縱或可能引發某種倫理道德問題。
社會心理學與人格心理學
社會心理學家與人格心理學家就其對個體的充分關注這一點無疑是統一的。所以,美國心理學會把這兩個領域歸入同一本期刊中[《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 》(JPSP)及《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簡報 》(PSPB)]。他們的不同之處在於社會心理學家對社會因素尤其關注。人格心理學家關注的焦點是個體內部功能以及個體間的差異 ,例如,為何有些人更具有暴力傾向。社會心理學家則關注我們共同的人性,即就總體而言,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他們感興趣的是社會情境如何使絕大多數 個體變得友善或無情,從眾或獨立,如何使他們對他人產生好感或偏見。
除此之外,二者還有其他的不同之處。社會心理學的歷史更短暫。許多人格心理學大師,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卡爾·榮格(Carl Jung),卡倫·霍尼(Karen Horney),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都活躍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而本書所介紹的許多社會心理學家仍然健在。社會心理學中廣為人知的理論比較少,更多的是“名不見經傳”的——那些富有創造力的研究者所貢獻的“微雕作品”。在零星閃現於本書中的“研究背後的故事”專欄中,我們將與許多這樣的研究者有一面之緣。
解釋的不同層面
我們從各個不同的學科角度研究人類,從基礎學科角度,例如物理與化學,一直延伸到綜合學科領域,例如哲學與神學。你究竟想探討哪個層面的內容決定了你採用的視角觀點。拿“愛”來說,生理學家可能會描述與熱戀有關的大腦化學物質;而社會心理學家可能會探討不同的個性與條件——出眾的外表,伴侶的相似性,或是僅僅多次重複出現在一個人面前——是如何增強我們所謂的“愛戀”;而詩人則可能去讚美偶爾伴隨愛而來的美妙體驗。我們並不需要假設,因為在以上不同層面的解釋中必定隱含某一個真理 。就拿剛才“愛”這個例子而言,生理學取向與情感取向只是看待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視角而已。同樣地,對於人類所共有的亂倫禁忌的進化論解釋(即亂倫會導致後代繁衍的基因遺傳出現問題)並不能替代社會學的解釋(即把亂倫禁忌看成是維持家庭完整性的手段)或神學的解釋(即把關注點放在道德倫理之上)。各種不同層面的解釋可以互為補充(見圖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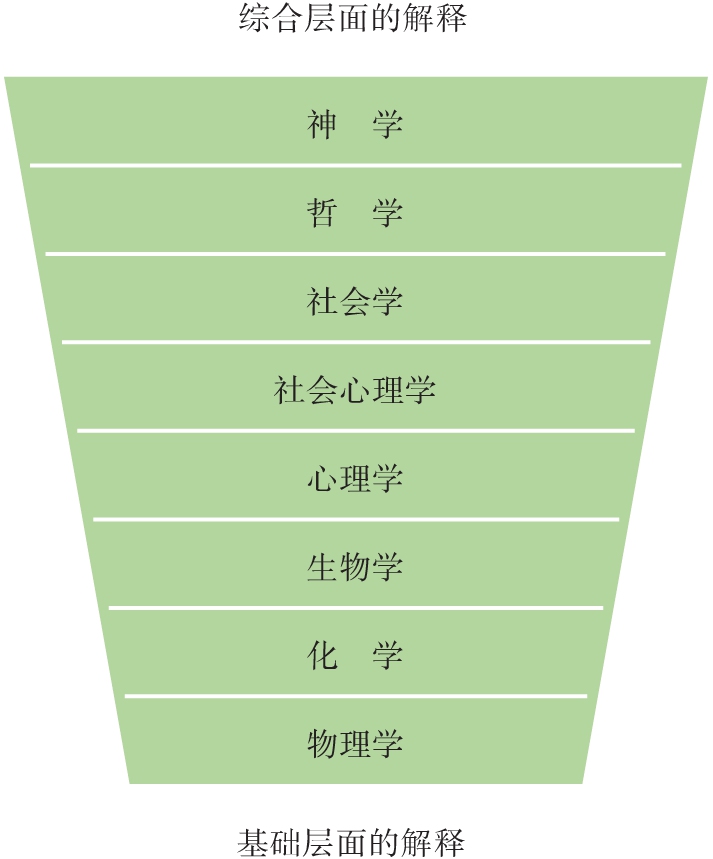
圖1-3 部分學科的層級關係
學科領域從研究自然構建的基礎學科到研究複雜體系的綜合學科。對人類機能某一個層面的正確解釋並不一定與其他層面的解釋相沖突。
假如所有的事實只是真理的一部分,那麼不同層面的解釋應該可以拼合成為一幅完整的圖景。史蒂文·平克(Pinker,2002)對此的詮釋是:“地理學家可能會如此解釋非洲大陸的海岸線與美洲海岸線的嵌合,因為這些大陸曾經是相互毗鄰的,但由於其各自屬於不同的板塊,所以導致最後漂移開來。板塊移動的問題可以交給地質學家,後者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岩漿的上湧推動了板塊的移動。至於為什麼岩漿會變得如此灼熱,則需要求助於物理學家來解釋地心與地殼之間的相互作用。”(p.70)一旦認識到不同層面之間解釋的互補性,我們似乎可以從應該科學地還是主觀地看待人性這類無益的爭論中解脫出來,因為這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
意識到不同解釋層面之間的互補性,讓我們得以從應該更科學還是更主觀地看待人性這一無謂的爭論中解脫出來:這並非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社會學家安德魯·格里利(Greeley,1976)解釋道:“不管怎樣,心理學無法解釋人類存在的目的,也無法解釋人類生活的意義,以及人類的最終命運。”社會心理學只是我們看待自我,瞭解自我的重要視角,但卻不是惟一。
小結
社會心理學是研究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聯繫的科學。它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構建社會世界,我們的社會直覺如何指引我們,而有時候又是如何誤導我們的,以及我們的社會行為如何受他人、我們自己的態度和生物性的影響。社會學和心理學是社會心理學的母體。相比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試圖在研究內容上更側重於個體,在研究方法上更側重於實驗。相比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對個體之間的差異關注得較少些,而更多關注人類如何看待影響彼此。
社會心理學是一門關於環境的科學。它揭示社會環境如何影響個人。就人類本性這個主題而言,還可以用其他的視角來看待此問題。每一個視角都對應各自的一系列問題與相應的解答。這些不同視角是互補的,而非衝突的。
社會心理學與人類價值觀
社會心理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對他們工作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這些影響表現在哪些方面呢?與其說社會心理學是種種研究發現的集合,還不如說是一系列回答問題的不同策略。在科學研究領域,就像是在法庭上一樣,個人觀點無足輕重。當思想等待審判時,科學證據是最終的裁判。但社會心理學家真能做到如此客觀嗎?他們作為人類中的一員,其價值觀——他們的是非善惡觀,以及人們該如何行事的個人信念——會不會滲透進他們的工作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社會心理學真的可以稱其為科學嗎?
價值觀直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當社會心理學家選擇研究課題 時,價值觀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在納粹蹂躪歐洲的20世紀40年代,興起了研究偏見的熱潮;50年代,強調同一性的風潮以及固執己見的現象推進了我們對服從的研究;60年代隨著暴力與犯罪率的增加,引發了有關暴力的研究興趣;70年代的女權運動掀起了有關性別與性別歧視的研究高潮;80年代則興起了關於軍備競賽的心理影響的研究興趣;而90年代的研究重點轉向了研究人們如何面對文化多樣性、種族多樣性以及如何面對不同的性取向。因此可以說社會心理學是折射社會歷史的一面鏡子。
價值觀還會影響投身於不同學科的人群類型 (Campbell,1975;Moynihan,1979)。在你的學校裡,那些研究人文科學、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同伴,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某些差異呢?社會心理學與社會學是否會更多地吸引那些相對來說更願意挑戰傳統,創造未來而非迷戀過去的人呢?
最後,價值觀對心理學的直接影響還表現在,它是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目標 。社會心理學家研究價值觀是如何形成的,為何會改變,以及它們又是如何影響態度與行為的。然而,所有這些都無法告訴我們何種價值觀才是“正確”的。
價值觀間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當價值觀以客觀事實的形式出現時,我們常常很難認出它們。請看下面三種價值觀間接影響心理學的方式。
科學的主觀性
現在科學家與哲學家已經達成了共識:科學並非是全然客觀的。科學家並非僅僅把自然這本書大聲朗讀出來而已。更確切地說,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心理類別來解釋自然。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是透過自己那副預先調好度數的眼鏡觀察這個世界的。暫停幾分鐘,你從圖1-4裡看到了什麼?

圖1-4 你看到了什麼
你是否看見了一隻大麥町狗在圖片的中心嗅來嗅去?如果事先沒有這個提示的話,大多數人會全然無視那隻大麥町狗的存在。一旦你的大腦印入了這個觀念,它也就控制了你對這幅圖片的解釋,所以這時對那隻大麥町狗的視而不見 可能會變得和先前同樣困難。
這就是我們大腦的工作方式。在閱讀這些文字時,你並沒有意識到你同時也在看著你的鼻子。如果大腦沒有預先設定你將知覺到某個物體,它便把這個物體阻隔在你的意識之外。我們對現實的知覺會為我們的預期所左右,這即是關於人類大腦的一個基本事實。1951年,普林斯頓大學與達特茅斯大學之間的一場橄欖球賽可謂是觀點影響人們解釋事物的經典例證(Hastorf & Cantril,1954;Loy & Cantril,1981)。這場比賽如預期的一樣演變成一場仇恨之戰,事實上,它成為兩校歷史上最激烈也是最不光彩的比賽。普林斯頓的一位全美最佳選手被一群對手摔倒在地,再被層層壓住,最後被迫出場,還弄傷了鼻子。接著便是一場拳腳大戰,雙方都有嚴重的“傷亡”。整場比賽簡直與常青藤聯盟的上層紳士形象相差千里。
比賽結束不久後,分別來自兩個學校的兩位心理學家在各自的校園裡為學生重放了比賽錄像,並把它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的一部分。要求學生以科學觀察者的身份,注意每一次摩擦,並確定哪一方對此負有責任。但是學生們卻無法將對各自學校的忠誠棄之不顧。普林斯頓的學生相比達特茅斯的學生更容易認定普林斯頓的選手為受害者。例如,普林斯頓的學生所認定的達特茅斯的犯規次數是對方所認定的兩倍。有箴言曰:客觀現實的確 存在,但我們總是透過信念與價值觀的眼鏡觀察它們。
由於在某個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通常持有共同的觀點,或來自相同的文化 (culture)群體之中,他們的研究假設一般不會受到挑戰。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那些東西——那些被歐洲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社會表徵 (social representation)的共同信念(Augoustinos & Innes,1990;Moscovici,1988)——通常是最重要,而且是無需加以檢驗的信念。然而,有些時候,圈外的人會引發我們去關注這些假設。在20世紀80年代,女權主義者將某些社會心理學家未加驗證的假設暴露在大家面前。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引發了人們對一些隱含偏見的關注,例如科學家的政治保守主義常使他們更樂於接受對社會行為中性別差異的生物學解釋(Unger,1985)。
隱含價值觀的心理概念
價值觀還會影響概念。試想一下我們如何定義美好的生活。心理學家提到某個個體時,往往把他們歸為成熟或不成熟,適應良好或適應不良,心理健康或心理不健康。在使用以上的形容詞時,看上去我們像是在陳述某種事實,其實我們所做的卻是價值判斷 。例如,人格心理學家馬斯洛因對那些“自我實現”人群的精準描述而享有盛名。自我實現的人在滿足了生存需要、安全與歸屬感需要、自尊需要之後,進一步上升至尋求人類潛能的實現。很少有讀者注意到,馬斯洛同時也受到他本人價值觀的影響而選擇加入了他所描述的那一類自我實現的群體。最終對自我實現人格的描述,即自發、自主、充滿神祕感以及其他的特徵,其實反映了馬斯洛的個人價值觀。如果他選擇以其他的著名人物為出發點,例如拿破崙、亞歷山大或洛克菲勒,這樣一來,他對自我實現人格的描述可能就與現在的大相徑庭了(Smith,1978)。
有關心理諮詢方面的意見同樣也反映了諮詢者的個人價值觀。當健康心理學專業人士建議我們應該如何生活時,當育兒專家指導我們如何養育子女時,當心理學家鼓勵我們不要考慮別人的想法而應該自由地生活時,其實他們所表達的是他們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在西方社會,這些價值觀通常是個人取向的,即鼓勵那些令“我”最感適宜的行為。非西方文化通常鼓勵那些令“我們”最感適宜的行為。)在許多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時,對所謂的專業人士不免言聽計從。但科學並不是回答何為終極道德義務,不是回答生活的目的與方向何在,不是回答什麼是生活的意義,事實上它也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隱含的價值觀甚至會滲入到心理學研究取向的概念 中。假設你完成了一項人格測驗,某個心理學家在給你的答案評分之後宣佈:“你在自尊項上得分很高。在焦慮項上得分很低。你的自我力量格外強。”“哈”,你想,“我對此表示懷疑,但聽起來還不錯。”現在,另一個心理學家讓你完成類似的測驗,出於某種原因,這個測驗問了些同樣的問題。之後,你被告知,你似乎有些自我防禦,因為你在自我壓抑項上得分很高。你不免會想,“這怎麼可能呢?另一個心理學家給我的評價著實不低啊!”可能這些評價標籤描述的都是同一類的行為反應(傾向於自我評價很高且不承認存在問題)。我們該把這類行為稱之為高自尊還是自我防禦呢?這些標籤無疑反映了心理學家的價值判斷。
社會心理學的語言中常隱含有這種價值判斷,但它並不能作為貶抑社會心理學的理由。我們的日常生活用語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有些時候我們謾罵咆哮,有些時候則溫言軟語。我們給那些參加游擊戰的人貼上“恐怖主義者”還是“自由戰士”的標籤,取決於我們對其行為原因的看法。我們稱公共補貼為“福利”還是“救濟”可以反映出我們的政治立場。當“他們”讚美他們的國家與人民時,可以稱其為民族主義;而當“我們”這樣做時,則稱之為愛國主義。一個捲入婚外情的人是在追求“婚姻解放”還是犯了“通姦”,這取決於我們的個人價值觀。我們把自己反對的社會影響稱為“洗腦”,把自己從不嘗試的性行為稱為“性變態”。諸如對“雄心勃勃”的男人與“盛氣凌人”的女人,“小心謹慎”的男孩子與“怯生生”的女孩子的種種評價都別有“深意”。
再次強調一下:價值觀隱含於我們對心理健康與自尊的文化定義中,隱含於我們對有關生活的心理學建議中,隱含於我們的心理學標籤之中。在整本書裡,我還會讓你看到有關隱含價值的其他例子。認為隱含的價值一定是毒草,這並非是我們的立場。我們的立場是:對於科學解釋而言,即使是停留在描述現象的層面上,那也是一種人類活動。那麼,已有的信念與價值觀會影響社會心理學家的思想行為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了。
“是”與“應該”間無通途
對於那些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來說,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錯誤便是從對“這是什麼 ”的描述偏轉到“這應該是什麼 ”。哲學家們把這種錯誤稱之為自然主義的謬論 (naturalistic fallacy)。哲學家休謨於200年前所指出的,在“是”與“應該”之間,在科學描述與道德處方之間的鴻溝,直到今天也絲毫沒有縮小。對於人類任何一種行為的考察,例如性行為,都無法在邏輯上指出何謂“正確”的行為。如果大多數人沒有表現出某種行為,這並不意味著它就是錯誤的行為。即使大多數人表現出某種行為,那也並不意味它就是正確的。一旦我們從對事實的客觀描述偏轉到了對“應該如是”的說明陳述時,我們便把自己的價值觀納入了其中。
社會心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他們的工作。我們每個人都不例外。我們的價值觀與假設令我們這個世界亮麗多彩。為了探討我們的價值觀與社會表徵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們原本以為就該如此的一切,這就需要接觸不同的文化。如果你不假思索地認為,首先人無論如何都應該對自己誠實,女性比男性就是更適合或不適合某些角色;或者認為浪漫的愛情應該先於婚姻,那麼你只能坐下來等待。
因為科學有主觀性的一面,我們就要放棄它嗎?恰恰相反:正是意識到人類思維的某種解釋性功能,我們才恰恰需要持有各種不同偏見的研究者從事科學研究分析。通過不斷地將我們的信念與事實相互印證,我們瞭解得越多,就越能對它們進行檢驗和約束。系統的觀察與實驗可以幫助我們清洗那些用以觀察這個世界的鏡片。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的價值觀直接地影響其工作,如對研究課題的選擇;同時也間接地影響著他們的工作,如當他們構建概念,選擇描述標籤,以及提供建議時所隱含於其中的價值觀。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了科學解釋中存在的主觀性,意識到在社會心理學的概念與標籤中隱含的價值觀,以及在對“這是什麼”的科學描述與“這應該是什麼”的道德處方之間存在的鴻溝。價值觀滲入科學的現象並非為社會心理學所獨有。正是因為人類思維鮮有不偏不倚,所以如果我們想將自己所珍視的思想結晶與真實的社會現實互相驗證的話,就需要系統的觀察與實驗研究。
我早就知道了:社會心理學不過是常識而已嗎
社會心理學的理論是否能為人類的處境帶來曙光?還是它們只不過在描述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已?
本書中所陳述的許多結論在你看來可能極為熟悉,因為社會心理學就在你的周圍。我們不斷觀察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互相聯繫。對面部表情的含義,如何差人做事,或者如何區分敵友都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多少個世紀以來,哲學家、小說家與詩人們就社會行為進行了大量的觀察與評論,而且都頗有見地。社會心理學關乎每個人的生活。
那麼,社會心理學難道就是用其他的語言表述常識嗎?社會心理學面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批評:一鑑於社會心理學記錄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所以它便無足輕重。二鑑於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可被用來操控人類,它便危險之至。批評之一,即社會心理學只不過把任何一個門外漢都心知肚明的東西拿來改裝一番,這是否正確呢?
作家卡侖·墨菲(Murphy,1990)認為此話不假:“社會科學家日復一日地深入這個領域,而且他們也日復一日地發現人們的行為與所料想的絲毫不差。”近半個世紀之前,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爵士(Schlesinger Jr.,1949)就社會學家對美國二戰士兵的研究進行了類似的嘲諷。
這些研究發現了什麼?另一個研究評論者,社會心理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1949)提供了一份解釋性評論的樣例,我把其中一部分列舉如下:
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兵比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適應方面遇到了更多問題。(比起那些“社會”大學的畢業生,知識分子對戰鬥帶來的焦慮更不適應。)
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適應炎熱的南海島嶼氣候。(南方人更適應炎熱的氣候。)
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多年的壓迫會降低成就動機。)
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歡來自南方的長官而非來自北方的。(因為南方長官更習慣與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然而,常識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知道事實之後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後聰明總比先見之明來得明顯容易。有實驗表明,當得知實驗結果時,人們便突然間覺得結果不是那麼令人驚訝,至少相對那些僅得知實驗程序或實驗預期結果的人們而言(Slovic & Fischhoff,1977)。一旦新知識在手,我們那卓有成效的記憶系統便會自動更新過時的假定(Hoffrage & others,2000)。
當讀到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總結時,你可能會產生同樣的體驗。但是拉扎斯菲爾德接著說:“這些陳述中的任何一條恰恰與實際發現的相反 。”事實上,書中還報告:教育水平較低的士兵適應性更差。南方人並不比北方人更喜歡熱帶氣候。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等等。“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給出了真正的結論(正如施萊辛格所感覺到的那樣),讀者也許會給這些事實打上‘顯而易見’的印章。”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體驗那種事後聰明。須臾間 ,我們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發生的種種力量而不覺得驚詫了。在大選或股市震盪發生之後,大多數的評論員對此並不感到意外:“該是整頓市場的時候了。”在2003年對伊戰爭之後,戰爭的結果——對於聯軍來說,勝利來得輕而易舉,但對於文明和民主而言卻並非如此——看上去再明顯不過了。許多人認為,考慮到美國對伊拉克有著3 300億美元對16億美元的優勢,任何人都會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但是,美國部隊應該事先預見到需要保護巴格達的博物館、圖書館和學校,以免於掠奪者的掃蕩。就像丹麥哲學家、神學家索倫·基爾愷戈爾(Soren Kierkegaard)所說的那樣:“生活是正著來活,卻是倒著去理解。”
如果這個“事後聰明式偏見 ”(hindsight bias)(也被稱為“我早就知道了”的現象)深入人心的話,你可能就會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結果。的確,幾乎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所得出的可信結論看起來都有些像常識,當然,這都是在你知道結果之後 。
你可以證明這種現象的存在。把一群人分成兩組,將一個心理學結論告知給其中一組,而給另一組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例如,告訴其中一組: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不同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異性相吸”。
而另一組則被告知: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相似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先讓人們解釋這個結論,然後問他們是否對此感到驚異。無論他們被告知的是哪種結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得到的那個結論並沒有讓其感到驚訝。
事實上,幾乎任何結論都會因諺語格言的解釋而變成常識。假如社會心理學家報告分離加深愛意,甲便回答道:“你就靠這個謀生?誰都知道‘小別勝新婚’。”若結果是分離會澆熄愛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訴你‘人走茶涼’。”
當卡爾·泰根(Teigen,1986)讓英國萊斯特大學學生來評價格言與其對立面時,他一定樂了好一陣子。當看到格言“恐懼比愛強大”時,大多數人認為此言不差,但對於其反面“愛比恐懼強大”,學生們也作出了同樣的評價。類似地,人們對真正的格言“墮落的人不能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對其反面“墮落的人能夠幫助另一個墮落的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我最欣賞的是這兩句得到普遍認同的:“智者造箴言,愚者重複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為編造的語句“愚者造箴言,智者重複之。”(更多的雙重格言請參見“專欄”:我早就知道的事實。)
事後聰明偏見給許多心理系學生帶來了麻煩。有些時候,結果的確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銀牌獲得者來說,奧運會銅牌獲得者對自己的成績更為滿意)。但更多的時候,你在教科書上學到的實驗結論,它們看上去很容易,甚至顯而易見。而之後當你進行多項選擇測驗時,面對多個看上去頗為可信的答案,任務難度會大大增加。備受打擊的學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我還以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的事實”這一現象不僅令社會科學的發現看起來與常識無二,它可能還會帶來致命的後果。它可能令我們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僅如此,由於結果看起來似乎具有預見性,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為那些事後看起來“顯而易見”的錯誤決策而責備決策者,卻並不因那些同樣“顯而易見”的正確決策去褒獎決策者。從9.11那天早晨開始回溯 ,指向災難的種種信號看起來似乎非常明顯。一份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列出了這些被人忽視或被人誤解的線索(Gladwell,2003)。CIA知道基地組織的爪牙已經潛入了境內。一個FBI情報員給總部的一份備忘錄是以這樣的警告開始的:“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本·拉登可能會將學生送到美國參加民辦航空院校的聯合行動。”FBI忽視了這份準確的預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預見恐怖分子可能會使用飛機作為武器的報告聯繫在一起。“這些該死的笨蛋!”這看上去就是事後聰明偏見,“他們怎麼就沒把所有線索串聯起來?”
聚焦 我早就知道的事實
卡倫·墨菲(1990)這位《大西洋》的執行編輯譏諷“社會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通常只不過是察覺那些顯而易見之事,或僅僅是證實常識而已。”他自己對社會科學發現所做的也只是隨意的調查“發現任何一種想法或是結論都能在巴特利特 [1] 的慣用語辭典,或是任何一本百科全書的引文中找到。”的確如此,因為對於許多可信的結論而言,都有某種“出處”可尋(Evens & Berent,1993)。儘管如此,為了詳細審查格言的準確性,我們仍需要做一些研究。請看:
這邊的更正確 |
還是這邊的…… |
人多手雜反而礙事。 |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 |
文勝於武。 |
事實勝於雄辯。 |
朽木不可雕。 |
活到老,學到老。 |
血濃於水。 |
親兄弟明算帳。 |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
三思而後行。 |
有備無患。 |
船到橋頭自然直。 |
[1] 原文是Bartlett's,應該是指巴特利特·約翰·羅素(1805-1886)美國歷史學家和文物工作者,編纂《美國慣用語辭典》——譯者注。
但就事後聰明看來十分清晰明瞭的事情而言,事前卻沒有那麼清晰可辨。情報機關充斥著大量的“噪音”——在點滴有用信息的周圍是堆積如山的無用信息。分析家們為此不得不就繼續調查什麼樣的問題做出抉擇。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怖機構有68000件事情毫無頭緒。在事後聰明眼中,那些極少的有用信息現在看起來是如此明顯。
類似地,我們有時也會為自己所犯的“愚蠢錯誤”——沒能更好地與人相處,或是沒能更好地應對事情——而自責不已。當回頭看時,我們明白了應該如何行事。“我早就該想到期末的時候會有多忙,早就該開始寫論文了。”但有時候我們會對自己過分苛刻。我們忘記了事後看來顯而易見的事情在當時並非那麼明顯。
當內科醫生得知病人的症狀與死因後(解剖得出的結論),有時會頗為疑惑:怎麼會做出如此不正確的診斷?其他那些只得知症狀的內科醫生並沒有覺得錯誤的診斷如此明顯(Dawson & others,1988)。(倘若迫使陪審團從先見而非後見的角度出發,他們給玩忽職守者評定過失時是否會有所遲疑?)
那麼,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難道常識通常是錯誤的?有些時候的確如此。常識與行醫經驗讓醫生們相信,放血對醫治傷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紀中葉,有人不怕麻煩做了一個實驗——把病人分成兩組,一組放血,一組僅僅臥床靜養,才證明兩者毫無關聯。
另外一些時候,常識是正確的,或者說正反兩面都有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還是沉迷幻想?是與人共處還是離群索居?觀點之多如一海之大,無論我們發現了什麼,總有人對此有所預見。(馬克·吐溫曾開玩笑說,亞當是惟一在口吐蓮花之後還能確信自己是“天下第一人”的人。)但在眾多爭論中,哪一個最符合現實呢?
問題是常識並非總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常識總在事後 證明是正確的。這樣一來,我們便免不了誤以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和過去知道的比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和過去已經做的要多。而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科學的理由:幫助我們區分真實與幻影,區分真正的預測與簡單的事後聰明。
小結
就像生活中的許多場景一樣,社會心理學的發現有時候看起來似乎顯而易見。然而,實驗研究所揭示的結果只是在事實知曉之後才變得“明顯”起來。這種事後聰明式偏見常導致人們對自己的判斷與預測做出過高評價。
研究方法:我們如何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的理論可以對他們的觀察活動加以組織,這其中包括可驗證的假設以及可用於實踐的預測原則。社會心理學家也使用相關研究對行為加以預測,這些研究通常在自然場景中進行。他們還試圖通過實驗解釋行為背後的原因,在這類實驗中,他們可控制條件對一個或多個因素進行操縱。
社會心理學與其他學科不同的是,它有將近6億業餘從業者。對人進行觀察是大家普遍的愛好——公園裡,街道上,學校中。我們在觀察別人的同時,就形成了關於人類如何看待彼此,如何互相影響與聯繫的種種想法。專業社會心理學家也做著同樣的事情,只不過會更系統(通過形成理論),也更費力些(通常通過實驗研究,在實驗中創構微縮的社會情境以探求因果關係)。他們經常採用這種方法,在最近的一次統計中,涉及到了包括了八百萬人在內的25 000個研究(Richard & Others,2003)。
假設的形成與驗證
社會心理學家在思考人類的存在上著實煞費苦心,而再也沒有比思考這個更讓人“神魂顛倒”了。如果真像蘇格拉底所忠告的那樣:“不加反省的生活根本不值得過”,那麼僅僅“瞭解你自己”便似乎就已經是個十分有價值的目標。
當我們與人性角力以期發現它背後的隱祕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與發現形成理論。理論 (theory)是一套原則的整合 ,它們可以對所觀察到的事件進行解釋與預測 。理論是科學性的速記。
在日常交談中,“理論”常常指“離事實還有些距離”——是從猜測到理論再到事實的信心階梯上中間的那一格。但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事實和理論完全是兩回事。事實是一種達成了共識的陳述,這種陳述有關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理論則是對事實進行總結與解釋的觀點 。正如朱爾斯·亨利·鮑因克(Jules Henri Poincare)所言:“科學由事實構建,就如房屋由磚頭搭建”,“但一堆事實並非就是科學,就如一堆磚頭並非一幢房屋一樣。”
理論不僅可以進行總結,同時它還隱含可驗證的預測,這些預測被稱為假設 (hypotheses)。假設有幾種不同的功能。首先,我們可以以證偽的方式來驗證某理論。某個理論可以按照它自己闡述的規律做出相應的預測。其次,預測可以為研究指出方向。如果任何一個學科領域中的研究者在研究時都更有方向性的話,那麼該領域也將會更迅速地成熟起來。理論預測可以探測新的研究領域,這樣,研究者可以將目光投向他們從未想像過的領域。第三,對於一個出色的理論來說,其預測性也使得它頗有應用價值 。舉例來說,一個完整的攻擊理論可以預測出何時會發生攻擊行為,這種行為又該如何控制。就像現代社會心理學的奠基者勒溫(Kurt Lewin)所斷言的那樣:“沒有什麼能比一個出色的理論更實用。”
請想像一下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比如,我們觀察到,當處在人群中時,人們有時候會變得十分暴躁。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建立起這樣的理論:他人在場使個體體會到了一種匿名感,從而降低了自我控制。讓我們將信將疑地考慮一下這個理論。或許我們可以構想一個實驗室實驗,模擬電椅實施酷刑的場面來驗證該理論。如果我們讓一群人對一個無助的“受害者”實施懲罰性電擊,但並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實施了電擊,結果會是什麼樣子?這些人是否會如我們的理論所預測的那樣,當一群人一起實施電擊時,相比只讓自己一個人實施電擊而言,每個人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
我們也可以操縱匿名性這個變量。如果人們藏在面具後面,他們是否會對“受害者”實施更強的電擊?如果實驗結果證實了上述的理論,它同時也提示了我們該理論可能具有的應用價值。如果警察佩戴醒目的警牌,開著寫有可辨認身份的巨大數字的警車,那麼警察暴力行為或許就會減少。而事實上,上述一切現在在許多城市已經實施。
但是,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哪一個理論更好呢?一個好的理論:(1)能對大範圍內的觀察結果進行有效的總結;(2)對我們如何(a)證明或修改理論,(b)進行新的探索,以及(c)指出可能的應用方向這些方面做出清晰的預測。當我們將某個理論扔進廢紙簍時,並非因為經證明它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它們就像是舊汽車一樣,需要被更新,用更好的型號來替代。
相關研究:探尋自然關係
有關大多數你要學到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你會在以後章節的閱讀中逐漸消化。不過,讓我們先到幕後簡單縱覽一下社會心理學是如何進行研究的。幕後的匆匆一瞥可能剛好讓你能夠欣賞眼前的研究發現,讓你對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事件做出正確的判斷。
社會心理學研究隨場所的不同而不同。研究既可以在實驗室 進行(在控制條件下),也可以在現場 (field)進行(日常生活場景中)。並且,它也隨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相關研究 (correlational)(探尋兩個或多個因素之間的自然關係),或是實驗研究 (experimental)(通過操縱一些因素來考察它們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對報紙雜誌上所發表的心理學研究論文有著最佳判斷力的讀者,那麼弄清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的區別是十分必要的。
讓我們先通過一些真實的例子來考查一下相關研究的優勢(通常在自然場景中包含有十分重要的變量),以及它的劣勢(對於因果關係的解釋十分模糊)。就像我們將在第14章中所看到的那樣,現在的心理學家正在把個人和社會因素與人類健康聯繫在一起。他們當中包括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的道格拉斯·卡羅爾(Douglas Carroll)以及他的同事,喬治·戴維·史密斯(George Davey Smith)及保羅·貝內特(Bennett,1994)等人。在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係的研究中,研究者們“闖入”了格拉斯哥的古老墓園。他們記下了墓碑上843個人的壽命,把壽命作為衡量健康的一個標準。他們還測量了墓碑的高度,推論認為墓碑高度可以反映出墓地的造價,而造價則可以反映出富足程度,由此把墓碑高度作為衡量地位高低的一個標準。如圖1-5所示,無論男性還是女性,墓碑越高,壽命越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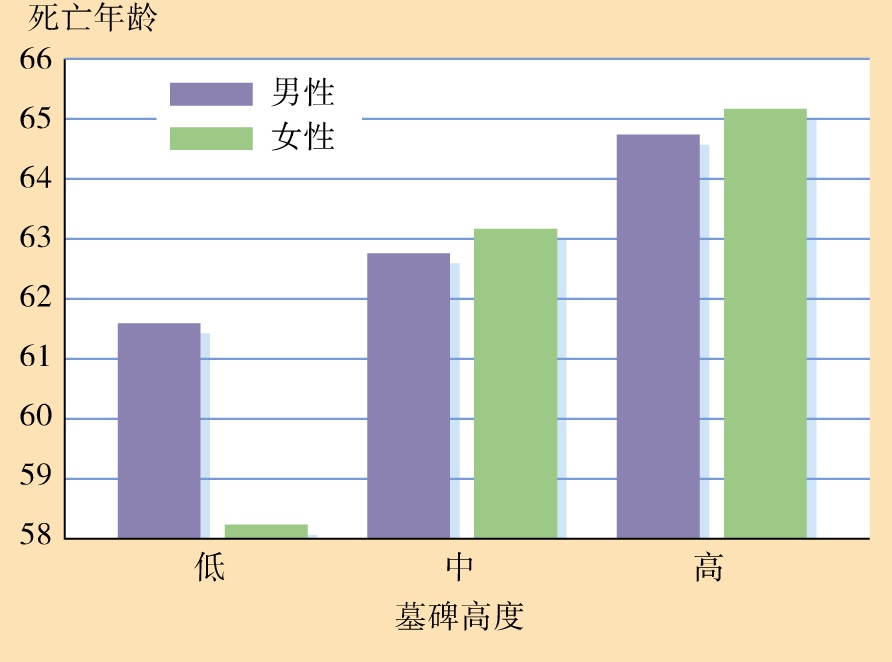
圖1-5 墓碑高度與長壽間的關係
卡羅爾及其同事用數據說明了地位與壽命之間的關係,而在該問題上其他研究者使用這個年代的數據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人口密度最低且失業率最低的蘇格蘭地區人的平均壽命也最長。在美國,壽命與收入有關(更窮、更底層的人們更有可能早逝)。在現代英國,壽命與職業地位有關。有一項對17350個英國公務員進行的10年跟蹤調查研究發現,與高級的行政官員相比,那些專業行政人員的死亡率是前者的1.6倍。文書和勞工的死亡率則分別是行政官員的2.2倍和2.7倍(Adler & others,1993,1994)。跨越不同的時空,地位與健康的相關關係似乎是可信的。
“相關”對“因果”
地位與壽命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學科業餘愛好者與專業社會心理學家可能都會犯的、也是最無法抗拒的思維錯誤:當兩類因素如地位與健康放在一起時,很可能會得出一個因素影響另一個因素的結論!我們可以假設,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護某人不受疾病的威脅。或者,反過來也會成立嗎?或許是健康促進了活力與成功。或許那些活得更長的人積累了更多的財富(使得他們能夠擁有造價更高的墓碑)。相關研究可以讓我們去預測 ,但它並不能推論改變一個變量(例如社會地位)將會導致 另一個變量的改變(比如說健康水平)。
在大眾心理學頗為混亂的思維背後便是相關與因果的混淆。再來看看另一個真實的相關——自尊與學業成績。那些高自尊的孩子往往有著較好的學習成績(就像任何一個相關一樣,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陳述:學業成績更高的人具有更高的自尊)。你為什麼做出這樣的假定(圖1-6)?[研究者發現:青少年對重金屬音樂的喜好程度與他們對婚前性行為、淫穢製品、惡魔崇拜以及毒品、酒精濫用的支持態度之間存在中度的正相關 (Landers,1988)。對於這種相關,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解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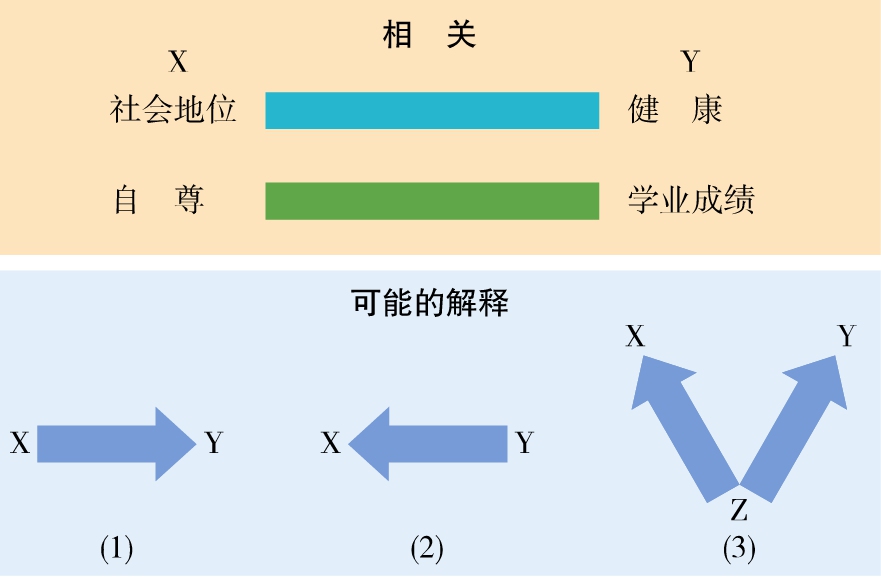
圖1-6 相關與因果關係
當兩個變量相關時,以下三種假設的任意組合都是可能的
有些人認為“健康的自我概念”有利於個體成就的獲得。那麼,提升孩子的自我形象便也可能會提高其學習成績。正是相信了這一點,美國的30個州頒佈了170多條增強個體自尊的條例。
但是還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心理學家威廉·戴蒙(Damon,1995)、羅賓·道斯(Dawes,1994)、馬克·利裡(Leary,1998)、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94),以及羅伊·鮑邁斯特(Baumeister,2003)對自信是否真的是一塊保護孩子不受學習成績不良(或是毒品濫用及少年犯罪)影響的盾牌表示懷疑。或許,事實是反過來的:可能是問題與失敗導致了低自尊。也可能是自尊通常可以反映出我們的真實狀況。或許自尊來源於拼搏之後的成就感。幹得好你可能會自我感覺良好;幹得不好你可能覺得自己是個傻瓜。一項對635名挪威學生的研究發現,在拼寫圖表上個人名下的一列金色星星,以及令人敬仰的老師不斷地給予褒獎可以提高一個孩子的自尊心(Skaalvik & Hagtvet,1990)。還有一種可能是,自尊與成就之所以相關是因為兩者都與潛在的智力與社會家庭地位等因素有關。
有兩個研究支持這一可能性:其中一個研究樣本是1600名美國男性青年,另一個研究樣本為745個明尼蘇達青少年(Bachman & O'Malley,1977;Maruyama & others,1981)。當研究者運用統計方法去除智力與家庭地位的影響效應後,自尊與成就之間的相關也化為烏有了。
高級相關分析可以揭示因果關係。時間序列相關 可以揭示事件發生的順序 (舉例來說,可以指出成就水平的變化是否更多地發生在自尊水平變化之前,還是發生在自尊水平變化後)。研究者還可以使用統計方法剔除“混淆”變量的影響。因而,在控制了智力以及家庭地位的影響後,自尊與 成就之間的相關隨之消失。(在有類似智力與家庭地位的人群中,自尊與成就之間的相關微乎其微。)考慮到吸菸這一現象在較高的社會階層中要少得多,蘇格蘭研究小組懷疑,當他們剔除了上述的影響之後,地位與壽命的相關是否還能存在。在控制了這個變量之後,如果兩者的相關仍然存在,這說明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更高的壓力,更低的自我控制感必然也會提高貧困階層的死亡率。
所以可以這麼認為,相關研究的巨大優勢在於,它通常發生在真實的場景中,在那些情境中我們可以考察諸如種族、性別、社會地位等這些難以在實驗室中操縱的變量。這種研究方法的最大劣勢在於研究結果的模糊性。這一點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你在耳提面命了25次也沒能聽進去之後,還是要嘗試第26次:兩個變量之間共同變化可以使我們運用一個變量對另一個變量進行預測,但是相關卻並不能清楚解釋因果關係。
調查研究
我們該如何測量類似地位與健康這樣的變量?一種方法是調查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本。調查研究者獲得具有代表性樣本的方法是隨機取樣 (random sample)——在研究總體中,每個人被抽到的概率是相同的 。通過這個方法取得的任何一個亞群體——金髮的人、慢跑的人或自由黨人,他們在調查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將與他們在整個總體中的代表性相一致。
無論我們調查一個城市的人,還是整個國家的人,1200個隨機取樣的個體都能使我們得以描述整個總體,而同時,我們有95%的把握認為該調查的誤差不超過3%,這實在太奇妙了!想像一個裝滿豆子的巨大廣口瓶,其中50%豆子是紅色的,50%是白色的。隨機選取其中的1200個,無論瓶子裡裝了10000個還是10億個,我們有95%的把握認為撿出的1200個豆子中,其中47%到53%的豆子是紅色的。如果你把紅色豆子想像成是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支持者,白色豆子是另一個候選人的支持者,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自1950年以來,在總統大選之前所進行的蓋洛普調查對選舉結果的預測只差了2%。就像幾滴血就能代表整個身體的信息一樣,隨機取樣的樣本也可以代表一個總體。
值得注意的是,調查並不能預測 選舉的結果,它只是描述公眾在接受調查那一刻所持的意見。公眾意見是可以變化的。在評估調查的時候,我們必須將以下四個可能會造成偏差的潛在影響因素牢記在心: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問題的順序,答案的選項和問題的措辭。
不具有代表性的樣本 在一個調查中,樣本數量並不是調查所要注意的惟一因素。樣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所研究的總體同樣也很重要。1984年,專欄作家安·蘭德斯(Ann Landers)接受了一個來信讀者的挑戰,就女性是否認為情感比性更重要做過一項調查。她的問題是:“你是否滿足於被擁在懷裡,接受對方的柔情蜜意而將‘那事’拋之腦後?”在十萬多女性的回答中,72%給予了肯定回答。隨後便是世界性的公眾輿論譁然。在迴應批評之詞時,蘭德斯(1995,P.45)承認:“這個抽樣也許並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國女性,但它的確提供了誠實而有價值的見解,而這些見解也來自於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是因為我的專欄讀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總人數大約有近七千萬。”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會懷疑,這七千萬就能代表所有的人嗎?在700個讀者中,回答問題的那一個難道就能代表其餘沒有回答的699個人的意見?
樣本代表性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1936年,當時有一家名為《文學文摘》的週刊雜誌向一千萬美國讀者郵寄了總統選舉調查的明信片。在兩百多萬讀者的回覆中,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以絕對的優勢戰勝了富蘭克林·羅斯福。而幾天之後正式選票統計的結果是,蘭登只獲得了兩個州的選票。因為該雜誌只向從電話簿和汽車登記處那兒得到姓名地址的人郵寄了明信片,這樣一來就將那些無力負擔電話與汽車的人群排除在外(Cleghorn,1980)。
問題的順序 假設我們的樣本具有代表性,我們也必須警惕其他的誤差來源,比如說我們問問題的次序。當問及“日本政府是否應該對美國工業品在日本的銷售數量設定限額”時,大多數的美國人給予了否定的回答(Schuman & Ludwig,1983)。然而,同時在與前一樣本相當的樣本中,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因為他們先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美國政府是否應該對日本工業品在美國的銷售數量設定限額?”大多數人都認為美國有權利設定進口限額。為了保持一致,他們也只好回答日本應當有同樣的權利。
答案選項的編制 讓我們再來設想一下答案選項編制的驚人效應。當普拉特及其同事(Plight & others,1987)詢問一些英國人,他們希望英國能源中有多大比例來自於核能時,這些人的平均喜好程度是41%。當他們詢問另一些英國人希望有多大比例的能源來自(1)核能(2)煤以及(3)其他能源,他們回答對於核能的偏好程度是21%。
類似的效應也發生在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 Scott,1987)的研究中。他們詢問一些美國人:“你認為現今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能源短缺,公共教育質量,墮胎合法化或汙染問題,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填寫你認為的最重要問題。”在給予上述選擇答案的人群中,32%的人認為公共教育質量是最大的問題。而在那些僅僅問及“你認為現今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的人群中,僅有1%的人提到了教育問題。所以請記住這一點:問題的形式可能會影響問題的答案。
問題的措辭 問題的精確措辭也會對答案造成影響。一項調查發現,僅有2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在“救濟窮人”上花銷過大。而53%的人認為政府在“福利問題”上花銷過大(《時代週刊》,1994)。類似地,大多數人同意削減“國外援助”資金而增加 “幫助他國飢餓民眾”的開支(Simon,1996)。甚至問問題語調上的細微改變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Krosnick & Schuman,1988;Schuman & Kalton,1985)。
“禁止”可能與“不允許”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然而在1940年,54%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禁止”發表攻擊民主的言論,7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不允許”發表這樣的言論。在2003年末,一項全國調查發現,55%的美國人贊成這樣的憲法修正案“只允許婚姻發生在男性和女性之間”,而在一項同步調查中,只有40%的人同意“禁止同性戀婚姻的修正案”(Moore,2004)。調查中問題的設置是十分精巧的環節。即使當人們說他們對某一個問題的回答非常肯定時,要注意問題的形式與措辭可能也會影響他們的回答。
順序、選項以及措辭的效力使政客們利用調查結果來顯示公眾對他們觀點的支持。諮詢師、顧問以及內科醫生通過“構建”選擇方式來給我們的決定施加影響。這就難怪在1994年肉製品聯盟議員否定了一項美國新食品商標法,以牛肉餡料為例,這項法案要求標註“含有30%脂肪”,而不是“70%瘦肉,30%脂肪”。
有箴言曰:措辭差之毫釐,實去之千里也。下面是一個有關蘇丹的故事,蘇丹夢見自己掉光了所有的牙齒。第一個被叫來解夢的人說,“天啊!掉牙齒說明您將會目睹家庭成員的死亡。”於是,怒不可遏的蘇丹下令給這個壞消息的使者50鞭子。
第二個解夢人聽了這個夢以後,他為蘇丹解釋這是好運氣的先兆:“你將比你的整個宗族還要長壽!”於是,安下心來的蘇丹下令管家獎給這個好消息的使者50個金幣。
途中,迷惑不解的管家向第二個解夢人請教:“你的解釋和第一個沒有什麼區別呀?”“啊,沒錯,”那個睿智的解夢人回答道,“不過,請記住這一點:重要的不僅僅在於你說話的內容,還在於你說話的方式。”[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僧侶詢問自己是否可以在祈禱時抽菸,但卻被一口回絕了。一個朋友給了他這樣一條建議:試試另一種問法,能在抽菸時祈禱嗎 ?(Crosser,1993)]
實驗研究:探尋因果關係
由於在自然相關的事物間辨別因果關係幾乎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任務,這就促使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在切實可行而又不違背倫理道德標準的情況下,在實驗室中模擬日常生活過程。這些模擬場景與航空學中的風力甬道有幾分相似。一開始,航天動力學工程師們並非在複雜多樣的自然環境中對各種飛行物體進行觀察。航空環境與飛行器兩者本身的多變性讓他們發現,要整理並使用這些數據來設計更好的飛行器顯然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於是,他們便構建了一種可以掌握的虛擬現實。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控制風力條件,就特定風力條件對特定機翼結構的影響進行觀察。
控制:變量的操縱
就像航天動力學的工程師一樣,社會心理學家也進行實驗研究,只不過是這些實驗模擬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特徵。通過一次改變一個或兩個因素——稱為自變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實驗研究者探察這一個或兩個變量的改變對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正如風力甬道幫助航天動力學工程師發現航天動力學的基本原理一樣,實驗使社會心理學家得以發現社會輿論、社會影響以及社會關係的基本原則。使用風力甬道的最終目的在於瞭解並預測複雜航天器的飛行特徵。社會心理學家通過實驗來了解和預測人類的複雜行為,其目的在於理解行為在人與人之間、情境與情境之間以及此時與彼時之間怎樣發生變化。
回顧歷史,社會心理學家在其大約四分之三的研究中都使用了實驗的方法(Higbee & others,1982),而超過三分之二的研究地點是實驗室(Adair & others,1985)。我們先來看兩個典型的實驗室研究,它們在之後討論偏見與暴力行為的章節中也會出現;這兩個實驗都可以作為實驗研究的例子。它們闡釋了相關研究發現中可能存在的因果關係。
第一個研究是有關對肥胖人群的偏見問題。人們常常認為那些肥胖者同時也是行動遲緩、懶散而馬虎的人(Ryckman & others,1989)。這些態度是否會成為歧視的溫床呢?抱著瞭解事實的希望,斯蒂文·高特麥克(Gortmaker & others,1993)對370名年齡在16~24歲之間的肥胖人士進行了研究。當7年之後再對這個人群進行回訪時,他們發現,與另一個近5000人的對照組女性人群相比,這一人群結婚的可能性與高薪收入的可能性都要更低。甚至在控制了智力測驗分數、種族以及父母收入這些變量之後,肥胖女性的年收入仍然比平均水平低7000美元。
在校正了其他某些變量之後,歧視看似能夠解釋肥胖與較低社會地位相關背後的原因,但我們仍難以對此下定論。(你是否還能想到一些其他的可能因素?)這就引起了社會心理學家馬克·斯奈德和朱利·豪根(Snyder & Haugen,1994,1995)的注意。他們讓76名明尼蘇達大學的男性學生分別與76名女性學生中的一位進行了一次電話交談。給每一名男性學生呈現一張照片,並告知 這就是與其交談的對象。其中一半是肥胖女性(並非真正的交談對象),另一半則是體重正常的女性。實驗還要求,男性學生要對那位與自己交談的女性形成某些自己的印象。在隨後的電話交談中,在女性學生身邊進行的現場分析發現,在被評價過的人群中,當交談的女性對象被假定為肥胖時,男性學生與其談話的熱情與愉悅程度都更低。很顯然,男性固有的想法影響了他們之後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又令其所謂的“肥胖”交談對象做出的某種行為“證實”了他們的印象——這樣的女性並不可愛。偏見與歧視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憶一下灰姑娘繼母的態度,或許我們應該把這種效應稱為“灰姑娘效應”。
在呈現第二個示例實驗研究以揭示因果關係之前,讓我們先想想電視輿論觀點與兒童行為之間的關係。那些觀看許多暴力電視節目的兒童,比起很少看這類節目的兒童有更嚴重的攻擊行為傾向。這表明兒童可能在模仿他們從熒幕上看到的場景。我希望你們現在已經辨別出,這是一個相關研究。圖1-5提醒我們,有兩種其他的因果關係解釋並不支持電視節目是導致兒童攻擊行為產生的原因。(那麼究竟是什麼呢?)
社會心理學家於是便把電視節目搬進了實驗室,在那裡可以控制兒童觀看暴力節目的數量。通過讓兒童觀看暴力節目或是非暴力節目,研究者可以觀察暴力節目的數量對兒童行為產生的影響。Chris Boyzatzis及其同事(1995)給一群小學生(而非其他人群)放映了一段20個世紀90年代最流行、也是最暴力的兒童電視節目——“強力突擊隊”。在剛看完電視節目之後,這些兒童在平均每兩分鐘的間隔中所表現出的暴力行為是沒有觀看節目兒童的7倍多。我們稱那些觀察到的暴力行為叫做因變量 (dependent variable)。這樣的實驗表明,電視節目可以成為導致兒童暴力行為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實驗研究的邏輯是十分簡單明瞭的:通過建構並控制一個模擬的現實世界,我們可以先變化一個因素,再變化另一個因素,以期發現這些因素或單獨作用,或聯合作用,會對人們產生怎樣的影響。
任何的社會心理學實驗都有兩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以上我們僅僅考慮了其中一部分——控制 。即我們在操縱一個或兩個自變量的同時也應該儘量使其他因素保持不變。而第二部分則是隨機分配 。
隨機分配:重要的平衡儀
讓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在相關研究的層面上,我們並不想假定肥胖(由於歧視的作用)導致了較低的社會地位,或觀看暴力場景導致了攻擊行為的發生(更多例子見表1-1)。一個調查研究者可能先去測量某些因素,然後運用統計方法剔除一些可能的相關因素,再回過頭來看最初的相關是否仍然存在。但是,沒有人能控制所有可以區分是否是肥胖人群,是否是暴力場景觀看者的因素。或許,那些暴力場景觀看者在教育水平、文化、智力水平,甚至在數十個研究者沒有考慮到的因素上都會存在差異。
表1-1 區分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

而隨機分配 (random assignment)似乎在須臾之間便消除了這些額外因素的干擾。通過隨機分配,每個人觀看暴力場景的機會是相等的。這樣一來,這兩組人群應該在其他任何可能的變量上——家庭地位、智力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初始暴力狀態等方面,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舉例來說,那些智力水平很高的人,在兩個組中出現的機會應該是相等的。由於隨機分配創建了兩個同質組,之後在兩組間出現的暴力行為的差異就可以歸結到惟一區分兩組的那個因素上——即實驗者是否觀看了暴力場景(圖1-7)。也正是由於將明尼蘇達學生隨機分配到兩個電話實驗組,那些女性的行為才可能受男性對於她們是否肥胖的認知信念的影響。

圖1-7 隨機分配
將實驗者隨機分配到接受實驗處理的實驗條件下,或是不接受實驗處理的控制條件下。這就使研究者相信:之後兩組之間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實驗處理所致。
實驗研究的倫理道德問題
有關電視節目的實驗可以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有些實驗在倫理道德問題上備受關注。社會心理學家不會讓一組兒童長期觀看暴力電視節目。他們只是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們的社會經歷,然後記錄下這種改變的影響。有些時候,實驗處理是無害的,甚至是相當愉悅的,參加這類實驗的人們都表示同意。但有些時候,研究者卻不得不承認他們正處於無害與冒險之間的灰色地帶中。
當社會心理學家設計那些引發個體強烈的思想與感情的實驗時,他們就常常冒險遊歷在道德灰色地帶中。實驗並不一定要符合阿倫森等人(Aronson & others,1985)所稱的現世實在論 (mundane realism)。即,實驗行為(舉例來說,將實施電擊作為研究暴力行為實驗的一部分)並非要與真實生活中的行為一模一樣。對於許多研究者來說,這種標準的確很生活化,但並不那麼重要。但是實驗研究應該 符合實驗現實主義 (experimental realism)即,它應該包括參與實驗的人群,並真的讓他們投入其中。研究者並不希望實驗者們有意識地去表演,或是應付了事;實驗需要真實心理過程的參與。舉例來說,迫使實驗者選擇給予他人重度還是中度電擊的確是衡量暴力行為的一個現實標準。它確實引發了真實的暴力行為。
為了符合實驗現實主義,有時候就要求研究者編個可信的故事暫時“矇騙”一下實驗者。如果事實上在隔壁房間的人並沒有受到電擊,研究者也並不希望實驗者知道這一點,否則就會將建立起來的實驗現實毀於一旦。基於這個考慮,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儘管這個數字呈下降趨勢)在其實驗中為了研究的真實性而使用了欺騙 (deception)的手段。
研究者們同樣也會將他們的預期實驗結果保密,以防實驗者們出於想成為“好被試”的熱誠,而表現出研究者希望他們表現的行為;或是出於逆反心理,表現出與預期相反的行為。烏克蘭的安納託利·科蘭登(Anatoly Koladny)教授曾談到,在1990年的蘇聯,只有15%的烏克蘭人承認他們有宗教信仰,但在蘇聯解體後的1997年,70%的人承認他們有宗教信仰,而這也沒什麼好驚訝的(Nielsen,1998)。研究者的措辭、語調、手勢也可能以微妙的方式讓實驗者做出令人期望的反應。為了將這種需要特徵 (demand characteristic)——那些看似“引發”特定行為的線索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研究者通常將他們的指導語標準化,或甚至使用計算機來呈現指導語。
在設計那些將會牽涉到倫理道德問題的實驗時,研究者常常像是在走鋼絲。意識到你正在傷害某些人,或是被置於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來觀察這是否會改變你的意見或行為,這都可能會引起暫時的不快。這類實驗又將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提了出來:這一切值得嗎?社會心理學家的欺騙比起真實生活,甚至電視真人秀節目來要短暫與溫和得多。即便如此,那些從實驗中獲得的領悟是否就能成為研究者的欺騙,甚至有時候對人們所造成困擾的託辭呢?
大學道德委員會現在正在對社會心理學研究進行評估,以期能保證研究不違背道德原則。美國心理學協會(2002)、加拿大心理學會(2000)以及英國心理學協會(2000)頒佈的道德原則嚴格要求研究者們做到如下幾點:
儘可能告知實驗者有關實驗的情況,這些情況要足以符合實驗者知會同意 (informed consent)的標準。
真誠。只有當必要,且實驗目的的確非常重要時,才允許使用欺騙手段,而並非出於“那些會挫傷實驗者積極性”的考慮來使用欺騙手段 。
保護實驗者不受傷害,保護實驗者不受嚴重不適的影響 。
對實驗者的個人信息保密 。
向實驗者做出 事後解說 (debrief)。在實驗之後告知實驗者有關實驗的一切情況,包括所使用的欺騙手段。但如果反饋可能會給實驗者帶來痛苦或困擾,例如他們意識到自己曾表現得很愚蠢或是很殘忍時,可視為該原則的惟一例外。
研究者必須足夠見多識廣且 充分考慮到這一點:實驗者離開時的心情至少與來之前同樣的愉快。若實驗者由於對心理學研究性質有所知曉而有所獲益的話,那就更好了。當實驗者得到尊重時,他們中很少有人會因自己被欺騙而耿耿於懷(Epley & Huff,1998;Kimmel,1998)。事實上,就像那些為社會心理學辯護的人所講,那些發下考試卷又將成績反饋給學生的教授們,他們所引發的焦慮與痛苦比研究者在實驗中的行為要嚴重得多。
從實驗室推廣到生活
就像研究兒童、電視節目與暴力行為的實驗研究所揭示的那樣,社會心理學將日常生活的經歷與實驗室的分析融合到了一起。在整本書中,我們也同樣這麼做,我們所用的絕大多數數據都來自於實驗室研究,而絕大多數的例證則來自日常生活。社會心理學的確可以展現出實驗室研究與現實生活之間互有助益的相互影響作用。來自生活的靈感常會激發實驗室研究,而研究又加深了我們對自己的經歷、體驗的理解。
這種相互影響作用在那個兒童電視的實驗中已經有所體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經歷為實驗研究指出了方向。那些電視節目與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們,那些有能力進行變革的人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電視節目的影響力。無論是在實驗室,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有關電視影響力的研究都得到了頗為一致的結論;在其他一些領域,諸如有關助人行為、領導風格、抑鬱以及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實驗室中發現的效應是現實生活的重現。克雷格·安德森及其同事(Craig Anderson & others,1999)寫道:“總體上來說,心理學實驗得到的是有關心理過程的真實反應,絕非皮毛或零碎。”
然而,在從實驗室推論到現實生活時,我們仍需抱著謹慎的態度。儘管實驗室研究揭示了人類存在的基本動態結構,但它仍然是一個簡化了的、控制條件下的真實。它可以告訴我們當其他的一切條件都保持不變時,變量X會產生怎樣的效應;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除此之外,正如你將會看到的那樣,許多被試都是大學生。儘管這可能會使你倍感親切,但大學生群體遠非是整個人類群體的一個隨機樣本。如果我們的被試是不同年齡,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還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嗎?這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把人類思維與行動的內容 (例如態度),及其思維與行動的過程 (例如,態度與行為如何互相影響)區別開來。在不同的文化下,思維與行動的內容比過程還要多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見解,但這些見解的構成卻很相似。比如:
波多黎各的大學生所報告的孤獨感比美國本土大學生所報告的更強烈。然而,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孤獨感的成分卻十分類似——羞怯,生活缺乏固定目標,低自尊 (Jones & Others,1985)。
戴維·羅及其同事報告 (Rowe & others,1994),不同民族的學生在學業成績與青少年犯罪的情況上有所差異,但這種差異“只是流於表面而已”。在一個民族群體中,家庭結構、同伴壓力以及父母教育程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預測其學業成績或犯罪情況;在其他民族群體中,這些因素也具有類似的預測能力。
我們的行為可能千差萬別,但卻受同樣的社會因素的影響。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將他們的想法與發現構建成理論。好的理論將會在一長串事實中提煉出許多簡短的預測原則。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預測原則對理論加以證實,或加以修改,以產生新的研究,並將其應用於實踐。
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主要是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這兩類。有時候相關研究會進行系統調查,以探尋不同變量之間的關係,例如教育水平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係。得知兩個事物之間有自然關係這一信息頗有價值,但這一信息並不能指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社會心理學家會儘可能運用實驗研究的方法來探尋因果關係。通過構建一種可控的模擬現實,研究者可以先變化一個因素,再變化另一個,以期發現這兩個因素究竟是單獨起作用,還是共同起作用,以及它們是如何對行為產生影響的。我們將被試隨機分配到不同的實驗條件下,即被試既可能被分配到實驗處理組的條件下,也可能被分配到實驗控制組(不接受實驗處理)的條件下。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個條件下產生的任何差異歸因於自變量的變化(圖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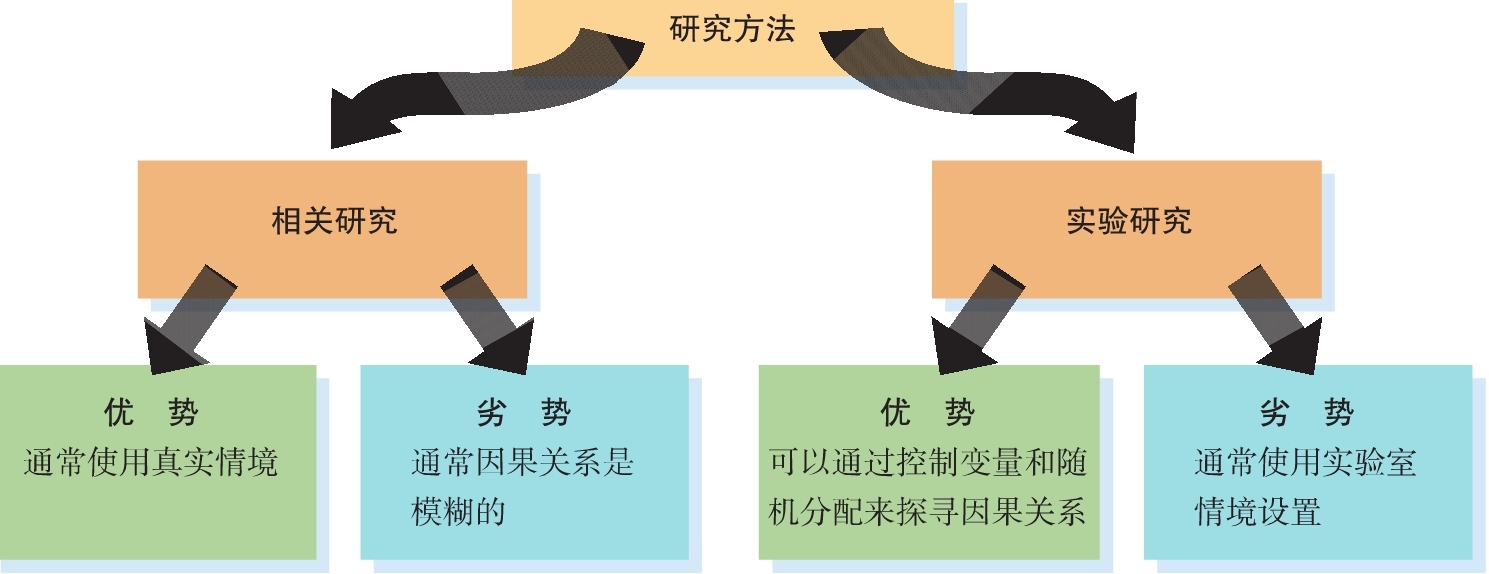
圖1-8 兩種從事研究的方法:相關研究和實驗研究
在設計實驗時,社會心理學家有時候會設計那些引發被試情感的場景。在設計並進行這樣的實驗時,研究者必須遵守職業道德準則,例如得到被試的准許,保護他們不受傷害,以及在實驗後向他們解釋任何先前的暫時欺騙行為。實驗室的研究使得社會心理學家能夠對來自生活經歷的點滴靈感進行驗證,然後再將這些原則與研究發現重新應用於真實的生活情境中。
個人後記: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我很高興能給大家寫下這些文字,同時也希望你能樂於接受社會心理學強有力且“千錘百煉”的原則。我相信,它們具有擴充你的頭腦,豐富你的生活的魔力。如果閱讀完整本書之後,你的批判思維能力得以提高;你對我們如何看待彼此,又如何互相影響——對為何我們有些時候互相欣賞,互相愛戀,互相幫助,而有時候則互相討厭,互相憎惡,互相傷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的話;那麼我就是個心滿意足的作者,而你,我相信也會是個頗有收穫的讀者。[在每一章節的末尾,我都會以社會心理學對人類的重要性做一個簡短的個人反思。之後,誠懇希望你提出自己的寶貴意見 。]
我希望我的文字所傳達的是加以限制的熾熱情感,因為我知道許多讀者正處在確定人生目標、身份、價值觀與態度的路程之中。小說家錢姆·波托克回憶了母親力勸他放棄寫作的情景:“做個神經外科醫生,你不但可以拯救許多人的生命,而且可以賺更多的錢。”波托克的回答是:“媽媽,我不想拯救別人的生命,我想做的是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活著”(Peterson,1992,p.47)。
我們這些教授、編寫心理學著作的人都被這樣一種情感所推動:那就是不僅傳播心理學,並且希望能幫助學生擁有更好的生活——更睿智,更有價值,更激情充溢地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就像其他領域中的教師與作者一樣。神學家羅伯特·麥卡菲·布朗曾問道:“我們為何要寫作?”“我承認,除了我們可以獲得的獎賞之外……我們寫作是因為我們希望改變什麼 。我們寫作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信念,我們能夠改變些什麼。這種‘改變’可以是一次對美的全新感知,可以是一次對自我的全新洞察,可以是一次對喜悅的全新體驗,也可以是一種投身變革的決定”(Marty,1988)。的確,我寫作是希望我能夠用批判的思維制約直覺,用判斷力提純情感,用理解替代幻想。
你的觀點是什麼
花一分鐘想想社會心理學將會以怎樣的方式與你的生活產生聯繫。是否有那樣的情景,你一直想令自己的社會直覺變得更加敏銳?你想贏得朋友也想影響他人?你想將仇恨消解成富有同情心的互相理解?
聯繫社會
當你閱讀本書時,你還會發現許多有趣的聯繫:將研究者的工作和其他社會心理學主題聯繫起來,將不同章節中提到的相同概念串聯起來。
同樣你還會注意到,許多在早些章節中介紹的概念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緊密聯繫。社會心理學中的某些概念同樣也可以應用到臨床心理學、法庭和對環境的保護中。這些應用將貫穿整本書,特別體現在第四編:社會心理學的應用。
所以,請你留心這些聯繫:聯結起研究者的工作,聯結起社會心理學的其他主題,聯結起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第一編
社會思維
這本書揭示了社會心理學的一些概念:對於我們是如何彼此理解(第一編)、影響(第二編)和聯繫(第三編)的科學的研究。第四編包括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和研究是如何應用於現實生活的。
第一編考察了關於我們是如何理解彼此的科學研究(也被稱為社會認知)。每一章都會直面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社會態度、理解和信念是否合理?我們給予自己和他人的壓力總是正確的嗎?我們的社會思維是如何形成的?人們為什麼會出現偏見和錯誤,而我們如何讓它更接近事實?
第2章探討了我們對自身的感覺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如何塑造我們的自我定義的?我們的自我利益是如何影響社會判斷、又是如何促進我們的社會行為的?
第3章關注的是我們形成對所處社會的信念的方式,這是令人驚異的、有時又是相當有趣的。這一章還會提醒我們注意一些社會思維的缺陷,並且告訴我們如何避免這些缺陷而更加理智地思考。
第4章探討了我們的思維與行動、我們的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我們的態度決定我們的行為嗎?還是我們的行為決定我們的態度?或者兩者都有?
第2章 社會中的自我
自我概念:我是誰
我們世界的中心:我們的自我感覺
社會自我的發展
自我與文化
自我認識
知覺到的自我控制
自我效能
控制點
習得性無助與自我決定
自尊
自尊動機
自尊的陰暗面
自我服務偏見
對積極和消極事件的解釋
每個人都高於平均水平,這可能嗎
盲目樂觀
虛假普遍性和虛假獨特性
對自我服務偏見的解釋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務偏見的反思
自我展示
虛偽的謙遜
自我妨礙
印象管理
個人後記:傲慢的危險與積極思維的力量——一對相反的事實
“有三樣東西是極端堅硬的,鋼鐵、鑽石以及認識自己。”(“There are three things extremely hard,Steel,A Diamond,and to know one's self .”注:hard 又能譯作困難)
——本傑明·富蘭克林
如 果你視力不好,你就得想辦法解決。你可能會戴眼鏡或隱形眼鏡。但如果你聽力不好,你有四分之三的可能會不去理睬這個問題,即不會戴助聽器。作為一個聽力很差的人,我常常思考這種差異。為什麼那些聽力差的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就不會要求配戴“耳朵的眼鏡”——助聽器呢?
對於美國人來說,部分原因在於助聽器比較貴。但是在英國和澳大利亞,那裡的國家健康系統提供免費的助聽器,很多可以通過助聽器獲得益處的人也不去佩戴它。出於對自我形象的關注——人類把無數錢財花費在染髮、牙齒漂白和整容上——我們不想讓任何人認為自己的聽力有問題或者自己變老了。
但是其他人是否真的關心我的耳朵上有什麼小儀器呢?還是他們一心想著自己以致沒有注意到那小東西?對話時,我的聽力很差(不戴助聽器)會不會比戴助聽器更引人注意呢?
很顯然,在我們的心中,自己比其他任何事更關鍵。通過自我專注的觀察,我們可能會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這種焦點效應 (spotlight effect)意味著人類往往會把自己看做一切的中心,並且直覺地高估別人對我們的注意度。
吉洛維奇等人(Gilovich & others,2000)演示了這種焦點效應。他們讓康奈爾大學的學生被試穿上Barry Manilow的T恤,然後進入一個還有其他學生的房間,穿T恤的學生猜測大約一半的同學會注意到他的T恤,而實際上注意到的人只有23%。
在我們另類的服裝、糟糕的髮型和助聽器上出現的現象同樣也會發生在我們的情緒上:焦慮、憤怒、厭惡、謊言和吸引力(Gilovitch & others,1998)。實際注意到我們的人要比我們認為的少。我們總能敏銳地覺察到自己的情緒,於是就常常出現透明度錯覺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我們假設,如果我們意識到自己很快樂,我們的面容就會清楚地表現出這種快樂並且使別人注意到。事實上,我們可能比自己意識到的還要模糊不清。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的社交失誤和公眾心理疏忽(public mental slips)的明顯度。如果我們觸按了圖書館的警鈴,或者自己是宴會上惟一一個沒有為主人準備禮物的客人,我們可能非常苦惱(“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怪人”)。但是研究發現我們所受的折磨,別人不太可能會注意到,還可能很快就會忘記(Savitsky,2001)。其實別人並沒有像我們自己那樣注意我們。
這種焦點效應和與之相關的透明度錯覺只是我們的自我感覺和我們的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兩個例子,因為他們發生在我們頭腦和我們周圍的世界之間。下面還有更多的例子:
社會環境對自我覺知的影響 。作為不同文化、種族、性別群體中的個體,我們可能會注意到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以及他人對這些差異的反應。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的一個歐洲裔的美國朋友剛剛從尼泊爾回來,他告訴我當他在一個鄉下的村莊生活時,如何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白人這一事實;一個小時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朋友告訴我,當她在非洲的時候如何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美國人。
帶有自利色彩的社會判斷 。人並不是完全客觀的,並不能總是對事件做出冷靜的判斷。當親密關係,比如婚姻關係中出現問題時,個體通常會把責任更多地推到配偶身上。離婚的人很少責備他們自己。可是當工作、家庭甚至遊戲中的情況好轉時,個體卻往往會認為自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為了獲取獎金,科學家很少低估他們自己的貢獻。1923年,班廷和麥克勞德(Frederick Banting & John Macleod)因發現胰島素而獲得諾貝爾獎後,班廷聲稱,作為實驗室領導者的麥克勞德更多的時候是他們的研究障礙而不是助手。麥克勞德則在有關該發現的演講中刪除了班廷的名字(Ross,1981)。
自我關注激發的社會行為 。人類的行為往往帶有一定的策略。為了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人們經常為自己的外表感到頭痛。(就算服裝和小缺點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會得到那麼多關注,一個人總體的吸引力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的,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就像一位理智的政治家一樣,我們同樣關注其他人的行為和期望,並隨之調整自己的行為。對自我形象的關注促使我們做出很多行為。
社會關係有助於我們界定自我 。安德森和陳(Andersen & Chen,2002)指出,在多變的關係中,我們的自我也不斷變化。可能和母親在一起時我們是一個樣子,與朋友在一起時則是另外一個樣子,而和老師在一起時又是另一個不同的樣子。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與此刻我們在關係中的角色緊密相連。
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我們和他人之間的交往是雙向的。我們對自己的想法和感情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和回憶,也會影響對其他人的反應。而他人也有利於我們進行自我塑造。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理由,所以現在的心理學研究中,自我成了最熱門的一個主題。在2002年的《心理學摘要》中,有10343本書和文章的摘要中出現了“自我”這個詞——這是1970年的7倍。人們的自我感覺組織著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行動。自我感覺使我們能夠回憶過去,評估現在,計劃未來——並因此做出適應性的行為。毫無疑問,正如利裡和巴特莫爾(Leary & Buttermore,2003)提出的那樣,人類的自我覺知比黑猩猩或(根據藝術、身體裝飾和語言判斷的)早期穴居人(尼安德特人)更敏銳。因此我們以自我概念(人們如何認識自己)和行動中的自我(自我感覺如何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動)為起點,開始社會心理學之旅。
自我概念:我是誰
無論我們這80年的生命中對世界做了些什麼,無論我們如何推斷和解釋,無論我們怎樣構想和創造,無論我們遇到和接納過哪些人,這都由我們自己來選擇。我們怎樣才能精確地認識自己?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
作為一個獨特而複雜的人,你有多種方式來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填空。(你可能會給出什麼樣的五種答案呢?)把這些答案綜合起來,就是你對自己的自我概念 (self-concept)的定義。
我們世界的核心:我們的自我感覺
自我概念的基礎、你對界定自我的特殊信念,是你的自我圖式 (self-schemas)(Markus & Wurf,1987)。圖式是我們組織自己所處世界的心理模板。我們的自我圖式——對自己的認識,身強力壯的、超重的、聰明的還是其他方面——有力地影響著我們對社會信息的加工。這會影響我們如何感知、回憶和評價他人和自己。如果體育運動是你自我概念的核心部分(假如成為一名運動員是你自我圖式的一部分),你會特別注意別人的身體和技巧。你可能會很快地回憶出與運動有關的經驗,而且你會特別記住與你自我圖式一致的信息(Kihlstrom & Cantor,1984)。自我圖式構成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幫我們分類和提取經驗。
自我參照
讓我們思考一下,自我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記憶?有這樣一種現象,叫做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當信息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時,我們會對它進行快速的加工和很好的回憶 (Higgins & Bargh,1987;Kuipern & Rogers,1979;Symons & Johnson,1997)。如果提問某一個特定的詞,比如“外向”,是否可以用來形容自己或者他人,那麼在稍後的測試中,那些回答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人能更好地回憶出這個詞。如果把我們自己和某個故事中的人物做比較的話,我們能更好地回憶出那個人物。在和某一個人談話的兩天後,我們對其說的與我們有關的話的回憶是最準確的(Kahan & Johnson,1992)。因此,記憶的構成離不開我們的主要興趣:自我。我們可以更好地回憶與自我有關的事情。
自我參照效應可以闡明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對自我的感覺處於我們世界的核心位置。由於我們傾向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核心,因此我們會高估別人對我們行為的指向程度。我們經常把自己看做是某件事情的主要負責人,而實際上我們只是在其中扮演很小的一個角色(Fenigstein,1984)。當評判其他人的表現和行為時,我們經常本能地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行為相比較(Dunning & Hayes,1996)。當我們和別人聊天時,如果無意中聽到屋裡其他人提起我們的名字,那我們的聽覺雷達會立刻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可能的自我
自我概念不僅包括我們是什麼樣子的自我圖式,還包括我們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我們的可能的自我 (possible selves)。馬庫斯及其同事(Inglehart & others,1989;Markus & Nurius,1986)注意到,我們的可能的自我包括我們夢想中自己的樣子——富有、苗條、充滿激情地愛與被愛的自我。同樣也包括我們害怕成為的樣子——失業的、沒有人愛的、學業上失敗的自我。這種可能的自我會用我們所渴望的生活遠景的特殊目標來激勵我們。
社會自我的發展
自我概念已經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焦點,因為它有利於組織我們的思想並指導我們的社會行為(圖2-1)。但是什麼會決定我們的自我概念呢?雙生子研究指出了基因對人格和自我概念的影響,但是社會經驗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影響包括:
我們扮演的角色
我們形成的社會同一性
我們和別人的比較
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其他人如何評價我們
周圍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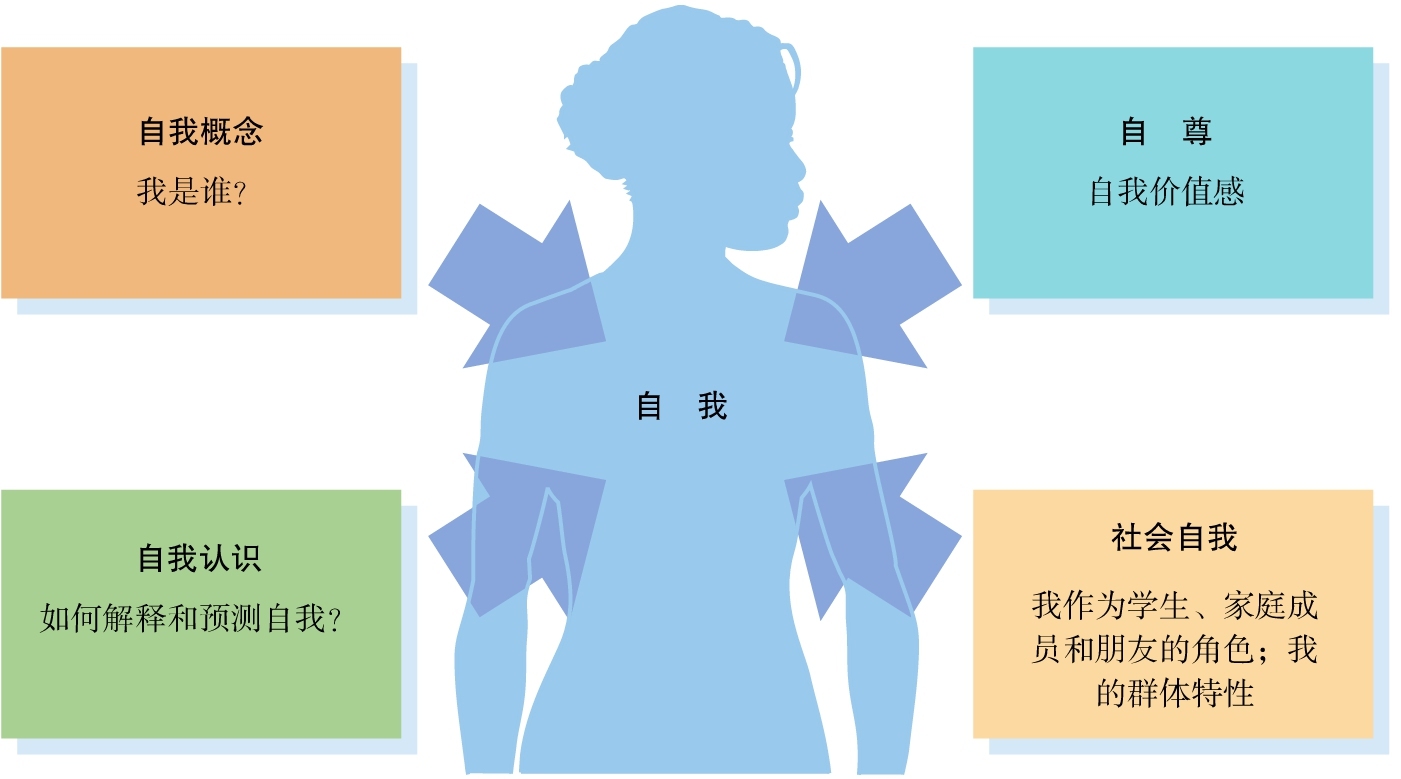
圖2-1 自我
我們扮演的角色
當我們扮演某一個新角色(大學生、父母、售貨員)時,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了自我覺察。無論如何,像發生在生活大舞臺上的事情一樣,該角色逐漸被我們的自我感覺所接受。舉例來說,當我們扮演角色時,我們可能會找一些證據來證實我們並沒有想太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努力地證明自己的行為。此外,觀察到的自我可能是自我暴露的;我們現在的自我感覺可能也會支持我們的觀點。就這樣角色扮演變成了事實(參看第4章)。
社會同一性
你的自我概念(對自己是誰的認識)不僅包括你的個人身份(你對自己個人屬性的認識),也包括你的社會身份。對於你是誰的社會定義——你的民族、信仰、性別、學術專業等等——也暗含著你不是誰的定義。這個範疇包括“我們”而排斥“他們”。
當我們是一個大團體中的某個小團體的一部分時,我們經常會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當我們的社會團體佔多數時,可能我們就不太考慮它。作為一個男性團體中單獨一名女性,或一個歐洲群體中的加拿大人,我們都會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作為白人學校中的黑人學生,或黑人學校中的白人學生,個體都會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身份並因此而做出反應。在加拿大,大多數人把自己看做是“加拿大人”——除非是在魁北克,那裡少數法國血統的人更多地感覺自己是“魁北克省人”(Kalin & Berry,1995)。
在英國,英格蘭人比蘇格蘭人多十倍,蘇格蘭人對自己身份的定義與英格蘭人不同。“蘇格蘭人,在某些程度上,不喜歡甚至憎惡英格蘭人”(Meech & Kilborn,1992)。英格蘭人作為多數,很少會意識到自己不是蘇格蘭人這個問題。在我最近入住的一家蘇格蘭賓館的客房登記簿上,所有的英格蘭房客在國籍一欄填寫了“英國”,而所有的蘇格蘭人(他們同樣是英國人)則在國籍一欄填成了“蘇格蘭”。此外,在大學中,英國學生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英國人,而很少把自己看做是歐洲人(Cinnirella,1997)。(更多請看第9章和第13章的種族認同)
社會比較
我們如何判斷自己是否富有、聰明或矮小?一種方式是通過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s)(Festinger,1954)。我們周圍的其他人會幫我們樹立富有或貧窮、聰明或愚蠢、高大或矮小的標準: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並思考自己為何不同。社會比較可以解釋為什麼學生進入一所優秀生很少的學校後,會有更高的學業自我概念(Marsh & others,2000)。當結束了名列前矛的中學學習後,很多在學業上非常自信的學生髮現,他們的學業自尊在進入了大型綜合性大學後受到了挑戰,因為大學的很多學生在畢業時都是當時班裡的尖子生。這就尤如放在小池塘裡的魚看起來會大一些。
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是圍繞社會比較而進行的。當別人不漂亮時我們就覺得自己英俊,當別人遲鈍時就覺得自己聰明,當別人無情時就覺得自己有同情心。當我們評價某個人的表現時,不可能不把他和自己做比較(Gilbert & others,1995)。因此,我們可能會為別人的失敗而暗自高興,特別是我們嫉妒的人遭受失敗或遇到不幸,而且當我們不太可能遇到這種倒黴事時(Lockwood,2002;Smith & others,1996)。
社會比較同樣會給人帶來煩惱。當人們的財富、地位或業績增長時,他們會提高對自己成就的評價標準。當人們感覺不錯並獲得成功時,通常會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Gruder,1977;Suls & Tesch,1978;Wheeler & others,1982)。當和競爭對手做比較時,我們常常認為競爭對手佔有優勢,以保護我們動搖的自尊(比如有更好的指導並且練習了更長時間——對大學游泳運動員的一個研究——Shepperd & Taylor,1999)。
成功和失敗
自我概念並不僅僅由我們的角色、社會認同和比較所決定,它也決定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嘗試挑戰現實的任務並取得了成功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很能幹。如果女性憑藉自己的力量擊退了性侵犯,她們會感覺自己並不是那麼容易受到攻擊,不用再那麼擔心焦慮,並且更可能感覺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Ozer & Bandura,1990)。學業上成功的學生會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做出更高的評價,從而激發其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Felson,1984;Marsh & Young,1997)。全力以赴並取得了成功會使人感到更加自信有力。
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樣,成功增強自尊的原則引發了很多研究,心理學家指出:用積極的信息(“你是重要人物!你與眾不同!”)來提高自尊,會激發個體做出更大的成就。低自尊有時確實會帶來問題。與低自尊的人相比,感覺自己有價值的人更加快樂,較少神經質,較少受潰瘍和失眠困擾,較少藥物和酒精依賴,失敗後具有更強的堅持性(Brockner & Hulton,1978;Brown,1991;Tafarodi & Vu,1997)。反過來也同樣成立,批評者聲稱:問題和失敗會導致低自尊。感覺緊跟現實。當我們征服挑戰或學到技術後,成功會讓我們具有一種充滿希望的、自信的態度。自尊不僅來自於告訴孩子他們有多棒,還要讓他們通過辛苦努力獲得成功。
其他人的評價
公認的成就能增強個體的自我概念,因為我們看到了別人對自己的積極評價。當別人認為我們很好時,我們也會認為自己不錯。如果我們稱讚某個小孩很有才華、刻苦學習或者樂於助人,那麼這個孩子就會把這些觀點融入到其自我概念和行為中去(參看第3章)。如果少數學生因為對自己學業能力的消極印象而感到恐懼,或者女性因為對自己在數學和理科上的較低期望而感到恐懼,那可以表明他們可能對這些領域“不認同”。他們不對這種預斷做出辯駁,而是認同自己的興趣在別處(Steele,1997,參看第9章)。
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Cooley,1902)用鏡像自我 來描述個體把別人當做鏡子來進行自我感知。庫利認為,我們根據自己出現在他人面前的樣子來感知自我。之後社會學家喬治·米德(Mead,1934)精煉了這個觀點,指出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的並不是別人實際上如何評價我們,而是我們覺得 他們如何評價我們。我們通常感到讚揚別人比批評別人更自在。(我們抑惡揚善。)如果個體因此而高估我們對他的評價,其自我意象會變得有些膨脹(Shrauger & Schoeneman,1979)。
自我膨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國家中最常見。Shinobu Kitayama(1996)報告說,日本人到北美后通常會因朋友間的互相恭維而感到驚訝。當他和同事詢問別人最後一次稱讚他人是多少天前時,美國人典型的回答是一天前。在日本,人們很少為自己個人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而是更多地為別人帶來的失敗感到可恥,因此,日本人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四天前。此外,如果告訴北美人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好,會比告訴他們做得不好而堅持更久。但是日本人在失敗時卻更能堅持(Heine & others,2001)。
我們祖先的命運決定於別人如何評價他們。當他們受其群體保護時,其生存的機會會變大。當他們意識到群體對自己不滿時,他們會感到羞愧並做出低自尊的行為反應。馬克·利裡(Leary,1998)指出,作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有類似的根深蒂固的歸屬需要,當我們面對社會排斥時會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還指出,自尊,是我們對他人如何評價我們的監控並做出相應行為反應的心理學尺度。
自我與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27頁中“我是_____”的陳述的?你給出的是你個人特點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是“我很外向”,還是描述你的社會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雙魚座的”、“我是快餐愛好者”,或是“我是基督教徒”?
對於某些人而言(特別是那些西方工業文化中的人),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是很盛行的。身份更多是獨立的。青春期是與父母分離的時期,個體開始依靠自己,並且開始定義個人獨立的自我 。即便個體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的特性——作為有特殊能力、特點、價值和夢想的獨特個體——可能會完整地保留下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假定,定義一個人的可能性自我並相信他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會使他的生活富足。在20世紀結束之前,個人主義已成為流行文化中的主導聲音(參看表2-1)。
表2-1 現代個人主義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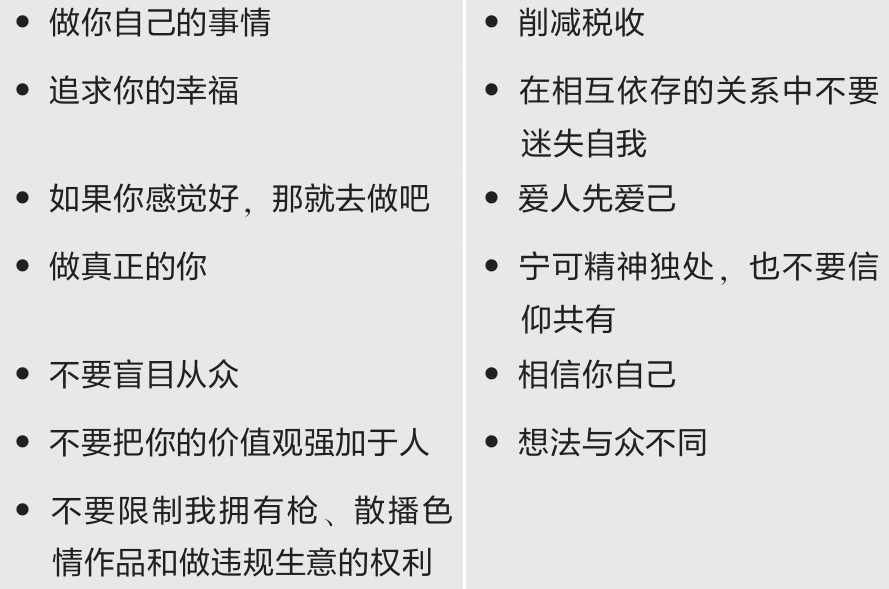
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多地讚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較少稱讚那些滿足別人願望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聲則宣告:“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Schoeneman,1994)。當人們經歷過富裕、變動、都市化和大眾傳媒後,個人主義就開始迅速發展起來(Freeman,1997;Marshall,1997;Triandis,1994)。
而亞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區的本土文化則把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 (Kitayama & Markus,1995)。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Heine & others,1999)。特性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尼亞人,舉例來說比如Maasai,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Kanagawa & others,2001;Ma & Schoeneman,1997)。聊天時,人們比較少地說“我”(Kanagawa & Kashima,1998,2003)。當語法或上下文能夠清楚地表明主語時,個體會說“去看電影”而不說“我去看電影”。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rt)在《思維地理》(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主張,其結果不只是社會關係與倡導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維方式也不盡相同。想一想:哪兩者——一隻熊貓、一隻猴子、一根香蕉——更可能在一起?可能是一隻猴子和一隻熊貓,因為他們都是“動物”類的?亞洲人卻比美國人更可能看到這樣一種關係:猴子吃香蕉。
當呈現一種栩栩如生的水下場景時(圖2-2),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徵,他們的講述更多以關係為主(青蛙在植物旁邊)。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比如單獨的大魚,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Nisbett,2003)。Shinobu Kitayama等人(2003)也發現日本人更多地是對知覺到的情境做出反應。呈現圖2-3的刺激,要求在一個更小的空盒子裡畫一條相同比例的線,日本人比美國人完成得更準確。要求畫一條長度完全相同的線,美國人可以準確地忽略關係並且畫出同樣的線。尼斯比特從這些研究中總結出東亞人的思維更加整體化——在與其他事物或環境的關係中知覺和思考對象與人。

圖2-2 亞洲和西方的思維
當呈現一種水下場景時,亞洲人常常描述環境和魚類之間的關係。美國人更多地注意單獨的大魚(Nisbett,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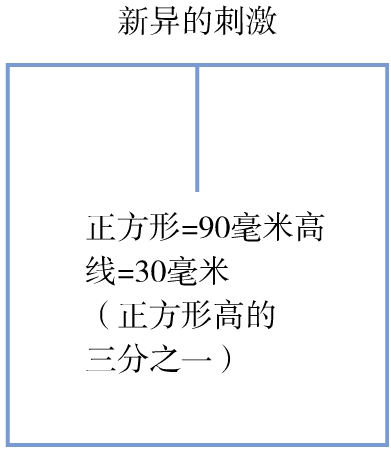
圖2-3 不同文化中的知覺
Shinobu Kitayama及其同事們(2003)給被試呈現上述刺激,然後讓他們在一個更小的或更大的盒子裡再畫一條與範例中同樣長或與盒子等比例的線。美國學生在畫同樣長度的線時更加準確;而日本學生在畫等比例的線時更準確。
無論如何,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樣分類如此鮮明的文化似乎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任何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都會在不同的個體之間發生變化(Oyserman & others,2002a,b)。這種變化同樣存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和政治觀點之間。在美國,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區比如俄勒岡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現得更為集體主義(Vandello & Cohen,1999)。保守派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者(“不要徵稅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體主義者(“制定法律來約束不道德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集體主義者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者。
一個具有相互 依賴自我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人在與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後,會失去那些定義自己的社會聯繫。他們不是隻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一起時的自我(Cross & others,1992)。如圖2-4和表2-2所示,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直接的交談比較少,更多是禮貌性交談(Holtgraves,1997)。其社會生活目標更多地不是增強個體自我而是協調並支持他所在的群體。金和馬庫斯(Kim & Markus,1999)指出:個性化的廣告板——“無咖啡因咖啡、單份的、小量的、高熱量”——在北美的咖啡店裡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在漢城就顯得有些怪異了。他們的研究證實,在韓國,人們並不把太多精力放在獨特性上,而是放在傳統文化和分享行為上(Choi & Choi,2002)。韓國的廣告較少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其特色是與眾人在一起(Markus,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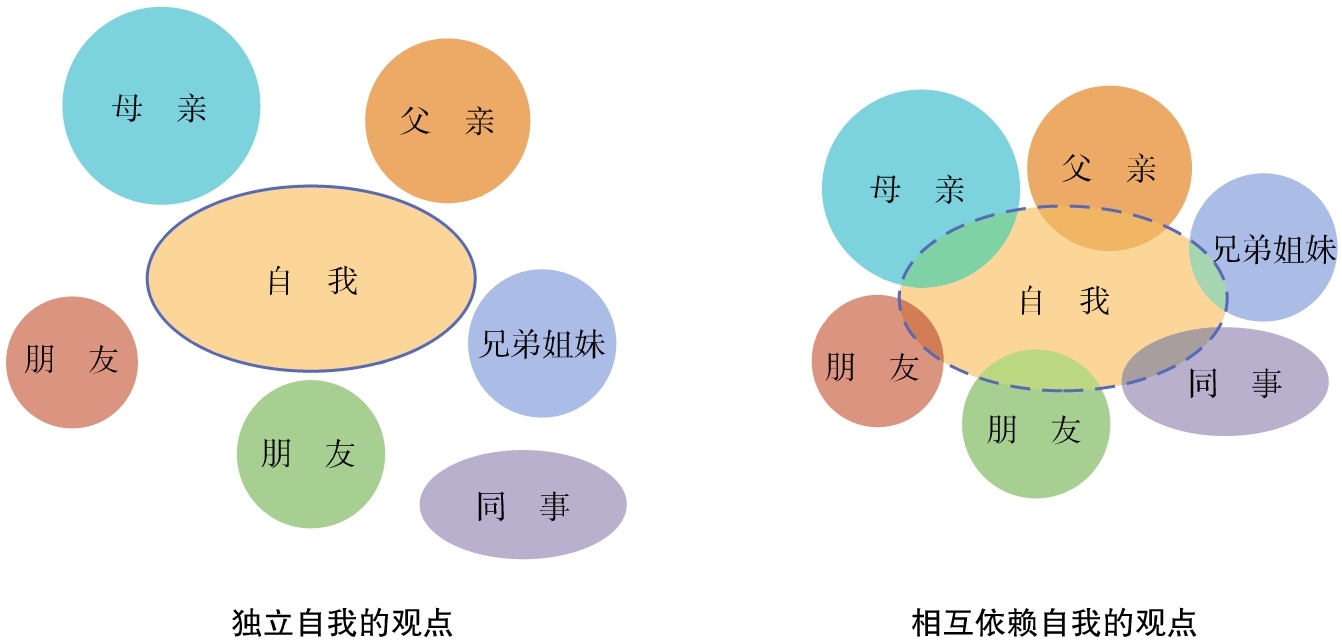
圖2-4 獨立的或相互依賴的自我建構
獨立的自我承認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但是相互依賴的自我會更深地融入他人(Markus & Kitayama,1991)。
表2-2 自我概念:獨立或相互依賴獨立自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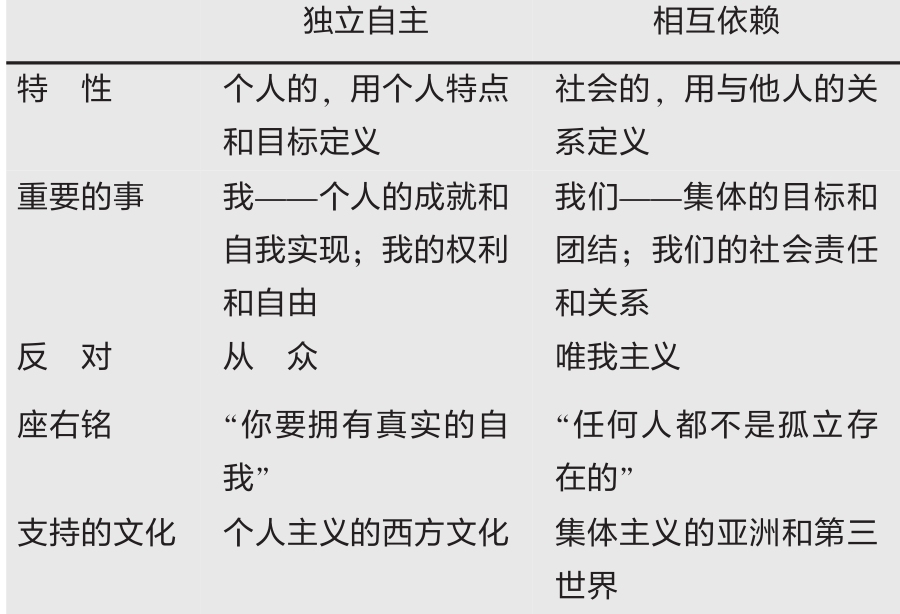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項研究中,認為在不同活動領域裡仍然保留了自我(內在自我)的加拿大學生為五分之四,而中國與日本的學生則僅為三分之一(Tafarodi & others,2004)。
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特別是那些少數學會不必太在意別人的偏見的人,“在他人的評價之外”並且認為他所在的群體沒有那麼重要(Crocker,1994;Kwan & others,1997)。自尊更多的是個人的而不是關係的。對個人特性的威脅會比群體特性的威脅更讓我們感到氣憤和鬱悶(Gaertner & others,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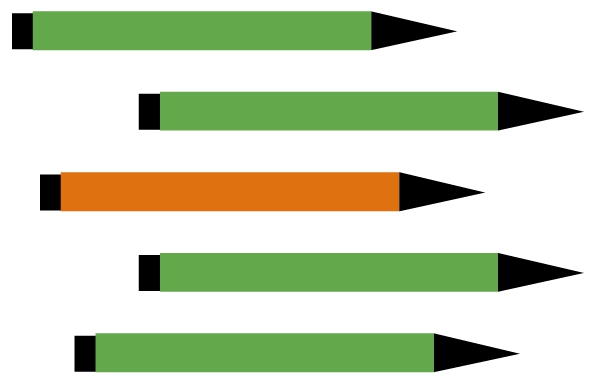
圖2-5 你會選哪支筆?
當金和馬庫斯(1999)要求美國人從中選擇一支筆時,77%的人選擇顏色不尋常的那支(不管它是橙色的還是綠色的)。對於同樣的選項來說,31%的亞洲人選擇了顏色不同的筆。研究者指出,該結果表明既有偏愛獨特性的文化也有偏愛一致性的文化。
現在請你想像一下,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日本大學生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大學生會如何報告他們的積極情緒,比如高興和得意?Kitayama和馬庫斯(2000)報告,對於日本學生來說,高興是伴隨積極的社會交往而來的——親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這種情緒通常伴隨解脫的情緒——效能感、出眾和驕傲。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Triandis,2000)。
在美國進行了10年的教學和研究後,Kitayama(1999)訪問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學,當他介紹西方的獨立自我的觀點時,研究生們感到“震驚”。“我堅持介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觀點(我的美國學生本能理解的觀點)並最終說服他們真的相信,很多美國人對自我都有這種分離的想法。儘管如此,最後還是有一個學生深深地嘆息道,‘這確實 是真的嗎?’”
當東西方文化不斷交流後——例如,多虧西方對日本大都市的影響以及到西方國家訪問交換的日本學生——他們的自我概念會變得越來越個人主義嗎?伴隨著“相信個體自己的能力”的忠告,伴隨著扮演個人英雄主義的警察不顧 他人阻撓捉住壞人的電影,西方宣揚個人成就對日本人的衝擊會比他們所受前輩的影響大嗎?根據斯蒂文·海因及其合作者(Heine & others,1999)的報告,好像確實是這樣的。日本的交換學生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活了七個月後,個人自尊增強了。在加拿大,那些長期的亞洲移民的個人自尊要高於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於生活在亞洲的人)。
自我認識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忠告我們:“認識你自己。”我們當然要嘗試。我們很容易形成對自己的信念,而且可以毫不遲疑地解釋我們的感覺和行為表現的原因。但是我們對自己真正瞭解多少呢?
研究背後的故事
里茲爾·馬庫斯論文化心理學
Shinobu和黑茲爾在好奇心的促使下開始了他們的合作。Shinobu想知道美國式的生活為什麼如此怪異。黑茲爾則認為日本也有一些奇妙的逸事。文化心理學就是使稀奇的事變成熟悉的,而使熟悉的事反倒變成陌生的了。我們分享了文化遭遇帶給我們的驚訝,並且確信當涉及心理機能時,問題就出現了。
在日本對英語很好的學生演講了幾周以後,黑茲爾想知道為什麼這些學生不發表任何言論——沒有問題,沒有評論。她以為學生的興趣點和她不同,否則為什麼沒有迴應呢?意見、爭論和批判思想的跡象會表現在哪兒呢?就算她直接詢問:“最好的麵店在哪兒?”答案依然是不變的沉默,而後幾個學生迴應“要看情況。”日本學生難道沒有偏好、想法、意見和態度嗎?如果沒有這些東西,那麼他們頭腦中有什麼呢?如果一個人不告訴你他在想些什麼,你怎麼去了解他呢?
Shinobu對美國學生不是僅僅聽講座而且有時經常打斷彼此並與教授互相交談的原因感到好奇。為什麼這些評論和問題帶有強烈的情緒情感並且伴有競爭意味?這種爭論可以表明什麼?為什麼智慧看上去似乎與得到他人的讚許有關,甚至是在彼此都非常瞭解的班級裡?
美國主人會給自己的客人各種選擇,這使Shinobu深感驚訝。你要白酒還是啤酒,軟飲料還是果汁,咖啡還是茶?為什麼讓客人承擔這些瑣碎的決定?主人當然應該知道在這種場合什麼是好的飲料,並且應該準備一些適當的好東西。
選擇是一種負擔嗎?黑茲爾想知道這是不是在日本的某種特殊受辱經歷的關鍵所在。一個8人小組在法國餐館用餐,每個人都遵循通用的用餐程序,首先是看菜單。侍者很靠近地站在他們旁邊。黑茲爾說她選擇開胃食品和主菜。接著是日本主人和日本客人之間的緊張談話。當正餐送上來時,她發現並不是她剛才要的那些。桌上每個人的食物都相同。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如果你都不能選擇自己的正餐,那你怎麼會覺得這是一種享受呢?如果每個人的食物都相同,那菜單還有什麼用呢?
在日本,一致性是他們想要的感覺麼?當黑茲爾走在京都的寺廟廣場上時,看到了小徑岔口處的一個標誌,上面寫著:“尋常小路。”誰會想走普通的小路啊?特殊的、較少人走的路在哪兒呢?選擇不尋常的路可能是美國人顯而易見的路線,但是在這個例子中它通向寺廟廣場。這種尋常小路不是無趣或沒有挑戰的路,而是意味著它是最適合的好路線。
這些交流促進了我們的實驗研究,並且提醒我們生活中總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好的路。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心理學實驗是心理學家在歐洲和美國的中產階級中進行的。在其他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有關如何做人和如何有意義地生活可能會有不同的思想和行為,這些差異會對心理學功能產生影響。這也是我們對合作研究和文化心理學一直保有興趣的燃料。
劉易斯(C. S. Lewis,1952,pp. 18-19)指出,“在整個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那就是我們知道的比我們能從外部觀察學到的還要多,”“這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可以這麼說,有內在信息;我們知道內情。”當然,有時候我們認為 自己知道,但是我們的內在信息是錯的。這就是一些看似吸引人的研究所無法避免的結論。
解釋我們的行為
你為什麼會選擇那所學校?你為什麼要攻擊室友?你為什麼會愛上他(她)?有時候我們知道原因,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當問到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和表現時,我們會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當原因有點微妙時,我們的自我解釋常常是錯誤的。我們會忽視影響別人的一些因素,但對自己就另當別論了。研究發現,人們錯誤地把雨天憂鬱症歸因為生活的空虛,把過吊橋時的興奮歸因為受過路人的吸引(Schwarz & Clore,1983;Dutton & Aron,1974),而且人們都矢口否認媒體對自己的影響,但是卻承認媒體會對其他人 產生影響。
尼塞特和沙克特(Nisett & Schachter,1966)用實驗證明了人們是怎樣誤解自己心理的。他們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實施一系列逐漸增強的電擊。給其中一些被試預先吃一片假藥,並告訴他們一會兒可能會導致心悸、呼吸不規律和神經質的發抖——而這恰恰是通常伴隨電擊的症狀。尼斯比特和沙克特預期人們會將電擊的症狀歸因為藥效作用,這樣他們就會比沒有吃藥的人更能忍受電擊。確實,這種效果非常明顯——吃過藥的人所忍受的電擊強度是沒吃藥的人的四倍。事後告訴吃藥的人他們忍受了比平均值高的電擊並詢問其原因,其答案都沒有提到藥。當被告知可能是之前服用的藥在起作用時,他們仍然否認藥的影響。他們大都說那藥可能影響一些人,但決不會是他們。典型的回答是,“我甚至沒有想到那片藥。”
還有一些研究也發人深思:要求人們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每天記錄自己的心情(Stone & others,1985;Weiss & Brown,1976;Wilson & others,1982)。他們同樣報告了一些可能影響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幾,天氣,睡眠時間等等。研究最後要求人們判斷每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注意事實上受其日常心情的影響),他們對因素重要程度的知覺和其心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發現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對讓自己高興或不高興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
而且我們對自己意願的自由度又有多少洞察力?如丹尼爾·韋格納(Dniel Wegnen)在《有意識的意願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Couscious Will ,2002)中所說,當人們與行動有關的思想先於其行為時,人們會感覺他們是按意願做出這種行動的。否則,那行為似乎就很難解釋了。在韋格納的一項實驗中,兩個人共同操作一個電腦鼠標在一覆蓋著小圖片的“I型偵探(I-spy)”木板上滑行。當鼠標滑行時,被試會通過耳機聽到物體的名稱,然後可以停在任何想要的圖片上。甚至當其中一個人(主試的同夥)在某些任務中強迫鼠標停在某張特殊圖片上時,那些真正的被試通常認為鼠標停在該圖片上是他們自己 的意願。在類似這種情況下,大腦會產生個人功效的直覺。其他時間,比如當探尋水源或當一個人的胳膊在催眠暗示下舉起時,人們會誤以為這種外部意願是(或不是)其行動的原因。人們有時會犯錯。
預測我們的行為
人們在預測他人行為時同樣會犯錯。如果詢問他們是否會服從命令對別人實施強烈的電擊,或是他人在場時會不會對受害者提供幫助表現出遲疑,個體毫不猶豫會否認他們容易受其影響。但是通過實驗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多數人還是容易受其影響的。而且,結合悉尼·施勞格(Shrauger,1983)的發現,他讓大學生預測其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經歷各種不同事件的可能性(談一場浪漫的戀愛,生病,等等):他們的自我預測並不比根據日常經歷做出的預測更準確。
人們在預測他們的關係命運時同樣也會經常犯錯。約會中的一對情侶往往過於樂觀地預言他們的關係會天長地久。他們往往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感覺他們肯定會是永遠的戀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們有更好的瞭解,麥克唐納和羅斯(MacDonald & Ross,1997)通過對滑鐵盧大學學生的研究做出了以上報告。他們的父母和室友的客觀預測往往更加準確。(許多親眼目睹過孩子不聽任何勸告陷入某種有始無終關係的父母對此很贊同。)而當預測自己消極的行為比如哭泣或說謊時,自我預測卻比父母和朋友的預測更準確(Shrauger & others,1996)。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未來有時候甚至連你自己都很難預測。當進行自我預測時,最好的建議是思考過去在相似情境下的行為(Osberg & Shrauger,1986,1990)。那些瞭解你的人可能會比你能更好地預測你的行為(例如,當你同一個陌生人見面時你會如何緊張和語無倫次)。因此,要預測你的未來,就應思考自己的過去。
埃普利和鄧寧(Epley & Dunning,2000)發現,有時候人們預測別人的行動比預測自己的更加準確。在康奈爾大學每年的“水仙花日”慈善活動的前五週,埃普利和鄧寧讓學生預測他們是否會為慈善活動至少買一支水仙花,同時讓他們預測自己的同學中可能購買的比例。超過五分之四的學生預測自己會購買水仙花。但是實際上只有43%的人買了,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購買比例56%的預測接近。在一個圍繞金錢進行的實驗室遊戲中,84%的參與者預測自己會與其他人合作以共同獲益,而實際上只有61%的人做到了(此外,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合作比例64%的預測接近。)如果老子所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正確的,那麼很明顯大多數人是智大於明的。
預測我們的感覺
人生中會有許多重大的決定,其中包括對我們未來感覺的預測。和這個人結婚能一輩子都幸福嗎?加入這個行業會有滿意的工作嗎?這次休假會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嗎?還是最後結果更可能是離婚、失業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感覺——如果我們考試不及格,在大型比賽中獲勝,或用半小時漫步來減輕我們的緊張情緒。我們知道什麼會讓自己愉快,什麼會讓自己擔憂或感覺無聊。當然有時候,我們可能錯誤地預測自己的反應。如果在求職面試時被問起性騷擾的問題,自己會有什麼感覺,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Woodzicka & LaFrance,2002)調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們感到憤怒。然而,當實際提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女性更多地體驗到害怕。“情感預測”的研究顯示人們很難預測自己未來情緒的強度 和持續時間 (Wilson & Gilbert,2003)。人們會錯誤地預測自己談過一場浪漫的戀愛、收到禮物、錯過選舉、贏得比賽和被汙辱後的感覺(Gilbert & Ebert,2002;Loewenstein & Schkade,1999)。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向男青年呈現引發性喚起的圖片,然後向他們提供一個充滿激情的約會情節,在他們約會時要求他們“停止”,他們承認自己可能無法停止。如果他們事先沒有看過引發性喚起的圖片,他們會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當沒有性喚起時,個體會很容易錯誤地預測一個性喚起的人會如何感覺和行為——這種現象受到性慾強烈時發表愛的宣言,意外受孕,以及真誠地發誓“再也不會那樣”的性虐待者的強烈挑戰。
飢餓的購物者會比那些吃完了很多越橘鬆餅的人有更多的購買衝動(“那些油炸圈餅會很美味!”)(Gilbert & Wilson,2000)。當飢餓的時候,個體會錯誤地預測自己對油炸圈餅的食量。當吃飽了以後,個體會錯誤地預測深夜喝牛奶時再吃個油炸圈餅會很美味。
只有七分之一偶爾抽菸的人(每天少於一支)預測自己五年內會一直吸菸。但是他們低估了自己對藥物成癮的依賴,大約一半的人會繼續吸菸 (Lynch & Bonnie,1994)。
人們會高估暖冬、體重減輕、更多的電視頻道或更多的休閒時間對自己的積極影響。甚至一些極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國家彩票或意外遭受癱瘓,對長期幸福的影響也會低於多數人的想像。
我們的直覺理論似乎是:我們想要。我們得到。我們快樂。如果這是事實,這一章的字數就會少很多。實際上,吉爾伯特和威爾遜(Gilbert & Wilson,2000)指出,我們常常“錯誤地想要得到某些東西”。人們常常想像擁有一個有陽光、海浪和沙灘的田園荒島假期,但當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多麼需要日常生活、智力開發或時尚流行打扮”時,可能會很失望。我們通常會認為如果我們的候選人或小組贏得勝利,那我們會高興很久。但多個研究顯示我們對這些好消息的情緒痕跡消失得比自己預期的要快。
在消極 事件之後我們尤其會傾向表現出“影響偏見”——高估情緒事件的持久性影響。要求人們進行HIV檢測時預測其知道結果的五週後會有怎樣的感覺,他們預期自己會對壞消息感到痛苦,對好消息感到興高采烈。當五週以後,與他們的預期相比,得到壞消息的人較少痛苦,得到好消息的人較少高興(Sieff & others,1999)。吉爾伯特及其同事(1998)讓教授的助手來預測自己獲得或沒有獲得職位的幾年後的快樂程度,多數人認為好結果對他們未來的快樂很重要。“失去工作會壓碎我的生活目標。那是可怕的。”然而當事件過去幾年後再調查時,那些沒有得到職位的人與得到職位的人幾乎同樣快樂。
讓我們說得更私人化些。吉爾伯特和威爾遜讓我們想像:如果我們失去了非優勢手,一年之後會有怎樣的感覺。與現在相比,你會多快樂?
思考這件事的時候,你也許會認為這種不幸可能意味著:不能拍手,不能繫鞋帶,不能打籃球,不能用鍵盤。儘管你可能會永遠為失去而遺憾,但你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的快樂會受“兩件事:a)這一事件,b)其他所有事情”的影響。因為關注消極事件,使得其他所有事件對快樂的貢獻均會大打折扣,所以就會過高地預期自己的痛苦。“沒有什麼你所關注的事會帶來和你所認為的那樣大的差異,”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Schkade & Kahneman,1998)如是說。
此外,威爾遜和吉爾伯特(2003)還認為,人們會忽視自己心理免疫系統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其合理化策略,忽視、原諒和限制情緒創傷。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略的心理免疫系統(吉爾伯特和威爾遜稱之為免疫忽視 現象)令我們比自己預期得更容易適應殘疾、戀愛關係的中止、考試不及格、失去職位和個人與團隊的失敗。令人驚訝的是,吉爾伯特與其同事報告(2004),重大的消極事件(可以激活我們的心理防禦機制)可能比輕微的憤怒(不能激活我們的防禦機制)所引發的痛苦持續的時間反而更短。換句話說,我們是有恢復力的。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錯覺
因此,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對什麼會影響自己以及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與感覺的直覺經常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誇大這種情形。當行為的原因很明顯,而正確的解釋又符合我們的直覺時,這種自我知覺是準確的(Gavanski & Hoffman,1987)。賴特和裡普(Wright & Rip,1981)發現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可以辨別一個大學的特點(比如規模大小、學費和離家的距離)能在多大程度會影響他們對其的反應。但是當行為的原因對一個觀察者來說不是顯而易見的時候,那麼它們對行為者來說也不是顯而易見的。
如第3章將要解釋的,我們對發生在自己心裡的大部分事都沒有覺察。有關知覺和記憶的研究顯示,我們對自己思維的結果比對思維的過程知道得要多。凝視我們心靈的海洋,我們在它的意識層面底下卻什麼也看不見。無論如何,當我們放置生物鐘記錄時間以在指定的時間喚醒我們時,或當我們在一個問題無意識地“孵化”後自發獲得一種創造性靈感時,我們的確經歷了心理的無意識工作。舉例來說,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常常不知該如何報告其產生靈感的思維過程。
威爾遜(1985,2002)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控制 我們社會行為的心理過程與解釋 我們行為的心理過程截然不同。理性的解釋可能會因此而忽略實際上指引我們行為的內在態度。在九個實驗中,威爾遜及其同事(1989)發現對事和人表現出的態度常常能較好地預測以後的行為。如果他們事先讓被試分析 自己的感覺,那麼他們的態度報告將變得無效。例如,情侶伴隨自己關係的快樂感覺可以很好地預測在幾個月後他們是否會繼續約會。但是,如果被試在評價自己的快樂程度之前就已經列出其關係好或壞的所有原因,那麼當完成這一切之後,他們的態度報告在預測未來關係時變得無效!很顯然,仔細研究自己關係的過程會使個體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實上這些因素並沒有關係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們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爾遜(2002)如是說。
在稍後的研究中,威爾遜及其同事(1993)讓被試從兩個藝術海報中選擇一個帶回家。那些被要求在做出選擇並說明選擇理由 的被試都指出海報的幽默感是促使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他們可以更容易地描述其積極的特點)。但是幾周以後,他們對自己選擇的滿意度比那些僅僅靠感覺或一般性地選擇海報的人的滿意度低。萊文及其同事(Levine & others,1996)報告,與人們根據多種面部特徵做出的原因判斷相比,本能反應更一致。第一印象可能很有效。
威爾遜及其同事(2000)認為,這說明我們有雙重態度系統 (dual attitude system)。我們關於人或事的自動的內隱 態度通常與受意識控制的外顯 態度不同。例如,從兒童時期開始,我們可能會對那些我們現在所說的尊敬和欣賞的人保持一種習慣的、自動的恐懼或嫌惡。威爾遜指出,儘管可能外顯態度改變起來相對容易一些,“內隱態度就像老習慣一樣,改變起來非常緩慢。”然而通過重複練習——形成新的態度——新的習慣態度就能夠代替舊的態度。
米勒和特瑟(Millar & Tesser,1992)認為威爾遜誇大了我們對自我認識的無知性。他們的研究指出,吸引人們對原因 的注意會減少態度報告對由感覺 引發的行為預測的準確性。如果威爾遜提問時不讓人們分析其戀愛關係,而是提問有關其感覺的問題(“你和伴侶在一起和分開時會有怎樣的感覺?”),那態度報告可能更有洞察力。其他行為領域——比如,根據花費、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等方面的考慮選擇讀哪一所學校,等等——似乎是更受認知驅動的。對於這些問題,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覺更有用。儘管感覺有一定理由,但有時候頭腦的理性是決定性的。
這些對我們研究自我認識的侷限性具有兩種應用價值:第一是對於心理學調查,自我報告常常是靠不住的 ,自我理解中的錯誤限制了主觀個人報告的科學性。
第二是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報告和解釋其經驗的真實性無法保證這些報告的有效性。個人的證言具有強大的說服力量(見第15章司法社會心理學),但是這有可能是錯誤的。牢記這種潛在錯誤可以幫助我們較少地產生受人脅迫和上當受騙之感。
小結
我們對自我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組織思想和行為。當我們加工有關自己的信息時,我們可以很好地回憶它(一種叫做自我參照效應的現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導我們對與自我有關的信息進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圖式,和我們夢想或害怕成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對自我價值的整體認識,影響我們如何評價自己的特點和能力。
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響因素,包括我們扮演的角色,我們所做的比較,我們的社會同一性,我們如何知覺別人對我們的評價,以及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文化也會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別是在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假定存在一個獨立的自我。還有一些人,主要存在於亞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假定存在一個相互依賴的自我。如第5章會進一步解釋的,這些不同的觀念有助於解釋社會行為的文化差異。
我們的自我認識存在有趣的缺陷。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以這種方式行動。當觀察者也無法發現我們行為的有力影響作用時,我們也會忽視它。這些控制我們行為的內部的微妙過程可能與我們對它有意識的、清楚的解釋不同。我們也往往會錯誤地預測自己的情緒。我們會低估心理免疫系統的力量,並且因此傾向於高估我們對重大事件的情緒反應的持久性。
知覺到的自我控制
一些概念和研究指出知覺到的控制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思考了什麼是自我概念,它是怎樣發展的,以及我們充分了解自己的程度。現在讓我們根據觀察行動中的自我來看看為什麼自我概念會如此重要。
鮑邁斯特等人(Baumeister & others,1998,2000;Muraven & others,1998)指出,自我的活動能力是有限的。努力進行自我控制的人——強迫自己吃蘿蔔而不是巧克力,或壓抑被禁止的思想——隨後在遇到無解的難題時會更快放棄。看過令人心煩意亂的電影后,努力控制自己情緒的人其體力明顯減少。有意的自我控制會耗盡我們有限的意志力儲備。鮑邁斯特和艾克斯林(Julia Exline,2000)推斷在操作方面,自我控制類似於肌肉力量:兩者在使用後都會變得比較虛弱,但在休息時可以進行補充,並且隨著練習而加強。
不過,自我概念確實會影響我們的行為(Graziano & others,1997)。接受挑戰性的任務,想像自己通過努力工作而獲得成功的那些人會勝過那些想像自己是失敗者的人(Ruvolo & Markus,1992);想像你的積極可能性會讓你更可能計劃和制定一個成功的策略。這便是知覺到的自我控制。
自我效能
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97,2000)在他的研究中捕捉到積極思維的力量,並提出了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的理論。對自己能力與效率的樂觀信念可以獲得很大的回報(Bandura & others,1999;Maddux,1998;Scheier & Carver,1992)。自我效能感較高的兒童和成人更有韌性,較少焦慮和抑鬱。他們還生活得更健康,並且有更高的學業成就。
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效能指引我們制定有挑戰性的目標,並在面對困難的時候具有較強的韌性。一百多個研究顯示,自我效能可以預測工人的生產力(Stajkovic & Luthans,1998)。當出現問題時,較高的自我效能感會指引工人保持平靜的心態並尋求解決方案,而不是反覆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努力加堅持等於成就。伴隨著成就的獲取,自信就會增強。像自尊一樣,自我效能伴隨著辛苦付出後得來的成就而增強。
甚至對自我效能的微妙控制都能影響行為。利維(Levy,1996)下意識地給90個老年人呈現“有激活性的”(啟動)消極或積極的年齡類型詞,從而發現了這個現象。以0.066秒的時間間隔呈現一系列詞語,比如“下降”、“遺忘”和“衰老”,或“明智”、“聰明”和“有學問”。這些被試僅僅下意識地知覺到了光的閃現和模糊的點。但呈現積極的詞會導致他們“記憶自我效能”(對記憶的信心)的提高。呈現消極的詞則會有相反的作用。中國的老年人普遍具有積極的、受人敬仰的形象,其記憶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會更高,看來比在西方國家觀察到的老人遭受較少的記憶喪失(Schacter & others,1991)。
你的自我效能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感覺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如果你相信你可以做好一些事,這個信念會有什麼不同嗎?這取決於第二個因素:你有沒有控制住 結果?例如,你可能感覺自己是個合格的司機(高自我效能),但是感覺醉酒的司機開車會有危險(低控制)。你可能感覺自己是個有能力的學生或工人,但是害怕因自己的年齡、性別或外表而受到歧視,所以你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前景是黯淡的。
控制點
“我沒有社交生活,”一個40歲的單身男人對學臨床醫學的學生傑裡·法里斯抱怨。在法里斯的力勸下,這個病人蔘加了一個舞會,在那兒有好幾個女士和他一起跳舞。“我只是有點兒幸運而已,”他在稍後報告,“這可能不會再發生了。”當法里斯向他的導師朱利安·羅特報告這件事時,他明確了一個之前已經形成的想法。在羅特的實驗和治療中,有些人似乎一直“感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被外部力量支配的,而還有一些人則感覺發生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的努力和技巧所支配的”(Hunt,1993,p. 334)。
你是怎麼認為的?人們更常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還是環境的犧牲品?他們是自己生活的編劇、導演和演員,還是自己處境的俘虜?羅特把這個維度叫做控制點 (locus of control)。與法里斯一起,他設計了29組語言陳述來測量一個人的控制點。假如你在做這個測驗,那麼你更贊成哪些?
從長遠來看,世界上的每個人都應該得到他人的尊敬。 |
或 |
不幸的是,不管人們多麼努力,其價值在未得到眾人認可前就一晃而過了。 |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自己的事。 |
或 |
有時候我感覺我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 |
即使一個普通人也可能對政府決議產生影響。 |
或 |
這個世界是靠少數有權勢的人運轉的,小人物沒有什麼可為的。 |
在對羅特問題的回答中(1973),你認為你的命運是由自己來控制的(內部 控制點)?還是認為機會和外部力量決定了你的命運(外部 控制點,如圖2-6)?那些認為自己是內控的人更可能在學校表現優秀,成功戒菸,系安全帶,直接處理婚姻的問題,掙很多錢,並且可以延遲滿足以實現長遠目標(Findley & Cooper,1983;Lefcourt,1982;Miller & others,1986)。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感覺到控制取決於我們如何解釋挫折。也許你已經明白了學生常常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將糟糕的學習成績歸因於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比如他們覺得自己很笨,或老師、課本、考試太“糟糕”。如果訓練這些學生採取更有希望的態度——相信努力、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自律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學習成績會直線上升(Noel & others,1987;Peterson & Barrett,1987)。一般而言,具有自我控制感的學生——例如,同意“我善於抗拒誘惑”並且不同意“我花了太多錢”——會得到更好的成績,擁有更好的關係,並且心理更健康(Tangney & others,2004)。

圖2-6 控制點
成功的人更可能把挫折看成是一次意外,或者認為,“我需要嘗試新的方法。”那些把失敗看成是可控制的人壽保險銷售代表(“雖然很困難,但是經過堅持我會做好”)會賣掉更多保險。與其更悲觀的同事相比,他們中可能只有一半會在第一年中放棄(Seligman & Schulman,1986)。在大學游泳隊隊員中,那些有樂觀的“解釋風格”的人比悲觀的人更可能比預期表現得還要好(Seligman & others,1990)。就像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在《埃涅阿斯記》(Aeneid )中說的,“他們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
習得性無助與自我決定
對具有控制感的好處的研究也同樣出現在動物研究中。被關入籠內而無法逃避電擊的狗,會習得一種無助感。之後這些狗就算處在其他可以 逃避懲罰的條件下也只會被動地畏縮。狗如果學會了自我控制(成功地逃避開第一次電擊),會更容易適應新的情境。研究者馬丁·塞利格曼(Seligman,1975,1991)指出這種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在人類情境中也有類似之處。例如,抑鬱或苦惱的人變得被動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努力沒有任何作用。無助的狗和抑鬱的人都遭遇了意志癱瘓,被動順從,甚至死氣沉沉的冷漠(圖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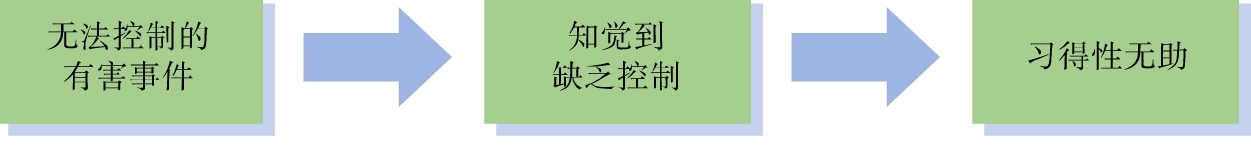
圖2-7 習得性無助
當動物和人經歷無法控制的有害事件時,他們就會習得一種被動和無助感。
在此我們想說明有些機構——不管是惡毒的,比如集中營,還是慈善的,比如醫院——如何令人失掉人性。在醫院裡,所謂的“好病人”是不按鈴,不問問題,不努力控制將要發生的問題的病人(Taylor,1979)。這樣的被動配合可能對醫院的效益有好處,但是卻不利於人的健康和生存。對你做的事和別人對你做的事失去控制可能會演變成令人不愉快的壓力事件(Pomerleau & Rodin,1986)。很多疾病與無助的感覺都與選擇性減少有關。這可能就是在集中營和療養院的病人會快速衰老和死去的原因。醫院裡那些通過訓練認為自己可以控制壓力的病人只需要較少的止疼藥和鎮靜劑,並且較少表現焦慮(Langer & others,1975)。
蘭格和羅丁(Langer & Rodin,1976)證實了個人控制的重要性,主要就是用兩種方法中的一種訓練一家高價的康涅狄格療養院的老年病人。一組慈善的看護者強調“我們的職責是讓你們為這個家感到自豪和幸福。”他們給被動的病人以正常的、好意的、有同情心的照料。三週以後,多數自我報告或由研究者和護士評價為更加虛弱。蘭格和羅丁另外一種訓練方法則促進了個人的控制,它強調選擇的機會、影響療養院政策的可能性和看護者的責任:“讓你過任何想要的生活。”這些病人可以做些小決定和履行一定的責任。在接下來的三週裡,這個組93%的病人表現出機敏、活力和快樂。
第一組的經驗與87歲的心理學家詹姆斯·麥凱(MacKay,1980)的經歷很類似:
去年夏天我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人。我妻子的膝蓋患有關節炎,而在那個時候,我的腿斷了。我們來到一個療養院。那兒只有療沒有養。醫生和護士長做所有的決定;我們僅僅是有生命的物體。感謝上帝那段時間只有兩週——療養院的護士受到了很好的訓練並且非常富有同情心;我認為那的確是城裡最好的療養院。但是我們從進入到離開都是微不足道的人。
研究證明,促進個人控制系統確實可以真正地增強個體的健康和幸福(Deci & Ryan,1987)。
對環境有一定控制權的囚犯——可以移動椅子,控制電視,並且開關電燈——會較少體驗壓力,較少出現健康問題,並且較少有故意破壞的行為 (Ruback & others,1986;Wener & others,1987)。
給工人完成任務的迴旋餘地和讓他們擁有一些決定權可以改善並重振士氣 (Miller & Monge,1986)。
和你一起住的人如果可以自己選擇早餐吃什麼,什麼時候去看電影,晚睡還是早起,那他們可能活得更久並一定會更快樂 (Timko & Moos,1989)。
庇護所裡無家可歸的居民很少可以選擇吃飯和睡覺的時間,更談不上控制自己的隱私權,所以在尋找住處和工作時更可能產生被動和無助感 (Burn,1992)。
像自由和自我決定這樣的好東西人們會嫌多嗎?Swarthmore大學的心理學家施瓦茨(Schwartz,2000,2004)聲稱個人主義的現代文化確實存在“過度的自由”,反而導致人們生活滿意度下降和臨床抑鬱症的增多。過多的選擇可能會導致無所適從,或像施瓦茨所說的“自由的專制”。在從30種果醬和巧克力中做出選擇後,人們表示其選擇的滿意度比那些從6種物品中做出選擇的人的滿意度低(Iyengar & Lepper,2000)。更多的選擇可能會帶來信息超載,也帶來更多後悔的機會。
在其他實驗中,人們對無法反悔的選擇(比如“最後大甩賣”中的選擇決定)的滿意度比對可以反悔的選擇(當允許退款和更換時)的滿意度要高。可笑的是,人們似乎喜歡和願意為推翻這種選擇的自由而付出代價。儘管這種自由“可能會讓你產生不滿意”(Gilbert & Ebert,2002)。擁有一些無法反悔的事會讓人們心理感覺好一點。該原則可能有利於解釋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Myers,2000a):國家調查數據顯示,過去人們對無法反悔的婚姻表示了更高的滿意度(“一次性成交”)。現在,儘管人們有了更多的婚姻自由,人們卻對他們擁有的婚姻表現出較低的滿意度。
總結反思 :儘管自由會走向極端,但個人控制總的說來還是有利於人的身心健康。心理學對知覺到的自我控制的研究是相對較新的,但是對其影響我們的生活和實現我們的潛能的強調卻是一貫的。阿爾傑(Horatio Alger)的書中“你能做好”的主題就是他一直堅持的思想。我們在諾曼·皮爾(Normen Vincent Peale)寫於20世紀50年代的暢銷書《積極思維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tive Thinking )(“如果你用積極的方式思考,你會得到積極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中發現了這種思想。我們在很多力勸人們以積極的心態取得成功的自助書和錄像中也發現了這種思想。
自我控制的研究為我們的傳統美德比如堅定不移帶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但是班杜拉強調自我說服(“我認為我能,我認為我能”)或有意地吹捧(“你太令人驚訝了!”)不能從根本上增強個體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的主要來源是對成功的體驗。如果你在減肥、戒菸或提高學習成績方面,通過努力獲得了成功,你的自我效能感就會增強。一個由鮑邁斯特(2003)領導的研究小組主張,“僅僅為他們是他們自己而稱讚所有的孩子,簡直是在使讚揚貶值。”有利於增強個體自尊的讚美會更好,“認可好的表現……當個體行為表現較好時,自尊因受到鼓勵而增強,僅其結果就會強化好的行為並使之加以改善。那些結果同時也有益於個體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
小結
很多研究表明了效能感和控制感的好處。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效率的人以及那些內控的人,比那些習得性無助和悲觀絕望的人會應對得更好,並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尊
自尊 (self-esteem)——我們全面的自我評價——是我們所有的自我圖式和可能的自我的總和嗎?如果我們把自己看做是有魅力的、強壯的、聰明的,並且命中註定會是富有的和被人愛的,我們就會有高自尊嗎?這就是心理學家們做的假設。根據這個假設他們提出,要使人對自己的感覺更好,就要讓他們感覺自己更有魅力、更強壯、更聰明等等。特別是克羅克和沃爾夫(Crocker & Wolfe,2001)主張,那些特殊領域對人們的自尊非常重要。“一個人的自尊可能取決於學校中的良好表現和外表的魅力,而另一個人的自尊可能取決於為上帝所愛和遵守道德標準。”因而,第一個人感覺自己很聰明很漂亮時會有較高的自尊,而第二個人則在感到自己很有道德時才會有較高的自尊。
但是布朗和達頓(Brown & Dutton,1994)主張,這種“自下而上”的自尊觀點並不全面。他們認為因果的箭頭可能是相反的。以綜合的方式評價自己的個體——那些高自尊的個體——更可能進一步評價自己的外表、能力和其他方面。他們更像是初為父母之人,愛他們的孩子,喜歡孩子的手指、腳趾和頭髮。(父母並不是先評價自己孩子的手指或腳趾,然後才決定如何從整體上評價孩子。)
為了證實他們關於整體自尊影響特殊自我感的觀點(“自上而下”),布朗和達頓給華盛頓大學的學生介紹了一種假設的品質,叫做“綜合能力”。(他們給學生呈現三個單詞——如“汽車(car)”、“游泳(swimming)”、“榜樣(cue)”——並要求他們想一個能聯結這三個詞的詞。提示:這個詞以p 開頭。)當告訴學生這種能力非常重要時,高自尊的人會比被告知這種能力沒什麼用時更可能報告他們有這個能力。看起來,在綜合方面對自己感覺良好的人,在其特殊的自我圖式(“我具有綜合能力”)和可能性自我上會發出玫瑰色光芒。
自尊動機
動機引擎(motivational engine)驅動著我們的認知機器(Dunning,1999;Kunda,1990)。面對失敗,高自尊的人會認為他人也和自己一樣失敗,並誇大自己相對於他人的優越性,以維持自己的自我價值(Agostinelli & others,1992;Brown & Gallagher,1992)。在失敗之後人們的生理喚醒水平越高,他們越容易以自我保護式的歸因來為失敗申辯(Brown & Rogers,1991)。我們決不只是冷冰冰的信息加工機器。
據佐治亞大學的特瑟(Tesser,1988)報告,“維持自尊”的動機可以預測許多有趣的發現,例如兄弟姐妹之間的摩擦。你是否擁有一個與你年齡相近的同性兄弟或姐妹?如果是的話,人們很可能會在你們成長的過程中對你們互相比較。特瑟推測,如果人們對你們倆中的一個人評價更高,就會促使另一個人以某種維持自尊的方式行事。(特瑟認為擁有一個特別能幹的弟弟或妹妹的人,其自尊受到的威脅是最嚴重的)。因此,那些擁有一個相當能幹的弟弟的人總能回憶起兄弟之間的相處不佳;而那些和弟弟能力不相上下的人,反而往往想不起來自己和兄弟之間有什麼摩擦。
自尊的威脅也可能發生於朋友之間,因為朋友的成功可能比陌生人的成功更有威脅(Zuckerman & Jost,2001)。它同樣可以在夫妻之間發生。儘管夫妻之間具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但相同 的事業目標仍然會使他們產生緊張和嫉妒(Clark & Bennett,1992)。類似地,人們最嫉妒那些既是同行裡的佼佼者又是情敵的人(DeSteno & Salovey,1996)。
維持或增強自尊動機的意義是什麼呢?利裡(Mark Leary,1998,1999)認為,我們的自尊感猶如汽車上的油量指示燈。正如我們先前注意到的,人際關係對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導向意義。因此,當我們遭遇威脅性的社會拒絕時,自尊指示燈會警告我們,以促使我們更敏銳地覺察他人對我們的期望。研究證實社會拒絕會降低我們的自尊,同時增強我們渴望被接受的意願。當我們被藐視或拋棄時,我們感到自己缺乏魅力,能力不足。這種痛苦如同駕駛艙裡閃爍的指示燈一樣,會驅使我們通過行動來發展自我,並在其他地方尋求社會接納和認同。
自尊的陰暗面
低自尊的人在抑鬱、濫用毒品和各種形式的行為過失方面面臨更多的風險。高自尊則有利於培養主動、樂觀和愉快的感覺(Baumeister & others,2003)。而那些在“很小的年齡”就開始性活動的男孩子傾向於有比平均值更高 的自尊。道斯(Dawes,1994,1998)指出,那些黑幫頭目、極端種族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也同樣具有更高的自尊。
當發現自己高傲的自尊受到威脅時,人們常常會以打壓他人的方式來應對,有時甚至是以暴力的方式反應。一個心高氣傲的孩子,如果又遭到社會性拒絕的威脅和挫折,那將是相當危險的。在一項實驗中,希瑟頓等人(Heatherton & Vohs,2000)以在能力測驗中的失敗性來威脅一組大學生,而另一控制組則不受此威脅。結果,只有那些高自尊的人在面對威脅時會表現出明顯的敵意(圖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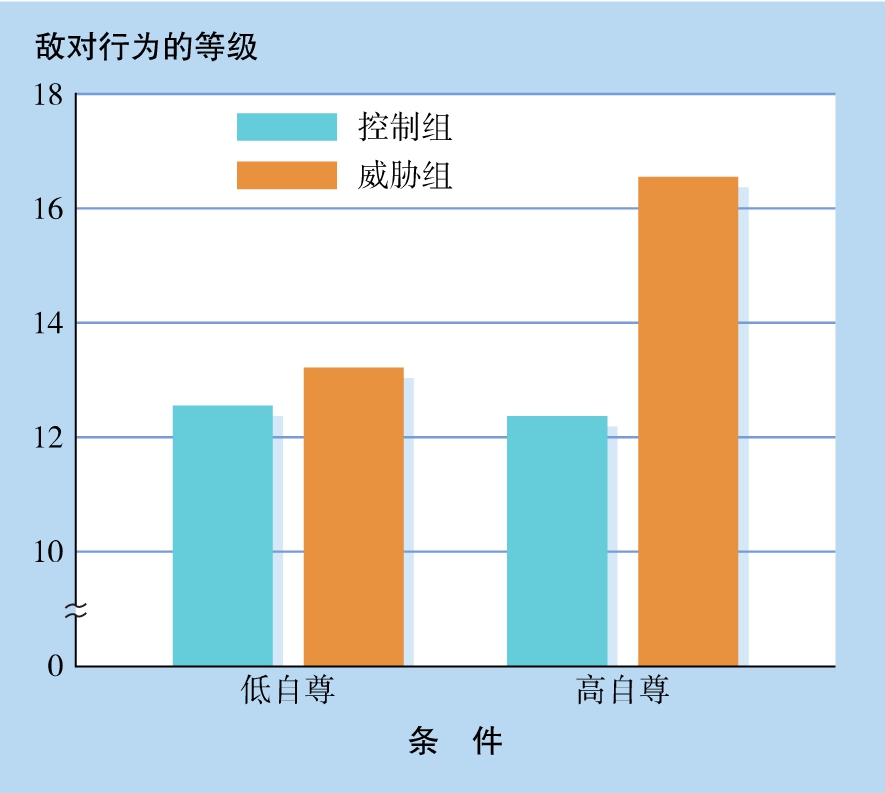
圖2-8 當高傲的自尊受到挑戰時
當感覺受到威脅時,只有高自尊的人會變得非常敵對——驕傲、粗魯而且不友好。
資料來源:From Heatherton & Vohs,2000.
在另一個實驗中,布什曼和鮑邁斯特(Bushman & Baumeister,1998)讓540名大學生志願者分別書寫一段話,並由另一個學生對他們進行誇獎(“好文章!”)或做出諷刺性的評價(“這是我所見過的最爛的文章”)。然後讓那些文章作者們和其他學生一起玩一個反應時的遊戲。當某個人的對手失敗時,該作者就可以用任意強度和任意時間長度的噪音來攻擊該對手。在文章受到批評後,那些自尊最強的人——同意“自戀的”陳述比如“我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具有異常的攻擊性。”他們使用噪音折磨的時間長度是普通自尊者的3倍。受傷的自尊心引發了報復性行為。
鮑邁斯特(1996)說,“那些滿懷熱情地倡導自尊運動的主張基本上不是幻想就是胡說八道,”他自稱“發表的有關自尊的研究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自尊的影響是微小的,有限的,而且並不都是好的。”他指出,高自尊的人常常是令人討厭的,而且常常喜歡插嘴打斷別人,他們喜歡對人評頭論足,而不是與人交談(與那些害羞、謙虛、不愛出風頭的低自尊的人相比)。“我的結論是,自制遠遠比自尊更有價值。”
那麼,那些常常做壞事的自我膨脹的人,是否是在掩飾他們的內在不安全感和低自尊呢?那些過分自信和自戀的人,是不是在用一個誇大自我的面具來掩蓋其弱小的自我呢?許多研究者都試圖要找到包藏在這種外殼裡的低自尊。然而,通過對欺詐者、黑幫成員、種族滅絕的獨裁者和令人討厭的自戀者的研究,並沒有發現相關的證據。鮑邁斯特和他的合著者(2003)指出,“希特勒具有非常高的自尊。”
道斯(1994)總結說,“隱蔽的自尊缺乏是新世紀心理學家的以太,以太曾經被認為是佈滿整個空間的光波媒介。經證實它是無法探測到的,而且以太的概念隨著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引入而被放棄了。認為隱蔽的低自尊是萬惡之源的信念甚至更加荒謬,所有現有的證據都和它矛盾。”
高自尊的陰暗面也存在於壓力中,同時也發現低自尊的人在各種臨床問題面前表現得更加脆弱,這些問題包括焦慮,孤獨,飲食障礙。當感覺很糟糕或受到威脅時,他們更傾向於透過有色眼鏡來看待一切——注意並記住別人最壞的行為並認為伴侶不愛自己(Murray & others,1998,2002;Ybarra,1999)。
薩米瓦利(Christina Salmivalli)和她在芬蘭特基大學的同事(1999)進一步指出,黑幫成員表現出的是一種自衛式的誇大自我的自尊模式。那些具有“真正自尊”的人,即那些無需通過尋求成為注意焦點或被批評激怒後才能明確感到具有自我價值的人,會更經常地去保護暴力行為中的受害者。當確信自己感覺很好的時候,我們的自我防禦意識會降低(Epstein & Feist,1988;Jordan & others,2003)。我們也不會那麼臉皮薄和好評論,不會去吹捧那些喜歡我們的人或指責不喜歡我們的人(Baumgardner & others,1989)。
和自尊脆弱的人相比,把自尊更多地建立在良好的自我感覺而不是分數、外貌、金錢或別人的讚美的基礎上的自尊感明確的人,會一直感到狀態良好(Kernis,2003;Schimel & others,2001)。克羅克及其同事(Crocker & others,2002,2003,2004)對密歇根大學的學生進行的研究證實了這一點。與自尊建立在如個人品質這樣的內部因素的人相比,自尊主要建立在外部因素基礎上的自我價值感脆弱者會經歷更多的壓力、憤怒、人際關係問題、吸毒酗酒以及飲食障礙。克羅克和帕克(Crocker & Lorar Park,2004)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試圖通過變漂亮、富有或受人歡迎來尋求自尊的人,對真正有利於提高生活質量的東西卻視而不見。進一步講,如果良好的自我感覺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就不會不把批評放在心上,我們會更加傾向於去批評別人而不是對他們傾注感情,更加傾向於在壓力下追求成功而不是僅僅在行動中獲得快樂。克羅克和帕克指出,時間久了,如此尋求自尊並不能滿足我們對能力、人際關係和自主性的深層需求。對自我形象少關注一些,多注意培養自己的才能和發展人際關係,因為這些最終會給你帶來更大的幸福感。
自我服務偏見
當我們加工和自我有關的信息時,會出現一種潛在的偏見。我們一邊輕易地為自己的失敗開脫,一邊欣然接受成功的榮耀,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把自己看得比別人要好。這種自我美化的感覺使多數人陶醉於高自尊光明的一面,而只是偶爾會遭遇到其陰暗的一面。
人們大都認為,我們中的多數人都受著低自尊的折磨。幾十年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斷言他所見過的多數人都“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既沒用又惹人煩。”許多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普及者也同意這一點。“我們所有人都有自卑情結,”約翰·鮑威爾(John Powell)聲稱,“那些看起來沒有自卑情結的人只是在偽裝而已。”正如馬克斯(Marx,1960)所嘲諷的:“我不想參加任何一個會接受我為其成員的社團。”
而事實上,我們多數人都對自己感覺不錯。在對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在給自己打分時也基本使用中等的評分標準,(一個低自尊的人也會用“有時”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限定性形容詞來給“我有些好主意”這樣的句子打分。)更進一步地講,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最富挑戰性而且證據確鑿的結論也和自我服務偏見 (self-serving bias)有關。
對積極和消極事件的解釋
好幾個實驗已經發現,當得知自己成功後,人們樂於接受成功的榮譽。他們把成功歸結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卻把失敗歸咎於諸如“運氣不佳”,“問題本身就無法解決”這樣的外部因素(Campbell & Sedikides,1999)。同樣地,在解釋勝利時,運動員一般會將其歸因於自我本身,對於失敗則推脫給其他因素,諸如錯誤的暫停,不公平的判罰,對手過於強大或是黑哨(Grove & others,1991;Lalonde,1992;Mullen & Riordan,1988)。還有,想想看汽車司機們願意為自己的事故承擔多少責任呢?在保險單上,司機們總是這樣描述他們的事故:“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輛車,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剛到十字路口,一個路障忽然彈起來擋住了我的視線,以至於我沒看見別的車。”“一個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鑽到我車輪下面去了”(Toronto News ,1977)。
在那些既靠能力又憑運氣的情境(遊戲、考試、應聘)裡,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成功者往往認為成功源於自己的能力,而把失敗歸因於壞運氣。我在拼字遊戲中贏了,那是因為我語感好。要是我輸了,那是因為,“遇到個Q卻沒有U,這種題誰做得出來?”類似地,政治家們也傾向於把勝利歸功於自己(勤奮工作,為選民服務,聲譽和策略),把失敗歸因於不可控的因素(本選區政黨的組織問題,對手的姓名,政治趨勢)(Kingdon,1967)。當公司利潤增加時,CEO們把這個額外的收益歸功於自己的管理能力,而當利潤開始下滑時則會想: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還能指望什麼呢?
羅斯和西科利(Ross & Sicoly,1979)還研究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務偏見。他們發現,加拿大已婚的年輕人通常認為,他們在清理房間或照顧孩子這些方面所承擔的責任,要比配偶認為得多。在一個全國性的調查中,91%的妻子認為自己承擔了大部分的食品採購工作,但只有76%的丈夫同意這一點(Burros,1988)。在其他研究中,妻子們對自己所承擔家務的比例的估計,也高於丈夫們對她們的評估(Bird,1999;Fiebert,1990)。每天晚上,妻子和我總會把要洗的衣服隨手丟到臥室盛衣籃的外面。第二天早上,我們中的一個會把衣服揀起來放進籃子裡。當她對我說:“這次可該你去揀了”的時候,我想,“哼,十有八九都是我去揀的。”於是我問她:“你覺得有多少次是你揀的?”“噢,”她答道:“差不多十有八九吧。”
這些有關承擔責任的自我服務偏見會導致婚姻不和,員工不滿和討價還價時的僵持局面(Kruger & Gilovich,1999)。對於離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責任歸罪於對方(Gray & Silver,1990),或是經理把低業績歸咎於員工缺乏能力或不夠賣力(Imai,1994;Rice,1985)就不足為奇了。(而工人們則更願意歸因於一些外在的東西——供給不足,負擔過重,同事太難相處,任務目標好高騖遠。)同樣地,當人們得到比別人更多的獎勵(如加薪)時,他們認為獎勵很公平(Diekmann & others,1997)。
我們總是將成功與自我相聯繫而刻意避開失敗對自我的影響,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ECON考試得了A”相對於“歷史考試教授給了我個C。”把失敗或挫折歸因於客觀條件甚至別人的偏見,這總不會比承認自己不配獲得成功更讓人沮喪吧(Major & others,2003)。威爾遜和羅斯(Wilson & Ross,2001)指出,我們更樂於承認那些已經快淡忘的從前具有的缺點,認為那是“過去的我”具有的。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們在描述上大學前的自己時,其肯定與否定的描述一樣多。但在描述現在的自己時,肯定的描述是否定的3倍。“我比原來見多識廣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數人這樣推斷說。過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軍。
學生也顯示出自我服務偏見。得知考試成績後,那些成績好的人傾向於接受個人型歸因,把考試看成對他們能力的一種有效檢驗(Arkin & Maruyama,1979;Davis & Stephan,1980;Gilmor & Reid,1979;Griffin & others,1983)。那些成績差的學生則更容易去批評考試本身。
看了上述這些研究後,我不禁覺得“這有什麼,我早就知道了。”然而再想想教師們是如何解釋學生們的好成績或差成績的。當無需故作謙虛時,教師們傾向於把優異的教學成績歸功於自己,而把失敗歸咎於學生(Arkin & others,1980;Davis,1979)。看起來,教師們更願意這樣推斷:“在我的幫助下,瑪莉亞順利地畢業了;不管我怎麼幫梅琳達,她還是因沒能及格而退學了。”
每個人都高於平均水平,這可能嗎
當人們拿自己和別人比較時,也會出現自我服務偏見。如果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譯者注:“所以明智的人去除過份,去除奢華,去除驕縱。”英文原文是At no time in the world will a man who is sane Over-reach himself,Over-spend himself,Over-rate himself.)是正確的,那我們多數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數主觀 的和社會讚許性 方面,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總體水平相比,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勝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並且在自我評價時也更為客觀(見“聚焦:自我服務偏見——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有哪些方面”)。
似乎每一個群體,都像加里森·基勒的小說《沃伯根湖》一樣,“所有婦女都很強壯,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也許造成這種樂觀主義的一個原因是:雖然12%的人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老,但遠多於此的人(66%)都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年輕(Public Opinion ,1984)。這上面的一切讓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個笑話:一個丈夫對妻子說:“如果咱們倆中的一個先去世,我想我會搬到巴黎去住。”
相對於客觀行為維度(如“守時的”),主觀行為維度(如“有教養的”)會引發更強烈的自我服務偏見。學生們在“品德”方面比在“智力”方面更可能把自己評為優秀的(Allision & others,1989;Van Lange,1991)。而絕大多數社區居民也認為自己比周圍的多數人更“關心 ”環境,飢餓和其他社會問題,雖然他們並不認為在這些問題上自己比別人幹 得更多,花的時間或金錢更多(White & Plous,1995)。教育無法消除這種自我服務偏見;甚至社會心理學家們也會暴露出這種自我服務偏見,他們認為自己比其他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更道德(Van Lange & others,1997)。
聚焦 自我服務偏見——如何愛自己?讓我們看看都有哪些方面
戴夫·巴里(Dave Barry,1998)指出,“無論年齡、性別、信仰、經濟地位或種族有多麼不同,有一件東西是所有人都有的,那就是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相信,我們比普通人要強。”我們也相信我們在多數主觀的和令人嚮往的特質上強於一般人,自我服務偏見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倫理道德 。大多數生意人認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Brenner & Molander,1977)。一個全國性調查有這樣一道題目:“在一個百分制的量表上,你會給自己的道德和價值打多少分?”50%的人給自己打分在90分或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給自己打分在74或74以下(Lotett,1997)。
工作能力 。90%的商務經理對自己的成就評價超過對其普通同事的評價(French,1968)。在澳大利亞,86%的人對自己工作業績的評價高於平均水平,只有1%的人評價自己低於平均水平(Header & Wearing,1987)。大多數外科醫生認為自己患者的死亡率要低於平均水平(Gawande,2002)。
優點 。在荷蘭,大部分高中生認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誠實,更有恆心,更有獨創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駕駛技術 。多數司機——甚至大部分曾因車禍而住院的司機——都認為自己比一般司機駕車更安全且更熟練(Guerin,1994;McKenna & Myers,1997;Svenson,1981)。
聰明才智 。大部分人覺得自己比周圍的普通人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Public Opinion ,1984;Wylie,1979)。當有人超過自己時,人們則傾向於把對方看成天才。
忍耐度 。在1997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中,只有14%的美國白人在黑人歧視程度的10點量表(0分到10分)上打分達到或超過5。可是在給其他白人打分時,44%的白人的分值達到或超過5。
贍養父母 。多數成年人認為自己對年邁父母的贍養比自己的兄弟姐妹們多(Lerner & others,1991)。
健康 。洛杉磯居民認為自己比大多數鄰居更健康,而多數大學生認為他們將比保險公司預測的死亡年齡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C.R. Snyder,1978)。
洞察力 。我們假定,他人的語言和行為能夠體現他們的本質。我們私下的想法也是如此。因此,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們比別人更瞭解我們自己。我們也認為比起別人來,我們更瞭解自己(Pronin & others,2001)。很少有大學生會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天真或更傻,但他們會認為別人要比他們傻得多(Levine,2003)。
擺脫偏見 。人們往往認為他們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偏見的影響(Provine & others,2002)。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比多數人更不容易產生自我服務偏見。
在我們構建成功的定義時,上述主觀因素會為我們提供一定的迴旋餘地(Dunning & others,1989,1991)。在評價自己的“運動能力”時,我可能會想到自己參加的籃球大賽,卻不會記起自己擔任少年棒球聯賽球員時躲在右外場的痛苦日子。在評價自己的領導能力時,我會想像出一個和我風格相近的偉大領袖的形象。通過為自己制訂一個模稜兩可的標準,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比較成功的。在高考委員會對829000名高中高年級學生的調查中,沒有人在“與人相處能力”這一主觀而讚許性的維度上對自己的打分低於平均值,然而有60%的人的自評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則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1%!
我們還會認為自己擅長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有利於維持我們的自我形象。在一學期結束後,那些在計算機科學導論課程中成績突出的學生會認為在當今世界一個懂計算機的人會具有更多的價值,而那些學得不好的人則更可能去嘲笑計算機只不過是雕蟲小計,並把計算機技能作為與自我形象無關的東西而排除掉(Hill & others,1989)。
盲目樂觀
樂觀主義為人生預先假設了一條積極的道路。“那些樂天派們”,傑克遜·布朗(Brown,1990,p.79)說,“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說:‘早安呀,上帝’,那些悲觀者則會在窗前說:‘天哪,又一個早晨來了。’”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就像研究者尼爾·溫斯頓(Weinstein,1980,1982)所形容的,“對未來的生活事件盲目樂觀。”例如,在Rutgers大學,學生們往往認為自己遠比其他同學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領高額薪水和擁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極的經歷,諸如酗酒成癮,在40歲以前突發心臟病,或遭遇槍擊則更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在蘇格蘭和美國,大部分處於青春期後期的孩子們認為自己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要比同伴們小得多(Abrams,1991;Pryor & Reeder,1993)。在經歷了1989年的大地震之後,舊金山灣區的學生們曾經一度放棄了他們關於“我可不像其他人那麼容易遭遇到天災人禍”的樂觀看法,但僅僅過了三個月,這種虛幻的樂觀 (illusory optimism)就復燃了(Burger & Palmer,1991)。
林達·波洛弗(Perloff,1987)注意到,虛幻的樂觀會增強我們的脆弱性。由於相信自己總能倖免於難,我們往往不去採取明智的預防措施。在一項調查中,137對婚姻裡剛好有一半是由離婚而終結,然而這些人在當初領取結婚證時絕大多數都認為自己將來離婚的可能性是零(Baker & Emery,1993)。性活動比較頻繁而不願堅持避孕的女大學生們則認為和學校裡其他同學相比,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懷孕(Burger & Burns,1988)。
那些滿不在乎地把車座安全帶丟在一邊的人,那些不肯承認吸菸會危害身體健康的人,還有那些陷入註定要結束的關係裡的人們,無一不提醒我們,盲目樂觀如同傲慢一樣,是失敗的先兆。
在賭博時,樂觀者比悲觀者更能堅持,即使是連續不斷地在輸錢(Gibson & Sanbonmastu,2004)。如果經營股票或房地產的商人覺得自己的商業直覺遠遠超過自己的競爭者,他們同樣也可能會體驗到嚴重的失落感。甚至17世紀人類理性經濟的捍衛者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預見人類將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認為,這種“對自己好運的荒謬的推斷,”來源於“絕大多數人對自身能力的一種自負的幻想”(Spiegel,1971,p.243)。
樂觀主義在增強個體自我效能感,促進健康和安寧方面確實比悲觀主義強得多(Armor & Taylor,1996;Segerstrom,2001)。作為天生的樂天派,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未來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更幸福——這種信念的確有助於營造當前的快樂心態(Robinson & Ryff,1999)。
18~19歲的美國青少年中有一半人想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或“非常”有可能富有時都會感到振奮(一種隨著年齡增長而信奉者越來越少的信念)。然而少量的現實主義——或者如朱莉·諾雷姆(Julie Norem)所稱的“防禦性悲觀主義”——可以把我們從盲目樂觀的危險中拯救出來。那些高估自己學習能力的大學新生經常會體驗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Robins & Beer,2001)。防禦性的悲觀主義者會預見問題的發生並且促使自己進行有效地應對。正如一句中國成語所說,“居安思危”。自我懷疑則可以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多數學生——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註定低分的學生——在考試來臨時都顯示出過分的樂觀(Prohaska,1994;Sparrell & Shrauger,1984)。(這種虛幻的樂觀常常隨著考試成績公佈日期的接近而消退——Tayor & Shepperd,1998。)那些過分自信的學生傾向於不做充分的準備。和他們能力相當但更焦慮的同伴們,則因為擔心在未來的考試中失敗而會加倍努力地學習,最後通常會獲得較高的成績(Goodhart,1986;Norem & Contor,1986;Showers & Ruben,1987)。
警世語:要想在學校裡獲得成功和出類拔萃,既需要足夠的樂觀精神以支撐希望,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悲觀心態以激起對利害的關注。
虛假普遍性和虛假獨特性
為了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常常表現出這樣一種奇怪的傾向:過分高估或低估他人會像我們一樣思考和行事。在觀點 方面,我們過高地估計別人對我們觀點的贊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現象被稱為虛假普遍性效應 (false consensus effect)(Kruenger & Clement,1994;Marks & Miller,1987;Mullen & Goethals,1990)。如果我們贊成加拿大全民公決或是支持新西蘭國家黨,我們會滿懷希望地以為別人也持同樣的觀點(Babad & others,1992;Koestner,1993)。好像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種常識。
如果我們行為不佳或是在任務中失敗,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失誤是正常的,以讓自己安心。當某個人對別人說謊之後,他便開始覺得其他人也是不誠實的(Sagarin & others,1998)。他會覺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樣思考和行事:“我是說謊了,可別人不也都如此嗎?”如果我們隱瞞個人所得稅或吸菸,我們常常會高估跟我們有同樣行為的人的數目。如果我們對另一個人產生了性興趣,我們也許會高估對方對自己的慾望。四個最近的研究指出:
在禁澡期間偷洗澡的人會認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樣的事情(Monin & Norton,2003)。
劇烈運動後口渴的人會想像,跟飢餓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會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溫斯坦(Boven & Lowenstein,2003)做的一項研究表明,88%剛做完運動的口渴者會做出這樣的猜測,而那些將要去運動的人中只有57%會這樣想。
當人們自己的生活發生變化時,可能會認為整個世界也在發生變化。具有保護意識的初為人父母者也會認為世界更加危險。此外,節食減肥的人會認為食品廣告更具欺騙性 (Eibach & others,2003)。
對其他民族懷有消極看法的人推測很多人都會懷有這樣消極的僵化思想 (Krueger,1996)。因此我們對別人思維的感知可能會揭示出一些我們自己的東西。
塔爾瑪德(Tahmud)說:“我們並不是客觀地看待事物,而是總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來看待事物。”
虛假普遍性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們的歸納性結論只是來自一個有限的樣本,而這個樣本顯然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Dawes,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們自己內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們自己的認識推及別人,用自己的反應作為線索來推斷別人的反應呢?此外,我們多半和那些同我們態度和行為相近的人交往,並透過這些熟悉的人來評判世界。
而在能力 方面,當我們幹得不錯或獲得成功時,虛假獨特性效應 (false uniqueness effect)則更容易發生(Goethals & others,1991)。我們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尋常的,以滿足自己的自我形象。這樣,那些喝得醉熏熏也不繫安全帶的司機會高 估(虛假普遍性)其他開車的醉鬼的數量,而低 估(虛假獨特性)系安全帶的普遍性(Suls & others,1988)。從我們更多地把優點而非缺點歸因於自己的傾向出發,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這樣的結論(Gross & Miller,1997;Krueger,1997;Krueger & Clement,1997)。某種行為越不常見,我們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頻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則人們會把相對於自己的其他人中自私者的數目估計得遠遠高於20%)。這樣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失誤是相對普遍的,而我們的優點卻是非同尋常的。
總之,自我服務歸因,自我恭維的比較,盲目樂觀,以及認為自己缺點的虛假普遍性,所有這些傾向是導致自我服務偏見的根源(圖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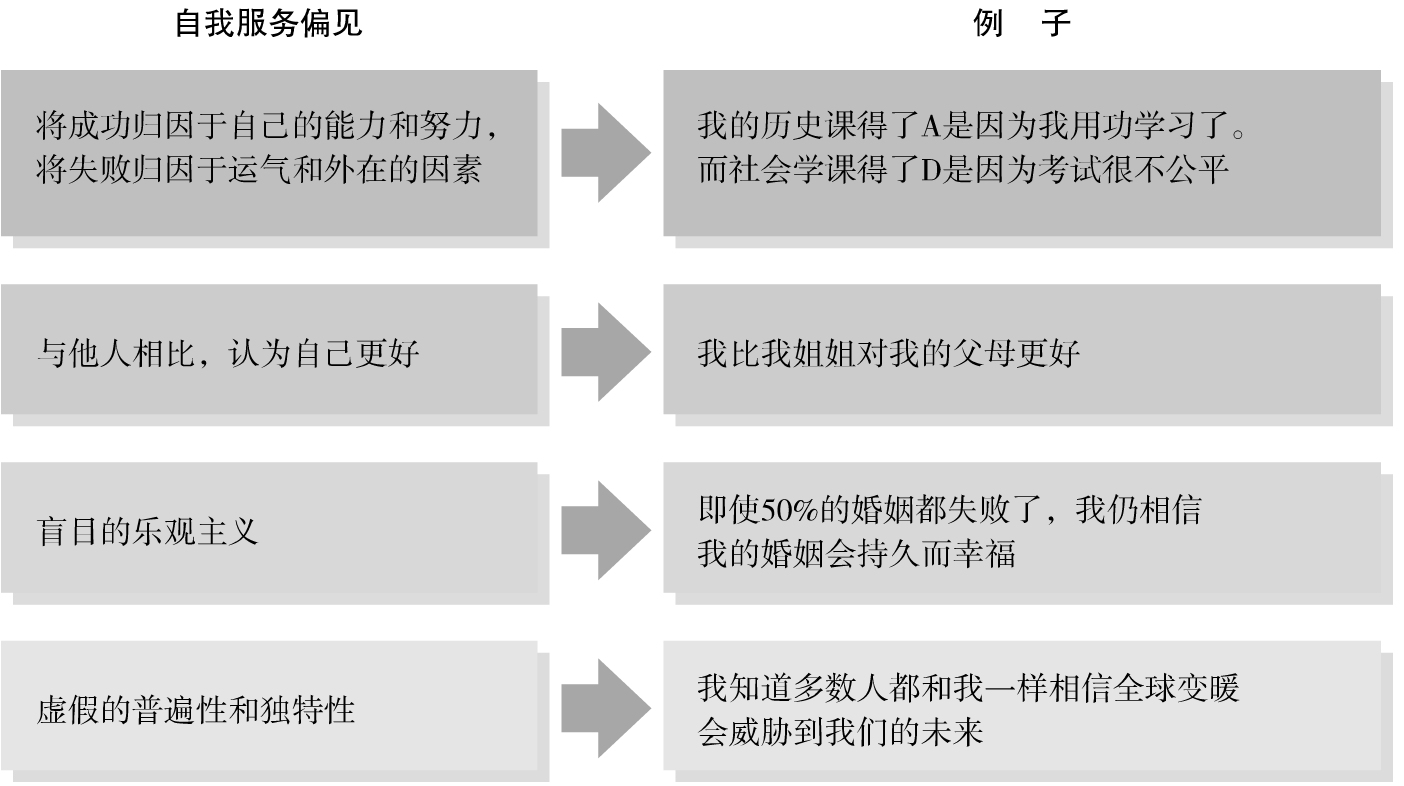
圖2-9 自我服務偏見如何起作用
對自我服務偏見的解釋
為什麼人們會以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呢?一種解釋將自我服務偏見看做是我們如何處理和記憶有關自己個人信息的副產品。回想一下之前的一個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務。正如邁克爾·羅斯和西科利(Sicoly,1979)所指出的,也許這不正是由於我們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過什麼而往往很難回憶起自己沒做過什麼或者僅僅是看他人在做嗎?我能很容易想到這樣的畫面,自己開始洗衣服,但我很少能意識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數有多少。
那麼這種有偏見的知覺僅僅是一種知覺錯誤,一種關於我們如何處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傾向嗎?或者,也會有自我服務動機在其中呢?現在,從研究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有多種動機。我們尋求自我認識,渴望評定自己的能力(Dunning,1995)。我們尋求自我證實 ,渴望驗證自我概念(Sanitioso & others,1990;Swann,1996,1997)。我們尋求自我確認,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Sedikides,1993)。自尊的動機也促進了自利偏差的出現。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務偏見的反思
許多讀者肯定會覺得,自我服務偏見或者給人們帶來沮喪苦惱感,或者讓人覺得自己能力很高。的確,當那些帶有自我服務偏見的個體面對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籌的人時,會有自卑感。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持有自我服務偏見。確實有一些人正承受著低自尊的痛苦。
在實驗中,自尊剛受到打擊的人(例如被告知在智力測驗中的成績很差),更容易去貶低他人(Beaureguard & Dunning,1998)。自我(ego)剛受到創傷的人相對於自我剛被提升的人會更傾向於用自我服務來解釋成功和失敗(McCarrey & others,1982)。因此自尊受到威脅後,可能會激活自我保護性的防禦機制。當個體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時,他們會使用自誇、推脫和貶低他人等方式來肯定自己。更普遍的是,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傾向於會對他人的怠慢作出過激的反應,其實他們感受到的拒絕並不存在,而只是因為他們慣於責備別人(Murray & others,2002;Wills,1981)。取笑別人的人其實和被取笑者一樣可笑。
高自尊和自我服務偏見總是形影不離。那些在自尊測驗中得高分的人,即那些用好話來評價自己的人,在解釋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時,在評估其所在的團隊時,在拿自己和別人相比時,同樣會用好話來評價自己(Brown,1986;Brown & others,1988;Schlenker & others,1990)。
自我服務偏見的適應性
自尊有其陰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當好的一面出現時,相比於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的人往往更能盡情享受並保持這種良好的感覺(Wood & others,2003)。即使是錯覺性的自我提升也是與許多心理健康指標聯繫在一起的。謝莉·泰勒和她的同事(Taylor & others,2003)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擁有更多的天賦和積極的品質能使我們對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覺,而且這種對自己的正性的感覺能為我們提供應付日常生活中的壓力環境的資源”(Snyder & Higgins,1988;Taylor & others,2003)。非抑鬱的人將他們的失敗歸於實驗任務或者其知覺受到的控制比實際程度更高。而抑鬱者的自我評價及其對他人如何真實看待他們的評價都沒有表現出誇大(詳見第14章)。
格林伯格等人(Greenberg,Solomon & Pyszczynski,1997)在他們的“恐怖管理理論”中提到了積極自尊適應性的其中一個理由——它可以緩解焦慮,包括我們對死亡的焦慮。童年我們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我們達到了父母的要求,就會受到關愛和保護;如果我們沒有達到這種要求,父母可能就會收回對我們的關愛和保護。這樣,我們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聯繫起來了。格林伯格等人認為,積極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們消除對最終的死亡的恐懼感。他們的研究表明,提醒人們個體終究都會面臨死亡(讓人們寫一篇關於死亡的短文)有利於個體肯定自我價值。而且,當面臨威脅時,較強的自尊可以減輕焦慮。
正如有關抑鬱和焦慮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務知覺中可能存在某些實用的智慧。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自我更聰明,更強大,更成功,這也許是一種有利的策略。騙子們同樣會顯得更誠實可信,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話。對自我的積極信念同樣會激發我們去努力(自我實現預言),並在艱難歲月中保持希望。
自我服務偏見的不良適應
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產生的驕傲感可以幫助我們抵制抑鬱,但它也會給人們帶來一些不良適應。那些因自己出現社交困難而責備別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夠承認是自己的問題的人更不快樂(Anderson & others,1983;Newman & Langer,1981;Peterson & others,1981)。
施倫克爾等人(Schlenker,1976;Schlenker & Miller,1977a,1977b)的研究同樣表明,自我服務知覺在一定程度上會毀掉一個群體。大學期間作為搖滾樂隊的一名吉他手,施倫克爾注意到“樂隊成員總是高估自己對群體成功的貢獻而低估他們對失敗所負的責任。許多很棒的樂隊都是由這些自我讚揚傾向所引發的問題而解體的。”後來他成為佛羅里達大學一名社會心理學家,並對群體成員的自我服務知覺進行了研究。在9個實驗中,他讓實驗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務。然後他故意告訴他們,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實驗中,成功組的成員宣稱自己為本組的成功所做的貢獻要高於失敗組成員。當小組成功時,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別人貢獻得多,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沒做什麼貢獻。
如果多數的群體成員都認為,雖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但自己的報酬卻太低且沒有得到應有的讚賞,那就可能引發不和與嫉妒。大學校長和教務主任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90%的大學員工都認為自己相對於同事們是很傑出的(Blackburn & others,1980;Cross,1977)。因此,當宣佈加薪時,總有一半的人會得到平均水平或低於平均水平的薪金,難怪他們會覺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務偏見還會誇大人們對自己群體的評價。當各個群體之間進行比較時,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群體是最傑出的(Codol,1976;Jourden & Heath,1996;Taylor & Doria,1981)。
多數大學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都認為自己群體內的成員不如其他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那樣愛逞能和勢利眼。
53%的荷蘭成年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或伴侶比其他大多數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Buunk & van der Eijnden,1997)。
66%的美國人給自己長子所在的公立學校的打分是A或B,與此同時幾乎同樣多(64%)的人給全國的公立學校的打分是C或D(Whitman,1996)。
大多數企業總裁和部門經理都會高估自己企業的生產力和增長率(Kidd & Morgan,1969;Larwood & Whittaker,1977)。
這種盲目樂觀常常是失敗的先兆。如果那些炒股者或房地產商直覺認為自己的生意要比對手們強,他們就可能會受到嚴重的挫敗。甚至17世紀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一個人類經濟理性的捍衛者,也預見到人們將高估他們盈利的機會。這種“對他們自己產品的荒謬假設”,來自“多數人對自己能力的自負的幻想”(Spiegel,1971,p.243)。
人們帶著讚許性的偏見來看待自己和他們的群體,這種觀點當然不是最新的——在古希臘悲劇中,狂妄和傲慢已被描述為悲劇性的缺陷。正如我們實驗中的實驗者們一樣,那些希臘悲劇人物並非有意地作惡;他們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學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樣被一遍遍地描述。在神學中,傲慢一向居於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歸屬於自我服務偏見,那謙虛呢?是對自己的輕視嗎?或者,如果沒有自我服務偏見,我們也會肯定和接受自己嗎?按英國學者作家劉易斯(C. S. Lewis)的說法,英俊的人覺得自己丑陋,聰明人覺得自己傻,這並非謙虛。虛偽的謙遜其實是為了掩飾個體認為自己真的優於眾人的想法。[James Friedrich(1996)報告,大多數人都認為,個體在“不確信自己比一般人更好”時,就要比一般人更有自知之明!]真正的謙卑,與其說是虛偽的謙遜,還不如說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讓人們為自己的專長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實事求是地認可到他人的專長。
小結
與“多數人可能都遭受低自尊和自卑感的折磨”的假設相反,研究者們發現多數人都表現出自我服務偏見。在實驗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發現,人們總是在失敗的時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時安享榮譽。我們在一些主觀性和盲目讚許性的特徵和能力方面,往往認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過分相信自己,使我們顯現出對未來的盲目樂觀。我們還容易高估自己觀點和弱點的普遍性(虛假普遍性),同時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虛假獨特性)。這些感知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我們“維持和增強自尊”的動機,這一動機有利於我們抵制抑鬱,但卻會引起錯誤評價和群體衝突。
自我展示
我們人類似乎不僅以自我美化的方式來認識自己,也同樣以受讚許的方式來向他人展示自己。那麼,我們的“印象管理”策略是如何把我們引向虛假的謙遜或自挫行為的呢?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自我位於我們社會世界的中心,自尊和自我效能確實帶來一些益處,而自我服務性的傲慢卻使自我評價出現偏差。也許你會問:那些美化自我的對外展示都是真實的嗎?人們當眾說出的話,是他們的真實感受嗎?還是,人們即使在懷疑自我的時候也會裝出一副積極的面容?
虛偽的謙遜
確實有證據表明,人們對外展示的自我和他們的自我感覺是不同的。最明顯的例子不是虛偽的傲慢,而是虛偽的謙遜。也許你現在已經想到一些人們自謙而不是自誇的例子了。這種自我貶低是一種很巧妙的自我服務,因為它很像安撫心靈的定心丸。一句“我太笨了”可能會引發身邊的朋友安撫說:“你做得很好!”甚至像“我多希望我沒這麼醜”這樣的評論,至少也會引發“那有什麼,我認識不少人,可比你醜得多”這樣的安慰。
人們之所以貶低自己,誇獎他人,還有另一個原因。想想那些在大賽前稱讚對手實力的教練。這些教練說的是心裡話嗎?當教練們公開誇獎對手時,他們展現出一種謙遜和極富運動員精神的形象,且無論輸贏都能為自己找臺階下。贏了,當然是值得褒獎的成就,輸了,則是因為對手的“防守太強”了。正如17世紀的哲學家培根所說,謙遜,只是一種“出風頭的詭計”。
古爾德等人(Gould,Brounstein,& Sigall,1977)發現,在一場實驗性的辯論中,馬里蘭大學的學生們在公開場合下都會誇獎他們的參賽對手,但在私底下,卻把參賽對手貶低一番。對自己的實力輕描淡寫,還可以減輕表演的壓力,並降低評價表演成績的基線(Gibson & Sachau,2000)。
虛偽的謙遜也表現為人們對自己成就的自傳式的解釋中。在頒獎慶典上,領獎人會衷心地感謝他人的支持。當得到一個學術獎項時,莫琳·斯特普爾頓(Maureen Stapleton)對“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和每個我一生中曾經遇到的人”表示感謝。這種對榮譽的慷慨分享,是否與“人們輕易地把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相矛盾呢?
為了弄清楚這一點,鮑邁斯特等人(Baumeister & Ilko,1995)要求學生們寫一篇題為“一次重要的成功經歷”的文章。那些被要求署名和預備要向大家當眾宣讀自己故事的學生,常常提到他們得到的他人幫助或情感支持。而那些匿名寫作的人則很少提到這些;相反,他們更多地描述自己是如何靠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的。在鮑邁斯特等人看來,這些結果暗示一種“表淺的感謝”——一種表面化的感謝只是為了表現 謙遜,而在道謝者自己內心裡,榮譽還是歸於自己的。
當我們勝過周圍的人,並擔心他們對我們的看法時,我們就很可能像斯特普爾頓那樣做出表淺的感謝。如果我們覺得自己的成功會使別人產生嫉妒或怨恨心理——這一現象被埃克斯林和洛貝爾(Exline & Lobel,1999)稱為“獲勝後的危險”——我們就會對自己的努力輕描淡寫並向他人表示感謝,獲勝者很自然會使用這種謙虛式的自我展現。
自我妨礙
有時人們通過設置障礙物來阻撓自己獲得成功。這種行為決不是一種故意破壞自我的行為,而恰恰是為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Arkin & others,1986;Baumeister & Scher,1988;Rhodewalt,1987):“我並沒有真的失敗——要不是因為這個我肯定能幹好。”
為什麼人們要用自挫行為來妨礙自己呢?回憶一下前面所講:我們通過把失敗歸於外因以保護我們的自我形象。由於害怕失敗 ,人們在就業面試前歡飲通宵,在大考來臨前玩視頻遊戲而非學習。當自我形象和行為績效緊密相連時,“全力爭取卻失敗了”要比“因延誤時間而有了失敗的好藉口”更讓人洩氣。如果我們在重重阻礙下失敗了,我們仍可以維持對自己能力的信任;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竟然成功了,那正好可以提升我們的自我形象。自我妨礙有利於我們把失敗歸於一些暫時的或外在因素(“我身體難受”;“我昨天晚上熬得太晚了”)而非自己的天賦或能力的匱乏,從而可以保護我們的自尊和公眾形象。
伯格拉斯和瓊斯(Berglas & Jones,1978)提出的自我妨礙 (self-handicapping)解釋,已經得到證實。其中一個實驗是關於“藥丸和智力測驗”的。想像一下你是杜克大學的一名被試。你通過猜測答出了一些智力難題,然後被告知:“您是目前為止的最高分!”當你還在為自己的幸運感到難以置信時,給你呈現兩種藥丸,你必須服用其中的一種,才能繼續下面的題目。一種藥丸有助於你的智力活動,另一種則會干擾你的智力活動。你會選哪種藥丸呢?多數學生會挑選第二種,以便為不久可能出現的糟糕成績提供藉口。
研究者們也證實了自我妨礙的其他方式。由於害怕失敗,人們會:
運動員減少對重要的個人賽事的準備 (Rhodewalt & others,1984)。
給對手提供一些有利條件 (Shepperd & Arkin,1991)。
在任務剛開始時不好好幹,這樣就不至於對自己產生過高的期望 (Baumgardner & Brownlee,1987)。
在那些關係到自我形象的困難任務中並不盡全力 (Hormuth,1986;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7;Riggs,1992;Turner & Pratkanis,1993)
[在敗給幾個年輕對手之後,網球巨星納夫拉蒂洛娃承認,她“在比賽時不敢盡全力……唯恐發現自己雖盡全力仍被擊敗,因為一旦如此,就證明我完了。”(Frankel & Snyder,1987)]
印象管理
自我服務偏見、虛偽的謙遜和自我妨礙都揭示出個體十分在意自我形象。在不同程度上,我們始終在管理自己給他人營造的印象。無論我們是引人注意、脅迫他人還是表現出無助的樣子,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我們總是在向周圍的觀眾表演。
自我展示 (self-presentation)是指我們想要向外在的觀眾(別人)和內在的觀眾(自己)展現一種受讚許的形象。我們致力於管理自己營造的形象。我們通過推脫、辯護和道歉等方式來支撐我們的自尊並檢驗我們的自我形象(Schlenker & Weigold,1992)。在熟悉的環境裡,這些並不需要意識參與就能發生。而在不熟悉的環境裡,例如我們想給宴會上的某個人留下印象或是在和異性聊天時,我們都能確切地意識到我們正在為自己營造印象,所以就不會像和熟識的老朋友在一起時那樣謙遜了(Leary & others,1994;Tice & others,1995)。當我們準備給自己拍照時,我們可能還會特意到鏡子前試試各種不同的表情。
出於我們對自我展示的關心,毫無疑問,當失敗可能會使人們看起來很糟時,人們就會採取自我妨礙的方式(Arkin & Baumgardner,1985)。例如,人們冒著健康的風險接受致癌射線的射入以至於皮膚出現皺紋;變得食慾不振;屈從於同伴壓力而去吸菸、酗酒和吸毒(Leary & others,1994)。當然,當人們的自我恭維,在一些明察秋毫的專家面前被揭穿時,人們會表現得更謙遜一些(Arkin & others,1980;Riess & others,1981;Weary & others,1982)。當史密斯教授把她的工作展示給同行時,顯然不像展示給學生時那麼自信。
對某些人而言,有意識地自我展示也許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不斷地監控自己的行為,注意他人的反應,校正自己的社會行為以達到社會讚許性效果。那些在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傾向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這些人往往贊成“我傾向於成為人們希望的樣子”)表現得像社會中的變色龍——他們不斷根據周圍環境來調整自己的行為(Snyder,1987;Gangestad & Synder,2000)。為了讓自己的行為和環境合拍,他們很可能會支持一些其實他們並不想贊成的觀點(Zanna & Olson,1982)。由於總是意識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們很少會依據自己的態度而行動。對於高自我監控者而言,個人態度是為其社會調節功能服務的。它可以幫助這些人適應新工作、角色和人際關係。
那些自我監控性差的人則很少關心別人是怎麼想的。他們更多地受其內在的指引,從而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感覺和信念來說話做事(McCann & Hancock,1983)。如果要他們列舉一下對同性戀伴侶的看法,他們會怎麼想就怎麼說,而毫不顧及聽眾的感受(Klein & others,待發表)。我們大多數人則處於行騙專家式的高自我監控和榆木疙瘩式的低自我監控這兩個極端之間。
展現自己以給人留下讚許性的印象真是一件很微妙的事。人們希望自己被看成是有才華的,同時又是謙遜和誠實的(Carlston & Shovar,1983)。謙遜可以營造良好的印象,無故地誇耀則恰恰相反。這樣,虛偽的謙遜現象:我們表現出的自尊常常要弱於我們私下感到的自尊(Miller & Schlenker,1985)。但當我們的確做得很好時,過分謙遜(“我是做得不錯,但這不算什麼”)反而會給人留下故作謙虛的印象。營造一個既謙遜又有才華的好印象,這確實需要一定的社會技能。
在一些以自制為美德的文化中,如中國和日本,人們更多地展現出謙遜和自制性的樂觀(Brown & Kobayashi,2003;Heine & others,2000,2002;Yik & others,1998)。在中國和日本,人們較少表現出自我服務偏見。孩子們要學會如何與別人分享成功的榮譽並勇於承擔失敗的責任。“當我失敗時,那是我的錯,不是集體的錯”(Anderson,1999)。在西方國家,孩子們則要學會在成功時感到驕傲而在失敗時歸因於環境。據菲利普·津巴多(Zimbardo,1993)報告,其結果是不愛出風頭的日本人,更謙遜和害羞了。
世界各地的人,儘管在自我展現方面互不相同,但在各自心裡卻都在自我美化(Brown,2003)。在荷蘭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中,在比利時的籃球運動員中,在印度的印度教徒中,在日本的大學生和司機中,在以色列和新加坡的學齡兒童中,在澳大利亞的學生和工人中,在中國大陸的學生中,在中國香港的學生和體育撰稿人中,以及法國各年齡的人群中,都發現了人們的自我服務偏見(分別見Brown & Kobayashi,2002,2003;Codol,1976;de Vries & van Knippenberg,1987;Falbo & others,1997;Feather,1983;Hagiwara,1983;Hallahan & others,1997;Jain,1990;Liebrand & others,1986;Lefebvre,1979;Murphy-Berman & Sharma,1986;Ruzzene & Noller,1986;Sedikides & others,2003;Yik & others,1998)。
小結
作為社會性動物,我們調整自己的言語和行為以適應我們的觀眾。我們在不同程度上監控自己;我們對自己的表現加以注意,不斷調整它以創造一個我們所希望的形象。這種印象管理的策略可以用來解釋虛偽謙遜的案例,在這些案例中,人們貶低自己,恭維未來的對手,或是當眾感謝他人而私下裡卻把榮譽歸於自己。有時人們甚至會以自挫行為來實現自我妨礙,用以為失敗提供藉口,從而保護自尊。
個人後記:傲慢的危險與積極思維的力量——一對相反的事實
自我效能感可以鼓勵我們在逆境中也不要輕言放棄,即使一開始就失敗了也要堅持下去,全力奮鬥而不要因為懷疑自己而過於分心。高自尊也具有類似的適應性意義。當我們相信自己的美好未來時,我們就不容易沉淪,同時也有利於我們的成功。
那些有關盲目樂觀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服務偏見 的事實,提醒我們自我效能感無法解釋自我在社會世界中的全部問題。要是積極思維就能夠挽回一切的話,那麼如果我們婚姻不和、貧困或是消沉時,我們就只能責怪自己了:“真不害臊!要是我們多努力一些,老實一些,不那麼愚蠢的話,哪會這樣啊!”卻沒有考慮到困難常常來自社會環境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這使我們不但責怪別人甚至苛責自己。生活中最了不起的成就,和最讓人沮喪的挫折,都來自對自己高標準的預期。
這一對相反的事實——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服務偏見——使我們想起300年前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帕斯卡爾所說的話:任何一個單獨的真理都是不充分的,因為世界是很複雜的。任何一個真理如果脫離了和它互補的真理,就只能算是部分真理而已。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回憶一下你盡你所能而獲得成功的情景。然後再設想一下,如果你非常努力,但結果並非如你所願,這時你體驗到了自我的侷限性。虛幻的樂觀會對你下一次的判斷產生影響嗎?
聯繫社會
本章關於自我和文化的討論,考察了馬庫斯和Shinobu Kitayama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研究。我們還將在以後的章節裡進一步討論他們的工作(如第6章和第13章)。
第3章 社會信念與判斷
我們如何解釋他人
歸因因果關係:歸因於個人還是情境?
基本歸因錯誤
我們為什麼會犯歸因錯誤?
基本歸因錯誤的原理是什麼?
研究歸因錯誤的必要性
我們怎樣感知和回憶我們的社會生活
知覺和解釋事件
信念固著
構建關於我們自己和身邊世界的記憶
我們怎樣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直覺判斷
過度自信傾向
直覺:心理捷徑
錯覺思維
情緒和判斷
我們的信念傾向於自我實現嗎
教師的預期與學生的表現
從他人那裡獲得我們的期望
結語
個人後記:反思直覺的力量和侷限性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喬納森·斯威夫特,《禮貌會話》(Polite Conversation ),1738
1997 年8月的一個夜晚,亨利·保羅駕車從麗茲酒店的後門駛出,隨後駛上沿塞納河方向的巴黎高速公路。車上的乘客是戴安娜王妃和她的伴侶法耶德以及他們的保鏢,汽車越駛越快,進入一條隧道。車子突然失去控制併發生傾斜,進而撞向一根柱子,奔馳車隨即被擠壓為一堆廢鐵,除了保鏢外,車上所有人都命喪黃泉。
隨後的幾周裡,人們無休止地分析和爭論著。是什麼導致了這次車禍呢?是因為司機喝酒了嗎?還是歸咎於尾隨他們並不斷對他們進行拍照的狗仔隊?“我已經厭惡透了,”法國電視臺晚間要聞節目的主持人說道,他將那些狗仔隊比喻為“老鼠”。然而流行刊物卻對這種解釋表示憤慨,上面這樣說:“那個司機根本就酩酊大醉,而這才是本次事故的關鍵所在。”
1999年4月的一天,哈里斯和科萊博德殘殺了他們在科羅拉多科隆比納中學的13名同學。對於持槍襲人者痛心不已的父母、同學以及他們的國家來說,其中的原因令人費解。我們應當將他們的殺人行為歸因於精神問題嗎?或者歸因於“其父母或其他人的疏忽”,就像後來一樁訴訟中所斷言的那樣?歸因於兩人沉迷其中的充斥暴力的遊戲,如《世界末日》,及觀看暴力電影《天生殺人狂》和《籃球日記》中瘋狂的屠殺場面嗎?歸因於二人在同學中飽受的奚落和排斥嗎?還是歸因於哈里斯近期約會被拒,以及入學申請被某些大學以及海軍陸戰隊拒絕呢?
我們將9.11事件歸結於什麼呢?是什麼驅使那19個人做出了那種自殺性的暴行?是他們特有的邪惡?瘋狂?精神問題嗎?(就算我們是他們的鄰居,我們會發現他們有顯著的惡魔或是發瘋行為嗎?)還是他們有著仇恨的歷史,並且以襲擊那些他們厭惡的人為己任(這樣的情境又會培養出更多這樣的人)?
正如這些案例所示,我們對人們的判斷基於我們如何解釋他們的行為。根據我們的解釋,我們可能判斷一樁殺人行為為謀殺、一般殺人罪、自衛,或者愛國主義行為。根據我們的解釋,我們可能將一個無家可歸的人看做一個懶漢或者是工作及福利緊縮的受害者。我們還可能將別人對我們友好的態度看做是情感的體現抑或逢迎討好之舉。
本章論述了這些觀點:
我們如何歸因他人的行為?
我們怎樣感知和回憶我們的社會生活
我們通過什麼方式來判斷他人?
我們什麼時候會傾向於實現他人對我們的期望?
我們如何解釋他人
人們將對他人做出解釋視為自己的事情,而社會心理學家將如何解釋人們的解釋視為自己的任務。那麼,人們是如何、並且能夠多麼確切地解釋他人的行為呢?歸因理論可以就此提供一些答案。
人類努力想使自己面對的世界合乎情理。如果工人的生產率下降,我們會認為是工人們變得懶惰了嗎?還是他們使用的機器變得不好用了呢?一個攻擊自己同學的男孩是真的具有敵對的個性?還是他只是在對無理的嘲弄做出迴應?當一個銷售員說:“那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真得很不錯。”這話究竟反映了他真實的感受,抑或僅僅是他的銷售策略呢?
歸因因果關係:歸因於個人還是情境
我們無休止地分析和討論事情為什麼發生,特別是當我們經歷一些消極事件或者預期之外的事件的時候(Bohner & others,1988;Weiner,1985)。霍爾茨沃思-芒羅和雅各布森(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1985,1988)報告,已婚人士經常分析自己伴侶的行為,特別是他們的消極行為。冷淡敵對的態度比溫暖的懷抱更容易讓伴侶思考“為什麼會這樣?”
配偶的回答與他們的婚姻滿意度相關。婚姻關係不愉快的人常常對伴侶的消極行為做出“維持痛苦”的解釋(“她遲到是因為她不在乎我”)。而愉快的夫妻則通常做出客觀的解釋(“她遲到是因為交通堵塞”)。對伴侶積極行為所做出的解釋在維持痛苦上(“他送花給我是因為他有性的需要”)或者在促進關係上(“他送花給我是因為他愛我”)也會起到類似的作用(Hewstone & Fincham,1996;Weiner,1995)。
阿比(Abbey,1987,1991,1998)和她的合作者多次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喜歡將女性的親密行為歸結於溫柔的性挑逗。而這種對熱情等同於性誘惑的錯誤理解(稱為錯誤歸因 ),常常引發被女性(尤其是美國的女性)指控為性騷擾或者強姦(Johnson & others,1991;Pryor & others,1997;Saal & others,1989)。許多男性認為頻繁的約會邀請會使女性非常開心,而事實上這種行為通常會被女人認為是騷擾(Rotudo & others,2001)。
當男性位高權重時,這種錯誤歸因尤其容易發生。一個老闆也許會曲解屬下女職員的順從或友善的行為,並完全從自己的角度出發,認為女性做出這樣的行為僅僅是從性的角度出發(Bargh & Raymond,1995)。男人比女人更容易想到性(見第5章)。男人也通常假定其他人,包括女人,和他們有著同樣的感覺(見第2章“虛假普遍性效應”)。因此,男人很容易會將女人友善的微笑誇大為性的要求(Nelson & LeBoeuf,2002)。也就是說簡僅僅想要“笑一下”,就會讓約翰產生錯誤的念頭。
如此的錯誤歸因可以用來解釋全世界範圍內的男性所表現出的大男子主義,以及不同文化中,無論是波士頓還是孟買,男性通過責備受害者的行為將強姦行為合理化(Kanekar & Nazareth,1988;Muehlenhard,1988;Shotland,1989)。而女性則通常將上述行為理解成為罪犯開脫罪名或是審判陷入僵局(Schutte & Hosch,1997)。錯誤歸因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23%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她們曾經被強迫進行性行為,3%的男性報告說他們曾強迫女性與之發生性關係,由此可以看出,男性報告的比例僅佔女性的八分之一(Laumann & others,1994)。具有性攻擊性的男性更容易誤解女性所表達的信息(Malamuth & Brown,1994)。他們“實在就是難以理解”。
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描述了我們怎樣來解釋人們的行為。不同的歸因理論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假設。像吉爾伯特和馬隆(Gilbert & Malone,1995)解釋的那樣,“可以將人類的皮膚看做是將一種形式的‘作用力’同另一種形式區分開的特殊的邊界。外表皮上的就是外力或者說是情境的力量,其方向是指向內部的;而內表皮上的則是內力,它們竭盡全力地向外施壓。有時這兩種力的作用是聯合的,而有時則是相反的,它們之間這種動態的相互作用表現出來的就是可觀察到的行為。”
海德(Heider,1958)被公認為是歸因理論的始創人,他指出人們都是以“常識心理學”的方式來解釋日常生活事件的。海德認為人們通常試圖將個體的行為或者歸結為內部原因(例如個人的性格),或者歸結為外部原因(例如人們所處的情境)。舉例來說,當老師發現一名學生成績不好時,那麼他可能想知道這是由於他本身缺乏動機和能力不足[性格歸因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還是由於身體情況和社會環境造成的[情境性歸因 (situational attribution)]。
內因(性格)和外因(情境)的界限通常是很模糊的,因為外部的環境因素會影響個體內部的改變(White,1991)。我們一般認為“學生害怕了”和“學校讓學生感到害怕”的含義是一樣的,只不過看起來前者是後者的簡單表達而已。然而,社會心理學家卻發現,通常情況下我們不是將他人的行為歸因於性格就是 歸因於外在情境。因此,當賽蒂科德斯和安德森(Sedikides & Anderson,1992)在一項調查中詢問美國學生美國背叛前蘇聯的原因時,80%的人將其歸於一時的“糊塗”、“忘恩負義”或者“背叛”等個性特徵 。而當詢問俄羅斯學生同樣問題時,則有十分之九的學生將其歸因於迫於當時蘇聯的國內形勢。
推斷特質
瓊斯和戴維斯(Jones & Davis,1965)指出,我們常常可以通過別人的行為來判斷他們的目的和意圖。如果我發現瑞克經常嘲笑琳達,那麼我就會推斷瑞克是一個不友好的人。瓊斯和戴維斯的“對應推論理論(theory of correspondent inferences)”具體描述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這種歸因更容易發生。例如,正常的和預料中的行為只能讓我們瞭解一個人很有限的一些方面,而其不尋常的行為則能讓我們更多地瞭解這個人。在面試中應聘者通常應該很和悅,而如果薩曼莎在一次面試中表現得很尖刻,比起她對朋友的尖刻,我們似乎可以更深入地瞭解她。
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推斷出個體行為背後的特質。在紐約大學的一項實驗研究中,烏爾曼(Uleman,1989)讓學生們記憶類似下列的陳述語句,“那個圖書管理員幫一個老婦人將雜貨送到了馬路對面。”參與實驗的學生會立即不經意地推斷出圖書管理員的一種特質。當後來給這些學生提供一些線索以幫助他們回憶記憶過的句子時,發現最有效的線索不是“書”(提示圖書管理員),也不是“揹包”(提示雜貨),而是“樂於助人”——自發推斷出的圖書管理員所具有的一種特質。
常識性歸因
像上面的例子所講到的那樣,歸因通常情況下都是比較理性的。歸因理論家哈羅德·凱利(Kelley,1973)描述了在我們試圖解釋行為時,我們怎樣利用“共同反應”、“區別性”和“一致性”三種信息(圖3-1)。當解釋為什麼當大部分人都能適當地使用×××牌電腦,而埃德加卻總是出問題時,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有:共同反應 (埃德加經常都無法使其電腦正常工作嗎?),區別性 (埃德加是僅僅不能使用×××牌電腦還是其他品牌的也不能使用?)和一致性 (其他人在用×××牌電腦時也會出現問題嗎?)。當我們瞭解到埃德加在使用所有品牌電腦都會遇到麻煩時,那麼我們往往會將原因歸結於埃德加,而不是×××牌電腦本身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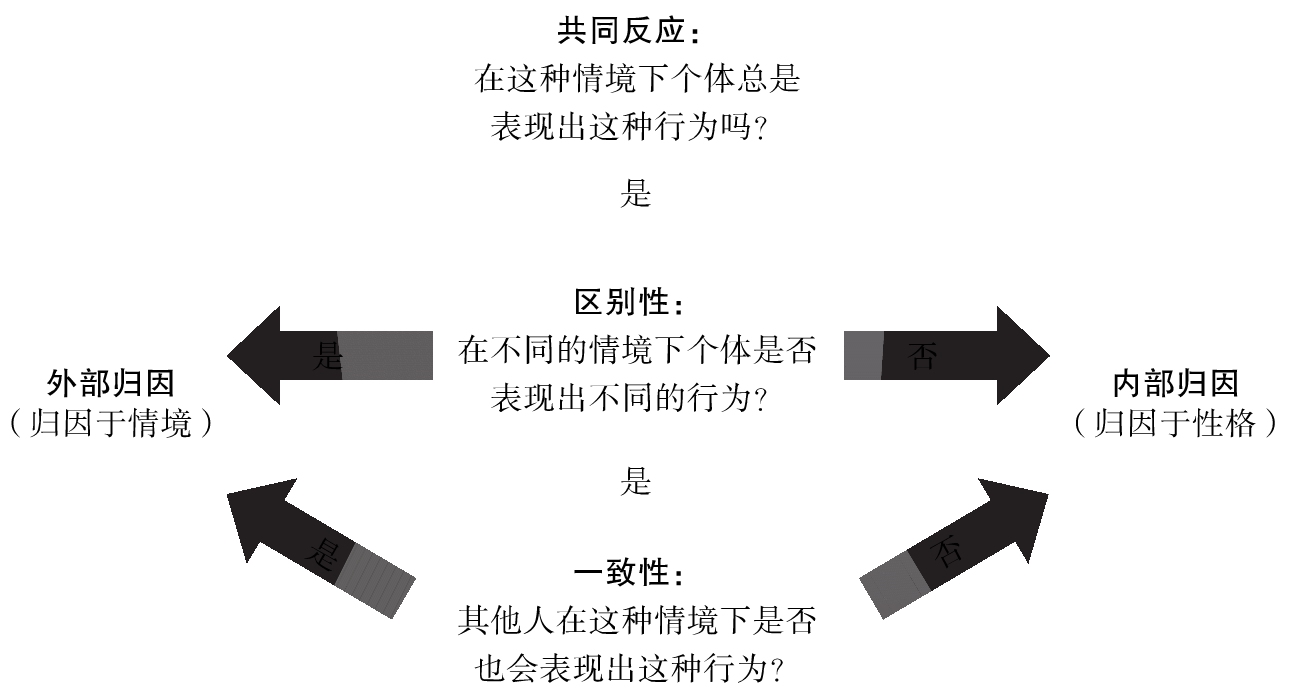
圖3-1 凱利的歸因理論
三種因素——共同反應、區別性和一致性——會影響我們將某人的行為歸結為內因還是外因。你要試著建立起自己的判斷標準,就像:如果瑪麗和其他許多人都批評史蒂夫(一致性),而瑪麗沒有受到其他人批評(較高的區別性),那麼我們就可以做出外部歸因(一定是史蒂夫有些問題)。但如果只有瑪麗一個人批評史蒂夫(較低的一致性),同時她又批評許多其他人(較低的區別性),那麼我們就可以做出內部歸因(瑪麗有些問題)。
因此,我們的常識心理學通常可以理性地解釋行為。然而凱利還發現,在對日常行為的解釋中,如果出現了其他似是而非的因果關係,我們就會對已經做出的歸因大打折扣。正如麥克盧爾(McClure,1998)說的那樣:如果我能詳細地指出一條或兩條能夠充分說明學生在考試中表現得很差的原因,那麼我們通常就會忽略或很少去考慮其他可能性。
基本歸因錯誤
就像我們在下一章將要闡述的那樣,對社會心理學家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是我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每時每刻,我們內部的心理活動和由此發出的言語和行為,都取決於我們所處的情境(以及我們給情境所帶來的改變)。研究表明,兩種情境下的微小的差異有時會對人們的反應產生很大的影響。對於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同樣是講課,但在上午8:30和晚上7:00我會得到不同的待遇。上午8:30會有無言的注視向我問候,而在晚上7:00時,我卻不得不拆散一個聚會。在每一種條件下都會有人比其他人更健談,與其說這是個體的差異,還不如說是由不同的環境造成的。
歸因理論的研究者發現人們在歸因時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當我們解釋他人的行為時,我們會低估環境造成的影響,而高估個人的特質和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儘管知道在一天的不同時間上課會對課堂討論產生不同的影響,我還是禁不住下結論說晚上7:00上課的學生比上午8:30上課的學生更加外向。
這種個體在歸因時低估情境因素作用的傾向,被李·羅斯(Ross,1977)稱為基本歸因錯誤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這已在許多實驗中得以證實。在有關這方面的第一個研究中,瓊斯和哈里斯(Jones & Harris,1967)讓杜克大學的學生們閱讀評論家有關支持或者攻擊A國領導人C的演講稿。當告訴學生該演講的立場是評論家自己選擇的時侯,學生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是評論家個人態度的反映。然而當告訴學生該演講的立場是被指派給評論家的,那麼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歸因呢?結果大大地超出了人們的預料(Allison & others,1993;Miller & others,1990)。儘管學生們知道評論家是以被指派的親C的立場進行演講,但這並不影響他們認為評論家本人具有一定的親C傾向(圖3-2)。人們似乎認為,“對,我知道他是被指派的,但他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有這方面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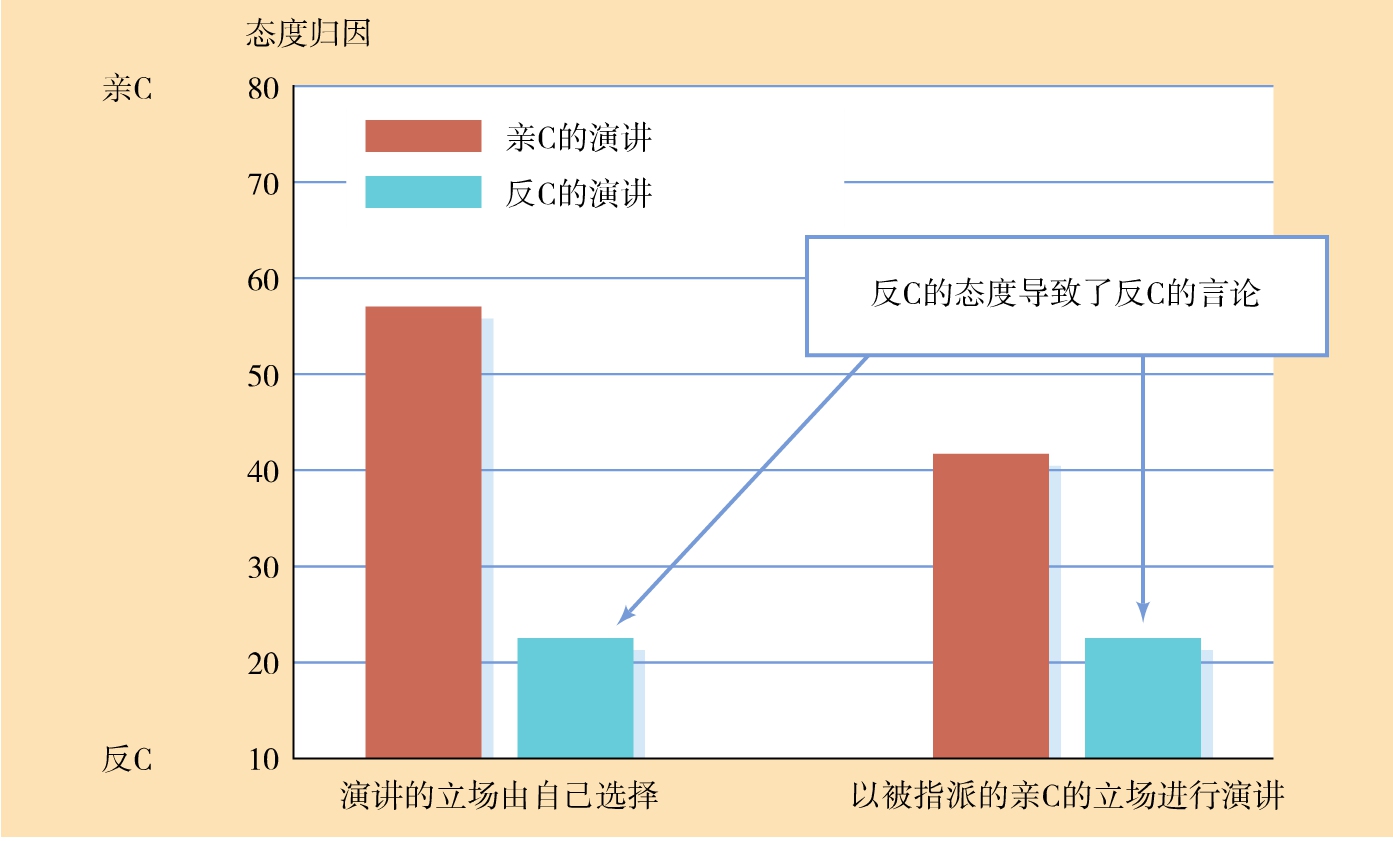
圖3-2 基本歸因錯誤
當被試讀到評論家關於支持或者反對C的演講時,他們通常將其立場歸結於評論家的個人態度,即使評論家是被迫站在該立場的。
資料來源:Data from Jones & Harris,1967.
迪特等人(Ditto & others,1997)讓男性被試和一名女性(事實上是實驗人員)進行約會實驗也得出了上述結論。實驗中,女性實驗人員對每一名男性被試寫出了自己假定的印象,之後要求被試根據這些印象的描述來猜測這名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喜歡他。當她僅僅列出消極的陳述時,如果告訴男性被試她是在別人要求下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時,他們不會介意她的批評。但當那名女性僅列出積極讚賞的印象時,男性被試會堅定地認為她確實 喜歡自己,而不管她是真正發自內心地表達還是被迫而表現出積極的評價。當歸因涉及到我們自己的個人利益時,基本歸因錯誤會表現得更為明顯。
這種歸因錯誤是難以避免的,即使人們清楚地意識 到某人的行為反應是受自己的影響,他們仍然低估外在因素的影響。如果某個人自己所持的觀點被其他人反覆表達,他會認為其他人確實也持有這種觀點(Gilbert & Jones,1986)。如果要求人們在面試中既表現出自信又表現出自謙,那麼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卻不 知道自己這樣做會對別人產生什麼影響。如果胡安在面試中表現得很謙恭,那麼作為他的同伴,鮑伯儘管不知道實驗的目的,但也傾向於表現出謙恭。胡安十分清楚自己為什麼表現出這樣的行為,但他卻不知道鮑伯為什麼也這樣做,甚至會認為可憐的鮑伯可能是自尊心太弱了(Baumeister & others,1988)。簡言之,我們通常認為他人的行為就是 其內在性格意圖等內部特點的直接反映。仔細分析一下即可得出,當灰姑娘畏縮在她那個難以忍受的家裡時,人們會認為她非常溫順;而在舞會上和王子跳舞的灰姑娘,則會被人們認為是自信而有魅力。
羅斯等人(Ross & others,1977)的一個令人深思的實驗深刻地揭示了人們會低估社會約束的影響作用,這個實驗重現了羅斯從畢業生到成為一名教授的親身經歷。因為那些著名的教授用他們自己所精通的專業題目來考察他,這令羅斯的博士生入學口試成為一次令他感覺恥辱的經歷。6個月後,羅斯親自作為一名施測者,提出了自己 擅長領域的一些尖銳的問題。羅斯那些倒黴的學生後來承認他們幾乎就和羅斯半年前的感覺一樣——對自己的無知和對施測者擺出的臭架子極為不滿。
在這項實驗中,羅斯和阿瑪比爾以及斯坦梅茨(Teresa Amabile & Julia Steinmetz)一起,進行了一項模擬測驗遊戲。他隨機指定了一些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扮演考官,一些學生扮演考生,其他一些學生作為旁觀者。研究者要求那些作為考官的被試編制一些能夠證明自己知識面豐富的難題。我們所有人都能想像到那些從個人專長領域出發而提出的問題會是什麼樣子:“班布里奇島在那裡?”“蘇格蘭女王瑪麗是怎麼死的?”“歐洲和非洲誰擁有更長的海岸線?”如果僅僅是這幾個問題就使你覺得自己很無知,那麼你就可以想像到這個實驗的結果了。 [1]
所有人都知道考官是佔優勢的。但考生和旁觀者(不是提問者)都會錯誤地認為那些考官確實 比自己懂得更多(圖3-3)。後續的研究表明,這些錯誤印象決不是較低社會智力的反映。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聰明的人和有社會地位的人更容易 犯歸因錯誤(Block & Funder,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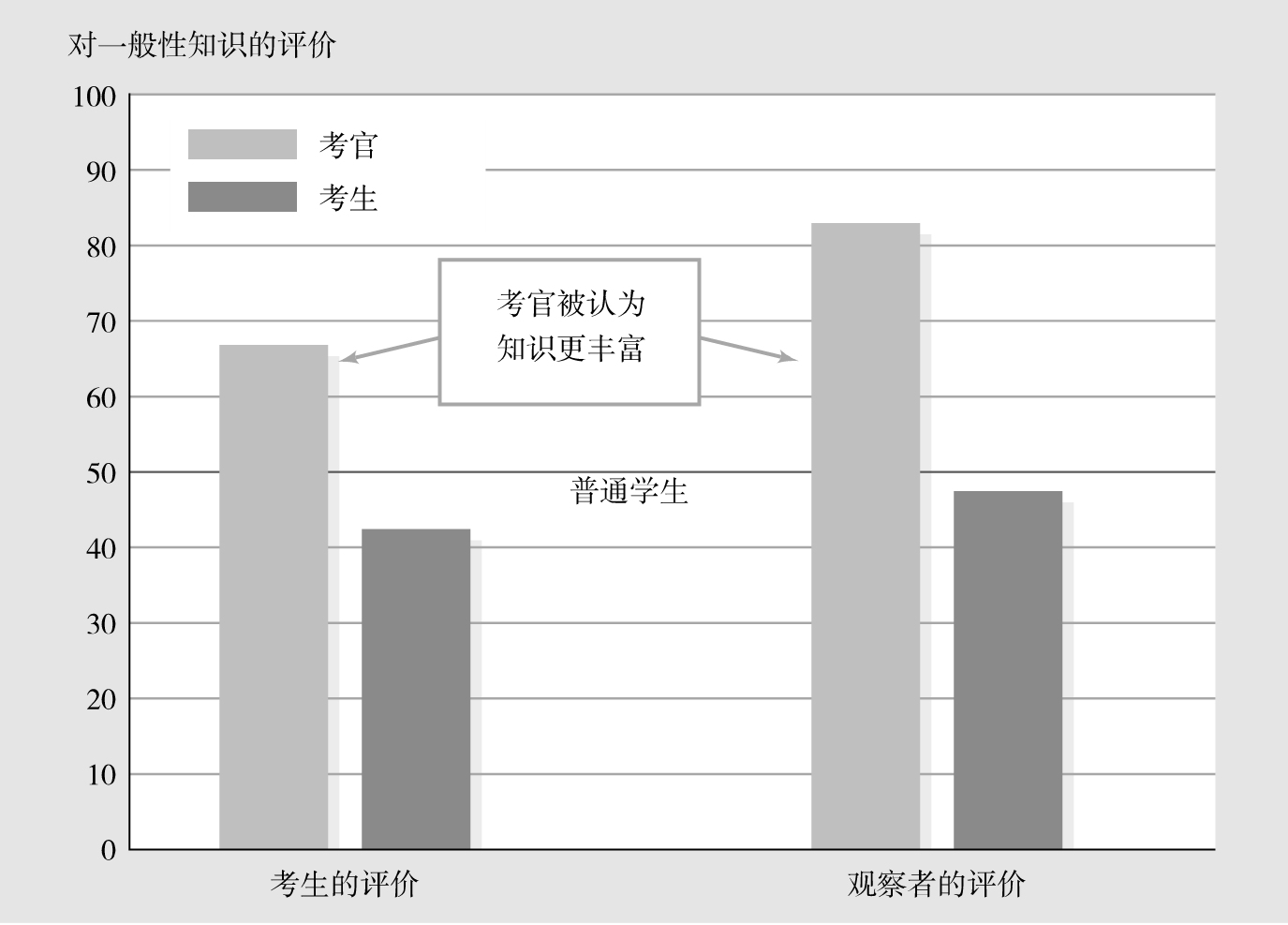
圖3-3
所有參加模擬測驗遊戲的考生和旁觀者都認為那些被隨機安排到考官組裡的學生都要比自己懂得更多的知識。事實上,考官和考生的隨機安排只不過從表面看上去好像考官顯得更有知識而已。這種錯誤認識的確證明了基本歸因錯誤。
資料來源:Data from Ross,Amabile,& Steinmetz,1977.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歸因錯誤
當我們解釋他人 行為的時候,我們會犯基本歸因錯誤。而對於我們自己的行為,我們卻通常用情境因素來解釋。因此約翰會將他自己的行為歸因於情境(“事情全都變得很糟,這令我很生氣”),但艾麗斯卻認為,“約翰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因此他總是不友好”。當涉及到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通常使用描述行為和反應的詞語(“當……的時候我會感到很苦惱”)。涉及到他人的時候,我們更經常用“那個人怎麼怎麼樣”之類的語言(“他真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Fiedler & others,1991;McGuire & McGuire,1986;White & Younger,1988)。那些將妻子的批評歸因為“吝嗇和冷淡”的丈夫更容易成為家庭暴力的實施者(Schweinle & Ickes,2003)。當妻子指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出現危機時,他們會非常憤怒。
在實際生活中,那些有權勢的人常常會主動提起一個話題並控制談話內容,這往往會使其下屬過高地估計他們的知識和能力。例如醫學博士常常會被認為在其他許多與醫學無關的領域也是專家。同樣地,學生們也常高估老師的能力(就像前面講述的實驗一樣,老師就是在他那所擅長的領域中的提問者)。然而當這些學生中的一部分人也成為老師後,他們會驚奇地發現,其實老師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有才氣。
要進一步舉例說明基本歸因錯誤,我們只需仔細看看自己的經歷就不難發現。為了結識一些新朋友,比弗強裝笑臉,並且小心翼翼地參加了一個聚會。在聚會上,別人都談笑風生,大家都顯得輕鬆愉快。比弗很奇怪,“為什麼其他人那麼輕鬆自在,而我卻緊張害怕呢?”實際上,其他人也與比弗一樣,自己內心緊張得要命卻認為比弗和其他人就像 他們所表現 的那樣——輕鬆愉快。
責任歸因是許多法院判決的核心內容(Ficcham & Jaspars,1980)。1994年,在辛普森因被指控謀殺前妻和另外一個男人而被捕後的一週裡,格雷厄姆(Sandra Graham,1997)領導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小組,對洛杉磯市一些確信辛普森有罪的市民做了調查。那些認為辛普森的行為是在特定環境下無法控制的市民提議減輕對他的懲罰,而那些認為他是主動犯罪的市民則主張對他施以重罰。該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許多司法審判中存在的爭議:起訴人說,“你犯了罪,應該被判刑”;而被告則辯護說,“那不是我的錯,我只是環境的犧牲品”;或者“在那種情境下我別無選擇,只能那麼做。”
我們為什麼會犯歸因錯誤
現在,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們在解釋他人行為時存在一種偏見:我們通常忽略情境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為什麼會低估環境對他人行為的影響而不是對自己行為的影響呢?
認知和情境意識
行動者和觀察者的不同 歸因理論學家指出當觀察他人和我們自己的親身經歷時,我們的觀點會有所不同(Jones & Nisbett,1971;Jones,1976)。當我們成為行為的執行者時,環境 會支配我們的注意;而當我們觀察別人的行為時,作為行為載體的人 則會成為我們注意的中心,而環境變得相對模糊。儘管魯道夫·霍斯(Rudloph hoss,1959)對自己的行為會表達出內心的痛苦,“我是如此的可憐以至於我都期盼自己能夠從這個環境中消失”,但這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依然是一個殘忍的工作人員,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點悔恨的意思。他推斷說猶太人是不值得關愛的——這是他們的種族特質,這些特質使得他們被趕進了毒氣室。
如果我們用知覺來分析圖形和背景,那麼人就是突出於周圍環境背景之外的圖形。所以作為圖形的人看上去似乎就是所有事情發生的根源。如果這個理論成立的話,那麼這種觀察反過來又會是什麼樣呢?如果我們像他人觀察我們那樣觀察自己,我們會看到什麼?如果我們通過別人的眼睛看世界又會是什麼樣子呢?這種反轉是典型的歸因錯誤嗎?
來看看你是否能預期到斯托姆斯(Storms,1973)做的一個巧妙的實驗結果。想像你自己是斯托姆斯實驗的一個被試。你坐在一個將要和你談話的學生的對面。你的旁邊有一架攝像機,用於拍攝你對面的學生。在那個學生旁邊面對著你的是另一架攝像機,然後要求你自己和那名觀察者來判斷你的行為更多是由環境引起還是由你的個性引起。
問題 你們中的哪一個——被試還是觀察者——會認為環境最不重要?斯托姆斯發現是觀察者(另一個基本歸因傾向的例證)。如果我們讓你和觀察者分別觀察自己對面的攝像機拍攝的錄像,那又會出現什麼現象?(現在你看到的是你自己,而觀察者看到的則是實驗時你所看到的。)這種做法正好將歸因也翻轉了過來:觀察者將你的行為更多地歸因於你所面對的環境,你卻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自己的個性。弗蘭克和吉洛維奇(Frank & Gilovich,1989)做的另一個從觀察者角度出發的實驗——從外部觀察自己的行為——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聚焦觀點偏見 (the camera perspective bias) 在一些實驗中,要求實驗者觀看審訊過程中嫌疑犯認罪的錄像。如果他們從聚焦在嫌疑犯身上的攝像機的角度觀看認罪過程,他們會認為罪犯的認罪是真誠的;如果他們從聚焦在審訊員身上的攝像機的角度觀看,他們就會認為嫌疑犯是被迫認罪的(Lassiter & Irvine,1986)。儘管在審訊過程中要求審訊員禁止對嫌疑犯進行不公正的審訊,但聚焦理論仍然會影響審訊。
在法庭上,大部分的錄像都是聚焦在疑犯身上的。就像我們所預見的那樣(Lassiter & Dudley,1991),將這樣的錄像帶播放給陪審團,幾乎會造成百分之百的宣判有罪。拉絲特(Lassiter)報告,根據這項研究,新西蘭在國內頒佈了一項新政策,這項政策規定,審判的錄像必須同時對審訊員和嫌疑犯做出同樣多的關注,即都從側面進行拍攝。
觀點在隨時變化 當觀察者回顧自己的記憶內容時,通常會分配給情境更多的權重。在聽到某人以某一指定的立場辯論後,如果要求聽眾立刻做出歸因,那麼人們會假定那個立場就是辯論者自己真正的立場。而一週後再讓他們做出歸因時,他們會更多關注情境的限制(Burger,1991)。總統選舉結束後的第二天,伯格和帕維裡希(Burger & Pavelich,1994)詢問投票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選舉結果,大部分人認為該結果恰恰說明這個候選人很有個人魅力及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來自執政黨的勝利者更可能如此)。當一年後詢問另一些投票者同樣的問題時,卻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將結果歸因於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大部分人更加重視當時的環境因素,例如國家良好的狀態和繁榮的經濟。
從1964年到1988年六屆美國總統選舉的相關評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上述研究相同的趨勢——隨著時間的變化,人們越來越重視社會環境的影響(Burger & Pavelich,1994)。1978年總統選舉之後,評論家特別關注了候選人的選舉活動和人格特點。而兩年後,環境的影響卻逐漸變大,就像《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報道的那樣,“水門事件……為卡特成為總統掃清了道路。”
對將來的預期也很重要。預期某人最近某一天的行為——“塔米卡這個週末會來參加我的生日宴會嗎?”——當前的情境就顯得尤為重要。預期某人很遠的將來行為——“塔米卡明年會參加我的生日宴會嗎?”——這種情況下她的性格似乎更重要。
自我覺知 環境可以改變我們對自己的認識。當我們從電視中看到自己時,我們的注意力會集中在自己身上。當我們照鏡子時,聽我們自己聲音的錄音帶時,照相時,或者填寫個人傳記性質的問卷時,都會將注意集中到自己身上,這更多地是靠自我 意識而不是環境 意識。當我們回顧類似泰坦尼克號 那樣的厄運時,我們很容易就會想到冰山(Berscheid,1999)。
威克倫德和杜瓦爾(Wicklund & Duval)與其合作者們發現了自我覺知 (self-awareness)效應(Duval & Wicklund,1972;Wicklund,1979,1982)。當我們把注意聚焦在自己身上時,我們更可能將原因歸結到自我。費內格斯騰和卡弗(Fenigstein & Carver,1978)通過讓學生想像自己處於一種假定的情境中證實了上述效應。實驗中,要求一部分學生傾聽自己的心跳聲,以這種方法使這部分學生進行“自我覺知”,結果發現這些學生更多地將這種想像的結果歸因於自我,而另一部分僅僅是被要求聽外部噪音的學生則很少將這種想像的結果歸因於自我。
有些人通常具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在實驗中,那些自我報告非常關注自己(這些人同意這樣的表述:“我通常注意自己的內部感覺”)的人的行為表現和通過鏡子觀察自己的人的行為很相似(Carve & Scheier,1978)。因此,當人們把注意聚焦在自己身上時——無論是在實驗期間還是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會比觀察者更傾向於將原因歸於自我而不是情境(但是存在這樣一種例外,人們經歷了失敗後,自我意識會激活防禦機制)。
上述所有實驗都可以揭示人們犯歸因錯誤的原因:我們在自己關注的地方尋找原因 。這可以從你的個人經歷中發現這一點,你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你的社會心理學老師是一個健談的人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
我猜你一定認為他(她)是一個非常外向的人。但請進一步仔細考慮一下情境吧:你的注意可能僅僅聚焦於老師在公眾場合的行為,而這種情境要求一名老師必須具備這種健談的能力。而老師本人所觀察到的自己則是在許多不同環境中的——在教室,在會議中,在家中。“我很健談?”你的老師也許會說,“嗯,那都取決於環境。當我上課或者和好朋友在一起時確實會表現得很外向。當我參加會議時或者處於一個陌生的環境中時,我會覺得很害羞。”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行為在不同情境中變化,所以與從別人的角度相比,我們更認為自己是多變的(Baxter & Goldberg,1987;Kammer,1982;Sande & others,1988)。“奈傑爾很緊張,菲奧娜很放鬆。而我是跟隨情境變化的。”
我們越是缺乏在不同情境下觀察人們行為的機會,就越容易將其行為歸因於他們的人格使然。吉洛維奇(1987)通過讓被試聽某個人的錄音帶並要求被試向其他人描述磁帶中人的行為的實驗證實了上述假設。二手的印象通常很極端,那可能是因為個體多次將注意集中在人而不是環境上(Baron & others,1997)。同樣,人們通過從朋友那裡聽說而獲得的關於某個人的印象通常比那個朋友親自獲得的第一手印象極端得多(Prager & Cutler,1990)。對於一個我們很熟悉並且在多種環境下相處過的人,在歸因時我們會對其所處的環境更加敏感(Idson & Mischel,2001)。只有當我們描述陌生人時,我們才會更穩固地貼上內在特質的標籤。
文化差異
文化同樣會影響歸因錯誤(Ickes,1980;Watson,1982)。一個持有西方式世界觀的人,更可能認為是人本身而不是環境導致了事件的發生,在這種文化下,用內部原因解釋人的行為更加受社會所讚許(Jellison & Green,1981)。“你能做到!”我們更多受西方積極思維文化中的通俗心理學支配。
在此我們提出一個假設,具備適當的特質和態度,幾乎任何人都會解決任何問題:你努力去獲取你應該得到的,而你也應該得到你所努力獲取的東西。因此我們通常喜歡給他人貼上“不正常”、“懶散”或者“有虐待傾向”等標籤以解釋那些不好的行為。在西方文化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也學會根據他人的人格特點來解釋個體的行為(Rholes & others,1990;Ross,1981)。作為一個一年級學生,我兒子給了我這樣一個例證:他將零散的單詞,“gate the sleeve caught Tom on his ”組合成這樣一句話:“The gate caught Tom on his sleeve 。”由於老師將西方文化觀應用於課堂中,所以老師認為這句話是錯誤的。老師認為,正確的答案應該將原因歸在湯姆身上:“Tom caught his sleeve on the gate。”
在所有被研究過的文化中都存在基本歸因錯誤(Krull & others,1999)。但是東亞文化下的人們通常對環境的作用格外敏感。因此,當意識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作用時,他們很難想像到他人的行為還與他們的內在特質相關(Choi & others,1999;Farwell & Weiner,2000;Masuda & Kitayama,2003)。
1990年的“流氓商人”醜聞(由於某些僱員私下進行未被授權的交易,結果造成了許多銀行和投資公司的重大損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件事情誰該負責任呢?美國報紙將這種混亂歸結於個人(“所羅門流浪的牛仔,”就是《紐約時報》對其中一個交易者的描述)。而日本的報紙則將該問題歸因於缺乏組織監控(Menon & others,1999)。
某些語言也有利於做出外部歸因。“我遲到了”,用西班牙的俗語可以說成“鬧鐘使我起晚了。”在集體主義的文化下,人們幾乎不會根據個人的人格傾向來進行歸因(Lee & others,1996;Zebrowitz-McArthur,1988)。他們並不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是其內在特質的反映(Newman,1993)。當談及某人的行為時,印度教信徒不像美國人那樣做出內在傾向的解釋(“她是友好的”),而更願意做出情境解釋(“因為她朋友和她在一起”)(Miller,1984)。
基本歸因錯誤的原理是什麼
就像許多引發爭論的觀點一樣,我們都會犯基本歸因錯誤這一假設一直受到人們的批評。我們承認自己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種歸因偏見 。但在所有給出的例子中,這種偏見不見得就是“錯誤”,就像父母傾向於相信自己的孩子不會吸毒也不見得是正確的(Harvey & others,1981)。我們傾向於相信真實的事物。
而且,在某些日常生活環境中(如去教堂或者參加面試)和我們先前提到的實驗幾乎是一樣的:都有一些明確的規範限制。行動者比觀察者更能意識到這些限制——因而也就容易產生歸因錯誤。但在其他環境中——在家中或是在公園裡——人們可以很自由地表現自我。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比旁觀者更容易認為環境較少 約束自己的行為(Monson & Snyder,1977;Quattrone,1982;Robins & others,1996)。所以並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低估情境的影響作用。因此,許多社會心理學家都支持瓊斯對基本歸因錯誤的解釋——行為是內在傾向的相應反應——對應偏見 (correspondence bias)。
然而實驗發現,即便我們清楚地意識到環境的作用我們仍會出現這種偏見——儘管我們知道在辯論中被指定某一立場並不代表辯論者的真實觀點(Croxton & Morrow,1984;Croxton & Miller,1987;Reeder & others,1987)以及在測驗遊戲中的考官是有優勢的(Johnson & others,1984)。我們清楚地知道,有一種社會加工會扭曲我們的思維,但我們仍然受其影響。這或許是因為要評價社會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比起僅僅將行為歸結為個人的內在傾向需要花費人們更多的腦力(Gilbert & others,1988,1992;Webster,1993)。就好像一個繁忙者想的那樣,“這也許不是做決定的最好依據,但這樣做很容易,也讓我有點時間去觀察它。”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過程是與環境相適應的(心理學家認為我們的偏見是為某一目的服務的,因為自然選擇保留了那些歸因偏見者)。將行為歸因於個體的內在特性而非環境是一種有效率的行為。此外,我們的特性通常會引導我們選擇自己的環境。像吉爾伯特和馬隆(Gilbert & Malone,1995)提到的那樣,銀行家如果穿得很保守,可能是這種職業的要求,也可能是保守的人通常會選擇這種職業。做出銀行家比藝術家更保守的推斷時,你正確的可能性很大。
歸因錯誤的根本性 在於它在本質上影響著我們的解釋。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研究者都發現人們的歸因傾向可以預測他們對窮人和失業人員的看法(Furnham,1982;Pandey & others,1982;Skitka,1999;Wagstaff,1983;Zucker & Weiner,1993)。那些將貧窮和失業歸因為個人特質(“他們就是太懶、太沒有追求了”)的人通常贊成政府的立場,並不同情這些人(圖3-4)。這種特質歸因 將行為歸因於人們的性格傾向和特質。這與那些做出外部歸因的人有所不同(“如果你和我也住在那樣擁擠的環境中,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經常受到歧視,我們會富裕嗎?”)。法國的研究者比弗斯和杜波依斯(Beauvois & Dubois,1988)報告,那些相對來說享有特權的中產階級比起那些處境不利的人們更容易對人們的行為做出內在的解釋。(他們通常會認為“你得到了自己所應得的”)。這也被稱為情境歸因 ——認為行為是由環境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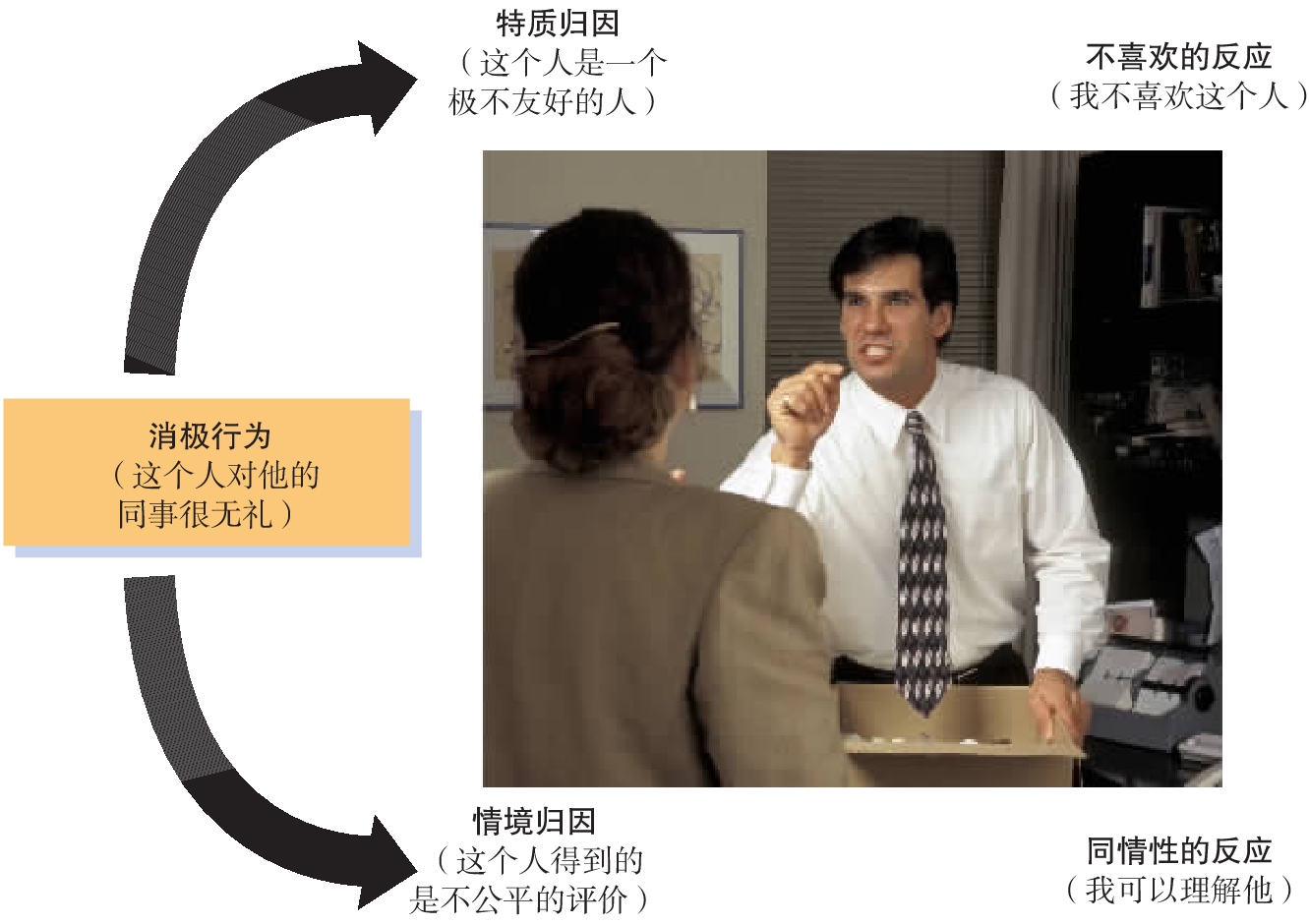
圖3-4 歸因和反應
我們對他人消極行為的解釋決定了我們對這種消極行為的感受
如果我們意識到歸因錯誤,這會對我們有所幫助嗎?我曾經參加過一些招聘職員的面試。每一位應聘者同時接受我們六個人的面試,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提問兩到三個問題。面試結束後我想,“這個人太呆板、太笨拙了。”第二個應聘者是我在喝咖啡時單獨會見的,談話不久我就覺得我們就像一對親密的朋友。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了她是一個“熱情、有魅力、有意思的人”的印象。過後我才意識到基本歸因錯誤,並且重新評價了我對這兩個人的分析。我將他的呆板和她的熱情歸結到了他們的人格特點上;而後來我才發現,事實上,他們的行為差異更多的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不同面試環境造成的。
研究歸因錯誤的必要性
本章和前一章解釋了我們社會思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怪僻和謬誤。正如我的一個學生說的那樣,看到這些你也許會想到“心理學家以取笑人們來獲得滿足。”事實上,這些實驗並不是為了證明“這些錯誤多麼愚蠢”(儘管有些實驗確實很有趣),其目的只是想揭示人類怎樣思考自身與他人。
如果我們具有驚人的幻想和自欺能力,那麼請記住我們的思維模式總的來說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幻想通常是我們將複雜的信息簡單化策略的副產品。這有點類似我們的知覺機制,一般情況下會帶給我們有用的信息,但有時又會帶來錯覺。
另一個關注諸如基本歸因錯誤這類思維偏見的原因就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吉洛維奇和艾巴赫(Eibach,2001)寫道:這是社會心理學家所傳遞的“人道主義信息”,即人們不應該總是因為自己的問題而被責備。“人們更願意承認失敗、殘疾和不幸是現實環境造成的結果。”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通常意識不到這種思維偏見。我的拙見是,與一系列關於人類邏輯思維能力和智力成績的研究相比,這種對歸因錯誤和偏見的研究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的驚喜、挑戰和好處。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的文學作品通常都會描述人類的驕傲和失敗。自由主義的教育讓我們瞭解自己思維荒謬的地方,以期我們變得更理性,更加貼近現實。
希望並不是沒用的:學心理學的學生在解釋行為的時候,就不像那些同樣聰明的學自然科學的學生那樣單純(Fletcher & others,1986)。所以請記住這個最重要的目的——發展我們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讓我們期待能夠改善我們社會推理的有關社會思維內容新研究的出現。
小結
歸因研究者研究了我們怎樣解釋行為,我們什麼時候會將人們的行為歸結於個人的特質,什麼時候該將其歸結為環境的影響?基本上我們都會做出合乎情理的歸因。然而,在解釋他人的行為時,我們卻常犯基本歸因錯誤(也叫對應偏見)。我們會把他人的行為更多地歸結為內在的特質和態度,而很少考慮環境的影響限制,即使它們是很顯著的。如果一個氣球的運動是由我們看不見的風的推動所造成,我們不會認為它是有內在動力的。但人不是無生命的物體,因此當一個人在活動時,我們通常輕視“環境的風”而集中考慮內在的動力。我們會犯這種歸因錯誤,部分原因是當我們觀察某個人的表現時,那個人就是我們注意的中心,而環境相對是不可見的。但當我們觀察自己的行為時,我們的注意力通常是放在需要做出反應的情境上,這個時候,情境就是可見的了,因此我們會對環境的影響更加敏感。
我們怎樣感知和回憶我們的社會生活
有十分明確的實驗結果向我們揭示出預先做出的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會使我們的知覺和解釋產生偏見,以及錯誤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回憶。
第1章提到了關於人類思維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的預期會引導我們對信息的知覺和解釋。我們透過“有色眼鏡”去觀察和解釋世界。人們承認預期會影響社會評價,但卻沒有想到這種影響會有那麼大。
讓我們來看看有關這一方面的一些研究,第一組實驗研究預先的 判斷怎樣影響人們對信息的知覺和解釋,第二組實驗研究在給人們提供信息後 再向他們灌輸某一種判斷方式,以觀察接受事實之後的判斷如何對回憶產生影響。總的結論是:我們並不是如實地對現實進行反應,而是根據我們對現實的解釋做出反應。
知覺和解釋事件
預先判斷和期待效應是心理學導論中的基本知識。讓我們回憶第1章大麥町狗的照片或者思考一下下面的短語:
A
BIRD
IN THE
THE HAND
你發現裡面有什麼錯誤了嗎?這不僅需要眼睛觀察,更需要知覺參與。這在社會知覺中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社會知覺主要產生於旁觀者的眼中,即使一個很小很簡單的刺激也會對兩個人造成不同的影響。我們說加拿大的保羅·馬丁是“一個還算過得去的總理”,對於他的那些熱情擁護者來說似乎在貶低他,而對不尊敬他的人來說卻像是在表揚他。當社會信息受到多重解釋的影響時,先入為主就很重要了(Hilton & Von Hippel,1990)。
沃倫、羅斯和萊珀(Vallone,Ross,& Lepper,1985)做的一個實驗解釋了先入為主到底有多重要。他們向分別支持以色利和阿拉伯的學生提供6段從網絡上下載的關於1982年在黎巴嫩兩所難民營屠殺難民的新聞片斷。像圖3-5解說的那樣,每一組被試都將新聞看成是反對自己觀點的。[1995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78%的黑人贊成辛普森沒有犯罪的裁決,而白人的贊成者僅佔42%。在兩年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71%的白人基本相信或確信對其謀殺的指控是真實的,而黑人的贊成者僅佔28%。 (Gallup Poll Monthly,October,1995;Newport & Saad,1997)。]這種現象很常見:
馬西森和杜森(Matheson & Dursun,2001)發現,波黑塞族和穆斯林對薩拉熱窩市場爆炸事件進行報道的時候,雙方的出發點都是自己帶有偏見的角度。
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擁護者幾乎總認為媒體對他們的理由無動於衷。
球迷們認為裁判在偏袒另一方。
衝突中的人們(已婚夫婦、勞動者和管理者、敵對的種族)認為公平的仲裁者在偏袒敵對的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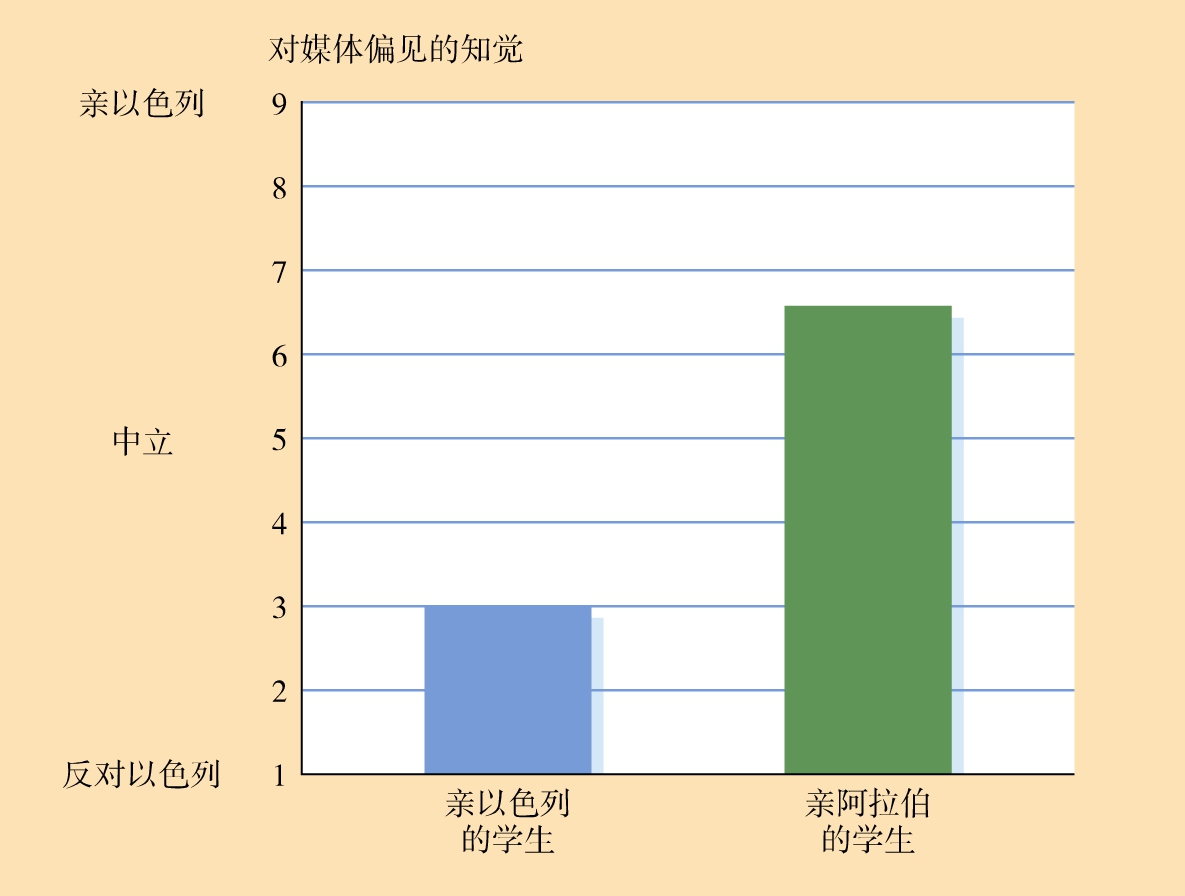
圖3-5
親以色列和親阿拉伯的學生在看了網絡上描述“貝魯特大屠殺”的新聞後,都認為這些報道是在極力反對自己的觀點。
資料來源:Data from Vallone,Ross,& Lepper,1985.
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媒體和調解人站在對方的立場。“人總是主觀的,”一家媒體評論這樣說道(Poniewozik,2003)。事實上,可以利用人們對偏見的知覺來評價他們的態度(Saucier & Miller,2003)。告訴我你從哪裡看到了偏見,我就能獲得有關你所持態度的線索。
我們關於世界的假定有時候甚至會使矛盾的事情看起來是有利於自己的。例如,羅斯和萊珀協助洛德(Charles Lord,1979)調查學生們對兩種假想的研究結果的評價。這些學生中有一半支持死刑,而另一半學生則反對死刑。其中一項研究支持了死刑具有威懾力量的觀點,而另一項研究的結果是反對死刑。研究結果發現:支持和反對死刑的學生都較容易接受與他們觀點相同的證據,而極力批評和反對與其觀點相背的證據。即使同一 個證據同時擁有兩種觀點也不會降低學生們對自己信念的支持,反而更起了促進 作用。在隨後的研究中,給人們提供由爭論性的證據所組成的混合信息,這種特殊的情景會引發被試對信息更仔細的思考,然後促使其猛烈批駁相反的觀點(Edwards & Smith,1996;Kuhn & Lao,1996;Munro & Ditto,1997)。最後,雙方都將證據知覺為支持自己的信念,之後對自己信念的堅持會變得更加強烈。
這是否就是為什麼政治、宗教和科學中模糊的信息通常會引起衝突的原因呢?美國總統競選的電視辯論很大程度上會使辯論觀點得到更多支持。那些明確支持某一個候選人的人在觀看1960、1976和1980年的辯論後就認為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已經贏得了競選(Kinder & Sears,1985)。芒羅(Geoffrey Munro)與其合作者們(1997)在1996年總統競選的第一次辯論中發現了同樣的現象,他們發現雙方的支持者在觀看完辯論後都更加支持自己的候選人。對於同樣的混合性信息,對立的雙方都會將其吸收同化為支持自己並更加堅持自己的觀點。
其他的實驗控制了先入為主,結果發現它在影響人們解釋和回憶自己所觀察到的內容時會產生令人驚奇的效應。羅斯巴特和比勒爾(Rothbart & Birrell,1977)讓俄勒岡大學的學生評價圖3-6中那個男人的面部表情。有一部分學生被告知他是蓋世太保的領導人,二戰中對在集中營難民身上實施野蠻的生化實驗負有重要的責任。這部分學生很自然地將他的表情知覺成“冷酷無情”。(你能僅僅從平靜的輕蔑表情中看到這些嗎?)而另一部分學生被告知他是反納粹組織地下運動的領導者,並勇敢地拯救了數以千計的猶太人。這些學生則認為他的表情充滿了熱情和慈善。(進一步考慮後,注意到那富有同情心的眼神和微笑的嘴角。)

圖3-6
你也來判斷一下:這個人到底是冷酷還是慈善?如果告訴你他是一個納粹分子,你會不會覺得他的臉有什麼不同?
電影製片人可以通過操縱人們看一張臉的背景來控制人們對情緒的知覺。他們稱其為“庫勒喬夫效應”。俄羅斯電影導演庫勒喬夫能夠巧妙地通過操縱觀眾的假設來引導他們做出推論。庫勒喬夫製作了三個短片:第一個短片呈現的是一個死亡的女人,第二個短片呈現的是一盆湯和一個玩耍的女孩子,第三個短片呈現的是一個演員的中性表情的面孔,最後要求觀眾判斷他們所知覺到的這個演員的表情是什麼樣的。在三個短片中,觀眾所知覺的表情依次為:悲傷、沉思和高興。庫勒喬夫通過這種方法證實了“庫勒喬夫效應”。它的意義在於:儘管事實擺在那兒,但我們的思維卻積極地去解釋它。人們會對這一事實做出不同的解釋然後據此做出不同的行為。
解釋的過程也會左右他人對我們的知覺。當我們說某人的好話或者壞話時,人們會試圖將那些特質和我們聯繫在一起(Mae,Carlston,& Skowronski,1999)。如果我們到處說某個人的閒話,人們就會不知不覺地將“說閒話”與我們聯繫在一起。如果稱某個人為傻子或者怪人,那麼過後人們可能就會認為你也一樣。如果我們將一個人描述為敏感的、迷人的、富有同情心的,我們自己也會被認為具有這樣的特點。這些都印證了一句古語中所體現出來的智慧,“我是橡膠,你是膠水,你所說的從我這裡彈出去粘住了自己。”
那裡存在著一個客觀現實,但我們都透過我們的信息、態度和價值觀去看待它。我們的信息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它們形成了我們對各種事件的解釋。
信念固著
假設深夜一個小嬰兒不斷地哭鬧,而一個保姆認為這時給孩子喂牛奶會讓他肚子痛:“仔細考慮一下,比起嬰兒來顯然小牛更適合喝牛奶。”如果嬰兒被診斷為發高燒,這會使保姆更加堅信是瓶裝牛奶造成了嬰兒的絞痛嗎(Ross & Anderson,1982)?為了證實這一假設,羅斯、安德森與其合作者事先給被試灌輸了一條錯誤的信息,然後試圖讓這些被試來否定它。
他們的實驗結果表明,一旦人們為錯誤的信息建立了理論基礎,那麼就很難再讓他們否定這條錯誤的信息。每一個實驗首先都給被試灌輸了一種信念 :或者直接宣稱某個結論是正確的或者向人們出示一些軼事式的證據。然後,要求被試解釋為什麼 該結論是正確的。最後,研究者會告訴被試真相以期讓他們徹底否定 最初的結論:那個結論是為實驗目的而人為捏造的,而且在實驗中給一半的被試提供相反的信息。然而,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結論,大部分人仍然堅持對他們已經接受的結論的解釋。這種現象被稱為信念固著 (belief perseverance),它證明了信念可以獨立存在,並且當支持其的證據被否定時仍會存在下來。
例如,安德森等人(Anderson,Lepper,& Ross,1980)首先要求被試分析兩個具體的事例,然後詢問他們有關喜歡冒險的人是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消防隊員的觀點。其中一組的被試認為喜歡冒險的人會是一個成功的消防隊員,而謹慎的人不適合做消防隊員。另一組的被試則持有完全相反的觀點。在被試們形成他們自己關於有冒險傾向的人是否適合做消防隊員的信念後,他們需要寫下自己這樣認為的理由——例如,有冒險傾向的人比較勇敢,而謹慎的人太過小心。當形成一種解釋後,它會獨立於最初推論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證明是虛假與錯誤的,被試們仍然會堅持他們自己歸納出的解釋,堅信有冒險傾向的人確實像自己想像的那樣會成為一名很棒的或者糟糕的消防隊員。
這些實驗給我們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我們越是極力想證明我們的理論和解釋是正確的,我們就對挑戰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閉。一旦我們確信一個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個令人討厭的陌生人的確會表現出那樣的行為,或者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會有所上升,那我們的解釋即使遇到了相反的證據也仍會保持不變(Davies,1997;Jelalian & Miller,1984)。
證據是有說服力的:我們的信念和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心理構造。就像科學家從創造某一個理論中獲益,引導他們觀察並解釋事件一樣,通常情況下我們的信念和預期也會使我們有所收益。但這種收益在某些時候是以一定的付出為代價的;我們成了自己思維方式的囚徒。由此,才會出現認為在火星上發現的“運河”其實是一種智慧生物的創造物這樣的謬誤。
有什麼方法能夠糾正我們的信念固著嗎?惟一的方法是:解釋相反的觀點 。洛德等人(Lord,Lepper,& Preston,1984)重複了對死刑的研究,並新增加了兩種實驗條件。首先他們要求被試“儘可能客觀無偏見 ”地評價事件。結果表明,這條指導語是無效的,不管是那些死刑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這條指導語下的被試與那些沒有得到該指導語的被試一樣存在偏見。
實驗要求第三組被試從相反的角度考慮問題——問自己:“假設我是一個持相反 觀點的人,我是否會在這個研究中同那些與我觀點不同的人得出同樣的結論呢?”當從相反的角度考慮這些問題後,這些被試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客觀地固執己見了。在安德森(1982;Anderson & Sechler,1986)的研究中發現,通過解釋與自己相左的觀點也可能是正確的——為什麼謹慎的人比愛冒險的人更適合做消防員——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信念固著。事實上,對各種可能結果的解釋,並不一定就是相反的觀點,會促使人們仔細考慮各種不同的可能性(Hirt & Markman,1995)。
構建關於我們自己和身邊世界的記憶
你是否同意下面的這段陳述?
記憶就好比大腦中的一個儲物箱,我們將各種材料儲存在其中,日後需要時可以再從中拿出來。偶爾,有些東西也會從“儲物箱”中丟失,那時我們就說我們忘記了。
大約85%的大學生同意這種觀點(Lamal,1979)。像一則雜誌廣告中說的那樣,“科學證實生活中積累的經驗可以非常完美地保存在記憶中。”
事實上,心理學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在我們將信息存儲在大腦的同時也就構建了記憶,因此記憶會引入許多事後的推理。它反映了當時的情況以及我們現在的信念或者知識。就像古生物學家能夠根據化石推斷出恐龍的實際樣子,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現在的感覺和解釋將許多不連貫的信息整合起來重構我們的過去(Hirt,1990;Ross & Buehler,1994)。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易地(無意識地)修正自己的記憶使其更符合我們現在的知識水平。
當研究者或者臨床醫學工作者操縱人們對自己過去的假設時,相當多的人會虛構自己的記憶。當要求被試生動地想像他們小時候的奔跑、被絆倒、摔倒,然後被玻璃劃破了手,或者在一次婚禮中摔碎了一個碗,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過後會認為這些虛構的事件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Garry & others,1996;Hyman & others,1995,1996;Loftus & Pickrell,1995)。因此,我們的心靈有時候會虛構記憶。
重構我們過去的態度
五年前,你對核能源持有什麼觀點?你又是怎樣看待布什總統和布萊爾首相的?你是怎樣看待你的父母的?如果你的觀點改變了,你知道這種改變的程度有多大嗎?
一些研究者已經嘗試去回答這些問題,但發現實驗的結果很令人洩氣。那些態度經常改變的人堅持說自己過去的感覺和現在的感覺沒有什麼差別。貝姆和麥康奈爾(Bem & McConnell,1970)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學生中做了一項調查。調查暗含的一個問題是學生對大學課程的控制。一週之後,那些學生同意寫一篇短文以反對學生對課程的控制。這樣做之後,他們的態度朝著反對學生控制課程的方向改變了。當詢問他們在寫那篇短文前填寫問卷時的態度時,他們回憶說當時自己堅持的是與現在 一樣的觀點,並且否認是實驗對他們的態度產生了影響。在觀察到克拉克大學的學生類似地也否認他們在實驗之前的態度之後,研究者威克森和萊爾德(Wixon & Laird,1976)發表評論,“那些學生改變自己態度的速度、程度和確定性真的非常令人震驚”。正如瓦利恩特(Vaillant,1977,p.197)在對一批成年人進行追蹤研究後得出如下結論,“當那些毛毛蟲變成蝴蝶的時候,它們認為自己‘小’時候是小蝴蝶而不是毛毛蟲那是很正常的,成熟對我們所有的人撒了謊”。
積極的記憶構建的確可以美化我們的回憶。米切爾和湯普森(Mitchell & Thompson,1994,1997)及其同事指出人們經常會給回憶 蒙上一層玫瑰色 ——他們把一些細小的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比實際所經歷的要美好得多。在澳大利亞經歷了為期三週的自行車旅行之後,無論是帶隊的成年人還是參加旅行的本科生都報告說自己在旅行中的經歷非常令人愉快。但是,之後他們在回想 這段經歷的時候,覺得它更加美好,而且將一些不愉快的或者無聊的事情最小化並最終將令人高興的事情留在了腦海中。因此,現在回想起我在愛爾蘭逗留的那段愉快的時間(而在辦公室裡則要面對許許多多的最終期限和干擾)感覺就像極樂世界一樣美好。對於任何積極的經歷,那些愉快的感覺保留在我們的期望裡,有一些在實際的體驗當中,還有一些留在玫瑰色的回憶中。
麥克法蘭和羅斯(McFarland & Ross,1985)發現我們同樣會改變同其他人關係的回憶。研究者讓大學生評價他們的約會伴侶。兩個月後,他們再一次評價先前的約會伴侶。那些更加相愛的人傾向於認為他們是一見鍾情,而那些已經分手的人則傾向於把自己的約會伴侶回憶成自私的或者是脾氣不好的。
霍姆伯格和霍姆斯(Holmberg & Holmes,1994)發現了同樣的現象。在393對新婚夫婦中,絕大部分的人報告說感到非常幸福。當兩年之後再次對他們進行調查時,那些婚姻已經變質的人回憶了他們經歷的一些事件。霍姆博格和霍姆斯提到,結果非常“恐怖”,“這種偏見導致了一種惡性的循環。你對伴侶的看法越糟糕,你的回憶就越差。這將促使你更加堅定你現在的消極態度。”
並不是說我們對過去的感覺毫無意識,只是當記憶模糊的時候,現在的感覺主導了我們的回憶。每一代的父母都在哀嘆下一代的價值觀,部分原因是他們錯誤地回想起自己年輕時候的價值觀與現在的價值觀很接近。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根據他們當前的感受將自己的父母描述成令人愉快或令人悲傷。
重構我們過去的行為
記憶的重構使得我們能夠改變自己的過去。布蘭克與其合作者(Blank & others,2003)就德國出現的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邀請萊比錫大學的學生回憶他們兩個月之前對投票結果的預測。他們發現大學生們表現出事後聰明式偏差,傾向於回憶自己的預測與後來實際的投票結果比較接近。
我們的記憶也會重構過去的其他行為。羅斯、麥克法蘭和弗萊徹(Fletcher,1981)對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傳達一種信息,使他們相信刷牙的必要性。之後,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實驗裡,這些學生回憶起在此之前的兩週內他們刷牙的次數比那些不知道那條信息的學生要多。同樣,美國人報告他們抽菸的數量比實際上銷售出去的煙支要少得多(Hall,1985)。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發現,人們回憶自己投票的數量要比實際記錄的投票數量多(Klein & Kunda,1993)。
社會心理學家格林沃爾德(Anthony Greenwald)提出的這些結論與喬治·奧韋爾的小說《1984》裡的那些發現很相似——小說認為事情是按照期望的方式發生的。格林沃爾德的確提到,我們都有一個極端的自我,它改變我們的過去使其符合我們現在的觀點。
有時候,我們現在的觀點是已經改善過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將自己的過去回憶得與其實際情況更加不同。這種傾向可以解釋令人困惑的一組比較一致的發現:那些參加心理治療、減肥項目、戒菸和鍛鍊的人實際上只是在平均的水平上表現出適度的改善。但是他們通常報告說有很明顯的收益(Myers,2004)。康韋(Michael Conway)和羅斯(1985,1986)解釋了為什麼人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在自我發展上,因為他們可能這樣想:“我現在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在此之前更糟糕,而且這些投資對我大有好處。”
重構我們的經歷:誤導信息和啟動
在一個20000多人蔘加的實驗中,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發現我們往往對自己的記憶力非常自信,儘管有些時候並不能很準確地重構我們的記憶。在這個經典的實驗中,人們目擊了一個事件,然後獲得了關於這個事件的誤導性信息(或者沒有),之後參加一項記憶測驗。研究一致發現了誤導信息效應 (misinformation effect),人們將誤導性的信息整合在他們的記憶當中:他們把一個轉彎的標誌回憶成停車的標誌,把錘子回憶成螺絲起子,把《時尚》雜誌回憶成《小姐》雜誌,把亨德森大夫回憶成戴維森大夫,把早飯的穀物回憶成雞蛋,把一個修過臉的男士回憶成一個有鬍子的小夥子(Loftus & others,1989)。洛夫特斯(1993)認為錯誤的信息甚至可能導致兒童時期的性虐待的錯誤記憶。
這一過程不但影響我們對社會事件的回憶,也影響對物理事件的回憶。克羅克斯頓等人(Croxton & others,1984)讓學生花15分鐘的時間跟另外一個人交談。那些隨後被告知這個人說過喜歡他們的學生將該人的行為回憶為放鬆、自在和開心。那些被告知這個人不喜歡他們的學生將該人回憶為緊張、拘束和不那麼開心。
為了解釋其原因,請將記憶想像為存儲在一個相互連接的網絡中,為了提取其中的一份記憶,我們需要激活某個引導線索,這個過程便被稱為啟動 (priming)(Bower,1986)。啟動就是哲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描述的“連接的激活”。
某一事件可能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被喚醒,或者說連接得以啟動。一個人在家裡看恐怖片會啟動我們的思維,它將激活令人恐懼的記憶,這些記憶甚至會令我們將爐子發出的聲響錯誤知覺為有人闖入。對很多學心理學的學生來講,閱讀有關心理異常方面的書籍會啟動他們對自身的焦慮和憂鬱的情緒。在實驗中,植根於被試頭腦中的觀念被當成先入之見:它們會自動不經意地、毫不費力地、無意識地啟動被試對事件的解釋和回憶(Bargh & Chartrand,1999)。如果人們先前看到了諸如“敢作敢為”和“充滿自信”這樣的詞,在隨後一個不同的情境中,人們就會對一個假想的登山者或大西洋上的水手形成積極的印象。而一旦他們的思維受到諸如“魯莽的”這樣的消極詞彙的啟動,他們就會對這個人形成相對消極的印象(Higgins & others,1977)。[在這個場景中你看到自己了嗎?假如看到了,你的記憶一定是一個重構,因為實際上你並沒有看到你自己 。]
小結
我們的先入為主會強烈地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和記憶。在許多實驗中,人們事先的判斷會強烈影響他們知覺和解釋信息的方式。其他一些實驗在給被試提供信息之後會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植下判斷或錯誤信念。這些實驗揭示出,正如事前判斷會扭曲我們的知覺一樣,事後判斷也會扭曲我們的回憶。
在第15章中我們將看到,精神分析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也具有這些傾向。我們都會選擇性地注意、解釋和回憶某些事件以支持自己的觀點。我們的社會判斷 (social judgment)是一個融觀察、期望、推理和熱情為一體的混合體。
我們怎樣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認知機制是有效和富於適應性的,然而也容易犯錯誤。通常情況下它們運作得很好,但有時醫生會對病人誤診,僱主會對僱員評價不公,某個種族的成員會歧視另一個種族的成員,夫妻一方也會錯怪另一方。其結果將導致誤診、罷工、種族歧視和離異。因此,我們應如何有效地做出社會判斷呢?
當歷史學家描述社會心理學的第一個世紀的時候,他們肯定會將最後30年看做社會認知時代。通過描繪認知心理學的進展——涉及人們如何知覺、表徵和記憶事件——社會心理學家已經對我們的評價機制有了初步的瞭解。讓我們看看該領域研究向我們揭示出的社會直覺的奇妙之處吧。
直覺判斷
我們直覺的力量是什麼呢?是指不經過推理和分析就迅速瞭解事情的能力嗎?直覺管理的擁護者認為,我們應該轉向直覺以尋求解釋。他們認為評價別人的時候,我們應該藉助右腦的非邏輯智慧。當我們要聘用或解僱某人,或者進行一項投資時,我們應該傾聽預感給我們提供的建議。在做出判斷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像影片《星球大戰》中的天行者盧克學習,不去理睬計算機系統的指揮,而相信自己心中的力量。
直覺主義者認為,重要的信息即使不經有意識的分析也是可以獲得的,這種觀點對嗎?懷疑論者則認為,直覺只不過是“我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而不管實際上是不是那樣”,這兩種觀點哪一種正確呢?
啟動實驗表明無意識確實控制我們的大部分行為。正如巴奇和沙特朗(Bargh & Chartrand,1999)解釋的那樣:“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其日常生活不是由有意識的目標和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決定的,而是受內部心理過程的控制,它通過對環境特徵的主觀加工影響人們的行為反應,並控制意識的覺察和導向作用。”例如,被試會非常迅速地將“美麗”知覺為一個好詞,但當眼前閃過一幅覺察不到的小狗圖片(而非蟑螂圖片)時,他們能更迅速地作出判斷(Giner-Sorolla & others,1999)。這樣的啟動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例如當交通燈變為紅色時,我們下意識便做出反應,踩下剎車。確實,麥克雷和約翰斯頓(Macrae & Johnston,1998)便認為:“幾乎對每一件事情(例如開車、約會、跳舞)來說,要想做好它,我們的行為在起始時就必須和效率低下的(如緩慢,序列處理,耗用心理資源)受意識控制的工作方式相分離,否則我們就什麼也幹不了。”
直覺的力量
17世紀的哲學數理學家帕斯卡爾指出:“心靈的活動有其自身的原因,而理性卻無法知曉。”三個世紀後,科學家們證實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我們知道的比我們意識到自己知道的要多得多。對我們的無意識信息加工過程的研究確證了這一點,即我們對在自己頭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Bargh,1994;Greenwald & Banaji,1995)。我們的思維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的 (controlled)(反應性的、深思熟慮的和有意識的),而還有很大一部分則是自動化的 (automatic)(衝動的、無需努力的、無意識的)。自動化的思維不是發生在屏幕上,而是發生在屏幕外,我們的視線外,在那裡沒有理性。請想像一下這些自動化思維或者我們經常稱之為直覺的例子:
圖式 ——心理模板——自動地和直覺性地我們對經驗進行知覺和解釋。我們是否會聽到某個人談論宗教教派 或性 的問題不僅取決於他所說的話,而且取決於我們對所聽內容的自動解釋方式。
情緒反應 通常是即刻的,在我們進行深思熟慮之前就已表現了出來。神經通路的捷徑是將從眼睛和耳朵那裡收集到的信息傳送到腦區的感覺交換臺(丘腦),並且下傳至它的情緒控制中心(杏仁核),而這些過程都發生在與思維活動有關的皮層以任何形式的介入之前(LeDoux,1994,1996)。
簡單的喜歡、不喜歡和恐懼通常並不涉及分析的過程。儘管我們的直覺反應有時並不符合邏輯規則,但是從適應角度講它們可能還是非常有效的。我們的祖先會出於直覺被灌木叢中不知名的聲響嚇住,而實際上那裡可能並沒隱藏什麼動物。但是與那些思維更縝密的族人相比,他們倒更有可能生存下來並將這種基因傳遞給後代。如果人們能夠擁有足夠多的專業知識 ,他們就可能利用直覺獲得問題的答案。那些有關情境線索的信息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打電話時我們只需聽到第一個詞便可以辨別出這是哪一位朋友的聲音,儘管我們對自己如何做到這一點一無所知。國際象棋大師憑直覺便可以抓住有意義的棋形,而一個新手只會讓它從眼前溜走。
我們對一些事物——事實、名字和過去的經驗——的記憶是外顯的(有意識的)。而對其他一些事物——技能和條件特徵——的記憶則是內隱的 ,無需也無從為意識所知曉。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而這一點在那些無法形成外顯記憶的腦損傷病人身上表現得更明顯。這樣的病人永遠無法學會辨認自己的醫生,醫生不得不每天握手和她再次認識。一天醫生在手上粘了枚針,當醫生和她握手時,她由於疼痛跳了起來。當醫生再次回來時,她依然無法認出他/她(外顯的)。但是這個病人保存著內隱記憶,不願意再次握手(LeDoux,1996)。
有關盲視 的例子同樣令人驚奇。當人們由於手術或中風失去一部分視皮層時,他們某一部分視野可能會功能性地失明。當在他們失明的區域內呈現一系列的細棒時,他們會報告說什麼也沒有看到。而當要他們猜測剛才的細棒是水平呈現還是豎直呈現的時候,他們猜測得完全正確,當得知這一結果後他們本人也大吃一驚。這再一次表明,人們知道的比他們意識到自己知道的還要多。看起來這似乎存在著難以察覺的無意識加工成分(平行加工單元)。
試想一下你自己認為理所當然的直覺性識別面孔的能力。正如你看相片時那樣,你的大腦首先將視覺信息分割為例如顏色、深度、運動和形狀這樣的附屬維度,並同時對它們進行加工處理,然後再將這些成分整合起來。最後,你的大腦以某種方式將知覺到的影像與之前儲存下來的影像進行對比。瞧,多麼迅速並且不費一點力氣,你就認出了你的祖母。假如直覺是指不經過推理分析就立刻明白某件事的能力,那麼知覺過程可以100%的算是直覺。
閾下 刺激可能反而會起著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以小於0.01秒的時間間隔向被試呈現幾何圖片,他們將除了一陣閃屏外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在隨後的測試中,他們對剛才看到的圖形表現出較高的反應傾向。有時我們就是直覺地感受到了我們無法做出解釋的某種東西。同樣地,不可見的閃屏詞彙也可以啟動我們對隨後問題的反應。如果“麵包”這樣的詞語閃屏呈現的時間短到被試無法看見,在隨後的實驗中我們很可能發現,被試對閃屏呈現的例如“黃油”這樣的相關詞語的反應要比對如“瓶子”這樣的無關詞語容易得多。
所以,許多習慣化的認知功能是在沒有覺察的狀態下自動和無目的地發生的。我們的心理機能很像一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我們的控制意識——處理著最重要或者是最新異的事件,而將日常事情分配給各個子系統處理。這種資源分配方式使我們能夠對許多情況做出快速、有效和直覺的反應。這就是“日常生活的自動化”。
直覺的侷限性
現在的研究者承認無意識的信息加工可以產生瞬間的直覺。巴奇(1997)指出,無意識並不像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思維簡單和缺乏理性。Gigerenzer和託德(Todd,1999)也同意這種觀點,認為自動化思維使我們在犯錯的同時也可以使我們變“聰明”。由於經驗的緣故,一個網球選手自動地——聰明地——就知道應該移動到哪裡,以怎樣的球拍角度去截擊來球。正如網球冠軍大威廉姆斯的擊球,有意識注意和無意識知覺以及二者天衣無縫地結合,結果就是她接近完美的直覺動作。
洛夫特斯和克林格(Mark Klinger)在談到當代一些認知心理學家對直覺的懷疑觀點時指出:“學術界大多數人都認為無意識過程可能沒有先前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敏銳。”例如,儘管閾下刺激可以激發個體做出微弱的快速反應——即使達不到有意識喚醒水平也足夠產生某種感覺——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用磁帶播放包含商業內容的閾下信息能夠“重構你的無意識心理活動”以幫助你贏得成功。[很多的新證據表明這些閾下信息做不到這一點(Greenwald,1992)]。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我們往往容易做出導致錯誤的事後聰明判斷(當事情發生後,會覺得自己早就預料到它會如此)。其他領域的心理學研究者發現了我們在錯覺上的潛能——即基於知覺的錯誤解釋、想像和建構性的信念。米歇爾·加扎尼加(Gazzaniga,1992)指出,那些在手術中被切斷了左右半腦聯繫的患者會立即虛構出——並且確信——對自己迷惑不解的行為的解釋。如果研究者將“四處走動”的指示通過屏幕呈現在這些患者非言語性的右腦半球,然後患者起身並走了幾步,這時主管言語的左腦半球將會立刻形成一個聽起來非常合理的解釋(“我想要喝點東西”)。
錯覺思維 (illusory thinking)這個概念最近也出現在論述我們如何感知、存儲和提取社會信息的許多文章中。正如知覺研究者試圖通過對視錯覺現象的探索,以揭示出一般的知覺機制一樣,社會心理學家試圖通過對錯覺思維的研究揭示出我們一般的信息加工過程。這些研究者想要給我們描繪一幅日常社會思維的地圖,並清楚地標出可能存在的危害。
當我們考察某些有效的思維模式時,一定要記住:關於人們如何創造出錯誤信念的例證並不能支持一切信念都是錯誤的這種觀點。儘管如此,對錯誤信念的瞭解有助於我們弄清楚它是怎樣產生的。所以讓我們來探索一下我們高效的信息加工過程是怎樣伴隨我們的自我認識被扭曲的。
過度自信傾向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認知系統在加工大量信息方面是自動而且高效的。但我們的效率卻存在一種權衡現象,當我們解釋自己的經歷和構建記憶時,我們的自動化直覺經常出錯。通常,我們意識不到這些缺點。對過去知識進行的判斷中存在一種“智力自負”現象(“我早就知道了”),這種現象會影響對目前知識的評價和對未來行為的預測。儘管我們知道自己過去出過錯,但我們對於未來的預期——我們會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務、很好地維持婚姻關係和遵守鍛鍊計劃——仍然相當樂觀(Ross & Newby-Clark,1998)。正如我們會解釋自己的過去和將來一樣,我們也會努力解釋不同的自我。
為了探討這種過度自信現象 (overconfidence phenomenon),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Kahneman & Tversky,1979)對被試提出一些實際問題,並要求他們填寫在下面的空白處:“我有98%的把握確信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航線距離要大於_____英里但是小於_____英里。”大部分被試都顯得過度自信。大約30%的正確答案都在他們98%的自信判斷區間之外。[新德里到北京的空中航線距離為2500英里 。]
為了證實過度自信傾向是否擴展到了社會判斷領域,鄧寧等人(Dunning & others,1990)設計了一個小小的遊戲,他們要求斯坦福大學的學生猜測一個陌生人對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如:“你是一個人準備一次很難的考試還是和同學一起準備?”和“你認為自己的筆記是整齊的還是凌亂的?”被試清楚問題的類型但並不知道實際的問題,他們先要通過訪談了解目標個體的背景、愛好、學業興趣、願望、星座——任何他們認為有用的內容。接著,要求目標個體單獨回答20個二選一的問題,然後這些訪談者對目標個體的答案做出預測並對自己預測的確信度進行評定。
在63%的情況下,訪談者猜對了答案,超過概率水平13%,但從總體來看,他們對自己的猜測有75%的確信度 。而當猜測自己室友的回答時,他們猜對了68%,但卻自認為有78%的確信度。除此之外,那些自信度最高的人恰恰最有可能過度自信。人們在判斷他人是否講真話、估計約會對象的性史或室友的活動偏好上表現出明顯的過度自信(DePaulo & other,1997;Swann & Gill,1997)。
具有諷刺的是,能力不足反而會促進過度自信傾向。克魯格和鄧寧(Kruger & Dunning,1999)指出,對能力的認識也是需要能力的,那些在語法、幽默以及邏輯測驗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反而最有可能高估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才能。那些不知道何謂好的語法和邏輯的人通常也不知道自己缺乏這些東西。假如無知可以產生自信的話,那麼我們可能會問,我們怎麼會有無法察覺的缺陷呢?
在第2章中我們曾注意到人們很容易過度估計自己對好事和壞事的長期情感反應。人們更善於估計自己的行為嗎?為了搞清楚這一點,沃倫等人(Vallone & others,1990)在9月份時讓大學在校生估計明年自己會不會有一門課不及格,申報一個專業,或者選擇搬出校園居住等等事情。儘管平均起來學生們對自己的預測有84%的確信度,但他們實際出錯的比率幾乎是預測率的2倍。即使那些對自己的預測具有100%的確信度的學生也出現了15%的錯誤。
為估計人們完成一個任務的可能性,例如一次學位考試,有研究發現,當人們遠離“真相”時,他們的確信度最高。臨近考試的時候,失敗的可能性逐漸顯露,而其確信度則明顯下降(Gilovich & others,1993)。比勒等人(Buehler & others,1994)報告說:大部分學生同樣很自信地低估論文和其他學位作業所需的時間。這並不是個別現象:
計劃者通常會低估工程所需的時間和費用。1969年,蒙特利爾市市長瓊·德拉波自豪地宣稱,他們將耗資1.2億美元建設一個屋頂可以伸縮自如的體育場以供1976年奧運會使用。結果,這個屋頂在1989年才完工,並且僅屋頂便花費了1.2億美元。1985年,官方人員估計波士頓的“大坑”高速公路工程將花費26億美元,1998年完工。而到2003年,造價飆升至146億美元,而工程仍未完工。
投資專家在將自己的服務投入市場時常伴隨著一個自信的假設,那就是他們能夠獲得超過股市的平均回報率,他們忘記了對於每一個股票經紀人和股民來說,在某一個價格上喊“賣出”的同時會有另一個聲音喊“買入”。而股價正是這種雙向信心判斷的平衡點。因此,這看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經濟學家馬爾基爾(Malkiel,1999)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由投資分析師選出的共同基金組合的表現並不比隨機選出的股票更好。
編輯對稿件的評價也顯示出驚人的錯誤。作家羅斯(Ross,1979)利用一個筆名將Jerzy Kosinski的小說《腳步》(Steps )的打印稿郵寄給了28家大型出版社和文學代理機構。他們都拒絕出版這部作品,其中包括蘭登書屋,而該出版社曾在1968年出版過這本書,並見證了它贏得國家圖書大獎且銷量突破40萬冊的歷史一幕。這本書差點被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接受,而它是Kosinski另外三部小說的出版者:“我們中的一些人拜讀了你未命名的作品,很欣賞你的語言文字和風格。我們彷彿看到了Kosinski的手筆……但事實是這樣,貴稿的缺陷在於未能結合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整體。”
過度自信的決定者可能會帶來一場浩劫。充滿自信的阿道夫·希特勒在1939~1945年間對整個歐洲發動了戰爭。充滿自信的約翰遜在20世紀60年代將武器和士兵投入越南,試圖挽救那裡的民主政權。充滿自信的薩達姆·侯賽因在1990年揮軍侵入科威特,並在2003年宣稱要打敗入侵者。充滿自信的布什宣稱和平與民主將遍佈解放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被銷燬。
個體為什麼會過度自信呢?為什麼經歷無法使我們的自我評價更客觀一些呢?這其中存在著不少原因。一方面,人們傾向於在他們幾乎完全正確的時刻回憶自己的錯誤判斷。泰特洛克(Tetlock,1998,1999)通過對許多學術界和政府專家的採訪發現了這一點,他要求這些人為——從20世紀80年代末的角度——蘇聯、南非和加拿大的未來政府管理做一個規劃。五年之後,前蘇聯解體了,非洲變成了各種族和睦相處的民主政體,而加拿大繼續維持著完整統一。這些專家對自己對這些轉折性事件的預測有80%的確信度,但這些預測的實際正確率不足40%。然而,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判斷之後,那些出錯的人仍然相信他們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基本上是正確的,”許多人說,“強硬派幾乎已經取得了反戈爾巴喬夫政變的勝利。”“魁北克分離主義者幾乎已贏得了關於分離的公民投票權。”“要不是德克勒克和曼德拉達成了一致,黑人佔多數的南非在上臺執政的轉型中肯定會有更多的流血事件發生。”在政治問題專家這個群體中——還有股評家、心理健康工作者和體育預言家——過度自信似乎是難以克服的。
驗證性偏見
人們往往會去尋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你也可以試一下,沃森(P.C. Wason,1960)通過給人們呈現符合某個規律的由三個數組成的系列——2,4,6——從而證實了這一點(規律只不過是任意三個以升序排列的數 )。為了保證人們能夠發現這一規律,沃森鼓勵每個人生成一系列由三個數組成的數字組。每一次沃森都告訴他們數字組是否符合他的規律。當人們確信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規律時,就可以停止並宣佈出來。
這會出現什麼結果呢?幾乎沒有人猜對但他們卻又個個確信不疑:29個人中的23個發現了一個錯誤的規律。他們一般會形成關於這個規律的錯誤信念(例如,逐次加2),然後試圖尋找支持性 的例證(例如,嘗試8,10,12),而並非嘗試去證明自己的直覺不成立 。與尋找證據證偽自己的信念相比,我們更願意證實它們。我們把這種現象叫做驗證性偏見 (confirmation bias)。
驗證性偏見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的自我意像是如此不同尋常的穩定。在奧斯丁(Austin)的得克薩斯大學做的一些實驗中,斯旺和裡德(Swann & Read 1981;Swann & others,1992a,b,1994)發現學生們常常尋找、引出並回憶那些能確證其自我信念的反饋。他們尋找那些支持他們自我觀點的人作朋友和配偶——即使他們對自己評價很低(Swann & others,1991,1992,2000)。斯旺和裡德把這種自我驗證 比作是一個擁有支配性的自我意像的人在聚會上的表現,從來的那一刻起,這個人便在尋找著那些她知道會承認自己支配地位的客人。在交談中,她以能夠引發別人尊敬自己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在聚會後,她很難回憶起那些自己在聚會上影響微乎其微的談話,而很容易便可回憶起在聚會中自己的能言善辯。這樣她在聚會上的經歷就證實了她的自我意像。
對過度自信的矯正
我們可以從對過度自信的研究中得到什麼啟發教訓呢?一個教訓是要對別人獨斷性的陳述保持謹慎。即便當人們看起來十分確信自己是正確的時候,他們也可能是錯的。自信和能力之間沒有什麼必然一致的關係。
兩種技巧可以成功地降低過度自信。一種是即時反饋(Lichtenstein & Fischhoff,1980)。在日常生活中,天氣預報員和那些設定賭馬賠率的人每天都會得到清晰的反饋信息。因此,這兩個群體中的專家在預測自己的準確率時都做得十分出色(Fischhoff,1982)。
當人們開始思考為什麼一個觀點可能 是正確的時候,該觀點就開始看起來像是正確的了(Koehler,1991)。因此,另一種降低過度自信的方法就是讓人們去設想自己的判斷可能出錯的原因 :迫使他們去考慮無法證實自己信念的信息(Koriat & others,1980)。經理們可以堅持要求所有的提案和建議都必須涉及導致它們可能無效的原因,以鼓勵更多合理現實的判斷。
儘管如此,我們在任何一點上都不應該低估人們的自信,即便是當自我懷疑成為削弱決斷力的陷阱的時候,它也很有價值。在那些需要他們表現出智慧的時刻,那些缺乏自信的人無法毫不猶豫地說出或做出堅定的決定。雖然過度自信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基於現實的自信是有適應意義的。
直覺: [2] 心理捷徑
有時需要在十分有限而寶貴的時間內同時加工眾多的信息,所以我們的認知系統形成了專門化的心理捷徑。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做出決定和生成解釋。我們通過直覺 (heuristics)可以做到這一點,它是一種簡單、快速而有效的思維策略。在許多情形中,我們倉促間做出的概括——“那是危險的”——是有適應意義的。這種直覺判斷的速度增加了我們生存的機會。思維的生物目的首先是使我們能夠生存下去,其次才是保證我們的正確性。儘管如此,在某些情形中,快速會帶來一系列錯誤。
代表性直覺
幾個心理學家對一個由30位工程師和70位律師組成的樣本進行了訪談,然後用非常簡短的描述歸納出對他們的印象。下面的描述是從這30個工程師和70個律師組成的樣本中隨機抽出來的:
經歷兩次離婚之後,弗蘭克將他的大部分空閒時間消磨在鄉村俱樂部裡。他在俱樂部酒吧裡的話題老是集中在他悔恨自己總是試圖追隨自己尊敬的父親的足跡。他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做學問這一苦差事上,而他本可以利用這些時間學會如何在與他人的交往中變得不那麼爭強好勝。
問題: 弗蘭克是一個律師而不是一個工程師的概率是多少?
要求被試猜測弗蘭克的職業,結果80%以上的大學生猜測他肯定是一個律師(Fischhoff & Bar-Hillel,1984)。但是當被告知樣本中工程師佔了70%時,你估計他們的猜測會怎樣變化?毫無變化。學生們根本不考慮工程師和律師的基礎比率,在他們的思維中,弗蘭克更具有律師的特徵,而這似乎就是所有起作用的因素了。
代表性直覺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是指對某個事物進行評價時,在直覺的引導下,將其與某一類別的心理表徵進行比較。與大部分直覺類似的是,表徵性(典型性)通常是真實情形的一個合理指導。但並不總是如此。設想一下琳達,她31歲,單身,性格坦率,並且很聰明。她在大學時主修哲學。學生時代她對歧視和其他社會問題十分關注,並且參加過反核武器示威遊行。以這些描述為基礎,你覺得以下哪一種表述的可能更大:
a: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
b: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並且在女權運動中很活躍。
大部分人認為b更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於琳達更好地表現 出了他們心目中女權主義者的形象(Mellers & Others,2001)。設想一下:琳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兼 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概率會比僅是一個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更大嗎(無論是不是女權主義者)?正如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1983)提醒我們的那樣,兩個事件同時發生的概率不可能比一個事件單獨發生的概率更大。
易得性直覺
設想一下:問題1:字母K在單詞中更多地是以第一個字母還是第三個字母出現?問題2:柬埔寨和坦桑尼亞哪個國家的人口更多?
你很可能會根據映入頭腦中的現成例證來做出回答。假如例子在我們的記憶中是現成可得的——就像以k開頭的字母或柬埔寨人一樣——那麼我們就會假定該事件是經常發生的。通常是這樣的,所以我們經常運用這一認知規則進行判斷,我們將其稱為易得性直覺 (availability heuristic)(表3-1)。
表3-1 快速而簡單的直覺
直覺 |
定義 |
例證 |
但可能導致 |
代表性 |
對某人或某事屬於某個類別的快速判斷 |
確定卡洛斯是圖書館管理員而非司機,因為他更符合圖書管理員的形象 |
忽視其他重要信息 |
易得性 |
對事件發生概率的快速判斷中(從記憶中提取的可得性有多高?) |
校園槍擊案後估計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 |
過度重視生動鮮明的例證,並因此對錯誤的對象產生不恰當的恐懼心理 |
但有時這個規則會欺騙我們。假如給人們聽由某一性別的名人(特雷莎修女,簡·方達,蒂娜·特納)和另一性別的非名人組成的一系列混合名字序列(唐納德·斯卡爾,威廉·伍德,梅爾·賈斯珀),那些名人的名字在隨後的認知活動中更容易被人們識別。因此大部分人會回憶說剛才聽到了更多的女性名字(Mc-Kelvie,1995,1997;Tversky & Kahnman,1973)。那些鮮明的更容易形象化的事件,例如那些具有很容易形象化症狀的疾病,與那些較難形象化的事件相比可能同樣會被認為是較容易發生的(MacLeod & Campbell,1992;Sherman & others,1985)。甚至那些小說、電影和電視中的虛構情節也會給人們留下印象,深深地影響我們隨後的判斷(Gerrig & Prentice,1991;Green & others,2002)。讀者越是全神貫注和“情緒激動”(“我可以很容易地描述這些事件”),故事對他隨後信念的影響越大(Diekman & others,2000)。例如被浪漫的愛情故事吸引的讀者更可能提取影響他們性態度和行為的語句段落。
易得性直覺的運用可以揭示出一條基本的社會思維規律:人們從一條一般公理演繹出一個具體例證是很慢的,但是他們從某一個鮮明的例證歸納出一般公理則是非常迅速的。毫無疑問,在聽到或讀完關於強姦、搶劫和毆打的故事之後,加拿大人十有八九會高估——通常幅度很大——與暴力有關的犯罪率(Doob & Roberts,1988)。
易得性直覺可以解釋為何生動的奇聞軼事通常會比統計信息更引人注目,以及為何感知到的風險和真實的風險間總是非常不匹配(Allison & others,1992)。因為飛機失事的場景對我們大多數人的記憶來說都是更容易聯想起來的,尤其是9.11之後,所以我們通常認為乘商用飛機旅行要比乘小汽車旅行風險更高。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旅行者在出行同樣距離的情況下,發生汽車事故死亡的概率是飛機失事的26倍(聯邦安全委員會,1991)。對大多數空中旅行者來說,旅行中最危險的一段便是飛機在機場降落的時候。
反事實思維
容易想像(具有認知易得性)的事件也會影響我們對負罪、遺憾、挫敗和寬慰的體驗。假如我們隊以一分之差輸掉(或贏得)了一場重要的比賽,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出這場比賽結果的另一種方式,因此我們會感到更大的遺憾(或寬慰)。設想更壞的可能情形會讓我們感覺好受一些。設想好的可能發生的情形,並且考慮我們該怎樣在下次做得更好,有助於為未來的出色表現做好準備(Boninger & others,1994;Roese,1994,1997)。
在奧運會比賽中,銅牌獲得者(他們很容易設想比賽結束後自己沒有獲得獎牌)比銀牌獲得者(他們很容易設想自己獲得金牌時的情景)顯得更快樂(Medvec & others,1995)。類似的是,學生在某一個評分等級(例如B+)內得分越高,他們的感覺就會越糟糕(Medvec & Savitsky,1997)。同樣是獲得B+,一個只差一分就可以得A-的學生就會比一個實際上做得更差一些,而剛好以多出一分獲得B+的學生感覺更糟糕。
這種反事實思維 (counterfactual thinking)——對將要發生事情的心理模擬 ——通常出現在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出可能結果的時候(Kahneman & Miller,1986;Markman & McMullen,2003)。假如我們剛剛錯過了飛機或公共汽車,我們就會想像假如 我們能在通常的時間從家裡出發,走通常的路線並且路上不聊天的話,那麼就能趕上那班飛機或汽車。假如我們誤了半個鐘頭或者走了通常的路線,那就很難設想一個不同的結果,所以我們體驗到的挫敗感要小一點。只差一點就能獲勝的球隊或競選者會反反覆覆地回想如果當時那樣做可能就會獲勝(Sanna & others,2003)。要是……就好了。
反事實思維是構成我們幸運感的基礎。如果我們剛剛好逃過了一場災難——避免了因為最後一分鐘的失球而敗北或者站在離一根墜落的冰柱非常近的地方——我們很容易想像一種負面的反事實情景(輸掉比賽,被擊中)並因此而感謝自己的“好運氣”(Teigen & others,1999)。從另一方面講,“壞運氣”則與那些本來可以不發生但卻發生了的糟糕的事情緊密相連。
事件本身越重要,反事實思維的強度就越大(Roese & Hur,1997)。那些因一場交通事故而失去愛人或孩子,或者自己的孩子被嬰兒猝死症奪去生命而受痛苦煎熬的人,通常會報告說正在重演這一悲劇而自己卻無能為力(Davis & others,1995,1996)。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場與醉酒駕車的司機相撞的事故中失去了妻子、女兒和母親。他說:“那幾個月,我將那天的那場事故在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我不斷地重演那一天,試圖改變事情發生的順序以避免那場事故”(Sittser,1994)。
儘管如此,絕大部分人對已做的事情的悔恨比對沒有做的事情的悔恨要小。例如:“我真希望我上大學的時候能夠更嚴肅一些”或者“我應該在爸爸去世之前就告訴他我有多麼愛他”(Gilovich & Medvec,1994;Gilovich & others,2003;Savitsky & others,1997)。(在一項針對成年人的調查中,最常見的悔恨是未能更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學業。)如果我們敢於更經常地在超出我們感到舒適的範圍外做出反應——去冒險,面對失敗,至少曾經嘗試過,我們是否能夠因此而少些悔恨呢?[儘管如此,人們更經常地為做為而非不做為感到歉意 (Zeelenberg & others,1998)。]
錯覺思維
另一種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思維方式是我們試圖在隨機事件中尋找規律,這種傾向會令我們誤入歧途。
錯覺相關
要在沒有相關的地方看到相關很容易。當我們期待發現某種重要的聯繫時,我們很容易會將各隨機事件聯繫起來,從而知覺到一種錯覺相關 (illusory correlation)。沃德和詹金斯(Ward & Jenkins,1965)向人們報告了一個假想的50天造雲試驗的結果。他們告訴被試在這50天中的哪幾天造了雲,哪幾天下了雨。這些信息只是一堆隨機信息的混合,有時造雲之後下了雨,而有時並沒有下。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確信——與他們對於造雲效應的觀點相一致——他們確實在人造雲和下雨之間發現了相關。
另一些實驗也證實了人們很容易將隨機事件知覺為對自己信念的支持(Crocker,1981;Jennings & others,1982;Trolier & Hamilton,1986)。假如我們相信事件之間存在相關,我們更可能注意並回憶出某些支持性的證據。假如我們相信前兆與事件本身有聯繫,我們就會有意注意並記住前兆和稍後相繼出現的一些事件。我們很少能注意到並記住一直以來不尋常的事件之間其實並無一致關係。假如在我們想起某個朋友之後,恰好他打來電話給我們,我們就會注意並記住這個聯繫。我們並不會去注意一直以來當我們想起某個朋友時並不會接著聽到他打來電話,或者我們接到的並不是我們所想念的朋友打來的電話。
人們不僅僅想看到他們期待的結果,而且還想看到他們想要 的聯繫。在一個實驗中,伯恩德森等人(Berndsen & others,1996)給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生展示虛構的學生言論,其內容為支持或反對在荷蘭大學中將荷蘭語課改為英語課,並且告訴他們這項政策將在獲得最高支持率的大學試點。接下來會讓學生們看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和另外一所大學的觀點分佈情況相同。對於有著既定傾向的學生來說,該結果是一種虛假的相關;反對語言轉換的學生更可能將自己所在大學學生的言論知覺為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學更反對這項政策。
控制錯覺
將隨機事件知覺為有聯繫的傾向往往容易產生一種控制錯覺 (illusion of control)——認為各種隨機事件受自己影響 。這是驅使賭徒不斷賭博的動力,也是令我們其餘的人為許多不可能完成之事努力拼搏的原因。
賭博 蘭格(Langer,1977)對賭博行為的實驗證實了控制錯覺的存在。與那些由別人分配彩票號碼的人相比,自己抽彩的人,當要求他們出售彩票的時候,其要價是前者的四倍。當和一個笨拙而緊張的人玩隨機遊戲時,他們會比和一個精明而自信的對手玩時下的注要多得多。擲骰子和轉動輪盤都會增加人們的信心(Wohl & Enzle,2002)。通過這些和其他一些方法,50多個實驗都一致發現人們行動時往往認為他們能夠預測並控制隨機事件(Presson & Benassi,1996;Thompson & others,1998)。
對真實生活中賭博行為的觀察驗證了這一實驗發現。擲骰子的人希望擲出小點時出手相對輕柔,而擲出大點時則出手相對較重(Henslin,1967)。賭博產業正是依靠這一賭徒錯覺而興旺發達起來。賭徒一旦賭贏了就歸因於自己的技術或預見力。如果輸了就是“差一點就成了”或者“倒黴”——也可能(對體育賭徒來說)是由於裁判的一個錯誤的判罰或足球的一次奇怪的反彈所致(Gilovich & Douglas,1986)。
股票交易者同樣喜歡由自己選擇和控制股票交易所帶來的“權力加強感”,就好像他們的控制比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做得還要好。一個廣告宣稱網上投資“就是和控制有關的”。唉,控制錯覺導致人們過度自信,同時,在考慮了交易成本後也會給人們帶來經常性的損失(Barber & Odean,2001)。
趨均數迴歸 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1974)發現了另一條可能產生控制錯覺的路徑:我們沒有認識到趨均數迴歸 (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這一統計學現象。由於測驗分數部分地由於隨機影響而上下波動,所以絕大部分上一次考試得分很高的人下一次的考試分數將稍有下降。因為他們第一次的分數達到了最高值,所以其第二次的分數更可能下降(“迴歸”),趨向其自身的均值而並非將最高值推向更高。(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每次作業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學生,即使並非每次都是最好,也很可能會在課程結束時在班級內成績名列第一的原因。)反過來講,在第一次考試中得分最低的學生很有可能在以後的考試中會提高成績。如果那些得分最低的學生在第一次考試後去老師那裡尋求幫助,當其成績提高時,老師可能會認為自己的輔導是有效的,儘管實際上它並沒起任何作用。
事實上,當事情處於最低谷時,我們會嘗試任何行為,而無論我們嘗試什麼——去看心理治療師,開始一個新的節食-鍛鍊計劃,閱讀一本關於自助的書——都更可能發生改善而非進一步惡化。有時我們會認識到事情不會持續停留在某一個極好或極壞的點上。經驗告訴我們,當所有事情都非常順利時,一定會在什麼方面出點問題。當生活給我們沉重打擊時,我們通常都期望事情會變得好起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認識到這種迴歸效應。我們經常困惑於為何棒球年度新人的第二個賽季總會相對平庸——是他過於自信了嗎?我們似乎都忘記了異乎尋常的表現總要回歸到正常狀態。
通過模擬運用獎勵和懲罰的結果,沙夫納(Schaffner,1985)演示出控制錯覺可能會怎樣滲透到人們的交往中。他邀請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的學生來訓練一個想像中的四年級生“哈羅德”在早晨8:30來到學校。在三週內的每一個上學日,一臺計算機顯示出“哈羅德”到校的時間,通常在8:20~8:40之間。接著學生們選擇一個針對哈羅德的反應,該反應在強烈表揚和批評之間。你可能已經料到了,通常當哈羅德在8:30之前到校時他們會表揚他,而如果哈羅德8:30以後才來,他們會批評他。由於沙夫納編制的使計算機演示到校時間的程序是隨機的,在受批評之後哈羅德的到校時間通常會有所改善(向8:30迴歸)。例如,如果哈羅德8:39分才來到學校,他肯定會被批評,而他隨機選擇的第二天的到校時間很可能會早於8:39,因此,儘管他們的批評不起任何作用 ,絕大部分學生在做完實驗後仍相信自己的批評是有效的。
這個實驗證實了特韋爾斯基和卡尼曼的富有挑戰性的結論:自然就是如此這般運作的,我們經常因為別人受到獎勵而感到自己受懲罰,卻因為懲罰別人而感到自己受獎勵。在現實中,正如每一個學心理學的學生都知道的那樣,對完成某事的積極強化通常更有效並且會有較少的負面效應。
情緒和判斷
社會判斷既包括有效但也容易出錯的信息加工過程,也包括我們的感覺:情緒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們並不是冷冰冰的計算機,我們是有感情的生物。一些最新的研究通過比較幸福和悲傷的個體揭示出了情緒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認知活動(Myers,1993,2000)。不幸的人,尤其是失去了親人或抑鬱病人,傾向於顯得無精打采,社會行為退縮,甚至變得很脆弱。他們也更傾向於自我關注和陷於冥想。只要沒有完全絕望,抑鬱的情緒會激發強烈的思索——尋找那些使個體的生存環境更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信息(Weary & Edwards,1994)。
快樂的人正好相反,是異常的精力充沛、果斷、有創造力和合群。與不快樂的人相比,他們更信任他人,更可愛也更有責任心。如果人們在商場購物時獲贈禮品,從而一時覺得心情愉快,那麼在一段時間之後的一個不相關的調查中,他們將報告說自己的車和電視都十分正常——如果你相信他們說的話,你會誤以為他們的車和電視真的比那些沒有獲贈禮物者的更好。
情緒會滲入到我們的思維中。對那些正在享受自己的球隊在世界盃上的勝利的西德人(Schwarz & others,1987)或者剛看完一部溫馨電影的澳大利亞人(Forgans & Moylan,1987)來說,人們似乎個個都是熱心腸,生活簡直好極了。在1990年阿拉巴馬和奧本的一場橄欖球賽後(而非賽前),獲勝的阿拉巴馬球迷與心情鬱悶的奧本球迷相比,前者認為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更低,潛在的破壞性也更小(Schweitzei & others,1992)。在愉悅情緒的感染下,世界顯得更友好,做決定似乎也很簡單,人們也更樂意回憶那些好消息(Johnson & Tversky,1983;Isen & Means,1983;Stone & Glass,1986)。
而如果心情陰鬱低落的話,思維將會轉向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軌道。摘下玫瑰色的眼鏡,換上深色的眼鏡。這時,壞心情將會啟動我們對消極事件的記憶(Bower,1987;Johnson & Magaro,1987)。我們的人際關係變質了,我們的自我意像驟然下降,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變黯淡了,別人的行為看起來似乎更包含惡意了(Brown & Taylor,1986;Mayer & Salovey,1987)。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約瑟夫·福格斯(Joseph Forgas)被抑鬱者的“記憶和判斷跟隨情緒色調而變化”現象所震驚。為了解釋這種“情緒浸入”,他開始做實驗。想像你自己正在這樣一個實驗當中。通過催眠,福格斯與其同事(1984)引發你愉悅或抑鬱的心情,然後讓你看一盤你與別人談話的錄像帶(前一天製作)。如果你正處於快樂的情緒中,你會對自己看到的感到十分滿意,並且能從中證實自己的自信、興趣和社會技能。如果你被置入了糟糕的情緒中,同一盤錄像帶好像揭示出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你——總是那麼拘謹、緊張和口齒不清(圖3-7)。考慮到你的情緒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你的判斷,所以在實驗結束前,研究者將把你喚回到歡樂的情緒下,你將為事情變得光明而感到安心。令人驚奇的是,羅斯和弗萊徹(Ross & Fletcher,1985)指出,我們並不將這種認知的轉變歸因於情緒的改變,而寧可相信世界確實看起來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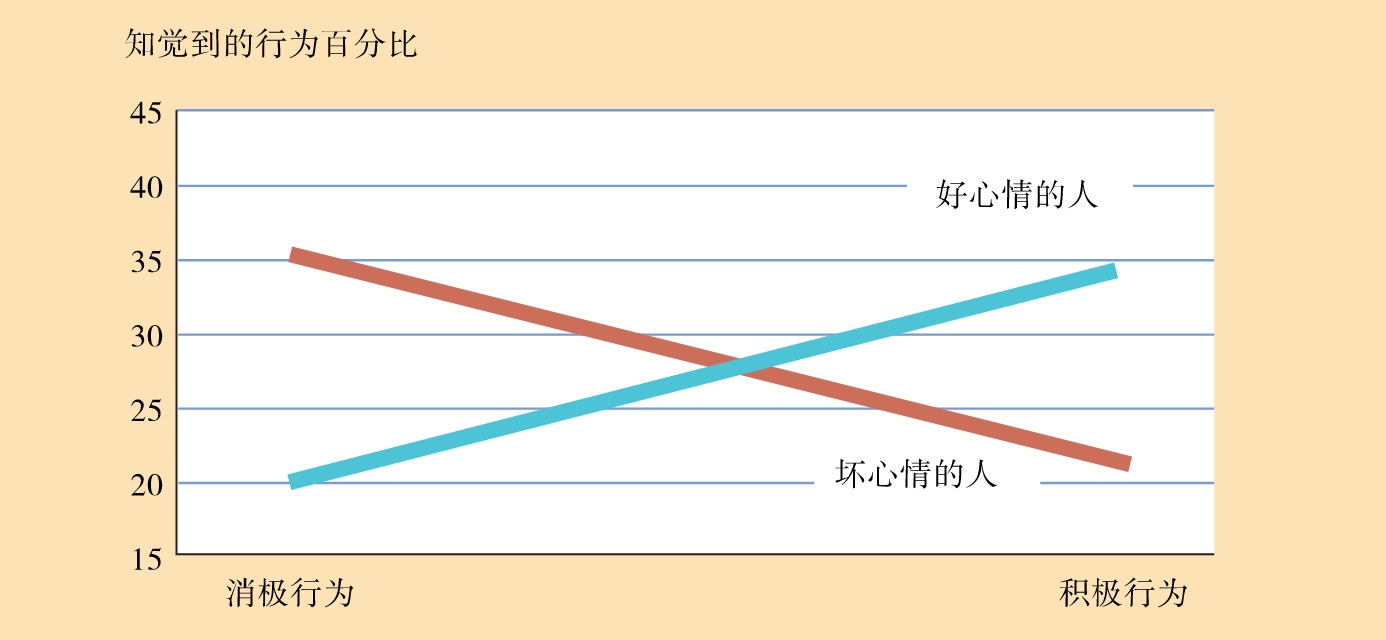
圖3-7
暫時性的好或壞情緒會強烈地影響人們對錄像帶中自己行為的評價。那些在壞情緒下的個體發現自己的積極行為明顯少得多。
我們的情緒部分地是通過將與其相關的經驗帶入頭腦來給我們的所見所聞著色。在糟糕的情緒下,我們的思維也更抑鬱。與情緒有關的思維可能會將我們從對其他事情的複雜思維引開。因此,當某種情緒被喚起——生氣或好心情,我們似乎更可能在倉促間做決定或者根據刻板印象來評價別人(Bodenhausen & others,1994;Paulhus & Lim,1994)。(除此之外,為什麼要冒事後大動感情的風險去深入地思考一些事情,例如戰爭爆發的可能性?)
情緒對簡單、“自動化”的思維的影響比對複雜、“有意控制”的思維要小(Hartlage & others,1993)。因此,福格斯在1993年就注意到,當我們評價與眾不同的人而非普通人、解釋複雜而非簡單的人際衝突時,我們的思維更可能受到情緒的影響。我們思考得越多,思維就越會受情緒的浸染。
小結
心理學研究者一直以來都在探索大腦信息加工方面的驚人能力。我們在自動、有效和直覺思維方面擁有巨大的能力。我們的認知效率儘管在通常情況下適應良好,但偶爾也會以出錯為代價。既然一般情況下我們意識不到這些進入我們頭腦中的錯誤,那麼明確我們形成並維持錯誤觀念的途徑——“非理性的原因”——對我們就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們經常高估自己的判斷。這種過度自信現象部分來源於我們更容易描繪自己正確而非錯誤的緣由。另外,人們更有可能去尋找那些支持而非否定自己的信息。
其次,當別人給我們提供很有說服力的軼聞或甚至是毫無價值的信息時,我們經常會忽視有用的基準信息。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更容易回憶起(易得性)生動的信息。
第三,我們經常在相關錯覺和個人控制之間搖擺。在不存在相關的地方知覺到相關(錯覺相關)和認為自己可以預測並控制隨機事件(控制錯覺)聽起來很誘人。
最後,情緒會影響判斷。好的和壞的情緒會激起個體對與之相關的經歷的回憶。情緒會給我們對當前經歷的解釋著色。通過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情緒還會影響我們做判斷時思考的深度和效率。
我們的信念傾向於自我實現嗎
在考慮過我們如何解釋和評價別人——高效、適應但有時會出錯——最後讓我們來思考我們的社會判斷結果。我們的社會信念起作用嗎?它們會改變現實嗎?
我們的社會信念和判斷是起作用的,因為它們確實起一定的影響作用。它們會影響我們的感覺和行動,並通過這樣做改變自己的現實。當觀念引導我們以證實自己的方式行動時,這就成為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所說的自我實現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錯誤的自我實現信念。默頓指出,如果人們相信銀行即將倒閉,紛紛排隊去提款,他們錯誤的直覺便可以創造出事實。如果人們相信股票會上漲那麼它們可能真的會上漲(參看“聚焦: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
在一個著名的關於“實驗者偏見”的研究中,羅伯特·羅森塔爾(Rosenthal,1985)發現研究中的被試會堅持等候他們期待結果的出現。在一個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試判斷照片中出現的不同人的成功。研究者給所有被試讀相同的指導語,並給他們看同樣的照片。儘管如此,那些被引導期望做出較高評價的研究者比那些認為被試會把照片中的人看做失敗者的研究者獲得的評價更高。更為令人吃驚且富有爭議的是,報告指出老師對學生的信念會產生類似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老師相信一個學生數學很好,他/她會真的做得很好嗎?讓我們來檢驗一下。
老師的期望與學生的表現
老師確實對一部分學生的期望比對其他學生更高。如果你在學校有一個成績比你好的兄弟或姐妹,如果你獲得老師諸如“很有才華”或“學習能力不足”這樣的評語,或者被認為是“能力很高”的或“能力一般”的學生,那麼你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可能和老師在辦公室的談話帶給你超出自己實際水平的名聲,也可能你的新老師仔細翻閱了你的學籍檔案或發現了你的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老師的這種期望會影響學生的表現嗎?很顯然老師的評價和學生的成績的確有相關:老師對那些做得好的學生的評價也高。那主要是由於老師準確地知覺到了學生的能力和成就(Jussim & others,1996;Smith & others,1998,1999;Trouilloud & others,2002)。
但是老師的評價是否真的是學生行為的原因 而不僅僅是結果呢?威廉·卡拉諾和菲莉絲·梅隆(Crano & Mellon,1978)對4300名英國學齡兒童做的一項相關研究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並不僅僅是良好的表現會伴隨老師的更高評價,相反的過程也同樣存在。
我們能用實驗的方法檢驗這種“教師期望效應”嗎?假如我們有意讓老師產生這樣的印象,達娜、薩莉、託德和曼紐爾——四個隨機選擇的學生——能力超常。老師是否會給這四個學生特殊的關照,引導他們做出更好的行為表現?在一個著名的研究中,羅森塔爾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1968)的確發現了這個現象。從舊金山的一所小學中隨機選擇幾名被試並告訴他們智力超常,而這些人真的在隨後的IQ測驗中出現了飛躍。
聚焦 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
1981年1月6日的晚上,佛羅里達一個著名的投資顧問約瑟夫·格蘭維爾拍電報給他的客戶:“股價將暴跌,明天拋出。”格蘭維爾的話不久就傳開了,1月7日成為紐約股市交易所建市以來交易量最大的一天。所有人都說,市值損失了400億美元。
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前,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將這樣的股市心理學比作當時由倫敦報界舉辦的選美競賽。為了獲得勝利,一份報紙必須在一百張面孔中選出六張,這六張同時也要被其他參賽報紙選中最多次數。因此,正如凱恩斯所寫的那樣:“每一個參賽者都不是要選出他自己認為最漂亮的面孔,而是要選出那些最可能滿足其他參賽者偏好的面孔。
同樣投資者不是要試圖選出滿足自己偏好的股票,而是選擇滿足其他投資者偏好的股票。這個遊戲的名稱叫做預測他人的行為。正如華爾街一位基金經理的解釋:“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格蘭維爾的觀點,但那根本不是關鍵所在。”如果你認為他的建議會使其他人賣出,那麼你會想在股價下跌更多之前儘快出手。如果你預測別人會買進,你現在就會快速買進以趕上股價的上漲。
股市的自我實現心理學在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表現到了極點,此時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下跌了20%。在這個大跌的過程中,媒體和各種謠言比較關注對這一壞消息的解釋。一旦報道出來,解釋性的新聞故事可能會進一步降低人們的預期,使正在下降的價格跌得更低。當然這個過程也可以完全反過來,即在股價上漲時進一步強化這一好消息。
在2000年4月,動搖的技術股市再次驗證了自我實現心理學,現在被稱為“動力投資。”在連續兩年熱情高漲地買進股票後(因為股價在上漲),人們開始瘋狂地拋售(因為股價正在下跌)。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指出,股市如此瘋狂地搖擺——“非理性繁榮”之後緊跟著暴跌——主要是自我造成的。
這個引人注目的結果好像顯示出學校中“差生”的問題可能折射出老師對他們較低的期望。這個發現很快在國家媒體上公佈於眾,同時也進入了許多大學的心理學和教育學的教材。進一步的分析揭示出這種“教師期望效應”並不像最初的研究那樣有說服力和可靠。事實上,後來發現這些研究“異常難以重複驗證”(Spitz,1999)。根據羅森塔爾的統計,在500個左右發表的研究中只有五分之二確實可以驗證期望顯著地影響行為(Rosenthal,1991,2002)。但是較低的期望並不會毀掉一個有能力的孩子,同樣較高的期望也不會魔術般地將一個學習吃力的孩子變成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詞的畢業生代表。人類的天性不是如此易變的。
較高的期望確實會影響成就低的人,對他們來說老師的正面態度可能是一縷帶來希望的清新空氣(Madon & others,1997)。期望是如何傳達的呢?羅森塔爾和其他研究者指出,老師對那些“潛力較高的學生”施以更多的關注、微笑和點頭。老師也有可能花更多的時間教導這些有才華的學生,給他們設定更高的目標,更多地對他們家訪,並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回答問題(Cooper,1983;Harris & Rosenthal,1985,1986;Jussim,1986)。
在一個研究中,巴巴德等人(Babad,Bernieri,& Rosenthal,1991)錄製了一段老師與學生談話或者談論學生的錄像,老師看不到這些學生,老師對這些學生報以較高或較低的期望。一段隨機10秒的有關老師聲音或面孔的畫面已經足以告訴觀眾們——既有兒童也有成人——這是一個出色的學生還是一般的學生以及老師在多大程度上喜歡這個學生。(你看到的完全正確,只需要10秒。)儘管老師認為他們能夠掩飾自己的感情,但是學生卻對老師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非常敏感(圖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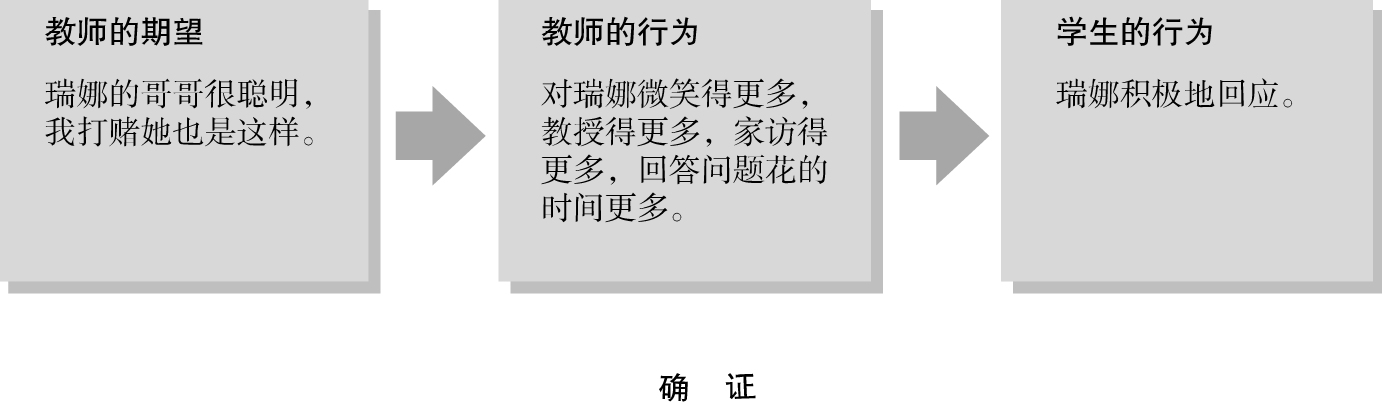
圖3-8 自我實現預言
教師的期望會變成自我實現預言。
看完關於老師對學生期望的實驗讓我也很想知道學生 對老師的期望效應情況。毫無疑問在課程開始之前你就已經聽說了“史密斯教授很有趣”和“約翰教授是一個乏味的傢伙”。費爾德曼等人發現(Feldman & Prohaska,1979;Feldman & Theiss,1982),這樣的期望對學生和老師都有影響。在一個學習實驗中,那些期望自己被一個出色的老師所教的學生比對老師期望較低的學生覺得老師更出色和有趣。此外,學生實際上學到的東西也更多。在一個後繼實驗中,費爾德曼和普羅哈斯卡錄製了一些老師的錄像並且讓觀看者評價他們的表現。當給某個老師分派的學生通過非言語行為傳達出積極的期望時,該老師被評價為最有能力。
為了看一看是否在實際的課堂上也存在這種效應,一個由戴維·賈米森(Jamieson,1987)領導的研究小組對安大略省的四個高中班進行了實驗研究,這四個班的一門課程由一位新調來的老師來教授。在個人訪談中,他們告訴其中兩個班的學生其他所有學生和研究者都對這位新老師評價很高。研究發現,與對照班級相比,被賦予了更好期望的學生在上課時聽得更專心。在學期末,他們也獲得了更好的成績並評價老師講得更清楚。看起來,一個班裡的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和老師對學生的態度同樣重要。
從他人那裡獲得我們的期望
雖然我們可以比較準確地測量研究者和教師的期望,而且偶爾這種期望會表現為自我實現預言。但這種效應的可推廣程度如何?我們能從別人那裡獲得我們的期望嗎?研究表明自我實現的預言在工作情境中(擁有較高或較低期望的經理)、法庭上(指導陪審團的法官)和模擬的警務情境中(認為嫌疑犯有罪或無辜的審訊者)也同樣存在(Kassin & others,2003;Rosenthal,2003)。
自我實現的預言會影響我們的人際關係嗎?要對我們懷有消極預期的人表現得友好並引起他們的善意回應是需要時間的,這種迴應會證偽 我們的預期。但在社會互動中另一個更為普遍的發現是:是的,我們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我們預期的結果(Olson & others,1996)。
在實驗室遊戲中,敵意幾乎總是招致敵意:那些將對手知覺為不合作的人很容易變得不合作(Kelley & Stahelski,1970)。在有衝突的地方,會存在許多自我驗證的錯誤信念。如果每一個團體都將其他團體知覺為攻擊性的、怨恨的和報復性的,那會招致其他團體表現出這樣的行為以進行自我防衛,從而形成一個不間斷的惡性循環。我猜想妻子心情很差還是心情舒暢而可愛會影響我對她的行為方式,從而引發她的某些行為以驗證我的信念。
那麼當伴侶理想化對方時是否更容易保持親密關係呢?對伴侶品質的積極錯覺會導致其自我實現?還是他們更經常表現出自我挫敗,一次次地製造自己無法實現並最終會破滅的期望?桑德拉·默裡等人(Murray & others,1996,2000)對滑鐵盧大學戀人進行追蹤研究,發現對伴侶積極的理想是好的預兆。理想化有助於減緩衝突,保持滿意度,將自我知覺的青蛙變為王子和公主。當某人真愛並崇拜我們時,這有助於我們成為他或她想像中的那個人。愛有助於創造出想像中的真實。
在夫妻之間同樣如此,那些擔心伴侶不愛和不接受自己的人將微小的傷害解釋為拒絕,導致他們貶損並疏遠伴侶。那些對伴侶的愛和接受抱有信心的人表現出較少的自我保護,與伴侶的關係也更親密(Murray & others,2003)。愛的確有助於創造出想像中的真實。
馬克·斯奈德(Snyder,1984)在明尼蘇達大學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揭示出,一旦形成錯誤的社會信念,就可能引發他人做出某些行為反應以支持這些信念,這種現象叫做行為確證 (behavioral confirmation)。在一個經典的實驗中,斯奈德等人(Snyder,Tanke,& Berscheid,1977)讓男學生和他們認為有吸引力和沒有吸引力的女性通電話(通過給他們呈現一張圖片)。對根據通話過程中女性聲音的分析假想為有吸引力的女性比假想為無吸引力的女性,男學生與之交談時要熱情得多。男性錯誤的信念會引導他們的行動,形成符合他們認為美麗的女人會悅人心意的刻板印象,從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人們與抱有錯誤信念的同伴交往時也會發生行為確證現象。那些被別人認為孤獨的人表現出更少的社會化行為(Rotenberg & others,2002),被認為大男子主義的男性對女性表現出更少的親善行為(Pinel,2002),被認為熱情的面試者會表現得更熱情。
當我們認為他人為我們所吸引時,也會出現這種行為確證現象。將你自己想像為羅伯特·裡奇和傑夫瑞·雷伯(Ridge & Reber,2002)最近所做的一個實驗中的60名年輕男性或60名年輕女性中的一位。每一位男性都將見到一位女性並評估她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教師的職位。在做這些之前,要告訴他對方被他吸引(根據他對自陳問卷的回答)或未被吸引(想像一下你被告知那個將要見面的人很想了解你,和你約會,或者對你一點興趣也沒有)。結果確實存在行為確證:應聘者認為感覺到了一種表現出更多輕佻的吸引(並且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裡奇和雷伯認為這一過程可能是性騷擾的根源之一。如果一位女性的行為看起來好像在確證一位男性的信念,他可能接著逐步將他的追求升級,直到足夠明顯使那位女性覺察並將這些行為解釋為不恰當或騷擾。
期望也會影響兒童的行為。在觀察了三個教室的垃圾量之後,理查德·米勒等人(Miller & others,1975)讓老師和其他人反覆在某一個班級講教室應該保持整潔和乾淨。這一行為使廢紙簍的垃圾量增加了15%~45%,但這只是暫時的。另一個班級,同樣只將15%的垃圾放進了廢紙簍,對這一行為進行反覆的表揚,稱讚他們保持很整潔和乾淨。連續表揚8天,在兩週後,這些兒童將80%的垃圾放進了廢紙簍,符合了老師對他們的期望。反覆告訴兒童們他們刻苦努力和真誠善良(而不是懶惰和自私),接著他們可能真的這樣行事。
這些實驗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信念,例如對殘疾人或某一種族或某一性別的人的刻板印象,如何促使個體進行自我確證。我們幫助建構我們的社會現實。別人怎樣對待我們可以反映出我們和別人怎樣對待他們。
像任何一種社會現象一樣,確證他人期望的傾向確實有其侷限性。期望常可以預測行為僅僅是因為它們很準確(Jussim,1993)。並且,如果個體預先被告知別人對他的期望,則可能引發他做出行動去克服它(Hilton & Darley,1985;Swann,1987)。假如查克知道珍妮認為他是一個愚蠢的傢伙,他肯定會去證明她的印象是錯的。假如珍妮知道查克認為她對人冷淡,她可能會主動地去反駁他的想法。
威廉·斯旺和羅賓·埃利(Swann & Ely,1984)報告了一種我們可能不會確證他人期望的例外情況:當他的期望與我們清晰的自我概念相矛盾時。例如,斯旺和埃利發現,假如一個相當外向的人被一個認為她很內向的人所採訪,這時採訪者的態度而非被採訪者的行為會發生變化。與此相反,對自己並不確定的受訪者會更經常地去迎合採訪者的期望。
個體對於自我的信念也存在自我實現。在一系列實驗中,斯蒂文·舍曼(Sherman,1980)發現人們通常會實現他們對自己行為的預測。當打電話要求布盧明頓和印第安那的居民為美國一個癌症團體做3小時駕駛志願服務時,只有4%的人同意這樣做。當打電話要求一個由其他居民組成的對照組預測如果自己接到這樣的一個請求將如何反應時,幾乎一半的人預測他們會提供幫助——並且當癌症團體和他們聯繫時,大部分人確實答應這樣做。在特定的情境中,當我們闡釋自己行動計劃時,我們似乎更可能會那樣做。
小結
我們的信念有時會產生重要的作用。通常,我們對別人的信念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但是對研究者偏見和教師期望的研究顯示,認為某些人的能力超常(或能力不足)的錯誤信念會引導教師和研究者給予那些人特別的關照。這可能會引發他們做出更出色(或平庸)的表現,並且因此看起來似乎會確證一個實際上錯誤的假定。與此相類似,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獲得對自己期望的行為確證。
結論
社會認知研究揭示出我們的信息加工能力的確有很高的效率和適應性(“具有上帝的理解力!”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驚呼),然而卻難以避免可預測性的錯誤和誤判(“頭腦裡裝滿了稻草”,艾略特說)。那麼從這種研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實用性的知識和對人類本性的洞見呢?
我們已經回顧了人們有時相信那些不正確的信念的原因。我們很難對這些實驗置之不理:因為其中的大部分被試是高智商人群,而且通常是頂尖大學的學生。除此以外,為保證他們做出正確的回答,即使用報酬激勵被試以最理想化的方式思考,仍然存在某些偏見和扭曲。正如斯洛維克指出,這類錯覺“有一種持久的性質,與知覺錯覺並無不同”(Slovic,1972)。
社會認知心理學的研究因此可以映照出文學、哲學和宗教等領域對人性的各種不同的反思。許多心理學研究者花費畢生的心血去探索人類心理的神祕力量。我們足夠聰明去破解自身的遺傳密碼,發明可以與人對話的電腦,以及將人類送上月球。為人類理性而三次歡呼。
兩次歡呼是因為對於高效判斷的偏向使我們的直覺難以避免誤判。我們相當容易形成和保持錯誤信念。我們容易受先入之見和過度自信引導,被鮮活的軼聞、甚至不可能存在的虛假相關和控制所說服,我們建構起自己的社會信念並繼而影響他人去確證它們。正如小說家馬德琳·恩格爾所言:“裸露的智力是一件十分不準確的工具。”
但是,這些實驗是否僅僅是在倒黴的被試頭上玩弄的把戲,使他們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糟糕?尼斯比特和羅斯(Nisbett & Ross,1980)主張,實驗程序高估了我們的直覺能力。實驗通常給被試呈現清楚的證據,並告知他們要對其認知能力進行測驗。生活從不會告訴我們:“這裡有一些證據,下面請將你的智力調整到最佳狀態來回答這些問題。”
通常我們的日常失誤無關緊要,但也並不總是如此。錯誤的映像、解釋和信念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後果。當我們要做出重大的社會判斷時,有時甚至很小的偏見就可以造成相當大的社會效應:為什麼如此多的人無家可歸?遭遇不幸?行凶殺人?我的朋友喜歡的是我本人還是我的錢?認知偏見甚至會潛入到複雜的科學思維。自從舊約的作者提出“沒有人能夠看出自己的錯誤”以來,人類的天性在過去三千年中幾乎沒有什麼改變。
為避免得出所有的信念都是荒謬的偏激結論,我趕緊平衡一下自己的描述。對我們思維不完美性的出色分析本身就是對人類智慧的一大貢獻(假如有人爭論說人類的所有思維都是錯覺,那麼該斷言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因為這句話本身也是一個錯覺。用邏輯語言可以這樣表述:“所有的概括都是錯誤的,這一個也不例外。”)
正如醫學假設任何器官都具有一定的功能一樣,行為學家發現,假設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在通常情況下是具有適應性的似乎很有用(Funder,1987;Kruglanski & Ajzen,1983;Swann,1984)。某些思維規則會令人們產生錯誤信念,而且導致了直覺思維中的缺陷,而它們在人類生活中卻運轉得很好。通常情況下,這些錯誤是我們對複雜信息進行簡化加工的心理捷徑的副產品。
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Simon,1957)第一次提出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西蒙指出,為了應對現實,我們會簡化思維過程。設想一盤國際象棋遊戲的複雜性:其中可能的局數比整個宇宙中的粒子數還要多。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我們可能會採用某些簡化的規則——直覺。這些直覺有時會使我們誤入歧途,但是它們確實可以幫我們做出高效而迅速的決定。
錯覺思維同樣可以產生於有利於我們生存的直覺。直覺以許多方式“使我們更聰明”(Gigerenzer & Todd,1999)。相信我們具有控制事件的能力有助於我們保持希望和努力。如果事情有時可以控制而有時卻無法控制,我們會通過積極的思維將成果最大化。看來樂觀主義是有益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信念像科學理論——雖然有時會出錯但總的說來卻十分有用。正如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Fiske,1992)所說,“思維是為了行動。”
當我們一直在試圖改進某種理論時,難道我們不能同樣試圖減少這種錯誤的社會思維嗎?在學校中,數學老師可以一直教學、教學、教學,直到大腦最終被訓練成可以自動而準確地加工數字信息。我們假定這種能力並非來自先天;否則,我們為什麼還為這許多年的訓練而煩惱呢?心理學研究者道斯(Dawes,1980)——他為一個接一個的研究所揭示出的人們在意識層面加工信息、尤其是社會信息的加工能力十分有限而感到沮喪——建議我們同樣應該教授、教授、教授自己如何加工社會信息。
尼斯比特和羅斯(1980)認為教育確實可以減少我們犯特定類型錯誤的可能性。他們建議:
我們可以訓練人們在其自身的社會直覺中識別錯誤的可能來源。
我們專門設計有關邏輯和社會判斷的日常問題的統計學課程。受過這樣的訓練之後,人們確實能夠更好地對日常事件進行推理 (Lehman & others,1988;Nisbett & others,1987)。
我們列舉日常生活中大量豐富而具體生動的趣事和例證來進行教學,其效果會更為明顯。
我們以令人印象深刻且實用性的話語進行講授,例如:“這是個經驗方面的問題。”或者“你可以用統計數字編造,但選擇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似乎可以更好地做到這一點。”
聚焦 記者的思維方式:新聞製作中的認知偏見
“那就是這樣,”CBS的新聞節目主持人在每次播報後都如此總結。這就是新聞的理想——呈現事實的本來面目。《華爾街日報》記者手冊十分清楚地闡明瞭這一理想:“一個記者永遠不能固守於自己的先入之見,費盡心力地尋找幾乎不可能存在的證據,忽略矛盾的事實……事件而非個人的先入之見才應該構成事件的本來面目”(Blundell,1986,p.25)。
我們可能會期望它是如此。但記者也是人,印第安那大學新聞學教授斯托金(Holly Stocking)和紐約心理學家兼律師格羅斯(Paget Gross)在其《記者的思維方式》一書中總結道,記者像外行人和科學家一樣“建構現實”。在這一章中涉及到的認知偏見因此在如下6個方面影響著新聞製作。
先入之見可能會影響解釋 。記者通常“緊跟某個觀點”,這會影響其對信息的解釋。一名記者如果一開始便認為無家可歸反映出這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存在問題,那麼他可能在解釋模糊信息的同時忽略其他複雜的因素。
確證偏見可能引導他們趨向能確證自己先入之見的信息來源和問題 。由於希望報道放射物洩漏會導致新生兒殘疾這樣的新聞故事,記者可能去採訪某個同意這一觀點的人,並且接著採訪由第一個人推薦的其他人。
堅定不移的信念可能會以懷疑的面目支持先入之見 。當“貪婪的”伊萬·伯斯基在1987年華爾街內部交易醜聞中等待宣判時,他一直在尋找志願者工作,這似乎是“很多白領詐騙犯企圖給法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慣用伎倆,”一個記者輕蔑地說。而另一方面,一名因說謊而被捕的政治家,假如受人尊敬的話,便被報道為“被迷惑”或者“忘記了”。
生動的軼聞趣事看起來可能比統計信息提供更多的信息 。像他們的讀者一樣,記者可能更容易被有關超感知覺的生動故事和其他心理現象而非客觀真實的研究所打動。他們可能更容易被新的治療方法治癒了某個患者而非該療法成功率的統計信息所吸引。在一場空難之後,他們可能描述“現代空中旅行存在令人恐懼的危險因素”,而毫不關注它實際的安全記錄。
實際上並不存在相關的事件可能看起來具有相關性 。在缺乏有說服力證據的情況下,一個令人震驚的偶發事件——講述了三位少數族裔的田徑選手存在服藥問題——可能會引導記者在種族和藥物使用之間建立聯繫。
事後聰明使事後分析變得非常容易 。卡特總統試圖營救伊朗大使館中美國人質的失敗行為“從一開始便受到了詛咒”,記者們在得知這一失敗事件後 如此說。在事實發生之後,最終被證明很糟糕的決定似乎看起來格外 愚蠢。
斯托金和格羅斯猜測,確實所有的信息都需要記者和編輯進行快速加工,那麼他們應該如何避免在這一過程中滲入人類思維中的錯覺思維傾向呢?但從積極的一面來看,這些偏見的暴露可能提醒記者注意那些減少這種偏見的方法——考慮相反的結論,尋找信息來源並提出可能反駁自己觀點的問題,或者首先尋找統計信息,然後尋找有代表性的事實,或者牢記善意的人在做出決定時不摻雜自己對結果的預期認識。
小結
對社會信念和判斷的研究揭示出:我們怎樣形成和維持通常運作得很好但有時會令我們誤入歧途的信念。正如視錯覺是幫助我們組織感覺信息的認知機制的副產品一樣,我們的錯誤判斷也是運作得很好的思維策略(直覺)的副產品。但是它們依然是錯誤,會扭曲我們對現實的知覺並削弱我們對別人的判斷。因此社會心理學同時關注社會思維的優勢和不足。
個人後記:反思直覺的力量和侷限性
對驕傲和錯誤的研究是否會令人感覺不快?的確我們不但承認人類具有某些侷限性這一確定的事實,而且贊同人類並不僅僅是機器這一更深一層的訊息。我們的主觀體驗是構成人性的材料——我們的藝術和音樂,我們對友誼和戀愛的享受,我們的神祕性和宗教體驗。
那些研究錯覺思維的認知和社會心理學家並不是要使我們成為毫無感情的邏輯機器。他們知道情感可以豐富人們的體驗和直覺,而且它還是創造性想法的一個重要來源。儘管如此,他們的發現卻可以提醒人們,我們容易犯錯誤,這也正好說明我們接受嚴格思維訓練的必要性。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將其稱為:“關於學習的最大真理:其目的是開啟人們的頭腦並將它發展為思維的器官——概念思維、分析思維、序列思維。”
對社會判斷中的錯誤和錯覺的研究提醒我們去“判斷不”——帶著少許謙遜,牢記我們出現錯誤判斷的可能性。它同樣鼓勵我們不被那些看不到自己的偏見和錯誤的人的自大嚇住。我們人類是一種了不起的智慧和錯誤的混合生物,具有高貴的自尊,但並不是神。
這種對人類能力的自謙和懷疑是科學和宗教的核心所在。許多現代科學的奠基者是宗教信徒,他們虔誠地在自然和對人類能力的懷疑面前保持謙卑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Hooykaas,1972;Merton,1938)。科學同樣包括直覺和嚴格檢驗的互相影響。從錯覺中尋找現實需要開放的好奇心和冷靜的頭腦。這種觀點被證明是對待生活的正確態度:批判而不憤世嫉俗,好奇而不受矇蔽,開放而不被操縱。
你的觀點是什麼
在閱讀本章時,你是否對人類行為產生某種假設或直覺?可能你會回想起自己或你知道的某人曾經置身其中的情境。那次經驗是否告訴你別人解釋自己所處情境的方式?是否告訴你別人如何判斷評價他人?現在,請你設計一個研究去檢驗你的假設。換句話說,在你擁有的關於人類的假設(理論)的基礎上設計一個研究——運用你自己的經驗。
聯繫社會
這一章建立在李·羅斯(Lee Ross)提出的基本歸因錯誤理論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個你在以後的章節中會不斷看到的概念。例如,我們怎麼解釋少數民族的行為(第9章:偏見)?什麼樣的錯誤知覺會導致衝突(第13章:衝突與和解)?當你在閱讀以後的章節時,不妨留意一下基本歸因錯誤,並看看人們是怎樣解釋他人行為的。
[1] 譯者注:班布里奇島從西雅圖橫穿普吉灣(Puget Sound)。瑪麗是被伊麗莎白一世下令砍頭的。儘管非洲的陸地面積是歐洲的兩倍還多,但歐洲的海岸線更長。(歐洲的海岸線更加曲折,擁有許許多多的海港和水灣,這樣的地理條件使歐洲在海上貿易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2] 譯者注:此處的直覺英文原文為heuristics,而第78頁所提及的直覺英文原文為intuition,從文中論述來看,heuristics的意思與直覺很相似,譯為直覺比譯為啟發法更便於讀者理解。
第4章 行為和態度
態度決定行為嗎
我們都是偽君子嗎
態度何時能預測行為
行為何時決定態度
角色扮演
語言何時變成信念
登門檻現象
邪惡的行為和態度
種族間的行為和種族態度
社會運動
為什麼行為會影響態度
自我展示:印象管理
自我辯解:認知不協調
自我知覺
理論比較
個人後記:通過行為改變我們自己
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做什麼樣的事,他做什麼樣的事就是什麼樣的人。
——Robert Musil,Kleine Prosa,1930
目 前,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是一種快速傳播並且有可能會引發呼吸系統急性綜合症(SARS)的致命病毒,據稱2002~2003年間發現大約800例病毒感染者。同時,受政府資助的菸草工業,每1個小時也會奪去大概同樣多數量的生命——每年大概有4900萬人(WHO,2002)。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大約將有五億 健康人將來會死於菸草導致的疾病。舉例來說,在美國,吸菸每年會導致42萬人喪生——超過了謀殺、自殺、艾滋病、交通事故和酒精藥物濫用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總和。雖然協助他人自殺也許是一種違法行為,但菸草工業似乎是個例外。
既然菸草工業為這種不幸承擔的責任相當於要為每天14架滿載的大型噴氣客機墜毀造成的不幸(還不算那些正在發展中的、難以統計的第三世界市場),承擔的責任,那麼,菸草公司的管理者們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呢。在世界兩個最大的菸草廣告商之一的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那些高層管理人員——大多是聰明的、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有合作精神的人——抱怨自己被稱為“大眾殺手”。當前任的美國衛生主管伊瓦特·庫普(Koop,1997)稱他們為誤導、欺騙我們並向我們撒了30年謊的惡棍時,他們非常氣憤。此外,他們辯護說這是吸菸者自由選擇的權利。“這是一個成癮的問題嗎?”一個副總裁問道,“我一點兒也不相信。人們可以做各種事情來表現自我和反抗社會,而吸菸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並不是最壞的一種”(Rosenblatt,1994)。
這些說法是否反映個人的態度?
如果這位管理者真的認為吸菸是一種相對健康的表現自我的方式,那這些態度是如何內化的?
或者這些說法反映了他在社會的壓力下被迫口是心非。
當人們詢問他人的態度時,他們會談及與某人或某事有關的信念和感覺,以及由此引發的行為傾向。綜合起來,態度 (attitude)可以界定為個體對事情的反應方式,這種積極或消極的反應是可以進行評價的,它通常體現在個體的信念、感覺或者行為傾向中(Olson & Zanna,1993)。態度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方法來評價世界。當我們必須對一些事情做出快速反應時,我們對其的感知方式可以指導我們的反應方式。比如,如果某個人認為 某個種族是懶惰、好鬥的,那麼他可能會不喜歡這個種族的人並且因而產生歧視。你可以按照組成態度三個基本要素的打頭字母“ABC”來記憶它們:感覺(affect)、行為傾向(behavior tendency)和認知(cognition,想法)(圖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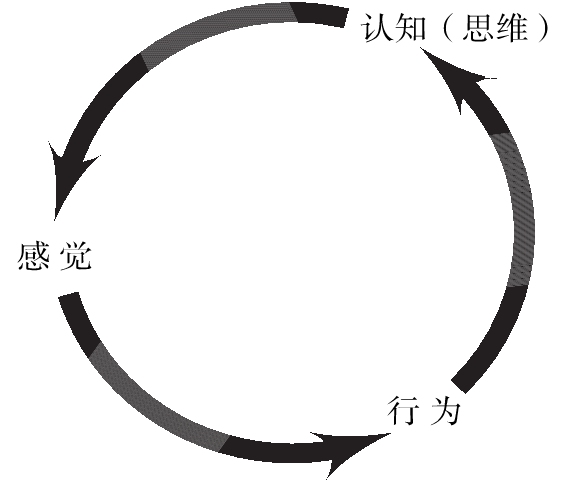
圖4-1 態度的ABC理論
態度的研究非常接近社會心理學的核心並且是其最早的關注點之一。一開始,研究者就想知道我們的態度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態度決定行為嗎
內在的態度在多大程度上,並在什麼條件下,會影響我們外在的行為?為什麼社會心理學家最初會對態度和行為之間的微弱相關感到驚奇?
“我們是 什麼(內在)”和“我們做 什麼(外在)”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關係?很久以來,哲學家、神學家和教育學家就一直在思考思維和行動、性格和行為、私人語言和公眾行為之間的關係。目前大多數教育、諮詢和兒童教養都基於這樣一種普遍性的假設,即我們的個人信念和感情決定我們的公眾行為,而且如果要改變行為,就必須改變精神和靈魂。
我們都是偽君子嗎
最初,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研究人們的態度就是為了預測他們的行為。19名劫機犯對美國的仇恨令他們製造了9.11自殺性恐怖事件,這說明了極端的態度可能會導致極端的行為。但是在1964年,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改變態度會導致行為的變化。他認為態度與行為之間是另外一種關係;如果我們的行為是馬,那麼我們的態度就是馬車。就像羅伯特·埃布爾森(Abelson,1972)認為的,我們“精通並擅長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原因,但卻非常不善於做我們已找到原因的事。”
社會心理學家艾倫·威克(Allan Wicker)的研究對態度可能具有的作用進一步提出了挑戰。通過對各種人群、態度和行為的綜述研究,他得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人們表現出的態度很難預測他們的各種行為。
學生對於作弊的態度與他們的實際作弊行為幾乎沒有關係。
對教堂的態度與星期天做禮拜的行為只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
自我描述的種族觀與真實情境中的行為幾乎不存在什麼相關。
一個態度和行為相分離的例子就是丹尼爾·巴特森等人(Batson & others,1997,1999)所說的“道德偽善”(表現出有道德水準,但實際上拒絕付出任何的代價)。他們給被試佈置了兩個任務,一個十分誘人(被試能夠掙到有可能中30美金獎的彩票),而另一個卻無聊且沒有獎勵。要求被試必須給自己安排一個任務並把剩下的一個任務安排給別人。20個人中僅僅有1人認為給自己安排有吸引力的任務是最道德的,而儘管80%的人是這樣做的。在接下來關於道德偽善的實驗中,研究者給被試一些硬幣,並且告訴他們,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可以通過私下拋擲硬幣的方法來決定任務的分配。即使他們選擇了拋擲硬幣,但還是有90%的人把自己安排在好的任務中!這一結果僅僅是由於他們自行決定硬幣朝上還是朝下的意義而導致的嗎?在另一個實驗中,貝斯頓在硬幣的每一面都貼了標籤,以明確拋擲的結果。但28人中仍然有24人給自己安排了好的任務。當道德與貪婪同處在競技場中時,通常是貪婪大獲全勝。
如果人們並不按自己所說的來做,那麼對於試圖通過改變態度來改變行為的努力常常以失敗告終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對於吸菸有害的警告也僅僅是在最低限度上影響那些吸菸者而已。公眾已經逐步認識到長時間觀看暴力電視節目會導致漠然和殘酷,因此許多人要求在電視節目中減少暴力——儘管他們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其他媒體上觀看謀殺節目。安全駕駛的呼籲對降低事故率幾乎不起什麼作用,其效力遠遠低於對限速駕駛、隔離高速路和酒後駕車的懲罰(Etzioni,1972)。
當威克和其他研究者在描述態度的弱點時,一些人格心理學家發現人格特點在預測行為上同樣無效(Mischel,1968)。如果我們想了解人們的能力,我們通常無法從自尊、焦慮或防禦性測驗中獲得更多信息。在要求明確的情況下,我們能更好地知道多數人的行為反應。
總體來說,對於控制行為因素的討論只強調了外部社會的影響作用,卻忽視了內部因素的作用,例如態度和人格。到了20世紀60年代,有人提出態度實際上什麼也決定不了,這對態度決定行為 的觀點提出了挑戰。
提出一個命題以後,隨之而來的是一個逆命題。會有一個綜合的結論嗎?對人們經常言行 不一的驚人發現促使社會心理學家去探尋其背後的原因。當然,我們推測,信念和感覺在某些時候可能 會有所不同。
的確如此。實際上,我將要解釋的內容看起來十分明顯,以至於我非常奇怪為什麼大多數的社會心理學家(包括我)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必須提醒自己:真理只有在被發現時才會變得顯而易見。
態度何時能預測行為
行為和我們表達出的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二者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一個社會心理學家找出了40個令他們之間關係複雜的因素(Triandis,1982;Kraus,1995)。如果我們能夠控制影響行為的其他因素——讓其他所有條件恆定——那態度可以精確地預測行為嗎?
什麼時候社會因素會對我們所說的話影響最小
不同於醫生測心率,社會心理學家從來就不可能在態度上得到一個直接的分數。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測量這種外顯 的態度。像其他行為一樣,外在的表現受制於外部因素的影響。以下的例子可以生動地證明這一點。美國眾議院在一次無記名投票中曾經以絕對優勢通過了一項提薪的議案,然而片刻之後的記名投票中卻以絕對優勢否決了同一項議案。在記名投票中,對批評的畏懼歪曲了其真實的觀點。在2002年底,美國許多立法者,由於感受到了9.11事件之後的恐懼、憤怒和愛國熱情,公開投票支持布什總統對伊拉克動武,但同時私下裡卻持保留意見(Nagourney,2002)。我們有時也稱之為見風使舵。
現在,社會心理學家想出了一些更巧妙的方法來精確評定態度。一種就是對講述時的面部肌肉反應進行測量(Cacioppo & Petty,1981)。面部肌肉能夠揭示出一個微笑或一個細微的皺眉嗎?另一種是,“內隱聯想測試”,用反應時來測量人們概念聯想的速度(Greenwald & others,2002,2003)。例如,我們可以通過測量人們是否會花更多時間將積極詞彙與黑人面孔聯繫起來(與將積極詞彙與白人面孔聯繫起來的時間比較)以測量內隱的種族態度。
由於知道人們並不將心事寫在臉上,社會心理學家早就渴望發現一條“通往心靈之路”。愛德華·瓊斯和哈羅德·西格爾(Jones & Sigall,1971)設計出了一種能誘發個體表達出他們真實態度的偽途徑 (bogus pipeline)法。在一個與理查德·皮治(Richard Page)一起進行的實驗中,西格爾(1971)讓羅切斯特大學的學生握住一個被鎖住的方向盤,如果沒上鎖的話,就能將一個指針撥到左面,表示不同意,或撥到右面,表示同意。當電極觸到他們的胳膊時,那個人工機器就假裝能夠測量實驗者細微的肌肉反應並告訴他們還可以測出他們將方向盤轉向左面(不同意)或右面(同意)的傾向。為了證實這一新儀器的可靠性,研究者問了學生一些問題。在一陣炫目的閃光和呼呼聲之後,儀器上的一個儀表顯示出學生的態度——不過是學生先前在一個調查中表達出的態度,只不過他們現在遺忘了。研究者用該程序讓每一個學生信服了這一實驗的可靠性。
當學生被說服之後,研究者就收走了那個態度儀器。當詢問他們對美國黑人的態度並且要求他們猜測儀器會顯示什麼時,你猜這些白人大學生會怎麼反應?相比於普通問卷測出的態度反應,實驗中的學生承認自己持有更多消極的看法。不像那些通過紙筆測驗做出反應的人——那些對美國黑人比其他美國人更敏感者——那些通過偽途徑法做出反應的人與前者的判斷正好相反。可能他們想:“我最好說實話,否則研究者會認為我自相矛盾。”
毫無疑問,最早認為測謊器有用的人可能會承認事實,對於這一點不足為奇(從這個角度來說,測謊器確實起作用了!)。同樣,有時態度—行為之間的確存在一種弱相關:平時,比如當面對菸草經營者和政客時,人們有時會表達他們私下裡並不贊成的態度。
其他因素何時對我們的行為影響最小
在任何場合下,引導我們做出反應的不僅僅是我們內在的態度,同時還有我們面對的情境。就如第5~8章將要反覆強調的,社會影響力真的非常大——大到能夠誘發人們違反他們最深層的信念。總統助理也許會做出他們明知是錯的行為。耶穌坦率的信徒彼得否認自己認識耶穌。戰俘也許會撒謊以平息俘虜自己的人的怒火。
既然如此,對許多偶然情境中的行為進行平均 估計就能讓我們更清楚地檢測到態度的影響作用嗎?預測人們的行為就像預測一個棒球或板球運動員的擊球行為一樣。任何特定情境下擊中的結果幾乎是無法預測的,因為這不僅僅受擊球者的影響,同時也受投擲者和機率因素的影響。瞭解運動員,有利於我們預測其大概的平均 擊球水平。
讓我們來看一個研究的例子,人們對於宗教的總體態度很難預測他們下週末是否會去做禮拜(因為天氣、傳教士、每個人的感覺等等都會影響做禮拜行為)。但是,宗教態度能夠很好地預測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個體總體的宗教行為(Fishbein & Ajzen,1974;Kahle & Berman,1979)。這個發現可以得出一個綜合原則 :當我們觀察個體總體的或通常行為而非單獨的某一次行為時,態度對於行為的預測效應會變得更明顯。
何時能檢測到影響行為的特定態度
其他條件可以進一步改善態度對行為預測的準確性。就像阿杰增和菲什拜因(Ajzen & Fishbein,1977;Ajzen,1982)指出的,當測量的態度非常籠統時——比如,對於亞洲人的態度——並且行為非常具體的時候——比如,是否去幫助某個具體的亞洲人——我們的確無法得出言行之間有緊密的聯繫。的確,正如菲什拜因和阿杰增所報告的,在27個這類的研究中有26個顯示態度無法預測行為。但是在所有26個研究中,當測量的態度直接與情境相關時態度確實能預測行為。因此,對於“身體健康”這樣一個籠統概念的態度並不能預測具體的鍛鍊行為和飲食習慣。人們是否會慢跑更可能依賴於他們如何看待慢跑的利弊。要更好地預測個體行為,正如在阿杰增和菲什拜因在“計劃行為的理論”中所說的,需要更好地瞭解個體的行為意向 ,和他們的自我效能與控制感(圖4-2)。

圖4-2 計劃行為的理論
菲什拜因與同事阿杰提出,個體的(a)態度、(b)知覺到的社會標準和(c)控制感共同決定行為意向。
進一步的研究——700多個,且有276000位參與者——證實了特定且相關的態度確實能夠預測行為(Six & Eches,1996;Wallace & others,1996)。例如,對避孕套的態度能有效地預測避孕套的使用行為(Sheeran & others,1999)。對於廢品回收的態度(但並非對環境問題的總體態度)能預測個體在廢品回收中的參與行為(Oskamp,1991)。要通過說服來使個體養成健康行為習慣,我們最好改變個體對於具體習慣的態度。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明確在兩種條件下態度一定能夠預測行為:(1)將影響態度和行為的其他因素最小化;(2)態度與觀察到的行為存在具體的相關。當然還有第三種情況:強有力的態度能夠更好地預測行為。
態度何時是有效的
當我們的行為是自發做出的時候,我們的態度經常是潛在地起作用。我們將熟悉的原型付諸實施,並不深入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當我們在大廳裡遇到熟人時,會下意識地打招呼“Hi”。當餐廳服務員詢問“吃得如何”時,我們下意識會回答說“很好”,即使我們覺得飯菜並不怎麼好吃。這種無意識的反應具有一定的適應性,它可以使我們騰出精力去做別的事情。就像哲學家懷特海所說:“隨著不假思索下意識即可操作的事情的增加,人類文明就提高了很大一步。”但是,當我們在一架無人駕駛的飛機上時,我們的態度是處於休眠狀態的。像習慣性行為——系安全帶、喝咖啡、上課——意識很難被激活(Ouellette & Wood,1998)。
在特殊情況下我們行為的自發性會大大降低;缺少原型,我們就需要三思而後行。如果要求人們考慮好自己的態度後再行動,那人們能否更真實地表現自我呢?這正是馬克·斯奈德和威廉·斯旺(Mark Snyder & William Swann)所研究的內容。他們先調查了明尼蘇達大學120個學生對某一僱傭政策的態度。兩週以後,斯奈德和斯旺邀請這些學生在一個性別歧視案件中擔任陪審員。僅僅那些被提醒要求記住自己態度的人其態度能預測判決結果——通過給他們“幾分鐘來組織自己對於確定性行為問題的看法和觀點。”當我們思考自己的態度時,態度才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具有自我意識的人通常會受自己態度的影響(Miller & Grush,1986)。這給人們提供了另一種關注自己內在信念的方法:讓 他們自我覺知,也許可以讓他們觀察自己在鏡子前的行為(Carver & Sceier,1981)。也許你立刻會明確意識到自己正呆在一個有一面大鏡子的房間裡。通過這種方法,人們進行自我覺知可以加強言行之間的一致性(Gibbons,1978;Froming & others,1982)。
愛德華·迪納和馬克·沃爾伯(Diener & Wallbom,1976)注意到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認為作弊是不道德的。但是他們會聽從莎士比亞筆下波洛尼厄斯的建議“真實地表現自我”嗎?迪納和沃爾伯讓華盛頓大學的學生猜一個字謎(說是測智商),並且告訴他們當屋裡的鈴響的時候就停止猜謎。在讓他們各自單獨做題的情況下,71%的學生在鈴響後繼續做題。而在那些可以自我覺知的學生中——讓他們在一面鏡子前做題同時聽錄有自己說話聲音的磁帶——只有7%的學生作弊。這就讓人想起:商店中與人等高的鏡子能讓人們更多地意識到自己對於盜竊的態度嗎?
還記得99頁巴特森對道德偽善的研究嗎?在最後的實驗中,巴特森與其同事(1999)發現鏡子確實能讓行為與內化的道德態度達成一致。當人們在鏡子前拋硬幣的時候,硬幣拋得十分公平。正好有一半的被試把好的任務安排給了其他人。
總而言之,我們不難發現,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表露出的態度和行為之間可能會從毫無關係到緊密相關(Kraus,1995)。在下述情況中,我們的態度能預測我們的行為:
其他因素的影響最小化,
態度是針對具體行為的,
當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態度是強有力的時候。
小結
我們內在的態度是如何與我們外部的行為相聯繫的呢?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態度和行為互相支持。流行的大眾觀點強調態度對行為的影響作用,但令人驚奇的是,態度——通常被認為是對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經常不能很好地預測行為。並且,改變人們的態度很顯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人們的行為。這些發現讓社會心理學家急於去尋找我們經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終得出的答案是:我們所表露的態度和做出的行為各自受許多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態度能夠預測我們的行為:(1)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響”最小化,(2)如果態度與預測的行為(比如對投票的研究)緊密相關,(3)如果態度是強有力的(以某一些事提醒我們牢記這點,或通過直接的經驗意識到這點)。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所想所感與我們的所為會緊密相關。
行為何時決定態度
如果社會心理學家在過去的25年中教給了我們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不僅我們的態度會影響行為,同時行為也會影響態度。有什麼證據支持這種觀點嗎?
現在我們轉向更令人吃驚的想法,即行為決定態度。有時我們確實堅持我們所相信的,但這同樣也是正確的,我們會逐步相信我們堅持的東西(圖4-1)。社會心理學理論中大多數的研究都為這個結論奠定了基礎。我們暫且不介紹這些理論,先讓我們看看將要解釋什麼內容。正如我們提供了很多行為影響態度的證據一樣,先讓我們來推測一下為什麼行為會影響態度,然後將你的看法與社會心理學家的解釋做一下比較。
請思考一下下面的事例:
薩拉被催眠了,催眠師要求她當一本書掉到地上時要她脫掉自己的鞋。15分鐘後一本書掉到了地上,薩拉安靜地脫掉了她的平底鞋。“薩拉,”催眠師問道,“你為什麼要脫鞋?”“嗯……我的腳很熱也很累,”薩拉回答道。“已經有一整天了。”可見,行為會影響觀點。
喬治大腦中控制頭部運動的區域暫時被植入了電極。當神經外科醫生約瑟·德爾加多(Delgado,1973)用遙控刺激電極,喬治總要轉頭。他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遙控的結果,而是給他轉頭做出了合理解釋:“我在找拖鞋。”“我聽到了一種聲音。”“我閒不住。”“我想看床下有什麼東西。”
當做外科手術將大腦兩半球分離後,卡羅爾嚴重的癲癇症狀有所緩解。現在,在一個實驗中,心理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在卡羅爾的左半視野中快速閃過一幅裸女的圖片。這幅圖片因而也就進入她的無言語功能的大腦右半球。這時,她靦腆地笑了,然後開始吃吃地笑。當問她為什麼笑時,她編造了——並且顯然相信——一個似是而非的解釋:“哦——那是個滑稽的機器。”當研究者將“微笑”這個詞從另一個腦裂患者弗蘭克的無言語功能的大腦右半球快速閃過時。弗蘭克勉強笑了。問他為什麼笑,他解釋說,“這個實驗很有趣。”
行為的這種心理後效確實在許多社會心理學實驗中出現過。下面的例子證實了自我說服的效力——態度緊跟隨行為。
角色扮演
角色 (role)這個詞來源於戲劇,正如在戲劇中一樣,它指的是那些處於特定社會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現出的行為。當我們扮演一種新的社會角色時,起初我們可能覺得很虛假,但很快我們就會適應。
想像一下你正在扮演一些新的角色——也許是你第一天上班,或上學,或在一個女大學生聯誼會或兄弟會上。比如在你剛進入大學校園後的第一週,你也許會對新的社會環境非常敏感,同時你會勇敢地嘗試著適應,並避免做出高中時的行為反應。此時此刻你也許感到了強烈的自我意識。我們會注意自己新的言語和行為方式,因為這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但某天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我們已經習慣於對女大學生聯誼會的狂熱,而我們虛偽地賣弄自己也變得十分自然了。這個角色就像我們的舊牛仔褲和T恤一樣已經與我們十分匹配了。
在一項研究中,斯坦福大學心理系教授菲利普·津巴多(Zimbardo,1971;Haney & Zimbardo,1998)設計了一個模擬的監獄實驗,要求大學生志願者在其中呆一段時間。津巴多想知道到底是邪惡的犯人和惡毒的獄卒導致了監獄的殘酷性,還是獄卒和犯人在制度上的角色令即便富有同情心的人也會變得十分怨毒和冷酷。是人們使這個地方變得暴力了,還是這個地方使人們變得暴力了?
津巴多用拋硬幣的方式,指派一些學生做獄卒。他給他們分發制服、警棍和哨子,並且命令他們按規則行事。另一半的學生則扮作犯人,他們穿著令人羞恥的衣服,並被關進單人牢房裡。在經過了一天愉快的角色扮演之後,獄卒和犯人,甚至研究者,都進入了情境。獄卒開始貶損犯人,並且一些人開始製造殘酷的汙辱性規則。犯人崩潰、造反,或者變得冷漠。津巴多(1972)報告說,“人們越來越分不清現實和幻覺、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這個創造出來的監獄……正在同化我們,使我們成為它的傀儡。”隨後津巴多發現社會病理學症狀正在出現,他不得不在第六天放棄了這個本來計劃為期兩週的實驗。
行為對態度的影響在戲劇中也會出現。當演員開始進入各自的角色並且體驗到真情實感的時候,他們就可能開始減少自我意識行為。在《烈火戰車》中扮演鎮靜而虔誠的奧林匹克英雄埃裡克·利德爾的伊恩·查爾森說,“當我進入角色的時候我的整個人格都改變了。”並不是我們沒有能力抵抗角色的影響。在一個稍做修改的模擬監獄實驗中,由於知道BBC電視臺在錄製,所以獄卒並沒有變得殘酷(Reicher & Haslam,2002;Muldoon,2003)。對於角色扮演的進一步研究關注的是虛幻(一個假想的角色)如何微妙地轉化為現實。在一個新的職業生涯中,比如教師、軍人或商人,我們扮演的角色會塑造我們的態度。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扮演的是奴隸角色——不是僅僅6天而是10年。如果津巴多“監獄”中人的行為在短短几天內就被改變,那想像一下幾十年的逆來順受會產生怎樣的腐蝕效應吧。扮演主子的人也許會被影響得更多,因為主人的角色是選定的。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曾經是一個奴隸,他回憶了自己的女主人在融入角色後發生的變化:
當我第一次在門口遇到新女主人的時候,她的外表和她的內心是那麼地一致——一個有著最仁慈的心和最美好情感的女人……我完全驚異於她的美德。在她的面前,我幾乎不知所措。她完全不像我所遇到的其他白人婦女……最卑微的奴隸也能夠在她面前完全放鬆下來,心裡只有因看到她而產生的美好感覺。她的面龐充盈著天使的微笑,她的聲音宛如靜謐的樂曲。
但是,唉!這顆善良的心並沒有維繫多久。她已經掌握了不負責任的力量,這種致命的毒性開始迅速展示它地獄般的威力。在奴隸制的影響下,那雙令人愉悅的眼睛已經由於暴怒而變得血紅;那充滿了甜蜜的聲音變成了刺耳可怕的噪音;而那天使般的面容也變為一張惡魔的臉龐(Douglass,1845,pp.57~58)。
語言何時變成信念
人們經常用語言來取悅自己的聽眾。他們傳播好消息比壞消息要快得多,並且會根據聽眾的立場來調整要說話的內容(Manis & others,1974;Tesser & others,1972;Tetlock,1983)。當誘導人們對其所懷疑的事做出口頭或書面證據時,他們常常為自己的欺騙行為感到不安。不過,他們會開始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假如 他們不是受賄或被逼才這樣做的。當一個人的話語沒有令人信服的外在解釋時,語言就會變成為信念(Klaas,1978)。
托裡·希金斯與其同事(Higgins & Rholes,1978;Higgins & McCann,1984)證實了語言是如何變為信念的。他讓一些大學生閱讀有關某人的人格描述,然後讓他對另一個人總結該描述,這個聽眾或者喜歡此人或者不喜歡此人。當聽眾喜歡此人時,這些學生會總結一個更積極的評價。說過好話以後,他們自己也會更喜歡這個人。讓他們回憶自己讀過的內容,他們會記起比實際更多的積極描述。簡而言之,我們似乎會傾向於根據自己的聽眾來調整我們的講話內容,並且在說過以後也會相信這歪曲的信息。
登門檻現象
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吧,許多時候在答應幫助某一個團體或一個組織以後,我們最後的麻煩會比最初設想得還要多,我們會發誓將來再也不答應這樣的請求。這是怎麼發生的呢?實驗表明,如果想要別人幫你一個大忙,一個有效的策略就是:先請他們幫一個小忙。這一登門檻現象 (foot-in-the-door phenomenon)被證實十分有效。研究者假扮成安全駕駛的志願者,他們請求加利福尼亞人在院子前面安置巨大的、印刷比較粗糙的“安全駕駛”標誌。結果只有17%的加利福尼亞人答應了。然後研究者就請求其他的人先幫一個小忙:他們可以在窗口安置一個3英寸的“做一個安全駕駛者”的標誌嗎?幾乎所有人都欣然答應了。兩週後,76%的人同意在他們的院子前豎立大而醜陋的宣傳標誌(Freedman & Fraser,1966)。一個挨家挨戶跑來跑去的項目助理後來回憶到,不知道自己曾經拜訪過哪些住戶,“我完全糊塗了,有些人如此容易就被說服了,而有些人卻又如此地頑固不化”(Ornstein,1991)。
聚焦 語言變成信念
俄勒岡大學心理學家雷·海曼(Ray Hyman,1981)描述了一個看手相的人是如何來說服自己相信手相術有用的。
我十多歲的時候開始看手相,以貼補魔術表演和心靈感應的收入。開始時我並不相信手相術。但是我知道要順利“叫賣”我就必須首先相信。幾年以後,我成了一個手相術的虔誠信徒。一天晚上,斯坦利·傑克斯——一個我尊敬的專業心相大師——巧妙地建議我,如果故意將手掌上的掌紋與書上描述的相反,那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我照這樣接待了幾個客戶。令我驚奇和恐懼的是,我的解釋像以前一樣成功。從那時起我對這種說服我們(包括“看手相”者和客戶)的巨大力量產生了興趣。當事實並非如此的時候,這種力量會讓我們說服自己它的確就是這樣的。(p.86)
還有一些研究者通過利他行為證實了登門檻現象的存在。
帕特里夏·普利納與其合作者(Pliner & others,1974)發現,在直接接觸的情況下多倫多郊區46%的住戶會樂意向癌症群體捐款。而如果在一天前讓他們戴著一個翻領別針宣傳這項活動(他們都願意這麼做的話),那募捐者的數量可能會是前者的兩倍。
安東尼·格林沃爾德與其合作研究者(Greenwald & others,1987)在1984年總統選舉的前一天抽樣調查了一些有註冊記錄的投票者,向他們詢問這樣一個簡短的問題:“你認為你是否會投票?”所有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相比於其他沒有被問到的投票者,這些被問到的人去投票的可能性要高出41%。
安傑拉·利普茲(Lipsitz & others,1989)發現,在獻血結束後,用下面的話提醒獻血者:“我們希望以後還能再見到你,好嗎?[暫停等待迴應]”,獻血者再次露面的機率會從62%增長到81%。
在互聯網上的聊天室裡,保羅·馬基與其同事(Markey & others,2002)發出了求助的請求(“我的電子郵件出問題了。你能幫我發一封電子郵件嗎?)。如果先請對方幫一個小忙(“我剛剛開始學習電腦,你可以告訴我怎麼來看別人的文件嗎?”),那麼其獲助次數會由2%增加到16%。尼古拉斯·吉根和塞琳·雅各布(Gueguen & Jacob,2001)通過邀請法國的互聯網使用者簽署反地雷的請願書,從而使他們為兒童地雷受害者組織募捐的比率達到原來的3倍(從1.6%到4.9%)。
請注意,在這100多個表現出登門檻現象的實驗中,人們最初的順從行為——在請願書上簽字,戴一個翻領別針,陳述個人的意圖——都是自願的。我們不斷髮現,當人們承諾公眾行為並且 認為這些行為是自覺做出的時候,他們會更加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
社會心理學家羅伯特·恰爾迪尼(Robert Cialdini)把自己形容為“易受騙者”。“在我的記憶裡,我一直都是被小販、募捐者或這類那類的騙子利用的傻瓜。”為了更好地瞭解為什麼個體會對別人說“是”,他在各種銷售、募捐和廣告組織中進行了三年的訓練,並最終發現了人們是如何利用“影響”這個武器的。他也將這種武器引入到簡單實驗的測試中。在其中一個實驗中,恰爾迪尼與其合作者(1978)發現了另一種登門檻現象,即一種被一些轎車經銷商靈活應用的低價法策略 (low-ball technique)。在顧客因為價格便宜答應買下一輛新轎車並開始辦理買賣手續的時候,銷售人員在顧客認為已經包括的選項上討價還價,或與說“我們已經賠錢了”而不做這一買賣的老闆協商,以去除價格優勢。據說,相比於剛開始,更多的顧客會在高價下堅持購買。
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航空公司和旅店也運用上述策略,通過吸引大量的顧客預訂少量的座位或房間,希望顧客能夠同意某一個更高的價位。恰爾迪尼與其合作者發現這種辦法確實管用。當他們邀請選修普通心理學課程的學生在上午7點整來參加一個實驗時,僅僅有24%的學生露面。但是,如果讓這些學生在事先不知道時間的情況下答應參加實驗,然後再要求他們在上午7點整來,結果53%的學生會來。
市場調查人員和推銷員發現,即使顧客意識到了存在一種利潤動機,上述這種法則仍然有效(Cialdini,1988)。一個最初沒有損失的承諾——返還一張寫有更多信息的卡片和一件禮物,答應去聽一種投資的介紹——經常會讓我們做出更大的承諾。售貨員有時會嘗試將人們捆綁在購買協議上來發揮小承諾的威力。現在許多州已經以立法的形式,允許那些面對上門銷售人員的顧客有幾天的自由時間來考慮他們的交易並可以取消這種交易。為了消除這種法律效應,許多公司開發了一個銷售培訓項目,這被百科全書的銷售公司稱為“防止顧客撤銷協議的非常重要的心理輔助”(Cialdini,1988,p.78)。他們只是簡單地讓顧客,而非銷售人員來填寫合約。在讓顧客自己填寫完了以後,他們通常會堅持自己的承諾。
登門檻的現象的確很值得研究。某些人試圖會誘導我們——在經濟、政治或性方面——表現出順從。現實的教訓在於:在我們答應某一個小要求之前,考慮一下後果是什麼。
邪惡的行為和態度
行為決定態度的定律也會引發不道德的行為。邪惡有時會來自逐漸升級的承諾。一個不起眼的惡行會很容易產生一種更惡劣的行為。惡行侵蝕人的道德感。為了解釋La Rochefoucaould的《格言》(Maxims ,1665),我們不難找到一個僅僅一次屈從於誘惑的人,但想找到一個從來沒有屈從誘惑的人卻十分困難。
比如,殘酷的行為會侵蝕行為者的良心。傷害無辜——通過發表傷害性的言論或實施強烈的刺激——通常會導致攻擊者去貶損受害者,以此為其行為的正當性辯護(Berscheid & others,1968;Davis & Jones,1960;Glass,1964)。我們不僅傷害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同時也不喜歡那些我們傷害的人。在這類研究中,人們會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特別是當他們被哄騙、而非被迫做某事的時候。當我們自願地認可某種行為時,我們會為它承擔更多的責任。
這種現象通常出現在戰時。集中營的守衛剛開始工作時,他們有時會以較好的行為方式對待囚犯,但這不會長久。那些執行死刑的士兵也許起初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反感,但這種感覺也不會持久(Waller,2002)。通常他們會用不人道的綽號來侮辱敵人。
在和平年代態度也會依從行為。一個奴役別人的群體很可能認為這些受奴役者生來就具備受壓迫的的特質。行為和態度也會互相支持,有時會達到道德麻木的程度。人們越是傷害他人並同時調整自己的態度,其傷害行為越容易出現。於是,道德變異了。
邪惡的行為會塑造自我,但是還好,道德的行為也會塑造自我。據說當我們認為沒有旁人在場的時候,我們的所作所為會反映出自己的性格。研究者給兒童提供誘惑物並使其看起來無人旁觀,以此來測試他們的性格。請想像一下當兒童抗拒誘惑的時候會發生什麼。在一個戲劇化的實驗中,喬納森·弗裡德曼(Freedman,1965)向小學生介紹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電池機器人,並告訴他們當他離開屋子的時候不許他們玩。弗裡德曼嚴厲地威脅一半的孩子而對另一半孩子則是溫柔地告誡。這兩種方法都有效地阻止了孩子。
幾周後另一個研究者——與先前的事件沒有明顯的聯繫——讓每個孩子在相同的房間中玩相同的玩具。在18個早先被嚴厲威脅過的孩子中,有14個現在正與機器人自由地玩耍;但是早先被溫柔地告誡過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二仍然拒絕玩這些玩具。他們先前是有意識地選擇不 玩玩具,這個決定很明顯被內化了。這種新的態度影響了他們隨後的行為。所以,如果威懾強大到能引發某種需要的行為,或者溫柔到讓他們覺得有主動選擇權的話,他們會內化這種憑良心做的行為。道德行為,特別是主動選擇而非被迫做出時,會影響道德思維。
種族間的行為和種族態度
如果道德行為影響道德態度的話,那麼積極的種族間的交流能減少種族歧視嗎——真的會像安全帶的使用會促使更多人贊成使用安全帶那樣嗎?這是美國最高法院於1954年決定廢除種族隔離制學校時社會學家的一部分證詞。他們這樣辯駁:如果我們要等待人心改變——通過鼓吹和教導——我們可能還要為種族平等等上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如果我們將道德行為立法,那我們就能在目前的情況下間接地影響人們的態度。
這個想法與“你無法給道德立法”的假設相沖突。然而態度確實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而發生了改變。請思考一下在這個巨大的社會實驗中一些相關的發現:
按照最高法院的決定,美國白人對綜合學校的支持率增加了一倍多,現在幾乎人人都支持這項決定。(有關過去和現在種族態度的其他例子,詳見第9章。)
在1964年頒佈人權法案後的十年,認為自己的鄰居、朋友、同事或同學全是白人的美國白人的比率在每項上都下降了大概20%。種族間交流的行為正在增加。與此同時,美國白人中認為黑人應該有自由居住權的比率由65%提高到87%(ISR Newsletter,1975)。態度也正在改變。
通過減少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階層和不同區域的人們對種族態度的差異,更多統一的全國性的反歧視法得以執行。隨著美國人表現得越來越一致,他們的態度也越來越一致(Greeley & Sheatsley,1971;Taylor & others,1978)。
實驗證明對他人的積極行為會增強對那個人的好感。給研究者或其他人幫忙,或輔導一個學生,通常會增強對受助者的好感(Blanchard & Cook,1976)。所以你要牢記:如果你想要更愛他人,你就要表現出你真的愛他。
1793年,本傑明·富蘭克林證實了給他人提供幫助會加強對其好感的觀點。作為賓夕法尼亞組織大會的祕書,他受到了另一個重要立法者的反對。所以富蘭克林想著手把他拉攏過來:
我並不……打算通過向他表示任何卑屈的尊敬來博得其好感,而是在一段時間後採取另一種方式。當我聽說他們圖書館裡有一本非常稀奇古怪的書後,我給他寫了封信表達了我十分渴望讀到這本書的熱切心情並且懇求他將書借我幾天。他立即就寄給我了,而我在一週之內歸還了,並強烈地表達了我的謝意。當我們再次在議會廳碰面的時候,他主動和我打招呼(他以前從來沒這麼做過),並且非常彬彬有禮;隨後他甚至說在任何情況下他願意隨時準備幫助我。就這樣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他去世(Quoted by Rosenzweig,1972,p.769)。
社會運動
社會行為對種族態度的影響暗示了存在這樣一種危險的可能性,即為了政治社會化而將這種影響運用在公眾人群中。對於20世紀30年代的許多德國人來說,參加納粹集會、身穿制服、示威,特別是公眾致意“嗨!希特勒”使其行為和信念之間產生了深刻的矛盾。歷史學家理查德·格倫伯格(Grunberger,1971)報告說,對於那些懷疑希特勒的人,“那種‘德國禮節’是一個強有力的調節器。一旦決定吟誦它並作為一種外在一致性的標誌,許多經歷過這些的人……對於自己的言語和感覺之間的矛盾深感不適。由於禁止他們發表自己相信的言論,他們就嘗試通過有意識地強迫自己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來平衡心態”(p.27)。
這個準則不僅限於極權主義 政權。政治儀式——學生每天升國旗敬禮、唱國歌——就是用公眾的一致來建立個人的愛國信念。記得我曾在西雅圖離波音公司不遠的一個小學裡參加空襲演練,由於我們反覆地演練,就好像我們真的是俄羅斯攻擊的目標,我們中的許多人就開始害怕俄國人了。觀察者也注意到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是如何強化遊行者的承諾的,他們的行為表達了一個已經建立起的觀念並將這個觀念植根心中。80年代針對包含性別的語言的運動同樣也強化了這種態度,而90年代的廢品回收項目則引發了人類對環境的關注。
在繼續閱讀下面的內容之前,我讓你來當一回理論家。請先問一問你自己:為什麼在這些研究和現實生活的例子中態度都會依從行為?為什麼扮演一個角色或做一次演講也可能會影響我們對一些事的感覺和態度。
小結
態度—行為之間的關係也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不僅態度會影響行為,行為也可能影響態度。當我們做事時,我們往往會誇大事情的重要性,特別是當我們為該事負責時。許多研究可以證實這一點。社會角色規定的行為鑄造了角色扮演者的態度。對登門檻現象的研究說明,對一個小行為的承諾可以讓人們更願意做一件更大的事。行為也影響我們的道德態度:我們傾向於將自己的行為解釋為正確的。同樣地,我們的種族政治行為也可以塑造我們的社會意識:我們不僅僅堅持自己相信的,我們也相信自己所堅持的。
為什麼行為會影響態度
什麼理論能夠幫助解釋態度—依從—行為現象?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是如何闡明這一科學解釋的過程的?
我們已經看到許多研究證實了行為對態度的影響作用。這些現象中有沒有什麼線索可以說明行為影響態度的原因呢?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者提出三個可能性原因。自我展示理論 認為,出於某些重要的原因,我們會表現出一定的態度,以使我們看起來一致。認知不協調理論 則認為,為了減少自己的內心不適,我們說服自己某些行為是合理的。自我知覺理論 假定我們的行為可以揭示自我(當對我們的感覺或信念不確定的時候,我們會觀察自己的行為,就像其他人那樣)。下面讓我們逐個分析這些理論。
自我展示:印象管理
最初對行為影響態度的解釋是從一個簡單的觀點開始的,你也許可以從第2章中回憶起。我們當中有誰不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嗎?我們在衣服、食品、化妝品和整形手術上花費了大量的金錢——那都是因為我們在意其他人的看法。給別人一個好印象常常能給自己帶來社會和物質的報酬,能讓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能讓我們的社會身份更有保障(Leary,1994,2001)。
沒人願意讓自己看起來自相矛盾。為了避免這一點,我們表現出與自己行為一致的態度。為了看起來一致,我們也許會假裝表現出某種態度,雖然那意味著有些做作或虛偽,但為了給他人留下好印象那是值得的。這就是自我展示理論大概的意思。
我們希望自己看起來一致的願望能夠解釋我們表達出的態度趨向與行為保持一致的原因嗎?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這樣的——如果虛偽的方式不能給別人留下好印象的話,人們往往會表現出自己真實的態度(Paulhus,1982;Tedeschi & others,1987)。
但是,我們發現自我展示理論不能解釋所有的態度變化,因為當面對一些根本不知道自己過去行為的人時,人們甚至也會改變自己的態度。另外兩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有時會內化自我展示,就像真的態度改變了一樣。
自我辯解:認知不協調
另一個理論的解釋是,我們的態度改變是因為我們想要保持認知間的一致性。這就是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提出的著名的認知不協調理論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這個理論很簡單,但是它應用的範圍很廣。該理論假定當兩種想法或信念(“認知”)在心理上不一致時我們就會感到緊張(“失調”)——因此,當我們決定說或做一些事時,我們會帶有一定感情。費斯廷格的研究表明,為了減少這種不愉快的感覺體驗,我們經常會調整自己的想法。現在已經有2000多項研究是建立在此理論觀點和其驚人預測力的基礎上(Cooper,1999)。
不協調理論主要用來解釋行為和態度之間的矛盾關係。這二者我們都能意識到。因此,如果我們感覺到不協調,也許有些虛偽,我們就會產生改變自己的壓力。這就有助於解釋在英國的一項調查中,半數的吸菸者與不吸菸者的意見為什麼不一致,後者幾乎都相信吸菸“真的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危險”(Eiser & others,1979)。在美國也一樣,40%的吸菸者——和13%的不吸菸者——認為吸菸並沒有多大害處(Saad,2002)。
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負責國際政策態度項目的理事開始意識到,一些美國人試圖減少他們“認知不協調的體驗”(Kull,2003)。這場戰爭主要起因於推測薩達姆·侯賽因(他不像其他殘酷的獨裁者)可能擁有威脅美國和英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爭伊始,僅有38%的美國人認為即使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場戰爭也是正義的(Gallup,2003)。大約五分之四的美國人相信他們的軍隊會找到這些武器,並且支持這場剛剛發動的戰爭(Duffy,2003;Newport & others,2003)。
而在戰爭中伊拉克沒有動用這種武器,並且其武器的數量並不足以對他們構成威脅,因而戰爭的大多數支持者體驗到了不協調。尤其是當他們意識到戰爭對經濟和人力的破壞,當他們看到伊拉克戰後的混亂,歐洲和穆斯林國家洶湧的反美浪潮,以及狂熱的恐怖主義後(印度尼西亞、約旦和巴勒斯坦權力組織現在都表示相信奧薩瑪·本·拉登“在世界事務中做正確的事情”),他們的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為了減少這種不快的體驗,國際政策態度項目記錄到,一些美國人修正了政府對外開戰的主要原因的記憶。這些原因現在被解釋為從殘暴的和種族滅絕的統治下解放被壓迫的人民,併為中東的和平與民主打下基礎。戰後一個月,曾經少數的支持性觀點變為了多數觀點:58%的美國人在即使沒有找到宣稱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下仍然支持這場戰爭(Gallup,2003)。“他們是否找到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無關緊要,”共和黨民意調查員弗蘭克·倫茲解釋說,“因為戰爭的根本原因改變了。”
認知不協調理論提供了對自我說服的一個解釋,並做出了一些驚人的預言。看看你能否猜出來。
理由不足
想像你自己正在參加一個由費斯廷格和學生梅里爾·卡爾史密斯(Carlsmith,1959)設計的一個著名實驗。在一個小時中,給你分配一些無聊的任務,比如反覆地轉木頭把手。在你結束實驗後,研究者(卡爾史密斯)解釋說這個實驗關注期望如何影響績效。同時,研究者希望在外面等著的另一個被試會認為將要做的實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看上去心煩意亂的實驗者(費斯廷格花了很長時間對他進行訓練直到他表現得非常逼真)對你解釋說參與設計該實驗的助手往往無法完成這一步驟,他緊握著你的手懇求道:“你能代替他嗎?”。
研究背後的故事:費斯廷格與減少不協調
1934年印度地震之後,災區之外謠傳更大的災難即將到來。我想這些謠言也許是“焦慮合理化”——證實自己揮之不去的恐懼是一種合理的認知。從這點出發,我提出了減少失調的理論——讓你對世界的看法與你的所感所為保持一致。
因為這是一項科學研究並且還會付給你報酬,所以你答應告訴下一名被試(實際上這才是實驗者真正的助手)你所經歷的實驗過程是多麼地令人興奮。“真的?”那個假被試問道。“我一個朋友在一週之前做過這個實驗,她說很無聊。”“哦,不,”你回答道,“它真的很有趣。在轉動把手時你會得到很好的鍛鍊。我保證你會喜歡。”最後,其他一些研究會讓你完成一份關於你對轉動把手喜愛程度的問卷。
現在讓我們來預測一下:在什麼情況下你最可能相信自己的小小謊言並且說實驗真的很有趣?是當你像其他被試一樣因此獲得1美元時?還是當你像其他人一樣獲得慷慨的20美元時?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高報酬會產生好的效應。但是恰恰相反,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作出了非常規的預測:那些僅僅得到1美元(撒謊的理由不充分)的被試將更可能調整他們的態度以適應這種行為。在他們行為的理由不足 (insufficient justification)時,他們更可能會感到不舒服(不協調)並因此更要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那些獲得20美元的被試,能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找到充足的理由,所以應該體驗到較少的失調。正如圖4-3所示,結果恰恰符合這個有趣的預測。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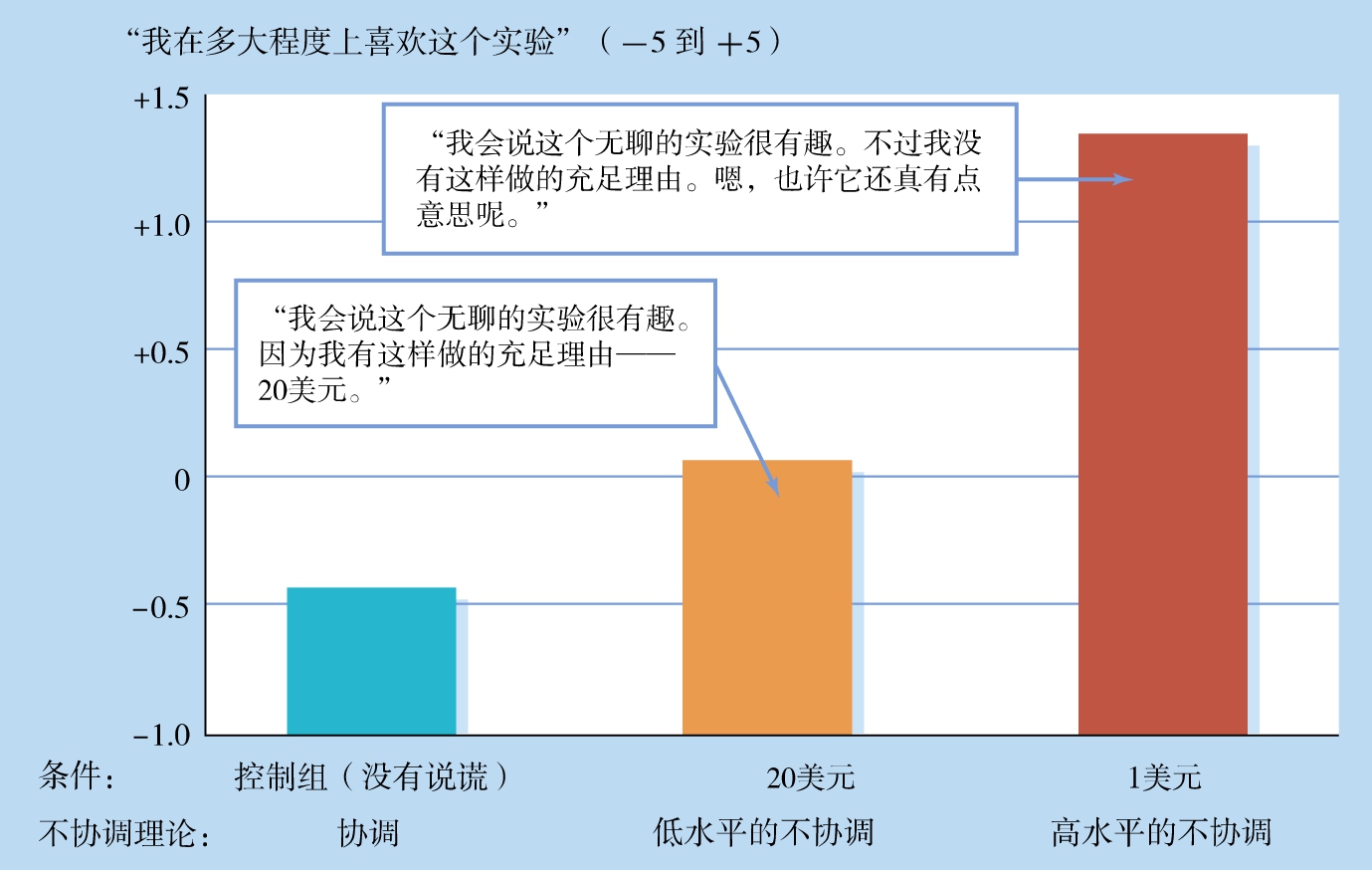
圖4-3 理由不足
不協調理論預測:如果我們的行為不能完全用外部報酬或強迫性因素來解釋,我們就會體驗到失調——我們可以通過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來減少不協調。
資料來源:Data from Festinger & Carlsmith,1959.
在許多後續實驗中,當人們擁有選擇權時,或當他們可以預見行為結果時,態度—依從—行為的效應是最強的。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讓人們讀貶損律師的笑話,並將其錄下來(例如,“你如何辨別律師在什麼時候說謊?他嘴脣動的時候”)。當被試是主動選擇參加該實驗而非被迫時,閱讀會讓他們對律師產生更多的消極情緒(Hobden & Olson,1994)。在其他實驗中,研究者讓人們寫文章,但只付給他們1.5美元。當文章涉及一些他們反對的內容時——比如提高學費——那些報酬過低的作者開始會對政策產生更多的同情心。倡導一項有利於另一個種族的政策也許不僅僅會改善你對政策的態度,也會改善你對那個種族的態度。特別是如果某些事讓你看起來很不協調,或如果你認為一些重要人物可能會讀到署你名字的文章的話,更是如此(Leippe & Eisenstadt,1994;Leippe & Elkin,1987)。當你覺得要對自己的話負責時,你會更加相信它們。託辭就變成了現實。
早期我們只是注意到理由不足的原則是如何在懲罰中發揮作用的。如果是溫和地告誡孩子,他們更可能內化不許玩誘人玩具的要求。因為這個溫和的告誡不能為他們聽話提供充足的理由,當一位家長說:“整理好你的房間,喬尼,否則我就狠狠地揍你,”喬尼不可能將打掃房間內化為合理的行為。因為嚴厲的威脅已經是個充足的理由了。
注意,認知不協調理論關注的並不是行為後的獎懲具有怎樣的相對效力,而是什麼因素會引發那種好的行為。理想化的目標是讓喬尼說:“我之所以打掃房間,是因為我想要一個整潔的房間,”而非“我之所以打掃房間,是因為如果我不做的話,我的父母會殺了我。”當學生們認為參加社團服務是自己的選擇而非被迫時,他們更可能參加以後的志願活動(Stukas & others,1999)。定理:如果我們覺得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話,我們的態度就會依從行為。
該理論認為,只有當權威在場時專制管理才是有效的——因為人們不大可能內化被迫的行為。布里——一匹在劉易斯的《馬和男孩》裡曾經被奴役的會說話的馬——觀察到,“做奴隸和被迫做某事的一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當沒有人再強迫你時,你會發現你已經失去了強迫自己的力量”(p.193)。不協調理論強調鼓勵和誘導應該足夠引發所期望的行動。從而這就暗示了管理者、老師和父母應用惟一足夠的刺激就可引發所期望的行為。
決策後的不協調
對這種選擇權和責任的強調意味著決策會產生失調。當我們面臨一個重要決策時——讀什麼大學、和誰約會、接受哪份工作——我們有時會掙扎於兩個同樣誘人的機會。也許你也有這樣的體會,當你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後,你開始痛苦地感到認知不協調——你所拒絕的那樣東西的好的方面,你所選擇的東西的不好的方面。如果你決定在校內居住,你也許就會意識到自己放棄了公寓的寬敞和自由而選擇了擁擠、吵鬧的宿舍角落。如果選擇住在校外,你也許就會意識到自己的決定意味著在生活上與校園和朋友隔絕,同時必須自己做飯。
當做出重要決策以後,我們經常會過高地評價自己的選擇而貶低放棄的選擇,以此來減少不協調。在最早發表的不協調實驗中(1956),傑克·佈雷姆(Jack Brehm)讓明尼蘇達大學的女生評價8種物品,例如烤麵包機、收音機和吹風機。然後佈雷姆讓她們看自己評價非常接近的兩件物品,並告訴她們可以拿走兩個中的任何一個。最後,當她們重新評價這8件物品時,她們提高了對自己所選物品的評價並降低了對放棄物品的評價。看來當我們做出決定以後,籬笆另一邊的草並不會長得更綠。
對於簡單的決定,這種決定—變成—信念效應會滋長自負(Blanton & others,2001)。“我決定的一定是對的。”這種效應出現得非常快。羅伯特·諾克斯和詹姆斯·英克斯特(Knox & Inkster,1968)發現剛投下錢的賭馬者對自己的猜測比那些打算下注者更加樂觀。從站在線上到離開下注的窗口這一段時間內,什麼都沒改變——除了下注和人們對它的感覺。也許有時在兩個選項之間會有一點輕微的差異,就像我記憶中決定人員的聘任一樣。一個勉強被聘上的人員和一個差點就能被聘上的人員的能力看起來應該相差不多——直到你做出決定並對外宣佈的那一刻。
一旦做出決定,它就會長出支撐自我的雙腿。通常,這些新腿非常強壯,即使當失去一條腿時——也許是最初的那條——決定也不會崩潰。艾莉森決定如果機票價格低於400美元的話她就坐飛機回家。而這是有可能的,於是她預定了機票並且開始考慮回家後的高興事兒。然而當她去買票的時候,她得知票價已經漲到475美元了。但無論如何,她現在已經決定走了。就像當汽車銷售商利用了低價法策略後,羅伯特·恰爾迪尼(1984,p.103)說:“在未做出決定以前,人們可能從未想過那些附加的原因。”
自我知覺
儘管不協調理論引發了許多研究,但似乎有一個更簡單的理論可以解釋這種現象。想一想我們如何推斷他人的態度。我們可以觀察在特殊情境下人們如何行動,然後將其行為歸因於個體的特性和態度或者歸因於環境的壓力。如果我們看到父母強迫小蘇茜說:“對不起”,我們會將蘇茜的道歉歸因於情境,而非她個人的歉意。如果我們看到蘇茜在沒有明顯誘導的情況下道歉,我們就會將道歉歸因於蘇茜自己(圖4-4)。

圖4-4 態度依從行為
自我知覺理論 (self-perception theory)由達里爾·貝姆(Daryl Bem,1972)提出,它假設當我們觀察自己的行為時我們會做出類似的推斷。當我們的態度搖擺不定或模糊不清時,我們就會處在局外人的位置上,從外部觀察自己。當人們能自由行為時,我們就可以近距離觀察他們的行為以洞悉他們的態度。類似地,我們也這樣洞悉自己的態度。傾聽自己的言語,則可以瞭解自己的態度;觀察自己的行為,則可以提示自我信念有多麼堅定,尤其是當我們無法將自己的行為簡單地解釋為外部約束的時候。我們自由地做出行動正是自我揭露的過程。
一個世紀以前,威廉·詹姆斯為情緒提供了一個類似的解釋。他指出,我們通過觀察自己的身體和行為推斷自己的情緒。一個女人在森林中受到刺激,例如遇到一隻凶惡的野熊。她感到緊張,心跳加快,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然後她逃走了。意識到這些以後,她體驗到了恐懼。我將要在一所大學發表演講,天亮前我就醒了並且再也睡不著了。意識到自己的失眠,我看出自己很焦慮。
如果人們發現自己答應了別人的一個小請求,他們是否認為自己熱心助人呢?是這個因素導致了人們在登門檻實驗中後來會答應別人更大的請求嗎?答案是肯定的(Burger & Caldwell,2003)。行為可以修正自我概念。
表情和態度
就像我最初那樣,你也許懷疑自我知覺的效應。但是面部表情效應的實驗卻提供了一種情緒體驗的方式。詹姆斯·萊爾德(Laird,1974,1984)要求大學生在電極接觸他們面孔的時候皺眉——“收縮肌肉”,“緊皺眉頭”——他們報告說自己體驗到了憤怒。萊爾德的其他發現更加有趣:那些被誘發出微笑表情的人體驗到更多的快樂並且覺得卡通片更加幽默(Schnall & Laird,2003)。在鏡中觀察自己的表情會放大這種自我知覺的效應(Kleinke & others,1998)。
我們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正感覺煩躁不安,但這時電話響了或有人來敲門,這令我們不得不以禮相待。“過得怎樣?”“還好,謝謝。你怎麼樣?”“哦,還不錯……”如果我們的感覺不是那麼強烈的話,這些溫和的行為也許會改變我們整個態度。要做到心裡不高興,但臉上還保持微笑確實很費力。當環球小姐嶄露笑顏時,她也許正在讓自己感到快樂。正如羅傑斯等人(Rodgers & Hammerstein)提醒我們的一樣,害怕時“吹一首愉悅的曲子”也許會有所幫助。我們的行為能觸發一定的情緒。
甚至步態也能影響你的感覺。當你開始閱讀這一章內容的時候,如果慢吞吞地踱上一分鐘,同時眼睛一直向下看。這會是體驗沮喪的絕佳方法。威廉·詹姆斯(1890,p.463)注意到,如果你“以一種頹廢的姿勢坐一整天,唉聲嘆氣,並且對所有事情都回應以一種陰沉的聲音,你的憂鬱會一直持續”。那怎樣做才能感覺好些呢?先大步流星走上一分鐘,同時甩動胳膊並直視前方。
如果表情會影響我們的感覺,那麼模仿他人的表情能幫助我們瞭解他人的感受嗎?凱瑟琳·沃恩和約翰·蘭澤塔(Vaughan & Lanzetta,1981)的實驗證實了上述結論。他們讓達特茅斯學院的學生觀察他人遭受電擊。他們要求一些觀察者在電擊到來的時候做出痛苦的表情。正如弗洛伊德和其他人假設的那樣,如果發洩情緒能釋放自我的話,那麼痛苦的表情應該可以使內心平靜下來(Cacioppo & others,1991)。實際上,相比於其他沒有表現出痛苦表情的學生而言,當看到電擊者時,這些扮苦相的學生出汗更多並且心率更快。表達出情緒顯然更能讓人們與他人感同身受。這似乎是,如果要體驗別人的感受,那麼就模仿他們的表情吧。
實際上,你根本不用去嘗試。觀察他人的面孔、姿勢和聲音,我們就會自然而然、無意識地模仿他們每時每刻的反應(Hatfield & others,1992)。我們儘量讓自己在行動、姿勢和嗓音上與他們保持一致。這樣我們就會體驗到他們的感受。這也同樣會產生“情緒傳染”。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我們在歡樂的人群中也感覺快樂,而在沮喪的人群中會感覺沮喪(第14章)。[巴勃羅·布里諾和理查德·佩蒂 (Brinol & Petty,2003)現在認為自我知覺不僅可能會在這裡起作用。當聽到一條有說服力的消息時,點頭似乎會證實人們的想法(贊成或不贊成)。 ]
面部表情也會影響我們的態度。在一個設計巧妙的實驗中,加里·韋爾斯和理查德·佩蒂(Wells & Petty,1980)要求艾伯塔大學的學生在收聽廣播社論時上下或者左右擺頭以“測試耳機裝置”。誰最有可能同意那篇社論?研究發現是那些曾經上下點頭的人。為什麼?韋爾斯和佩蒂猜測積極的想法與上下點頭一致,而與左右擺頭相反。當聽他人說話的時候你可以自己試試:當你點頭而非搖頭的時候你是否覺得自己更贊同他的觀點呢?
在一個更為滑稽的實驗中,約翰·卡喬波與其同事(Cacioppo & others,1993)讓實驗者評價漢字。當分別將他們的手臂向上彎(如同舉起物體)或向下彎(如同將某物或某人推開)時,你猜哪種彎曲條件能帶來最積極的評價?實驗發現是向上的彎曲。嘗試一下:當你掌心朝上抬桌子而非向下壓時,你是否體驗到一種更積極的感覺呢?這種動作—影響—情緒的現象能使人們在聚會上拿著食物或飲料時體驗到更好的感覺嗎?在接下來的實驗中,羅蘭·紐曼和弗裡茨·斯特拉克(Neumann & Strack,2000)對符茲堡大學的學生進行實驗研究,以考察他們辨別詞的褒貶義的速度。每個學生通過按左右鍵(用一隻手的兩個手指)來判斷。與此同時,另一隻手或者向上推(臨近的肌肉)或者向下壓。你能猜出結果嗎?實驗發現,如果學生的另一隻手朝正方向活動臨近的肌肉,他們就能更快地對褒義詞進行分類。
過度合理化和內部動機
回想理由不足效應——即最小的刺激能夠最有效地促使人們對一個活動產生興趣並樂於繼續做下去。認知不協調理論對此做出了一種解釋:如果外部刺激不足以證明我們行為的合理性,我們會通過內部心理活動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以減少不協調。
自我知覺理論則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人們通過關注周圍情境來解釋自己的行為。想像一下如果某人收下20美金後,他會開始宣傳學費上漲的合理之處。毫無疑問,與毫無報酬相比,他的這種宣揚似乎顯得不那麼真誠。也許當我們自我觀察時也會做出類似的推斷。
自我知覺理論還會得出更進一步的結論。與報酬總會增強動機的觀點相反,該理論認為不必要的報酬有時會帶來一些隱性的代價。給人們報酬讓他們做自己喜歡的事會讓他們將其行為歸因於報酬,這樣就會削弱他們的自我知覺——因為興趣而去做。愛德華·德西和理查德·瑞安(Deci & Ryan,1991,1997)在Rochester大學、馬克·萊珀和戴維·格林(Lepper & Greene,1979)在斯坦福大學、安·博吉亞諾與其同事(Boggiano & others,1985,1987)在科羅拉多大學的一系列實驗均證實了過度合理化效應 (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給錢讓人們玩智力遊戲,他們以後繼續玩遊戲的行為就會少於那些沒有報酬玩遊戲的人。答應給孩子報酬來讓他們做自己心裡喜歡的事情(例如,玩魔術牌),孩子們就會將這種遊戲變為工作(圖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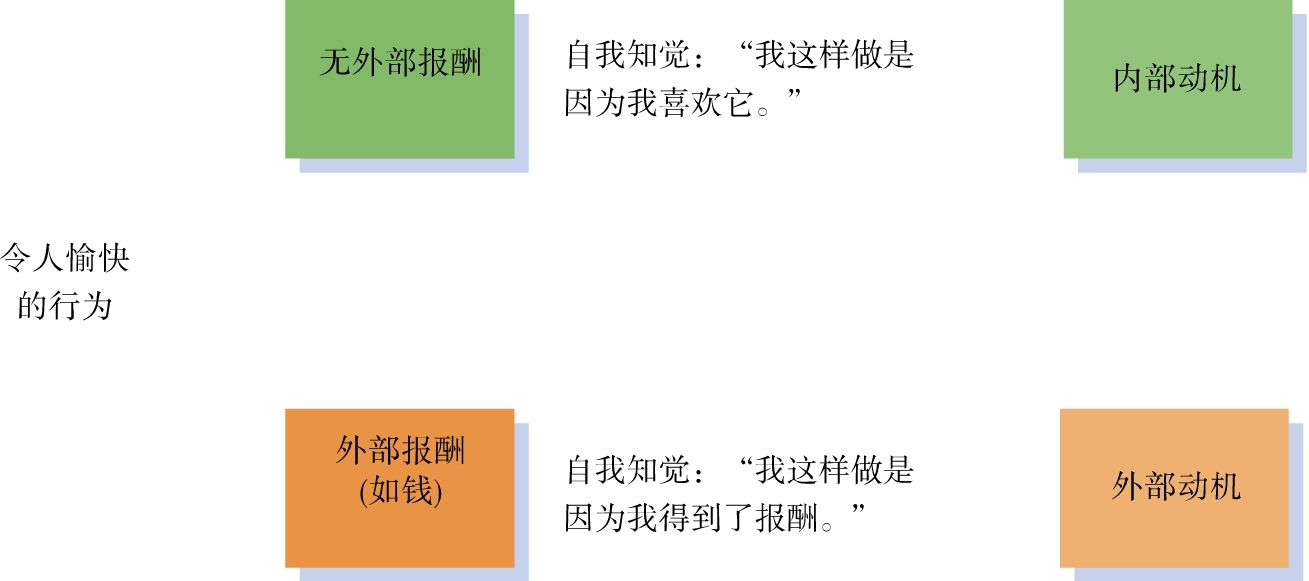
圖4-5 內部動機與外部動機
當人們在沒有報酬或強迫的情況下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他們會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對這種活動的興趣。而外部報酬引導人們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激勵性因素,從而破壞了內部動機。
一個民間故事也證實了過度合理化效應。一位老人獨自一人住在某一條街上,每天下午都有一群吵鬧的男孩在這兒玩耍。這種喧囂惹煩了他,於是他把這些男孩叫到了家門前。他告訴男孩們他喜歡聽他們那令人愉悅的聲音,並且許諾如果他們明天再來的話他將給每人50美分。第二天下午,這群孩子又跑來了並且玩得比以往更加放肆。這位老人又給了他們錢並許諾下次來還有報酬。第三天,他們又來了,大肆慶祝,而這個老人又給了他們錢,這次是25美分。第四天孩子們僅得到了15美分,老人解釋說他那乾癟的錢包已經快被掏光了。“求求你們,儘管這樣,你們明天還能以10美分的價格來玩嗎?”這些孩子失望地告訴他他們不會再來了。他們說,這樣得不償失,因為在他房子前玩整整一個下午才只有10美分。
正如自我知覺理論所暗示的,沒有預期的報酬並不會破壞內在的興趣,因為人們仍然可以將他們的行為歸因於自己的動機(Bradley & Mannell,1984;Tang & Hall,1994)。(就像與樵夫墜入情網的女主人公發現他實際上是一個王子。)如果因工作出色而獲得的讚揚能讓我們覺得自己更有能力和更成功的話,這確實能增加我們的動力。如果我們能恰當地給予報酬,這也許同樣可以提高創造力(Eisenberger & others,1999,2001)。
當個體很明顯是為了控制別人而事先付出不相稱的報酬時,就會發生過度合理化效應。關鍵是報酬意味著什麼:如果報酬和讚賞是針對人們的成就(那會讓他們覺得:“我很善於如此”),則它們會增加個體的內部動機。而如果報酬是為了控制人們,而且人們自己也相信是報酬導致了他們的努力,那麼這會降低個體對工作的內在興趣(Rosenfeld & others,1980;Sansone,1986)。
我們如何才能使人們對沒有吸引力的任務感興趣呢?楊·瑪莉亞也許覺得自己的首次鋼琴課很令人沮喪。湯米也許不喜歡五年級的課程。桑德拉也許不希望進行首次銷售會談。在這些情況下,父母、老師或管理者也許應該利用一些刺激來引發出好的行為(Boggiano & Ruble,1985;Workman & Williams,1980)。在他們順從以後,你可以給他們暗示一個這樣做的內在原因:“我並不奇怪銷售會進行得如此順利,因為你非常善於與人交際。”
如果我們為學生們學習提供充分的理由,並且給予他們報酬和讚賞,讓他們覺得自己很有能力,我們也許就能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繼續學習的慾望。當存在其他多餘的理由時——比如在教室裡老師一邊強迫學生學習一邊又以鼓勵來控制他們——學生自我驅動的行為就會減少(Deci & Ryan,1985,1991)。我的小兒子急於在一週裡讀完六到八本從圖書館借的書——直到我們的圖書館成立了一個讀書俱樂部,並承諾任何人只要在3個月裡讀了10本書就可以參加一次聚會。三週以後,他開始每週只借一兩本書。為什麼?“因為你僅僅需要讀10本書。”
理論比較
自我展示理論解釋了為什麼只是從表面上看起來行為會影響態度。而另外兩種理論則解釋了行為確實影響態度的原因:(1)不協調理論假定我們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並以此來減少我們內部的不適;(2)自我知覺理論則假定我們觀察自己的行為並對自己的態度做出合理的推斷,就如同我們觀察他人一樣。
最後兩種解釋看起來似乎互相矛盾。到底哪一種是正確的?這似乎很難做出權威的結論。在多數情況下它們可以做出同樣的預測,並且我們可以調整每個理論以適應我們大多數的研究發現(Greenwald,1975)。達里爾·貝姆(Daryl Bem,1972)甚至將自我知覺理論濃縮為一個忠誠和美學的問題。這驗證了科學理論中的主觀性(見第1章)。不協調理論和自我知覺理論都不是自然產生的,它們都是人類想像的產物——創造性地去嘗試簡化和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
可以用不止一種理論來預測某種科學規則,比如“態度依從行為”,這並不稀奇。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Feynman,1967)認為“自然最令人驚奇的特徵之一”就是“存在多種完美的方式”。在這裡,它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物理學的正確法則可以用如此之多的方式來表達。”(pp.53-55)。就像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樣,不同的假定也可以得出同樣的定律。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它加強了我們對該定理的信心。其可信性不僅因為有數據支持,還因為它有多個理論基礎。
不協調的激活
我們能說哪個理論更好一些嗎?在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已經出現了對不協調理論的強有力的支持。不協調被定義成一種對令人不適的緊張的激活狀態。為了減少這種緊張感,我們會相應改變自己的態度。自我知覺理論認為,當我們的行為和態度不一致時並不會產生緊張。它只不過是假定當我們的態度不堅定時,我們會用自己的行為和環境來解釋那種態度(就像有人說:“如果我聽不到自己說什麼,我怎麼能知道自己感覺到了什麼?”)。
那些可能引發不協調(例如,做出與自己態度相反的決定或行為)的條件真的都會激活個體的不適感嗎?很顯然答案是肯定的。倘若行為引發了不必要的後果,而個體會認為自己需要對其負責(Cooper,1999)。如果,你一個人在密室裡說你不相信某些東西,那不協調將會是最小的。如果有不良後果那麼不協調就會嚴重得多——如果某些人聽到了並且相信了你,如果無法避免消極的後果,或者如果傷害了你喜歡的人。此外,如果你覺得你應為這些後果負責——如果因為你自己同意這樣而且你事先就已經預見到事情的嚴重後果,那你就很難為自己的行為找到合適的藉口——這種不適的不協調就會被激活。而且,這可以通過排汗量的增加和心率加快表現出來(Cacioppo & Petty,1986;Croyle & Cooper,1983;Losch & Cacioppo,1990)。所以,如果你覺得你要對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件負責的話,你就會體驗到不協調的激活。
為什麼“自願”去說或做令人不快的事會激活不協調呢?克勞德·斯蒂利(Claude Steele,1988)的自我肯定理論 (self-affirmation theory)解釋說,因為這種行為很令人尷尬。它使我們覺得自己很愚蠢。它破壞了我們的自我能力和善良感。因此證明自己的行為和決定其實是一種自我肯定 ;它保護並維持了我們的誠信和自我價值。
那麼,如果我們幫助那些在行為上自相矛盾的人重建他們的自我價值,例如做好事,你認為會出現什麼結果?在一系列實驗中,斯蒂利發現,隨著他們自我概念的恢復,人們(特別是那些具有很強自我概念的實驗者)感到沒有什麼必要再去證明自己的行為(Steele & others,1993)。那些自尊感很強的人也較少地去自我辯解。
所以,不協調條件確實會激發緊張感,特別是當它威脅到對自我價值的積極體驗時。但是態度—依從—行為效應一定會激發這種情緒嗎?斯蒂利與其同事(1981)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當喝酒減少了不協調引發的情緒時,這種態度—依從—行為的效應就消失了。在其中一個實驗中,他們讓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撰寫贊成學費大幅上漲的文章。這些學生通過緩解自己反對學費的態度以減少失調的產生——除非 在寫了令人不悅的論文之後去喝酒,這大概也可以作為啤酒或伏特加酒品嚐實驗的一部分。
大約在費斯廷格首先提出其理論的50年後,社會心理學家們繼續研究和探討不協調產生的原因。有些人認為費斯廷格的觀點是正確的,即僅僅當行為與態度表現得不一致時就足以引發態度的改變(Harmon-jones & others,1996,2000;Johnson & others,1995;McGregor & others,1998)。實際上,在對健忘症患者的研究中——被試不能清晰地回憶起自己的行為——態度依然隨著行為發生變化(Lieberman & others,2001)。(這個令人吃驚的結果表明:不僅僅是有意的自我辯解在起作用,似乎其中也同時存在無意識的加工過程。)
其他一些人則認為最主要的不協調產生於個體的行為和自我概念之間(Prislin & Pool,1996;Stone & others,1999)。日本人很少肯定對自己的感覺,所以在不協調實驗中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常見的合理行為(Heine & Lehman,1997)。儘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形成定論,但毫無疑問,就像理查德·佩蒂等研究者(Petty,Wegener,& Fabrigar,1997)說的那樣:“其他任何理論都不能像不協調理論那樣攫住社會心理學家的想像力,而且它還會繼續激發有趣的新研究。”
當沒有自我矛盾時的自我知覺
不協調過程會激活不適感,同時當行為與態度之間出現矛盾時,它還可以進行自我說服。但是不協調理論並不能解釋所有的發現。當人們表明的立場與他們的態度相符時,儘管可能還有一些差距,但不適感的消除並不能排除態度的改變(Fazio & others,1977,1979)。不協調理論同樣無法解釋過度合理化效應,因為在有報酬的情況下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不應喚起高度的緊張感。並且對於那些行為與態度並不矛盾的情境——例如,要求人們微笑或做鬼臉時——似乎也不應該出現不協調。對於這些情況,自我知覺理論似乎有更好的解釋。
簡言之,不協調理論可以成功地解釋行為與明確的態度衝突時出現的結果:由於感到緊張,所以我們調整態度來緩解緊張。那麼,不協調理論就解釋了態度的改變 。在我們的態度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情形下,自我知覺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態度的形成 。當我們做出行為反應時,我們會產生更可接受的態度來指導自己未來的行為(Fazio,1987;Roese & Olson,1994)。
小結
三種不同的理論可以解釋行為對態度的影響。自我展示理論假定人們適當調整自己的態度以使其看起來與行為一致,尤其是那些為了給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控制自己行為的人。我們可以找到證據證實人們確實會因他人的想法而調整自己的態度,但與此同時也發現有時真的會引發真實態度的改變。
另外兩種理論認為我們的行為會促使真實態度做出改變。不協調理論的解釋是,當我們的行為與態度相反或者很難做決定時,我們會感到緊張。為了降低這種情緒的激活,我們會通過一系列的心理活動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不協調理論進一步認為,我們不當行為的外在理由越少,我們越覺得自己對其負有責任,從而會產生越多的不協調,態度也改變得越多。
自我知覺理論則假定,當我們的態度不很堅定時,我們就通過觀察自己的行為及其環境來推斷我們的態度。自我知覺理論的一個有趣的推論是“過度合理化效應”:付給人們報酬讓他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能將他們的這種樂事轉化為苦差(如果這些報酬使他們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報酬)。研究都證實了這兩種理論的預期,這表明它們分別描述了特定條件下產生的結果。
個人後記:通過行為改變我們自己
“要想養成某種習慣,那就去付諸行動。
要不想養成某種習慣,那就避而遠之。
要想改變一個習慣,那就做點別的事來取代它。”
——希臘斯多噶派哲學家,埃皮克提圖
這一章闡述的態度—依從—行為法則為我們的生活上了有意義的一課:如果我們想在某個重要的方面改變自己,最好不要等待頓悟或靈感。有時真的需要我們做出行動——開始去寫那篇論文,去打那個電話,去見那個人——儘管我們非常不情願那麼做。雅克·巴曾(Barzun,1975)十分認可行為的這種巨大力量,他因此建議那些具有一定雄心壯志的作家,即使冥思苦想令自己無法理清頭緒,那也還是要拿起筆來進行寫作。
如果你過於謙虛或者漠不關心潛在的讀者,但卻不得不寫作的話,那麼你就要假裝去寫。記住,你要讓周圍的人相信你,換句話說,選定一個主題並且開始構思……在開始做出這些小小的努力後——對言辭的一種挑戰——你就會發現自己的藉口消失了,並且開始真正地去關心這件事。你將會繼續做下去,就像所有慣於寫作的人那樣。(pp.173-174)
這種態度—依從—行為的現象既不是不合理的,也不是什麼魔法,它會促使我們去行動,可能也同時促使我們去思考。寫一篇評論或說出一種相反的觀點會迫使我們去思考可能被自己忽視的觀點。而且,當我們主動用自己的語言去解釋某些事時我們會記得最牢。就像一個學生寫信對我說:“直到我試著講出自己的見解我才真正理解它們。”因此,作為一名老師和作家,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要總是擺出最終的結果,而最好鼓勵學生自己思考理論的含義,並讓他們成為積極的聽眾和讀者。即使是做筆記也可以加深印象。哲學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1899)在一個世紀之前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沒有反應就沒有接受,沒有相關的表達就不會產生印象——這是教師應該牢記的最偉大的格言。”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能回憶起一次行動改變態度的經歷嗎?描述一下這次經歷。你現在能採取什麼行動來改變自己的態度嗎?你是否想改善對某個人或某門課程的感覺?如果是的話,假裝一開始就喜歡他們,那是否會對你有所幫助?
聯繫社會
作為探討態度和行為的一部分,這一章講述了菲利普·津巴多經典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當我們在第8章講解在擁擠環境中自我意識如何失去作用時,我們會再次提到津巴多。
[1] 以下是這個20世紀50年代的實驗很少被報告的一些內容。想像一下最後你面對研究者,他正在真誠地給你解釋整個研究,你不僅僅知道自己被騙了,而且研究者會要回20美元。你會順從嗎?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注意到,所有斯坦福的學生被試都願意還回錢。這的確很令人吃驚。這將出現在第6章對依從和從眾的討論中。我們將會看到,當社會情境令要求十分明確的話,人們通常會據此做出相應的反應。
第二編
社會影響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討論的大都是“個體內”的現象——我們如何思考對方。現在我們考慮一下“個體間”的事件——我們如何彼此影響、彼此聯繫。因此,在第5章到第8章中,我們將會探討社會心理學的核心問題:社會影響的威力。
這些影響我們而我們卻看不到的社會力量是什麼?它們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有關社會影響的研究幫助我們理解那些無形卻推動著我們的力量。這一部分將會向我們展示這些微妙的力量,尤其是態度與行為的文化根源(第5章)、社會服從的力量(第6章)、說服的原理(第7章)、群體參與的結果(第8章),以及所有這些影響是如何在日常情境中共同發揮作用的。
瞭解了這些影響後,也許我們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人們會那樣想、那樣做。而且,我們自己也許能夠更好地抵禦那些有害影響的操縱,並且更好地把握自己的行為。
第5章 基因、文化和性別
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樣性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基因、進化與行為
文化與行為
社會角色
如何解釋性別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獨立性與聯繫性
社會支配性
攻擊性
性特徵
進化與性別:什麼樣的行為是天生的
性別與擇偶偏好
性別與荷爾蒙
對進化心理學的反思
文化與性別:我們的行為是由文化影響的嗎
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不同時代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同伴相傳的文化影響
結論
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
環境與人的力量
個人後記:我們應該把自己看做社會的產物還是社會的建築師
“我們發現自己是文化、傳統和記憶的產物;相互尊重使我們可以向別的文化學習;同時我們也可以將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結合以獲得新的力量。”
——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獲諾貝爾和平獎時的演說,2001
從 遙遠星球趕來研究現代人 的外星科學家們感到異常興奮,他們終於有機會觀察兩個隨機抽取的地球人了。第一個被試簡,是一個在納什維爾長大,而後來到洛杉磯工作的律師。他離過一次婚,不過現在已經再婚了,而且生活得很幸福。朋友們認為他是一個自信、有能力而且很獨立的人。
第二個被試是Tomoko,她和丈夫、孩子住在日本的一個山村小鎮裡,離雙方父母的住處很近。Tomoko為自己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忠誠的妻子、負責的母親而感到很自豪。她的朋友認為她善良、溫柔、細心,值得尊敬。
根據這兩個由不同性別和文化組成的小樣本,外星科學家會對人類的特性做出什麼樣的結論呢?他們會懷疑這兩個人屬於同一個物種嗎?他們是否會為兩人不同面貌下的深層的相似性而感到震驚?
外星科學家遇到的問題也是當代地球科學家需要回答的問題:人類的差別存在於何處?我們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這已經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的關鍵問題,正如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Schlesinger,1991)所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爆炸性問題”。在一個由文化差異所組成的世界中,我們能否學會接納我們的多樣性,尊重我們的文化特性,並認識到我們人類彼此之間的聯繫?我相信我們能做到。讓我們來思考一下人類的進化和文化根源吧,以便考察它們各自對性別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影響。
人類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樣性會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人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方面,存在兩種佔統治地位的觀點:進化觀點,強調人類的聯繫;文化觀點,強調人類的多樣性。幾乎每個人都會同意,我們同時需要兩種觀點:我們的基因設計出一個具有適應性的人腦——一個可以接收文化“軟件”的硬件系統。
簡和Tomoko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非常相似。作為擁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中的成員,他們不僅具有相同的生理基礎,還具有相似的行為傾向。他們都可以感知這個世界,都會有飢渴感並能夠通過相同的機制獲得語言。簡和Tomoko都偏愛甜味而不是酸或者苦,都能感知到相同的顏色,都可以理解他人的表情。
簡和Tomoko——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類——都是社會動物。他們分別屬於某個團體組織,會服從並認可社會地位的差異。他們會知恩圖報、懲惡揚善,並且會為一個孩子的死亡而悲傷。當他們還是嬰幼兒時,8個月大小就表現出對陌生人的恐懼。而長大後他們會更加喜歡自己所屬團體的成員。他們會以謹慎或消極的態度對待那些擁有不同習慣和態度的個體。如果外星科學家來到地球人群中,他們會在各個地方都看到人類宴請賓客、跳舞,嬉笑或哭泣、唱歌、崇拜。世界各地的人類更喜歡集體生活如家庭和公共群體,而不喜歡獨處。人類學家布朗(Brown,1991,2000)確認了上百種這樣普遍的行為和語言模式。比如統計了所有以字母“V”開頭的單詞,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有動詞,暴力行為,探訪和元音。
這些共同點定義了我們人類的共同天性。我們人類之間確實具有深層的親緣關係。
基因、進化與行為
用來界定人類天性的普遍行為來源於我們的生理相似性。大部分人類學家認為,在大約10萬年前,人類起源於非洲。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離開非洲,尋找新的家園。為了適應新環境,早期人類開始出現了許多新的變異。根據人類學量表測量發現,這些變異相對而言是新近產生的,並且是相對膚淺的。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較深的膚色——“熱帶地區所需的遮陽罩”(Pinker,2002),那些搬遷到遠離赤道的北極人進化出更淺的膚色,以便在陽光較少直射的地區合成維生素D。因此,從歷史的角度講,我們都是非洲人。
實際上,我們只是最近才成為非洲人,那時,我們的祖先已減少到很小的數量,正如史蒂文·平克(Pinker,2000,p.143)記載的那樣,“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積累新的基因形式”。所以,如果在外星科學家看來,我們人類的基因型是極其相似的,很像一個部落的人。儘管人類數量比黑猩猩多得多,但黑猩猩之間的基因差異比人類卻大得多。
為了解釋種群特性,英國自然學家達爾文(1859)提出了進化論的觀點,他主張重視基因的作用。由於生物的多樣性,自然會選擇那些最適合某種環境下生存和繁衍的物種。那些有利於物種生存的基因會逐漸增多。比如,在北極嚴寒的條件下,北極熊的那些可以形成厚皮膚和白色長毛的基因在競爭中獲勝並佔有主導地位。這一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過程,最近也成為心理學界的一個重要原則。
進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不僅研究自然選擇如何影響那些適應特定環境的生理特徵——北極熊的皮毛、蝙蝠的聲波定位儀、人類的色彩視覺,而且還研究那些有利於基因存活和延續的心理特徵和社會行為。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人類就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因為在我們祖先眾多的後代中,自然選擇了那些偏愛食用蛋白質、糖、脂肪等營養食物的個體。因為那些沒有這類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來繁衍後代。作為流動的基因機器,我們繼承了祖先的適應性偏好。我們追求任何有利於祖先生存、繁衍並養育後代的事物,並以此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從生物學的角度講,生活的主要目標是留下後代。“心臟的目的就是要泵血”,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巴拉什(Barash,2003)說,“而大腦的目的,就是以最有利於我們成功進化的方式來引導我們的生物器官和行為。”
進化論的觀點強調我們人類共同的屬性。我們不僅具有相似的食物偏好,而且對一些社會問題具有同樣的答案,例如:“我該信任誰,害怕誰?我應該幫助誰?我應該在什麼時候和誰結婚?我應該服從誰?我應該控制誰?”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對這些問題所做出的情感和行為答覆與我們的祖先非常相似。
正是由於這些社會性的任務對世界各地的人類都是相似的,所以人們才會傾向於做出類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類都會按照權威和地位來對他人劃分等級,而且每個人都相信經濟的公平性(Fiske,1992)。進化心理學家強調這些比較一致的特性是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然而,文化則給我們提供了弄清這些社會生活基本元素的明確規則。
文化與行為
也許我們最重要的相似性(我們種群標誌的特性)就是我們有學習和適應的能力。進化使我們做好準備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在一個變幻莫測的世界中生存,可以適應從赤道附近的熱帶雨林到北極冰原的各種環境。與蜜蜂、鳥、狗相比,自然對我們的基因控制沒有那麼嚴格。然而,正是我們人類共有的生理基礎使得我們具有了文化上的多樣性。它可以令一種文化 (culture)裡的人們注重敏捷迅速、強調坦白或者接受婚前性行為,而另一個文化裡的人們則可以完全相反(圖5-1)。我們是否把苗條作為美的標準取決於我們何時生活在何處。我們將社會公正定義成平等(平均分配)還是公平(多勞多得),這取決於我們的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我們是傾向於表現自己還是相對保守,行為隨意還是比較正式,這和我們生活在非洲、歐洲還是亞洲文化環境下有很大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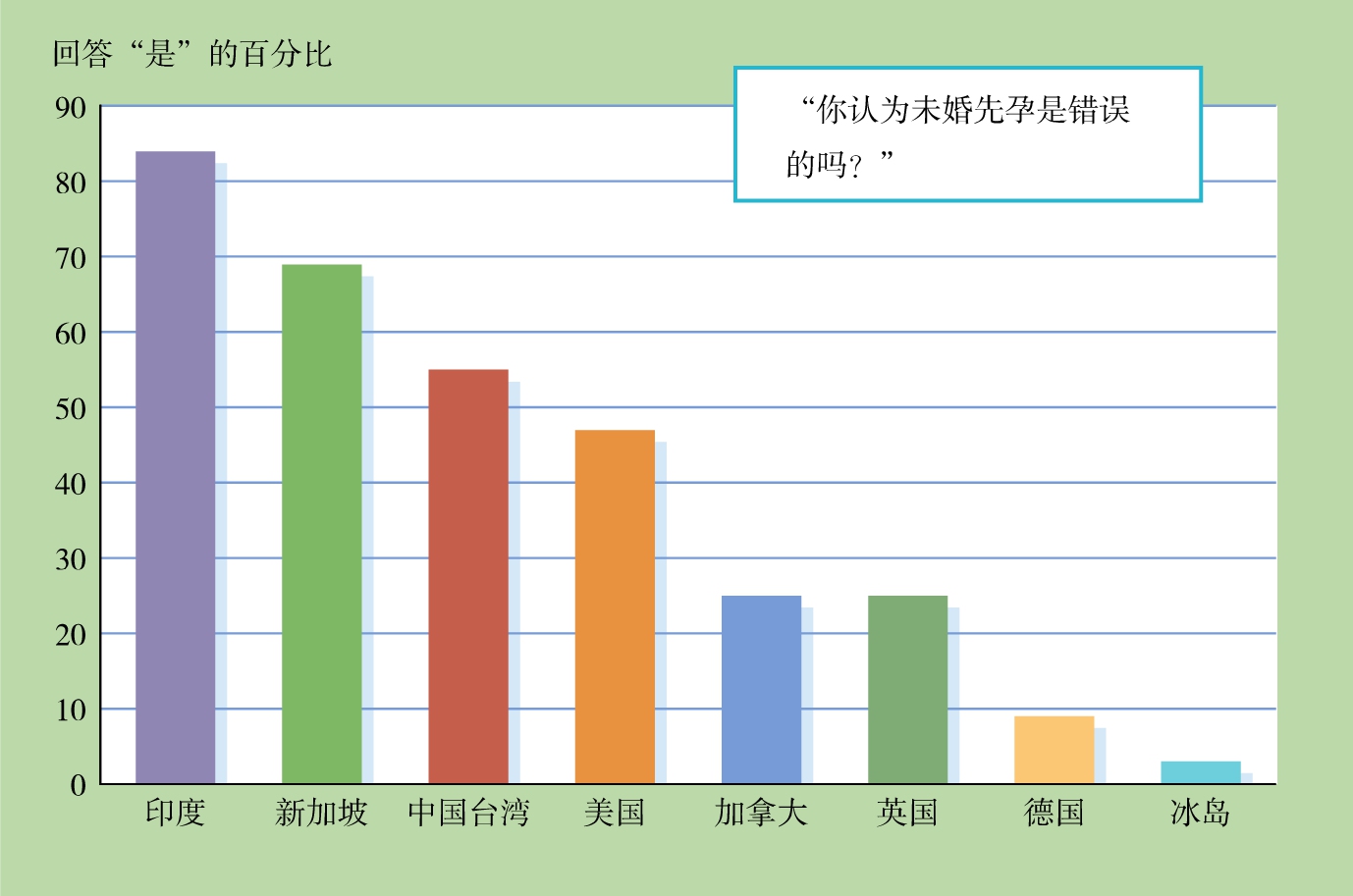
圖5-1 文化影響
1997年世界範圍的調查結果顯示了我們文化的巨大差異性。資料來源:Gallup & Lindsay,1999.
進化心理學家也承認環境的影響作用。自然選擇不僅賦予人類較大的頭腦和雙足,也賦予其適應性的社會能力。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需要具備學習語言並能與他人合作以獲取食物、照料小孩、保護自己的能力。自然使我們具有學習的特質,不論是出生在哪種文化環境下(Fiske & others,1998)。文化的觀點雖然也承認所有的行為都受到基因進化的影響,但是更強調人類的適應性。
文化的多樣性
人類語言、習慣、行為表現的多樣性表明,我們大多數行為都是受社會影響的。基因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其表現形式取決於環境(Lickliter & Honeycutt,2003)。因此,基因鏈比較長,如社會學家羅伯遜(Robertson,1987)提到:
美國人吃牡蠣但不吃蝸牛。法國人吃蝸牛卻不吃蝗蟲。祖魯人吃蝗蟲卻不吃魚。猶太人吃魚卻不吃豬肉。印度人吃豬肉卻不吃牛肉。俄國人吃牛肉卻不吃蛇肉。中國人吃蛇肉,但卻不吃人肉。新幾內亞的加爾人卻覺得人肉很美味。(p.67)
如果我們人人都像世界上個別地區那些相同的種群那樣生活的話,那文化多樣性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就沒有那麼大。日本有1.27億人口,其中1.26億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內部的文化差異性遠遠小於洛杉磯地區,因為後者學校裡的語言竟然多達82種(Iyer,1993)。
文化多樣性會逐漸地將我們包圍起來。我們越來越像居住在一個地球村中,通過電子郵件、巨型飛機、國際貿易等方式與同伴聯繫。“美國”牛仔褲其實是一個德國移民斯特勞斯(Levi Strauss)將熱那亞水手的褲型和法國一個小鎮的粗紋棉布相結合的產物(Legrain,2003)。一位不知名的學者指出,戴安娜王妃之死似乎突顯了全球化進程。“英國的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一個法國隧道里發生了車禍。他們的德國汽車有著荷蘭的發動機,由一名喝多了蘇格蘭威士忌的比利時人駕駛著。後面緊跟著騎著日本摩托車的意大利狗仔隊。最後是一名美國醫生用來自巴西的藥對他們進行了救治。”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存在這種文化多樣性,英國、加拿大、美國和澳大利亞都具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大眾化的語言,大眾傳播媒體,法定的假期,以及民主政治體制。但他們仍然有各自不同的地區文化,比如不同移民背景的人群,不同的氣候,飲食口味和價值觀。比如在美國,新英格蘭人對獨立與自治的價值觀念(“自由地生存與死亡”是新罕布什爾州的箴言),與南方人對熱情、合作、榮譽的價值觀就有很大不同(Plant & others,2002)。
移民或難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明顯地發揮文化融合的作用。19世紀英國作家基普林(Rudyard Kipling)曾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這二者永不相連。”但是在今天,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幾乎完全聯繫起來了。意大利有很多阿拉伯人,德國有很多土耳其人,英國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其結果是友誼與仇恨同在。對於北美人和澳大利亞人來說也是一樣的,國家越來越多地融合了各種文化。每六個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當我們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娛樂、生活的時候,我們會更容易理解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自己以及如何對待這種重要的文化差異。在一個由矛盾衝突組成的世界中,真正的和平需要求同存異。
要了解自己文化的影響,我們只需要接觸另外一種文化。美國男性看到中東領導人親吻美國總統的面頰可能會感到不快。一個習慣了向教授致敬的德國學生看到在我的學院中,大多數辦公室的門都敞開著,學生們可以自由地駐足停留這種情景會感到很奇怪。一個第一次來到麥當勞的伊朗學生會很自然地在她的紙帶中四處摸索吃飯的用具,直到她發現周圍的人都是直接用手代勞為止。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你和我的好習慣可能會嚴重違背禮節。訪問日本的外國人會發現學習日本的社會規則實在很麻煩——什麼時候脫鞋,如何倒茶,什麼時候送禮物,怎麼對待地位較高或較低的人。
規範:期待的行為
正如禮節規範所反映的那樣,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對於適當行為的解釋。我們經常把這些社會期待或者社會規範 (norm)看做是一種強迫人們盲目遵從傳統的消極力量。社會規範確實可以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們,以至於我們幾乎沒有察覺。就像在海底生活的魚類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浸泡在各自的文化環境之中,以至於我們必須從中跳出來以理解文化的影響。荷蘭心理學家威廉·庫曼和安頓·迪克(Koomen & Dijker,1997)說:“當我們觀察其他荷蘭人按照被外國人常常稱之為的荷蘭方式行事時,我們自己常常很難意識到這些行為具有典型的荷蘭特徵。”
瞭解我們文化中社會規範的最好方法就是進入到另一種文化環境中,觀察他們是那樣 行事,而我們是這樣 行事。在蘇格蘭生活時,我告訴孩子們,歐洲人確實用左手拿叉子吃飯,但“我們美國人卻認為先用左手切開肉,然後將叉子換到右手是禮貌的。我承認這缺乏效率,但這就是我們 吃飯的方式。”
對於那些無法接受這種社會規範的人來說,如此的社會規範似乎過於武斷而具有約束力。對於西方世界的大多數人來說,穆斯林婦女的面紗看起來似乎有點讓人受束縛,但對於穆斯林人來說恰恰相反。但是正如一場戲劇需要演員們知道自己的臺詞才能順利演出一樣,社會行為同樣需要人們明白對自己的期待是什麼。社會規範可以使整個社會機器順利運轉。如果身處一個不熟悉的環境中,由於不瞭解其社會規範,因而我們會觀察他人的行為,並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來到一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中,開始很可能會感到緊張和不自然(參見第2章),反之亦然。而在熟悉的環境下,我們說話、行動都會比較自然隨意。
不同文化在表達以及私人空間等方面也會存在差異。一個比較正式嚴肅的北歐人來到熱情奔放的地中海地區,很可能覺得這裡的人“熱情、有魅力,但缺乏效率,浪費時間”;地中海人則覺得北歐人“有效率,冷淡,過於看重時間”(Triandis,1981)。拉丁美洲的商人很可能會在一次晚餐遲到之後,為他們的北美朋友如此準時而費解。
私人空間 (personal space)是一種我們想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間維持潤滑或緩衝的區域。隨著情境的變化,空間大小會有所改變。和陌生人在一起時,我們會保持一個相對較大的私人空間,大約4英尺以上。在過於擁擠的公車上,在休息室或圖書館,我們會保護自己的空間並尊重他人的空間。我們允許讓朋友靠近些,大多在2~3英尺。
個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有些人的私人空間相對較大(Smith,1981;Sommer,1969;Stockdale,1978)。不同群體之間也存在差異:成人之間比兒童之間的距離大,男人彼此間的距離要比女人之間的距離大。不知道什麼原因,靠近赤道的文化圈偏愛更小的距離和更多的接觸或擁抱。於是英國和斯堪迪納維亞半島的人相對於法國人和阿拉伯人就會保持更大的私人空間。北美比拉美的私人空間大。
為了觀察侵入他人私人空間的影響效果,你可以扮演一個空間侵略者。你可以站在距離朋友一英尺的地方與他聊天,觀察他是不是會感到不安,眼睛看向別的地方,後退或者表現出其他不舒服的姿態?這些都是研究者考察的空間侵入指標(Altman & Vinsel,1978)。
文化相似性
正是由於人類的適應性,才出現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差異。然而在文化差異的表面之下,跨文化心理學家發現了“內在的統一性”(Lonner,1980)。作為同一種族的成員,差異表面下的行為機制仍舊是相同的。人類甚至制定了跨文化的規範來指導戰爭。在殺敵的過程中,會有一些公認的規則。你必須穿上確認身份的制服,使用一種妥協的姿勢投降,並且人道地對待戰犯(如果在他們投降之前不殺他們,你還應該給他們提供食物)。伊拉克的部隊打出投降旗號後轉而又進攻,並把士兵偽裝成平民百姓以建立伏兵,他們就違反了這些規範。美國的一個軍事發言人譴責道:“這些行為是對戰爭規範的最嚴重的褻瀆”(Clarke,2003)。
儘管社會規範隨著文化而有所不同,但人類社會往往會有一些共同的規範。最明顯的是對亂倫的限制:父母不可以和孩子發生性關係,兄弟姐妹之間也不可以。儘管實際上亂倫的發生比心理學家原先估計的要多,但這一社會規範的確是相同的,所有的社會都不贊成亂倫。考慮到對於生育的生物學懲罰,進化心理學家很容易理解為何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反對亂倫。
各地的人們也有一些關於友誼的相同規範。在英國、意大利、香港和日本進行的研究中,阿蓋爾和亨德森(Argyle & Henderson,1985)提出了在定義朋友角色的社會規範方面的幾種文化差異。(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不能當眾批評朋友令其難堪)。但也有一些統一的規範:尊重朋友的隱私,交談時要進行眼神的接觸,不洩漏彼此的祕密。這些都是友誼的基本規則,一旦破壞這些規則,友誼也就結束了。
在全世界,人們傾向於用穩定、外向、開放、友好、盡責來形容他人(John & Srivastava,1999;McCrae & Costa,1999)。有關的人格調查問卷可以很好地考察你在這樣的“大五”人格維度方面的位置,它可以很好的描述你的人格,而不論你在哪裡生活。同樣,香港的社會心理學家樑和彭邁克(Leung & Bond,2004)認為存在五個普遍的社會信念的維度。他們對38個國家的研究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認可和應用這些社會信念的程度不同:玩世不恭的程度、社會複雜度、應用的回報、精神性和對命運的控制(圖5-2)。人們堅持這些社會信念以指導自己的生活。那些崇尚玩世不恭的生活信念的人表現出較低的生活滿意度,贊成果斷的影響策略和右派政治。那些贊成應用回報的人傾向於在學習、計劃和競爭中進行自我投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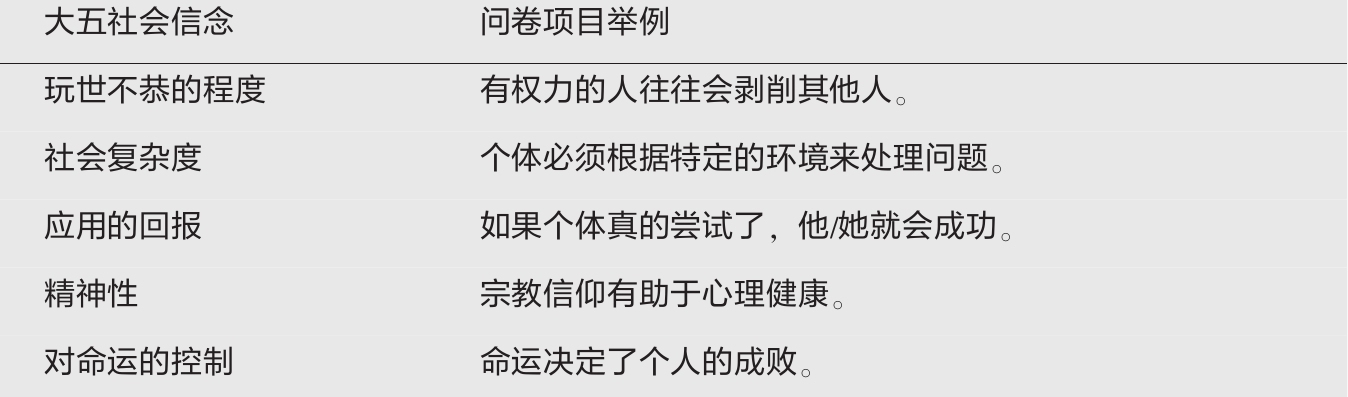
圖5-2 樑和彭的社會信念維度
羅傑·布朗(Brown,1965,1987;Kroger & Wood,1992)提出另一種一致性的規範。無論在什麼地方,人與人之間不僅僅形成某種等級地位,而且人們在對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說話時通常會採用較為尊敬的語氣,就好像是和陌生人聊天一樣。而他們對地位較低的人說話則更像是和熟人聊天。病人會叫醫生“某某醫生”,而醫生往往會以病人的名字來回答。學生和老師之間也以這種熟悉的非對等的方式稱呼彼此。[在 《女太監 》(The Female Eunuch )一書中,傑曼·格里爾 (Germaine Greer)提到語言是如何將女性降低到食物及小動物層次的——蜂蜜、羊羔、糖、甜派、小貓、小雞 ]
很多語言有兩種第二人稱:尊敬的形式和隨意的形式(例如,德語中的Sie 和du ,法語中的vous 和tu ,西班牙語中的usted 和tu )。人們通常對熟人和下屬採用隨意的形式(不僅對親密朋友和家人,還包括對小孩和小狗說話)。當陌生人用“Sie”而不是用“du”稱呼一個德國小孩時,這個小孩會受到極大的鼓舞。
布朗的一致性規範的第一部分——強調溝通的形式不僅反映社會距離也反映社會地位 ——與第二部分緊密相關:親密關係的發展往往由處於較高地位的人控制 。在歐洲,大部分個體之間的交往都從禮貌的正式稱謂“您”開始,逐漸向親密的隨便稱謂“你”發展,很明顯有人會控制這種親密感的發展。你認為誰有這樣的權力呢?在多數情況下,年長者、富人或更傑出的人會提出:“為什麼我們不用du稱呼彼此呢?”
這一規範也可以超越語言,擴展到每一種形式的親密關係發展中。向別人借筆或者把手搭在別人肩膀上的行為,最好還是跟自己的熟人或者下屬做,而不要對陌生人或者自己的上司這樣做。同樣,大學校長會首先邀請老師們到他家裡去。總體上,地位更高的人是親密關係發展的設定者。
因此,有些規範是帶有文化特色的,而另一些規範是比較普遍的。文化的力量會使社會規範和人們所扮演的角色有所差異。各地的文化都會規定人們的角色並對其產生影響。第4章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扮演某種角色通常會使人們內化自己的行為。行動就變成了信念。所以讓我們來考察社會角色在文化內和文化間有何差異吧。
社會角色
世界是一個大舞臺,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舞臺上的演員;
他們都有上場的時候,也有下場的時候;
一個人一生中會扮演許多角色。
——威廉·莎士比亞
就像莎士比亞說的那樣,角色理論假定,社會生活就像一部舞臺劇,有場景、面具和臺詞。就像雅克在《因為你喜歡》中說的這幾句話一樣,社會角色比角色扮演者具有更長久的生命力。父母、學生、朋友的角色在我們不存在之後仍然會繼續。這些社會角色允許扮演者有一定的自由發揮空間,優秀的表演是由角色扮演的方式決定的。然而我們還必須 要限制角色的某些方面。學生最起碼要參加考試和交論文,並有最低成績的限制。
當只有很少的社會規範與一個社會分類(比如行人靠右行走,不要隨意橫穿馬路)有關的時候,我們不會將其看做一種社會角色。定義一種角色需要一系列的社會規範。我很容易就可以列出做一名教授或父親的一系列要求。儘管我可能會違反一些不太重要的規則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考慮到效率問題,我很少提前上課),但如果我違反了一些重要規則(比如沒來上課,體罰孩子),那麼我可能會被解僱或者不得不失去我的孩子們。
社會角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第4章中,我們提到我們傾向於接納自己的角色。在第一次約會或者第一天上班時,你的角色可能會扮演地不自然,但當你將角色內化以後,你就會感到很隨意自然了。以前覺得尷尬的事情現在會覺得很真實自然。
這是很多難民、移民、傳教士、和平組織成員、留學生以及執行官的經歷。當到一個新國家生活時,需要花很多時間學習如何在新的環境中交談並做出適當的行為。一旦適應了,再回到自己家鄉時可能又會感到不適應了(Sussman,2000)。以前美好的家鄉現在似乎沒有那麼美好了。在一些人們沒有意識到的方面,其行為、價值觀和認同都已經適應了另一個地方的角色。於是人們不得不重新來適應自己的文化。
被綁架的報業巨頭女繼承人帕特里夏·赫斯特的案例充分顯示出了角色扮演的力量。1974年,赫斯特被一些自稱是SLA的年輕革命者綁架了。她隨後選擇宣佈脫離自己原有的生活,放棄她富有的父母和未婚夫,並加入綁架她的組織。她要人們“試著理解她的變化”。12天后,一臺銀行攝像機拍攝下她參與SLA的搶劫活動。
19個月後,赫斯特被捕並經歷了長達兩年的禁閉和“重塑”,她重新接受了自己作為家族繼承人的角色。後來在一個偏遠的名為康涅狄格的小鎮,她成了一位母親和作家,她將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慈善事業中(Johnson,1988;Schiffman,1999)。如果赫斯特真的是一個虔誠的革命者或者只是假裝配合綁匪,人們似乎可以理解她的行為。但人們無法理解的是(這也成為20世紀70年代最轟動的新聞故事),這正如布里克曼寫道:“她可以成為一名家族繼承人,但曾經卻做過革命者,而後又重新成為了一名家族繼承人。”這很令人費解。當然,這是不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的,對吧?
可能,也不可能。正如在這一章的最後一節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行為不僅僅取決於社會情境,也受我們自己傾向性的影響。並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應對壓力。在赫斯特所處的困境中,你我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然而某些社會情境卻可以讓絕大多數“正常”人以“不正常”的方式行動。在一個實驗中,讓善良的人們處於一種困難的環境中,以觀察正邪之間的較量,令人沮喪的是,最終是邪惡獲勝了。善良的人最終沒能堅持到底。
高—低社會地位角色
在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莊園》一書中,家畜推翻了人類的統治,建立了一個“所有動物都平等”的王國。然而那些負責管理角色的豬很快就違反了規定,享受安逸,他們認為這與自己的身份相符。他們強調“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要更平等一些。”
勞倫斯·梅塞等人(Messe,Kerr,& Sattler,1992)提到地位對自我知覺的影響不僅僅限於奧韋爾筆下的豬。在很多日常或實驗室情境下,地位更高的人認為自己更應該受到優待或者應該有能力做出更好的表現。羅納德·漢弗萊(Humphrey,1985)設計了一個模擬的商業辦公室以證實這一現象。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其中一些人扮演經理,而另一些人則扮演僱員。和在真正的辦公室裡一樣,經理給僱員發佈命令,自己負責較高級的工作。結果,僱員和經理認為同等能力的經理(隨機任命的)更有智慧、自信和樂於助人——就好像真的是領導者一樣。
同樣,扮演一個屬下 的角色會產生降低自我感覺的效果。埃倫·蘭格和安·比尼圖(Langer & Benevento,1978)在讓紐約市的女性解答數學問題時發現了這一現象。在她們獨立完成後,讓她們一起工作,再指派其中一位女性為“老闆”,另外一位為“助手”。最後她們重新獨立解答,結果發現扮演老闆的人成績比最初一輪的成績好,而扮演助手的人成績比最初的差。在一些初中生中也發現了被任命的地位對成績表現的類似影響(Jemmott & Gonzalez,1989;Musser & Graziano,1991)。較低下的角色會削弱個體的自我效能感。
角色互換
角色扮演同樣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特意地去扮演某個新角色,人們會有意改變自己或者重視那些與自己角色不同的人。在蕭伯納的《窈窕淑女》一書中,杜利特爾是一個賣花女,當她扮演一個淑女的角色並得到他人認可的時候,她就真的成為了一位淑女。
角色通常按照某種關係成對出現——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老師和學生,醫生和病人,僱主和僱員,警察和市民。角色互換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對方。La Rochefoucauld發現,人類大部分的衝突和爭論都源於人們過於關注自己的意見而並非去尋找問題的正確答案。“即使是最有魅力和最聰明的人往往也意識不到,因為過於緊張而侷限在自己的觀點上”(1665,No.139)。談判者或者領導者可以通過角色互換來營造更好的交流氣氛。或者要求雙方從對方的利益出發重新考慮對方的觀點。下次當你和朋友、父母吵架時,嘗試一下中途停止,如果你們每個人都重新考慮他人的觀點和感受,而後再思考自己的觀點,就會增進雙方之間相互的理解。
到目前為止,本章證實了我們作為人類大家庭成員之間的生物親緣關係,承認文化的多樣性,並探討了社會規範和角色在文化內和文化間的差異。請記住,社會心理學最重要的任務不是對差異進行編目,而是去尋找行為的統一原則。我們的目標如同跨文化心理學家沃爾特·朗納(Lonner,1989)提出的:“一個統一的心理學是——在奧馬哈和大阪,以及在羅馬和博茨瓦納都有效而有意義的心理學。”
態度和行為總會因文化而產生差異,但態度影響行為的過程卻差異不大。尼日利亞和日本人對少年的角色定義與歐洲人和北美人不同,但在所有的文化背景下角色期待都影響社會關係。切斯頓(G. K. Chesterton)在一個世紀前就提出:“當人們發現邦德街的男人戴黑帽子時,他們同時也會理解為什麼廷巴克圖(Timbu Ctoo,非洲古地名)的男人戴紅色羽毛。”
小結
我們人類有哪些地方相似?又有哪些地方不同?為什麼?進化心理學家研究自然選擇如何使那些有利於基因延續的特性保留下來。儘管人類在學習和適應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但進化的觀點仍然強調人類天性中共有的親緣關係。
文化的觀點則強調人類的差異性——那些有助於界定一個群體,並代代相傳的行為、思想、傳統等。不同文化在態度和行為上的顯著差異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人類其實是社會文化規範和角色的產物。
然而,跨文化心理學家也試圖尋找人類“內在的統一性”。儘管不同的文化存在著差異,但是它們也有一些相同的社會規範。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規範是關於地位不平等的人們之間如何進行交流。
所有的文化都會賦予個體一定的角色。扮演一定的角色常常會使人們內化自己的行為。改變角色也能夠改變我們的觀點。
如何解釋性別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進化心理學家和跨文化的心理學家都試圖解釋性別差異。在考察他們的觀點之前,讓我們先來看一些基本的問題:男人和女人之間,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為什麼?
人類的差異表現在很多維度上——身高、體重、髮色等等。但是對於個體意識和社會關係而言,最重要的是兩個維度:種族和性別(Stangor & others,1992)。身高和髮色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自我意識和個體識別,影響我們對朋友或伴侶的選擇,影響他人如何評價與對待我們。但是種族和性別似乎更為重要。當你出生時,人們最先問的問題往往是“男孩還是女孩?”當一個同時帶有男性和女性特徵的雙性兒童誕生時,醫生和家庭都迫切地選擇為孩子確定一種性別,並通過手術去除性別的模糊性。簡單說來,每個人必須 擁有某一種性別。在白天與黑夜之間可以有黃昏黎明,但是從社會意義上講,男性與女性之間沒有任何其他選項。
在第9章,我們會探討種族和性別如何影響他人評價和對待我們的方式。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性別 (gender)——與男人、女人有關的特徵。哪些行為是 典型的男性行為?哪些行為是典型的女性行為?
哈里斯(Harris,1998)提到:“人類共有46條染色體,其中有45條與性別無關。”因此在很多身體特徵上,男性和女性沒有什麼差異,比如開始坐立、長牙和行走的年齡。同樣,男女在很多心理特徵上也極其相似,包括詞彙量、創造性、智力、自尊、幸福感等。女人和男人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喜歡小孩,都有相似的大腦結構(儘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經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經連接)。事實上,異性與你有很多相似之處。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解剖特徵以外,其本質完全相同?事實上,男女之間仍然存在著一些差異,正是這些差異而非相似性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並引發了許多相關研究。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差異總是會引發人們的興趣。與男性相比,女性的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而且女性平均比男性矮5英寸。女性對味覺和聲音更為敏感。女性更容易焦慮失調和沮喪。而與女性相比,男性進入青春期時間較晚(晚2年),但是死亡時間較早(早5年)。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3倍,服用利他林以治療多動症的男性高出女性4倍。男性酒精成癮者是女性的5倍。死於電擊的男性是女性的6倍。而且男性比女性會轉動自己的耳朵。
在20世紀70年代,很多學者擔心這樣考察性別差異會增加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性別差異是否可以解釋成女性的缺陷呢?社會學家傑西·伯納德(Bernard,1976,p.13)警告說,對性別差異的關注很可能為攻擊女性者提供武器。確實,對差異的解釋往往聚焦在被認為有所不同的那個類別。例如,探討選舉中的兩性差異時,與男性經常選擇保守派相比,學者們更奇怪的是為什麼女性常常支持民主黨。人們會問為什麼亞洲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勝過其他種族,而不會問為什麼其他的種族群體沒有如此優秀。在每種情況下,人們總會根據某一個群體制定標準,而驚奇於其他的群體為什麼會如此不同。人們常常奇怪為什麼會有同性戀而不去思考異性戀的原因(或者性取向的決定因素)。人們奇怪為什麼亞裔學生在數學等科學領域表現優異,而不去思考為什麼其他種族表現較差。在上述每個例子中,人們以某一群體為標準,同時奇怪為什麼其他群體是“如此不同”。“不同”與“不正常”或“低水平”之間只有一個短暫的跨越。[甚至在身體特徵方面,男性與女性各自的個體差異也遠遠超過了兩性之間的平均差異。斯科蘭德1964年創下的男子400米自由泳世界記錄——4分12秒,如果放到2000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也不過是女子比賽的第7名,比那年的冠軍貝內特慢了7秒 。]
從20世紀80年代起,學者們較多地考察性別的多樣性。最初,性別差異的研究支持兩性無差別的假設,希望能減少對不同性別的刻板印象。然而,根據伊格利(Eagly,1995)的研究報告,80~90年代,很多研究發現性別差異——這差異與心理學其他領域中的重要行為差異一樣大。這些發現支持了原有的對女性的印象——更少攻擊性,更多關心他人,更敏感——這些正是女權主義者與絕大多數人所欣賞的特性(Prentice & Carranza,2002;Swim,1994)。因而,對於許多人在評價他們的信念和感受時認為“女人”比“男人”更受歡迎 就不足為奇了(Eagly,1994;Haddock & Zanna,1994)。
接下來讓我們比較一下男人和女人在社會關係、支配性、攻擊性和性特徵等方面的異同。描述了這些區別後,我們可以思考進化和文化觀點是如何對此進行解釋的。性別差異是否反映了自然選擇的確定趨勢?這是由文化造成的嗎——即反映的是男人、女人通常扮演的角色與其所處的情境?還是說基因和文化共同造成了這種性別差異?
獨立性與聯繫性
從激烈的競爭到養育關愛都可以表現男性不同的見解和行為。對女性個體也是如此。但是南希·霍多羅夫等人(Chodorow,1978,1989;Miller,1986;Gilligan & others,1982,1990)提出,從總體上來說,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親密關係。
與男孩相比,女孩之間的談話更加親密,而且遊戲也更少攻擊性,埃莉諾·麥科比(Maccoby,2002)經過數十年對性別的研究作出了這樣的總結。而由於他們各自和同性別的人交往,所以男女之間的差異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對成年人而言,生活在個人主義文化中的女性經常用更富有關係性的詞彙來形容自己,樂於接受更多別人的幫助,體驗更多與關係有關的情感,並努力使她們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更加協調(Addis & Mahalik,2003;Gabriel & Gardner,1999;Tamres & others,2002;Watkins & others,1998,2003)。男性在談話時常常關注任務以及與大群體的關係,而女性則更多關注個人關係(Tannen,1990)。打電話時,女性和朋友的聊天時間更長(Smoreda & Licoppe,2000)。在電腦面前,女性花費更多的時間發送電子郵件以表情達意(Crabtree,2002;Thomson & Murachver,2001)。在群體中,女性之間會相互分享她們各自的生活,為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Dindia & Allen,1992;Eagly,1987)。當面臨壓力時,男性傾向於以搏鬥迴應,通常以反抗來應對威脅。謝利·泰勒(Shelley Taylor,2002)指出,幾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遭遇壓力的女人更多的是需要他人的照顧和幫助。她們向家人和朋友尋求幫助。在大學一年級學生中,10個男生中有5個認為“幫助有困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而女生每10個裡面就有7個人具有同樣的想法(Sax & others,2002)。
費利西亞·普拉圖及其同事(Pratto & others,1997)報告說,總體上,男性總是會被那些增強性別之間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訴律師,廣告策劃者等);女性則被那些減少性別之間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訴人,慈善工作的宣傳者)。對64萬人的工作偏好的研究發現,男性更傾向於看重報酬、提升機會、挑戰和權力,而女性則更看重合理的時間安排、私人關係、幫助他人的機會(Konrad & others,2000)。確實,北美大多數需要關注他人的職業,比如社工、教師、護士等,女性從業者都比男性要多。此外,女性似乎更加仁慈,在所有資產超過500萬美元的人中,48%的女性做了慈善捐款,而男性的比例只有35%。女子學院很少得到男校友的支持(女性研究的國家理事會,1994)。
作為母親、女兒、姐妹、祖母身份的女性可以很好地維繫家庭(Rossi & Rossi,1990)。女性會花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和老人(Eagly & Crowley,1986)。與男性相比,女性會花3倍的時間購買禮物和賀卡,用2~4倍的時間處理私人信件,給朋友和家庭打的長途電話要多10%~20%(Putnam,2000)。當要求被試提供可以描繪自己的照片時,女性提供的照片更多地包含了父母和其他人(Clancy & Dollinger,1993)。尤其對於女性來說,相互支持的感覺對於女性的婚姻滿意度是極為關鍵的(Acitelli & Antonucci,1994)。
當然,在不同的情境下,微笑也會有所不同。但在400多項研究中,女性較高的聯繫能力表現在更高頻次的微笑上(LaFrance & others,2003)。比如,瑪麗安娜·拉弗朗斯(LaFrance,1985)分析了9000張學校畢業冊中的照片,哈伯斯塔特和塞塔(Halberstadt & Saitta,1987)考察了1100張雜誌和報紙的照片,觀察了超市、公園、街道上的1300個人,均發現女性的微笑次數更多。
接受調查時,女性更傾向於將自己描述為能夠“共情” (empathy),能夠感受他人的感覺——為他人的喜悅而高興,為他人的悲傷而哭泣。儘管在實驗室條件下,共情的性別差異沒有那麼顯著,但的確存在。在觀看幻燈或者聽完故事以後,女孩會有更多共情的反應(Hunt,1990)。在實驗室的模擬情境或實際生活中令人沮喪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為他人遭受相似的經歷而表現出共情的反應(Batson & others,1996)。女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多地報告為他人的悲傷而難過(Eisenberg & Lennon,1983)。12%的美國男性和43%的美國女性報告說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哭泣(Gallup,2003)。而自閉症,一種缺乏共情能力的障礙,也多發於男性。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與男性的友誼相比,為什麼男性和女性都報告說和女性的友誼更加親密、愉悅並容易維持(Rubin,1985;Sapadin,1988)。當需要別人共情和理解時,男性和女性都傾向於向女性傾訴自己的快樂或者傷痛。
對男性和女性共情差異的一種解釋是女性具有更強的理解他人情緒的能力。朱迪思·霍爾(Judith Hall,1984)對125項考察男女對非言語線索敏感程度的研究分析發現,總體而言,女性更善於發覺他人的情緒線索。例如,呈現一個2秒鐘的無聲影片,內容是一個悲傷女性的面孔,女性被試在猜測她究竟是在批評某人還是在考慮離婚的問題上表現出更高的準確性。女性對非言語線索的敏感性有助於解釋她們在積極、消極情境下更強的情緒反應(Grossman & Wood,1993;Sprecher & Sedikides,1993;Stoppard & Gruchy,1993)。女性也能根據某些情境更準確地預測複雜而細微的情緒[比如與你一起工作的一個朋友,因為工作獲得了嘉獎,你心情如何?你的朋友心情如何?(Barrett & others,2000)]。
為了考察人們“共情的準確性”,威廉·伊克斯(Ickes,2003)及其同事們對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進行錄像(包括陌生人之間,朋友或夫妻之間,病人與醫生之間)。而後他們要求每個談話者觀看錄像,在任何一個產生想法或感受的時刻停止播放,並記錄自己的想法或感受。而後再次播放錄像,要求觀看者(有時候是談話的另一方)猜測在這些時候,另一個人在想什麼或感受如何。
結果發現,理解朋友的感受比理解陌生人的感受,其共情的準確性更高。但確實有些人具有更好的共情能力。有些人是較好的共情者。而女性共情的準確性,總體來說,比男性的準確性要高(Thomas & Fletcher,2003)。此外,也發現女性在記憶面部特徵和其他外表特徵方面更為準確(Horgan & others,2004)。
霍爾報告說,女性非言語地表達 情緒能力同樣非常出色。根據科茨和羅伯特·費爾德曼(Erick Coats & Robert Feldman,1996)的報告,這個特點在積極情緒下更為明顯。他們要求被試談論令自己感到快樂、悲傷和生氣的情境。而後給觀察者呈現5秒鐘有關這些陳述的無聲影片。結果發現在快樂情境中,觀察者對女性情緒的推測更加準確。相反,男人在傳達憤怒時似乎更加出色。[你是否認為:西方女性應該更自立,以適應西方社會的個體主義文化?還是說她們應該藉助女性注重關係的傾向來改變西方社會的權力導向(以較多的兒童被忽視、孤獨感和抑鬱為代表),使其成為充滿關懷的社會。 ]
不管是對女性還是對所有人類,像溫柔、敏感和溫情這類的特性都對親密關係的維繫有重要作用。在悉尼,約翰·安蒂爾(Antill,1983)對已婚伴侶的研究發現,如果丈夫或者妻子其中一方擁有上述這些傳統上屬於女性的特點的話——雙方 都有則更好——他們的婚姻滿意度會更高。如果配偶很有教養並且會給對方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他們會體驗到較高的婚姻滿意度。
社會支配性
想像一下有這樣兩個人:一個“喜歡冒險,獨裁,粗心,控制慾強,堅強,獨立,強壯”,而另一個“感情豐富,依賴性強,愛幻想,情緒化,服從,弱小”。如果你覺得前者更像男人,而後者更像女人,那麼按照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Williams & Best,1990a,p.15)所講,你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樣。從亞洲到歐洲到澳洲,人們對男人的評價離不開富有控制慾、積極進取和攻擊性。
這些觀點、期望與事實是相符合的。幾乎在所有社會中,都是 男性處於統治地位。而已知的社會中,沒有一個是女性統治男性的(Pratto,1996)。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不同的文化中性別差異會有所不同。如果女性更多處於管理者和領導者的位置,那麼這種性別差異就會縮小。但是我們還要看到:
2002年,在全世界所有的立法者中,女性只佔14%;在所有的首相和總統中,女性只佔5%(CIA,2002;IPU,2002)。而世界500強企業中的首席執行官中,女性僅僅佔1%(Eagly & others,2003)。
男性比女性更關心社會統治問題,更傾向於支持保守的政治候選人和維持男女不平等的措施(Eagly & others,2003;Sidanius & Pratto,1999)。
在陪審員團體中男性大約佔一半,但在被選舉的陪審團領袖中卻佔到90%,並且主要的實驗室小組負責人都是男性(Davis & Gilbert,1989;Kerr & others,1982)。
在工業化國家中,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77%。這樣大的工資差距中,僅有1/5可以被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和工作特性等因素加以解釋(世界銀行,2003)。
雖然男性佔據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首先發出約會邀請的大多是男性,最後負責駕車和買單的也多為男性(Laner & Ventrone,1998,2000)。
男性交流的方式可以加強他們的社會權力。在某些情境中,並沒有清晰地界定領導的角色,但男性傾向於採取指示性的領導方式,而女性則傾向於採取民主化的方式(Eagly & Johnson,1990)。在領導角色中,男性傾向於做那種指示性的、強調任務的領導,而女性則擅長變革型的領導方式,這種領導方式受到越來越多的組織歡迎,主要採用靈活的社會技巧建立團隊精神(Eagly & others,2003)。男性比女性更強調勝利、超前以及控制他人(Sidanius & others,1994)。他們也更愛冒險(Byrnes & others,1999)。如果領導方式是民主型的,那女性領導和男性領導同樣受歡迎。如果領導方式是獨裁型的,則男性領導更受歡迎(Eagly & others,1992)。人們通常更容易接納男性“強硬、獨裁”的領導而不是女性“壓迫性的、攻擊性的”領導。
在寫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聯繫性介詞(比如with)以及現在時態,更少使用數量性名詞。一個根據詞彙使用和句型結構來判斷性別的程序,正確地確認了920本英國小說及非文學作品中作者的性別,其準確率高達80%(Koppel & others,2002)。
男性談話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們對獨立的關注,而女性更重視關係。男性更可能表現出權力慾——自信地談話,直接打斷他人,相互握手,更多地注視對方,很少微笑(Anderson & Leaper,1998;Carli,1991;Ellyson & others,1991)。從女性角度考慮,她們更多采用間接方式影響他人——較少打斷他人,更敏感,更禮貌,較少驕傲。
那麼這是否可以斷言(就像20世紀90年代一本暢銷書的名字一樣)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呢 ?事實上,如同凱·杜克斯和瑪麗安娜·拉弗朗斯(Deaux & LaFrance,1998)提到的那樣,男女之間不同的交談方式可能與社會背景有關。我們賦予男性的大多數特徵往往是屬於那些處於更高社會地位的人的特性(不論男女)。而且,個體差異十分顯著。有些男性相當的猶豫和恭敬順從,而有些女性則相對自信而專斷。很顯然,認為男性和女性來自不同行星的說法過於簡單。
意識到男女兩性之間這種不同的交流方式,南希·亨利(Henley,1977)呼籲女性不要再假裝微笑、低眉順眼或者忍氣吞聲了,相反她們應該注視別人的眼睛,自信地講話。瓊·吐溫(Twenge,2001)從1931年以來一直研究女性的果斷性問題,她發現,在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的年代,她們確實 會變得更加果斷。然而,霍爾(1984)則重視女性那種平易的交流方式,他說:“不論什麼時候,如果假定女性的非言語行為是不好的,那麼就等於承認男性的行為是正常的,而女性的行為是不正常且需要解釋的”(p.152-153)。
攻擊性
心理學家把攻擊性 (aggression)定義為想要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在全世界,捕獵、打鬥、戰爭等主要是男性的行為活動。調查顯示,男性承認自己比女性有更多的攻擊行為。在實驗中,男性確實表現出更多的身體攻擊,比如實施具有傷害性的電擊等(Knight & others,1996)。在加拿大,犯有謀殺罪的被捕男女比例為8:1(加拿大統計,2001)。在美國,92%的罪犯是男性,犯謀殺罪的男女比例為10:1(美國聯邦調查局,2001)。但是,性別差異隨著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挑釁情境下,幾乎不存在男女性別差異(Bettencourt & Miller,1996)。而且在一些傷害性較小的攻擊形式中——比如說毆打家庭成員、摔東西,或者言語攻擊等——女性的攻擊行為並不比男性少(Björkqvist,1994;White & Kowalski,1994)。確實,約翰·阿徹(Archer,2000,2002)根據數十項研究的統計分析指出,女性似乎會發起更多的攻擊行為。但是男性更容易造成傷害;其中62%的受害者是女性。
性特徵
在有關性的態度和主張方面,男女之間也存在差異。儘管男女在面對性感刺激時的生理和主觀反應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Griffitt,1987),但是,請思考:
“我可以想像自己正愉悅地享受與不同伴侶的‘偶爾’性關係。”澳大利亞的一項調查顯示,48%的男性和12%的女性對此表示同意(Bailey & others,2000)。
美國教育委員會最近調查了25萬個大一新生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如果兩個人真的彼此喜歡,那就可以發生性關係,即使他們認識的時間很短暫。”其中53%的男生表示贊成,而女生只有30%表示贊成(Sax & others,2002)。
在一項調查中,隨機抽取3400個美國人,年齡在18到59歲之間,48%的女性和25%的男性認為情感是他們發生第一次關係的原因。在對性活動頻率問題的回答上,19%的女性和54%的男性回答“每天”或者“一天幾次”(Laumann & others,1994)。
男女在性態度上的差異也反映在行為層面上。跨文化心理學家馬修·西格爾及其同事(Segall & others,1990,p.244)報告說:“在全世界各個地方,幾乎無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發動性活動。”與女同性戀相比,男同性戀更多報告說對無婚姻關係的性愛感興趣,且對視覺刺激的反應更強烈,更關心伴侶的性魅力(Bailey & others,1994)。史蒂文·平克(Pinker,1997)觀察說,“並不是說男同性戀性愛次數更多,他們只是表現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不過對象也是男人罷了。”
確實,鮑邁斯特和凱塞琳·沃斯(Baumeister & Vohs,待發表;Baumeister & others,2001)觀察到,男性不僅進行更多的性幻想,態度也更開放,而且會試圖尋找更多的性伴侶,也更容易引發性喚醒,更多的要求性愛,更多手淫,不習慣獨立生活,很少拒絕性愛,更容易冒險並花費更多的資源以便獲得性愛,且更偏愛形式各異的性愛。一個考察了52個國家16288個人的調查要求人們回答在未來一個月中,他們需要幾個性伴侶。結果發現在未婚群體當中,29%的男人和6%的女人報告說需要一個以上的性伴侶(Schmitt,2003)。這些結果在同性戀個體中也是類似的(29%的男同性戀和6%的女同性戀需要兩個以上的性伴侶)。
人類學家唐納德·西蒙(Symons,1979,p.253)指出,“在世界各地,性都被理解成為女性所擁有的、男性想得到的東西。”難怪鮑邁斯特和沃斯說,各地的文化都更重視女性的性行為,正如在賣淫與求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性別不對稱。男人一般提供金錢、禮物、稱讚和承諾以暗示與女性進行性交易。他們注意到,在人類的性經濟中,女性很少進行性交易。就像工會反對“不罷工的工人”一樣,他們認為這種人會毀壞他們自身的勞動價值,大多數的女人反對其他的女人提供“廉價的性”,這會降低她們自身性行為的價值。在185個國家中,男人越稀少,懷孕的比率就越高 ——因為當男人稀缺時,“女人們會以低價提供性的方式相互競爭”(Barber,2000;Baumeister & Vohs,待發表)。當女人稀少時,女性性行為的市場價值就會提升,她們會要求更高的價格。
性幻想也表現出兩性差異(Ellis & Symons,1990)。在以男性為觀眾的言情劇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滿慾望。以女性為主要市場的浪漫小說中,一個溫柔的男性總是會全身心地愛自己的心上人。看來並不是只有社會學家才注意到了男女兩性的這種差異。幽默評論家戴夫·巴里(Barry,1995)觀察說“女人們可以為一部長達4個小時的電影而著迷,儘管整個情節就是一男一女嚮往發展出一段戀情,甚至有時候最終都沒有什麼結果。而男人極其憎恨這樣的事情。男人的嚮往一般只能持續45秒,而後就希望大家都開始脫衣服。然後再來一場汽車追逐的戲。一部命名為‘車戰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會很符合男人們的需求。”
小結
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然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卻更為引人注目。儘管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個體差異遠遠超過了性別差異,但是社會心理學家仍然考察了在獨立性與關聯性之間的性別差異。女性通常更關心他人,表達更多的共情和情緒反應,用更多關係性的詞彙描述自己。男女兩性似乎表現出不同的社會支配性,攻擊性和性特徵。
正如偵探對犯罪比對美德更感興趣一樣,心理學家對差異的興趣遠遠超過了相似性。讓我們牢記這一事實:個體差異遠遠超過性別差異。女性和男性並不是完全相反的兩種性別,他們更像一個人的兩隻手,相似但卻不完全一樣,彼此非常協調,但當他們緊緊相握時卻有所差異。
進化與性別:什麼樣的行為是天生的
在解釋性別差異時,人們通常關注兩點:進化和文化。
“你認為是什麼因素造成了男女兩性的不同人格、興趣和能力?”這是蓋洛普公司(1990)在一項全國調查中的一個問題。“主要是由男女不同的成長方式?還是由其生理差異所導致?”在99%的回答中,認為養育和生物因素起作用的人幾乎各佔一半。
當然,兩性之間的確有明顯的生物意義上的差異。男性有更發達的肌肉以便進行狩獵活動;而女性能夠哺乳。這種生物意義上的差異是否僅僅侷限在生殖和運動系統呢?還是男女兩性的基因、荷爾蒙以及腦機制的差異導致了上述的行為差異?
性別與擇偶偏好
意識到世界範圍的兩性間普遍具有的攻擊性、支配性和性特徵的差異後,進化學派心理學家道格拉斯·肯裡克(Kenrick,1987)認為,“我們無法改變自己種群進化的歷史,我們彼此之間的一些差異毫無疑問受這段歷史的影響。進化學派的心理學家預測,如果兩性面對完全相同的適應挑戰,那麼兩性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差異(Buss,1995b)。兩性都通過分泌汗液調節體溫,在口味上都偏好那些有營養的食物,皮膚磨損時會起老繭。但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同時預言,兩性在約會、婚配以及繁殖行為等方面會存在差異。
比如,讓我們來思考一下男性在性活動中更高的主動性。正常的男性在其一生中會產生億萬個精子,所以相對於卵子來講精子要便宜很多。(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男人,在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你會產生1000多個精子。)而且,當女性孕育一個受精卵時,男性還可以與其他女性性交來增加自己基因的傳播機會。於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女性會更加小心地考察男性的身體健康及資源狀況的信號,以便謹慎處理自己的繁殖機會。男性則需要與其他人競爭,以便將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男人尋求廣泛的繁殖,而女性則需要明智的繁殖。男性尋找的是能夠播種的肥沃土壤,而女性則尋求那些能幫助她們整理花園的男人——擁有資源且比較專一的父親,而不是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
此外,進化學派心理學家提出,在身體運動能力方面處於優勢的男性會獲得更多機會以得到女性,於是人類漫長的演化歷程增強了男性的攻擊性和支配性。那些使Montezuma二世成為阿茲臺克國王的基因特性很自然地通過他的4000個女人遺傳給了他的後代(Wright,1998)。如果我們的祖先母親通過讀懂自己孩子和求婚者的情緒情感而獲得益處的話,那麼自然選擇就會同樣賦予女性情感理解能力。在所有這些假設之下的原則是自然會選擇那些有助於基因遺傳的特性。(Secretariat ,現代最成功的種馬,留下了400只馬駒。)
這些影響過程幾乎是無意識的。很少有人會在痛苦的情緒之下停下來思考,“我要把我的基因遺傳給後代。”甚至更少有人會思考“哦,我多想有一個孩子,能夠養育他,而且還想有外孫。”通過精心的設計,男人不會讓自己排列在基因庫之外。而是像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說的那樣,我們天生追求那種增加基因遺傳性的生活方式。情緒負責執行這種進化機制,就像飢餓促使人體攝取營養物質那樣。
劉易斯·托馬斯(Thomas,1971)在描述雄蛾對雌蛾釋放蠶蛾性誘醇(bombykol)的反應時想到了隱性進化選擇的理論。蠶蛾性誘醇是一種很小的分子,它可以刺激雄蛾的毛髮使之從幾英里以外的地方逆風而上尋找雌蛾。但雄蛾是否意識到受某種化學物質的驅使是令人懷疑的。相反,它可能只是突然覺得那天天氣很好,該活動活動翅膀逆著風向去玩玩。
戴維·巴斯(1995a)說,“人類是有生命的化石——是先前應對壓力時產生的諸多機制的集合。”而且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這不僅有助於解釋男性的攻擊性,也可以解釋男性和女性的性態度和性行為的差異。儘管男性把女性的微笑解釋為性愛的信號常常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萬一猜對了,那他就會在繁殖機會上獲益。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也預測男性會努力為女性提供她們所需要的——外界資源和身體保護。雄孔雀會炫耀它們的羽毛,男性人類也會顯示他們的財富。在一個實驗中,如果一位年輕的男性和一位年輕的女性單獨在一間房間裡,他會把“擁有很多金錢”看得更加重要(Roney,2003)。“男性的成就最終會變成求愛本錢”格倫·威爾遜(Wilson,1994)認為。女性也可能會隆胸、去皺紋、抽脂以提供男性需要的年輕、健康的外表等。巴斯和艾倫·範戈爾德(Buss,1994a;Feingold,1992)十分肯定女性和男性的擇偶偏好可以證實上述假設。請思考一下:
從澳大利亞到贊比亞的37種文化背景下,進行的研究顯示,那些暗示生殖力旺盛的外表,比如年輕的臉孔等等會使女性對男性更加富有吸引力。而女性則被那些富有、有權力和資源的男性所吸引,因為他們可以為後代提供足夠的保護和撫養條件(圖5-2)。男性對外表的興趣使他們成為世界上色情產品的主要消費者。但兩性同樣也存在相似性:不論是定居在印度尼西亞群島還是聖保羅的市郊,男女都渴望親善、愛情和雙方的相互吸引。
各地的男性都傾向於娶更年輕的女性。而且越老的男性,他選擇伴侶時偏好的年齡差距越大。在男性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們喜歡娶比自己年輕一點點的女性。但到了六十多歲,從總體來看,男性會娶比自己小十歲左右的女性(Kenrick & Keefe,1992)。各個年齡階段的女性都偏愛比自己大一點的男性。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再次強調,我們可以看到是自然選擇令男性偏愛與生殖能力有關的女性特徵。
基於這些發現,巴斯(1999)報告說對此感到有點意外:“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在擇偶偏好上的差異如此精確地符合進化學派的預測。就像我們對蛇、高度和蜘蛛的恐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窗口以瞭解進化過程中祖先們遭遇的生存危機一樣,我們的擇偶偏好同樣為我們提供了用以瞭解祖先繁衍所需資源的線索。今天的我們都帶有在競爭中獲勝的祖先的需求。”

圖5-3 人類的擇偶偏好
戴維·巴斯和50位同事調查了各個種族、宗教、政治體制下的1萬多人,包含6個大陸和5個島嶼。發現各地的男性都偏愛那些顯示出年輕健康——適於繁殖的女性,而女性則偏愛有財產和地位的男性。
資料來源:From Buss,1994b.
性別與荷爾蒙
如果基因預先設定了與性別有關的特性,它們肯定會通過對我們身體的影響表現這一點。男性生殖細胞中,影響睪丸形成的基因也會指導分泌睪丸素,一種刺激肌肉表層的激素(Berenbaum & Hines,1992;Hines & Green,1991)。性激素的差異是否也會影響心理層面的性別差異呢?
攻擊性方面的性別差異似乎受到睪丸素的影響。給很多動物注射睪丸素都會增加其攻擊行為。人類中,極端暴力的男性罪犯往往有高於正常水平的睪丸素含量;國家橄欖球聯隊的運動員和狂歡兄弟會的成員也同樣如此(Dabbs,2000)。此外,人類和猴子的兩性攻擊差異在生命早期就表現出來了(在文化發生影響作用之前),並且在成年後隨著睪丸素水平的下降而趨於消失。當然這些證據都不是結論性的。總體來講,這令多數學者相信性激素確實有影響。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文化同樣也是如此。
隨著人類進入中年甚至老年期,出現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女性變得更加獨斷和自信,而男性則更多地與他人共情,更少地支配他人(Lowenthal & others,1975;Pratt & others,1990)。激素變化可能是性別差異減小的一種解釋。角色需要是另一方面原因。另外有一些學者推測在求愛階段和為人父母的最初階段,社會期待會使兩性強調那些能增強他們角色的特性。在求愛、提供資源和保護的過程中,男性會更強調自己的男人氣質,放棄自己對相互依賴和養育的需要(Gutmann,1977),而年輕的女性在求愛和撫育孩子的時候則會控制自己獨立和專斷的傾向。隨著男性和女性逐漸適應了成年早期的角色,他們會更多地表現原先受到限制的特性,他們都變得更加中性 ——兼具獨斷性和養育的能力。
對進化心理學的反思
並非批評自然選擇一說——自然選擇的身體、行為特徵確實增加了基因生存概率——評論家們指出了進化解釋可能存在的兩個問題。第一,進化心理學家通常從一個結果出發(比如兩性在性活動主動性方面的差異)去構建一種解釋。這種方法是倒推的機能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曾是心理學的主流理論。“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行為?因為那樣的行為具備這樣的功能。”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和費爾德曼(Ehrlich & Feldman,2003)指出,這種事後的解釋確實很有說服力,但是正像古生物學家斯蒂芬·古爾德(Gould,1997)諷刺的那樣,這種方法不過是“雞尾酒式的投機性的猜測”。
防止事後推測偏見的方法是想像一下可能出現的其他發展方式。我們不妨來試試。想像一下女性更加強壯而且更富有攻擊性畫面。有些人會解釋說:“當然啦,這樣有助於保護她們的孩子。”而且如果男性從來沒有婚外情的話,我們是否很難發現這種忠誠背後的進化意義呢?多蘿西·艾尼恩(Einon,1994)認為,如果說女性在整個經期甚至懷孕和哺乳時都可以交配,這就意味著,一個忠誠的已婚男性較之於具有相似性活動水平的不忠誠的男性而言,也很有可能讓一位女性多生育後代。而且由於養育後代比交配更重要,所以如果男女共同投入來養育孩子的話,那麼雙方都會受益。那些對伴侶和後代忠誠的男性會更具有適應性,以確保他們可以成功地撫養後代,使之繁衍生息。一夫一妻制可以增加男性父權的確定性。(事實上,對於那些後代需要更多的雙親投資的人類和其他物種傾向於配對生活,實行一夫一妻制,對此進化學派提供瞭解釋。男女之間的愛情如此普遍是因為它在基因傳遞上的優勢:那些忠誠男性的後代在掠奪者面前不會那麼脆弱。)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這些批評“坦率但不正確”。他們認為,倒推法在文化的解釋中也有使用:為什麼男女會有差異?因為他們的文化塑造 了他們的行為!當人們的角色隨著時間地點有所變化的時候,“文化”更多地描述 那些角色而不是解釋它們。而且進化學派心理學家認為他們的學說遠遠超越了倒推式的臆測,是一門利用動物行為的數據、跨文化的觀察以及激素、基因研究來檢驗進化學派假設的實證性科學。正像很多學科一樣,觀察激發了理論的靈感從而產生新的可以檢驗的預測(圖5-4)。這些預測不但可以使我們對未注意到的現象有所警覺,而且可以證實、反駁或是修正某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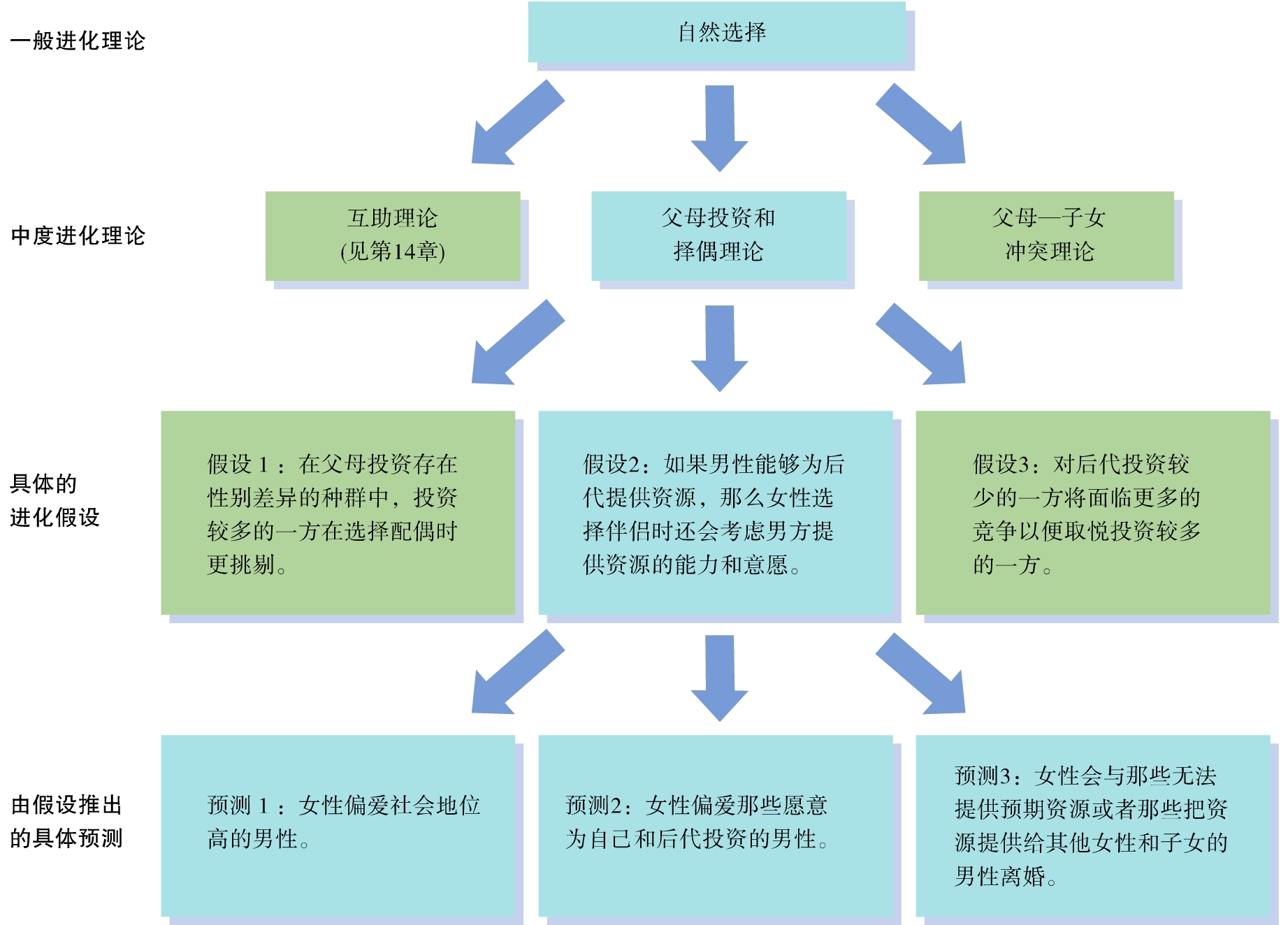
圖5-4
預測的樣例摘自進化心理學(Buss,1995a)。
然而批評者也擔心進化學派關於性和性別的解釋會增強對男女兩性的刻板印象(Small,1999)。進化學派的解釋會不會使黑社會暴力行為,傷人事件以及強姦罪由於男性天生的攻擊性而使其成為正當合理行為呢?而且如果進化學派心理學家使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這就是自然天性所致,那麼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購買家庭保安系統呢?但是進化學派心理學家回答說,這種進化意義是屬於過去 的理性選擇,它只是告訴我們在過去什麼樣的行為有用。至於這些行為現在是否仍然具有適應性,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比如說,儘管人們傾向於被那些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形象的人所吸引,但實際上,他們卻報告說和那些相對中性的人在一起更滿意(Ickes,1993)。
進化心理學的批評者承認進化確實有助於解釋我們人類的異同之處(一定程度的多樣性有利於生存)。但是他們強調我們的進化遺傳無法預測同時受文化影響的人類婚姻行為(從一夫一妻到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還有交換夫妻的行為),而且它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文化能夠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就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看起來自然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特徵似乎就是適應的能力——學習和改變。因而,實際上我們贊同的是文化的塑造力量。
小結
進化學派心理學家提出進化如何決定兩性在行為上的差異的理論,比如攻擊性和性活動的主動性。他們認為,自然界中的擇偶行為要求男性對女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較強生殖力的生理特徵的女性——更加主動,而且要求男性通過攻擊和支配來與其他男性競爭。女性由於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生殖機會,所以會仔細考慮男性保護和撫育後代的能力。批評者認為進化學派的解釋是從事實倒推出的,而且無法解釋文化差異。達成一致的觀點是自然賦予了我們適應各種不同環境的能力。
文化與性別:我們的行為是由文化影響的嗎
文化的影響可以通過不同時間和地點的性別角色生動地體現出來。
正如我們在前幾章就提到的那樣,文化是由一個大群體共享的並代代相傳的東西——思想、態度、行為和傳統。我們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塑造男女兩性的行為觀念以及當人們違反社會期待時將會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Kite,2001)。在各個國家,女孩會花更多的時間做家務和照顧孩子,而男孩則把時間花在自由遊戲上(Edwards,1991)。即使在當代,北美的雙職工家庭中,也是男性做大多數的家務修理工作,而女性負責照看孩子(Bianchi & others,2000;Biernat & Wortman,1991)。
據說,性別社會化給了女孩子“根”,給了男孩子“翅膀”。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在獲得考爾德科特獎(Caldecott Award)的兒童書裡面,拿著家務用具(比如掃帚,針線,鍋,碗等)出現的女孩形象是男孩的4倍。而拿著生產用具(比如乾草叉,犁,槍等)出現的男孩形象是女孩的5倍(Crabb & Bielawski,1994)。而成人的結果是這樣的:聯合國1991年報告說:“世界各個地方,都是女性負責多數的家務勞動。而且在夫妻共同做的家務中,烹飪和洗盤子是最少被分享的家務活。”這些對男女的行為期待界定了性別角色 (gender role)。
在對普林斯頓大學的女大學生所做的一項實驗中,馬克·贊那和蘇珊·帕克(Zanna & Pack,1975)發現了性別角色期待的重要影響作用。要求女大學生填寫一份問卷,要她們向一位即將見面的高大、未婚的高年級男生形容她們自己。那些被告知男方更偏愛家庭型女性的被試比那些被告知男方偏愛強壯有進取心的女性更多地把自己形容為傳統女性。而後者則在隨後的問題解決測驗中表現出更高的智力水平:她們解答的問題比前者多出18%。如果男性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形象,比如矮小的已婚新生,那麼這種迎合男性期待的行為就會有所減弱。在迪安·莫里爾和卡拉·塞羅(Morier & Seroy,1994)合作的一實驗中,男性同樣讓自己的表現與女性的性別角色期望相符合。[你是否在同性面前表現一個自己,而在異性面前表現另外一個自己呢 ?]
那究竟是不是文化構築了性別角色呢?還是性別角色只是反映了男女的自然行為?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性別角色差異表明,文化確實會影響性別角色。
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夫婦兩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顧孩子,或者丈夫外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裡照顧孩子,這兩種生活哪一種更令人滿意?這是皮爾(Pew)全球態度調查(2003)向38000人提出的一個問題。44個國家中有41個國家,其大多數人都認為夫婦兩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顧孩子更令人滿意。但如圖5-5顯示,國家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埃及人不贊成世界觀點的比例是2:1,而越南人贊成的比例則高達11:1。在工業化國家,婦女的地位也有很大差異。日本女性中只有1/10可以做經理,而德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做經理的女性則高達1/2(ILO,1997;Wallace,2000)。在北美,大多數的醫生和牙醫都是男性;在俄羅斯,大多數的醫生是女性;同樣丹麥大多數的牙醫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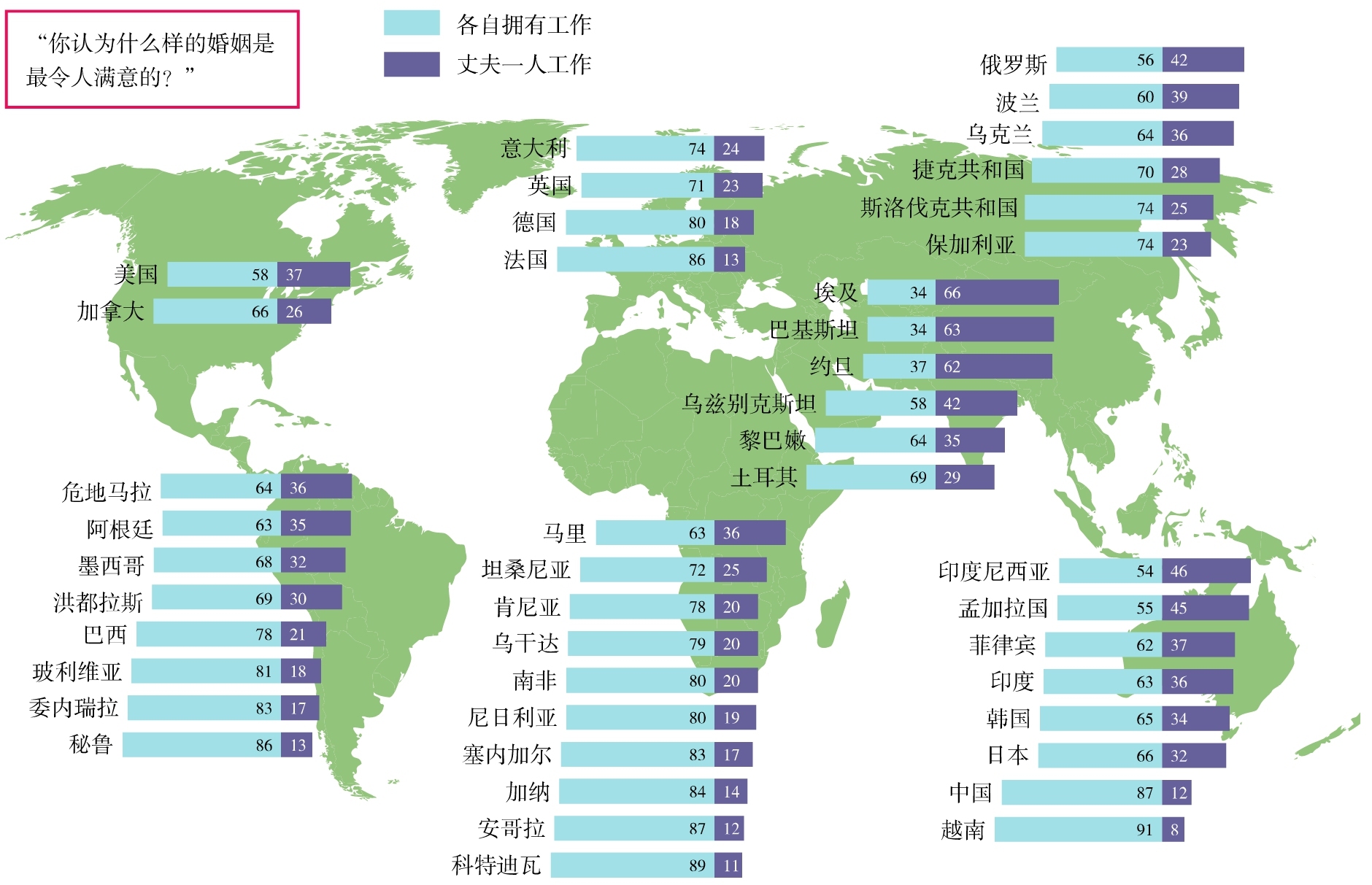
圖5-5 人們贊成的性別角色隨文化而有不同
資料來源:Data from the 2003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不同時代下的不同性別角色
在剛剛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歷史一頁——性別角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38年,只有1/5的美國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去工作掙錢,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養家餬口。”到1996年,4/5的人都贊成這種觀點(Niemi & others,1989;NORC,1996)。1967年,美國57%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贊同“已婚婦女的活動應該限制在家庭範圍內。”而到2002年,只有22%的人同意(Astin & others,1987;Sax & others,2002)。
行為的變化伴隨著態度的轉變。從1960年到1998年間,在職的40歲已婚婦女的比例上升了1倍——從38%到75%(人口調查署,1999)。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大量婦女進入勞動市場。
1965年,哈佛商學院從沒有一個女性畢業生。到20世紀末,其30%的畢業生是女性。從1960年到20世紀末,醫學院的畢業生中女性比例由6%上升到43%,法學院則從3%上升到45%(Hunt,2000)。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已婚婦女花費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是她們丈夫的7倍 ;而到90年代中期,該比例下降到了2倍(參見圖5-6)。如此顯著的跨文化、時間的差異表明,進化和生物學並不能解釋性別角色差異,而是文化塑造了性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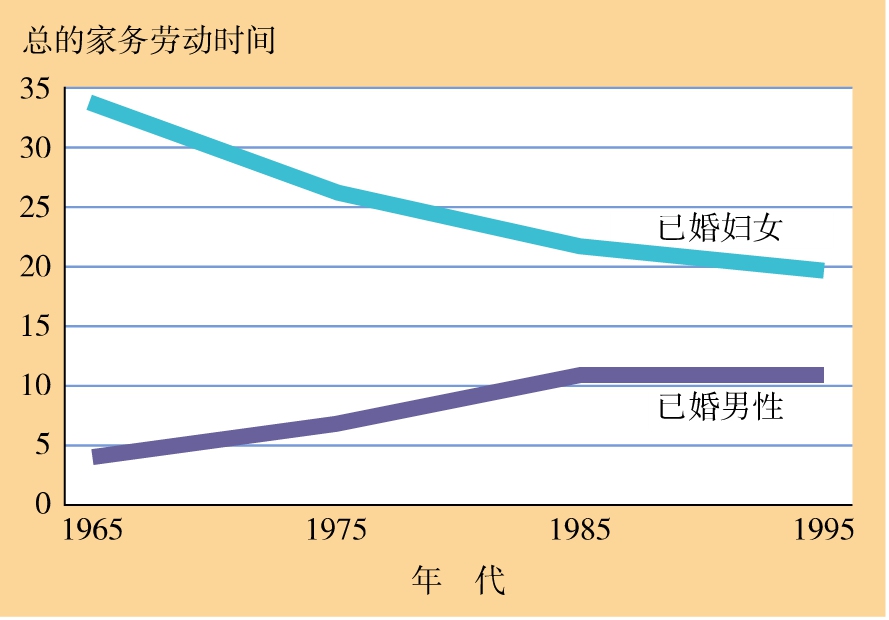
圖5-6 “誰做家務?”
從1965年到1995年,女性花在家務上的時間越來越少了,而男性所花費的時間卻有所增加。
資料來源:From Bianchi & others,2000.
民意調查:女孩打電話和男孩約會,是否恰當?
回答“是”的比率
1950年 29%
1999年 70%
同伴相傳的文化影響
文化,就像冰淇淋,有很多不同的口味。在華爾街,男性幾乎都穿西裝,女性幾乎都穿襯衫和裙子;在蘇格蘭,很多男人都穿著方格裙;在靠近赤道的一些地區,人們幾乎不穿什麼衣服。那麼這些傳統是如何代代相傳的呢?
影響比較大的是哈里斯(Harris,1998)的“教養論 ”:父母撫育孩子的方式決定孩子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弗洛伊德派和行為主義流派的許多學者以及很多普通人都支持這一觀點。比較那些受父母溺愛和打罵的孩子的極端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父母的養育方式確實 有影響作用。而且,孩子會接受父母的很多價值觀,包括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宗教信仰等。但是如果孩子的人格是在父母的榜樣示範以及撫育下形成的,那麼同一家庭長大的孩子應該差不多是相同的,對嗎?
這個理論被發展心理學近期一廣泛認可的令人震驚的研究結果所推翻。用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勞敏和丹尼斯·丹尼爾斯(Plomin & Daniels,1987)的話來說“兩個在同一家庭長大的孩子之間的差異和從眾多家庭中隨機抽取的兩個孩子之間的差異一樣大。”
由對雙生子及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和收養家庭的研究發現,基因的影響大約可以解釋人格特性中50%的個體差異。共享環境影響——包括共享家庭影響——只能解釋0~10%的人格差異。那麼剩下的40%~50%由什麼來解釋呢?哈里斯認為,答案是同伴的影響 。孩子們比較關注的其實並不是父母怎麼想,而是他的同伴怎麼想。孩子們主要從同伴會那裡學習怎麼玩遊戲,音樂愛好,口音,甚至髒話也大部分來自於同伴群體。事後想想,這也很有道理。他們畢竟是和同伴一起玩耍,到最後可能會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請思考一下:
學前兒童經常會拒絕嘗試某一種食物,即使父母要求也不行。但是一旦他們和一組喜歡這種食物的孩子一起吃飯,他們就會有所改變。
儘管吸菸者的孩子更可能吸菸,但是最主要的影響仍然來自同伴。這些吸菸的孩子大多有一些吸菸的朋友,向他們介紹吸菸的快樂,並給他們提供香菸。
戴維·羅(Rowe,1994)提到,60年前納粹少年團的成員大多數來自給他們提供情感關懷的中產階級家庭。腐蝕他們的並不是家庭不良的教養方式,而是周圍環境變化導致的“更大”的影響。
移民家庭的孩子通常偏好新環境中同伴的語言與習慣。如果回到祖國,他們可能會轉換回國內的傳統文化,但是其內心深處仍然接受同伴的文化。同樣,父母正常的失聰兒童,如果被送到聾啞學校的話,通常都會放棄父母的文化,而被失聰者的文化所同化。
因此,如果我們讓一組兒童呆在相同的學校,社區和同伴關係中,只是把他們的父母換掉的話,如哈里斯(Harris,1996)預測的,他們“會成長為相似的成年人。”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這些成年人通常和父母很相似,但是她指出文化似乎很少從單個的父母傳遞給孩子,而是從父輩群體傳遞給後輩群體。父母會決定孩子所在的學校、社區和同伴關係,而這些環境反過來也會影響孩子們的違紀行為,使用毒品以及懷孕的機率。此外,孩子們常常會受比他們稍微大一點的同伴的影響,而這些孩子再從比他們大一點的孩子身上學習,直到那些和父母同屬一代的年輕人。
父母一代與孩子一代之間的聯繫相對鬆散以至於文化的傳承並不十分理想。而且在人類社會和靈長類的社會文化中,變化往往都來自年輕一代。當一個猴子發現一種更好的清洗食物的方式,或者當人們追求新的流行時尚或者性別角色時,這種創新大多來自年輕人,而且通常首先會被其他年輕人所接受。於是,文化傳統在延續中變化著。
小結
受到最多研究的社會角色——性別角色,反映了文化的重大影響。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時代的性別角色差異非常大。主要的文化影響並不是由父母直接帶來的,而是通過同伴的影響。
結論
生物和文化並不是截然對立的,因為文化是在生物因素的基礎上對個體施加影響的。那麼,生物和文化如何相互影響呢?而且我們自身的人格特點又如何與環境相互影響呢?
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
我們不需要把進化影響和文化影響看做是對立的成分。文化規範對我們的態度和行為有微妙而強大的影響,但是它並不能獨立於生物因素而起作用。所有的社會和心理因素歸根結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待能影響我們,那這其實也是我們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對於那些生物遺傳所引發的因素,文化則起到加強的作用。如果基因和激素預先設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富有攻擊性,那麼文化可能會以那些期待男性堅強而女性親善的社會規範來強化這種設定。
生物和文化因素也有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interact)。當今的遺傳科學顯示出經驗是如何運用基因改變大腦的(Quarts & Sejnowski,2002)。環境刺激能夠產生新的腦細胞以分化感受器。視覺經驗可以生成發展大腦視覺區的基因。父母的愛撫可以產生有助於後代應對未來壓力事件的基因。基因不只是限制我們,它還會根據我們的經驗做出適應性的行為反應。
生物因素和經驗因素可以相互作用,儘管生物特性會影響環境的反應方式。人們對貝克漢姆和木訥的伍迪·艾倫會有不同的反應方式。男性,身高比女性高8%,肌肉含量高一倍,因此他們可能會有不同於女性的經歷。或許應該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存在這樣一個非常強硬的文化規範規定,男性應該比他們的女性伴侶高。在一個研究中,720對夫婦中只有一對不符合上述規範(Gillis & Avis,1980)。我們可以推測出心理學的解釋:也許身高(或者年齡)優勢有利於幫助男性維護對女性的社會權力地位。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推測到這種社會規範深層的進化意義:如果人們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侶,那麼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找不到合適的伴侶了。進化要求男性趨向於比女性更高,而文化也會做類似的設定。於是選擇伴侶時的身高規範就是生物和 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艾利絲·伊格利和溫迪·伍德(Eagly & Wood,1999;Eagly,1987)提出了生物與文化因素的交互作用理論(圖5-7)。他們認為存在許多不同的因素,包括生物影響,兒童期的社會化經歷,導致了男女兩性不同的社會分工。成年以後,直接影響社會行為性別差異的是反映兩性勞動方式的社會角色 。男性由於他們的力量和速度,似乎被放置在需要身體力量的角色中。而女性由於其生育和撫育孩子的能力使得她們更多地屬於照顧者的角色。於是男女兩性就各自傾向於表現那些符合角色期待的行為,同時進一步塑造自己的技能和信念。因而自然和養育構成了一張“彼此纏繞的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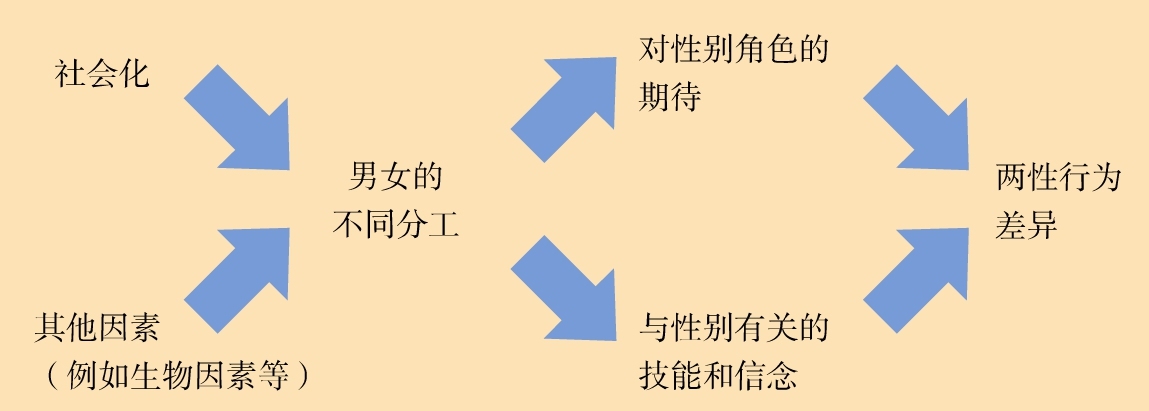
圖5-7 兩性社會行為差異的社會角色理論
各種影響因素,包括童年經歷等,使得男女兩性具有不同的角色。正是這些不同角色的期待和信念影響了男女兩性的行為。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Eagly,1987,and Eagly & Wood,1991.
研究背後的故事:
艾麗斯·伊格利關於性別相似性與差異性的研究
我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因為一項社會影響的研究項目開始涉足性別領域的研究。像今天的許多女性主義活動家一樣,我最初認為,儘管對女性有消極的文化刻板印象,但女性和男性的行為本質上是相同的。經過這麼多年,我的看法有了相當大的改變。我發現男性和女性的一些社會行為還是存在一定的差異,特別是在那些考慮了性別角色的條件下。
人們不應該認為這些差異必然反映出對女性的不公。女性對他人的高敏感性以及更加民主化的待人方式在很多情況下都具有優勢。事實上,我通過性別刻板印象的研究發現,如果我們把所有積極和消極的特質都考慮進去,似乎女性的刻板印象比男性的刻板印象更受歡迎。然而,善良等特性會削弱女性在那些需要果斷與競爭行為的情境中的能力和效率。
對185個社會的分析表明男性大多從事狩獵和伐木工作,女性負責90%的洗衣做飯等工作,而在種植、收割和擠牛奶的工作中兩性比例相似。隨著性別角色變得越來越平等,伊格利預測說性別差異“將會逐漸縮小”。
確實如伊格利和伍德(1999)提到的,那些性別角色相對平等的文化中,男女選擇伴侶方面的偏好差異(即男性追求年輕女性及打理家務的能力,女性要求男性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就會更小。同樣,隨著在傳統男性崗位中工作的女性越來越多,自我報告的男性特徵/女性特徵中的性別差異也越來越小(Twenge,1997)。由於男性和女性開始扮演越來越相似的角色,他們的心理差異也越來越小。儘管生物因素將男性設定為從事力量型工作,而女性從事照顧孩子的工作,但是伍德和伊格利(2000)總結說,“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是可塑的,以至於兩性個體都能夠在各種水平上有效扮演社會角色。”除了現在對於高社會地位角色所需要的男性能力和進取性的重要性逐漸降低以外,低出生率意味著女性較少地受懷孕和撫育後代的束縛。伴隨著反種族歧視法的出臺和僱用最優秀人才(不論性別如何)的競爭壓力,結果將會不可避免地提高兩性地位的平等性。
生物和社會化對人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影響到目前為止似乎都很重要,因為我們扮演的角色會直接影響我們的行為。如果男性更加專斷而女性更加關懷他人,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各自分別扮演的是強有力的角色和提供關懷的角色。當工人(不論男女)從與上司談話轉向與下屬談話時,他們會變得更加自信(Moskowitz & others,1994)。
環境與人的力量
物理學家尼爾·玻爾(Niels Bohr)說:“有微不足道的事實,也有偉大的真理髮現。微不足道事實的反面很顯然是錯誤的,而偉大真理的反面依舊是事實。”這一部分關於社會影響的各個章節都揭示出這樣一個偉大的事實:社會環境具有巨大的力量。這種關於外部強大壓力的事實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有時我們像牆頭草那樣做出被動的行為。但是,我們並不像牆頭草那樣完全被環境操縱。我們行動,我們反抗。我們對環境做出反應,並獲得環境的應答。我們可以抗拒社會情境,甚至有時候可以改變環境。因此,關於“社會影響”的每一個章節都會在結論中呼籲人們關注重要事實的對立面:人的力量。[請思考:如果玻爾的陳述是一個偉大的真理,那麼其對立面是什麼 ?]
也許對文化力量的強調會令我們有些不舒服。多數人不喜歡聽到外部力量決定我們行為的解釋;我們把自己視為自由的生靈,是我們自己行動的主宰(至少是我們比較好的行為)。我們意識到相信社會決定論會引發如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所稱的“錯誤信念”——以指責其他人或事物來逃避責任。
事實上,社會控制(環境的作用)和個人控制(個人的作用)並不是相互對立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對行為的解釋都是有效的,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是社會的產物和創造者。我們更可能是基因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但事實是未來即將到來,我們的任務就是決定未來的方向。我們今天的選擇將會決定明天的環境。
社會情境的確會強烈地影響個體。但是個體也會影響社會情境。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追問到底是外部情境還是內部傾向(文化或進化)決定了行為就好像是追問到底是長還是寬決定了矩形的面積一樣。
這種交互作用至少是以三種方式進行的(Snyder & Ickes,1985)。首先,某一種特定的社會情境通常會對不同人產生不同的影響 。由於我們的心靈並不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來理解現實,所以每個人都會按照自己對情境的解釋進行反應。有些人比其他人相對更加敏感,更容易對社會環境做出反應(Snyder,1983)。比如日本人對社會期待就比英國人更敏感(Argyle & others,1978)。
第二,由於人們通常會選擇自己所處的環境 ,於是人的因素就會和環境因素髮生交互作用(Ickes & others,1997)。假如面臨一種選擇,社交型的人會選擇能引發社會交往的情境。當你選擇某一個大學時,你也在選擇將自己放置在什麼樣的社會影響中。激進的自由主義者不太可能定居在加利福尼亞的Orange縣,也不太可能參加商業會議。他們更傾向於住在多倫多並參加綠色和平組織的活動(或者閱讀《曼徹斯特衛報》,而不是《倫敦時報》)。換句話說,他們會選擇一個強化自身傾向的社會環境。
第三,人們會創造自己的環境 。回想一下我們先前對自我實現的定義:如果我們期待某人特別外向,富有敵意,很女性化,或非常性感,那麼我們就會引導那個人按照我們的期待來行動。除了置身於環境中的人以外,還有什麼因素會決定社會情境呢?一個自由的環境往往是由自由主義者創造的。婦女聯誼會的活動也是由其成員決定的。社會環境和天氣不一樣——僅僅發生在我們周圍。環境更像我們的家園——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地方。
小結
生物和文化解釋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實際上它們是相互影響的。生物因素在文化背景下起作用,而文化因素則在生物因素基礎上施加影響。
如果不考慮人的力量的話,有關社會影響的重要事實就只是半個事實而已。個人和情境至少通過三種方式相互影響。首先個體對某一個特定情境的解釋和反應有差異。其次,人們會選擇對自己有影響的環境。第三,人們會創造自己的社會環境。因此力量根植於個人和環境之中。所以我們既創造我們的世界,也被我們的世界所塑造。
個人後記:我們應該把自己看做社會的產物還是社會的建築師
情境與個人之間雙向的聯繫使我們與環境之間存在互動 。我們既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境的建築師,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那麼是不是哪一種說法更為明智呢?從某種角度講,把自己看做環境的產物(否則我們一方面會因為自己是社會的建築師而過分驕傲,另一方面會為自己的問題而過分指責自己),同時把他人視為自由的行動者(否則我們會變得過於集權而專斷)比較明智。
也許我們按照相反的方式理解會更好——把自己看做自由者,同時關注他人受到的環境影響。這樣我們看待自己時會更強調自我效能,同時在看待他人時更多地理解他們的處境(如果我們認為他人是受自己所處環境的影響,這樣我們就會更可能理解他人,而不是簡單地把其不良行為歸因於“不道德”、“殘酷”、“懶惰”)。但多數的宗教都鼓勵我們對自己負責同時儘量少地評價他人。這難道是因為我們人類的天性就是更多地給自己的失敗尋找藉口而同時卻會責怪他人?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閱讀上面喬治·阿爾比(George Albee)的引言。你見過一些類似引言中所提到的具有某種問題的人嗎?如果你認為他們的問題是由於其自身的無能或可以避免的疏忽所造成的,你將對他們說些什麼以表示支援?
如果你認為這些問題是由他們所處的情境導致的,你又將對他們說些什麼?
現在思考一下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三種方式,描述一下這些人是如何與他或她的環境相互作用的?
聯繫社會
性別和文化遍及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例如,文化可以預測人們的順從行為嗎(第6章:從眾)?文化在人們看待愛情的方式上有何不同?男性和女性的愛情觀有何不同(第11章:吸引和親密)?
第6章 從眾
什麼是從眾
什麼是經典的從眾研究
謝里夫的規範形成研究
阿施的群體壓力研究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
什麼因素引起了服從
對經典研究的反思
什麼因素可以預測從眾
群體規模
一致性
凝聚力
地位
公開的反應
無事前承諾
個體為什麼會從眾
誰會從眾
個性
文化
我們如何抵制從眾的社會壓力
逆反
堅持獨特性
個人後記:因為你是社區中一員
“任何壓制個性的行為,均為專制,而不論名稱為何。”
——古典經濟學家,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論自由》,1859
“社會帶來的壓力是我們道德價值的重要支柱。”
——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社會精神》,1993
你一定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當一場辯論賽或音樂會結束時,前排的讚賞者起立鼓掌。緊跟其後具有同樣感受的人也起立鼓掌。現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到了未受鼓動者,他們也從舒適的椅子上站起來,給予了禮節性的喝彩。可是,你還想坐著(“這位演講者根本就不代表我的觀點”)。但是,當起立鼓掌的浪潮掃過時,你還會獨自坐著嗎?成為少數與眾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
這一從眾的場面引出了本章的一系列問題:
群體由各種各樣的個體組成,為什麼他們的行為常常如此一致?
人們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會表現出從眾行為?
某些人更可能表現出從眾行為嗎?
誰更可能抵制從眾的壓力?
從眾和唯唯諾諾的形象一樣很消極嗎?還是我應該將其描述為“群體團結性”和“社會敏感性”?
先讓我們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從眾是好還是壞?對這個問題,沒有科學的答案。但是,就我們大多數人共同的價值觀而言,我們可以說,從眾有時是壞的(會導致有些人酒後開車或表現出種族歧視行為),有時是好的(可以阻止人們在劇院排隊買票時插隊),而有時卻無關緊要(例如網球運動員喜歡穿白色球衣)。
什麼是從眾
然而,“從眾”一詞確實不含消極的價值判斷。如果你常聽到某個人說你是一個“真正徹底的從眾者”,你會有什麼感受?我想,你可能會有受傷感,因為西方文化並不讚賞屈從同伴壓力。所以,北美和歐洲的社會心理學家給從眾貼上了消極的標籤(從眾、屈從、服從),而不是賦以積極的含義(社會敏感性、反應性、團隊合作精神),這反映的是他們的個體主義文化。
在日本,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不是軟弱的表示,而是忍耐、自我控制、成熟的象徵(Markus & Kitayama,1994)。蘭斯·莫羅(Lance Morrow,1983)觀察到,“無論在日本的什麼地方,你都可以體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平靜感,這種平靜來自人們確切知道彼此之間的相互期待。”
道德:我們會選擇符合自己價值觀和判斷的標籤。對少數投票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立法者,人們把他們看成是“獨立的”和“內控的”人,但是對少數投票反對公民權利的立法者而言,人們把他們看成是“叛逆的”和“自我中心的”人。我們既可以描述標籤,也可以評價標籤,但是,我們卻不能對其避而不用。因為不用標籤,我們便無法討論本章的內容。所以,先讓我們弄清楚下述標籤的含義:從眾、服從、接納。
從眾不僅僅是與其他人一樣地行動;而是指個人受他人行動的影響。從眾不同於你單獨一人時的行動。因此,從眾 (conformity)是指根據他人而做出的行為或信念的改變。作為人群中的一份子,當你為一個贏得比賽勝利的漂亮進球起立歡呼時,你是不是在從眾?當你和其他人都認為,女性留長髮要比留短髮好看時,你是不是在從眾?也許是,也許不是。關鍵是,當你脫離群體時,你的行為和信念是否仍保持不變。如果球場上只有你一個球迷,你會起立歡呼嗎?
從眾可以表現為許多形式(Nail & others,2000)。讓我們考慮一下這兩種行為:順從和接納。有時我們會順從一種期望或要求,但並不真正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我們有時會穿禮服打領帶,儘管自己並不喜歡這樣。這種靠外在力量而表現出的從眾行為叫做順從 (compliance)。我們之所以順從,主要是為了得到獎勵或避免懲罰。如果我們的順從行為是由明確的命令所引起的,那麼我們稱它為服從 (obedience)。
有時我們真的相信群體要求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會與成千上萬的人一起喝牛奶,因為我們認為牛奶是有營養的。這種真誠的、內在的從眾行為叫做接納 (acceptance)。有時,接納會緊跟順從。正如第4章所強調的,態度緊跟行為一樣。除非我們覺得對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責任,否則,我們通常會贊成自己堅持做的事情。
什麼是經典的從眾研究
社會心理學家如何在實驗室裡研究從眾?有關社會壓力和罪惡本性的研究,他們的發現揭示了什麼內容?
研究從眾的學者們設計了一些微型的社會世界——實驗室微觀文化,簡化和模擬了日常社會影響的主要特徵。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三組有名的實驗。每一組實驗都提供了從眾的研究方法和驚人的發現。
謝里夫的規範形成研究
三個經典研究中的第一個,是架設在第5章和本章內容之間的橋樑,第5章關注於文化的力量,描述了文化如何創造出權威性的社會規範並使之代代相傳,而本章則注重於從眾。謝里夫(Muzafer Sherif,1935,1937)想知道,在實驗室情境下是否有可能觀察到社會規範的形成。就像生物學家想努力把病毒分離出來,以便對之做實驗一樣,謝里夫也想把社會規範分離出來,然後對其進行研究。
請想像自己作為謝里夫實驗之一的被試,你會發現自己坐在一個非常黑暗的屋子裡。在你對面15英尺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小光點。起初,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了幾秒鐘,這個光點不規則地動了起來,最後消失了。現在,你必須猜測光點移動了多長的距離。黑暗的屋子使你根本無法準確做出判斷,因此,你不大確定地說,“6英寸”。實驗者又重複了這個程序。這次你說,“10英寸”。隨著重複次數的增加,你的估計會接近一個平均值,譬如說8英寸。
第二天你來參加實驗時,另有兩個人加入。在前一天他們與你有相同的經歷。當第一次光點消失後,這兩個人根據前一天的經驗說出了最佳的估計。“1英寸”,其中一個人說。“2英寸”,另一個人說。輪到你了,你有些猶豫,還是回答,“6英寸”。在接下來的兩天裡,你們不斷地重複做這樣的實驗,你的反應會改變嗎?實驗發現,參加謝里夫實驗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被試明顯地改變了他們的估計。如圖6-1所示,很明顯,群體規範就這樣產生了。[這個規範是錯誤的。為什麼?光點根本沒有移動!那只不過是謝里夫利用了稱之為似動現象 (autokinetic phenomenon)的視錯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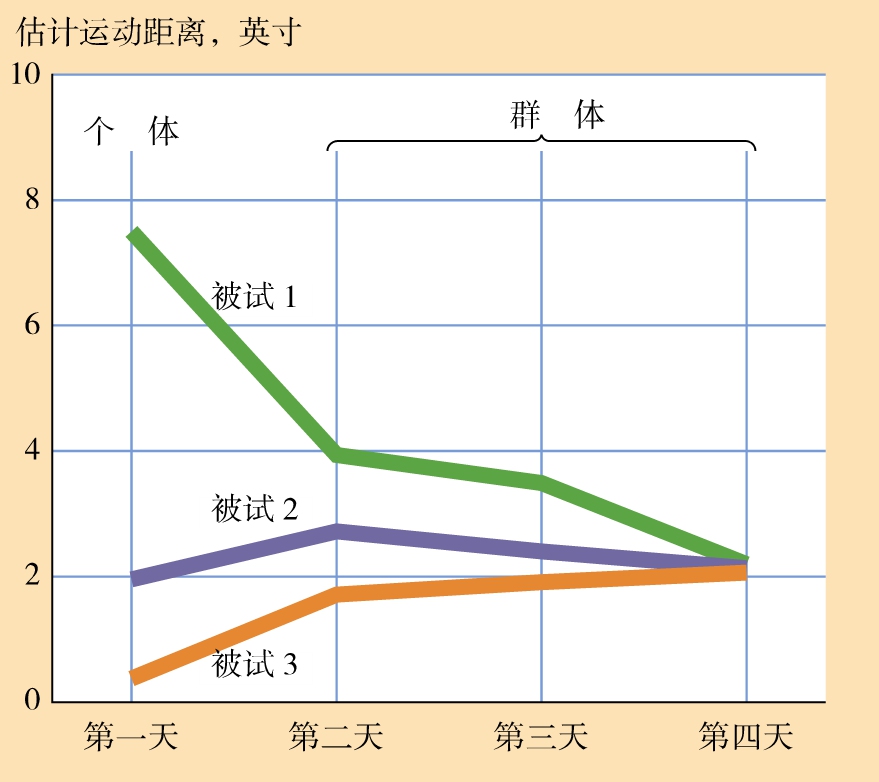
圖6-1 謝里夫規範形成研究中的一個樣本群體
當對光點的移動距離反覆進行估計時,三個被試的估計值匯聚了。
資料來源:Data from Sherif & Sherif,1969,p.209.
謝里夫和其他人利用這一技術回答了個體易受暗示性的一些問題。如果一年以後再對人們單獨地重測,那麼,他們的估計是分散的還是依然遵循群體規範呢?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依然遵循群體規範(Rohrer & others,1954)。(這是順從還是接納?)
被文化支持錯誤信念的巨大力量所震驚,羅伯特·雅各布斯和唐納德·坎貝爾(Robert Jacobs & Donald Campbell,1961)在西北大學實驗室裡研究了錯誤信念的傳遞作用。利用似動現象,研究者讓同謀者 (confederate)給出一個光點移動距離的誇張估計。接著,同謀者離開了實驗室,被一個真正的被試所代替,這個被試後來又被另一個新成員所代替。這種誇張的錯覺(儘管是逐漸減少的)一直持續到第5個被試。這些人成了“令錯誤文化傳承下去的不知情的共謀者”。這些實驗的啟迪是: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未必就是我們自己的觀點。
在日常生活中,暗示的結果有時很有趣。一個人咳嗽、笑或打呵欠,然後周圍其他人也這樣。喜劇所具有的笑的軌跡,就是利用了這種暗示作用。處在愉快的人中間會使我們有愉快感,彼得·托特德爾等人(Peter Totterdell & others,1998)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心境聯結”(mood linkage)。對英國的護士和會計師所做的研究發現,在同一工作群體中人們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
社會傳染效應的另一種形式是塔尼亞·沙特朗和約翰·巴奇(Tanya Chartrand & John Bargh,1999)所謂的“變色龍效應”。想像一下,你參加了他們其中這樣一個實驗,與一位同謀者一起工作。這位同謀者一會兒擦擦臉,一會兒晃晃腳。像其他參與者一樣,與經常擦臉的人在一起,你也更會擦自己的臉嗎?與晃腳的人在一起,你也更會晃腳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它很可能是一種自動的行為,你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從眾,它還會令你和其他人感同身受(Neumann & Strack,2000)。
暗示也能在更大範圍內發生。1954年3月底,西雅圖報紙報道了距北方80英里的一個城市裡汽車擋風玻璃被損壞的事件。4月14日早晨,距65英里的地方以及同一天稍後,在45英里處均發現汽車擋風玻璃被損壞。到了傍晚,損害汽車擋風玻璃的主謀已擴展到了西雅圖。4月15日午夜之前,西雅圖警方已接到3000多起報告汽車擋風玻璃損壞的事件(Medalia & Larson,1958)。那天晚上西雅圖市長向艾森豪威爾總統發出了求助。
那時我在西雅圖,正好11歲。我記得自己也在小心注意擋風玻璃,被當時的解釋嚇壞了——太平洋上的氫彈實驗引發的暴風雨將橫掃西雅圖。然而,到了4月16日,報紙報道,真正的罪犯是人群暗示。4月17日之後便沒有任何有關該事件的報告。對凹陷的汽車擋風玻璃的事後分析認為這不過是普通的道路破壞。為什麼我們只是在4月14日以後才注意這一點呢?在暗示的影響下,我們只會仔細地察看擋風玻璃,而不會透過 現象去尋找其他原因。
在現實生活中,暗示並非總是這樣有趣。劫機、看見UFO,甚至自殺,往往像浪潮般湧現(參見“聚焦:群體妄想”)。社會學家戴維·菲利普與其同事(David Philips & others,1985,1989)認為,當媒體報道了自殺事件之後,一些自殺事件,以及致命的車禍,私人飛行事故(有時是偽裝的自殺)也會迅速增加。例如,1962年8月6日,瑪莉蓮·夢露自殺後,美國8月份的自殺事件比往年同期多了200多起。更進一步講,所增加的自殺事件只是發生在自殺被報道的區域。報道得越厲害,以後的災禍增加得就越多。
儘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發現有模仿自殺的現象,但是在德國卻出現過這種現象,同時在倫敦一家精神病院裡,該院一年內就有14位病人自殺,而且在一所高中學校裡,18天內,發生2起自殺,7起自殺未遂事件,23個學生報告說有自殺念頭(Joiner,1999;Jonas,1992)。不僅在德國,就是在美國,當肥皂劇裡出現虛構的自殺情節後,現實生活中的自殺率也會略有上升。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使在關注自殺問題的嚴肅的話劇上演後,仍會出現這種情況(Gould & Shaffer,1986,Hafner & Schmidtke,1989,Phillips,1982)。菲利普報告說,青少年是易感人群,該研究結果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有時青少年會發生群體模仿自殺。
阿施的群體壓力研究
謝里夫實驗中的實驗者面對的是模糊的現實情景。想像一下一個名叫所羅門·阿施(Solomon Asch,1907~1996)的小夥子面對的不是那麼模糊的知覺問題吧。阿施回憶起參加傳統的猶太教逾越節家宴的情景,
我問坐在我身旁的叔叔,為什麼要開著門。他回答道,“先知以利亞今晚會造訪每個猶太家庭,從特意為他準備的杯子裡呷一口葡萄酒。”
我對此感到很驚訝,又問,“他真的會來嗎?他真的會呷一口酒嗎?”
叔叔說,“如果你仔細地盯著,當門開時,你會看到——你注意到杯子——你真的會看到酒少了一些。”
果然如此。我的眼睛盯著葡萄酒杯,下決心看看是否有變化。對我來說這是很折磨人的,當然,也很難說有絕對的把握——酒杯邊緣確實發生了一些事,酒真的少了一點點(Aron & Aron,1989,p.27)。
聚焦 群體妄想
人群暗示往往以集體妄想的形式出現——自發地散播錯誤信念。有時,它表現為“群體癔症”——在一所學校或一個車間內散播的軀體病痛,卻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器質性病變。一所2000人的高中被關閉了兩個星期,就是因為有170名學生和教職工由於胃疼、眩暈、頭痛和嗜睡而尋求緊急治療。人們對病毒、細菌、殺蟲劑、除草劑——任何可能使人致病的東西——作了檢查,翻了個底朝天,結果卻什麼也沒有發現(Jones & others,2000)。
9.11以後,美國各地的學校有很多孩子染上了一種疾病,即皮膚上生出疥癬般的紅疹子,但沒有找到任何顯而易見的原因(Talbot,2000)。不像濾過性病毒的產生條件,這種紅疹子是通過“目光”傳染的。當看 到其他人生了紅疹子後,他也開始長紅疹子了(他們甚至沒有接觸)。同樣,每天的皮膚狀況——溼疹、粉刺以及過熱的教室所引發的皮膚乾燥——都引起人們的重視,焦慮也令事態嚴重化了。正如其他的群體癔症那樣,謠言四起,令人們過分關注普通的日常不適,而且將這一切歸因於學校。
社會學家羅伯特·巴塞洛繆和埃裡克·古德(Robert Bartholomew & Erich Goode,2000)報告了發生在上個千年的另一起群體妄想。在中世紀,歐洲的修道院報告說那裡開始大規模暴發各種模仿行為。在一所大的法國修道院,人們在那段時間內都相信,人可以由動物所附身,於是一個修女開始像貓一樣咪咪叫。最後,“每天在特定的時間所有修女都像貓一樣叫。”在一所德國修道院裡,一個修女開始咬她的同伴,不久後,“這個修道院裡所有修女都開始互相啃咬”。隨後,啃咬的狂熱擴散到其他修道院。
在1914年的英屬南非,報紙曾錯誤地報道,德國飛機將飛臨該國上空,目的是為即將到來的戰略進攻做準備。而且所報道的飛機調遣能力和飛行距離都超出了1914年那時的飛行能力。然而,無數的人們把晚上所有模糊的刺激,如星星,都錯誤地認作是敵機。
1947年6月24日,肯尼思·阿諾德(Kenneth Arnold)駕駛他的私人飛機飛向雷尼爾峰,其間他發現了空中有九個閃閃發光的物體。由於擔心看到的可能是外國飛來的導彈,他趕緊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這個情況。但發現辦公室已關門,於是他去了地方報社,報告說自己看見了新月形的物體,它們運動起來“像劃過水麵的碟子”。聯合報社隨後報告,有150多家報道說看見了“碟子”,於是“飛碟”這個詞語就被頭版頭條的作者創造出來了,這一行為觸發了1949年夏天餘下的日子裡世界範圍內看到飛碟的狂潮。
數年以後,社會心理學家阿施在實驗室裡重演了孩提時代的經歷。想像一下,你是阿施的一名志願者被試。你坐在7個人一排的第6個位置。在向你們解釋你們參加的是一個知覺判斷的實驗之後,研究者要求你說出,圖6-2中的3條線段中哪一條與標準線段一樣長。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線段2。當你前面的其他5個人都說“線段2”時,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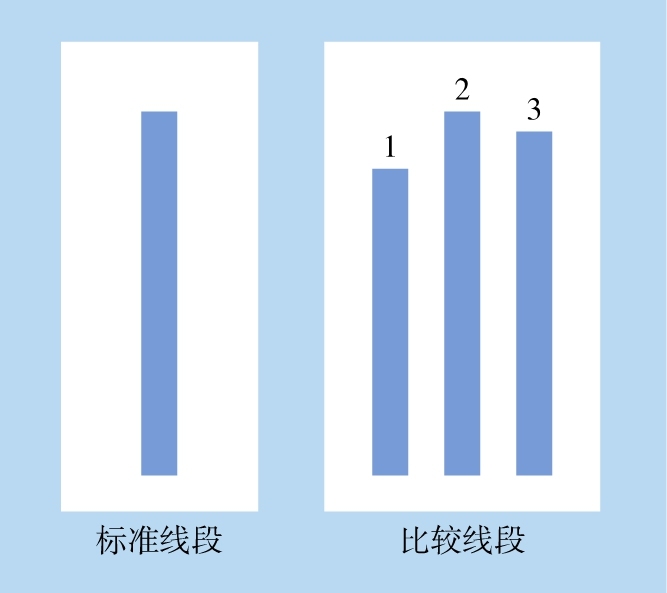
圖6-2 所羅門·阿施的從眾實驗程序中的比較舉例
實驗者要判斷3條線段中哪一條與標準線段一樣長。
接下來的比較同樣很簡單,你似乎正處於一個簡單的測試中。但第三次判斷卻令你大吃一驚。儘管正確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第一個人答錯了。在第二個人也答錯時,你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使勁盯著卡片。第三個人也同意前面兩人的答案。你張大嘴巴,渾身開始冒汗,“怎麼回事?”你問自己,“是他們瞎了,還是我瞎了?”第四、第五個人也同意前面幾個人的答案。接著,研究者看著你。現在,你面臨著認識論上的兩難困境:“什麼才是正確的呢?是同伴告訴我的是正確的呢,還是我的眼睛告訴我的是正確的?”
很多大學生在阿施的實驗中也都經歷了這類衝突。控制條件下的被試,單獨回答時正確率是99%。阿施想知道:如果其他幾個人(經過研究者訓練的同謀者)給出一致的錯誤答案,那麼個體是否會給出在其他場合下否認的答案呢?儘管有些人從來不從眾,但四分之三的人至少有過一次從眾行為。研究發現有37%的回答是從眾的(還是應該說“相信他人 ”?)。當然,這也意味著有63%的人沒有從眾。儘管有很多實驗者表現出獨立性,但阿施(1955)對從眾的感覺就像對自己問題的答案一樣清楚:“看上去聰明而善良的年輕人願意把白說成黑,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這對於我們的教育方式以及指導我們行為的價值觀提出了質疑。”
阿施的實驗程序成為後來許多實驗的標準程序。但是這些實驗缺乏第1章所說的日常從眾的“世俗現實性”,但確實有“實驗現實性。”在這種經歷中人們變得情緒化。謝里夫和阿施的研究結果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他們並未涉及到明顯的從眾壓力——既無“團隊合作”的獎勵,也無個體化的懲罰。如果在這樣小的壓力下人們表現出從眾行為,那麼,在直接強迫情形下,他們會表現出怎樣的順從行為呢?能強迫普通美國人或英聯邦公民做出殘忍的行為嗎?我認為不能:他們的人性、民主、個體主義的價值觀會使他們抗拒這種壓力。此外,這些實驗中的口頭語言,同實際傷害他人還有很大的距離;你和我決不會屈服於傷害他人的壓力。我們真的會這樣嗎?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很想知道這一答案。[道德上的解釋:職業道德規範通常要求在實驗做完之後做出必要的解釋(參見第1章)。想像一下你是一位研究者,剛剛與一位順從的實驗者完成一組實驗。你能解釋一下這個騙局,讓實驗者不至於產生受騙和愚蠢感嗎? ]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
米爾格拉姆(1965,1974)的實驗考察了當權威的要求與道德的要求相牴觸時會發生什麼行為。這些實驗構成了社會心理學最著名也是最有爭議的實驗。“也許在社會科學中這比其他任何實證研究的貢獻要大得多”,李·羅斯(Lee Ross,1988)評論說,“它們構成了我們社會共有智慧遺產——歷史事件、聖經寓言和經典文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偉大的思想家在探討人類本性和思考人類歷史時可以對其自由引用。”
這是米爾格拉姆設計的場景,這位頗具創造性的藝術家撰寫了故事並設計了劇本:兩個人來到耶魯大學心理實驗室參加一個學習和記憶的研究。研究者穿著灰白色的技術人員的長褂,嚴肅地解釋說,這是有關懲罰對學習影響的預研究。研究者要求其中一人教給另一個人一組成對出現的單詞,如果出錯,就要對其進行懲罰,懲罰就是實施逐漸增強的電擊。為了分配角色,他們要從帽子裡抽籤。兩人中的一人,溫和的47歲的會計師,他是研究者的同謀者,假裝說自己抽到了“學習者”的籤,並被領進隔壁房間。“教師”(看到了報紙廣告的應徵者)體驗一次輕微的電擊後,看著研究者把學習者綁在椅子上,並在其手腕上縛上電極。
然後,教師和實驗者回到主房間(見圖6-3)。教師坐在“電擊發生器”前,該儀器上有一排開關,相鄰開關之間間隔15伏,從15伏一直到450伏。開關上寫著“輕微電擊”、“強電擊”、“危險:高強電擊”等等。在435-和450-伏的開關上有“×××”字樣。研究者告訴教師,學習者每答錯一次,“就在電擊發生器上提高一個檔次實施電擊”。每次只要輕按開關,燈光就會閃爍,繼電器開關隨之“咔嗒”一聲響,電流就嗡嗡地響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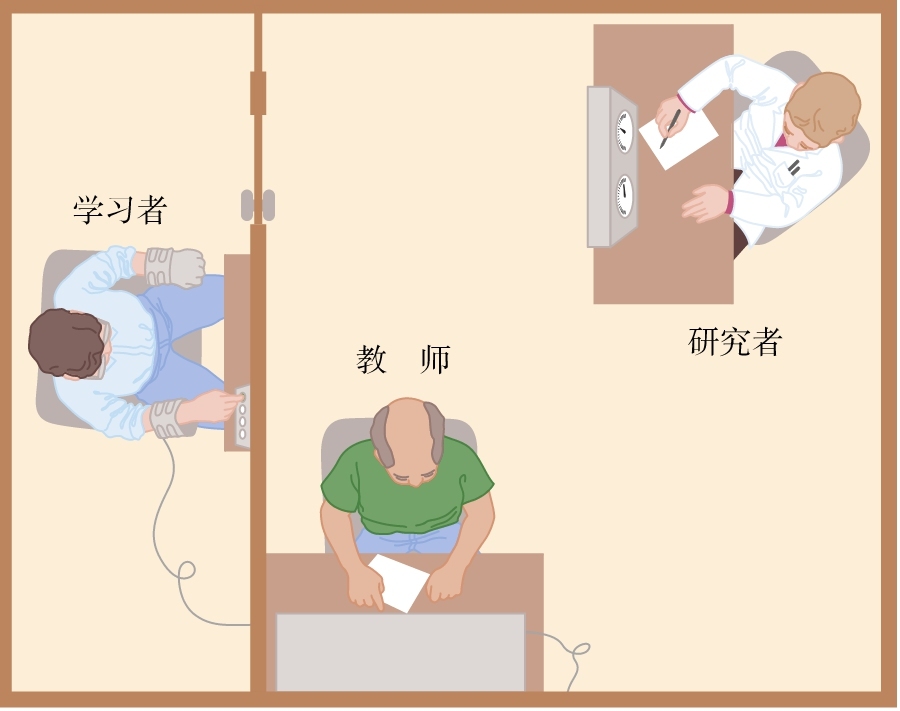
圖6-3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
資料來源:Milgram,1974.
如果實驗者服從研究者的要求,那麼,他會在75、90和105伏時聽到學習者的哼哼聲。在120伏時學習者大喊電擊太疼了。在150伏時他咆哮著,“實驗者,把我從這裡弄出去!我不再參加這個實驗了!我拒絕繼續做下去!”在270伏時學習者的抗議聲成了痛苦的尖叫聲,並堅持要出去。在300和315伏處,他尖叫著拒絕回答。330伏後他再也沒有聲音了(見表6-1)。研究者在回答“教師”的詢問和停止實驗的請求時說,學習者不回答就算回答錯誤。為了使實驗者繼續下去,研究者採用了四種口頭鼓勵:
鼓勵1:請繼續下去(或請繼續)。
鼓勵2:該實驗要求你繼續進行下去。
鼓勵3:你繼續進行下去是絕對必須的。
鼓勵4:你沒有其他選擇,必須進行下去。
表6-1 米爾格拉姆令人“緊張不安”的實驗中學習者的抗議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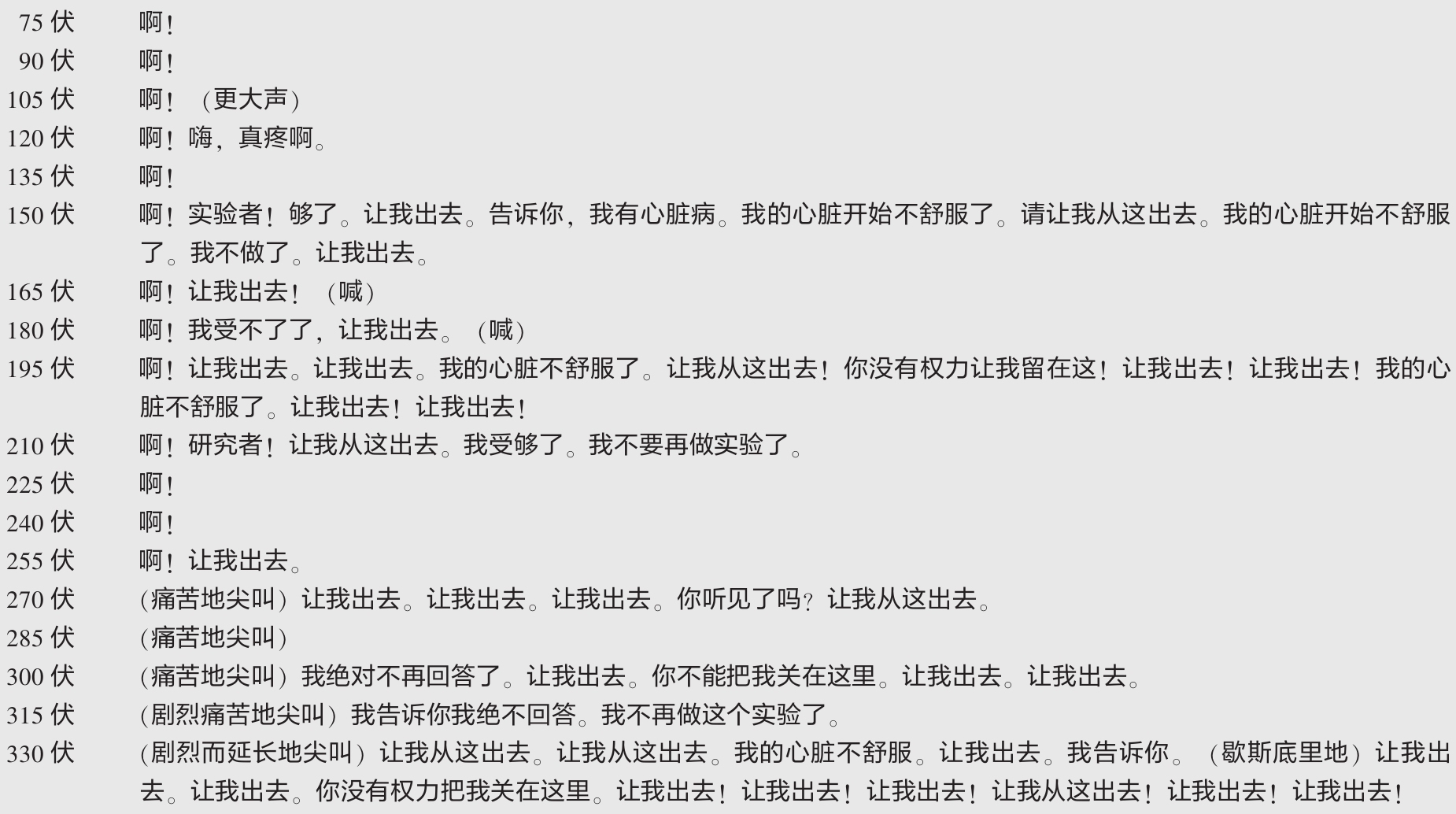
資料來源:Fro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by Stanley Milgram. New York:Harper & Row,1974,pp.56~57.
你會進行到什麼程度?米爾格拉姆對110個精神病學家、大學生、中產階層成人描述了這個實驗。這三個群體的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在135伏處會不服從命令;沒人想進行到300伏以上。考慮到自我估計可能反映其自我服務偏見,米爾格拉姆要求他們估計其他人 會進行到什麼程度。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期望他人使用電擊發生器中的×××處開關(精神病學家估計大約1000人中會有1人這樣做)。
然而,當米爾格拉姆用40個被試——不同職業,20~50歲的人——做這個實驗時,有26人(65%)一直進行到450伏。事實上,所有進行到450伏的人都服從了命令,繼續 接著又做了兩次進一步的測驗,直到實驗者喊停為止。
由於預期服從的比例較低,米爾格拉姆本計劃在德國重複這個實驗以評價文化差異,但實際的研究結果令他有點憂心忡忡(A. Milgram,2000)。米爾格拉姆不準備去德國了,而是讓學習者的抗議更加引人注目。當學習者被綁在椅子上時,教師聽他提醒說“有輕微的心臟不適”,並聽到研究者再次保證“儘管電擊可能很疼,但不會對器官造成永久性傷害。”結果發現學習者痛苦的抗議聲沒起多大作用;40個新被試中,有25人(63%)完全服從了研究者的要求(圖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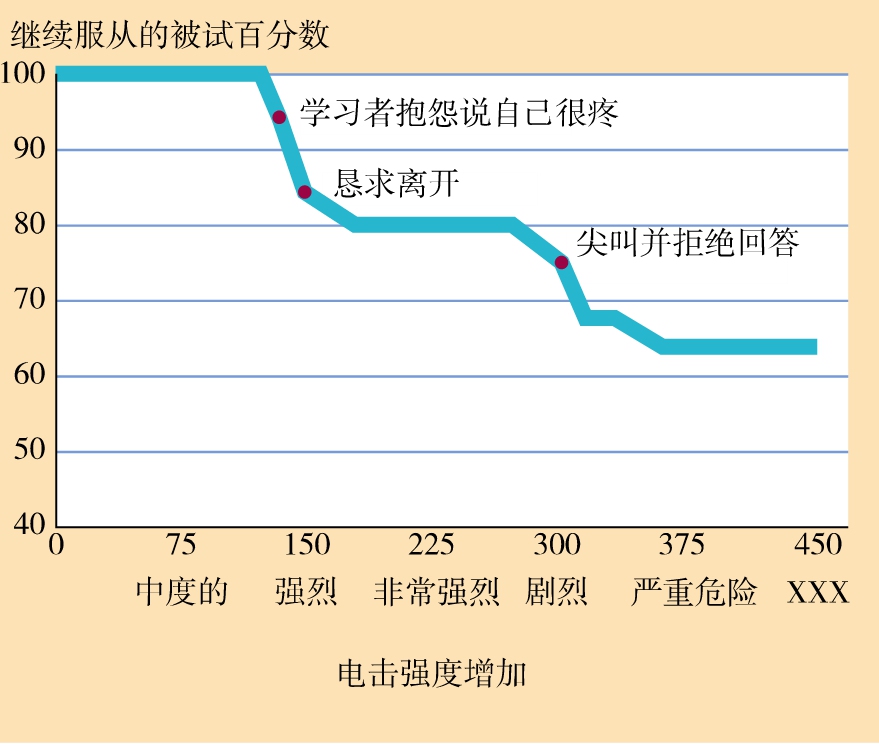
圖6-4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
服從被試的百分比,而不管學習者抗議性的哭喊和無法回答。
資料來源:From Milgram,1965.
米爾格拉姆實驗的道德倫理問題
被試的服從令米爾格拉姆憂心忡忡。他所用的程序也令許多社會心理學家驚心難安(Miller,1986)。在這些實驗中,“學習者”實際上沒有受到任何電擊(他離開了電椅,打開磁帶錄音機,播放抗議聲)。然而,有批評說,米爾格拉姆對被試所做的事,就是他們對受害者所做的事。他強迫他們違背自己的意願。實際上,許多“教師”確實體驗到了極度的痛苦感。他們流汗、顫抖、緊閉嘴、咬嘴脣、呻吟,甚至暴發出無法控制的神經質大笑。一位《紐約時代》評論員控訴說,“該實驗對毫不知情的被試所實施的殘忍,使他們只好去引發別人的痛苦,以此相抵”(Marcus,1974)。
批評家也認為,被試的自我概念會因此而改變。一位被試的妻子對他說,“你可以稱你自己為艾希曼了”(指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執行官阿道夫·艾希曼)。哥倫比業廣播公司的電視改編了一出兩個小時的戲劇,由出演《星際旅行》的著名演員威廉·沙特納(William Shatner)扮演米爾格拉姆,描述了該研究結果及其爭論。“罪惡的世界是如此恐怖,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敢於洞察其祕密!”為這個節目做廣告的《電視導報》如此評論(Elms,1995)。
在為自己進行辯護時,米爾格拉姆指出了由1000多個各種被試所做的20多個實驗獲得的經驗教訓。他也引用了支持自己的一些評論,這些評論是對實驗的解釋和揭露了騙局之後從被試那裡獲得的。隨後的調查發現,84%的被試說他們很高興參加了實驗;只有1%的人對做志願者表示遺憾。一年以後,精神病學家對痛苦體驗較強烈的40名被試作了訪談,得出結論說,不管暫時的應激如何,確實沒有人受到傷害。
倫理上的爭論是“極其過分”,米爾格拉姆認為:
從對自尊影響的角度上說,與大學生參加一門普通課程的考試,但沒有得到想要的學分相比,這個實驗對被試所造成的後果要小得多。……看來,在考試時,我們對緊張和自尊造成的結果已有相當的心理準備,而對於產生新知識的過程,我們卻沒有表現出一丁點寬容(Blass,1996)。
什麼因素引起了服從
米爾格拉姆不只是揭示出人們服從權威的程度,他也考察了服從產生的條件。在進一步的實驗裡,他變化各種社會條件,得到了從0~93%的服從率。結果發現有四個因素會影響服從,即受害者的情感距離、權威的接近性與合法性、權威的機構性和不服從的同伴參與者的釋放效應。
受害者的情感距離
米爾格拉姆的被試在無法看到“學習者”(“學習者”也無法看到他們)的情況下,其行動表現出的同情最少。當受害者距離遙遠,教師聽不到其抗議聲時,幾乎所有的服從者都能鎮靜地把實驗做完。相對於研究者的影響而言,這類情景把學習者的影響減小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我們使學習者的抗辯和研究者的命令一樣顯而易見的話會出現什麼情況呢?當學習者在同一房間時,那麼,“只有”40%的被試服從把實驗進行到450伏。當要求教師把學習者的手強制按在電擊板上時,那麼,完全服從的比例下降到30%。
聚焦 讓受害者人格化
如果對受害者進行人格化的話,無辜的受害者會博得更多的同情。在同一個星期內,奪去3000人生命的伊朗大地震很快被世人遺忘,而在意大利一個男孩掉進礦井裡死去,全世界都為之悲傷。一場核戰爭所統計的死亡人數是無法人格化的,所以也就很難被人理解。因此,國際法教授羅傑·費希爾(Roger Fisher)提出了一個對受害者人格化的方法:
如果這事發生在一位年輕人身上,通常是一位海軍軍官,他是總統的隨從,隨身帶著一隻裝有發射核武器必需密碼的黑色公文箱。
我可以想像總統在和幕僚討論一個非常抽象的核戰爭問題。他可能決定,“關於SIOP一號計劃,該決定是毫無疑問的了。接通阿爾法線XYZ。”這種術語能長距離傳遞,不用擔心洩密。
那麼我的建議很簡單。把所需密碼裝入一個膠囊裡,再把膠囊植入一位志願者的右胸裡。當他伴隨總統時,總是隨身帶著一把大而重的屠刀。如果總統想要發射核武器了,惟一的辦法,就是他要首先親手殺死這個人。
“喬治,”總統會說,“我很抱歉,但成千上萬的人真的該死。”然後總統不得不看著這個人,意識到什麼是死亡——一個無辜者 的死亡。血流在白宮的地毯上:這個現實會使他清醒過來。
當我把這個建議講給五角大樓的朋友聽時,他們說,“天啊,那麼可怕。必須殺死一個人,這會糾正總統的決斷。他可能永遠都不會摁按鈕了。”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Preventing Nuclear War”by Roger Fisher,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 1981,pp.11-17.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如此,我們很容易貶低遠離自己的人或失去個性的人。甚至對於巨大的災難,人們也無動於衷。劊子手常常用布矇住受刑者的頭,使其失去個性。戰爭法允許從40000英尺高的地方對手無寸鐵的村民投擲炸彈,但不允許對他們開槍射擊。在與敵人進行近距離肉搏時,許多士兵既不開火,也不瞄準。這種不服從行為,對於那些接到命令後以遠距離火炮或飛機進行殺戮的人來說是很罕見的(Padgett,1989)。[想像一下你有能力阻止會令另一半球25000個人喪命的潮水,或有能力阻止本地機場會令250人喪生的事故,或有能力阻止會令一位密友死亡的車禍。你會阻止哪一個呢? ]
從積極一面講,人們對於個性化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這就是在替未出生的、飢餓的人或動物權力進行呼籲時,為什麼人們總是用令人感動的照片或描述來賦予其個性化。也許最令人感動的是正在發育的胎兒的超聲波圖像。約翰·萊登和克里斯蒂娜·鄧克爾-謝特(John Lydon & Christine Dunkel-Schetter,1994)曾問過準媽媽並發現,當她們看到自己胎兒的部分身體被超聲波圖像清楚地顯示出來時,她們對懷孕表達了更強烈的承諾。
權威的接近性與合法性
研究者的親自在場也會影響服從。當米爾格拉姆通過電話下達命令時,整個服從比例下降到了21%(雖然許多人撒謊並且說自己正在服從)。其他研究也證實,要求命令的發出者在空間距離上的接近性會增加服從率。輕微碰觸一下手臂,會使人更願意捐一個硬幣,在請願書上簽名,或品嚐新的比薩餅(Kleinke,1977;Smith & others,1982;Willis & Hamm,1980)。
但是,權威必須被認為是合法的。在米爾格拉姆式實驗的另一變式中,研究者假裝要去接一個電話,該電話要求他不得不離開實驗室。他說,因為儀器是自動記錄數據的,所以“教師”可以繼續做實驗。研究者離開後,另一個人代替研究者(實際上是研究者的另一個同謀者)來發布命令。該職員“命令”,每一錯誤回答就增加一檔電擊,並且他還相應地指導教師。現在,有80%的教師完全拒絕服從。同謀者裝作厭惡這種不滿,在電擊發射器前坐了下來,試圖代替教師實施電擊。這時,極大多數不滿的被試發出了抗議。一些人還試圖拔下發生器的插頭。一個高大的男子把同謀者從椅子里拉了出來,把他推出房間。這種對不合法權威的反叛,與之前在研究者面前常常表現出來的恭敬和禮貌的被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從下述研究中護士的行為表現,我們也可以證實這一點。在這個研究中,護士被一名不認識的醫生叫去,要求她執行一個非常明顯的藥物過量的任務(Hoffling & others,1966)。研究者把這個實驗講給一群護士和學護理的學生聽,問她們會如何反應。幾乎所有人都說自己不會服從命令。其中一人說她會這樣回答:“我很抱歉,先生,在沒有處方的情況下我不會聽從權威給病人服任何藥,尤其是過量的藥品和我不熟悉的藥品。當然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會很願意去做,但是這不但違反醫院的政策,也違揹我的道德標準。”然而,當22名護士在接到給病人過量服藥的電話命令後,只有一人除外,其餘的護士毫不猶豫地服從了(直至在去病人的路上被攔截為止)。雖然並非所有護士都如此順從(Krackow & Blass,1995;Rank & Jacobson,1977),但是,這些護士都執行著一個熟悉的腳本:醫生(一個合法的權威)命令,護士服從。
在一個很奇怪的稱之為“直腸耳朵疼”的案例中,我們可明顯看到個體對合法權威的服從(Cohen & Davis,1981)。醫生命令對右耳感染的病人往耳朵裡滴藥。在處方上,醫生把“滴入右耳”寫成了“滴入直腸耳朵”。看了醫生的處方後,順從的護士把所要求的藥滴入了順從病人的直腸裡。
權威的機構性
如果權威的聲望很重要,那麼,耶魯大學的機構聲望也令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命令變得合法化了。在實驗後的訪談中,參與者說,如果不是耶魯大學的名聲,他們堅決不會服從。為了考察一下真實情況,米爾格拉姆把實驗移到康涅狄格的布里奇波特。他在一座並不豪華的商務大樓裡成立了“布里奇波特研究會”。然後由同樣的操作人員來實施那令人“憂心忡忡”的實驗,你猜完全服從的比例是多少?雖然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驚人——48%。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如此,有機構作背景的權威易發揮社會權力。羅伯特·奧恩斯坦(Robert Ornstein,1991)講述了一件事,他的朋友是精神病學家,被叫到加利福尼亞的聖·馬蒂奧山的懸崖邊。因為他的一個病人艾爾弗雷德威脅要跳崖,精神病學家的苦口婆心仍無法使艾爾弗雷德離開,無奈之中,他只能期望警察中的危機干預專家能快點到達。
儘管專家沒有到來,但另一名完全不知情的警察恰巧來到現場,拿出他的手提式擴音喇叭,對聚集在懸崖邊的人群大叫:“哪個笨蛋把貨車並排停在另一輛車旁邊的馬路中間?我差點撞上。不管你是誰,現在就把它開走 。”聽到這些,艾爾弗雷德馬上乖乖地走下來,把車開走,然後一聲不吭地鑽進警車去了附近的醫院。
群體影響的釋放效應
這些經典實驗使我們形成了從眾具有消極性的觀點。但是,從眾也可以是積極有效的。也許你會回憶起,當你面對不公正的教師,完全有理由指責他時,你還是猶豫了。後來同學們接二連三地紛紛指出不公平的事實後,你也跟著他們一起指責起來,這就是釋放效應。米爾格拉姆也觀察到了這種從眾的釋放效應。他讓教師和兩個同謀者在一起,同謀者是來幫助完成這個實驗的。在實驗中,兩個同謀者都公然反抗研究者,研究者命令那個真正的被試一個人繼續下去。被試會嗎?不會。通過模仿反抗的同謀者,90%的被試釋放了自己。
研究背後的故事: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
當為所羅門·阿施工作時,我想,他的從眾實驗是否可以設計得對人類更有意義一些呢。首先,我設想實驗應類似於阿施的實驗設計,但有一點不同,即群體誘發個體對抗議的受害者實施電擊。但是這還需要一個控制組,以說明在缺乏群體壓力下,個體會實施多大的電擊。某個人,假如說是研究者,命令被試實施電擊。但是這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如果發出命令以後,那麼他會走多遠?在我腦海裡,這個問題成為人們順從破壞性命令的意願。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我意識到,這個簡單的問題既對人類非常重要,又很容易獲得準確答案。
實驗室程序,對權威的普遍關注,對我們這一代人的關注,特別是對像我這樣經歷二戰暴行的猶太人的關注,做出了一個科學的解釋。大屠殺對我心靈的影響,激發了我對服從及其特定變式的濃厚興趣。
資料來源:Abridged from the original for this book and from Milgram,1977,with permission of Alexandra Milgram.
對經典研究的反思
對米爾格拉姆研究結果的普遍反應是大家意識到這與近代世界史有異曲同工之處:納粹德國的阿道夫·艾希曼辯解說,“我只是執行了命令而已”;威廉·卡利中校在1968年指揮了一場大屠殺,在越南米萊村殺死了數以百計的無辜平民後也是這樣辯解;發生在伊拉克、盧旺達、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種族大屠殺”也都這樣辯解。
訓練士兵服從上級。米萊大屠殺中的一位參與者回憶道:
[上校卡利]命令我開始射擊。所以我就開始射擊。我向人群發射了四個彈夾的子彈……他們乞求著,“不要,不要。”母親緊緊護著孩子,……我們一直不停地射擊。他們揮動著手,乞求著(Wallace,1969)。
服從實驗中“安全”的科學研究環境,畢竟不同於戰爭環境。更有甚者,戰爭期間的大部分惡行和殘暴遠遠超出了服從(Miller,2004)。服從實驗就社會壓力的強度而言也與其他從眾實驗不同;服從中命令非常明確。沒有強迫,人們不會殘忍地行動。但是,阿施和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也有共同之處。他們都揭示出服從如何先於道德發生。就強制人們違背自己的意願而言,他們都成功了。他們不僅僅是在探討學術課題,而且在提醒我們注意自己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衝突。他們揭示了,也證實了,某些熟悉的社會心理學原理:行為與態度之間的關係,情境的力量,以及基本歸因錯誤的強度。[美國軍隊訓練士兵拒絕服從不恰當的、不合法的命令 。]
行為和態度
第4章我們講到,當外界的影響作用超過了內在的信仰時,態度便無法決定行為。這些實驗也生動地證實了這一點。當一個人單獨行動時,個體幾乎總能做出正確的反應。而個體單獨反對群體就是另一碼事了。
在服從實驗中,強有力的社會壓力(研究者的命令)超越了力量較弱的因素(遠距離受害者的抗爭)。在受害者的抗爭和研究者的命令之間的權衡中,在希望避免造成傷害和希望成為一個好被試的思想鬥爭中,極大多數人選擇了服從。
為什麼參與者無法擺脫自己?他們如何陷入圈套的?想像一下你作為教師參加米爾格拉姆實驗的另一個版本,一個他從來沒做過的實驗。假定當學習者第一次做出一個錯誤的回答後,研究者要求你摁330伏的按鈕快速電擊他。在摁了按鈕後,你聽到學習者發出的痛苦尖叫聲,訴說自己心臟不好,乞求憐憫。你會繼續做下去嗎?
我想不會。回憶一下登門檻現象(第4章)中人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墮入陷阱的,並將這個假設的實驗與米爾格拉姆的被試所經歷的事件作一比較。他們最初的承諾是輕微的——15伏——並沒有出現抗議。你也會同意繼續做下去。當電擊達到75伏,並聽到學習者第一次呻吟聲時,他們已經順從五次了。而接下來的一次,研究者只要求被試承諾比早先略微極端一點的行動而已。在他們進行到330伏電擊時,這已經是第22次服從的行動了,被試早已降低了不協調感。此時,他們的心態與實驗開始時的心態完全不同。正如我們在第4章所看到的那樣,外在的行為和內在的心理傾向可以彼此影響互相促進,有時還是螺旋型上升的。正如米爾格拉姆所報告的(1974,p.10):
許多被試嚴重地貶低受害者,就是為了反對他。像這些評論,“他如此得愚蠢和固執,應該受到電擊”,是十分常見的。一旦做出了針對受害者的行為,被試必然會把他看成是沒有價值的個體,這種懲罰不可避免地是他自己智力或性格的缺陷導致的。
20世紀70年代初,希臘的軍政府就是利用這種“譴責受害者”的過程來訓練拷問官(Haritos-Fatouros,1988,2002;Staub,1989,2003)。正如納粹德國早期訓練黨衛軍官一樣,軍隊選擇候選人是基於其對權威的尊重和順從。但是,單有這些傾向還不能造就一個拷問官。於是,他們就委派受訓者去看守囚犯,接著,參加搜捕隊,然後,毆打囚犯,再接下去,觀看整個拷問過程,最後親自動手拷問。就這樣一步一步,一個服從的但其他方面仍正常的個體,逐漸發展成一個殘暴的君王。順從滋生了接納。
作為大屠殺的倖存者,麻薩諸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歐文·斯托布(Ervin Staub)非常瞭解這種把公民轉變為劊子手的力量。根據對世界各地種族滅絕的研究,斯托布(2003)展示了這個過程是如何發展的。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批評會產生輕視,輕視會引發殘暴,而當殘暴被認為是合理行為時就會導致獸行,接著便是殺戳,然後是大規模的殺戳。所形成的態度緊隨著行動,又為行動辯護。據此,斯托布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結論:“人類有一種潛能,那就是把屠殺他人不當一回事”(1989,p.13)。
但是,人類也有另一種潛能,這就是英雄主義。在納粹大屠殺期間,將要被放逐到德國的3500個法國猶太人和1500個其他難民被勒尚朋的村民所蔽護。這些村民絕大多數是新教徒,是受迫害一代的後人,其權威人物、牧師教導他們“無論何時,如果敵人要求我們服從有違福音書上的命令,我們都要反抗”(Rochat,1993;Rochat & Modigliani,1995)。接到要報告所掩護的猶太人的命令後,本堂首席牧師樹立了不服從的榜樣:“我不知道什麼猶太人,我只知道人類。”不管戰爭有多可怕,也不管自己會因此而遭受多大的災難,他們一直堅持最初的承諾,在信仰的支持下,在權威的支持下,在互相支持下,一直對抗到戰爭結束。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對納粹統治的最終反應通常在早期就已出現。開始做出順從或抵抗的行動,這就會形成一種態度,而態度隨後又會影響行為,行為又反過來加強了態度。最初的幫助強化了承諾,而承諾導致了更多的助人行為。
情境的力量
第5章所講的最重要的一點——文化是生命最有力的塑造者——以及本章最重要的一點——即時的環境力量也同樣強有力——都證明了社會背景的影響力。要想親自體會這一點,請想像一下你正在做出一些違反細小規範的行為:在一節課的中間起立;在餐館裡大聲唱歌;穿一套西服打高爾夫球。在試圖打破社會束縛時,我們才突然意識到它們是多麼強有力。
當米爾格拉姆和約翰·薩比尼(John Sabini,1983)要求學生幫助他們研究觸犯了簡單的社會規範後會出現什麼後果時,這些學生意識到了上述這一點。這個簡單的社會規範就是:要求乘坐紐約地鐵的乘客讓座。使他們感到十分驚訝的是,56%的人讓了座,即使沒有正當理由時也如此。而學生自己提出要求的情形也同樣很有趣,絕大部分學生髮現要這樣做真的很難。通常,他們欲言又止,那一刻自己有想逃的衝動。一旦說出了請求,得到座位後,他們時常假裝生病,以此作為觸犯規範的藉口。這就是沒有明文規定的規則的影響力,它指導著公眾行為。
在最近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實驗中,學生同樣發現很難把挑戰性的話語說出口。讓這些學生想像自己正與其他三個人討論挑選誰到荒島去生活。主試要求他們想像另外兩個人中的一個,一位男生,插入三句與性有關的評論,例如,“我想島上需要有更多的女人,以便使男人更滿意。”他們對這種性評論的反應會怎樣呢?只有5%的人預測自己會忽略每一句評論,或者等待看看其他人會如何反應。但是,在珍妮特·斯溫和勞裡·海爾斯(Janet Swim & Lauri Hyers,1999)研究中,讓一個男性同謀者說出這些評論,然後讓學生進行討論,結果55%(而不是5%)的人啞口無言。這個研究再一次證實了社會規範所具有的壓力,以及要預測行為,即使是我們自己的行為,也非常困難。
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也提供了有關邪惡的訓誡。邪惡有時由少數壞傢伙所為。那些是在懸念疊起的小說和恐怖電影裡由墮落的殺手扮演的形象。在現實生活裡,讓我們思考一下,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薩達姆·侯賽因對庫爾德人的趕盡殺絕,奧薩瑪·本·拉登所密謀的恐怖事件。但是,邪惡有時也會來自於社會力量——來自於高溫、潮溼和疾病,它們可能使整筐蘋果變壞。正如實驗所表明的,情境有時會誘使普通人贊同謬誤或向殘忍屈服。
就像在複雜的人類社會中常常發生的那樣,當最可怕的邪惡從小小的邪惡發展而來時,這一點顯得尤其正確。“確實,”約翰·達利(John Darley,1996)說,
“很難辨認那些犯過邪惡罪行的人;傷害[正如福特公司有意推銷油箱有毛病的斑馬車]可能是有組織的結果,而做出邪惡罪行的人是沒有明顯標記的。……當查明罪行背後的真相時,人們往往發現,並不是一個邪惡者明目張膽地在實施惡魔式的計劃,相反,卻是普通人在從事邪惡活動,因為他們已被複雜的社會力量俘虜了。
德國公務員願意處理有關大屠殺的公文,這使納粹領導非常驚訝。當然,他們並沒有屠殺猶太人;他們只是在做文書工作(Silver & Geller,1978)。當分散工作,大家各司其職時,邪惡似乎更易進行。米爾格拉姆對邪惡的分隔作用進行了研究,他讓另外40個人以間接方式參與實驗。他們只負責學習測驗,而其他人實施電擊。結果發現40人裡有37個人完全服從了。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是這樣:對邪惡的聽之任之常常會使之日積月累,儘管自己並不是有意識地去做惡。拖延同樣是對自我傷害的無意識的放任(Sabini & Silver,1982)。一位學生知道就要交期末論文了。可他每次做論文時都分散注意力——一會兒是視頻遊戲,一會兒是電視節目——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危害。但是,漸漸地,這個學生根本就無法完成論文了,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已經決定不做該論文了。
基本歸因錯誤
為什麼這些經典實驗的結果那麼令人吃驚呢?是因為我們總是期望人們按照他們的內在心理傾向行動嗎?如果我們期望一個乖戾的人很骯髒下流,一個具有愉快性格的人很仁慈,那麼對此我們並不感到驚訝。壞人做壞事,好人做好事嘛。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聽到,“愚蠢的”9·11事件是“瘋子”、“邪惡的懦夫”、“惡魔”一樣的人乾的。
當你清楚了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後,對於服從的被試,你對其會形成什麼印象?如果要談論這些服從被試中的一兩個人,絕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是攻擊性的、冷酷無情、無動於衷的——甚至在瞭解到他們的行為是典型的代表之後(Miller & others,1973)。我們認為,內心的殘忍會導致殘忍的行動。
岡特·比爾鮑姆(Gunter Bierbrauer,1979)試圖消除人們對社會力量的低估(基本歸因錯誤)。他生動地再現了米爾格拉姆這個實驗,並讓大學生觀看,或者讓他們親自扮演服從的教師角色。結果被試仍然預測,在重複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時,他們的朋友的服從程度最低。於是,比爾鮑姆得出結論說,雖然社會學家積累了大量證據,證實我們的行為是社會歷史和當前環境的產物,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認為,人們的內在品質依然會頑強地表現出來——好人做好事,壞人做壞事。
人們可能認為,艾希曼和奧斯威率死亡集中營的軍官都是缺乏文明的惡棍。但是,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後,這些軍官會欣賞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樂來放鬆自己。參加1942年1月萬西會議(Wannsee Conference)和制定納粹大屠殺的最後解決方案的14個人中,有8個獲得歐洲大學的博士學位(Patterson,1996)。像絕大多數納粹分子一樣,艾希曼從表面上看來跟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沒什麼兩樣(Arendt,1963;Zillmer & others,1995)。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9.11恐怖事件的主謀,有報告說他曾是一個“好孩子”,是良好家庭出身的優秀學生。札卡里斯·穆索伊(Zacarias Moussaoui),9.11事件中的第20個嫌疑犯,在申請學習飛行課程和購刀時,十分有禮貌。他稱呼婦女為“女士”。如果這樣的人住在我們隔壁,這似乎與我們對有關惡魔的形象根本不相符。
或者認為德國的警察營應該為在波蘭射殺近40000名猶太人負責,他們中的許多婦女、孩子和老人是從背後被射殺的,腦被射穿,腦漿迸裂。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1992)描述了這些殺手“正常”的一面。就像蹂躪歐洲猶太人區、駕駛放逐犯人的火車、管理死亡集中營的許多人一樣,他們不是納粹黨徒,不是黨衛軍成員,也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是體力勞動者、售貨員、職員和工匠——有家庭的、退伍的老年人,但是,當接到殺人命令時,他們並沒有拒絕。
米爾格拉姆的結論,也同樣使我們難以把納粹大屠殺歸因於德國人獨特的人格特質。“我們研究的最基本的結論是”,他說道,“普通人,只是做自己的本職工作,心中並沒有任何仇恨,也可以成為可怕的破壞性活動的執行者”(Milgram,1974,p.6)。正如米斯特·羅傑斯(Mister Rogers)常常提醒觀看電視節目的兒童觀眾,“好人有時也做壞事。”如此說來,那麼我們應該謹防那些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領導人哄騙我們,讓我們認為他們決不會做壞事。在邪惡力量的支配下,善良的人們有時也會墮落,他們會對不道德的行為進行合理化的歸因(Tsang,2002)。所以,正是這些普通的士兵最終會遵照命令槍殺手無寸鐵的百姓,普通僱員會遵從指示生產和配送殘次產品,普通的小組成員也會按照指令殘忍地折磨新成員。
表6-2 對經典服從研究的總結
研究課題 |
研究者 |
方法 |
現實生活範例 |
規範形成 |
謝里夫 |
根據光點似動現象評價暗示性 |
聽到別人的觀點後改變了對事物的評價;欣賞別人喜愛的美味佳餚 |
從眾 |
阿施 |
贊成他人非常明顯的錯誤知覺判斷 |
別人做什麼你就做什麼,隨大流,如紋身 |
服從 |
米爾格拉姆 |
服從命令電擊他人 |
士兵或僱員執行不正確的命令 |
最後,我們要對從眾研究中所使用的實驗方法作一評論(參見表6-2的介紹):在實驗室中的從眾情景與日常生活明顯不同。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是不是經常判斷線段的長度或對他人實施電擊?點燃一根火柴與燃起森林大火,其燃燒過程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假定,實驗室中的心理過程與日常生活中的心理過程也是一樣的(Milgram,1974)。從點燃一根火柴的簡單事件,概括到複雜的森林大火,我們必須非常謹慎。但是,關於點燃火柴的可控性實驗能夠使我們看透燃燒的本質,而這種本質是觀察森林大火所無法獲得的。由此可見,社會心理學實驗能為我們的行為研究提供啟示,而這種啟示在日常生活中難以獲得。實驗情境是獨特的,每一個社會情境也是獨特的。通過考察各種各樣的獨特任務,通過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重複實驗,研究者逐漸探索出深埋於表面現象之下的共同原理。
小結
從眾——由於群體壓力而引起的個體行為或信念的改變——有兩種主要的表現形式。順從是表面上與群體相一致而內心並不贊同。接納是不僅在行動上而且也在信念上與社會壓力保持一致。
三組經典實驗展示了研究者如何研究從眾的。謝里夫觀察到,他人的判斷會影響人們對光點移動距離的錯覺估計。就這樣形成了“正確”答案的規範,並且該規範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並在一批一批的研究參與者中流傳下來。這種實驗室暗示類似於現實生活中的暗示。
所羅門·阿施設計的實驗任務非常清晰,不像謝里夫採用的是模糊任務。阿施先讓實驗者聽到其他人做出三條線段中哪一條與標準線段相等的判斷,然後自己做出判斷。當其他人一致地給出一個錯誤的答案後,結果發現有37%的實驗者會從眾。
謝里夫的程序引發了接納;另一方面,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引發了順從的極端表現形式——服從。在最理想的條件下——合法、近距離的命令者、遙遠的受害者以及沒有一個不服從的榜樣——65%的成年男性參與者完全服從命令,對隔壁發出尖叫的、無辜受害者實施具有傷害性的電擊。
這些經典的實驗揭示了社會力量的潛能和順從導致接納的容易程度。罪惡不只是美好世界中壞人的行為,而且也可能是強有力的情境誘使人們對謬誤的從眾或向殘忍屈服投降的結果。
經典的從眾實驗解答了一些問題,但也提出了另一些問題:(1)人們有時從眾,有時不從眾,那麼他們什麼時候會從眾?(2)為什麼人們會從眾?為什麼他們不忽視群體“做真實的自己”呢?(3)是否有一種人特別容易從眾?接下來讓我們依次來探討這些問題。
什麼因素可以預測從眾
有些情境可以引發較多的從眾行為,而有些情境引發的從眾行為較少。如果你想要引發最大程度的從眾效應,你會選擇什麼條件呢?
社會心理學家想知道,如果阿施的非強制性、清晰的情境能引發37%的從眾比率,那麼,其他的情境是否會產生更多的從眾行為呢?研究者立即發現,如果任務判斷非常困難,或者,參與者感到無力勝任,那麼,從眾比率會大大增加。我們對自己的判斷感越不確定,我們就越容易受他人影響。
群體的特徵也很重要。如果群體由3個或更多個體組成、凝聚力高、意見一致和地位較高的話,那麼從眾的程度最高。如果是在公眾場合做出行為反應,並且事先沒有任何承諾,那麼從眾的比率也很高。讓我們考察一下上述每一個條件。
群體規模
在實驗室實驗裡,一個規模較小的群體就可以引起較大的效應。阿施和其他研究者發現,3至5個人比只有1個或2個人能引發更多的從眾行為。當人數增加到5個人以上時,從眾行為會逐漸減少(Gerard & others,1968;Rosengerg,1961)。在現場研究中,米爾格拉姆及其同事(1969)讓1、2、3、5、10或15個人停留在紐約市繁忙的人行道上,並抬頭觀望。如圖6-5所示,過路人也抬頭觀望的比率在從1人增加到5人時也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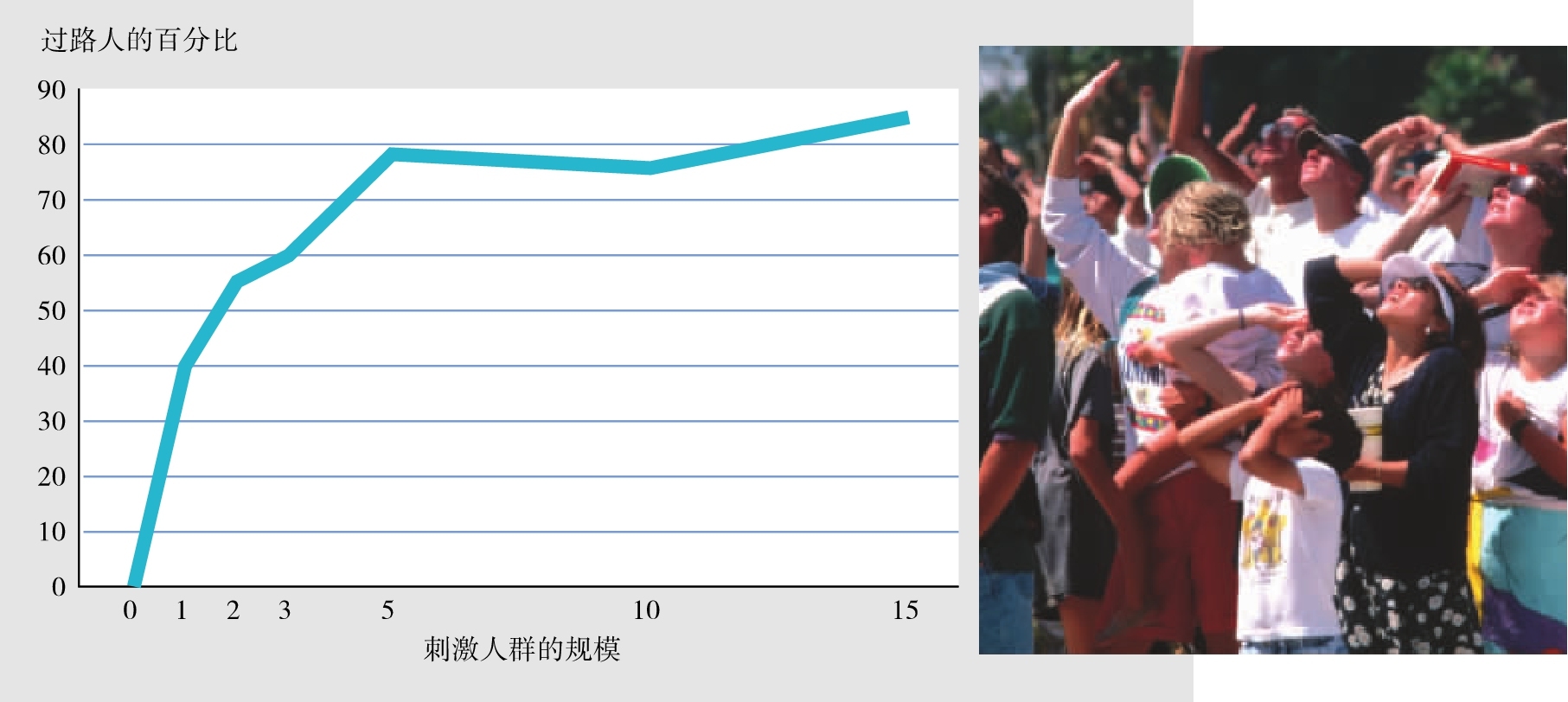
圖6-5 群體規模與從眾
過路人模仿一個群體抬頭觀望的百分比隨著群體規模逐漸增加到5個人而增加。
資料來源:Data from Milgram,Bickman,& Berkowitz,1969。
群體“抱成團”的方式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Rutgers大學的研究者戴維·懷爾德(David Wilder,1977)給學生一個有陪審團參加的案子。在講出他們自己的判斷前,先讓學生觀看由4個同謀者做出判斷的錄像。當同謀者是以兩個兩人組單獨出現時,參與者從眾的比率要比同謀者是以一個四人組出現時的比率高。同樣,兩個三人組引發的從眾比率要比一個六人組所引發的從眾比率高。三個兩人組引發的從眾比率更高。很顯然,多個小群體的一致意見會使某個觀點更可信。
一致性
想像一下你自己正參加一個從眾實驗,所有的人都給出同一個錯誤答案,但除了在你前面的那個人。這樣一個非從眾的同謀者作為榜樣,他會像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中的個體那樣起到一種釋放效應嗎?一系列實驗揭示出,如果有人破壞了群體一致性,那麼會降低群體的社會影響力(Allen & Levine,1969;Asch,1955;Morris & Miller,1975)。正如圖6-6所示,如果剛巧有一個人說出了自己的心聲,那人們幾乎總會做出同樣的行為。參加這些實驗的被試事後常常說,對於他們不從眾的同伴,他們感到一種溫暖、親近的感覺。但是,他們同時又否認同伴對自己的影響作用:“如果他不這樣做,我也會說出同樣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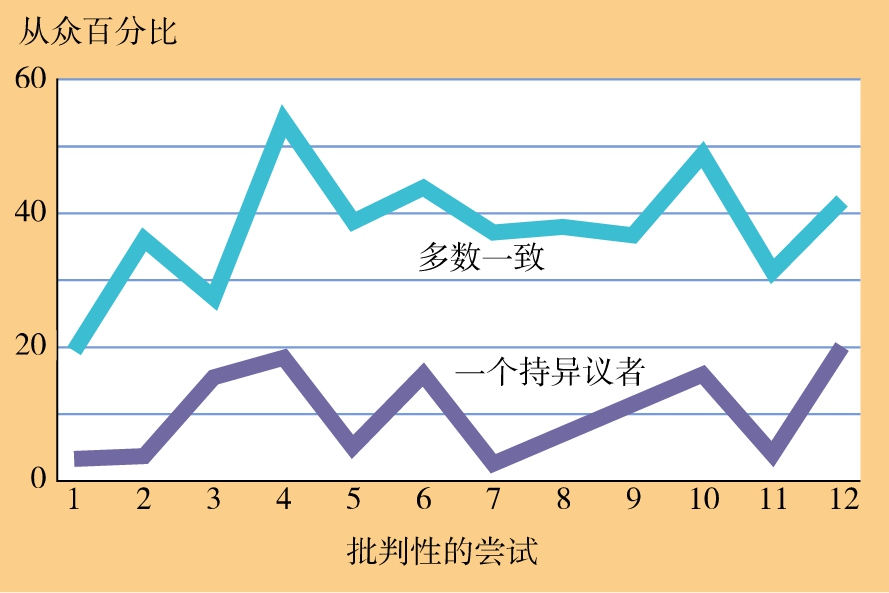
圖6-6 一致性對從眾的影響
當有人做出正確回答破壞了群體的一致性時,個體的從眾行為只有通常的四分之一。
資料來源:from Asch,1955.
成為某一個群體的少數成員是很難受的;有好幾個陪審團被閒擱起來,就因為其中一個人持有異議。這些實驗給我們上了一堂實踐課,即如果你能找到某個人和你立場一致的話,那麼你為某件事站出來就容易得多。許多宗教團體也都意識到了這一點。耶穌派遣門徒時是成對的,效仿耶穌的榜樣,摩門教也成對地派遣傳教士到鄰國去,同伴的支持極大地增強了一個人闖蕩社會的勇氣。
觀察到其他人持有異議——即使這種異議是錯誤的——會增強我們自己的獨立性。內梅斯和辛西婭·奇利斯(Charlan Nemeth & Cynthia Chiles,1988)發現了這一點。他們讓人們觀察四人小組中的一個人錯誤地把藍色判斷為綠色。儘管持異議者是錯誤的,但卻能鼓勵觀察者表現自己的獨特性——在76%的次數裡,他們正確地把紅色幻燈片判斷為“紅”,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說是“橙”色。而在缺乏有勇氣的榜樣人物鼓勵的其他觀察者中,其從眾的次數達70%。
凝聚力
我們認為群體之外的人——另一個大學裡的人或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提出的少數派觀點,對我們的影響要小於我們自己群體內的少數派觀點對我們的影響(Clark & Maass,1988)。異性戀者為同性戀者的權利呼籲,與對同性戀者的影響相比,其對異性戀者的影響更有效。那些聲稱與自己生日相同、名字相同或指紋特徵相同的人提出要求後,人們似乎更願意順從。
一個群體的凝聚力 (cohesive)越強,對成員的影響力就越大。例如,在大學的女生社團裡,朋友們有在一起狂飲作樂的傾向,特別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Crandall,1988)。在一個種族群體裡,人們會感到一種共同的“歸屬群體的從眾壓力”——講話、行動、穿著都應該像“我們”。像“白人那樣行動”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樣行動”的白人,都會遭到同伴的嘲笑(Contrada & others,2000)。
在實驗中人們也發現,那些感到自己受群體吸引的成員更可能對群體影響做出反應(Berkowitz,1954;Lott & Lott,1961;Sakurai,1975)。他們並不喜歡與其他成員唱反調。害怕被他們喜歡的人所拒絕,他們允許群體中的某些成員擁有一定的權力,特別那些能代表群體特徵的人(Hogg,2001)。17世紀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人類理解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提到凝聚力這個因素:“一萬個人中也難找到一個人,他能在自己的團體里長期忍受厭惡和譴責而麻木不仁、無動於衷。”
地位
正如你所猜測的那樣,地位高的人往往有更大的影響力(Driskell & Mullen,1990)。有時,人們會想方設法避免與地位低的或受別人嘲笑的人的意見相一致。珍妮特·斯溫等人(Janet Swim,Melissa Ferguson,& Lauri Hyers,1999)讓異性戀女學生做阿施從眾實驗的被試,並作為第五位和最後一位被試回答,結果得出了上述結論。提問所有被試,“你是否願意與一位異性度過一個浪漫的夜晚?”第四個人有時這樣回答,“我不願意與一位男子度過一個浪漫的夜晚,因為我是一個女同性戀者。”當挑明身份後,如果提問真正的被試是否認為對女性的歧視是一種社會問題,被試往往回避做出回答。
在24000個過路行人無意識地參與幫助下,對亂穿馬路行為的研究顯示,亂穿馬路的基線比率為25%,當遵守交通規則過馬路的同謀者出現時,行人亂穿馬路的比率下降到了17%,而當另一個亂穿馬路者出現時,該比率一下子上升到了44%(Mullen & others,1990)。如果不亂穿馬路的人衣著整齊高雅,那麼這對亂穿馬路的人起的示範作用最佳。在澳大利亞,服飾也能“塑造人”。邁克爾·沃克等人(Michael Walker,Susan Harriman,& Stuart Costello,1980)發現,悉尼的行人更容易服從衣著整齊高雅的調查者而不是穿著破爛的調查者。
米爾格拉姆(1974)報告說,在他的服從實驗中,地位低的人比地位高的人更願意服從研究者的命令。在實施了450伏電擊以後,一位37歲焊工轉向研究者,恭敬地問,“教授,現在我們還去哪裡?”(p.46)。另一個參與者,一個神學院的教授,在150伏時就開始不服從了,說“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實驗要建立在一個人的生命之上”,並且不斷地質問研究者關於“這件事的道德”問題(p.48)。
公開的反應
研究者想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人們在公眾場合中要比在私底下更可能從眾嗎?還是他們在私底下更可能猶豫不決而在公開場合上更不願從眾,免得自己看上去軟弱膽小?答案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在實驗中,人們必須面對他人做反應時要比私下裡回答問題會表現出更多的從眾行為。阿施實驗中的被試在看到其他人的反應之後,如果寫下自己的答案只供研究者看,那麼他們就較少受到群體壓力的影響。與面對群體相比,在祕密投票間裡,我們更容易堅持自己的信仰。
無事前承諾
1980年,傑尼·里斯克是在肯塔基·德彼賽馬會上取得第二名的一匹小雌馬。在第二輪普里克尼斯賽事中,她在最後一圈轉彎處超過了領跑馬科德斯,一匹小雄馬。當它們肩並肩地出現在轉彎處時,科德斯稍稍靠向傑尼·里斯克一邊,從而使她猶豫了一下,結果在這場比賽中科德斯險勝里斯克。科德斯碰到了傑尼·里斯克嗎?騎手的鞭子劃到了傑尼·里斯克的臉嗎?裁判員召開了祕密會議。在簡單的商議後他們判定這不是犯規,科德斯贏。這個決定引起了軒然大波。重放的電視錄像帶表明科德斯確實擦到了傑尼·里斯克。人們提交了抗議書。官員們重新審查了他們的決定,但是最終沒有改變主意。
是不是比賽後立即宣佈的決定影響了官員後來做決定的開放性?對於這一點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們可以以人為被試,進行實驗室研究,觀察有無事前承諾對結果會造成什麼樣的差別。想像你再一次成為阿施實驗的被試,研究者呈現了線段,並要求你第一個回答。在你做出回答後,聽到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同意,然後研究者給你一個重新考慮的機會。面臨群體壓力,你會放棄原來的意見嗎?
人們幾乎就不可能這樣做(Deutsch & Gerard,1955):個體一旦在公眾面前作出承諾,就會堅持到底。最多,也是在以後的情景中改變自己的判斷(Saltzstein & Sandberg,1979)。因此,也許我們可以預測,譬如說跳水或體操比賽的裁判,當看到其他裁判的評分後很少改變自己的分數,儘管在稍後的成績評定中會加以調整。
事前承諾也會抑制說服力。在模擬陪審團做決定時,如果不是祕密投票,而是舉手表決,那麼常常會發生擱置裁決現象(Kerr & MacCoun,1985)。做出公開的承諾往往會使人們難以後退。
聰明的說客們往往知道這一點。銷售員所提的問題往往會鼓勵我們對其所推銷的東西做積極的評價而不是消極的評價。環境保護主義者要求人們對回收廢品、節約能源或乘公共汽車做出承諾——與聲嘶力竭地呼籲相比,這更可能改變人們的行為(Katzev & Wang,1994)。14~17歲公開宣誓要保持童貞直至結婚的青少年,據報道,與沒有發出這樣誓言的人相比,在某種程度上更可能節制性慾或延遲性活動(Bearman & Brueckner,2001)。
小結
利用從眾實驗程序,研究者考察了從眾產生的環境條件。某些情境看起來特別有影響力。例如,從眾會受到群體特徵的影響。當面臨意見一致的、3個或更多個有吸引力的、地位高的人時,人們最容易從眾。如果個體是在公眾場合做出反應並且沒有做出事先承諾,那麼人們也最容易從眾。
個體為什麼會從眾
“你看到那片像駱駝一樣的雲嗎?”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問波洛涅斯。“它真像一頭駱駝,”波洛涅斯回答。“我想它還像一隻鼬鼠,”哈姆雷特過一會兒說,“它拱起了背,真像是一隻鼬鼠啊,”波洛涅斯承認道。“還是像一條鯨魚呢?”哈姆雷特又說。“真的很像一條鯨魚,”波洛涅斯贊同地說。問題:為什麼波洛涅斯如此贊同這位丹麥王子呢?
我作為一名美國人,在德國一所大學作長期訪問時第一次去聽演講。演講結束時,我舉起手加入了鼓掌行列。然而卻不是鼓掌,其他人開始用他們的指關節叩敲桌子。這是什麼意思?他們對演講不滿意嗎?顯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對這位德高望重的演講者公然表現得如此粗魯。而且他們的面部表情也沒有絲毫不快。不,我斷定這必然是一種德國式的喝彩方式。於是,我也加入了叩敲桌子的大合唱。
什麼引發了這種從眾行為呢?為什麼當其他人叩敲桌子時,我開始沒有這麼做?這有兩種可能。一個人可能屈服於群體是因為(1)想被群體接納和免遭拒絕,或者(2)獲得重要信息。莫頓·多伊奇和哈羅德·傑勒德(Morton Deutsch & Harold Gerard,1955)把這兩種可能性命名為規範影響 (normative influence)和信息影響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規範影響是“與群體保持一致”以免受拒絕,得到人們的接納,或者獲得人們的讚賞。也許,波洛涅斯追隨哈姆雷特是為了獲得這位地位較高的丹麥王子的歡心。在實驗室和日常生活中,群體常常拒絕某些行為偏離者(Miller & Anderson,1979;Schachter,1951)。當異議不只限於“家庭內部”而是擴展到群體之間的交往時,上述這點就更為明顯了。議會或國會成員在戰前討論中不同意國家的戰爭計劃,這是允許的。但是一旦戰爭爆發,就會期望每個人“支持我們的軍隊”。正如絕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那樣,遭到社會拒絕是令人痛苦的;如果我們偏離了群體規範,我們常常要付出情緒上的代價。傑勒德(1999)回憶起,在他的一個從眾實驗中,一位最初非常友善的被試變得非常沮喪,要求離開房間,回來時看上去:
虛弱而且抖得厲害。我有點擔心並建議停止實驗。他斷然拒絕停止,繼續進行完所有36輪實驗,沒有一次屈服於其他人。實驗結束時,我向他解釋了實驗設計中使用的花招,他整個身體慢慢放鬆下來,長嘆了一口氣,臉色又紅潤起來。我問他為什麼中途要離開房間。“去嘔吐”,他說。他沒有屈服,但這是怎樣的代價啊!他多麼渴望得到其他人的接納和喜歡,多麼擔心自己做不到這一點,因為他正站在群體的對立面。站在群體的對立面,你可能會遭到規範壓力所帶來的猛烈報復。
有時偏離的高昂代價會迫使人們支持自己不相信的東西,或至少壓制自己的反對性意見。不願意對大屠殺發表異議的一位德國軍官解釋說,“我害怕萊德利茲和其他人會認為我是一個懦夫(Waller,2002)。害怕軍事法庭懲罰自己的不服從,所以在米萊的一些士兵參與了大屠殺。特別對於那些最近看到過其他人被嘲笑或者那些順社會地位的階梯往上爬的人而言,規範性影響易導致服從(Hollander,1958;Janes & Olson,2000)。正如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56)回憶道,“當我進入國會時就有人告誡我,‘與人相處的方法就是跟隨大家一起走。’”
另一方面,信息影響會導致人們接納。當現實較為模糊時,正如光點似動情境中的被試者那樣,其他人可能就會成為有價值的信息來源。個體可能這樣推論,“我難以辨別光點移動的距離。但是這個小夥子看來知道。”甚至獨立宣言也認為我們要“向人類思想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人的反應也會影響我們對模糊刺激情境的解釋。就變幻莫測的雲朵而言,波洛涅斯看到的實際上是哈姆雷特幫他看到的。那些看到其他人贊成“應該限制言論自由”的人,與看到反對此觀點的人相比,更可能推論出十分不同的含義(Allen & Wilder,1980)。與群體保持一致會使人們特別容易獲得證實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解釋(Buehler & Griffin,1994)。
所以,對社會形象的關注往往容易產生規範影響。而希望自己行事正確則往往容易產生信息影響。在日常生活中,規範影響與信息影響往往是同時發生的。在德國演講廳裡喝彩的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規範影響),但其他人的行為同時向我展示了應該如何表達自己的讚賞之情(信息影響)。
對人們什麼時候會從眾的實驗有時需要將規範影響與信息影響分離。當人們需要面對群體作出反應時,會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從眾行為,這反映的是規範影響(因為不管人們公開反應還是私下反應接受的是同樣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任務難度比較大,個體感到自己無力勝任,也就是當個體關心行為的正確性時——所有這些都是信息影響的標誌,也會表現出較高程度的從眾行為。為什麼我們會從眾?有兩種主要理由:因為我們想得到別人的喜歡和讚賞,或者因為我們想要做出正確的行為。
小結
實驗表明人們之所以從眾主要出自兩個理由。規範影響來自於人們希望獲得別人的接納。信息影響來自於其他人為自己提供事實證據。當公開作出反應時從眾程度較大,這反映出規範的影響力。當遇到難以決策的任務時從眾程度也比較大,這反映出信息的影響力。
誰會從眾
從眾不僅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還表現出一定的個體差異。到底有多大的個體差異呢?在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中個性特質能發揮其最大的作用?
通常情況下,是不是有些人更容易受到社會的影響?你能從自己的朋友中找出一些“從眾者”和一些“獨立者”嗎?在對從眾者的判別中,研究者主要關注兩個預測指標:個性和文化。
個性
從20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末,人們一直在努力尋找個性特徵與社會行為(例如從眾)之間的關係,但僅發現二者之間有微弱的聯繫(Mischel,1968)。與情境因素所具有的影響力相比,個性得分是個體行為的一個很差的預測指標。如果你想要知道,某個人在多大程度上會從眾,多大程度上會攻擊或幫助他人,你最好先去了解一下情境的細節,而不是一組心理測驗分數。正如米爾格拉姆(1974)做出結論說,“我確信,的確存在一個與服從和不服從有關的複雜的人格基礎。但是,我知道我們還沒有找到它”(p.205)。
菲利浦·津巴多在反思模擬監獄和其他實驗時,認為最終的信息
指的是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來衝破自我中心主義;指的是你沒什麼不同,任何人所做過的任何事都不會與你的不同,你無法脫離它。我們必須打破這種由性情取向所產生的“我們-他們”的觀念,必須明白,在任何時候,作用於個體身上的情境力量是如此的強有力,以致會壓倒一切——先前的價值觀、歷史、生物、家庭、宗教等因素(Bruck,1976)。
20世紀80年代,人格研究者們在個體的心理特徵並沒起那麼大作用的觀點的引導下,正確地指出環境特質卻可以預測個體的行為。他們的研究證實了我們在第4章講過的一個原則:內在的因素(態度、特質)很難準確地預測行為,與此同時,它們卻能較好地預測個體跨情境的一般行為(Epstein,1980;Rushton & others,1983)。一個類比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點:正如很難預測你在某一次測驗中的行為反應一樣,同樣,也難以根據單一情境來預測你的行為。正如根據你在許多測驗項目所得的總分更具有預測力那樣,你的許多跨情境行為就可預測你整體的從眾性(或外向或攻擊性)。
當社會影響非常微弱時,個性也能較好地預測行為。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創造了“強有力”的情境;明白無誤的命令使個性差異很難發揮作用。即便如此,米爾格拉姆的被試還是在服從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並且,我們有理由懷疑,有時被試的仇視、對權威的尊重和對滿足他人期望的關注也會影響他們的服從(Blass,1990,1991)。在納粹死亡集中營裡,有些衛兵也會表現出仁慈;其他人則把活生生的嬰兒作為射擊的標靶或者把他們扔到火裡去。個性確實是起作用的。在“微弱的”情境中——正如兩個陌生人坐在會客室裡,沒有任何線索影響他們的行為——個性可以更好地自由發揮作用(Ickes & other,1982;Monson & others,1982)。如果在不同的情境裡對兩種類似的個性作比較,那麼情境的影響作用會超過個性差異的影響作用。如果我們根據日常生活情境片斷來比較薩達姆·候賽因一類人與特雷莎修女一類人,那麼,個性的影響會顯得非常大。
有趣的是,心理學專家對此的觀點有些類似鐘擺的運動。在並不小視社會力量具有不可否認的影響的同時,專家觀點的鐘擺現在又擺回到個性和基因的決定傾向。正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態度研究者那樣,人格研究者正在努力弄清楚並確定我們是誰與我們做什麼之間的關係。在感謝他們努力的同時,今天的社會心理學家贊成先驅理論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1936)的名言:“所有的心理事件都取決於個體的狀態,與此同時,也取決於環境,儘管它們的相對影響依情況而有所不同”(p.12)。
文化
文化背景有助於我們預測人們的從眾行為嗎?確實可以。詹姆斯·惠特克和羅伯特·米德(James Whittaker & Robert Meade,1967)在七個國家和地區重複了阿施的從眾實驗,發現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從眾比率比較接近——黎巴嫩31%,中國香港32%,巴西34%——但是在津巴布韋的班圖為51%,班圖是一個對不從眾者施加強力制裁的部落。當米爾格拉姆(1961)用不同的從眾程序來比較挪威和法國的學生時,他一致地發現法國學生表現出較少的從眾行為。
在澳大利亞、奧地利、德國、意大利、約旦、南非、西班牙和美國,研究者重複了服從實驗,你想一想,與美國被試的比較結果會如何?服從比率非常類似,甚至更高——在慕尼黑高達85%(Blass,2000)。
然而,文化也不斷地在變化。對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大學生被試重複進行阿施的實驗,與二三十年前阿施所觀察到的情況相比,有時人們會表現出較少的從眾行為(Lalancette & Standing,1990;Larsen,1974,1990;Nicholson & others,1985;Perrin & Spencer,1981)。
可見,從眾和服從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但是它們也會表現出文化和時代的差異(Bond,1988;Triaandis & others,1988)。羅德·邦德和彼得·斯密斯(Rod Bond & Peter Smith,1996)對17個國家的133個研究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文化價值觀確實對從眾有影響。與個人主義國家的人們相比,集體主義國家(在這裡,和諧受到讚揚,關係有助於定義自我)的人們更容易受到人影響而作出反應。
小結
“誰會從眾?”這個問題沒有找到確定的答案。一般人格測驗分數無法準確地預測個體的特定從眾行為,但卻是個體一般從眾傾向(和其他社會行為)較好的預測指標。特質效應在“微弱的”情境中顯得最為強有力,在這種情境中社會力量並不比個性差異佔絕對優勢。雖然從眾和服從是普遍的社會現象,但是文化卻使人們表現出或多或少的社會敏感性。
我們如何抵制從眾的社會壓力
人們是否願意主動抗拒社會壓力?如果迫使他們做A,他們會去做Z嗎?什麼因素可以引發這種反從眾行為?
就像第5章一樣,本章也強調社會力量的強大作用。因此這就有利於我們做出推論,即再次提醒自己,人所擁有的力量。我們不是檯球,任由外力推動;我們會對加於自己身上的力做出反應。知道某人要強迫我們,這也許恰恰會使我們做出相反 的行為反應。
逆反
個體非常看重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會壓力非常明顯,以至於威脅到個體的自由感時,他們常常會反抗。想一想羅密歐與朱麗葉,兩個家族的對立反而加深了他們的愛情。我們再想一想兒童,他們通過做與父母要求相反的行為來證實自己的自由度和獨立性。所以,聰明的父母通常不是下命令,而是讓孩子自己選擇:“到了洗澡的時間了,你想要盆浴還是淋浴?”
逆反 (reactance)心理理論——人們確實採取行動來保護他們的自由感——已被數個實驗研究所證實,這些實驗表明,努力限制人們的自由常常會導致反從眾和一種稱作“回飛鏢的效應”(Brehm & Brehm,1981;Nail & others,2000)。當今的西方女大學生在思考了傳統文化對女性行為的期望之後,她們就很少表現出傳統的淑女形象(Cialdini & others,1998)。或者,假定有人在街上攔住你,要你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字,而這件事你只是在心理有點兒贊成。當你正在考慮時,這個人告訴你,有些人認為“應該絕對禁止散發或簽署這份請願書。”逆反理論預測,這類明顯的限制自由的企圖事實上會增加你簽署的概率。這就是馬德琳·海爾曼(Madeline Heilman,1976)在紐約市街頭的實驗所發現的。
逆反理論有助於我們解釋青少年酗酒行為。加拿大藥物濫用中心(1997)對18~24歲的青年做的調查表明,69%的達到法定飲酒年齡(21歲)的人在過去一年中喝醉過,而不足 21歲的人群中這樣的比率卻達77%。在美國,一項對56個校園所做的調查表明,達到法定飲酒年齡(21歲)的學生中有25%是滴酒不沾的,而21歲以下的學生中這類人的比率只有19%(Engs & Hanson,1989)。羅伊·鮑邁斯特等人(Roy Baumeister,Kathleen Catanese & Henry Wallace)提出,逆反理論也有助於解釋強姦和性脅迫。當女性拒絕男性的性要求時,男性可能就對自己受限制的自由產生了一種挫折感,於是增強了其實施違法行為的慾望。逆反與自戀——對名譽的自我服務意識和對他人的低移情——相結合,這種不幸的結果也許就會產生強迫的性行為。
堅持獨特性
想像一下一個完全從眾的世界,人與人完全沒有區別。這樣的世界是個天堂嗎?如果不從眾令人不舒服的話,那完全一模一樣就會產生舒服感嗎?
當個體與周圍其他人太不一樣時會感覺不舒服。但是,至少在西方文化中,如果個體與周圍其他人完全一樣的話,也會感覺不舒服。C·R·斯奈德和霍華德·弗羅姆金(C. R. Snyder & Howard Fromkin,1980)的實驗表明,當個體認為自己是獨特的並且這種獨特感是中等程度時會產生較好的自我感覺。進而,他們將以維護自己個性的方式來行動。在斯奈德(1980)的一個實驗中,他讓普度大學的學生相信,他們的“10個最重要的態度”與其他1萬個學生的態度不同,或者與之基本相同。然後,讓他們參加一個從眾實驗。那些認為自己沒有獨特性的被試在實驗中傾向於以不從眾來維護自己的獨特性。在另一個實驗中,那些聽到其他人表達的態度與自己相同的人,反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獨特性。[當肩膀紋身被看做是一種時髦行為時——從眾而非個性化的表示——我們可以預期,其流行已經在走下坡路了。 ]
不僅是社會影響,而且是對獨特性的願望,甚至在給嬰幼兒起名字中都可以表現出來。追求新異名字的人們,卻常常在同一時間取了相同的名字。2002年在10個最靠前的流行的女孩名字中有麥迪遜(2)、亞歷克西絲(5)、奧利維婭(10)。佩姬·奧倫斯坦(Peggy Orenstein,2003)注意到,60年代,那些想打破傳統的人給自己的嬰兒取名為麗貝卡,結果發現他們的選擇也成了時尚的一部分。希拉里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個很流行的名字,當希拉里·克林頓成為名人後,就顯得不那麼有獨創性,人們也用得少了(甚至在她的崇拜者中也是這樣)。奧倫斯坦觀察到,儘管這些名字的流行性在減弱,但在下一代可能會重新流行。馬克斯、露絲、索菲聽上去好像是隱居家族或一個馬戲團的花名冊。
把自己看成是獨特的個體,也出現在“自發性自我概念”中。耶魯大學的威廉·麥圭爾及其同事(McGuire & Padawer-Singer,1978;McGuire & others,1979)報告說,當邀請兒童“給我們描述一下你自己”時,他們最可能提到的是自己獨特的特徵。在國外出生的孩子與其他孩子相比最可能提到的是他們的出生地。與黑頭髮和棕色頭髮的孩子相比,紅頭髮孩子更願意提到自己的頭髮顏色。體重較輕和體重較重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體重。少數民族的孩子更可能提及自己的種族。
同樣,當我們與異性相處時,我們會對自己的性別更敏感(Cota & Dion,1986)。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美國心理學會議,恰巧其他10個參會者都是女性,我立刻意識到了自己的性別。第二天結束時,我們休息了一會兒,我開玩笑說,我去洗手間時隊伍最短,這引發了坐在我旁邊的女性未曾注意到的事——這個群體的性別構成。
麥圭爾說,其規則就是,“只有當個體與眾不同時,也只有以這樣一種方式,個體才會意識到自我。”因此,“如果在一群白人女性中我是一個黑人婦女的話,那麼,我往往會認為自己是一個黑人;而如果我轉到了黑人男性群體中,那麼我的黑肌膚就沒有那麼突出了,我更會意識到自己是一位女性”(McGuire & others,1978)。這種洞察力有助於我們解釋為什麼少數民族群體容易意識到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有助於我們理解周圍的文化如何與之相互聯繫。由於多數民族意識不到這種民族特點,可能認為少數民族群體過於敏感。有時我會居住在蘇格蘭,在那裡,我的美國重音使我成為一個外國人,我意識到這種民族的認同感使我對其他人對我的反應非常敏感。生活在西方文化中,我們的與眾不同是自我認同的關鍵部分(Vignoles & others,2000)。
就算兩種文化中的人們非常類似,他們仍然能注意到彼此之間微小的差別。甚至非常細微的差別也會觸發歧視和衝突。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格列佛遊記》中以小Endians人反抗大Endians人的故事諷刺了這一現象。他們的區別是:小Endians人喜歡從蛋的小頭處打碎雞蛋,而大Endians人則喜歡從蛋的大頭處打碎雞蛋。從全世界範圍來說,蘇格蘭人與英國人、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或天主教徒與北愛爾蘭新教徒之間的差別看來並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別有時卻意味著極大的衝突(Rothbart & Taylor,1992)。當其他群體和你的群體最相像時,衝突常常也是最劇烈的。
似乎我們並不喜歡太離群,然而有趣的是,我們大家都希望與眾不同,並關注自己如何與眾不同。但是正如自我服務偏見(見第2章)所揭示的那樣,我們並不只是追求某種獨特性,而是追求正確方向上的獨特性。我們的要求不只是與眾人不同,而是要好 於眾人。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強調社會壓力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強調人的力量。我們並不是玩偶。當社會強制變得非常明顯時,人們常常會表現出逆反心理——為了恢復自由感而公然蔑視強制力量的動機。當群體所有成員同時表現出逆反時,其結果便是反叛。
與群體偏離太遠,我們會感到不舒服,但是我們也不想與其他人太一致。於是,我們就會以那種堅持自己獨特性和個性的方式行事。在群體中,我們最可能意識到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
個人後記:因為你是社區中一員
做你自己的事。責疑權威。如果感覺良好,那就做下去。跟著幸福走。不要從眾。仔細地思考一下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將一切好的東西歸功於自己。
如果 我們生活在個體主義的西方國家裡,例如西歐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尤其是美國,你會一次又一次地聽到上述這些話。個體主義是好的,從眾是不好的,這一無可置疑的假設,就是第1章所謂的“社會表徵”,一種集體共有的信念。我們文化中神話般的英雄——從哈克貝利·費恩(Huckleberry Finn)到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到天行者盧克到《黑客帝國》三部曲的尼奧,全都站出來反抗傳統規則——都認為個人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並高度讚美那些站出來反抗團體的人。
1831年,法國作家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次美國之旅創造了“個體主義”這個術語。他認為,個體主義,是指不把“任何事情歸功於任何人,也不期望從任何人那裡得到些什麼。他們形成了孤立地看待自己的習慣,想像整個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一個半世紀以後,精神治療學家弗裡茨·珀爾斯(Fritz Perls,1972)在他的《格式塔的祈禱者》(Gestalt Prayer )中概括了這種基本的個體主義: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並不生活在符合你期望的世界裡。
你也不生活在符合我期望的世界裡。
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1985)對這種說法表示贊同:“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真的能以極端滿足自我和真正表現自我的方式來生活嗎?’”
正如我們在第2章所講,對其他許多文化(包括亞洲)中的人們來說,很難把上述問題看做是惟一重要的問題。在那裡,社區 是受到讚賞的,從眾也為人所接受。學齡兒童通常穿著校服以示其團結一致。人與人之間的依戀關係影響深入。人們常抑制自己的衝突和不滿以求融洽相處。“槍打出頭鳥,”日本人說。
阿米泰·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1993),美國社會學聯合會的新主席,鼓勵我們朝向“共同式的”個體主義前進,這可以平衡我們不從眾的個體主義與社區精神。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1996)也表示贊同。“公有社會建立在個人神聖的價值觀基礎之上,”他解釋說。但是,它同時“認可團結一致的核心價值觀……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成為我們自己。”
作為各個不同國家的西方人,閱讀本書的絕大多數讀者都會欣賞不從眾的個體主義的好處。但是,公有社會者認為,我們要為整個社會的幸福付出代價。我們喜歡感受獨特性,喜歡自己控制生活,但是我們同時是社會動物,具有歸屬的基本需要。從眾並不是全壞,也不是全好。作為個體,我們需要平衡自己的獨立性需要和依戀需要,私密性和公共性,個體性和社會同一性。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以什麼方式表現獨立?你以什麼方式表現出依戀?對於平衡你有什麼感受?你認為西方人應該更為個人主義還是更為集體主義?
聯繫社會
本章介紹了歐文·斯托布(Ervin Staub)對服從和殘忍的研究工作。我們將在第10章再次介紹斯托布:探討種族滅絕的攻擊性和之後的一個更愉快的話題,即我們應該如何教導別人助人(第12章)。是對權威的服從導致了種族滅絕嗎?
第7章 說服
說服的途徑有哪些
中心途徑
外周途徑
說服的要素有哪些
誰是發言者?傳達者
說了些什麼?信息內容
怎麼說?溝通渠道
對誰說?聽眾
現實生活中的說服:邪教是如何進行精神灌輸的
態度依從行為
有說服力的因素
團體效應
應該如何抵制被說服
加強個人承諾
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免疫計劃
態度免疫的意義
個人後記:開明但不要天真
“輕信和盲從,無論是對舊的教條還是新的宣傳,仍然是支配人類心靈的弱點。”
——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人類的工作》,1904
“請記住,改變自己的想法並且跟隨它走向正確的方向,這依然意味著你是一個自由人。”
——奧利里亞斯,《沉思錄》
1933 到1945年間擔任德國“大眾啟蒙”和宣傳部長的戈培爾深刻地意識到了說服 (persuasion)的力量。他曾經承諾,只要讓他控制出版物、廣播節目、電影和藝術,他就能夠說服德國人接受納粹思想。另一個納粹分子施特賴歇爾出版了一份名為《先鋒》的反猶太週報,發行量達到50萬份;這份報紙是他的密友希特勒惟一一份從頭到尾閱讀的報紙。施特萊歇爾同時也出版反猶太的兒童讀物,並且和戈培爾一起在那些宣傳納粹思想的大眾集會上發表演講。
那麼,戈培爾、施特賴歇爾和其他一些納粹鼓吹分子的收效如何呢?是否正像阿萊斯在紐倫堡審判施特賴歇爾時所斷言的那樣,“給成千上萬人的大腦注入了毒藥”呢(Bytwerk,1976)?雖然大部分德國人並沒有被說服而瘋狂地仇恨猶太人,但的確有很多人被說服了。其中一部分人贊成反猶太措施,其餘大部分人的態度要麼變得猶豫不決,要麼被迫參與了這場浩大的種族屠殺,或者,至少默認了它的發生。如果不是有數百萬的同謀,這場大屠殺或許根本就不會發生(Goldhagen,1996)。
最近,就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這一主題而做的一項名為“美國人與西歐人的分歧”的調查研究(2003)恰好證實了說服的這種巨大力量。舉例來說,戰爭即將開始時的調查顯示,在歐洲人(以及加拿大人)中,反對戰爭和支持戰爭的人數之比是2:1,而美國人中支持與反對戰爭的比例與之相同(Burkholder,2003;Moore,2003;Pew,2003)。戰爭爆發以後,美國人中支持與反對戰爭的人數之比超過了3:1(Newport & others,2003)。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參與調查的所有其他國家的人都反對這場戰爭。
且不說發動這場戰爭是否明智——這個論題我們可以留給歷史來判斷——美國人與他們在其他國家的“遠房兄弟”間的巨大分歧證實說服正在發揮作用。是什麼說服了美國人支持這場戰爭呢?同時,又是什麼說服了其他地方的人反對它呢?(告訴我你住在哪裡,我就可以猜出你認為美國扮演的是一個保護者還是一個掠奪者的角色。)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人們傾向於與他們所在的團體保持一致並且表達自己團體所持有的態度(見第9章,偏見)。例如,國民對死刑的態度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時策。美國是一個允許對凶殺犯判處死刑的國家,有3/4的美國人支持死刑(Jones,2003)。而其他大多數國家沒有死刑,因此其大部分國民對死刑持反對態度(加拿大、西歐、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美大多數國家的讀者一定會點頭同意這樣的說法)。
除了對“我的國家”的行為做出合理化解釋的可能性之外,那些有說服力的信息同樣會塑造某種態度;這些信息讓一半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和9·11事件有直接關係,並且讓4/5的人相信在伊拉克會發現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Duffy,2003;Gallup,2003;Newport & others,2003)。社會學家亨特(Hunter,2002)認為文化塑造是自上而下發生作用的,文化的中堅分子控制著信息和觀念的傳播。因此,美國人和其他地方的人們看到的和聽到的是不同的戰爭(Cava,2003;Friedman,2003;Goldsmith,2003;Krugman,2003;Tomorrow,2003)。根據你的居住地,你可能會認為:
“美國解放伊拉克”或者“美國入侵伊拉克”。
“爭取伊拉克自由的軍事行動”或者“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殺人小分隊”或者伊拉克“游擊隊”。
“美軍與伊拉克人在緊張僵持中爆發流血衝突”(《洛杉磯時報》中模糊而帶有被動色彩的標題)或者“美軍向伊拉克人開火;13人死亡”(在報道同一事件時,加拿大的CBC使用主動語氣的標題)。
被俘和死亡的伊拉克人的場景或者被俘和死亡的美國人的場景。
對“正常示威遊行者”的簡短報道(福克斯新聞)或者對大規模反戰遊行的特寫。
對於美國人來說,其他國家的媒體帶有普遍的反美偏見,並且無視薩達姆的威脅。但是對於其他國家的人來說,那些美國“職業”戰地記者似乎將宣揚這場戰爭視為自己愛國的責任。那麼他們是不是真的像德國媒體界所質疑的那樣正在經歷“一體化 ”——用來描述納粹將德國媒體統一化的一個貶義詞——的過程呢(Goldsmith,2003)?如果不考慮偏見的來源和哪種觀點更正確的話,似乎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由於人們的居住地不同,所以他們所接受的(討論的並且相信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這說明的確是說服在發揮作用。
說服的力量同樣被用來促進人們以更健康的方式來生活。疾病控制中心的報告顯示,美國人的吸菸率為23%,僅僅是40年前的一半稍多一點,這部分得益於宣傳健康運動的興起。加拿大的統計 報告顯示,在加拿大也有同樣的下降趨勢。同時,美國大學新生的戒酒率有所上升——從1981年的25%到2002年的53%(Sax & others,2002)。在近十年中,通過進行健康和安全意識教育,成年人中戒菸和戒酒者前所未有的多了起來。
從以上這些例子來看,說服有利有弊。說服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而是信息背後的目的及其所包含的內容決定了我們對好和壞的判斷。我們稱不好的說服為“灌輸”,而好的說服則為“教育”。與灌輸相比,教育以事實為基礎,並且較少使用強制性手段。通俗一點來說,也就是我們把自己信仰的東西稱為“教育”,而不信仰的東西稱為“灌輸”(Lumsden & others,1980)。
我們的觀點總是有一定來源的。因此,無論是教育還是灌輸,說服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說服在政治、市場營銷、求愛、子女教育、談判、傳教和庭審判決中無處不在。因此,社會心理學家試圖探討是什麼導致了有效和持久的態度改變。哪些因素會影響說服?同時,作為說服者,我們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教育”別人?
想像你是某個市場部或者廣告部的經理;或者是一個傳教士,想在你的教區傳播更多愛和仁慈的教義;或者你希望促進節能運動,鼓勵母乳餵養,或者幫助某個政治候選人做宣傳。為了使你自己和你所傳達的信息更具有說服力,你會做什麼?反過來,如果你不想被這些誘惑所操縱,你又會採取什麼策略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社會心理學家通常採用地理學家研究地質侵蝕的方法來研究說服:運用簡化和控制良好的實驗來觀察各種因素所起的作用。當其影響作用比較小而又不觸及到我們價值觀的時候,說服效果最好(Johnson & Eagly,1989;Petty & Krosnick,1995)。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他們就可以讓我們明白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的。
說服的途徑有哪些
產生影響力的兩條途徑是什麼?每條途徑涉及到哪種類型的認知加工過程,它們會起到什麼作用?
二戰期間擔任美國戰爭部首席心理學家的耶魯大學教授霍夫蘭及其同事們(Hovland & others,1949)通過研究說服為戰爭做出了貢獻。為了鼓舞士氣,霍夫蘭等人系統地研究了訓練影片和歷史記錄怎樣影響新兵對戰爭的態度。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回到耶魯大學繼續研究那些能夠令信息更加具有說服力的因素。他們改變與溝通者、信息內容、傳播渠道和聽眾有關的各種因素。
如圖7-1所示,要引發行為,說服必須清除幾個障礙。任何有利於人們清除這些障礙的因素都會增強說服的可能性。例如,如果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信息源引起了你的注意,那麼這個信息就會更有可能說服你。耶魯大學這個研究小組對說服的研究方法有利於我們瞭解說服在什麼時候 更容易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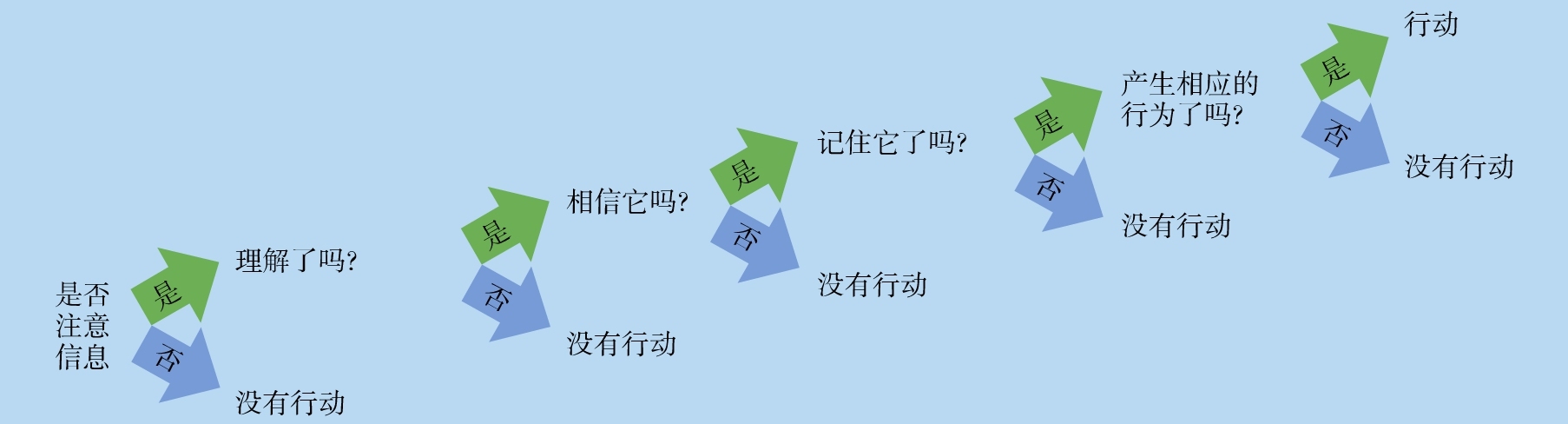
圖7-1
為了引發行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信息必須清除幾個障礙。關鍵並不在於記住信息本身,而在於記住自己做反應時的想法。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W. J. McGuire.“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of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Behavioral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in Marketing ,edited by H. L. Davis and A. J. Silk,1978. Copyright © 1978.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 Sons,Inc.
俄亥俄大學的研究者在20世紀60、70以及80年代提出,在對說服信息做出反應時,人們的想法也會起一定作用。如果某個信息清晰易懂,但同時充斥著令人難以信服的論據,那麼你會輕易地反駁這個信息,而不會被它說服。相反,如果某個信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據,那麼你會更加贊同它並且很可能被說服。這種“認知反應”理論有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 說服在某些情境中更容易發生。
中心途徑
佩蒂和卡喬波(Petty & Cacioppo,1986;Petty & Wegener,1999)以及伊格列和柴肯(Eagly & Chaiken,1993,1998)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們認為說服可能通過以下兩種途徑中的一種發生作用。當人們在某種動機的引導下,並且有能力全面系統地對某個問題進行思考的時候,他們更多地使用說服的中心途徑 (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也就是關注論據。如果論據有力且令人信服,那麼人們就很可能被說服。如果信息包含無力的論據,思維縝密的人會很快注意到這一點並且進行反駁。
外周途徑
但有時論據的有力與否並不重要。有時候我們完全不可能在某種動機的引導下去仔細地思考。如果我們忙於其他的事情而沒有專注於信息,那我們就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去仔細推敲信息所包含的內容。此時我們會使用說服的外周途徑 (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也就是關注那些可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線索,而不考慮論據是否令人信服。當人們轉移了注意力或者沒有足夠的動機去思考的時候,熟悉易懂的表達比新異的表達更具有說服力。比如說,對於一個外行人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來說,“不要把你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要比“不要在一次冒險行為中壓上你所有的賭注”更有影響力(Howard,1997)。
聰明的廣告商會努力調整廣告使其更加符合消費者的思維。對於諸如公告牌和電視購物這些消費者很少去關注的媒體來說,視覺形象就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外周線索。我們對於食品、飲料、菸草和衣服這一類商品的看法往往是基於感覺而不是基於邏輯。這些產品的廣告通常也都使用外周線索。菸草廣告總是將產品與那些漂亮且令人愉悅的形象聯繫在一起,而不是提供一些支持吸菸的論據。軟飲料廣告也是如此,例如宣傳“可樂的樂趣”或者將快樂、年輕、充滿活力的北極熊的形象與實物相聯繫。另一方面,對於計算機廣告,感興趣的理性消費者會花一定的時間對此進行評價,因此計算機生產商很少用好萊塢明星或者體育明星來做廣告;相反,他們向消費者提供產品具有競爭力的特點以及價格信息。如果信息類型符合信息接收者的接受途徑,那麼就能增強接收者對信息的關注程度(Shavitt,1990;Petty,Wheeler,& Bizer,2000)。
但是廣告商、傳教士甚至教師的最終目的並不只是引起人們對信息的注意,然後又接著做其他的事情。通常他們的終極目的是引發個體某種行為的改變。那麼,是不是上述這兩種途徑都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呢?佩蒂及其同事(1995)注意到中心途徑過程能引起個體更持久的行為改變。當人們對論點進行仔細思考的時候,他們依賴的不僅僅是信息自身所具備的說服力,同時也依賴自己對信息做出迴應時的想法。當某個論據引人深思的時候,它才最具說服力。那些經過人們深層而不是膚淺的思考之後所產生的態度變化會更加持久,更能對抗反擊,並且更能影響行為(Petty & others,1995;Verplanken,1991)。因此,中心途徑能引起人們更加穩定的態度和行為的改變,而外周途徑的影響要短暫和表淺得多。因此如果你真的想通過自己傳遞的信息來說服一個人戒菸的話,最好的方法是不僅提供強有力的論據,同時也要增強他對那些論據進行思考的動機和能力。
即使是那些樂於思考的人有時候也使用外周途徑來形成自己初步的觀點。我們經常會使用一些簡單而具有啟發性的拇指原則,例如“相信專家”或者“長信息更可信”(Chaiken & Maheswaran,1994)。我所居住的社區居民最近正在就一個有關當地醫院合法所有權的複雜問題進行投票。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親自去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我需要寫完這本書),而且我發現那些居民投票支持者中既有我喜歡的人,也有專家,在此我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啟發性策略:朋友或者專家是值得信賴的,並據此進行投票。我們都會使用一些其他的啟發性策略來迅速做出判斷:如果一個演講者的表達清晰流利,富有魅力,而且具有非常好的動機和一定數量的論據(或者最好這些論據有不同的來源),我們通常會使用外周途徑不假思索地接受他們的信息(圖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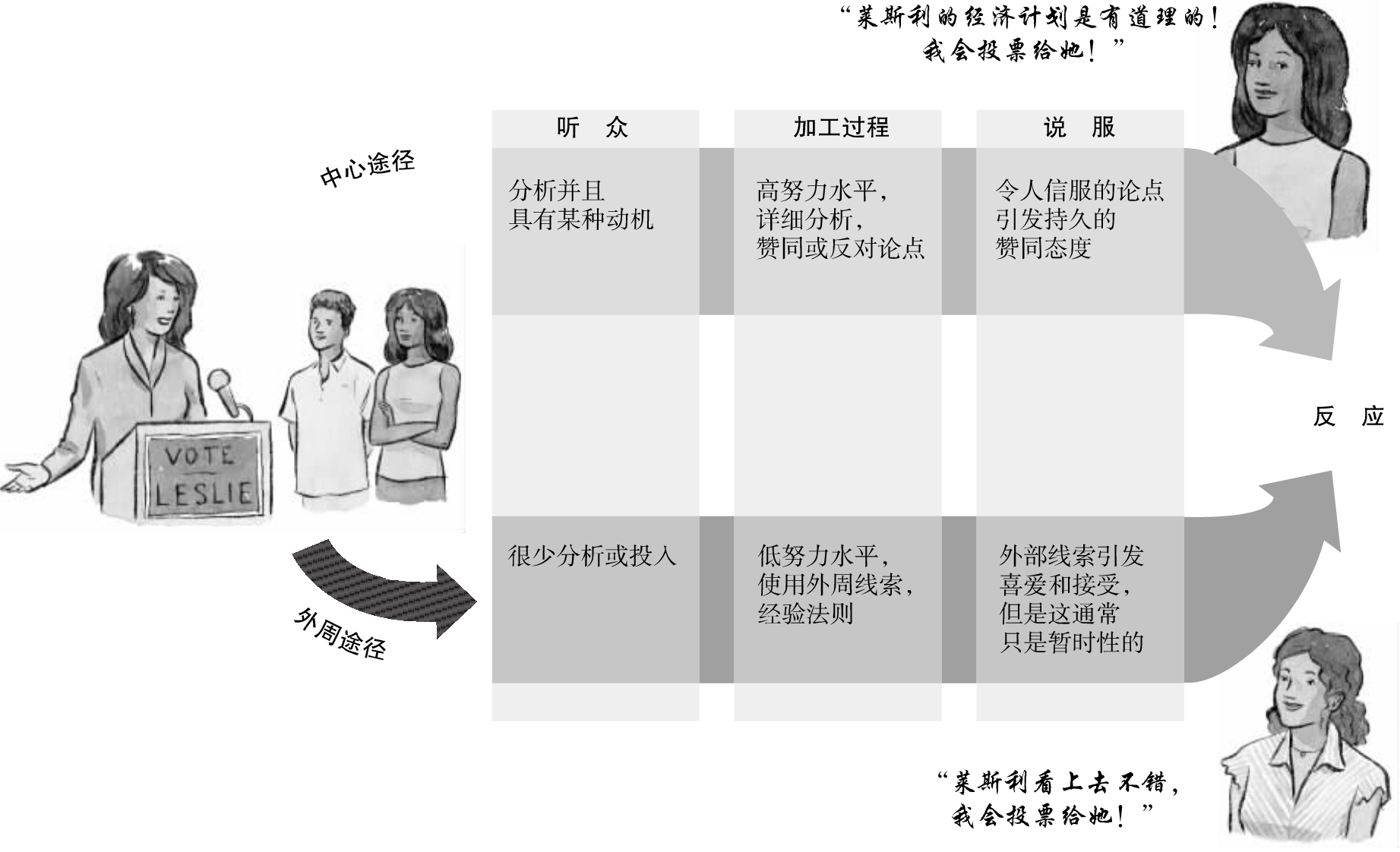
圖7-2 說服的中心途徑和外周途徑
計算機廣告商通常使用中心途徑法,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廣告的觀眾需要系統地比較各種產品之間性能和價格的差異。而軟飲料的廣告商則使用外周途徑,他們僅僅是將自己的產品與魅力、愉快以及好心情相聯繫。中心途徑加工過程更可能產生態度的持久改變。
小結
有時候說服是發生在人們關注於某個論題並且對其做出積極思考的時候。當人們自然而然地對論點進行分析時,使用的是說服的“中心途徑”。如果論題沒有引發個體做出系統的思考,個體只是根據一些具有偶然提示性的線索下論斷時,說服會通過速度更快的“外周途徑”發生。由於中心途徑的說服更具理性,因此更加持久,也更有可能改變行為。
說服的要素有哪些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說服主要包括以下四個組成部分:1)傳達者;2)信息內容;3)溝通渠道;4)聽眾。換句話說,就是誰用什麼方法將什麼信息傳遞給了誰?那麼這些因素是怎樣影響我們對中心途徑或者外周途徑的選擇呢?
誰是發言者?傳達者
請想像以下的情境:懷特是一箇中年美國人,正在收看晚間新聞。第一部分新聞正在播放一小撮激進分子焚燒美國國旗,其中一人用擴音器高喊著,當一個政府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的時候,“人民有權改變它或者廢除它……這是他們的權利,是他們的義務,讓這樣的政府見鬼去吧!”懷特先生很窩火地對他妻子嘀咕道:“聽這些人叫囂這樣的教條真是令人感到噁心。”在節目的下一個部分,一名在反稅收集會中演講的總統候選人宣稱:“節約應當成為我們政府開支的主導性原則。每一個政府工作人員都應當清醒地意識到腐敗和浪費是一種極大的罪惡。”懷特先生對這個論斷明顯感到滿意,他放鬆地笑道:“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判斷力嘛,這才像是我們的人呢!”
現在讓我們改變一下場景。請想像懷特先生是在7月4日紀念獨立宣言(下述觀點即出於此)的致詞中聽到這種“人民的權利”的觀點,他現在會有不同的反應嗎?
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信息的傳達者會影響聽眾對信息的接受。在一個實驗中,荷蘭社會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在其議會上用相同的語言表達相同的觀點,但結果每一方的論點都只對本黨的成員最有影響力(Wiegman,1985)。不僅信息本身非常重要,傳達者同樣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得某些傳達者比另外一些傳達者更具說服力呢?
可信度
幾乎所有人都會發現,有關鍛鍊益處的報告如果來自皇家科學院或者國家科學院就要比來自小報讓人覺得可信得多。但是這種信息源的可信度 (credibility)(可知覺到的專業性和可信賴性)效應在數月之後就會消退。如果說一個令人信賴的人所傳達的信息具有說服力的話,那麼這種影響會隨著對信息源的遺忘或者信息源與信息之間的分離而消退。而與之相反,那些可信度低的人的影響力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增加(如果人們更多的記住了信息內容本身而不是記住了令這些信息大打折扣的原因的話)(Cook & Flay,1978;Gruder & others,1978;Pratkanis & others,1988)。這種當人們遺忘信息來源或來源與信息之間的聯繫之後的延滯性的說服,被稱作“睡眠者效應 (sle eper effect)”。
可知覺的專家性 一個人如何才能成為具有權威性的專家呢?一種方法是從傳達聽眾贊同的觀點開始,這樣會使你看上去很聰明。另一種則是以在某一專題內的學識淵博 者身份被介紹給大家。一個關於牙刷的信息來自於“加拿大牙科協會的詹姆斯博士”,就要比來自“吉米,當地一個和同學一起做了一個有關牙科衛生學項目的高中生”的同樣信息令人信服得多(Olson & Cal,1984)。在對高中生吸食大麻問題做了十多年的研究之後,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們(Bachman & others,1988)發現,那些從不可靠來源發佈的恐嚇信息在20世紀60~70年代並沒有影響到大麻的使用。但是生物學和心理學對於長期使用大麻的科學報告作為一個可靠的信息來源,“在減少藥物濫用上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種增加可信度的方法是自信的表達方式。埃裡克森及其同事們(Erickson & others,1978)讓南加州大學的學生評價兩種法庭證詞,一種表達方式直截了當而另一種卻猶豫不決。例如:
問題: 在救護車到達之前你呆在現場大約有多長時間?
回答: [直截了當]20分鐘。足夠給戴維小姐的傷口做一些清理。
[猶豫不決]恩,似乎有,大概,嗯,有20分鐘吧。正好有足夠的時間給我的朋友,你知道的,戴維小姐的傷口做些清理。
學生們發現那些直截了當的目擊證詞更可信,更有說服力。
可知覺的信賴性 演講風格同樣會影響演講者的可信賴度。赫姆斯利和杜布(Hemsley & Doob,1978)發現,目擊者在作證的時候如果是直視 質問者而不是低頭看著地面,那麼他們會給那些觀看這一場景錄像的人留下更為可信的印象。
如果聽眾認為傳達者並不是在努力說服 自己,這時傳達者的可信賴度會更高。在一個後來演變為電視廣告中的“隱藏的攝像機”法的實驗中,哈特菲爾德和費斯汀格(Hatfield,Walster,& Festinger,1962)讓一些斯坦福大學的本科生去偷聽研究生的談話(實際上他們聽到的是一些錄音)。當談話內容與偷聽者有關時(與學校的規定有關),按道理來說,那些不知情的談話者對偷聽者的影響要大於那些知道有人正在偷聽的談話者。畢竟,如果人們不知道有人在偷聽自己和別人的談話,他們又有什麼好隱瞞的呢?
同樣,我們會認為那些站在自身利益對立面 的說話者是真誠的。伊格利等人(Eagly,Wood,& Chaiken,1978)給密歇根大學的學生播放了一段攻擊某公司汙染河水的演講。如果告訴學生這既是一個有商業背景的政治候選人同時又是這家公司的支持者所做的演講,那麼學生們就會認為它是沒有偏見而且具有說服力的;同樣是這個反商業的演講,如果出自一個支持環境保護的政治家並且對象是一些環境論者,那麼聽眾會將這番政治論調歸結於演講者或者聽眾的個人偏見。正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和其他一些偉大的領袖所做的一樣,甘心為了自己的信仰而承受痛苦的精神,也有助於人們相信個體的真誠之心(Knight & Weiss,1980)。
所有這些實驗都指出了歸因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如何判斷一個演講者的立場,究竟是出於個人的偏見和自私的動機還是出於客觀事實?伍德和伊格利(1981)發現,當一個演講者站在一個出人意料的立場上時,我們更傾向於將他們的論點歸因於客觀事實,並且認為它們是具有說服力的。一個吝嗇鬼式的人物提出要為一起人身傷害事件提供慷慨的補償會具有最強的說服力。一個和藹慷慨的人提出吝嗇的補償時也會產生相同的影響效果(Wachtler & Counselman,1981)。
南加州大學的米勒及其同事(Miller & others,1976)發現,當一個人的說話速度比較快的時候,他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度都會升高。當人們聽一段有關“喝咖啡有害”的錄音時,他們會認為一個速度較快的說話者(大約每分鐘190個字)比一個速度較慢的說話者(大約每分鐘110字)要更客觀、更聰明,也更有見地。研究者同時發現越是說話快的演說者越有說服力。約翰·肯尼迪是非常出色的公眾演說家,他有時忽然蹦出的幾句話的語速可達每分鐘300個單詞。
對於美國人來說(儘管對韓國人不是這樣),較快的語速代表著力量和能力(Peng & others,1993)。較快的語速雖然無法留給聽眾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有利的推敲,但同時也杜絕了一些不利思維的產生(Smith & Shaffer,1991)。如果一個廣告商以“每小時70英里”的語速對你進行遊說的話,你是很難用相同的速度來反駁他的。
很明顯,一些電視廣告使傳達者的形象表現得既具有專家性又有可信賴性。藥品公司在推銷他們的止疼藥時會使用身著實驗室白大褂的人物形象,他們很自信地宣稱大部分醫生都推薦其中的某種重要成分(當然,這種成分是阿司匹林)。有了這樣的外周線索之後,不對論據進行仔細分析的人就會簡單地推斷這種產品的價值。其他的廣告看上去並沒有使用可信度原則。泰格·伍茲對運動服飾的專業性瞭解恐怕並不是耐克公司花一億美元請他出演其廣告的主要原因。
吸引力和偏好
大多數人都否認體育和娛樂明星對某些產品的認可會影響自己。他們都清楚明星們對自己所推薦的產品其實知之甚少。除此以外,我們也明白我們並不是偶然地偷聽到泰格·伍茲在談論服飾和汽車——這類廣告的意圖就是要說服我們。這類廣告利用了有效傳達者的另一個特徵:吸引力。我們可能認為自己不會被他人的吸引力或者個人偏好所影響,但研究者們卻發現了相反的結果。對那些我們偏好的東西,我們更有可能做出迴應,那些慈善募捐、糖果銷售和特百惠家用塑料製品聚會的組織者非常清楚這種現象。甚至僅僅一次短暫的談話也足以增強我們對某個人的偏好和對其影響力的迴應程度(Burger & others,2001)。個人偏好使我們樂於接受傳達者的觀點(中心途徑的說服),或者,事後當我們見到那些產品的時候,能夠引發積極的聯想(外周途徑的說服)。正如可信度那樣,這是偏好引發的說服原則在起作用(見表7-1)。
表7-1 六個說服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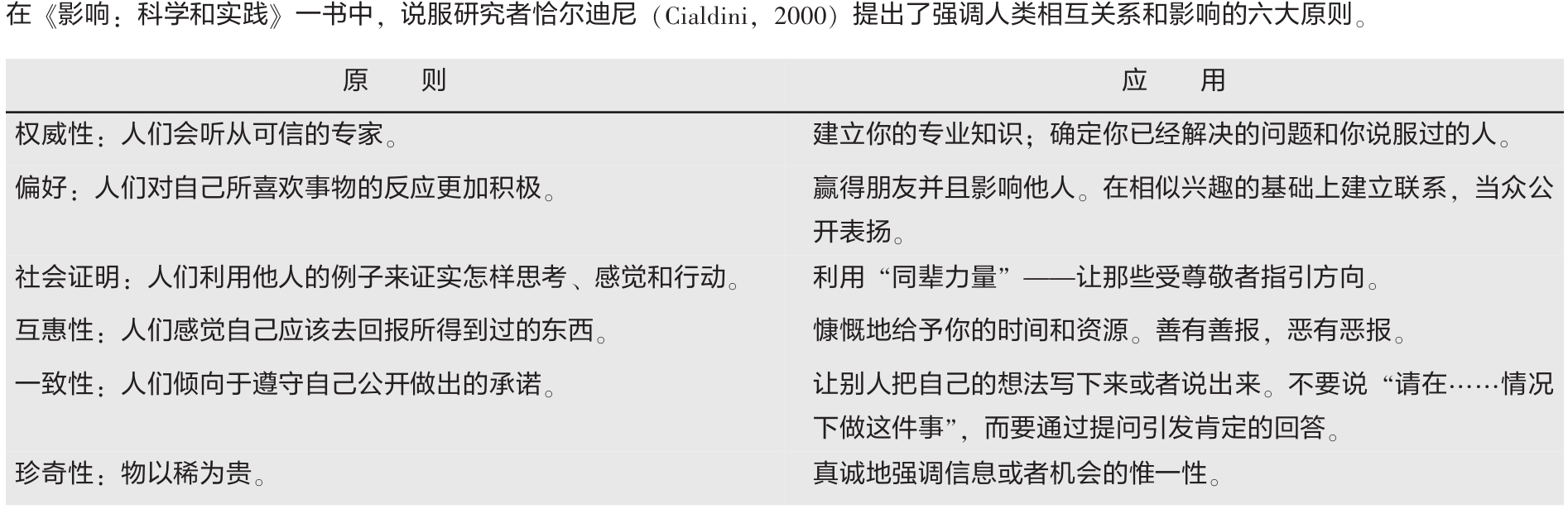
吸引力 (attractiveness)可以表現在許多方面。外表吸引力 就是其中一方面。當一個論點(尤其是感情方面的論點)來自於一個漂亮的人時,往往具有更大的影響力(Chaiken,1979;Dion & Stein,1978;Pallak & others,1983)。相似性 是另外一種表現。正如我們將在第11章中強調的那樣,我們傾向於相信那些與我們相似的人,我們會受這樣的人影響。例如在登布羅斯基等人(Dembroski,Lasater,& Ramirez,1978)的實驗中,他們給一些美國黑人中學生看一個倡議正確的牙齒護理的錄像。第二天,當牙醫對他們的牙齒清潔度進行評價的時候,那些聽了來自黑人牙醫倡議的學生牙齒要更白一些。通常來說,人們對來自自身團體的信息的迴應要更好(Knippenberg & Wilke,1992;Wilder,1990)。
相似性是不是比可信度更重要呢?有些情況是,但有些情況並非如此。布羅克(Brock,1965)發現,對於油漆店的顧客來說,親眼看到一個剛剛買了和自己的購買計劃相同數量的普通顧客與一個買了其20倍數量的專家相比,前者的陳述更容易影響他們。但在討論牙齒衛生時,一個一流的牙科醫生(不熟悉但具有專業知識的來源)要比一個學生(熟悉但不具有專業知識的來源)更具有說服力。
這種表面上的矛盾性引發了科學家們的探索。他們認為可能有一個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當因素X存在時,相似性更加重要;而當因素X不存在時,可信度更加重要。戈瑟爾斯和納爾遜(Goethals & Nelson,1973)發現,這個因素X指的是某個主題側重的是主觀偏好 還是客觀現實 。如果某種選擇關係到個人價值、品位或者是生活方式,那麼相似的 傳達者具有最強的影響力。但如果是對事實 做判斷,例如悉尼的降雨是否比倫敦要少這樣的問題,一個不熟悉 的人的確認對增強信心更有幫助。因為一個不熟悉的人,而且他也是一個專家的時候,能提供更加獨立的判斷。
說了些什麼?信息內容
不僅說話者對說服有影響作用,這個人說了些什麼 也同樣非常重要。如果你正準備發起一個倡議,希望人們投票支持學校稅收、戒菸或者捐錢救濟全球正在遭受饑荒的人,那麼你一定很想知道應該怎樣恰當地使用說服的中心途徑。對於以下問題,我們的常識似乎可以同時支持雙方的論點:
是純粹邏輯性的還是那些能喚起情緒反應的信息更具有說服力?
提倡哪一種觀點會造成更大的態度轉變,是一個與聽眾已有的立場相差無幾的觀點,還是一個與其截然不同的觀點?
信息表達中只包含你一方的觀點好,還是先接受對方的觀點然後再將其駁倒比較好?
如果雙方人員同時在場,例如在一個社區會議上人們需要依次發言,那麼是先發言佔優勢還是後發言佔優勢呢?
我們將逐一討論這些問題。
理智對情感
假設你正參加一個支持救濟全球饑荒難民的活動。擺出你個人觀點最好的辦法是引用一大堆令人印象深刻的統計數據,還是使用一種更加具有感情色彩的辦法,例如講述一個令人關注的快要餓死的孩子的故事更加有效一些?當然,一個論點可以同時包括理智與情感。你可以把感情和邏輯結合起來。然而,哪一個更 具有影響力呢?是理智還是情感?我們或許會問,誰的話更具有智慧呢?是莎士比亞筆下的萊桑德(《仲夏夜之夢》中的人物)說的:“人類的意志來源於他們的理智”?還是切斯特菲爾德的忠告:“把你自己交給感覺吧,交給你的心,交給人類的弱點,但千萬不要交給理智”?
答案是:這取決於聽眾。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善於分析思辨的人比受教育水平不高或不善於分析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說服(Cacioppo & others,1983,1996;Hovland & others,1949)。有思想和積極參與的聽眾會使用說服的中心途徑,他們對邏輯的論點回應最為強烈。而不感興趣的聽眾則會使用說服的外周途徑,他們更可能受對傳達者偏愛程度的影響(Chaiken,1980;Petty & others,1981)。
從大選前的訪談來看,多數選民在選前並非積極參與者。相對於候選人的特質和行為適當性來說,選民對他們的情感反應對選舉結果具有更強的預測性(Abelson & others,1982)。態度形成的過程對此也會產生影響。如果一個人初始的態度來源於情感,那麼他更容易被情感性的論點說服;如果其初始態度主要來源於理智,那麼理性的論點則更加有效(Edwards,1990;Fabrigar & Petty,1999)。新的情感信息會動搖基於情感而形成的態度。但是如果要改變一種基於信息而形成的態度,那麼就需要更多的信息。
好心情效應 當信息與好心情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它們會具有更強的說服力。賈尼斯及其同事們(Janis & others,1965;Dabbs & Janis,1965)發現,如果在閱讀信息的時候讓耶魯大學的學生享用花生和可樂,那麼他們會更容易被說服(圖7-3)。類似地,加利佐和亨德里克(Galizio & Hendrick,1972)發現,令人愉快的吉他伴奏的民歌比無伴奏的民歌對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來說更具有說服力。那些喜歡在有輕音樂伴奏的豪華午餐中開展商務活動的人一定會對這樣的結果感到滿意。[一項對168個電視廣告的說服力的研究表明(Agres,1987),最有效的廣告既包括理性內容(使用X去汙劑會使白色衣物更亮白),也包括情感內容(聰明的媽媽選擇吉夫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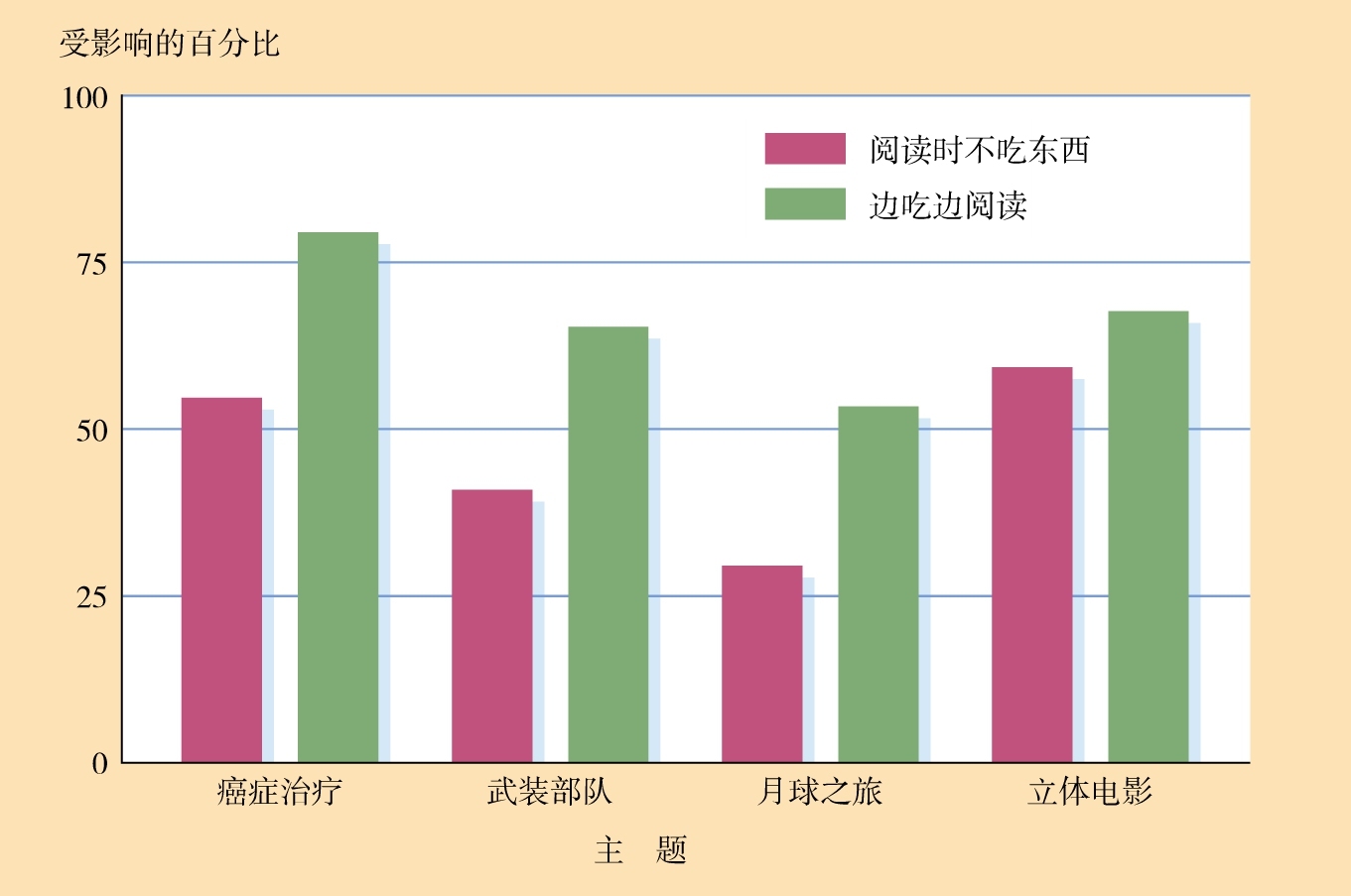
圖7-3 邊吃邊閱讀的人比那些沒有吃東西的人更容易被說服
資料來源:Data from Janis,Kaye,& Kirschner,1965.
好心情通常可以增強說服力,一方面它有利於個體進行積極的思考(如果人們在某種動機的引發下進行思考),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與信息相互聯繫(Petty & others,1993)。像第3章所提到的那樣,當人們有一個好心情的時候,他們會透過“玫瑰色的眼鏡”來看待這個世界。他們會更快做出決定,而且做決定時也更衝動,更多地依賴外周線索(Bodenhausen,1993;Schwarz & others,1991)。心情不好的人在做出反應之前會更多地反覆考慮,所以他們很難被無力的論據動搖。所以,如果你的論證不夠有力的話,你最好先設法使你的聽眾有一個好心情,然後他們才可能不假思索就對你的信息產生好感。
喚起恐懼效應 信息也可以通過引發消極的情緒起作用。當我們試圖說服人們減少吸菸量、更勤快地刷牙、打破傷風針或者小心駕駛的時候,那種能喚起恐懼情緒的信息是有效的(Muller & Johnson,1990)。給吸菸者展示吸菸的可怕後果會更有說服力——正是基於這一事實,加拿大政府要求菸草廠商在每一包香菸上圖示吸菸的危害(Newman,2001)。但是,到底應該要喚起多高恐懼程度的情緒呢?是應該只稍微喚起一丁點恐懼心理,以免人們因為太害怕而回避這些令人痛苦的信息?還是讓他們墮入黑暗的恐懼深淵?威斯康星大學的利文撒爾等人(Leventhal & others,1970)以及亞拉巴馬大學的羅傑斯等人(Robberson & Rogers,1988)發現,通常情況下,人們的恐懼程度越高,其迴應就越多。
以喚起恐懼心理的方式來進行信息傳達的有效性不僅體現在鼓勵戒菸的廣告中,而且還應用到減少危險的性行為、戒酒以及小心駕駛的廣告中。Claude Levy-Leboyer(1988)發現喚起恐懼心理的圖片能有效改變法國青少年對酒和飲酒行為的態度,之後,法國政府就將這些信息加入到電視節目中。恐懼心理的喚起可以大大增強人們對有關疾病和預防信息的興趣(Das & others,2003;Ruiter & others,2001)。而且,同正面的信息相比(“禁慾可以表明個體的責任感、自尊心和對未來的規劃”),負面的信息(“過多的性行為意味著個體缺乏責任感和自尊以及對將來的無計劃性”)使人們知覺到有關積極行為(性節制)更強烈的規範性,而這種規範性能夠增強說服力(Stuart & Blanton,2003)。
以喚起恐懼心理的方式進行信息傳達也會增強人們對行為的監測性,例如去做乳腺X光檢查,對乳腺和睪丸做自我檢測,以及檢查皮膚癌的早期症狀。班克斯和薩洛維(Banks,Salovey,& others,1995)讓那些沒有做過乳腺X光檢查的40~66歲婦女觀看一個關於乳腺X光檢查的錄像。在那些接收到積極信息(強調做乳腺X光檢查能夠幫助你及早發現疾病以挽救你的性命)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在12個月內去做了乳腺X光檢查;但是在那些接收到恐懼結構信息(強調不去做乳腺X光檢查會使你付出生命的代價)的人中,有2/3的人在12個月之內去做了乳腺X光檢查。
在恐懼上做文章並不總是一定會增強信息的說服力。對艾滋病的恐懼並沒有使人因此而禁 欲或者使用避孕套;許多人雖然害怕吸菸會引發死亡,但過後仍然繼續吸菸。阿倫森(Aronson,1997)注意到,當恐懼心理和一個令人愉快的行為有關時,其結果通常不會引發行為的改變而是否認這一事實。
人們之所以會產生否認的態度,是因為在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避免這種危險的情況下,恐懼信息的力量非常強大(Leventhal,1970;Rogers & Mewborn,1976)。只有在讓人們意識到威脅的嚴重性和可能性的同時告訴他們一個解決的方法,那麼喚起恐懼心理的信息才會更加有效(DeVos-Comby & Salovey,2002;Maddux & Rogers,1983;Ruiter & others,2001)。引發人們焦慮的健康信息,比如說攝入高膽固醇的危險性,會增強人們食用低脂肪、低膽固醇食品的傾向(Millar & Millar,1996)。
很多意在減少危險性行為的廣告在使用“艾滋病殺手”這樣的口號喚起人們的恐懼心理的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防護性的措施:禁慾、使用安全套或者保持固定的性伴侶。20世紀80年代,對艾滋病的恐懼確實使很多男性改變了他們的行為。一項對5000名男同性戀的研究發現,1984到1986年間,當爆發了艾滋病危機之後,宣稱自己為獨身主義者或者有固定性伴侶的人從14%上升到39%(Fineberg,1988)。
形象化的宣傳經常會引發恐懼心理。施特賴歇爾的《先鋒》雜誌就用很多沒有事實根據的奇聞軼事來引發成千上萬人的恐慌。他侮蔑猶太人,說他們把老鼠碾碎了做菜,引誘非猶太的女人,並詐騙她們的畢生積蓄。施特賴歇爾的言論就像大多數鼓吹納粹思想的宣傳品一樣,是感性而非邏輯的。這些言論同時還提供了與這些“危險分子”鬥爭的清楚詳盡的方案:他們列出所有猶太人商店的名稱以使讀者避免光顧它們,鼓勵讀者公佈資助猶太商店和猶太從業者的德國人的名單,指導讀者編寫本地區猶太人的名冊(Bytwerk & Brooks,1980)。
當猶太大屠殺發生之後,出現了一本由一個小女孩寫的生動日記,就像舍曼、貝克和賴亞爾斯(Sherman,Beike,& Ryalls,1999)所稱的那樣“具有強大的衝擊力”。曾經出版了成百上千本描述納粹暴行的書,“但是從來沒有一本書能像這個女孩寫的這本一樣,幾乎被翻譯成每一種語言,銷量超過納粹期間所有歷史文獻的總和。事實上,在遊覽阿姆斯特丹這個擁有不計其數的博物館和歷史悠久的城市時,更多的人選擇去拜訪“安妮·弗蘭克的小屋”,而不是其他的名勝。
差異
請想像以下的情景:萬達回家過春假並且希望說服人到中年已發福的父親採用新的“健康適宜的生活方式”。她自己每天慢跑5英里,但她父親覺得鍛鍊就像電視頻道預覽一樣讓人眼花繚亂。萬達想:“究竟怎樣才可能說服頑固的老爸呢?是推薦一個溫和一點的鍛鍊計劃,比如每天散步好呢?還是乾脆建議讓他投入到一個強度更大的鍛鍊計劃中,比如有氧操或者跑步好呢?如果我讓他實施一項嚴格的鍛鍊計劃,他最後或許會妥協,並且至少會認為其中一些方案還是值得一試的。但也有可能他覺得我太瘋狂,進而乾脆什麼都不做了。”
就像萬達一樣,社會心理學家也可以用任意一種方式進行推理。意見不同會造成不適,而這種不適又會推動人們去改變自己的觀點(回憶一下第4章中提到的不協調效應)。因此較大程度的意見不同可能會導致更多的改變。同時也存在這種情況:傳達令人不舒服的信息的人可能會遭到別人的懷疑。當人們不贊同一個新聞評論員的論斷時,他們會越發認為他有偏見、不客觀而且不值得信賴。如果論點在人們可接受的範圍之內時,他們似乎會更具有開放性(Lierman & Chaiken,1992;Zanna,1993)。所以也許較嚴重的分歧造成的改變會更小。對於性行為較活躍的人群來說,健康教育者最好提倡更安全的性行為,但是對於性行為本來就不多的人群來說,則不妨提倡禁慾(DeVos-Comby & Salovey,2002)。
阿倫森、特納(Judith Turner)和卡爾斯密斯(1963)由此推論,如果存在一個可信、不容忽視的信息來源 ,那麼一個與信息接收者差異很大 的立場會引發最大程度的觀點改變。很明顯,像愛略特這樣可信度高的人去高度讚賞一首不受歡迎的詩對改變人們觀點的作用要大於他模糊的積極評價。但是,如果是“阿格尼絲,一個密西西比州立師範學院的學生”對你不喜歡的詩進行評價,無論是高度讚賞還是模糊的積極評價對你都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圖7-4顯示了可信度和差異之間的交互作用 :差異大小的影響作用取決於信息傳達者是否具有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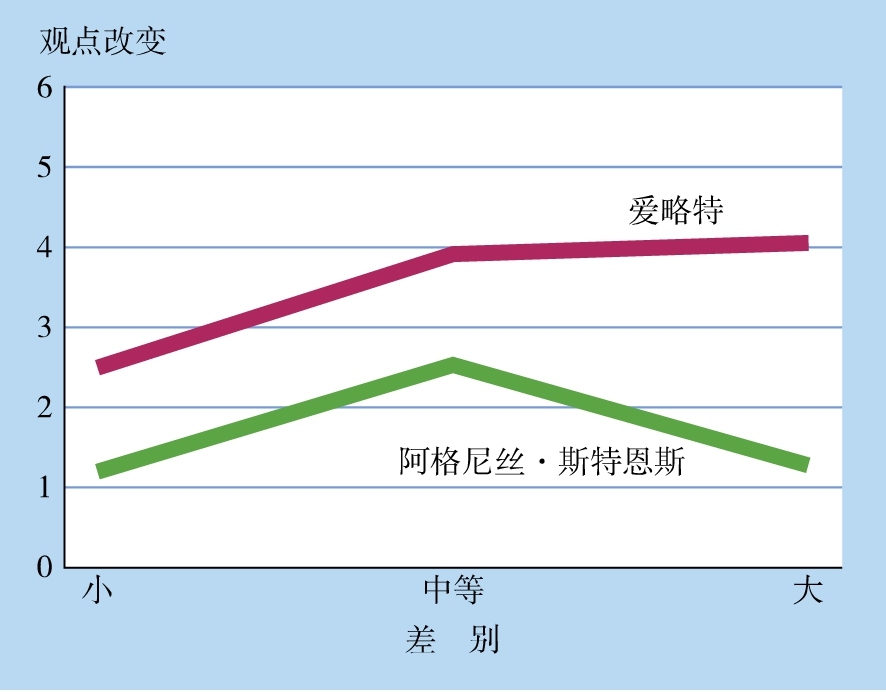
圖7-4 差異和信息傳達者可信度之間的交互作用
當處於一個極端立場時,只有那些高可信度的信息傳達者才最有說服作用。
因此,對於萬達“我是否應該站在一個極端的立場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要視情況而定。在萬達敬仰的父親心目中,她是一個有聲譽而且權威的信息來源嗎?如果是,那麼萬達應該推出一個完整的健身計劃;如果不是,那麼採用一個溫和一點的方案則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取決於萬達的父親在多大程度上會參與到這件事情中來。積極參與者能夠接受的觀點的範圍較小。對他們來說,稍有差異的信息看上去激進而愚蠢,尤其是信息支持的是他們反對的觀點而不是與他們已經接受的觀點相吻合(Pallak & others,1972;Petty & Cacioppo,1979;Rhine & Severance,1970)。如果萬達的父親還沒有考慮或者很關心鍛鍊的問題(而不是完全反對鍛鍊計劃的話),她可以嘗試一個極端一些的立場。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可信度高的權威而且你的聽眾又不十分關心談論的話題,那麼不妨嘗試一下 ,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吧。
單方面說服和雙方面說服
說服者似乎還面臨另外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怎樣處理相反的觀點。在這一點上,我們會再次發現常識無法給我們一個清楚的答案。承認相反的觀點可能會使聽眾感到疑惑並且會削弱自己的觀點。但是,承認相反的觀點也可能使聽眾覺得我們毫無偏見,從而消除他們的戒心。
沃納等人(Werner & others,2002)在一個實驗中顯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雙面信息,其對戒心的消除能夠提高鋁製罐頭盒的回收率。他們在猶他州立大學教學樓的垃圾桶上貼上諸如此類的標籤:“請不要將鋁製罐頭盒投入垃圾箱!!!!!請將其投入一樓入口處的回收箱。”最後,當呈現一個有說服力的信息,同時承認並且迴應了主要的反對觀點時——“這樣做可能會給你帶來不便。但這的確很重要!!”——回收率達到了80%(是沒有任何信息時的兩倍,而且要高於呈現其他信息的條件)。
當德國人在二戰中投降的時候,美國軍隊並不希望他們的士兵因此而放鬆警惕或者認為接下來與日本的戰鬥是很容易的。於是部隊情報和教育中心的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及其同事們(1949)設計了兩段無線電廣播,論證太平洋戰爭至少還將持續兩年。其中一段廣播是單方面的說服,並沒有對相反觀點做出迴應,例如只是應對一方敵人而不是兩方敵人的優勢。而另一段廣播則是雙方面的說服,它提到並且迴應了相反的觀點。如圖7-5所示,信息的效果取決於聽眾。對那些已經持贊成態度的人來說,單方面的論證更有說服力;而雙方面的論證則對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比較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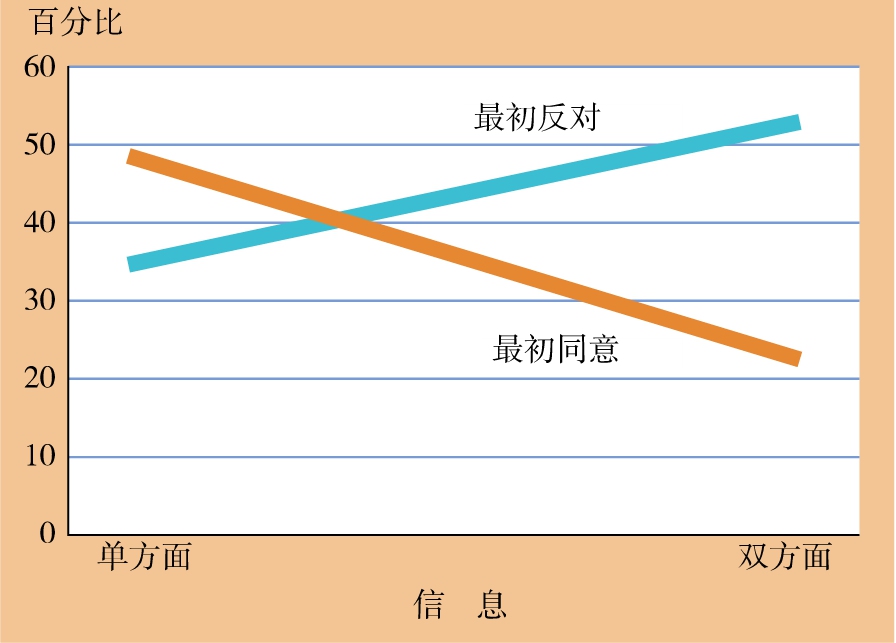
圖7-5 最初觀點和單、雙方面說服的交互作用
德國在二戰中戰敗以後,對日本的實力強大這一信息持懷疑態度的美國士兵更容易被雙方面信息所說服。而對那些一開始就贊成這一信息的士兵,單方面信息對其觀點的強化作用更大。
隨後的一些實驗也發現,如果人們對(或者將對)相反的觀點有所瞭解的話,雙面論證會更具有說服力,並且說服效果更加持久(Jones & Brehm,1970;Lumsdaine & Janis,1953)。在模擬審訊中,如果被告在原告之前就提出不利於自己的證據的話,他就會顯得更具有可信度(Williams & others,1993)。很明顯,單方面的信息會使那些比較聰明的聽眾想到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該信息傳達者持有偏見。因此,一個政治候選人如果面對一個對政治有所瞭解的團體做演講的話,對對立觀點做出一定的迴應顯然更加明智。因此,如果你的聽眾已經瞭解或者有機會了解對立的觀點,你應該進行雙方面的論證。
這種交互作用效應是說服研究的典型代表。對於樂觀者而言,正面說服的效果最好(“按照這個新計劃,只要在課餘時間在校內勤工助學就可以減免學費”)。對於悲觀者而言,負面說服的效果更好(“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在課餘時間進行勤工助學,以此來掙得高額學費”)(Geers & others,2003)。我們可能希望說服的各種變量的效應比較簡單(這樣會使這一章學起來比較容易)。遺憾的是,大多數變量,就像佩蒂和韋格納(Petty & Wegener,1998)提到的那樣,“都具有複雜的效應: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增強說服力,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卻反而會削弱說服力。”
作為學生和科學家,我們信奉“奧卡姆簡化律”(Occam's razor)原則,也就是說,尋找儘量簡單的原則。但是,如果人類的現實生活確實非常複雜的話,那麼我們的原則也應該非常複雜。
首因對近因
請想像你自己是一名傑出政治家的顧問,而這位政治家不久將要就一項有關全球變暖的協議與另一位同樣卓越的政治家進行辯論。在投票前三個星期,每個候選人都需要在晚間新聞中做一個充分準備的演講。抽籤決定你們一方可以選擇是否首先發言。大家都知道你以前學過社會心理學,因此都期待著你提出建議。
你在腦海裡回憶了一下自己所學的課本和筆記。第一個會是最好的一個嗎?人們的預先觀念控制對信息的解釋。況且,某種信念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因此首先表達的觀點可能會不利於人們對隨後的觀點進行沒有偏見的感知和解釋。除此之外,人們似乎總是格外關注最早出現的事物。而從另一方面來講,人們似乎對最近發生的事情印象最深。那麼,最後一個發言效果會不會更好呢?
你最初的推理過程就體現了一種最普遍的現象,即首因效應 (primacy effect):最先出現的信息最具說服力。第一印象很重要。舉例來說,你能感覺出以下兩種描述之間的差異嗎?
約翰聰明,勤奮,做事衝動,愛挑剔,頑固而且忌妒心很強。
約翰忌妒心強,頑固,愛挑剔,做事衝動,勤奮而且很聰明。
當阿施(1946)將這些句子呈現給紐約的大學生時,那些按照聰明—妒忌心強 順序閱讀這些形容詞的人對約翰的積極評價要多於那些按照妒忌心強—聰明 的順序閱讀的人。最先出現的信息似乎影響了他們對後來信息的加工,由此產生了首因效應。類似的效應也出現在一個有關猜測任務的實驗中,其中每個人猜對的概率都是50%。但是那些在前一半猜測中正確率較高的人比後一半正確率高的人看起來能力更強(Jones & others,1968;Langer & Roth,1975;McAndrew,1981)。
是否像判斷問題那樣,首因效應也是說服過程的規律呢?米勒和坎貝爾(Miller & Campbell,1959)給西北大學的學生看一份縮簡過的民事訴訟文件。他們將原告的證詞和觀點放在一組,被告的證詞和觀點放在另一組中。學生們都要閱讀這兩組文件。一個星期後,當要求他們表明自己的立場時,大部分人都站在他們首先閱讀的那組文件一方。那麼,另外一種可能性是什麼呢?我們可能都體驗過這樣一句諺語所描述的情形:“在有其他人站出來並反覆檢驗之前,首先說話的人看起來總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對最近信息更好的記憶會不會造成近因效應 (recency effect)呢?從我們的經驗中(還有某些記憶實驗中)可以體會到,對當前事件的記憶總是比過往事件的記憶要更深一些。為了驗證這個現象,米勒和坎貝爾給另一組學生也閱讀了其中一組證詞。一個星期之後,研究者又讓他們閱讀了另一組證詞,並且要求他們立即表明自己的立場。結果跟前一個實驗正好相反:近因效應出現了。很明顯,第一組證詞經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記憶中消退了。
遺忘在兩種情況下會造成近因效應:(1)當時間長到足夠分離兩種信息,同時 (2)聽眾在接受第二種信息後立即表態時。如果兩種信息依次連續呈現,並且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此時就會出現首因效應(如圖7-6),尤其是在第一種信息引發了思考的情況下更是如此(Haugtvedt & Wegener,1994)。那麼現在你會給你的政治辯論家提供什麼樣的建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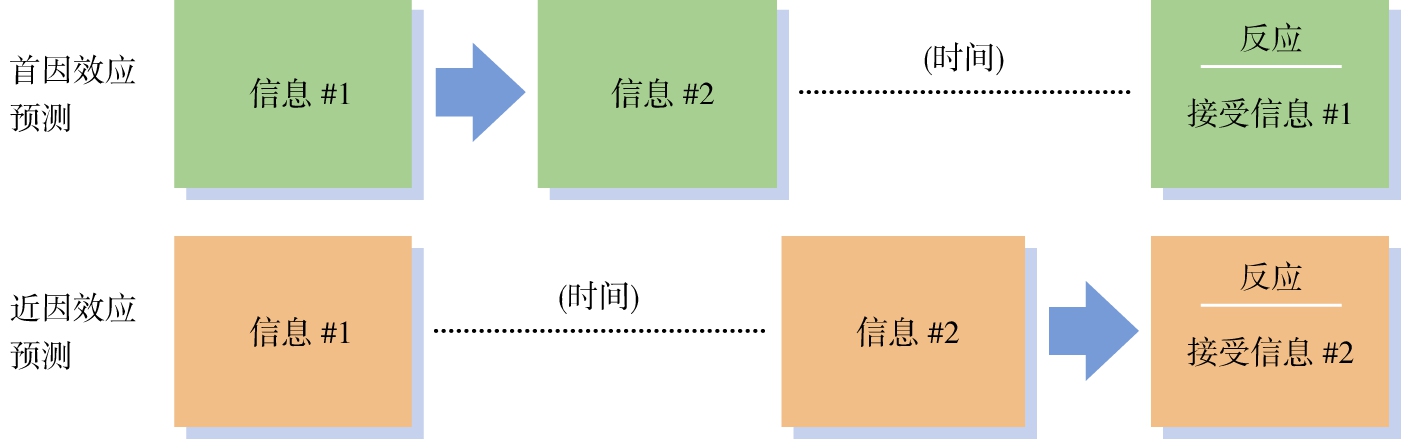
圖7-6 首因效應和近因效應
如果兩種信息接連出現,並且聽眾經過一段時間後再做反應,那麼首先出現的信息最有利(首因效應)。如果兩種信息在時間上是分離的,而要求聽眾在聽完第二種信息後立即判斷的話,那第二種信息最有利(近因效應)。
怎麼說?溝通渠道
在第4章中,我們曾經提到,行為塑造了我們的自我概念。當我們做出行動時,我們會將過去行為背後隱藏的觀念放大,當我們感覺到責任感的時候尤為如此。同時,我們也會注意到,那些植根於經驗的態度要持久得多,對我們行為的影響也更大。和那些被動形成的態度相比,以經驗為基礎的態度更自信、穩定,並且在面對攻擊的時候也不會那麼脆弱。
然而常識心理學總讓人們相信書面文字的力量。為了讓人們知道一起發生在校園裡的事件,我們會貼告示;為了讓司機們減速駕駛並且注意行駛的道路,我們會在廣告牌上寫上“小心駕駛”的字樣;為了勸阻學生們不要在校園裡亂扔垃圾,我們則會用反對亂扔垃圾的信息填滿公告牌和信箱。
人們很容易就能被說服嗎?看一看以下兩個出於善意的例子吧。在加利福尼亞的斯克里普斯學院,為期一週的反垃圾運動向學生們提出了“保持斯克里普斯校園的美!”、“讓我們徹底清除垃圾!”等要求。每天早晨學生們的信箱裡滿是這些口號,貼在全校園最顯眼的海報欄上。在這個活動開始的前一天,社會心理學家帕洛特茲安(Paloutzian,1979)在一個行人較多的人行道的垃圾桶旁邊扔了一堆垃圾。然後他退到一旁記錄了180個過路人的行為。結果沒有一個人撿起這堆垃圾。在活動的最後一天,他又重複了這個實驗,觀察了另外180名過路人。那麼現在的行人是否會爭相響應那些呼籲呢?答案是幾乎沒有。180人中只有2個人撿起了垃圾。
主動參與還是被動接受
口頭的呼籲是否更具有說服力呢?那也並不一定。我們中那些需要在公眾場合發言的人,比如教師或者說客,常常因為沉醉於自己的言論而高估了它們的力量。當詢問一個大學生他們大學生活中哪些方面的經歷最有價值,或者在他們第一年的大學生活裡,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時,我不無遺憾地說,幾乎沒有人會回憶起我們這些老師所記得的那些精彩的講課。
克勞福德(Crawford,1974)及其同事們在研究口頭語言的影響力時,對正要去十二個教堂聽佈道以及剛聽完佈道回到家中的人們進行上門訪談,其佈道的內容是反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在第二次面談中,當詢問他們是否在前一次面談之後聽到或者讀到過某些有關種族偏見或歧視的信息時,只有10%的人自發地回憶起佈道的內容。而剩下90%的人,當直接詢問他們牧師在“上兩個星期中,有沒有提到過偏見和歧視”時,30%以上的人否認聽過這樣的佈道。最後的結果是:佈道並沒有改變人們對於種族問題的態度。
如果你停下來仔細想一想的話,會發現一個卓有成效的傳教士必須克服很多阻礙。如圖7-1所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演說者不僅要傳達能夠引起聽眾注意的信息,還要使他的觀點容易理解、具有說服力、容易記憶,並且使人心悅誠服。一個深思熟慮的呼籲必須同時考慮到說服過程中所有這些步驟。
被動接受的信息也不總是無效的。在我的藥店裡,有兩個牌子的阿司匹林,其中一個牌子做過很多廣告而另一個牌子則沒有做廣告。除了在口中分解的速度有細微的差別以外,任何藥劑師都會告訴你兩種牌子的藥實質上是完全相同的。阿司匹林就是阿司匹林。你的身體並不能分辨出他們的差別,但是你的錢包卻可以。做過廣告的阿司匹林以沒有做過廣告的三倍的價錢賣給了成千上萬的人。
擁有這樣一種力量的媒體是不是可以幫助一個富有的政治候選人用錢贏得選舉呢?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活動中,那些花錢越多的候選人贏得的選票也越多(Grush,1980)。媒體的宣傳使一個不為人知的候選人變得家喻戶曉。就像我們將在第11章見到的那樣,僅僅是暴露在不熟悉的環境刺激中,就可以引起偏好。就像“水銀比銅的沸點高”這樣的觀點,如果在一個星期前就讀到過並已做出評價的話,則人們會認為它們更加可信。阿克斯(Arkes,1991)指出這些結果很讓人恐慌。就像政客們所知的那樣,看上去可信的謊言能取代證據確鑿的事實,重複的陳詞濫調可以掩蓋複雜的現實。
僅僅是對某種陳述的簡單重複就有助於增強其流利程度——這對我們的舌頭來說是易如反掌——從而增強它的可信度(McGlone & Tofighbakhsh,2000)。像押韻這樣的因素也會增強其流利程度,以及可信度。“多姿多彩可以避免讓人生厭”和“變化可以避免讓人生厭”基本上表達的是同一件事,但是前者看起來更加真實。任何增強流利程度的因素(熟悉性和押韻),都有利於增強可信度。
那麼媒體對一些重大問題和廣為人知的候選人是否也具有這樣的影響力呢?歐洲人所看到的伊拉克戰爭和展示給美國人的戰爭是不同的,因此他們形成了不同的態度。但是研究者們反覆觀察研究發現,政治宣傳在最終大選時對選民的態度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儘管事實是,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很小的影響力就可能徹底改變選舉的結果)(Kinder & Sears,1985;McGuire,1986)。[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數人都同意大眾傳媒能夠對態度產生影響——但影響的是別人而不是他們自己 (Duck & others,1995)。]
既然被動接受的信息有時有效而有時無效,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預先確定欲要說服的相關話題呢?這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法則:隨著觀點熟悉性和重要性的增加 ,被動說服的影響力越來越小 。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例如購買哪個牌子的阿司匹林,媒體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但在那些人們更熟悉並且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在一個種族關係緊張的城市裡,試圖改變人們對於種族問題的態度,就像是要搬一架鋼琴上山那麼困難。雖然這並非不可能,但也決不是一蹴而就的。
個人與傳媒的影響
關於說服的研究表明,對於我們而言,最主要的影響不是來自於傳媒,而是我們和他人之間的接觸。下面以兩個現場實驗來證實個人影響的力量。幾年前,艾德斯威爾德和道基(Eldersveld & Dodge,1954)曾經研究了密歇根州Ann Arbor地區的政治說服。他們把那些不想為修訂城市憲章投贊成票的市民們分成三組。其中一組的所見所聞僅僅限定於大眾傳媒的範圍內。在這一組中,19%的人改變了他們的初衷,並在選舉那天投了贊成票。第二組的市民們收到了4封支持修訂的郵件,結果發現,45%的人投了贊成票。而對第三組的市民進行私人拜訪,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勸說,結果發現75%的人為憲章修訂投了贊成票。
在另一個現場實驗中,一個由法夸爾和麥科比(Farquhar & Maccoby,1977;Maccoby & Alexander,1980;Maccoby,1980)率領的研究小組試圖減少加利福尼亞三個小型城市中的中年人心臟病的發病率。為了考察個人和傳媒影響相比哪一種方式更有效,他們在項目開始前以及在隨後三年中每一年年底都對其中的1200人進行拜訪和醫療檢查。加利福尼亞特雷西地區的居民除了當地常規的傳媒以外沒有接受別的說服主張。在加利福尼亞的吉爾羅伊地區,一項為期兩年的多媒體宣傳活動主要採用電視、廣播、報紙以及郵件等方式告訴人們冠心病的危險以及降低發病率的方法。而在加利福尼亞的沃森維爾,除了採用多媒體的方式以外,還運用另外一種方式作為補充,即對三分之二的在血壓、體重以及年齡上處於高危人群的人進行私人接觸。依照行為矯正的原則,研究者幫助人們設立明確的目標並對其成果加以強化。
如圖7-7所示,在一年、兩年、三年以後,特雷西地區的高危人群(作為控制組的城鎮)還處於和原來相差無幾的危險狀態。吉爾羅伊地區那些被諸多傳媒信息所淹沒的高危人群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健康習慣,降低了患病的風險性。而沃森維爾地區那些既受到傳媒影響,同時還接受私人接觸的人們,其改變最為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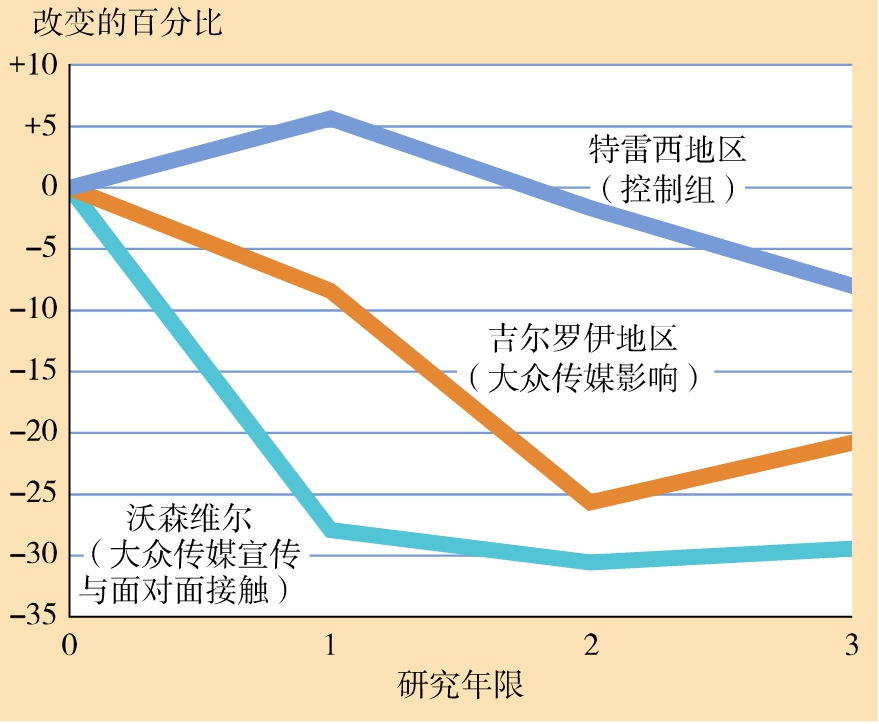
圖7-7
患冠心病的風險性與基線水平(0)相比,經過一年、兩年或三年健康教育後的百分比變化。
資料來源:Data from Maccoby,1980.
你是否意識到在你的生活經歷中個人具有的強大影響力?大多數大學生都回憶說他們從朋友以及其他同學那裡所學到的東西要多於從書本和教授那裡所學到的。教育研究者證實了學生們的直覺:課堂外的人際關係對大學生的身心成熟有重要的影響(Astin,1992;Wislon & others,1975)。
儘管面對面接觸的影響通常比媒體的影響要大,但我們還是不能低估媒體的作用。那些能夠對我們造成影響的個人,他們的想法必然有一定的來源,而這些來源往往就包括媒體。卡茨(Katz,1957)觀察到,多數媒體影響都是通過溝通的兩步流程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來起作用的,即從媒體到其意見有影響力的人、再到普通群眾。假如我要評估電腦配件,我會聽從兒子的意見,而他的大部分想法就是來自於那些宣傳材料。
溝通的兩步流程模型提醒我們,媒體正在以一種微妙的方式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即使媒體對人們的態度不會產生直接影響,但它們仍然會以間接的方式對人們產生影響作用。就算是那些少數沒有看過電視的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仍然會受到電視的影響。如果不是像隱居者一樣生活,他們還是會在學校操場上參加從電視上模仿來的遊戲活動。他們會向父母們索要同伴們都有的和電視內容有關的玩具。他們會懇請或要求觀看自己的朋友們都喜歡的電視節目。父母們可以直截了當地拒絕,但卻無法消除電視對孩子們的影響。
對所有的媒體泛泛而談,從大批量的郵件到電視,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做法。對不同媒體形式的比較研究表明,媒體越貼近生活,其信息就越具說服力。因此,說服力從大到小排列應該是:現場、錄像、錄音和文字。然而,文字形式的信息通常其理解 和回憶 的效果最好,這使得情況更為複雜。理解是說服的基礎步驟之一(請回顧圖7-1)。柴肯和伊格利(1976)認為,如果一條信息難於理解,那麼用文字形式表達時其說服的效果會最佳,因為讀者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閱讀速度來接受信息。研究者們給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們提供文字、錄像和錄音等不同形式的簡單易懂或複雜難解的信息。結果如圖7-8所示:難度較大的信息以文字方式呈現時的確最具說服力,而簡單的信息則以錄像呈現時效果最佳。是電視媒體,而不是觀眾,控制著信息傳遞的節奏。通過將人們的注意力從信息本身轉移到傳遞者,它也令人們更關注像播音員的吸引力這樣的外周線索(Chaiken & Eagly,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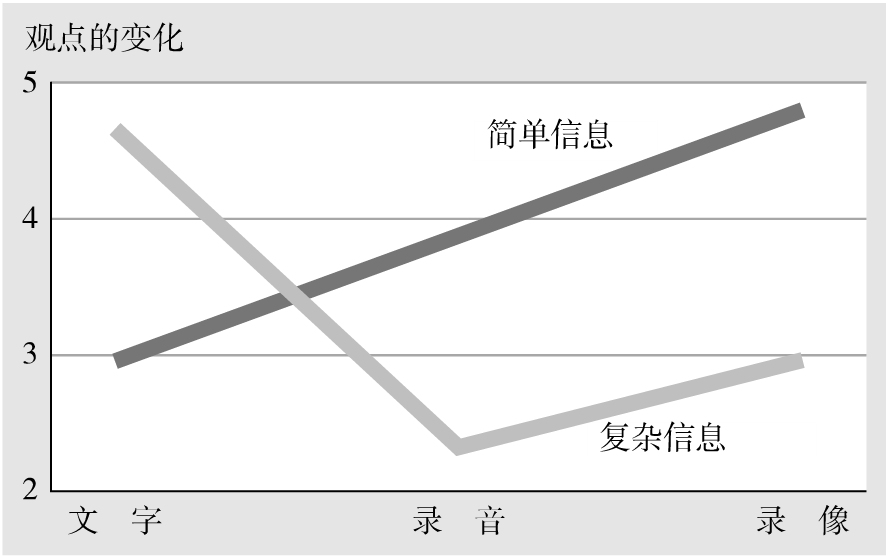
圖7-8
容易理解的信息以影象形式呈現時最具有說服力。而難於理解的信息則以書面形式呈現時效果最佳。因此,在說服的過程中,信息的難易度和媒體形式會產生交互作用。
資料來源:Data from Chaiken & Eagly,1978.
對誰說?聽眾
就像在第6章裡我們看到的那樣,個體的特質通常無法預測他們受社會影響後做出的反應。某種特定的特點可能會使說服過程的某一個環節得到加強,但可能卻會阻礙另一個環節。以自尊為例:自尊水平較低的個體理解信息的速度通常較慢,因此難以說服。但是,那些自尊水平高的人理解信息之後往往還是堅持己見。於是便得出結論:中等自尊水平的人們最容易受到影響(Rhodes & Wood,1992)。
讓我們再來考慮信息接收者的另外兩個特徵:年齡和思維的縝密性。
他們有多大年齡
隨著年齡的變化,人們傾向於持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態度。社會心理學家對這種差別做出了兩種解釋。一種是“生命週期理論 ”:態度隨著人們的成長而逐漸改變(例如,變得更為保守)。另一種是“生活時代解釋 ”:人們年紀大時所持有的態度和他們年輕時基本沒什麼兩樣;由於這種態度和當今那些年輕人的態度不同,代溝由此而產生。
現有的大多數證據都支持生活時代解釋。在對年輕人和年長者長達數年的多次訪談中發現,年長者的態度相對於年輕人來說較少改變。如同戴維·西爾斯(Sears,1979,1986)評價的那樣,研究者們“幾乎只發現了生活時代效應,而沒有發現生命週期效應”。
年紀大的人不夠靈活,但是五六十歲的人們通常會持有比他們在三四十歲時更開放的性觀念以及種族觀念(Glenn,1980,1981)。我們中很少有人能絲毫不受社會文化規範變化的影響。此外,維瑟和克羅斯尼克(Visser & Krosnick,1998)的研究指出,接近生命盡頭的年長個體,大概由於其自身態度的強度有所減弱,可能又會容易受到觀念改變的影響。
然而,十幾歲以及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處於非常重要的人生時期(Kronsnick & Alwin,1989),此間形成的態度很可能到中年都一直保持穩定。因此,應該對年輕人加以指導,引導他們慎重選擇自己的社會影響因素——包括他們所加入的組織、所關注的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等等。
佛蒙特州本寧頓(Bennington)大學提供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範例。從20世紀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期之間,本寧頓的學生,即那些來自保守的特權家族的女學生們,在一位左翼年輕教員的帶領下,處於一種思想開放自由的環境氛圍中。該校的一名教授,社會心理學家紐科姆(Theodore Newcomb)後來否認那位教員曾試圖在學生中培養自由主義者。但是那位教員真的成功了。這些學生們比那些來自同樣社會背景的典型人物代表要開放得多。另外,這種在本寧頓形成的態度會一直保持很久。半個世紀過去了,本寧頓的女生,現在已經年過七旬了,她們在1984年的總統選舉中以3:1的優勢支持民主黨,而其他當年受過大學教育的七旬婦人們則以3:1的優勢支持共和黨(Alwin & others,1991)。可見,這些在人生重要時期信奉的觀點影響了她們一生。
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經歷有利於其人格定型的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能夠給個體留下深刻和持久的印象。舒曼和斯科特(Schuman & Scott,1989)要求人們說出半個世紀以來一兩件最重要的國內或國際事件,結果發現他們所回憶起的大部分事件都發生在其十幾、二十歲間。對於那些在16~24歲期間經歷過經濟大蕭條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這些事件的影響大大超過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人權運動以及肯尼迪遇刺事件,60年代晚期的越南戰爭和登月成功以及70年代的女權運動。因此,我們或許可以預測今天的年輕人會將像電子郵件、互聯網以及“9.11”這樣的現象看成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
他們在想些什麼
說服過程的關鍵因素不在於信息本身,而在於它所激發個體的思維反應方式。我們的大腦並不像海綿一樣能吸收乾淨所有傾入其內的東西。如果信息喚起了我們偏好的想法,那它就會說服我們。如果它促使我們想起相反的觀點,我們可能就會固執己見。
預先警示可能會有一場說服戰——假如你很在乎辯駁的話 什麼樣的環境會引發辯駁呢?其一是警示可能有人試圖說服你。如果你不得不告訴家人你想退學,你很可能已經預料到他們會勸說你應該繼續完成學業。於是你可能需要準備好一系列的論點來應付所能想像到的他們可能會提出的所有觀點。
弗裡德曼和西爾斯(Freedman & Sears,1965)證實了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說服人們的難度。他們警示一組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說他們將要聽到一場演說:“為什麼不準年輕人駕車”。結果發現這些預先被警示過的學生們沒有改變原先的想法,而那些預先沒有被警示過的學生則發生了改變。在法庭上也是如此,辯護律師有時會在原告出示證據之前提醒陪審團。對模擬陪審團來說,這種“先聲奪人”中和了它自身的消極影響(Dolnik & others,2003)。
對態度進行悄悄攻擊對於那些積極參與的人們尤為適用。提前幾分鐘發出預警,那些積極參與者便會準備好抵禦(Chen & others,1992;Petty & Cacioppo,1977,1979)。當事先被警示過的人們認為某種觀點是微不足道的時候,那麼哪怕是在收到這種信息之前也往往會表示同意,以免事後容易上當受騙(Wood & Quinn,2003)。
分心會減少辯駁 當人們的注意力被別的東西吸引並阻礙其反駁時,言語的說服效果會得到加強(Festinger & Maccoby,1964;Keating & Brock,1974;Osterhouse & Brock,1970)。政治宣傳通常會利用這項技術。一方面,廣告中的聲音文字為候選人做宣傳,而另一方面,畫面卻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無暇分析那些文字。當信息較為簡單的時候,分心的效果尤為顯著(Harkins & Petty,1981;Regan & Cheng,1973)。
不積極參與的聽眾會使用外周線索 回顧一下說服的兩條途徑——系統思考的中心途徑以及啟發式線索的外周途徑。正像穿越城鎮的側路一樣,中心途徑在思維分析觀點以及做出反應時會出現起止點。而外周途徑則載著人們直達目的地,就像環城高速公路那樣。思辨性強的個體表現出強烈的認知需求 (need for cognition),喜歡仔細思考並偏好中心途徑(Cacioppo & others,1996)。而那些喜歡節省自己腦力資源的個體則表現出較低的認知需求,通常對於外周線索反應較快,比如信息傳達者的吸引力以及周圍環境的舒適度,等等。
但是觀點本身也很重要。我們所有人都會同那些與自身有關的問題糾纏不休,而同時對於無關緊要的事情迅速做出判斷(Johnson & Eagly,1990)。當我們在頭腦裡對一個重要問題深思熟慮時,論點以及我們自身的想法會決定我們的態度(如圖7-9,上半部分)。如果事情看起來無關緊要,像該信息的專業與否之類的外周線索對我們態度形成的影響比信息觀點的力量更大(如圖7-9,下半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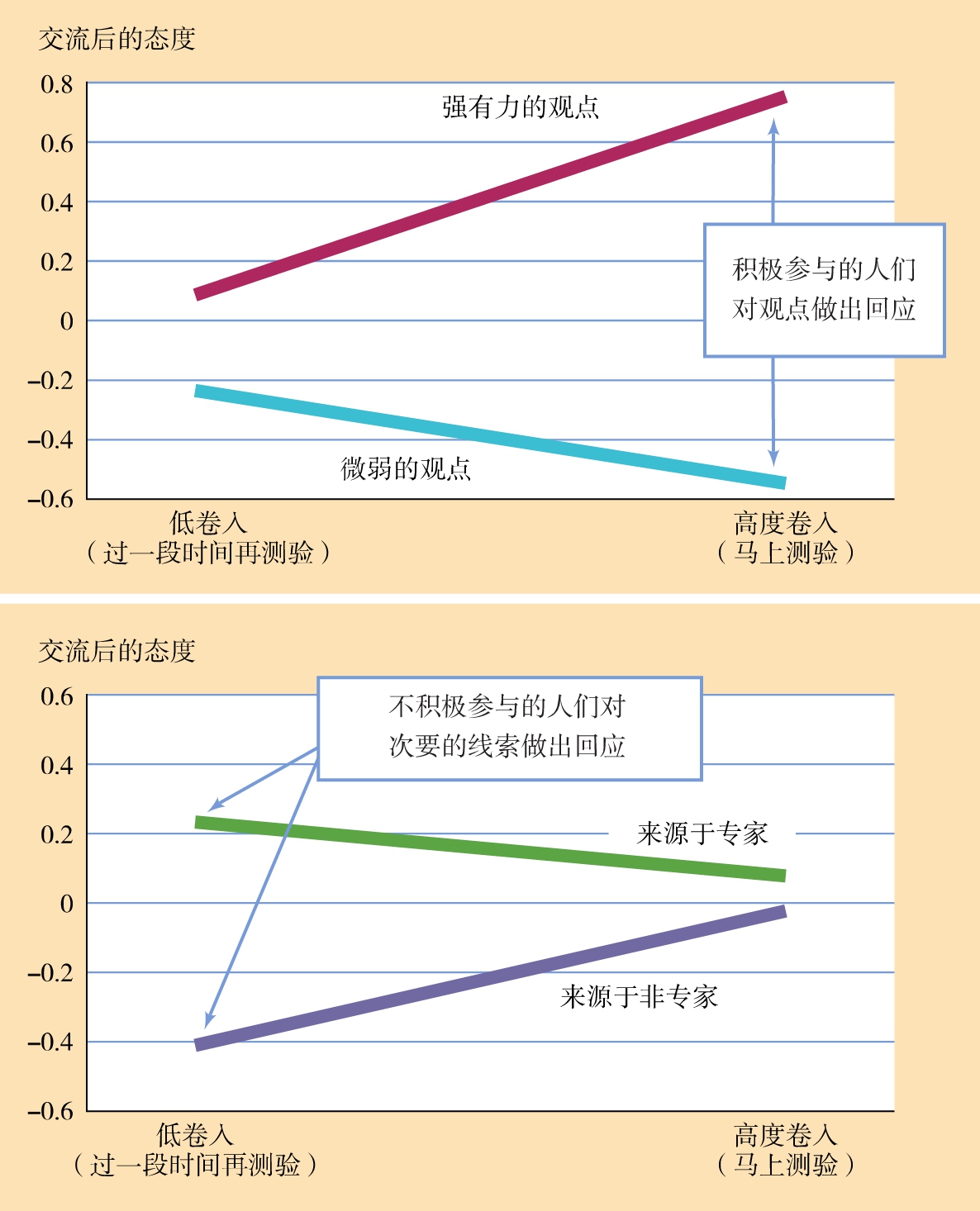
圖7-9 改變態度的中心途徑和外周途徑
中心途徑:當積極參與的大學生們聽到一條很有說服力的消息,即主張畢業前進行一次專業考試時,他們發現微弱的觀點沒有說服力,而強有力的卻很讓人信服(上半部分)。
資料來源:From R. E. Petty,T. J. Cacioppo and R. Goldman,“Personal Involvement as a Peterminant of Argument-Based Persua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1981,pp.847-855.
對信息做出反應時我們的想法很關鍵 ,當我們在某種動機的引發下並且有能力考慮信息時尤其明顯——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理論,能夠有利於我們解釋許多研究發現。例如,如果我們採用外周途徑,就會更容易相信那些可信賴的專家式的傳達者。當我們信賴信息源的時候,我們會想到那些有利的觀點,同時不大可能進行反駁。而對信息來源的懷疑則會使我們更可能採用中心途徑。如果我們不相信銷售人員,就可能會批判性地思考他們的銷售腔調。
根據這一理論我們提出了許多預測性觀點,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佩蒂、卡喬波等人的證實(Axsom & others,1987;Harkins & Petty,1987;Leippe & Elkin,1987)。許多實驗研究探索了激發人們思考的方法——使用反問句 ;使用多個演說者 (例如讓三個演說者各自敘述一個觀點,而不是由一個演說者敘述三個觀點);使人們感覺自己有責任 對信息進行評價和傳達;使用放鬆的姿勢 而不是站姿;重複 信息以及吸引人們集中注意力 ,等等。他們使用這些方法得出的一致結論是:激勵思考可以使強有力的信息更具說服力,並且(由於反駁的影響)微弱的信息不大具有說服力。
該理論同樣也具有現實意義。有效的信息傳達者不僅應該注重自己的形象以及所傳達的信息,還應該注重聽眾可能會出現的反應。最好的教師總是能夠鼓勵學生們積極思考。他們以反問的方式提出問題,舉出引人入勝的範例,還會用難題挑戰學生。所有這些技術都可能使信息沿著中心途徑來達到說服的目的。當課堂講授沒什麼意思時,你可以建立自己的中心加工過程。如果你對那些材料加以思考並仔細分析的話,你很可能會把那門課學得更好。
在1980年那次激烈的總統競選的最後日子裡,里根成功地使用了反問句並使選民們頭腦中產生如他所願的想法。總統競選辯論的總結性陳述中,他以兩個強有力的反問句開頭,並且在剩下一個禮拜的競選過程中經常反覆地提到這些問題:“你們是不是比四年前更富有呢?你們在商店裡購物時是不是比四年前更輕鬆呢?”許多人持否定答案,然後里根大獲全勝,其中有一部分功勞來自於他引導人們選擇了中心途徑法。
小結
什麼因素會使說服有效呢?研究者們考察了四個因素:傳達者、信息、溝通渠道以及聽眾。
誰是發言者? 可信的傳達者給人的感覺就是值得信賴的專家。那些講話語氣果斷、語速較快並直視聽眾眼睛的人通常較為可信。那些持與個人利益相悖觀點的人也會讓人產生同樣的感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信息傳達者在品位和個人價值方面也非常有效。
說了些什麼? 當一條信息與好心情聯繫起來的時候會更有說服力。人們在情緒好的時候一般會做出更為爽快、不假思索的判斷。而一些引起恐懼心理的信息也同樣有效,如果信息接收者能夠採取預防行為的話,則更是如此。
一種信息與聽眾已有觀念之間會產生怎樣的差異,取決於傳達者的可信度。而究竟是單方面信息還是雙方面信息更有說服力取決於:如果聽眾已經贊成該信息,而且過後不大可能會考慮相反的意見,那麼單方面的觀點可能更有效。而當聽眾心思較為縝密或者並不贊同該信息時,那麼包含正反兩方面的信息則更為有效。
當涉及某個問題的正反兩方面時,觀點出現的哪種順序會更有優勢呢?最具普遍性的結論是首因效應。但是如果觀點之間存在時間間隔,那麼較早呈現的信息作用會減小;如果在第二條信息呈現完後立即做出判斷,那麼對於該信息的印象還很清晰,很可能會出現近因效應。
溝通渠道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是如何被傳達和交流的。面對面的溝通交流通常都是最有效的。然而對於複雜難懂的信息來說,書面文字媒介則是卓有成效的。當問題無關緊要(例如該買哪個牌子的阿司匹林)或情境比較陌生(如在兩個不知名的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時,大眾傳媒則較為有效。
聽眾 最後,信息的接收者也很重要。聽眾們接收信息的時候會想些什麼呢?他們是在考慮有利的想法還是想做出反駁?他們是否被事先警示過了?此外聽眾的年齡也有影響作用。對人們做過長期反覆調查的研究者們發現,年輕人態度的穩定性較差。
現實生活中的說服:邪教是如何進行精神灌輸的
“新宗教運動”(邪教)利用的是何種說服和團體影響的原則呢?
1997年3月22日,馬修·阿普爾懷特以及他的37名信徒認定,擺脫自己那僅僅是“容器”的身體,乘緊隨哈雷彗星之後的飛碟通往天堂之門的時刻到了。他們將催眠劑摻在布丁或蘋果醬裡,用伏特加酒沖服來使自己入睡,並用塑料袋綁住頭部,以便自己能夠在睡眠中窒息。同一天,在一個叫聖卡西米爾的法裔加拿大人村莊裡,一棟農舍發生爆炸,5人死亡——他們是散佈在加拿大、瑞士和法國的74名太陽神教徒中的最後幾位。這些人都希望自己能夠被送到9光年以外的天狼星上去。
許多人都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是什麼使得人們拋棄了以往的信仰,而加入這一禁錮精神的團體呢?我們是把他們的詭異行為歸因於奇特的人格呢?還是說他們的經歷正體現了社會影響以及說服之間正常的動態變化?
請牢記以下兩點。首先,這些都只是事後的分析。這只是在事件發生之後,使用說服原則作為歸類範疇來解釋那些引人入勝同時也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其次,從對人們信仰的解釋 上我們無法知道其信仰的真實性 。那在邏輯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宗教心理學可能會告訴我們為什麼 有神論者相信上帝而無神論者卻不相信上帝,但是它不能告訴我們哪一方是正確的。對任何一種信仰作出解釋並不是對它進行辯護。所以如果有人試圖對你的信仰提出質疑,並說道:“你相信那個是因為……”,你可能會想到大主教坦普爾(William Temple)對一個挑釁者的答覆。那人說:“那麼,當然,大主教,問題是你相信自己的信仰是因為你是在那種方式下長大的。”大主教答道:“這也有可能。但是,你說你認為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信仰是因為我是在那種方式下長大的,真實原因也有可能是你也是在那種方式下長大的。”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一些邪教組織 (cults)——有些社會學家更願意稱其為“新宗教運動 ”——已經引起了公眾注意:文鮮明(Sun Myung Moon)的統一教團 ,瓊斯(Jim Jones)的人民聖殿教 ,科瑞什的(David Koresh)的大衛分支教 (Branch Davidians),以及阿普爾懷特的天堂之門。
文鮮明將基督教、反共思想以及對他自己的讚頌混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彌賽亞,在世界範圍內吸引了眾多追隨者。文鮮明宣稱:“我的願望就是你的願望”;許多人對此積極響應,把身家性命以及全部財產都獻給了統一教團。
1978年在圭亞那,914名從舊金山追隨而來的瓊斯信徒,遵照他的命令,集體服下了摻有鎮靜劑、止痛劑以及致命氰化物的葡萄汁自殺身亡,全世界為之震驚。
1993年,高中輟學的科瑞什利用他對經文超強的記憶力以及對人們催眠的天賦,控制了一個叫做大衛分支教的教派。一段時間之後,教派成員們慢慢交出了自己的銀行存款以及財產。科瑞什還說服男人們應過獨身生活,而他卻和他們的妻子及女兒上床,並且使他的19名“妻子”相信她們應當為他生兒育女。在一場槍戰中,6名教派成員和4名聯邦警員遇難,之後他們遭到了圍攻。科瑞什告訴他的追隨者說他們不久就會死去,並且和他一起直接升上天堂。聯邦警員們用坦克撞擊該建築物,試圖噴放催淚瓦斯,但襲擊結束時,還是有86人在大火中喪生,建築物也被摧毀。
阿普爾懷特卻沒有同樣的性興趣。由於和學生髮生同性戀行為而兩次丟掉音樂教師的工作,之後,他和另外17名與他一起死掉的天堂之門成員中的7個,通過閹割來追求一種無性的宗教虔誠(Chua-Eoan,1997;Gardner,1997)。1971年,在一所精神病院裡,阿普爾懷特和護士同時也是宇航愛好者的內特爾斯相識,內特爾斯向熱切而具有感召力的阿普爾懷特指出了以一種宇宙哲學的視角看待通往“下一個層次”的途徑。通過滿懷激情的鼓吹說教,他說服他的追隨者們與家庭斷絕關係、禁止性生活、停止使用藥物並散盡個人錢財,並承諾用宇宙飛船拯救他們。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是什麼讓這些人如此地俯首貼耳?我們能通過責備受害者來得出有關性格特質的解釋嗎?我們應該把他們看做易上當的傻瓜或是啞巴怪人嗎?或者說那些我們熟悉的從眾、順從、失調、說服以及團體影響的原則也可以用來解釋他們的行為——把他們放在和我們相同的層面上,以這些影響因素來對他們作出解釋?
態度依從行為
就像在第4章裡我們反覆提到的那樣,人們通常會內化那些自動、公開和反覆做出的行為。邪教的領導者們似乎深諳此道。
順從導致了接納
新的皈依者們很快便會認識到成員身份並非無足輕重。他們很快就會被塑造成為組織內的活躍分子。邪教組織裡的典禮儀式以及公開的遊說和籌款,可以強化那些新成員對成員身份的認同感。在一些社會心理學實驗中,人們逐漸相信那些他們親眼所見的事情(Aronson & Mills,1959;Gerard & Mathewson,1966),所以,邪教中的新成員也會成為有責任感的擁護者。個人責任感越強,他們就越想去證實這一點。
登門檻現象
我們是怎樣被誘導做出承諾的?人們很少會突然、有意識地下決定。我們通常不會立即決定說:“我要和主流宗教決裂,去尋找一種邪教”。而那些邪教的徵募者也不會在大街上見著一個人就說:“嗨!我是統一教團的成員,你願意加入我們嗎?”相反,他們的徵募策略恰恰利用了登門檻技巧。統一教團的徵募者會請人們吃飯,並且度過一個充滿溫馨友情的週末,共同談論生活的哲學。週末結束時,他們會邀請那些參與者和他們一起唱歌、活動和討論。然後,力勸那些有可能入會的人蔘加訓練性的宗教靜思。最後,那些活動逐漸變得越來越艱鉅——懇求捐獻財物以及試圖改變他人。
瓊斯同樣也是利用了這種登門檻技巧。心理學家奧恩斯坦(Ornstein,1991)回憶道,他曾經聽過瓊斯說起自己引人入道的成功經歷。和那些為窮人謀利益的募捐者不同,瓊斯的工作人員可能只會要求路人“花五分鐘幫忙封好並郵寄一些信件”。做完這些事情之後,瓊斯解釋說:“他們會回來索要更多的東西。你知道,一旦我選上誰,我能讓他做任何事。”
一旦加入邪教後,教徒們往往會自願捐出自己的財物。瓊斯最初提出的是10%收入捐贈制,不久便漲為25%。最後,他要求成員上交他們的所有財產。工作量同樣也變得越來越大、勞神費力。曾是邪教成員的斯道恩回憶了這段漸變的過程: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就是瓊斯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你會慢慢地放棄一些東西同時忍受得也越來越多,但這些都是一步一步進行的。那是很奇妙的一種感覺,因為你可能偶爾會坐起來感慨到:哇喔,原來我可以放棄這麼多東西!我確實忍受了許多。但是這種節奏如此緩慢,以至於讓你覺得既然已經做了這麼多了,再多做一點又何妨呢?(Conway & Siegelman,1979,p.236)
有說服力的因素
我們也可以用本章中討論過的因素(在圖7-10中作了總結)來分析邪教的說服過程:誰 (傳達者)對誰 (聽眾)說了什麼 (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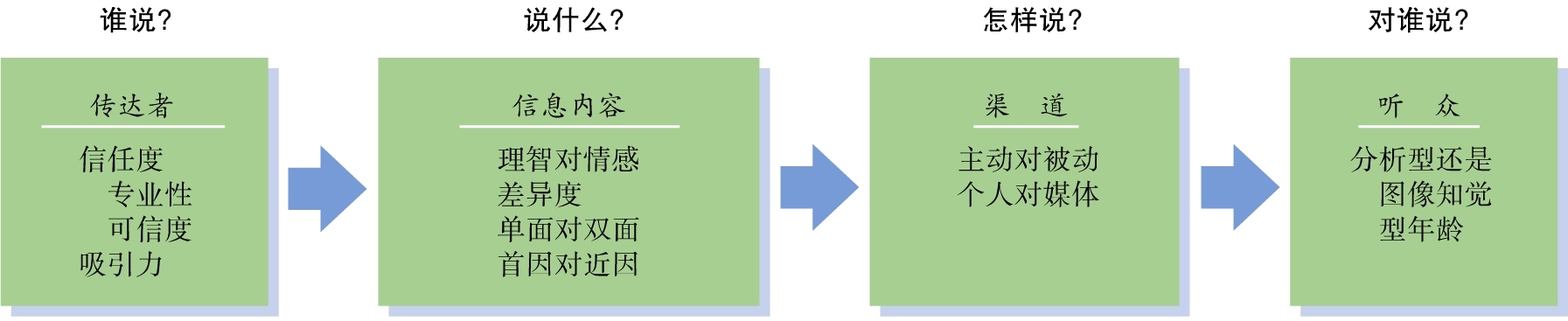
圖7-10 已知的對有說服力的交流過程產生影響的變量
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變量之間可能會產生交互作用;一種因素的影響效果取決於另一種因素的水平。
傳達者
成功的邪教團體肯定有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領導者,可以吸引和指揮其成員們。就像說服實驗那樣,一個可信的傳達者會被聽眾知覺為專家和值得信賴的人——例如,像“父親”。
瓊斯運用“心理解釋”來建立自己的可信度。新成員在進入教堂進行宣誓之前必須首先確認其個人信息。這時他的一個助手會立刻給那人的家裡打電話說“你好!我們正在做一項調查,想問你幾個問題。”一個曾是其成員的人回憶說,宣誓時,瓊斯會叫出那人的名字,並且說:
你以前見過我嗎?嗯,你住在某某地方,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多少。在你的起居室裡放著什麼東西,然後,你家的沙發上放著那樣一個枕頭……現在你能夠記起我曾經到過你家嗎(Conway & Siegelman,1979,p.234)?
信任是可信度的另一個方面。邪教研究專家辛格(Margaret Singer)注意到,中產階級的白人青年更易於被說服,因為他們更傾向於相信別人。他們缺少低社會階層青年的那種“街頭智慧”(知道怎麼抗拒推銷的誘惑),以及上等階層青年的謹慎(從小就警惕綁架者)。許多邪教成員都是被他們自己的親信,即朋友或親戚拉入的(Stark & Bainbridge,1980)。
信息
生動、感性的信息以及團體給那些孤獨和憂鬱的人所帶來的溫暖和包容,都是極具吸引力的:相信這個領導者,加入我們的大家庭;我們有答案,有辦法。這些信息通過演講、小組討論以及直接的社會壓力等各種各樣的渠道不斷在耳邊迴響。
聽眾
新會員通常都很年輕,不到25歲,處在思想相對開放的時期,其態度和價值觀都還不十分穩定。其中有些人,就像瓊斯的追隨者,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喜歡簡潔易懂的信息,不善於爭辯。但是大多數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被理想觀念衝昏了頭,以至於對那些自稱無私實則貪婪,貌似關心他人實則冷漠無情的人服服帖帖,而沒能看出其中的矛盾。
入會可能性高的人通常正處於人生的轉折點,或者面臨個人危機、外出度假或是遠離家鄉獨自生活。他們有某種需要,而邪教們恰好給了他們一個答案(Singer,1979;Lofland & Stark,1965)。梅德在她的T恤衫商店倒閉後加入了天堂之門。摩爾在19歲時入會,那時他剛剛高中畢業,正值尋找人生方向。社會和經濟劇變時期似乎給那些能對困境做出貌似簡單解釋的人提供了一種有利的契機(O'Dea,1968;Sales,1972)。
團體效應
邪教也證實了下一章節的主題:團體用來塑造其成員的觀點和行為的力量。邪教組織通常會將成員與其先前的社會支持系統割裂開來,同時也避免他們和其他異教成員相互接觸。這樣可能會出現斯塔克和班布里奇(Stark & Bainbridge,1980)稱之為“社會閉塞”的現象:外部聯繫逐漸減弱,直到團體完全承擔向內的社會性作用,每一個人都只和組織內其他成員發生聯繫。一旦與家人和朋友失去了聯繫,他們就無法進行反駁。這時,團體會向他們提供認同感並且界定事實。由於那些邪教分子反對或懲罰不一致的聲音,所以表面上的意見統一顯然有助於消除任何零星的懷疑。另外,壓力以及情緒的喚起往往會縮小人們的注意面,使人們“更容易接受那些毫無根據的觀點,順從社會壓力,並傾向於詆譭那些非本組織的成員”(Baron,2000)。
阿普爾懷特和內特爾斯(1985年死於癌症)最初起家的時候是隻有兩個人的團體,他們互相強化彼此異常的想法——這種現象被精神病學家稱為“兩個人的精神錯亂 ”。隨著越來越多人的加入,團體的社會孤立更強化了這種荒謬的想法。像互聯網共謀理論討論組所詮釋的那樣(天堂之門在網絡徵募方面非常在行),精神組織可以滋生偏執和妄想。
與認為邪教把倒黴不幸的人變成沒有思想的機器人的觀點不同,這些技巧——增強行為承諾、說服以及團體孤立——的力量並不是無限的。統一教團成功招募進來的成員還不到參加其研討會人的十分之一(Ennis & Verrilli,1989)。大多數曾加入天堂之門的人在那個災難日之前就離開該組織了。科瑞什會綜合使用說服、脅迫以及暴力來維持統治。隨著瓊斯的要求越來越苛刻,他自己也不得不更多地利用脅迫來控制人們。他對那些逃離的成員實施傷害性恐嚇,打擊不順從的成員,還會為了壓制不順從的成員而使用藥物。最終,在成為精神控制者的同時,他也淪為了一個武器濫用者。此外,邪教施加影響的技術在某些方面上和我們所熟悉的團體影響技術很相似。兄弟會和婦女聯誼會的成員報告說,邪教對可能的入會者最初“愛的轟炸”和他們的“招新”時期並沒有什麼兩樣。成員們有意濫用各種入會儀式來使自我感覺與眾不同。在入會階段,由於邪教切斷了新成員與他們沒有入會的老朋友的聯繫,所以他們往往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他們就會花時間來研究新團體的歷史和規則。他們為新團體的利益而投入自己的時間,並遵從團體的一切要求。結果就成了一名忠心耿耿的新成員。
這與那些幫助藥物和酒精濫用者康復的治療團體很是相似。狂熱的自助組織形成一個具有很強凝聚力的“社會繭子”,有激進極端的思想,並且對成員的行為施加深刻的影響(Galanter,1989,1990)。
說服的另一項具有建設性的應用體現在心理諮詢與治療當中,社會諮詢心理學家斯特朗(Stanley Strong)稱其為“應用社會心理學的分支”(1978,p.101)。和斯特朗的觀點相似,精神病學家弗蘭克(Frank,1974,1982)多年前就意識到了說服對於改變自我挫敗態度和行為的作用。弗蘭克注意到,心理治療的情境和邪教以及狂熱的自助組織一樣,會提供:(1)支持性的、相互信任的社會支持;(2)專業知識以及希望;(3)獨特的理念以及信念,用以解釋個體的困難並提出新的視角;(4)一系列的儀式以及學習經歷,以保證獲得一種平靜、愉快的新感覺。
我之所以選擇兄弟會、婦女聯合會、自助組織以及心理治療為例,並不是為了詆譭它們,而是要證實最後兩個觀點。首先,如果我們把“新宗教運動”歸因於領導者的神祕力量或者其追隨者罕見的軟弱性,那麼我們會誤認為自己可以抵制這種社會控制技術。事實上,我們自己所在的團體——以及那些數不清的政治領導人、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的說服者們——已經在我們身上成功地運用了這些策略。教育與灌輸,啟蒙與宣傳造勢,轉變與脅迫,治療與精神控制之間的界限本來就是模糊不清的。
其次,瓊斯以及其他邪教領導者濫用說服力量這一事實並不能說明說服的本質是邪惡的。核反應的能量既可以用於發電,給我們帶來光明,又可以摧毀我們的城市。性的力量既可以讓我們盡情表達和讚頌付出承諾的愛情,又可以讓人們為了滿足私慾而壓榨別人。說服的力量讓我們能夠去啟發或欺騙別人。瞭解了這種力量可以為邪惡的目的服務後,這警示我們,作為科學家和普通公民,都應該抵制其不道德的運用。但是這種力量本身並沒有本質的罪惡與優良之分,其作用是建設性的還是毀滅性的取決於我們怎樣運用它們。因為其欺騙性而去譴責說服就像因噎廢食一樣。
小結
宗教邪教的成功讓我們有機會見識了強有力的說服過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種成功看來是源於對行為承諾的強調(如第4章所述),運用有效的說服原則(如本章所述),以及將人們孤立在思想同化的團體當中(這將在第8章中討論)。
應該如何抵制被說服
在深入探討了“有影響力的武器”之後,讓我們來考慮一些抵制影響的策略。我們如何才能使人們抵制令人生厭的說服呢?
武術教練教授學員們防禦招式、偏轉以及躲閃技巧所用的時間與教授正面進攻的時間是同樣多的。薩格瑞恩及其同事(Sagarin & others,2002)注意到,“在社會影響的戰場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進攻型說服而不是防禦型說服。吉爾伯特和他的同事(Gilbert & others,1990,1993)認為,說服過程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接受有說服力的信息比懷疑它們似乎更容易一些。理解 一個觀點(例如,鉛筆有損健康)就是相信 它——至少是暫時的,直到個體能夠主動地放棄其最初的自動接受。如果某一分心事件妨礙了這種放棄的過程,那麼接受就會持續下去。
當然,在邏輯、信息以及動機的幫助下,我們確實可以抵制謬誤和謊言。如果是由於在信任光環的籠罩下,維修工人的制服和醫生的頭銜迫使我們無條件地贊成,那麼我們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對權威的習慣性反應。在投入時間和錢財之前我們可以先搜尋更多的信息。我們可以對那些不明白的事情提出疑問。
加強個人承諾
第6章中我們講過另一種抵制方法:在別人進行判斷之前,先對自己的立場做出公開表態。公開站在自己信念的一邊之後,你就不太容易再受到別人觀點的影響(或者我們應該說不那麼“開放”了?)。在模擬民事審訊中,陪審團的投票過程可能會出現公開表達的堅定立場,以至於使審判過程陷入更大的僵局(Davis & others,1993)。
挑戰信念
我們怎樣可以使人們深信不移呢?基斯勒(Kiesler,1971)通過他的實驗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法:溫和地攻擊他們的立場。基斯勒發現,已經投入自己信任的人們受到攻擊時會促使他們發起反擊,但是在攻擊強度還不能完全駁倒他們時,他們會變得更為投入和堅定。基斯勒解釋說:“當你對那些篤信不移的人們發起攻擊而攻擊的強度又不那麼強烈時,你會激發他們採取更為極端的行為來維護其先前所信奉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的篤信程度會逐漸加強,因為與他們信念一致的行為的數量增加了”(p.88)。你可能會回憶起辯論賽中的情境,隨著辯論雙方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同時雙方的觀點也越來越走向極端。
引發反駁
此外,之所以溫和式的攻擊能夠起到抵制作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當有人攻擊自己所持的態度之一時,我們通常會感到憤怒,並且盤算著如何進行反駁。反駁有利於人們抵制說服(Jacks & Cameron,2003)。駁倒某人的說服,並且得知自己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那麼你會產生較高的自我肯定感(Tormala & Petty,2002)。
就像注射疫苗以抵禦疾病那樣,再微弱的觀點也會引發反駁,這時就有可能演變成一次更強烈的攻擊。麥圭爾(McGuire,1964)在一系列的實驗中證實了這一點。麥圭爾想知道:我們是否可以運用像通過注射疫苗來使人們抵制病毒那樣的方法來抵制說服的影響?是否存在類似態度免疫 (attitude inoculation)這樣的東西?我們是否能夠讓人們在一個“無菌的意識形態環境”中成長——人們所持的觀點不會受到任何質疑——然後激起他們的精神防禦?或者給他們提供較少攻擊該信念的資料,這是否可以讓他們具備抵禦日後說服的能力?
這正是麥圭爾所做的。首先,他收集了一些具有文化真實性的說法,例如“儘可能做到在每天餐後刷牙是明智之舉”等。隨後,他發現當該信條遇到大量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攻擊時,人們較容易受其影響(例如,一個聲望很高的權威人士說,刷牙次數過多可能會破壞牙齦)。但是,假如在他們的信條被攻擊之前,先讓他們接受對於該信念的一個小小挑戰作為“預防針”,並且讓他們讀或寫一篇關於駁斥這種輕微攻擊觀點的文章,那麼他們抵制更強烈攻擊的能力就會有所增強。“預防針”同價值和真實性共同起作用。當要求Cardiff大學的學生充分想像自己的平等觀念可能會受到何種的抨擊後,他們會做出更加有效的反駁,並在現實生活中也能有效抵制觀點的改變(Bernard & others,2003)。
恰爾迪尼(Cialdini,2003)及其同事贊同適當的辯論是抵制說服的絕佳途徑,但是他們想知道個體在對一個帶有對立觀點的廣告做出迴應時——尤其是當對手(像大多數當職政治家那樣)在經費上比你寬裕很多的時候,如何才能回憶起反駁的內容。他們建議說,答案就是進行“有毒寄生者”式的反駁,也就是將毒藥(強有力的反駁)與寄生者(在看到對立觀點的廣告時能夠在腦中呈現用來提取觀點的線索)結合起來。他們的研究發現,如果被試事先看到了附在一個熟悉的政治廣告上的反駁信息,那麼他們很難被這個廣告說服。因此再次觀看這一廣告同樣會讓人們想起那些尖銳的反駁信息。舉例來說,反對吸菸的廣告有效地做到了這一點,它們對“萬寶路男人”廣告進行了二次創新,同樣是在條件惡劣的野外場景中,但是其中的牛仔卻衰老不堪,並且不停地咳嗽。
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免疫計劃
態度免疫真的能夠幫助人們抵制令人討厭的說服嗎?有關預防吸菸和消費者教育的應用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令人振奮的答案。
使孩子們抵制來自同伴吸菸的壓力
我們會將實驗室研究的成果如何在實際中加以應用做出清楚詳盡的闡述,麥卡利斯特(McAlister,1980)率領的研究小組給中學七年級的學生針對同伴的吸菸壓力“注射疫苗”。他們教育那些七年級學生們對吸菸廣告做出這樣的反應:例如對於暗示解放女性抽菸的廣告,教導說:“假如她無法擺脫香菸,就不能算真正地獲得瞭解放。”學生們還進行角色扮演遊戲,如果不抽菸就會被叫作“小雞”;他們會這樣回答:“假如抽菸只是為了給你留下什麼印象的話,我倒寧願自己真的是一隻小雞”。對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一直持續進行若干次這樣的活動,那些打過疫苗的學生們開始抽菸的比率只有另外一所中學的一半,而兩所學校學生家長的吸菸率是差不多的(如圖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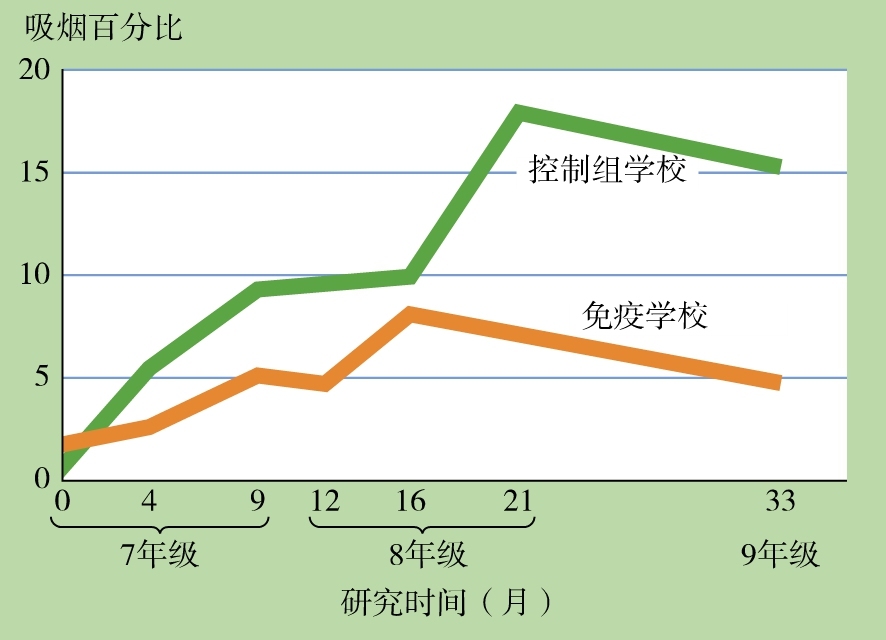
圖7-11
“注射過疫苗”的中學裡,吸菸學生的百分比遠遠低於採用一般吸菸教育方法的匹配控制組學校。
資料來源:Data from McAtister & others,1980;Tetch & others,1981.
其他一些研究小組也證實了這種預防程序——當然有時需要其他生活技能的訓練作為補充——能夠減少青少年吸菸(Botvin & others,1995;Evans & others,1984;Flay & others,1985)。最近大多數研究都強調抵制社會壓力的策略。其中的一個研究是給六到八年級的學生們放映抵制吸菸的電影,或者提供有關吸菸的信息,同時還有學生們自己總結出的抵制吸菸的角色扮演活動(Hirschman & Leventhal,1989)。一年半之後,曾經看過反吸菸電影的學生中有31%的人開始抽菸。而參與角色扮演的學生中,只有19%的人開始抽菸。
反對吸菸以及毒品教育計劃也採用了其他的說服原理。他們使用有吸引力的同齡人進行交流,喚起學生們自身的認識過程(“有些事是需要你思考一番的”),要求學生作出公開承諾(做出一個有關抽菸的理性的決策,並且連同自己的推理過程,在全班同學面前公佈)。這些預防吸菸的項目中,有些只需要2~6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僅僅使用準備好的印刷材料或是錄像資料即可。如今,任何希望通過社會心理學的方法來防止吸菸的學校或教師都能夠做到這一點,簡單易行,成本較低,並且有望減少青少年未來的吸菸率和降低有關的健康費用。
研究背後的故事:
麥圭爾關於態度免疫的研究
在從事這項免疫工作時,我承認自己感覺像一名清潔工,因為我在研究如何幫助人們免受操縱。當我們的研究發表公佈之後,一位廣告經理打來電話說:“非常有趣,教授。很高興能夠看到這樣的研究。”我比較公正地回答道:“非常感謝您,經理先生。但實際上我是站在另一面的。你試圖說服人們,我則努力讓他們更具抵制性。”“哦,不要看輕你自己,教授先生,”他說,“我們可以利用你的成果來降低我們競爭者廣告的作用。”的確,這已經成為廣告商們提及其他品牌並貶斥其名聲的標準策略。
使孩子們對廣告產生免疫力
瑞典、意大利、希臘、比利時、丹麥和愛爾蘭都嚴格限制以兒童為對象所做的廣告,而且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一直都在討論是否要採取相同的措施(McGuire,2002)。萊文(Robert Levine)曾在《說服的力量:我們是如何被買入並賣出的》一書中指出,一個普通的美國兒童每年要看1萬多條商業廣告。“20年前”,他說,“孩子們喝的牛奶是汽水的兩倍。正是拜廣告所賜,這個比例現在顛倒過來了”(2003,p.16)。1981年一份來自Philip Morris(菸草商每年花費112億美元做廣告,Philip Morris是其中的巨頭)研究人員的報告顯示,吸菸者通常在青少年時期就形成了所謂的“最初品牌選擇”(FTC,2003)。“如今的年輕人很可能就是未來穩定的消費者,絕大多數的吸菸者都是從十幾歲時開始的”(Lichblau,2003)。
作為迴應,研究者一直在探討如何使孩子們對電視裡的商業廣告產生免疫力。有研究表明,小孩子,尤其是8歲以下的孩子,(1)不能很好地區分電視節目和商業廣告,並且難以知曉其說服目的;(2)不加區分地相信電視廣告的內容;(3)懇求或逼迫父母購買做廣告的產品(Adler & others,1980;Feshbach,1980;Palmer & Dorr,1980)。這些研究部分促發了對預防的研究。孩子們看起來是廣告商們的最愛:輕信、易受影響,這使銷售變得簡單容易。
有了以上這些數據,民眾組織對這些商品的廣告商們提出了批評(Moody,1980):“如果一個精明世故的廣告商,花幾百萬美元把不健康的產品賣給單純、輕信的孩子們,那麼這隻能被稱為剝削。”在《母親對廣告商的宣言》(母性計劃,2001)中,美國婦女的廣泛聯合就是一種憤怒的迴應:
對我們而言,孩子是無價之寶。對你們來說,孩子僅僅是顧客,而童年是一塊極富開採價值的市場份額……那些訓練有素並且富有創造力的專家對孩子進行研究、分析、說服以及操縱後發現,滿足 和創造 消費者的需求與慾望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那些令人心動的信息,諸如“你今天該休息一下了”、“嘗試你自己的方式”、“跟著你的感覺走”、“放手去做吧”、“沒有任何限制”和“抓住你的願望了嗎?”這些話語證實了廣告和營銷傳遞出這樣一種主要信息:即生活就是自私自利、及時享樂和物質至上。
另執一詞的是那些從廣告獲利的人,他們宣稱廣告可以幫家長們教會孩子消費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可以為兒童電視節目提供資金。在美國,受學術界的研究結果和政治壓力雙方面的推動,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於是否應該對不健康食品的電視廣告以及限制級電影制定新的限制這一問題上保持中立。
同時,研究者們想知道孩子們是不是能夠被教會抵制欺騙性的廣告。在其中的一項研究中,由費什巴赫(Feshbach 1980;Cohen,1980)率領的研究小組給洛杉磯地區的小學生們上了三堂持續半小時的廣告分析課。孩子們通過觀看廣告並加以討論來增強對其的免疫力。例如,在看完一段玩具廣告後,他們會立即得到那個玩具,研究者要求他們嘗試像廣告中所呈現的那樣玩這個玩具。這樣的經歷能夠幫助孩子們建立對廣告更現實的理解。
消費者利益維護者擔心,僅僅預防可能還不夠充分。淨化空氣比戴防毒面具要好得多。廣告商向孩子們兜售產品並把它們放在商店較低的貨架上,這樣孩子們就可以看見這些商品,拿在手裡面,向父母軟纏硬磨,直到把父母弄得筋疲力盡之後向孩子妥協。因此,“母親應對廣告商”組織強烈要求杜絕在學校裡做廣告,不針對8歲以下兒童做廣告,不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播放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商品,以及任何廣告都不得引導兒童和青少年養成自私自利和只重視及時享樂的惡習(母性計劃,2001)。
態度免疫的意義
要對洗腦產生抵制,最好的方法並不是對當前信念進行更大強度的教化灌輸。如果父母們擔心自己的孩子可能會成為邪教分子,那麼他們最好能夠給孩子們講解各種邪教,並幫助孩子抵制那些誘人的請求。
同樣,宗教教育者應該對在教堂和學校裡建立“無菌意識形態環境”保持警惕。如果某種攻擊受到反駁的話,它很可能會更堅定,而不是動搖人們的立場;當這些威脅性資訊可以在其他有類似想法的個體身上得到驗證時更是如此。邪教是這樣運用這條原則的:提前警告其成員,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會攻擊邪教的思想和理念。當預期的挑戰出現時,成員已經做好了反駁的充分準備。
另一層意義是針對說服者提出的:應該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效果不佳的說服還不如沒有。你知道是為什麼嗎?那些拒絕請求的個體會對以後更進一步的請求產生免疫力。讓我們來看看達利和庫珀(Darley & Cooper,1972)所做的實驗,他們要求學生們寫一篇有關贊成嚴格限制著裝的文章。由於這和學生們自己的立場相違背,並且文章會被發表出來,所以所有的人都斷然拒絕,即使有報酬也不幹。拒絕報酬之後,學生們對自己反對限制著裝的觀點更加堅定,而且更加極端。在對限制著裝做出公然抵制的決定後,學生們的反對態度變得更加強烈。那些曾經拒絕過戒菸勸說的人很可能對以後的任何勸說都有了免疫力。效果不佳的勸說,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引起聽者的防禦心理,使得他們對於隨後的勸說變得更加“鐵石心腸”,不為所動。
小結
人們應該如何抵制被說服呢?預先公佈自己的立場(這可能是受到別人對自己立場輕微的攻擊而引發出來的),會導致個體抵制隨後的勸說。溫和的攻擊還可以起到免疫的作用,使個體對可能到來的更強烈的攻擊做好反駁的準備。結論看似矛盾:加強現有態度的方法之一竟然是對其發出挑戰;當然,這種挑戰的強度必須適中,不至於顛覆其已有的觀點。
個人後記:開明但不要天真
作為說服的接受者,我們人類的任務就是在天真輕信和憤世嫉俗之間求生存。有人認為,容易被說服是人類的一個弱點。我們主張“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思考”。但是,拒絕一切信息的影響到底是一種優點呢,還是一種對狂熱的遮掩?我們如何能夠在保持謙卑和開明的同時,對說服進行批判性思考呢?
作為開明的人,我們可以假設自己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在某方面都可以充當我們的指導老師。我所遇到的每個人都有某種超越我的專長,因此總有可以教給我的東西。當我們建立聯繫的時候,我希望能夠從這個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並且能夠與他分享我所擁有的知識來作為回報。
作為批判性的思考者,我們可以從預防研究中得到啟示。你是否想在接觸確鑿的信息之前就建立對說服的防禦機制?做一個積極的傾聽者和批判性的思考者吧。強迫自己與之爭論。聽完一次政治演說之後,與別人一起討論。換句話說,不要光聽,還要做出反應。如果該信息經不起仔細推敲,那麼它就再糟糕也不過如此。如果它經得起推敲的話,它對你的影響可能會更為持久。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什麼時候曾被說服過?你很高興自己被說服嗎?如果未曾被說服過,那麼你可能採取了什麼樣的行為來使自己產生免疫力?
聯繫社會
這一章著重講述了佩蒂的說服理論及其研究。在第4章(行為與態度)中,我們也討論過佩蒂有關失調的觀點。
第8章 群體影響
什麼是群體
社會助長作用:我們是怎樣受他人在場影響的
純粹他人在場
擁擠現象:眾多他人在場
為什麼我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起
社會懈怠:個人在群體中會減少努力嗎
人多好辦事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懈怠
去個體化:人在群體中何時會失去自我感
一起做一些我們單獨一個人時不會做的事
弱化自我意識
群體極化: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風險轉移”的案例
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對極化的解釋
群體思維:群體會阻礙還是促進好的決策
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
對群體思維的批評
預防群體思維
群體問題解決
少數派影響:個體是怎樣影響群體的
一致性
自信
從多數派中叛離
領導是否屬於少數派影響
個人後記:難道群體不利於我們嗎
“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
——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
託 娜即將跑完每日長跑的全程時,已經累得不行了。儘管她腦子裡想著要堅持跑完,可身體卻向她央求說還是步行回家吧。最後,她選擇了折衷的辦法,用極慢的速度跑回了家。第二天,除了有兩個朋友和她一起跑以外,情況還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樣。但是託娜卻比上一次少花了2分鐘就跑完了全程。她覺得很奇怪:“我能跑得更快就是因為和她們一起跑嗎?和別人一起我總是能跑得更快嗎?”
我們幾乎無時無刻不生活在群體中。我們的社會不僅僅由64億個體組成,它同時包括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400萬個地方性社區、2000萬個經濟組織,以及幾億個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群體——比如,約會中的戀人、家庭、教堂、正在交談的同室好友等等。那麼,這些群體是如何影響個體的呢?
群體互動常常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有學識的大學生和其他博學多才的人在一起,會促進彼此的才智。不良少年和不良少年在一起,彼此的反社會傾向也會愈演愈烈。不過,群體是以什麼方式來影響群體內成員的態度呢?又怎樣影響群體做出明智或是愚蠢的決策呢?
個體也會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1957年一部經典影片《12個憤怒的男人》中以這樣的情節展開:審理謀殺案的12名警覺的陪審員列隊走進陪審室。那天天氣很熱,陪審員們疲憊不堪,急於對一個少年以刺殺其父親為名做出有罪判決。在他們就快達成一致意見時,其中卻有一個人獨立特行,拒絕投票。接下來,隨著討論的繼續進行,陪審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改變了自己的裁決直至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無罪。”雖然在真實的審判中,單獨一個個體極少能夠支配整個群體,然而,歷史就是由少數支配多數的事件鑄成的。到底是什麼因素令一個少數派——或者是一個有效的領導者——如此具有說服力呢?
我們將逐一來探討這些有趣的群體影響現象。不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群體?群體為什麼會存在呢?
什麼是群體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一旦有幾個人互相比較他們所給出的定義時,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一起長跑的同伴們是一個群體嗎?飛機上的乘客是一個群體嗎?一個群體是否指彼此認同,感覺應該在一起的一群人?一個群體是否指具有相同目標,相互依賴的一群人?是不是當個體變得有組織時,就形成了群體?在什麼情況下群體成員之間的關係會長期持續下去?所有這些問題在社會心理學關於群體的定義中都有所涵蓋(McGrath,1984)。
群體動力學家肖(Shaw,1981)認為所有的群體都有一個共同點:群體成員間存在互動。因此,他把群體 (group)定義為兩個或更多互動並相互影響的人。另外,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特納(Turner,1987)認為,群體成員把自己群體中的人看做是“我們”而不是“他們”。所以,就此而言,一起長跑的同伴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群體。而群體的存在可能有許多理由——為了滿足歸屬的需要,為了提供信息,為了給予報酬,為了實現目標等等。
如果按照肖的定義,在計算機房上機,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學生不能稱做一個群體。雖然他們也是在一起,但他們只是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互動的群體(不過,其中的每個人卻可能是某一網上聊天室這樣一個無形群體的一員)。計算機房裡無關個體的集合與由互動個體組成的更具影響力的群體行為之間的區別有時候是模糊不清的。僅僅是有其他人在場有時也會對個體產生影響。就好像在一場比賽中,人們會把那些和自己支持同一個參賽隊的人看做是“我們”,而與之相對的,把那些支持別的參賽隊的人看做是“他們”。
本章我們將先考察有關集體影響的三種實例: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 和去個性化 。這三種現象都可以在低限交互的情況下(在我們稱之為“低限群體情境”下)發生。然後我們將探討在互動的群體中有關社會影響的三個例子:群體極化,群體思維 和少數派影響。
社會助長作用:我們是怎樣受他人在場影響的
讓我們從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開始:純粹他人在場會不會影響我們?“純粹在場”是指,在場的他人實際上只是作為一個被動的觀眾或共事者(co-actors)存在,並不具有競爭性,也不會實施獎勵或懲罰。他人在場會對一個人的長跑、用餐、打字或考試成績產生影響嗎?科學家們尋找該問題答案的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神祕的科學故事。
純粹他人在場
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個對自行車賽感興趣的心理學家特里普利特(Triplett,1988)注意到:自行車手在一起比賽時,他們的成績要比各自單獨和時間賽跑時的成績好。在把自己的直覺發現公佈於眾(他人在場能提高作業水平)之前,特里普利特進行了首例社會心理學實驗室研究。在實驗中,他要求兒童被試以最快的速度在漁用卷軸上繞線,結果發現,當兒童們在一起做這件事時要比單獨做時快得多。
隨後的實驗發現他人在場能夠提高人們做簡單乘法和劃銷指定字母等任務的速度,同時證實了他人在場能提高人們完成簡單動作任務[比如保持一根金屬棍與一個在轉盤上的硬幣大小的圓盤接觸的任務(F. W. Allport,1920;Dashiell,1930;Travis,1925)]的準確性。這種社會助長作用 (social facilitation)也同樣會發生在動物身上。當有同類在場時,螞蟻能挖掘出更多沙子,小雞會吃更多的穀物,交配中的老鼠會表現出更多的性活動(Bayer,1929;Chen,1937;Larsson,1956)。
不過現在就下結論似乎還為時過早。另一些研究發現,在完成某些任務時,他人在場會妨礙 當事人的成績表現。有同類在場時,蟑螂、長尾小鸚鵡、金絲雀學會走迷宮的速度都比較慢(Allee & Masure,1936;Gates & Allee,1933;Klopfer,1958)。這種干擾效應在人類中也會發生。他人在場會降低人們學習無意義音節、走迷宮遊戲以及演算複雜乘法問題的效率(Dashiell,1930;Pessin,1933;Pessin & Husband,1933)。
如果說他人在場有時有助於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有時卻會妨礙作業成績,那這種說法比起典型的英格蘭天氣預報來也好不到哪兒去——那兒的天氣預報會說今天可能是晴天,然後接著又說也可能會下雨。到1940年為止,這個領域的研究幾乎停滯不前,並且一直沉寂了25年,直到受某一個新觀點的啟發才又復興起來。
社會心理學家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想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發現融合到一起。正如科學界中常有的創造性瞬間一樣,扎伊翁茨(1965)用一個領域的研究點亮了另一個領域的研究。這一次是受到了實驗心理學中一個成熟定律的啟示:喚起能夠增強任何優勢反應的傾向。喚起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而在這些簡單任務中“優勢”反應往往是正確的。人們在喚起狀態下,完成簡單的字謎任務——辨別出打亂了字母順序的單詞,比如“akec ”,是最快的。而在複雜任務中,正確答案往往不是優勢反應,所以,喚起增強的是錯誤 反應。因此,在更難一些的字謎任務中,焦慮被試的成績表現會更差。
這個規律能夠解開社會助長作用之謎嗎?假設人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起或激活似乎很有道理,而且現在也有許多證據證實這一假設是正確的(Mullen & others,1997)。(我們都能回想出面臨一群聽眾時自己的緊張或者興奮感。)如果社會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那麼它應該會提高簡單任務的作業成績 ,並且會降低困難任務的作業成績 。至此,我們可以對以前令人迷惑不解的結果做出比較圓滿的解釋。在漁用卷軸上繞線,做簡單乘法題,或者吃東西都是一些簡單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都是人們掌握得非常好的反應或很自然的優勢反應。毫無疑問,他人在場會提高這些任務的作業成績。而學習新材料,走迷宮遊戲,或者解複雜的數學題都是一些較難的任務,這些任務的正確反應很難一下子就做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就會增加個體錯誤 反應的次數。可見,同一個規律: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 ,在兩種情況下都有效了(見圖8-1)。突然之間,先前看起來互相矛盾的結果也不再矛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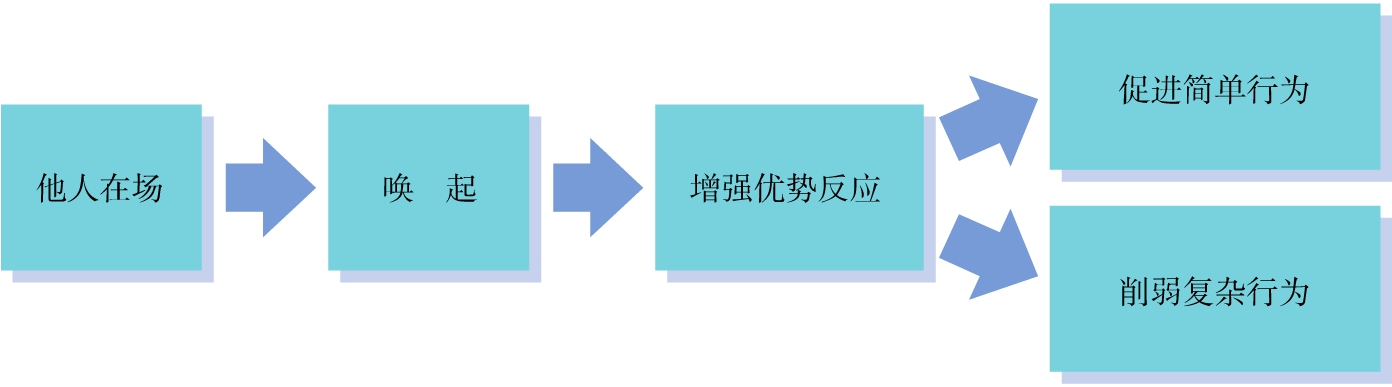
圖8-1 社會喚起效應
扎伊翁茨提出的他人在場可以增強個體的優勢反應(正確反應僅僅出自簡單或掌握得非常好的任務中)的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研究結果。
扎伊翁茨的解決方案是如此的簡單而出色,這令其他社會心理學家們想到了赫胥黎第一次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後的想法:“怎麼以前從來就沒這樣想過呢,我是多麼地愚蠢啊!”當扎伊翁茨指出來之後,這個道理就似乎顯而易見了。然而,也有可能是因為戴著事後聰明的有色眼鏡,所以那些破碎的結果看起來融合得如此完美。扎伊翁茨的這個解決方案能經受住實驗的直接檢驗嗎?在對25000個志願者被試進行了差不多300個研究之後,證實這個解決方案仍舊有效(Bond & Titus,1983;Guerin,1993,1999)。
隨後的實驗也以不同的方式驗證了這個規律:無論優勢反應是正確反應還是錯誤反應,社會喚起都會促進這種優勢反應。亨特和希勒裡(Hunt & Hillery,1973)發現:他人在場時,學生們學習走簡單迷宮所需的時間會變少,而學習走複雜迷宮所需的時間會增加(和蟑螂是一樣的!)。邁克爾等人(Michael & others,1982)發現:在一個學生社團裡面,優秀的撞球選手(在隱蔽觀察條件下擊中71%的選手)在有四位觀察者來觀看他們表現的情況下,他們的成績會更好(80%的擊中率)。而差勁的選手(先前平均擊中率為36%)在被密切觀察的條件下表現更差(25%的擊中率)。
由於運動員們所表現的都是熟練掌握的技能,這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觀眾的支持性反應常常能夠激勵他們表現出最佳狀態。在對加拿大、美國、英國舉行的總計8萬項大學體育賽事或專業體育賽事的研究顯示:主場隊會贏60%的比賽(棒球和橄欖球會少一些,籃球和足球會多一些——見表8-1)。這種主場優勢有可能是來自於運動員對主場環境的熟悉,較少的旅途勞頓,源於對領土控制的優越感,或者是源於觀眾狂熱的喝采而激起的更高的團隊認同感(Zillmann & Paulus,1993)。
表8-1 大型團體體育比賽中的主場優勢

資料來源:Data from Courneya & Carron(1992). Baseball data from Schlenker & others(1995).
擁擠現象:眾多他人在場
綜上所述,人們的確對他人在場有所反應。但是,觀察者的在場真的會激發人們的喚起狀態嗎?當面臨壓力的時候,身邊擁有一個夥伴可能是令人安慰的。可是,他人在場時,人們的出汗量會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縮次數增加,血壓升高並且心跳加速(Geen & Gange,1983;Moore & Baron,1983)。在完成有挑戰性任務時,甚至一群支持性觀眾的在場可能會引發個體做出比平常更差的表現(Butler & Baumeister,1998)。你在第一次鋼琴獨奏會上的表現不會因為父母的到場而有所提高。
他人的影響效應會隨人數的增加而遞增(Jackson & Latané,1981;Knowles,1983)。有時候龐大的觀眾群體所激起的喚起狀態和有意注意甚至會干擾熟練掌握的、自動化的行為,例如講話。在極大 的壓力情境下,我們很容易哽住。當口吃者面對一大群聽眾時,會比只對一兩個人講話時口吃得更加厲害(Mullen,1986)。大學生籃球運動員在球場座無虛席的情況下會處於高度喚起狀態,這時,他們無防守投籃的準確率會稍差 於球場幾乎無人的情況(Sokoll & Mynatt,1984)。
“處在人群之中 ”對個體的積極或消極反應都會有增強作用。當人們在一起坐得很近時,友善的人會更受人歡迎,而不 友善的人會更令人討厭 (Schiffenbauer & Schiavo,1976;Storms & Thomas,1977)。弗裡德曼及其同事(Jonathan Freedman & others,1979,1980)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以及安大略科學中心的訪問學者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他們讓一個“同謀者”和其他被試一起聽搞笑的磁帶或者看電影。當所有人在一起坐得很近的時候,“同謀者”更容易誘導被試們發笑或者鼓掌。正如戲劇導演和體育迷們所認為的那樣:一間“好屋子”就是一間坐滿人的屋子,這一點也已經被研究者們證實(Aiello & others,1983;Worchel & Brown,1984)。[在擁擠房間裡的高喚起趨向於給個體增加壓力。然而在分隔成許多空間的房間裡,個體能夠退回到其私人領域,故而擁擠所帶來的壓力會小一些 (Evans & others,1996,2000)。]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一個35人的班級坐在正好能容納 35人的教室裡會比散坐在一個能容納100人的教室裡感覺更溫馨更活躍。部分原因是由於當我們和別人坐得很近時,我們會更容易注意別人並且融入到他們的笑聲和掌聲中去。另一方面,埃文斯(Evans,1979)發現擁擠也會增強喚起狀態。他對馬薩諸塞大學的學生進行了一些測試。學生們每10人為一組,每組人會呆在一個20×30英尺大小的房間或一個8×12英尺大小的房間。結果發現呆在人口稠密擁擠的房間裡的被試比呆在寬敞房間裡的被試心率更快,血壓也更高(喚起的指標)。納格和潘迪(Nagar & Pandey,1987)對印度大學生做的一個研究也發現,擁擠使人在完成複雜任務時更容易出錯。由此可見,擁擠能增強喚起狀態,而喚起能夠促進優勢反應。
為什麼我們會因他人在場而被喚起
在他人面前時你會受到激勵而把自己擅長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經過度喚起或者處於自我意識狀態了)。然而在同一情景下,你原本覺得困難的事情就會顯得更不可能實現了。那麼,他人在場是如何引起人們喚起的呢?有證據表明可能是以下三個因素:評價顧忌、分心以及純粹在場。
評價顧忌
科特雷爾(Nickolas Cottrell)猜測觀察者在場使我們憂慮的原因在於我們想知道別人怎麼樣評價我們。為了證實評價顧忌 (evaluation apprehension)是否存在,科特雷爾及其同事給觀察者蒙上眼睛,結果發現與可以自由觀察的觀眾不同,僅僅是這些蒙上眼睛的人的在場並沒有 產生預期的反應。
其他實驗也證實了科特雷爾的結論:如果人們認為自己正在受在場的人評價,那麼他們的優勢反應提高得最明顯。有這樣一個實驗,實驗者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長跑者,這些長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時會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 這位女士是面對著他們的,那麼與她背對著他們相比,長跑者跑步的速度會更快一些(Worringham & Messick,1983)。
評價顧忌也有助於解釋以下問題:
為什麼當與比自己稍微優秀一點的人一起共事時,人們的表現最好 (Seta,1982)
為什麼一個高層領導小組的喚起狀態會在意見無關痛癢之人加入時有所降低 (Seta & Seta,1992)
為什麼那些最擔心別人對自己如何評價的人往往最容易受他人在場影響 (Gastorf & others,1980;Geen & Gange,1983)
為什麼當在場者是密切注意人們行動的陌生人時,社會助長效應最大 (Guerin & Innes,1982)
受評引發的自我意識也會干擾我們熟練掌握的自動化行為(Mullen & Baumeister,1987)。如果籃球運動員在投非常關鍵的一球時自覺主動地分析自己身體的運動,那他就很可能無法命中。
分心
桑德,巴倫和穆爾(Sanders,Baron,& Moore,1978,1986)對評價顧忌進行了更深入地研究。他們認為:當考慮共事者在做什麼或者觀眾會怎麼反應的時候,我們已經分心了。這種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 使認知系統負荷過重,於是就引起了喚起。一些實驗表明,不僅他人在場會引起社會助長效應,有時其他非人的分心物的出現,比如光線的突然照射,也會產生這種效應。這就提供了證實人們“受分心的影響”的證據。
純粹在場
然而,扎伊翁茨認為即使在沒有評價顧忌或沒有分心的情況下,他人的“純粹在場”也會引發一定程度的喚起。例如,他人在場情況下讓被試判斷對顏色的喜好,他們的好惡程度會有所增強(Goldman,1967)。在這個任務中,答案沒有對錯好壞之分,別人也無從評價,也就沒有理由去關注他人的行為反應了。但是,這種情況下,他人在場還是有喚起作用的。
前面提到過非人類的動物社會中也存在社會助長效應。這暗示我們天生的社會喚起機制在動物界中是十分普遍的。(動物們也許並不能有意識地關注別的動物對自己的評價。)在人類社會中,許多長跑者都會因為有人跟他們一起跑而得到激勵,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們的競爭對手,也不會對他們進行評價。
這裡有必要提一下我們提出某一個理論的目的是什麼。正如我們在第1章裡所提到的那樣,一個好的理論是一篇科學性的速記:它能簡化並且歸納總結各種各樣的觀察資料。社會助長理論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它是許許多多研究發現的一個簡單概述。一個好的理論也應該能提供明確的預期,這些預期會(1)有助於該理論的驗證和修正;(2)引導全新的探索;以及(3)對實際應用提出建議。社會助長理論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前兩種預期:(1)理論基礎(他人在場會引發喚起,並且這種社會喚起會提高個體的優勢反應)已經被證實了,而且(2)這個理論給一個沉寂已久的研究領域帶來了勃勃生機。
它是否也(3)對實際應用提出了建議呢?我們可以對可能的應用作一些有根據的推測。如圖8-2所示,在許多新寫字樓裡,用一些低矮的隔離物劃分出的寬敞、開放的辦公區域已經替代了私人辦公室。意識到他人在場是有助於個體提高熟練任務的作業成績,還是會干擾其對複雜問題的創造性思維?你還能想到其他可能的應用案例嗎?

圖8-2
在“開放辦公室計劃”裡,人們都在他人在場的情境下工作。這會如何影響工作者的效率呢?
資料來源:Photo courtesy of Herman Miller Inc.
小結
他人在場問題是社會心理學最基本的問題之一。對於該問題的早期研究發現,觀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會提高個體的作業成績。另一些人則發現他人在場會降低個體的作業成績。扎伊翁茨用一個知名的實驗心理學定律把這些發現融合了起來。這個定律即是:喚起能促進優勢反應。由於他人在場能引發喚起狀態,所以,觀察者或共事者在場,會提高簡單任務(其優勢反應是正確的)的作業成績,但會降低複雜困難任務(其優勢反應是錯誤的)的作業成績。
然而,我們為什麼會因為他人在場而被喚起呢?實驗表明:這種喚起部分來自於評價顧忌,部分來自於分心——注意他人和注意當前任務之間的矛盾衝突。而另一些實驗(包括一些動物實驗)表明,即使我們不存在評價顧忌或者分心,僅僅是他人在場也會引起喚起的。
社會懈怠:個人在群體中會減少努力嗎
八個人一隊的團體拔河比賽中隊員們使出的力氣,與他們各自參加個人拔河比賽所使出的最大力氣的總和一樣大嗎?如果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對於工作群體中成員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應該抱何種期望呢?
社會助長作用經常發生在人們為個人目標努力時,比如繞漁線或解數學題等,在這種情況下,他人可以對個人作出的努力做出單獨的評價。上述情境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工作情境十分類似,而與另一些大家為同一 個目標一起努力的情境迥然相異 。因為後一種情形中,個人的努力是無法 被單獨評價的,比如,團體拔河比賽、集資籌款(共同經營糖果生意賺錢付班級旅行的費用)、大家得同一分數的班級項目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樣的“加合任務”,即小組成績有賴於成員個人努力之總和的任務中,團隊精神是否會提高產出呢?作為一個團隊一起工作時,泥瓦匠們會比他們單獨工作時更快嗎?實驗室模擬是解答這些問題的一種方法。
人多好辦事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工程師林格曼(Ringelmann)發現,在團體拔河中集體所付出的努力僅有所有個人單獨努力之總和的一半。這表明,與“團結就是力量”的普遍觀念恰恰相反,實際上,在集體任務中小組成員的努力程度反而較小。也許,糟糕的表現源於糟糕的合作——人們一起拉繩子的時候,用力的方向和時間是稍有差異的。由英厄姆(Ingham,1974)領導的一個馬薩諸塞研究小組巧妙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使被試認為自己在和其他人一起拉繩子,而實際上是被試一個人在拉。矇在鼓裡的被試們被排在如圖8-3所示裝置的第一個位置,並且要求他們:“盡你的全力去拉。”結果是,如果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人在拉,那麼使出的力氣比以為身後還有2~5個人和自己一起拉時多出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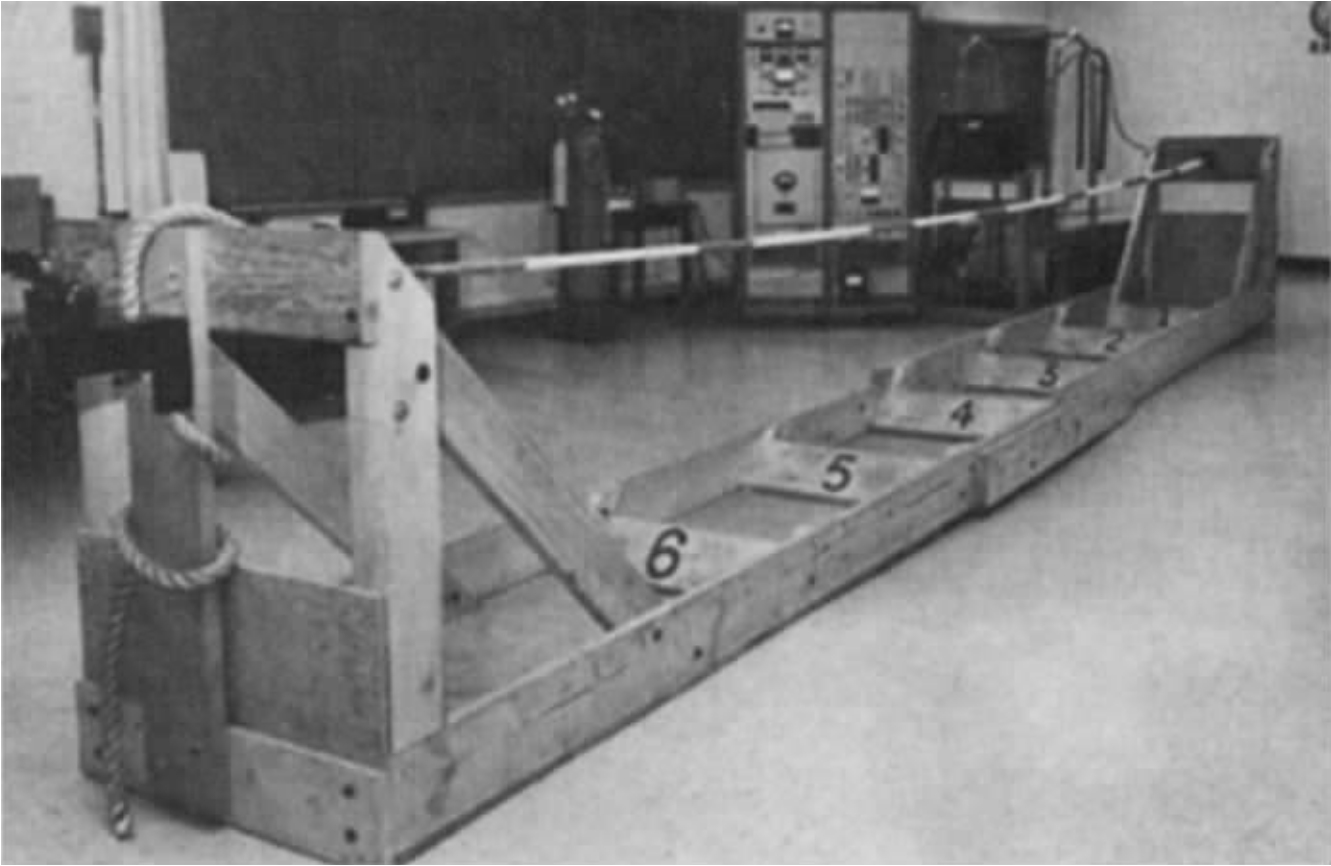
圖8-3 拉繩裝置
如果站在第一個位置的人認為後面有人和自己一起拉,那麼他使出的力氣就會較小些。
資料來源:Data from Ingham,Levinger,Graves,& Peck ham,1974. Photo by Alan G. Ingham.
拉坦,威廉姆斯和哈金斯(Latané,Williams,Harkins,& others,1979,1980)等研究者同時也注意到了研究社會懈怠 (social loafing)現象的其他方法。他們觀察到:6個人一起盡全力叫喊或者鼓掌所發出的喧鬧聲還沒有1個人單獨所發出喧鬧聲的3倍響。就像拔河比賽一樣,製造喧鬧聲的任務也很容易受群體無效率的影響。所以拉坦及其助手們沿襲了英厄姆的方法,他們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生為被試,也使被試們認為自己是在和其他人一起叫喊或者鼓掌,而實際上他們是獨自做這件事。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的:讓6個人蒙上眼睛坐在一個半圓形中,給他們戴上耳機,從中他們可以聽到別人叫喊或者鼓掌的聲音。這樣,如果被試聽不見自己的叫喊或鼓掌聲,那別人的聲音就更聽不見了。在不同輪的實驗中,或者要求他們單獨叫喊或鼓掌,或者要求他們整組一起做。有些知道這個實驗的人猜測,和他人一起做的時候被試會叫得更響,因為這時候抑制性會降低(Harkins,1981)。而真實的結果卻證實了社會懈怠:被試認為自己正和其他5個人一起叫喊或鼓掌時所發出的喧鬧聲要比他們認為自己正單獨做時少三分之一。甚至在高中的啦啦隊長中也會發生這種社會懈怠現象(Hardy & Latané,1986)。
有趣的是,那些單獨鼓過掌也和他人一起鼓過掌的人,並不認為自己懈怠;他們認為在兩種情況下自己的努力程度是一樣的。這和學生們一起完成某一個共同的項目時發生的現象很相似。威廉斯說道,所有人都同意發生了懈怠——但是沒有一個人承認是自己製造了懈怠。
斯威尼(Sweeney,1973),一個政治學家,對於社會懈怠的政策性含義很感興趣,在得克薩斯大學所做的一項實驗中,他觀察了其中的現象。當學生們知道自己被單獨評價(以電量的輸出來計量)時,與其認為自己的成績還要考核其他人的行為表現時相比,他們踩自行車練習器要更加賣力。在群體條件下,人們就會受到搭 集體便車 (free-ride)的誘惑。
從這個以及其他160個研究(Karau & Williams,1993,及圖8-4)中,我們可以看到,引發社會助長作用的心理力量,即評價顧忌,受到了扭曲。在社會懈怠實驗中,個體認為只有在他們單獨操作時才會受到評價。群體情境(拔河,喊叫等等)降低 了個體的評價顧忌。當人們不單獨為某事負責或者並不對其努力程度進行單獨評價時,所有小組成員的責任感都被分散了(Harkins & Jackson,1985;Kerr & Bruun,1981)。相反地,社會助長實驗則增強 了個體的評價顧忌。一旦成為注意的焦點,人們就會自覺監控自己的行為(Mullen & Baumeister,1987)。所以規律還是一樣的:一旦受他人觀察,個體的評價顧忌會有所增強 ,這樣社會助長作用就發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個體的評價顧忌就會減小 ,社會懈怠就發生了(圖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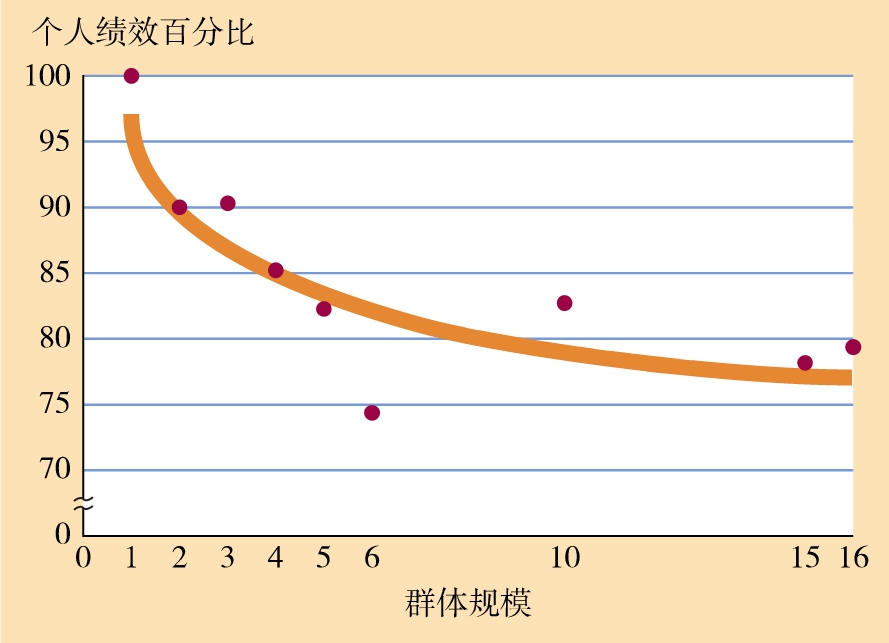
圖8-4 隨著群體規模的增大
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對包括4000多名被試的49個研究所做的統計性摘要表明,隨著群體規模的增大,個體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減小(社會懈怠增加)。每個點代表其中一項研究的全部數據。
資料來源:From Williams,Jackson,& Karau,in Social Dilemmas :Perspective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dited by D. A. Schroeder,1992. Praeger Publishers,an imprint of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Westport,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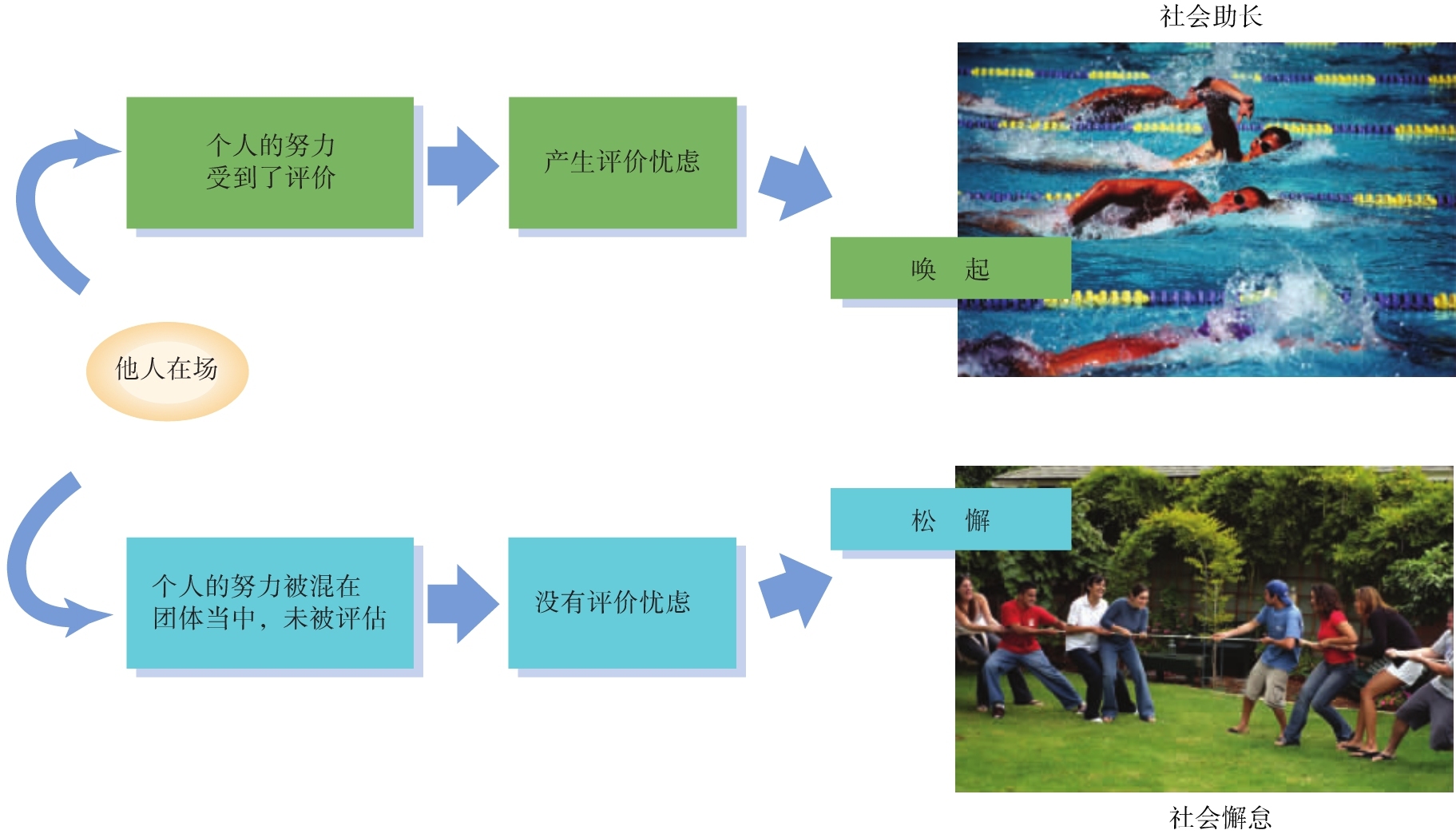
圖8-5 是社會助長還是社會懈怠?
如果無法對個體進行評價或者個體無需為某事單獨負責時,更可能發生社會懈怠。
激勵小組成員的一種策略是使個體作業成績可識別化。有些橄欖球教練通過錄像和對運動員進行個別評價的方法來達到這一目的。無論是否在一個小組中,當個體的行為可以單獨評價時,人們會付出更大的努力:大學游泳隊的隊內接力賽中,如果有人監控大家並且單獨報出每個人所用的時間,那麼整體游泳的速度會有所提高(Williams & others,1989)。一個對流水線工人所做的小實驗發現,一旦可以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單獨評價,即使沒有額外的報酬,工人們生產的產品仍然增加了16%(Faulkner & Williams,1996)。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懈怠
社會懈怠很普遍嗎?在實驗室中,此現象不僅在拔河比賽,蹬自行車,叫喊和鼓掌等任務中發生,同時也出現在泵空氣或水,評價詩歌或社論,發表觀點,打字和信號偵察等任務中。那麼這些結果能夠推廣到工人的日常生產中去嗎?
前蘇聯集體農場裡的農民們今天耕作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對任何一塊特定的土地都沒有直接的責任感。因為農民們自己只有一塊很小的私有土地。調查分析發現,雖然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全部耕種面積的1%,但其產出卻佔全蘇維埃農場產出的27%(H. Smith,1976)。在匈牙利,農民的私有土地只佔農場總面積的13%,但其產量卻佔了總量的三分之一(Spivak,1979)。自從中國開始允許農民在上交公糧後,可以出售富餘的糧食,其糧食產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漲——是前26年的年增長率的2.5倍(Church,1986)。
在北美,不向工會或行業協會交會費也不參加義務勞動的那些工人,卻往往非常樂於接受工會帶來的福利。那些不響應公共電視臺基金籌款動員的觀眾們同樣也是如此。這暗示了對於社會懈怠的另一種可能解釋。如果不管個人對群體做出多少貢獻,都是平均分配報酬,那麼付出單位勞動所得報酬多的人就等於是搭了集體的便車。因此,人們就會想在自己的努力無法被單獨監控或者單獨評價的時候偷懶。用一個公社成員的話來說,能很方便地搭便車的社會就是“寄生蟲的天堂”。
比如,在泡菜廠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從傳輸帶上挑出大小合適的半塊頭蒔蘿泡菜塞進罐子裡。不幸的是,因為無法識別出這些產品分別是誰做的(所有的罐子都會在接受質量檢查之前進入同一個斗車),工人們常常會隨便把任何大小的泡菜都塞進罐子。威廉姆斯等人(Williams,Harkins,& Latané,1981)提出,有關社會懈怠的研究建議“使個人的產出可識別化,並且提出問題說:‘假如工廠只按包裝合格的泡菜付給工人相應的工資,那麼一個工人會包裝多少泡菜呢?’”
當然,集體性質的工作也不總是引發個體的偷懶行為。有時候,群體目標極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個人都盡最大的努力,這時團隊精神會維持並且增強個人努力的程度。在奧運會划艇賽中,劃手在參加8人一組的團體划艇賽時會比單人劃或雙人劃時更不賣力嗎?
有證據表明答案是否定的。當任務具有挑戰性、吸引力、引人入勝 的特點時,群體成員的懈怠程度就會減弱(Karau & Williams,1993)。面臨挑戰性的任務時,人們可能會認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Harkins & Petty,1982;Kerr,1983;Kerr & Bruun,1983)。假設人們認為小組中的其他成員靠不住或者沒有能力做出多少貢獻,那他們也會付出更大的努力(Plaks & Higgins,2000;Williams & Karau,1991)。對群體實施激勵性措施或者讓群體為一個有挑戰性的目標而奮鬥也可以提高整體的努力程度(Harkins & Szymanski,1989;Shepperd & Wright,1989)。只要團體成員堅信高的努力程度能夠取得好的作業成績並且會帶來回報,他們就會努力工作(Shepperd & Taylor,1999)。
如果小組成員彼此都是朋友 而非陌生人或成員都很認同自己的群體,那麼懈怠就會有所減少(Davis & Greenlees,1992;Karau & Williams,1997;Worchel & others,1998)。甚至是有想與某人再見面的願望也能提高團隊的效率(Groenenboom & others,2001)。在班級中與常常見面的同學之間的合作就比與那些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再見面的人之間的合作動機水平更高。拉坦指出,以色列集體農場的產量實際要比個體農場的產量高(Leon,1969)。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那麼集體主義文化中是否存在社會懈怠呢?為了查明真相,拉坦及其同事們(Gabrenya & others,1985)前往亞洲,在日本、泰國、中國臺灣省、印度和馬來西亞重複了他們的製造喧鬧聲音實驗。他們發現了什麼?結論是社會懈怠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同樣非常顯著。
不過,在亞洲進行的17個後續研究顯示:集體主義文化下,人們表現出的社會懈怠的確不如個體主義文化下強烈(Karau & Williams,1993;Kugihara,1999)。我們在第2章中曾提到過,對家庭和集體的忠誠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第5章中解釋過)不如男性個人化——其社會懈怠也不如男性強烈。
上述有些發現與對日常工作群體對象的研究發現相吻合。當群體被賦予挑戰性的目標任務時,當他們因成功而被授予獎勵時,當他們有一種把自己的隊伍看做“團隊”的信念時,成員們就會努力工作(Hackman,1986)。保持工作群體較小的規模並使構成群體的成員實力均衡也有助於使成員們相信自己對群體的貢獻必不可少(Comer,1995)。因此,假如小組成員在一起集體工作,而個人的成就又無法單獨評價的話,那麼社會懈怠的發生就不足為奇了,這種情況下,就未必是人多好辦事了。
小結
社會助長研究的是個人作業成績能得以單獨評價的任務中人們的行為表現。然而,在許多工作情境中,人們彙集個人的努力以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個人的努力卻無法單獨被評價。研究表明群體成員在完成這樣的“集體任務”時,就不會那麼努力了。這正如我們平常所見的:如果個人的責任被群體分散了,那麼就容易導致個體成員搭群體便車的現象。
去個體化:人在群體中何時會失去自我感
群體情境可能會使人失去自我覺知能力,並導致個體喪失自我和自我約束。什麼樣的情境會引發這種“去個體化”呢?
2003年4月美軍抵達伊拉克後,從薩達姆的高壓政策下“解放”出來的掠奪者活動猖獗。在這“瘋狂的掠奪”中,醫院損失了床位,國家圖書館損失了上萬冊珍貴的手稿,大學也損失了大量的電腦、椅子,甚至燈泡。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在48小時內被掠走了幾千件珍品——儘管大部分珍品在這之前就已被運送到安全的地方(Burns,2003a,b;Lawler,2003c)。《科學》雜誌報道說:“自從西班牙征服者的劫掠之後,阿茲臺克和印加文明還從沒有這麼嚴重地流失過。”(Lawler,2003a)一位大學院長這樣描述:“暴徒成群地湧進來,來了50個,又走了,然後又來了一群。”這樣的報道讓人們很驚異:這些搶劫者的道德感哪兒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行為呢(Lawler,2003b)?
一起做一些我們單獨一個人時不會做的事
社會助長實驗表明群體能引發人們的喚起狀態。社會懈怠實驗表明群體能擴散責任。一旦喚起和責任擴散結合到一起,常規的約束就會變小,後果可能令人震驚。從輕微的失態(在大餐廳裡扔擲食物,怒罵裁判,在搖滾音樂會上尖叫)到衝動性的自我滿足(集群破壞公物,縱酒狂歡,偷竊),甚至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暴力(警察暴力,暴動,私刑),人們都可能幹得出來。1967年發生過這樣一起事件,200名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圍觀一個聲稱要從塔頂跳下來的同學。下面的人起勁地同聲呼喝著:“跳!跳!……”最後那個學生真的就跳下來了,當場身亡(UPI,1967)。
這些失控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體引發的。群體能產生一種興奮感,那是一種被比自己更強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覺。很難想像,單獨一個搖滾迷會在一個私人搖滾音樂會上發狂地叫喊,單獨一個俄克拉荷馬大學的學生會試圖誘勸他人自殺,或者,單獨一個警察會暴打一個手無寸鐵的乘客。在某些群體情境中,人們更可能拋棄道德約束,以至於忘卻了個人的身份,而順從於群體規範——簡言之,也就是變得去個體化 (deindividuated)。什麼環境會引發這種心理狀態呢?
群體規模
一個群體不僅能引發成員們的喚起狀態,也能使他們的個體身份模糊化。尖叫的人群遮蔽了尖叫的球迷。一個濫用私刑的暴徒組織會使成員堅信自己不可能被起訴;他們把這種行為看做是群體 的所作所為。處在一群暴民之中而不必暴露自己姓名的暴動者們會任意地搶掠。經過對21起人群圍觀跳樓或者跳橋事件的分析,曼(Mann,1981)發現:如果人群規模小且曝於日光之下的話,人們通常是不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的。但如果人群規模比較龐大或夜幕賦予人們匿名性的身份,那麼,人群中的大多數人會誘勸當事者往下跳並且加以冷嘲熱諷。
馬倫(Mullen,1986)指出,在使用私刑的暴徒中也存在類似的效應:暴徒團伙的規模越大,成員越有可能失去較多的自我意識,他們就更樂於去幹諸如縱火、砍人、肢解等暴行。從體育觀眾到用私刑的暴徒,所有這些例子中,個體的評價顧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為“每個人都如此行為,”因此,所有的人都會把其行為的責任歸因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選擇。
津巴多(Zimbardo,1970)推斷僅是城市人山人海這一特點就足以產生匿名性的效應,從而使損壞公物成為個體道德中所許可的行為。他買了兩輛已使用過十年的舊車,然後把它們的牌照拆掉,把引擎蓋掀開,他把其中一輛車放在紐約大學布朗克斯校區附近,另一輛放在斯坦福大學的帕羅奧托校區附近,這是一個比前者小得多的城市。結果發現在紐約,第一批“汽車清理者”在十分鐘之內就到達了;他們拿走了電池和散熱器。在三天的時間內,發生了23起偷竊和破壞事件,最後汽車成了一堆被敲碎的沒用的廢銅爛鐵了。相反,在帕洛·奧托觀察到的惟一一個碰過那輛車的人,是一個多星期之後,一個過路人在天要下雨的時候把引擎蓋合上了。
身體匿名性
我們怎麼能斷言布朗克斯和帕洛·奧托之間關鍵的差別就在於布朗克斯的匿名性更大呢?我們做不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就匿名性設計一個實驗,看它是不是真的能減少抑制性的行為。津巴多(1970,2002)從他學生那裡獲得了實驗的靈感,那個學生問他,在戈爾登的《蠅王》中,那些本來很善良的男孩為什麼會在臉上塗上東西以後突然間變成了惡魔呢?為了實驗這種匿名性,津巴多(1979)讓紐約大學的女學生穿上一樣的白色衣服和帽兜,這和三K黨(Ku Klux Klan)成員(圖8-6)非常相似。然後讓她們按鍵對另一個女性實施電擊,結果發現她們按鍵的時間要比那些可以看見對方並且身上貼著很大名字標籤的女生長一倍。

圖8-6
匿名女生給無助的受害者實施的電擊強度要比非匿名女生實施的大。
互聯網也提供了類似的匿名性。幾百萬驚愕於巴格達暴徒的掠奪行徑的人自己卻在利用網上的共享軟件製作盜版光盤。因為這樣做的人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們幾乎不會認為下載別人版權所有的音樂到MP3裡有多麼不道德,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因此而被逮捕。網絡聊天室、新聞工作組的匿名性也使其中敵對而激進的行為比面對面交談中要多得多(Douglas & McGarty,2001)。
為了在街上證實這種現象,埃利森、戈文及其同事們(Ellison,Govern,& others,1995)僱了一個“司機同謀者”,讓她遇到紅燈時先暫停一會兒,並且當後面有一輛敞篷車或者有一輛4×4輪子車的時候等上12秒鐘再開。在等待的時候,她記錄後面車所發出的喇叭聲(一種輕微的攻擊性行為)。相對於敞篷車的司機,那些把頂蓋放下來的4×4輪子車司機是匿名的,他們鳴喇叭的速度要比前者快1/3,而頻率是前者的兩倍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幾乎是前者的兩倍。
一個由迪納(Diener,1976)領導的研究小組以巧妙的研究設計分別在群體情境中和 身體匿名情境中都發現了這種效應。在萬聖節前夕,他們在西雅圖觀察了1352個孩子玩“不請吃糖,就惡作劇”的遊戲。那些孩子或單獨或結伴,他們走訪了全城1/27的家庭,有一名研究者也熱情地招待了他們,並邀請他們“從這些糖果裡拿一粒 ,”然後就離開了房間。隱藏在暗處的研究者注意到,結伴的孩子們比單獨的孩子多拿糖的可能性要大一倍。而且,那些匿名的孩子比那些被問及姓名和住處的孩子違規的可能性也要大一倍。如圖8-7所示,違規率依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孩子會因群體的掩蓋和匿名性而去個性化,因此會偷拿額外的糖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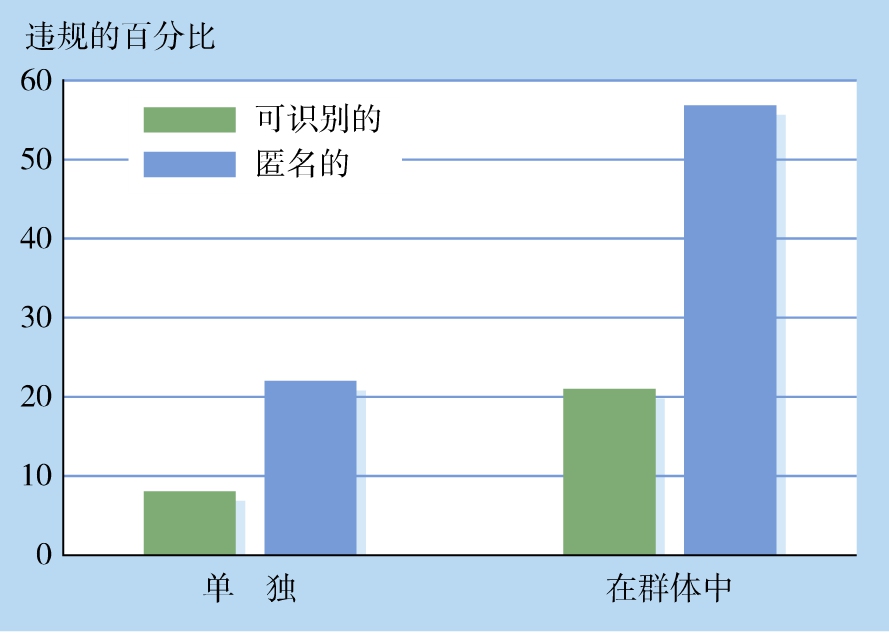
圖8-7
結伴或者匿名時,尤其是當群體性和匿名性條件都俱備時,孩子們更可能違規去偷拿額外的萬聖節糖果。
資料來源:Data from Diener & others,1976.
這些實驗令我想知道穿制服的作用效果。為了準備作戰,一些部落中的鬥士(像一些狂熱的體育迷一樣)會用油彩或者面具裝扮自己的身體和臉孔,使自己去個性化。戰鬥結束後,有一些部落會殺死、折磨或者摧殘任何倖存的戰俘;而另一些部落會讓戰俘活著。沃森(Watson,1973)仔細研究了一些人類學檔案後發現,那些去個性化的鬥士部落幾乎都會對其敵人施以暴行。那些毆打羅德尼·金的穿制服的洛杉磯警察被他反叛性的拒絕停車行為惹怒並且喚起了。他們享受著彼此之間的友愛之情從而對外界將會如何看待他們置之度外。就這樣,他們忘記了社會的常規,而被情境捲入其中。
在北愛爾蘭,西爾克(Silke,2003)發現,在500例暴力事件中,有206例襲擊者都頭戴面具、頭巾或其他面部偽裝物。與未偽裝的襲擊者相比,這些匿名的襲擊者表現出更嚴重的襲擊行為。
身體匿名性是否總 能引發人們釋放最邪惡的衝動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這些情境中,人們顯然是對一些反社會的暗示線索作出了反應。約翰遜和唐寧(Johnson & Downing,1979)指出津巴多的被試們類似三K黨成員的裝扮可能會慫恿敵意行為。在佐治亞大學進行了這樣一項實驗,即是要求女被試在決定給別人實施多大程度的電擊之前穿上護士制服。在實施電擊時,這些穿護士制服的被試如果得以保持其匿名性,那她們的攻擊性就遠不如說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時的情況大。波斯特梅斯和斯皮爾斯(Postmes & Spears,1998;Reicher & others,1995)對60項去個體化研究做了分析,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匿名性使人們的自我意識減弱,群體意識增強,更容易對情境線索作出迴應,無論這線索是消極的(三K黨制服)還是積極的(護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線索,去個體化的人們甚至會施捨更多的錢財(Spivey & Prentice-Dunn,1990)。
喚起和分心活動
群體表現出攻擊性之前常常會發生一些較小的引發人們喚起狀態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體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們熱情似火又能減少其自我意識。一位文鮮明統一教團的(Moonie)目睹者回憶起“choo-choo”歌就是這樣使人們去個體化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們手拉著手熱情地高唱,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CHOO!YEA!YEA!POWW!!!這樣的行為使我們組成了一個群體,似乎我們一起以一種很奇怪的方式來體驗某種重要的東西。choo-choo的力量令我震驚,但它使我感覺很舒適而且令我很放鬆(Zimbardo & others,1977,p.186)。
迪納的實驗(1976,1979)表明,像扔石頭、小組合唱這樣的活動可能會成為其他更放肆行為的前奏。當人們看到別人和自己做出同樣的行為時,會對自己做出衝動性的舉動產生一種自我強化的愉悅感。當看到別人和自己做得一樣時,我們會認為他們也和我們想得一樣,因而這又會強化我們自己的感受(Orive,1984)。而且,衝動性的集體行為能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當我們衝著裁判大喊大叫時,並不會想到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念,而只是對情境做出一種即時的反應罷了。有時,當我們事後停下來反省自己所做過的事和所說過的話時,會覺得很懊惱,但這只是有時候而已。還有一些時候,我們會主動尋找去個體化的群體體驗——跳舞,宗教體驗,群體交流等等,從中我們能體驗到強烈的積極情感以及與他人親密無間的關係。
弱化自我意識
能弱化自我意識的群體體驗通常能分離個體的行為和態度。迪納(1980)以及鄧恩(Steven Prentice-Dunn)和羅傑斯(Rogers,1980,1989)所做的實驗表明:無自我意識、去個體化的人更不自控,更不自律,更可能毫不顧及自己的價值觀就做出行動,對情境的反應性也更強烈。這些發現正好可以補充和強化第3章中提到有關自我意識 的實驗。
自我覺察是去個體化的對立面。自我覺察的人,以站在鏡子或者攝像機面前的人為例,會表現得更加 自控,這時他們的行為也能夠清晰地反映他們的態度。比如,如果人們在鏡子面前品嚐各種奶油乾酪,就會挑那些低脂肪的品種來吃(Sentyrz & Bushman,1998)。這樣看來,也許節食者們應該在廚房裡安一面鏡子。
自我覺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Beaman & others,1979;Diener & Wallbom,1976)。那些一直堅信自己是獨立而與眾不同之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騙行為(Nadler & others,1982)。自我意識的個體,或僅是受他人驅使而產生暫時性自我意識的個體,他們在情境中會表現出更大程度的言行一致性。這些個體也會越來越理智,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受有悖於自己價值觀的呼聲所影響(Hutton & Baumeister,1992)。
喝酒之類的情境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覺察,從而增強個體的去個性化(Hull & others,1983)。而能夠增強自我覺察的情境,比如:鏡子和攝像機,小鎮,明亮的光線,很大的姓名標籤,凝神靜思,個性化的著裝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降低個體的去個性化(Ickes & others,1978)。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去參加聚會時,父母可能會這樣說,“玩得開心,還有要記住你自己的身份。”這是父母在孩子臨行前給其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說,和大傢伙一起享受歡樂的同時要保持自我覺察;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被去個性化。
小結
高水平的社會喚起與責任擴散的結合有可能使人們放棄自己的道德約束或者喪失自己的個性。當個體處在一個大的群體之中或者身穿有隱蔽作用的服裝時,會被喚起,或者分心,進而體驗到一種匿名性,在這樣的情境中,尤其可能發生去個性化現象。其結果就是自我覺察和自我約束減弱,而對積極或消極的直接情境因素的反應性增強。
群體極化: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許多矛盾都是由於雙方總和與自己思想觀念相似的人交流而產生的。這種互動是否會加強個體原本的態度呢?如果是的話,那是為什麼呢?
群體互動通常會產生哪種效果呢?積極的?抑或消極的?警察暴力和團伙暴力都證明了群體互動潛在的破壞性。但是另一方面,支持型群體領導、管理顧問和教育理論家都肯定了它的益處,而且社會活動和宗教活動也激勵其成員通過和持有相同想法的其他成員建立聯繫來加強自身的信念。
這方面的研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效應。我們從對小群體中人們的研究得出了一條準則,它有利於我們對積極和消極的結果都作出解釋:群體討論通常可以強化其成員最初的意向。群體極化 的研究體現了探索的過程——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如何導致研究者們草率地做出錯誤的結論,而最終這些結論又被更準確的結論所代替。作為研究者之一,這是一個我能夠與大家直接討論的科學謎題。
“風險轉移”的案例
一篇涵蓋了300多個研究的文獻在其開篇就引用了一項驚人的發現,它的提出者斯托納(Stoner,1961)當時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他的工業管理碩士論文中,斯托納對人們普遍認同的一種看法——群體比個人在決策時更為審慎——進行了研究。他設計了一些決策時的兩難情境,被試的任務是建議假想的人物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承擔風險。假設你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名被試,你會在以下的情境中給該人物提供什麼樣的建議呢?
海倫是一名很有創作天賦的作家,但是迄今為止她都是依靠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最近她突然萌生了一個念頭,想要寫一部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如果這部小說能夠完成並且被人們接受的話,它可能會在文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且這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她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如果她的想法最終沒能實現,又或者這部小說是一部失敗之作,那麼她將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得不到任何回報。
設想你正在給海倫提建議。請指出你所認為的她會嘗試寫這部小說的最低 可能性。
當這部小說取得成功的概率至少為_____時,海倫會嘗試寫這部小說?
_____1/10
_____2/10
_____3/10
_____4/10
_____5/10
_____6/10
_____7/10
_____8/10
_____9/10
_____10/10(選擇這一項是指你認為海倫只有在認為這部小說絕對會成功的情況下才會嘗試寫 。)
當你做出決定後,猜猜這本書的所有讀者平均而言會提出怎樣的建議。
在對很多這樣的問題給出自己的建議後,每五個人左右會被安排在一起進行討論,並就每一個問題達成共識。你認為群體決策與討論之前所有人單獨決策所得的平均值相比,會有什麼差別呢?群體會傾向於冒更大的風險?還是更為審慎?又或是與個體沒有差別?
令大家吃驚的是,群體決策往往會更加冒險。這個被稱為“風險轉移”的發現推動了一股研究群體冒險性的浪潮。這些研究指出,冒險轉移不僅發生在需要達成共識的群體中,在某一次短暫的討論之後,個體也會改變他們以前的決定。此外,研究者們選取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和不同國家的被試,都得出了與斯托納的發現相同的結果。
在討論中,不同的看法會趨於統一。但奇怪的是,人們趨於統一所得出的觀點往往比他們原始觀點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傾向於冒險。這是個令人振奮的謎題。風險轉移效應是可信的,也是意料之外的,並且無法立刻找出任何明顯的解釋。群體影響的什麼因素可以產生這種效應呢?這種效應的作用範圍有多大?陪審團、商業委員會以及軍事機構中所展開的各種討論是否也會促進人們的冒險行為呢?如果以死亡率作為衡量標準,在有另兩名同伴的情況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魯莽駕車的可能性幾乎是車上沒有任何同伴情況下的兩倍(Chen & others,2000),這是否也能用上述效應來解釋呢?
在數年的研究之後,我們發現,風險轉移並不是普遍適用的。在我們所設計的某些兩難情境中,人們在討論之後會變得更為謹慎 。其中一個情境的主人公叫羅傑。羅傑是一名已婚的青年男子,他有兩個正值讀書年齡的孩子,有一份穩定但是薪酬不高的工作。他能負擔得起必需的生活用品,但對豪華用品就不敢奢望了。他聽說一家不怎麼有名的公司的新產品如果銷路很好的話,那這家公司的庫存品價值會迅速升值為以前的三倍,但是如果新產品賣不出去的話,那庫存價格就會下跌。羅傑沒什麼積蓄,為了投資這家公司,他正考慮賣掉自己的人壽保險。
你能找出一條一般性的規律來解釋為什麼人們在討論了海倫情境之後會傾向於冒進,而在討論了羅傑情境之後卻會傾向於謹慎行事嗎?
如果你和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建議海倫冒更大的風險而不是建議羅傑去冒風險,即使在和其他人討論之前也會如此。事實上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會加強人們最初的看法。
群體會強化我們的觀點嗎
由此我們意識到,這種群體現象的結果並不是一味地朝冒險的方向偏移,但是群體討論卻傾向於使群體成員的初始觀點得到加強 。這種觀點促使研究者們提出一個被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Moscovici & Zavalloni,1969)稱為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的概念:討論通常可以強化群體成員的平均傾向。
群體極化實驗
群體討論會引發改變的新觀點啟發了研究者們,他們在實驗中組織人們討論大多數成員都贊同的觀點或大多數人都反對的觀點。在群體中進行的這種談話會像在兩難決策情境中那樣,加強成員最初的傾向嗎?在群體中,是否冒險者會表現得更加冒險,頑固者會更為頑固,樂於助人者會更加樂善好施呢?因為這些正是群體極化理論所預言的(圖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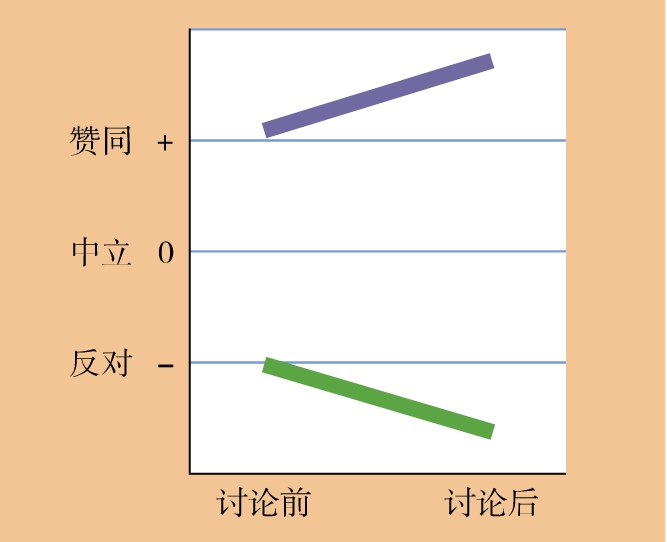
圖8-8 群體極化
群體極化理論預測討論會強化群體成員的共同態度。
很多研究證實了群體極化現象的存在。
莫斯科維斯和扎瓦羅尼(1969)觀察發現,討論可以加強法國學生本來就對總統所持的積極態度,同時也可以加強他們原本對美國所持的消極態度。
Isozaki(1984)發現,當日本的大學生集體討論了一宗交通事故案例以後,他們對“有罪”有了更明確的裁定和判斷。
懷特(Whyte,1993)指出,群體可以加劇“投資過多難以抽身而退”的現象,使許多商業活動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加拿大的商學院學生想像自己必須做出決定:是否為了避免在某些瀕臨失敗項目上的損失,而對這些項目追加投資(比如,是否應該為了保護之前的某項投資而冒很大的風險去貸款),他們表現出了典型的效應:72%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但是,如果這是一個全新的項目,在考慮該項目自身優缺點的條件下,他們幾乎都不會對其投資。當他們是在群體中作相同的決策時,94%的人都表示會追加投資。
另一種研究方法是選擇一些觀點存在分歧的事件,然後把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分隔開,把觀點相同的人們安排在一起。觀點相似的人們在一起討論的結果是否會加強他們所共同認可的觀點呢?討論是否會加深兩種不同態度之間的鴻溝呢?
畢曉普(George Bishop)和我對此都很好奇。因此,我們選擇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群體:相對而言有種族偏見和無種族偏見的高中生。我們要求他們在討論之前和之後對某些有關種族態度的問題做出反應,例如財產權和居住條件(Myers & Bishop,1970)。我們發現在觀點相似的學生群體裡進行的討論確實可以加深兩個群體之間觀點的差距(圖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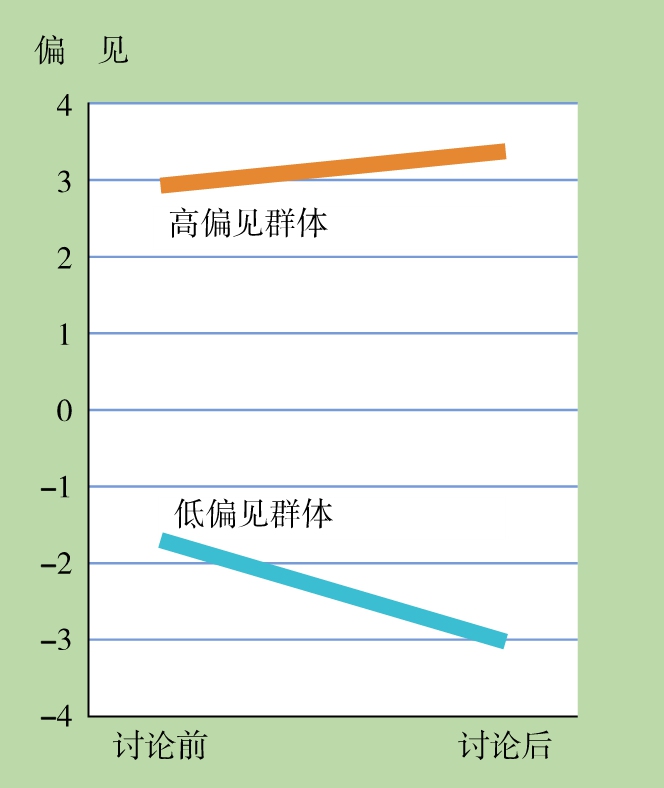
圖8-9
在具有高種族偏見和低種族偏見的兩個匹配的高中生群體中,討論加深了極化程度。談論與種族相關的問題增強了高偏見組的種族偏見,降低了低偏見組的種族偏見。
資料來源:Data from Myers & Bishop,1970.
日常生活中的群體極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往往是和與自己觀點相似的人進行交往(第11章)。(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與這些觀點相似的朋友之間的日常交流是否會強化大家共同認可的觀點呢?這樣是否會令討厭的人變得更為可憎,純真的人變得更為純真呢?
的確如此。麥科比(Maccoby,2002)提出,男孩群體和女孩群體的性別隔離能夠加強他們最初中度的性別差異。男孩們在一起遊戲時,會漸漸變得更加富於競爭性並做出行動取向。而女孩們在一起則會越來越傾向於做出關係取向。斯凱德和森斯坦(Schkade & Sunstein,2003)發現,在美國聯邦法庭裡,“共和黨任命法官會挑選那些更像共和黨的人,而民主黨任命法官則傾向於挑選那些更像民主黨的人。”和觀點相似的法官在一起又會強化這種傾向。“一個共和黨法官和其他兩個共和黨成員在一起時,比和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民主黨成員在一起時審判更保守,而民主黨法官也表現出這一傾向。”
學校中的群體極化 與實驗室的結果相一致的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現象是教育研究者稱之為的“加劇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生群體之間最初的差異會被擴大化。如果X大學的學生最初就比Y大學的學生善於思考,那這種差異多半會在大學期間擴大。類似地,和各種群體以及姊妹會的成員相比,無黨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這種差異即是在大學生活中逐漸形成的(Pascarella & Terenzini,1991)。研究者認為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群體成員會強化他們彼此共有的傾向。
社區中的群體極化 極化現象也發生在社區中。在社區衝突中,想法相似的人們會逐漸聯合起來,使他們共有的傾向得以加強。在相鄰團伙相互強化的過程中,犯罪團伙便產生了,他們的成員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質和敵意性人格(Cartwright,1975)。“如果,在你的街區住進來了第二個無法管束的15歲少年,”萊肯(Lykken,1997)總結道,“他們作為一個團伙所帶來的破壞性可能並不僅僅是第一個人單獨所帶來的損害的兩倍……一個團伙的危險性遠遠大於其成員個體之和。”確實,根據維齊和梅斯納(Veysey & Messner,1999)的報告,缺乏監管的同齡人群體是預測一個社區的犯罪受害率的最有力指標。而且,實驗發現將未成年違法者和其他違法者放在同一個群體中——不出任何一個群體極化的研究者所料——會增加問題行為的發生率(Dishion & others,1999)。[在兩次審判中,南非法庭在學習了社會心理學現象是怎樣使一群人犯下殺人罪行之後,減輕了對他們的判決,這些社會心理學現象當然包括去個性化和群體極化(Colman,1991)。你是否同意法庭應該考慮社會心理學現象並將其作為可能的減刑條件? ]
在對全世界恐怖組織進行分析後,麥考利和西格爾(McCauley & Segal,1987;McCauley,2002)指出,恐怖主義並不是突然間爆發的,而是擁有相同不滿情緒的人們走到一起而產生的。他們脫離了能令自己的不滿情緒緩和下來的影響,彼此之間相互交流,逐漸變得更加極端。社會放大器將信號變得更為強烈。結果是,個體成員表現出了在遠離群體時決不會做的暴力行為。
舉例來說,9.11恐怖事件就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在長期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極化效應造成的。國家研究委員會的專家稱,成為一個恐怖分子的過程可能就是把個體和其他信念系統隔離開,使潛在的目標失去人性,而且令其不能忍受任何異議(Smelser & Mitchell,2002)。麥若瑞(Ariel Merari,2002)是一位中東和斯里蘭卡自殺性恐怖主義的研究者,他認為製造自殺性恐怖事件的關鍵因素就是群體過程。“據我所知,還從未出現過因個人一時的興致而導致的自殺性事件。”大屠殺都是殺人者相互慫恿而造成的團體現象(Zajonc,2000)。
互聯網上的群體極化 電子郵件和電子聊天室為群體交流提供了一種潛在的新媒介。在新世紀之初,85%的加拿大青少年平均每週會有9.3小時使用互聯網(TGM,2000)。互聯網上數不勝數的群體使得和平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雜耍演員和野蠻人,陰謀家和癌症患者都能找到與之具有相同的關注點、興趣和疑問的人(Gerstenfeld,2003;McKenna & Bargh,1998,2000;Sunstein,2001)。沒有了面對面接觸的非言語差異,這樣的討論會產生群體極化嗎?和平主義者是否會變得更加反戰,而主張戰爭的成員是否會變得更有恐怖主義傾向?懷特(Robert Wright,2003)指出,電子郵件、搜索引擎和網絡聊天室“提供了一種便利條件,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結起來,令分散的敵意更加明確,也能夠動員致命的武裝力量。”隨著寬帶的普及,由互聯網產生的極化也越來越多,他推測,“是否曾經看過拉登的招兵錄影帶?這非常有效,利用寬帶網,它們能夠更方便地抵達其目標人員。”
聚焦 群體極化
莎士比亞以凱撒的擁護者們的一段對話描述了觀點相同的群體所具有的極化力量:
安東尼 :善良的靈魂啊,當你而不是我們凱撒的衣袍被損壞時,你為什麼會哭泣?你來看看吧。就像你看到的那樣,這就是被叛徒弄傷的他。
市民甲 :多可憐的景象啊!
市民乙 :高貴的凱撒啊!
市民丙 :真是糟糕的一天!
市民丁 :叛徒,惡棍!
市民甲 :最血腥的景象!
市民乙 :我們要報仇!
所有的人 :報仇!就在附近!去搜查!燒吧!放火吧!殺吧!不能讓任何一個叛徒活著!
資料來源:From Julius Caesar by William Shakespeare,Act Ⅲ,SceneⅡ,lines 199-209.
對極化的解釋
為什麼群體會採用比其個體成員的平均觀點更為誇大的觀點呢?研究者們希望通過解決群體極化的謎題來為此提供思路。解答小謎題有時候會為大謎題提供線索。
在提出的幾種群體極化理論中,有兩種理論已被科學實驗所證實。其中一種著重於討論中所提出的觀點,另一種著重於群體成員如何看待他們自己和其他成員。第一種觀點恰好是第6章所提到的信息影響 (由於接受了事實的證據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而第二種觀點是規範影響 (基於人們希望被他人接受或敬仰的願望而產生的影響)的例證。
信息影響
從最受支持的解釋出發,群體討論可以產生一系列觀點,而大多數觀點都和主導性觀點一致。那些對群體成員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識的觀點也會被帶入討論,這些觀點即使沒被提及,也會被連帶著影響討論(Gigone & Hastie,1993;Larson & others,1994;Stasser,1991)。其他觀點也許會包含一些群體成員在此之前並沒有考慮到的具有說服力的觀點。當討論作家海倫時,也許有人會說:“海倫應該著手去做,因為她幾乎不會有什麼損失。如果她的長篇小說失敗了,她仍然可以像從前那樣去寫通俗的西部小說。”這樣的說法通常是將提出者的觀點 和他的立場 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們不瞭解他人的特定立場而只是聽到相關的觀點時,他們仍然會改變自己的立場(Burnstein & Vinokur,1977;Hinsz & others,1997)。觀點 就其本質而言事關重大。
但是,態度的轉變並不僅僅由於聽到他人的觀點。討論中的積極參與 會比消極聆聽更容易導致態度的轉變。參與者和觀察者聽到的是相同的觀點,但是一旦參與者用自己的話語表達該觀點時,言語的使用會擴大這種影響作用。群體成員對別人觀點重複得越多,他們就越可能在不斷的複述中認同這些觀點(Brauer & others,1995)。僅僅是在某一次電子討論的準備中寫下某人的觀點也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的態度極化(Liu & Latané,1998)。
這印證了第7章提到的一個觀點。人們的大腦並非像白板那樣供說服者們填寫,在核心路線的說服中,人們怎樣看待 某條信息很關鍵。事實上,僅僅對某一個觀點思考上幾分鐘也會使看法得以強化(Tesser & others,1995)。(或許你會回想起,當你僅僅想起某個你不喜歡或喜歡的人時,你的感受也會變得極端起來。)甚至當人們只是設想 將和一位持有相反觀點的專家一同討論某一事件時,他們也會充滿動力去編排論點並且採取更為極端的立場(Fitzpatrick & Eagly,1981)。
規範影響
第二種對極化的解釋涉及到與他人的比較。費斯汀格(Festinger,1954)在其極具影響力的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理論中提出,我們人類希望能對自己的觀點和能力做出評價,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將自己的觀點與他人比較來達成。我們常常被“參照群體”中的人們所說服(Abrams & others,1990;Hogg & others,1990)。所謂參照群體就是與我們相一致的群體。而且,當我們發現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觀點時,為了使其他人喜歡我們,我們會將觀點表達得更為強烈。
巴倫及其同事們(Baron & others,1996)發現了令個體的觀點得到社會化鞏固所產生的極化效應。他們詢問愛荷華大學牙科診所的病人們認為牙科診所的椅子是“舒適的”還是“不舒適的”。其中一部分被試會聽到主試詢問:“順便問一句,XX醫生,剛才的那位病人是怎麼回答的?”然後牙科醫生會把之前那位病人的回答重複一遍。最後,病人們會在一個150~250點的量表上對椅子的舒適程度做出評定。與沒有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被試相比,那些聽到自己的觀點被證實的病人斷然地做出了更為極端的評定。
當我們要求人們預測在類似海倫困境一類的問題中其他人的反應方式(就像我之前要求你們去做的那樣)時,他們通常會表現出人眾無知: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其他人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會普遍認同的傾向(在這個例子中,是指寫長篇小說)。即使成功的機會只有4/10,一個典型有代表性的被試也會建議海倫寫那部長篇小說,而且他估計其他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5/10或6/10。(這個發現使我們想起了自我服務偏見: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要好於社會普遍所希望具有的特質和態度。)當開始討論時,大部分人都發現自己的觀點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出眾。事實上,其他一些人比自己更為超前,對於寫小說這件事採取了更為堅定的立場。於是他們不再受對群體規範的錯誤約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強烈地表達自己的偏好。
或許你能回憶起曾經有一次你和其他人都希望外出遊玩,但是你們每個人都害怕邁出第一步,以為其他人可能對此並沒有興趣。這樣的人眾無知 (pluralistic ignorance)會阻礙人際關係的開始(Vorauer & Ratner,1996)。
又或許你會回憶起曾經有一次在一個群體中,你和其他人都很拘謹地沉默著,直到某個人打破沉默說道:“嗯,坦白說,我認為……”於是很快地,你們都驚訝地發現原來大家都強烈地支持彼此所認同的觀點。有時,當教授問大家有什麼疑問時,沒有人會做出反應,因為每個學生都怕別人以為他或她是惟一一個沒聽懂的人。所有人都認為自己保持沉默是害怕出醜,而別人保持沉默是因為他們已經聽懂了教授的材料。
米勒和麥克法蘭(Miller & McFarland,1987)從一個實驗室實驗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他們讓人們閱讀一篇很難理解的文章,並告訴他們在理解文章時遇到“任何確實難以理解的問題”時可以尋求幫助。儘管沒有一個被試尋求幫助,但他們卻認為其他被試不會和他們自己那樣被害怕出醜的念頭約束。他們錯誤地認為那些沒有尋求幫助的人是因為他們不需要任何幫助。為了克服這種人眾無知,就必須有人站出來打破沉寂,使其他人能夠發現並且強化他們共同的觀點和反應。
這種社會比較理論引發了一系列的實驗,在這些實驗中人們面對的是他人的立場而不是觀點。這大致上類似我們閱讀一個民意測驗的結果或是選舉的最終結果時的體驗。如果人們瞭解了他人的立場——在沒有討論的情況下——那他們是否會改變自己的反應來迎合一個被社會認同的立場呢?(見圖8-10所舉的例子。)這種基於比較的極化效應通常沒有現場討論所產生的極化效應那麼強烈。但是,令人吃驚的是,人們並不是簡單地向群體平均值靠攏,而是比其更勝一籌。人們是否期望通過比規範更勝一籌來將自己與群體區分開來呢?這是否是我們需要體驗到自我獨一無二的又一例證呢(第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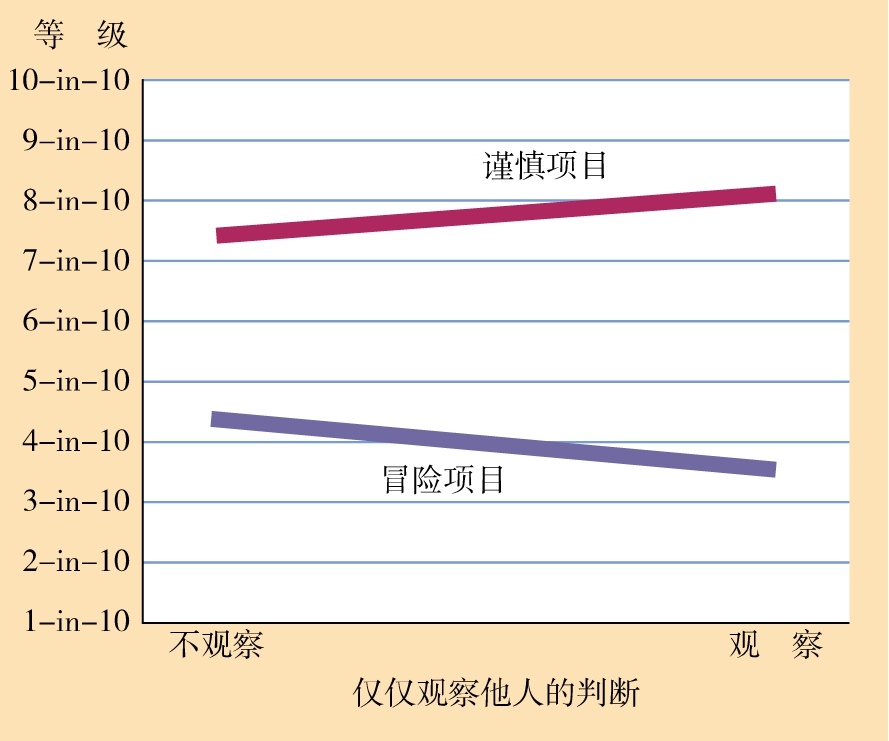
圖8-10
在“冒險”困境中(如海倫的例子),僅僅是觀察他人做出判斷就會增強個體的冒險傾向。在“謹慎”困境中(如羅傑的例子),觀察他人做出判斷可以增強個體的謹慎性。
資料來源:Data from Myers,1978.
群體極化的研究表明社會心理學調查的複雜性。儘管我們十分希望對某種現象的解釋能儘量簡潔,但一種解釋很少能解釋所有的數據。由於人類的複雜性,致使一個以上的因素常常會影響最終結果。在群體討論中,有說服力的論點往往主宰那些涉及事實的問題(“她是否為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愧疚?”)。而社會比較會影響那些涉及價值判斷的反應(“她應該被判多長時間的徒刑?”)(Kaplan,1989)。在很多既涉及事實又涉及價值判斷的事件中,這兩個因素會共同起作用。發現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會比較)會使每個人暗自贊成的那些觀點(信息影響)被釋放出來。
小結
潛在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來自群體討論。在你試圖理解群體討論會加強個體的冒險性這一有趣的發現時,研究者發現實際上是討論加強了原本的主導觀點,無論是冒險的還是審慎的。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樣,群體交流會強化觀點。群體極化現象為研究者觀察群體影響打開了一扇明窗。研究者證實了兩種群體影響:信息影響和規範影響。從討論中收集起來的信息大多有利於大家最初的選擇,因此會強化對其的支持。而且,如果人們在比較了各自的立場後,驚奇地發現其他人都對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態度,那他們就會表現得比以前的意向更勝一籌。
群體思維:群體會阻礙還是促進好的決策
什麼情況下群體影響會阻礙好的決策?什麼情況下群體會促進好的決策,以及我們應怎樣引導群體做出最好的決策?
我們在前八章所討論的社會心理學現象是否同樣會發生在公司董事會或者總統內閣這樣複雜的群體中呢?他們是否會出現自我合理化行為?或者自我服務偏見?那種有凝聚力的“我們的感受”是否會喚起從眾或是拒絕異議的行為?公開承諾是否可以抗拒改變?是否存在群體極化現象?社會心理學家賈尼斯(Irving Janis,1971,1982)想知道這些現象是否能幫助解釋20世紀的美國總統及其顧問怎樣做出好的或壞的群體決策。為此,他分析了幾次大的失敗決策的過程:
珍珠港 。1941年12月的珍珠港被襲事件使美國也加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事件發生之前的幾個星期,夏威夷的軍事指揮收到了一條可靠的消息:日本計劃襲擊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某個地方。之後軍事情報失去了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聯繫,那時航空母艦正徑直朝夏威夷前進。空中偵察隊本來應該能偵察出航空母艦的位置或者至少發出幾分鐘的警報。但是自以為是的司令們完全無動於衷。結果是:直到日軍開始對這個毫無防備的基地發動襲擊,警報才被拉響。襲擊後美軍損失了:18艘艦艇、170艘飛機,以及2400條生命。
入侵豬灣 。1961年,總統肯尼迪及其顧問們試圖用1400名由CIA訓練過的古巴流放者來襲擊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羅政權。幾乎所有的襲擊者都被殺或是被抓獲,美國顏面盡失,而且古巴與前蘇聯更為團結了。在得知後果以後,肯尼迪大呼:“我們怎麼做出瞭如此愚蠢的事呢?”
越南戰爭 。在1964到1967年之間,由總統約翰遜及其政治顧問組成的“週二午餐團”決定擴大對越南的戰爭,因為他們預測美國的空中轟炸、空降以及搜索搗毀任務會迫使北越南接受和談,而南越南人民出於感激也會支持和談。儘管政府的情報專家以及所有美國的盟國都對他們提出警告,但他們還是繼續將戰爭擴大化。這場災難使58000多美國人和100萬越南人喪生,美國人變得極端化,總統被迫下臺,龐大的財政赤字加速了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
研究背後的故事:
賈尼斯對群體思維的研究
當我閱讀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描述關於肯尼迪政府如何決定襲擊豬灣的內容時,我萌發了群體思維的念頭。一開始,我很困惑:像肯尼迪及其顧問那樣聰明雄辯的人怎麼會捲入由CIA愚蠢拼湊起來的計劃中呢?我開始關注其間是否涉及一些心理學因素,例如社會從眾或是我在團結的小型群體中所觀察到的尋求一致。進一步的研究(開始是受我女兒夏洛特高中論文的啟發)使我相信一些微妙的群體過程阻礙了他們仔細地評估風險和討論問題。接著當我分析了其他的美國外交失誤以及水門事件後,我發現了同樣不利的群體過程。
賈尼斯認為釀成這些大錯的原因是由於在群體決策中人們為了維護群體和睦而壓制異議,他把這種現象稱為群體思維 (groupthink)。在群體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產力(Mullen & Copper,1994)。而且,團隊精神有助於鼓舞士氣。但是在決策時,緊密團結的群體可能反而不利。賈尼斯認為友善的、凝聚力強 的群體,對異議的相對排斥 ,以及從自己的喜好出發做決策的支配型領導 都恰是培養群體思維的溫床。
在計劃那次不幸的豬灣襲擊時,剛剛當選的肯尼迪總統和他的顧問們高興地組成了一個極有團隊精神的隊伍。而對這次計劃十分關鍵的觀點都被壓制或是排除了,總統本人很快就對這次襲擊表示了認同。
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
從歷史記錄以及參與者和觀察者的回憶來看,賈尼斯列出了八條群體思維的症狀表現。這些症狀集中反映了對異議的排除,表面上看來就是群體成員在遇到威脅時,會努力保持他們的積極群體感(Turner & others,1992,1994)。
前兩條群體思維症狀表現往往導致群體成員高估群體的力量和權利 :
無懈可擊的錯覺 。賈尼斯所研究的群體都表現得過分自信,以致矇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險警報。當珍珠港的海軍總指揮基梅爾(Admiral Kimmel)得知他們已經與日本航空母艦的無線電失去聯繫後,還開玩笑說或許日本人打算繞檀香山轉一圈。事實上日本人確實這樣做了,但基梅爾對這種想法的嘲諷使人們認為這不可能是事實。
對群體道義無可質疑 。群體成員接受了其所在群體內在的道義,卻忽略了倫理和道義上的其他問題。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顧問和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議員對於襲擊一個小小的鄰國在道義上持保留態度,但整個群體從沒接納或討論過這些道義上的疑慮。
群體成員還會在想法上變得越來越接近 :
合理化 群體以集體將決策合理化的方式來減少挑戰。比起自省和重新考慮以前的決定,約翰遜總統的週二午餐團花了更多的時間來使擴大戰爭的決策合理化(對其進行解釋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個行為都變成了掩飾和合理化。
對對手的刻板印象 陷於群體思維的人們往往會認為自己的對手不是太難於協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於難以抵抗他們的計劃。肯尼迪等人自認為卡斯特羅的軍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勢力也很弱,因此僅僅一個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權。
最後,群體會受制於追求一致性 的壓力:
從眾壓力 群體成員會抵制那些對群體的設想和計劃提出疑問的人,而且有時候這種抵制並不是通過討論而是針對個人的嘲諷。有一次,當約翰遜總統的助理莫伊斯抵達會場時,總統嘲笑他說:“噢,‘阻止爆炸的先生’來了呀!”面對這樣的譏諷,很多人都選擇了從眾。
自我審查 (self-censorship)壓力 由於異議往往會令人不舒服,而且整個群體似乎表現出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會將自己的疑慮壓制下來。在豬灣襲擊之後的幾個月,施萊辛格(1965,p.255)自我譴責說,他在“內閣進行的那些重要會議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對意見也無濟於事,我仍將被人們厭惡,這樣的念頭壓倒了我的愧疚感”。
一致同意錯覺 不要去破壞一致性的這種自我潛意識壓力會導致一致同意錯覺。而且,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堅定了群體的決策。這種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誤中十分明顯,在其前後的其他失誤也是如此。斯皮爾(Speer,1971),希特勒的顧問之一,把希特勒周圍的氛圍描述為,從眾的壓力壓制了一切異議。異議的缺乏造成了一致同意錯覺:
在正常的氛圍中,背離事實的人們會很快被拉回正軌,因為他們會受到周圍人的嘲弄或批評,這樣他們就會意識到自己已經失去了可信度。而在第三德意志帝國,沒有這樣的矯正措施,尤其是對那些身處社會高層的人們而言。相反,每個人的自我欺騙都被放大了,就好像是身處一個擺滿哈哈鏡的大廳裡,人們脫離了殘酷的外界,夢幻世界般的圖景被反覆強化。在那些鏡子中,除了被不斷複製的自己的臉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外界沒有什麼因素能干擾這許多不變的臉的一致性,因為那全都是我自己的臉。(p.379)
心理防禦 有些成員會保護群體,使那些質疑群體決策效率和道義的信息不會對群體構成干擾。在豬灣襲擊之前,肯尼迪把施萊辛格叫到一旁,告訴他說:“不要把話題扯遠了。”國務卿臘斯克(DeanRusk)作為外交和情報專家所應提出的反對襲擊的警告也就此打住。就這樣他們完全服從於總統的“心理防禦”作用,使他沒受到不同意見的侵擾,但卻無法保護其身體不受到危害。
群體思維的各種症狀表現會阻止群體成員對相反信息以及問題的各種可能性的探尋以及討論(見圖8-11)。當領導主張某種觀點而整個群體又排斥異議時,群體思維可能就會產生錯誤的決策(McCauley,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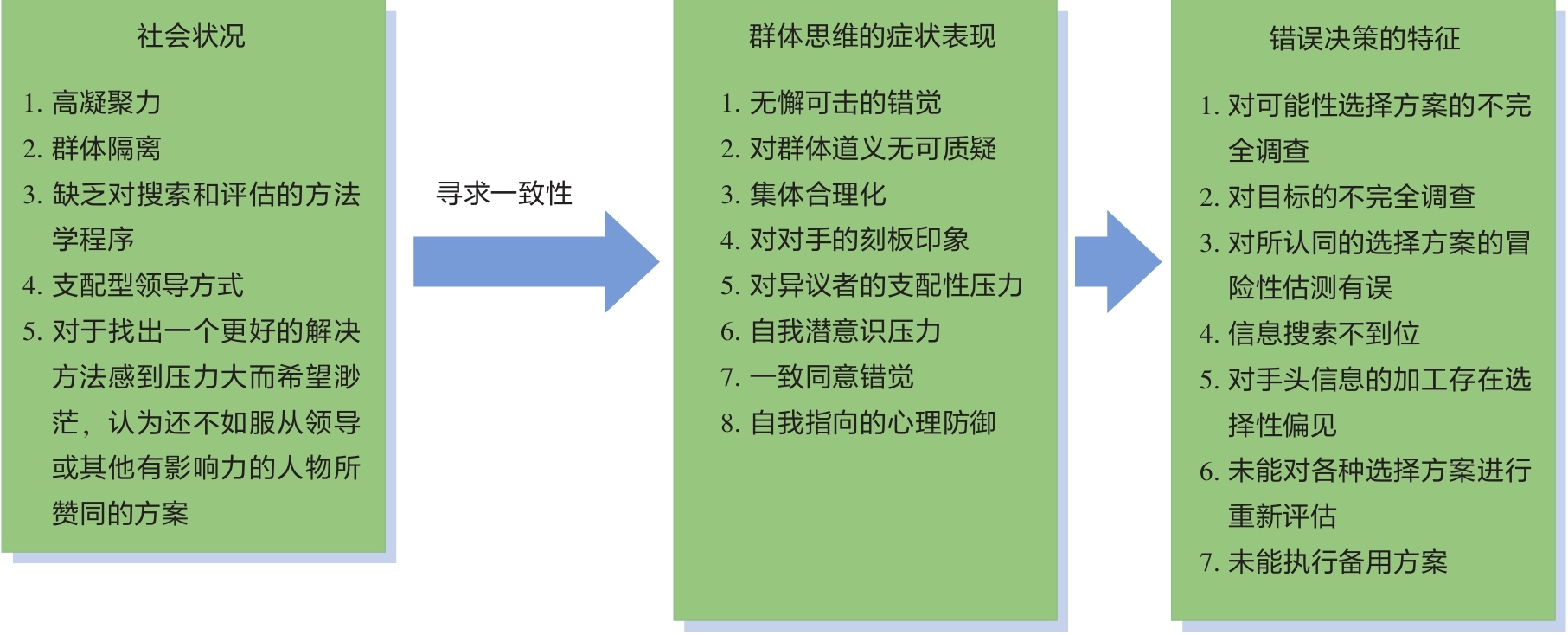
圖8-11 對群體思維的理論分析
資料來源:Janis & Mann,1977,p.132.
英國心理學家紐厄爾和拉格納多(Newell & Lagnado,2003)認為群體思維還可能解釋伊拉克戰爭。他們指出,無論是薩達姆還是布什,身邊都有一大群和他們具有同樣目的的進言者,這就迫使反對者閉嘴,而令其只過濾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對入侵者進行反抗,而美國的假定則是成功地入侵會帶來短暫而和平的領土佔領和今後長期的民主統治。
對群體思維的批評
雖然賈尼斯的想法和觀察結果引起了廣泛關注,但一些研究者仍對此持懷疑態度(Fuller & Aldag,1998;t'Hart,1998)。賈尼斯的證據都是回溯性的,因此他可以挑出支持自己觀點的例證。後來的研究也表明:
支配型的領導方式確實和糟糕的決策相關,有時下屬會認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Granstrom & Stiwne,1998;McCauley,1998)。
群體確實傾向於支持極富挑戰性的信息 (SchulzHardt & others,2000)。
當成員們希望從群體中獲得接納、讚許和社會認同時,他們會壓抑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想法 (Hogg & Hains,1998;Turner & Pratkanis,1997)。
但是友情並不會滋生群體思維(Esser,1998;Mullen & others,1994)。安全而高度團結的群體(例如,一對夫妻)會為成員提供自由的氛圍來提出異議。凝聚力比較高的群體規範既能夠導致意見統一(從而造成群體思維),也可以進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現群體思維(Postmes & others,2001)。而一個組織嚴密的部門學術夥伴彼此分享手稿時,他們想要 的就是批評:“盡你所能地來給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圍中,團結會提高團隊工作的效率。
而且,當泰特洛克及其同事(Tetlock & others,1992)在各個歷史時期大範圍地蒐集樣本時,清楚地發現即使是好的群體交流過程有時也會做出錯誤的決策。1980年,當卡特總統及其顧問們密謀營救在伊朗的美國人質時,他們一度歡迎大家提出各種觀點,而且很現實地考慮到了行動的危險性。要不是一架直升飛機出了問題,營救行動可能已經成功了。(卡特事後回憶說,如果他當時能多派一架直升機,自己可能已經連任總統了。)在此又得提起羅傑斯先生,有時候好的群體也會做出錯誤的事情。
縱覽對群體思維的各種批評,保盧斯(Paulus,1998)用費斯汀格(Festinger,1987)的話來提醒我們,只有那些無法用實驗證實的理論才是不會改變的。“如果一個理論完全可用實驗來驗證,它就不可能永遠保持不變。它必須做出改變。所有的理論都是不完美的。”費斯汀格說,因此我們不應該問一個理論是對還是錯,而應問“它能對我們的經驗領域做出多少解釋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必須被修改。”賈尼斯直到1990年去世之前,都在對自己的理論進行測試和修改,他也一定非常歡迎其他人繼續對它進行修正。在科學領域,這就是我們探索真理的方法:根據事實來設計實驗,修改它們,然後再進行更多的實驗。
聚焦 群體思維與挑戰者號的災難
1986年1月,當美國宇航局(NASA)決定發射挑戰者號 航天飛機時,群體思維很顯然導致了悲劇的發生(Esser & Lindoerfer,1989)。考慮到零下溫度會對設備造成損害,在Morton Thiokol製造航天飛機火箭加速器的工程師們,以及在Rockwell International製造繞行太空船的工程師們都反對這次發射。Thiokol的工程師們擔心低溫會使火箭四個部分之間的橡膠封口變脆,以至於不能封住過熱的氣體。公司的高層專家在回憶中都提到,在這次註定失敗的任務之前的幾個月,他們已經警告說無論封口能否封住,飛船就像一個“跳球”,如果飛行失敗了,“結果將是最高階層帶來的災難”(Magnuson,1986)。
在發射前一天晚上的電話討論中,工程師們向拿不定主意的主管們以及宇航局的官員們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宇航局的官員們原本就很希望將這次已經被耽擱的發射繼續進行下去。一個Thiokol的官員後來證實說:“我們都陷入思考的過程,試圖找出一些跡象來證明它們(加速器)確實不能工作。但我們並不能完全證明它們不能工作。”結果就形成了無懈可擊的錯覺。
從眾壓力 也在其間起了作用。宇航局的一個官員解釋說:“我的天,Thiokol,你希望我什麼時候發射,明年4月?”Thiokol的首席執行官宣佈說:“我們需要做出一個管理決策,”然後他要求自己的工程師兼副總經理“摘下工程師帽子,換上管理者帽子”。
為營造一致同意錯覺 ,這位執行官只讓管理官員投票,而把工程師排除在外。做出繼續執行任務的決策後,一名工程師曾提出讓一位宇航局的官員再考慮一下:“如果這次發射出了任何意外,”他預言道,“我肯定不願意做那個不得不當眾解釋為什麼要進行這次發射的人。”
最後,出於心理防禦 ,做出最後決定的宇航局的首席執行官根本不在乎工程師們的觀點,也不理會Rockwell官員們所持的保留意見。他在排除了異議的情況下,自信地將挑戰者 號送上了它的悲劇之旅。
在2003年,宇航局由於專家顧問小組警告其航天飛船因老化存在安全隱患而撤銷了5個顧問成員資格之後,災難再次降臨(Broad & Hulse,2002)。宇航局說這只是為了吸收新鮮血液,但是幾名顧問成員認為是當局企圖壓制他們提出的批評,而且宇航局對他們的擔憂漠然置之,當2月1日哥倫比亞號在返回地球途中發生斷裂事故,這一切顯得更為可信了。哥倫比亞號事故調查小組(2003)總結道:“技術的原因與組織的原因在哥倫比亞號事故中不分伯仲,泡沫材料撞擊上升中的航天飛機與事故關係密切,而宇航局的組織文化也是一樣難逃罪責,”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組織內的阻礙者“屏蔽了關鍵安全信息的有效溝通,抑制了專家意見中的不同聲音。”
預防群體思維
不良的群體動力能幫助解釋很多錯誤的決策,正如有時候廚子過多往往會搞砸一鍋湯。不過,在開明的領導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團隊精神的確有助於決策。有時三個臭皮匠真的能頂一個諸葛亮。
為了找出產生良好決策的條件,賈尼斯分析了兩個看起來比較冒險的成功事例:杜魯門政府為了恢復二戰後歐洲經濟而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以及1962年肯尼迪政府對於前蘇聯意欲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一事的處理。賈尼斯(1982)提出預防群體思維的建議就融合了這兩大事例中很多有效的群體過程:
公平——不能偏向任何立場。
鼓勵批評性評價;設置一個“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個真正的反對者就更好了,這會刺激原發的想法並使群體對反對意見持開放態度 (Charlan Nemeth,2001a,2001b)。
有時可以將群體劃分成幾個小組,然後再重組在一起表達不同的意見。
歡迎局外的專家和夥伴提出批評。
在實施之前,召開被稱為“第二次機會”的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
這些被用來改善群體動力的部分實用準則現在被教授給航空人員。之所以要發展宇航員資源管理的訓練項目,是因為人們意識到2/3以上的飛機事故都是由於航空人員的失誤造成的。在駕駛艙中安排兩個或三個人應該能增加發現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機會——如果大家共享交流信息的話。但是有時候,群體思維的壓力會導致從眾或自我潛意識壓力。
對航空人員的行為表現進行研究的社會心理學家赫爾姆裡希(Helmrich,1997)指出,1982年冬季的一天,當佛羅里達航空公司的一架飛機從華盛頓國際機場起飛時,其不良的群體動力是非常明顯的。傳感器上的冰塊使得速度顯示器的讀數過高,以致機長在飛機上升時無法提供足夠的動力:
副機長 :啊,那裡有問題。
機長 :沒有問題,它就是80(指速度)。
副機長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呃,不過也許它沒問題。
機長 :120。
副機長 :我也搞不清了。
速度確實有問題,副機長的沉默導致了飛機失速並且撞上了波托馬克河上的一座橋,整架飛機除了五個人以外全部遇難。
但是在1989年,當聯合航空公司DC-10航班的三名航員駕駛飛機從丹佛飛往芝加哥時,這個面臨災難的群體的反應堪稱典範。這些受過航員資源管理訓練的航員們所面對的是裂開的中央引擎。而中央引擎連接著駕駛飛機所需的方向舵和副翼。飛機在蘇克斯機場跑道墜毀前的短短34分鐘內,航員們必須制定出策略讓飛機不致失控,同時還要估算損失,選擇著陸地點,並且讓航員和乘客為墜機做好準備。駕駛艙中分秒必爭,大家熱烈地交流意見——每分鐘31次交流(最快時一秒鐘一次)。在這段時間裡,航員們將一名乘客招募來做了第四名飛行員,他們各司其職,並對公開的事件和決定互通有無。初級航員可以自由地對策略的可能性選擇提出建議,機長會給出恰當的號令。社會性對話交流的激烈展開為他們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使得航員們對這一極度壓力做出了很好地應對,並且救出了飛機上296人中的185人。
群體問題解決
在某些條件下,三個臭皮匠頂 一個諸葛亮,實驗也證實了群體思維的正確性。勞克林和艾達摩浦勒斯(Laughlin & Adamopoulos,1980,1996;Laughlin & others,2003)用各種智力任務證實了這點。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個類比問題:
主張 (assertion)對應於被反駁 (disproved)正如行動 (action)對應於
a. 被阻礙 (hindered)
b. 被反對 (opposed)
c. 不合法 (illegal)
d. 輕率 (precipitate)
e. 挫敗 (thwarted)
很多大學生在獨立作答時都選擇了錯誤的答案,但在討論之後都選擇了正確的答案(選擇挫敗)。而且,勞克林發現如果一組中的6個人最初只有2個人做對,那2/3的時侯他們都能說服其他人。但如果最初只有一個人正確,那這“作為少數派的一個人”幾乎有3/4的時候都不能說服其他人。
“兩個預報員在一起會比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單獨工作時作出更準確的預報,”最大的私人預報服務機構的董事長邁爾斯(Myers,1997)曾這樣說過。沃尼克、桑德斯以及錫恩茨(Warnick,Sanders,& Hinsz,1980,1990)研究了在犯罪錄影帶以及工作面試中,目擊證人報告的準確性,結果證實了多個頭腦會好過一個頭腦。群體目擊者比起單獨的個體給出了更為準確的描述。幾個頭腦的相互批評碰撞可以使群體能避免某些形式的認知偏見並且產生出一些奇思妙想(McGlynn & others,1995;Wright & others,1990)。我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像我們在一起時那樣明智。
利用電腦交流的頭腦風暴法使得創造性的想法能自由地流露出來(Gallupe & others,1994)。儘管公眾認為面對面的頭腦風暴法能比人們單獨工作時產生更多的創意,但研究者們卻並不這樣認為(Paulus & others,1995,1997,1998,2000;Stroebe & Diehl,1994)。在群體中產生想法時,人們會更有成就感 (部分是由於人們誇大自己對集體的貢獻)。但是研究者卻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單獨工作的人們通常會比在團隊中產生更多 更好的想法(頭腦風暴法只在被高度激勵和多樣化的群體中才十分有效,並且這些群體要事先準備好可能的觀點)。龐大的頭腦風暴群體通常都是低效的,它們會導致某些個體肆意地嘲弄他人的努力成果,或是對提出古怪的念頭感到忐忑不安。正如沃森和克里克(Watson & Crick)發現DNA那樣,鼓勵二人對話會有效地增進創造性思維。心理學家卡尼曼和特韋爾斯基(Kahneman & Tversky)合作研究了直覺及其對經濟決策的影響(見第3章和“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
諾貝爾獎背後的故事: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
1969年的春天,我和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的同事特韋爾斯基(Amos Tversky)在午餐時碰面,並分享了我們關於不斷出現的錯誤判斷的想法。我們對人類直覺的研究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我對我們以前的合作很滿意,不過這次更神奇。特韋爾斯基非常聰明,也十分有趣。我們能在長達幾個小時的工作中享受彼此給自己帶來的樂趣。他工作時總是帶著自信和優雅的氣質,令人高興的是,我現在的想法也與這些特徵聯繫在了一起。當我們合作寫出第一篇論文的時候,我非常清楚,它比我先前自己寫的那一份要強很多。
我們所有的想法都是共有的。我們在一起完成了幾乎是合作計劃的全部工作,包括設計問卷和撰寫論文。我們的原則是把每一個分歧都討論到解決,而且直到彼此都滿意為止。
我們合作的最大樂趣——可能這就是合作的成功所在——來自於我們能夠詳盡地描述出彼此剛剛產生的想法:如果我表達了一個未成型的看法,我知道,特韋爾斯基一定會明白,甚至可能比我自己都要更明白些。而且如果這個看法有什麼優點,他都非常清楚。
我和特韋爾斯基共同分享擁有一個能下金蛋的鵝的喜悅之情——聯合起來的智慧勝過我們各自的頭腦。我們是一個團隊,而且這種關係已經持續了十年以上。我們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就是那時我們緊密合作的產物。
不過,布朗和保盧斯(Brown & Paulus,2002)提出了三種促進群體大腦風暴的方法:
將群體和個體的頭腦風暴相結合 。他們的數據顯示,先進行群體頭腦風暴,再進行個體頭腦風暴,比反過來進行和單獨使用效果要好。有了在群體頭腦風暴中產生的新想法,個人可以繼續思考,而不必受群體中每次只能有一個人發言所束縛。
讓小組成員通過書寫互動 。讓小組成員用書寫和閱讀來代替說和聽,這樣也可以解決每次只能聽一個人意見的矛盾。布朗和保盧斯將這種傳紙條和補充想法的過程稱作“頭腦寫作”,這可以讓所有人都能積極參與。
結合電子頭腦風暴 。對於較大的群體而言,一個能更有效防止傳統頭腦風暴的口頭交流發生交通阻塞的方法是:讓個體利用聯網的計算機來交流看法。
小結
對幾大國際事件失敗決策的分析表明,群體對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可能會壓倒對相反觀點的真實評價。特別是當群體成員強烈地渴望統一性,或是他們與相反的觀點相隔絕,又或是領導暗示了他或她本人的意願時,這表現得尤其突出。
這種以群體思維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和睦過分的關注,其症狀表現有(1)無懈可擊的錯覺(2)合理化(3)對群體道義無可質疑(4)對對方立場的刻板印象(5)從眾的壓力(6)對異議的自我潛意識壓力(7)一致同意錯覺(8)保護群體不受不愉快信息干擾的“心理防禦”。對賈尼斯的群體思維模型的批評指出,該模型的某些方面(例如支配型領導方式)與錯誤決策的聯繫要大於其他方面(例如凝聚力)。
但是,無論是在實驗中還是歷史事實中,群體有時候也會做出英明的決策。這些案例說明了群體思維的理論仍需加以修正。通過從各方面搜索信息以及改善對各種可能性選擇方案的評價,群體能夠從其成員整合後的洞察力中獲益。
少數派影響:個體是怎樣影響群體的
群體會影響個體,但個體會在什麼情況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呢?什麼因素會影響領導(個體的能力)的有效性呢?
社會影響這一編的每一章都提醒我們個體所具有的力量。我們看到: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們,但我們也幫助創造並選擇了這些背景。
從眾壓力有時會埋沒更好的判斷,但張揚的壓力能激勵我們展現自己的個性與自由。
說服的力量確實很強,但我們可以通過公開承諾和預估說服的感染力來抵制被說服。
這一章著重強調了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因此我們以個體如何影響他們所在的群體來作結論。
許多社會運動開始時,一小部分人有時會成為主導,接著甚至會演變為大多數。“所有的歷史,”愛默生寫道,“都是關於少數派力量的寫照,以及只由一個人組成的少數派的寫照。”想想哥白尼、伽利略、馬丁·路德·金和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美國民權運動也是由一名美國黑人婦女帕克斯(Rosa Parks)點燃的,她在阿拉巴馬蒙哥馬利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拒絕讓出自己的座位。科技的發展史也是由一小部分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所譜寫的。正如富爾頓(Robert Fulton)改良他的輪船——“富爾頓的愚行”——後所忍受世人的嘲笑:“在我的道路上從沒有任何鼓勵的評論、明朗的希望和溫馨的祝願”(Cantril & Bumstead,1960)。
是什麼使得少數派具有如此的說服力呢?施萊辛格為使肯尼迪等人考慮其對襲擊豬灣的疑慮應該做些什麼就好了呢?由莫斯科維斯(Serge Moscovici)在巴黎進行的實驗證實了少數派影響的幾大決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叛離。這裡要注意:“少數派影響”是指少部分人的意見 ,而不是種族上的少數民族。
一致性
比起搖擺不定的少數派,那些堅持自己立場的少數派更具有影響力。莫斯科維斯及其助手(1969,1985)發現,如果少數人一致認為藍色幻燈片是綠色的,那麼佔大多數的成員偶爾也會表示贊同。但如果這少部分人搖擺不定,認為其中1/3的藍色幻燈片是藍色的,而其他的是綠色的,那麼事實上佔大部分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會同意“綠色”。
實驗表明——經驗也證實——不從眾,特別是一直堅持不從眾,結果往往很痛苦(Levine,1989)。那可以用於解釋少數派緩慢效應(minority slowness effect)——相對於多數派而言,少數派往往更慢地表達他們的觀點(Bassili,2003)。如果你決定做愛默生所說的一個人的少數派,你必須準備好接受嘲弄——特別是你所提出的觀點與大多數人息息相關,並且群體正試圖就某一問題達成一致(Kameda & Sugimori,1993;Kruglanski & Webster,1991;Trost & others,1992)。人們或許會認為你提出異議是由於心理怪癖(Papastamou & Mugny,1990)。當內梅斯(Charlan Nemeth,1979)將兩個人安排在一個模擬陪審團中,並讓他們反對大多數人所提的意見時,這倆人確實變得不受歡迎。儘管如此,多數派公認這兩人的堅持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促使他們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少數派或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刺激創造性的思維(Martin,1996;Mucchi-Faina & others,1991;Peterson & Nemeth,1996)。從自己群體內所產生的異議中,人們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並且常常會做出更好的決策。內梅斯認為個體並不需要通過贏得朋友來影響他人,他引用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說:“我們不喜歡任何類型的爭論;它們總是無禮的,但又總是令人信服的。”
一些成功的公司已經認識到創新有時候是由少數派的觀點引起,然後可以帶來新思想,同時也激勵同事們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問題。以崇尚“尊重個體的原創力”而聞名的3M公司就鼓勵員工進行大膽的想像。可粘貼的便箋紙就是西爾弗(Spencer Silver)嘗試創制強力膠失敗的產物。弗賴伊(Art Fry)在沒能用小紙片給自己的讚美詩集作記號的時候,就想到“需要一種邊緣有Spence貼紙的書籤。”即使這樣,最終還是這些少數派的觀點最後贏得了好懷疑的市場部。
自信
一致性和堅持性是自信的表現。而且,內梅斯和瓦赫特勒(Nemeth & Wachtler,1974)報告說,少數派表達自信的任何行為——例如,坐在桌子的上座——都會使多數派產生自我懷疑。通過堅定有力的行為表現,少數派明顯的自我支持會促使多數派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當事關觀點而非事實的時候,尤是如此。馬斯及其同事(Maass & others,1996)在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學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在關注事實(“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是從哪個國家進口的?”)的時候,少數派的說服力沒有其關注態度(“意大利大部分的原油應該從哪個國家進口?”)的時候強有力。
從多數派中叛離
堅持己見的少數派會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錯覺。當少數派對多數派的判斷力提出質疑後,多數派的成員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達他們自己的疑慮,甚至會倒向少數派的立場。萊文(Levine,1989)在對匹茲堡大學的學生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如果少數派中的某個人是從多數派中投奔過來的,那麼他會比那些自始至終居於少數派的人更有說服力。在她的模擬陪審團實驗中,內梅斯發現一旦開始出現叛離行為,其他人常常也會緊緊追隨,產生滾雪球效應。
這些加強少數派影響的因素是否只對少數派起作用呢?沃爾夫(Sharon Wolf)和拉坦(Latané,1985;Wolf,1987)以及克拉克(Russell Clark,1995)認為不是這樣。他們指出同樣的社會力量對多數派和少數派都同樣起作用。信息和規範影響同時可以增強群體極化和少數派影響。如果一致性、自信和從另一方叛離能夠使少數派得到加強的話,那麼這些變量也能加強多數派。任何立場的社會影響力取決於它的力量、即時性以及支持者的數量。少數派之所以沒有多數派的影響力大,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的規模較小。
馬斯和克拉克(1984,1986)同意莫斯科維斯的觀點,但是,他們認為少數派更可能使人們發生轉變而接受 他們的觀點。萊文和莫蘭(Levine & Moreland,1985)通過對群體隨時間演化過程的分析,總結出一個群體的新成員與老成員表現少數派影響的方式有所不同。新成員通過引發他人對他們的關注,以及在老成員中引起群體知覺來施加影響。而老成員通常能夠較為自由地表達異議或是實施領導。
在強調個體對群體影響的同時,還存在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直到最近,這種少數派能夠動搖多數派的觀點其本身就是社會心理學領域少數人的看法。儘管如此,通過不懈而有力地提出這種觀點,莫斯科維斯、內梅斯、馬斯、克拉克和其他人已經說服了群體影響研究中的多數人:少數派影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這些少數派影響的研究者們對這一領域產生興趣的原因也許並不會讓我們吃驚。馬斯(1998)成長在二戰後的德國,在聽完祖母對法西斯的描述後,她對少數派如何影響社會變革產生了興趣。內梅斯(1999)對此產生興趣是源於當她作為訪問教授在歐洲與“泰菲爾(Henri Tajfel)和莫斯科維斯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三個都是‘局外人’——我是一名在歐洲的美籍羅馬天主教女性,她們兩個都是在二戰中活下來的東歐猶太人。對價值觀的敏感性以及為了少數派意見的抗爭研究成了我們的主要工作。”
領導是否屬於少數派影響
1910年,挪威人和英國人開始了前往南極的宏偉之旅。由阿蒙森(Roald Amundsen)有效領導的挪威人成功地到達了南極。而英國人由於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不當領導而沒能成功,斯科特和三名隊員遇難。阿蒙森形容領導 (leadership)就是特定個體動員和引導群體的過程。金斯利(Kinsley,2003)觀察到,布什在職期間的行為就顯示了“個人的力量”,“在布什指稱薩達姆是個嚴重的威脅並需要被驅逐之前,人們並沒有這種想法。或許你可以用很多詞彙描述這種情況,但‘領導’必然是其中之一。如果真正的領導是指能夠帶領人們去他們不想去的地方,那麼布什的確證實了自己是個真正的領導者。”
有些領導是正式任命或選舉產生的,而有些是在群體交流中非正式地產生的。怎樣能產生好的領導往往取決於情境——領導工程隊的最佳人選可能並不是銷售人員的好領導。有些人能出色地擔任任務型領導 (task leadership)——組織工作、設置規範、聚焦於目標的實現。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擔任社會型領導 (social leadership)——建立團隊、調解矛盾、表達支持。
任務型 領導通常是支配型的——如果領導能夠睿智地發出指令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Fiedler,1987)。由於是目標取向的,這樣的領導會將群體的注意力和努力都放在任務上。實驗表明,特定的、有挑戰性的目標再加上週期性的進程報告會促進高成就的實現(Locke & Latham,1990)。
社會型 領導通常具有民主風格——他們代表了權威,接納團隊成員的意見,並且像我們看到的那樣,避免出現群體思維。很多實驗表明這樣的領導有利於鼓舞士氣。群體成員在參與決策時通常表現出更高的滿意度(Spector,1986;Vanderslice & others,1987)。如果對員工們的任務加以控制,他們也會更受鼓舞去獲取成就(Burger,1987)。
如果能有機會在決策過程中發言,人們會對決策結果表現更積極(van den Bos & Spruijt,2002)。因此看重群體感受並且為成就感到驕傲的人們會在民主的領導下蓬勃發展。在許多商業運營向參與式管理——一種在瑞典和日本普遍的管理模式——邁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民主型領導方式(Naylor,1990;Sundstrom & others,1990)。另外,女性比男性更慣於採用民主型的領導風格(Eagly & Johnson,1990)。
一度流行的“偉人”領導理論——所有的優秀領導都具有某些特質——被人們拋棄了。現在我們知道,有效的領導風格會隨情境而改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們可能會討厭任務型領導,但不知道的人們也許會對此表示歡迎。但是最近,社會心理學家們又開始關注,是否可能存在某些品質是很多情境下的優秀領導都具有的(Hogan & others,1994)。英國社會心理學家史密斯和泰博(Smith & Tayeb,1989)報告說,在印度、中國臺灣和伊朗進行的研究,都發現在礦區、銀行和政府辦公室的優秀主管在任務型和 社會型領導上的得分都很高。他們既主動關注工作的進展,同時 對下屬的需要也很敏感。
研究還表明,許多實驗室群體、工作團隊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領導都表現出了能令少數派觀點具有說服力的行為。這樣的領導靠不懈 堅持自己的目標來贏得信任。他們常常流露出自信 的領導氣質來贏得下屬的忠誠(Bennis,1984;House & Singh,1987)。具有領導氣質的領導們通常對所希望的事件狀態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洞察力 ,能用簡單明晰的語言與其他人就此進行交流 ,並有足夠的樂觀精神和團隊信念來使 他人信服自己。由此,人格測驗顯示有效的領導大多是外向的、充滿活力的、正直的、易於相處的、情緒穩定的和自信的個體,對此我們也就不足為奇了(Hogan & others,1994)。
事實上,群體也會影響他們的領導。有時候,那些站在群眾最前方的人已經察覺到了事態的走向。政治候選人知道怎樣從民意測驗中得知民眾的態度。能夠代表群體觀點的人更有可能被選為領導;而一個過於偏離群體規範的領導往往會被抵制(Hogg & others,1998)。明智的領導通常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並且謹慎地施加自己的影響。儘管如此,有效的個體領導有時會通過動員和引導群體力量來施加少數派影響。西蒙頓(Simonton,1994)指出,在個別的情況下,適當的特質與適當的情境相匹配,可以產生出改寫歷史的偉大人物。丘吉爾、傑菲遜、馬克思、拿破崙、林肯或馬丁·路德·金等偉大人物的誕生,都需要有恰當的人恰當的地點和恰當的時間。當才智、技術、決心、自信和社會領導氣質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並遇上難得的機會,那結果就會是冠軍、諾貝爾獎或是社會革命。去問問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就知道了。
小結
如果少數派的觀點永遠都不會成功,那麼歷史就會是靜止的,一成不變。在實驗中,當少數派具有一致性並且自信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時,當多數派中開始有人叛離時,少數派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即使這些因素並不能使多數派採納少數派的觀點,它們也會令多數派產生自我懷疑並且促使多數派考慮其他的可能性選擇,並通常可以誕生更好的、更具創造性的決策。
任務型與社會型領導,正式和非正式群體的領導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影響力。那些朝著既定目標堅持不懈並且表現出自信領導氣質的人們通常能贏得信任並鼓舞其他人追隨自己。
個人後記:難道群體不利於我們嗎
我必須承認,對這一章有選擇地閱讀會使讀者產生這樣一種印象,那就是認為總體而言群體是不好的。在群體中,我們容易被煽動,更有壓力,也更緊張,在複雜任務中更易出錯。沉浸在給我們提供匿名權的群體中,我們更容易虛擲光陰或是由於去個性化而釋放出最糟糕的衝動。政治暴行、私刑、團伙破壞和恐怖分子都是群體現象。群體討論常常會使我們的觀點極化,增強種族主義和敵對主義。它還可能壓制異議,產生出導致災難性決策的一致性的群體思維。難怪我們會頌揚那些為了真理和公正而站出來的個體——由一個人組成的少數派,也就是那些獨自反對群體的人。群體看上去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但這只是真相的一半。另一半是,作為社會動物,我們是群居生物。就像我們的遠祖一樣,我們為了生活資料、支持和安全感而相互依靠。而且,當我們的個體傾向十分積極時,群體交流能使我們變得更好。在群體中,奔跑者會跑得更快,觀眾會笑得更大聲,捐贈者會更加慷慨。在自助的群體中,人們可以增強自己戒酒、減肥和努力學習的決心。在志趣相投的群體中,人們會將自己的精神意識擴大化。“有時候精神層面的真誠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有利於心靈的健康,”15世紀的牧師坎佩斯(Thomasa Kempis)觀察後這樣說道。當人們的信念“相遇、交談並共同交流”時,尤其如此。
從群體正在擴大或放任自流的傾向出發,群體可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壞的。所以我們最好能明智而有目的地選擇群體影響。
你的觀點是什麼
想像你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群體中的一員——有積極影響的群體。這個群體是否獲益於有效的領導?它是否證實了某些在本章中討論過的原理,如社會助長作用、社會懈怠、去個性化、群體極化、群體思維或是少數派影響?
聯繫社會
本章我們討論了群體極化以及群體是否會被強化的觀點。這一現象在第16章我們對陪審員及其決策過程的探討中也會有所涉及。你還能想到其他發生群體極化效應的場合嗎?
第三編
社會關係
社會心理學是關於我們是如何對彼此思考、彼此影響和相互聯繫的科學的研究。在已經探討過我們是如何彼此理解和影響之後,我們現在來考慮我們彼此之間是如何聯繫的。我們對人們的感覺和行動有時是負性的,有時是正性的。第9章“偏見:不喜歡他人”和第10章“攻擊行為:傷害他人”分析了人際關係中醜陋的方面:為什麼我們不喜歡、甚至是鄙視彼此?我們在何時、為什麼彼此傷害?然後在第11章“吸引與親密:喜歡他人和愛他人”和第12章“利他:幫助他人”中,我們探討了好的方面:為什麼我們喜歡或者愛特定的人?為什麼我們給朋友或者陌生人提供幫助?最後,在第13章“衝突與和解”中,我們思考了社會衝突是如何發展的,以及如何才能公正和平的解決這些衝突。
第9章 偏見:不喜歡他人 [1]
偏見的本質和作用是什麼
界定偏見
種族偏見
性別偏見
偏見有哪些社會根源
社會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與偏見
社會化
社會制度的支持
偏見有哪些動機根源
挫折與攻擊性:替罪羊理論
社會同一性理論:感覺比他人優越
避免偏見的動機
偏見有哪些認知根源
類別化:將人歸入不同群體
獨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歸因: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嗎
偏見的後果是什麼
自我永存的刻板印象
歧視的影響:自我實現的預言
刻板印象威脅
刻板印象會使個體判斷出現偏差嗎
個人後記:我們能夠減少偏見嗎
“偏見,一種沒有明顯依據的易變的觀點。”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魔鬼詞典》,1911
偏 見以多種形式顯現——喜歡自己的群體,不喜歡其他一些群體,如:喜歡“東北部的自由主義者”(northeastern liberals)或“南部的山地人”(southern hillbillies),討厭阿拉伯“恐怖分子”或美國“異教徒”(infidels),討厭那些矮個子、肥胖,或者不好看的人。
“9.11”事件及其後果說明了仇恨和偏見的威力:
“我們的恐怖主義針對的是美國。我們的恐怖主義是神聖的恐怖主義。”——引自本·拉登在“9.11”事件之後的一段錄像講話。
“假如我看見某人進入(一個機場),他頭上戴著尿布似的東西,而且用風扇皮帶(帶動汽車等散熱器風扇的皮帶)將那玩意纏在腦袋上,那麼這傢伙就應該被逮起來。”——引自美國國會議員約翰·庫克西(John Cooksey)在“9.11”事件之後的一次電臺訪談節目。
“9.11”過後不久,對那些被認為具有阿拉伯血統的人的敵意情緒高漲起來。在紐約城郊,一位男士試圖(開車)撞倒一位巴基斯坦婦女,嘴裡還喊叫著他是“為了我的國家”(Brown,2001)。在得克薩斯州的丹頓市,一家清真寺受到燃燒彈的攻擊(Thomson,2001)。在波士頓大學,一位中東學生被人刺傷,在科羅拉多大學,學生們在圖書館用油漆噴寫“阿拉伯人滾回老家去。”這些事件並非孤立的。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整理的清單列出“9.11”事件之後的一週之內,美國大學校園裡發生的250多起針對阿拉伯裔美國學生的暴力襲擊事件(cnn.com,2001)。對中東移民的負面看法根深蒂固。“9.11”事件6個月之後美國的一項調查表明,人們對巴基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評價與對毒品販子的評價相當,非常負面(Fiske,2002)。
其他群體也同樣面臨著由來已久的偏見。在尋求愛情或工作時,肥胖者——尤其是超重的白人婦女——前途黯淡。在若干相關的研究當中,肥胖者結婚的更少,只能獲得初級的或不大好的工作,收入也更低。在實驗研究中(讓其中的一些人扮成肥胖者),他們被知覺為缺乏魅力、不太聰明、不太快樂、缺乏自我修養,不夠成功(Gortmaker & others,1993;Hebl & Heatherton,1998;Pingitore & others,1994)。人們甚至會貶低那些僅僅是站在或者坐在肥胖者周圍的人(Hebl & Mannix,2003)。事實上,體重歧視明顯超過了種族或性別歧視,它表現在職業的每一個階段中——僱用、安置、晉升、薪酬、獎懲和解僱(Roehling,2000)。
偏見的本質和作用是什麼
“偏見”與“刻板印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有何區別?刻板印象必然錯誤或懷有惡意嗎?偏見在今天以怎樣的形式呈現?
界定偏見
偏見、刻板印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這些術語往往相互重疊。讓我們來澄清這些概念。上述的各種情況,正好都涉及到了對某些群體的負面評價。這正是偏見 (prejudice)的本質:對一個群體及其個體成員的負性的預先判斷。(有些偏見定義也包含了積極的 預先判斷,但在應用“偏見”一詞時幾乎都指負面 傾向——或如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其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 )中所界定的那樣,“基於錯誤和頑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惡感”。[1954,p.91])偏見讓我們基於對某人所屬群體的認識而不喜歡這個人。
偏見是一種態度。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所見的,態度是感情、行為傾向和信念的某種獨特結合物。這一結合物是態度的ABC理論:情感(感情)[affect(feelings)],行為傾向(behavior tendency),認知(信念)[cognition(beliefs)]。一個存有偏見的人,可能不喜歡 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以歧視性的方式行為 ,並相信 那些人無知並且危險。與許多態度一樣,偏見非常複雜,而且可能包含某種傲慢的情感成分,這種情感起到了使對方總是處境不利的作用。
負面評價是偏見的標誌,它可能根源於情緒性的聯想,根源於行為辯解的需要,或者源自被稱為刻板印象 (stereotypes)的負性信念。刻板印象就是概括。為了簡化世界,我們概括出:英國人保守;美國人開朗;教授則心不在焉。下面列舉了近期研究中所揭示出的廣泛存在的刻板印象:
在20世紀80年代,與那些以“小姐”(Miss)或“夫人”(Mrs.)自稱的女子相比,採用“女士”(Ms.)作為頭銜的女子顯得更為自信,志向更為遠大(Dion,1987;Dion & Cota,1991;Dion & Schuller,1991)。現在“女士”一詞的使用更加普遍,因此刻板印象也變化了。那些保留自己姓氏的已婚女子被認為更加自信,志向更為遠大(Crawford & others,1998;Etaugh & others,1999)。
公眾輿論調查顯示,歐洲人對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具有明確的觀念。他們認為德國人相對勤勞,法國人喜歡安逸享樂(pleasure-loving),英國人淡漠並且不易激動,意大利人多情,荷蘭人可靠。[來自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威廉·庫門和米基爾·巴爾(Koomen & Bähler,1996),人們覺得這些發現是可靠的。]
歐洲人還認為歐洲南部的人比歐洲北部的人更易動感情,效率比較低(Linssen & Hagendoorn,1994)。甚至很多國家都存在“南方人更善於表達”這樣的刻板印象。詹姆斯·潘尼貝克及其同事(Pennebaker & others,1996)報告說,20個北半球國家(不包括南部的6個國家)的人們都認為同一國家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善於表達。
這樣的概括或多或少是真實的(而且並不總是負性的)。北半球靠南部的國家暴力事件發生率的確更高。有報告說,這些國家中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確比北方人更善於表達。就不同性別、種族和階層背景學生的成績差異,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往往能真實地反映現實(Madon & others,1998)。“刻板印象”,正如賈西姆等人(Jussim,McCauley,& Lee,1995)指出的那樣,“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準確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稱其為“差異敏感性”或“多元世界中的文化覺知”。形成英國人比墨西哥人更關心準時的刻板印象,就是理解使摩擦最小化情況下,在每一種文化下該期望什麼以及該如何行動。
當刻板印象是過度概括 或明顯不對的時候就會出問題。假如說美國享受福利的人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這一概括就有些過度,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大學生對特定的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例如,更喜歡外語課而不是經濟學,或者說更喜歡壘球而非網球),它們包含了一定的事實,但卻被過分誇大了。被刻板化的群體中,個體間的差異要比想像的更大(Brodt & Ross,1998)。
偏見 是一種負面態度 ;歧視 (discrimination)是一種負面行為。歧視行為的根源往往在於偏見態度(Dovidio & others,1996)。但是,正如在第4章中所強調的那樣,態度和行為常常是鬆散地聯結在一起的。偏見性的態度並不一定滋生出敵意行為,同樣道理,並非所有的壓迫都來源於偏見。種族歧視 (racism)和性別歧視 (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視活動,即使在沒有偏見意圖的時候也如此。在一家清一色為白人的公司裡,假如從結果來看,面試招聘活動確實剔除了潛在的非白人僱員,那麼,即使僱主並無歧視之意,但這種活動也可以稱為種族歧視。
種族偏見
普天之下,每個種族都是少數民族。例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僅佔全世界人口的1/5,不到半個世紀之後,該比例將會變成1/8。感謝過去兩個世紀裡的遷徙和移民,世界各民族現在互相融合,有時彼此敵對,有時又友好相處。
對於一個分子生物學家而言,膚色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體特徵,它受種族之間微小的基因差異所控制。而且,自然界並不按整齊界定的類別來區分種族。是我們人類而非自然界,將伍茲(Tiger Woods)標定為“非裔美國人”(他的祖先是25%的非洲人),或“亞裔美國人”(他也是25%的泰國人和25%的中國人),或者甚至是土著美國人或荷蘭人(各有1/8的血統)的。
多數人看到其他人身上的偏見。在1997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中,美國白人估計他們的同伴中有44%的人偏見很深(在10點量表上得分為“5”,甚至更高)。有多少人給自己也打高分呢?只有14%(Whitman,1998)。
種族偏見正在消失嗎
一方面是感受到每一角落無所不在的頑固偏見,另一方面是認為自我沒有什麼偏見,到底哪種認識正確?種族偏見正在成為歷史嗎?
種族態度可以非常迅速地發生改變。1942年,大部分美國人贊同“應該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為黑人設置隔離區”(Hyman & Sheatsley,1956)。事到如今,這樣的問題會顯得稀奇古怪,因為如此明目張膽的偏見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1942年,不到1/3的白人(南部只有1/50)支持學校合併;到1980年,支持學校合併的佔到90%。自1942年以來的歲月是多麼的短暫,即使自實施奴隸制的日子開始算,經歷的也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瞬間,有鑑於此,這種變化確實是天翻地覆的。加拿大也是如此,近幾十年來人們對於種族多樣性及各種移民群體的接受程度都有所提高(Berry & Kalin,1995)。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非洲裔美國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雖然在40年代如同克拉克等人(Clark & Clark,1947)所指出的那樣,許多人都懷有反黑人的偏見。(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宣佈隔離學校違背憲法。法院當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當非洲裔美國兒童有機會在黑人玩偶和白人玩偶之間做出選擇時,多數人選擇的是白人玩偶。在20世紀50~70年代所做的研究中,黑人兒童喜歡黑人玩偶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加。同時,成年黑人開始認為在諸如智力、懶惰和可靠等特質方面,黑人與白人非常相似(Jackman & Senter,1981;Smedley & Bayton,1978)。
埃米塔·埃齊奧尼(Etzioni,1999)指出,不同種族的人們具有很多相同的態度和志向。每10名黑人和白人當中,有9人以上表示他們願意投黑人總統競選者的票。兩個群體中,10人有8人以上都贊同“要高中畢業,學生必須瞭解將美國人民聯繫在一起的共同歷史和思想”。兩個群體中大約有類似比例的人追求“公正對待所有人,毫無偏見或歧視。”兩組人當中都有約三分之二的人認為道德和倫理標準在淪喪。埃齊奧尼指出,多虧了這些共同的想法,才使得美國和西方大多數民主國家避免了種族部落制的傷害,導致科索沃和盧旺達分裂的正是種族部落制。[心理學家通常使用大寫的“黑”(Black)和“白”(White),以強調這些是社會意義上的種族標籤,並非是對有非洲和歐洲祖先的人所做的膚色標籤。 ]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結論,種族偏見已經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裡消失了呢?2002年一年當中,在有記錄的仇視犯罪案件裡,7314名犯罪者顯然仍持有偏見(FBI,1997)。如圖9-1所示,極少數白人也存有偏見,他們不願意投黑人總統候選人的票。這些人有助於解釋為何有半數美國黑人認為在近30天裡遭遇過歧視——10次有3次是在購物時遇到,2次是在外出就餐或工作時遇到(Gallup,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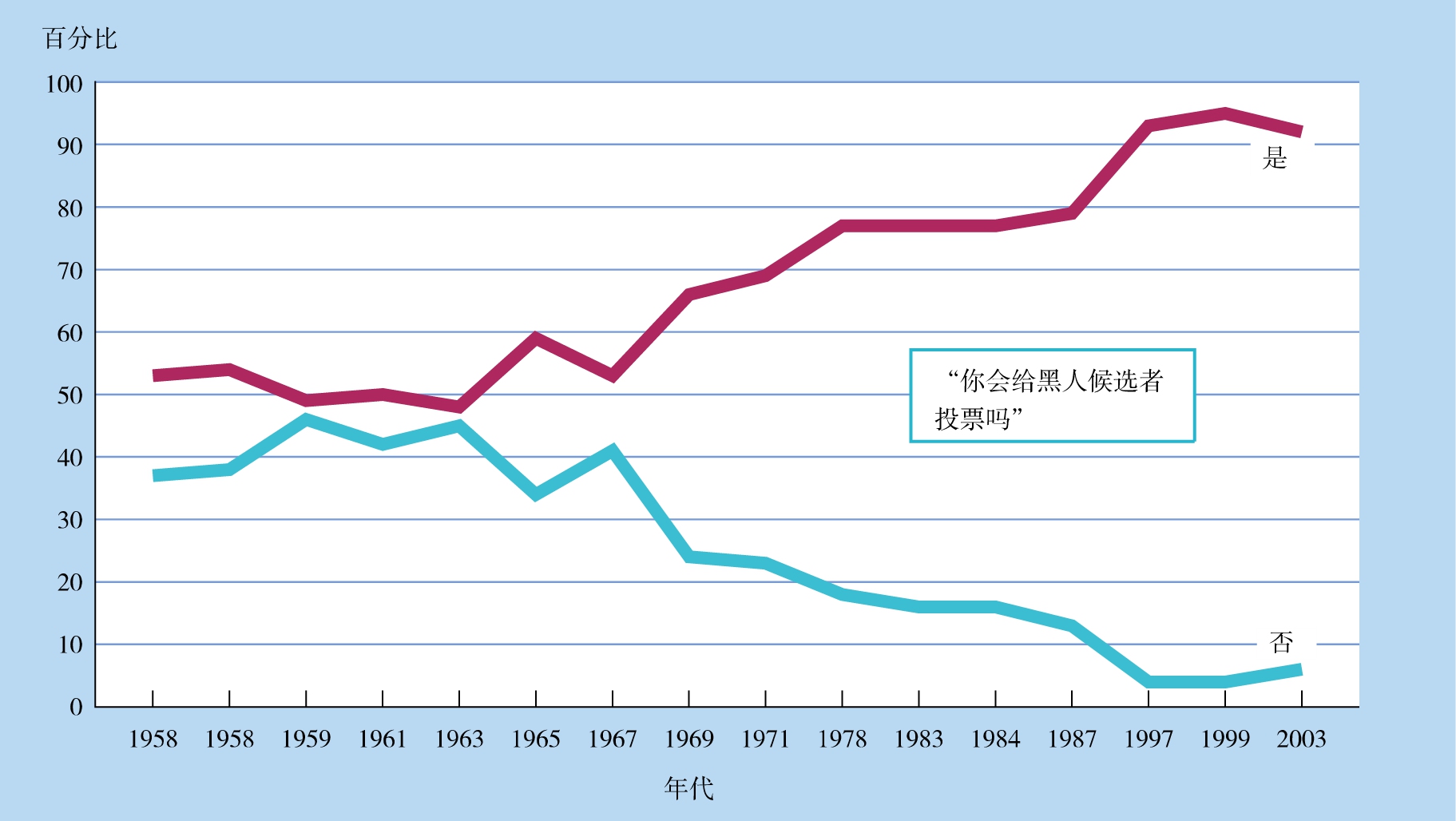
圖9-1 1958~2003年美國白人種族態度的變遷
資料來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gallup.com).
有關種族之間親密接觸的問題,仍然能夠檢測出偏見。同“與黑人一塊乘坐公交車可能會令我感到不適”這個問題相比,“與黑人在公共場合跳舞我可能會感到不適”能在白人身上檢測出更多的種族體驗。許多人歡迎不同的人做自己的同事或同學,但他們仍然在自己的種族之內與人交往、約會以及結婚。這有助於解釋在一項針對390所學院和大學的大學生所做的調查中為什麼會有53%的非裔美國大學生感到被排除在社會活動之外(Hurtado & others,1994)。這種多數—少數的關係不僅僅停留於種族問題上。在NBA的籃球隊中,少數派球員(在這裡是白人)有著被隔離於隊伍社交圈之外的類似感受(Schoenfeld,1995)。
最親密的社交領域中出現最大的偏見 ,這種現象似乎十分普遍。在印度,接受世襲等級制度的人,通常會允許某個來自底層階級的人到他們家裡來,但卻不會考慮與這種人結婚(Sharma,1981)。在美國一項全國性調查中,75%的人表示他們願意“在同性戀者開的商店購物”,但只有39%的人願意“找同性戀醫生看病”(Henry,1994)。
偏見的微妙形式
回憶第4章的例子,佩戴上假定的謊言探測器後,當白人大學生表明他們的種族態度,並且男士們表明他們對女性權利的同情時,他們承認持有偏見。其他實驗評估的則是人們對於白人和黑人的行為 。正如我們將在第13章看到的,白人對於任何需要幫助的人都是同樣樂於提供幫助的,除非需要幫助的人太不相干(比如說,有一位打錯電話的人,明顯帶有黑人口音,要求轉達一個消息)。同樣的,當要求人們採用電擊來“教授”某個任務時,白人給黑人的電擊並不比給白人的多——除非他們被激怒了,或對方無法報復,或者不知道是誰幹的(Crosby & others,1980;Rogers & Prentice-Dunn,1981)。[在美國的一些州,黑人摩托車手代表了州際高速路上少數的駕駛者和違章超速者,然而他們卻是最容易被州警察阻擋下來接受檢查的人(Lamberth,1998;Staples,1999a,1999b)。在針對新澤西收費公路的一項研究中,黑人佔駕駛者的13.5%,超速者的15%,被阻攔檢查者的35%。 ]
因此,偏見態度或歧視行為一旦能隱身於某些其他動機之後,便可能浮出水面。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及荷蘭,微妙的偏見(誇大種族差異、對少數民族移民不那麼尊重和有好感,以想像的非種族原由拒絕他們)正在替代公開的偏見(Pedersen & Walker,1997;Pettigrew,1998)。一些研究者把這種微妙的偏見稱為“現代種族歧視”(modern racism)或“文化種族歧視”(cultural racism)。現代偏見通常以微妙的形式表現在我們對那些熟悉、相似以及感覺舒適的事物的偏好上(Dovidio & others,1992;Esses & others,1993a)。
在紙筆問卷中,珍妮特·斯溫(Janet Swim)和她的合作者(1995,1997)發現與微妙(“現代”)的種族歧視並存的還有微妙(“現代”)的性別歧視。兩種形式的歧視都表現為否認歧視、反對努力增進平等(例如,“黑人在爭取平等權益方面要求太多了”)。
我們還能覺察到行為層面的偏見。由伊恩·艾爾斯(Ian Ayres,1991)領導的研究小組做的正是這類研究。小組成員走訪了芝加哥地區90多家汽車銷售商,採用統一的策略討價還價,就銷售商的一款成本價約為11000美元的新車,詢問最便宜的售價。給白人男性的最終售價平均為11362美元;給白人女性的平均售價為11504美元;給黑人男性的平均售價為11783美元;給黑人女性的平均售價為12237美元。為了檢驗勞動力市場可能存在的歧視現象,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者針對1300份不同的招聘廣告發送了5000份簡歷(Bertrand & Mullainathan,2003),隨機分配的白人姓名(如Emily、Greg)的應聘者,每發送10份簡歷收到一個回覆,而那些取了黑人姓名(如Lakisha、Jamal)的應聘者,每送出去15份簡歷才收到一個回覆。
現代偏見甚至表現為種族敏感性,它致使人們對被隔離的少數民族人士反應過度——包括對他們的成功讚揚過度,對他們的過失批評過度(Fiske,1989;Hart & Morry,1997;Hass & others,1991)。它同時也表現為某種憐憫姿態。例如,肯特·哈伯(Harber,1998)將一篇寫得很糟糕的文章給斯坦福大學的白人大學生,請他們做出評價。相對於被引導認為作者是白人的情形而言,當大學生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黑人時,評定的分數相對較高 ,他們很少發表嚴厲的批評。這些評定者,或許是為了避免表現出偏見,他們採用不大嚴厲的標準,對黑人作者更寬容。哈伯指出,這種“讚揚過度和批評不足”,可能會阻礙少數民族學生取得好成就。
多維達、卡韋凱姆和蓋特納(Dovidio,Kawakami,& Gaertner,2002)讓白人大學生與白人或黑人同伴交流互動。他們發現,大學生在種族量表上的反應,能夠預測他們在互動時言語當中的種族偏見。但是,他們對黑人的自動的情緒反應能預測他們的非言語行為。
自動偏見
這類現代偏見再次說明了我們的“雙重態度 ”體制(dual attitude system)(參閱第2章)。針對同一對象,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外顯(意識)和內隱(自動)態度。因此,對於那些我們目前表示尊重和欣賞的人,我們可能保留源自孩提時代的習慣性的、自動的恐懼或者厭惡。儘管外顯態度可以隨教育而發生巨大的變化,內隱態度則徘徊不去,除非我們通過練習而形成新的習慣(Kawakami & others,2000)。
耶魯大學(Banaji & Bhaskar,2000)、印第安那大學(Fazio & others,1995)、科羅拉多大學(Wittenbrink & others,1997)、華盛頓大學(Greenwald & others,2000)以及紐約大學(Bargh & Chartrand,1999)的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的實驗,確認了自動刻板化和偏見的現象。這些研究通過快速閃現詞語或面孔來“啟動”(自動激活)有關某類種族、性別或年齡群體的刻板印象。參與者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他們被激活的偏見可能隨後會引起他們行為的偏差。例如,針對令人厭惡的主試要求,人們如果受到與非裔美國人有關的圖像啟動,他們對主試煩人的要求可能會產生更加具有敵意的反應。在安東尼·格林沃爾德和他的同事(Greenwald & others,1998,2000)所做的巧妙實驗中,當結合黑人面孔而非白人面孔的時候,10名白人中有9人要用更長的時間來認定愉快的單詞(例如“和平 ”和“天堂 ”)是“好的”。你會注意到,參與者一般幾乎或沒有明確表示出偏見,只有無意識、非故意的反應。不僅如此,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Hugenberg & Bodenhausen,2003)報告說,這種內隱偏見表現得越強烈的人,越容易從黑人面孔中感知出憤怒(參閱圖9-2)。

圖9-2 面對偏見
憤怒到哪裡就不見了?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向大學生展示一系列從憤怒到快樂的面孔變體。同看白人的面孔相比,那些(在內隱種族態度測驗中)根據得分被認定為最有偏見的人,他們在模稜兩可的黑人面孔系列中更容易看到憤怒的影子。
科雷爾及其同事(Correll & others,2002),格林沃爾德及其同事(2003)在他們各自的實驗中,邀請人們快速按鈕“射擊”或者“不射擊”那些在屏幕上突然出現的人,這些人或者手握槍械,或者手持諸如閃光燈或瓶子之類的無害物品。參與者(其中一個研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更容易誤擊黑人目標。在一個相關的系列研究當中,佩恩(Payne,2001),賈德及其同事(Judd & orhers,2004)都發現,當用黑人而非白人面孔啟動時,人們想到的是槍:他們更快辨認出槍,他們更多地將扳手之類的工具誤認為是槍。這些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阿馬都·戴羅(Amadou Diallo)(紐約市的一名黑人移民)被警察開槍射擊了41次,就因為他將錢包從後面口袋中拿出來。
格林沃爾德和舒(Greenwald & Schuh,1994)指出,即使是那些研究偏見的社會科學家似乎也容易有偏見。他們選定了一些非猶太人姓名(Erickson,McBride,& others)和猶太人姓名(Goldstein,Siegel,& others),分析這些人的社會科學文章引文中的偏見。他們分析了近30000條引用,包括了17000條關於偏見研究的引用,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結果:與猶太裔作者相比,非猶太裔作者引用非猶太裔姓名的概率要高出40%。(格林沃爾德和舒不能確定是否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他們的猶太裔同行的文章,還是非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非猶太裔同僚的文章,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性別偏見
對女性的偏見有多普遍?我們在第5章中考察了性別角色規範——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應該 如何言行舉止的觀念。這裡我們關注性別刻板印象 ——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事實上 如何言行舉止的信念。規範帶有約定 性質,而刻板印象則是描述 性的。
性別刻板印象
從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兩個結論是毫無疑義的:存在很強的性別刻板印象,並且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刻板化群體的成員也接受這種刻板印象。男性和女性會一致認為你可以 根據書的性感封面來判斷一本書。在一項調查中,傑克曼和森特(Jackman & Senter,1981)發現性別刻板印象要比種族刻板印象更強。例如,認為兩性同樣“易動感情”的男性只有22%。剩餘的78%的男性中,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遠遠多於認為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其比例是15:1。那麼女性如何看這個問題呢?她們的答案是一樣的,差異不超過1個百分點。
再來看看波特、蓋斯和沃爾斯德(Porter,Geis,& Walstedt,1983)的一項研究。他們向學生展示一些照片,上面是“一組研究生,他們作為一個研究項目團隊而一起工作”(圖9-3)。隨後他們讓學生做一個“第一印象”測試,要求他們猜測其中誰對小組的貢獻最大。除了位於桌子首席的那位女士之外,圖9-3中的每位男士被選為領導者的次數比3位女士的總和還多!這種視男性為領導的刻板印象不僅真實地存在於女性以及男性當中,同時也存在於女權主義者以及非女權主義者當中。新近的研究表明,如果由女性來實施領導行為,那麼她們相對就不被人們看好(Eagly & Karau,2000)。斬釘截鐵的風格,在女性身上就不如在男性身上顯得那麼適宜(這使得女性更難成為領導或者取得成功)。性別刻板印象有多普遍?非常普遍。

圖9-3
在這些人當中,你猜測哪一位對小組的貢獻最大?大學生看到這張圖片的時候,他們通常猜測為兩位男士當中的一位,儘管那些看到由同一性別構成的小組圖片的人多數會猜測坐在桌子首席的人。
要記住,刻板印象是有關一群人的概括,它們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或者過度概括偏離了真理的核心。(它們也可能帶有自我實現的性質。)我們在第5章中提到過,普通男性和普通女性之間在社會聯繫、移情、社會權力、攻擊性和性愛主動性(然而並不包括智力)等方面確實存在某些差異。那麼據此我們能否得出結論認定性別刻板印象準確呢?刻板印象有時會誇大差異,但據珍妮特·斯溫(1994)的觀察,並非總是如此。她發現賓州州立大學的學生有關男性和女性在不安分性、非言語敏感性、攻擊性等方面的刻板印象有其合理性,比較接近於真實的性別差異。而且,這些刻板印象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綜合考察了27個國家的數據之後,約翰·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1999,2000)發現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女性更為宜人,而男性則更開朗。性別刻板印象的持續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進化論心理學家相信性別刻板印象反映出了天生、穩定的本質特性(Lueptow & others,1995)。
刻板印象(信念)並不是偏見(態度)。刻板印象可能為偏見提供支持。不過,拋開偏見而言,人們可能會贊同男性和女性“有差別但平等”。讓我們就此來看看研究者如何探討性別偏見。
性別態度
根據人們對調查研究者的陳述,針對女性的態度與人們的種族態度一樣,變化得非常快。1937年的時候,如果面對一名獲得政黨提名作為總統候選人的合格女性,1/3的美國人聲稱他們願意投票支持;到2003年,聲稱願意投票的人有87%(Jones & Moore,2003)。1967年,56%的美國大學一年級學生贊同“已婚女性的活動最好限定在家庭中”;到2002年,贊同該觀點的人只有22%(Astin & others,1987;Sax & others,2002)。
伊格利和她的同事(1991),哈多克和贊納(Haddock & Zanna,1994)也報告說,人們可能會以發自肺腑的負面情緒來對待某些群體,但他們不會這樣來對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歡女性而非男性。他們感覺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藹、樂於助人。因此,一種好的 刻板印象導致了一種好的態度,伊格利(1994)為這種好的刻板印象起名為“女性妙效應 ”(women-are-wonderful effect)。
不過,性別態度往往是好惡相伴的,這是格利克,菲斯克以及他們的同事(Glick,Fiske,& others,1996,2000,2001)報道的結論,他們調查了19個國家的15000人。他們常常將一種仁慈的性別偏見 (女性的道德敏感性更高)和敵意的性別偏見 (一旦男性作出承諾,那麼她就會牢牢束縛他)混合在一起。
對於那些受性別偏見困擾的人來說,好消息也不少。一項曾被廣為宣傳的有關女性偏見的研究發現,它來自1968年戈德堡(Goldberg)所做的一項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戈德堡給康涅狄格(Connecticut)學院的女學生一些短小的文章,要求她們評定每篇文章的價值。有時一篇特定的文章署名為一名男性作者(例如,John T. McKay),有時則署名為一名女性作者(例如,Joan T. McKay)。總體上看,當文章署名為女性時,所獲得的評分比署名為男性時要低。壓迫的歷史印跡——自我貶低——清晰地浮現出來:女性對女性存在偏見。
由於急於展示存在性別偏見的微妙現實,我於是採用了戈德堡的材料,通過用我自己學生的便利條件,重複了他的實驗。學生們(女性和男性)並未表現出諸如貶低女性工作的傾向。因此,斯溫、博格達、馬魯亞瑪(Borgida,Maruyama)和我(1989)查閱了文獻,與調查者聯繫,盡我們所能地瞭解有關評價男女工作的性別偏見研究。出乎我們的意料,偶爾出現的偏見針對男性與針對女性的頻率一樣多。但是,在涉及將近20000人的104項研究中,最普遍的結論是“沒有差別 ”。在大多數的比較中,某項工作是由男性還是女性來承擔,不影響到對該項工作的評價。艾麗斯·伊格利(1994)總結了其他有關評價男性和女性作為領導、教授及其他身份的工作的研究,她說,“實驗並沒有 證實存在貶低女性工作的任何總體 趨勢。”
問題: “Misogyny”是對婦女的憎恨。與討厭的男人對應的詞是什麼?
答案: 在大部分詞典中不存在這樣的詞 。
性別偏見在西方國家是否正在迅速消失?女權運動是否已經接近完成其使命?與種族偏見一樣,堂而皇之的性別偏見已然滅亡了,但微妙的偏見依然存在。例如,採用偽渠道方法(bogus-pipeline method)便可揭露偏見。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所指出的,那些相信實驗者可以通過一個敏銳的測謊儀來了解自己的真實態度的人,對女性權利的同情就表現得少一些。[2000年一項對美國婦女的調查中,65歲及以上年齡的婦女有22%說她們曾受到過歧視,而28~34歲的婦女中有50%的人說有相同的情況(Hunt,2000)。活動:為什麼會存在如此的差異? ]
在西方民主國家以外,性別歧視的情況更嚴重:
世界上未上學的兒童當中有2/3是女孩(聯合國,1991)。
沙特阿拉伯禁止婦女駕駛車輛(Beyer,1990)。
就全世界而言,人們傾向於生男孩。1941年,美國有38%的懷孕父母說他們如果只養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喜歡要男孩;24%的人喜歡要女孩;23%的人說他們無所謂。到2003年,答案幾乎沒有變化,依然是38%的人喜歡要男孩(Lyons,2003;Simmons,2000)。隨著人們廣泛採用超聲技術來檢測胎兒的性別,以及越來越多的墮胎可行性,這些偏好正在影響男孩和女孩的數量。2000年中國人口統計表明,新生兒當中每出生100名女嬰,就會出生119名男嬰(Walfish,2001)。2001年印度人口統計報告指出,旁遮普省每出生100名新生女嬰就會對應出生126名男嬰(Dugger,2001)。最終結果就是數以千萬計的“遺失女性”。
總的來說,對有色人種和女性的公然偏見已遠不如40年前那樣普遍。對於同性戀者的偏見也同樣如此。然而,採用對微妙偏見敏感的技術手段依然能檢測到廣為存在的偏見。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性別歧視簡直是要命的。因此,我們必須審慎深入地考察偏見的社會、情感和認知緣由。
小結
刻板印象是有關其他群體的信念,信念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或者過度概括,但是它是基於真理核心的。偏見是一種預斷性的負面態度。歧視是不合理的負面行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可能指個體的預斷態度,或者歧視行為,或者壓制性的制度實踐(即使並非有意帶有偏見)。
刻板化的信念、偏見性的態度和歧視性的行為長期以來一直在危害著人們的生存。根據過去40年美國人對調研人員的陳述來判斷,他們對黑人和女性的偏見已經驟然減少。然而,微妙的調查問題、評估人們態度和行為的間接方法,依然能揭示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相當程度的掩飾過的種族和性別偏見。偏見雖然不再那麼明顯,但它依然潛伏著。
偏見有哪些社會根源
什麼社會條件滋生偏見?社會如何維持著偏見?
偏見起源於多種根源。它的產生可能源於社會地位的差異,人們想證明這些差異是正當的,並且願意維持這些差異。偏見也可能是我們坐在父母的膝蓋上習得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瞭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差異。最後,我們的社會制度可能起到了維持和支持偏見的作用。先考慮偏見是如何發揮作用來保護自尊和社會地位的。
社會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與偏見
要記住的一條原則: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滋生了偏見 。主人視奴隸為懶惰、不負責任、缺乏抱負——正因為他們擁有那些特點,所以他們適合被奴役。歷史學家在爭論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不過,一旦這些不平等業已存在,偏見就在幫助使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將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特權合理化。告訴我兩個群體之間的經濟關係,我便可以預測群體之間的態度。刻板印象使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合理化(Yzerbyt & others,1997)。即使是社會地位發生臨時變化,也能影響到偏見。裡奇森和安貝蒂(Richeson & Ambady,2003)引導白人大學生相信自己通過計算機在與黑人或者白人同伴相配合,他們扮演同伴的上司或者下屬,如果大學生扮演上司,當他們與一個假定的黑人同伴配合時,更容易表現出自動偏見。
現實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直至今日,在施行過奴隸制的地區中偏見還最為嚴重。19世紀的歐洲政治家和作家們通過把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護”的、是一種需要忍受的“負擔”從而認為帝國擴張是正當的(G. W. Allport,1958,pp. 204-205)。40年前,社會學家海倫·邁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關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助長人們認為其低下社會地位的合理化:許多人認為這兩個群體智力低下、情緒化、未開化,“滿足”於他們從屬的角色。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則是“軟弱的”。黑人的處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則是在家中。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利克和菲斯克所區分出的“敵意”和“仁慈”的性別歧視,衍生到了其他的偏見上。我們會認為其他群體能幹,或者是可愛,但通常不會兼而有之。我們敬重 那些地位高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同時也喜愛 那些欣然接受較低地位的人。菲斯克和她的同事們報告說,在美國,亞洲人、猶太人、德國人、非傳統的女性、自信的非裔美國人以及男同性戀者往往會受到尊重,但卻不怎麼被人喜愛。傳統的下層美國黑人、西班牙裔、傳統婦女、女子氣的男同性戀者、殘疾人,往往被視為能力較弱,但卻因情感、精神、藝術或運動能力上的品質而受到喜愛。
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態度很容易隨行為而改變。人們往往不把敵人當人看,用各種各樣的標籤來貶低他們的人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成了“日本鬼子”。戰爭結束後,他們成為“睿智、勤奮的日本人”。態度的適應能力令人驚訝。正如我們在前幾章所指出的那樣,殘酷的行動導致殘酷的態度。
性別刻板印象也使得性別角色的合理化。在研究了世界範圍內的這些刻板印象之後,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1990b)提到說,如果女性在照顧小孩方面付出大部分關愛,那就可能認為女性天生就善於養育孩子;如果男性做生意、打獵以及參與戰爭,那就很自然地認為他們咄咄逼人、獨立、愛冒險。實驗表明,在看待未知群體的成員時,人們認為這些人具有一些正適合他們角色的特質(Hoffman & Hurst,1990)。
有些人能注意並且調整適應社會地位的差異。那些在社會支配性取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中得分高的人,傾向於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人。他們願意讓他們的社會群體社會地位高一些——他們喜歡位於社會階層的頂層。處於社會高層支配位置,也傾向於促進這種取向(Guimond & others,2003)。Jim Sidanius,Felicia Pratto以及他們的同事(Pratto & others,1994;Sidanius & others,1996;Sidanius & Pratto,1999)解釋說,這種希望出人頭地的想法導致那些社會支配性高的人樂於接受偏見,支持那些為偏見做合理辯護的政治立場。在社會支配性取向上得分高的人,事實上往往支持那些諸如為富人減稅之類的維護階層等級的政策,反對諸如遵從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之類的破壞階層等級的政策。社會支配取向得分高的人,還偏好做專業人士、從事政治和商業活動,以提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維持階層等級。他們不願意做破壞社會階層等級的工作,如社會工作者。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滋生偏見,但相比於其他人,有些人會更多地追求社會經濟地位,並且試圖維持這種地位。
社會化
偏見起源於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其他社會原因,包括我們習得的價值觀和態度。
權威人格
20世紀40年代,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研究者——其中有兩位從納粹德國逃離出來的——設立了一個緊迫的研究任務:揭示反猶太人的心理根源。反猶太人政策影響之壞,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而且讓那麼多歐洲人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在研究美國成人的時候,西奧多·阿多納(Adorno & others,1950)發現,敵視猶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時敵視其他少數民族。偏見似乎不只是具體針對某一群體的態度,而是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不僅如此,這些自以為是的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c)者普遍擁有獨裁的傾向——不能容忍軟弱,具有懲罰性的態度以及服從群體內部的權威。這些獨裁傾向,反映在他們贊同諸如“服從和尊敬權威是孩子們應該學習的最重要的品質”之類的陳述上。
權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時代往往經歷過苛刻的規矩。這可能導致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敵意和衝動,並將這些敵意和衝動“投射”到了外群體身上。權威人格兒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們傾向於特別關注權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對即錯的頑固思維方式,難以忍受模糊性。因此,這類人就傾向於服從那些權力比自己大的人,攻擊或者懲罰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學者們對該研究持批評態度,因為該研究只盯著右翼權威,忽略左翼的教條權威主義。儘管如此,該研究的主要結論依然成立:權威主義傾向,有時候在種族緊張局勢中有所反映,在經濟衰退、社會鉅變、日子變得艱難的時候,權威傾向也會急劇高漲(Doty & others,1991;Sales,1973)。在當代俄羅斯,人們在權威主義上的得分非常高,這就助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回潮和對民主改革的抵制(McFarland & others,1992,1996)。
不僅如此,馬尼托巴大學心理學家鮑勃·阿爾特邁耶(Altemeyer,1988,1992)對右翼權威主義的近期研究證實了有 些個體以偏見來表達恐懼和敵意。感覺自己在道義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會野蠻地對待自認為劣等的人。
不同形式的偏見——對黑人、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者——的確 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Bierly,1985;Crandall,1994;Peterson & others,1993;Snyder & Ickes,1985)。正如阿爾特邁耶總結的,右翼權威主義往往是“均等機會頑固分子”。
特別讓人感到震驚的是社會支配取向和權威主義人格得分高的人。阿爾特邁耶(待發表)報告說,這些“雙高”人士“屬於我們社會當中偏見最深的人”,這一現象並不令人感到吃驚。他們在各種人格特點上似乎都表現得最差,他們一方面武斷教條、充滿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則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來努力謀求社會經濟地位。阿爾特邁耶指出,儘管這些人相對很少,但他們往往會成為仇視群體的領袖。
宗教與偏見
那些得益於社會不平等的人,在聲稱“人生而平等”的同時,還需要為讓各種事情維持現狀而尋求合理化的辯解。相信是上帝規定了現存的社會秩序,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斯指出,對所有的殘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1902,p.264)。
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都利用宗教來使當前的秩序神聖化。利用宗教來維護不公正,這有助於解釋有關基督教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兩個相互印證的發現:(1)教會成員比其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種族偏見;(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傳統信仰不那麼明顯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傳統或正統基督教的人表現出更多的偏見(Altemeyer & Hunsberger,1992;Batson & others,1993;Woodberry & Smith,1998)。
瞭解到宗教和偏見這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並不能讓我們瞭解它們的因果聯繫。它們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聯繫。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許更信奉正統基督教,同時又更多地抱有偏見。可能是偏見導致宗教信仰,即偏見引導人們創造宗教觀念來維護他們的偏見。也可能是宗教導致偏見,即宗教引導人們相信所有人都擁有自由意志,貧困潦倒的少數民族應該就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責備自己。
如果的確是宗教導致偏見,那麼越虔誠的教會成員偏見就越深。但另外三個研究一致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在教會成員中,同偶爾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誠的信徒在26次對比中有24次顯示出較少的偏見。
奧爾波特和羅斯(Allport & Ross,1967)發現,相對那些將宗教多少視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們會認同這樣的陳述:“我對宗教感興趣,主要是因為做禮拜是件令人愉悅的社會活動”),那些以宗教本身為目的的人(例如,他們會認同這種陳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為什麼這麼生活的理由”)表現出較少的偏見。而且,在蓋洛普的“宗教承諾”(spiritual commitment)指數中得分高的人,更歡迎其他種族的人做鄰居(Gallup & Jones,1992)。
新教牧師和羅馬天主教牧師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權運動(Fichter,1968;Hadden,1969)。1934年,德國45%的神職人員與組織起來反對納粹統治的懺悔教堂(Confessing Church)結盟(Reed,1989)。
那麼,宗教和偏見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 提問。如果我們將宗教虔誠定義為成為教會成員或至少在表面上認同傳統信仰的意願,那麼越虔誠的人就懷有越多的種族偏見。頑固分子往往藉助宗教使其固執合理化。可是,如果我們以其他幾種方式來評價宗教虔誠的程度,那麼越虔誠的人則懷有越少的偏見——因此,現代民權運動具有宗教的根基,該運動的領導者當中有許多基督教牧師和基督教新教牧師。正如戈登·奧爾波特所總結的那樣,“宗教的作用顯得自相矛盾。它製造偏見,同時又廢除偏見。”(1958,p.413)。
從眾
偏見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會由於慣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見被社會所接受,那麼許多人將會跟從遵循最為暢通無阻的道路,順從這種潮流。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因為恨的需要而產生,但更可能是因為被人喜歡和接受的需要而產生。
托馬斯·佩蒂格魯(1958)研究了南非和美國南部的白人,研究揭示了在20世紀50年代,那些最遵從其他社會規範的人同時也是最具有偏見的人;那些不怎麼遵從的人身上則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見。對於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師來說,不從眾的代價顯然是痛苦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在學校解除種族隔離的決議就是在那裡執行的。大多數牧師願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這麼說;他們害怕公開宣稱會使他們失去教會成員、失去捐助者(Campbell & Pettigrew,1959)。或者考慮一下同一時代印第安那州的鋼鐵工人和弗吉尼亞州西部的煤礦工人,在工廠和礦井中,工人們認可種族的融合。而鄰里關係的規則卻是嚴格的種族隔離(Minard,1952;Reitzes,1953)。偏見顯然並非“病態”人格的反映,它只不過是社會規範而已。
從眾同樣也維持著性別偏見。“如果我們來思考一下託兒所和廚房為什麼是女性的天然領域”,蕭伯納在1891的一篇文章中寫到,“我們的所作所為與英國孩子開始思索籠子為什麼是鸚鵡天生應該呆的地方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從未看到過鸚鵡。”曾 見到女性在別處的孩子——那些職業女性的孩子——對男性和女性的看法相對而言刻板化程度要低一些(Hoffman,1977)。
所有這些觀點中,尚有一線希望。如果偏見並非植根於人格,那麼隨著潮流的改變,新規範的演進,偏見便可能消除。事實上,它的確在變。
社會制度的支持
種族隔離是社會制度(學校、政府、媒體)助長偏見的一種形式。政治領袖既能反映各種盛行的態度,又能強化這些態度。1957年,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奧維爾·福伯斯(Orville Faubus)關閉了小石城的中心學校的大門,以阻止種族融合。他所做的,不僅僅是代表他的選舉人,更主要的是,他在使他們的觀點變得合理化。
學校同樣也在強化主流的文化態度。一項研究分析了1970以前寫作的134份兒童讀物中的故事內容,發現男性人物角色比女性人物角色要多,比例是3:1(文字和圖片上的女性,1972)。被描寫為主動、勇敢和富有能力的人會是誰?在來自經典兒童讀物《迪克和簡》(Dick and Jane )的一段摘錄當中可以看到答案:簡仰面摔倒在人行道上,身邊是她的溜冰鞋,聽聽馬克向他母親所做的解釋:
馬克說,“她不會滑冰”。
“我可以幫助她。
我想要幫助她。
你看她,媽媽。
你先看看她。
她就像個女孩子。
她放棄了。”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有關男性和女性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使得人們對這類描述有了新的看法,這種公開的(對我們而言)刻板印象才被廣為關注,並且隨之發生了改變。
社會制度對偏見的支持往往來得不知不覺。一般說來,它們並非故意要壓制某一群體。更多的時候,它們只是反映了理所當然的文化假定,正如蠟筆盒中標有“肉”色的蠟筆就是粉白色的。
當代還有哪些制度性偏見的例子依然沒有被注意到?下面是一個我們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例子,儘管它就在我們眼前:在查閱了來自雜誌和報紙的1750張照片之後,戴恩·阿徹和他的合作者們(Archer & others,1983)發現,大約2/3的普通男性照片專注於面部,而專注於面部的普通女性照片只有不到一半。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阿徹發現這種“面孔歧視”(face-ism)十分普遍。在其他11個國家的期刊上,在6個世紀的藝術作品中收集的920幅人物肖像中,以及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大學生的業餘作品中,他都發現了這一現象。喬治婭·尼格羅和她的同事(Nigro & others,1988)證實,在其他許多雜誌,包括《女士》(Ms. )也存在面孔歧視現象。
研究者猜想,對男性面孔和女性軀體的視覺突出,既反映了性別偏見,同時也在延續性別偏見。諾伯特·施瓦茨和伊娃·庫爾茨(1989)在德國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照片中面孔被突出的人顯得更有智慧、更有抱負。不過,全身刻畫總好過沒有任何視覺表現。露絲·蒂博多(Thibodeau,1989)分析了過去42年中《紐約客》(New Yorker )上的卡通畫,她僅找到一幅與種族無關的畫,上面有一名美國黑人(流行的卡通畫大都沒有表現民族多樣性,所以本書用照片來描繪多樣性要比用卡通畫容易得多)。
電影和電視節目同樣也包含並且強化了各種盛行的文化態度。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裡,笨拙、天真的非洲裔管家和女僕形象促進了它們所反映的刻板印象經久不衰地延續下去。儘管如今我們多數人會反感這類形象,但即使是一部有關一位具有犯罪傾向的美國黑人的現代戲劇幽默電視片,隨後也可能使得另一名被控傷害罪的非裔美國人的罪行顯得更為嚴重(Ford,1997)。發源於黑人藝術家的極端說唱(rap)音樂,導致黑人和白人聽眾都對黑人形成了某種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具有暴力傾向(Johnson & others,2000)。
小結
社會情境以多種方式滋生並且維持著偏見。一個沉醉於社會和經濟優越感中的群體,往往會以偏見的信念來為他們的地位做辯解。人們同樣也在孕育或者減少偏見的方式下被撫養長大。家庭、宗教團體及更廣闊的社會都可能維持或者減少偏見。社會制度部分出於慣性的原因也支持助長偏見。
偏見有哪些動機根源
偏見可能由於社會情境而滋生繁衍,但偏見中的敵意和希望不偏不倚的願望背後都有動機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發偏見,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體高人一等的意願一樣。但在有些時候,人們也希望避免偏見。
挫折與攻擊:替罪羊理論
在第10章我們將看到,痛苦和挫折(目標受阻)常常引起敵意。當我們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膽怯或者莫名其妙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轉移我們的敵對方向,這種“替代性攻擊”現象,也許助長了(美國)內戰之後南方地區對美國黑人濫施私刑的行為。1882~1930年之間,當棉花價格下跌、經濟受挫的時候,濫用私刑的情況大致就越嚴重(Hepworth & West,1988;Hovland & Sears,1940)。近幾十年來,仇視性犯罪似乎並不隨著失業率的波動而波動(Green & others,1998),但是,當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社會民眾就對(民族)多樣性和反歧視法案持更開放的態度(Frank,1999)。在繁榮時期,更容易維護民族和睦。
這種替代性攻擊的目標是變化不定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隨之又出現經濟的混亂,許多德國人都把猶太人看成是罪魁禍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德國一位領導人就闡述道:“猶太人只不過是替罪羊。……如果沒有猶太人,反猶太分子也會創造出猶太人來”(G. W. Allport,1958,p.325)。在幾世紀以前,人們曾經把他們的恐懼和敵意發洩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時在公共場合被燒死或溺死。憤怒激起了偏見。
競爭是挫折的來源之一。當兩個群體為工作、住房或社會聲望而競爭的時候,一個群體實現了目標,這將成為另一個群體的挫折。因此,現實群體衝突理論 (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認為,一旦群體為稀缺資源而競爭,就會出現偏見(Esses & others,1998)。高斯定律(Gause's law)就是一個與此有關的生態學原則,它認為有同樣需求的物種之間競爭將最大化。
例如,西歐有些人贊成這種說法,“過去5年當中,像你這樣的人經濟狀況比大多數(此處是該國某個少數民族的名字)人都差。”這些飽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偏見(Pettigrew & Meertens,1995)。在加拿大,自1975年開始,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牴觸隨失業率而上下波動(Palmer,1996)。在美國,敵視黑人的偏見在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與黑人最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Greeley & Sheatsley,1971;Pettigrew,1978;Tumin,1958)。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偏見——對某些人來說——就成為報復的手段。
社會同一性理論:感覺比他人優越
人是群居性動物。我們的祖先教會了我們如何滿足和保護我們自己——在群體中生存。人類為其群體而歡呼,為其群體而殺戮,為其群體而獻身。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納和米歇爾·霍格(Turner,1981,1987,1991,2001;Hogg,1992,1996,2003)以及他們的同事注意到,我們還很自然地以我們的群體來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們感覺自己是誰——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同一性 (我們對自己的個人特性和態度的感受),而是一種社會同一性 (social identity)。菲奧娜把自己看做是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黨黨員,一名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學生,一名麥克唐納家族的成員。我們肩負如此多的社會身份,如同玩紙牌,在最恰當的時候打出各張牌。
在與英國已故社會心理學家亨利·託什菲爾(Henri Tajfel)一起工作時,特納提出了社會同一性理論 。特納與託什菲爾觀察到一下現象:
我們歸類 :我們發現將人,包括我們自己,歸入各種類別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時候,給這個人貼上印度人、蘇格蘭人或公共汽車司機的標籤,不失為一種簡略的方法。
我們認同 :我們將自己與特定的群體[我們的內群體 (ingroups)]聯繫起來,並以此獲得自尊。
我們比較 :我們將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群體[外群體 (outgroup)]進行比較,並且偏愛自己的群體。
我們在評價自己的時候,會部分地依據自己的群體成員身份。擁有一種“我們”的感覺能增強我們的自我概念。這種“感覺 ”好極了。我們不僅在群體中為我們自己尋求尊重 ,還在群體中尋求自豪感 (Smith & Tyler,1997)。而且,認為我們的群體比較優秀,有助於讓我們感覺更好。這就像我們都想過的,“我是一名X(說出你的群體)。X很好,所以,我很不錯。”
如果缺乏積極的個人同一性,人們往往會通過認同某一群體來獲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輕人通過加入幫派來尋找自豪感、權力和同一性;許多極端的愛國者以他們的國別來描述自己(Staub,1997)。很多迷茫的人投身於新的宗教運動、自助群體和兄弟會後,在其活動中找到同一性(圖9-4)。

圖9-4
個人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內群體偏見
以群體方式來描述你是誰——如你的種族、宗教、性別、所學專業——意味著在描述你不是誰。包含“我們”(內群體)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們”(外群體)。因此,僅僅是感覺到被歸入某一群體,也可能增加內群體偏見 (ingroup bias)。如果問孩子們:“你們學校的學生和他們(附近另一所學校的學生)比起來,哪裡的學生更優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會說自己學校的學生更優秀。對成年人來說也同樣如此,離家越近的東西看上去就越好。有超過80%的白人和黑人都認為他們鄰里之間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但僅有不到60%的人認為整個國家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Sack & Elder,2000)。在實驗情境中,僅僅與某個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以強大的聯繫,激發密切的合作(Miller & others,1998)。
內群體偏見是人們尋求積極自我概念(參閱第2章)的又一個例證。我們的群體意識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只要有理由認為我們是一個群體,我們就會這麼做,隨後就會表現出內群體偏見。僅根據駕駛證的最後一位號碼將人們歸入不同的群體,他們就會感覺到號碼匹配的夥伴之間存在某種親密的關係。託什菲爾和比利希(1974;Tajfel,1970,1981,1982)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只需一些十分細小的線索,就能激發出人們對我們 的偏袒和對他人 的不公。在一項實驗中,託什菲爾和比利希讓英國的青少年被試評價現代抽象派繪畫,然後告訴他們,他們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賞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而不太喜歡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畫。最後,甚至在從沒有見到群體其他成員的情況下,這些青少年就開始在成員之間分錢了。
這個實驗以及其他一些實驗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來定義群體,但也產生了內群體偏愛。懷爾德(Wilder,1981)總結了典型的結果:“當獲得機會來分配15分的分值(值錢的)時,被試一般都給自己的群體9~10分,其他群體5~6分。”這種偏見在不同性別、各種年齡、各種國籍的人身上都會發生,尤其是來自個體主義文化的人(Gudykunst,1989)。(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相對更認同所有的同伴,因而更能夠做到一視同仁。)
當我們的群體相對於外群體而言規模較小、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時候,我們就更容易表現出內群體偏見(Ellemers & others,1997;Mullen & others,1992)。當我們屬於一個較小的群體,被一個較大的群體包圍時,我們同樣也會意識到我們的群體成員屬性;當我們內群體是多數派時,我們倒不怎麼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會當中,作為外國留學生、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者、少數民族或弱勢性別的一員,人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社會身份,並且做出相應的反應。
即使是毫無 邏輯依據而組成的群體意識——比如說,僅僅通過投擲硬幣來組建X組和Y組——也會產生某種內群體偏見(Billig & Tajfel,1973;Brewer & Silver,1978;Locksley & others,1980)。在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的小說《打鬧劇》(Slapstick )當中,電腦給每個人名和姓之間取了一箇中間名字;於是,所有中間名字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們彼此之間團結一致,疏遠那些中間名字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務偏見(第2章)再次出現,使得人們獲得更積極的社會同一性:“我們”比“他們”好,即使“我們”和“他們”是隨機界定的!
因為我們有社會同一性,所以我們服從於我們的群體規範。我們為團隊、家庭和國家犧牲自我。我們可能不喜愛外群體。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越重要,我們就越強烈地感受到對群體的依戀,面對來自其他群體的威脅,我們的反應就越充滿偏見(Crocker & Luhtanen,1990;Hinkle & others,1992)。伊斯蘭曆史學家、前耶路撒冷副市長梅倫·本維尼斯提(Benvenisti,1988)說過,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當中,社會同一性對於自我概念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它能不斷地提醒著人們他們不是誰。因此,他生活在一個混合居住的街區,但他自己的孩子——令他驚訝的是——“沒有結識任何一位阿拉伯朋友”。
當我們的群體已經獲得成功時,通過更強烈地認同於該群體,我們也可以使自己感覺更好。大學生在他們的橄欖球隊獲勝之後一旦被人詢問,他們通常回答說“我們 贏了”。當他們的球隊輸了以後被問人及時,他們更可能說“他們 輸了”。對於那些剛剛經歷突如其來的自我打擊的個體,諸如瞭解到他們在“創造性測驗”中表現很差,內群體成員的成功所折射的光芒最讓他們揚揚自得(Cialdini & others,1976)。一位朋友的成就所折射出的光輝同樣讓我們得意洋洋——除非該朋友在某些與我們的認同有關的事情上勝過我們(Tesser & others,1988)。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傑出的心理學學生,你可能因為一位朋友優秀的數學成績而感受到更多的喜悅。
內群體偏見即偏袒某個人自己的群體。這種偏愛可以反映在:(1)喜歡內群體;(2)討厭外群體;(3)兩者兼而有之。如果兩者兼而有之,那麼對自己群體的忠誠應該會造成對其他群體的貶低。真是這樣嗎?種族自豪感會導致偏見嗎?強烈的女權主義認同,會使女權主義分子討厭非女權主義者嗎?忠誠於某一特定兄弟或姐妹聯誼會,是否會導致其成員貶低那些獨立者和其他聯誼會的成員?
實驗同時支持兩種解釋。當人們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內群體身份時,諸如當人們與其他內群體成員在一起時,外群體刻板印象就容易盛行(Wilder & Shapiro,1991)。在俱樂部聚會時,我們會最強烈地感受到我們與其他俱樂部成員之間的差別。當預期自己的群體會遭遇偏見的時候,我們會更強烈地蔑視外群體(Vivian & Berkowitz,1993)。
然而,內群體偏見的產生,可能是源於感覺到其他群體很糟糕(Rosenbaum & Holtz,1985),同樣或者更多的原因可能是認為自己的群體很不錯(Brewer,1979)。因此,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所持的積極感受,並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對外群體同樣強烈的消極感受。積極投身於自己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有時的確使某人傾向於貶低其他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但這一系列關聯並非是自動化的。克里斯托弗·沃爾斯科(Christopher Wolsko,2000)等人根據他們對大學生所做的研究指出,事實上,多元文化而非色盲視角,不會導致對群體差別的敏銳知覺。但是,多元文化觀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的卻對外群體有利。他們指出,為了心理和社會健康,我們需要同時承認我們的個體獨特性、我們的群體同一性以及我們共同的人性。
社會地位、自我關注和歸屬的需要
社會地位是相對的:認為自己有地位,我們就需要有人不如我們。因此,從偏見或任何地位等級系統中可以獲得的一個心理學收益就是感覺到高人一等。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經因為別人的失敗而竊喜的情景——比如看見兄弟或姐妹被懲罰,或者同學考試不及格。在歐洲和北美,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體,以及那些積極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脅的群體,偏見往往更為強烈(Lemyre & Smith,1985;Pettigrew & others,1997;Thompson & Crocker,1985)。在一項研究中,同社會地位較高的女生聯誼會成員相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女生聯誼會成員更容易蔑視其他的女生聯誼會(Crocker & others,1987)。也許那些有著穩定社會地位的人對於優越感的需要相對弱一些。
然而,與地位低下相關聯的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釋偏見現象。設想你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一名學生,參加了羅伯特·恰爾迪尼和肯尼思·理查森(1980)的一項實驗。你正獨自在校園裡漫步,有人走近你,並請你幫忙完成一項5分鐘的調查。你同意了。研究者給你一個簡短的“創造性測驗”,之後他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在這個測驗上的得分相對較低”,你倍感挫折。然後,研究者在結束調查之前,向你詢問了若干有關你們學校或者一貫對手——亞利桑那大學——的評價性問題。你的受挫感會影響你對這兩所學校的評價嗎?通過對比自尊沒有受到威脅的控制組,體驗到挫折感的學生對他們自己學校的評價更高,對競爭對手的評價更低。顯然,通過吹噓自己的群體、詆譭外群體來維護自己的社會同一性,能夠提高一個人的自我。
詹姆斯·邁因德爾和梅爾文·勒納(Meindl & Lerner,1984)發現,一次羞辱性的經歷——如不小心打翻了某人很重要的一疊電腦卡——會引起講英語的加拿大學生對講法語的加拿大學生表現出更多的敵意。特雷莎·阿馬比爾和安·格萊茲布魯克(Amabile & Glazebrook,1982)發現,達特茅斯學院那些被引發出不安感的學生,在評價別人的工作時更加苛刻。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慮一下自己的死亡問題——寫一篇短文談談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發的情緒——也會引發人們足夠的不安全感以強化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Greenberg & others,1990,1994;Harmon-Jones & others,1996;Schimel & others,1999;Solomon & others,2000)。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會使他們更青睞鼓吹自己群體優越性的種族主義分子(Greenberg & others,待發表)。心中想到死亡的時候,人們就會採用“恐懼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即蔑視那些不斷挑戰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感到更焦慮的人。當人們已經感覺到他們有可能死亡,偏見有助於支撐一個受到威脅的信念系統。不過,有關死亡的消息並非一無是處,想到死亡,也能導致人們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團結精神和利他主義(McGregor & others,2001)。
所有這些都說明,一個懷疑自己的力量和獨立性的男人,可能通過宣稱女人的弱小和依賴是如何令人可憐,以此來誇耀自己的男子漢形象。當喬爾·格魯伯和蘭迪·克萊恩漢斯林克等人(Grube,Kleinhesselink,& Kearney,1982)讓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男生觀看一些年輕女士的求職面試錄像時,確實發現自我同一性低的男生不喜歡強勢、非傳統的女士。自我同一性高的男生則喜歡這些女士。實驗研究證實了自我形象(self-image)和偏見之間的聯繫:獲得肯定,人們將對外群體做出更積極的評價;自尊受到威脅,人們就會詆譭外群體,以恢復自尊(Fein & Spencer,1997;Spencer & others,1998)。
被蔑視的外群體還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對一個內群體的歸屬需要。我們將在第13章看到,知覺到一個共同的敵人會使一個群體變得團結起來。只有在與主要競爭對手較量的時候,學校精神才會變得少有的高昂。當員工感到都與管理層對立的時候,員工之間的同事情誼往往最為強烈。為了鞏固納粹對德國的統治,希特勒利用了“猶太威脅論”(Jewish menace)。蔑視外群體可以強化內群體。馬里奧·米庫爾林塞和菲利普·謝弗(Mikulincer & Shaver,2001)指出,一旦歸屬感需要獲得滿足,人們就變得更為接納外群體。他們採用一些能夠引發歸屬感的詞(愛、支持、擁抱 )和一些中性詞,對一些以色列學生進行閾下啟動。學生隨後閱讀一篇假定是由猶太學生或者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當以中性詞彙啟動時,這些以色列學生認為猶太學生寫的文章比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要好。當以引發歸屬感的詞來啟動之後,這種偏見就消失了。
避免偏見的動機
動機不僅使人們持有偏見,而且會使人們去努力避免偏見。儘管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想有偏見,但偏見的習慣卻歷久猶存。帕特里夏·迪瓦恩和她的同事(1989,2000)指出,無論是偏見高的人還是偏見低的人,有時具有相似的自動化的偏見反應。
我們儘可能地壓抑不合時宜的想法,如對食物的想法、對朋友的同伴的浪漫想法、對其他群體的評判想法,但這些想法有時卻頑固得揮之不去(Macrae & others,1994;Wegner & Erber,1992)。這一點對老年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老年人喪失了一部分抑制不好想法、壓抑陳舊的刻板印象的能力(Von Hippel & others,2000)。下面的結論適合我們所有人:不好(不和諧)的想法和情感往往經久不衰。打破這種偏見習慣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一個少數民族人士就可能觸發一種類似於膝跳反射的刻板印象。對同性戀者持接受或反對態度的人,在公共汽車座椅上與一名男同性戀者坐一塊,都會感覺不大舒服(Monteith,1993)。人們遇到一名不熟悉的黑人男士時——即使是那些以自己毫無偏見而引以為榮的人——也會小心翼翼地做出反應。在E. J. 範曼及其同事(E. J. Vanman & others,1990)所做的一項實驗中,白人觀看一些白人和黑人的幻燈片,想像自己與這些人物來往,評定對這些人物可能的喜愛程度。雖然參與研究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更喜歡幻燈片中的黑人而不是白人,但他們的面部肌肉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儀器顯示,當出現黑人面孔時,參與者面孔上的皺眉肌比微笑肌更加活躍。當一個人觀看其他種族的一個不熟悉的人時,大腦中的情緒加工中心也會變得更加活躍(Hart & others,2000)。
研究刻板印象的學者以比較樂觀的態度指出,偏見反應並非不可避免(Crandall & Eshelman,2003;Kunda & Spencer,2003)。避免偏見的動機會使人們調整自己的思維和行動。當意識到他們應該 如何去感受和他們實際 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間的差距時,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就會產生內疚感,並努力抑制他們的偏見反應(Bodenhausen & Macrae,1998;Macrae & others,1998;Zuwerink & others,1996)。迪瓦恩和她的同事(Devine & others,發表中)指出,當人們避免偏見的動機是內在(因為偏見是錯誤的)而不是外在(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別人把他們想得太壞)的時候,即便是自動的偏見也會有所衰減。
啟示:要克服迪瓦恩所說的“偏見習慣”(the prejudice habit)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反應有一種膝跳反射般的假設或情感,不要失望,這並不稀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對待這種意識。你是否讓這些感受主宰了你的行為?或者是你採取了一些彌補措施,控制和調整你在未來情境中的行為?
小結
人們的動機會影響其偏見。挫折滋生敵意,人們有時候會將這種敵意發洩到替罪羊身上,有時會更直接地針對競爭性的群體來表現這種敵意。人們還有一種願望,即認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群體比其他群體優越。即使很普通的群體成員身份,也會使人們喜歡自己的群體要勝於喜歡其他群體。自我形象受到威脅會增強這種內群體偏愛,歸屬感的缺失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從相對樂觀的角度看,避免偏見的動機能夠引導人們打破偏見習慣。
偏見有哪些認知根源
理解刻板印象和偏見,還有助於瞭解我們的心理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我們思考世界、簡化世界的方式如何影響我們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又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
上述有關偏見的說法大都發表於20世紀60年代——但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則不同。對偏見的這種全新視角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2100多篇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文章促進了這一觀點的發展,它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來探討社會思維(social thinking)。這種視角的基本觀點是:刻板信念和偏見態度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條件作用以及因為這些條件作用能讓人們發洩敵意,還因為它們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副產品。許多刻板印象,與其說源於內心深處的怨恨,還不如說產生於心理活動機制。知覺錯覺是我們解釋世界的技巧的副產品,與此類似,刻板印象可以是我們簡化複雜世界的心理機制的副產品。
類別化:將人歸入不同群體
我們簡化環境的方法之一就是分類 (categorize)——通過把客體歸入不同的類別來組織世界(Macrae & Bodenhausen,2000)。生物學家區分出植物和動物。一個人也會將人分類。這樣做了之後,我們思考這些事物的時候就會更輕鬆。如果一個群體內部的人具有一些相似性——如“門薩”(MENSA)成員大都很聰明,籃球運動員大都很高——那麼我們瞭解一個人的群體成員身份,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很多有用的信息(Macrae & others,1994)。刻板印象有時能提供“獲得的信息與付出的努力二者間的一個較好獲益率”(Sherman & others,1998)。正因為如此,所以海關檢查員和飛機反劫機人員為可疑分子給出了“輪廓描述”(Kraut & Poe,1980)。
自發類別化
在以下情形中,我們會發現依賴刻板印象能使我們既輕鬆又高效:
時間緊迫 (Kaplan & others,1993);
心事重重 (Gilbert & Hixon,1991);
疲憊不堪 (Bodenhausen,1990);
情緒激昂 (Esses & others,1993b;Stroessner & Mackie,1993);
年輕氣盛無法欣賞多樣性 (Biernat,1991)。
種族和性別,是當前世界當中最有效力的對人進行分類的方式。想像一下,湯姆,45歲,非裔美國人,新奧爾良房地產代理商。我可以推測,你的“黑人男性”形象遠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國南方人”等類別要突出。而且,當呈現黑人或白人的個體照片時,我們的大腦有不同的反應,這種差異大約在最初的1/10秒就開始了(Ito & Urland,2003)。
實驗結果表明,我們會根據種族對人進行自發分類。正如顏色實際是一個連續光譜,但我們把它知覺為相互區別的顏色一樣,我們無法抗拒將人歸入不同群體的傾向。人們的祖先千差萬別,我們簡單地將他們標定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這些類別黑白分明一樣。當個體觀看不同的人發表言論時,他們常常不記得誰說了什麼,但是他們記得每個發言者的種族(Hewstone & others,1991;Stroessner & others,1990;Taylor & others,1978)。這種類別化本身並不是偏見,但它的確為偏見提供了基礎。
事實上,偏見是必要的。在社會同一性理論看來,那些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敏感的人,會十分關注他們自己,正確地把人們區分為“我們 ”或“他們 ”。為了檢驗這一預測,吉姆·布拉斯科維奇和他的合作者(Jim Blascovich & others,1997)比較了具有種族偏見的人(他們能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種族同一性)和沒有種族偏見的人——經過證實他們能同樣快速地分辨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橢圓形物體,但是兩組人分別花了多長時間將人 按種族進行分類呢?尤其在所呈現面孔的種族特徵模稜兩可的時候(圖9-5),具有種族偏見的人花費的時間更長,更明顯地在考慮把人歸類為“我們”(某人自己的種族)還是“他們”(另一個種族)。偏見需要做種族分類。

圖9-5 種族分類
快速回答:這個人屬於什麼種族?偏見少的人反應較快,因為他們不那麼明顯地擔心把人分錯了類別(就好像在想“誰在乎呢?”)。
知覺到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請畫出以下物體:蘋果、椅子和鉛筆。
讓一個群組中的物體看做比實際上的更為統一,這是人的一種強烈的傾向。你看到的蘋果都是紅的嗎?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嗎?你的鉛筆都是黃色的嗎?一旦我們把兩個日子歸在同一月份,那麼同跨月份但間隔相同的兩個日子相比,它們看起來就更相像,氣溫更接近。比如說,人們來猜測8天平均氣溫的差別,11月15日至23日之間的氣溫差異比11月30日至12月8日之間的8天的氣溫差異要小(Krueger & Clement,1994)。
對人也一樣。一旦我們把人分成群體——運動員、戲劇專業學生、數學教授——我們就有可能誇大群體內部的相似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S.E. Taylor,1981;Wilder,1978)。僅僅區分出群組,就能造成“外群體同質效應 ”(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即認為他們 都是“相似的”,不同於“我們”和“我們的”群體(Ostrom & Sedikides,1992)。因為我們一般都喜歡那些我們覺得與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歡那些我們認為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所以,內群體偏好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Byrne & Wong,1962;Rokeach & Mezei,1966;Stein & others,1965)。
僅僅是群體決策這一事實,也能使外人高估一個群體的全體一致性。如果保守派憑藉微弱優勢贏得全國的大選,觀察者就會推斷“人們已經轉向保守”。如果自由主義者以類似的微弱優勢獲勝,儘管選舉人的態度基本上沒變,但觀察者會認為整個國傢俱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心態”。斯科特·艾利森及其合作者(1985~1996)注意到,無論決定是按多數人原則做出的還是由指定的群體領導做出的,人們通常會假定該決定反映了整個群體的態度。在1994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以53%的選票(該選舉中大部分成年人沒有投票)控制了國會——產生了被評論員解釋成為的,美國政治上的一場“革命”、一次“山崩地裂”、一次“突變”。甚至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當中,事實上的平局,被某些人解釋成對落選者阿爾·戈爾(Al Gore)的拋棄,而他實際上贏得了更多的選票。
當面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時,我們更容易看到多樣性:
歐洲以外的很多人將瑞士人看成相當同質的人。但對瑞士人來說,瑞士人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講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的群體。
許多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把“拉丁美洲人”混為一談。墨西哥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和波多黎各美國人則能看出重要的差別 (Huddy & Virtanen,1995)。
女生聯誼會成員容易把她們自己的成員看成大雜燴,而認為其他聯誼會的成員則大同小異 (Park & Rothbart,1982)。
一般而言,我們越是熟悉某一社會群體,我們就會看到其越多的多樣性(Brown & Wootton-Millward,1993;Linville & others,1989)。我們越是不熟悉,我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嚴重。同樣,一個群體的規模越小、力量越弱,我們對他們的關注也就越少,我們的刻板印象也就越嚴重(Fiske,1993;Mullen & Hu,1989)。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群體。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他們 ——你自己的種族群體以外的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甚至看起來 都很相似。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令我們尷尬不已的記憶:將另一個種族的兩個人混淆為一個人,結果被我們叫錯名字的人提醒說,“你以為我們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美國學者布里格姆、錢斯、戈爾茨坦和馬爾帕斯,蘇格蘭學者埃利斯通過實驗發現,與我們自己種族的人相比,其他種族的人的確看起來 更為相像(Chance & Goldstein,1981,1996;Ellis,1981;Meissner & Brigham,2001)。他們向白人大學生顯示幾張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後要求他們從一排照片當中挑選出這些曾看過的面孔,結果顯示出具有“同種偏差 ”(own-race bias)。白人大學生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們常常錯誤地選擇一些從沒有看過的黑人面孔。[後續研究還發現存在“同齡偏差 ”(own-age bias):人們能更準確地再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人 (Wright & Stroud,2002)。]
如圖9-6所示,與識別白人面孔的情況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別其他黑人的面孔(Bothwell & others,1989)。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識別幾個小時前見過的其他美籍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別同樣在此之前見過的盎格魯人(Platz & Hosch,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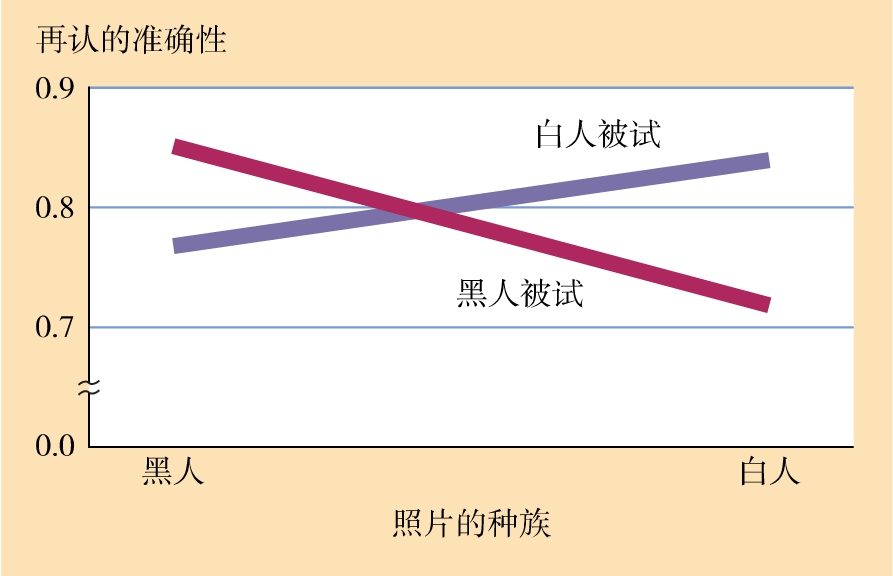
圖9-6 同種偏差
白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
資料來源:P.G. Devine & R.S. Malpass,1985.
實驗室以外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例如,丹尼爾·賴特及其同事(2001)發現,先讓一名黑人研究者或者白人研究者在南非和英國的購物中心接近黑人或者白人,隨後要求這些被試從一隊人中辨認出實驗者,結果表明人們能更好地識別出與他們同一種族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感知其他種族面孔之間的差異。實際上當我們看到另一個種族群體的面孔時,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種族(“這個人是黑人”),而不是個人特徵。當觀看我們自己種族的面孔時,我們相對較少去考慮其種族,而是更多地關注於個人的細節(Levin,2000)。
獨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我們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會導致刻板印象的產生。獨特的人、生動或者極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並歪曲我們的判斷。
獨特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情境:你周圍與你同性別、種族或國籍的人別無他人?如果這樣,那麼你的與眾不同可能會使你更引人注目,成為更惹人關注的目標。一位身處白人群體之中的黑人,一位身處女性群體中的男士,或者是一位身處男性群體之中的女士,都會顯得比較突出、比較有影響力,這個人的優點或缺點都會被誇大(Crocker & McGraw,1984;S. E. Taylor & others,1979)。當群體中的某個人變得顯而易見(顯著)時,我們傾向於認為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這個人引起的(Taylor & Fiske,1978)。假如我們把目光定位在喬身上,那麼儘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群體成員,但喬看上去對群體具有超乎平常的影響力。吸引我們注意的人,似乎對所發生的一切承擔有更大的責任。
你是否注意到,人們也是以你最獨特的特質和行為來描述你。洛麗·納爾遜和戴爾·米勒(Lori Nelson & Dale Miller,1995)報告說,如果某人既是跳傘運動員又是網球運動員,那麼在向人們介紹這個人的時候,他們會想起來這是一名跳傘運動員。當要求為這個人挑選一本禮品書的時候,人們會挑選跳傘書籍而不是網球書籍。一位既養寵物蛇又養寵物狗的人,看上去更像是養蛇而不是養狗的人。人們同樣也關注那些違背期望的人(Bettencourt & others,1997)。“意料之外的智慧更為奪目,就像冬天盛開的花朵,”斯蒂芬·卡特(Carter,1993,p.54)說出了自己作為一名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體會。這種知覺到的獨特性使得來自社會底層但很有才能的求職者更容易脫穎而出,儘管他們也必須努力工作以證實其具有真才實學(Biernat & Kobrynowicz,1997)。
埃倫·蘭格和洛伊絲·英伯(Langer & Imber,1980)非常巧妙地證明了人們如何關注那些與眾不同的人。他們讓哈佛的大學生觀看一位男士閱讀的錄像。當引導大學生認識到這個人非同尋常——癌症患者、同性戀者或百萬富翁時,大學生表現出了更多的關注。他們發現了其他觀察者所忽略的一些特徵,他們對這個人的評價也比較極端。同其他觀眾相比,那些認為自己正在面對一名癌症患者的大學生注意到了對方與眾不同的面部特徵和軀體活動,因此更傾向於認為這個人大大“不同於大多數人”。我們對與眾不同者的極度關注製造了一種錯覺,使得這些人比實際上更顯得與眾不同。如果人們認為你擁有天才般的智商,那他們就會留意到許多你身上那些平常被人忽略不計的事情。
當週圍都是白人的時候,黑人有時能覺察到人們針對他們的獨特之處所做出的反應。許多人說到自己被目不轉睛地盯著或者被人怒目而視,遭遇刺激人的評論,或者受到很差的服務接待(Swim & others,1998)。有時我們會錯誤地認為他人的反應是針對我們的獨特性來的。在達特茅斯學院,羅伯特·克萊克和安傑洛·施特塔(Kleck & Strenta,1980)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們讓女大學生覺得自己變醜了。女生們以為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要評估某些人對她們面部通過誇張的化妝製造出來的疤痕會如何反應。疤痕在右側臉頰,從耳朵一直到嘴。事實上,實驗的目的是要看這些女生在感到自己怪模怪樣之後,會如何看待他人針對自己所做出的行為。化妝之後,實驗者會給每位女生一面小鏡子,讓她們看到臉上逼真的疤痕。女生放下手中的鏡子之後,實驗者就使用一些“保溼霜”,以“避免疤痕出現裂紋。”事實上,“保溼霜”的作用是去除疤痕。
接下去的場景是令人痛苦的。一位年輕女性因為擔心自己按理說已經被醜化的臉龐而自我感覺糟糕透頂,她與另一位女士交談,後者其實根本看不到這種醜態,對此前發生的一切事情一無所知。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也許是某種生理殘疾、粉刺,甚至是某日的髮型很糟糕——那麼也許你就能理解那些女生此時此刻的自我感受了。與那些被告知她們的談話對象只是認為她們有些過敏的女生相比,那些“被醜化”的女生對同伴觀看自己的方式變得十分敏感。她們將談話夥伴評價為比較緊張、冷漠,一幅屈尊俯就的樣子。事實上,事後觀看錄相帶的觀察者分析了談話夥伴是如何對待“被醜化”的人,結果發現並不存在這種對待上的差別。“被醜化”的女性自我感覺變得不一樣了,進而曲解了他人的行為方式和評價,而在其他情形下她們並不會注意到這類誤解。
因此,即使雙方都是善意的,一個強勢的人和一個弱勢的人之間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仍會令人感到緊張(Devine & others,1996)。已知湯姆是個同性戀者,他遇到坦誠直率的比爾。寬容的比爾希望自己的反應不帶任何偏見,但比爾對自己不是很有把握,他略微猶豫了一下。然而,湯姆預期大多數人會持有負面態度,他把比爾的猶豫錯誤地理解為是一種敵意,並且做出了似乎心懷怨恨的迴應。
任何人都能體驗到這種現象。多數派群體成員(如某研究中加拿大馬尼托巴的白人)對少數派成員會如何刻板化地看待他們,往往都心中有數——“元刻板印象”(meta-stereotypes)(Vorauer & others,1998)。即使是相對沒有偏見的加拿大白人、以色列猶太人、美國基督徒,也會感到其他少數派群體刻板地認為他們持有偏見、傲慢或儼然一副屈尊俯就的樣子。如果喬治擔心加默爾把自己視為“有教養的種族主義者”,那麼他在同加默爾交談的時候就會時刻加以提防。
人們的汙名意識 (stigma consciousness)千差萬別。汙名意識就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預期他人會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例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對於其他人怎樣從同性戀的角度來“解釋我的所作所為”上的假定程度是有差異的(Pinel,1999)。把自己看成是流行偏見的受害者,這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Branscombe & others,1999;Dion,1998)。消極的一面在於:那些認為自己屢屢成為受害者的人會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脅、想像中的對立等壓力當中,因此體驗到較低的幸福感。居住在歐洲,具有汙名意識的美國人認為歐洲人比較反感美國人——同那些感覺被接納的美國人相比,在歐洲生活時感覺活得更累。
積極的一面在於:偏見知覺為個體的自尊提供了緩衝。如果某人骯髒不堪,他會說“噢,人們並不是針對我個人。”此外,知覺到的偏見和歧視強化了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讓我們做好準備參與集體性的社會行動。
生動的案例
我們的心靈也利用一些獨特的案例,以此作為判斷群體的一條捷徑。黑人是優秀的運動員嗎?“嗯,看看威廉姆斯姐妹和奧尼爾,是的,我想是這麼回事。”注意這裡所採用的思維過程:針對特定的某一社會群體,給定的經驗非常有限,我們回憶其樣例,並由此概括出結論(Sherman,1996)。不僅如此,遇到負面刻板印象的典型例子時(比如說,遇到一位有敵意的黑人),這種刻板印象就會被啟動,導致我們儘可能地減少與該群體的接觸(Hendersen-King & Nisbett,1996)。
根據個別案例來做出概括會引起一些問題。儘管生動的例子更容易出現在回憶之中,但它們很難代表更大的群體。傑出的運動員雖然鶴立雞群、令人難忘,但據此來判斷整個群體的運動天賦情況著實有些不妥。
來看看1990年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報告,報告表明普通的美國人都大大地高估了美國人口當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人口比例(見圖9-7)。2002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普通的美國人認為21%的男性和22%的女性是同性戀(Robinson,2002),而反覆的調查表明,具有同性性取向的男性約在3%或4%,女性約在1%或2%(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1991;Smith,1998,Tarmann,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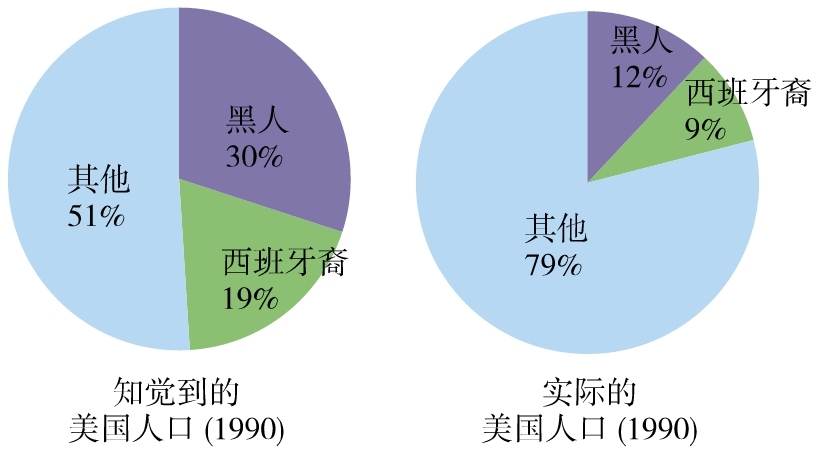
圖9-7
資料來源:1990 Gallup Poll(Gates,1993).
邁倫·羅思巴特及其同事(Rothbart & others,1978)發現,獨特的案例也會強化刻板印象。他們讓俄勒岡大學的學生觀看50張幻燈片,每張幻燈片都描述了一位男士的身高。對其中一組學生來說,50張幻燈片中有10張當中的男士身高略高於6英尺(高度為6英尺4英寸)。對另一組學生來說,這10位男士身高明顯超過6英尺(高度為6英尺11英寸)。隨後詢問這些學生這些男士中身高超過6英尺的人有多少。那些接觸普通身高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的人比實際要多出5%;而那些接觸特別高的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的人比實際要多出50%。在後續的一個實驗中,學生們閱讀有關這50位男士所作所為的描述,其中10人要麼有過諸如偽造文書罪這樣的非暴力犯罪,要麼有過強姦之類的暴力犯罪,那些看過暴力犯罪描述清單的學生,多數會高估犯罪行為的數量。
獨特、極端的案例具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產階層人士會極力誇大他們與低層階級的差異。我們對一個群體瞭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受少數生動樣例的影響(Quattrone & Jones,1980)。人們對“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的刻板印象是她們開著卡迪拉克四處招搖,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生活貧困的人通常與中產階層有著同樣的志向,他們寧願自食其力也不願接受公共救濟(Cook & Curtin,1987)。
獨特事件
刻板印象假定在群體成員身份和個人特徵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意大利人多愁善感”,“猶太人精明能幹”,“會計師吹毛求疵”)。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對非同尋常的事情的格外關注也會產生出一些虛假相關。因為我們對獨特事件比較敏感,所以當這樣的事情有兩件同時發生時就特別引人注意——比非同尋常的事情每一次的單獨發生更加惹人注目。因此,魯珀特·布朗和阿曼達·史密斯(Brown & Smith,1989)發現英國的大學老師會過高地估計他們大學裡女性高級教員的數量(儘管引人注意但相對罕見)。
戴維·漢密爾頓和羅伯特·吉福德(Hamilton & Gifford,1976)在一個經典實驗中證實了虛假相關的存在。他們給大學生呈現上面有許多人的幻燈片,這些人要麼屬於“A組”,要麼屬於“B組”,並且說兩組的成員做了一些好事或者不好的事情。例如,“約翰,A組成員,他探望了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對A組成員的描述比對B組的多一倍,但兩組都是每4件不好的事情就相應有9件好事。因為B組以及不好的事情出現的頻率都相對較低,所以當它們共同出現時——如艾倫,B組成員,他把路邊停放著的小汽車的擋泥板撞癟了,但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就成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組合而吸引住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參加實驗的大學生們就會高估“少數派”群體(B組)行為出現失當的頻率,並且對B組的評價相對比較苛刻。
請記住,B組人做壞事的比率與A組實際上是完全一樣的。而且,這些大學生對B組成員並沒有預先存在的偏好或對立的偏見,同任何日常生活體驗相比,他們在實驗中接受的信息相對而言更加系統。儘管研究者還在爭論這種現象的原因,但他們一致認為確實出現了虛假相關,並且為種族刻板印象的形成提供了又一個來源(Berndsen & others,2002)。
大眾媒體反映並助長了這種現象。當一個自稱是同性戀的人謀殺某人或者對其實施性虐待,人們往往會提到同性戀這一點。如果某位異性戀的人做了同樣的事情,他的性取向卻很少會被提及。同樣道理,當有精神病史的馬克·查普曼和約翰·辛克利(Chapman & Hinckley)分別行刺約翰·列儂和里根總統之後,刺客們的精神病史主導了人們的注意力。刺客和住進精神病院,兩者都是相對少見的,二者結合在一起就特別具有新聞價值。這樣的報道加劇了人們的錯覺,誤以為暴力傾向和同性戀或者住精神病院二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往往有預先存在的種種偏見,這一點與上面對A組和B組進行判斷的大學生很不一樣。戴維·漢密爾頓與特倫斯·羅斯(1980)一同開展的進一步研究顯示,我們預先存在的刻板印象能引導我們“看到”根本不存在的聯繫。研究者讓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學生閱讀一些句子,句子採用了各種形容詞來描述不同職業群體的人士(“道格是一名會計,膽小害羞、細緻周到”)。事實上,在描述每個職業的時候,每個形容詞所採用的頻率是相同的。會計、醫生和推銷員按同樣的頻率被描述為膽小害羞、富有、健談。但是,這些大學生認為 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有關害羞的會計、富有的醫生、健談的銷售員的書面描述。他們的刻板印象讓他們感知到了根本不存在的關聯性,他們的刻板印象也因此而得以保持。正所謂“心想事成”。
歸因: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嗎
在解釋別人的行為時,我們常常犯第3章所說的基本歸因錯誤:我們總是熱衷於將人們的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內在傾向,以至於不大理會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之所以犯這類錯誤,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焦點在人而不是情境。一個人的種族或性別總是非常鮮明並且引人注意的,而作用於這個人的情境力量通常卻不那麼顯而易見。我們常常忽略奴隸制度是奴隸行為的原因之一;代之以奴隸們自身的天性來解釋奴隸行為。就在不久之前,我們在解釋已知的男女差異時,同樣的思路再次重現。由於性別角色的羈絆難以看到,所以我們把男性與女性的行為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天生傾向。人們越是認為人的特質是一成不變的,他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強烈(Levy & others,1998)。
利群偏差
托馬斯·佩蒂格魯(1979,1980)的研究表明了歸因錯誤是如何使得人們在解釋群體成員的行為時出現偏差的。我們總是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成員給予善意的理解:“她之所以捐贈是因為她心腸好;他不捐助是迫於目前的處境。”在解釋其他群體的成員行為時,我們更容易從最壞的角度去設想:“他之所以捐贈是為了博得好感;她不捐贈是因為她很自私。”因此,就像我們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同樣的推搡動作,如果是其他白人所為,那麼白人會認為只是“胡鬧”;一旦是黑人所為,該行為就會變成“暴力行為”。
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相對而言經常被人忽略。它可以被視為只是一個“特例”(“他的確聰明並且努力——完全不像其他人……”),由於運氣或者某種特殊優勢(“她之所以被錄取,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報考的那所醫學院必須完成女生招生名額”),由於情境的要求(“在那種情形下,那個吝嗇的蘇格蘭人除了掏錢照單結賬還能幹什麼?”),或者歸因於額外的努力(“亞洲學生成績之所以比較好,是因為他們太用功了”)。出於不利位置的群體、強調謙虛的群體(諸如中國人),較少表現出這種利群偏差 (group-serving bias)(Fletcher & Ward,1989;Heine & Lehman,1997;Jackson & others,1993)。
利群偏差能非常微妙地影響我們的言語風格。帕多瓦大學一組由安妮·馬斯(Anne Maass)領導的學者(1995,1999)發現,內群體其他成員的積極行為往往被描述成一種普遍品性(例如,“露西樂於助人”)。當同樣的行為是由外群體的成員所為時,人們常常將其描述為一個特定、孤立的行動(“瑪麗亞為那個柱柺杖的男人打開了門”)。當我們描述消極行為時,特點正好相反:“喬推桑了她一下”,對應於“胡安好鬥”。馬斯把這種利群偏差稱為“語言性群體間偏差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指責受害者能起到為指責者本人的優越地位進行辯護的作用(見表9-1)。責備的出現,是因為人們把外群體的失敗歸結於該群體成員的內在品性有問題。邁爾斯·休斯敦(Hewstone,1990)年指出,“他們失敗是因為他們很笨;我們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嘗試。”如果女性、黑人或者猶太人受人虐待,那他們一定是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當英國人在二戰結束之際讓一群德國平民去參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時候,一名德國人的反應是:“這些囚犯一定犯了特別可怕的罪行所以才會受到這樣的懲處。”
表9-1 自我強化的社會同一性如何支持刻板印象
內群體 |
外群體 |
|
態度 |
偏愛 |
詆譭 |
知覺 |
異質性 |
同質性 |
對消極行為的歸因 |
歸於情境 |
歸於內在傾向 |
公正世界現象
在滑鐵盧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經過一系列的研究之後,梅爾文·勒納及其同事(Lerner & Miller,1978;Lerner,1980)發現:僅僅是觀察 到其他無辜者受害,就足以讓受害者顯得不那麼值得尊敬。設想你同其他人一道,參加了勒納的一項被說成是感受情緒線索的研究(Lerner & Simmons,1966)。以抽獎的方式選擇一名參與者承擔一項記憶任務。這個人一旦給出錯誤答案,就要接受痛苦的電擊。你和其他人要注意她的情緒反應。
在觀看了受害者接受這些顯然十分痛苦的電擊之後,實驗者讓你對受害者進行評價。你會怎麼做呢?是深表同情的憐憫嗎?我們可能會這樣期待。就像愛默生所寫的那樣:“烈士是無法玷汙的。”與此相反,實驗結果表明,烈士是可以被玷汙的。當觀察者無力改變受害者的命運時,他們就經常會否定和貶低受害者。羅馬諷刺作家尤維納利斯(Juvenal)早就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羅馬盜賊信奉的是運氣……他們討厭那些被判過刑的人。”
琳達·卡莉和她的同事(Carli & others,1989,1999)指出,這種公正世界現象 (just-world phenomenon)會使我們對強姦受害者的印象蒙上一層色調。卡莉讓人閱讀有關一位男性和一個女性交往的詳細描述。例如,一位女性和她的老闆相約共進晚餐,她來到老闆的家,每人飲了一杯紅酒。有些人閱讀的故事有一個快樂的結局:“他將我引到沙發旁。握著我的手,向我求婚。”憑著事後的聰明,人們不覺得這個結局有什麼大驚小怪,還十分讚賞男女主人公的表現。其他人看到的故事則是另一個不同的結局:“但他隨後變得非常粗暴,把我推向沙發。他把我按倒在沙發上,強姦了我。”如果是這個結局,人們會覺得它在所難免,並且指責那位女士故事前段當中的行為就顯得非常不妥當。
勒納(1980)指出,人們認為“我是一個公正的人,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這種認識的需要導致人們這樣貶低不幸者。他說,從孩提早期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勤奮工作和高尚情操會換來獎賞,而懶惰和不道德則不會有好結果。由此我們很容易跨越一步,進而認定春風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那些受苦受難的人是他們的命中註定。
最經典的例子是基督教《舊約全書》當中有關約伯的故事。約伯是一位好人,卻歷經可怕的厄運。約伯的朋友紛紛猜測,這個世界是公平的,約伯一定是做了什麼缺德的事,引發這樣可怕的苦難。跟約伯的朋友一樣,美國人以超過2:1的差別認同這樣的說法:“大多數一事無成的人不應該責怪這個體制,他們只能怪他們自己”(Morin,1998)。因此,意在矯正以往歧視現象的《反歧視行動法案》之所以遇到一些抵制,不僅僅是偏見的原因,還在於有人認為《反歧視行動法案》違反了公正和公平的規範(Bobocel & other,1998)。
這類研究表明,人們之所以對社會不公漠不關心,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正義,而是因為他們眼裡看不到不公正。那些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認為強姦受害者一定行為輕佻(Borgida & Brekke,1985);遭遇虐待的配偶一定是自己惹火上身才捱打的(Summers & Feldman,1984);窮人註定就過不上好日子(Furnham & Gunter,1984);生病的人應該為他們的疾病負責(Gruman & Sloan,1983)。這些信念使得成功人士確信他們所得到的一切也是命中註定的。富有和健康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好運、別人的厄運,一切猶如天經地義的事情。把好運和美德、厄運和不道德聯繫起來,能使幸運的人在自豪的同時,也不必對不幸的人承擔責任。
人們非常厭惡失敗者,即使失敗者倒黴的原因明顯僅僅是因為運氣不好。人們明白 賭博結果純粹是運氣的好壞,不應該影響他們對賭博者的評價。然而,他們還是忍不住要放馬後炮——根據人們的結果去評價他們。好的決策也可能帶來壞的結果,可人們無視這一事實,他們認定失敗者能力較差(Baron & Hershey,1988)。與此類似,律師和股市投機商可能根據自己的結果來評價自己。成功的時候自鳴得意,失敗的時候自責不已。不能說天才和主動與成功無關,但公正世界假說不重視不可控制的因素,這些因素會使一個人竭盡全力的努力付諸東流。
小結
近期的研究對偏見有了新的視角,這些研究展示了偏見背後的刻板印象怎樣成為我們思維——我們簡化世界的方式——的副產品。首先,將人分門別類的做法,誇大了群體內部的一致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第二,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諸如孤零零的一位少數派人士,具有無法抗拒的特點。這種人會讓我們意識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異。兩個獨特事件的發生——或許是一位少數派人士犯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罪行——幫助建立了人與行為之間的錯誤相關(illusory correlation)。第三,將他人的行為歸結於內在品質,會導致利群偏差:將外群體成員的消極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天生特點,對他們的積極行為則閃爍其詞。指責受害者,還源於一個公認的假設:因為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
偏見的後果是什麼
除了偏見的原因之外,考察偏見的後果也非常重要。刻板印象能自我永存——它們的存在就能阻止它們的變化。刻板印象還能將自身變成現實。儘管最初它們並不是事實,但刻板印象的存在能使它們成為事實。偏見的消極斷言還能在無形之中損害人的行為表現,影響人們對歧視的看法。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見是一種預斷。預斷是在所難免的:我們誰也不是毫無私心雜念的社會事件記錄員,一五一十地記錄贊同或者反對我們各種偏見的事實。我們的預斷能引導我們的注意、解釋以及記憶。
只要群體成員行為舉止符合我們的預期,我們就會重視這一事實;我們先前的看法獲得驗證。當群體成員的行為舉止與我們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就會以特殊情形為由對這類行為閃爍其詞(Crocker & others,1983)。某人的表現與刻板印象截然相反,也會讓這個人看上去像個特例。告訴一些人說“瑪麗打過籃球”,同其他人說“馬克打過籃球”,這會令瑪麗顯得比馬克更加健美(Biernat,2003)。因此,刻板印象會影響我們如何分析人的行為(Kunda & Sherman-Williams,1993;Sanbonmatsu & others,1994;Stangor & McMillan,1992)。
也許你也能回憶起在過去某個時候,你無論怎樣努力都擺脫不了某人對你的評價,當時你無論做什麼,始終被人誤解。一旦某人預期 與你見面不會愉快時,誤解就很有可能會發生(Wilder & Shapiro,1989)。威廉·伊克斯和他的同事(Ickes & others,1982)在一個實驗研究中證明了這一點,他們針對的是幾組正處於大學年齡階段的男士。當這些男士來到實驗室時,兩兩配對為一組,實驗者向每對當中的一人預先給予虛假的告誡:另外那個人是“我近來交談過的人當中最不友好的人之一”。隨後介紹兩個人相互認識,並讓他們單獨相處5分鐘。在實驗的另一條件下,引導這些學生,讓他們以為參與的另一方特別友善。
在兩種條件下,對方對新結識的人都非常友好。事實上,預期對方不 友好的人,異乎尋常地試圖表現出友好,而且他們的微笑及其他友好舉止激起了熱烈的迴應。但與有積極偏差的學生有所不同,這些預期自己會遇到不友好夥伴的人,把這種相互友好歸結於是他們自己“小心翼翼”地對待對方的結果。他們事後表現出對對方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喜歡,並且認為對方的行為不那麼友好。儘管他們搭檔實際上很友好,但消極的偏差誘導這些學生“看見”了隱藏在對方“強顏歡笑”背後的敵意。如果他們不曾這樣想過,他們是看不到這些的。
我們的確會注意到那些與刻板印象明顯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這類信息,它們的影響可能比我們預期的要小。當我們集中關注一個反常的事例時,我們可以分出一個新的範疇來維護已有的刻板印象(Brewer,1988;Hewstone,1994;Kunda & Oleson,1995,1997)。英國學齡兒童對和藹可親的學校警官形成了非常積極的良好印象(他們把學校警官視為特殊的一類),但這絲毫改善不了他們對整個警察的看法(Hewstone & others,1992)。這種再分類法 (subtyping)——把偏常的人歸入一個不同的類群——幫助維持了警察不友善、可怕這樣的刻板印象。認識到刻板印象並非適合一類人當中的每一個人,這是應對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周圍的黑人鄰居和藹可親,房屋主會形成“職業的、中產階級黑人”這樣一個新的不同刻板印象。這種再分群法 (subgrouping)——形成一個子群體的刻板印象——傾向於讓越來越分化的刻板印象做一些適度的變化(Richards & Hewstone,2001)。子類別是群體的例外;子群體則是作為整個群體的一部分而獲得承認。
歧視的影響:自我實現的預言
態度之所以可能與社會階層等級相一致,不僅僅是由於合理化的需要,還因為歧視影響到了它的受害者。“個人聲望”,奧爾波特寫道,“一點一點地被敲打深入大腦,它不可能對一個人的性格絲毫不產生影響”(1958,p.139)。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彈指一揮間結束一切歧視,那我們就會天真地宣稱,“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同胞們!你們現在可以穿上西裝或盛裝,成為體面的管理者或專業人士。”壓迫結束了,但它的影響還將延續,猶如一種社會遺物。
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奧爾波特列舉了15種可能的受害效應。奧爾波特認為這些反應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種涉及責怪自我(退縮、自我痛恨、攻擊自己的群體),一種涉及責怪外部的原因(反擊、懷疑、群體自豪感增強)。如果最終結果是負面的——比如說犯罪率比較高——人們可以藉此為歧視進行辯解,並促使其得以繼續存在,“如果我們允許那些人搬進我們可愛的社區與我們為鄰,房價會一落千丈的。”
歧視是否是以這種方式影響著受害者?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很謹慎,不能誇大這一說法。對許多人來說,黑人文化的靈魂和風格是一筆令人驕傲的遺產,這並不僅僅是受傷害後的反應(Jones,2003)。因此,查爾斯·賈德和他的合作者指出(Judd & others,1995),一方面是白人青年正在學習不去強調種族差異以避免刻板影響,另一方面是非裔美國青年“正日益以他們的種族特性為榮,積極地評價種族差異”。文化差異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缺陷。
然而,社會信念能夠 自行驗證,如同沃德,曾納和庫珀(Word,Zanna,& Cooper,1974)的一對巧妙實驗所展示的那樣。在第一個實驗中,白人和黑人研究助手冒充求職者,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白人男子來進行面試。與求職者為白人的時候相比,當求職者為黑人時,面試官坐得更遠,平均提前25%的時間結束面試,並且多犯50%的言語失誤。想像一下在接受面試的時候,人家遠遠地坐在那裡,說話結結巴巴,急急忙忙就結束了面試。你的表現或你對面試官的感受是否會受到影響?
為找到答案,研究者進行了第二個實驗,經過培訓的面試官對待學生的方式,就像第一個實驗當中面試官對待黑人一樣以同樣的方式對待白人和黑人求職者。稍後對面試錄像進行評定,結果發現,那些受到類似於第一個實驗中黑人的待遇的學生顯得更為緊張、表現更差。而且,面試者自己也可以感到區別;那些被當作黑人對待的學生認為他們的面試官舉止相對不大妥當,不那麼友善。研究人員總結說,“黑人表現方面的‘問題’,部分在於互動情境本身”。如同其他自我實現的預言(回憶第3章的內容)一樣,偏見對其對象產生了影響(Swim & Stangor,1998)。
刻板印象威脅
當你置身於別人都預期你會表現很差的情境當中,你的焦慮可能會致使你證實這一信念。我是一個60歲出頭的矮個子。當我與一群高個、年輕的選手臨時湊合在一起玩籃球比賽時,我常常懷疑他們是否會認為我是隊裡的累贅,這將削弱我的信心,影響我的表現。克勞德·斯蒂爾和他的同事稱這一現象為刻板印象威脅 (stereotype threat)——一種自我驗證的憂慮,擔心有人會依據負面刻板印象來評價自己(Steele,1997;Steele & others,2002)。
在一些實驗中,斯潘塞、斯蒂爾和奎因(Spencer,Steele,& Quinn,1999)給學生一個難度非常高的數學測驗,這些男女大學生具有相同的數學背景。當告訴學生這個測驗沒有 性別差異,不會對任何群體刻板印象作評價時,女生的成績始終與男生相同。一旦告訴學生存在 性別差異,女生就會戲劇性地使得這種刻板印象得以驗證(見圖9-8)。當遇到難度很大的題目而受挫時,她們明顯地感到格外擔憂,這影響到了她們的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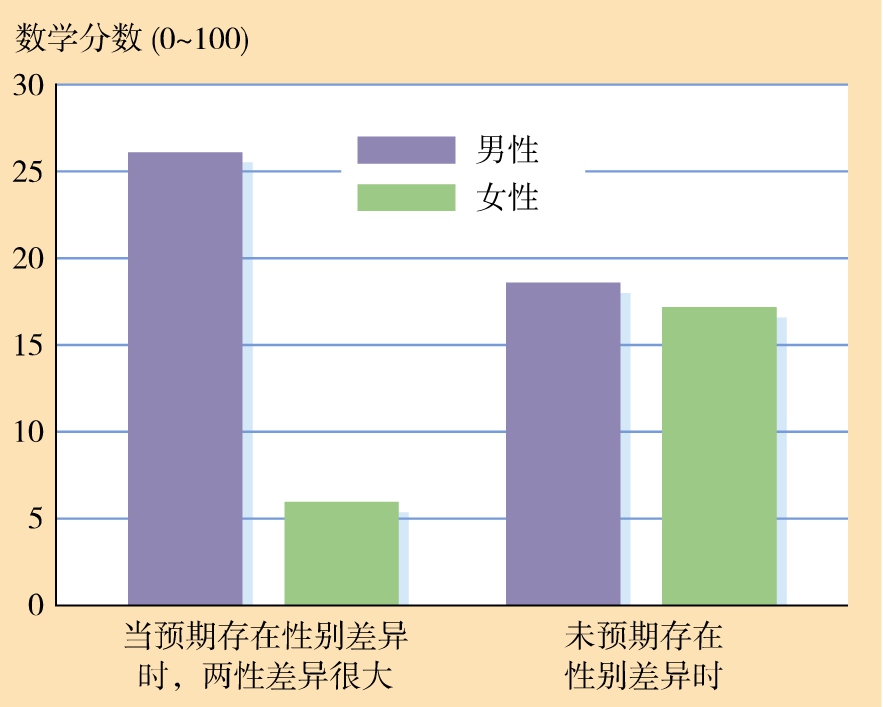
圖9-8 刻板印象弱點與女性的數學成績
史蒂文·斯潘塞,克勞德·斯蒂爾和戴安娜·奎因(1999)讓能力相當的男女被試參與一次難度很大的數學測驗。當引導參與者相信測驗具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得分會低於男性。一旦去除驗證刻板印象的威脅(當不預期會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表現就和男性一樣。
媒體能激起刻板印象威脅。保羅·戴維斯及其同事(Davies & others,2002)讓男性和女性觀看一系列電視廣告,讓他們覺得自己將要參加細節記憶測驗。對其中的一半參與者來說,廣告中只包含中性的刺激;對另一半參與者來說,有些廣告包含“沒頭腦”(air-headed)的女性形象。看過刻板化的形象之後,女性不僅在數學測驗中表現得比男性差,並且對數學及理科專業表現出更少的興趣,或者說不願意進入數學或理科職業生涯。
種族刻板印象是否也可能以類似的方式自我實現?斯蒂爾和阿倫森(Steele & Aronson,1995)的研究確認,當給白人和黑人一些難度較大的語言能力測驗時,情形確是如此。在接受測驗時,黑人只是在受到較高的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形下表現比白人差。傑夫·斯通及其同事(Stone & others,1999)報告說,刻板印象威脅同樣也會影響運動員的成績。當把高爾夫活動表述為“運動智力”測驗時,黑人的表現就比平時要差;當表述為“天生運動能力”測驗時,白人的表現比較差。斯通(2000)推測認為,“當人們想起有關自己的負面刻板印象時,如‘白人男子不擅於跳躍’或者‘黑人男子不擅於思考’,它就會對運動成績產生不良的影響。”
斯蒂爾(1997)認為,如果你告訴學生他們有失敗的危險(猶如少數群體輔助項目經常說的那樣),那麼刻板印象就可能侵蝕他們的行為表現,並且導致他們“不認同”學校,到其他地方去尋求自尊(見圖9-9)。事實上,隨著美國黑人學生從8年級升入10年級,他們的學習成績與自尊之間的相關有所減弱(Osborne,1995)。而且,那些被引導認為自己進入大學或學術群體是受惠於種族或性別偏見的學生,表現傾向於比那些被引導認為自己很能幹的學生差(Brown & others,2000)。因此,斯蒂爾評述說,最好給學生一些挑戰,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潛力。他的研究小組進行了另一項實驗,其中的黑人學生因為他們的寫作而受到批評,同時還告訴他們,“根據我看你的來信,我認為你有能力達到我所說的更高水準,否則我不會自找麻煩給你這樣的反饋”,如此一來,黑人學生會做出較好的迴應(Cohen & others,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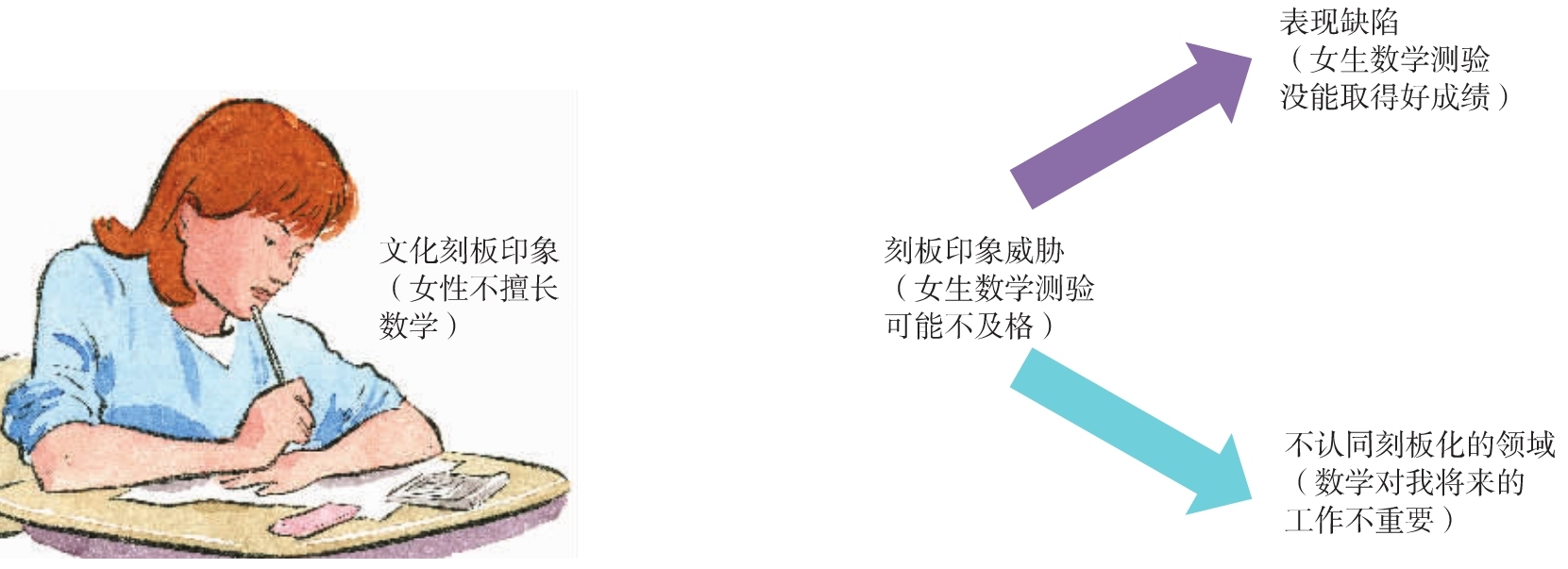
圖9-9 刻板印象威脅
面對負面刻板印象而引起的威脅可能造成表現缺憾以及不認同。
但是,刻板印象威脅是如何破壞表現水平的呢?有一種途徑是認知性的。刻板印象威脅令人心煩意亂:不理會其說法需要付出努力,這會增加心理負擔,降低工作記憶(Croizet & others,2004;Schmader & Johns,2003;Steele & others,2002)。另一個效應是動機性的:在刻板印象威脅下擔心犯錯可能損害一個人的表現(Keller & Dauenheimer,2003;Seibt & Forster,2004),而且生理喚醒伴隨著刻板印象威脅而生,它會妨礙人們在困難測驗中的表現(O'Brien & Crandall,2003;Ben-Zeev,Fein,& Inzlicht,2004)。(回憶第8章的內容,由他人喚起的群體影響;他人在場可能會提高簡單任務的成績,但會干擾困難任務的成績。)
如果刻板印象威脅能干擾成績,那麼正面 刻板印象會提高成績嗎?希、皮廷斯基和安巴蒂(Shih,Pittinsky,& Ambady,1999)證實了這種可能性。在做數學測驗之前,向亞裔美國女性詢問一些個人經歷問題,藉此提醒她們自己的性別身份,她們的成績(相對於控制組而言)陡然下降。當以類似的方式提醒她們的亞洲身份,她們的成績有所提高。負面刻板印象干擾成績,而正面刻板印象似乎能促進成績。
研究背後的故事:
克勞德·斯蒂爾談刻板印象威脅
20世紀80年代後期,在密歇根大學學生多元化委員會會議期間,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各級SAT入學分數水平中,少數群體學生所取得的大學成績總是比非少數群體同伴要低。很快,史蒂文·斯潘塞、喬舒亞·阿倫森和我發現這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它存在於絕大多數的大學裡,存在於其他能力被負面刻板化的群體中,諸如在高級數學課程中的女性。這種成績低下並不是由考試者群體差異造成的,所有各級考試者(按SAT得分)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我們最終在實驗室裡再現了這種成績低下,我們只是鼓勵人們去做一項困難的任務,而他們的群體在這個領域給人以負面的刻板印象。我們還發現,通過讓相同的任務顯得與刻板印象無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去除“刻板印象威脅”,我們能夠消除這種成績低下。第二個發現激發了很多研究:探討如何減少刻板印象威脅及其不好的影響。通過這些工作,我們欣然獲得兩大收穫:首先是生活情境在塑造心理功能上的重要性,其次是像年齡、種族和性別這樣的社會身份在塑造這類生活情境中的重要性。
刻板印象會使個體判斷出現偏差嗎
是的,刻板印象導致判斷出現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人們在評價個體的時候,往往比評價由這些個體構成的群體時更為積極 (Miller & Felicio,1990)。安妮·洛克斯里,尤金·博吉達和南希·布里克(Anne Locksley,Eugene Borgida,& Nancy Brekke)發現,一旦某人認識一個人,那麼“對這個人的判斷中刻板印象的影響即使有也微乎其微”(Borgida & others,1981;Locksley & others,1980,1982)。他們是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大學生身上發現這一結論的。他們給大學生看有關“南希”最近生活事件的秩聞趣事。在一個假定的電話會談記錄中,南希給朋友講述針對三種情境(比如,在購物時受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的騷擾)她是如何做出反應的。有些學生讀到的材料把南希描繪成斷然做出反應(直接叫那衣衫襤褸的傢伙走開);其他人看到的報道是被動的反應(只是不理會他,直到他最終無聊地離去)。還有其他一些學生也接受了同樣的信息,只是人物姓名是“保羅”而不是“南希”。一天之後,學生們預測南希(或保羅)針對其他情境會如何反應。
知道當事人的性別是否會影響這些預測呢?一點也不會。判斷某個人是否過分自信,僅僅受到前一天學生們所瞭解到的當事人行為的影響。甚至有關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判斷,也不受學生是否瞭解當事人的性別的影響。性別刻版印象被束之高閣,學生們把保羅和南希當作單獨的個體進行評價。
這一發現可以用第3章裡討論過的一個重要原理來進行解釋。假定有:(1)有關一個群體的泛泛(基本比率)信息;(2)有關一個群體特定成員的瑣碎但生動的信息,生動的信息通常在效果上要超出泛泛的信息。當這個人與我們有關該群體成員的典型形象不符時,這一效應尤為突出(Fein & Hilton,1992;Lord & others,1991)。例如,設想有人告訴你在一個從眾實驗中大多數 人的實際行為如何,然後讓你觀看一個簡短對話,對話一方為假定的參與過實驗的人。你的反應是否會類似於普通的觀眾呢?一般觀眾都是根據對話來猜測這個人的行為,忽略多數人實際如何行為的基本比率信息。
人們常常相信一些刻板印象,然而一旦接觸到生動的軼聞趣事時,他們又會無視這些刻板印象。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家是騙子”,但“我們的參議員瓊斯是誠實正直的”。(難怪為什麼人們對政治家的評價如此之低,卻常常反覆去選自己的代表)。
這些發現解決了本章前面所關注的一系列研究結果所留下的疑惑。我們瞭解到,性別刻板印象(1)非常突出,但是(2)基本不影響人們針對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評價判斷。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人們可能具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但在評判特定的個體時又會無視這些刻板印象。
強烈的刻板印象並非無關輕重
不過,強烈 而且顯然相關的刻板印象確實能影響我們對個體的判斷(Krueger & Rothbart,1988)。托馬斯·納爾遜,莫妮卡·比爾奈特和梅爾文·馬尼斯(Nelson,Biernat,& Manis,1990)讓大學生估計男女單人照當中每個人的身高,他們總是判定男性個體更高,即使他們的身高是一樣的,即使告訴他們這個樣本性別不能預測身高,即使實驗對預測準確性提供現金獎勵。
在一個後續研究中,納爾遜,阿克和馬尼斯(Nelson,Acker,& Manis,1996)讓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看其他來自該大學的工學院或護理學院的學生的照片,同時給出有關每一位學生的興趣描述。即使告訴他們來自兩個學院的男生和女生數量相同,當呈現的是女生面孔時,同樣的描述更有可能被判斷為來自護理學校。因此,即便已知與眼前的事毫不相干,但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影響力。
刻板印象扭曲認知解釋和記憶
戴維·鄧寧和戴維·舍曼(1997)指出,刻板印象同樣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如果告訴人們,“有人覺得那個政治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就會推斷那個政治家在騙人;如果告訴他們,“有人覺得那個物理學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只是推斷那個物理學家有所失誤。當被告知有兩個人發生了爭吵的時候,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伐木工人,人們會以為發生了鬥毆;但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婚姻顧問,人們會認為發生了口角。同樣是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態,如果是模特,就會顯得很虛榮;但如果是三項全能運動員,則顯得具有健康意識。人們實際上常常會在事後“重新組織”某一事件的錯誤描述,使其符合他們受刻板印象影響所形成的解釋。鄧寧和舍曼總結說,如同監獄對囚犯進行管理和限制,我們刻板印象的“認知監獄”管理和限制著我們的印象。
我們在做判斷或者與某人交往時,有時除了刻板印象外幾乎毫無所獲。在這種情形下,刻版印象能強烈地扭曲我們對人的解釋和記憶。例如,查爾斯·邦德及其同事(1988)發現,在逐漸瞭解病人後,白人精神病護士對黑人和白人病人進行人身限制的頻率是一樣的。但是,白人精神病護士更多地對那些新來的 黑人病人施加人身限制,同樣的白人病人較少受到限制。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形下,刻板印象的影響就會舉足輕重。
這種偏差還能以更微妙的方式起作用。在約翰·達利和佩吉特·格羅斯(Darley & Gross,1983)的一個實驗中,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觀看了一個名為漢娜的四年級女孩的錄像。錄像帶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貧困的市區,父母是社會下層人士;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富裕的郊區環境,父母是職業人士。兩組觀眾都被要求就不同主題猜測漢娜的能力,但他們都拒絕用漢娜的社會階層背景來預先判斷她的能力水平;各組都根據漢娜的年級來評估她的能力水平。另一些學生還觀看了第二部錄像帶,描述漢娜參加在一個口試,她在其中的回答有對有錯。
那些經過事先介紹以為漢娜來自社會上層家庭的學生,判定認為她的回答表現出了較高的能力,並且回憶中記得她多數回答都正確;那些以為自己遇到社會下層家庭子女漢娜的學生,認定她的能力低於她的年級水平,回憶中記得她幾乎答錯了一半題目。但是請注意:對兩組學生來說,第二部錄像帶是完全一樣 的。因此我們看到,當刻板印象足夠強,而關於某人的信息又模稜兩可(不同於南希和保羅的例子)時,刻板印象能微妙 地扭曲我們對個體的判斷。
最後,當人們的行為違背了我們的刻板印象時,我們會對他們做出比較極端的評價(Bettencourt & others,1997)。當一個婦女在電影院排隊時,指責一個在她前面插隊的人(“你該排到最後去!”)會讓她比一位做出類似反應的男士還要顯得強硬(Manis & others,1988)。在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和她同事(Fiske & others,1991)的證詞的幫助下,美國最高法院看到了這類刻板印象所起的作用。在案件中,普華公司(Price Waterhouse),全美頂尖的會計公司之一,拒絕讓安·霍普金斯晉升為合夥人。在88名晉升候選人中,霍普金斯是惟一的女性,她給公司帶來的業務量位居第一。並且在所有客戶眼裡,她是一個勤奮、嚴謹的人。但在其他客戶看來,她需要參加“禮儀學校的培訓課程”,學習“像女人一樣走路,像女人一樣說話,像女人一樣穿著打扮……”。在反思了案情以及刻板印象的有關研究之後,最高法院於1989年做出裁決,認為鼓勵男性而不是女性更加進取,是“基於性別”的行為:
我們開庭並不是要確認霍普金斯夫人是否友善,而是要裁定合夥人對她人格的負面反應是否是因為她是女性……一個老闆反對女性身上表現出來的進取精神,但她的職位又要求這一品質,這讓女性處於難以容忍的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行為積極進取,她們將得不到一份工作;如果不積極進取,她們也得不到一份工作。
小結
偏見和刻板印象會造成非常重要的後果,尤其是當它非常強烈的時候、在判斷不了解的個體的時候、在就整個群體做政策決定的時候。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趨向於自行永久存在,並且拒絕改變。它們還會通過自我實現的預言創造出它們相應的現實。偏見通過刻板印象威脅,讓人擔心其他人會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因而還能妨礙一個人的表現。
個人後記:我們能夠減少偏見嗎
相對於減少偏見而言,社會心理學家在解釋偏見方面做得更為成功。因為偏見源於很多相互關聯的因素,所以沒有簡單的糾正方法。不過,現在我們有望找到一些辦法來減少偏見(隨後一章將做深入的探討):假如不平等的狀態滋生偏見,那麼我們可以謀求建立合作、地位平等的關係。如果偏見常常使得歧視行為合理化,那我們可以通過法律要求非歧視。如果社會制度支持偏見,那麼我們就取消這些支持(例如,說服媒體宣揚種族之間的和睦)。如果外群體看起來比事實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體,那麼我們可以努力將他們的成員個性化。如果自發的偏見致使我們做出一些讓我們羞愧難當的行為,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種羞愧感激勵我們打破偏見。
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系列這類矯正方法一直在得以應用,種族和性別偏見的確減弱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也一直在幫助突破歧視的壁壘。
蘇珊·菲斯克(1999)後來寫道:“代表安·霍普金斯來作證,我們是冒了很多風險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據我們所知,以前沒有人把有關刻板化的社會心理學引入性別歧視的案件中……假如我們獲得成功,我們將讓有關刻板印象的最新研究從滿是灰塵的期刊中走出來,進入法庭辯論的泥潭,在其中發揮可能的作用。假如我們失敗了,我們將傷害我們的委託人,損毀社會心理學的形象,損害我作為一名科學家的聲譽。當時,我對於我們的證詞是否最終能在最高法院取得成功沒有一點把握。
下一個世紀是否能繼續取得進展,或者像人口增加、資源減少的時期容易發生的那樣,對立是否會再次迸發出來成為公開的敵意。對此,我們現在還要拭目以待。
你的觀點是什麼
請描述一件事情,你在其中觀察或者體驗到了種族或性別偏見。這類偏見的根源是什麼?其動機是什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減少這類偏見?
聯繫社會
克勞德·斯蒂爾有關在刻板印象威脅上的工作只是他對社會心理學的諸多貢獻之一。例如,比如在第4章中,我們提到了他在有關“自我肯定”方面的工作。你是否曾經關注過你正在被刻板化?
[1] 本版的第9章是與滑鐵盧大學社會心理學副教授和項目主席史蒂文·斯潘塞合作撰寫的。
第10章 攻擊行為:傷害他人
什麼是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理論
攻擊行為的生物學理論
攻擊行為的挫折—攻擊理論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攻擊行為的影響因素
厭惡事件
喚醒
攻擊線索
媒體影響:色情文學和性暴力
媒體影響:電視
媒體影響:電子遊戲
群體影響
如何減少攻擊
宣洩
社會學習觀點
個人後記:對暴力文化的改革
人際行為是人類社會中最奇怪、最不可預測和最難以解釋的現象。自然界中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恰是人類本身。
——劉易斯·托馬斯(Lewis Thomas,1981)
喜 劇演員伍迪·艾倫曾半開玩笑地預言:“到1990年時,綁架將成為社會交往的主要方式”,雖然這一預言沒有實現,然而這些年來,世界並不太平。9.11恐怖事件可以說是最為嚴重的暴力案件;但從傷亡人數來講,大約與之同時發生的剛果的種族大屠殺事件才算是最為慘重的。據報道,死亡人數約300萬。部分民眾被砍刀活活砍死,其他民眾大多在逃離村莊後死於飢餓和疾病(Sengupta,2003)。在鄰國盧旺達,約75萬人——包括圖西族總人口的一半——在1994年夏天的種族滅絕性屠殺中慘遭殺害(Staub,1999),顯示了人類可以何等殘忍。
2000年以後,這種暴力和毀滅性衝突不再只侷限於中東和非洲地區。全世界,人類每天要花費20億美元在武器和軍隊上——這20億美元本可以為世界上數百萬貧困人口提供足夠的食物、教育資源並進行環保投資。回顧剛剛過去的20世紀,250場戰爭奪走了1.1億人的生命——足夠建立一個人口超過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芬蘭、挪威和瑞典總人口之和的“死亡國度”(圖10-1)。造成世界範圍內大規模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世界大戰外,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5~1923年間,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民族人民進行了瘋狂的屠殺;1971年巴基斯坦對300萬孟加拉國的移民進行了大規模的種族屠殺;150萬柬埔寨民眾死於始自1975年的恐怖時期(Sternberg,2003)。總之,從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斯大林對俄國人民的殺戮,到早期美州移民對當地土著的屠殺,無不揭示了整個人類潛質中異常殘忍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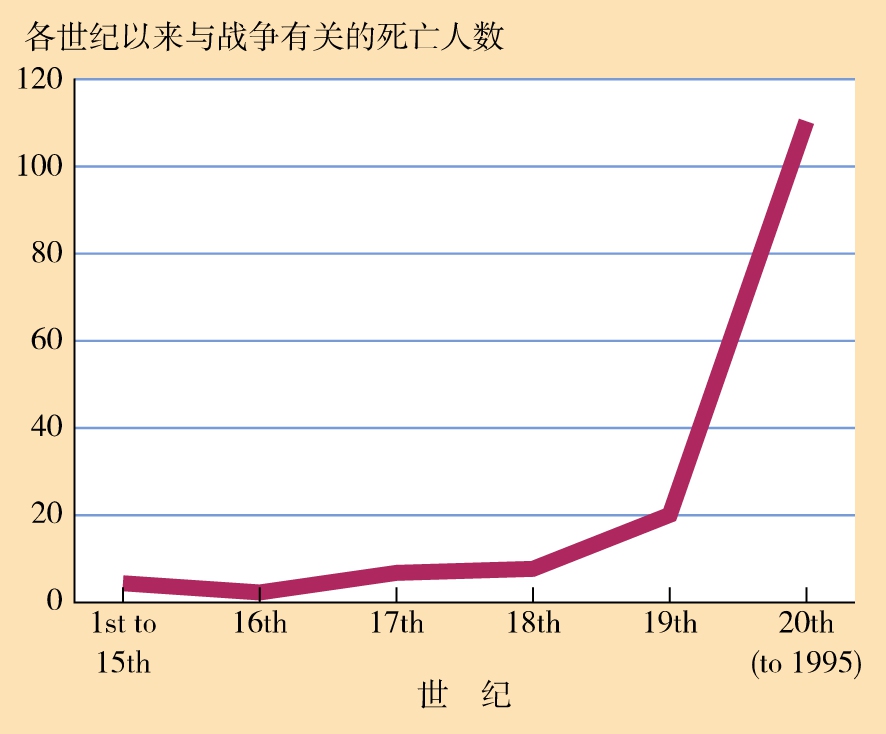
圖10-1 最血腥的世紀
回顧人類歷史,20世紀的人們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同時卻也是最嗜好殘殺的(數據來自Renner,1999)。包括種族屠殺和人為的饑荒在內,有大約1.82億人死於類似的“大規模不幸事件”(White,2000)。
難道說我們像希臘神話中的米諾陶斯(Minotaur)一樣是半人半獸嗎?1941年仲夏的一天,在波蘭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一個小鎮上,非猶太的一半居民對另一半的猶太居民進行瘋狂屠殺,1600名猶太人中只有十幾人倖存(Gross,2001)。如何解釋人類的這種攻擊傾向呢?
攻擊行為取決於先天的生物基礎還是後天習得的?
什麼樣的情境更容易誘發敵對行為呢?
大眾媒體對攻擊行為有影響嗎?
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攻擊行為?
這些就是我們在本章中要討論的問題。
當然,首先我們需要澄清“攻擊行為”這一術語的含義。
什麼是攻擊行為
在印度北部,曾有一個犯罪團伙,這些最早的暴徒在1550到1850年間絞死了200萬以上的人,聲稱這是為一位女神服務,他們無疑是具有攻擊性(aggressive)的。但人們同樣使用“有進取心(aggressive)”來形容一個熱情的售貨員。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為區別於傷害、損毀、破壞性行為,前者稱為敢於自表性(assertiveness),後者稱為攻擊行為(aggression)。
在第5章中我們把攻擊行為 (aggression)定義為意圖傷害他人的身體行為或者言語行為。這一定義排除了車禍,牙科治療和人行道上的碰撞,但包括打耳光,當面侮辱,甚至說風涼話。研究者通常通過讓人們決定傷害他人的程度,如施加多強的電刺激,來度量攻擊行為。
該定義涵蓋了兩種不同的攻擊行為。當動物發怒時,它們在展示典型的社會性 攻擊行為;而當掠食者潛行在獵物之後時,它們表現的是靜息的 攻擊行為。社會性和靜息攻擊行為分屬不同的腦區。對於人類,心理學家把攻擊行為分為“敵意性”和“工具性”兩種。敵意性攻擊行為 (hostile agression)由憤怒引起,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行為 (instrumental aggression)只是把傷害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大多數恐怖活動屬於工具性攻擊。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2003)對1980~2001年間發生的所有自殺性爆炸事件進行研究後指出:“所有自殺性恐怖活動的一個共同特徵是都有明確的、現實的和戰略性的目標——迫使自由的民主國家從恐怖分子眼中屬於他們家園的領土上撤軍。”
謀殺大多是敵意性的。其中約有一半因為意見不合而爆發,其餘的源自戀愛中的三角關係和酒精或致幻毒品導致的爭吵(Ash,1999)。這些謀殺是衝動性的情感爆發,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來自110個國家的數據顯示:更為嚴厲的死刑懲罰並沒有減少殺人案件的發生(Costanzo,1998;Wilkes,1987)。儘管如此,一些謀殺以及由於報復、性脅迫導致的暴力活動卻是工具性的(Felson,2000)。1919年以來,發生在芝加哥的1000多起團伙謀殺中,大部分是冷靜並有計劃的。
攻擊行為的理論
在分析敵意性和工具性攻擊行為的原因時,社會心理學家主要有三種觀點:(1)人類有基於生物本能的攻擊性驅力;(2)攻擊行為是對挫折的自然反應;(3)攻擊行為是習得的。
攻擊行為的生物學理論
哲學家關於人性的爭論由來已久,有人認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慈、知足而高貴的,另一些人則認為人性的本質是殘忍的。第一種觀點以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1712~1778)為代表,把社會罪惡歸咎於社會而非人性。第二種觀點則以英國哲學家霍布斯(Hobbes,1588~1679)為代表,將社會法律視為控制殘忍人性的必要手段。20世紀,“性惡論”,即攻擊性驅力與生俱來、無可避免的觀點得到了弗洛伊德和德國的洛倫茲(Konrad Lorenz)的贊同。
本能論和進化心理學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攻擊行為根源於一種自我破壞的衝動。攻擊行為把這種對死亡原始的強烈欲求所蘊涵的能量轉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稱這種強烈欲求為“死本能”)。作為動物行為專家,洛倫茲認為攻擊行為更多是適應性的而非自我破壞。兩種理論都認為,攻擊性的能量來自本能 (instinctual),是非習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釋放,這種能量就會越積越多,直到爆發為止;或者有一個合適的刺激使之得到發洩,就像老鼠擺脫捕鼠器一樣。雖然洛倫茲(1976)認為我們同樣擁有一個可以抑制攻擊行為的先天機制(如消除我們的防備),但他為人類在不斷武裝自己好戰本能的同時,卻未能增強控制能力而深感擔憂。人們對兩種釋放攻擊性本能的方法關注的失衡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20世紀,死於戰爭的人數多於此前所有戰爭的總和。
為了涵蓋幾乎每一種可以想見的人類行為,假設的本能的清單越來越長。這時,“攻擊是一種本能”的觀點開始瓦解。1924年一項對社會科學著作的調查,列出了近6000種假設的人類本能(Barash,1979)。社會科學家試圖通過“命名 ”來解釋 社會行為,就像玩一個循環論證的遊戲:“為什麼綿羊總呆在一起呢?”“因為它們有群居的天性。”“你怎麼知道它們有群居的天性?”“只要看看它們就好了:它們總呆在一起!”
本能理論也無法解釋攻擊行為在個體和文化之間的多樣性。如果攻擊行為只是一種人類共有的本能,那又如何解釋易洛魁人(Iroquois)在白人入侵者到來之前是如此的愛好和平,而在那之後又是如此充滿敵意呢(Hornstein,1976)?雖然攻擊行為的確有其生物學基礎,但人類的攻擊傾向不能僅僅被限定為一種本能行為。
進化心理學家巴斯和沙克爾福德(Buss & Shackelford,1997)發現,攻擊行為對我們的遠古祖先在特定情況下的確有著適應意義。攻擊行為對於獲得資源、抵抗攻擊、威嚇乃至幹掉情敵、防止配偶的不忠都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在前工業化時代的一些社會裡,一名優秀的戰士可以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繁衍機會(Roach,1998)。巴斯和沙克爾福德相信,攻擊行為的適應性價值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種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更多地出現在男性之間。“這並非因為男人有一種‘攻擊本能’,感覺到一些能量被壓抑著必須釋放。這是男人從他們成功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一種心理機制”,從而幫助他們提高自己的基因在下一代中得到保留的機率。
神經系統的影響
攻擊行為是複雜的,並非簡單地受大腦中某個特定區域控制。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在動物和人類身上發現了一些能夠促進攻擊行為的神經機制。當科學家激活這些腦區時,人們的敵意程度增加了;當這些腦區的活動被抑制,敵意程度下降。通過這樣的方法,溫馴的動物也可以被激怒,同樣可以讓狂怒中的動物恢復順從。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以一隻行為專橫的猴子為研究對象,將電極安置在抑制其攻擊行為的腦區。另一隻小猴子掌握著激活電極的按鈕,它很快就學會了在這隻跋扈的大猴子變得危險時按下按鈕。對腦區的激活機制在人類身上同樣有效:一位婦女在其腦區的杏仁核受到無痛的電刺激後發怒,把她的吉他砸向牆壁,差點砸中她心理治療師的頭(Moyer,1976,1983)。
既然如此,那些有暴力傾向的人是否在大腦某些方面存在異常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阿德里安·雷恩等人(Adrian Raine & others,1998,2000)利用大腦掃描來測量殺人犯的腦活動,並測量了有反社會行為障礙的人的大腦灰質總量。結果發現,未受過虐待的殺人犯的前額葉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會者的前額葉則比正常人小15%,而前額葉被認為是對與攻擊性行為有關的腦區進行緊急抑制的。其他對殺人犯和死囚的研究也證實,腦區異常可能導致異常的攻擊行為(Davidson & others,2000;Lewis,1998;Pincus,2001)。僅僅大腦異常本身就可以導致暴力行為嗎?也許答案並不那麼簡單,但對於一些有暴力傾向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因素(Davidson & others,2000)。
基因的影響
遺傳因素影響神經系統對暴力線索的敏感性。我們早就知道,很多種動物可以被馴養得有很強的攻擊傾向。有時這是為了一些實際目的,如培養鬥雞等;有時,這種馴養只是為了科學研究。芬蘭心理學家Kirsti Lagerspetz(1979)在一組正常白鼠中挑選出攻擊性最強的和攻擊性最弱的分別飼養,在此後它們繁殖的26代中始終重複這一選擇過程,最終她得到了一組凶猛的老鼠和一組溫順的老鼠。
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攻擊性天然有著較大的多樣性(Asher,1987;Olweus,1979)。我們的氣質(即我們的反應性和反應強度)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同時也受交感神經系統反應性的影響(Kagan,1989)。一個人在幼年表現出來的氣質通常是穩定的(Larsen & Diener,1987;Wilson & Matheny,1986)。一個大膽、衝動、容易發脾氣的孩子更有可能發展出青春期暴力行為(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93)。在8歲時沒有表現攻擊性傾向的兒童,成年後到48歲時也不會成為富有攻擊性的人(Huesmann & others,2003)。在分開詢問的條件下,相對異卵雙胞胎來說,同卵雙胞胎更可能在“脾氣很大”或者“經常打架”的問題上給出一致的回答(Rushton & others,1986;Rowe & others,1999)。如果同卵雙胞胎中的一個被判有罪,那另一個雙胞胎有一半的可能也有犯罪記錄,而在異卵雙胞胎中這一比率僅為五分之一(Raine,1993)。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幾百名新西蘭兒童進行了追蹤,結果顯示攻擊行為是由一種能夠改變神經遞質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時期的受虐待經歷共同決定的(Caspi & others,2002;Moffitt & others,2003)。攻擊性和反社會行為並非單純地只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環境的影響;相反,基因會使某些兒童對虐待更敏感,反應更強烈。先天和後天因素是互相影響的。
生物化學因素
血液中的化學成分同樣可以影響神經系統對攻擊性刺激的敏感性。實驗室研究和警方資料都表明,一旦人們被激怒,酒精會使攻擊行為更容易發生(Bushman,1993;Taylor & Chermack,1993;Testa,2002)。有暴力傾向的人比一般人更可能飲酒,在喝醉以後更可能變得具有攻擊性(White & others,1993)。請看以下材料:
在一項實驗研究中,喝醉的人會施加更強的電擊,在回憶人際關係衝突時感覺到更強烈的憤怒(MacDonald & others,2000)。
一項對強姦犯的調查顯示,他們中有略多於一半的人在犯案前喝了酒。在最近一項對171所大學近9萬名學生的調查中,五分之四有過不愉快交往經歷的學生承認在那之前使用了酒精飲料或藥物(Pressley & others,1997)。由此可以推測,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也大多如此。
在65%的殺人案件和55%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攻擊者和(或)受害者喝過酒(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1993)。
如果虐待配偶的酗酒者能夠在治療後終止他們的問題飲酒行為,那他們的暴力行為通常也會停止(Murphy & O'Farrell,1996)。
酒精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覺知和考慮後果的能力,進而增加暴力行為發生的可能(Hull & Bond,1986;Ito & others,1996;Steele & Southwick,1985)。酒精使人們的個性弱化,降低我們的抑制能力。
暴力行為與雄性激素即睪丸激素也有關係。儘管激素的影響對低等動物比對人類要強烈得多,但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藥物的確可以削弱有暴力傾向男性的攻擊性。在聽到尋呼機的嘟嘟響聲時,睪丸激素水平很高的個體報告,他們感覺到了更多的不安與緊張(Dabbs & others,1997)。他們顯得較為衝動、易怒,挫折忍受能力也相對較低(Harris,1999)。
25歲以後,暴力犯罪率與人們的睪丸激素水平均下降。被判為蓄意的或無端的暴力犯罪的罪犯,其睪丸激素水平比非暴力犯罪的罪犯要高(Dabbs,1992;Dabbs & others,1995,1997,2001)。在正常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那些睪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出現不良行為、使用致癮麻醉品以及對挑釁產生攻擊性迴應(Archer,1991;Dabbs & Morris,1990;Olweus & others,1988)。正如詹姆斯·達布斯(Dabbs,2000)所言,睪丸激素“分子雖小,但作用巨大”。給男性注射睪丸激素並不能直接使人變得富於攻擊性,雖然睪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擊性行為(Geen,1998)。睪丸激素大致可比作電池的電力,只有電力水平很低時,暴力犯罪才會有明顯下降。[為了擺脫自身持久存在的破壞性衝動,也為了縮短他們的刑期,一些因性暴力而入獄的罪犯主動請求對他們施行閹割。相比女性子宮切除,這種手術對人體的侵入性危害較小。應否同意他們的要求呢?如果這一要求得到滿足,並且此後他們被認為不再有實施性暴力的危險,他們的刑期是否應該被縮短甚至取消呢 ?]
暴力行為另一個常見的元凶是神經遞質5-羥色胺的缺乏,在控制衝動的額葉區有其許多接受器。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有暴力傾向的幼兒和成人5-羥色胺水平均偏低(Bernhardt,1997;Mehlman,1994;Wright,1995)。此外,在實驗室條件下降低人們的5-羥色胺水平,可以增強他們對厭惡事件的反應和釋放電刺激的意願。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睪丸激素、5-羥色胺和行為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比如,睪丸激素可以促進支配欲和攻擊行為的產生,但同時支配或取勝的行為也會提高睪丸激素的水平(Mazur & Booth,1998)。在勁敵之間進行的一場世界盃足球賽或者重大籃球比賽之後,勝利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顯著上升,而失敗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則下降了(Bernhardt & others,1998)。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人5-羥色胺水平往往也比較低。進化心理學家認為,這也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這種狀態使他們敢於承擔風險去增進他們的利益和地位(Wright,1995)。
綜上所述,神經系統、基因、生物化學因素對某些人在面對衝突、挑釁時會不會做出攻擊行為都有重要的影響。但攻擊性是否真的如此多地源自人類本性,乃至使世界和平的願望無法實現呢?美國心理協會(APA)和國際心理學家理事會(ICP)已經聯合其他組織簽署了一份由來自12個國家的科學家起草的有關暴力行為的聲明(Adams,1991):“在科學上,(聲稱)戰爭與其他暴力行為是世代相傳的人類天性(或者)戰爭是由‘本能’或者某個單一動機引發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正如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方法減少人類的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挫折—攻擊理論
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在兩個小時的認真學習之後,你覺得又累又渴,於是你向朋友借了一些零錢,走向最近的一個自動售貨機。你把錢放入機器裡,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一口冰涼爽口的可樂。但是,當你按下提貨的按鈕時,售貨機卻完全沒有反應。你又按了一次,然後按下了把錢退回的按鈕,機器仍然毫無動靜。你用力地敲打著按鈕,然後用拳頭捶它們。最後你晃動、敲打售貨機。可一切仍然無濟於事。你跺著腳回到自己的房間,兩手空空。此時,你的室友是不是該很小心地對待你呢?那時的你是否更容易說出一些傷人的話語,甚至做出一些傷害性的事情呢?
作為最早對攻擊行為進行解釋的心理學理論之一,流行的挫折—攻擊理論 (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對此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約翰·多拉德和他的同事認為(Dollard & others,1939,p.1),“挫折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攻擊行為。”這裡的挫折 (frustration)指的是,任何阻礙我們實現目標的事物(比如那個出現故障的自動售貨機)。當我們達到一個目標的動機非常強烈,當我們預期得到滿意的結果,卻在行動過程中遇到障礙時,挫折便產生了。魯珀特·布朗和他的同事(Brown & others,2001)對乘渡船去法國的英國乘客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當法國的漁船堵塞碼頭,擋住渡船前行時,他們的攻擊性顯著增強了。由於達成目標的願望受阻,在看了一些圖片後,乘客們愈加同意打翻咖啡杯的法國人應受到斥責,對威脅到當地鄉村麵包師生計的法國糕點應予抵制。
如圖10-2所示,攻擊的能量並非直接朝挫折源釋放。我們學會剋制直接的報復,特別當別人會對這種行為表示反對或者進行懲罰時;相反,我們會把我們的敵意轉移 到一些安全的目標上。一則古老的故事為轉移 (displacement)做了很好的詮釋:一個被老闆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後大聲斥責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兒子咆哮,兒子只能踢狗解氣,而狗則把來送信的郵遞員咬了一口。在實驗情境和現實生活中,當新的目標與挫折源有相似之處,並且稍稍刺激了攻擊能量的釋放時,攻擊的轉移最容易發生(Marcus-Newhall & others,2000;Miller & others,2003;Pedersen & others,2000)。相信大多數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當一個人滿懷著怒火時,哪怕是平時根本不予理會的輕微冒犯也可能引發一個爆炸性的過度迴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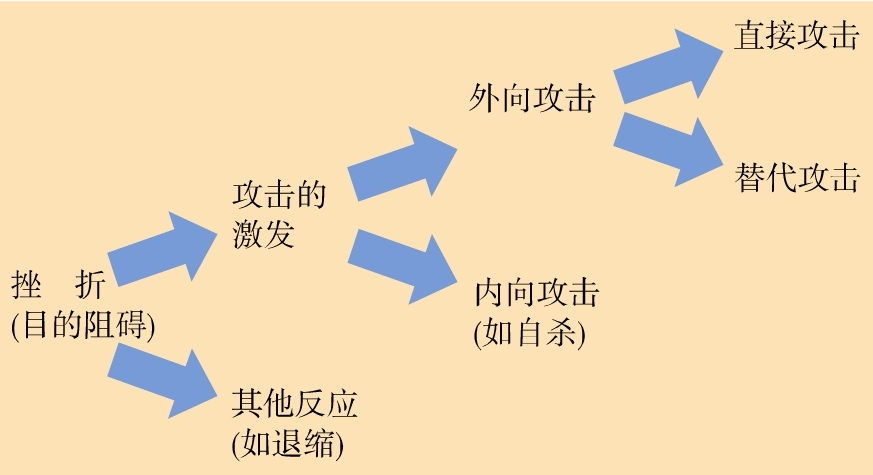
圖10-2 經典挫折—攻擊理論
挫折產生攻擊的動機。由於對反對和懲罰的畏懼,人們往往不直接對挫折源進行攻擊,因此攻擊驅力可能會被轉移,指向其他目標,甚至轉而指向自己。
資料來源:Based on Dollard & others,1939,and Miller,1941.
許多評論認為,可以理解,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強烈憤怒,促成了其對伊拉克發動襲擊。美國人此時需要尋找宣洩憤怒的對象,於是把矛頭指向了罪惡的暴君——薩達姆·侯賽因,他們昔日的盟友。2003年,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指出:“發動這次戰爭的真正原因在於:9.11事件後,美國需要對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進行打擊。而之所以選擇薩達姆,原因很簡單:他罪有應得,而且他正處於這一世界的中心部位。”戰爭的另外一位發動者,副總統理查德·切尼(2003)似乎同意這一觀點。他在被問及為什麼大多數國家都反對美國發動戰爭時指出:“因為他們沒有經歷9.11事件。”
修正後的挫折—攻擊理論
對挫折—攻擊理論的實驗檢驗得到了不盡一致的結果:有些情況下挫折增加了被試的攻擊性,另一些卻並沒有。如果這種挫折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一項實驗中,如果一名成員是因為他的助聽器發生故障而不是粗心大意阻礙了團體的問題解決時,那麼它只會導致憤怒,而不是攻擊行為(Bernstein & Worchel,1962)。
伯科威茨(Berkowitz,1978,1989)認為原有的理論誇大了挫折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伯科威茨認為挫折產生的是憤怒 ,攻擊行為的一種情緒準備狀態。憤怒起源於某個有其他行為選擇可能的人阻撓了我們實現目標(Averill,1983;Weiner,1981)。一旦有攻擊線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別容易大發雷霆,把憤怒“倒個底兒朝天”(圖10-3)。有時瓶塞也可能在沒有這樣線索的情況下被打開。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與攻擊行為有關的線索會放大這種攻擊行為(Carlson & others,1990)。[請注意:挫折—攻擊理論是用來解釋敵意性攻擊而非手段性攻擊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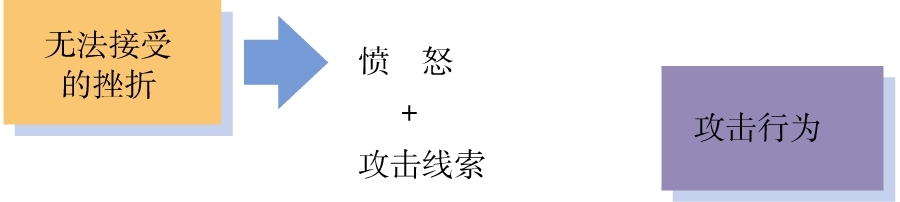
圖10-3 經倫納德·伯科威茨修正的挫折—攻擊理論簡圖
挫折是否與剝奪相同
請描繪一下一個極端受挫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不論是經濟方面、性方面還是政治方面的挫敗。
憑直覺,我猜你在想像的一定是一個在經濟方面、性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被剝奪 的人,並且自認為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一旦社會失業率上升,暴力犯罪率也隨之上升(Catalano & others,1997)。當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失業人數大幅下降時,暴力犯罪也顯著減少了。21世紀初,失業率再次上升,暴力犯罪亦然。
但是,我們所說的挫折可能和這種剝奪並沒有關係。在性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獨身的人;在經濟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那些生活在牙買加臨時陋屋裡的貧困者。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經濟破產的人,但暴力犯罪率並沒有因此顯著上升。如暴力成因與預防國家調查組1969年總結的那樣,經濟上的進步甚至可能增加挫折的發生,使暴力犯罪逐步上升。同樣地,巴勒斯坦的“人體炸彈”也並不是巴勒斯坦最貧困的人。如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意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Bader-Meinhof團伙,大都是中產階級(Krueger & Maleckova,2003;Pettigrew,2003)。9.11恐怖襲擊者也是如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且遊歷過世界各地。集體的羞恥感與敵意催生了恐怖主義,而遠非單純的剝奪。讓我們來探一究竟。
1967年的一天,密歇根州長向媒體吹噓:該州在公民權立法上在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在過去的5年時間裡,3.67億美元的聯邦救助被投放到底特律。這些話剛剛在電臺廣播完,底特律一個大型黑人居住區就爆發了美國20世紀最嚴重的城市暴亂,43人死亡,683處建築被焚燬。
人們驚呆了:為什麼暴亂會發生在底特律?雖然相對於當地白人的富裕生活,黑人居住區仍然較為貧困落後,但在其他一些地方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要嚴重得多。為回答此類問題而建立的民事動亂國家顧問委員會得出這樣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公民權立法和司法的成就提高了人們對生活狀況的期望,而當預期與現實存在差距時,挫折感便產生了,這是暴亂髮生的一個直接的心理原因。當底特律等地市民的預期發生“革命性上升”時,挫折感就可能漸漸積累,即使真實的生活狀況正在得到改善。
這一原則普遍適用。伊沃和羅莎琳·費厄瑞本德(Ivo & Rosaline Feierabend,1968,1972)組成的政治科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小組應用挫折—攻擊理論來研究84個國家政治的不穩定性。在高速現代化的國家裡,隨著城市化程度和人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他們對物質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來越敏感。但富裕群體通常只能較慢地擴展。因此,人們的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使得他們的挫折感變得更為強烈。一旦人們的期望超過了現實生活,即使我們完全消除剝奪現象,挫折和政治攻擊行為也依然會逐步增加。
並不是說,剝奪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無關;關鍵在於,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產生挫折感 。當你的所得滿足了你的期望,你的需求是你的收入水平可以實現的,這時你會感到滿足,而不會是挫折感(Solberg & others,2002)。
相對剝奪
當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我們的挫折感就會變得較為複雜。工人的幸福感取決於和同一條工作線上其他人相比他們獲得的報酬是否公平(Yuchtman,1976)。提高城市警察的工資水平雖然可以暫時提高他們的士氣,卻可能同時降低該市消防員的士氣。
這種感覺稱為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它可以預測少數人群體在感覺到不平等待遇時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Kawakami & Dion,1993,1995)。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貧富差距大的國家和社會裡,人們的幸福感較低而犯罪率較高(Hagerty,2000;Kawachi & others,1999)。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東德人民反抗他們的政權的原因: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要高於一些西歐國家,但卻低於他們的西德同胞,從而使他們有挫折感(Baron & others,1992)。
“相對剝奪 ”這一術語是學者在研究美國二戰士兵滿意度時首先使用的(Merton & Kitt,1950;Stouffer & others,1949)。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空軍士兵對於自己獲得晉升的機會比軍警有著更 強烈的挫折感,而事實上軍警的晉升要比空軍士兵緩慢而不可預期得多。空軍的晉升是很快的,而大多數的空軍人員可能都覺得自己比一般的空軍成員更為出色(自我服務偏見),因此他們所期望的要比實際獲得的更多。結果,當然就是挫折感啦。
今天,電視節目和廣告中所描繪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一個可能的來源。在電視普及的社會裡,它把絕對剝奪(缺乏別人擁有的東西)的感覺轉化為相對剝奪(被剝奪感)。卡倫·亨尼根和她的同事(Hennigan & others,1982)考察了電視在美國城市中推廣的時期內犯罪率的變化。在被考察的34個城市中,電視從1951年開始普及,而當年的盜竊犯罪率(如在商店中行竊、偷自行車等)出現了跳躍性的上升。在另外34個由於政府控制而使電視的普及被延遲到1955年的城市裡,一個相似的盜竊犯罪率的飛昇也出現了,而時間正是在1955年。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基於本能和挫折的攻擊行為理論認為:充滿敵意的強烈衝動來自內在的情緒,這些情緒可以把體內的攻擊慾望“釋放”出來。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學習同樣可以“引導”出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回報
通過親身經歷和對別人的觀察,我們學習到攻擊行為通常需要付出什麼。實驗可以把溫馴的動物改造成凶殘的好戰者,嚴重的挫敗則可以導致順從(Ginsburg & Allee,1942;Kahn,1951;Scott & Marston,1953)。
同樣,人類也可以習得攻擊行為的回報。兒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脅迫了其他兒童,他很可能會越來越富於攻擊性(Patterson & others,1967)。那些最常因為比賽中的粗野動作而被處罰的強攻擊性曲棍球手比攻擊性不太強的運動員得分更多(McCarthy & Kelly,1978a,1978b)。在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手中,那些父親贊同身體攻擊性動作的選手顯示了最富攻擊性的比賽態度和方式(Ennis & Zanna,1991)。在這些例子裡,攻擊行為是為了得到特定回報而採取的手段。
集體暴力也有類似的效果。在1967年底特律暴亂後,福特汽車公司加大了僱用少數民族工人的力度。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裡(Dick Gregory)為此開玩笑說:“去年夏天的大火燒得離福特的工廠太近了。寶貝,別把小野馬(the Mustangs)烤焦了。”
恐怖主義活動同樣如此:它們可以使無職無權的人得到廣泛的關注。如中國古語所說:“殺一儆百”。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殺幾個人就可以恐嚇住上億人口。傑弗裡·魯賓(Jeffrey Rubin,1986)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謂“公開性的氧氣”(oxygen of publicity),恐怖主義必然會被消滅。這就好像20世紀70年代經常發生的觀眾為了在電視上能有幾秒鐘的上鏡時間而裸體飛奔入足球場的事件一樣,一旦社會決定不再理睬這樣的事情,這一現象也就消失了。
觀察學習
班杜拉(Bandura,1997)提出了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他認為,人們對攻擊行為的學習不僅發生在親身體驗其後果時;通過觀察別人,人們也可以進行同樣的學習。像很多社會行為一樣,當看到別人表現攻擊行為並沒有受到懲罰時,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
班杜拉曾做過這樣一項實驗(Bandura & others,1961):實驗者讓斯坦福幼兒園的一個小朋友做一項有趣的繪畫活動,同時一個成年人在房裡的另一個角落,那裡有組合玩具——萬能工匠、一個錘子和一個充氣娃娃。在玩了一分鐘萬能工匠之後,成年人站起身,對充氣娃娃進行了持續10分鐘的攻擊。她用錘子重重地砸它,踢它,把它扔來扔去,一邊還大叫著:“揍他的鼻子……把他打翻……踢死他……”
目睹了這次突然爆發之後,小朋友被帶到另一個屋子,裡面有很多漂亮可愛的玩具。但在兩分鐘之後,實驗者打斷了小朋友,說這些是她最好的玩具,她必須“把它們留給別的小朋友”。受到挫折的小朋友現在到了另一個房間,裡面有各種玩具,有的可用於攻擊,另一些則不能,其中包括充氣娃娃和錘子。
如果小朋友沒有看到成年人富於攻擊性的示範,他們很少表現出攻擊性的言語和行動。雖然有挫折感,他們仍然很平靜地玩著。但那些觀察到成年人攻擊行為的小朋友則很可能拿起錘子擊打玩具娃娃,這一現象的發生概率要比沒看過的小朋友高出許多倍。對成人攻擊行為的觀察降低了他們對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複示範者的動作和話語。所以觀察攻擊性行為不僅降低了孩子對自我的控制,還教給了他們怎樣去攻擊。
班杜拉(1979)認為,日常生活中,我們受到來自家庭、文化和大眾媒體的攻擊性榜樣的影響。
家庭 身體富於攻擊性的兒童往往有慣用體罰的父母。父母用尖聲訓斥和拳打腳踢管教他們,從而塑造了他們的攻擊性行為(Patterson & others,1982)。這些家長通常也受過來自他們父母的體罰(Bandura & Walters,1959;Straus & Gelles,1980)。雖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後並不一定變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確實對自己的孩子實施了類似的虐待,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Kaufman & Zigler,1987;Widom,1989)。在家庭裡,暴力的結果往往是新的暴力。
家庭的影響還表現在社會中較高的暴力犯罪率與缺少父親的家庭的關係(Triandis,1994)。美國司法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佔了青少年拘留案件中的70%(Beck & others,1988)。利用這些數據,戴維·萊肯(Lykken,2000)經過分析發現:相比其他孩子,成長過程中父親不在身邊的孩子被虐待、輟學、離家出走、成為未婚少年父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要高出7倍。雙親家庭的好處在於,不僅能夠得到父親更多的關懷和正面教導,還意味著貧困可能性的降低和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更不會無家可歸。父母的缺失(通常是缺少父親)和暴力之間的相關不因種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地區的不同而改變(Staub,1996;Zill,1988)。英國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追蹤了1萬名兒童從出生到33歲的成長曆程,發現在父母關係破裂之後,兒童發生問題的危險也隨之增加(Cherlin & others,1998)。
這種關係還表現在時代的變遷中。1960年,只有略多於1/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因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只有16000人。到了2000年,有3/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雖然青少年總數與1960年基本相當,卻有10萬人因暴力犯罪被捕。並不是說在缺少父親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兒童就會去違法或者有暴力傾向(如果有母親或者大家庭的精心呵護,這類兒童都可以健康成長),也不是說缺少父親是惟一可信的解釋。關鍵在於,無論何時何地,若缺少父親,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確實增加了。看來,家庭情況確實是有影響的。
文化 家庭之外的社會環境也給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在崇尚“男子漢氣概”的社會裡,攻擊行為可以很容易地傳遞給下一代(Cartwright,1975;Short,1969)。青少年團夥的暴力的亞文化為新成員提供了攻擊行為的榜樣。
更廣義的文化也有影響,來自經濟不發達、貧富嚴重不均、尚武且參與過戰爭的非民主文化的人,會傾向於支持和參與攻擊行為(Bond,2003)。尼斯比特和科恩(Nisbett,1990,1993;Dov Cohen,1996,1998)補充道,來自崇尚榮譽的文化的人,也會有攻擊性的心理傾向。據他們報告,在美國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居住在新英格蘭、東海岸中部地區的民族冷靜而注重合作,而定居在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民族(他們大多是蘇格蘭、愛爾蘭後裔)則崇尚武力和個人榮譽。前者多是農場主和手工工匠,後者則是富於攻擊性的獵人和牧人。因此到目前為止,在南方人居住的地區中,白人的殺人案發率要比北方人定居的地區高。例如,得克薩斯州狹長地帶(移民者來自上南部地區)白人的殺人率是內布拉斯加州(移民者來自東部、中西部和歐洲)的4倍。相比內布拉斯加州貧困程度更高的城鎮,得克薩斯州貧困率較低的城鎮殺人案發率卻更高。
南方人並不提倡在任何情況下都使用武力,但捍衛自己的財產與尊嚴、懲戒惡行的暴力行為則是受到推崇的(Nisbett & Cohen,1996)。只有18%的白種非南方人同意“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我們有權殺人”,而36%的南方白人都這樣認為。南方白人的持槍率是中西部鄉村的白人的兩倍;南方人還更傾向於支持戰爭和打屁股的懲罰方式(塑造社會關係中的暴力行為方式)。
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攻擊性的榜樣,都可以習得攻擊性的反應方式。但什麼情況下會真的出現這種反應呢?班杜拉(Bandura,1979)認為,攻擊行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體驗激發的(圖10-4),這些體驗在情緒上把我們喚醒。但我們是否真的選擇攻擊性行為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當攻擊行為看上去比較安全甚至會帶來好處時,我們在被喚醒之後就很可能會那麼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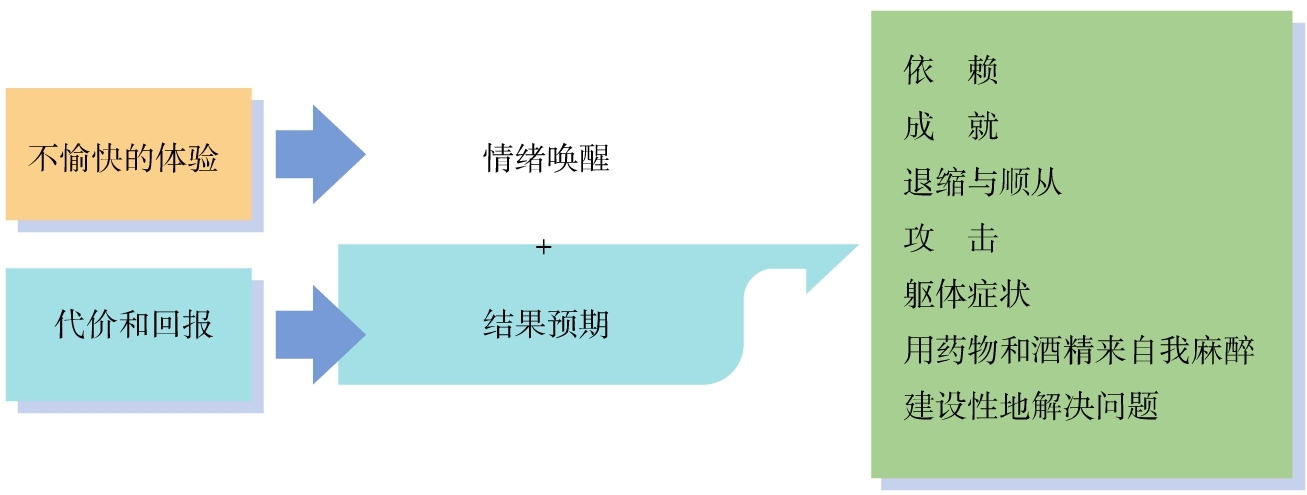
圖10-4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由不愉快體驗產生的情緒喚醒激發攻擊行為。但我們是真的發起攻擊行為,還是做出其他的迴應,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這是通過學習獲得的。
資料來源:Based on Bandura,1979,1997.
小結
攻擊行為有兩種形式:敵意性攻擊,由憤怒等情緒引起並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關於攻擊行為有三種主要理論。與弗洛伊德和洛倫茲關係密切的本能觀點認為攻擊性的能量會在體內不斷積累,就像水在大壩後積聚一樣。雖然這種觀點很少有直接證據的支持,但攻擊行為確實受到遺傳、血液化學成分和大腦等生物學因素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是挫折產生了憤怒和敵意,如果存在攻擊性的線索,這種憤怒就可能激起攻擊行為。挫折感不僅來自剝奪本身,還來自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我們的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別人的成功,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的好處。社會學習使家庭、亞文化和大眾媒體都能對攻擊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攻擊行為的影響因素
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攻擊他人?誘發因素包括厭惡事件、喚醒、媒體和群體氛圍。
厭惡事件
能誘發攻擊行為的事件通常不僅包括挫折,還有一些令人厭惡的體驗:疼痛、令人不適的炎熱,受攻擊、過度擁擠等。
疼痛
內森·阿茲林(Nathan Azrin)曾經試圖研究,切斷足部電擊,是否可以強化兩隻老鼠間積極的關係。他計劃先對老鼠進行電擊,一旦兩隻老鼠互相接近,就把帶來疼痛的電流切斷。但讓他十分吃驚的是,這個實驗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一旦老鼠感覺到疼痛,馬上就開始互相攻擊,實驗者根本來不及把電流切斷。電擊(和疼痛)越強烈,攻擊就越猛烈。
是否只有老鼠才這樣呢?研究者發現,對於很多種動物,遭受的待遇越殘酷,它們對同伴施加的行為也就越殘忍。如阿茲林(1967)所述,這種疼痛—攻擊反應
在多種不同品種的老鼠身上都會發生。然後我們發現,當以下任何一種動物被關在同一個籠子裡時,電擊都會產生攻擊行為:某些品種的老鼠,倉鼠,負鼠,浣熊,狨猴,狐狸,海狸鼠,貓,海龜,猴子,白鼬,紅松鼠,矮腳雞,公雞,短吻鱷,小龍蝦,兩棲鯢類,幾種蛇,包括大蟒蛇、響尾蛇、褐鼠蛇、棉口蛇、銅斑蛇和黑蛇。很顯然,電擊—攻擊反應在多種生物中普遍存在。所有這些動物在電擊下做出的攻擊反應都迅速而穩定,和老鼠一樣,彷彿是由“按鈕操控”的。
這些動物不會挑剔攻擊目標,不論同類還是異類的動物,甚至是充氣娃娃和網球,它們都會發動攻擊。
研究者還考察了其他形式的疼痛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結果發現:不光電擊會引發攻擊,強烈的炎熱和“心理疼痛”——比如,一隻飢餓的鴿子在訓練過程中,只要啄一個圓盤就可以得到食物作為獎賞,這次卻突然沒有獲得食物——都可以帶來相同的反應。當然,這裡的“心理疼痛”就是我們所說的挫折。[現在的倫理準則限制了研究者對可以帶來疼痛的刺激的使用 。]
疼痛同樣會提高人類的攻擊性。大概我們每個人在頭痛或者絆了腳之後,都曾有過那樣的反應。伯克威茨和他的同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以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為被試,讓他們把手放在一杯微熱的水,或者一杯冰涼刺骨的水中。結果,對旁邊一個不斷髮出討厭聲音的傢伙,那些將手放在冰水中的被試更為急躁和煩惱,並且更傾向於對此人表示強烈的不滿。基於這些結果,伯科威茨(Berkowitz,1983,1989,1998)認為,厭惡事件而非挫折才是敵意性攻擊行為最基本的誘發因素,雖然挫折確實是一類重要的不愉快事件。事實上任何形式的厭惡事件,比如希望破滅、人身侮辱、軀體疼痛等,都可以激起情緒爆發,甚至沮喪狀態造成的折磨也會增加敵意性攻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炎熱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認為氣候對人類行為有著影響。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337)把當時文明的希臘人和現屬德國、瑞士的地區未開化的野蠻人進行比較,他認為造成他們之間顯著差異的原因是北歐嚴酷的氣候。後來,英國人把他們“優越”的文化歸功於英格蘭 理想的氣候,法國思想家對他們的法國也有著同樣的看法。但一個地區的氣候總是穩定的,而文明的特性卻會發生改變,因此文明的氣候理論在有效性上顯然有其侷限性。
儘管如此,短時的天氣變化還是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令人厭惡的氣味、香菸味、空氣汙染都與攻擊性行為有著某種聯繫(Rotton & Frey,1985),但得到最廣泛研究的環境誘發因素還是炎熱。威廉·格里菲特(William Griffitt,1970;Griffitt & Veitch,1971)研究發現,相比那些在室溫條件下回答問卷的被試,在炎熱的房間裡(高於90°F)完成任務的被試感覺更為疲憊,更富攻擊性,對陌生人表現出更強的敵意。隨後的實驗發現炎熱還可以引發報復行為(Bell,1980;Rule & others,1987)。
實驗室條件下如此,真實世界裡令人不快的炎熱是否也會增加人們的攻擊行為呢?請看以下的材料:
當熱浪侵襲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時,那些汽車裡沒有空調的司機更可能對堵住路口的車大按喇叭(Kenrick & MacFarlane,1986)。
在全美棒球聯賽1986~1988的幾個賽季中,當比賽在華氏90多度的氣溫下進行時,擊球手被球擊中的事件比在華氏80度以下進行的比賽多出三分之二(Reifman & others,1991)。在炎熱的天氣裡,投手不會為如何投球而迷惑猶豫。他們不再走來走去,猶豫著該投什麼樣的球。他們投出的球也更多重重地打在擊球手身上。
1967~1971年發生在79個美國城市的暴動更多地發生在炎熱的日子裡。
在6個城市進行的研究都表明,天氣炎熱時更易出現暴力犯罪(Anderson & Anderson,1984;Cohn,1993;Cotton,1981,1986;Harris & Stadler,1988;Rotton & Frey,1985)。
在整個北半球,不僅酷熱的日子會發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在一年中較為炎熱的季節裡,在更為炎熱的那些夏季,更為炎熱的年份、城市或地區,也都是如此(Anderson & Anderson,1998,2000)。安德森等人認為,如果全球溫度上升4°F(約2℃),那麼僅美國每年就會增加至少5萬起嚴重的襲擊事件。
真實世界裡的這些情況是否足以說明炎熱帶來的不適直接導致了攻擊行為的發生呢?雖然這個結論看上去有道理,但溫度和攻擊行為之間的這些相關 並不能證明這一點。在炎熱潮溼的天氣裡,人們當然會更加急躁;在實驗室裡,高溫的確能增強我們的情緒喚醒和帶有敵意的想法(Anderson & others,1999)。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夏季炎熱的夜晚只是把人們從家裡趕到了大街上,在那裡,其他相關的群體因素髮生了作用。
攻擊
受到攻擊或侮辱尤其容易引發攻擊行為。日本大阪大學的Ohbuchi和Kambara(1985)的實驗都證實蓄意的攻擊將招致報復性回擊。此類實驗中,有兩名被試在一項反應時測試中進行比賽;每組測驗之後,由獲勝者決定給失敗者施加多大強度的電擊。事實上,每個被試的對手都是一個設計好的電腦程序,該程序會穩步地、逐級增加電擊的強度。我們真實的被試在反應上是否會比較仁慈呢?事實幾乎都不是這樣的,大部分的迴應方式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喚醒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種厭惡刺激可以喚起人們憤怒的情緒,是否其他形式的喚醒,如伴隨體育鍛煉或性興奮的情緒喚醒,也有相似的效果呢?試想,塔娜在高強度的短跑鍛鍊後回到家,發現本來說好晚上約會的男孩來過電話,留言說他晚上另有計劃。相比在小睡醒來時收到這樣的消息,此時剛跑完步的塔娜是否會更容易發怒呢?或者,剛做完運動之後,她的攻擊傾向會被削弱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些關於我們如何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進行解釋分類的有趣實驗。
在斯坦利·沙克特和傑爾姆·辛格(Schachter & Singer,1962)的著名實驗中,發現人們可以通過不同方式體驗到機體的喚醒狀態。實驗以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為被試,給他們注射腎上腺素,使其達到喚醒狀態,這種藥物可以使人臉紅、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如果告訴被試注射的藥物會產生這些效果,即使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一起等待,人們的情緒波動也會很小。顯然,他們會把自己的軀體感覺歸因於藥物作用。但另一組被試被告知藥物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同樣,他們被安排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待在一起,他們又是如何反應的呢?和不友好的人在一起,被試會被激怒;而和歡快的人在一起時,被試則過得很愉快。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總結出這樣的原則:一種軀體喚醒狀態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取決於人們對這種喚醒的解釋和分類。
但另一些實驗卻顯示,喚醒並非像沙克特相信的那樣,在情緒上無所差別。軀體的興奮狀態確實可以強化幾乎所有情緒(Reisenzein,1983)。例如,如保羅·比內(Biner,1991)所報告的,在被明亮的燈光喚醒時,被試對無線電廣播中的靜電噪聲尤其 反感;多爾弗·齊爾曼(Zillmann,1988),詹寧斯·布萊恩特及其合作者發現,剛剛參加完自行車鍛鍊,或者剛剛看完有關披頭士的搖滾音樂會的電影,人們都會更容易錯誤地把他們的喚醒狀態歸因於挑釁,然後用更強烈的攻擊行為進行反擊。雖然我們可能想當然地認為,劇烈運動會消耗掉塔娜攻擊性的緊張壓力,讓她可以平靜地接受壞消息,但以上實驗證明,喚醒的狀態只會強化情緒。
因此,性喚醒和憤怒等其他各種形式的喚醒狀態之間是可以相互增強的(Zillmann,1989)。性愛只有在打完架或者受到驚嚇之後才最富激情。在實驗室條件下,那些剛剛受到驚嚇的被試被色慾刺激喚醒的程度更高。類似的,坐一次過山車引起的喚醒狀態也可能使人深深陷入對伴侶的浪漫感覺之中。
挫敗、酷熱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會提高我們的喚醒水平。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喚醒狀態就會與敵對的想法和情緒一起,促成攻擊性行為(圖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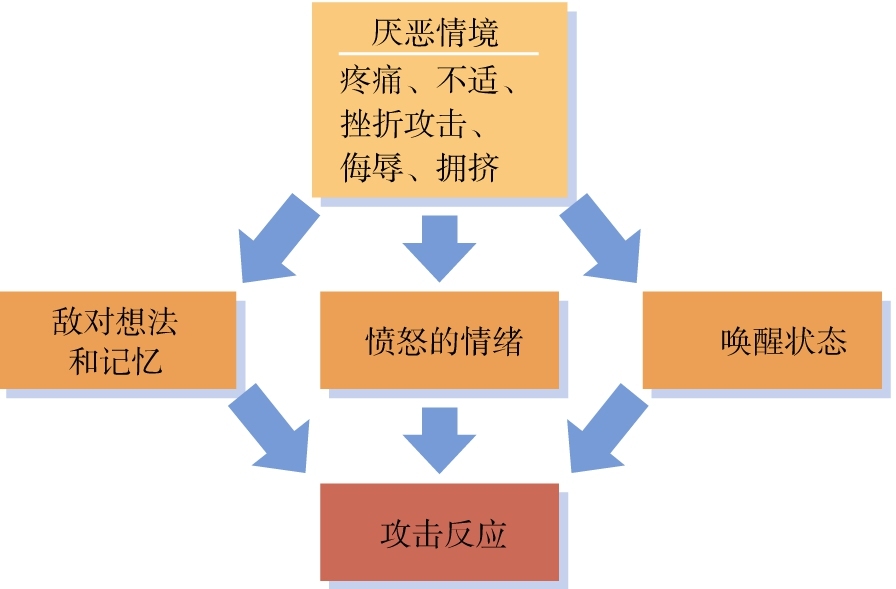
圖10-5 敵意性攻擊行為的要素
厭惡性情境可以激起人們敵對性的認知、敵對情緒和喚醒狀態,繼而引發攻擊行為。這樣的反應使我們更容易將他人意圖理解成惡意的,並報之以攻擊。
資料來源:Simplified from Anderson,Deuser,and DeNeve,1995.
攻擊線索
如前所述,當攻擊線索“拔掉瓶塞”,胸中怒火噴湧而出時,攻擊行為最容易發生。伯科威茨(Berkowitz,1968,1981,1995)等人發現,看到武器就是這樣一種線索,尤其是當它被看做一種暴力工具而非消遣時。實驗中,剛玩過玩具槍的小朋友更願意推倒另一個小朋友堆起的積木。在另一個實驗中,相比附近只有羽毛球拍的情況,當附近有來複槍或者左輪手槍(被試以為這是上一個實驗遺留下來的)時,憤怒的威斯康星大學被試對給他們造成痛苦的人施加了更為強烈的電流刺激(Berkowitz & LePage,1967)。所見即為所思。槍支會啟動敵對性想法和懲罰性的判斷(Anderson & others,1998;Dienstbier & others,1998)。因此,伯科威茨認為:美國一半的謀殺是用手槍完成的,而家藏的手槍殺死家庭成員的可能性遠高於殺死入侵者這樣的事實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認為:“槍支不僅使暴力成為可能,還可以刺激它的發生。手指扣動扳機,但扳機同樣可以拉動手指。”
伯科威茨同樣認為,禁止持有手槍的國家謀殺率較低是合情合理的。英國人口為美國的1/4,但謀殺案只有它的1/16。美國每年有1萬起手槍槍殺案件;澳大利亞約有12起,英國24起,加拿大100起。在華盛頓特區通過了限制人們持有手槍的法律後,與槍有關的謀殺案和自殺事件都迅速降低了25%。但其他形式的謀殺和自殺案件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該法案適用範圍之外的臨近地區也都沒有發生類似的下降(Loftin & others,1991)。
研究者還考察了持有或不持有槍支的家庭發生暴力事件的危險性。由於這些家庭在相關的背景上都有可能不同,因此這項研究受到置疑。一項由疾病控制中心發起的研究中,對相同性別、種族、年齡和住所的槍支持有者和非槍支持有者進行比較。研究結果帶有諷刺和悲劇意味,那些家中藏有槍支(通常是為了自衛)的人被謀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7倍——幾乎都是被家人或者密友殺死的(Kellermann,1993,1997)。同樣,藏有槍支的家庭發生自殺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Taubes,1992)。與相同性別、年齡、種族的其他人相比,家有槍支者被殺的可能性要高出41%,而自殺的可能性則高出3.4倍。家中有槍與否,往往意味著這樣的區別:是爭鬥還是葬禮,是忍受折磨還是飲彈自盡。
槍支並不只是提供攻擊線索,它們還拉大攻擊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就像米爾格拉姆(Milgram)的服從實驗告訴我們的那樣,與受害人的遠離使我們更加殘忍。刀也可以殺人,但遠遠地扣動扳機要比持刀發動攻擊容易得多(圖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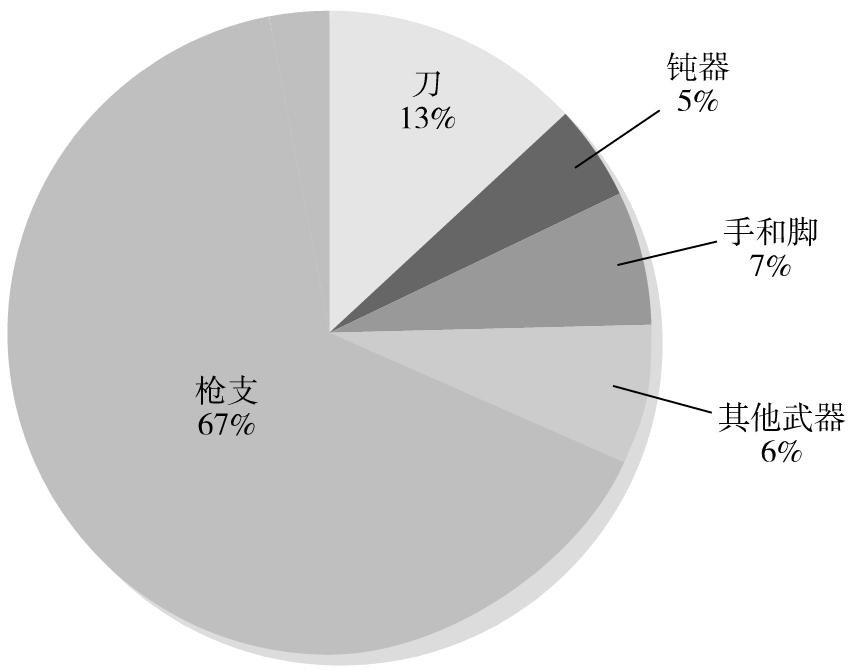
圖10-6 2002年美國發生的謀殺案所用凶器示意圖
資料來源: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媒體影響:色情文學和性暴力
1960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特別是在青少年中,這促使我們發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什麼樣的社會力量導致了暴力的迅速增加?
酒精可以引發攻擊行為,但是酒精的使用自1960年以來並沒有改變很多(McAneny,1994)。別的生物因素(睪丸激素,基因,神經遞質)同樣影響了攻擊行為,但無法解釋文化的巨大改變。暴力事件的急劇增多難道說是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膨脹導致的嗎?還是由於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是由於雙親家庭的減少與無父家庭的增多?還是因為媒體中越來越多的暴力形象和對性的大肆渲染?最後一個問題的產生,源於暴力、性攻擊的增長同媒體混亂、對性的渲染是同時發生的。這種歷史上的一致性純屬巧合嗎?色情文學(《韋氏字典》的定義:用以提高性興奮水平的性愛描寫)的社會效果是什麼?電視和電影中的暴力榜樣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在當今的美國,色情行業迅速發展,其規模大於職業橄欖球、籃球和棒球的總和。每年用於色情業的投資達100億,包括工業電纜和衛星網絡的架設,提供相關服務的劇院、收費電影、酒店室內電影、色情雜誌、性服務電話,還有預計40萬的收費色情網站等等(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2;Rich,2001;Schlosser,2003)。在一項對大學生的調查中,57%的男生和35%的女生報告自己曾經搜索過與性有關的網頁,有6%的男生和1%的女生報告他們經常登陸此類網站(Banfield & McCabe,2001)。
社會心理學對色情文學的研究著重於對性暴力的描寫。一個典型的性暴力場景中,一個男人硬要和一個女人性交。最初她會抵抗並試著擊倒襲擊她的人。但逐漸地,她被性喚醒,也停止了抵抗。最後她完全進入了欣快狀態,並不斷地要求更多。我們都看過或者閱讀過對這一場景的非色情的描寫:她反抗,他堅持。精力充沛的男人抓住並強吻抗拒的女人。不一會兒,女人本來一直推搡著男人的手已經緊緊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經被他釋放的激情壓倒了。在《飄》一書中,斯佳麗被帶到床上的時候還是抗拒和踢鬧的,但是當她醒來,就又放聲歌唱了。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觀看這樣的小說情節(一個男人制服一個女人,激起她的性興奮)可以:(1)歪曲其關於女人對性攻擊的真實態度的認識;(2)增加男人對女人的攻擊行為。至少實驗室情境下是如此。
對性現實的歪曲理解
觀看性暴力是否可以強化所謂“強暴謬論”:女性會歡迎性騷擾——女性在說“不要”的時候並非真的意味著“不要”?為了找出答案,馬拉默斯和切克(Malamuth & Check,1981)給曼尼託巴大學的男生觀看兩個沒有性的電影或是描寫性的電影(一個男人制服了一個女人)。一個星期以後,做另外一個主試的實驗時,看過有適度性暴力描寫電影的被試更容易接受對女人施以暴力的行為。另外也有相關研究顯示:接觸色情信息會增強人們對“強暴謬論”的接受度(Oddone-Paolucci & others,2000)。在馬林和林茨(Mullin & Linz,1995)的實驗中,連續看了3天的性暴力的電影后,男性被試對強姦和砍殺的焦慮水平逐漸降低了。和其他沒有觀看這種電影的被試相比,他們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現出更少的同情心,對受害者受傷害的程度估計偏低。正如唐納斯坦等人(Donnerstein,Linz,& Penrod,1987)所說,要使人們接受一個邪惡的角色、面對受到折磨與摧殘的女性無動於衷,恐怕沒有什麼方法比給他們看逐步升級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啟示(即“許多女人喜歡被征服”)是非常微妙、不大可能招致反駁的。媒體常常把性攻擊描述為:女性的抗拒融化在男性有力的臂膀中。我們不難理解,甚至許多女性也會相信:或許其他 女性喜歡被征服——而實際上沒人認為自己會是這樣(Malamuth & others,1980)。“我被一個攻擊我的男人激起性慾?下輩子的事兒吧!”
針對女性的攻擊
有證據表明,色情文學也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實際攻擊。相關水平的研究增大了這種可能性。約翰·柯特(John Court,1985)指出,由於20世紀60、70年代色情文學的蔓延,世界各地報告的強姦案發率陡然上升——除了那些色情文學得到控制的國家和地區。(與這一潮流相反的例子,如日本,暴力色情文學比較普遍而強姦案發率卻較低。這提醒我們,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夏威夷,報告的強姦案數目1960~1974年增長了9倍,實行了對色情文學的限制措施後下跌,措施取消後再次回升。
在另一項相關研究中,拉里·巴倫和默裡·斯特勞斯(Baron & Straus,1984)發現,露骨的色情雜誌[如《好色客》(Hustler)和《花花公子》]在50個州的銷售量與該州的強姦案發率存在相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各州的青年男性人口比重)之後仍然如此。阿拉斯加在色情雜誌銷量和強姦案發率上均排名榜首,內華達州則在兩項指標上均列次席。
在採訪中,加拿大和美國的性罪犯普遍承認了色性文學的作用。例如:威廉·馬歇爾(Marshall,1989)報道說:安大略省的強姦犯和猥褻兒童的罪犯看的黃色書刊,要遠多於非性罪犯的男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項研究也報道了連環案的凶手對黃色書刊的使用,洛杉磯警察局則是發現了對兒童性虐待的犯人和黃色書刊間的相關(Bennett,1991;Ressler & others,1988)。
雖然實驗室研究僅適於短期行為,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它相比相關研究的優越之處在於能夠揭示現象間的因果關係。21位主要的社會科學家對研究的成果做了總結: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對女性的懲罰性行為。其中之一的唐納斯坦(1980)做了這樣一個實驗:給威斯康星大學的120名男生觀看中性、色情和色情暴力(強姦)的影片各一部。然後,這些學生作為另外一個實驗的部分被試,需要教他們的一個男性或女性同伴學習一些無義音節,並由他們控制對同伴的錯誤答案給予多強的電擊。看過強姦電影的男生傾向給予同伴更強的電擊(圖10-7),尤其當他們感到憤怒而且同伴為女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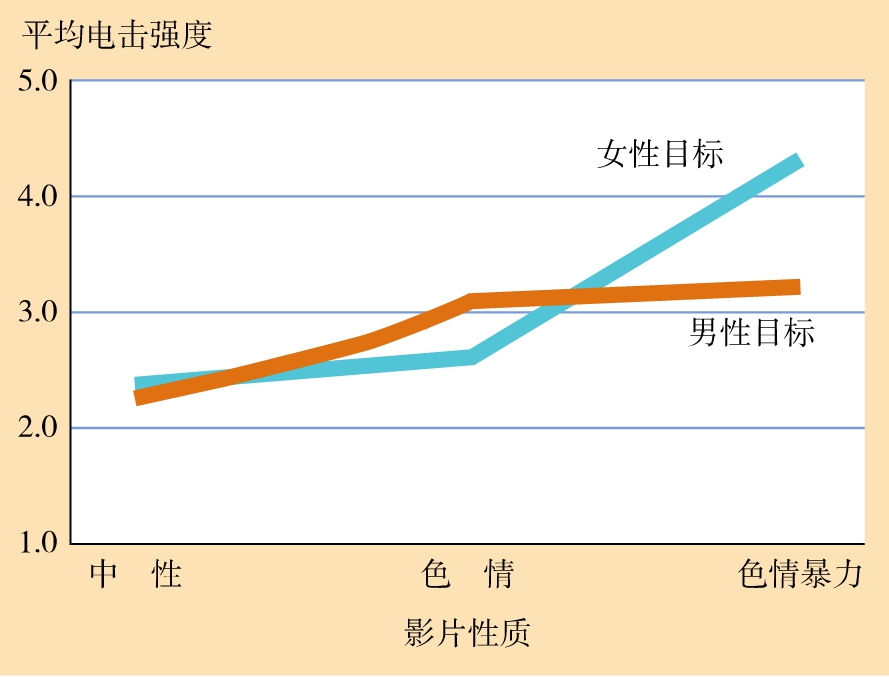
圖10-7
在觀看了一個色情暴力片後,男大學生選擇了比以前更強的電擊(對別人),尤其是對女性。
資料來源:Data from Donnerstein,1980.
反覆觀看以快速、強迫的性行為為特徵的色情片容易導致:
性伴侶的吸引力下降;
對通姦和女性對男性的性順從更容易接受;
男性對女性的感知更容易從性的角度出發。
資料來源:See Myers,2000.
如果你為此類實驗涉及的倫理問題而擔憂,那麼請放心,這些研究者已經考慮到了他們給予被試的這些體驗可能引起的爭議及其影響。實驗必須是在被試知情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而且實驗完成後,主試會針對影片傳達的荒謬說法對被試進行矯正(Check & Malamuth,1984)。
進行此類實驗,不僅是為了科學研究,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在一項細緻的全國性調查中,22%的婦女報告曾被男性強迫與之發生與性有關的行為(Laumann & others,1994)。
另一項研究中,18%的婦女報告曾有過符合強姦定義的經歷(Tjaden & Thoennes,2000)。七分之六的作惡者是她們認識的人。
瑪麗·科斯及其同事(Koss & others,1988,1990,1993)對全國範圍內6200名大學生和2200名俄亥俄州職業女性的調查發現,28%的女性報告曾有過符合法律上強姦或強姦未遂定義的經歷[但其中的多數發生在約會時或是發生在與熟人之間,並未將它說成強姦;女性對強姦的描述,通常包括陌生人施予的暴力行為(Kahn & others,1994)]。
其他工業國家中進行的調查得到了類似的結果(表10-1)。3/4的陌生人強姦和幾乎所有的熟人強姦都未曾報告警方。因此,報告的強姦案發率嚴重低估了實際的強姦案發率。
表10-1 五個國家中女性報告有被強姦經歷的比例

資料來源:Studies reported by Koss,Heise,and Russo(1994)and Krahé(1998).
有8項不同的調查,都是詢問男大學生,“如果你確定絕對不會有人知道,而且絕對不會因此被懲罰,那麼你是否有可能強姦女性?”(Stille & others,1987)。一個令人擔憂的比例——1/3左右的人——承認至少有微小的可能會這樣做。和表示絕對不會強姦的人相比,他們在許多方面與強姦犯有更多共同之處,如相信“強暴謬論”,很容易被強姦片段的描寫引起性興奮,以及對女性採取攻擊性行為(在實驗室情境中和在約會中)。在那些接受了色情文學所宣揚的贊同強姦的態度的人中,這種攻擊是最強烈的(圖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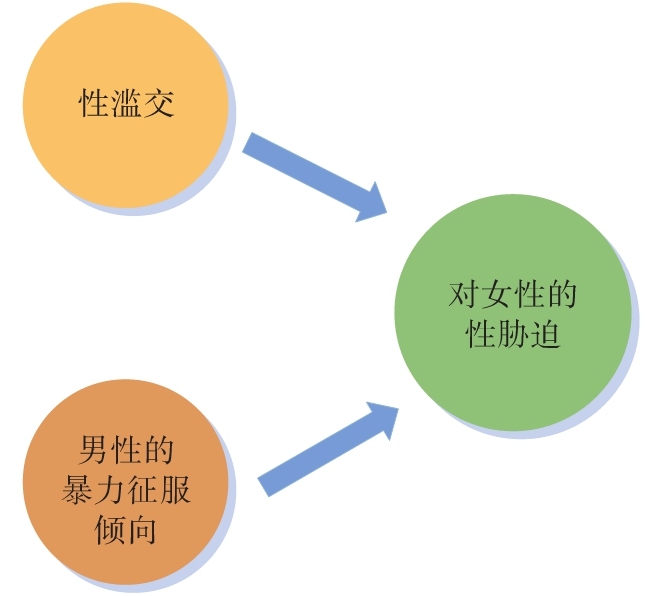
圖10-8 性侵犯的男性
對女性施以性脅迫的男性,常常既有不涉感情的性經歷,又有男性特有的暴力征服傾向(Malamuth,1996,2003)。
媒體意識教育
正如二戰時,大多數德國人已對大屠殺中充斥的可恥的反猶行徑熟視無睹;今天,對於媒體中充斥的對婦女的騷擾、虐待、強迫的畫面,人們業已司空見慣。那麼,我們是否應當對媒體中貶低、侵犯女性的內容進行限制呢?
在對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比較中,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傾向於認為個人權利高於集體權利。作為媒體監管制度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很多心理學家都喜歡使用“媒體意識訓練”。以往對色情文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成功地教育被試並使他們重新認識女性對性暴力的真實態度;那麼同樣的,教育者能夠促使人們對色情作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嗎?通過增強人們對色情作品中“女性主導”的觀點和存在的性騷擾、性暴力等問題的警覺性,我們或許可以揭穿女性喜歡受脅迫的謬論。正如唐納斯坦等人(Donnerstein,Linz,& Penrod,1987,p.196)所說,“我們理想主義乃至天真的願望,就是:科學所揭示的真理終將勝利;公眾將會相信,這些作品不僅貶低了其中的角色,也貶低了它們的觀眾。”
這個願望天真嗎?試看:在沒有禁止香菸的情況下,美國的菸民從1965年的42%降到了本世紀初的23%。在沒有對種族歧視進行審查的情況下,一度常見的非裔美國人在媒體中的形象:單純、迷信的小丑形象已近乎絕跡。隨著公眾意識的改變,劇本作者、製作人以及媒體監製開始覺得醜化少數民族是不合適的。最近,他們開始認為藥物沒有20世紀60、70年代的歌和電影裡所描繪的那樣迷人,卻非常危險,不過高中生在過去一個月中吸食大麻的比率已經從1979年的37%降到1992年的12%。由於社會上反對毒品的呼聲有所緩和,1996年又反彈至23%,於是一些音樂電影又開始渲染毒品的使用(Johnston & others,1996)。將來有一天,當我們回顧起當年的電影通過醜化黑人、血腥殘殺、性暴力來取悅觀眾時,是否會倍覺尷尬?
媒體影響:電視
我們已經知道,觀看一個攻擊者可以引發孩子的攻擊慾望,並教給他們實施攻擊的新辦法。我們還知道,在看過性暴力影片後,很多憤怒的男性會對女性更加暴力。那麼觀看電視是否會有類似的效應呢?
我們來看看與看電視有關的一些研究結果。1945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曾調查美國人,“你知道什麼是電視嗎?”(Gallup,1972,p.551)。今天在大多數工業國家,基本上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機(如在澳大利亞,電視機的普及率為99.2%),超過了電話的擁有率(Trewin,2001)。大多數家庭擁有不止一臺的電視機,這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家長報告他們的孩子看什麼,與孩子自己報告他們看什麼之間的相關很低(Donnerstein,1998)。隨著MTV在140個國家普及,CNN的勢力跨越全球,電視正在創造一種全球的流行文化(Gundersen,2001)。
在一般的家庭中,電視機一天開7個小時,平均每個家庭成員要看三四個小時,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可以活到80歲,那麼他有10年都花在了看電視上面。女性比男性看得更多,非白人比白人看得更多,學齡前兒童和退休的人比上學的和工作的人看得更多,教育程度低的比高的看得更多(Comstock & Scharrer,1999)。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人在觀看習慣上的這些特點同樣也存在於歐洲人、澳大利亞人和日本人(Murray & Kippax,1979)。
在這7小時中,哪些社會行為被模仿了呢?從1994到1997年,國家電視暴力研究中心的職員日夜不停地對來自各大網絡和有線頻道的約一萬個節目進行調查。他們發現了什麼?10個節目中有6個包含暴力內容(“以身體上的脅迫恐嚇說要傷害和危及生命,或是造成實際傷害和殺害”)。在格鬥中,佔下風的人往往擺脫掉對手,再回來的時候變得更強了——不像真正的格鬥那樣,最後一擊決定結果(其下場往往是傷到下巴或手)。73%的暴力情景中,攻擊者沒有受到懲罰。58%的受害者沒有表現出疼痛。在兒童節目中,只有5%的暴力情景顯示其有長期的後果;2/3只是拿暴力描寫取樂。
結果是什麼呢?正如專家所言,電視發射的電磁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以至於他們花在電視上的時間甚至多於花在學業上的。實際上,比花在任何一項清醒狀態下的活動上的時間都多。到了小學畢業,平均每個兒童在電視中看了8000個謀殺案和10萬種其他的暴力行為(Huston & others,1992)。格布納(Gerbner,1994)在經過了長達22年的對暴力節目的統計以後,悲嘆道:“人類曾經有過許多更嗜血的時代,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像現在這樣暴力影像 無處不在。我們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沒,這個潮流是前所未見的……它用經過專業編排的殘忍畫面淹沒了每個家庭。”
黃金時段播放的犯罪節目會刺激類似行為的產生嗎?還是說,觀眾通過觀看節目間接地參與了暴力行為,從而釋放了其攻擊性的能量?
後面的那個觀點,是宣洩 (catharsis)假說的一個變體,這個理論主張,觀看暴力節目可以讓人們釋放他們被壓抑的敵意。為媒體辯護的人經常援引該理論,並提醒我們,暴力行為是先於電視出現的。倘使和批評電視的人進行一次想像中的辯論,維護媒體的人會爭辯說,“電視沒有參與對猶太人和印第安人的滅絕性屠殺。電視僅僅反映和迎合了我們的口味。”“這個我同意,”批評者回答,“但是你無法否認,自從有了電視以後,美國報告的暴力犯罪增長的速度遠遠高於人口的增速這一事實。顯然你不會這樣認為:流行文化只是被動地反映公眾意識卻對其沒有任何影響,或者說,廣告商所信賴的媒體的力量只是一種幻覺。”辯護者回答:“暴力氾濫的原因很多。通過把人們套在家裡而不是街上,以及為他們發洩攻擊能量提供無害的機會,電視可能反而在減少攻擊行為。”
對看電視與攻擊行為關係的研究,旨在發現比吸引公眾眼球的偶發的“照貓畫虎”式謀殺案更為微妙、也更為普遍的效應。它們想要知道的是:電視怎樣影響觀眾的行為 和觀眾的思想?
電視對行為的影響
觀眾會模仿暴力榜樣嗎?大量的例子表明,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重演著電視上的犯罪。在一項對208例判刑罪犯的調查中,10人之中有9人承認他們通過觀看犯罪節目學習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說他們曾經嘗試在電視中看到的那些犯罪(《TV Guide》,1977)。
看電視與行為的相關研究 犯罪故事不能算是科學的證據。因此研究者用相關和實驗研究來檢驗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應。一種經常用於學齡兒童的技術可以用來檢驗,觀看電視是否可以預測他們的攻擊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預測是可行的。一個兒童看的電視節目中包含越多的暴力內容,那麼他的攻擊行為就會越多(Eron,1987;Turner & others,1986)。這種相關不高,但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都存在。
由此我們是否能夠得出結論,觀看暴力電視會助長攻擊行為?也許你早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相關研究,相反方向的因果關係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許是攻擊性強的兒童喜歡暴力節目。還可能是某些潛在的其他變量(如低智商),使得有些兒童既喜歡暴力節目同時又表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
研究者們發展了兩種方法來檢測這些可能的解釋。他們用統計方法去除某些可能因素的影響,以考察“潛變量”解釋。例如,威廉·貝爾森(Belson,1978;Muson,1978)對1565個倫敦男孩進行了研究。與那些沒觀看多少暴力的孩子相比,看了大量的(尤其是現實中的而不是動畫中的)暴力節目的兒童,在過去6個月中多表現出了50%的暴力行為(例如,“我破壞了電話亭裡的電話”)。貝爾森還檢查了22個可能的干擾因素,比如家庭規模。在控制了干擾因素後,看得多和看得少的被試間仍舊表現出了差異。所以他推測,看得多的人的確是因為 看了更多的電視,而增加了暴力行為。
類似地,倫納德·伊儂和羅威爾·霍斯曼(Eron & Huesmann,1980,1985)發現在875個觀看暴力電視的8歲兒童中,即使在統計上剔除了一些明顯可能的干擾因素,也能發現兩者間存在相關。而且,當這些人19歲時再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在8歲的時候對暴力的接觸能夠中度預測他們在19歲時的攻擊性,但是在8歲時的攻擊性並不能預測19歲觀看暴力的多少。攻擊行為隨著觀看出現,但是反過來卻不能成立。此外,到了30歲,童年看了大量的暴力電視的人因罪判刑的可能性更大(圖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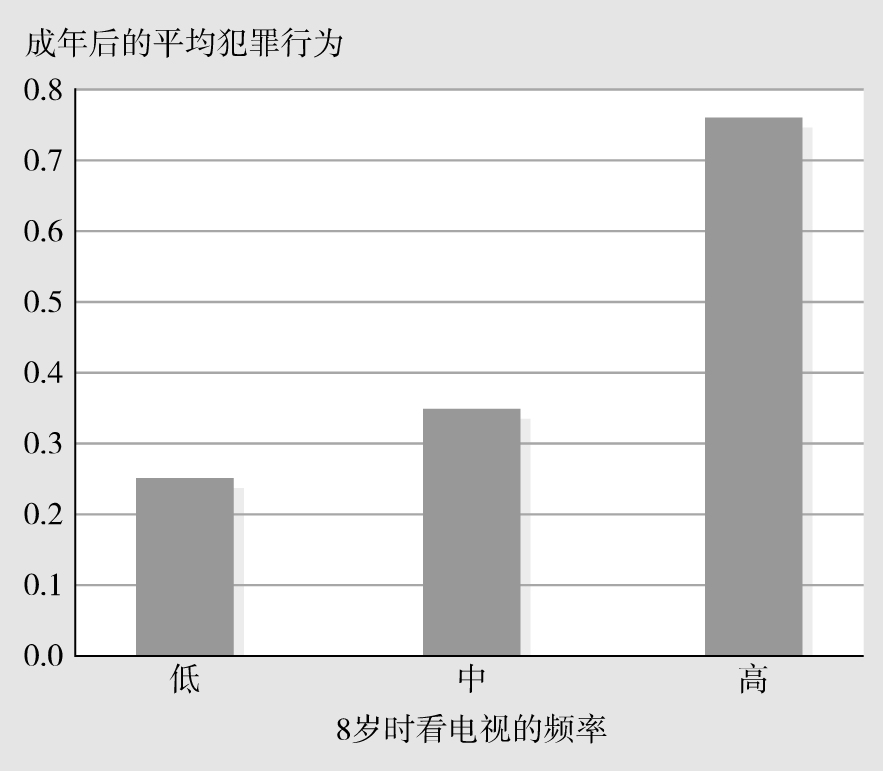
圖10-9 兒童看電視的頻率與隨後的犯罪行為
在8歲時觀看暴力可以預測其30歲時的嚴重犯罪行為
資料來源:Data from Eron and Huesmann(1984).
休斯曼和他的同事(Huesmann & others,1984,2003)對芝加哥地區的青少年進行的追蹤研究,再一次證實了上述結論。研究者發現: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後,承認自己有過推、搶或是毆打妻子行為的人是其他人的兩倍。相應地,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女孩,報告自己曾對丈夫扔東西的是其他人的兩倍。
傑弗裡·約翰遜和他的合作者(Johnson & others,2002)對700名個體進行的追蹤研究結果顯示:青春期時,對暴力電視的接觸也可以預測其成年之後的攻擊行為。14歲時,每天看電視少於一個小時的個體,在16~22歲之間,有6%的人報告曾經參與攻擊性活動(如,毆打,搶劫,威脅恐嚇),而每天看電視多於3小時的個體,有29%的人報告參與攻擊性活動,是前者的5倍。
目光敏銳的同學這時可能會提出置疑:這些相關關係,只是源自於那些最初觀察時已富於攻擊性的,或者受教育、智力水平較低的個體所表現出的較高水平的攻擊性(受教育和智力水平較低者,的確會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看電視上)。事實上,當休斯曼和約翰遜小組對這些因素進行有效控制後,仍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事實是:哪裡有電視,暴力便隨之增多,乃至於謀殺率也是隨著電視的出現增長。在加拿大和美國,1957~1974年,殺人案發生率隨著暴力電視的傳播增長了2倍。在人口普查地區內,電視出現得晚的那些地方,殺人率的攀升也出現得晚些。在南非白人聚集的地方,電視直到1975年才被引進,而這種類似的殺人率的翻倍也直到1975年才出現(Centerwall,1989)。一個對電視出現得很晚的加拿大鄉村的嚴密的研究,結果表明:運動場上的暴力行為在電視出現後很快翻了一番(Williams,1986)。
要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顯示了研究者現在是怎樣利用相關研究的結果來間接推論 因果關係的。然而,仍舊可能是那數不清的潛在變量造成了看暴力節目與攻擊行為之間純屬巧合的聯繫。幸運的是,實驗方法可以控制這些無關的因素。如果我們隨機的選擇一些兒童來觀看一個暴力電影而另外一些看非暴力電影,之後兩組在攻擊行為上表現出來的什麼任何差異都應歸因於他們之間惟一不同的因素:他們觀看的是什麼。
看電視的實驗研究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沃爾特斯(Bandura & Walters,1963)所做的開拓性試驗中,有時讓幼兒觀看成人重擊一個充氣娃娃的電影而不是親眼觀看這個場面——發現兩者產生了幾乎一樣的效果。之後,伯科威茨和吉恩(Berkowitz & Geen,1966)發現,觀看了一部暴力電影的憤怒的大學生比觀看一部非暴力電影的同樣憤怒的大學生表現出更強的攻擊性。這些實驗室實驗,加上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促使美國醫事總署(U.S. Surgeon General)在20世紀70年代初批准了50項新的研究項目。隨著這些研究及後來100餘項研究的開展,逐漸證實了觀看暴力導致攻擊增加的結論(Anderson & Bushman,2002;Bushman & Anderson,2001)。
例如,分別由美國的羅斯·帕克(Parke,1977)和比利時的雅克·萊恩斯(Leyens,1975)所領導的研究小組給收容的美國和比利時少年犯男孩觀看攻擊性或非攻擊性的商業電影。結果一致表明:“觀看暴力電影……導致觀眾的攻擊性增加。”與看電影前一個星期相比,觀看暴力電影的男孩們在小屋裡出現身體襲擊的數量暴增。與之類似地,多爾弗·齊爾曼和詹姆斯·韋弗(Zillmann & Weaver,1999)給男性和女性被試在連續的4天內觀看暴力或非暴力的電影。第5天,當他們參與另外一項研究時,看暴力電影的人對研究助手表現出了更多的敵意。
這些實驗激發出的攻擊並不是襲擊和毆打;它更多地表現為買午餐排隊時的推搡,出口傷人和威脅性動作這一水平。無論如何,這些證據的一致性還是令人吃驚的。“不可辯駁的結論,”美國心理學會青年暴力委員會1993年這樣表示,“是觀看暴力節目導致了暴力的增加。”對於有攻擊傾向的人尤其如此(Bushman,1995)。當一個有魅力的人因正當理由而實施了適度的暴力,而這種暴力未受懲罰且沒有表現出造成了任何傷害時,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果是最為顯著的(Donnerstein,1998)。
總而言之,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Bushman & Craig Anderson,2001)總結道,觀看暴力之於攻擊行為的影響,要勝過被動抽菸之於肺癌,鈣的攝入量之於骨質密度,和家庭作業之於學業成就。正如抽菸之於癌症,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表現出這種影響——因為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值得擔憂的是這種影響的長期累積可能會使公眾忽視其存在。但是,現在這種證據已經是“壓倒性的”,布什曼和安德森指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會導致攻擊行為的顯著增加。”一項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項目中,主要的媒體暴力研究者均認為,研究的基礎是廣泛的,方法是多樣的,而總的發現則是一致的(Anderson & others,待發表)。“我們深入的回顧發現,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無論是即時的還是在長期的情況下,均會增加攻擊行為和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鑑於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結論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為什麼 觀看暴力節目會有這種效果。考慮三種可能性(Geen & Thomas,1986)。其一,導致社會暴力行為的不是暴力內容本身,而是由它造成的喚醒狀態 (Mueller & others,1983;Zillmann,1989)。而如前所述,喚醒狀態容易引發其他行為。
另一些研究顯示,觀看暴力使人們降低抑制 。在班杜拉的實驗中,成人對充氣娃娃的重擊似乎使這種發洩方式顯得合理,從而減低了兒童的抑制。觀看暴力內容通過激活與暴力關聯的想法,進而引發了觀眾的攻擊行為(Berkowitz 1984;Bushman & Geen,1990;Josephson,1987)。聽歌詞中含有性暴力的音樂似乎有類似的效果(Barongan & Hall,1995;Johnson & others,1995;Pritchard,1998)。
媒體內容同樣引起模仿 。班杜拉實驗中的兒童模仿了他們之前看到的特定行為。商業電視對於電視導致人們的模仿行為很難辯駁:它的廣告商引導了消費。然而,媒體的主管聲稱,電視只是對這個暴力社會的鏡像反映;藝術是對生活的模仿;因此膠片上的世界(“reel”World)向我們展示了真實的世界(real world)。這些說法是對是錯?事實上,電視節目中,攻擊行為遠遠超出愛撫行為,二者比例為4:1。同樣地,電視在其他方面也塑造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表10-2)。
表10-2 美國電視中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

來自喬治·格布納從1969年起對近35000個電視角色的分析(Gerbner,1993;Gerbner & others,1986);電視性別數據來自於費爾南德斯等人(Fernandez-Collado & others,1978);電視中宗教信仰數據來自於斯基爾(Skill & others,1994);真實的宗教信仰數據來自於薩德(Saad & McAneny,1994)—他們對信仰的比例看待得相當重要;酒精數據來自於NCTV(1988)。非婚姻伴侶中的性行為的比例顯然只是電視中描述的一小部分,因為大多數成年人都結婚了,已婚的性交頻率高於單身的,而且婚外情比我們通常認為的少(Greeley,1991;Laumann & others,1994)。謀殺的數據來自奧利弗(Oliver,1994)。
有一種對電視的批評認為,如果現實生活中的人按電視裡的速度被謀殺的話,那麼50天之內人就會被殺絕了(Medved,1995)。
不過這裡也有好消息,如果電視上塑造的聯繫和問題解決的方式真的導致了模仿,特別是在年輕的觀眾中,那麼對親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的塑造對社會就將是有利的。第12章中有好消息:電視微妙的影響在於,它確實可以教孩子學習積極的行為。
電視對思想的影響
我們之前關注的是電視對行為的影響。研究者同樣也考察了觀看暴力對認知的影響:持續的觀看是否讓我們對殘忍的行為麻木了?它是否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覺知?它是否引發了攻擊的想法?
脫敏作用 重複一個激發情緒的刺激,例如一個猥褻的詞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會發生什麼?回想普通心理學有關內容,我們知道情緒性反應會“消失”。在看了上千遍殘忍的行為後,我們有同樣的理由相信會發生類似的情緒麻痺。最通常的反應也變成“一點也不困擾我”。這樣的反應正好是維克托·克萊因和他的同事們(Cline & others,1973)從121個剛看了一場野蠻的拳擊賽後的猶他州男孩那裡所觀察到的結果。和很少看電視的男孩相比,這些男孩的反應更多的只是聳聳肩,而非關注。
當然,這些男孩也許在別的方面也存在差異。但是在考察觀看性暴力的影響的實驗中,觀看暴力影片的年輕男性出現了類似的情緒敏感度降低——一種心理麻痺。此外,羅納德·德拉布曼和瑪格麗特·托馬斯(Drabman & Thomas,1974,1975,1976)證實:看完這類暴力影片之後,再看打鬧的電影或是真實地觀察兩個孩子在打架,更易使人產生膩煩的反應。
一項對5456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觀看暴力電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Sargent & others,2002)。三分之二的學生看到過痛苦的尖叫 。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蓋洛普青年調查中,儘管有那麼多極端暴力的鏡頭(或者毋寧說正是由於 它們),調查結果卻顯示13~17歲青少年中感到電影中有太多暴力的人所佔比例在下降,由1977年的42%下降到了2003年的27%。現在電影中,有關性的鏡頭更加暴露,卻已經不能再吸引青少年的眼球。蓋洛普研究員Mazzuca(2002)指出:如今,有關暴力和性主題的影像描寫對孩子的吸引力遠遠低於他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了。
改變知覺 難道電視虛構的世界也塑造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嗎?格布納和他大學的同事(1979,1994)猜測這是電視最強烈的影響。他們對成年人和兒童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看電視多的人(每天看4個小時以上)比看電視少的人(2個小時或更少)更容易誇張周圍世界暴力發生的頻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擊。南非女性在觀看了對女性使用暴力的節目以後也產生了類似的脆弱感(Reid & Finchilescu,1995)。一個在全美國7~11歲的兒童中進行的調查發現,看電視多的人比看電視少的人更容易承認他們害怕“一些壞人可能會闖入你的家”或者“當你外出,別人可能會傷害你”(Peterson & Zill,1981)。
認知啟動 最後,有新證據表明,觀看暴力錄影帶可能會激活與攻擊有關的概念網絡(Bushman,1998)。在觀看了暴力節目之後,人們對他人的行為會作出更富敵意的解釋(推搡行為是有意的嗎?),解釋同音異義字的時候選擇更具攻擊性的意義(把“punch”解釋為擊打而不是一種飲料),而且對攻擊性詞語的識別更加迅速。
也許,電視的最大影響是間接發生的,每年電視代替了上千小時或更多別的活動的時間。如果你跟別人一樣,每年花費上千小時的時間看電視,試想一下,你將如何度過沒有電視的日子。為了尋求20世紀60年代後期市民活動和組織成員數減少的原因,帕特南(Putnam,2000)報告說每一點增加在電視上的時間都是在與市民參與活動競爭。電視從俱樂部會議、志願活動、教堂禱告和政治活動那裡偷走了時間。
媒體影響:電子遊戲
“科學界關於媒體傳播暴力對人們是否 有影響的爭論已漸漸平息。”金泰爾與安德森(Gentile & Anderson,2003)認為。研究者現在將注意力轉向了電子遊戲。電子遊戲作為一種娛樂產品正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歡迎,而且其中暴力血腥內容愈來愈多。金泰爾與安德森指出,教育研究表明“電子遊戲是一種良好的教學工具。如果健康的電子遊戲能夠使人們學會健康的行為,模擬飛行的電子遊戲可以教會人們如何飛行,那麼人們從模擬謀殺的遊戲中會學到什麼呢?”
兒童電子遊戲
2002年,電子遊戲工業成立30週年。如表10-3所示,自從1972年推出第一個電子遊戲以來,已經由電子乒乓遊戲發展到暴力遊戲(Anderson,2004;Gentile & Anderson,2003)。
表10-3 暴力電子遊戲發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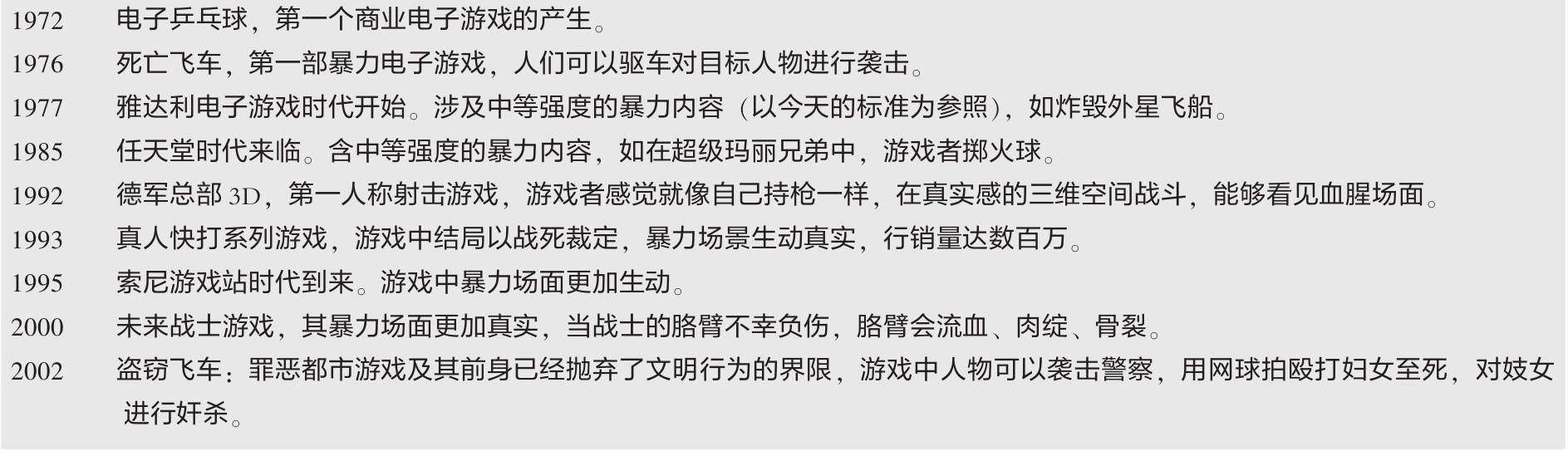
這些暴力遊戲很流行。據統計,本世紀初,一年的遊戲銷售量達2億,2~17歲的未成年人,平均一週玩電子遊戲的時間為7小時。在一項對四年級學生的調查中,59%的女生和73%的男生報告,暴力遊戲是他們最喜歡的遊戲(Anderson,2003,2004)。雖然遊戲會以“M”(成年人)為標誌,以示其只對17歲以上的成年人出售。但在市場上,卻常常對未成年人出售。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發現,未成年兒童嘗試購買暴力遊戲的成功率為五分之四(Pereira,2003)。
電子遊戲對兒童的影響
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科羅拉多州,十幾歲的青少年模仿他們在屏幕上玩的暴力恐怖遊戲,這一現象的出現引起了人們對暴力遊戲的關注。人們開始擔心:當年輕人在遊戲中體驗對人進行襲擊和對人體進行肢解,他們習得的某些東西是否會一直伴隨他們?
大多數菸民並不是因為心臟病死掉的,大多數受過虐待的兒童也沒有因之而變得殘忍,去施虐於人。大部分在凶殺模擬器上花掉數不清的時間的人,其實過著文雅的生活。所以暴力遊戲的支持者可以宣稱,和人們對菸草、電視感興趣一樣,暴力遊戲是無害的。交互數碼軟件協會主席洛溫斯坦(Lowenstein,2002)指出:“至今為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玩暴力遊戲可以導致攻擊行為。”金泰爾和安德森卻給出了一些理由,證明為什麼玩暴力遊戲有可能 比觀看暴力電視更容易誘導人們做出攻擊性行為。在玩電子遊戲時,遊戲者:
認同暴力人物的身份並進行角色扮演。
積極地演練暴力行為,而不是被動地觀看。
參與扮演暴力活動的全過程——選擇刺殺對象,購買槍支彈藥,靠近目標,進行瞄準,扣動扳機。
參與持續武裝暴力活動並進行威脅恐嚇。
不斷地重複暴力行為。
從有效攻擊中獲得獎賞。
基於上述原因,軍隊為使戰士在戰鬥中英勇射擊(據報道,二戰時許多士兵顯得動作遲疑),常常訓練他們玩模仿攻擊遊戲。
但實際中,科學的研究結果又有怎樣的發現呢?克雷格·安德森(Anderson,2003,2004;Anderson & others,待發表)對36個研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五種一致的效應。與非暴力電子遊戲相比,玩暴力電子遊戲更容易:
提高喚醒水平 ——心跳加速和血壓升高。
引發攻擊性思維 ——如布什曼和安德森(Bushman & Anderson,2002)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玩一組暴力遊戲後,請其對汽車尾部受到撞擊的司機的行為進行預測時,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司機會做出攻擊性反應,如言語辱罵,打架,踢破窗子。安德森和同事(2003)發現含暴力內容的歌詞也會啟動人們的攻擊性思維:學生在進行補筆測驗時,更容易將“h_t”補成“hit”而不是“hat”。
喚醒攻擊性情緒 ——挫折體驗增強,表達出的敵意也更多。
誘發攻擊性行為 ——玩過暴力遊戲的兒童,在與同伴相處時,更容易表現出攻擊性傾向,與老師爭執,喜歡集群打架。無論是同伴、教師還是家長報告,無論是實驗室內還是實驗室外,這一效應均普遍存在。原因見圖10-10。
減少親社會行為 ——人們在玩暴力遊戲之後,在幫助在走廊上哭泣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反應變得遲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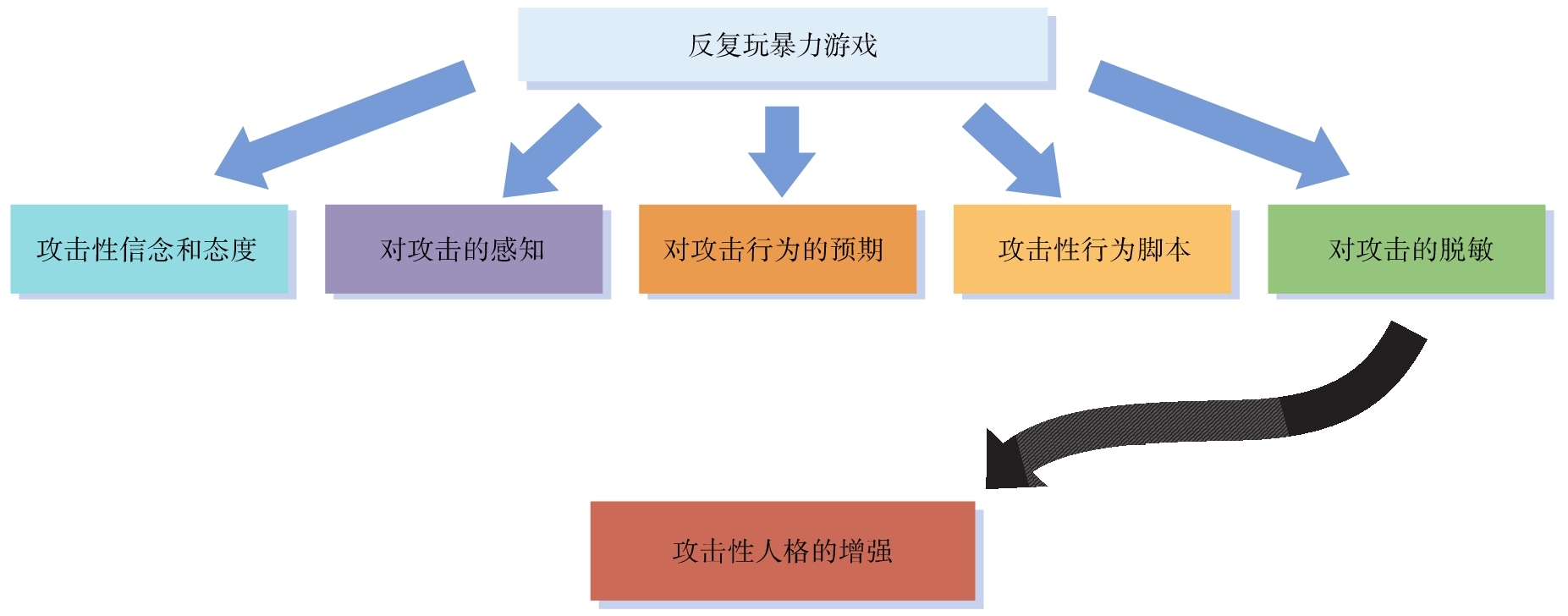
圖10-10 暴力遊戲攻擊傾向的影響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Craig A. Anderson and Brad J. Bushman(2001).
此外,玩暴力遊戲的時間越長,這種效應越明顯。現在,電子遊戲中的暴力不斷升級,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影響是最大的。還有更多影響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與宣洩假說相反,過多地模擬暴力行為只會促使其攻擊性傾向增強,而不是宣洩暴力情緒。
安德森(Anderson,2003,2004)憂心忡忡地向家長呼籲,父母應該關注孩子周圍的媒體,並保證其接觸健康的媒體。至少在家裡,應該完全做到這一點。雖然家長不可能完全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為,但是最起碼在家裡,應為孩子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鼓勵其參與健康的遊戲。也可以與其他父母進行交流,共同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長環境。學校應該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媒體意識教育。
群體影響
前面我們已經考察了哪些因素會激發個體 的攻擊性。如果挫折、侮辱和攻擊性榜樣能夠增強孤立個體的攻擊傾向,那麼這些因素也一樣會對群體有類似的影響。當一場騷亂開始的時候,一旦有人開始對抗,便如同扣動了扳機,攻擊行動迅速蔓延。看著別人肆無忌憚地瘋搶,搬走電視機,守法的旁觀者可能會違背道德,仿效前者的行為。
研究背後的故事:
克雷格·安德森與暴力電子遊戲
由於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暴力電影或電視會對人們產生不良的影響,看到如今電子遊戲中的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時,我開始擔憂。於是在我的研究生卡倫·迪爾(Karen Dill)的協助下,我開始進行暴力電子遊戲領域的相關和實驗研究,與此同時也愈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我曾到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作證,並且許多政府和公共政策組織,包括父母與兒童權益維護組織等,也向我諮詢有關方面的問題。
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產生了積極影響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但是電子遊戲工業界卻在竭盡全力抵制這些研究。就像30年前,香菸製造商嘲笑基礎醫學的研究,戲謔地問:一隻老鼠要抽多少根萬寶路煙才會得癌症?我也收到很多遊戲玩家的電子信件,信件內容令人感到不快,也有許多人要求我提供有關信息,於是我將有關的信息和問題回覆發在瞭如下網頁上:www.psychology.iastate.edu/faculty/caa。
很多人認為,加深人們對某一問題認識的最好方法就是給予反對者與支持者同等的機會發表觀點。媒體中有關暴力的新聞故事,確實給了電子遊戲工業界代表及其偏愛的“專家”、年僅14歲不用為其言論負責的少年以同等的機會。而最後留給我們的印象僅是——我們知道的還沒有我們實際做過的多。如果某個領域的專家意見完全一致的話,那麼“公正”和“平衡”又有什麼意義呢?或者,我們能期望這些合法的專家手頭拿著受到平等對待的、已出版的原始研究報告嗎?
群體通過責任擴散使攻擊行為增大。在戰爭中,進攻決策是遠離前線的戰略家做出的。他們下命令,但是由別的人執行。這種距離是否會讓下命令發動攻擊變得更為容易吧?
蓋布蘭和曼德(Gaebelein & Mander,1978)在實驗室中模擬這種情景。他們讓自己學校——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博羅大學的學生電擊 某人,或者是給某人提建議 應該給予多強的電擊。如果執行者還沒有像攻擊的受害者那樣被激怒過,那麼這些親自執行的人會給予比所建議的小一些的電擊,而那些建議者不會覺得自己應該對任何傷害負直接責任。
責任擴散隨著距離的增大和人數的增多而變強(回想一下第8章去個體化的現象)。布賴恩·馬倫(Mullen,1986)對1899~1946年間的60起私刑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參與私刑的暴民越多,謀殺和殘害就越殘酷。
通過社會“傳染”,群體能夠放大攻擊傾向,正如他們極化其他傾向一樣。例如:青年團夥,足球球迷,搶奪的士兵,本地暴徒以及斯堪迪納維亞人所說的匪徒——結夥的學生不斷地騷擾和攻擊沒有安全感的軟弱的同學(Lagerspetz & others,1982)。這是一種群體行為,單個欺凌弱小的人極少進行嘲弄和攻擊。
具有共同的反社會傾向、缺乏緊密的家庭聯繫、對學業成就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會在幫派中找到社會認同。隨著群體認同的發展,服從的壓力和去個體化在增加(Staub,1996)。自我認同隨著成員把他們自己完全投入了群體而逐漸消失了,經常感到與他人融為一體而十分滿足。通常的結果是群體喚醒、去抑制和極化。團伙專家阿諾德·戈爾茨坦(Goldstein,1994)解釋道,直到團伙成員結婚了,年老了,找到了工作,進了監獄或是死了,他們才退出。他們確定自己的地盤,張揚他們的個性,挑戰對手,有時也犯罪以及為了藥物、恐怖、榮耀、女孩或者凌辱而戰鬥。
20世紀超過1.5億人的大屠殺“不是個體行為的集合”,羅伯特·扎伊翁茨(Zajonc,2000)指出,“種族屠殺不是殺人行為的複數 。”大屠殺是被道德規範所強化的社會 現象——一種集體思想(包括圖騰,辯術和意識形態)動員一個群體或是一種文化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對盧旺達圖西族人的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的屠殺以及對美洲土著的屠殺都是集體現象,它需要廣泛的支持、組織以及參與。盧旺達胡圖族政府和商業領袖出錢購買並分發了200萬把中國大砍刀“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
以色列的傑夫和義農(Jaffe & Yinon,1983)的實驗證明群體可以強化攻擊傾向。在一個實驗中,大學男生被一個虛擬同伴激怒,他們在群體條件下決定的電擊比獨自一人時強度更大。在另一個實驗中(Jaffe & others,1981),人們單獨或是在群體中決定對某人在ESP任務中回答錯誤的懲罰。如圖10-11所顯示的,隨著實驗的進行,個體使用的虛擬電擊逐漸增大,群體決策增強了這種個體傾向。當環境激發了一個個體的攻擊反應,額外的群體互動往往會增大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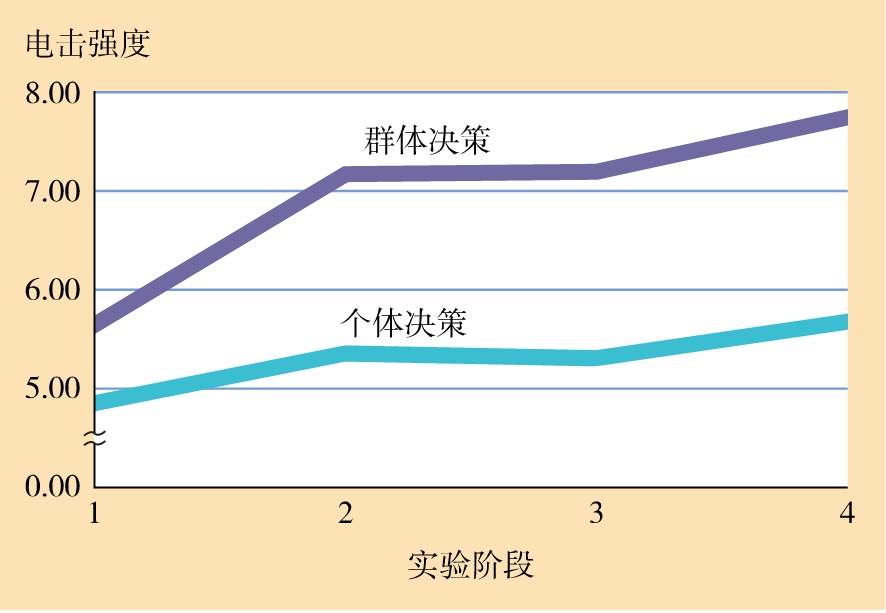
圖10-11 群體增強攻擊
當個體選擇執行多大的電擊作為對回答錯誤的懲罰時,隨著實驗的進行,他們選擇的電擊水平逐漸增高。群體決策進一步極化了這種傾向。
資料來源:Data from Jaffe & others,1981.
我們可以以對攻擊行為的研究為契機,探討社會心理學的實驗室研究在日常生活的適用性。導致人們採取電擊的實驗情景與現實中使得人們出口傷人或打人耳光的情境能有多大可比性呢?克雷格·安德森和布拉德·布什曼(Anderson & Bushman,1997;Bushman & Anderson,1998)指出:社會心理學已經對實驗情景和日常世界中的攻擊進行了研究,而且結果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在兩種情景下,攻擊的增強可以被這些因素預測:
男演員
攻擊性或A型人格
酗酒
觀看暴力
匿名
被激怒
武器的存在
群體互動
實驗室使得我們可以在控制條件下檢驗以及修訂理論。現實事件給我們靈感並且為理論的應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攻擊研究顯示控制性的實驗室研究和複雜的現實社會間的相互影響,可以增進心理學對人類福祉的貢獻。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得到的靈感激發了理論,理論刺激了實驗室研究,而實驗室研究又深化了我們的理解和把心理學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能力。
小結
厭惡事件不僅包括挫折,也有不適、疼痛,和身體、言語上的人身攻擊。幾乎由任何一種來源,甚至包括身體鍛鍊或性刺激導致的喚醒,都能被轉化成憤怒。
電視表現了相當多的暴力。相關和實驗研究得出一致的結論:觀看暴力節目會(1)導致攻擊行為出現一定的增長,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2)降低觀眾對攻擊的敏感度和改變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這兩個發現和對觀看暴力色情文學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觀看色情文學會增加男性對女性的攻擊,而且扭曲他們對於女性對性脅迫的態度的知覺。反覆玩暴力遊戲則會引發更多的暴力攻擊性的想法、情緒和行為。
很多攻擊行為是群體發生的。激怒個體的情境同樣可能激怒群體。通過分散責任和極化行為,群體情境能夠增強攻擊反應。
如何減少攻擊
我們考察了攻擊的本能論,挫折-攻擊理論以及社會學習理論,我們也詳細考察了影響攻擊行為的各種因素。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攻擊行為呢?理論和研究可以提供控制攻擊行為的方法嗎?
宣洩
“年輕人應該學會排解他們的憤怒。”安·蘭德斯(Landers,1969)建議道。如果一個人“壓抑了自己的憤怒,我們就要找到一個出口。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排出憤怒的湍流。”傑出的精神科醫生弗里茲·珀爾斯(Perls,1973)這樣主張。沙利文(Sullivan,1999)在《紐約時代週刊》的一篇文章中則主張,“一些偏激的言論……幫助釋放了憤怒……它通過言語轉移了衝突,避免見諸行動。”兩個觀點都採取了“水壓模型”——聚集的攻擊能量就像用壩攔住的水,需要一種釋放。
宣洩的概念一般認為是亞里士多德創造的。雖然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攻擊的內容,但他確實提到,我們可以通過體驗情緒而擺脫它們,通過觀看經典悲劇而達到一種對憐憫和恐懼情感的宣洩(“淨化”)。他相信,讓某種情緒興奮,就是讓那種情緒得到釋放(Butcher,1951)。宣洩假設已經擴展到不僅僅包括觀看戲劇,也包括回憶、重新體驗往事,表達情緒和各種行動。
在攻擊行為或幻想耗盡了被壓抑的攻擊能量這一假設下,一些臨床醫學家和群體的領導鼓勵人們通過攻擊行為來疏導受壓抑的攻擊能量——用泡沫塑料球棒互相痛打,或一邊尖叫一邊用網球拍打被子。如果人們相信宣洩能夠有效地改善情緒,那他們在面對侮辱時,將會表現出更強的敵意,來釋放不良的情緒(Bushman & others,2001)。一些心理學家認為宣洩具有心理治療作用,並建議家長鼓勵孩子在攻擊型遊戲中釋放他們的情緒壓力。實際上布什曼(Bushman,2002)指出:通過發洩來減少憤怒的情緒,如同火上澆油。
很多普通民眾接受了這種觀點,反映在3個人中有2個贊同這樣的觀點:“性用具為禁錮的衝動提供了出口”(Niemi & others,1989)。但是之後其他的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同樣贊成“性用具引發人們強姦。”那麼,宣洩理論到底有效嗎?
如果觀看色情作品為性衝動提供了出口,那麼性期刊訂閱率高的地方強姦率應該很低,而且人們在看了色情作品以後,對性的慾望應該消失了,男人應該不會把女人看作和當作發洩對象。但是研究顯示,事實完全相反(Kelley & others,1989;McKenzie-Mohr & Zanna,1990)。錄影帶中露骨的性描寫是一味春藥;它誘發性幻想,繼而催生各種性行為。
社會心理學家一致認為,與弗洛伊德、洛倫茲及其追隨者的猜想正相反,暴力並不能實現宣洩(Geen & Quanty,1977)。例如,羅伯特·阿姆斯(Robert Arms)和他的同事報告說,加拿大和美國的足球、摔跤和曲棍球比賽的觀眾在觀看了賽事之後表現出更多 的敵意(Arms & others,1979;Goldstein & Arms,1971;Russell,1983)。乃至戰爭似乎也沒有減少人們的攻擊情緒。戰爭過後,國家的謀殺率有竄升的趨勢(Archer & Gartner,1976)。
在對宣洩假說的實驗室檢驗中,布什曼(2002)安排已被激怒的被試擊打沙袋,控制其中一組被試回想惹自己生氣的人,另一組則想像通過擊打使自己身體得到鍛鍊,並設置控制組不擊打沙袋。接下來,實驗者告知被試可以對惹自己生氣的人大聲吼叫,結果顯示:擊打沙袋並進行回想的那組被試的行為最具攻擊性。由此觀之,也許什麼都不做反而比“發洩怒火”能更有效地減少人們的攻擊傾向。
在一些真實生活情境的實驗中,同樣發現攻擊行為增強了攻擊性。埃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夥伴(Ebbesen & others,1975)在100個工程師和技師收到解僱通知並被此激怒後的很短時間內採訪了他們。先詢問一些問題,給他們提供向其僱主或主管表達敵意的機會——例如,“你認為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公司對你的不公正待遇?”之後他們回答了一個問卷,評價對公司和主管的態度。之前“發洩”或“排出”敵意的機會減少了這個評價裡的敵意了嗎?相反,他們的敵意增加了。表達敵意導致了更多的敵意。
聽起來很熟是嗎?第4章提到,殘忍的行為引起了相應的態度。更進一步,正如我們在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順從實驗的分析中提到的,輕微的攻擊行為可以為自己找到正當理由。人們貶低受害者,從而使進一步的攻擊合理化。即使有時(在短期內)合理化降低了壓力,最終也會降低抑制。即使當憤怒的人們擊打一個沙袋,相信 這樣能夠宣洩,但影響是相反的——導致他們表現得更 殘忍,布拉德和他的同事這樣報告(1999,2000,2001)。“這就像那個老笑話,”布什曼(1999)說道。“如何趕上卡內基·霍爾?實踐,實踐,再實踐。你如何成為一個憤怒的人?答案是一樣的,實踐,實踐,再實踐。”
我們應該因此而禁錮憤怒和攻擊的慾望嗎?生悶氣顯然不是更好的辦法,因為它讓我們能夠在頭腦中導演著談話的同時仍不斷髮著牢騷。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用非攻擊的方法來表達我們的感覺和告知別人,他們的行為是怎樣影響了我們。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夠把對“你”的指責重組成“我”的信息——“我很憤怒”或者“你把髒盤子留在那裡讓我很不愉快”——以一種能使別人更好地做出積極反應的方法交流他們的感受(Kubany & others,1995)。我們可以不用攻擊性的方式,而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
社會學習觀點
如果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那麼就存在控制它的希望。讓我們大概回顧一下影響攻擊行為的因素和考慮如何消除它們。
厭惡體驗,如期望的破滅、人身攻擊等都會導致敵意性攻擊。所以避免給人們以錯誤的、不可達到的預期是明智的。預期的回報與代價會影響工具性攻擊。它建議我們應該獎勵合作性的非攻擊的行為。在實驗中,當看護者忽略他們的攻擊行為,並強化其非攻擊性行為時,兒童的攻擊性降低(Hamblin & others,1969)。懲罰攻擊者的效果不那麼穩定。只有當懲罰措施強大,及時並且確定;當它和對期待的行為進行獎勵結合起來;而且接受者不憤怒這樣的理想條件下,威脅懲罰才能消除攻擊行為(R.A. Baron,1977)。若缺少這種威懾力量,可能導致攻擊行為的爆發。這一點在1969年和1992年分別被證實。1962年,蒙特利爾警察進行了一場持續16小時的罷工;1992年,對洛杉磯暴動進行的直升機電視報道顯示,有部分地區沒有警力。在兩種情況中,直到警方返回時,爆發性的破壞和掠奪才停止。
聚焦 一位臨床研究者看宣洩理論
約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在他的暢銷書《迴歸家園——找回和守護你的內心》(Homecoming :Reclaiming and Championing Your Inner Child )中,詳述了他的想像技術:向你的內心請求寬恕,與你的父母斷絕關係並尋找新的(像耶酥),撫摸你的內心,寫一段你的童年曆史。這種技術稱為“宣洩”,即將情緒投入對充滿傷痛的往事的體驗之中。宣洩給人的體驗強烈、印象深刻。放聲痛哭,對去世已久的父母大發雷霆,緊緊擁抱受傷的小男孩(自己童年的影子)——這些都讓人心緒難平。除非你是鐵石心腸才不會落淚傷情。數小時後,你會感到清白、平和——或許是多年來第一次。醒來,繼續前行,新的生活在向你召喚。
宣洩,作為一種治療技術已經存在一百多年了。它一度是心理分析療法的中流砥柱,但現在已經不是。它的主要缺點是,沒有證據證明它起作用了。當你調查人們是否喜歡宣洩療法,你聽到了很高的讚譽。當你考察它是否帶來了變化時,宣洩則鮮有建樹。
資料來源:From Martin E. P. Seligman,What You Can Change and What You Can't :The Complete Guide to Successful Self-Improvement ,Alfred A. Knopf,1994,pp.238~239.
但是懲罰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大多數致命的攻擊是一時衝動、激烈的攻擊——因爭辯、侮辱或受攻擊而起。所以我們必須在攻擊發生之前阻止它。我們應該學會以攻擊之外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除非這種致命的攻擊是冷靜的工具性攻擊,我們才能期望等到它發生之後,通過重典懲治來杜絕此類行為。在這樣的世界中,實行死刑的州謀殺率會低於沒有死刑的州。但在我們這個世界,殺人多是一時衝動,情況就不同了(Costanzo,1998)。
體罰同樣能產生消極作用。懲罰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刺激;它塑造了我們所盡力防止的行為。而且它是強迫的(回顧一下,我們從沒有因為很強的外部理由的強迫而內化某種行為)。暴力少年和虐待孩子的家長大多出自以嚴酷體罰來管教孩子的家庭,便不足為奇了。
為了創造一個更溫柔的世界,我們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塑造並獎勵敏感性和合作,或許可以通過訓練家長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達此目的。訓練計劃鼓勵家長強化期待的行為,積極地表達觀點(“清理完你的房間以後,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間,你哪兒也別去”)。一個“替代攻擊項目”通過教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交流的技巧、訓練他們控制自己的憤怒並提高他們道德推理的水平,已經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團伙成員的再犯率(Goldstein & others,1998)。
如果觀看攻擊榜樣可以降低抑制和引起模仿,那麼我們也可以減少電影和電視上野蠻、缺乏人性的表演——這些步驟可以和已經使用的減少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表演的措施相媲美。我們也可以讓兒童對媒體暴力的影響免疫。我們對於電視網絡“面對現實,並改變他們的節目”已不抱任何希望。埃倫和休斯曼(Eron & Huesmann,1984)訓練來自伊利諾伊州奧克公園的170名兒童:電視描述的世界是不真實的,攻擊並不是像電視說的那樣常見和有效;實際上,我們並不提倡攻擊行為(利用態度探討法,研究者鼓勵兒童自己做這些推理,從而把對電視的批評歸因為自己的信念)。在兩年後的再次研究中,這些孩子比沒有受過訓練的孩子受電視暴力的影響要小。在一項最新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用了18個學時來勸服兒童,僅僅是為了減少他們看電視和玩電視遊戲的量(Robinson & others,2001)。他們看電視的時間下降了1/3——而且他們在學校的攻擊行為和控制學校的兒童相比,下降了25個百分點。
攻擊性的刺激也會引發攻擊。這提示我們應該增大武器(例如手槍)的獲取難度。牙買加1974年施行了一個大規模的反犯罪計劃,包括加大槍支控制的力度,和嚴格對電視電影中的槍戰場面的審查制度(Diener & Crandall,1979)。在之後的一年中,搶劫下降了25%,非致命的槍擊降低了37%。在瑞典,玩具產業不再銷售戰爭玩具。瑞典新聞署(1980)表明了國家的態度:“拿戰爭當遊戲,意味著學習用暴力手段解決爭端。”
類似這樣的建議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攻擊。但是我們知道導致攻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而且控制起來不那麼容易,那麼誰還能理解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20世紀做的樂觀的預言呢:“殺一個人將會被認為是令人憎惡的,正如今天的我們認為吃人是令人憎惡的那樣。”自從他1900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已經有20億人被殺了。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儘管今天我們已經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攻擊性,但是人性中的暴虐卻依然如故。但是,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正如納塔莉·安吉爾(Natalie Angier)所言,“北歐海盜曾燒殺搶掠,而他們在瑞典的後裔近200年來卻沒有打過一次仗。”
小結
我們如何減少攻擊?與宣洩假設相反,發洩攻擊更多地引發攻擊的產生,而非減少進一步的攻擊。社會學習觀點建議通過消除引發攻擊的因素來控制它——通過減少令人厭惡的刺激,獎勵和塑造非攻擊行為,和產生與攻擊行為不一致的反應。
個人後記:對暴力文化的改革
美國在1960年(首先向其他國家的讀者表示抱歉,不過我們美國確實存在特殊的暴力問題)在平均每起報道的暴力案件中有3.3個警官負責。到了1993年,就變成了每個警官平均負責3.5起案件(Walinsky,1995)。從那時候起,犯罪率開始有輕微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監獄監禁了相當於1960年時的6倍的人數,而且現在15~25歲的男性的人數有個暫時的下降。然而,在我所在的這所大學裡,在1960年不需要任何校警,而現在僱用了6個全職和7個兼職保安,而且我們提供了夜間班車,以護送住在校園周邊的學生。
美國人自我保護的措施:
買一把槍用於自我保護(我們有……2.11億把槍支……這使得被謀殺的風險提高了兩倍,經常是被某個家庭成員殺害,而且自殺的機率提高到了原來的5倍。更為有效的方式,應該是服從國家的政策——禁止私人持槍)。
建更多的監獄[犯罪案件一直在持續增加,直到最近仍是如此。此外,社會和國庫在監禁200萬犯人上的支出(大多數是男人)相當龐大]。
利用“三振出局”的規則終生監禁那些犯了三次暴力罪行的人(但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負擔所有這些嗎?新的監獄——以及監獄醫院和護理病房——用以容納和照顧這些昔日的暴徒)。
阻止野蠻的犯罪和消滅窮凶極惡之徒——像伊朗和伊拉克那樣,槍決那些罪犯。為了說明殺人是錯誤的——殺掉殺人的人。(但是幾乎所有擁有高暴力犯罪率的12個城市和州業已實施死刑。但由於大多數的殺人行為只是一時衝動或是在藥物或酒精的影響下進行,所以殺人者很少會考慮到後果。)
比懲罰的嚴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的確定性。國家研究委員會(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3)報告說,與將刑期加倍相比,拘捕率增加50%,犯罪量的減少是前者的兩倍。儘管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主管路易斯(Louis Freeh,1993)還是相信更強硬、更及時的懲罰措施才是最為根本的方法:“我們所面臨的無視法律的程度是如此可怕,它更像一場瘟疫,已不是單純的執法問題。絕望的貧民、缺少關愛的兒童、濫用毒品導致的犯罪與混亂的泛濫,不是單單靠無底的監獄、依法審判、增加警力就能解決的。”等犯罪發生後才有所反應,其社會效果就如同拿創可貼治療癌症。
另一種觀點來自於在急流中拯救落水者的故事。在成功地進行了急救以後,幫助者發現另外一個掙扎的人,然後把她也拉了出來。如此反覆發生數次後,救人者突然打住,跑開了,無視這時流水卷著另外一個溺水的人進入視線。“你不準備救那個傢伙了嗎?”有旁觀者問道。“當然不,”救人者吼道,“我非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什麼見鬼的東西把這些人推到水裡。”
為了得到保障,我們需要警察、監獄和社會工作者,以幫助我們對付這些困擾我們的社會病。打蚊子確實不錯,但弄乾淨那些潮溼的地方會更好——通過改造我們的文化,挑戰那些腐蝕年輕人的社會毒瘤和重建我們的道德根基。
你的觀點是什麼
在你所生活的社區裡(你居住的小區或你就讀的學校)存在什麼樣形式的暴力呢?暴力組織受到了什麼樣的懲罰呢?居民對此滿意嗎?這些措施消除了社區中的暴力衝突嗎?在仔細閱讀本章的基礎上,請思考暴力行為的本質,以及哪種攻擊理論最有可能適用。有哪些因素影響了攻擊行為,怎樣才能在你的社區裡減少這些攻擊性行為呢?
聯繫社會
在這一章裡,我們主要考察了戴維·巴斯(David Buss)對攻擊的進化心理學解釋。你可能回顧第5章中,戴維·巴斯關於進化、性別和交配選擇的觀點。在第11章中,我們會遇到巴斯對身體吸引力的進化心理學的闡述。
第11章 吸引和親密:喜歡他人和愛他人
什麼造就了友誼和吸引
接近性
外表吸引力
相似性與互補性
喜歡那些喜歡我們的人
關係中的回報
什麼是愛情
激情之愛
伴侶之愛
哪些因素促進了親密關係
依戀
公平
自我表露
親密關係是如何結束的
離婚
分離的過程
個人後記:經營愛情
“靠著朋友的點滴幫助我才得以度日。”
——約翰·列儂和保羅·麥卡特尼,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1] ,1967
人與人之間終生的相互依賴性使得人際關係成為我們生存的核心。開天闢地以來,就存在著吸引——男性和女性間的吸引,我們應該為自己得以來到世間而對它心存感激。亞里士多德將人稱為“社會性動物”。確實,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歸屬需要 (need to belong)——與他人建立持續而親密的關係的需要。
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和馬克·利裡(Baumeister & Leary,1995)闡釋了社會吸引的力量,而這種力量正是源於我們的歸屬需要。
對我們的祖先而言,只有相互依存才能使族群得以生存。當狩獵或搭棚時,眾人共同協作要比一個人單幹更好。
對男性和女性而言,因愛結合而有了孩子,隨後,父母相互支持,共同撫養,孩子才得以成長。
對孩子和養育者而言,社會性依戀促進了他們的共存。如果毫無理由地將他們分開,養育者和孩子都會感到恐慌,直至重新團圓。忽視孩子或將孩子置於無人關心的機構中,孩子就會傷心並焦慮。
對世界各地的人們而言,之所以有豐富的思想和多彩的情緒,正是因為那些真實的和想像的親密關係。如果有一個能提供精神支持、可相互信賴的伴侶,我們就會感到被接納和被讚許;墜入情網,人們會感到抑制不住的愉悅。正是因為人們渴望被接納和被愛,所以才會在化妝品、服裝和塑身上有鉅額花費。
被流放的人、坐牢的人或被單獨監禁的人,總是會想念他們的親人和故土。人們被拒絕時,就會感到抑鬱(Nolan & others,2003),會覺得度日如年,生活乏味(Twenge & others,2003)。
失戀的人、喪偶的人以及旅居異鄉的人,會因為喪失社會聯繫而變得痛苦、孤獨或孤僻。失去精神上的伴侶,人們會變得嫉妒、發狂或產生剝奪感,會對死亡和生命的脆弱變得更加敏感。
死亡會提醒我們重視歸屬需要,重視與他人的關係並與我們所愛的人保持親密(Mikulincer & others,2003,Wisman & Koole,2003)。面對9·11恐怖事件,數以百萬的美國人都與自己心愛的人通了電話。同樣道理,同學、同事或家庭成員的突然死亡也會使人們之間的關係得到加強,無論他們曾經有過什麼分歧。
我們確實是社會性動物。我們需要歸屬於某一群體。就像第14章所證實的那樣,當我們有所歸屬時——當我們感到被一種親密的關係所支持時——我們會更加健康和快樂。
在澳大利亞的新南威爾士大學,基普林·威廉斯等人(Williams & others,2001)考察了歸屬需要被排斥行為(拒絕或忽視的行為)阻礙時的結果。研究發現,所有文化中的人們,無論在學校、工作場所還是家庭中,都會使用排斥來調節社會行為。那麼,被故意迴避——避開、轉移視線或默然以對——是一種什麼滋味呢?人們(尤其是女性)對排斥的反應常常是抑鬱、焦慮、感到情感被傷害並努力修復關係,以致最後陷入孤僻。從家庭成員或同事那裡遭受這種沉默對待的人,都會認為這種對待是一種“情感上的虐待”,是一種“非常非常可怕的武器”。在實驗中,那些在一個簡單的球類投擲遊戲中被忽略的人們,也感到了挫折和沮喪。
有時被小瞧也會令人厭惡。在幾項研究中,瓊·特溫格等人(Twenge,2001,2002;Baumeister & others,2002)給一些被試提供社會接納的體驗,而另一些被試則體驗社會排斥:他們(根據一項人格測驗)被告知“要註定一生孤獨”,或者遇到的人都不願意接納他們加入自己的團體。結果發現,這些做法誘發了被試的社會排斥感,在隨後的表現中,他們不但增多了自暴自棄的行為,比如在態度測驗中表現不好,而且還更可能對曾經得罪過自己的人進行貶損或抱怨。一段實驗室中的小小經歷都能引發如此強烈的攻擊行為,這使得研究者更想知道,“持續的重要的拒絕或長期的排斥又會導致怎樣的攻擊傾向呢?”
威廉斯等人(2000)驚訝地發現,即使在虛擬世界中,被一個永遠不可能見面的人拒絕,也會引起挫折感。(或許你有過在聊天室裡被忽視或發出的電子郵件石沉大海的經歷。)研究者從62個國家招募了1486名被試,讓每個被試與另外兩人一起玩一種網絡飛碟遊戲(另外兩人實際上是電腦模擬的)。結果,那些遭到另外兩人排斥的被試感到情緒低落,並且在完成隨後的知覺任務時,也更容易服從他人的錯誤判斷。後續實驗發現,他們的大腦皮層活動性較高的區域,與身體創傷所激活的腦區是一樣的(圖11-1)。被排斥,看來是一種實在的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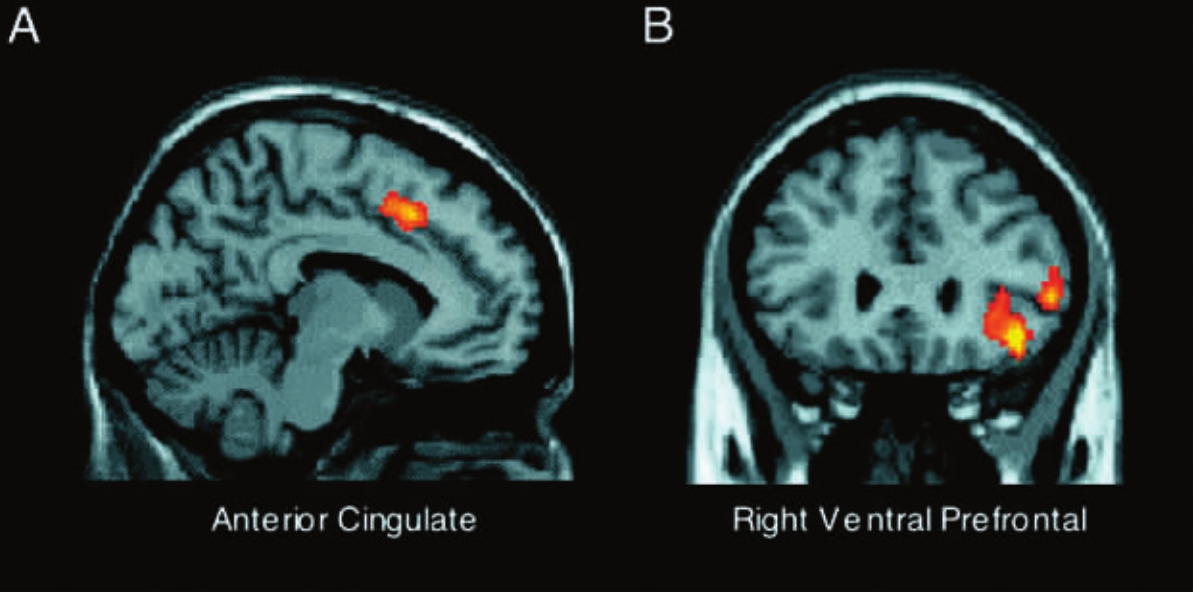
圖11-1 遭拒絕的創傷
艾森伯格等人(Eisenberger,Lieberman,& Williams,2003)報告說,社會排斥誘發了與身體疼痛所致的相似的大腦反應。
威廉斯和他的四個同事(2000)甚至還發現,若其中四人約定,某天他們都不理睬某人,則那個人也會感到因受排斥而帶來的壓力。他們原以為,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玩的角色扮演遊戲,但事實與之相反,模擬的排斥情境也會使工作中斷,妨礙令人愉快的社會功能的產生,甚至“引起暫時的擔憂、焦慮、偏執和通常的精神衰弱”。這與人們期望要去參加一個充滿歡聲笑語的角色扮演遊戲時的反應正好相反。可見,內心深處的歸屬需要得不到滿足,就會使我們感到不安。
什麼造就了友誼和吸引
什麼因素孕育著喜歡和愛情呢?讓我們來討論那些有助於最初的人際吸引的因素:接近性、外表吸引力、相似性和被喜歡的感覺。
什麼因素使一個人喜歡或愛另一個人呢?有關人性的問題中,沒有比這個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了。肥皂劇、流行音樂、小說,以及我們的日常交談中,愛情之花的綻放與凋零是永恆的話題。在我還不知道社會心理學這一領域之前,我就已經記得戴爾·卡耐基關於“如何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的祕訣了。
以喜歡和愛情為主題的文章太多了,幾乎所有可能的解釋——和對其對立面的解釋——都已經被闡述過。對多數人來說——也包括你——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喜歡和愛情呢?不見面使彼此的心更加炙熱,還是“眼不見,心不念”呢?因為喜歡而吸引,還是因為吸引而喜歡?漂亮的外表重要嗎?什麼因素促進了你與他人的親密關係?下面,我們先討論那些有助於友誼建立的因素,然後再討論如何維持和加深關係,從而滿足我們的歸屬需要。
接近性
兩個人能否成為朋友?接近性 (proximity)是一個強有力的預測源。儘管接近也可能誘發敵意,大多數攻擊和謀殺都發生在住得很近的人們中間,但接近性更容易產生喜歡。對於那些沉浸於神祕的浪漫愛情幻想的人來說,接近也許是乏味的;但是社會學家已經證實,大多數人的婚姻對象是那些和他們居住在相同的小區,或在同一個公司或單位工作,或曾在同一個班裡上過課的人(Bossard,1932;Burr,1973;Clarke,1952;Katz & Hill,1958)。環顧四周想一想,如果你要結婚的話,他或她也很可能是居住、工作或學習在你步行可及範圍之內的人。
相互交往
事實上,地理距離並不是關鍵,功能性距離——人們的生活軌跡相交的頻率——才是關鍵。我們常常與那些共享居住區的入口、停車場和娛樂場所的人成為朋友。隨機分配到同一宿舍的大學生,當然不可避免地頻繁交往,所以他們更可能成為好朋友而不是敵人(Newcomb,1961)。這樣的交往能使人們尋求彼此的相似性,感受對方的喜愛並把自己和他們知覺為一個社會的單元。
我所在的大學裡,男生和女生曾經住在校園的兩頭,可以理解,他們經常抱怨缺乏異性朋友。現在,他們住在同一宿舍區的不同地方,並共享過道、休閒室和洗衣設備,男生和女生之間的友誼較之此前多得多了。所以,如果你剛到一個城市而且想交朋友,就嘗試一下去租靠近郵筒的房子,坐靠近咖啡壺的桌子,在靠近主要建築的停車點停車,這些都是幫你建立友誼的基石。
這種接觸的偶然性有助於解釋下面這個令人驚奇的發現。試想一下,如果你有一個孿生同胞,他(她)已經與某人訂婚,你(有那麼多的地方與他或她相似)難道不會覺得自己也會愛上那個人嗎?答案卻是否定的。萊肯和奧克·特利根(Lykken & Tellegen,1993)報告說,只有一半的孿生同胞說他們確實喜歡自己同胞的選擇,但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說“我可能會愛上我孿生同胞的未婚妻(或未婚夫)”。萊肯和特利根猜測,浪漫的愛情常常更像雛鴨的印刻,只要是經常與我們在一起,我們會愛上幾乎是任何一個與自己有著大致相同的人格特徵並且會回報我們感情的人。
為什麼接近會誘發喜歡呢?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易得性;很顯然,我們很少有機會認識一個不同學校的人或住在另一城市的人。但是事實遠不限於此,大多數人更喜歡他們的舍友,更喜歡隔壁的人,而不是隔了一個房間的人。而隔著幾個門或是住在樓下,還沒有遠到令人感到不便的地步。此外,那些距離接近的人,就像容易成為朋友一樣,也容易成為敵人。那麼,為什麼接近性更容易培育感情而不是滋生仇恨呢?
對相互交往的預期
前面我們已經注意到,接近性能使人們發現共性並交換回報。更重要的是,僅僅是對相互交往的期待 就可以引發喜歡。達利和伯奇德(Darley & Berscheid,1967)發現了這一點。他們以明尼蘇達大學的女生為被試,向她們提供一些關於另兩位女生的模糊信息,並告訴她們待會兒須與其中的一位進行親密的交談。然後問她們對那兩名女生的喜歡程度。結果發現,被試更偏好須與之見面的那位女生。對與一個人約會的預期也能促進喜歡(Berscheid & others,1976)。甚至那些大選中落敗方的支持者,也會發現自己對於獲勝方——現在是他們的對立方——的看法也有所改善(Gilbert & others,1998)。
這種現象具有適應性的意義。預期的喜歡——期望某人是令人喜愛的和容易相處的——能增加與之建立互惠關係的機會(Knight & Vallacher,1981;Klein & Kunda,1992;Miller & Marks,1982)。我們更喜歡那些經常見面的人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的生活充滿了與他人的關係,並不是所有的都是我們能選擇的,但我們卻必須與他們——室友、兄弟姐妹、祖父母、老師、同學、同事等進行持續的交往。喜歡他們必定有助於和他們建立更好的關係,反過來,這樣的關係也造就了更快樂、更有成就的生活。
曝光效應
接近性引發的喜歡不僅是因為接近性能產生相互交往和預期的喜歡,而且還有另一個原因:200多個實驗結果顯示,熟悉不會導致輕視。這和一個古老的諺語正好相反。事實上,熟悉誘發了喜歡(Bornstein,1989,1999)。對於各種新異刺激——無意義音節、漢字、音樂片段、面孔——的曝光 (mere exposure)都能提高人們對它們的評價。虛構的土耳其文字,諸如nansoma、saricik 和afworbu ,比真正的文字iktitaf、biwojni 和kadirga 意味著更好還是更不好的事物呢?密歇根大學的學生接受了羅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1968,1970)的測試,結果顯示,他們更加偏好那些出現頻率高的單詞,看到無意義詞語或中國表義文字的次數越多,他們便認為這些字詞表示的意思也越積極(圖11-2)。這使我萌發了做一個課堂驗證的想法,先是週期性地在屏幕上用動畫呈現某些無意義詞語,在學期末,學生們對這些“詞語”的評價比那些他們從沒見過的無意義詞語的評價要更積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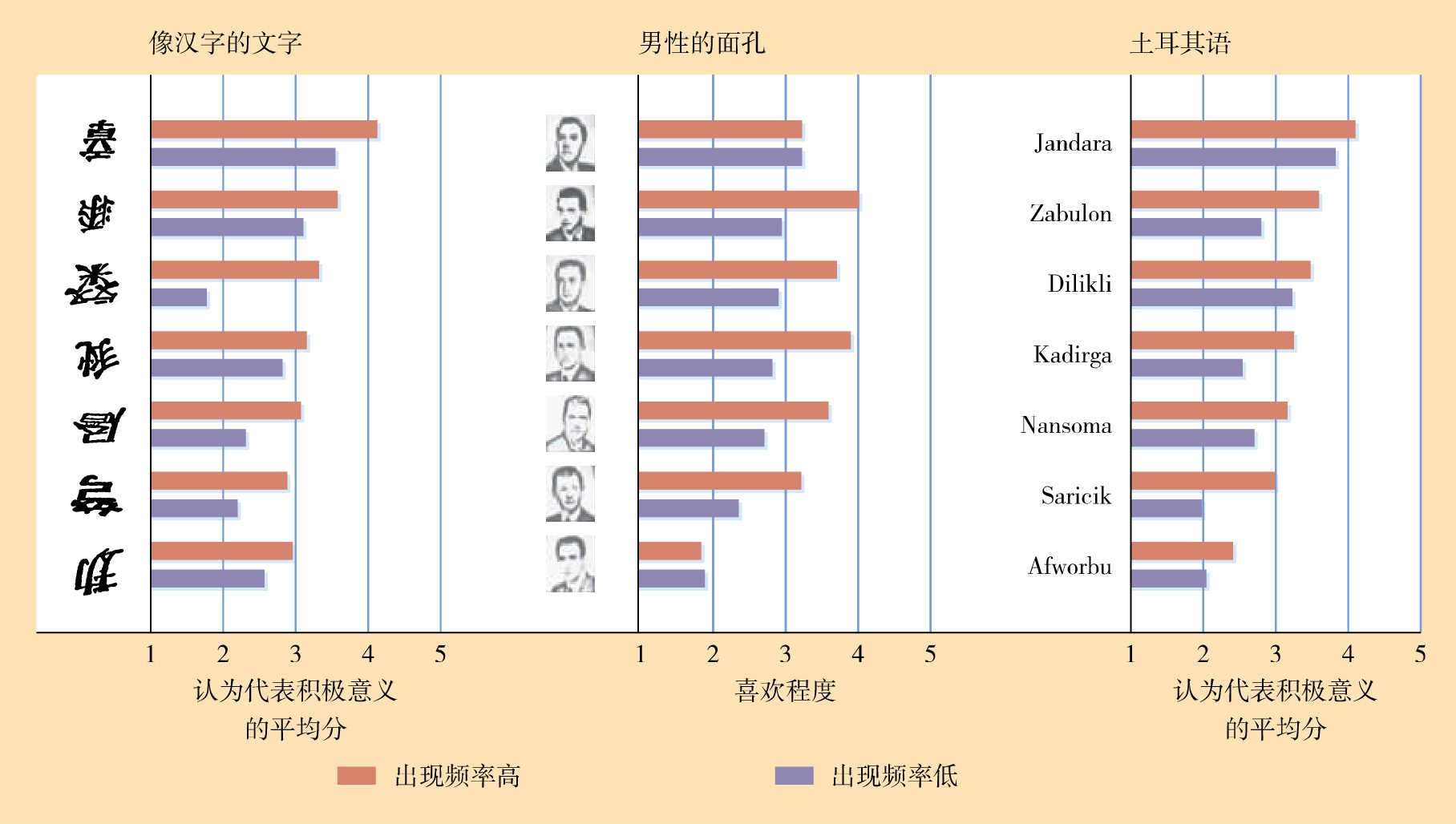
圖11-2 曝光效應
在多次呈現刺激之後,學生們對刺激的評價(此處呈現了樣本中的一個)更為積極。
資料來源:from Zajonc,1968.
請考慮一下,你最喜歡字母表裡哪些字母?不同國家、不同語言和不同年齡的人都偏好他們名字中的字母,以及那些在母語裡頻繁出現的字母(Hoorens & others,1990,1993;Kitayama & Karasawa,1997;Nuttin,1987)。法國學生把大寫字母W評價為最不喜歡的字母,而W正是法語裡最不常見的。日本學生不但偏好他們姓名中的字母,而且還偏好與自己生日對應的數字。當然,這種“姓名效應”也不單純是“曝光效應”的反映——有關內容詳見“聚焦:喜歡與自己相關的事物”。
曝光效應違背了我們通常對厭倦的預測——重複聽到的音樂和反覆吃的食物會引起厭倦——興趣減低(Kahneman & Snell,1992)。除非這種重複是沒完沒了的(有一句朝鮮諺語:“即使是最好的音樂,聽多了也會厭倦”),否則通常它的確會使喜歡增加。當巴黎的埃菲爾鐵塔在1889年完工時,曾被嘲笑是奇形怪狀的東西(Harrison,1977)。今天,它卻變成了巴黎倍受喜愛的標誌物。
這種改變使人們對那些對新事物的最初反應感到好奇。到巴黎盧浮宮的遊客是真的欣賞名畫《蒙娜麗莎》呢,還是他們僅僅是樂於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也許二者都有:瞭解她是為了喜歡她。哈蒙-瓊斯和艾倫(Harmon-Jones & Allen,2001)利用實驗證實了這一現象。他們給被試呈現一個女性的面龐,發現隨著觀看次數的增多,被試的面部(微笑的)肌肉變得更活躍了。曝光效應誘發了愉快的情感。
扎伊翁茨和他的同事報告說,甚至當人們未能意識到他們所接觸者為何的時候,熟悉也能引起喜歡(Kunst-Wilson & Zajonc,1980;Moreland & Zajonc,1977;Wilson,1979)。事實上,當人們無意識地接受刺激時,曝光效應往往會更強烈(Bornstein & D'Agostino,1992)。在一項實驗中,女學生使用耳機一隻耳朵聽一段散文,然後要求她們大聲重複聽到的詞彙,並和書面文字對照來檢查錯誤。同時,簡短、新穎的樂曲播放給她們的另一隻耳朵。這個程序要求被試把注意力集中在言語材料上,而忽略樂曲。隨後,把聽過的這些樂曲分散在其他類似的但是之前並沒有播放過的樂曲中呈現給被試。結果發現,這些女學生聽到後,雖然不能將先前聽過的樂曲辨認出來,但對它們卻是最為喜歡的。
聚焦 喜歡與自己相關的事物
人類總是喜歡對自己感覺良好,而且一般來說,我們都是這個樣子。我們不但有一種自我服務的傾向(第2章),而且還表現出佩勒姆等人(Pelham,Mirenberg,& Jones,2002)所說的那種固有的自我中心主義:我們喜歡與自己相關的事物,不但包括我們姓名中的字母,還包括潛意識中與自己有關的人、地方和其他東西(Jones & others,2002;Koole & others,2001)。
佩勒姆及其同事報告,這種偏愛會對我們生活中的重大抉擇,包括我們的住址、職業等產生微妙的影響。費城(Philadelphia)中名叫傑克的人只是傑克遜維爾(Jacksonville,一個比費城小的城市)城中的2.2倍,但叫菲利普(Philip)的人卻是它的10.4倍。同樣的,弗吉尼亞海灘(Virginia Beach)有更多的人名叫弗吉尼亞(Virginia)。
這一現象,是否有可能只是反映了為孩子起名時會受其居住地的影響?是否喬治亞州(Georgia)的居民就更喜歡為他們的孩子取名為喬治(George)或者喬治亞(Georgia)呢?可能是這樣的,但這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各州都相對有更多人的姓氏 與州名是相似的。例如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姓以Cali開頭(如Califano)的人佔了更大的比例;同樣,在加拿大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姓與城市名有交迭的人也比想像的多;多倫多(Toronto)就有更多人的姓是以Tor開頭的。
此外,很多叫“喬治亞”的女性傾向於搬家 到喬治亞州,而叫弗吉尼亞的人則傾向於搬家到弗吉尼亞州。這種遷移特點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住在聖路易(St. Louis)的人中,姓路易斯(Louis)的人比全國平均數高49%,以及姓希爾、帕克、比奇、萊克或羅克的人大都喜歡居住在城市名包含了他們姓的地方,如帕克城等。佩勒姆等人推測,“市名與自己的姓名相像的城市對人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還有不可思議的,這並非憑空編造,人們好像還偏愛與他們的姓名有關的職業。在美國,傑裡、丹尼斯(Dennis)和沃爾特這些名字的普遍程度是相同的(這些名字中的每一個均佔總人口的0.42%),然而,在美國的牙醫(dentists)中,叫丹尼斯的人卻幾乎是叫傑裡或沃爾特的兩倍。叫丹尼斯的牙醫也是叫貝弗利或塔米(與其普遍程度相同)的2.5倍。叫喬治(George)或傑弗裡(Geoffrey)的人在地學家(Geoscientist,包括地質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地球化學家)中佔了更大的比例。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姓以B開頭的人大都支持布什(Bush)而姓以G開頭的人大都支持戈爾(Gore)。
閱讀了基於固有的自我中心的偏愛的文獻後,我不得不停筆仔細考慮一下:難道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去Fort Mayers旅行的原因嗎?為什麼我寫了關於心境(moods)、媒體(media)以及婚姻(marriage)方面的文章?為什麼我要與默多克(Murdoch)教授合作?
請注意,這個實驗發現,關於刺激的有意識的判斷,並未對人們的所見所聞提供什麼線索,而人們的直接感受對此則頗有助益。人們大概能夠馬上記起喜歡或厭惡的事或人,但卻意識不到喜歡或厭惡他們的原因。扎伊翁茨(Zajonc,1980)認為,情緒相比于思維是更即時的東西。扎伊翁茨的驚人設想——情緒半獨立於思維(“情感可以先於認知”)——在最近的腦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情緒和認知可由不同的腦區引發。破壞猴子的杏仁核(一個與情緒有關的腦結構)以後,它的認知功能受到了損害,但情緒反應卻保持完好(Zola-Morgan & others,1991)。
扎伊翁茨(1998)指出,曝光效應具有“巨大的適應意義”。它是一種可以預定我們的吸引和依戀傾向的“硬件”現象。它有助於我們的祖先把熟悉的或安全的事物,與不熟悉的或不安全的事物區分開來。曝光效應還使我們在評價他人時戴上有色眼鏡:我們喜歡熟悉的人(Swap,1977)。當然,曝光效應也有缺點,正如我們在第9章中提到的,對陌生人的警惕——這能解釋當人們面對那些不同於自己的人時,為什麼會產生一種原始的、自動的偏見。害怕或帶偏見的感受並不總是刻板印象的表現;有時候,刻板印象是為了對直覺的情感進行辯護而出現的。
我們也更喜歡以常見的方式展現的自我。在一個有趣的實驗中,米塔等人(Mita,Dermer,& Knight,1977)給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的女生拍了照片,隨後給她們呈現一張真實的照片和將其做了鏡像變換(左右反轉)後的照片。研究者詢問她們更喜歡哪個形象,結果發現,她們更喜歡那張鏡像版的——這是她們習慣的形象(難怪我們的照片看上去從沒有覺得完全稱心的)。但當給這些女生呈現她們最要好的朋友的照片(同樣是兩種形式)時,她們報告說更喜歡那張真實的照片——即她們習慣的形象。
廣告商和政治家們充分利用了這種效應。即使人們對某一商品或候選人沒有什麼強烈的感情,僅僅通過簡單的重複,也可以增加商品的銷量或得票率(McCullough & Ostrom,1974;Winter,1973)。如果一個商品在廣告中沒完沒了地出現,那麼,購物者常常會對該商品做出不假思索的、自動化的偏愛反應。如果候選人不為人們所熟悉,那麼,一般而言,那些在媒體上曝光最多的候選人更容易獲勝(Patterson,1980;Schaffner & others,1981)。懂得曝光效應的政治戰略家,通常使用簡短的廣告來代替理由充分的長篇大論,在廣告中突出強調候選人的名字和錄音片段等信息。
1990年,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德高望重的法官基思·卡洛在競選中輸給了一個無名的對手查爾斯·約翰遜,吃的就是這個虧。約翰遜是一個沒有名氣的律師,負責處理一些情節輕微的刑事案件和離婚案件,他參加競選的口號是“法官需要被挑戰”。兩個人都沒有開展競選活動,媒體也沒有對這次競選進行報道。在投票的那天,兩個候選人的名字相繼出現在選民面前,沒有做任何區分。結果,約翰遜以53%比37%的優勢勝出。這個結果令法律界很吃驚,事後,卡洛解釋說:“名叫約翰遜的人比叫卡洛的人要多得多”。的確,該州規模最大的報紙統計發現,在當地的電話登記薄中,就有27個叫查理·約翰遜的人。還有一個叫查爾斯·約翰遜的地方法官。此外,在鄰近的一個城市,有一個電視新聞節目的主持人也名叫查爾斯·約翰遜,他主持的節目在全州的有線電視上都可以看到。因此,在兩個陌生的人之間被迫做出選擇的時候,大多數選民偏向於選擇讓人感覺更舒服、更熟悉的名字——查爾斯·約翰遜。
外表吸引力
在約會中,你看重的是對方的哪些特質呢?誠實、美貌、個性、幽默,還是談吐?智慧的人們並不在意諸如美貌之類的外在特徵;他們知道“美麗紮根於內心深處”,而且“你不可以通過封面來判斷一本書的好壞。”至少,他們懂得應該 如何去感受“美”,正如西塞羅的忠告:“抵制外表”。
要說外貌不重要,其實,那只不過是我們拒絕承認現實對我們的影響的又一個例證而已。因為現在有許多研究都顯示:外貌的確 是很重要的。外貌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了一致性和普遍性的特點,這的確令人感到不安。然而事實上,美貌的確是一種財富。
吸引力和約會
不管大家喜歡與否,的確存在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一位年輕女士的外表吸引力可以中度預測她約會的次數,而一位男性的外表對他約會次數的預測力則要略小一些(Berscheid & others,1971;Krebs & Adinolfi,1975;Reis & others,1980,1982;Walster & others,1966)。而且,相比於男性,更多的女性表示,她們寧願選擇一個相貌平平但很熱誠的配偶,而不是一個外表好看卻很冷淡的人(Fletcher & others,2003)。這是否表明女性,正如很多人所猜測的那樣,能更好地遵從西塞羅的忠告呢?還是說它僅僅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約會邀請更常是由男士發出的?如果讓女性在不同的男性中選擇出她們所喜愛的類型,那麼,外貌對於她們來說,是不是跟對於男士一樣重要呢?哲學家羅素(Russell,1930,p.139)不這樣認為:“整體上來說,女人傾向於因性格而愛上男人,男人則傾向於因外表而愛上女人。”
為了考察男人是否真的更在意外表,研究者分別給男、女學生提供了有關某一異性的一些信息,包括一張照片。或者,研究者簡單地介紹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相互認識,並詢問他們是否有興趣跟對方約會。這些實驗的結果表明,男人的確更在意異性的外表吸引力(圖11-3)(Feingold,1990,1991;Sprecher & others,1994)。也許正因為如此,女性才如此在乎自己的外表,進行外科整形的人當中90%都是女性(ASAPS,2003)。當然,女性同樣也會注意男性的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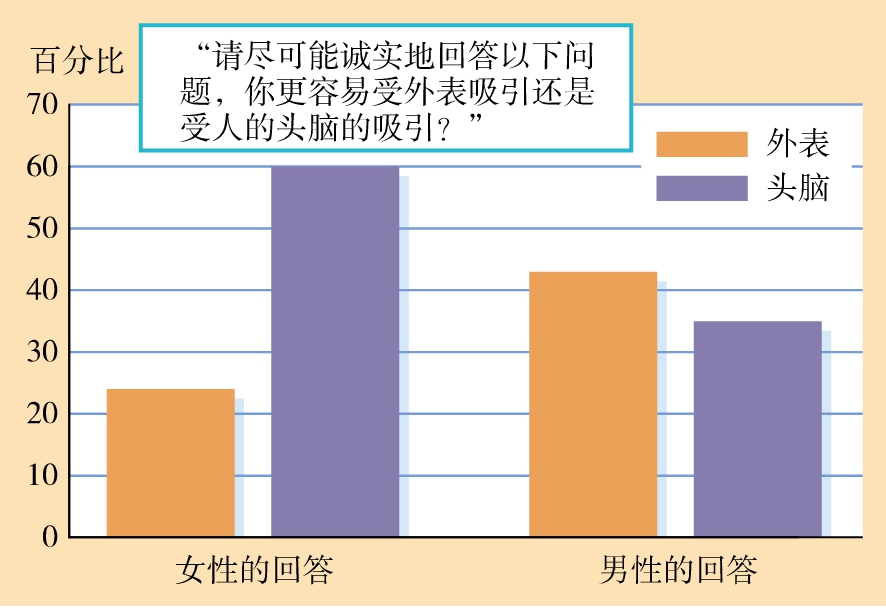
圖11-3 女性和男性報告的最在意的品質
資料來源:Fox News/Opinion Dynamics Poll of registered voters,1999.
哈特菲爾德等人(Hatfield & others,1966)進行了一項大型研究,他們在明尼蘇達大學“迎新周”裡舉辦了一個計算機舞會,752名一年級的學生參加了這個舞會。研究者給每個學生都進行了人格和能力測試,然後對他們進行隨機匹配。在舞會那天晚上,一對對被試跳舞聊天,為時兩個半小時。在短暫的間歇中,研究者讓他們評價自己的舞伴。人格和能力測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預測人們的吸引力呢?人們是更喜歡那些具有較高自尊或較低焦慮感的人,還是喜歡那些在內、外性向方面與自己不同的人?研究者考察了各種可能性。如果說他們能夠非常肯定哪個因素的重要作用的話,那就是個人的外表吸引力(研究者在實驗前對被試的外表吸引力進行了評定)。某位女性外表的吸引力越大,男性就越喜歡她,並且願意跟她繼續約會。同樣,男性的外表吸引力也有這樣的效果。美貌能使人愉悅。
匹配現象
並非人人都能與一位魅力非凡的人廝守終身。人們是怎樣結成連理的呢?伯納德·默斯坦等人(Murstein & others,1986)的研究表明,人們一般與跟自己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結成伴侶。研究表明,夫妻、約會對象,甚至志趣相投者之間的吸引力都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Feingold,1988)。人們選擇朋友,尤其在選擇終身伴侶的時候,通常傾向於選擇那些不僅在智力上,而且在外表吸引力方面都能與自己匹配的人。
很多實驗都證實了這種匹配現象 (matching phenomenon)的存在。在知道對方可以自由地同意或拒絕的情況下,在選擇與誰接近時,人們通常會接近那些在吸引力方面與自己大致匹配(或者對方的吸引力高出自己不多)的人(Berscheid & others,1971;Huston,1973;Stroebe & others,1971)。正如格雷戈裡·懷特(White,1980)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進行的有關約會的研究結果:外表上的匹配將有利於良好關係的發展和維持。九個月後,那些外表吸引力最為相似的人們,更有可能墜入情網。
那麼,哪些人群在吸引力上最匹配呢——是已婚的伴侶,還是約會的對象呢?跟其他研究者一樣,懷特發現:已婚的伴侶之間更匹配。
也許你會想,有很多夫妻的吸引力並不匹配,但他們卻很幸福。在這種情況下,吸引力較差的一方常常具有其他方面的品質,可以對自己的外表進行補償。每一方都把自己的品質拿到社會市場中,對各自品質的價值進行了合理的匹配。徵婚廣告充分展示了這種品質交換(Cicerello & Sheehan,1995;Koestner & Wheeler,1988;Rajecki & others,1991)。男性通常強調自己的財富或地位,並且希望尋求年輕和有吸引力的女性;女性則相反,例如一則廣告這樣寫道:“一位有吸引力、聰明的女子,26歲,身材苗條,欲覓熱情而有穩定工作的職業男士。”那些在廣告中強調自己的收入和學歷的男性,以及強調自己的年輕和美貌的女性,通常能得到更多的反饋(Baize & Schroeder,1995)。這種品質匹配的現象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年輕貌美的姑娘通常會嫁給一個社會地位較高的年長男人(Elder,1969)。
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這種外表吸引力效應是否完全來源於性的吸引力?顯然不是!休斯頓和布爾(Houston & Bull,1994)讓化妝師為一個實驗助手整容,使得實驗助手的臉上看起來有一道明顯的疤痕,或青腫,或有胎記。在格拉斯哥(Glasgow)客運地鐵線上,當這位助手以醜陋的面貌出現時,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都不願意坐在她旁邊。研究者還發現,就像成人喜歡有吸引力的成人一樣,小孩之間的喜愛也受到外表吸引力的影響(Dion,1973;Dion & Berscheid,1974;Langlois & others,2000)。通過考察嬰兒注視他人的時間,研究者發現,即便是嬰兒也偏愛有吸引力的面孔(Langlois & others,1987)。三個月大的嬰兒還沒有看過《護灘使者》(Baywatch )或者《單身漢》(Bachelor )之類的影片,他們不會受到這些經驗的影響。
成人在對兒童的態度中也顯示出了相同的偏好。克里福德等人(Clifford & Walster,1973)在密蘇里州做了一個實驗,他們給五年級的老師提供了有關某個男孩或女孩的信息,並且附有照片。這些信息的內容相同,但是照片卻分為有吸引力和無吸引力兩種。在相同的信息之下,老師們傾向於認為那些有吸引力的孩子在學習上更聰明、更成功。讓我們來想像一下,你正在負責監管操場,必須訓練一個很不守紀律的孩子。你是否會像卡倫·戴恩(Karen Dion,1972)研究中的女被試那樣,對那些沒有吸引力的孩子表現出更少的熱情和關注?令人遺憾的現實是所謂的“巴特·辛普森效應”(Bart Simpson effect)——大多數人都認為,長相一般的孩子,他們的才幹和社交技能都不如那些漂亮的同齡人。
而且,我們也以為漂亮的人擁有社會所需的某些其他特質。雖然漂亮並不一定讓人聯想到正直或關心他人,然而,在其他各方面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我們仍會猜測漂亮的人會更快樂、性感熱情,更開朗、聰明和成功(Eagly & others,1991;Feingold,1992b,Jackson & others,1995)。在倡導集體主義的韓國,人們很看重正直的和關心他人的品質,並且,人們往往把這些品質與個人的吸引力相聯繫(Wheeler & Kim,1997)。
綜上所述,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physical-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美的就是好的。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形成了這種刻板印象。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是美麗的——也是善良的。女巫和繼母是醜陋的——同時也是邪惡的。“如果你想得到某個非本家庭成員的愛,那麼,長得漂亮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一個八歲的女孩猜測。當問一個幼兒園裡的女孩,美麗意味著什麼時,她回答說:“就像小公主那樣,人人都喜歡你”(Dion,1979)。讓我們想想黛安娜王妃,就更能理解這種現象了。
既然外表吸引力如此重要,那麼,永久地改變一個人的外表,就將會改變人們對待他的方式。但是,改變一個人的外貌是否合乎道德?整形外科醫生和正牙醫生每年都要給上百萬的人做手術。牙齒變得整齊,鼻子變得挺拔,頭髮再生、染色,拉緊面部皮膚,去除多餘脂肪,以及隆胸、使胸部堅挺或者減小等等,是否在經歷過這樣的改變之後,一個原本對自己不滿意的人就會變得快樂呢?比起20世紀70年代來,儘管婦女在化妝品和整容方面的投資大大增加,但是,對自己的外貌深感不滿的人也越來越多(Feingold & Mazella,1998)。
為了檢驗整容的效果,邁克爾·卡利克(Michael Kalick,1977)以哈佛的學生為被試做了一個實驗,他讓學生們看八位女士整型手術前後所拍攝的側面照片,然後對她們進行評價。結果表明,被試不僅認為女士們手術後的外表更有吸引力,而且也認為她們更善良、更敏銳、更性感熱情、更有責任感,更討人喜歡等等。伯奇德(Ellen Berscheid,1981)則指出,雖然整容可以提升自我形象,但也會帶來一時的麻煩:
大多數人——至少那些沒有整過容的人——會繼續相信,在別人如何對待自己方面,外表的吸引力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對於那些整過容的人來說,則很難否認或低估外表的吸引力在他們生活中產生的影響——事實上,即使這種變化是往好的方向,它也會令人不安。
我們說吸引力很重要,是在假設其他條件都一樣的情況下來談論的。並不是說,任何時候外表的吸引力都比其他任何特質更重要。一些人通過外表來評價他人,另一些人則不是這樣(Livingston,2001)。而且,吸引力可能對第一印象的影響最大。當然,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隨著社會的變動性增大,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越來越短暫,第一印象就顯得愈加重要了(Berscheid,1981)。
雖然很多面試考官可能會加以否認,但是,吸引力和外表的修飾的確影響著面試時的第一印象(Cash & Janda,1984;Mack & Rainey,1990;Marvelle & Green,1980)。這個現象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有吸引力的人,通常能獲得聲望較高的工作,能賺更多的錢(Umberson & Hughes,1987)。羅瑟爾等人(Roszell & others,1990)在加拿大全國範圍內進行取樣,讓面試考官對樣本的吸引力進行了五點量表的等級評定(1表示相貌平平,5表示非常有吸引力)。結果發現,在吸引力上的得分每增加一個單位,每年平均能多賺1988美金。弗里茲等人(Frieze & others,1991)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們根據照片,對737個MBA畢業生的外表吸引力進行了五點評價,結果表明,吸引力得分每增加一個單位,男士可多掙2600美元,女士則可多掙2150美元。
漂亮的人是否真的具有讓人滿意的特質呢?還是如同列夫·托爾斯泰所說,這是“一個奇怪的錯覺……認為美的就是好的”?然而,有時候這種刻板印象的確得到了事實的證明。研究表明,有吸引力的孩子和青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不那麼拘謹、更加外向,而且社交技能更好(Feigold,1992b;Langlois & others,2000)。戈德曼和劉易斯(Goldman & Lewis,1977)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讓佐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的60名男生每人跟3位女生分別在電話裡聊5分鐘。之後,男生和女生都對和自己聊天的人進行評價,他們都沒有見過對方。結果,被評為最具外表吸引力的人,是那些最有社交技能和最討人喜歡的人。外表有吸引力的個體,也往往更受歡迎,更外向,更具典型的性別特徵(如果是男性,則更有傳統的男人氣概;如果是女性,則更有傳統的女性氣質)(Langlois & others,1996)。
有吸引力的人和無吸引力的人,他們之間的微小差異很可能來源於自我實現的預言。有吸引力的人通常更受重視,更討人喜歡,並且,大多都因此而變得更自信(正如第2章裡的一個實驗:男士對沒見過面,但被他們認為 是很有吸引力的女士,做出了熱情的迴應)。這樣看來,影響你社交技能的關鍵,並不在於你看起來怎樣,而在於別人怎樣看待你,以及你對自己的感覺怎麼樣——你是否接納自己,喜歡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雖然長得漂亮有這麼多的好處,但是,人際吸引的研究者哈特菲爾德等人(Hatfield & Sprecher,1986)認為,漂亮同樣也會帶來很多麻煩。特別有吸引力的人可能會遭受令人不快的性騷擾、同性的嫉妒和排斥。他們可能並不確定別人對他們的反應,到底是基於自己的能力、內在品質,還是僅僅基於外表,而美貌總是會隨時光而逝的(Satterfield & Muehlenhard,1997)。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可以依賴自己的外表,往往就不太願意發展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了。伯奇德說,如果相貌平平且出奇矮小的電學天才查爾斯·施坦因梅茨 [2] ,也遭遇過像丹澤爾·華盛頓 [3] 經歷的社交誘惑的話,我們現在是不是仍然只能用蠟燭來照明呢?
誰具有吸引力
我曾經把吸引力描述成一種像身高那樣的客觀特徵,某些人擁有的多些,而某些人擁有的少些。但嚴格說來,吸引力指的是,無論何時何地,人們所發現的任何具有吸引性的特徵。當然,這是有所變化的。世界小姐的選美標準就不可能適用於世界上的所有人。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時代,人們會給鼻子穿孔、拉長脖子、染髮、紋身、瘋狂地吃東西以使自己變得性感,或節食使自己變得苗條,用皮外衣包裹自己使胸部看起來小些,或使用硅膠和填充乳罩使胸部看起來大些等等。
儘管有這麼多的變化,但是朗格盧瓦等人(Judith Langlois & others,2000)認為,對於“誰有吸引力和誰沒有吸引力這個問題,在同一文化內部或不同文化之間,仍然存在強有力的共識”。當男性評價女性的時候,他們關於吸引力的一致程度非常高,但是當男性評價男性的時候,這種一致性就降低了(Marcus & Miller,2003)。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吸引力其實就是完美的平均。得克薩斯大學的朗格盧瓦等人(Langlois & Roggman,1990,1994)以及利特爾等人(Little & Perrett,2000)所領導的研究小組,與聖安德魯斯大學的Ian Penton-Voak合作,他們對大量的面孔進行了數字化處理,並用計算機對它們進行了平均。結果勿庸置疑,與幾乎所有的真實面孔相比,人們認為合成的面孔更具有吸引力。
研究背後的故事:
伯奇德關於吸引力的研究
我真切地記得那個下午,我開始理解外表吸引力的深刻含義。研究生卡倫·戴恩(現在已經是多倫多大學的教授了)聽說我們兒童發展研究所的一些研究者已經收集了幼兒園孩子們受歡迎的等級評定,並給每個孩子都拍了照片。雖然這些孩子們的老師和看護者都勸我們說“所有的孩子都是美麗的”,不應對他們的外表吸引力加以區別,但是戴恩還是建議,我們應該評價一下每個孩子的外貌,並將它與孩子們受歡迎的程度聯繫起來。結果發現,我們最初的冒險是正中要害的:有吸引力的孩子正是那些受歡迎的孩子。事實上,這種效應遠比我們和其他人所想像的還要強烈,研究者現在仍在尋求它們背後隱含的意義。
由計算機平均出來的面孔也趨向於完美的對稱——這是具有吸引力,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人所具有的另一個特徵(Gangestad & Thornhill,1997;Mealey & others,1999;Shackelford & Larsen,1997)。由羅茲(Gillian Rhodes,1999)和Ian Penton-Voak(2001)所帶領的研究小組發現:如果你能把你的任意半邊臉與它的鏡像結合——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完美對稱的新面孔——那麼你的外貌特徵就會有些許的改善。如果把多個這樣對稱的面孔再加以平均,你就會得到一個更加漂亮的面孔。因此,在某些方面,完美的平均是很有吸引力的。哈伯斯塔特和羅茲(Halberstadt & Rhodes,2000)報告說,甚至對於狗、鳥和手錶而言也是如此。例如,人們評價被平均後的狗時,也同樣會認為它是有吸引力的。
完美的平均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我們也會覺得那些具有吸引力的人比那些非典型的、沒有吸引力的人看起來更熟悉,這是莫寧(Monin,2003)所觀察到的結果。但是,更有吸引力的人卻是對有吸引力的特徵進行適度誇大了的面孔。因此,對於那些由計算機生成的面孔,她們中最漂亮的人往往都傾向於高度的女性化,擁有比平均面孔稍小的下巴,更豐滿的嘴脣和更大的眼睛(圖11-4)。

圖11-4 你覺得這兩個面孔中哪個更有吸引力?
生理心理學家維克托·約翰遜(Victor Johnson,2000)將16個白人女性的面孔進行平均,創造了左邊的面孔。然後他對女性面孔不同於男性面孔的那些地方稍微進行了誇大處理,得到右邊這個高度女性化的面孔。結果,大多數人都認為右邊的面孔更具有吸引力。
進化與吸引力 持進化觀的心理學家用繁殖策略來解釋這些性別差別(第5章)。他們認為,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美麗其實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健康、年輕和富於生殖能力。逐漸地,喜歡看起來富有生殖能力的女性的男性繁衍的後代,超過了樂意與青春期前和絕經後的女性結婚的男性。同樣,研究者認為,進化使女性也傾向於喜歡那些能顯現提供資源和保護能力的男性特徵。戴維·巴斯(Buss,1989)相信,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所研究的37種文化中的男性——從澳大利亞到贊比亞——都的確更喜歡那些能顯現生殖能力的女性特徵。而且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傾向於嫁給地位高的男性,以及為什麼男性都決心相互競爭以獲得名譽和財富來顯示自己的地位。諾曼·李等人(Norman Li & others,2002)報告說:在挑選伴侶時,男性希望女性要有適度的外表吸引力,而女性則希望男性擁有地位和財富,但兩性都喜歡有愛心的人和聰明的人。
進化心理學家還考察了男性和女性對暗示著生殖優勢的其他線索的反應:從古石器時代的小雕像,到今天雜誌上的裸體照片插頁,以及選美獲勝者的特徵來看,無論何地,男性都認為那些腰部比臀部窄30%的女性最有吸引力——這是一種與最高的性生育力相關的體形特徵(Singh,1993,1995a;Singh & Young,1995;Streeter & McBurney,2003)。那些削弱女性生殖能力的因素——營養不良、懷孕和絕經都會改變她們的體形特徵。
當判斷男性是否為可能的結婚對象時,女性也偏向於上述的腰臀比例,因為它暗示了健康和活力,而且在排卵期,女性會更加喜歡那些具有高度男性化特徵的男性(Gangestad & others,2003;Macrae & others,2002)。這就具有了進化的意義,正如戴蒙德(Diamond,1996)所說:一個肌肉發達的人要比一個骨瘦如柴的人更有可能獲得食物,更有可能建造房子以及更有可能擊退敵人。但是,今天的女性卻更喜歡高收入的男性(Singh,1995b)。
因此,在所有的文化中,美容業都是一個巨大而且不斷增長的行業。亞洲人、英國人、德國人和美國人,要求做美容手術的人都在飛速增長(Wall,2002)。例如,在美國,美容手術如抽脂術、隆胸術和肉毒毒素(Botox) [4] 注射在1997~2002年間增長了228%(ASAPS,2003)。比弗利地區(Beverly Hills)現在的美容醫師也已經是兒科醫師的兩倍多了(People ,2003)。很多有缺損或脫色牙齒的時髦而富有的人都會去重新換牙。越來越多的那些有著很多皺紋和鬆弛肌肉的人也是如此。
進化心理學家認為,我們是被原始的吸引力所驅動的。就像吃飯和呼吸一樣,吸引力和婚配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它不可能歸結為文化的偶然現象。
社會比較 雖然我們的婚姻心理學有其生物學的一面,但是吸引力並不只是取決於生物特性。什麼對你是有吸引力的?這還取決於你自己的比較標準。
肯裡克和古鐵雷斯(Kenrick & Gutierres,1980)讓他們的男性助手進入蒙大拿州立大學的男生宿舍,向學生解釋說,“我們的一個朋友這個星期要來,我們想給他介紹個女朋友,但是我們又不能確定,這個女生到底適不適合與他約會,所以我們想徵求你的意見……想請你在一個7點量表上進行評價,評價一下這個女生的吸引力。”然後,研究者向被試呈現了一張普通的年輕女性的照片,結果發現,那些剛剛看過了一部描述三位漂亮女性的電視劇《查理的天使》的男生,比那些沒有看過這部電視劇的男生對這個女生的評價要低。
實驗室研究也證實了這種“對比效應”。對於那些剛剛看過雜誌中裸體照片插頁的男性而言,普通女性,甚至他們妻子的吸引力都會減小(Kenrick & others,1989)。觀看誘發強烈性慾的色情電影同樣也會降低對自己伴侶的滿意度(Zillmann,1989)。性喚起可能暫時地 使異性看起來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觀看完美得可以打10分的或非現實的性描寫所產生的持續影響,會使伴侶吸引力降低——更有可能被評為6分而不是8分。
對比效應同樣也在我們的自我知覺過程中起作用。看到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同性之後,人們會覺得自己缺乏吸引力,而觀看一個相貌平平的同性之後,我們不太會產生這種感覺(Brown & others,1992;Thornton & Maurice,1997)。這種現象對於女性尤為明顯。但是,男性進行自我評價的願望也會因為接觸了一個更有權力、更成功的男性而變得不強烈。古鐵雷斯等人(1999)認為,應該感謝現代傳媒的存在,它使我們在一小時內可能看到“很多更有吸引力、更成功的人,而我們的祖先則要花費一年甚至是一生的時間才能看到那麼多有吸引力的人”。這種超乎尋常的比較標準也捉弄著我們,使我們低估伴侶和我們自己,使我們花費大量的金錢來化妝、減肥和進行整容手術。
我們所愛的人的吸引力 讓我們以一種樂觀的態度來結束我們對吸引力的討論吧。首先,一個17歲女孩的面部吸引力對她在30歲和50歲時的吸引力的預測力令人吃驚地低。有時,一個相貌平平的青少年,尤其是一個擁有熱情、迷人個性的人,成年後會變成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Zebrowitz & others,1993,1998)。
其次,我們不僅會認為有吸引力的人是討人喜歡的,而且會認為討人喜歡的人是有吸引力的。也許你會想起,當你越來越喜歡一個人時,他對你的吸引力也會不斷上升。而他們外表上的不完美之處也就不那麼明顯了。格羅斯和克羅夫頓(Gross & Crofton,1977)讓學生先閱讀關於某人討人喜歡或不討人喜歡的人格描述,然後再看這個人的照片。結果發現,那些被描述為熱情、樂於助人和善解人意的人看起來會更有吸引力。而那些與我們自己有著相似點的人也似乎更吸引人(Beaman & Klentz,1983;Klentz & others,1987)。
此外,還有情人眼裡出西施的現象:當一個女孩愛一個男孩時,她就會覺得他的外表越來越有吸引力(Price & others,1974)。而且,人們愛得越熱烈,他們就越不覺得任何其他異性吸引人了(Johnson & Rusbult,1989;Simpson & others,1990)。“草坪的另一邊可能更綠”,米勒和辛普森(Miller & Simpson,1990)說,“但快樂的園丁卻很少能注意到。”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說就是,當吉爾墜入情網時,她會覺得傑克比他的任何朋友都英俊。
相似性與互補性
從以上的討論來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列夫·托爾斯泰完全正確:“愛依賴於……頻繁的接觸,依賴於彼此的髮式,依賴於服飾的顏色和款式。”但是,當人們逐漸瞭解對方以後,其他的因素也會影響到熟人是否可以變成朋友。
物以類聚嗎
對於這一點,我們可能深信不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朋友、訂婚的情侶以及夫妻,會比那些隨機配對的人更可能擁有相同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此外,丈夫和妻子間的相似性越大,他們就越幸福而且越不容易離婚(Byrne,1971;Caspi & Herbener,1990)。這種相關關係是有趣的,但是它們之間孰因孰果卻還是個謎。到底是相似性導致了喜歡,還是喜歡導致了相似呢?
相似產生喜歡 為了弄清楚相似性與喜歡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做了一個實驗。想像一下:在一次校園聚會裡,勞拉和萊斯、拉里一起進行關於政治、宗教和個人好惡的討論。她和萊斯發現,他們幾乎對所有事情的觀點都是一致的,而她和拉里只在少數觀點上一致。之後,她回憶說:“萊斯真的很聰明……而且很可愛……希望我們能再見面。”在實驗裡,唐·伯恩(Byrne,1971)和他的同事抓住了勞拉體驗的實質。他們一次又一次發現,當某人的態度與你自己的越相似時,你就會越喜歡他。相似性產生喜愛,這不僅對於大學生,而且對於兒童和老人,對於不同職業以及不同文化的人也都適用。
對於那些對自己感到滿意的人則更是如此(Klohnen & Mendelsohn,1998)。如果你喜歡自己,就會更有可能與一個同樣喜歡你的人結為伴侶。
這種“相似性導致喜歡”的效應已經在現實生活情境中得到驗證。
在密歇根大學,紐科姆(Newcomb,1961)研究了兩組轉學的男生,每組17人,他們彼此不認識。但在共同度過了13周的寄宿公寓生活後,那些一開始就表現出高度相似性的被試更容易成為親密的朋友。研究發現,其中一組朋友包括5個文科生,他們的政治觀點都很自由,他們都很聰明;另一組朋友由3個保守而老練的人組成,他們都是工學院的學生。
格里菲特等人(Griffitt & Veitch,1974)模擬了人與人的認識過程,他們讓13名互不相識的男被試(這些被試都是有報酬的志願者)呆在一個臨時的處所裡,以此來了解他們相互認識的過程。通過了解每個人對不同問題的看法,研究者就能在高於概率的精確性水平上預測他們各自最喜歡的人和最不喜歡的人。
在香港的兩所大學裡,李和彭邁克(Lee & Bond,1996)發現,若同居一室的學生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個人特質,那麼舍友間的友誼在六個月內便可形成;而當他們將舍友看成與自己相似時尤其如此。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現實情況很重要,而對現實的知覺更重要。
人們不僅喜歡那些和他們想法一樣的人,而且還喜歡那些和他們行為一致的人。微妙的模仿會產生喜愛之情。你是否注意到過這樣的現象:當某人對某事的觀點與你一樣,並附和你的想法時,你就會感到些許友善和喜愛之情呢?瑞奇·範·巴倫及其同事(Baaren & others,2003a,2003b)認為這是常見的現象,在荷蘭的飯店裡,那些僅僅通過重複客人點菜方式來模仿客人的服務員,通常能得到更多的小費。此外,那些最初就喜歡某人的人,更可能喜歡模仿對方——例如,當對方做出擺腿或摸臉的動作時,他也會不知不覺地這樣做。傑西卡·萊金和塔尼婭·沙特朗(Lakin & Chartrand,2003)指出,模仿能增進和諧,對和諧的渴望也能增進模仿。
彼得·巴斯頓和斯蒂芬·埃姆倫(Buston & Emlen,2003)對近1000名與大學生年齡相仿的人進行了調查,他們發現:人們渴望相似伴侶的願望遠遠強於渴望漂亮伴侶的願望。外表漂亮的人也尋求外表漂亮的伴侶。有錢的人也想找到有錢的伴侶。家庭定向的人當然也渴望有一個以家庭為定向的伴侶。
所以,相似性產生了滿足感。物以類聚,的確如此。當你發現某個獨特的人與你擁有相同的想法、價值觀和願望時,當你發現心心相印的伴侶與你喜歡一樣的音樂、一樣的活動甚至一樣的食物時,你就會更確信這一點。
不相似導致不喜歡 們有一種偏好——錯誤的一致性偏好——傾向於認為別人與我們擁有同樣的態度。當我們發現某人與我們的態度不一致時,我們就會不喜歡這個人。同一政黨的人之所以在一起,與其說他們喜歡那些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其他成員,還不如說他們討厭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Rosenbaum,1986;Hoyle,1993)。
總之,不同的態度對喜歡的抑制作用甚於相似態度對喜歡的促進作用(Singh & others,1999,2000)。人們在自己的團體中,都期望成員具有相似性,人們發現自己很難喜歡一個與自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Chen & Kenrick,2002)。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戀人和舍友會隨著相處時間的增加,在對各種事情的情緒反應和態度上變得越來越相似(Anderson & others,2003;David & Rusbult,2001)。“態度一致性”有助於人們促進和維持親密的關係,也能夠導致同伴高估他們態度的相似性(Kenny & Acitelli,2001;Murray & others,2002)。在共同生活了40年之後,我妻子和我在思考問題方面已經非常一致,儘管其程度沒有我們設想的那麼高。雖然我們知道彼此在對待親密朋友和伴侶方面也偶爾有所不同,但是,“錯誤的一致性”傾向能夠幫助我們保持志趣相投的感覺。
人們把其他種族的人看做與自己相似還是不相似,也會影響人們的種族態度。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只要一群人將另一群人看成是“別人”——看成是說話、生活和思維方式都不同於己的異類——發生種族壓迫的可能性就會很大。事實上,除了像戀人那樣的親密關係以外,思想上的相似性所產生的吸引力比膚色的相似性更為重要。大多數白人表示,他們更喜歡、更願意與一個想法與自己一致的黑人,而不是和想法不同的白人共事(Insko & others,1983;Rokeach,1968)。白人越是認為黑人支持他們的價值觀,他們的種族態度就會越積極(Biernat & others,1996)。同樣,蒙特利爾的居民越認為某一個加拿大的人種與他們是相似的,他們就會更願意與該群體的成員建立聯繫(Osbeck & others,1996)。
詹姆斯·瓊斯(Jones,1988,2003,2004)指出,“文化種族主義”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為文化差異本來就是現實生活的事實。現實生活中既存在現實取向,自然表露,注重精神和由情感驅動的黑人文化;也存在未來取向,注重物質和由成就驅動的白人文化。瓊斯認為,與其想方設法要消除這些差異,還不如好好感激這些差異“對多元文化社會的文化結構所做的貢獻”。在某些情境中,善於表達是優點,但在另一些情境中,未來取向才是優點。每一種文化都有許多要向其他文化學習的地方。在一些國家,如加拿大、英國、美國,移民和不同的出生率造成了發展的多樣性,如何教育人們去尊重和欣賞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是最大的挑戰。由於文化多樣性程度的提高,而我們對於差異又有天生的警惕性,尊重和欣賞差異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的社會挑戰。
對立引發吸引嗎
我們不是也會被這樣的人吸引嗎——他們在某些方面與我們不同 ,但又與我們的某些人格特質互補?研究者考察了這個問題,他們不但比較了朋友和配偶們的態度和信念,而且還比較了他們的年齡、宗教信仰、種族、吸菸行為、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身高、智力以及外貌。在所有這些方面乃至更多的方面上,相似性仍然是主導因素(Buss,1985;Kandel,1978)。聰明者聚在一起。同樣,富裕的,同樣教派的,高大的,美麗的也各自聚在一起。
研究背後的故事:
詹姆斯·瓊斯論文化多樣性
在我還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時,我應邀寫一本關於偏見的書。出於希望能夠使讀者排除對偏見的個人責任的考慮,我為書起名為“偏見與種族主義”,我解釋了種族問題如何植根於我們的社會。偏見根本就不是一個種族問題,而是文化問題。歐洲傳統和非洲傳統的文化有很大不同,它們的差異是文化種族偏見產生的根源——那就是無法容忍文化差異。在今天這個種族融合的世界中,我們必須學會接納文化多樣性,即使我們正在努力尋求統一的思想。
但我們仍然要問:我們真的就不會被那些需要和人格品質正好與我們互補的人吸引嗎?一個虐待狂和一個受虐狂在一起能否找到真愛呢?甚至《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都告訴過我們:“對立相吸……愛社交的人與不愛社交的人配對,求新獵奇的人與不願變化的人配對,揮金如土的人和節儉的人配對,冒險的人與謹小慎微的人配對”(Jacoby,1986)。社會學家羅伯特·溫奇(Winch,1985)解釋說,一個外向的、具有支配性的人的需要正好和靦腆的且喜歡服從的人能天然成對。這個邏輯看起來是很有說服力的,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把夫妻之間的差異看做是一種互補:“我的丈夫和我是天生的一對。我是寶瓶座的——堅決果斷的人。他是天秤座的——優柔寡斷的人。但他總是樂意遵從我所做的安排。”
這種觀點聽起來具有說服力,但令人驚奇的是,它未能得到研究者的證實。例如:大多數人會被富於表現力且外向的人所吸引(Friedman & others,1988)。但當一個人正處於沮喪的情緒中時,情況還會是這樣嗎?沮喪的人會去尋找那些快樂的人來使自己快樂起來嗎?事實正好相反,那些心情好的人最樂意跟愉悅的人為伴(Locke & Horowitz,1990;Rosenblatt & Greenberg,1988,1991;Wenzlaff & Prohaska,1989)。當你感到憂鬱的時候,一個生龍活虎的人可能會使你感覺更糟糕。這種對比效果會使一個相貌平平的人在與漂亮的人相處時感到自己的長相更為一般,也使傷心的人在與開心的人相處時倍覺淒涼。
某些方面的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的確可以促進關係的改進(即使是兩個同卵雙生子之間的關係)。然而,人們似乎更傾向於喜歡並和那些在需求和人格方面相似的人結為夫妻(Botwin & others,1997;Buss,1984;Fishbein & Thelen,1981a,1981b;Nias,1979)。也許某一天,我們會發現一些方法(除了異性相戀之外)能使差異產生喜歡。支配性和被支配性也可能會是其中的一種(Dryer & Horowitz,1997)。我們通常不會認為,那些表現出與我們自己相同的不好的特徵的人是有吸引力的(Schmiel & others,2000)。研究者戴維·巴斯(1985)對互補性提出了質疑:“除了性別因素以外,因彼此擁有對立的特徵而結婚或同居的趨勢……從來就沒有得到過有效的證實”。
喜歡那些喜歡我們的人
喜歡通常是相互的。接近性和吸引力影響我們最初為誰所吸引,而相似性會影響長期的吸引。如果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歸屬需要,和被喜歡、被接納的需要,我們還會不喜歡那些喜歡我們的人嗎?最好的友誼不正是發生在相互欽慕的社會交往中嗎?的確,一個人喜歡他人的程度,可以反過來預測對方喜歡他的程度(Kenny & Nasby,1980)。
但是一個人喜歡另一個人就可以使對方反過來也欣賞自己嗎?一份人們講述自己如何墜入情網的報告給予了肯定的回答(Aron & others,1989)。發現一個有魅力的人真的喜歡你,似乎能喚起一種浪漫的情感。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告知某些人他們被別人喜歡或仰慕時,他們就會產生一種回報的情感(Berscheid & Walster,1978)。
來看一下伯奇德及其同事(1969)研究的發現吧:被試更喜歡那個在八個項目上都對他們做積極評價的學生,而不太喜歡那個在七個項目上對他們做積極評價、一個項目上做消極評價的學生。我們對最微弱的批評暗示都是十分敏感的。作家拉里·金(Larry L. King)曾多次強調了否定的作用:“多年來,我發現了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積極的評價無法總讓作者產生好的感覺,而消極的評價則總會讓他產生壞的感覺。”無論我們評價自己,還是評論別人,消極信息都佔了更大的權重,這是因為,較之於積極信息,消極信息更不尋常,也更能抓住人們的注意力(Yzerbyt & Leyens,1991)。人們在大選投票時,更容易被總統候選人的弱點而不是優點所左右(Klein,1991),這是那些為競選對象做消極設計的人從未放棄利用的一種策略。羅伊·鮑邁斯特及其同事(2001)指出,生活中一條普遍的規律,是缺點比優點更有影響力(見“聚焦:缺點比優點更有影響力”)。
很久以前我們就認識到,我們喜歡那些我們認為是喜歡我們的人。從古代哲學家希卡託(Hecato,“如果你希望被別人愛,那你就去愛別人吧”)到愛默生(“擁有朋友的惟一方法就是成為別人的朋友”),再到戴爾·卡內基(“慷慨地去讚美別人吧”),都預見了我們的發現。他們所不能預見的是這一規律起作用的精確條件。
歸因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奉承有時的確會使你感覺良好。但也並非總是如此。如果讚美明顯地違背了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如果有人說:“你的頭髮看起來真是太美了!”可事實是我已經好幾天沒有洗它了——或許我再也不會尊重這個奉承者,並會懷疑這種讚美是否出於一種不可告人的動機(Shrauger,1975)。因此我們常常認為批評比表揚更真誠(Coleman & others,1987)。
聚焦 缺點比優點更有影響力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不同的態度更容易使我們討厭他人。別人的批評比表揚更能抓住我們的注意力,更能影響我們的情緒。鮑邁斯特及其同事(Baumeister,Bratslavsky,Finkenauer,& Vohs,2001)稱這只是冰山一角:“在日常生活中,壞事總是比好事更有影響力,而且影響更持久。”試看:
破壞性行為對親密關係的傷害程度要比建設性行為對親密關係的促進作用更大。(冷酷的言辭比甜言蜜語能持續更長的時間。)
壞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影響我們的思維和記憶。(即使我們天性樂觀,也更容易想起過去那些引起不良情緒反應的事情。)
表達消極情緒的詞語比表達積極情緒的詞語更多,而且要求人們想出表達情緒的詞語時,他們更容易想出消極的詞語。(傷心、生氣、害怕是最常見的三個。)
一件壞事(創傷)比一件好事能夠產生更為持久的效應。(一個強姦事件所產生的傷害是讓人感到最快樂的浪漫經歷所無法彌補的。死亡比出生更能引起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探尋。)
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壞事比好事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思考。(丟了錢給人帶來的不安,遠勝於得到同樣多的錢所帶來的快樂。)
非常惡劣的家庭環境超出遺傳對智力的影響的程度,要遠遠大於良好家庭環境。(差勁的父母可能會使他們天資聰慧的孩子變得不那麼聰明;而明智的父母要使不聰明的孩子變得聰明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一個不好的名聲比起一個好名聲更容易獲得,而且更難以擺脫。(僅僅一次說謊就可以毀掉一個人“誠實”的美譽)。
糟糕的健康狀態對幸福感的影響要遠大於好的健康狀態所增加的快樂。(疼痛產生的痛苦遠遠大於舒服產生的快樂。)
壞事帶來的好處是可以使我們做好準備去面對危險,保護我們遠離死亡和殘障。對於生存來說,壞事變壞要比好事變好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更大。為什麼心理學在誕生後的第一個世紀中,關注的消極事件要多於積極事件?壞事的這種重要性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自1887年以來,《心理學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 ,一本心理學文獻導讀)中共有11195篇文章提到“生氣”,73223篇提到“焦慮”,90169篇提到“抑鬱”。這些主題的每18篇文章中,只有1篇涉及到“喜悅”(1205),生活滿意(4585),或幸福(4100)等積極情緒。同樣,“害怕”(23153篇)已經遠遠超過了“勇氣”(904篇)。然而,鮑邁斯特及其同事認為,消極事件的力量“或許正是積極的心理學運動發起的最重要的原因”。為了克服個別消極事件的不良影響,“人類的生活需要更多積極的事情而不是消極的事情”。
實驗室實驗揭示了一些前面章節中提到的內容:我們的反應依賴於我們的歸因。我們是不是把讚美歸因為一種討好 (ingratiation)——自我服務的一種策略呢?這人是不是想讓我們為他買什麼東西?或是謀求性順從?還是希望給予回報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奉承者和他們的讚美都會失去魅力(Gordon,1996;Jones,1964)。但是如果沒有明顯的別有用心的動機,我們就會接受奉承者和他們的奉承。
我們如何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塞利格曼等人(Seligman,Fazio,& Zanna,1980)給正在戀愛的大學生報酬,讓他們回答“為什麼你要和你的女/男朋友出去約會?”之類的問題。研究者要求一部分被試對7種內在原因進行排序,例如“我和_____約會,是因為我們在一起很開心”,和“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興趣和關注點。”另一部分被試則被要求對可能的外在原因進行排序:“因為自從我和他/她交朋友後,其他朋友們都比以前更看得起我了”和“因為他/她認識很多重要人物。”然後,要求他們填寫一份“愛情量表”,發現那些注意力被引到外在原因方面的人,比那些關注了內在原因的人,對他們的戀人表示出較少的愛戀,認為結婚的可能性也較小。(由於敏感於倫理道德問題,實驗之後,研究者詢問了所有被試,確定該實驗對被試的戀愛關係沒有長期影響。)
自尊和吸引
哈特菲爾德(Walster,1965)想弄清楚在我們四面楚歌時,別人的支持是否顯得尤為珍貴,正如齋戒之後的進食是最好的獎賞一樣。為了驗證這一想法,她先給斯坦福大學的女生進行了人格分析,劃分出令人非常愉悅的人,讓人感到不快的人。通過這種辦法,研究者肯定了一部分人,而否定了另一部分人。然後,要求她們評價幾個人,其中包括一個很有魅力的男性,他正好在實驗之前曾與每名被試有過熱情的聊天,並邀請每個被試去約會(無一人拒絕)。你猜哪些女生最喜歡這位男士呢?答案恰恰是那些自尊心剛剛遭受了暫時打擊並極為渴望獲得社會承認的人(實驗之後,哈特菲爾德花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解釋這個實驗,並且和每位女生進行了交談。她報告說,後來沒有一個人因自尊受到短暫的打擊而煩惱或影響正常約會。)
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人們有時在一次自尊遭受很大創傷的拒絕之後,會表現出反彈行為——陷入充滿激情的戀愛當中。然而,不幸的是,低自尊的個體傾向於低估同伴對他們的欣賞程度,並且也不積極給予同伴回報性評價,因而對與同伴關係的滿意程度也較低(Murray & others,2000)。若你對自己信心不足,你也可能會對你們的關係持悲觀態度。對自己感覺良好,你才會對約會夥伴或配偶的看法更有信心。
獲得他人的尊重
如果不被承認之後再得到承認是一種有力的獎賞的話,那麼,我們是否更喜歡那個起初不喜歡我們,後來又喜歡我們的人?還是更喜歡那個從一開始就喜歡我們(因而也給了我們更多承認)的人呢?迪克正在和室友的表妹簡參加一個小型討論會。在第一週的課程之後,迪克通過他的“信息通道”瞭解到,簡認為他很淺薄。隨著時間的推移,迪克瞭解到簡對他的看法在逐漸變好;慢慢地,簡把他看成一個聰明的、有頭腦的且很有魅力的人了。如果簡一開始就認為他不錯,是否更能得到迪克的喜歡呢?如果迪克簡單地根據他所得到的承認的量來判斷的話,那麼後者應該得到迪克更多的喜歡。但是,如果簡拒絕之後的承認更有力的話,前者就會得到迪克更多的喜歡。
為了確定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哪一個正確,阿倫森和林德(Aronson & Linder,1965)設計了一項精巧的實驗,該實驗抓住了迪克經歷的本質。他們讓80名明尼蘇達大學的女生“無意中”聽到了另一位女生對她們的一系列評價。有些女生聽到的是持續的對自己的積極評價,有的女生聽到的是持續的對自己的消極評價。還有的女生聽到的評價是從消極到積極(如簡對迪克的評價),或從積極到消極。結果發現,當個體獲得 了目標人物的尊重,尤其當這種尊重的獲得是逐漸發生的,並且還推翻了目標人物先前的批評之詞時,個體就會更加喜歡這個目標人物(Aronson & Mettee,1974;Clore & others,1975)。簡先說了一些不太友善的話,可能正因為如此,她隨後對迪克的讚美之辭才更加可信。或者是,由於先前對美言的吝惜,才使得對方聽到讚賞後特別滿足。
阿倫森認為,頻繁的讚揚可能會失去價值。當一個丈夫第五百次說,“呀,親愛的,你看起來真美啊”,這話給妻子的觸動遠不如他說,“哦,親愛的,你穿那件衣服不是很好看。”要讓所愛的人滿意很難,但傷害所愛的人卻很容易。這說明,與壓抑不快情緒和戴爾·卡內基所說的“過度讚揚”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誠的關係——即互相尊重、彼此接納、保持忠誠——更可以持續地讓對方感到滿意。阿倫森(1988)這樣解釋道:
當關系向更加親密的方向發展時,真誠變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再一味努力給對方留下好印象,而是開始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展示給對方,哪怕有些方面令人生厭……如果兩人真心喜歡對方,如果他們能在對方面前坦然表露自己的積極和消極情緒,而不是總是“友善”地對待對方,那麼他們將持久地擁有更滿意、更富有激情的關係。(P.323)
在大多數社會交往中,我們會對自己的消極情緒進行自我檢查。因此,斯旺及其同事(1991)提出,某些人根本沒有獲得矯正性的反饋。他們生活在充滿愉悅的幻境中,他們的行為方式使他們逐漸疏遠了潛在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那些能把壞消息也告訴我們的人。
有些真愛我們的人雖然也很誠實,但他們也傾向於透過玫瑰色的眼鏡(過分樂觀地)來看待我們。桑德拉·默裡等人(Murray & others,1991)對戀愛的情侶和已婚的夫婦進行的研究表明,那些相互理想化的伴侶過得最開心(或隨相處時間的增加而更加快樂),他們看待自我伴侶的態度甚至比伴侶看待自己的態度更加積極。戀愛中的人總是傾向於認為自己的伴侶不僅外表具有魅力,而且在社交上也頗具魅力。而且,那些對婚姻感到最滿意的夫婦,在遇到問題時並不會馬上批評和指責對方,也不會馬上追究到底是誰的錯(Karney & Bradbury,1997)。真誠對營造兩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很重要,但假定對方是天性善良的也同樣重要。
關係中的回報
當問及為什麼會跟某人交朋友,或為什麼會被他們的伴侶所吸引時,大多數人的答案都可以脫口而出。“我喜歡卡羅爾,因為她熱情、聰明而博學。”這樣的解釋所忽略的——也是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最為重要的——就是我們自己。吸引牽涉到被吸引的一方和吸引別人的一方。因此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更為準確的答案應該是,“我喜歡卡羅,是因為跟她在一起感覺如何如何。”我們是被那些令我們感到滿意和開心的人所吸引。吸引體現在被吸引一方的眼中(和腦中)。
可以將這種觀點總結為一個簡單的吸引的回報理論 (reward theory of attration):我們喜歡那些回報我們或與我們得到的回報有關的人。如果跟某人交往所得到的回報大於付出的成本,那我們就喜歡並願意繼續維持這種關係。尤其當我們在這種關係中的收益大於其他可能的關係時更是如此(Burgess & Huston,1979;Kelley,1979;Rusbult,1980)。當一方滿足了另一方沒有得到滿足的需求之後,就會產生相互吸引。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國作家——譯者注](1665)在《箴言集》(Maxims )一書中指出,“在友誼中,雙方的長處和優勢得以互換,這可能有益於雙方的自尊。”
我們不僅樂於跟那些能帶來報償的人交往,而且根據回報理論所說的第二種原則,我們還喜歡與那些能讓我們心情愉悅的人交往。根據理論家伯恩和克洛爾(Donn Byrne & Gerald Clore,1970)、洛特(Albert Lott & Bernice Lott,1974)以及Jan DeHouwer與他的同事(2001)的理論,人們通過條件反射形成了對那些與回報性事件有關的事和人的積極感受。在一週的緊張工作之後,當我們圍坐在篝火前,享受著可口的食物、醇香的美酒和美妙的音樂時,就可能覺得身邊的一切都那麼溫馨。而如果我們正經受著頭痛的折磨,那麼我們就可能對遇到的人沒什麼好感。
Pawel Lewicki(1985)對這種“聯繫-喜歡”(liking-by-association)原則進行了檢驗。在一項實驗中,要求來自華沙大學(University of Warsaw)的學生從兩張女士的照片(圖11-5中的照片A或B)中選出一個看上去比較友善的,結果這兩張照片被選擇的比率是50:50。而另外的學生在選擇照片之前,先與一位熱情、友善、長相像A的實驗者進行了交往,結果他們選擇A、B照片的比率為6:1。隨後的實驗中,被試在選擇照片之前也會跟同一位實驗者進行交往,但這時實驗者對待其中一半的人的態度非常不友善 。結果被試在選擇A、B照片時,幾乎都沒有 選擇那個和實驗者很像的女士的照片。(回想一下,你可能在某些時候也曾以積極或消極的態度對待過讓你聯想到另外某個人的那個人。)

圖11-5 “聯繫-喜歡”
在與友好的實驗者交往後,人們更傾向於選擇那個像實驗者的女士(A),而不選不像實驗者的女士(B)。在與不友好的實驗者交往後,人們不會選擇像實驗者的女士(Lewicki,1985)。
還有其他一些研究也證實了“聯繫-喜歡”和“聯繫-不喜歡”的現象。有研究發現,讓大學生對陌生人進行評價時,在舒適房間中的大學生的評價要高於在燥熱難耐的房間中的大學生的評價(Griffitt,1970)。在另外一項研究中,讓被試對他人的照片進行評價,被試所處的環境不同,要麼是在裝飾雅緻而豪華的房間裡,要麼是在破舊、骯髒的房間裡(Maslow & Mintz,1956)。結果再次證明,舒適的環境能激發被試對被評價者的好感。哈特菲爾德和沃爾斯特(Hatfield & Walster,1978)通過這些研究,發現了一條與人相處時很實用的小貼士:“浪漫的晚餐、在劇院觀看演出、在家共度夜晚、度假,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希望維繫與伴侶的關係,那麼你和你的伴侶都要繼續把你們的關係跟美好的事物聯繫起來。”
這個簡單的吸引的回報理論——即我們喜歡那些回報我們或與我們得到的回報有關的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所有的人都會被那些熱情、可靠、敏感的人所吸引(Fletcher & others,1999;Regan,1998;Wojciszke & others,1998)。這一理論還有助於解釋吸引力的一些影響因素:
接近性 能夠帶來報償。從與近鄰和同事的關係中獲得友誼的好處,所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都較少。
我們喜歡有吸引力 的人,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會具備其他一些我們所期望的品質,與他們結交能使我們獲益。
如果他人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相似 ,我們會覺得得到了回報,因為我們假定他們也喜歡我們。而且,與我們持有共同觀點,會使得我們更加確信這些觀點是正確的。我們尤其喜歡那些被我們成功說服、從而開始認同我們觀點的人(Lombardo & others,1972;Riordan,1980;Sigall,1970)。
我們喜歡被人喜歡和被人所愛。因此,喜歡常常都是相互的。我們喜歡那些喜歡我們的人。
小結
我們考察了影響喜歡和友誼的四個強有力的因素。兩個人能否成為朋友的最好預測因素是他們相互之間的接近性。接近性有利於雙方不斷表露自己,從而進行相互交往,這也促使雙方去發掘兩人的相似之處,感受彼此的喜愛。
決定吸引力的第二個因素是外表吸引力。對約會陌生人(blind dates)進行的實驗室研究和現場研究都表明,大學生更傾向於選擇有吸引力的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實際上願意選擇那些大體上與自己的吸引力相當(或者,對方魅力不足但具有其他補償性品質)的人結婚。對有吸引力的人的積極歸因形成了關於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美即是好”的假設。
雙方在態度、信仰和價值觀上的相似性,會極大地增進一方對另一方的喜歡。相似導致喜歡;對立則很少能產生吸引。我們也很可能和那些喜歡我們的人建立友誼關係。
一個簡單的原理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些因素能夠影響人們彼此之間的吸引力:我們喜歡那些能給我們帶來回報,或者那些與回報事件相聯繫的人。
什麼是愛情
什麼是愛情?激情之愛能否持久?如果不能,那麼什麼可以取代它?
愛情比喜歡更復雜,因而也就更難進行測量和研究。人們渴望愛情,為它而生,因它而死。然而僅僅是在最近幾年,愛情才成為社會心理學中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
大多數投身於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都研究了最容易研究的方面——即陌生人之間短暫接觸(brief encounters)時所做出的反應。那些影響起初我們對他人喜愛與否的變量——接近性、吸引力、相似性、他人是否喜歡自己以及其他一些回報性的特質——也會影響到我們長期、親密的關係。約會雙方會很快形成對對方的最初印象,這就為他們之間的長期交往提供了基本線索(Berg,1984;Berg & McQuinn,1986)。的確,如果北美人的愛情的發生是隨機的 ,而不考慮接近性與相似性等因素的話,那麼就會有很多天主教徒(屬於少數群體)與基督教徒結婚,就會有很多黑人與白人結婚,而大學生與大學生結婚的可能性,應和與高中輟學者結婚的可能性相當。
因此,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長期的愛情並不僅僅是初時好感的延續和增強。於是,社會心理學家們轉而開始研究持久、長期的親密關係,而不再將研究興趣只集中於初次相遇所體驗到的吸引力。
激情之愛
對愛情進行研究,也同研究其他變量一樣,第一步就是要決定如何界定和測量它。我們有很多方法,用以測量攻擊、利他、偏見和喜好——但是,怎樣測量愛情呢?
勃朗寧夫人 [9] 在她的詩中寫道:“我是怎樣地愛你?讓我逐一細算。”社會科學家們列舉了幾種方式。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Sternberg,1988)認為愛情是個三角形,這個三角形的三邊(不等長)分別是:激情、親密和忠誠(如圖11-6)。根據古代哲學和古代文學的有關觀點,社會學家約翰·艾倫·李(Lee,1988)、心理學家亨德里克等人(Hendrick & Hendrick,1993,2003)確認了愛情的三種基本形式——情慾之愛 (eros)(充滿自我展露的浪漫激情的愛),遊戲之愛 (ludus)(視愛情為無需負責的遊戲),以及友誼之愛 (storge)(如友誼般的感情)——它們就像三原色一樣,組成不同種類的次級愛情形式(secondary love styles)。有的愛情,如情慾之愛和友誼之愛相結合,能夠預測較高的關係滿意度;而另一種愛情,如遊戲之愛,則能夠預測較低的關係滿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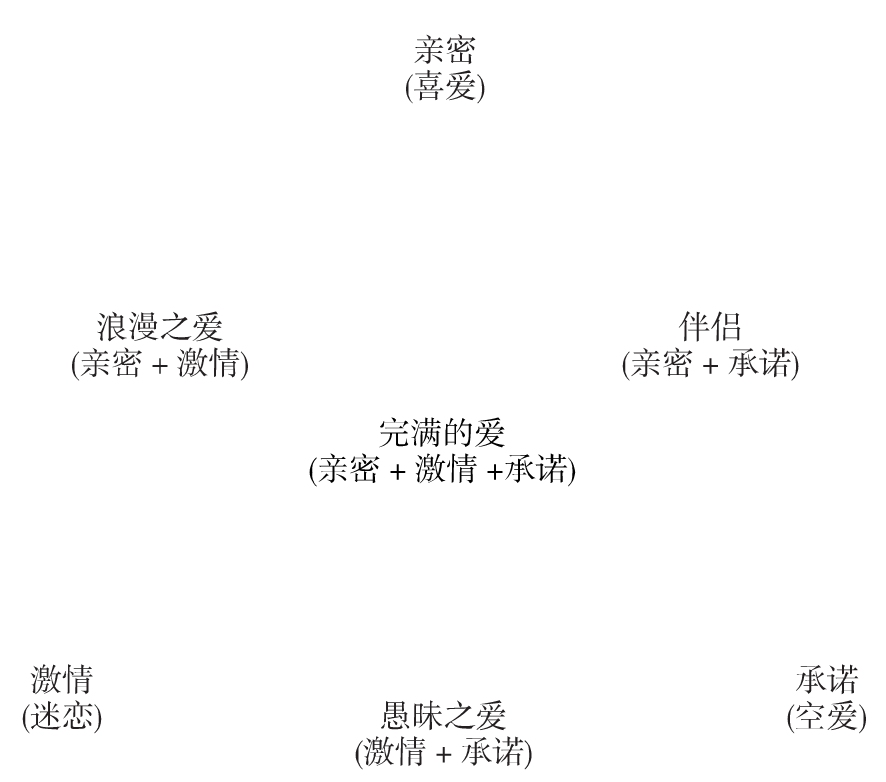
圖11-6 斯騰伯格(1988)愛情三成分理論
有些元素是所有的愛情關係都共有的,如相互理解、相互扶持、以愛人的陪伴為樂等等。有些元素則具有特定性。如果我們經歷的是激情之愛,那麼我們就會通過身體來表現這種愛,我們期望這種關係具有排他性,我們還對自己的伴侶非常著迷。外人可以通過我們的眼睛看出這一切。魯賓(Zick Rubin)的研究支持了這一點。他對幾百對密歇根大學的情侶施測了一份愛情量表。隨後,他又通過設置在實驗等候室的單向玻璃,觀察並記錄了熱戀(strong-love)和非熱戀(weak-love)的情侶的目光接觸時間。結果並不出人意料:熱戀的情侶會長時間地注視對方的眼睛。吉安·岡薩格等(Gonzaga & others,2001)對情侶們進行的觀察也表明,當情侶們交談時,熱戀的情侶還會互相點頭致意、自然地微笑或是輕輕倚在對方身上。
激情之愛 (passionate love)是深情的、極富激情的愛。哈特菲爾德(Hatfield,1988)把激情之愛界定為“強烈渴望和對方在一起的一種狀態 ”(p.193)。對滿懷激情之愛的一方而言,如果對方對自己的熱情做出了迴應,那麼他就會感到滿足而快樂;如果對方對自己的熱情沒有做出迴應,他就會覺得空虛而絕望。就像其他激動的情緒一樣,激情之愛也包含著情緒的急轉突變,忽而興高采烈,忽而愁容滿面;忽而心花怒放,忽而傷心絕望。弗洛伊德曾說過,“再沒有比戀愛時更容易受傷的了。”激情之愛使人專注於自己的愛人——正如羅伯特·格雷夫斯 [10] 所說的,“傾聽敲門聲的響起;期待對方做出表白。”
當你不但是在愛戀著某人,而且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時,那種感受就是激情之愛。邁耶斯和伯奇德(Meyer & Berscheid,1997)說過,我們能夠理解那些說“我愛你,但我們並不相戀”的人要表達什麼,他們實際上是在說:“我喜歡你,我關心你,我覺得你很棒,但是我覺得你對我來說不具有性吸引力。”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自己感受到的是友誼之愛 ,而不是激情之愛。
關於激情之愛的一個理論
為了解釋激情之愛,哈特菲爾德指出,任何一種既定的生理喚醒狀態最終都可以被歸結為某種情緒,究竟被歸結為哪一種情緒則取決於我們對這種喚醒狀態如何進行歸因。每一種情緒都包含著身體和心理反應——既有生理喚醒,還有我們如何詮釋和標識這一生理喚醒。想像一下,你現在正心跳劇烈、雙手發抖:你是在經歷恐懼?焦慮?還是喜悅?從生理上講,這些情緒很相似。當你處在愉快的環境中時,你就可能把這種生理喚醒體驗為喜悅;而當你處於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時,你可能把這種生理喚醒體驗為憤怒;而假如你正處在浪漫的情境中,你就可能把這種生理喚醒體驗為激情之愛。從這個角度來看,激情之愛就是由於我們在生理上被有吸引力的人所喚醒而知覺到的心理體驗。
如果激情是一種被標識為“愛情”的能帶來興奮感的狀態,那麼任何一種可以增加興奮感的東西都應該可以增強對愛情的感受。有些實驗通過讓男性大學生閱讀色情小說或觀看色情電影而提高他們的性喚起,結果發現這些男生此時對女性有更強烈的反應——比如,當他們描述自己的女友時,在愛情量表上的得分更高(Carducci & others,1978;Dermer & Pyszczynski,1978;Stephan & others,1971)。沙克特和辛格(Schachter & Singer,1962)提出的情緒的兩因素理論 (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認為,當處於興奮狀態的男性對女性做出反應時,他們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某些生理喚醒錯誤地歸因於這位女性。
根據這一理論,倘若可以自由地把生理喚醒歸因於某些浪漫的刺激,那麼由任何 來源所引發的生理喚醒都應該可以增強激情的感受。達頓和阿倫(Dutton & Arthur Aron,1974)設計了一項精妙的實驗來證實這一現象。他們讓一位魅力十足的年輕女子,站在位於英屬哥倫比亞卡普蘭諾河(Capilano River)上230英尺高、450英尺長的一座狹窄而搖晃的吊橋上,請求過往的單個男性幫助她完成一份課堂問卷。當對方完成問卷後,這名女子會留下自己的姓名和電話,然後告訴他如果想了解更多該項目的信息就可以打電話找她。結果大部分的男性都收下了她的電話號碼,而且有一半的男性確實打了電話。而與此相對,在低矮、堅固的橋上遇到這位女性的男性當中,以及在高吊橋上遇到男性 調查者的男性當中,則很少有人打電話。這一研究結果再次證明,生理喚醒促進了羅曼蒂克式的反應。
觀看恐怖電影、乘坐過山車,以及體育鍛煉等也都有同樣的效果,特別是對那些我們覺得有吸引力的人(Foster & others,1998;White & Kight,1984)。這種效果也存在於已婚夫婦中。那些經常在一起做一些可以提升彼此興奮度活動的夫婦,所報告的婚姻滿意度最高。相對於完成一般的實驗室任務,如果夫妻雙方能共同完成一項提高激活水平的活動(比如兩人的綁腿賽跑等)的話,往往會對其關係的總體情況報告較高的滿意度(Aron & others,2000)。腎上腺素使兩顆相愛的心貼得更近了。
影響愛情的因素:文化與性別
我們總是傾向於認為大多數人會和自己擁有相同的感受和想法。比如,我們會認為愛情是婚姻的前提。在大部分的文化背景中——在一項對166種文化的分析中佔到89%——人們都抱有浪漫愛情的觀念,這種觀念通過男女之間的調情和私奔等行為反映出來(Jankowiak & Fischer,1992)。但也有一些文化,特別是在那些實行包辦婚姻的社會中,愛情出現在婚姻之後而非先於婚姻。此外,直到最近,北美地區的人們(特別是女性)在做婚姻選擇時,依然會受到對方經濟條件、家庭背景、社會地位等方面因素的影響。
男女兩性在熱戀階段的體驗是否有所不同?關於男性和女性“墜入情網”和“結束愛情”等現象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結論。大部分人,包括以下這封信(寫給一家報社的專欄作家)的作者都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墜入情網:
親愛的“大哥哥”博士:
您覺得一個19歲的小夥子在愛情中陷得很深會不會顯得很“女人氣”呢?就像整個世界都掉了個個兒。我想我真的是瘋了,因為這樣的事情已經多次發生,愛情似乎會突然擊垮我……我父親說這是女孩子們的戀愛方式,男孩不會這樣——至少男孩不應該這樣。我無法改變自己的戀愛方式,但是這確實很令我煩惱。—P.T.(Dion & Dion,1985)
很多重複研究所得的結果應該會讓P. T.打消顧慮,這些研究的結果表明,其實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墜入情網(Dion & Dion,1985;Peplau & Gordon,1985)。男性似乎更難從一段愛情中解脫出來,而且,相比於女性,男性很少會結束一段即將邁向婚姻的愛情關係。但是,熱戀中的女性則一般會有像她們的伴侶一樣多的情感投入,甚至會比對方投入得更多。她們更傾向於報告自己體驗到了愉悅和“無憂的眩暈感”,就像“在雲中漂浮”一樣。同樣,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加註重友誼中的親密感,也會更多地關心她們的伴侶。男性則比女性更多地想到戀愛中的嬉戲以及性的方面(Hendrick & Hendrick,1995)。
伴侶之愛
儘管激情之愛可以熱火朝天,但最終還是會平靜下來。一段關係維持的時間越長,它所引發的情緒波動就會越少(Berscheid & others,1989)。浪漫愛情的高潮可能會持續幾個月甚至一兩年,但是正像我們在對適應的討論中說到的(第10章),從沒有一種高峰期可以永久地維持下去。喜劇演員理查德·劉易斯(Richard Lewis)曾經詼諧地說過,“如果你正處在戀愛之中,那在你一生中最為絢麗多彩的時間也就只有兩天半”。那種新奇感,對對方的強烈迷戀,激動人心的浪漫,那種令人眩暈的“浮在雲端”的快感,總會逐漸消逝。結婚兩年的夫妻所報告的情感體驗比他們新婚時報告的少了一半以上(Huston & Chorost,1994)。在世界範圍內,結婚四年之後的離婚率都是最高的(Fisher,1994)。如果一段親密的感情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那麼它就會最終成為一種穩固而溫馨的愛情,哈特菲爾德稱之為伴侶之愛 (companionate love)。
與激情之愛中狂熱的情感不同,伴侶之愛相對平和。它是一種深沉的情感依戀,就如同真實生活一樣。身處非洲南部的Kalahari沙漠中遊牧民族(Kung San)的婦女Nisa說:“兩個人最開始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心好像在燃燒,他們的激情非常高漲。而後,愛情的火焰會冷卻,並且會一直維持這個狀態。他們繼續彼此相愛,但這種相愛是通過另一種方式——溫馨而相互依賴的方式實現的”(Shostak,1981)。
那些聽過搖滾樂“戀愛成癮”(Addicted to Love )的人一定不會對這種現象大驚小怪:浪漫愛情的產生和消退趨勢與人們對咖啡、酒精以及其他藥物的成癮方式很相似。最初,人們對某種藥物的使用給自身帶來了一種很大的衝擊,可能會是一種高峰體驗;隨著不斷重複的使用,相對立的情緒逐漸佔據上風,抗藥性就出現了。曾經可以帶來很大刺激的用藥量現在變得效果甚微了。然而,停止用藥並不能使你恢復原先的狀態,而是會激發強烈的戒斷反應(withdrawal symptom):難受,抑鬱,厭煩等。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愛情中。激情會逐漸消退直至變得冷淡,這種不再浪漫的關係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直到它結束。那些失戀的人、離異的人都會吃驚地發現,雖然早已對伊人失去了那種強烈的愛戀,但離開以後,生活竟感覺如此空虛。過於關注那些已然不再的東西,使他們忽視了他們仍然所擁有的(Carlson & Hatfield,1992)。
激情隨著時間而冷卻,而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卻隨之增強,比如共有的價值觀。我們可以在印度的一些包辦婚姻家庭和自由戀愛的家庭成員感受的差異中看出這種變化。Usha Gupta和Pushpa Singh(1982)讓印度齋浦爾(Jaipur)地區的50對夫婦完成一份愛情量表,研究者發現,那些結婚五年以上的自由戀愛夫婦,會覺得彼此之間“有愛情”的感覺越來越少了。相反,那些包辦婚姻的夫婦則會在新婚之後隨時間的推移而報告出更多的愛情體驗(圖11-7)。另外一些研究者對包辦婚姻也做了全面的描述,他們發現,儘管印度的情況和Gupta及Singh的研究結果相符,但是在日本和中國,自己選擇伴侶的女性更多地感覺到快樂(Blood,1967;Xu & Whyte;1990;Yelsma & Athappily,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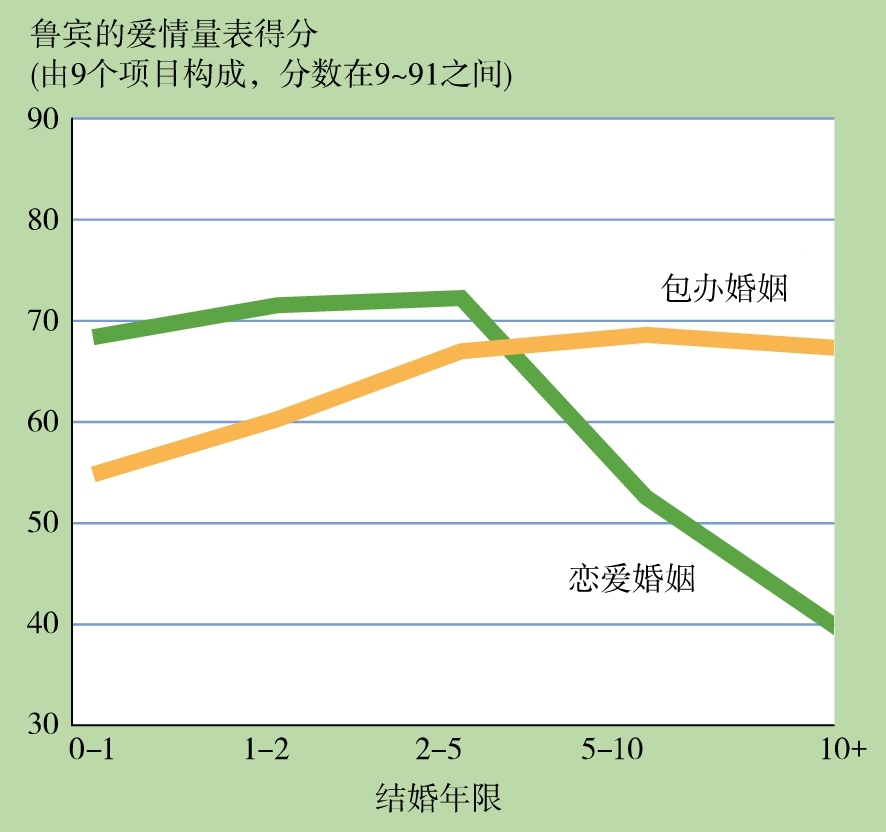
圖11-7 印度齋浦爾地區包辦婚姻夫婦與自由戀愛夫婦對浪漫愛情的評價
資料來源:Data from Gupta & Singh,1982.
隨著強烈的浪漫之愛逐漸冷卻下來,人們經常會感到幻想破滅,特別是對於那些將浪漫之愛視作雙方結合和維持長久婚姻的基礎的人來說,這種感覺就會更強烈。辛普森等人(Simpson,Campbell,& Berscheid,1986)對“過去二十年陡然增高的離婚率,至少部分地源自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強烈積極的情緒體驗(比如浪漫的愛情)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這些體驗又難以持久”的觀點表示懷疑。相比於北美,亞洲社會似乎較少強調個人感受,而是更多強調現實的社會性依戀(Dion & Dion,1988;Sprecher & others,1994,2002)。因此,他們就可能較少受到由於浪漫的幻想破滅而帶來的消極影響。亞洲人也不太傾向於自我關注(self-focused)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行為方式,因為那種方式從長遠來看會損害一段感情,並可能導致離婚(Dion & Dion,1991,1996;Triandis & others,1988)。
互相迷戀的強烈情感的衰減似乎是物種生存的自然適應策略。激情之愛的結果往往使一對夫婦得到孩子,而孩子的生存使得父母不能再只關注彼此(Kenrick & Trost,1987)。然而,對於那些婚齡超過二十年的夫婦,隨著孩子長大成人、開始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家庭中出現“空巢”的情況,一些曾經失去的浪漫感覺又重新出現了,父母可以重新關注彼此(Hatfield & Sprecher,1986)。馬克·吐溫說,“沒有一個人會真正理解愛情,直到他們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上的婚姻之後。”如果一段感情曾經是親密的而且是互相回報的,那麼伴侶之愛就會植根於共同體驗的人生風雨歷程,從而愈久彌醇。
小結
有的時候,熟悉關係不僅僅會發展為友誼,而且會成為激情之愛。這樣的愛情常常是狂喜與焦慮、興奮與痛苦的混合體。情緒的兩因素理論認為,在一個浪漫的情境中,任何刺激(甚至疼痛)造成的喚醒水平都可以被解釋為激情。在最完美的感情關係中,最初的浪漫興奮會逐漸成為更加穩定、更加溫情的關係狀態,這種關係就被稱為伴侶之愛。
哪些因素促進了親密關係
什麼因素會影響人們親密關係的起伏?讓我們來討論以下幾個因素:依戀類型,公平和自我表露。
依戀
愛情不僅僅是一種選擇的體驗,它其實更是一種生物性的驅使。我們,從根本上說就是社會性動物,註定要和他人聯繫在一起。正如本章開始部分提到的,我們的歸屬需要具有適應性意義。合作可以促進我們種族的生存。在單打獨鬥中,我們的祖先並不是最厲害的捕食者;但是作為狩獵和採集者,以及抵禦其他捕食者方面,他們通過集體行動獲得了足夠的力量。由於群居者能夠生存並繁衍生息,所以今天的我們攜帶了那些預先註定我們與他人聯繫的基因。
嬰兒期對成人的依賴增強了人類之間的聯繫。人在剛出生不久就會表現出許多社會性反應——愛、恐懼、憤怒。但是最首要的是愛。作為嬰兒,我們幾乎是最先產生了對熟悉的面孔和聲音的偏好。在父母注意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咕咕囔囔並且報以微笑。到八個月時,我們就可以跟在父親或母親後面爬,而且一旦和父母分離就會哭鬧,等到重新見到父母時,就會緊緊粘住不放。社會依戀作為一個強大的生存推動力,使得嬰兒和父母保持著親密的關係。
如果剝奪兒童熟悉的依戀對象,或者在極端受忽視的情境下,兒童可能會變得退縮、畏懼,沉默寡言。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1980,p.442)對無家可歸的兒童的心理健康情況進行研究之後,向世界衛生組織反映:“與他人的親密依戀關係構成了一個人生活的核心,……人們都是通過這些親密依戀來獲得力量和享受生活的。”
研究者比較了親子之間、朋友之間、配偶或情侶之間等不同的親密關係之中的依戀和愛的特性(Davis,1985;Maxwell,1985;Sternberg & Grajek,1984),發現在所有的愛的依戀(loving attachment)中都有一些共有的元素:雙方的理解,提供和接受支持,重視並享受和相愛的人在一起。然而,激情之愛似乎還有一些額外的特性:身體上的親暱,排他性的期待,以及對愛人的強烈迷戀。
激情之愛並不專屬於情侶。菲利普·謝弗等人(Shaver & others,1988)指出,週歲的嬰兒會對父母表現出強烈的依戀,這和青年人熱戀時所表現出來的依戀非常類似,他們會期望得到愛撫,分離時會感到沮喪,重聚時會表現出強烈的情感反應,並會由於對方的注意和支持而表現出強烈的喜悅情緒。由於嬰兒和他們的看護者之間產生依戀的風格不同,謝弗和哈贊(Shaver & Hazan,1993,1994)就試圖探討嬰兒的依戀類型是否會延續到成人期的關係中去。
依戀類型
大約七成的嬰兒以及接近這個比例的成年人,都會表現出安全型依戀 (secure attachment)(Baldwin & others,1996;Jones & Cunningham,1996;Mickelson & others,1997)。當嬰兒被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通常是一個實驗用的遊戲室)時,如果母親在場,他們就會很舒適地玩耍,快樂地探索這個陌生的環境。母親一旦離開,他們就會變得緊張起來;當母親重新回來時,他們會跑向母親,抱住她一會兒,然後才放開母親繼續剛才的探索和玩耍(Ainsworth,1973,1989)。很多研究者相信,這種信任的依戀能夠形成一種親密的運作模式——為個體繪製一幅成年期所形成的親密關係的藍圖。安全型依戀的成人很容易和別人接近,並且不會由於對別人太過依賴或被拋棄而感到苦惱。這樣的戀人也會在安全的,以及忠誠的相互關係中享受性愛。而且他們的關係趨於令人滿意和持久的狀態(Feeney,1996;Feeney & Noller,1990;Simpson & others,1992)。
大約兩成的嬰兒和成人表現出迴避型依戀 (avoidant attachment)。迴避型的嬰兒在和母親分離或重逢時,雖然會出現內部的生理喚醒,卻極少表現出悲傷。這種類型的成人往往會迴避親密的關係,他們往往對這種關係表現出較少的興趣,更傾向於擺脫這些關係。他們更可能涉足沒有愛情、只有性的一夜情。巴塞洛繆等人(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指出,迴避型個體可能既害怕他人(“當我與別人太接近時我可能會感到不舒服”),又排斥他人(“獨立和自足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大約一成的嬰兒和成人會表現出焦慮和矛盾的行為,稱為不安全型依戀 (insecure attachment)。在陌生環境中,這類兒童會充滿焦慮地粘在母親身邊。母親離開時,他們會哭泣;母親回來後,他們卻會對母親表現出冷漠或敵意。成年的焦慮—矛盾型個體對他人也不夠信任,因此會產生較強的佔有慾和忌妒心。他們和同一個人的關係可能會反覆地出現破裂的情況。在討論出現衝突時,他們會變得情緒激動而且易怒(Cassigy,2000;Simpson & others,1996)。當不安全型的女性懷孕並覺察到來自丈夫的怨怒或得不到丈夫的支持時,那麼,她們會比安全型女性更容易在孩子出生的頭六個月陷入抑鬱(Simpson & others,2003)。
一些研究者將這些不同的依戀類型歸因於父母的反應方式。哈贊(Cindy Hazan,待發表)概括出了如下觀點:“早期的依戀經驗形成了內部工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s)或關於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獨特思考方法的基礎。”安斯沃思(Ainsworth,1979)和埃裡克森(Erik Erikson,1963)觀察發現,敏感的、反應型的母親——會讓孩子對於世界的可靠性形成一種基本的信任感——她們一般都會培養出安全型依戀的孩子。而那些童年曾經受到過悉心養育的人往往會和他們日後的愛情伴侶發展出溫馨而具有支持性的感情(Conger & others,2000)。其他研究者相信,依戀類型還可能會反映出個體不同的天生的氣質類型(Harris,1998)。不管怎樣,早期的依戀類型看來的確為後來人際關係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平
如果感情關係中的雙方毫不考慮對方,而都只追求個人需求的滿足,那麼友誼就會結束。因此,我們的社會教育我們彼此之間要交換饋贈,這被哈特菲爾德等人(Hatfield,Walster,& Berscheid,1978)稱為吸引的公平 (equity)原則:你和你的伴侶從感情中所得到的應該和你們雙方各自投入的成正比。如果兩個人的所得相同,那麼他們的貢獻也應該是相同的;否則其中的一方會覺得不公平。如果兩個人都覺得自己的所得和付出成正比,那麼他們都會覺得公平。
陌生人之間,以及日常的熟人之間通過交換利益來保持公平:你借給我課堂筆記,將來我會把我的借給你;我邀請你參加我的聚會,你又邀請我參加你的。而在那些持續時間較長的人際關係中,比如室友或者愛人之間,則並不會追求完全相同的交換——“筆記對筆記,聚會對聚會”(Berg,1984)——而是更隨意地通過一些不同利益的交換來達成公平(“你過來把筆記拿給我,為什麼不留下來吃晚飯呢?”)。最終也就不再追究誰欠誰的了。
長期的公平
認為友誼和愛情植根於公平交換回報之上很愚蠢嗎?難道我們有時候在滿足愛人需要的時卻沒有考慮任何回報嗎?確實,那些處於公平的長期關係中的人並不在乎短期的公正。克拉克和米爾斯(Clark & Mills,1979,1993;Clark,1984,1986)認為,人們甚至會努力避免 算計交換的利益。當我們幫助一個好朋友的時候,我們並不在意馬上獲得回報。如果有人請我們吃了飯,我們會過一陣子才向這個人發出回請,以免讓他認為,對他的回請只是對“社交債務”的償還而已。什麼是真正的友誼呢?就是人們在幾乎不可能得到回報的時候也會去幫助朋友(Clark & others,1986,1989)。當人們看到自己的夥伴犧牲了自我利益,他們彼此的信任就會有所增長(Wieselquist & others,1999)。怎樣判斷一個人是否已成為了你的好朋友呢?就是在你根本料想不到他會和你分享的情況下,他卻做出了這樣的分享行為。幸福的夫妻是不會 斤斤計較自己付出幾許,收穫幾許的(Buunk & Van Yperen,1991)。
克拉克和米爾斯在馬里蘭大學的學生中進行了實驗,他們發現,不斤斤計較 是友誼的標誌。在正式場合中,投桃報李會促進雙方的關係,但在友誼中卻不是這樣。克拉克和米爾斯猜測,在婚姻中,如果夫妻指出自己期望對方做出什麼樣的行為的話,這樣的做法只會破壞他們之間的關係。只有當對方自願做出某種正向的行為時,我們才會把它歸因為愛情。
此外,這種長期公平原則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婚姻雙方的“資源”往往是相當的。他們在外表吸引力、社會地位等方面往往是匹配的。如果他們在某一方面不匹配,比如外表吸引力,那麼他們在另外的方面也會出現不匹配,比如社會地位。但總體上他們之間的資源是平衡的。沒有人會這樣說,甚至很少有人會這樣想:“我的美麗外表可以換取你的鉅額收入。”但是,公平原則確實是存在的,在那些持久的感情中更是如此。
對公平的知覺與滿意度
處於公平關係中的人們往往滿意度更高(Fletcher & others,1987;Hatfield & others,1985;Van Yperen & Buunk,1990)。那些認為其關係不平等的人往往會覺得不舒服:佔了便宜的一方會覺得內疚,而被佔便宜的一方會感到憤怒。(考慮一下自我服務偏見——大部分的丈夫會覺得他們自己做的家務比妻子認為的要多——那些“佔了便宜”的人對於不公平較為不敏感。)
謝弗和基思(Schafer & Keith,1980)調查了幾百對各個年齡段的夫婦,他們發現,那些覺得自己婚姻不公平的人大多是因為某一方在烹調、家務、照顧孩子等工作中貢獻過少。知覺到的不公平會導致這樣的結局:覺得不公平的一方會更加沮喪和苦惱。在哺乳期,很多妻子都會覺得自己付出的多,而丈夫付出的少,於是這一階段的整體婚姻滿意度會降低。而在蜜月和“空巢”期,夫婦往往更容易覺得公平和滿意(Feeney & others,1994)。如果雙方的付出和獲益都是自願的,並且他們一起做決定,那麼他們的愛情更容易持久而美滿。
格羅特和克拉克(Grote & Clark,2001)根據他們對結婚伴侶的長期追蹤研究結果,得出結論認為,知覺到的不公平引發了婚姻緊張(marital distress)。但據他們報告,不公平與緊張的關係是雙向的:婚姻緊張又會加劇知覺到的不公平(圖11-8)。關係不佳時,我們尤其會覺得不公平,自己付出得多收穫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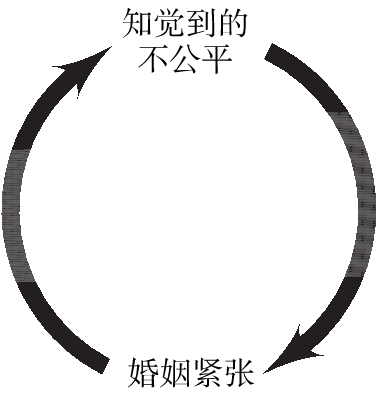
圖11-8 知覺到的不公平會導致婚姻緊張,而又進一步加強了不公平感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Grote & Clark,2001.
自我表露
深厚的伴侶關係是親密無間的。這種關係使人們能真實地展現自己,並且可以從中知道自己是被他人接受的。我們會從美滿婚姻和親密友誼中獲得這種美好體驗——這時候,信任取代了焦慮,使我們更容易展現自己,而不需要擔心失去他人的友情或愛情(Holmes & Rempel,1989)。後來,這種特點就被Sidney Jourard歸結為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Derlega & others,1993)。隨著相互關係的深入和發展,自我表露的伴侶會越來越多地向對方展現自我;他們彼此的瞭解越發深入,直到一個適當的水平為止。
研究發現,大多數人都會喜歡這樣的親密關係。如果一個平時很內向的人說我們的某些東西讓他覺得“願意敞開心扉”,並分享他的祕密,那麼大部分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感到十分高興(Archer & Cook,1986;D. Taylor & others,1981)。被他人挑選為自我表露的對象,是很令人高興的事情。我們不僅喜歡那些敞開胸懷的人,而且也會向自己喜歡的人敞開我們的胸懷,而且在自我表露之後,我們會更加喜歡這些人(Collins & Miller,1994)。如果缺乏發展這種親密關係的機會,我們就會有孤獨的痛苦感受(Berg & Peplau,1982;Solano & others,1982)。
很多實驗試圖探索自我表露的原因和效果。人們什麼時候最願意談論這樣的私密信息呢——比如“你喜歡自己的哪些方面,不喜歡自己的哪些方面?”或者“你最羞愧的事情是什麼?最驕傲的事情是什麼?”這樣的表露對雙方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在沮喪的時候會更多地自我表露——比如生氣和焦慮的時候(Stiles & others,1992)。對於那些我們期望與之有更多交往的人,我們會更多地自我表露(Shaffer & others,1996)。而且安全型依戀的人會比其他類型的人自我表露更多(Keelan & others,1998)。最值得信賴的結論是,人們之間存在表露互惠效應 (disclosure reciprocity effect):一個人的自我表露會引發對方的自我表露(Berg,1987;Miller,1990;Reis & Shaver,1988)。我們會對那些向我們敞開胸懷的人表露更多。但是親密關係的發展並不是隨之即來的。(如果親密關係立即產生,那這個人就會顯得不謹慎和不可靠。)合適的親密關係的發展過程就像跳舞一樣:我表露一點,你表露一點——但不是太多。然後你再表露一些,而我也會做出進一步的迴應。
對於那些戀愛中的人們,親密關係的不斷加深會使他們興奮。鮑邁斯特等人(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認為:“親密關係的增強會創造很強的激情感覺。”當親密關係穩定時,激情就相對較少。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喪偶再婚的人會在婚姻開始時有相對較高的性交頻率,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嚴重衝突得到和解後,親密關係可以激發更高的激情。亨德里克等人(Hendrick & Hendrick,1997)說:“激情和友誼是感情滿意度的兩個主要預測指標。”這兩者可以相互影響:友誼的增進可以提高激情水平。
有些人——主要是女性——特別善於使人“敞開心扉”。她們可以輕易地引發他人進行親密的自我表露,即使是那些通常很少表露自己的人(Miller & others,1983;Pegalis & others,1994;Shaffer & others,1996)。這樣的人似乎都是好的傾聽者。在交談中,他們會一直保持高度注意的面部表情而且總是顯得很樂意傾聽(Purvis & others,1984)。對方說話時,他們也會時不時地插一些支持性的話語,以此表達自己對交談的興趣。心理學家羅傑斯(Rogers,1980)把這些人稱為“促進成長”的聽眾——他們是真正表露自己情感的人,接受他人情感的人,以及共情、敏感並且善於思考的人。
這樣的自我表露有什麼效果呢?Journard(1964)認為,這樣的方式——扔掉我們的面具,真實地表現自己——是培植愛情的方式。他認為對他人敞開自我,同時將他人的自我表露當做是對自己的信任,可以使人們之間的交往更加愉快。例如,擁有一位親密朋友,我們可以與他討論我們對自我形象的恐懼,那麼我們這方面的壓力就得以減緩了(Swann & Predmore,1985)。一段真正的友誼還可以幫助我們處理其他關係上出現的問題。羅馬的戲劇作家塞內卡(Seneca)這樣說道:“當我和好友在一起時,就像跟我自己在一起一樣,我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推到極致,婚姻也正是這種友誼,它以彼此的忠誠為特徵。
自我表露也是伴侶之愛所帶來的快樂之一。那些經常敞開自己心扉的夫婦或情侶,他們會報告更高的滿意度並且更容易保持長久的感情(Berg & McQuinn,1986;Hendrick & others,1988;Sprecher,1987)。那些認為自己“總是把自己最隱私的感情以及想法和自己的伴侶分享”的夫妻,往往對婚姻的滿意度最高(Sanderson & Cantor,2001)。蓋洛普進行的一項全國婚姻調查結果顯示,共同祈禱的夫婦中有75%(不共同祈禱的夫婦中只有57%)的人報告說他們的婚姻非常幸福(Greeley,1991)。在信徒中,發自內心的共同祈禱是謙卑的、私密的、觸及靈魂的表露,那些共同祈禱的夫婦也更經常地討論他們的婚姻,更尊敬自己的配偶,並把自己的配偶評價為善解人意的愛人。
研究者還發現,女性通常比男性更願意表露自己的恐懼和弱點(Cunningham,1981)。正像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75)所說的,“女性表達自己,男性壓制自己。”然而,現在的男性,特別是那些持男女平等觀點的男性,似乎也越來越傾向於表達自己內在的感受,並樂於享受伴隨雙方信任和自我表露而來的滿足感。阿倫等人(Aron & Aron,1994)指出,這正是愛情的精髓——兩個自我相互聯繫,相互傾訴,從而相互認同;兩個自我保持其個性,但又共享很多活動,為彼此的相同之處而感到愉悅並且相互支持(圖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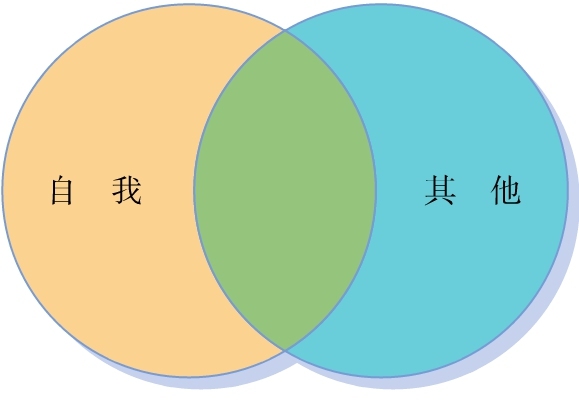
圖11-9 愛情:自我的交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A. L. Weber & J. H. Weber,《對親密關係的看法》。
資料來源:Copyright © 1994 by permission. From Aron & Aron,1994.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通過萌發友誼的親密感的提高所反映出來的經驗,來培養更親密的關係呢?阿倫夫婦和他們的同事(1997)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把互不相識的被試分為兩兩一組,讓他們共處45分鐘。在最初的15分鐘裡,讓他們交流一些低親密性的話題和想法,比如“你最近一次自己唱歌是什麼時候?”接下來的15分鐘,討論比較親密的話題,比如“你最寶貴的記憶是什麼?”最後的15分鐘,要引發更多的自我表露,比如:“完成下列句子:‘我希望有一個人能和我一起分享……’”以及“你最後一次在別人面前哭是什麼時候?自己哭泣呢?”
相比於花45分鐘討論一般問題(“你的高中是什麼樣子?”“你最喜歡哪個節日?”)的控制組被試,那些在近一小時的時間裡經歷了自我表露逐漸升級的被試,明顯感覺自己與交談夥伴更親密——事實上,研究者報告:“有30%的學生認為,這些交談夥伴比生活中最親密的朋友還要親密”。這些關係顯然並不包含真正友誼中的那種忠誠和承諾,但是,這項實驗卻提供了一個驚人的結果:自我表露可以如此輕易地幫助個體建立對他人的親密感——在互聯網上正是如此(見“聚焦:互聯網究竟創造了親密關係還是人際隔絕?”)。
聚焦 互聯網創造了親密關係還是人際隔絕
如果你是這本大學教科書的讀者,那幾乎可以肯定你是世界上大約6億(2003年數據)互聯網用戶中的一員。在北美,大約花費了70年,才使家庭電話普及率由1%上升到75%。而互聯網,大約只花費了7年的時間,普及率就達到了75%(Putnam,2000)。你和其他的大眾(很快就會達到10億)可以輕鬆享受電子郵件,網絡衝浪,閱讀新聞,聊天等等服務。
你對這些現象怎麼想:以計算機為媒介的溝通,能夠替代發展人際關係的真實的溝通嗎?它是擴展我們社交圈的絕佳方式嗎?互聯網使得我們能夠更容易尋找到新朋友,還是佔用了我們面對面的交往時間?讓我們來看看下面的討論。
正方觀點 :就像印刷品和電話一樣,互聯網擴展了溝通,而溝通使人際關係得以發展。印刷品使面對面講故事的時間減少了,電話使面對面聊天的時間減少了,但它們都使我們可以更加方便地與他人接觸,而不受時間和距離的限制。社會關係需要建立社會網絡,而互聯網正好可以達到這一目的。它使我們可以高效地與家人、朋友、志趣相投的人聯繫——包括那些用別的方式不可能發現並結為朋友的人,如多發性硬化症(MS)病人,還是聖尼古拉斯的收藏者,或者是哈里·波特迷。
反方觀點 :誠然網絡可以用於溝通,但這種手段傳遞的信息相當貧乏。它無法反映目光交流、非言語線索、身體接觸等微妙的變化。除了一些簡單的表情符號——比如表示微笑的不帶任何差別的:-)——電子信息缺乏手勢、面部表情、語調等信息。難怪它們容易讓人產生誤會。缺乏富有表現力的電子表情(e-motion),使得情緒(emotion)容易被人誤讀。
比如,語調的細微差別可以表示一個陳述是嚴肅的、開玩笑的,還是神聖的。賈斯汀·克魯格等人(Kruger & others,1999)表明,儘管人們覺得自己開玩笑的意圖在e-mail中或是口頭表達中是同樣清晰的,但實際上,在e-mail中卻不是如此。由於匿名的原因,誤會有時甚至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果。
此外,互聯網還像電視一樣,佔用了人們用在真實關係中的交流時間。虛擬愛情還沒有發展到與現實約會同等的地位,而網絡性愛也是人為製造的親密假象。個體化的網絡娛樂取代了橋牌之類的遊戲。這種虛擬化與隔絕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我們進化的歷史決定了我們天生需要真實的相互關係,充滿了傻笑、微笑、相吻相依的交流。難怪斯坦福大學的一項調查發現,在4000名被調查者中,有25%的人報告說,他們的在線時間減少了他們與家人和朋友面對面交流和打電話的時間(Nie & Erbring,2000)。
正方觀點 :但是,大多數人並沒有覺得互聯網使他們孤立了。另外的一個全國調查發現:“一般的互聯網用戶——特別是那些女性用戶——都相信他們利用e-mail增強了他們的人際關係,並增加了與親朋好友的交流機會”(Pew,2000)。互聯網的使用可能會取代人際間的親密交流,但它也同時取代了花費在看電視上的時間。而且,如果點一下鼠標在網上購物不利於你住所附近的書店的話,那麼,它也為你的人際交往騰出了時間。電信交流也是同樣的,它使很多人可以在家工作,並且為他們的家庭生活贏得更多時間。
為什麼說通過互聯網形成的關係不真實呢?在互聯網上,你的相貌和所處的場所都無所謂,年齡、種族也不再有影響,你的友誼決定於更重要的東西--你們共同的興趣和價值觀。在工作中,以計算機為媒介的討論更少受到地位的影響,從而使人更為坦誠,且參與機會均等。並且,以計算機為媒介的溝通還往往比面對面的溝通更能引發人們自發的自我表露(Joinson,2001)。
到2003年為止,每個月都有4500萬人報告,他們在使用互聯網的約會網站(Harmon,2003)。在2003年的上半年,僅就美國人而言,在這類互聯網約會網站上的花費就達到了2億1400萬美元之多,這個數字幾乎是2001年總和的3倍(Egan,2003)。
大部分互聯網上的調情都會無疾而終,一位多倫多婦女談道:“所有我知道的嘗試過網上約會的人……都承認,她們對於和一個網友花費了幾個鐘頭閒聊之後見面,卻發現他是個溜鬚拍馬之徒這樣的事情感到十分厭惡”(Dicum,2003)。但是麥克納和巴奇等人(McKenna & Bargh)的報告中卻提到:通過互聯網形成的友誼和浪漫關係更容易保持至少兩年時間(Bargh & others,2002;McKenna & Bargh,1998,2000;McKenna & others,2002)。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還發現,人們在互聯網上表露得更多,表現得更加誠實而少浮華。如果拿互聯網上相處20分鐘的人與面對面相處20分鐘的人相比,人們更喜歡那個網上的人。甚至在兩種條件下碰到的是同一個人時,情況也仍然如此。在現實生活中的調查也顯示,人們認為網上的友誼與現實中的友誼一樣真實、重要和親密。
反方觀點 :互聯網可以使人們展現真實的自我,但同時也可以使人們假裝成任何他們想要的樣子,有時候甚至還為了達到性欺詐的目的而不擇手段。而且,網絡色情和其他形式的色情作品一樣,會扭曲人們對性的實際情況的認知,降低他們真實伴侶的吸引力,使男性更多地從性的角度看女性,將性脅迫當作小事,為人們在性情境中怎樣行為提供心理圖式,提高喚醒水平,從而減低抑制並導致對無愛的性行為的模仿。
最後,羅伯特·帕特南(Putnam,2000)提出,以計算機為媒介的溝通帶來的社會收益受到兩個現實方面的限制:“數字鴻溝”加劇了既得利益者與未得利益者之間的社會和教育不公現象。“計算機割據”使得德國寶馬汽車公司2002的業主們都湧入了互聯網,如我們在第8章中闡述的,這種“割據”也使得白種人至上主義者得以相互聯絡而彼此促進。數字化隔離問題可以通過降低互聯網費用和增加公共使用場所來解決,而計算機割據問題是任何媒體都具有的。
隨著對於互聯網對社會影響的討論不斷持續,帕特南(p.180)說:“最重要的問題並不是互聯網對我們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而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互聯網?……我們如何利用這種技術手段增強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如何改進技術以增加社會性的存在,增強社會性的反饋,以及社會性的線索?我們如何利用這種快速而經濟的溝通手段去彌補現實溝通手段的不足?”
小結
從嬰兒到老年,依戀都是人類生活的中心。安全的依戀會使婚姻持久,生活美滿。
伴侶之愛的一個好處就是彼此有機會進行親密的自我表露,這是一種雙方隨著對方表露程度的提高而做出迴應從而逐步達到的一種狀態。如果雙方覺得相互關係是平等的,他們的付出與回報是成比例的,伴侶之愛就能更持久。
親密關係是如何結束的
不是所有的愛情都能天長地久。那麼,哪些因素可以預測婚姻的解體?夫妻通常如何分手或複合?
1971年,一個小夥子給自己的新娘寫了一首情詩,然後把它塞進瓶子並扔到了西雅圖和夏威夷之間的太平洋海域。10年後,有人在關島附近海岸慢跑時發現了這首裝在瓶子裡的情詩: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可能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但我相信我們的愛情仍然會像現在一樣鮮活。
這封信可能要花上一週,甚至幾年的時間才能“找到你”……即使它永遠都不能到你手中,我仍然銘記於心的就是,我會不顧一切地去證明我對你的愛。——你的丈夫,鮑伯。
發現情書的人通過電話找到了那位十年前的新娘。當把情書的內容讀給她聽時,她竟然大笑起來,而且越聽笑得越厲害。最後,她只說了一句“我們已經離婚了”就掛斷了電話。
事實通常如此。人們將自己不滿意的婚姻關係與想像中可從別處獲得的支持和情感相比較,越來越多的人會選擇離婚,今天的離婚率已經是1960年時的2倍。目前,美國人的婚姻大約有半數是結束於離婚,而加拿大大約是40%。婚姻的長久,不僅源自長久的愛情和滿足,還源自對其他可能伴侶的忽視、對離婚代價的恐懼,以及道德責任感(Adam & Jones,1997;Miller,1997)。20世紀60和70年代,部分是由於進入職場的女性越來越多,經濟和社會因素對離婚的阻礙作用被削弱了,離婚率不斷上升。吉尼絲(Os Guiness,1993,p.309)的話很有諷刺意味:“我們活得更長了,但愛得更短了。”
英國溫莎皇室早已領教了現代婚姻的風險。公主瑪格麗特和安妮、王子查爾斯和安德魯童話般的婚姻都以失敗告終,微笑被無情的對視所取代。1986年,剛嫁給安德魯王子不久,薩拉(Sarah Ferguson)便對外宣稱,“我愛他的智慧,他的魅力,他的外貌。我仰慕他。”安德魯對她的迴應是,“在我的生命中,她是最美好的。”而6年後,安德魯挑剔薩拉的朋友“沒有教養”,薩拉也嘲笑安德魯的行為“極其粗魯”,二人宣佈離婚(Time ,1992)。
離婚
離婚率在不同的國家差異較大,在玻利維亞、菲律賓和西班牙,每年離婚的人口僅佔總人口的0.01%,而世界上最具離婚傾向的美國,離婚率已達到4.7%。若要預測一種文化中的離婚率,最好是瞭解這種文化的價值觀(Triandis,1994)。相對於集體主義文化(在那裡愛情意味著承擔責任,人們在意的是“別人會怎樣說?”),在個人主義的文化(在那裡愛情是一種感受,人們在意的是“我自己怎麼想?”)中會有更多人離婚。個人主義者結婚是“為了我們彼此相愛”,而集體主義者更多是為了生活而結婚。個人主義者期待婚姻中有更多激情和個人的自我實現,這給婚姻關係帶來了更大的壓力(Dion & Dion,1993)。在一項調查中,有78%的美國女性認為“保持浪漫”對良好的婚姻十分重要,而在日本女性中則只有29%(American Enterprise,1992)。
然而,即使是在西方社會,那些在結婚時已經考慮成熟而且打算長相廝守的人,確實也會有更健康、穩定而長久的婚姻(Arriaga,2001;Arriaga & Agnew,2001)。那些對婚姻的承諾比結婚的意願還要看重的人通常能夠容忍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和不滿。一項全國性的調查發現,那些婚姻不幸福但仍然維持婚姻關係的人,五年後被再次訪談時,有86%的人認為自己的婚姻現在“非常”或“相當”幸福(Popenoe,2002)。相比之下,那些“自戀者”——更關注自己的意願和形象的人——結婚時則沒有那麼堅定的承諾,因此他們擁有一段長久的成功婚姻的可能性要小一些(Cmpbell & Foster,2002)。
離婚的風險有多大同樣取決於誰跟誰結婚(Fergusson & others,1984;Myers,2000;Tzeng,1992)。符合下列條件的夫婦通常不會離婚:
20歲以後結婚。
都在穩定的雙親家庭里長大。
結婚之前談了很長時間戀愛。
接受過較好且相似的教育。
有穩定收入。
居住在小城鎮或農場裡。
結婚之前沒有同居過或懷孕過。
彼此之間有虔誠的承諾。
年齡、信仰和受教育水平相似。
這些預測因素中沒有一個能夠獨立作為穩定婚姻的實質要素。但是,如果某個人的情況跟以上各條全都不符的話,那麼他的婚姻幾乎必定要破裂。如果一對夫妻的情況與以上各條全部符合的話,他們非常有可能白頭到老。英國人在幾個世紀之前的想法可能是對的,他們當時認為,陶醉於一時激情所做出的長相廝守的決定是愚蠢的。他們認為,基於穩定的友誼和相近的背景、興趣、習慣和價值觀去選擇伴侶會比較好(Stone,1977)。
分離的過程
一刀兩斷會產生一系列可以預料的結果,最初是對失去的伴侶不能釋懷,然後是深深的悲傷,最後開始了情感上的分離並回到正常生活中(Hazan & Shaver,1994)。即使早已沒有感情的夫妻,在剛離婚的時候也會驚訝於自己還有接近對方的意願。深入而長久的依戀關係很難快速地分離;分離是一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事件。
在約會的情侶中,關係越是親密、長久,可選擇的其他對象越少,分手時就越痛苦(Simpson,1987)。令人驚訝的是,鮑邁斯特和沃特曼(Baumeister & Wotman,1992)的報告指出:在數月或數年之後,拒絕別人的愛比自己的愛被拒絕能夠喚起人們更多的痛苦。人們的痛苦來自於對傷害他人所感到的內疚,來自於心碎的愛人的執著所引起的不安,也來自於不知該如何做出反應。對已婚者來說,離婚還有額外的代價:父母和朋友感到震驚,對自己違背誓言感到內疚,養育孩子的權利可能受限。然而,每年仍有上百萬對夫妻願意付出這個代價而使自己獲得解脫,因為他們覺得持續一段痛苦而無所獲益的婚姻關係將是更大的代價。在一項對328對已婚夫婦的研究中發現,持續一段不幸婚姻的代價還包括,與婚姻美滿者相比,婚姻不和諧者抑鬱症的患病率會高出10倍(O'Leary & others,1994)。
當婚姻關係令人感到痛苦時,那些沒有更好的可選對象或感覺自己為婚姻投入(時間、精力、共同的朋友、財產,也許還有孩子)太多的人,通常會去尋找離婚之外的其他應對方式。Caryl Rusbult和她的同事(1986,1987,1998)發現了人們處理失敗婚姻關係的三種方法(表11-1)。一些人會忠誠 於伴侶,等待時機以改善關係。婚姻關係問題如此痛苦,令人不願提及,加之離婚的成本太高,因此忠誠的一方會堅持下去,期待昔日美好光陰的重現。另一些人(尤其是男性)會忽略 伴侶,他們無視另一方的存在並任由婚姻關係繼續惡化。當他們將痛苦和不滿忽略掉,情感上的分離便隨之而來,伴侶之間談話更少並開始重新定義他們沒有彼此的生活。還有一些人會表達 他們在乎的內容,並採取積極措施改善婚姻關係,如討論問題、尋求建議、嘗試改變。
表11-1 對痛苦婚姻關係的反應被動的
被動的 |
主動的 |
|
建設性 |
忠誠:等待改善 |
表達:試圖改善關係 |
破壞性 |
忽略:忽視對方 |
退出:結束婚姻關係 |
資料來源:Rusbult & others,1986,1987,1998,2001.
涉及45000對夫妻的115項研究顯示,不幸福的夫妻彼此爭吵、命令、責難和羞辱,而幸福的夫妻通常更加一致、贊同、妥協並且愉快(Karney & Bradbury,1995;Noller & Fitzpatrick,1990)。在觀察了2000對夫婦之後,約翰·戈特曼(Gottman,1994,1998)提出,健康的婚姻並不見得沒有衝突,而是夫妻雙方能夠調和差異,並且他們的情感能夠勝過相互的指責。在成功的婚姻中,積極互動(微笑、觸摸、讚美、歡笑)與消極互動(譏諷、反對、羞辱)的數量之比至少為5:1。
戈特曼和他的同事(1998)對130對新婚夫婦進行了為期6年的追蹤研究。發現如果丈夫能夠接受妻子的批評(對“別插嘴”的反應可能是“對不起,你剛才說什麼了?”),他們的婚姻通常能夠繼續下去。如果丈夫反脣相譏(“如果有我說話的份兒,我還會插嘴嗎”),他們離婚的可能性就會增大。休斯頓等人(Huston & others,2001)對新婚夫婦的追蹤研究發現,痛苦和爭吵並不能預測離婚。(大多數新婚夫婦都經歷過衝突。)真正能夠預測婚姻危機的因素是冷漠、希望破滅和無助。斯旺等人(Swann & others,2003)發現,當羞怯的男性找了挑剔的女性為妻時(違背傳統的性別期望),情況更是這樣。
婚姻成功的夫妻有時能從溝通訓練中獲益,學會如何抑制惡性侮辱、避免大動肝火、平息怒火(通過採用非侮辱性言語表達感受)以及不將衝突的矛頭指向個人,比如可以說,“我知道這不是你的錯”(Markman,& others,1988;Notarius & Markman,1993;Yovetich & Rusbult,1994)。如果雙方都願意像幸福的夫妻那樣做——減少抱怨和責難,增加肯定和贊同,騰出時間表達彼此的觀點,每天一起祈禱或休閒——不幸的婚姻關係是否會得到改善?態度可因行為而變,那麼情感是否也會這樣呢?
凱勒曼等人(Kellerman,Lewis,& Laird,1989)想知道這個猜測是否成立。他們知道,在熱戀的情侶中,眼神的凝視通常是持久而相互的(Rubin,1973)。親密的凝視是否也能激發非情侶的異性之間產生愛戀呢(就像45分鐘逐步增強的自我表露能夠在不相識的大學生中產生親密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要求不相識的一對男女專心地彼此凝視兩分鐘,一種實驗條件是凝視對方的手,另一種實驗條件是凝視對方的眼睛。當兩人分開後,凝視眼睛者報告了觸電般的感覺且被對方所吸引。模仿相愛的行為也能夠激發愛情。
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1988)認為,通過扮演和表達愛意,最初的浪漫和激情能夠發展成持久的愛情:
“永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並非只能出現在童話故事中。如果將其變為現實,那麼幸福一定是基於愛情關係在不同發展階段所產生的相互情感的不同構造。渴望激情永存或親密關係不受挑戰的伴侶一定會感到失望……我們必須致力於不斷地理解、創建和重建我們的愛情關係。關係是一個建構物,如果沒有得到維持和改善,就會隨著時間而衰退。我們不能簡單地期望愛情關係會像建築物那樣保持自身的穩定。我們有責任去創造我們愛情關係的最佳狀態。
小結
愛情並不總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由於離婚率不斷上升,研究者探明瞭婚姻解體的預測因素,包括強調感受重於承諾的個人主義文化,以及雙方的年齡、受教育水平、價值觀和相似性等。研究者也弄清了夫妻雙方分手或重建其婚姻關係的過程。他們也在試圖弄清健康而穩定的婚姻所需要的積極的、非對抗的溝通方式。
個人後記:經營愛情
現代生活的兩個事實似乎無可辯駁:其一,親密而持久的婚姻關係是幸福生活的標誌。國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自1972年起對40605個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有40%的已婚者、22%的未婚者、19%的離婚者和16%的分居者認為他們的生活“非常幸福”。加拿大和歐洲各國的全國性調查中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Inglehart,1990)。
其二,親密而持久的婚姻關係正在減少。與幾十年前相比,人們現在更經常搬家、獨自生活、離婚以及擁有接連數段婚姻關係。
假如婚姻幸福的心理要素是心意相通、交往和性的親密、平等地給予和獲取情感和物質資源,那麼法國的這句諺語:“愛情消磨了時間,時間也消磨了愛情”就可能站不住腳。但人們必須付出努力才能防止愛情的衰退。例如,每天擠出時間來聊聊當天發生的事情;剋制自己的嘮叨,不爭吵,袒露自己並傾聽對方的感傷、關注和夢想;努力使婚姻關係達到理想的完美境界,成為“社會平等的、無階級的烏托邦”(Sarnoff & Sarnoff,1989),伴侶雙方都能自由地給予和獲取,能夠共同做出決策並一起享受生活。
哈維等人(Harvey & Omarzu,1997)指出,“用心照顧”我們的親密關係能夠使我們獲得更長久的滿足。澳大利亞婚姻關係研究者諾勒(Patricia Noller,1996)也認為:“成熟的愛情能夠維繫婚姻和家庭,因為它為每個家庭成員都創造了成長的環境……成熟的愛情是被一種信念所支撐的:愛情本身就包括對差異和缺點的承認和接納;愛情是在內心決定去愛一個人並對其做出長相廝守的承諾;愛情是可以經營的,它需要相愛的人共同去培育。”
那些承諾要創造一段平等、親密、相互支持的婚姻關係的人可能會從持久的伴侶之愛中獲得安全和快樂。是否有一個人“長期愛戀著你”,年長的智者Skin Horse對Velveteen Rabbit解釋道:
“他不僅僅是想跟你一起玩,而且是真的愛你,你也會變得認真起來。”
“他會傷害我嗎?”Rabbit問。
“有時會”,Skin Horse說,他總是以實相告。“如果你認真,你就不會介意受到傷害。”
“他的愛是一次性迅速發生嗎,就像被上了發條那樣?”Rabbit問,“還是漸漸發生?”
“並不是一次性發生的”,Skin Horse說,“需要很長時間。這就是為什麼長久的愛情通常不會發生在那些輕易分手,稜角分明或需要小心對待的人身上。一般來說,當你投入真愛時,你會變得毛髮脫落、目光遊離、筋骨鬆弛而且衣衫不整。但是這並不重要,因為一旦你投入真愛,你就不會是醜陋的,除非那個人不懂你的愛。”
你的觀點是什麼
想想你的依戀類型。你覺得你是安全型的,不安全型的,還是迴避型的?如果可以的話,你想在自己的依戀風格上做出哪些改變?
聯繫社會
在這一章的開頭,我們提到了基普林·威廉斯關於排斥的研究。他與第8章(群體影響)中研究社會墮化的基普林·威廉斯是同一個人。本章強調了關係,包括拉斯比爾特和斯騰伯格有關關係如何終止的研究。第2章提到了埃默裡教授所做的有關已婚夫婦對於他們離婚可能性的不現實的樂觀態度的研究。那麼關於離婚趨勢還有了哪些研究?
[1] Beatles樂隊的一張專輯——譯者注。
[2] Charles Steinmetz(1865~1923),美國電工學家、發明家——譯者注。
[3] Denzel Washington,當代偉大的實力派黑人演員,也是目前好萊塢身價最高的黑人影星——譯者注。
[4] Botox,主成分為高度純化的肉毒桿菌素A型,是一種神經肉傳導的阻斷劑,用以治療過度活躍的肌肉。在美容醫學中常用於消除皺紋——譯者注。
[9]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十九世紀英國著名女詩人。這裡引用的這句詩選自她抒情十四行詩集的第四十三首——譯者注。
[10] Robert Graves(1895~1986):英國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譯者注。
第12章 利他:幫助他人
我們為什麼會有幫助行為
獲得回報,避免懲罰
進化心理學
比較和評價幫助行為的理論
真正的利他主義
我們何時會幫助
旁觀者數量
當別人也提供幫助時
時間壓力
相似性
誰會提供幫助
人格特徵
宗教信仰
如何增加幫助行為
去除對幫助的抑制
利他主義的社會化
個人後記:讓社會心理學走進生活
“愛能拯救人——不論是施與愛的人還是得到愛的人。”
——精神病學家卡爾·梅寧格(Karl Meninger,1893~1990)
紐約地鐵列車進站的隆隆聲越來越響,埃弗裡特·桑德森卻跳下路軌奔向迎面而來的列車,去救一名從站臺上掉下去的4歲女孩,她的名字叫米歇爾·德耶色斯。就在列車將要碾過女孩之前的3秒鐘,桑德森把米歇爾拋向了站臺上擁擠的人群。列車呼嘯將至,而桑德森卻沒能靠自己的力量跳上站臺。在最後緊急關頭,旁人把他拉到了安全的站臺上(Young,1977)。
下面是另一個捨身救人的震憾人心的事例:1997年的一個晚上,23歲的美籍黑人建築工奧帝斯·蓋瑟,看見一團火焰從一間由汽車拖拉的活動房裡噴出來,他便破門而入,找到並救出了已經昏迷的44歲的白人拉里·惠滕,而且還為他做人工呼吸。蓋瑟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並沒有計較頭頂上飄動著的南部聯盟(南北戰爭時南部邦聯是反對解放黑奴的——譯者注)的旗幟。當別人讚頌他超越種族的英勇事蹟時,蓋瑟說:“我並不值得關注,換了其他人也會這樣做。”(Time ,1997)
耶路撒冷的“正義之路”位於一個山坡上,由好幾百棵樹構成,每棵樹下都有飾板,上面刻著一些歐洲基督教徒的名字,這些人曾經在納粹大屠殺時期給猶太人提供過庇護。這些“正義的異教徒”(在當時的耶路撒冷,把信奉非猶太教的人稱為異教徒——譯者注)知道,如果被納粹政府發現,他們將與猶太人一樣承受被處死的命運,但仍有很多基督教徒庇護了猶太人(Hellman,1980;Wiesel,1985),還有不計其數的庇護者沒有留下姓名。每一個在納粹恐怖中倖存下來的猶太人背後,離不開數十人的英勇行為。樂隊指揮康拉德·拉特是居住在遠離戰爭的柏林的2000名猶太人之一,他就是因為受到50名英勇的德國人的保護而活了下來(Schneider,2000)。
“9.11”及之後的日子裡,這一蓄意發動的罪惡襲擊引發了不計其數的善行。血庫擠滿了人,食品站擠滿了人,衣物站也擠滿了人,人們都從內心深處希望能夠貢獻一些什麼,去安慰那些受到嚴重傷害的人並滿足他們的需要。很多都是自我犧牲的利他行為。當世貿中心的北樓遭到撞擊後,埃德·埃默裡護送5名在南樓90層的Fiduciary Trust公司的同事下了12層樓,讓他們進了一趟已經擠得滿滿的快速電梯,他自己又回到97層,希望再帶著6位正在備份電腦資料的同事撤退。就在這一剎那,他們這座樓被擊中了,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後來,他的同事愛德華·麥克納利也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自己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能夠幫助所愛的人?就在大樓開始坍塌的時候,麥克納利打電話給妻子麗茲,講述了人壽保險的條款和賠付。“他說我對他來說就意味著整個世界,他愛我。”麥克納利太太后來回憶說,他們似乎已經做了最後的告別(《紐約時報》,2002)。但是,她的電話再一次響起。麥克納利不好意思地說,他已經為他們預定了到羅馬慶祝她40歲生日的機票。“麗茲,你得取消它了。”
不那麼傳奇的利他行為更是不勝枚舉,諸如安慰、照料和同情等,人們通常不求任何回報地為別人指路,捐款,獻血,做義工。
人們為什麼、什麼時候會做出幫助行為?
誰會做出幫助行為?
怎樣才能減少冷漠而增加幫助行為?
這就是本章的基本問題。
利他主義 (Altruism)是自私自利的反義詞。一個利他的人即使在無利可圖或不期待任何回報的情況下,也會關心和幫助別人。耶穌關於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寓言為此提供了經典的詮釋:
一名男子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Jericho),途中落入強盜之手,強盜搶光了他的財物,並打得他半死不活,然後跑掉了。這時,恰好有一名傳教士經過這兒。傳教士看到了受傷的男子,便從路的另一邊走過去了。這時又來了一個利未人(Levite),他同樣看見了受傷的男子,也從路的另一邊走過去了。但是撒馬利亞人(Samaritan)卻不同,他途經這裡,看見受傷的男子,就動了惻隱之心。他走到受傷人的身邊為他包紮傷口,還在傷口上搽上油和酒。然後,他把受傷人放到自己的馬背上,帶他到一家小旅館並照料他。第二天,他掏出一些錢給老闆,說:“好好照顧他;等我回來,錢不夠,我會補給你。”(聖經·路加福音10章30~35節)
這個撒馬利亞人的行為詮釋了利他主義。他完全為同情心所驅動,為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奉獻了時間、精力和金錢,卻既沒有期待任何回報,也沒有期待任何感激。
我們為什麼有幫助行為
為了研究幫助行為,社會心理學家們考察了人們做出幫助行為的各種條件。在瞭解實驗所揭示的內容之前,讓我們先考慮一下哪些事物會激發人們的幫助行為。
獲得回報,避免懲罰
幾種關於幫助行為的理論都一致認為,從長遠來看,幫助行為會使施與者和接受者同樣受益。有一種解釋假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受“社會經濟學”指引。人們相互之間不僅交換物質性的商品和金錢,而且還交換社會性的商品——愛、服務、信息、地位等(Foa & Foa,1975)。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採用“極小極大化(minimax)”策略——令花費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exchange theory)並不主張我們要有意識地去監控花費和收益,只是表明這類因素能預測人們的行為。
假設你的校園裡有一輛獻血車,有人要你參加獻血。難道你會不權衡一下獻血的代價(針紮下去的疼痛,時間,疲乏)和不獻血的代價(負罪感,他人指責)嗎?難道你會不考慮獻血的收益(因幫助別人而產生的愉悅感,免費的點心)和不獻血的好處(節約時間,不至於不安和焦慮)嗎?根據社會交換理論——該理論得到來自皮列文(Jane Allyn Piliavin)及其研究小組(1982,2003)對威斯康星獻血者研究的支持——人們在決定是否提供幫助之前有精細的盤算。人們像是要為自己的同情心找些藉口,有人發現,當給捐獻者提供一些諸如糖果、蠟燭之類的小物品時,他們就會向慈善機構捐獻更多的錢,即使他們其實並不需要(也永遠不會買)這些東西。這就解釋了社會交換(Holmes & others,1997)。
社會交換
催生幫助行為的報償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商人捐款能提高其企業形象,讓順路的人搭車能獲得稱讚或友誼,這些回報都是外部的。我們的付出是為了收穫。因此我們會最熱心地幫助那些對我們有吸引力的人,幫助那些我們渴望得到其讚許的人(Krebs,1970;Unger,1979)。
幫助行為也能提升我們的自我價值感。在皮列文的研究中,幾乎所有的獻血者都承認獻血“使你對自己感覺良好”和“給予你自我滿足感”。的確,一張傳統的紅十字會海報這樣寫道:“獻血!只會使你感覺良好。”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離家在外的人會為那些他們以後再也不會見面的陌生人做善事。
幫助行為對自我價值感的積極作用,為因何那麼多的人在做過好事之後更會做好事提供了一種解釋。一項為時一個月的針對85對夫婦的研究發現,給予對方情感支持,對自己也具有積極的作用,會使自己產生積極的心境(Gleason & others,2003)。皮列文(2003)和蘇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1998)指出,大量研究結果顯示,投身於社區服務計劃,投身於以學校為基礎的“幫助他人學習”或輔導兒童等活動的年輕人,都發展了社會技能和積極的社會價值觀。這些年輕人明顯地更少面臨犯罪、未婚懷孕、輟學等危機,而更可能成為良好公民。志願者行動也同樣地有益於成年人的精神狀態乃至健康狀況。所以,人們做了好事之後還會做更多的好事。
這樣的成本—收益分析看起來有失身份。然而,這個理論是有一定道理的。難道“善有善報”不是對人性的一種信任嗎?難道我們不相信人們的大多數行為不是“反社會”的,而是“親社會”的嗎?難道我們不相信人們可以從愛心奉獻中獲得滿足嗎?如果人們就是為了自我獲得快樂,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有些讀者會迴應說:“說的不錯,但回報理論難道不是意味著幫助行為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利他行為嗎?當回報是無意識地獲得時,我們可能會說那種行為是利他的。但是如果我們幫助一位嚇得尖叫的女士是為了獲得社會讚許,釋放我們的壓力,避免內疚,或者提升我們的自我形象,那麼這能算真正的利他嗎?”這樣的爭辯要追溯到斯金納(B. F. Skinner,1971)對幫助行為的分析。斯金納認為,只有當我們不能解釋別人做好事的原因時,我們才會因此而信任他們。只有當我們找不到外在的解釋時,我們才會把他們的行為歸因於他們內在的品質,而當外部原因明顯時,我們就會相信外部原因,而非個人品質。
然而,回報理論也有一個弱點。它容易陷入循環論證的境地。如果一個人志願參加“大姐姐指導計劃(Big Sister tutor program)”,很容易讓人把其富有同情心的行為解釋為那樣能為其帶來滿足感。但這種對回報進行事後命名的做法又引起了循環的解釋:“她為什麼會做志願者呢?”“因為有內部回報。”“你怎麼知道有內部回報呢?”“那除了這個,她還會因為什麼去做志願者呢?”因為有這樣的瑕疵,利己主義 (egoism)——主張自我利益驅動所有行為的觀點——在研究者中名聲不佳。利己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利他主義的終極目標則是增加他人的福利。
為了避免陷入這樣的循環,我們必須把收益和成本獨立於幫助行為之外。如果社會讚許引發了幫助行為,那麼在實驗中我們就能發現,幫助行為之後就會有讚許,而事實也正是如此(Staub,1978)。
內部回報
目前為止,我們主要分析的是促使人幫助他人的外部回報,現在,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內在的原因,比如幫助者的情緒狀態或者個人品質。
幫助行為的收益也包括內部的自我回報。接近一個痛苦的人,我們也會感到痛苦。窗外一聲婦女的尖叫驚動並困擾你,如果你不能視它為鬧著玩而減少對它的關注,你就會去查看一下或給予幫助,從而減輕你因它而產生的痛苦(Piliavin & Piliavin,1973))。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 Krebs,1975)發現,哈佛大學生的生理反應和他們的自我報告都揭示,由他人的痛苦喚起的反應最強的,給別人提供的幫助最多。[克雷布斯(1999)報告說:“那些曾幫助我度過難關的人的慷慨行為燃起了我對利他主義的興趣。”作為一名被放逐的14歲的學生領袖,克雷布斯從溫哥華到加利福尼亞,他與法律不斷周旋,進過少管所和監獄。後來逃出牢獄,回到英屬哥倫比亞,獲准進入大學,畢業時成績名列前茅,被哈佛大學接受去攻讀博士學位。克雷布斯沒有隱瞞他的過去,他的經歷公開後,他曾被孤立,後來又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獲得諒解。最後,他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繼而當了西蒙弗雷澤大學心理系的主任。他說:“我透露這段歷史,是想以此鼓勵那些連遭人生打擊的人繼續與命運抗爭。” ]
內疚感 痛苦(distress)並不是我們要減輕的惟一的消極情緒。從古至今,內疚感一直是一種令人痛苦(painfal)的情緒,以至於我們總是要設法避免內疚感的產生。就像埃弗裡特·桑德森救了掉下路軌的小女孩後說的那樣,“如果我沒有設法去救她,只是像其他人一樣站在那兒,那我的內心其實已經死了,從那時起我就不再有良好的自我感覺了。”
文明進化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形成了各種方式來緩解內疚感:用動物和人做祭品、供奉穀物和金錢、懺悔、認罪、否定等等。在古代以色列,人們定期地將自身的罪過加諸於作為“替罪羊”的動物身上,然後把動物放到野外,讓它帶走人類的罪責感。
為了測查內疚感導致的結果,社會心理學家設法引出人們的違規行為:說謊、釋放電擊、打翻放著按字母順序排列卡片的桌子、損壞設備、欺騙等。然後,給這些負罪的被試提供一個可以緩解內疚感的機會:認錯,貶低被傷害者,或者將功補過。結果顯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人們會盡其所能去消除內疚感,減少不良感覺,並恢復自我形象。
假設你正作為一名被試,與密西西比州立大學(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的學生一道,參加戴維·麥克米倫和詹姆斯·奧斯汀(David McMillen & James Austin,1971)進行的一項實驗。你和另一個學生一起為了得到學分而來參加這個實驗。就在這時,一個自稱是先前的被試的人走進來找丟在這兒的本子,他和你們攀談起來,說這個實驗要做一份多項選擇測驗,而測驗的正確答案多為“B”。他離開後研究者進來了,研究者先介紹了實驗,然後問:“你們倆以前參加過這個實驗或者聽到過有關它的任何事情嗎?”
你會說謊嗎?那些先於你參加實驗的被試的行為已經告訴我們了答案,他們100%地撒了這個小謊。做完測驗後(沒有任何反饋),研究者說:“你們可以走了。但是你們如果有空的話,能幫忙給一些問卷評分嗎?”假設你已經說了謊,現在你會更樂意無償地付出一點時間嗎?結果表明,答案又是肯定的。平均說來,那些沒有被引誘說謊的被試只給出了2分鐘,而說了謊的被試則很明顯地渴望補救他們的自我形象,他們平均慷慨地獻出了63分鐘。我們自己的實驗中,有一個7歲的小女孩對這一實驗的寓意做了恰如其分的解釋,她寫道:“別說謊,不然你會生活在內疚裡”(並且你還會感到有一種要緩解它的需要)。
我們在犯錯之後的行善願望反映出,我們既需要減輕個人的 (private)內疚感,也需要恢復動搖了的自我形象和期望確立積極的公眾(public)形象。當我們犯下的錯誤被他人知曉時,我們就更加想要用幫助行為來挽回我們自己(Carlsmith & Gross,1969)。但是,即便我們的內疚感是他人所不知的,我們也會以行動來減輕它。丹尼斯·裡甘及其助手(Dennis Regan & others,1972)在紐約的一個購物中心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使一些婦女相信她們弄壞了相機,過一會兒,研究者的同夥提著一袋蠟燭從婦女的身邊經過,蠟燭從裝得滿滿的購物袋中掉了出來。沒有負疚感的婦女中只有15%的人會提醒提蠟燭袋的人,而有負疚感的人發出提醒的比率是前者的四倍。儘管有內疚感的婦女沒有必要在研究者的同夥面前挽回自己,但助人之舉的確減輕了她們心中的內疚感,挽回了她們的自我形象。解除內疚感的其他方法——如坦白——則會減少由內疚而引起的助人行為(Carlsmith & others,1968)。
總而言之,內疚感有許多益處。它促使人們坦白、道歉、幫助、避免再犯錯誤,它還使人們更敏感,並使親密關係能夠持久。
消極心境 如果說內疚感能增加幫助行為,那麼其他的消極感受是否也能這樣呢?如果你正為考試成績不好而悶悶不樂,看到一個人手上拿的報紙散落一地,你會比平時更可能去幫助他呢,還是更不可能幫助他呢?
乍一看,結果令人迷惑。將人們置於消極心境中(通過讓他們閱讀或想像不愉快的事情),有時候會增加幫助行為,有時候則相反。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就能在混亂中找到一些規律。首先,那些發現消極心境減少幫助行為的研究通常涉及的是兒童(Isen & others,1973;Kenrick & others,1979;Moore & others,1973);而發現增加幫助行為的研究則通常涉及的是成人(Aderman & Berkowitz,1970;Apsler,1975;Cialdini & others,1973;Cialdini & Kinrick,1976)。為什麼消極心境對兒童和成人所起的作用不一樣呢?
恰爾迪尼等人(Robert Cialdini,Douglas Kenrick & Donald Baumann,1981;Baumann & others,1981)推測,利他主義對於成人是一種自我滿足,可以帶來自己內在的回報。獻血者因為自己的獻血行為而使自我感覺更好,幫人撿起散落物品的學生也同樣因為自己的幫助行為而使自我感覺更好(Williamson & Clark,1989)。因此,當成年人處於內疚、悲傷或其他消極心境時,幫助行為(或其他任何改善心境的經歷)都有助於抵消不良的感受。
為什麼這些在兒童身上不奏效呢?恰爾迪尼等人認為,幫助行為對兒童不能起到類似的獎賞作用。兒童讀故事時,他們會認為不幫助別人的角色比幫助別人的角色更快樂,稍大之後,他們才會轉變看法(Perry & others,1986)。儘管年幼的孩子就能表現出共情,但他們並不會從助人中得到很多快樂;幫助行為來自於社會化過程。
為了驗證他們的觀點,恰爾迪尼及其同事讓低年級小學生、高年級小學生和高中生們回憶他們悲傷的和中性的經歷。然後給他們一個把獎券悄悄贈予其他孩子的機會(Cialdini & Kenrick,1976)。研究發現,當悲傷時,年幼的孩子捐贈得稍少,中間年齡的孩子捐贈得稍多,而高中生則捐贈的顯著得多。似乎只有青少年才把慷慨視作一種使自己振奮的自我滿足的方法。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這些結果與“人生來自私”的觀點相一致。結果也與另一觀點一致,即孩子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學會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問題,幫助行為也隨之自然地發展起來了(Bar-Tal,1982;Rushton,1976;Underwood & Moore,1982)。恰爾迪尼及其同事認為,最初幫助行為是因物質回報而產生,其後是社會性回報,最後才是自我回報。
壞心情—好行為現象的例外 在社會化正常的成人中,我們是不是總能發現壞心情—好行為現象呢?不。在前面的一章中,我們瞭解到,有一種消極心境即憤怒,是不可能產生同情的。另一個例外就是極度的悲痛。沉浸在因死亡或分離而失去配偶或孩子的痛苦中的人,常會經歷一段強烈的自我關注(self-preoccupation)時期,而這種心境抑制了對別人的付出(Aderman & Berkowitz,1983;Gibbons & Wicklund,1982)。
在一項有影響的實驗室模擬研究中,湯普森等人(William Thompson,Claudia Cowan & David Rosenhan,1980)以斯坦福大學的學生為被試,研究了自我關注的悲傷的效應。研究者讓被試獨自傾聽描述一個人(將他想像成自己最要好的異性朋友)因患癌症而生命垂危的錄音磁帶。研究者用指導語使一半被試的注意集中於他們自己的擔憂和悲傷:
他(她)就要死去了,你即將失去他,再也不能跟他說話。更糟糕的是,他會慢慢死去。你知道每一分鐘都有可能是你們在一起的最後時光。幾個月裡,儘管你非常難過,但為了他,你也要裝出快樂的樣子。你將看著他像雪片一樣,一片一片地離你而去。當他的最後一片消失後,你就成了孤單的人。
研究者用指導語使另一半被試的注意集中於朋友身上:
他躺在病床上打發時光,捱過那些沒有盡頭的時日,等待著、期冀著發生什麼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他告訴你,沒有比這更令人感到痛苦的了。
研究者報告說,不論被試聽的是哪一種磁帶,他們都被深深地觸動並潸然淚下,他們也不後悔參加這個實驗(有些聽無聊錄音磁帶的控制組被試有點後悔)。那麼,他們的心境會影響他們的助人性嗎?當研究者立即給予他們一個機會,去匿名幫助一位研究生進行她的研究時,發現自我關注組的被試有25%給予了幫助,而關注他人組的被試則有83%給予了幫助。兩組被試受到了同樣的觸動,但只有關注他人的被試才認為幫助他人特別有意義(Barnett & others,1980;McMillen & others,1977)。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抑鬱和悲痛中,悲傷的人們是敏感而樂於助人的。
好心情,好行為 快樂的人不願意幫助別人嗎?正好相反。心理學中再沒有比這更一致的發現了:快樂的人更樂於幫助別人。這個效應同時適用於大人和孩子,不論好的心境是來自於一次成功,想到高興的事情,還是其他任何積極的經驗(Salovey & others,1991)。一位墜入愛河的女士回憶道:
在辦公室裡,我幾乎忍不住要大聲喊出我感到了多麼巨大的快樂。所有的工作都變得簡單了;以前讓我煩惱的事情現在都變得順理成章了。而且我有了強烈的衝動想要幫助別人;我想與他人分享我的喜悅。當瑪麗的打字機壞了的時候,我衝過去幫忙。瑪麗!那可是我昔日的“對頭”啊!(Tennov,1979,P.22)
在關於愉快的心境和助人之間關係的實驗中,受助者通常可能是一位募捐者,一位需要幫忙做文書工作的研究者,或一位不慎撒落紙張的女士。下面是兩個例子:
在波蘭的Opole城,多林斯基和諾拉特(Dariusz Dolinski & Richard Nawrat,1998)發現,積極的輕鬆心境能夠顯著地促進幫助行為。現在想像你也是其中一位不知情的被試。你把你的汽車停在了不許停車的地方一小會兒,回來時發現車窗的雨刷下(違章停車的罰單常放在這個位置)有張看似罰單的東西。“真倒黴!”你心裡嘀咕著撿起紙片,卻發現它只是張廣告(或是獻血車的宣傳單),你鬆了口氣。過了一會兒,有個大學生向你走來,請求你花15鍾回答幾個問題——“請您幫助我完成我的學士學位論文。”這時,你積極的、輕鬆的心境會使你更樂於幫這個忙嗎?事實上,62%的從害怕轉為輕鬆的人都很樂意地答應了,這幾乎是那些看到的紙片不像罰單,或將紙片放在車門上(通常不是放罰單的位置)的情況的被試所做的兩倍。
在另外一項實驗中,伊森等人(Alece Isen,Margaret Clark & Mark Schwartz,1976)讓一名合作者打電話給在0~20分鐘之前剛剛收到贈送的文具樣品的人們,對他們說自己打電話的錢不夠了(實際不然),請他們回一個電話告訴她樣品的信息。如圖12-1所示,被試回電話的樂意程度在收到樣品後的前5分鐘內是上升的,之後隨著好心境的消逝,助人性也隨之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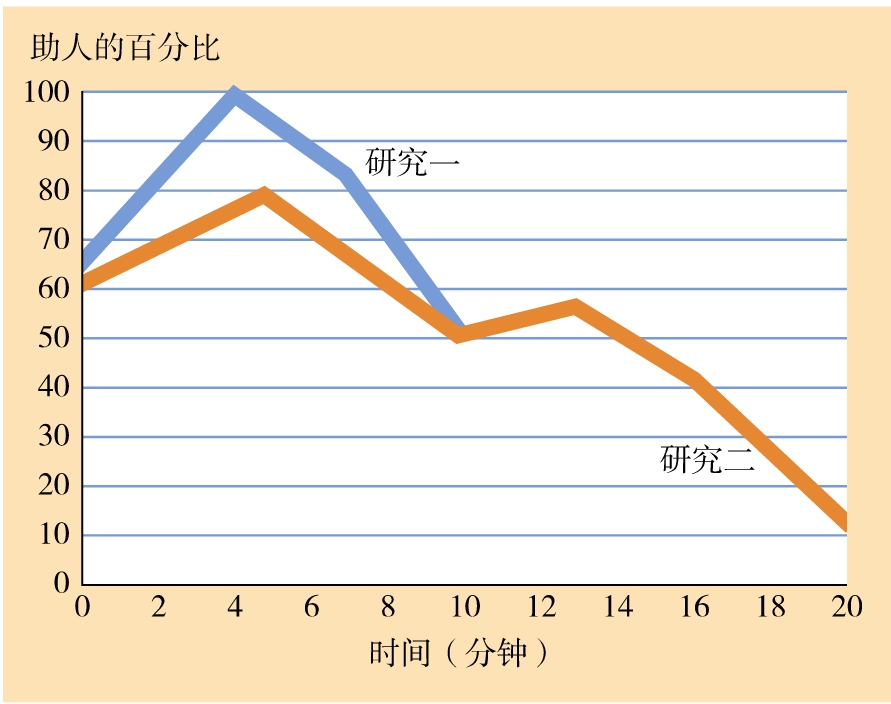
圖12-1 收到贈品0~20分鐘後願意回覆電話的百分比
沒有收到禮物的控制組被試當中只有10%的人幫了忙。
資料來源:Data from Isen & Others,1976.
如果說悲傷的人有時會格外樂於助人的話,那麼快樂的人為什麼也會如此呢?實驗揭示了一些起作用的因素(Carlson & others,1988)。幫助行為能緩解不好的心境,也能維持好的心境。反過來,積極心境又會產生積極的想法和積極的自尊,從而導向積極的行為(Berkowitz,1987;Cunningham & others,1990;Isen & others,1978)。處於好的心境——比如收到一份禮物或者為成功所激動——的人們更可能有積極的想法,並樂於助人。所以,有積極想法的人往往也更可能有積極的行動。
社會規範
很多時候,我們幫助別人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意識地去算計那樣的行為符合自身利益,而是由於自身利益的更為微妙的一種形式:因為某些東西告訴我們應該這樣做。比如我們應該幫助新來的鄰居搬家,應該歸還撿到的錢包,應該保護戰友免受傷害。規範(可以回憶第5章的內容)就是社會期望。它們規定 了我們生活中適宜的行為和應盡的義務 。研究幫助行為的研究者們確認了兩種驅動利他主義的社會規範:互惠規範和社會責任規範。
互惠規範 社會學家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1960)認為,一個普遍的道德準則就是互惠規範 (reciprocity norm):對於那些曾幫助過我們的人,我們應當施以幫助,而不是傷害 。古爾德納認為,這個規範是普遍的,就像禁止亂倫一樣為人們所接受。我們對他人“投資”,期待獲得紅利。由於認為人們會報答恩惠,因此郵寄調查問卷和發出請求時,通常會附贈小禮物或個性化書籤。政治家們懂得,如果有人給予別人恩惠,他就有望在日後得到回報。互惠規範甚至還適用於婚姻。有時候,某人付出的好像多於他收穫的,但從長遠來看,交換會是平衡的。在所有這些交往中,接受了而沒有回報,就違背了互惠規範。社會網絡中的互惠性幫助我們解釋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含義——支持性的聯繫,信息交流,信任與合作行為——這些保證了一個團體的正常運作。彼此幫忙照看對方的家,其實就是社會資本在運作。
人們對別人曾經對自己所做事情的公開反應,最能說明這個規範的有效運作。在一項模擬日常生活的實驗室遊戲中,人們對偶然碰到的以後不再見面的人比對有持久關係的人,表現出了更多的自私行為。然而,即使在無記名的反應中,人們有時也會正確行事並報答恩惠。馬克·惠特利及其同事(Mark Whatley & others,1999)在一個實驗中發現,更多的大學生願意承諾為曾經給予過他們恩惠的人所屬的慈善機構捐獻(如圖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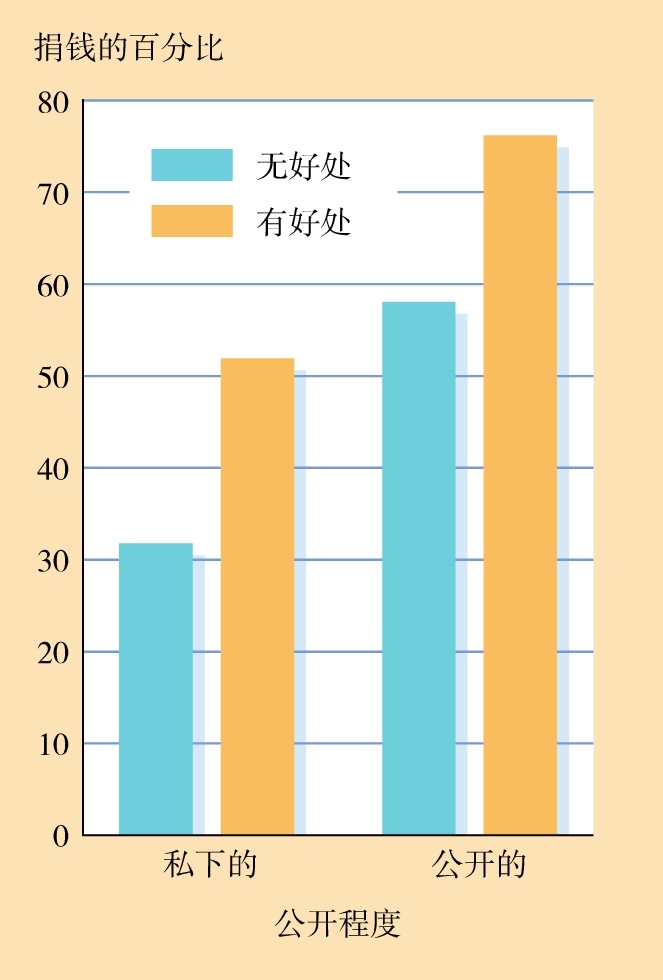
圖12-2 對所獲恩惠的私下的和公開的回報反應
如果實驗助手曾有小惠於人的話,則人們更願意承諾向他所屬的慈善機構捐獻,特別是當那個助手可以知道他們的回報行為時。
資料來源:From Whatley & others,1999.
當人們不能給予回報時,他們會因接受了援助而感到受威脅和被貶低。因此,驕傲、自尊心強的人通常不願意尋求幫助(Nadler & Fisher,1986)。接受別人主動提供的幫助會打擊他們的自尊心(Schneider & others,1996;Shell & Eisenberg,1992)。研究表明,這種情況常發生於積極行動的受惠者身上,特別是當積極的行動未能證實個人的能力和保證將來有成功的機會時(Pratkanis & Turner,1996)。
社會責任規範 互惠規範提醒我們要保持社會關係中的予取平衡。然而,如果只有這麼一條互惠規範,那麼撒瑪利亞人就不會成為善良的撒瑪利亞人了。在寓言中,耶穌明顯地有更人道的想法,他是這樣教誨的:“如果你只愛那些愛你的人[互惠規範],那麼你有什麼權力去要求任何信任呢?……我告訴你,愛你的敵人吧”。(馬太福音5:46,44)
對於一些依賴性很強,又無力回報的人——比如孩子,非常貧困的人,殘疾人,一些被認為是不能夠全部回報其所受恩惠的人——另一個社會規範就引發了我們的幫助行為。社會責任規範 (social-responsibility norm)就是人們應該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而不要考慮以後的交換(Berkowitz,1972b,Schwartz,1975)。比如,這個規範驅使人們為一個拄著柺杖的人撿起掉落的書本。在印度這一相對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度裡,人們比個人主義的西方人更強烈地支持社會責任規範(Baron & Miller,2000)。他們提倡一種幫助人的義務,即使不涉及他人生命危險的時候或是有迫切需要的人——或許是一個陌生人需要骨髓移植——超出幫助者自己家人範圍之外。
實驗表明,即使幫助者不為人知,或他們不能期待任何回報,他們仍會經常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Shotland & Stebbins,1983)。然而,社會規範使他們有選擇地只幫助那些有需要,但不是由於自己的疏忽才產生這種需要的人。在保守派中尤為如此(Skitka & Tetlock,1993),這個規範似乎是:給予人們他們應得的。如果他們是環境的受害者,如遇到自然災害等,他們就會得到全力的援助。如果他們的困境是自找的,如懶惰、不道德、缺乏遠見等,那麼,社會規範就會讓他們自食其果。因此人們的反應與其所做的歸因密切相關。如果我們把別人的需要歸因為不可控的困境,我們就會幫助他們;如果我們把別人的需要歸因為他個人的選擇,公平的觀念就並不要求我們去幫助他;我們會認為那是他咎由自取(Weiner,1980)。
假設你是威斯康星大學的一名學生,正在參加理查德·巴恩斯等人(Richard Barnes,William Ickes & Robert Kidd,1979)的一項研究。你接到了一個叫託尼·弗里曼(Tony Freeman)的人的電話,他說他是你心理學導論班上的同學。他說他從班級登記冊中知道了你,因為考試即將到來,他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他解釋說:“我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幾乎沒怎麼記筆記,我知道我能記,但有時候我就是不喜歡去記,因此我記的筆記不好,不利於複習。”你會在多大程度上同情他?借筆記給他會使你付出多大的犧牲?如果你也像這個實驗中的學生一樣,你大概不太會幫助他。但是,如果他僅僅解釋說他的麻煩超出了他的控制,情況就會不一樣。
社會責任規範使人們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和最應該得到幫助的人。雜貨店的老闆一般更願意給一個想買牛奶的婦女一些零錢,而不是給想買小甜餅的婦女(Bickman & Kamzan,1973)。
性別與助人規範 假如對他人需要的知覺強有力地決定著一個人樂意幫助的程度的話,那麼被知覺為更柔弱和更具依賴性的女性是否會得到比男性更多的幫助呢?事實的確如此。艾麗絲·伊格利和莫琳·克勞利(Alice Eagly & Maureen Crowley,1986)考察了35個比較男性和女性受助者接受幫助的研究。(事實上這些研究都採用了偶遇需要幫助的陌生人的研究模式——一種預期男性表現俠義精神的情境——伊格利和克勞利注。)
當處於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時,男性會提供更多的幫助。而女性則對不同性別的求助者一視同仁。有幾項實驗都發現,女性的車出了毛病(如車胎沒氣了)的時候,她們會比男性得到多得多的幫助(Penner & others,1973;Pomazal & Clore,1973;West & others,1975)。同樣地,單獨的女性搭車者也比單獨的男性或一對夫婦能得到多得多的幫助(Pomazal & Clore,1973;M. Snyder & others,1974)。當然,男性向一位獨行的女性表現俠義風度,也許是由利他主義之外的動機所驅動的。也不奇怪,男性會更多地幫助那些外表有吸引力的女性,而不是那些外表不具吸引力的女性(Mims & others,1975;Stroufe & others,1977;West & Brown,1975)。
女性不僅在特定情境下能獲得更多幫助,她們也更多地尋求幫助。她們對身體上和精神上幫助的尋求都兩倍於男性。電臺的電話諮詢來訪者和校園諮詢中心的來訪者也大部分是女性。她們向朋友求助則更為經常。阿里·納德勒(Arie Nadler,1991),一位Aviv大學的電話求助專家,將這個現象歸因於獨立與相依的性別差異(第5章)。
進化心理學
對幫助行為的第三種解釋就是進化理論。你也許會想起第5章和第11章的內容,進化心理學認為,生命的本質就是使基因存活下來。我們的基因驅使我們採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機會最大的方式。我們的祖先去世後,他們的基因卻得以延續,規定我們的行為方式,以繼續延續它們。
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暢銷書的書名《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進化心理學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醜陋的人類形象——心理學家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1975a,1975b)把它稱做人類深刻的、自利的“原罪”的生物學再現。那些預示個體為了陌生人的利益而自我犧牲的基因,是不會在進化的競爭中存活下來的。然而,基因的自私性卻預示我們將以兩種獨特的無私的,甚至是自我犧牲的幫助行為的方式來行事:那就是親緣保護和互惠。
親緣保護
基因使我們願意關心與我們有親緣關係的人。因此,能夠提高基因存活可能性的自我犧牲的一種方式,就是為我們的孩子做奉獻。把孩子的利益看得高於其自身利益的家長,比忽視孩子的家長更能傳承其基因。進化心理學家戴維·巴拉什(David Barash,1979,p.153)寫道:“基因靠善待自身來幫助自身傳遞,即使這些基因存在於不同個體內。”基因的利己主義(生物水平上)促使了父母的利他主義(心理水平上)。雖然進化支持人們為自己的孩子做出自我犧牲,但孩子卻不太會為父母的基因存活而去冒風險。因此,父母對其孩子的奉獻比孩子返之於他們的要多得多。
其他親戚按生物學的緊密程度與我們也擁有一定比例的相同基因。你的基因有一半和你的兄弟姐妹相同,有八分之一和你的表兄弟姐妹相同。親緣選擇 (kin selection)——偏袒那些和自己擁有共同基因的人——使進化生物學家霍爾丹(J. B. S. Haldane)開玩笑說,他不會為兄弟而犧牲妻子,卻會為3個親兄弟,或9個表兄弟犧牲自己。霍爾丹不會對同卵雙胞胎的行為感到驚奇,他們普遍來說比異卵雙胞胎明顯地更願意互相支持(Segal,1984)。在一項遊戲實驗中,同卵雙胞胎被試中的每一個都願意與另一個合作,以便在贏錢遊戲中能與對方分享收穫(Segal & Hershberger,1999)。
並不是說,我們會在發出幫助之前先計算基因的相關度,而是說幫助近親是我們的本性(也是文化)。為英勇行為而頒發的卡耐基獎章不會授予幫助直系親屬的人。當多倫多猛龍隊的卡洛斯·羅傑斯(Carlos Rogers)要結束自己的職業生涯,是為了捐獻一個腎臟給他的妹妹(可惜她在腎臟移植前去世了)時,人們為他無私的愛而喝彩。但像這樣的幫助近親的行為不是完全難以預料的。真正讓我們出乎意料(因此也敬重)的應該是像我們的地鐵英雄桑德森(Sanderson)先生那樣捨身勇救一個陌生人的行為。
除了親屬,我們還和很多人擁有共同的基因,如藍眼睛的人之間有共同基因。我們怎樣分辨出那些基因與我們最為相近的人呢?藍眼睛的例子說明,其中一個線索就在於外表的相似性。同樣,從進化的歷史上看,人們與鄰近的人比與外國人共享更多基因。那麼,是否在生物學意義上已註定我們會有所偏向,對那些與自己相似的人和住在自己附近的人做出更多幫助行為呢?自然災害和其他生死抉擇情境的結果顯示,人們對施與幫助的人的排序符合進化心理學家的邏輯:先年輕人後老人,先家人後友人,先鄰居後陌生人(Burnstein & others,1994;Form & Nosow,1958)。
一些進化心理學家認為,親緣保護還決定了種族的群體內偏好——歷史上和現實中數不清的種族衝突的根源(Rushton,1991)。威爾遜(E. O. Wilson,1978)認為,親緣選擇是“社會文明的敵人。如果人類在更大範圍內被引導去……偏愛他們的親人和部落,那麼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將非常有限”(p.167)。
互惠
基因的利己性同樣預示著互惠行為。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認為,一個有機體幫助其他個體,是因為它期待得到回報性的幫助(Binham,1980)。付出者希望日後成為獲得者,不做出互惠行為則會受到懲罰。騙子、背叛者、賣國者之流普遍遭人唾棄。
互惠在那些小的、與外界隔離的群體中能最好地起作用,在這樣的群體中,人們能經常看到被自己幫助過的人。一隻吸血蝙蝠如果一兩天沒吃東西——超過60小時就會餓死——它會要求同住的吃得很飽的蝙蝠吐出些東西給它吃(Wilkinson,1990)。而同住的蝙蝠也願意這樣做,即使它會比受助者更快地感到飢餓。但這樣的好行為只會發生在相熟的且同甘共苦的同住者當中。那些只索取不給予的,以及那些與可能給予食物的蝙蝠沒有任何關係的蝙蝠就會捱餓。
同樣道理,互惠行為在偏遠的鄉村就比在大城市中發生得更多。在小的學校、城鎮、教堂、工作團隊、宿舍中,所有的人都易於形成互相關心的共同信念。與在小城鎮和鄉村環境中生活的人們相比,那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更不願意轉達一個電話留言、處理寄錯了的信件、配合來調查的訪談者、幫助走失的兒童和做一些小的善事(Hedge & Yousif,1992;Steblay,1987)。
在基因競爭中,如果說個人的私利性必然會獲益的話,為什麼人們還會幫助陌生人呢?為什麼還會幫助那些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回報的人呢?是什麼使戰士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擋手榴彈呢?達爾文認為,其中一個答案就是群體選擇(此解釋曾一度因基因自私的理論而大打折扣,但現在又重新流行):當群體之間進行競爭時,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體比不利他的群體會持續更長的時間(Krebs,1998;McAndrew,2002;Sober & Wilson,1998)。
唐納德·坎貝爾(Donald Campbell,1975)指出,還有另一個非互惠利他主義的基礎,即人類社會形成的倫理和宗教規則,它們能阻止指向自私的生物性偏好。像“愛你的鄰居”這樣的戒律訓誡我們要兼顧自我和群體,這樣才能有利於群體的存活。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提出一個相似的論斷:“讓我們盡力去宣揚 慷慨和利他吧,因為我們天生是自私的。讓我們懂得自私的基因是怎麼回事吧,因為這樣我們至少能有機會顛覆其設置,這是其他物種無法企及的”(p.3)。
比較和評價幫助行為的理論
現在你可能注意到社會交換、社會規範和進化理論對於利他主義解釋的相似性了。如表12-1所示,每一個理論都引出兩種親社會行為:投桃報李的互惠交換和無條件的幫助。它們分別在三個互為補充的層次上進行了論證。如果進化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基因的傾向性應該能在心理的和社會的現象中證明自己。
表12-1 利他理論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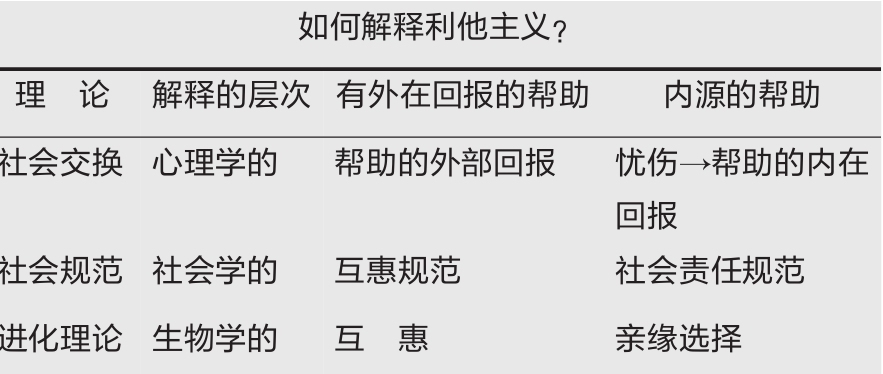
每個理論都言之成理,但又都有推測性和事後解釋的嫌疑。當我們從已知的事實(日常生活中的付出與獲取)入手,用推測一個社會交換過程,推測一種“互惠規範”,或者推測進化起源來解釋這些事實時,我們可能僅僅是以命名代替解釋(explaining-by-naming)。“行為的發生是因其生存功能”的觀點則很難證偽。事後諸葛總是很容易地認為“事情本應如此”。如果我們能把任何 可以想到的行為,在事後將它解釋為社會交換、規範或自然選擇的結果,這些理論就很難證偽。因此,每個理論的任務就是提出一些能讓人們去檢驗的假設。
一個有效的理論也應該能提供一個一致的結構,以概括各種各樣的觀察結果。在這條標準下,三個利他理論應獲得更高的評價,它們都為我們解釋人們幫助行為提供了非常廣闊的視角,無論是持久的承諾還是自發的幫助。
真正的利他主義
那些挽救他人生命的英雄,那些平日裡的獻血者,那些維和部隊的志願者們,他們所做的一切,是出於毫無私利的關心他人的終極目標,還是也混有其他動機?或者他們的終極目標乾脆就是簡單的要自我獲利,比如獲得獎賞、避免懲罰和愧疚,以及緩解壓力?
有一次,亞伯拉罕·林肯在馬車上和另一名乘客討論起利他主義這個哲學問題。林肯認為,自私能引發所有的善行。就在這時他聽到一聲母豬的哀嚎——她的小豬掉進一片水塘快要被淹死了。林肯讓馬車停下來,他跳下車跑回去,把小豬救了上來。他回到馬車後,同伴問道:“嗯,亞伯,剛才的小事中,自私在哪兒呢?”“當然在,就是保佑靈魂啊。愛德華,這正是自私的本質!如果我剛才徑直走過,扔下痛苦的在擔心其孩子的母豬不管,我就一整天不會得到心靈的寧靜。我剛才救小豬只不過是為了安心,你難道不明白嗎?”(Sharp,轉引自Batson & others,1986)。直到最近,心理學家仍支持林肯的觀點。
然而,心理學家巴特森(Batson,2001)的理論認為,我們幫助別人的意願同時受利己和無私的考慮的影響(圖12-3)。因某人不幸而感到的痛苦既能驅使我們逃離這種情境(如傳教士和利未人),也能驅使我們提供幫助(如撒馬利亞人),從而解除我們的痛苦。巴特森和他的同事認為,特別是當我們感到我們與某人有所關聯時,我們就會產生共情 (empathy)。愛護子女的家長會因孩子痛苦而痛苦,因孩子高興而高興——這就是那些虐待兒童的人和殘忍的罪犯所沒有的共情(Miller & Eisenberg,1988)。我們還會對那些我們認同的人共情。1997年9月,很多人都為英國皇妃黛安娜(英國皇妃黛安娜在巴黎死於車禍——譯者注)的去世,以及她的失去母親的兒子而落淚,雖然這些人從來沒有接近過黛安娜,但他們認為通過各種報章雜誌裡的文章已經很瞭解她了。但是,這些人卻沒有為另外一些遭遇更慘的人流過淚,如自1994年以來,死於骯髒的庇護所裡的或被殺害的姓名不詳的近一百萬名盧旺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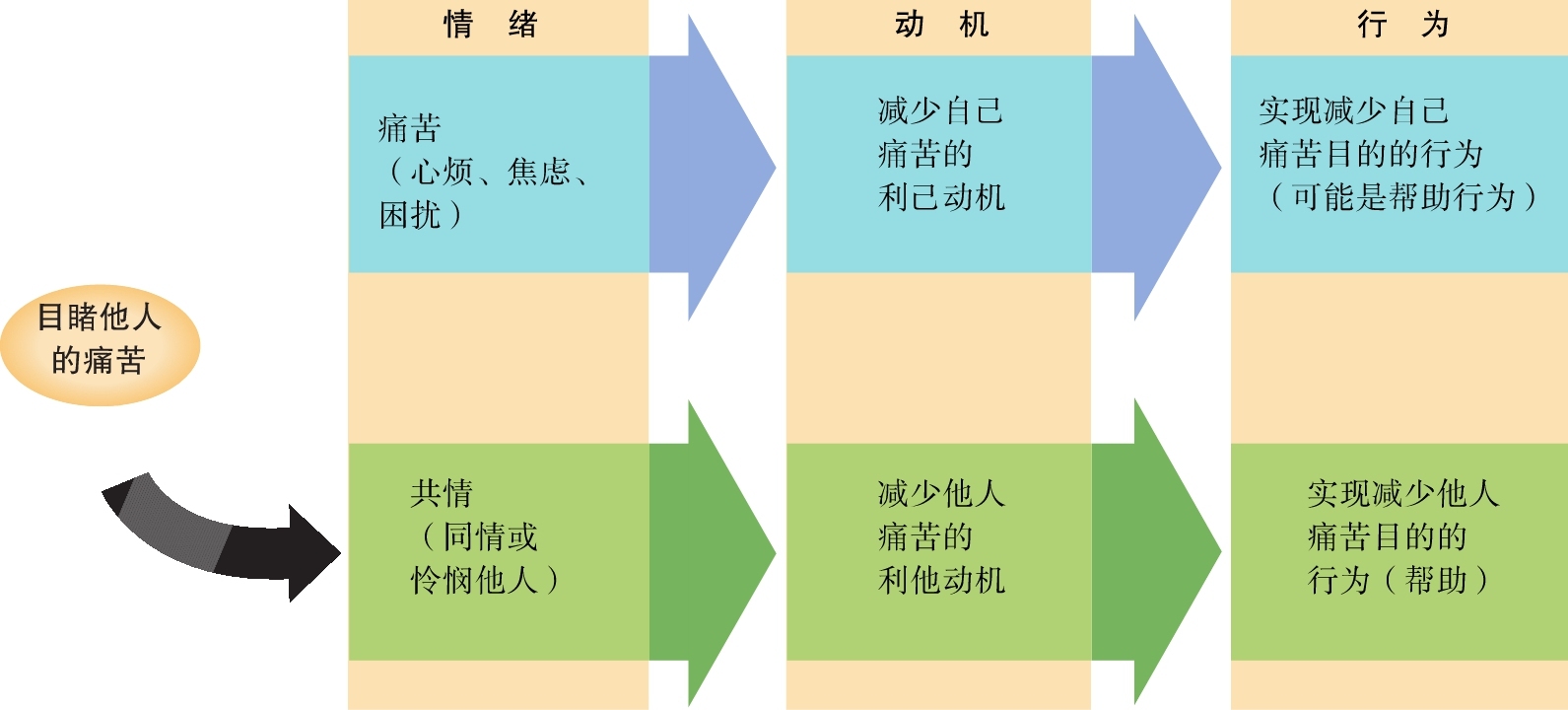
圖12-3 利己的和利他的幫助行為的路徑
對他人憂傷的目睹,會引發兩種情緒的混合:關注自我的痛苦和關注他人的共情。研究者一致認為痛苦能引發利己的動機,但他們對共情是否能引發純粹意義上的利他動機仍有爭議。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Batson,Fultz & Schoenrade,1987.
當我們產生共情時,我們就不會更多地關心自己的痛苦,而會去關注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同情和憐憫驅使我們為了別人的切身利益而幫助他們。這種共情是自然產生的。即使才出生一天的嬰兒也會因別的嬰兒的哭聲而啼哭(Hoffman,1981)。在醫院的育嬰室裡,一個嬰兒的哭聲通常會引發一片啼哭的浪潮。從某種程度說,這表明共情是我們與生俱來的能力。
痛苦和共情通常共同作用,促使人們對危機做出反應。1983年,人們通過電視看到澳大利亞的墨爾本附近發生了森林大火,大火吞噬了成百上千的房屋。事後,保羅·阿馬杜(Amato,1986)研究了人們捐錢捐物的情況,他發現那些對大火感到生氣或表現冷漠的人捐得較少,而那些對火災感到痛苦(震驚或驚厥)的人,或產生共情(同情受難者或為其擔憂)的人捐得更多。
為了從基於共情的利他主義中分離出利己的為了減輕痛苦而做出的利他行為,巴特森的研究小組通過喚起共情的情感,以及改變人們從目睹他人痛苦的情境中逃離的難度,來研究共情被喚起的人是通過逃離情境來減少自己的痛苦,還是通過對困境中的他人施與幫助來減少他人的痛苦。結果是一致的,共情被喚起的人通常會施與幫助。
在其中一項研究中,巴特森及其助手(1981)讓一名年輕婦女假裝成正在遭受電擊的痛苦,然後讓堪薩斯大學的女生們觀看。實驗間歇時,那個看起來已經很痛苦的遭受電擊的女士向研究者解釋說,她童年時曾掉進電柵中,因此她對電擊非常敏感。出於同情,研究者會建議觀察者(本實驗中的真正被試)或許能與她調換一下位置,接受餘下的電擊。而在這之前,一半被試被告知這個遭受電擊的年輕女子與她們有相似的價值觀和志趣(以此來喚起她們的共情),其中一些被試還被告知,她們看完那個女子遭受電擊的情景後,實驗任務就完成了,不需繼續留下。然而,研究發現,這一組已經被喚起共情的被試,基本上都表示願意代替那個年輕女子來接受剩下的電擊。
這是否是真正的利他主義呢?馬克·沙勒和羅伯特·恰爾迪尼(Schaller & Cialdini,1988)表示懷疑。他們承認,對受害者的共情感受的確會使人悲傷,但在一個實驗中,他們使被試確信,他們產生的悲傷可以通過另外一種提升情緒的體驗來減輕——聽那些令人開心的磁帶。結果,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即使喚起了共情,也不是特別願意提供幫助。沙勒和恰爾迪尼總結道,如果我們產生了共情,但同時知道還有別的方式能讓我們好過些,我們就不太可能幫助別人。
除了上述研究以外,還有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可能存在真正的利他主義:
共情會產生幫助行為,即使對方是敵對群體的成員;不過,只有人們確信對方會接受幫助時才會如此(Batson & others,1997)。
當人們的共情被喚起後,即使他們瞭解自己的幫助行為不會被人知道,他們也願意提供幫助,直到受助者脫離困境(Fultz & others,1986)。如果他們的努力不成功,哪怕並不是他們的錯,他們也會感到沮喪(Batson & Weeks,1996)。
有時候,即使人們知道他們痛苦的情緒已經被“情緒調節劑”暫時緩解,但他們仍會堅持幫助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Schroeder & others,1988)。
所有的人都承認,一些幫助行為明顯是利己的(為了獲得回報或避免懲罰),一些是隱蔽利己的(為了獲得內在回報或減輕內在痛苦)。是否存在第三種形式的幫助行為——只是為了增加他人福利(自己的愉快感僅僅是副產品)的真正的利他主義?基於共情的幫助行為是否是這種利他主義的一個來源?恰爾迪尼(1991)和他的同事馬克·沙勒和吉姆·富爾茨(Jim Fultz)對此仍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目前還沒有實驗能夠排除對幫助行為的所有可能的利己解釋。
但是,在做了25個考察利己主義和利他的共情實驗之後,巴特森(2001)和其他一些研究者(Dovidio,1991;Staub,1991)指出,人們有時候確實關注別人的福利,而不關注自己的福利。巴特森,這個昔日學習哲學和神學的學生,是在這樣的理念下開始他的研究的:“如果能夠確定人們對他人的關心是真誠的,而不是利己的隱蔽形式,那麼我們就能夠對人性的這一根本問題做出新的解釋”(1999a)。20年後,他相信自己已經找到了答案。真正的“由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確實是人性的一部分”(1999b)。巴特森還指出,他所做的研究使人們產生了新的希望,即通過共情能夠改善大眾對弱勢人群——包括艾滋病患者、流浪者、坐牢者和其他少數群體的態度(見“聚焦: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的益處與缺點”)。
在越南戰爭中,63名戰士因在戰火中用身體掩護戰友而獲得榮譽獎章(Hunt,1999)。他們大多數在嚴密組織的格鬥隊裡,很多人用身體擋住手榴彈,其中59人因此而犧牲。這些戰士和其他的利他主義者不同,如他們就不同於納粹時期幫助20萬名猶太人的5萬名非猶太人,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考慮退縮的恥辱或自我犧牲的最終回報。然而,還是有某些東西驅使他們做出了那樣的捨生為人的行為。
小結
三個理論通過外部的和內部的回報分別解釋了利他行為。社會交換理論把幫助行為看做和其他社會行為一樣,是由對代價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所驅動的。收益也可以是內部的。人們在違規後,經常會更願意為他人提供幫助,顯然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消除內疚感和維護自我形象。悲傷的人也傾向於做出幫助行為,但是這種壞心情—好行為效應並不在年幼的兒童身上發生。這種現象說明,幫助行為帶來的內部獎勵是後期社會化的產物。最後,存在著顯著的好心情—好行為效應:快樂的人一般也是樂於助人的人。
社會規範同樣要求人們幫助他人。互惠規範使我們要對幫助過自己的人報之以幫助而不是傷害。社會責任規範召喚我們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只要他們值得幫助,即便他們不能回報,我們也無所謂。處於危難中的女性,部分原因是她們看起來更需要幫助,因此,通常會比男性接受到更多的幫助,特別是來自男性的幫助。
進化心理學假定,有兩種形式的幫助行為:奉獻於近親和奉獻於有互惠關係的人。然而,很多進化心理學家認為,自私的基因比勇於自我犧牲的基因更有可能存活下來,因此,整個社會必須教導人們去幫助他人。
除了由內部的和外部的回報所驅動的幫助行為,以及為躲避懲罰和痛苦而做出的幫助行為以外,似乎還存在著真正的、基於共情的利他主義。由於共情的喚起,許多人被驅動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和處於痛苦中的人,即便他們的幫助是無人知曉的,即便他們的心境不會受其影響。
聚焦 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的益處與缺點
堪薩斯大學研究利他主義的巴特森及其同事(2004)承認,人們所做的大多數行為,包括他們為別人所做的行為,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但是,研究者還相信,幫助行為並不完全出於利己主義動機,還存在真正的利他主義,它起源於共情,一種同情和關心他人福利的情感。我們是最高級的社會性動物。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有許多益處:
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
產生敏感的幫助行為 。當移情產生的時候,它不是僅停留在想法層面,還會付諸行動以減輕他人的痛苦。
抑制攻擊 。巴特森給那些產生了共情感的個體呈現一個潛在的攻擊目標,他發現,這個個體往往不願意實施攻擊,而寧願採取寬恕的態度。一般來說,女性比男性報告了更多的共情感,她們也通常不支持戰爭和其他形式的攻擊(Jones,2003)。
增加合作 。在實驗室實驗中,巴特森和納迪亞·阿瑪德(Nadia Ahmad)發現,處於潛在的衝突情境中時,如果人們對對方產生了共情的話,就會更信任對方,也會與對方合作。通過讓個體認識外群體中的其他個體,就可以使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個人化,這有助於他們理解他人的觀點。
改善對弱勢群體的態度 。採擇他人的觀點,使人們能理解他人的感受,從而能使人們更為支持、同情與他們類似的人(比如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患艾滋病的人,甚或是罪犯)。
但是,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也有缺點,巴特森的研究小組總結道:
有傷害性 。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冒著生命危險的人們有時的確會因此獻身。打算為他人做好事的人們有時候也會做出壞事,比如無意識地羞辱了對方或使對方產生無能感。
不能照顧到所有的需要 。我們更容易對一些特定個體的需要產生共情,而我們的地球母親——她的環境正遭到破壞、氣候在變暖,令我們的子孫後代生存堪憂。
產生枯竭感 。感覺到他人的痛苦自己也會痛苦,這就會使我們儘量避免能喚起我們共情的情境,否則的話就會經歷枯竭(burn-out)或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
引起偏愛、不公正,並對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冷漠 。共情具有特定性,它要求產生偏愛——對個別的孩子或家庭,甚至寵物。道德原則是普遍的,它要求對所有的人,包括未曾謀面的人產生同樣的關心。基於共情的狀態是要把好處給予獨特的所關心的人,而基於道德的狀態則是更多的包容。人們如果喚起了對某人的共情,就會違反他們的公正和公平原則,而對那個人採取偏袒的對待(Batson & others,1997,1999)。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情導致的利他主義可能會因此“對普遍的善良造成強烈的威脅,(通過引導)我的注意力侷限地集中於我給予特別關心的人——我的處於需要中的朋友——而無視那正在流血的一群人”。毫不奇怪,善行往往發生於家庭附近。
我們何時會幫助
什麼環境促使人們提供或不提供幫助?為什麼在場的他人數量、個人的情緒狀態、人格品質和價值觀念都會影響幫助行為?它們是如何產生影響的?
1964年3月13日凌晨3點,紐約,酒吧經理基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在即將到達寓所時,遭到持刀暴徒的侵犯,她驚恐地尖叫並懇求幫助——“我的天啊!他刺傷了我!來人哪!請幫幫我!請幫幫我!”——聲音迴盪在寧靜的夜中,顯得分外刺耳。她的38戶鄰居,很多人走到窗戶邊觀望了片刻,目睹她在歹徒手中掙扎。但直到歹徒離開,才有人打電話報警,但基諾維斯卻因未能得到救治而很快就死去了。
為什麼吉諾維斯的鄰居中沒有一個人去援助她?他們麻木、冷漠、毫無同情心嗎?如果是,那麼這樣的人多著呢。
安德魯·莫米勒(Andrew Mormille)在乘地鐵回家時,被歹徒用刀捅傷了腹部,在歹徒下車後,其他11名乘客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年輕人因流血過多而致死。
埃莉諾·布拉德利(Eleanor Bradley)在購物時被絆倒並摔傷了腿。她眼花繚亂且疼痛難忍,於是她呼救,但在40分鐘內,購物的人流只是從她旁邊走過而沒有人管她。最後,一名出租車司機把她帶去看醫生(Darley & Latané,1968)。
2000年6月前後,正當超過百萬的本地人和遊客們在溫暖的陽光下漫步於紐約中央公園時,一群酗酒的年輕人對60名單獨出行的婦女進行性侵犯——撫摩她們,甚至還脫她們的衣服。次日,媒體針對性侵犯背後的群體心理和警察們的無動於衷(當時至少有兩名受害者跑向警察,但他們卻沒有任何反應)展開了討論。周圍成千上萬的遊客都怎麼了?他們為什麼能夠容忍這樣的行為呢?很多旁觀者都有手機,為什麼就沒有一個人報警呢(Dateline,2000)?
使人震驚的不是個別人在緊急情況下不伸出援助之手,而是牽涉在內的人(上述事例中的38人、11人、40人甚至成百上千的人)幾乎100%都無動於衷。為什麼呢?如果你我處在同樣的和相似的情境中,是否也會和那些人一樣呢?
社會心理學家感到好奇並關注的是,在像吉諾維斯這樣的殺人案裡,旁觀者為什麼都如此無動於衷。因此他們設計實驗,來考察人們什麼時候才會在危難之中伸出援手。他們還進一步考察,哪些人最有可能在非緊急情況下幫助別人——如捐錢、獻血、提供時間等行為。下面讓我們回顧這些實驗,我們先分析增加幫助行為的環境因素 ,然後再分析助人者的特徵 。
旁觀者數量
旁觀者在緊急情況下的冷漠使得社會評論員們感到悲哀,他們哀嘆人們的疏遠、無情、漠不關心和無意識的殘酷衝動。大多數人都把緊急事件中的不干預行為歸因於旁觀者的個人特點,因為這樣可以使人們自己感覺舒服一點,人們通常認為自己是有同情心的人,他們在類似情境中是會提供幫助的。那麼,那些旁觀者就如此沒有人性嗎?
社會心理學家拉塔奈和達利(Latané & Darley,1970)不這樣認為。他們利用設計巧妙的危急情境進行研究,發現了一個情境因素——其他旁觀者的在場——會大大降低人們對事件的干預。直到1980年,研究者做了48個實驗,比較了個體認為自己作為旁觀者獨自在場,和認為除了自己外還有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所給予的幫助的可能性。發現大約有90%的被試,也就是將近6000人,認為自己單獨在場時更願意伸出援助之手(Latané & Nida,1981)。
有時候,在有更多人在場的情況下,那些受害者卻更少有機會得到幫助。拉塔奈、達布斯(Latané & Dabbs,1975)和145名合作者共測試了1497次,他們在乘坐電梯時裝作不經意地掉落了一枚硬幣。發現當旁邊只有一名乘坐者時,他們得到幫助的可能性有40%。當旁邊有6名乘坐者時,他們得到幫助的可能性不超過20%。
為什麼會這樣?拉塔奈和達利猜測,當旁觀者的數目增加時,任何一個旁觀者都會更少地注意 到事件的發生,更少地把它解釋 為一個重大問題或緊急情況,更少地認為自己有採取行動的責任 (圖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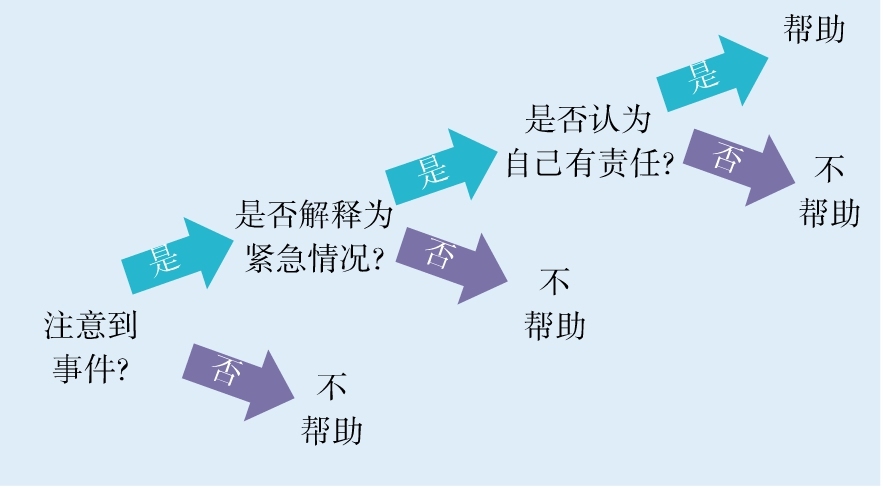
圖12-4 拉塔奈和達利的決策樹
決策樹上只有一條路能導致幫助行為。在每一個分岔處,在場的他人都會使人走向不幫助的分支。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Latané and Darley,1968.
注意
在擁擠的街道上,有一個叫埃莉諾·布拉德利的女子不小心被絆倒並摔傷了腿。假設20分鐘後,你正好經過這裡,你的眼睛看著前面行人的背部(一般來說,盯著周圍的來往行人看被認為是不禮貌的),你的腦子裡還想著白天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時你會注意到路旁有一個受傷的女子嗎?如果此時街上十分冷清,你是否會更容易注意到受傷的女子?
為了得到答案,拉塔奈和達利(1968)招募了一些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來做實驗,讓他們在一個房間裡填寫問卷,有些被試單獨填寫,有些被試則和兩個陌生人一起填寫。就在他們正埋頭填寫問卷時(研究者通過單向玻璃可以觀察他們),一個緊急情況出現了:濃煙從牆上的通風孔吹了進來。那些獨自填寫問卷的學生——他們通常會時不時地瞄幾眼周圍的環境——幾乎立刻就發現了濃煙——通常在5秒鐘之內。而那些與他人一起填寫問卷的學生,則專注於他們的問卷,多數到了20秒鐘以後才發現濃煙。
解釋
一旦我們注意到了模糊事件,我們就會去解釋它。如果你呆在滿是濃煙的房間裡,即使擔憂,你也不願意表現得很緊張從而使自己丟臉。你通常會看看其他人的反應,如果他們看起來很平靜,漠不關心,你就會認為一切都正常,你也許會聳聳肩然後又繼續工作。另一個人也發現了濃煙,而他看到你表現得無所謂,就同樣也不做聲了。這也是信息影響的另一個例子(第6章)。每個人通常都以他人的行為作為現實情況的線索。
人們的上述錯誤通常被透明錯覺(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所助長。透明錯覺由吉洛維奇等人(Thomas Gilovich,Kenneth Savitsky & Victoria Husted Medvec,1998)提出,指高估他人瞭解我們內心狀態能力的傾向。在他們的實驗中,面臨緊急情況的被試都認為,自己對情境的關心比實際情況要更為明顯。我們的厭惡、欺騙、警告,比我們通常所認為的要隱晦得多;由於對自身情緒非常敏感,我們通常認為它們非常明顯,別人很容易就能看穿。的確,有時別人真的能看出我們的情緒,但多數時候我們都能很好地掩藏它們。這就是第8章談到的“人眾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人們其實對他人關於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無知的。在緊急情況下,每個人也許都認為“我很關心外界”,但認為他人十分平靜——因此得出“情況可能並不緊急”的結論。
研究背後的故事:
達利對旁觀者反應的思考
由於震驚于吉諾維斯案,拉塔奈和我就開始在飯桌上分析旁觀者的反應。作為社會心理學家,我們不僅要思考“冷漠”個體的人格缺陷,還要思考為什麼那種情境下的所有人都變得如此冷漠。當這頓飯吃完時,我們已經找到了幾個因素,它們可以共同解釋為什麼會出現無人伸出援手的這種令人驚訝的狀況。然後我們開始設計實驗,來分別證明這些因素在緊急情況中的重要性。
因此有了拉塔奈和達利的實驗結果。那些單獨工作的人發現了煙霧,通常猶豫一下,然後走上前,到通風孔旁感覺一下、聞一下、揮手驅散煙霧,再猶豫一下,然後去報告。與此形成戲劇性對照的是,那些三人一組的人沒有任何行動。在8個組的24人中,只有一人在頭4分鐘內報告看見了煙霧(圖12-5)。在持續了6分鐘的實驗結束時,煙霧濃到人們要揉眼睛並且咳嗽。而儘管如此,8個組中只有3個組中有一人去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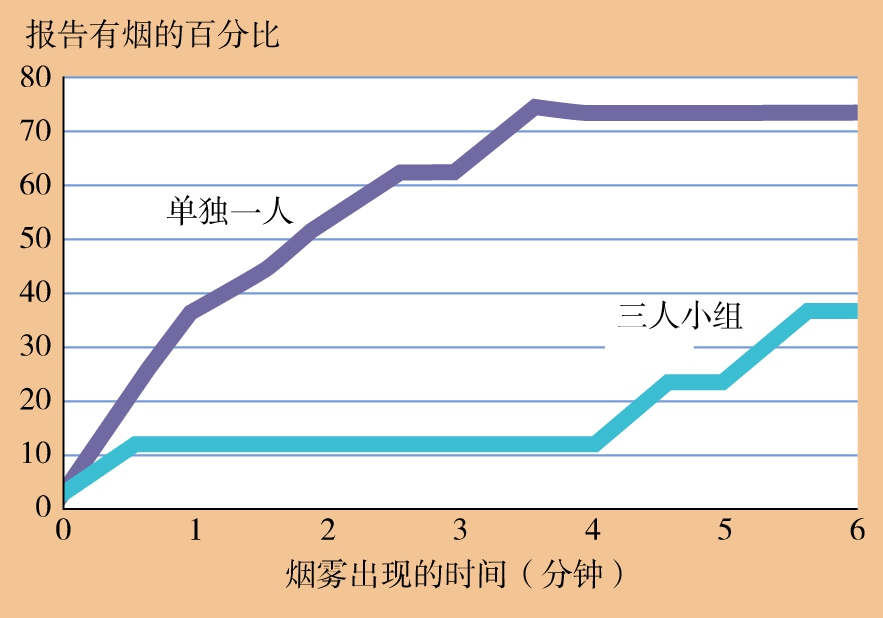
圖12-5 “房間充煙”實驗
單獨工作的人比三人一組共同工作的人更多地報告有煙霧進入了實驗室。
資料來源:Data from Darley & Latane,1968.
同樣有趣的是,群體的被動性還影響了其成員對事件的解釋。是什麼導致了煙霧呢?“空調設備洩漏。”“樓內有化學實驗室。”“蒸汽管的問題。”但是沒人說“著火了。”不做出任何行動的組內成員,對情境的解釋顯然受到了彼此的影響。
實驗中的兩難局面與平常我們所面對的兩難情境相似。窗外的尖叫是否只是開玩笑,還是真的有人因遇襲而呼救?是一群小孩在嬉戲廝打還是真的惡意鬥毆?有人睡在街上,是因其吸毒過量還是真的有嚴重疾病,如因糖尿病而昏迷?所有經歷過悉尼·布魯克林(Sidney Brookins)(AP,1993)事件的人肯定都思考過這個問題。布魯克林被毆打至腦震盪,躺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商店門口附近足足兩天,然後死去。也許那些目睹布蘭登·韋達斯(Brandon Vedas)(家住鳳凰城的一名21歲的美國男青年,一向標榜自己特例獨行、與眾不同。2003年2月10日在聊天室與網友聊天時,吞食大量處方藥而死亡。他的網友通過攝像鏡頭目睹了他死亡的整個過程,但卻沒有人干預,其間還有不少人不斷地鼓勵他繼續吞食藥物,挑戰自己——譯者注)由於用藥過量而在線死亡的人們,也會經歷同樣的困境。當布蘭登的生命逐漸衰弱的時候,他的觀眾們感到奇怪,他是否在做戲呢?由於錯誤理解了相關線索,他們沒有及時與警察聯絡(Nichols,2003)。
與房間充煙實驗不同,上述每一個日常情境中都有他人處於急需之中。為了檢驗這樣的情境是否也會發生同樣的旁觀者效應 (bystander effect),拉塔奈和朱迪斯·洛丁(Rodin,1969)設計了一個“遭難女士”實驗。一名女研究者讓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些學生在一個房間裡填寫問卷,她自己從一個掛有門簾的房門進入裡間辦公室。4分鐘後,外間的被試聽到(用錄音機播放)她爬上椅子取高處的紙張、然後尖叫、椅子倒下和她跌倒在地的聲音,“噢,我的天啊,我的腿……我……我……不能動了”,她嗚咽道,“噢……我的腳踝……我……不能把壓在我身上的東西推開。”在2分鐘的呻吟之後,她才能勉強走出辦公室。
單獨填答問卷的被試中,有70%的人聽到意外發生後,立即走進辦公室或出去求救。2個陌生人一起答卷子時,只在40%的小組中有一個人去幫助。那些在這個過程中什麼也沒做的人,顯然認為這件事並不是緊急情況。“只是輕微的扭傷”,有人說。“我不想讓她覺得尷尬”,另一些人解釋道。這又一次證明了旁觀者效應。當瞭解到注意到緊急情況的人增加時,人們施予幫助的可能性變小。所以,對於受害者來說,處於人群中也許是不安全的。
人們的解釋同樣會影響他們對街頭犯罪事件的反應。肖特蘭和斯特勞(Shotland & Straw,1976)設計了一項研究,他們讓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打架。結果發現,當女子大叫“走開,我不認識你”時,有65%的情況會有人幫助,但當她說“走開,我不知道我怎麼就嫁給了你”時,只有19%的情況會有人幫助。看起來被假設為夫妻間的衝突的話,就不會得到更多的關心,而陌生人之間的暴力會得到更多的干預行為。
塔庫申和博丁格(Takooshian & Bodinger,1982)提出,旁觀者的解釋也會影響他們對盜竊的反應。研究者在18個城市中安排實施了上百個汽車盜竊行為(用一個衣架伸進汽車,然後拿走值錢的東西如電視機、皮大衣等),他們的實驗結果令人震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路人對這些行為發出疑問,甚至很多人注意到之後還站在一旁邊看邊笑,有的還提供幫助。有人顯然把這些“盜賊”當成汽車的主人了。
確定責任
未能引起注意和產生誤解,並不是旁觀者效應的全部成因。塔庫申和博丁格報告說,即使當“夜盜賊”是一個衣衫襤褸的14歲的男孩時,當兩輛相鄰的小汽車同時被撬開時,或者當旁觀者看見撬車的人不是剛從車上走下來的汽車主人時,紐約人仍然還是不會干預這些事情。那麼,在明顯的緊急情境中,人們的這種反應又做何解釋呢?那些看見和聽到吉諾維斯求救的人雖然能正確解釋正在發生的事件,但鄰居的燈光和窗邊的側影又告訴他們,還有其他人注意到了這件事,這就分散了他們做出反應的責任。
很少會有人親眼目睹謀殺案,但所有的人都會有當他人在場時,自己援助他人的反應會延遲的經歷。與在鄉村路上讓站在路邊等待搭車的人上車相比,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卻更少為汽車拋描者提供幫助。為了解釋在明顯緊急的情況下旁觀者不作為的現象,達利和拉塔奈(1968)模擬了吉諾維斯案。他們讓紐約大學的學生用實驗室中的聯絡設備,在隔開的房間裡討論大學生活中的問題。被試們通過設備討論,並能通過設備聽到求助者的呼救聲。研究者告訴被試,沒人看到他們,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連實驗人員也不會偷聽他們的談話。在討論正在進行的時候,研究者播放了一個人突然癲癇發作的聲音,那人的說話越來越困難,預示病情越來越重,他在懇求幫助。
那些相信除自己外再沒有其他人知情的被試,有85%離開了他們的房間出手相助。那些認為除自己以外還有另外4人聽到了呼救聲的人,只有31%去幫助。那些不做出任何反應的人是否就無動於衷或冷漠無情呢?當研究者走過來說結束實驗時,她發現並不是這樣。因為很多人立刻表示出關心,很多都感到手在顫抖或掌心出汗。他們相信有緊急情況出現了,但不能決定是否該行動。
在做了“房間充煙”、“遭難女士”、“癲癇發作”這些實驗後,拉塔奈和達利都詢問被試,在場的他人是否會影響他們?雖然我們已經看到了在場的他人所產生的奇妙影響,但被試卻幾乎總是否認這樣的影響。他們只是回答說:“我知道有其他人,但我的所做所為與他們不在時是一樣的。”這些答案強化了一個我們熟悉的觀點:我們通常其實並不知道自己所作所為的原因 。這就是這些實驗的揭示作用所在。在真正的緊急事件發生之後,對袖手旁觀者的事後調查會掩蔽旁觀者效應。
進一步的實驗顯示,某些情境中,他人在場有時不會抑制人們提供幫助。皮列文和他的同事(Pilliavin & others,1969)在地鐵列車上做了一個緊急情境的實驗。被試是4450名不知情的紐約地鐵乘客。在總共103個情境的每一箇中,都有一名合作研究者進入地鐵列車,靠在車廂中央的一根柱子上。列車開出車站後,他搖搖晃晃,最後跌到在地。研究發現,如果這個人再拿著柺杖的話,就會有一個或多個旁觀者幾乎立刻提供幫助。即使他拿著瓶子而且一身酒氣,他通常也能獲得幫助——特別是當有幾名男性旁觀者在附近時。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是因為在場的其他乘客為幫助者提供了一種安全感?難道是因為這種情境更清楚,他人的反應更明顯?(乘客們一般會忍不住去注意和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為了檢驗後一種可能性,琳達·所羅門等人(Solomon,Solomon,& Stone,1978)設計了一個實驗,讓人們看到並聽到他人的痛苦情形,就如同地鐵列車的實驗,或者只聽到痛苦的聲音,就如同“遭難女士”實驗(會有更多解釋這種情境的可能)。研究發現,當緊急情境非常清晰的時候,那些處於群體裡的人比獨處的人願意幫助的可能性只少一點點;但是當情境模糊時,處於群體中的人提供幫助的可能性就遠遠小於獨處的人。[即使只是想像他人在場(例如,想像劇院裡的陌生人),也會減少人們的幫助和給予 (Garcia & others,2002)。]
紐約人和其他城市裡的人一樣,在公共場所時很少會獨自一人,這幫助我們理解了為什麼城裡人通常比鄉村人更不願意去幫助別人的現象。在世界各大城市,因遇到需要幫助的人太多而產生的“同情疲勞”和“感觀超載”,也能限制人們提供幫助(Yousif & Korte,1995)。疲勞和超載有助於解釋羅伯特·列文及其同事(Levine & others,1994)的實驗結果,他們在美國的36個城市中測試了幾千人,他們設置了各種場景,掉下一支不起眼的鋼筆,請求換零錢,假裝成需要幫助的盲人待在拐角處等。結果發現,在人越多、人口越稠密的城市裡,人們提供幫助的可能性越小。列文及其同事(2001,2003)還發現,人們幫助陌生人的可能性也隨地域的不同而變化(如圖12-6)。經濟發達國家的人們往往為陌生人提供更少的幫助,那些文化中含有“親切”、“和睦”成分(例如,西班牙語:simpatia;葡萄牙語:simpatico)國家的人們,往往會為陌生人提供更多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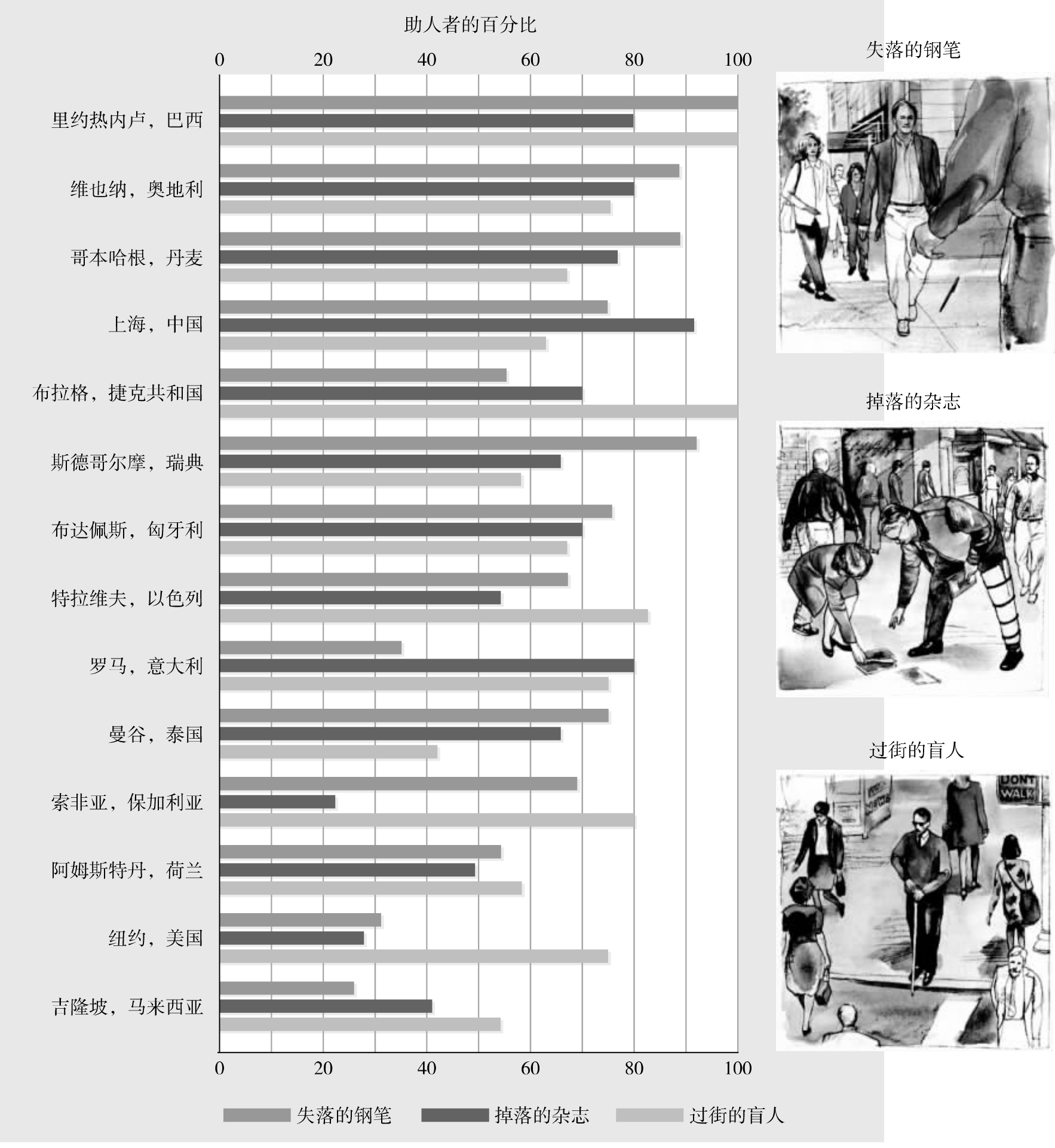
圖12-6 不同地域的人們對陌生人提供幫助的差異
為了比較不同城市和文化中幫助行為的差異,羅伯特·列文及其同事設置了一些“偶然”事件,諸如掉落鋼筆,帶著明顯有傷的腿不方便地行走時掉落雜誌,或者一個假裝的盲人在路口等著過馬路。結果發現,以撿起掉落的鋼筆為例,里約熱內盧人的幫助行為是紐約人或吉隆坡人的4倍。(圖中數據來自14個城市的樣本。)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R. V. Levine(2003),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American Scientist ,91,226-233.
國家之間,通常也會袖手旁觀別國的大災難、種族屠殺等事件。當80萬名盧旺達人被屠殺時,所有人都袖手旁觀。“由於有很多人都能做出行動,個人感覺應負的責任就少了。”斯托布(Staub,1997)解釋道。“這不是我們的責任,”沒有受影響的國家領導人說。心理學家彼得·蘇德菲爾德(Suedfeld,2000)——像斯托布一樣,是一名大屠殺的倖存者——解釋說:責任擴散同樣能解釋“為什麼絕大多數的歐洲人在其猶太同胞遭到迫害、驅逐和殘殺時的袖手旁觀。”[“作為38名目擊者之一”,羅森塔爾 (A. M. Rosenthal)反思吉諾維斯謀殺案時,不禁質問:為了擺脫責任,一個人與一件他所知道的謀殺案要保持多遠的距離?一個街區?一英里?還是一千英里 ?]
在皮列文的地鐵實驗中,乘客們面對面地坐著,他們能互相看到彼此臉上的驚慌。為了考察表情交流的效果,達利等人(Darley,Teger,& Lewis,1973)讓兩名被試在一個房間裡面對面或背靠背地工作,這時旁邊房間裡發出了碰撞聲,好像是有幾個金屬屏風壓在了一名工人身上。實驗結果發現,那些背靠背工作的被試,與那些單獨工作的被試(他們幾乎總是提供幫助)不同,他們很少提供幫助。而那些面對面工作的人,彼此能看到相互的表情,知道對方也注意到旁邊房間裡發生的事情。很顯然,彼此的表情讓他們把旁邊發生的事情解釋為緊急事件,並覺得有責任採取行動。這樣的一對被試,他們會像單獨工作的被試一樣給予援助。
最後,我們上面考慮的所有實驗都涉及的是陌生人群體。現在,想像你和你的一群朋友一起面對其中任何一種緊急情境。你認為旁觀者是熟人或陌生人會對你的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嗎?在以色列的兩個城市和在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大學進行的實驗表明,兩者確實存在差異(Rutkowski & others,1983;Yinon & others,1982)。相對於彼此孤立的個體,相互聯繫的群體會提供更多幫助。總之,在場的其他旁觀者會抑制個體的幫助行為,尤其是當緊急情境不甚明瞭 或旁觀者是不容易理解彼此行為的陌生人 時。
重溫研究倫理
這些實驗又一次引出了研究倫理的問題。應該強迫幾百名地鐵乘客目睹某人摔倒在地嗎?在癲癇發作的實驗中,研究者迫使被試決定是否要打斷討論而去報告出現的狀況,這樣做符合倫理嗎?你會反對參加這樣的實驗嗎?請注意,你參加這樣的實驗時是不可能擁有“知情同意權”的,難道研究者就有權利這樣做嗎?
研究者辯解說,他們總是很認真地聽取實驗被試的報告。在完成癲癇發作實驗——這項實驗讓被試承受的壓力也許是最大的——之後,研究者對被試做了問卷調查,最能說明實驗成功的是,所有被試都認為實驗中的欺騙是可以接受的,他們願意以後再參加類似的實驗。沒有人報告對研究者有憤怒的情感。其他研究者也證實,這些實驗的絕大多數被試都認為他們參與的實驗是有益的且符合倫理(Schwartz & Gottlieb,1981)。在現場實驗中,如在地鐵列車中進行實驗時,如果沒有旁人提供幫助,研究助手就會提供幫助,用這樣的方式使旁觀者確認那個問題已被解決。
必須牢記社會心理學家擔負著雙重的倫理責任:其一是保護被試;其二是通過發現影響人類行為的因素來改善人類生活。前面說的那些發現可以提醒我們留意一些不必要因素的影響,並且知道如何發揮因素的積極作用。倫理原則應該是這樣的:在保護被試利益的前提下,社會心理學家做研究,以實現其對社會的責任。
當別人也提供幫助時
攻擊性榜樣助長攻擊行為(第10章),漠然視之的榜樣也增加冷漠的反應,那麼熱心幫助的榜樣是否也會促進幫助行為呢?想像突然聽到撞擊聲,然後是哭泣和呻吟,這時如果一名旁觀者說道:“啊,出事了!我們得去幫幫忙。”這會引得其他人一起去嗎?
答案是肯定的:親社會的榜樣能夠促進利他行為。下面是一些例證:
布萊恩和特斯特(Bryan & Test,1967)對洛杉磯駕車者的研究發現,如果讓這些駕車的人在四分之一英里前目睹一個提供幫助行為的榜樣時,他們將更可能幫汽車拋錨的女士換輪胎。
另一項研究中,布萊恩和特斯特觀察到,新澤西的聖誕購物者在看到其他人將錢投入慈善募捐箱後,也更可能照樣去做。
拉什頓和坎貝爾(Rushton & Campbell,1977)發現,英國成人假如看到已經有人獻血的話,就會更樂意答應獻血。
目睹令人感動的善舉——比如我們在本章開頭所列的英雄事蹟——常常會引發海特(Haidt,2003)所稱的“昇華(elevation)”狀態:“一種胸腔被溫暖和激情膨脹的特殊感覺”,這種狀態會使得人們戰慄、流淚、喉嚨抽緊,人們這時變得更富於自我奉獻精神。
然而,榜樣卻並不總是言行一致。父母可能告訴孩子:“照我說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實驗表明,孩子不僅從耳濡的教誨,也從目染的行為中學習道德觀(Rice & Grusec,1975;Rushton,1975)。假使碰到偽善者,他們也會去模仿:照榜樣說的去說,照榜樣做的去做。
時間壓力
達利和巴特森(1973)從“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寓言中找到了另一個影響助人的決定性因素。牧師和利未人都是忙碌的大人物,可能正趕著去履行他們的職責呢,而悠然的撒馬利亞人一定是沒有多大的時間壓力。為了弄清匆忙中的人們是否就會跟牧師及利未人一樣不願管他人的事,達利和巴特森巧妙地展現了寓言中的情境。
研究者讓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生們做被試,在瞭解了他們的想法後,這些被試前往附近的錄音室作一個即興演講的錄音(其中一半被試的錄音主題是“善良的撒馬利亞人”寓言)。在他們去錄音室的途中,要經過一個癱坐在門口的老人,那老人垂著頭咳嗽、呻吟著。一部分被試在臨行時接受的不是催促的指示:“現在離準備就緒還有幾分鐘時間,你會早到的。”結果,這些被試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停下來幫助了老人。另一些被試則被催促:“噢,你要遲到了。錄音室在幾分鐘前就在等你了……最好快點。”結果,這些被試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停下來提供幫助。
對於這個結果,達利和巴特森評論道:
一個悠閒的人,可能停下來幫助處於困境中的人。一個有急事的人則會繼續趕他的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當他正是要趕去演講“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時也不例外,無意間正合了這個寓言的題中之義。(事實上,有一些趕去演講“善良的撒馬利亞人”寓言的神學院學生徑直地跨過了需要幫助的老人!)
我們對這些學生的評論是否不公平呢?畢竟,他們是要趕去幫助 研究者的,也許他們敏銳地感受到了社會責任規範,但卻又陷入了兩難境地——該向著研究者還是該向著那個老人?在另一個類似“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情境中,巴特森及其助手(1978)讓40位堪薩斯大學的學生前往另一座樓參加實驗。告訴一半被試說他們遲到了,告訴另一半被試說還有充足的時間。一半的被試認為自己的參與對實驗者至關重要,另一半則認為無關緊要。結果是:那些時間充裕且認為自己的參與無關緊要的被試常會停下來提供幫助。那些認為自己的參與很重要,而又延誤了時間的被試——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白兔一般——則很少有人會停下腳步去幫助別人。
難道我們能夠由此得出結論,說那些匆忙趕路的人是冷漠無情的嗎?神學院的學生們注意到了老人的困境卻有意地置之不理嗎?不,匆匆忙忙中,他們根本就沒有太留心周圍的事情。為了按時到達,他們著急地、全神貫注地向前衝著,沒有空暇注意到有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正如社會心理學家常常觀察到的那樣,行為受情境的影響比我們通常認為的還要大。
相似性
因為相似性容易喚起喜歡(第11章),而喜歡又會引起幫助行為,因此我們更多地對那些跟我們相似 的人產生共情,也更樂於幫助他們(Miller & others,2001)。相似性偏愛既包括外表,也包括信仰方面。艾姆斯韋勒及其同事(Emswiller & others,1971)讓助手穿上保守的或另類的服裝,然後向穿著“整齊的”或“嬉皮的”普度大學的學生求助,向他們要一枚硬幣打個電話。結果發現,三分之二的被試幫助了與自己相像的求助者,而向與自己不相像的人提供幫助的比率還不到一半。同樣地,在反對同性戀的時代,蘇格蘭的購物者對那些T恤上印有提倡同性戀口號的人,也不太願意換零錢給他們(Gray & others,1991)。
沒有哪張面孔比我們對自己的面孔更熟悉了。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會出現德布魯因(DeBruine,2002)的實驗結果。研究者要求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的學生與另一名假想的同伴玩一種互動遊戲,結果發現,被試對那些照片上看來具有某些自己特徵的同伴更信任,也更慷慨(如圖12-7)。我相信我自己。哪怕是與自己的生日相同、名字相同,甚至指紋相同都能引起人們更多的幫助行為(Burger & others,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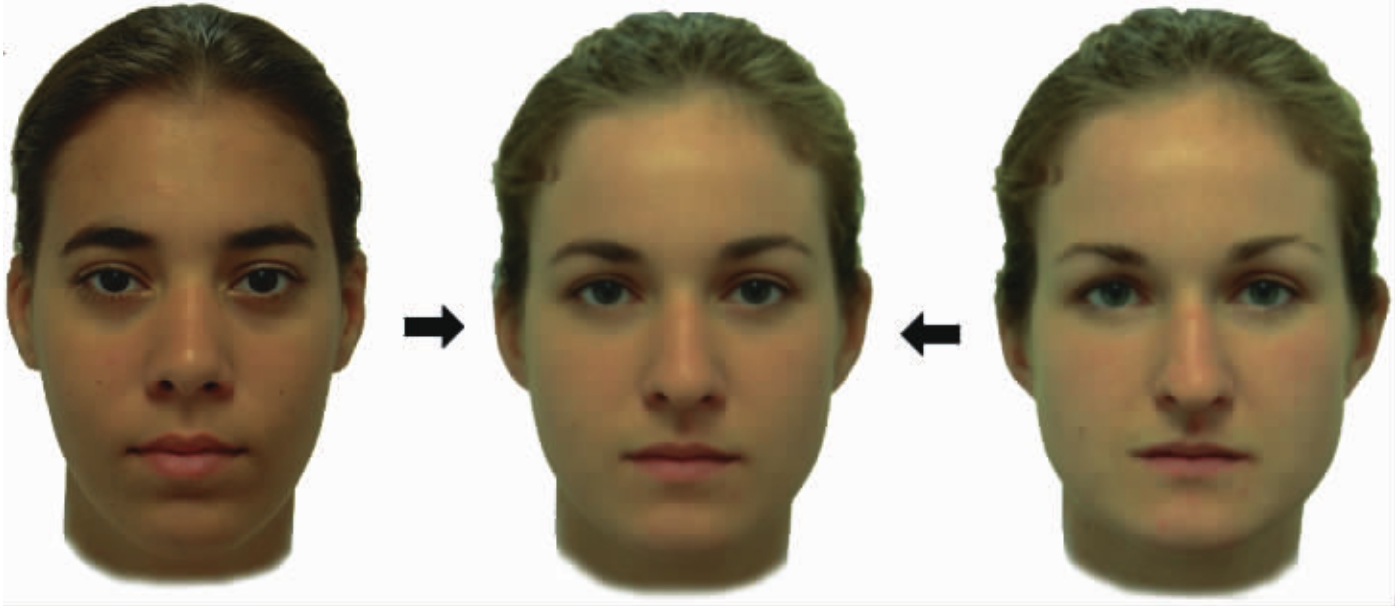
圖12-7 相似性導致合作
具有由被試的面孔(左)和陌生人的面孔(右)組合成的中間面孔的虛擬陌生人,能夠使被試對之更為慷慨。
這種相似性偏愛也能延伸至全種族之間嗎?20世紀70年代,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矛盾的結果:
一些研究發現了同種族偏愛的傾向 (Benson & others,1976;Clark,1974;Franklin,1974;Gaertner,1973;Gaertner & Bickman,1971;Sissons,1981)。
另一些研究沒有發現偏愛的傾向 (Gaertnher,1975;Lerner & Frank,1974;Wilson & Donnerstein,1979;Wispe & Freshley,1971)。
還有一些研究——尤其是涉及面對面情境的研究——發現了幫助異族人的偏好傾向 (Dutton,1971,1973;Dutton & Lake,1973;Katz & others,1975)。
有沒有一個普遍的規律可以用來解決這些看似矛盾的發現呢?
很少有人希望表現出偏見。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人們雖然喜歡自己的同族,但又要守住這一偏愛的祕密以維護自己積極的形象。所以,只有當人們可以將自己不幫助其他種族的行為歸因於非種族因素時,才會表現出同種族偏愛。蓋特納和德維迪奧(Gaertner & Dovidio,1977,1986)的實驗正說明了這一切。研究者以特拉華大學的白人女大學生為被試的實驗發現,當有其他旁觀者分散責任時,被試寧願幫助“困境中的”白人而不太樂於幫助“困境中的”黑人婦女(“我沒有幫助那個黑人婦女,是因為有其他人會幫助的”)。當沒有其他旁觀者時,這些被試對黑人和白人婦女則給予同等的幫助。似乎存在這樣的規律:當適宜行為的標準有明確界定時,白人不會表現種族差別;當標準模糊或者衝突的時候,種族相似性可能引起有偏愛的反應。
對於我自己,最近就遇到了一次實驗中的情境。我在華盛頓參加完宴會,回旅館的途中,我走在僻靜的人行道上。這時,一個穿著體面、與我差不多年紀、神色驚慌的男子向我走來,他向我要1美元。他解釋說他剛從倫敦來到這裡,參觀完大屠殺博物館之後,意外地把錢包落在出租車上了。他被困在這兒了,需要24美元才能打車到達他暫住的郊區的朋友家裡。
“那1美元怎麼能讓你到達那兒呢?”我問。
“我曾向人們要多一些的錢,但是沒有人肯給我,”他幾乎哽咽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向人們少要一點,多要幾個人也許可以攢夠。”
“你為什麼不去乘地鐵呢?”我質疑。
“地鐵站離我要去的Greenbriar還有5英里。”他解釋道,“老天爺!我那樣還是到不了目的地啊!如果你肯幫我,我會在週一把錢寄還給你。”
我站在那兒,猶如一個在街上做利他主義實驗的被試。我從小在城市裡長大,是紐約和芝加哥的常客,我已經習慣了那些乞討者,從不施捨他們。但是,我仍然認為自己是有同情心的人。況且,眼前這個人跟我見過的任何乞丐都不像。他穿著整齊,聰明伶俐,說的也頭頭是道令人信服。而且,他看起來像我!如果他說謊,他就是個混蛋,我對自己說,給他錢是愚蠢、天真的,還縱容了騙子。但如果他是個誠實的人,而我卻拒絕了他,那麼我就是個混蛋。
他想要1美元,而我給了他30美元以及我的姓名地址。他感激地收下了,而後消失在夜色裡。
我繼續向前走著,漸漸意識到——如後來事實所表明的——我受騙了。我自己就曾生活在英國,為什麼沒有考他一下有關英國的知識?為什麼沒有帶他到電話亭給他的朋友打個電話?為什麼沒有把錢給出租車司機讓其送他而要把錢給他呢?為什麼平生一直抵制欺詐的我,這回卻上當了呢?
因為我寧願認為自己不受種族刻板印象的影響,所以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使我上當的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富於社交技巧的、獨特的欺騙方法,而且在於他與我具有相似性這一純粹的事實。
誰會提供幫助
我們已經討論過影響幫助行為的內部因素(比如內疚感和心境)以及外部因素(比如社會規範、旁觀者數目、時間壓力、相似性等)。我們還要討論幫助者本身的特點,包括他們的個性特點和宗教信仰等。
人格特徵
特雷莎修女 [1] 確有一些獨特的品質。面對同樣的情況,一些人會積極地反應,向他人提供幫助,但也有人無動於衷。那麼,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成為助人者呢?
很久以來,社會心理學家一直沒有發現一種人格特徵能像情境、內疚感和心境等因素那樣,對利他行為有預測力。研究發現,幫助行為和某些人格變量——如社會讚許需要——有中等程度的相關。但總的來看,人格測驗並不能區分出助人者。對歐洲納粹時期猶太人的營救者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社會環境明顯地影響著幫助的意願,卻並不存在明確的利他人格特徵(Darley,1995)。
這令我們想起了有關從眾研究的類似結論(第6章):從眾,也似乎更容易受到情境的影響,而不太受那些可測量的人格特徵的影響。也許,你想起了第2章裡討論過的內容:我們的人品影響著我們的所作所為。但是態度和特質的測量很少能夠預測一個特定 的行為,而絕大多數利他性的實驗研究都是以此為度量的(這跟聖母特雷莎畢生的利他主義品質不同)。但在預測多種情境下的平均行為表現方面,態度、特質就更為準確。
人格研究者對這一質疑作出了迴應。首先,他們發現了助人性的個體差異 ,並證實這種差異具有時間上的持續性,而且可被同伴注意到(Hampson,1984;Penner,2002;Rushton & others,1981)。有一些人更傾向於助人。其次,研究者正在蒐集能夠預測人們助人性的相關人格特徵(network of traits)線索。那些具有較高的積極情緒性、共情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關心人,也更容易表現出幫助行為(Bierhoff & others,1991;Eisenberg & others,1991;Krueger & others,2001)。再次,人格影響特定的個人對特定情境 的反應(Carlo & others,1991;Romer &others,1986;Wilson & Petruska,1984)。那些自我監控能力強的人,如果認為助人能夠得到社會讚許的話,就會迎合他人期望從而顯得樂於助人(White & Gerstein,1987)。他人評價不太能影響那些內向的、低自我監控的人。
在172項大概包括了5萬名男女被試的助人性的比較研究中,也體現了人和情境的交互作用。伊格利和克勞利(Eagly & Crowley,1986)在分析了這些結果後指出,當面對的求助者是陌生人並且情境有潛在危險時(如車胎破了或者掉下地鐵軌道),男性更常伸出援手。(伊格利和克勞利還報告,在6767名因救人的英雄行為而獲得卡耐基獎章的人中,有90%是男性。)但在安全的情境中,如志願幫助研究者做實驗,或者花時間陪伴殘疾兒童時,則是女性樂意幫忙者略多於男性。因此,性別差異交互作用(取決)於情境。伊格利和克勞利還猜測,如果研究的是長時間的基於親密關係的關心行為而不是幫助不期而遇的陌生人的話,女性將顯著地更具幫助性。的確,喬治及其合作者(George & others,1998)報告,婦女對朋友碰到的問題更容易產生共情,更願意付出較多的幫助時間。
宗教信仰
在納粹潛水艇擊沉艦艇的速度超過盟軍所能補給的情形下,戰艦道徹斯特(Dorchester)號載著902人從紐約港向著格陵蘭島出征了(Elliott,1989;Parachin,1992)。在這些不得已離開牽腸掛肚的家人們的士兵中,有四位隨軍牧師:衛理公會傳教士喬治·福克斯、拉比亞歷山大·古德,天主教牧師約翰·華盛頓和基督教牧師克拉克·泡靈。戰艦在離目的地150英里處遭遇納粹潛水艇U-456的魚雷襲擊,戰艦開始下沉,熟睡中的人們被從鋪位上拋下。護衛船隊對這場慘劇還渾然不覺,仍在黑暗中繼續前進。而旗艦的甲板上此時已是混亂一團,恐慌中的人們從船艙裡湧出,沒穿救生衣就跳上已經相當擁擠的救生艇。
四位牧師走上已嚴重傾斜的甲板,他們開始引領人們各就各位。他們打開儲藏室分發救生衣,一邊還安撫著人們。當軍官約翰·馬哈尼回頭尋找他的手套時,拉比古德說:“不要緊,我有兩副。”但是馬哈尼後來才知道,拉比並沒有帶多餘的一副,他給出的是自己的手套。
在冰冷的、漂著油汙的海水裡,士兵威廉·貝德納在牧師們佈道的鼓勵下,才有了從船底下游過來爬上救生艇的力量。甲板上,格雷迪·克拉克帶著敬畏看著牧師們發出最後一件救生衣,然後無私地脫下他們自己身上的救生衣。當克拉克躍入水中時,他回過頭看到了畢生難忘的場景:四位牧師站立著,手挽著手用拉丁語、希伯來語和英語禱告著。其他人在逐漸下沉的艦艇上也加入了禱告。“這是我此生見過的,也是在有生之年希望見到的最美好的事情,”約翰·拉德說道。他是230名倖存者中的一個。
四牧師的這一英雄事蹟是否說明,信仰提升了勇氣和關懷?大量有關幫助行為的研究都是針對自發的幫助行為。當面臨一個不那麼緊急的事件時,虔誠的教徒只是比一般人有稍微強一點的反應(Trimble,1993)。如今,研究者開始探索有計劃的幫助——像艾滋病志願者,大哥哥和大姐姐(Big Brother and Big Sister)志願者,以及校園服務組織的支持者們提供的那樣持久的幫助。研究發現,在對長期幫助作自願選擇時,宗教信仰有更好的預測性。
研究者對人們做志願者,比如幫助艾滋病患者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斯奈德等人(Snyder,Omoto,& Clary)(Clary & Snyder,1993,1995;Clary & others,1998,1999)總結了六種動機。有一些幫助行為源於回報——希望加入一個群體,獲得讚揚,尋求職業的提升,減少內疚感,學習技能或提高自尊等。另一些幫助行為則源於人們的宗教信仰或人道主義的價值觀,以及對他人的關心。
對大學生和普通民眾的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從事志願者工作(諸如課外輔導員、救濟工作、維護社會治安等)上花的時間更多(Benson & others,1980;Hansen & others,1995;Penner,2002)。在12%被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1984)稱為有“高度精神信仰”的美國人當中,有46%的人稱自己正在為窮人、病人和老人們做一些事情——這個比例遠遠高於那些“高度無信仰”的人中的比例(22%)(圖12-8)。隨後的一個蓋洛普調查(Colasanto,1989)結果顯示,把宗教評估為生活中“不太重要”的人中有28%,評估為“非常重要”的人中有50%報告參與了慈善和社會服務活動。另一個蓋洛普調查發現,那些一年只去一次或更少去教堂的人中,只有37%的人把“對窮人的責任”評估為至少是“相當重要”,而那些每週都去教堂的人中,則有76%的人這麼做(Wuthnow,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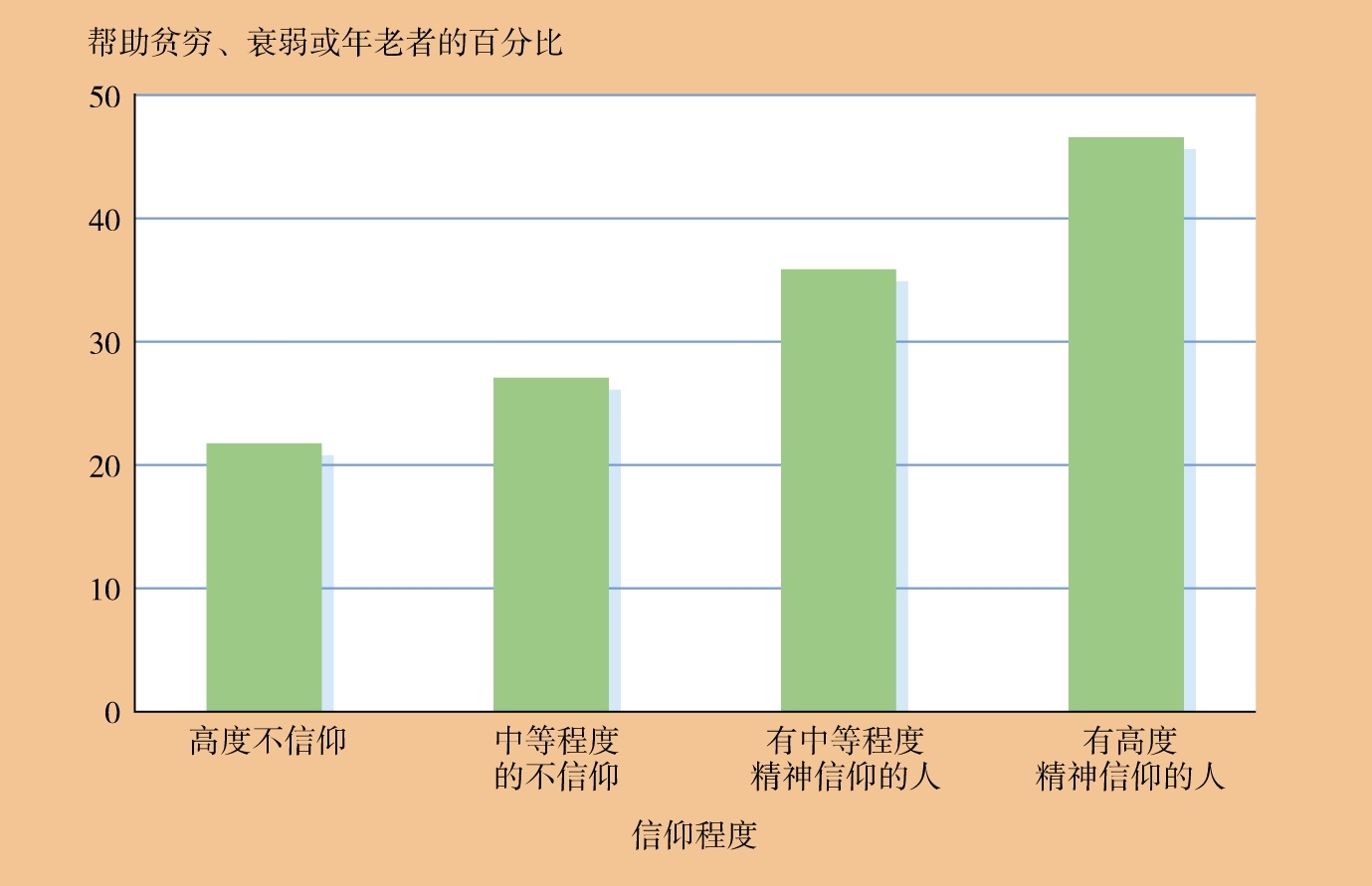
圖12-8 宗教信仰和長期的利他主義
被喬治·蓋洛普(George Gallup,1984)稱為有“高度精神信仰”的人更可能對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
資料來源:Simplified from Anderson,Deuser,and DeNeve,1995.
此外,利文森(Sam Levenson)的俏皮話——“奉獻的時刻來到,有人卻無端地逃掉”——極少適用於基督教和猶太教徒。1987年的一項蓋洛普調查報告顯示,自述從不去基督教堂或猶太教堂的美國人會捐出他們收入的1.1%給慈善事業(Hodgkinson & others,1990),而每週去教堂的人捐款的數額要2.5倍於此。這些常去教堂的人佔美國總人口的24%(也就是四分之一),他們的慈善捐款比率卻高達48%(總捐款的一半),另外四分之三的美國人捐獻另一半。隨後的1990和1992年的蓋洛普調查,以及2001年的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調查也都確認了信仰和慈善事業的相關(Hodgkinson & Weitzman,1990,1992)。
宗教信仰與有計劃的幫助之間的聯繫能夠擴展到其他公共組織嗎?羅伯特·帕特南(Putnam,2000)分析了22類組織的全國調查數據,包括業餘俱樂部、專業協會、自助團體和服務社。“宗教團體的成員,”他報告道,“跟公民參與的多種形式有最緊密的聯繫,比如像投票、陪審團工作、社區方案、與鄰居交談以及慈善捐助等”(p.67)。
小結
不同的情境影響因素抑制或鼓勵了利他主義。緊急事件中隨著旁觀者數目的增加,每一位旁觀者將(1)更少注意這個事件,(2)更少將其解釋為緊急事件,以及(3)更少感到責任。
人們在什麼時候最有可能去幫助呢?(1)觀察到其他人的幫助行為之後;(2)時間不太緊的時候。個人因素,如心境也有影響。
與潛在的情境因素和心境因素不同,人格測驗分數對助人性只有中度的預測力。但是,最新的證據表明,一部分人能夠持久地比其他人更樂於幫助,並且人格特徵和性別的效應可能取決於情境。宗教信仰能夠預測長期的利他主義,如志願者工作和慈善捐獻。
如何增加幫助行為
我們能否通過把那些抑制幫助的因素反過來用以增加幫助呢?或者我們教化幫助的社會規範,通過社會化使人們自視為樂於助人的人。
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目標是理解人類行為,從而提出改善行為的方案。因此我們想知道,應該怎樣利用研究所得的知識來增進幫助行為。
去除對幫助的抑制
促進利他主義的一種方法就是把那些抑制它的因素反過來。既然那些匆忙的、關注自我的人們較少去幫助,那麼我們能否想出辦法來,鼓勵他們放慢腳步並將注意力轉向外部呢?如果他人的在場削弱了每個旁觀者的責任感,我們又怎樣來提高他們的責任感呢?
減少模糊性,提高責任感
如果拉塔奈和達利的決策樹(圖12-4)描述了旁觀者面臨的兩難選擇,那麼幫助人們正確地解釋事件和確認責任就應當可以增加他們的參與性。比克曼及其同事(Bickman & others,1975,1977,1979)在一系列關於犯罪檢舉的實驗中檢驗了這一假設。每個實驗中,研究者讓超市或書店的購物者目擊一次商店偷竊行為。其中一些目擊者曾看到過有關警惕商店偷竊並說明怎樣檢舉的標誌,但結果發現,這幾乎沒起什麼作用。另一些目擊者能聽到一名旁觀者對事件的解釋:“哎,看她。她在偷東西,她把那個放進了她的包裡。”(這名旁觀者隨後離開去尋找他的孩子。)還有一些人聽到他繼續說著,“我們看見了,我們應該去報告。我們有責任。”研究發現,後兩種安排都顯著地增加了購物者對偷竊行為的檢舉。
個體因素的潛力也不容質疑。羅伯特·福斯(Foss,1978)調查了幾百名獻血者,他們發現,與那些經常獻血的人不同,偶然的獻血者往往是應他人的個人邀請而來的。賈森及其同事(Jason & others,1984)證實,對於獻血來說,來自朋友的個人懇請比海報和媒體宣傳要有效得多。個人的、非言語的懇請也是有效的。斯奈德及其同事(1974;Omoto & Snyder,2002)發現,搭車者通過直視司機的眼睛可以得到兩倍的搭車機會,許多幫助艾滋病人的志願者也是受到了他人的個人因素的影響才參與進來的。個人化的方式,如前面說過的向我求助的那個人所熟諳的,能使人感到不是匿名的,因而有更高的責任感。
亨利·所羅門和琳達·所羅門(Solomon & Solomon,1978;Solomon & others,1981)探索了降低匿名性的方法。他們發現互相介紹過姓名、年齡等的旁觀者比互不知名的旁觀者更可能向生病的人提供幫助。同樣地,如果女研究者與一位購物者有過對視並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微笑的話,隨後在電梯上,當女研究者說“糟糕,我忘了戴眼鏡。誰能告訴我雨傘在哪層?”的時候,曾遇到的那位購物者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會遠遠大於其他人。甚至一小段很短的對話(“不好意思,您是蘇茜·斯皮爾的妹妹嗎?”“不,我不是。”)都會戲劇性地增加人們隨後的幫助性。
當人們預期會與求助者及其他在場者會再度碰面時,幫助性也會增加。戈特利布和卡弗(Gottlieb & Carver,1980)利用實驗室的內部通信系統,使邁阿密大學的學生相信,他們正與其他學生討論大學生活的問題(事實上,其他討論者的聲音是播放的錄音)。當其中一位假想的討論者突然痙攣發作呼喊求助時,那些以為待會兒要與其他討論者見面的被試最快地伸出了援手。簡而言之,任何能使旁觀者變得能凸現出個人特徵的事情——個人請求、目光接觸、告知名字、會面的預期——都增加了幫助的可能性。
凸現個人特徵使旁觀者提高了自我意識,從而更傾向於使自己與內在的利他主義觀念相合拍。回憶前面章節中講過的,讓被試處於鏡子或攝像機前展示自己時,他們的態度和行動間的一致性增加了。相反,“去個體化”會使人們的責任感變低。因此,提高自我意識的做法——貼上姓名標籤、被觀察和評價、注意集中的安靜狀態——能夠增加幫助行為。謝利·杜瓦爾等人(Duval,Duval,& Neely,1979)證實了這一點。他們給一些南加州大學的女生看她們自己的錄像,或者讓她們填寫個人背景問卷,緊接著給她們一個向需要幫助的人奉獻時間或金錢的機會。發現,那些喚起自我意識的被試獻出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同樣地,剛拍了照片的行人更可能幫助另一名行人撿起掉落在地的信封(Hoover & others,1983)。自我意識高的人更經常地將理想付諸於實踐。
內疚和對自我形象的關心
前面我們注意到,感到內疚的人會以行動來減輕內疚感並維護他的自我價值感。我們能否通過提升人們對違規行為的意識來增加他們的幫助意願呢?一項由裡德大學(Reed College)的理查德·卡切夫(Katzev,1978)領導的研究小組考察了這個問題。當波特蘭藝術博物館的遊客違反了“請勿觸摸”的提示時,研究者對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批評道:“請不要觸摸這些展品。如果每個人都觸摸的話,就會毀壞它們。”同樣地,當波蘭動物園的遊客擅自拿食物喂熊時,其中一部分也受到批評:“嘿,不要給動物喂未經許可的食物。你不知道這樣會對它們有害嗎?”在兩種情形下,有58%負有內疚感的被試隨後向另一名“意外”掉落東西的研究者提供了幫助。而未被批評的人則只有三分之一給予了幫助。
人們也關心自己的公眾形象。當羅伯特·恰爾迪尼及其同事(1975)請一部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學生陪伴一些行為不良的孩子去動物園遊玩時,只有32%的人答應。對另一些學生,研究者先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請求——請求他們承諾給行為不良兒童做為期兩年的無償諮詢。在得到對這個留面子 (door-in-the-face)的要求的反應(全部拒絕)後,再側面切入陪伴的請求:“好吧,如果你不願做那個,這點小事願意幫忙嗎?”使用這一技巧時,近兩倍的人(56%)同意幫助。
恰爾迪尼和薛德爾(Cialdini & Schroeder,1976)提供了另一個可以引發個體關注自我形象的實用的方法:請求很微小的幫助,以至於使個體不能拒絕,除非他認為自己是個吝嗇鬼。恰爾迪尼(1995)有一次在家門口遇到一位街頭募捐者時發現了這一點。當募捐者懇請他捐助時,他已經在腦海裡預備好了如何拒絕——直到她說出那句神奇的話,粉碎了他的經濟藉口:“哪怕一便士也是幫助啊。”“我不得不順從了。”恰爾迪尼回憶道,“這次經歷還有個有趣的地方。等我的咳嗽停下來(我真的把到嘴邊的拒絕給嚥了回去),我給了她不是她所說的一便士,而是通常派給正式慈善募捐者的金額。她謝了我,純真地一笑,繼續前行。”恰爾迪尼的反應不具有典型性嗎?為了找出答案,他和薛德爾讓一名募捐者接近一些郊區居民。當募捐者說“我在為美國抗癌組織募集資金”,有29%的人平均每人捐獻了1.44美元。當募捐者補充說“哪怕一便士也是幫助”時,有50%的人平均捐獻了1.54美元。詹姆斯·韋恩特(James Weyant,1984)重複了這一實驗,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哪怕一便士也是幫助”這句話,使捐助者從39%增加到了57%。當6000人收到美國抗癌組織的募捐信時,那些被請求捐獻較少數量的人更可能捐助,並且給出的數量平均而言並未減少(Weyant & Smith,1987)。若遇到的是先前捐獻過的人時,那麼更大的請求(附帶理由)就會引起更多的捐助(Doob & McLaughlin,1989)。但是對於挨戶訪問的募捐,請求小金額的捐助則更可能成功,因為這使人們不好拒絕,而且又使他們有機會維護利他的自我形象。
貼上樂於助人的標籤也能加強人們樂於助人的自我形象。羅伯特·克勞特(Kraut,1973)對一部分參加慈善捐助的康涅狄格的婦女說:“你真是一個慷慨的人。”兩週後,這些婦女比那些沒有被貼上標籤的婦女更可能為另一個慈善團體捐助。
利他主義的社會化
如果我們能夠習得利他主義,那麼該如何教化而使它社會化呢?這裡有四種方法(圖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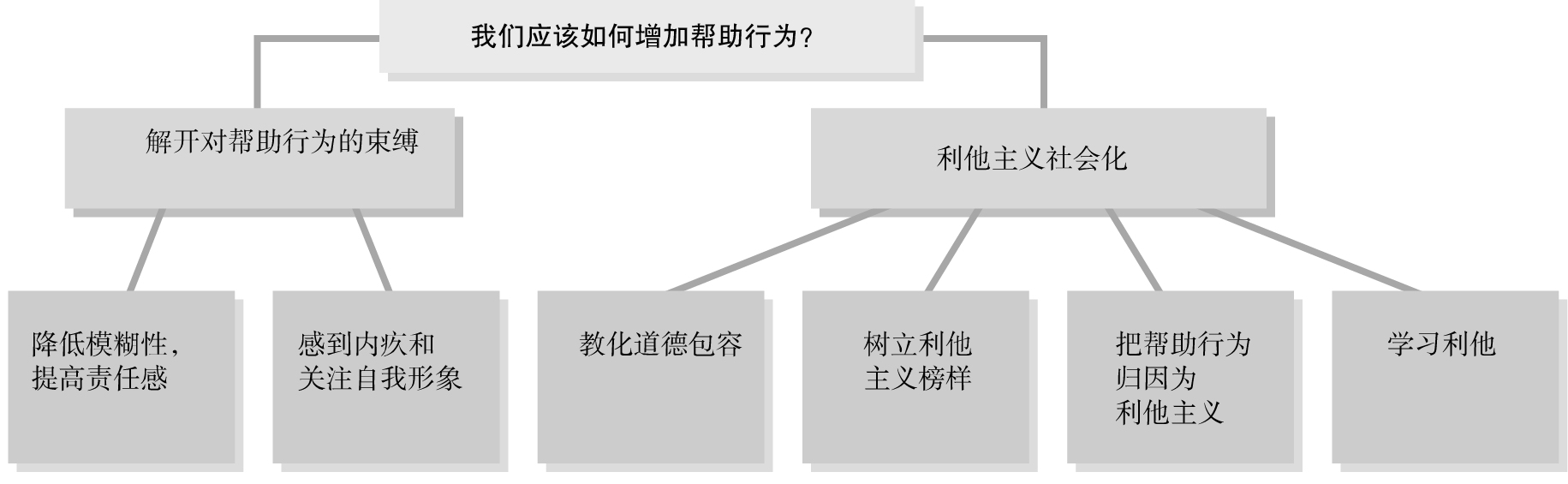
圖12-9 增加幫助行為的常用方法
教化道德包容
對於那些納粹歐洲時救助猶太人的人、美國反奴隸運動的領袖,以及巡迴義診的傳教士們而言,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把那些區別於自己的其他人都看做是一樣的人類,以他們的道德價值觀和正義準則來對待他們。這些人們在道德上具有包容性 ,正如一位婦女所做的,她為了救助一名藏匿的猶太孕婦而假裝懷孕——這樣她就把即將降臨人世的猶太孩子看做是自己的孩子。
道德排除 (moral exclusion)——將某些人(或動物)排除於自己的道德關懷之外——則起相反的作用。從歧視到滅絕性的大屠殺,它令所有的傷害性行為都變得合理(Opotow,1990;Staub,待發表;Tyler & Lind,1990)。人們認為,對那些沒有價值的人或該受排擠的人(被排除於關懷之外的動物也是如此),剝奪和殘忍就會變得可以接受,甚至是適當的。納粹就是將猶太人排除於他們的道德共同體之外。任何參與奴役、行刑或者拷問的人,實際上都實踐著相似的道德排除。在較小的程度上,道德排除可用來描述這樣的行為:我們將我們的關心、喜愛和遺產都集中於“我們的人”(比如我們的孩子)身上,而排除其他人。
因此,利他主義社會化的第一步是去除天然的內群體偏愛,比如親緣喜愛或部族喜愛,而擴展我們關心他人福利的界線。巴特森(Batson,1983)解釋宗教教育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時指出,他們就是宣揚要對整個人類“大家庭”中所有的人的愛,這就把兄弟姐妹之間的血親之愛擴展到了“上帝的孩子”之間的愛,從而擴展了利他主義的邊界。如果每個人都是我們家庭的一分子,那麼每個人就都對我們有道德要求。“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界線將被消除。使人們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想像他人的感受,也有助於增加幫助行為(Batson & others,2003)。“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就怎麼對待別人”,人一定要學會採擇別人的觀點。
樹立利他主義榜樣
前面我們曾講到,目睹無同情心的旁觀者使人們更少去幫助。被極端懲罰性的父母撫養大的孩子,就像很多違法者、長期犯罪者和納粹重戰犯那樣,他們極少表現利他主義者的特徵——共情和道義上的關心。
如果人們看見其他人的幫助行為或讀到他人幫助的故事,是否會更有可能做出幫助行為?羅伯特·恰爾迪尼和他的合作者(2003)發現,不是大肆宣傳偷稅漏稅、亂扔垃圾、青少年吸菸,而是強調——把它們作為人們的行為規範——人們普遍的誠實可靠、講究衛生、戒菸戒酒的話,社會現實會更好。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讓遊客不要拿走化石森林國家公園中的樹木化石,一些遊客被告知,“以前的遊客都把樹木化石拿走了。”另一些遊客則被告知,為了保護公園“以前的遊客從不拿樹木化石”。結果後者幾乎沒有人拿走樹木化石。或許一些慷慨的準則也能通過簡單的方式教給人們,比如在稅單上多設計出一行讓人們填寫——以便於知曉——他們每年捐獻的數額佔他們收入的百分比(Ayres & Nalebuff,2003)。人們知道,而且有時也討論他們支付小費的百分比(對此有明確的規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慈善。
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冒著生命危險救助猶太人的歐洲基督教家庭中,以及50年代的公民權力運動中,榜樣作用也很明顯。在這兩個例子中,那些不凡的利他主義者與其父母的至少一方有著溫暖親密的關係,他們之間非常相似,都是同樣熱烈的“道德家”或投身於人道主義理想(London,1970;Oliner & Oliner,1988;Rosenhan,1970)。他們的家庭——常常還有他們的朋友和教友——教給了他們幫助和關愛他人的準則。斯托布(Staub,1989,1991,1992)解釋道:這種“親社會的價值取向”引導他們將其他群體的人們包容到自己的道德關懷範圍中,並感到對他們的福利負有責任。
斯托布(1999)曾述說自己的經歷:“我,一個布達佩斯的猶太人孩子,在那場大多數歐洲猶太人遭到納粹德國及其盟國屠殺的災難中能倖存下來。拯救我生命的是一位幾番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和我的家人的女基督徒,還有一位瑞典人勞爾·沃倫伯格(Raoul Wallenberg),他憑著勇氣、智慧和承諾拯救了成千上萬將被送往毒氣集中營的猶太人。這兩位英雄都不是被動的旁觀者,我現在的工作也是不使自己變成只顧自己的一種做法。”(見“聚焦:猶太人救助者的行為和態度”。)
電視上的積極榜樣也會助長幫助行為嗎,就像攻擊的榜樣會助長攻擊行為一樣?事實上,親社會的電視榜樣所起的作用遠大於反社會榜樣的作用。蘇珊·希羅德(Hearold,1986)統計並綜合了108項看親社會的電視節目和看中性的電視節目或不看電視節目的比較研究。她發現,平均來說,“如果觀看親社會的節目而不是看中性節目的話,個體的親社會行為——典型的是利他主義行為——(至少暫時地)會從50%上升到74%。”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和施坦(Friedrich & Stein,1973;Stein & Friedirich,1972)每天給幼兒園的孩子們看《羅傑斯先生的鄰居們》片斷,連續看了四周,以此作為幼兒園課程的一部分。(《羅》片意在促進孩子們的社會性和情感的發展。)在看這個電視片的期間,那些來自受教育程度較低家庭的孩子們變得更樂於合作、樂於助人和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情感。在後繼研究中,看了四周《羅傑斯先生的鄰居們》節目的幼兒園孩子,不論是在測試中,還是在木偶戲表演中,都能夠表達出它的親社會內容(Friedrich & Stein,1975;Coates & others,1976)。
把幫助行為歸因於利他主義動機
另一條利他主義社會化的線索來自第4章提到的被叫作“過度辯護效應”(over justification effect)的研究:當對一種行為給予超過適度的反饋時,個體可能會將行為歸因為獎勵這一外部反饋而非內部動機。因而獎勵人們本來就會做的事情反而會削弱其內在動機。我們可以將這一原理積極地表述為:對人們的良好行為給予恰到好處的反饋(必要時應戒除收買與威脅),我們也許可以增加他們自己從做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樂。
丹尼爾·巴特森及其助手(1978,1979)實踐了“過度辯護效應”。在幾個實驗中,他們發現,堪薩斯大學的學生在沒有報酬也沒有潛在社會壓力的條件下,如果答應幫助別人的話,會產生最強的無私感。當有報酬或者社會壓力存在時,他們實施幫助行為之後產生的無私感較弱。
在另一個實驗中,研究者引導學生將幫助行為歸因為順從(“我想我們的確別無選擇”)或同情(“這個人真的需要幫助”)。隨後,當請求學生們拿出時間參與當地的一個服務機構時,認為自己先前的幫助行為僅僅是順從的學生中,有25%的人報名;而認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學生中,有60%的人報名。這是為什麼呢?當人們疑惑“我為什麼幫助?”的時候,如果情境能讓他們這樣回答:“因為有人需要幫助,而我又是個有愛心、樂於奉獻和樂於幫助的人。”那結果是最好不過的。
雖然把獎賞用作控制性的收買時會破壞內在動機,但是一個意外的褒揚卻能令人感到勝任和有價值。如果喬瑟琳被強迫:“如果你收起你的怯懦去獻血,我們就能憑最多的捐獻得到互助獎了。”那麼,他不太可能將自己的獻血歸因為利他主義。而喬瑟琳被讚揚:“你這周忙成這樣,還抽出一個鐘頭來獻血真不容易。”她則更可能懷著無私的自我形象離開——從而還會再次捐獻(Piliavin & others,1982;Thomas & Batson,1981;Thomas & others,1981)。
聚焦 猶太人救助者的行為和態度
仁慈和邪惡一樣,通常都是逐步發展而成的。救助猶太人的異教徒常常也是開始於一個微不足道的承諾——藏匿某人一天或兩天。當邁出這一步之後,他們就開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了,他們會把自己看成一個幫助別人的人。隨後,他們會更熱情地投入到這種幫助之中。奧斯卡·辛德勒在接手一家被充公的猶太工廠後,開始為給他帶來可觀利潤的猶太工人們做點小事。漸漸地,為了保護他們,他冒的風險也越來越大。他通過抗爭得到在工廠旁邊為工人修建住所的許可,他救出被捕的猶太人讓他們與愛人團聚。最後,隨著蘇軍的挺進,他假稱要在家鄉新建一個工廠,需要帶走他所有的“熟練工人”,從而救了1200名猶太人。
其他人,如勞爾·沃倫伯格,開始時也只是答應一個人的請求而伸出了援手,但後來多次冒生命危險去幫助他人。沃倫伯格是駐匈牙利的瑞典大使,他保護了成千上萬名匈牙利的猶太人免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屠殺,其中一個獲救者的身份證顯示他就是當時六歲的艾爾文·斯托布,斯托布後來成為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正是那段經歷使他決定以此為畢生事業:去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犯下罪惡,有些人會袖手旁觀,而有些人會無私援助。
為了使人們在大多數人都不會幫助的情境下實施幫助行為,也可以通過引出他們暫時性的積極承諾,從而使其得出自己樂於助人的結論,而更傾向於提供幫助。西奧菲和加納(Delia Cioffi & Randy Garner,1998)發現,如果先給大學生髮個號召獻血的電子郵件,一週後把獻血車開到校園中,那麼收到電子郵件通知的學生只有5%的人對獻血車做出了迴應。研究者要求另一些學生接到獻血通知時,“如果你認為你可能去獻血的話”,便回覆一個“是”。結果,這些人中有29%的人作了回覆,但實際去獻血的只有8%。研究者要求第三組被試在接到獻血通知時,如果不打算獻血就回復一個“不”。結果有71%的人沒有回覆,這相當於暗示著有可能獻血。現在把你想像成第三組被試中的一員,你沒有說不,也許是因為你畢竟覺得自己是個有同情心的人,所以沒準你還會去獻血呢。這樣的想法可能使你在隨後一週更容易被校園海報和傳單的宣傳所說服。事實正是這樣,這組被試中有12%的人後來獻了血,高於通常比率的兩倍。
在多林斯基(Dariusz Dolinski,2000)的實驗中,也有把自己推斷成樂於助人的人的情節。研究者在波蘭的Wroclaw街道上,攔住行人詢問根本就不存在的“Zubrzyckiego街”在哪兒,或者問一個錯誤的地址。研究發現,被詢問的每個人都試圖幫助卻又無能為力。就在前方100米處,有另一個人請求行人花五分鐘時間幫忙看管他們的重物或自行車,大約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答應幫忙了,這個數字是那些沒有獲得試圖幫助機會的人所給予幫助的兩倍。在更大範圍內說,把“服務學習”和志願者計劃編入學校的課程,提高了日後的公民參與、社會責任感、合作以及領導能力(Andersen,1998;Putnam,2000)。態度緊隨行為。助人行動能夠促進把自己看做是“富有同情心和樂於助人的人”的自我知覺,而這種自我知覺又反過來促進了進一步的幫助行為。
習得的利他主義
研究者還發現了一條推進利他主義的途徑,這給了本章一個令人愉快的結尾。有些社會心理學家擔憂,隨著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發現逐漸為人所知,人們的行為就會發生變化,從而使這些發現失去了應有的效果(Gergen,1982)。瞭解了抑制利他主義的因素就會減少這些因素的影響嗎?有時候,這種“啟迪”並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阿瑟·比曼及其同事(Arthur Beaman & others,1978)對蒙大拿大學學生的實驗表明,人們一旦瞭解了為什麼旁觀者在場會抑制幫助,他們在群體情境下幫助的可能性就會增加。研究者在演講中,告訴一部分學生,旁觀者的冷漠如何影響個體對突發事件的解釋以及責任感。另一部分學生則聽一個別的演講或者沒聽任何演講。兩週之後,作為在另一地點的另一個實驗的一部分,被試(與一個冷漠的合作研究者)一道走著,路上遇見一個人摔倒或者趴在自行車底下。結果發現,那些沒有聽有關幫助內容演講的人只有四分之一停下來實施幫助行為,而接受了“啟迪”的人實施幫助的則兩倍於此。
讀了這章之後,你可能也已改變。當你瞭解了什麼因素會影響人們的反應之後,你的態度和行為還會跟以前一樣嗎?
小結
研究表明,我們可以用兩種方法來增加助人性。首先,我們可以把那些抑制幫助的因素反過來。我們可以採取步驟來減少突發事件的模糊性,產生個體化的吸引力,並增加旁觀者的責任感。我們甚至可以採用申斥或留面子技巧來激起人們的內疚感或對自我形象的關注。其次,我們可以教化利他主義。關於電視中親社會的榜樣形象的研究,已經顯示了媒體在教化積極行為上的力量。觀看幫助行為的孩子們也傾向於做出幫助行為。
如果我們想誘導人們的利他主義行為,我們還應當記住過度辯護效應:強制行善常常會減少行善者對善行的自發之愛。如果我們給決定做好事的人提供足夠的獎勵,但又不過分的話,做好事的人就會把自己的行為歸因於自己的利他動機,從而會更樂於幫助。對於利他主義的學習,如你剛剛所做的,也會使人們作好準備,更好地知覺他人的需要並進行反應。
個人後記:讓社會心理學走進生活
我們這些研究、講授社會心理學,並寫作社會心理學文章的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相信我們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它研究人類的重要現象。學習社會心理學可以開拓我們的思維,幫助我們帶著更高的自覺和同情心去生活和行動,至少我們假定如此。
當現在的和以前的學生們用社會心理學如何跟他們的生活相聯繫的故事證實我們的假定時,那種感覺實在是太好了。就在我寫下最後一段之前,一位現住在華盛頓特區的以前的學生來訪。她提起最近的一次經歷:一名男子不省人事地躺在人行道上,旁邊的行人紛紛走過。“這讓我回想起了社會心理學課程,還有此情此景下人們為什麼無動於衷的原因。我想道:‘如果我也走過去了,誰來幫助他呢?’”於是,她撥了急救電話並陪著那個倒在地上的人——其他旁觀者也加入進來了——直到救護車到來。
你的觀點是什麼
過去的一週裡,你曾注意到有人需要幫助嗎?你,或者其他人是否幫助了他?如果他獲得了幫助,那麼是什麼促成了幫助行為呢?你認識到了由幫助所帶來的回報嗎?其他旁觀者有何影響?時間壓力的影響如何?人格特徵的影響如何?
聯繫社會
這章作為對利他主義探索的一部分,我們介紹了達利關於旁觀者效應的經典研究。在前面有關偏見(第9章)的章節中,我們還介紹了達利關於刻板印象如何微妙地使我們對個體的評價帶有偏見的研究工作。為什麼他人的在場就抑制了人們的幫助行為呢?
[1] 著名的慈善家。出生於馬其頓一個富裕的阿爾巴尼亞家庭,放棄優越的生活去加爾各答的貧民窟為貧困無助和瀕臨死亡的人服務,她認為應該讓窮人們死得像天使一樣。成立了很多臨終關懷醫院幫助窮人們走完最後的人生路。她所創建的“仁愛傳教修女會”在100多個國家設立了500多家慈善機構和場所,數以百萬計的人從中得到了幫助。她被尊稱為“聖母特雷莎”,曾獲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譯者注。
第13章 衝突與和解
什麼會引起衝突
社會困境
競爭
知覺到的不公正
誤解
怎樣獲得和平
接觸
合作
溝通
和解
個人後記: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之間的衝突
“如果你想獲得和平,那就為正義而努力吧!”
——羅馬教皇保羅六世
有 一種論調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領導人用不同的語言重複著:“我們國家從來都是愛好和平的,但是,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其他國家擁有的新式武器對我們造成了威脅。因此我們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別國的攻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衛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維護持久的和平”(Richardson,1960)。幾乎每個國家在強調和平是自己的惟一目標的同時,也表現出對其他國家的不信任,並通過武裝自己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這樣做的結果是全球每天在軍隊和武器上花費達20億美元,同時卻眼睜睜地看著數以億計的人們死於營養不良或缺少醫療。
衝突 (conflict)的成分在各種層面上都是類似的,從國與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到中東地區的衝突;從公司管理者與一般職員關於工資水平的爭吵,到長期不和的夫婦。不論處於衝突中的人們能否正確地知覺雙方的行為,他們總是認為一方的獲益就是另一方的損失。“我們想要和平和安全感。”“我們也是,但是你們威脅到我們了。”“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報酬。”“我們不能提供那麼多。”“我希望你能把音樂關掉。”“我就喜歡放音樂。”
從另一個方面看,缺乏衝突的關係或組織可能是死氣沉沉的。衝突體現了參與、承諾和關心。如果能夠被理解和解決,衝突可以促進人際關係的變化和發展。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很少會想到要面對並解決他們的問題。
在最積極的意義上,和平 指的不是對公開衝突的壓制,也不是一種處於緊張和脆弱狀態下的表面的平靜,它是通過創造性地處理衝突得到的結果,不同的團體協調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並達成了真正的一致:“我們獲得了加薪,你們也得到了更多的利潤。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在幫助其他人達成願望。”
在這一章中,我們通過下面幾個問題探討衝突與和解。
什麼樣的社會情境引發了衝突?
誤解是如何加深衝突的?
和另一方的接觸會減少衝突嗎?
什麼時候合作、交流與調和能夠促成和解?
什麼會引起衝突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了一些導致衝突的因素,令人吃驚的(同時也簡化了我們工作的)是,這些因素在社會衝突的各個層面中普遍存在,不管是國與國之間,還是團體之間或個人之間的衝突。
社會困境
一些對人類未來威脅最大的問題——核武器,全球性氣候變暖,人口過度增長,自然資源枯竭——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不同的團體追逐他們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行為最終都損害了集體的利益。很多人都會這樣想:“為了那個昂貴的汙染控制計劃,我可要花一大筆錢,但是我自己造成的汙染不過是一點點而已。”其他人也有類似的想法,這樣想的結果就是我們要面對汙濁的空氣和不潔的水源。
在某些社會中的人會有這樣的觀點: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夠對家庭式的勞作有所幫助,並能在父母年老後提供保障。但是當大多數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之後,結果是人口過剩給整個社會帶來危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個體有利的決策對整體而言可能是不利的,於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兩難問題也就產生了:我們如何能讓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和集體利益協調一致?
為了分離並更好地說明這一困難的選擇,社會心理學家們進行了一些實驗室遊戲,它們很好地體現了許多真實的社會衝突的實質。在這些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思維正常的人是如何陷入相互矛盾的行為,它們揭示了人類生存過程中一些奇妙但是使人困惑的悖論。
“研究衝突的社會心理學家,在許多方面處於與天文學家類似的地位上,”一位衝突的研究者多伊奇(Morton Deutsch)這樣寫道。“在社會學問題上我們無法完成樣本容量較大的現場實驗研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大樣本與小樣本之間的相似性來推導我們的理論,二者的關係正如天文學家眼中的行星與牛頓的蘋果間的關係。因此在實驗室中少量被試進行的遊戲可能會加深我們對戰爭、和平以及社會公正的理解。”
在這裡我們將考慮兩個例子:囚徒困境和公共地悲劇。
囚徒困境
這個難題源於一個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兩個犯罪嫌疑人由地方檢察官進行分別審問時採取的策略(Rapoport,1960)。他們合夥犯罪,但是檢察官掌握的證據只能判他們很輕的罪。因此檢察官為了使嫌疑犯願意單獨承認自己的罪行,設置了一種鼓勵辦法:
如果一個嫌疑犯認罪而另一個沒有,認罪的嫌疑犯將贏得豁免(並利用他的供詞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嚴厲的判決)。
如果兩個嫌疑犯都認罪,他們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決。
如果兩個人都不認罪,他們都會得到較輕的判決。
圖13-1的矩陣總結了各種選擇帶來的結果,面對這樣一個情境,你會認罪嗎?
為了使對自己的判決減至最輕,很多人都會承認罪行,儘管實際上兩個人互相指控會比都不認罪帶來更加嚴厲的懲罰。從圖13-1的矩陣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選擇,認罪總是比較有利的做法。一名嫌疑犯的思路可能是這樣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認罪,那自己將會得到中等懲罰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認罪,那麼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由。兩名嫌疑犯當然都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就陷入了社會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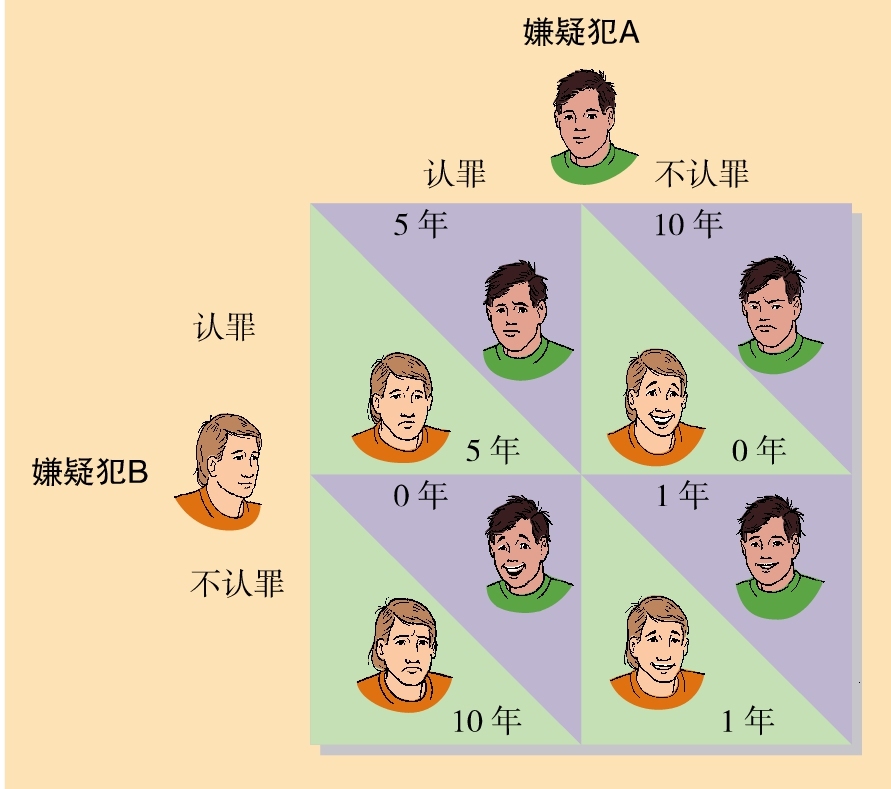
圖13-1 經典的囚徒困境
在每個格子中,斜線以上部分表示嫌疑犯A得到的處罰。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兩名嫌疑犯都認罪,他們都會被關5年;如果兩人都不認罪,那麼都被關1年;如果只有一人認罪,那麼他就會因為表現良好而被釋放,另一個倒黴鬼則要被關上10年。如果你是其中一個嫌疑犯,而且你沒法和你的同夥商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認罪嗎?
在2000個左右的研究中(Dawes,1991),大學生們被要求在類似於囚徒困境的各種情境下做出選擇,在這些實驗情境中,他們考慮的結果並不是牢獄之災,而是薯條、錢或是學分等不同的事物。如圖13-2所示,在任何一種選擇中,背叛對方總是能得到較好的結果(因為這一行為可以從對方合作的企圖中得到好處,或是防止對方背叛給自己帶來嚴重後果)。但是問題是如果雙方不合作,他們得到的結果總是比在他們互相信任併合作的情況下要壞得多。這個難題常常使人處於令人發狂的困境中,一方面雙方都知道他們都可以從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們卻無法溝通從而相信對方,所以難以脫離不合作的行為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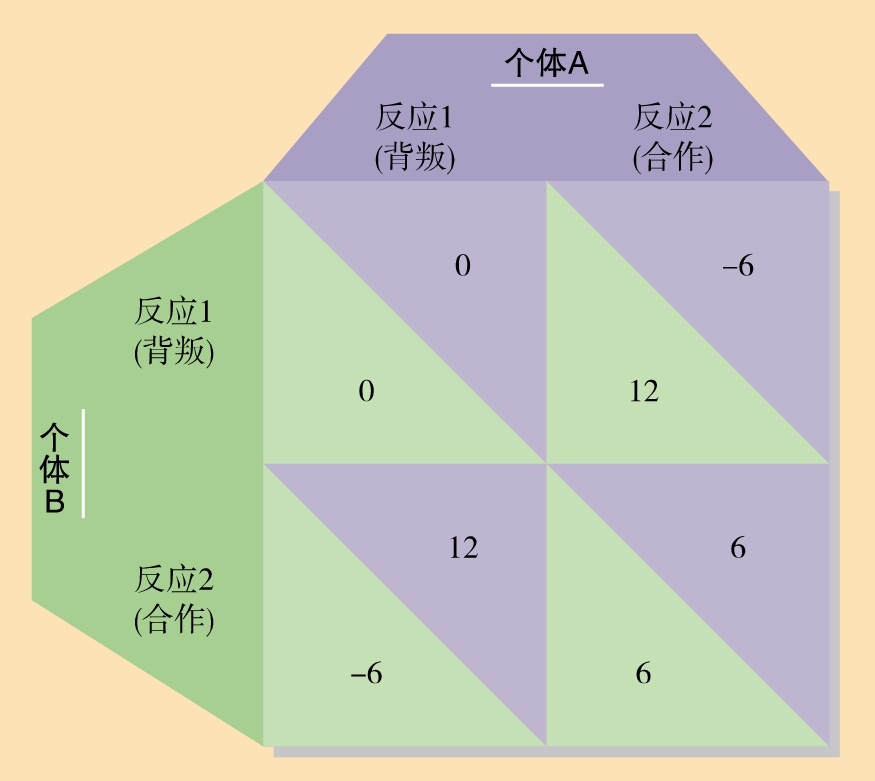
圖13-2 實驗室版的囚徒困境
表格中的數字代表了某種獎勵,比如金錢。在每一個格子中,斜線上方的數字代表了A能夠得到的獎勵數量。和經典的囚徒困境(只有一次決策)不同的是,實驗室版本可以多次進行。
在這樣的困境中,個體未經約束的追求於群體而言,可能是有害的。1945年後美國與前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也是如此。一個外星的觀察者很可能認為這個“相互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軍事政策正如這個詞組的縮寫(MAD)一樣,是瘋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哀嘆道:
每一杆槍,每一艘戰艦,每一支發射的火箭,在它們最深層的意義上,都是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人的剝削。這個武裝自己的世界花費的不僅僅是錢本身,它花費的是勞動者的汗水,是科學家的智慧,也是孩子們的希望……就我們最真實的感受來說,在戰爭陰雲的威脅下生活根本不是一種合適的方式,在這樣的生活中,人性被鐵十字碾過。
在一個國家可能對其他較弱的國家發動攻擊並獲得利益的情況下,一種恐怖威脅形成的平衡可能會防止戰爭的發生。但是無論從歷史紀錄還是我們即將看到的心理學研究中,試圖用大棒(比如核武器)威脅敵人來防止戰爭的做法都難以得到支持(Lebow & Stein,1987)。在武器裝備氾濫的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發生的戰爭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Sivard,1991)。此外,如果能夠消除武器帶來的威脅,並且能夠將軍事開銷用於生產上,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會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們獲准持有槍支以維護個人安全的國家中,整體上的安全程度往往不如那些禁止私人持槍的國家。
對囚徒困境做出這樣的分析並不難,但是國家領導人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當在實驗室中將大學生置於類似於軍備競賽的情境當中時,如果有一方單方面進行裁軍,就會使自己處於一種脆弱而容易遭到攻擊或敲詐的境地。在實驗室中,那些無條件地對其他人採取信任和合作態度的人經常使自己陷於不利的境地(Oskamp,1971;Reychler,1979;Shure & others,1965)。所以世界各國仍在不斷地把錢花費在武器上。
公共地悲劇
很多社會困境都包含了兩個或更多的利益集團。例如,全球性氣候變暖問題的根源,包括日益嚴重的濫砍濫伐,世界各地的汽車、使用油料的燃爐和火力發電廠排放的廢氣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但是每一輛汽車排放的尾氣對整個問題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一點點的危害在分攤到所有人身上之後會變得極小。為了建立能夠描述這一困境的模型,研究者們在實驗室對現實問題進行了模擬,並研究了不同類型人的行為反應。
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把這種社會困境表現出的醜惡人性比喻為公共地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這一名稱來源於舊時英格蘭鄉鎮中心的牧場,但是“公共地”在這裡包括了空氣、水、海洋中的鯨類、罐子裡的餅乾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資源。當所有人都適度地對資源進行利用時,資源自行進行再生的速度可以與資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夠生長,鯨魚能夠繁衍生息,餅乾罐也會被重新填滿。而一旦對資源的利用超過限度,公共地悲劇就會發生。
假設有100個農民佔有了一塊能夠供應100頭牛足夠牧草的草地,當每一個農民在這塊地上養一頭牛的時候,對資源的利用是最優的。但是某一個農民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多養一頭牛,我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而土地只會受到一點點影響。”因此他很有理由添加他的第二頭牛。而當所有的農民這樣想並這樣做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公共地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一片荒蕪的土地。
很多現實中的問題在本質上與上面的故事都是類似的。在對互聯網的使用中,所有人都希望在網上衝浪,並無節制地試圖提高自己的效率,他們會同時打開很多鏈接,這時網絡傳輸線中充斥著數字和圖片信息,網絡塞車也因此產生了(Huberman & Lukose,1997)。類似地,人類對環境的汙染也是由很多輕微的汙染一步步累積起來的。對每一個汙染者來說,停止汙染所能給他們(也給環境)帶來的好處,與汙染給他們帶來的方便來說仍是不值一提的。我們在保持個人居所衛生的同時,在公共場所——諸如宿舍走廊、公園、動物園等——隨地扔垃圾。我們也會為了對我們來說很直觀的利益而消耗人類的自然資源,洗一個長長的舒適的熱水澡能夠對環境產生什麼影響呢?捕鯨者知道即使他們不去捕鯨,別人也會,況且多捕幾條鯨魚對物種能造成什麼影響呢?悲劇就這樣發生了,與所有人都有密切關係的事情(比如環境保護)竟成了無人關心之事。
這種個人主義是否為美國所獨有?薩託(Kaori Sato)在1987年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不過被試來自文化更加傾向於集體主義的日本。實驗開始時,被試都支付相同數量的錢來種植一片虛擬的森林,在實驗中他們可以通過砍伐虛擬的樹木得到現金,實驗的結果與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超過一半的樹木在生長到最佳的砍伐時機之前就被搶著砍掉了。
薩託的森林讓我想起了自己家裡的餅乾罐子。如果按照局外人的看法,我們應該在重新裝滿罐子之前保證罐子不是空的,以確保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能吃兩到三塊餅乾。但是,缺乏節制和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不信任使我們禁不住要增加自己對餅乾的消費,於是每個人都一塊接一塊地填充自己。結果是24小時內餅乾就被徹底消滅了,罐子空空如也。
當一種資源未獲得明確的分配時,人們往往會不自覺地消費更多(Herlocker & others,1997)。例如當一盆土豆泥在有10個人的桌子上傳遞時,會有更多的人傾向於舀出不適當的分量;但是把土豆泥換成10只烤雞,情況就要好得多。
囚徒困境和公共地悲劇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在兩種情境下參與者都會把自己的行為動機解釋為外界的壓力(“我不得不提防被對方利用”),而且不客觀地評價對方的行為(“她很貪婪”,“他是不可靠的”)。多數人從未意識到對方看待他們時,同樣會有這樣的基本歸因偏差(Gifford & Hine,1997;Hine & Gifford,1996)。
其次,行為的動機是在變化的。在一項任務中,開始時人們的動機可能是掙些小錢,然後變成了減少自己的損失,到了最後就只是保存臉面防止徹底的失敗(Brockner & others,1982;Teger,1980)。這種動機的變化在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戰爭剛開始的時候,約翰遜總統在他的演講中常常強調戰爭是以自由、民主和正義為目標的,但是隨著衝突的升級,總統的論調便成了為了美利堅的榮譽並防止戰敗帶來恥辱而戰。
再次,現實生活中的多數衝突,就像囚徒困境或是公共地悲劇一樣是非零和博弈 (non-zero-sum games)。衝突雙方得到的利益和損失之和並不一定為零。雙方可能都贏,也可能都輸。每種情境都將個人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的回報與群體的長期利益對立起來。在面對這類令人頭疼的問題時,即使每個人都表現出了足夠的“理性”,其結果仍有可能是災難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氣層內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層並不是某個喪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劃的,而是由許多看似合理的行為造成的總體後果。
並非所有的利己行為都對集體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當時社會的描述——由於每個個人都試圖通過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也將必然使整個社會的產值達到最大。亞當·斯密通過對生產行為的觀察得出:“我們能夠得到我們的晚餐,並不是因為那些屠夫、釀酒師或是做糕點的師傅大發善心,而是因為他們關心自身的利益。”
解決社會困境
在這些使人左右為難的社會困境中,我們如何使人們願意通過合作,以提升他們共同的利益呢?一些針對兩難情境的實驗研究提供了幾種可能的途徑(Gifford & Hine,1997)。
適當的管制 哈丁(Hardin,1968)這樣總結了公共地悲劇:“當一個社會中的人們對公共資源的使用享有完全的自由時,他們便會一擁而上試圖獲得最多的好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公共地’最終必然會成為一堆廢墟。”試想:如果稅收的徵繳完全依靠人們的自覺性,那麼有多少人會交出應當交付的數目呢?很顯然對多數人來說是做不到的,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不能依靠慈善事業來支付學校、公園以及國防安全的開支。
為了保護公共資源,人們發展出了相應的法律和規範系統:國際捕鯨者協議 規定了一個使鯨魚能得到足夠繁殖機會的捕撈限制;美國與前蘇聯簽署的核武器試驗禁令,減少了空氣中的放射性物質。這類協議將環保的責任分攤至每個人頭上,沒有哪一個鋼鐵廠需要擔心其他廠家會不顧環保責任以獲得競爭優勢。
在日常生活中,管制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包括強制執行這些管制的成本,以及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這樣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便產生了:在什麼情況下,管制的成本會超出它們帶來的好處呢?
小即是美 另一種解決社會困境的方法是:縮小群體的規模。在一個較小的集體中,每個人都能更加明確地感受到自己的責任和自己對集體的影響(Kerr,1989),而當一個集體變得較大時,人們就更容易有這樣的想法——“反正我也不會起多大作用”,正是這一想法常常導致不合作(Kerr & Kaufman-Gilliland,1997)。在較小的集體中,團隊的成功也能夠給成員帶來更多的滿足感。此外,其他任何使人們團隊意識增強的因素,也會增加合作行為。甚至幾分鐘的討論,或者認為和團隊其他成員有某些相似之處的想法,都會增加集體成員的“我們感”(we feeling)和合作的可能(Brewer,1987;Orbell & others,1988)。
此外,在較小的團體中,成員對公共資源的消費也會較有節制並通常能夠維持在平均應得的水平(Allison & others,1992)。在我童年時居住的位於太平洋西北部的島嶼上,生活用水的來源是以幾戶鄰居為單位共享的蓄水池。在炎熱的夏天當蓄水池水位下降時,池上的警示燈會亮起,提醒我們15個家庭該注意節約用水了。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對於其他家庭的責任,並能感覺到我們的節約真的起了作用的時候,每個家庭都會節約。於是蓄水池從未乾涸過。
在大得多的群體中——比如說城市,自覺的節約則很少能夠成功。這是因為一個人造成的危害會被很多其他的人所分擔,因此每個人都可能不再考慮對群體的責任。因此一些政治理論專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建議,只要可行,就應當將公共資源劃分為較小的單位(Edney,1980)。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論》(Mutual Aid )上,俄羅斯革命者Pyotr Kropotkin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由小型共同體根據公共利益來決策,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出重要決策的社會體系(Gould,1988)。
溝通 人們只有通過溝通才能解決某些社會困境。在實驗室創造的情境中,實驗小組內部的交流有時會惡化成恐嚇和罵人(Deutsch & Krauss,1960)。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溝通可促成人們的合作(Bornstein & others,1988,1989)。對兩難問題的討論會增進小組成員的群體意識,並使成員們更加關注小組的整體福利。通過溝通,也使小組能夠達成一致的意見和期望,並對組內成員產生一定的服從小組內部規範的壓力。在溝通過程中,尤其是當人們面對面交流時,他們可以產生很好的合作行為(Bouas & Komorita,1996;Drolet & Morris,2000;Kerr & others,1994,1997;Pruitt,1998)。
羅賓·道斯(Dawes,1980,1994)設計了一個精巧的實驗來說明溝通對衝突解決的重要性。設想一下:在這個實驗中,你將與6個陌生人組成一個小組,你們每人會得到6美元。你們可以選擇保留這6美元或是將它捐獻出去。如果你選擇捐獻,則實驗者會將它翻倍並使其他6個人均得到2美元。別人不會知道你的選擇。因此,如果7個人都選擇捐獻,那麼每人可以得到12美元;但如果只有你選擇保留而其他人都選擇捐獻,你就能得到18美元;如果不幸只有你選擇捐獻而其他人都選擇保留,那麼你什麼也得不到。很明顯,對於群體來說,合作是最有利的行為,但是也需要個人的犧牲、信任並有一定的風險。道斯的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實驗參與者沒有進行過討論,大約只有30%的人會選擇捐獻,而在討論之後這一數字將升到80%。
開放、明確而坦誠的交流也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那些預期別人不會有合作行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會表現出任何合作的傾向(Messé & Sivacek,1979;Pruitt & Kimmel,1977)。缺乏信任之人不會與別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帶來了進一步的不信任(“我還能怎麼樣呢?這個世界就是黑吃黑”)。在實驗中,溝通減少了不信任感,使人們有可能達成使他們共同的福利得到增加的一致觀點。
改變激勵機制 當實驗者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行為能夠得到更多的強化,而自私行為能夠得到的好處變少時,人們的合作行為就會增加(Komorita & Barth,1985;Pruitt & Rubin,1986)。激勵機制的改變也有助於解決一些實際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於開私家車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現堵塞並且造成嚴重的空氣汙染。人們喜歡開私家車的原因之一是這樣比較舒適,而且每個人都認為多一輛車對交通情況和汙染只能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為了使人們的想法發生改變,許多城市對政策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對公共交通服務的激勵,包括在高速公路上開闢公交專用車道,以及降低通行稅。
倡導利他規範 在第12章中,我們已經瞭解到,增加人們對他人的責任感有助於利他行為的產生。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通過增加利他動機,促使人們更多地為公共利益著想呢?
我們從事實中得到了不同指向的證據。一方面,對非合作行為帶來的可怕後果的瞭解,並沒有對合作行為的出現產生多大的影響。在實驗室情境下,人們即使清楚他們的利己行為會帶來對整體而言非常糟糕的結果,他們仍然不會改變自己的選擇。在現實生活中,對世界末日的警告和對節約資源的呼籲,也是應者廖廖。1976年剛剛上臺的美國總統卡特提出,美國人對能源危機的態度應當與他們對戰爭的態度一樣,並強烈號召人們節約能源。在接下來的一個夏天,美國對汽油的消費比以往都要多。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人們已經認識到全球性氣候變暖正在日益嚴重——而對耗油的運動型多用途汽車的購買量也達到了歷史新高。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態度對行為的影響有時並不明顯;對很多人來說,知道 怎麼做是好的與實際的行為 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儘管如此,多數人仍能較好地遵守社會責任、互惠、公平的規範,始終承擔著個人的義務(Kerr,1992)。問題在於如何激發出他們的這種情感,一種有效的方法是通過一個有超凡魅力的、無私的領導的影響來鼓勵其他人進行合作(De Cremer,2002)。另一種方法是以合作規範來定義情境。在李·羅斯與安德魯·沃德(Ross & Ward,1996)進行的實驗中,他們請來斯坦福大學的一些宿舍管理員對他們熟悉的男學生在囚徒困境中可能出現的行為做出預測,指出他們認為哪些大學生更富於合作性,哪些更可能背叛。實際結果顯示,這兩組學生在合作行為上並沒有什麼差異。有趣的是研究者對實驗情境的不同命名對學生們的合作行為有較大影響:當實驗情境被稱為“華爾街遊戲”時,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參與者表現出合作行為;但當實驗情境被稱為“團體遊戲”時,合作者的數量增加到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二。
溝通也能促進利他規範的產生。在實驗中當允許參與者交流時,他們往往會尋求一致的社會責任規範:“如果你背叛了我們這些人,你的餘生必將一直揹負這一惡行”(Dawes & others,1977)。羅賓·道斯(1980)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和助手改變了實驗的程序。在實驗開始之前,主試先向實驗的參與者就集體的利益、自私的行為以及道德等進行佈道,這一程序能夠很好地引導參與者們的利他行為。在加入這一程序後,參與者們會更加堅定地為了集體的利益放棄個人的眼前利益(請注意在第12章中我們提到過,經常在教堂做禮拜或接受佈道的人與其他人相比,會有高得多的獻身精神和慈善之心,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
能通過類似的引導解決更高層面上的社會難題嗎?傑弗裡·斯科特·米奧和他的同事(Mio & others,1993)發現,當實驗的參與者閱讀過有關社會困境的材料後(正如你們現在所做的),他們在公共場合隨地扔垃圾的行為比起只閱讀了與競選有關的材料的參與者要少得多。此外,當合作行為很明顯可以增加公共福利時,個人就更可能表現出符合社會責任規範的行為來(Lynn & Oldenquist,1986)。例如在人們都知道使用公共交通能夠比私人交通工具節省時間的情況下,如果他們還知道公共交通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汙染,那麼他們使用公共交通的傾向就會更強(Van Vugt & others,1996)。在爭取公民權利的鬥爭中,許多領導者往往會情願為了大集體的利益而遭受折磨、拷打和牢獄之災。在戰爭時期,人們為了自己國家或民族的利益也常常會做出巨大的個人犧牲。正如溫斯頓·丘吉爾對二戰中英國軍人做出的評價,戰爭中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行為是徹底無私的:明知在每一次任務中都有大約70%的飛行員無法平安回來,他們依舊堅定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Levinson,1950)。
綜上所述,能夠減少社會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確立法規以限制利己行為;將群體分為較小的單位;讓人們能夠充分地溝通;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報;倡導利他的行為規範。
競爭
當不同的群體為稀缺的職位、住所和資源進行競爭時,敵意便產生了。當利益相牴觸時,衝突便產生了——這就是“現實群體衝突理論”所描述的現象。生存空間、工作崗位以及政治權力上的競爭也是引燃北愛爾蘭長期衝突的一些因素。從1969年起,在北愛爾蘭佔多數並具有統治地位的新教徒和佔少數的天主教徒衝突不斷,已經有超過3200人為此喪生。(這一人口比例大約與美國的515000人、英國本土的107000人、加拿大的57000人或澳大利亞的36000人相當)。
競爭加強了知覺到的差異。當一個人處於和他人競爭的情境中時,他們的態度有更大的不同(Holtz & Miller,2001)。但引發敵對性衝突的僅僅是競爭本身嗎?為了找到答案,克雷格·安德森和梅利莎·莫羅(Anderson & Morrow,1995)進行了一個實驗,在實驗中參與者們兩兩配對一起玩任天堂的超級馬利兄弟遊戲。一半被試玩的是競賽模式(比較兩人的得分),另一半玩的是合作模式(最後將兩人分數相加得總分)。實驗結果顯示,在競爭模式下,遊戲者會更加經常而不必要地殺死一些遊戲中的動物(通過腳踩或發射火球),比合作模式下游戲者這種行為的總數要多出61%。因此,競爭會引發較多的攻擊行為。
那麼在現實的情境下,競爭是否也會誘發更多的破壞性行為呢?為了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隨機地將一些人分為兩組並讓他們為某種稀缺的資源而競爭,然後觀察他們在競爭中體現出的行為模式。謝里夫(Sherif,1966)和他的同事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以一群典型的11~12歲的男孩為被試進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實驗。這一實驗的靈感,來源於謝里夫對1919年目睹希臘軍隊入侵他的家鄉土耳其的回憶。
他們開始四處殺人。(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並使我開始對人類為何會有這樣的行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或者任何別的專業手段,來理解群體之間野蠻行為的產生(quoted by Aron & Aron,1989,p.131)。
在研究了野蠻行為的社會根源之後,謝里夫將可能的要素用於幾個為期三週的夏令營活動中。在其中一個研究中,謝里夫將22名來自俄克拉荷馬的普通男孩分成了兩組,並將他們用巴士分別運到了不同的童子軍營地。兩個童子軍營地均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山賊洞州立公園,相距半英里。在活動的第一週,兩組童子軍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通過準備食物、紮營、修建游泳池和建立繩橋等活動,兩組童子軍內部分別形成了比較親密的關係,並且給自己的小組起了名字:“響尾蛇”和“老鷹”。為了表達對童子軍生活的滿意,其中一間小木屋上還寫上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
當團體的認同感確立之後,兩個小組也將進入衝突的產生期。在第一週即將結束的時候,響尾蛇組成員“發現老鷹組的成員出現在‘我們’的棒球場上。”此後,夏令營活動的組織者在兩組童軍間開展了一系列競爭性的活動(包括棒球比賽、拔河、營地內務檢查、尋寶等),兩個小組對這些活動均顯示了很高的熱情。在遊戲中兩組必須分出輸贏,所有的優待(獎章、小刀之類的獎品)都屬於勝利一方。
結果如何呢?整個營地逐漸進入了公開的戰爭狀態,一切就像威廉·戈爾丁的小說《蠅王》中描寫的場景——在荒島上野營的男孩之間的社會瓦解。在謝里夫的研究中,衝突是從比賽過程中雙方對罵開始的,然後迅速升級為餐廳內的“垃圾大戰”,燒燬對方的旗幟,對對方營地進行搶掠甚至互毆等嚴重的爭鬥行為。當被要求對另一個小組進行描述時,男孩們使用的形容詞包括:“卑鄙的”、“自作聰明的”和“臭鬼”,而在評價自己的組員時使用的則是:“勇敢的”、“堅強的”和“友好的”。[鮮為人知的事實:謝里夫怎麼能夠自然地觀察到孩子的行為,而不會抑制孩子的行為呢?答案就是謝里夫擔任了營地的維護者 (Williams,2002)。]
分勝負的競爭活動帶來了激烈的衝突,對別組成員的歧視,在組內強烈的團結意識和集體榮譽感。群體極化也加劇了衝突。根據實驗觀察,在鼓勵競爭的環境中群體總會表現出比個人更多的競爭性行為(Wildschut & others,2003)。
兩組之間沒有任何文化、體質或是經濟上的差異,而且在與他們相熟的人眼中都是溫和可愛的“社會未來的希望”,但還是發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謝里夫提到,如果我們此時來到這個營地,我們會認為這些男孩是“一幫邪惡、自私而貪婪的混小子”(1966,p.85)。事實上,他們的邪惡是被邪惡的環境誘發的。後來的研究表明,尤其在(a)人們知覺到諸如金錢、工作崗位和權力這些資源是有限的,並且是零和的(一個人的獲得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損失),(b)一個明顯的外團體成為潛在的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更易於引發衝突(Esses & others,2004)。因此,那些把移民看成是他們工作的競爭者的人,更傾向於對移民者和移民制度持否定態度。
幸運的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謝里夫不但將陌生人變成了敵人,他在最後又將敵人變成了朋友。
知覺到的不公正
“不公平!”“多麼卑劣啊!”“我們應該得到更多的!”類似的話語代表了由於覺察到不公正而產生的衝突。但什麼才是“公正”(justice)呢?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理論,人們將公正理解為公平(equity)——或者說是付出與獲得之間要成比例(Walster & others,1978)。如果你和我有某種關係(例如僱主—僱員、老師—學生、丈夫—妻子或是同事關係等),當我們的付出和所得滿足下列等式時,我們之間是公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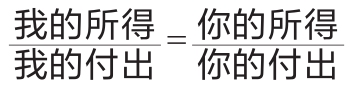
如果你的貢獻比我要大而獲得的收益卻沒有我多,你就會感到不滿和惱火;而我可能覺得冒犯了你並感到內疚,不過你可能比我對不公平更加敏感(Greenberg,1986;Messick & Sentis,1979)。在實驗中我們看到,人們通常不會主動要求對自己或自己所在團體給予優待,但是讓他們接受更多的好處時,他們是絕對會欣然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的(Diekmann & others,1997)。拉提沙不會要求超出平均水平的獎金,但是如果有人做出利於她的決定的話,她會很容易地證明這是正當的。
我們也許會同意用公平原則來定義公正,但對我們的社會關係是否公平卻往往不能達成一致。對於一家公司中的兩個職員來說,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紀較大的一個可能會希望按照資歷來安排工資水平,而年紀較輕的則會希望按照產出評價績效。當出現這樣的分歧時,誰的意見會勝出呢?事實上,在多數情況下,有較強社會影響力的人會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別人相信,他們獲得的就是他們應得的(Mikula,1984)。這一現象被稱為“黃金定律”:總是由擁有黃金的人來制定規則。
佔了便宜的小組會有一種集體負罪感,就如同個人在獲得自己不該得到的東西時會有負疚感一樣。為了公平,這種集體負罪感會引發道歉或是提供補償(Mallet & Swim,2003)。然而,這些自利者也可以通過貶低他人的付出來緩解自己的罪惡感。正如我們在第9章中提到的,有的罪犯會對被害者進行指責,從而維持他對公正世界的信念。
那麼那些利益受損害者是如何迴應的呢?伊萊恩·哈特菲爾德等人(Hatfield,Walster,& Berscheid,1978)發現了三種可能性。他們可能接受並認同自己較低的地位(“我們窮,但是我們很快樂”)。他們可能會尋求補償,例如騷擾、為難或者欺騙那些侵害了他們的人。如果上述兩種可能都沒有實現,他們可能會嘗試通過報復來獲得心理平衡。
從公平理論中能推出一個有趣的結論——這個結論也在實驗中得到了證明——當一個人越是感覺自己有較高的能力和價值時(他們對自己的投入評價越高),他就會越容易感到懷才不遇並意圖報復(Ross & others,1971)。對社會強烈不滿者大都是受過教育、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比實際所得更多的那些人。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從事專業性工作的機會顯著增加了。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認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更加嚴重了(表13-1)。於公平理論者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女性只和其他女性比較自己得到的機會和掙得的錢,她們一般會感到比較滿意,正如她們常常分擔更多的家務一樣(Jackson,1989;Major,1989,1993)。當女性更為經常地視自己與男性平等時,她們的相對剝奪感就會增強(Desmarais & Curtis,2001)。如果我們認為祕書工作與開卡車具有“相同的價值”(對技術有類似的要求),那麼這兩樣工作也應當得到相當的報酬;提倡男女平等的人們認為,這樣才算公平(Lowe & Wittig,1989)。
表13-1 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人們對性別歧視的知覺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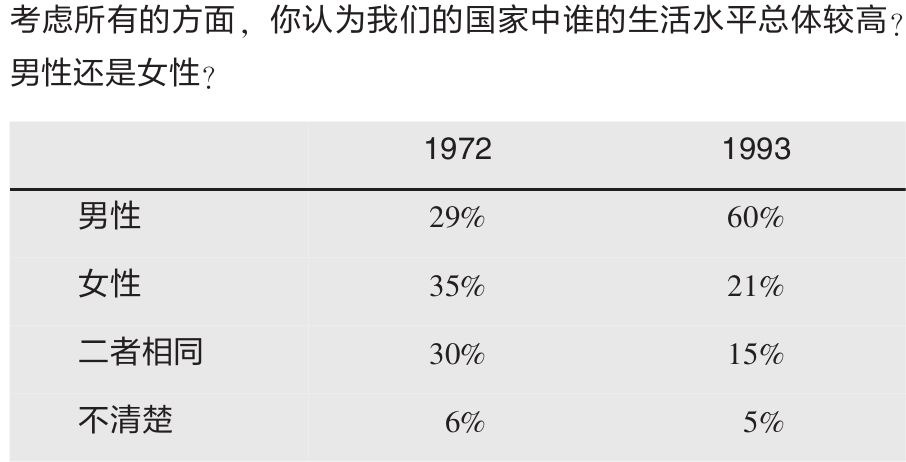
資料來源: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7.
批評者認為公平並不是公正惟一的定義。(你能想到另一個嗎?)愛德華·桑普森(Edward Sampson)認為,公平理論的倡導者錯誤地以為指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原則具有普適性。事實上,一些非資本主義國家並不認為公正就是公平,而是將公正看做平均或按需分配:“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卡爾·馬克思)。當利益在同一團體內部進行分配時,來自集體主義文化背景(如中國和印度)的人們,比來自個人主義文化背景的美國人,會更多地按照平等性或是各人的需要進行分配(Hui & others,1991;Leung & Bond,1984;Murphy-Berman & others,1984)。
在崇尚集體主義並尊重老年人的日本,工資水平常常與資歷而不是績效有更密切的關係(Kitayama & Markus,2000)。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多達53%的被調查者認為工資水平應當與工作業績有關,而在英國和西班牙,相應的比例則只有32%和26%。那麼政府是否需要減少收入差異或設定最低工資呢?有39%的美國人、48%的加拿大人和65%的英國人持贊成態度(Brown,1995)。由此可見,即使在個人主義的文化背景下,人們有時也會用公平以外的其他標準來定義公正(Deutsch,1985)。那麼,在家庭或是一個利他性的情境下,人們會考慮按需分配;在朋友關係中,可能是平均分配;而在完全競爭型的關係中,則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那麼把公正定義為公平這種傾向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報酬應該 基於什麼標準進行分配呢?按價值?平均分配?按需分配?還是把這些方式結合起來?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請我們設想這樣一個未來,我們所有人都不清楚自己在社會經濟階梯中處於哪個階層,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公正標準?格雷戈裡·米切爾和他的同事(Mitchell & others,1993)報告了美國大學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們希望一部分報酬是基於績效進行分配,同時也有學生認為如果自己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會優先選擇平均分配來滿足他們的需要。
誤解
在本章開頭的時候我們提到,衝突是被知覺到的 行為或目標的不相容。實際上,很多衝突中真正對立的目標只是核心處的一小部分;更大的問題來自對對方動機和目標的誤解。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老鷹組和響尾蛇組的男孩們確實有一些相互對立的目標,但是他們對對方的誤解在主觀上誇大了他們的差異(圖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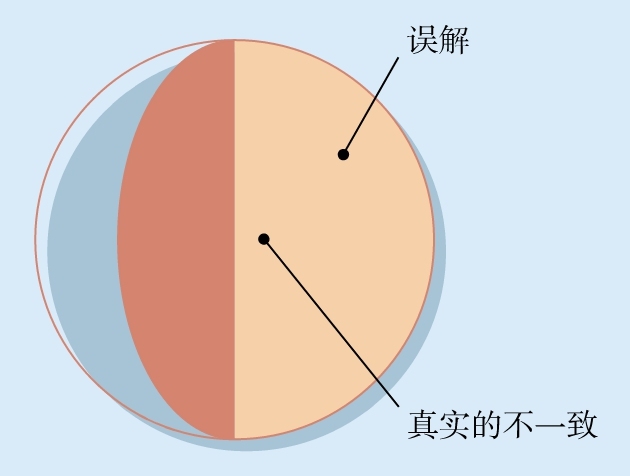
圖13-3
多數衝突中只有核心的一小部分來自真正的矛盾,外面包裹著的則是各種各樣的誤解。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討論過引起類似誤解的原因。自我服務偏見 會使個人或群體樂於承認自己做的好事,而對自己做的壞事卻推卸責任,同時並不會考慮對方的類似行為方式。當無法擺脫自己的醜惡行徑時,自我合理化 的傾向進一步使人們向否認錯誤傾斜。由於基本歸因偏差 ,衝突中的雙方都認為對方的敵意行為反映了他們邪惡的品質,然後他們將會按照自己的成見過濾並理解得到的信息。而在一個群體中,利己、合理化和偏見都會得到極化。群體思維 的一個表現就是將自己所屬的群體描述為高尚而強大的,並將對立的群體描述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數人認為是殘酷暴行的恐怖主義行為在一些人眼中卻是“聖戰”。事實上,僅僅是成為一個群體的成員,就會使人產生群體偏見 ,而負面的刻板印象 一旦形成,就很難被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明確肯定,在衝突的雙方眼中,對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儘管這種誤解很容易被我們理解,但它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行為。無論你居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難道你們國家發動的最近的一次戰爭不是披著道德的外衣嗎?難道在戰爭發動前沒有極力醜化敵人嗎?然後人民接受了政府的藉口並集結在它的旗下。社會心理學家艾爾文·斯托布和丹尼爾·巴塔爾(Ervin Staub & Daniel Bar-Tal)認為,一個處於難以處理的衝突中的群體具有如下幾個特徵:
把自己的目標看做是最重要的。
為“我們”感到驕傲,而極度貶低“他們 ”。
堅信自己是受到損害的。
強調對集體的熱愛、團結,和對集體利益的忠誠。
表揚自我犧牲,並壓制批評。
雖然衝突的一方可能更有理些,但問題在於敵人的臉譜是很容易預見的,甚至更有趣的是,連誤解的類型都是可以預見的。
鏡像知覺
在衝突中,雙方對對方的誤解常常具有令人吃驚的一致性,他們都會美化自己和醜化對方。當1960年美國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er)到前蘇聯對很多普通的蘇聯公民進行訪談時,他吃驚地發現:蘇聯人對美國人的描述,與美國人對蘇聯人的印象驚人地一致。在蘇聯人眼中,美國政府在軍事上具有很強的侵略性,它蠱惑並剝削美國的民眾,而且在外交上美國從來不可信賴。“我們慢慢而痛苦地發現,蘇聯人對美國人歪曲的印象與我們對他們的印象具有奇怪的一致性,二者正如鏡像一般。”
根據心理學家(Tobin & Eagles,1992;White,1984)和政治學家(Jervis,1985)的研究,美蘇之間類似鏡像的偏見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任何一方來說,同樣的舉動(潛艇出現在對方的海域;向小國出售武器等)由對方完成時,看起來更具敵意。
這種鏡像知覺也推動了軍備競賽。如果我們能夠相信政治聲明的話我們將會發現,對兩個國家來說:(1)比起其他任何情況來說,它們都更加希望雙方都能夠解除武裝;(2)當另一方具有強大武裝時,絕對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裝;(3)認為對方會試圖實現軍事上的霸主地位(Plous,1985,1993;表13-2)。因此兩個國家在聲稱自己希望解除武裝的同時,都感到不得不把自己武裝起來。
表13-2 導致軍備競賽的鏡像知覺前提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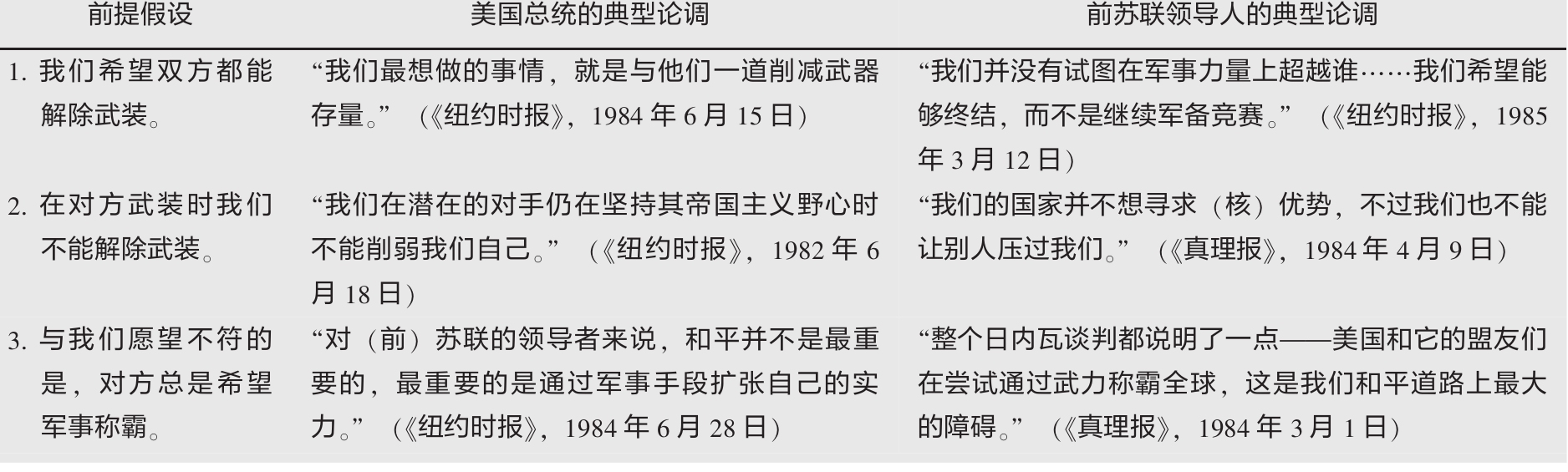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Scott Plous(1985,1993).
當雙方知覺到衝突時,至少有一方對另一方存在誤解。當出現這樣的誤解時,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就後果的嚴重性而言,這一心理現象是無與倫比的……因為這種印象的特點就是,它們可以自我證實(self-confirming)。”也就是說當A認為B對他有敵意時,那麼A就會以充滿敵意的方式對待B,那麼A的期望就得到了證實,因此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莫頓·多伊奇(Morton Deutsch)解釋道:
你從小道消息中聽說你的一個朋友在說你的壞話,儘管這個消息是錯的但是你相信了,於是你開始反擊——侮辱這位實際上是無辜的人,他當然不能忍受於是也回擊了,而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類似地,東西方的政治家總會沉浸在對戰爭威脅的擔憂中,並認為對方會試圖通過軍事稱霸,因此他們採取了不斷加深對方誤解的行動。
負面的鏡像知覺 (mirror-image perceptions)在很多地方都成了通往和平的障礙:
阿以衝突的雙方都堅持認為,“我們”進行軍事活動的動機,是保衛自己的人身和領土安全;而“他們”的意圖,則是將我們消滅並奪取我們的土地;“我們”是這裡的原住民而“他們”是侵略者;“我們”是受害者,“他們”則是侵犯者(Heradstveit,1979;Rouhana & Bar-Tal,1998)。在這樣極端不信任的情況下,進行和平談判顯然是一件困難的事。
在北愛爾蘭的阿爾斯特大學,亨特(J. A. Hunter)和他的同事(1991)給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學生播放了兩段錄像,錄像的內容分別是一群新教徒對一場天主教葬禮的襲擊和天主教徒對新教徒葬禮的襲擊。多數學生在觀看錄像後認為,與自己持相反信仰的攻擊者的攻擊動機顯示了他們嗜血的本性,而與自己信仰相同的攻擊者則不過是為了自衛或者還擊而已。
美國和伊拉克在備戰時期,雙方在談到對方時多次使用“邪惡的”這種說法。在喬治·布什看來,薩達姆·侯賽因就是一個“殺人的暴君”和“瘋子”,他擁有威脅世界和平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伊拉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才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一群瘋子,他們只是貪婪地想獲得中東的石油”(Zajonc,2003)。
津巴多(Zimbardo,2004)指出,這種衝突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即好人(像美國人)和壞人(比如“他們”)之間的衝突。衝突中對立的雙方常常誇大這種差異(Sherman,Nelson,& Ross,2003)。在墮胎、移民和其他一些議題上,並不是像對手想像的那樣,支持者就是那麼激進的,而反對者就是那麼保守的。對他人想法的理解有助於衝突的解決,但並非易事。羅伯特·賴特(Robert Wright)指出,“如果一個人做了一件你很討厭的事情,而讓你站在他的立場去思考,這無疑是道德訓練中最難的一課了。”
具有破壞性作用的鏡像知覺在較小的團體或個人之間也有所體現。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博弈遊戲中,雙方都會有這樣的反應:“我們想合作,但對方的拒絕態度使我們也不得不採取自我保護的策略。”在對經理人的研究中,肯尼斯·托馬斯和路易斯·龐迪(Thomas & Pondy,1977)發現了這樣一種歸因的傾向。當被要求回憶最近遇到的一次較嚴重的衝突時,只有大約12%的人認為衝突的另一方具有合作的意願;而74%的人認為自己是願意合作的。在解釋衝突發生的原因時,這些經理人認為,自己在交流時採取的是“建議”、“暗示”和“勸告”的方式,而對手的態度則總是“提出要求”、“認為自己的意見一無是處”或是“拒絕合作”。
激化衝突的另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是,認為儘管對方的領導階級是邪惡的,但是他們控制和操縱著的民眾則是支持我們的,這種“領導邪惡—民眾善良論”明確地體現在美蘇冷戰的雙方身上。在越戰之前,幾乎整個美國都相信,美軍士兵一進入這塊被越共“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區,就將有大批被壓迫的民眾揭竿而起加入戰鬥,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痴人說夢。2003年,美國開始了對伊拉克的戰爭,他們以為“存在大量的地下組織會支持聯軍,幫助他們建立安全和法律體系”(Phillips,2003)。哎,地下組織沒出現,戰後的安全真空倒是使搶劫、破壞和對美國士兵的襲擊不斷。
鏡像知覺的另一種形式是誇大雙方的分歧。在諸如墮胎、死刑或政府預算削減這些問題上有分歧的人們一般很難覺察到,他們的分歧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嚴重,實際上雙方往往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將對方的觀點極端化了。雙方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完全依據事實說話的,而對方的觀點則是對實際情況不負責任的主觀臆斷(Keltner & Robinson,1996;Robinson & others,1995)。這類對雙方分歧的誇大有時會導致文明間的戰爭。
簡單化思維
當形勢緊張時,正如在國際危機中發生的那樣,理智的思考變得非常困難(Janis,1998)。對敵人的看法變得更加簡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現憑經驗式(seat-of-the-pants)的判斷。卡內瓦萊和普羅布斯特(Carnevale & Probst,1998)進行的實驗研究表明,即使是對衝突的預期都會固化人們的思維,阻礙他們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對俄羅斯和美國在1945年後的政治語言的複雜性進行分析之後,發現了非常僵化的思維方式。在柏林封鎖、朝鮮戰爭和蘇軍入侵阿富汗期間,政治聲明被簡單化為刻板的、非好即壞的措辭。在其他時期,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之後(圖13-4),政治用語公開承認每個國家的動機都是複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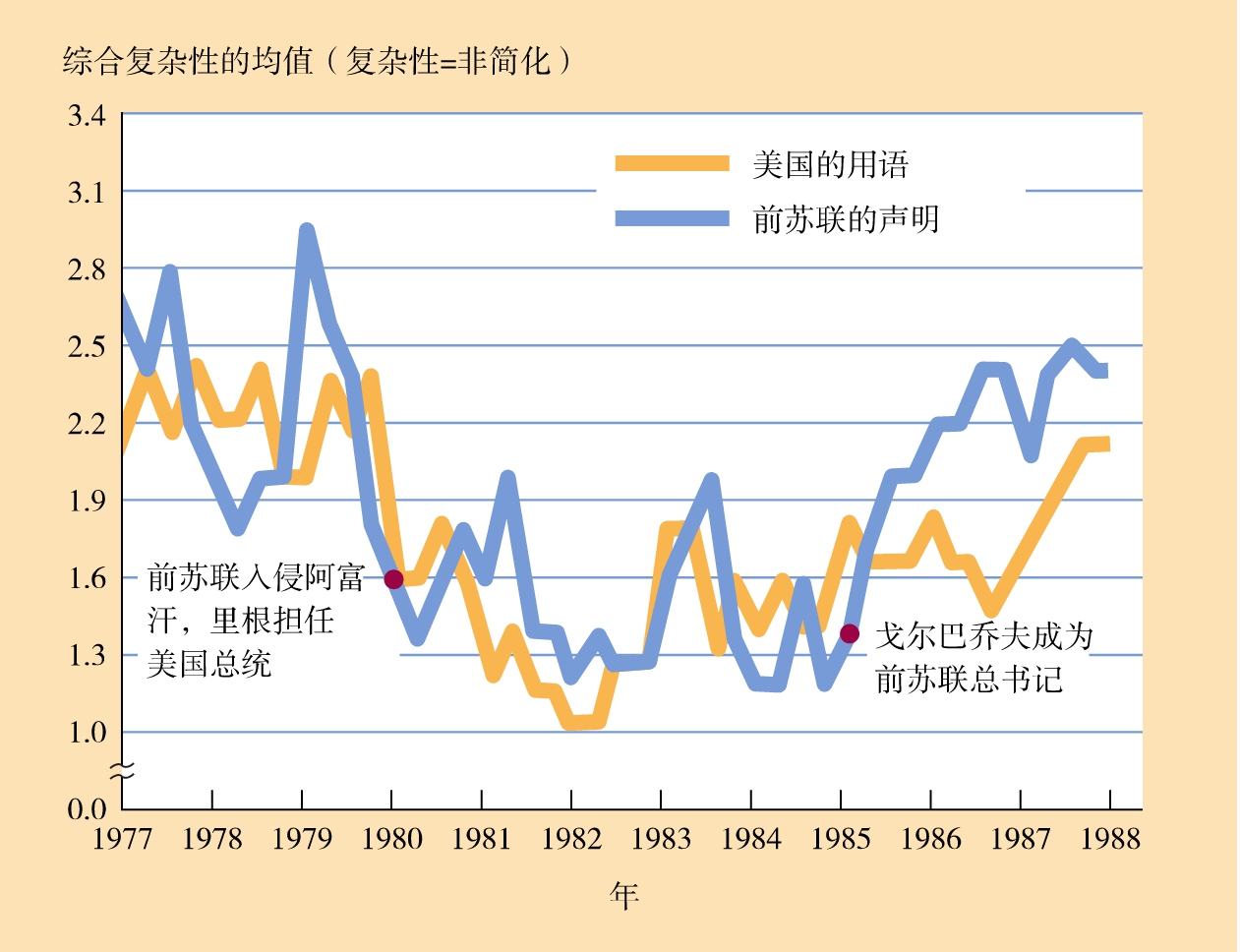
圖13-4 美國和前蘇聯官員的政治用語的複雜性
資料來源:From Tetlock,1988.
研究者還分析了在大戰爆發、軍事突襲、中東衝突和革命前的政治語言(Conway & others,2001)。幾乎在所有的事件中,那些發起攻擊的領導者就在他們開始攻擊行動前,都會顯示出愈加簡化的思維方式——我們是好的而他們是壞的。泰特洛克認為,擺脫這種簡單化思維,將使美俄達成新的一致。他的樂觀主義在後來得到驗證,1988年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莫斯科並簽署了美俄中程核武器(INF)條約,隨後戈爾巴喬夫訪問了紐約,並向聯合國聲明俄羅斯將從東歐撤走50萬軍隊:
我相信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我們能夠實現這些願望,使戰爭、地區衝突與對峙、對自然的掠奪、對飢餓和貧窮的恐懼以及政治恐怖主義都成為歷史。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而且只有我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這一切。
知覺轉換
如果說誤解與衝突總是一同出現,那麼隨著衝突程度的起伏變化,誤解也會不斷出現和消失。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而且有著極強的規律性。當一股勢力成為敵人時,我們會將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敵為友之後它的形象也會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二戰中美國民眾和傳媒眼中“嗜血、殘暴、奸詐、長著兔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戰後迅速變成了美國媒體和人民心目中“聰明、勤勞、自律而足智多謀的盟友”(Gallup,1972)。
德國人,他們因為世界大戰的緣故兩次成為全世界人民憎恨的對象,又兩次重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對他們的民族性中是否包含了殘酷已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而儘管伊拉克使用了化學武器並在國內展開對庫爾德人的大屠殺,它對伊朗的戰爭仍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不過是由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當兩伊戰爭之後伊拉克開始侵略重要產油國科威特時,它的行為立刻成為了“野蠻的行徑”。由此可見,觀念變化的速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在衝突之中誤解的嚴重程度讓我們感到心寒:一個既不瘋狂也不邪惡的人,在衝突中可以很容易地產生對對方的歪曲印象。在與另一國家、另一個群體甚至是與室友或家長的衝突中,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動機和行為誤解為完全的正確,而將對方的行為理解成徹頭徹尾的邪惡,同時我們的對手也會對我們形成鏡像式的誤解。
因此,在受困於社會難題、為了稀缺資源而競爭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時候,我們只有同時拋開偏見並努力解決確實存在的分歧,才能使衝突結束。一個好的建議是,在衝突中不要認為別人與你在價值觀與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進行換位思考,設想一下:也許對方會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理解這個問題。
小結
當兩個人、兩個群體或是兩個國家交往時,他們就可能因為需要或某個目標產生衝突。當人們將個人的利益看得比集體的利益更重要時,很多社會困境就會出現,囚徒困境和公共地悲劇很好地詮釋了這種個人與集體利益間難以抉擇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正如在實驗中那樣,我們的解決辦法包括:通過制定法律規則限制利己行為,通過劃分較小的社會群體使人們有更多責任感,通過增進交流減少不信任感,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行為能得到更多回報,以及倡導利他的行為規範。
當人們為了某種稀缺資源而競爭時,人際關係也常常陷入偏見和敵意。在謝里夫著名的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非贏即輸式的競爭使陌生人迅速成為了敵人,即使對那些正常而優秀的男孩,都會引發徹底的爭鬥。
當人們認為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衝突常常會爆發。根據公平理論,人們以付出和獲得的均衡來定義公正,當人們認為他們的付出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時,他們就會感到不公正,併產生衝突。
在衝突中,雙方真正在目標或行為上的對立只是衝突的一小部分,不過由於對對方動機或目標的誤解,使衝突往往顯得更加嚴重。此外,群體的衝突中雙方常常會產生鏡像知覺,即雙方都相信“我們愛好和平,而他們則具有侵略性。”在這種誤解之下產生的行為,往往會強化原有的誤解。而在國際性的衝突當中,“領導邪惡—民眾善良”也是一種常常被信以為真的假象。
怎樣獲得和平
儘管那些有害的力量會導致毀滅性的衝突,我們卻可以藉助其他的力量把衝突引向具有建設性的解決途徑。這些能夠帶來和平與調解的因素是什麼呢?
我們已經瞭解了衝突是怎樣由社會困境、激烈的競爭、知覺到的不公正以及誤解引起的。儘管這種圖景看來頗為殘酷,卻不是絕沒有希望得到解決的。我們可以把敵意轉變為友誼,把握緊的拳頭變成張開的雙臂。社會心理學家在幫助人們“化敵為友”的策略上有四個建議,我們可以把它們記成“和解的四C”:接觸(contact)、合作(cooperation)、溝通(communication)、調和(conciliation)。
接觸
能不能把兩個互相沖突的個人或者團隊放在一起,進行近距離的接觸,以使得他們互相瞭解彼此並喜歡上彼此呢?在第3章中,我們已經看到負面的期待是如何影響判斷和產生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些似乎都告訴我們這樣做是不可能的。當緊張開始升級,接觸可能會導致打鬥。
但是,在第11章中,我們也瞭解到接近性——以及互動、對互動的預期和曝光效應——都能夠增加喜愛的程度。在第4章中,我們還學習到了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頒佈之後,對種族的偏見怎樣大幅度地減少了,這表明“行為決定態度”。如果這個社會心理學理論現在看來是順理成章的話,請記住:一旦你瞭解了事件,那麼它們看起來就是那樣。1986年對於美國最高法院來說,決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廢除種族隔離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對於不同種族的態度。那麼在那個時期看起來最明顯的事情就是:“立法對於消除種族歧視無濟於事”。
在美國,近30年來,種族隔離和歧視已經一併漸漸消亡。這是不是因為種族間的接觸改善了人們的態度呢?那些經歷過“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人是否受到了該制度的影響呢?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是否改善了對少數民族的態度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學校裡產生了明顯的好處,比如使得更多的黑人進入大學並在學校取得成功(Stephan,1988)。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學校、鄰里、工作場所是否都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呢?這方面的證據是模糊的。
一方面,二戰結束後頒佈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這期間和之後不久進行的研究表明,白人對黑人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善。不論是百貨公司的職員、顧客、店主、政府工作人員、警察、鄰居或者學生,種族接觸都使得歧視減少了(Amir,1969;Pettigrew,1969)。比如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美國的軍方部分地解除了一些來複槍製造公司中的種族隔離制度(Souffer & others,1949)。當這些被問及對於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看法時,在有種族隔離的公司中的11%的白人士兵表示支持這個法案,而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公司中,60%的白人士兵支持該法案。
莫頓·多伊奇和瑪麗·柯林斯(Deutsch & Collins,1951)利用一個預定的自然實驗,觀察到了相同的結果。根據本州法律,紐約廢除了公眾按種族居住的方案,把家庭不按種族分配到各個公寓。而河對岸的內瓦克(Newark)也經歷了同樣的進程,白人和黑人最初分別住在不同的住宅裡面。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地區,白人婦女更加支持不同民族的混居,並且說他們對黑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善。被誇大的刻板印象在事實面前臣服了,就像其中一個婦女說的:“我真的變得喜歡這種制度了,我發現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在非種族領域中,接觸也能預期寬容的態度。琳達·特羅普和托馬斯·佩蒂·格魯(Linda Tropp & Thomas Pettigrew,待發表)收集了515個研究的數據,這些研究是對38個不同國家或民族的250513人進行的。他們對這些數據進行了艱苦而完整的分析,最後得出,94%的研究表明,增加接觸能夠預測偏見的減少 。邁爾斯·休斯頓(Hewstone,2003)指出,這種相關不僅存在於種族間的接觸,還存在於和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戀者以及殘疾兒童的接觸。
上述的這些研究結果使得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在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決定,並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的公民權利運動(Pettigrew,1986)。但是後來對學校的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效應的研究卻變得不是那麼令人振奮了。沃爾特·斯蒂芬(Stephan,1986)在對所有此類研究進行回顧後,得出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對於種族觀念的改變幾乎沒有作用”的結論。對於黑人來說,廢除學校種族隔離最明顯的結果是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能夠進入聯合大學(或者主要是白人的大學),住在種族混合的居民區,同時在種族混合的地方工作。
很多國際學生交流項目同樣不能使學生對居住國的印象產生所預期的積極影響。比如,當一個上進的美國學生來到法國學習時,他通常仍然跟其他的美國人住在一起,因此他們對法國的刻板印象並沒有得到改善(Stroebe & others,1988)。同樣,接觸也不能減少盧旺達的圖西人被他們的胡圖人鄰居嫌惡的情況,頻繁的接觸也並未減少很多男性的性別歧視。通常人們很容易去歧視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同性戀者或者移民,但是他們也會輕視那些他們經常見到的人。
所以,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有時能夠改善對少數民族的態度,而有時則不能。這種不一致的情況激起了科學家的探索熱情。如何解釋這種差異呢?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提到了各種各樣的廢除種族隔離的做法。真正地廢除種族隔離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實行。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何時能夠改善種族態度
種族間接觸頻率會是一個因素嗎?看起來的確如此。很多研究者調查了數十個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並觀察了那些和他們一起吃飯、談話和遊戲的特定種族的兒童。種族的不同影響了孩子之間的接觸。白人孩子更願意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則和黑人在一起(Schofield,1982,1986)。在一個夏日(12月30日)的午後,約翰·狄克遜和凱文·多爾漢姆(Dixon & Durrheim,2003)對在南非一個廢除種族隔離的海灘上散步的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進行觀察時,發現種族隔離的情況也是很明顯的(圖13-5)。促進交流的努力有時會奏效,有時則無濟於事。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年輕人在和北愛爾蘭的學校進行交換學習後解釋道:“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一些新教的學校。因為你知道,現在有些學校好像是混合性的,但實際上很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並不是我們不想,只是真的覺得很尷尬”(Cairns & Hewstone,2002)。

圖13-5 廢除種族隔離並不意味著接觸
在廢除種族隔離之後,南非的斯科特堡海灘成為“開放的”,但黑人(圖中的紅色圓點)、白人(藍色圓點)和印第安人(黃色圓點)還是傾向於和他們自己種族的人們聚集在一起。
資料來源:From Dixon & Durrheim,2003.
友誼 相對來講,早期的那些對於商店店員、士兵和安居計劃的鄰里關係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結果,是因為有大量的種族之間的接觸,使得那種由於最初的不同種族的接觸產生的焦慮得到緩解。另一些研究涉及到長期的、個人之間的接觸——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監獄,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參加的夏令營——得到了同樣好的結果(Clore & others,1978;Foley,1976)。那些曾經在德國或者英國留過學的美國學生中,跟當地的人民接觸越多,對他們的印象也就越好(Stangor & others,1996)。在一些實驗中,那些和其他群體的人建立了友誼的人,往往容易對這些群體產生積極的態度(Pettigrew,2000;Wright & others,1997)。並不僅僅是由於對他人的瞭解,還有情感 紐帶形成了親密的友誼並降低了焦慮(Hewstone,2003;Pettigrew & Tropp,2000)。
然而,“群體突顯”(group salience)也會起作用。如果你總是把你的朋友看成是單一的個體,你對他的情感紐帶也不會推廣到你朋友所在群體的其他成員身上(Miller,2002)。因此很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突破群體界限的相互信任的友誼,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們的朋友能夠代表他所在的群體,他們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弱化了他們的外群體身份——認為他們在本質上和我們是一樣的,而不是覺得他們的不同會威脅到我們,那麼我們就更可能友好相待。如果我們能將自己對新朋友的喜歡擴大到對他人身上,那麼他們的群體特性也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突顯。因此,為了減少偏見和衝突,我們最好一開始就將群體差異最小化,然後承認這種差異,最終跨越這種差異。
一項針對4萬歐洲人的調查顯示,友誼關係是成功接觸的關鍵:如果你有一個少數群體的朋友,那麼你就更有可能對這一群體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會更為支持他們移民到你的國家。無論是西德人對土耳其人的態度,還是法國人對亞洲和北非人,或者是荷蘭人對蘇里南人以及土耳其人,英國人對西印度和亞洲人的態度都是如此(Brown & others,1999;Hamberger & Hewstone,1997;Pettigrew,1997)。同樣,對同性戀的厭惡情緒也會由於自己有一個同性戀的朋友而減少(Herek,1993)。另外還有一些針對人們對於老人、精神病人、艾滋病人以及殘疾人的態度的研究,發現態度也會因為經常的接觸而得到改善。
地位平等的接觸 那些支持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社會心理學家,也並不認為所有類型的接觸都能夠改善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他們認為,如果接觸是競爭性的,或沒有權威機構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麼結果必然是惡化的(Pettigrew,1988;Stephan,1987)。在1954年以前,很多持偏見的白人經常和一些黑人接觸——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僕人等。但就像第9章中指出的那樣,這種不平等的接觸只能讓那些白人繼續認為白人和黑人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觸必須是雙方地位平等的接觸 (equal-status contact)才是有效的,比如在商店店員、士兵、鄰居、囚犯或者夏令營參與者之間。
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中,學生之間的接觸往往是不平等的。白人學生往往更加活躍,更有影響力,更成功(Cohen,1980a;Riordan & Ruggiero,1980)。當一個7年級的黑人女孩從一個較差的學校轉到一個以中產階級白人的孩子為主的高中班級,同時她的白人中產階級教師也有點看不起她時,她的同學包括她自己都會認為她是一個比較差的學生。
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們(Gurin & others,2002)從一項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得到,在高等院校或是綜合大學裡,種族多樣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內互動對所有的學生都是有益的。這樣的互相接觸能夠促進智力的提高,並培養出對差異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從而達到各社會單元的融合——這一結果推動了美國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決議——種族多樣化是高等教育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而且可以作為招生的一個標準。
合作
儘管地位平等的接觸有助於改善態度,但有時這還是不夠的。謝里夫在他的夏令營實驗中阻止了“老鷹”和“響尾蛇”之間的競爭,讓這兩個團體進行一些非競爭的活動,比如看電影、放焰火和吃飯等——但是這些行動卻並沒有帶來效果。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敵意非常強烈,簡單的接觸只能給他們提供一個互相嘲弄和攻擊的機會而已。當“老鷹”隊中的一個成員被一個“響尾蛇”隊員弄傷後,他的夥伴會鼓動他去雪恥。顯然,在這兩個團體之間消除隔離基本無法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敵意,那麼該怎麼做才能達成和解呢?回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廢除種族隔離的努力。軍隊中的來複槍公司把不同種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僅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觸的機會,而且使他們變得彼此依賴。他們在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打敗共同的敵人。
這是否表明了預測廢除種族隔離有效性的第二個因素?是否競爭性的接觸只能分化他們的關係,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觸才能使他們團結?看看那些面臨共同困境的人們是怎麼做的吧。
共同的外部威脅能建立內部的團結
你是否曾經和別人一起站在大街上等待一場大雨的結束呢?是否曾經由於煩惱而和別人一起加入了一個團體?是否曾經和同學一起被老師批評過?是否由於你的社會地位、種族以及宗教信仰而與他人一起被迫害或嘲笑呢?如果是,那麼你就可以清楚地回憶起對那些跟你一起面對困境的人的親切感。當你們互相幫助一起掃雪開闢道路或者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時,你們之間的社會性障礙就有可能消除。
這種友善的行為經常在人們共同面對危機的時候出現。約翰·蘭則塔(Lanzetta,1995)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來證明,共同的危機對人們彼此態度的改變的作用。他讓四人一組的海軍軍官後備學校的學生完成一個問題解決的任務,然後用廣播告之其中一些組,他們的答案是錯誤的,並且他們答題的效率不可饒恕地低,他們的想法都非常愚蠢。其他的組則沒有受到這樣的懲罰。蘭則塔發現:那些受到批評的組員們彼此變得更加友好、更合作,以及出現更少的爭吵和競爭。他們團結在一起,意氣相投。
在謝里夫的夏令營實驗中,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可以統一那些彼此懷著競爭的男孩們——其他很多類似的實驗也都證明了這一點(Dion,1979)。民族間的多次衝突會提高民族自尊心。比如在多倫多的中國留學生面對歧視時,會和其他的中國人產生更加強烈的歸屬感(Pak & others,1991)。當一個人被提醒不屬於某個群體(如別的學校)時,會增強他對於自己群體的責任感(Wilder & Shapiro,1984)。當我們明確意識到“他們”是誰時,我們同時也明確了“我們”是誰。
在戰爭時期面對一個明確的外部威脅時,我們的群體歸屬感高漲。公民組織的會員數快速增長(Putman,2000)。公民們團結在他們的領導人周圍並支持他們的軍隊。這種情況在9.11災難之後,當人們面臨著進一步的恐怖襲擊的威脅的時候尤為明顯。《紐約時報》報道,在紐約城,“由來已久的種族對抗已經緩和”,至少是在一段時間內(Sengupta,2001)。“在9.11恐怖事件發生以前只以為自己是一個黑人”,18歲的路易斯·約翰遜說道:“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覺得自己是一個美國人。”這是9.11之後人們思想變化的一個例證。另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紐約市長朱利亞尼在9.11後的新聞發佈會上使用的“我們”這個詞比以前多了一倍(Liehr & others,待發表;Pennebaker & Lay,2002)。
喬治·布什的政績支持率也反映了這種外部威脅帶來的內部團結。就在9.11之前,他的民眾支持率只有51%。而9.11之後,他的支持率則高達90%。在公眾看來,這個得到90%人們支持的平庸總統已經成為了人們100%高貴的總統——在我們同“那些憎恨我們的人”的戰爭中的“我們的領袖”。在那之後,他的支持率逐漸下降,但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前他的支持率再度攀升(圖13-6)。當所羅門和他的同事(Solomon & others,2004)在讓美國學生回憶9.11事件時(而不是回憶即將到來的考試),這些學生更可能會同意這種說法——“我贊同美國總統布什和他的官員們在伊拉克進行的勇敢的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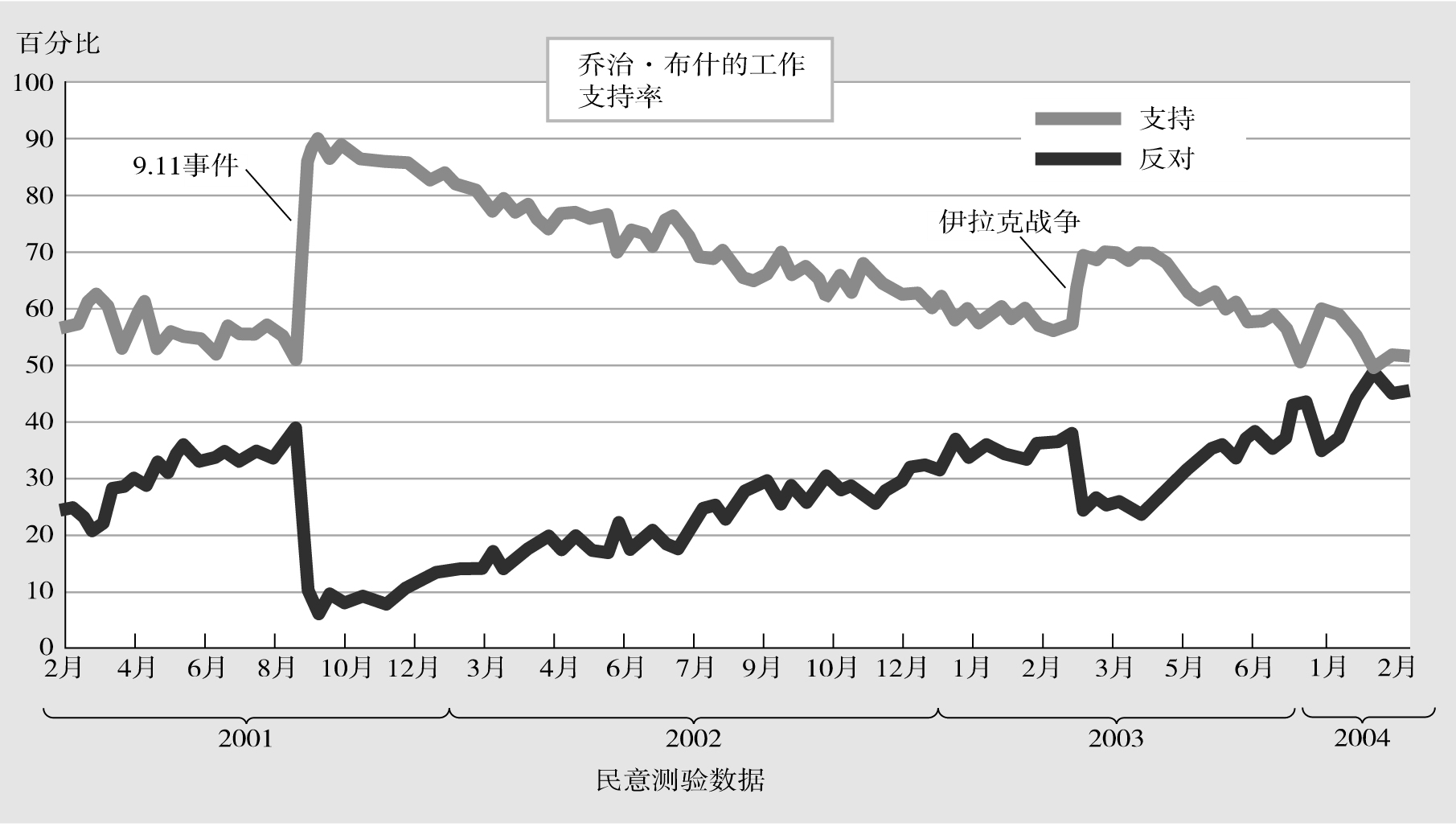
圖13-6 外部威脅會導致內部的團結
從總統喬治·布什的支持率的起伏可以看出,國家衝突可以影響公眾的態度(Gallup,2003)。
有時候,領導人會刻意創造 出一個假想的敵人來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喬治·奧維爾的小說《1984》中就描寫了這樣的一個策略:國家的領袖利用增加和其他兩個強大勢力的對抗來減少民族內部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敵人不停地變換,但是敵人永遠存在。事實上,國家似乎就需要 這樣一個敵人。對於整個世界,對於一個國家,對於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的敵人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量。
同時發生的外部威脅也會導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團結。發生在以色列的自殺性爆炸事件使分散的猶太人集結在總理沙龍和他的政府旗下,而當以色列的防禦力量殺死了幾名巴勒斯坦人並破壞了他們的財產時,穆斯林的各個派別都把他們的仇恨指向了沙龍(Pettigrew,2003)。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Pew研究中心(2003)對印尼和約旦的穆斯林進行民意調查,發現他們的反美情緒高漲。2002年有53%的約旦人表示他們對美國人持有積極的看法,然而在戰後急劇下降到18%。“在戰前,如果我說奧薩瑪(本·拉登)對兩座高樓真的負有責任,我們不會為此事感到自豪,”敘利亞一個研究伊斯蘭法律的21歲學生說道。“但如果他現在這麼做,我們會為他驕傲”(Rubin,2003)。
超級目標會促進合作
與面對一個共同的外部危機時形成的凝聚力量緊密相聯的另一個凝聚力量是超級目標 (superordinate goals)。它是能夠將群體的所有成員團結起來、共同合作來完成的目標。謝里夫為了促成彼此競爭的露營者的和解,曾使用過這樣的目標。一次,他讓夏令營的供水出現了問題,使得營員們必須通過合作來修復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一個可以租借影碟的機會,但是所需的費用必須動用兩個團隊的共同資金,這時他發現合作又一次發生了。還有一次,他們在行進途中有一輛卡車“拋錨”,實驗人員在路邊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繩,於是其中一個男孩就提議大家用繩子把客車拉到啟動。當卡車啟動後,所有的成員互相擊掌表示慶祝。
聚焦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誰獲勝
為什麼世界各地的體育迷都那麼在意誰獲勝呢?為什麼紐約人也那麼在意喬治棒球隊的那24名身價數千萬的臨時球員能否在世界職業棒球大賽中獲勝,儘管這些球員大部分來自其他州或國家?為什麼在美國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瘋狂三月”籃球賽中,那些完全正常的成年人會瘋狂地支持自己的球隊,而當球隊輸掉比賽時又極度沮喪?為什麼在世界盃足球賽中,世界各地的球迷都夢想著自己的國家獲勝?
理論和事實都表明,這種競爭有很深的根源。當兩個球隊一上場群眾就爆發出熱情,其中有一些原始的東西在起作用。正是一種原始部落時期就有的東西支持著他們兩個小時的熱情,使他們的反應隨著那個橘黃色的皮製小球起起落落。我們的祖先生活在那樣一個世界,相鄰的部落間常常會突襲並劫掠其他部落的營地,因此他們更明白團結就意味著安全(那些不能團結在一起的人們留下的後代較少)。無論是打獵、防禦或攻擊他人,10隻手總是好過2隻手。把這個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要承擔沉重的代價,比如種族主義和戰爭,但是也會使群體內部更加團結。為了區分我們和他們,我們的祖先——離今天的那些狂熱的球迷並不遙遠——穿著具有群體特色的服裝或使用特殊的顏色標識自己。
作為社會性動物,我們群居在一起,我們為自己的群體歡呼,為自己的群體戰鬥,甚至為自己的群體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們用我們的群體來定義我們自己。我們的自我概念,即我是誰,不僅包括我們個人的品性和態度,還包括我們的社會同一性。我們的社會同一性,即“我們”是誰,能強化自我概念和自豪感,尤其是當知覺到“我們”是優越的。因為缺乏積極的社會同一性,很多年輕人從團伙中尋求自尊、權力和認同。很多極端的愛國者用他們的民族身份來定義自己。
對於“我們是 誰”的群體定義同時也暗示了我們不是 誰。許多社會心理學實驗都表明只要把人們分組,哪怕只是任意的分組都會促使“內群體偏見”的產生。如果你問孩子們,“是你們學校的孩子好還是鄰校的孩子們好?”毫無疑問,所有的孩子都會說,他們自己學校的孩子更好。如果你只是按人們的出生日期或是駕照的尾數把人們分成組,那麼他們也會感到和自己的組員存在某種相近,而且會對組員表現出喜愛。因此群體意識如此強烈,以至於就算我們只是隨機地分開“我們”和“他們”,人們也會覺得“我們”看起來好於“他們”。
就像9.11之後美國所表現的那樣,當人們面臨共同的敵人時,群體的團結性高漲。謝里夫的強盜野營實驗,也生動地證明了競爭會製造敵人。在競爭的推動下和群體匿名的情況下,人們在一些惡性體育事件中的激情會達到頂點——球迷們辱罵對手,向裁判尖叫,甚至向裁判員丟啤酒瓶。
伴隨著成功,人們的群體認同也會高漲。球迷可以通過個人的成功獲得自尊,但當他們支持的球隊獲勝時,他們也能通過和那些勝利的運動員聯繫在一起獲得自尊,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在足球隊大獲全勝之後,羅伯特·恰爾迪尼和他的同事(Cialdini & others,1976)詢問了一些大學生,他們一般都會說“我們贏了”,他們從他人的榮譽中得到滿足。然而在球隊輸掉比賽後詢問這些學生,他們更經常地回答“他們輸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常常把我們最強烈的感情留給和我們相似的競爭對手。弗洛伊德在很久以前就說過,仇恨總是圍繞著小差異形成。“在兩個相鄰的城市,一方總是成為另一方猜疑的對手。每一個小的行政區都會輕視其他的行政區。緊密相關的兩個種族會互相疏遠對方;南德人不能忍受北德人,英格蘭人用各種手段誹謗蘇格蘭人,西班牙人也看不上葡萄牙人。”芝加哥小熊隊和白襪隊的球迷會心照不宣地同意這種說法。
作為蘇格蘭的臨時居民,我目睹了很多能反映蘇格蘭人仇外原則的例子——蘇格蘭人把非蘇格蘭人“分成兩個主要的群體:(1)英格蘭人;(2)其他人。”正像小熊隊狂熱的球迷在小熊隊贏的時候或白襪隊輸的時候都會高興一樣,蘇格蘭足球隊的球迷在蘇格蘭隊贏的時候或英格蘭隊輸的時候都會感到欣喜。“喲,他們輸了”,1996年英格蘭隊在歐洲盃中被德國隊擊敗後,蘇格蘭一家小報的頭版頭條就欣喜地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經過這樣幾次共同完成超級目標的活動後,男孩子們開始在一起吃飯,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誼在兩個團隊之間蔓延開來。敵意直線下降(圖13-7)。在最後一天,男孩們決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們不再按照團隊分開乘坐。當巴士到達他們的家俄克拉荷馬州時,他們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中道別。就這樣,謝里夫用隔離和競爭製造了陌生人之間的敵意,又用超級目標使得這些敵人變成了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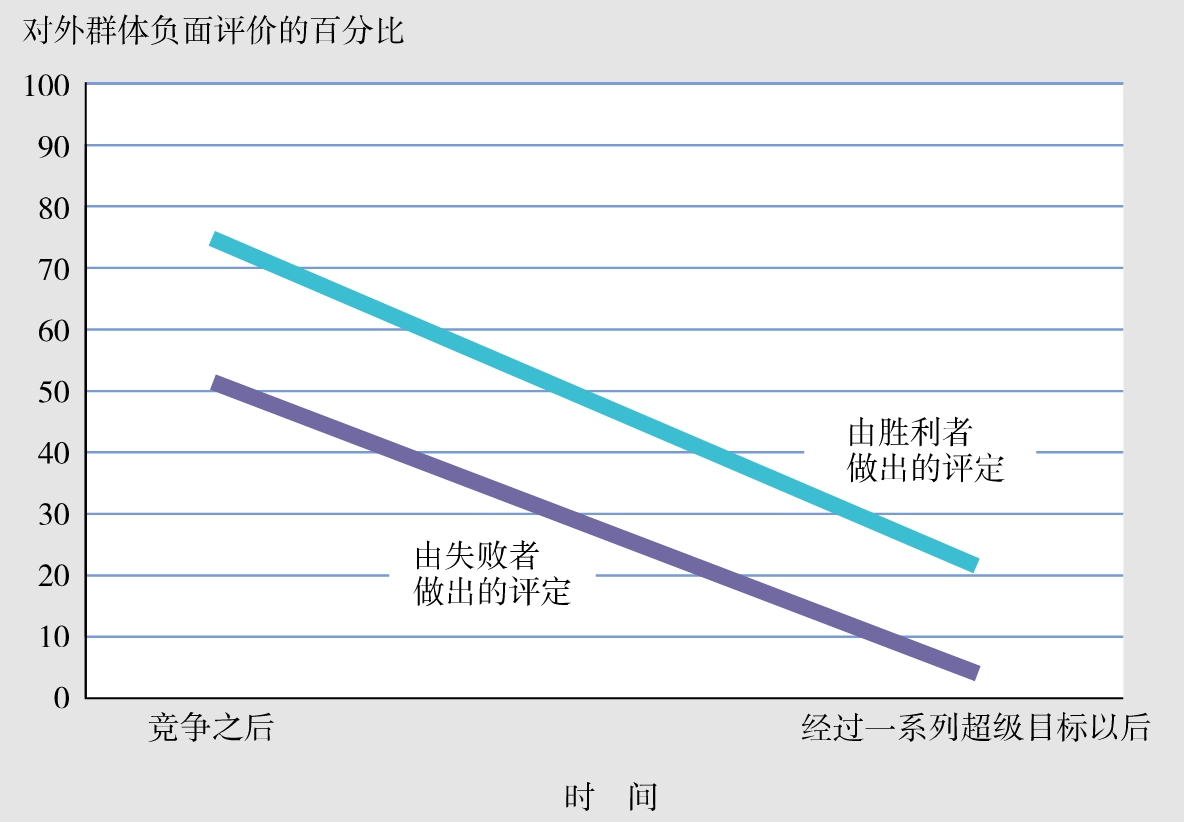
圖13-7
競爭之後,“響尾蛇”和“老鷹”之間對彼此的評價是負面的;在一起為了超級目標合作之後,“響尾蛇”和“老鷹”之間的敵意下降了。
資料來源:Data from Sherif,1966,p.84.
謝里夫的實驗僅僅是小孩子的遊戲嗎?或者說對於成人來說,把彼此衝突的人們叫到一起完成一個超級目標也會取得類似的結果嗎?羅伯特·布萊克和簡·穆頓(Blake & Mouton,1979)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系列為期兩週的實驗中,共有150個不同的團體,1000個經理人,他們重現了“響尾蛇”和“老鷹”之間競爭情境的基本特徵。一開始每個團體各自活動,然後組與組之間互相競爭;而後讓不同的組在一個超級目標之下合作。他們的結果明確顯示,成年人和謝里夫實驗中那些年輕被試是一致的。
塞繆爾·蓋特納和約翰·多維迪奧和他們的合作者(Gaertner & Dovidio,1993,2000)拓展了這些結果,他們發現在一起工作尤其對分解小群體,建立一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群體很有用。當兩個團隊選擇圍著圓桌坐下來(而不是對立地坐著),給他們的新團隊起一個名字,然後在一個良好的氛圍下一起工作時,他們原先對彼此的那種帶有偏見的不良感覺就會減少。“我們”和“他們”合在一起就可以成為“咱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打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美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國家組成了“同盟國”。只要“打敗共同的敵人”這一目標存在,那麼美國對俄國的態度總是支持的。
“響尾蛇”和“老鷹”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後以成功告終。但是,如果當時供水並沒有恢復,影碟沒有買成,或者那輛卡車仍然停在路中央,男孩之間的和解還會出現嗎?似乎不會了。在對弗吉尼亞的大學生做的一個實驗中,斯蒂芬·沃謝爾和他的助手們(Worchel & others,1977,1978,1980)發現,成功 的合作能夠增強兩組人之間的吸引力。如果曾經敵對的組在一個合作的任務上失敗 了,並且他們又可以把失敗的責任推卸到對方身上時,他們之間的衝突反而會惡化。謝里夫的實驗中,團隊之間已經彼此懷有敵意,因此如果他們想要集資租影碟時不能湊夠足夠的錢,那麼他們很可能歸結為對方的組員太“小氣”或“自私”。這不僅不能減輕他們的衝突,反而會加重矛盾。
合作學習能夠改善種族態度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在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有限的社會好處(尤其是沒有友誼帶來的情感紐帶或平等的關係相伴時)。我們也看到了在兩個敵對的群體之間進行成功的、合作性的接觸所帶來的戲劇性的社會好處。這兩方面的研究結果結合起來,是不是能夠讓我們對傳統的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實踐提供更好的選擇呢?一些獨立的研究小組認為是可以的。每個小組都希望知道,我們能否在不影響學業成績的情況下,通過把那些激烈競爭的學習環境變成一種合作的環境,從而改善種族之間對彼此的態度呢?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中,幾乎每一個都涉及到讓學生參加一個學習小組,有時會要求他們和其他的組競爭——這些研究的結果是令人吃驚和振奮的。
那些參加了現有的合作活動的學生,比如種族間的田徑隊和課程小組,是不是會有更少的偏見呢?羅伯特·斯萊文和南希·馬登(Slavin & Madden,1979)對71所美國高中的2400名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鼓舞。那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學習和遊戲的學生更多地報告說有非本族的朋友,對其他民族的態度也更加積極。查爾斯·格林和他的同事們(Green & others,1988)對上述的結果做了進一步的證實。他們對3200名佛羅里達的中學生進行的調查表明:相對於在傳統的、充滿競爭的學校裡學習的學生而言,那些在學校參加混合民族的學習小組的學生,有著更好的種族態度。
從上面這些相關研究中,我們是否能得出結論說,在種族間合作性的活動能夠改善他們對彼此的看法呢?應該說,我們仍然是需要實驗的證據的。隨機地抽取一部分學生參加種族混合的活動,而另一些不參加,這樣才能看出真正的差異。斯萊文(1985,2003)和他的同事們把班級拆分成各個種族混合的學習小組,每個組包括四到五個學習成績水平各異的學生。每個小組的成員坐在一起,學習各種科目,並在每週末的班級競賽中和其他小組競爭。小組的成員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小組的總體成績,他們既可以和其他組同等程度的學生比,也可以和自己以前的成績比。每個人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並且,小組成員都被鼓勵互相幫助準備每週的競賽——比如準備一些小知識,拼寫,或者歷史事件的背誦——各種小事都可以。和單打獨鬥的學生相比,這種組與組之間的競爭使學生們有更親密的接觸,也更容易產生互助和支持的關係。
另一個由阿倫森(Aronson,1978,1979,2000;Aronson & Gonzalez,1988)領導的研究小組使用“拼圖”(jigsaw)的方法進行了類似的小組合作的研究。在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小學中,研究者根據學生的種族和學習成績把他們分成六人小組。這樣一來,一個科目就可以變成六個部分,而每個小組成員將成為他自己那一部分的專家。在關於智利的一個單元中,其中一個學生可能是關於“智利的歷史”的專家,而另一個則是智利的地理專家,還有精通智利文化的專家等。一開始,這些所謂的“歷史專家”、“地理專家”們分別聚在一起研究他們的學習材料。然後他們回到自己原來的小組把所學的知識教給同學。也就是說,每個小組成員都有了一塊“拼圖”。沉默寡言的學生也可以向那些平時很自信的學生講述他們的意見,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對於同伴的重要性。其他的研究,比如戴維·約翰遜和羅傑·約翰遜(Johnson & Johnson,1987,1994,2000)在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伊麗莎白·科恩(Cohen,1980)在斯坦福大學,施羅默·沙蘭和亞爾·沙蘭(Sharan & Sharan,1976,1994)在特拉維夫大學,斯圖爾特·庫克(Cook,1985)在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都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合作性學習。
從所有的818個研究中(Druckman & Bjork,1994),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在合作性的學習中,我們發現學生不僅學到了知識,他們還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斯萊文和羅伯特·庫珀(Slavin & Cooper,1999)說:“合作性學習讓所有的學生在得到學業上的成就的同時,也改善了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之間的關係。”阿倫森(1980,p.232)也報告說:“在存在‘拼圖’的班級裡面,孩子們互相幫助,對於同伴也更加喜愛,對學校的感覺也更加良好,同時他們的自尊也比在傳統的班級中的孩子要高。”
同時,民族間的友誼也在飛速增長。少數民族學生的考試成績有了提高(也許因為現在的學業成績是同伴間互相支持的)。在實驗結束之後,許多老師仍然繼續採用合作學習的方式(D. W. Johnson & others,1981;Slavin,1990)。“很顯然,”種族關係專家約翰·麥科納希(John McConahay)寫道,“合作學習是目前為止在那些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中,最為有效的改善種族關係的實踐方法。”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知道這個規律。早在1954的最高法院決議中,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代表很多社會心理學家預言,“歧視可以通過主流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為實現同一個目標而進行的平等接觸來消除”(1954,p.281)。合作學習的實驗研究支持了奧爾波特的預言,使得斯萊文和他的同事(Slavin & others,1985,2003)很樂觀地表示:“在奧爾波特提出基本原則30年後的今天,我們將這一原則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實現了可操作化,終於用實驗證明了,在廢除種族隔離的課堂中實行接觸可改善態度的理論的正確性……關於合作學習的研究,是教育研究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因此,無論是對露營的男孩們,還是工廠的經理人,大學生們,或者中小學校的孩子們,合作與地位平等的接觸都能夠產生積極的影響。那麼,這個規律是不是對於所有的人際關係都適用呢?通過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參加農園勞動,或是修理舊屋,或是駕駛帆船能夠促進家庭的團結嗎?社區中的人對於社區的認同會因為一起飼養家禽,或者合唱,或者一同踢足球而得到增強嗎?國家之間的理解會因為在科技和空間技術上的合作,或者對地球的自然資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過不同國家之間個體的接觸而得到改善嗎?很多跡象表明,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Brewer & Miller,1988;Desforges & others,1991,1997;Deutsch,1985,1994)。因此,對於我們目前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超級目標,並建立合作的關係來實現它。
群體和高級認同
我們每天都在處理各種各樣的身份(Gaertner & others,2000,2001;Hewstone & Greenland,2000;Huo & others,1996)。我們認同小群體中的身份(作為父母或者孩子),然後超越這種身份(把更大的群體認同為家庭)。離異父母再婚組合的家庭,兼併的公司等都讓我們提醒著自己,我們曾經是誰,現在又是誰。在我們繼承的道德情操中,自豪感需要我們擁有更為廣泛的群體的、民族的身份認同。小群體和社會中的身份認同是可以同時存在的(Brewer,2000;Crisp & Hewstone,1999,2000)。
但是,在種族多元的文化中,人們怎樣平衡他們的種族身份和國家身份的關係呢?
他們可能具有身份認同研究者珍妮·菲尼(Jean Phinney)所說的“雙文化”認同,既認同他本身的種族文化,又認同更大的社會文化。生活在英國的民族意識清晰的亞洲人,也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英國人(Hutnik,1985)。法裔加拿大人根據自己的種族根基來認同自己,因此他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強烈地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Driedger,1975)。那些仍然覺得自己是“古巴人”(或者墨西哥、波多黎各人)的西班牙語裔美國人也會強烈地覺得自己是美國人(Rogers & others,1991)。正像杜波依斯(W. E. B. DuBois,1903,p.17)在《黑人的靈魂》中闡述的那樣,“美國黑人渴望自己既是一個黑人,也是一個美國人。”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於新文化的身份認同會增加。前東德和西德人都逐漸把自己看成是“德國人”(Kessler & Mummendey,2001)。移民到澳洲和美國的中國人的第二代中,對於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有所下降,而對於新的國家公民的身份認同卻比那些在中國出生的移民要強(Rosenthal & Feldman,1992)。不過,通常第三代的移民,也就是孫子輩 的孩子會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好的認同(Triandis,1994)。
研究者們也希望知道,個體對自己群體的認同與對更大的文化背景的認同之間會不會出現競爭。我們在第9章中已經知道,我們有時會根據我們所在的群體來評價我們自身。如果我們把所在的群體(學校、僱主、家庭、民族、國家)看成是優秀的,那麼我們也會覺得自己很優秀。因此,積極的民族身份認同有助於提高積極的自尊心。同樣,那些融入主流文化的人也會擁有一個積極的社會身份認同。而那些既沒有民族身份認同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邊緣人”(表13-3)通常自尊心就比較低。“雙身份認同”的人則通常有很強的積極自我概念(Phinney,1990)。他們能夠在兩種身份之間變換,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時就採取什麼樣的語言和行為方式(La Fromboise & others,1993)。
表13-3 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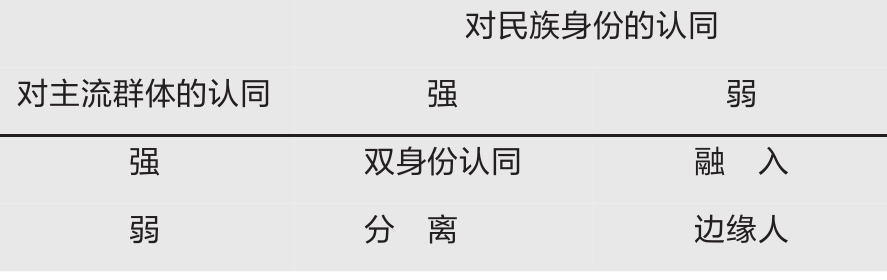
聚焦 裡基,羅賓遜和棒球運動的一體化
1947年4月10日,19個詞永遠改變了棒球運動,同樣也驗證了社會心理學家的規則。在布魯克林道奇隊表演賽的第六局,蒙特利爾隊的廣播臺的播音員雷德·巴伯朗讀了來自道奇隊的主席布蘭奇·裡基的一段講話:“道奇今天和來自蒙特利爾的羅賓遜簽約了,他很快就會來隊裡報到。”五天後,羅賓遜成為自1887年以來擔任棒球隊主力的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在秋季賽上,道奇的球迷們終於實現了進軍世界職業棒球大賽的夢想。羅賓遜在遭受了種族的嘲笑、抨擊和挖苦之後,被《體育新聞》評為年度最佳新人,並在一次民意調查中成為僅次於賓·克羅斯比的最受歡迎的美國人。棒球比賽中的種族障礙被徹底打破了。
社會心理學家普拉特卡尼斯和特納(Pratkanis & Turner,1994a,b)報告說,在道義和對球隊成功的渴望的驅動下,裡基打算引進羅賓遜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三年前,一個社會學家,同時也是團結市長聯盟的主席,找到裡基,要求在他的球隊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他回答說,需要一些時間使得僱用黑人不會給球隊帶來太大的壓力,以及計劃好的方法來實行它。早在1945年,裡基是惟一一個反對在球隊排除黑人的球隊負責人。1947年他所採用的僱用黑人的方法,被普拉特卡尼斯和特納總結如下:
讓球員們認識到改變是在所難免的 。給那些反對者和頑固派不留反駁的餘地。播音員雷德·巴伯,一個典型的南方人,回憶說1945年裡基有一次和他一起吃午飯,用很慢但很堅決的語調向他解釋他的球隊正在尋找一名“可以和白人一起打球的黑人運動員。我不知道他是誰,在哪裡,但我知道他即將到來。”憤怒的巴伯一開始想要離開。但是,他及時地接受了這個不可避免的決定,繼續他所熱愛的“世界上最好的體育新聞播報工作”。裡基1947年和他球隊裡的隊員也進行了類似的溝通,並且提出:如果有人不願意和羅賓遜一起打球,他可以更換球隊。
用一個超級目標使球員進行地位平等的接觸 。就像一個社會心理學家跟裡基解釋的那樣,當大家關注於一個超級目標時,比如取得比賽勝利,那麼“所有人都會自動地調整他們的態度和行為。”一個最初強烈反對羅賓遜的球員,後來在比賽中幫助他進球,他說:“當你們在同一個球隊裡的時候,你們必須團結在一起以取得勝利。”
打破偏見 。在裡基的帶領下,其他人也積極地幫助破除偏見。球隊的隊長擊球手裡斯,一個南方人,作為表率和羅賓遜坐在一起吃飯。一天在辛辛那提州,人群在高呼“把黑鬼從球場上踢走”時,里斯離開他自己的擊球手位置,走到羅賓遜所在的一壘,微笑著和他交談,並在眾目睽睽之下,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通過不斷地實踐和平來消除暴力 。裡基希望球員們能夠有足夠的胸襟,不要互相攻擊。因此,儘管羅賓遜受到攻擊和辱罵,裡基希望他承諾不要用暴力來對抗暴力。當羅賓遜被嘲笑或者扔東西的時候,他只是把迴應的事情留給他的隊友。就這樣,球隊的凝聚力就增強了。
羅賓遜和鮑伯·費勒後來成為棒球史上最早因出色的才能而進入名人紀念館的運動員。當他接受這項榮譽時,他邀請了三個人站在他身旁,一個是他的母親瑪麗;一個是他的妻子雷切爾;還有就是他的朋友裡基。
發展到極端的話,民族自豪感會演變成破壞性的種族主義。對多樣性的成見可能會與能夠促進衝突解決的團結感發生牴觸(Mayton & others,1996)。甘地、馬丁·路德·金和納爾遜·曼德拉等人通過和平的方式爭取公正,比如尋求理解、體諒、保護所有的人等。
通過提出一致的理想來推廣公民身份的認同,使得很多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避免了民族之間的戰爭。在這些國家中,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瑞典人和蘇格蘭人,亞洲人和非洲人很少為捍衛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廝殺。然而,即使在移民國家中,也為分裂與整合,民族尊嚴和國家統一,承認現實的多樣性和尋求共同的價值觀而鬥爭。對於一個“共性整合多元 ”(community incorporating diversity)的社會的追求造就了美國人的格言:合眾為一。
溝通
群體間的衝突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當夫妻之間、勞資雙方或者兩個國家之間發生不同的意見時,他們可以直接談判 (bargain);可以請第三方通過提議或促進協商來調解 (mediate);或者將雙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進行研究並仲裁 (arbitration)。
談判
如果你想要買或者賣一輛新車,你是選擇進行一場激烈的討價還價——開一個極端的價格然後尋求妥協比較好呢?還是一開始就出一個善意的價格?
實驗沒有給我們簡單的答案。一方面,那些出價高的人賣得也高。羅伯特·恰爾迪尼等人(Cialdini,Bickman,& Cacioppo,1979)提供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結果:在控制條件下,詢問很多雪佛蘭牌汽車的經銷商一輛蒙特卡洛汽車的價格。而在實驗條件下,他們跟另一些經銷商接洽,並且一開始就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詢問另一種汽車的價格然後表示太貴(“我需要更便宜的價格,那樣太貴了”)。當這些人再次詢問這些經銷商蒙特卡洛汽車的價格時(就像控制條件中的那樣),但這次他們得到了平均下降了200美元的出價。
激烈的討價還價可以降低對方對你的期望,從而使他們願意降價(Yukl,1974)。但有時也會被反咬一口。如果衝突一直持續,那麼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大小不變的蛋糕,而是一個縮水的蛋糕。協商有時並不能夠實現雙方共同的利益,大約有20%的協商最後以“雙輸”告終,雙方利益都受損(Thompson & Hrebec,1996)。
而遲來的協議也代價不菲。當一個罷工長期持續時,勞資雙方都遭受損失。激烈的討價還價還可能失去達到真正一致的機會。如果其中一方堅持與另一方同樣極端的條件,那麼雙方可能都會因為面子上下不來而僵持。在1991年海灣戰爭的前一星期,布什總統在公眾場合威脅說要“踢薩達姆的屁股”。薩達姆·侯賽因毫不示弱地表示要讓異端的美國人“在自己的血海中游泳”。在這樣好戰的宣言之後,雙方都很難既挽回面子又避免戰爭的發生了。如果雙方都給對方留一點面子,也許協商能夠避免戰爭。
調解
第三方調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議,使得衝突的雙方可以在做出讓步的同時,仍挽回面子(Pruitt,1998)。如果我的讓步是對調解人的,並且他同時也從我的對手那裡取得了讓步,那麼我們都不會把這種讓步看做是對對手要求的滿足。
把“非贏即輸”變成“雙贏” 調解人也可以通過促進雙方建設性的溝通來解決衝突。他們首先要做的是讓雙方重新思考這個衝突,並知道對方的利益所在(Thompson,1998)。通常,衝突雙方都有一個“非贏即輸”的想法:如果對方對結果感到失望,那麼他們就成功了;如果對方對結果滿意,他們則失敗了(Thompson & others,1995)。調解人要通過讓他們暫時放下衝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換位思考對方的需要、利益和目標,從而把這種“非贏即輸”的想法變成“雙贏”的取向。利·湯普森(Thompson,1990a,b)在實驗中發現,有經驗的協商者更能夠作出折衷的讓雙方都有利的決定,從而達成雙贏的解決方案。
一個關於“雙贏”的經典故事,來自爭桔子的兩姐妹(Follett,1940)。最終她們的決定是把桔子平分成兩半,其中一個女孩把她的一半榨成橙汁,另一個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來做蛋糕。迪安·普魯伊特(Dean Pruitt)和他的同事在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實驗中,鼓勵被試對這個故事找出更好的整合性協議 (integrative agreements)。如果這兩個女孩同意分享桔子,其中一個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個得到全部的桔子皮,那麼他們就得到了兼顧雙方利益的決定(Johnson & Johnson,2003;Pruitt & Lewis,1975,1977)。和那種要讓雙方犧牲掉一些東西的妥協來說,整合性協議更具有持久性。因為他們是互相滿足的,因此也可以帶來持續的夥伴關係(Pruitt,1986)。
用剋制的溝通來消除誤會 溝通可以減少自我證實的誤解。回憶一下,也許你也能想起和這個大學生類似的經歷:
我經常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和瑪莎交流後,就覺得她這種沉默是不喜歡我的表現。而她也認為我的寡言是對她厭惡的結果。我的沉默導致了她的沉默,而這又使得我更加沉默……這種滾雪球效應直到一次我們必須交流的意外事件的發生才得以打破。而我們通過交流消溶了彼此之間所有的誤解。
像上面這種衝突的結果,往往取決於人們怎樣 彼此交流他們的感受。羅傑·克努森及其同事(Knudson & others,1980)邀請已婚夫婦到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心理實驗室,通過角色扮演重新體驗他們過去的衝突。在他們的談話(往往產生和先前的真實矛盾同樣激烈的衝突的談話)之前、中間和之後,都仔細地觀察和詢問了他們的情況。那些迴避問題的夫婦——或者不能夠澄清他們的處境或者未能認清其配偶的處境——讓他們自己有一種比以前更和諧的錯覺。他們會覺得彼此現在能夠在更多的事情上達成一致,而事實上只是更少的一致。而那些主動面對問題的夫婦——能夠認清他們的處境並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並且對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確切的瞭解。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什麼直接、開誠佈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婦通常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Grush & Glidden,1987)。
上述的結果引發了一個教育夫婦和孩子如何建設性地解決衝突的活動(Horowitz & Boardman,1994)。如果能夠建設性地解決衝突,那麼衝突能夠提供和解的機會和更多真正的和諧。心理學家伊恩·戈特利布和凱瑟琳·科爾比(Ian Gotlib & Catherine Colby)提出了關於如何避免破壞性的爭吵和怎麼進行建設性的爭吵的幾點建議(表13-4)。比如,孩子們應該瞭解到生活中的衝突是正常的,人們可以試著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很多爭吵可以“雙贏”地解決,非暴力的溝通是暴力和欺凌的替代品。這種“阻止暴力的課程……並不是被動的,”德博拉·普羅思羅-斯蒂思(Deborah Prothrow-Stith)認為,“它是旨在讓人們合理地引導自己的憤怒以免傷及自己或他人,旨在改變這個世界。”
表13-4 怎樣建設性地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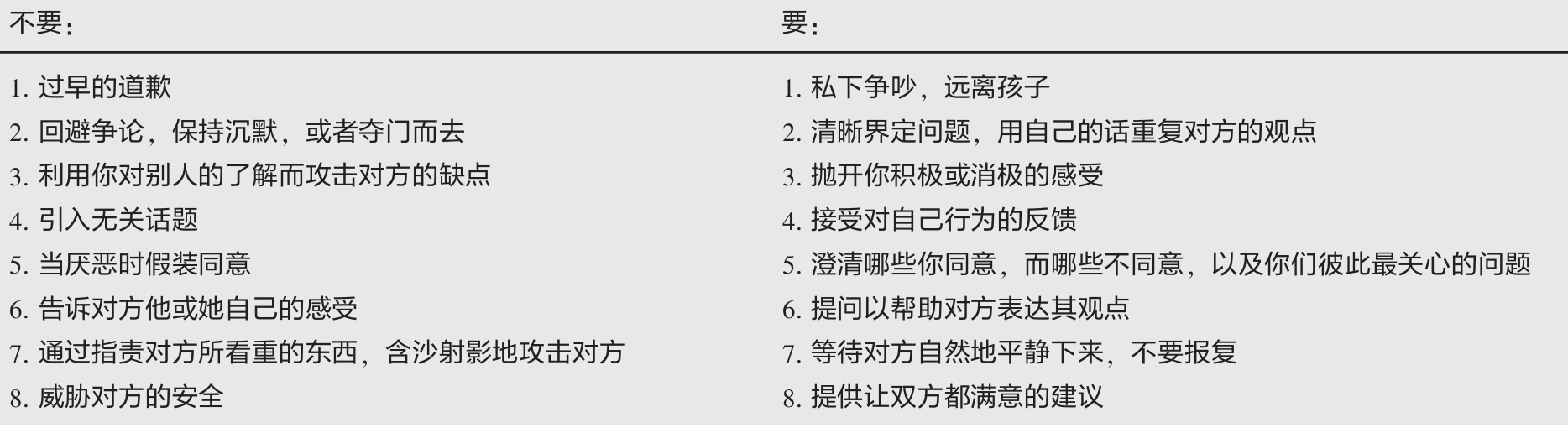
戴維·約翰遜和羅傑·約翰遜(Johnson & Johnson,1995,2000)讓六個學校的一到九年級的孩子進行約12個小時的衝突解決訓練,得到了非常令人振奮的結果。在訓練之前,這些孩子總是糾纏在日常的小衝突中——互相奚落嘲笑,運動場上互相廝打,爭奪東西——所有的衝突都導致一勝一負的結果。在訓練之後,孩子們經常能找到雙贏的解決方案,更好地調解朋友的衝突,並在整個學年都能把他們的新技能用於校內外的各個地方。當整個學生群體都經過這樣的訓練後,學校社區變得非常和諧安靜,孩子的學習成績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衝突研究者認為信任 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Ross & Ward,1995)。如果你相信對方是善意的,你就會更容易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沒有這樣的信任,你可能就會擔心你的坦誠會給了對手反對你的信息。
當雙方互相不信任並且進行無效的溝通時,第三方的調解者——婚姻顧問,勞資調解員,外交官——有時候是有幫助的。通常調解者是衝突雙方都信任的人。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在20世紀80年代充當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調解人,而羅馬教皇則化解了阿根廷和智利在領土上的分歧(Carnevale & Choi,2000)。
在說服衝突雙方重新思考他們所認為的“非贏即輸”的衝突之後,調解人讓雙方都確認自己的目標,並按重要性給目標排序。如果目標是相容的,那麼排序的過程就可以讓雙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標上讓步,以實現最主要的目標(Erickson & others,1974;Schulz & Pruitt,1978)。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認可對方的最高利益——以多數決定原則代替種族隔離,同時保護白人的安全、財產和權利,通過這種方式南非獲得了內部的和平(Kelman,1998)。
一旦勞資雙方彼此相信,管理者提高生產效率和利潤的目的與勞動者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是一致的話,他們就可以共同尋求雙贏的解決方案了。如果員工能夠放棄那些對他們有一點小利益卻可能讓老闆花費很多的好處(比如公司提供牙科護理費),如果老闆能夠放棄對管理者有一點小利益卻可能讓員工感到非常反感的安排(比如不固定的工作時間),這樣的話勞資雙方都獲益了(Ross & Ward,1995)。與其說這樣做是讓步,不如把這種協商看成是用做交換更有價值的東西的籌碼。
當兩個衝突的群體聚在一起開始直接的對話時,不能天真地認為光靠眼球對著眼球,衝突就會自動地解決。在一個具有威脅性的、劍拔弩張的衝突中,高亢的情緒經常阻礙人們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問題。在最需要溝通的時候,溝通往往變得最困難(Tetlock,1985)。這時調解人需要建立一種情境,幫助雙方去理解對方,並感到被對方理解。調解人可以讓衝突中的雙方把爭論僅限於對事實的描述,包括陳述如果對方怎麼做他們就會有什麼樣的感覺,會做出何種反應:“我喜歡開著音樂,但如果你開得過大,我會覺得注意力難以集中,那就會使我感到很暴躁。”另外,調解人也可以讓人們角色互換,去討論對方的處境或者想像和解釋對方所體驗的經歷。(實驗證明引發共情能夠減少刻板印象,增加合作性——Batson & Moran,1999;Galinsky & Muskowitz,2000。)或者調解人可以讓雙方在描述自己感受之前描述對方的處境:“我把音響開得過響使你很煩躁。”
中立的第三方還可以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建議,而這些建議如果由衝突的任何一方提出均會被駁回(“相對貶值”)。康斯坦絲·斯蒂林格(Constance Stillinger)和她的同事(1991)發現,當解除核武器的建議由前蘇聯提出時,美國人表示不同意,但當這個建議由中立的第三方提出時就變得可接受多了。類似地,人們對於對手提出的讓步總是嗤之以鼻(“他們肯定不在乎這一點”);而當這種讓步由第三方提出時,他們就不會覺著這是一種虛假姿態了。
這些調停的原則,有的基於實驗研究,有的基於實踐經驗,它們對國際和工業上的衝突的調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Blake & Mouton,1962,1979;Fisher,1994;Wehr,1979)。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凱爾曼(Herbert Kelman)帶領一個由阿拉伯人和美國猶太人組成的小團隊,曾舉辦了許多工作坊,使阿拉伯和以色利的名流坐到了一起。另一個社會心理學家組成的團隊是由斯托布和皮爾曼(Ervin Staub & Laurie Ann Pearlman)領導的,他們1999~2003年在盧旺達工作,他們訓練了一些記者,理解並準確地寫出盧旺達的創傷,以便能夠治癒創傷,達成和解。凱爾曼和他的同事運用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當遭遇誤解的時候時,讓他們主動去尋求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辦法。被試在單獨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地和他們的對手直接交談,不必擔心他們的委託人會在猜測他們在說什麼。結果如何呢?來自雙方的人都開始漸漸瞭解對方的觀點,以及他們的行動會使對方有什麼樣的反應。
仲裁
有些衝突是很難解決的,雙方的潛在利益有很大分歧以至於無法達成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之間不能對同一塊土地擁有主權。在一次關於孩子的監護權的離婚爭論中,父母雙方不可能同時擁有孩子的監護權。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其他很多情況(比如是否由房客來付房屋修理費,運動員的工資,國家領土爭端等),在解決這種衝突時,第三方調解者可能發揮作用,也可能起不到作用。
如果調解解決不了,衝突雙方應該採用仲裁 ,由調解人或者其他的第三方組織來做一個決定。爭論的雙方通常並不喜歡用仲裁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他們擔心會對結果失去控制。尼爾·麥吉利卡迪等人(McGillicuddy & others,1987)在一個實驗中觀察到了這種傾向性。實驗中,爭論者來到一個矛盾解決中心。當他們意識到如果調解失敗,他們將面臨仲裁時,他們會竭盡全力去解決問題,表現出更少的敵意,也更容易達成協議。
在那種矛盾非常明顯難以妥協的事件中,意識到將面臨仲裁時,衝突的雙方會固守他們的立場,並希望在仲裁人選擇一個折衷方案時,自己能從中獲益(Pruitt,1986)。為了消除這種傾向,一些比如涉及到棒球運動員個人工資的爭論中,採用“最後提議仲裁”的方法,也就是第三方在最後的兩個方案中選擇一個。最後提議仲裁能夠促使矛盾雙方做出比較合理的建議。
但是通常情況下,如果雙方不能夠擺脫自私的偏見,從對方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建議,那麼最後提議仲裁就不是所想的那麼合理了。協商的研究者們報告說,大多數的爭論者最後被“樂觀的過於自信”所羈絆,變得非常固執(Kahneman & Tversky,1995)。通常是雙方都深信,他們有贏得最後提議仲裁的三分之二的好運氣,結果導致調解的失敗(Bazerman,1986,1990)。
和解
有時衝突雙方的緊張和懷疑程度如此地高,不要說解決問題,就是溝通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方都會威脅、脅迫或者報復對手。更不幸的是,這種行為是相互的,使得衝突愈演愈烈。因此,是否可以通過一方的無條件合作來安撫對方,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呢?事實上通常是不行的。在實驗室的遊戲中,那些百分之百合作的人最後往往會被傾軋。比較明智地說,單方面的妥協是行不通的。
GRIT
社會心理學家查爾斯·奧斯古德(Charles Osgood)提出了第三種方案,即和解,直到足可以消除傾軋。奧斯古德把它叫做“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動(initiative)地減少緊張(tension reduction)”。他戲稱之為“GRIT ”,標明它所需要的決心。GRIT致力於通過引發互惠的衝突的逐步降級來扭轉衝突的“螺旋上升”。它引進了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來構建理論,比如互惠規範,動機歸因等。
GRIT要求一方在宣佈希望調和的願望 之後,做出一些小的意在降低衝突的行為。發起調和的一方,在實行每一個表示調和的行為之前都聲明這種希望減少緊張的主張,並邀請對手進行回報。這種聲明可以建立一種框架,使對手能正確理解其意圖,而不是當作示弱或欺詐。並且這種聲明也給對手造成了輿論上的壓力,使他們必須遵循互惠的規範。
接下來,發起者必須如聲明中所說的做出一些可以證實的和解行動 ,以建立信任與真誠。這可以對回報行為施加壓力。調和行動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比如提供一些醫藥信息,關閉一個軍事基地,取消貿易禁令——但是不要讓發起者在任何一個領域做出非常大的犧牲,並且要讓對手能夠自由地選擇他們做出回報的方式。如果對手出於自願地進行回報,那麼它自身的和解行為會緩和它的態度。
GRIT是和解性的。但並不是屈服於“分期付款計劃”。這一計劃的另一面是可以通過“維持報復的能力 ”來確保雙方各自的利益。最初的一些調和的行為可能要使雙方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是並不會危及到各自的安全;相反,這是讓雙方從劍拔弩張的臺階上面下來的一個方法。比如:若其中一方採取了暴力行動,而對方卻報以友善,並申明他們不會容忍任何傾軋。而如果這時對手也提供了相當的或者稍超出的回報行為,那麼,這種回報就不是一種會導致衝突升級的過激行為了。莫頓·多伊奇(Deutsch,1993)在建議協商時對GRIT作出了概括,可以說抓住了精髓:“‘堅定、公平、友善’,堅定 就是反對脅迫、傾軋和骯髒的手段;公平 就是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無論對手怎樣挑釁,決不回敬對方不道德的行為;友善 則是指人們願意發起和回報合作行為”。
GRIT真的有用嗎?在實驗室的兩難遊戲中,一個簡單的“投桃報李”的策略被證明是成功的。大家開始進行一個合作的開放性遊戲,然後雙方儘量配合對手的最後一個反應(Axelrod & Dion,1988;Parks & Rumble,2001;Van Lange & Visser,1999)。雖然一開始都是友好的,“投桃報李”會及時地懲罰出現不合作行為的成員,但也會立即原諒那些願意重新合作的反覆無常的對手。在俄亥俄大學進行的一系列的實驗中,斯文·林德斯格爾德(Svenn Lindskold)和他的助手們(1976~1988)發現了對GRIT策略的不同步驟的強有力的支持。在實驗室的遊戲中,聲明合作的願望的確 大大地促進合作。不斷的和解行為可以培養更大的信任感(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總是讓人覺得自己的行為比對方更加具有和解性,更少具有敵意)。保持一種力量上的平衡,可以避免傾軋。
林德斯格爾德認為實驗室的小環境並不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複雜世界,但是實驗可以使我們構建並證明一些理論,比如互惠規範和自我服務偏見。林德斯格爾德(1981)寫道:“最終被用於解釋現實世界的是理論,而不是單獨的實驗。”
在現實世界中的運用
類似GRIT的策略在實驗室之外也偶爾被運用,並取得了不錯的結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柏林危機中,美國和俄國的坦克炮管對炮管地碰頭了。這場危機由美國一步一步地撤回自己的坦克而得以化解。美國人每退讓一步,俄國人也予以回報。而以色列和埃及的緊張關係也因為小小的讓步(比如,以色列允許埃及開放蘇伊士運河,而埃及則允許去以色列的貨船通過)得到緩解,從而使協商成為可能(Rubin,1981)。
在眾多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數所謂的肯尼迪實驗(Etzioni,1967)。在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總統發表了一個重大的演說——“實現和平的策略”。他說:“我們的問題都是人為造成的……並且可以由人來解決”,然後他聲明瞭他的第一個和解行動:美國停止所有的大氣核試驗,除非其他國家進行試驗否則將不會再繼續。在前蘇聯,肯尼迪的演講被全文發表。五天之後,前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做出迴應,聲明他已經停止生產戰略導彈。不久,進一步的回報行為出現了:美國同意賣小麥給俄國,而俄國則同意在兩國之間開通“熱線”,兩國很快還簽署了“停止核試驗”的協議。在一段時期內,這些和解行動使得兩國的關係變得趨於緩和。
和解行動能夠減少個人之間的緊張情緒嗎?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它會。當兩個人的關係受阻,溝通難以進行下去的時候,通常一個小小的和解姿態——一個溫和的回答,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個輕柔的觸摸——可以使雙方從緊張的臺階上下來,使得接觸、合作以及溝通重新變得可能。
小結
儘管衝突經常被社會困境、競爭和誤解所引發,但是一些強大的力量,比如接觸、合作、溝通與和解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把人們召集在一起進行密切的接觸,是否能夠減少他們之間的敵意呢?無論一些早期的研究結果有多麼鼓舞人,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學校中,僅僅廢除種族隔離對於改變民族態度並無多大影響。但是,當種族間的接觸促進了與其他種族的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並且這種接觸是建立在雙方地位平等的情況之下時,敵意通常能夠減少。
當人們為了克服同一個困難或者實現同一個超級目標而在一起工作時,接觸會變得特別有益。一些研究合作性接觸的實驗中,研究小組把競爭性的課堂變成了合作學習的樂園,取得了令人振奮的結果。
衝突的雙方還可以通過直接談判,或者第三方調解人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第三方的調解人可以促使敵對的雙方把他們競爭性的“非贏即輸”邏輯變成更富合作性的“雙贏”取向。調解人還可以創造消除誤會、增加互相瞭解和信任的溝通氛圍。當協商不能達成共識時,衝突的雙方可能就需要一個仲裁人來做一個決定,或者從他們提供的最後建議中選擇其一。
有時候,衝突的氣氛太緊張了,以至於實質性的溝通變得完全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動可以引發對方回報性的和解行動。其中的一種調和策略就是GRIT(逐步、互惠、主動地減少緊張)的行動,致力於減少國家之間的緊張狀態。
調解勞資矛盾和國際爭端的人有時也使用其他的和解策略。他們在衝突進行時指導參與者瞭解衝突與和解的機制,就好像這一章指導你的一樣,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建立並享受和平的世界,和良好融洽的人際關係。
個人後記: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之間的衝突
很多社會衝突是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競爭。一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和他的鄰居享受安全的社區的權利之間有衝突;一個人抽菸的權利和其他人享受一個清潔的無煙環境的權利之間有衝突;一個工業廠商進行任意生產的權利和社區需要淨化空氣的權利之間有衝突。
為了使個人和集體的利益都得到最大化,一些社會科學家——包括我自己——正在探索平衡個人與公共權利以增進共同利益的共產主義社區。“如果我此刻在阿爾巴尼亞,”共產主義社會學家阿米泰·埃奇奧尼(Etzioni,1991)說,“我多半會認為,那裡關心太多集體利益而忽視了個人權利。”不過,共產主義者同時也質問另一種極端——那些粗魯的個人主義和放縱:20世紀60年代(“做自己的事”),70年代(“我的時代”),80年代(“慾望是好的”),90年代(“尋找自己的幸福”)。他們說,無節制的個人自由毀壞了社會的文化結構;他們還認為,無節制的貿易自由會掠奪我們公共的環境。回憶一下:法國革命者的座右銘,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
在20個世紀後半葉,西方的個人主義開始氾濫。父母開始對孩子的獨立和自我依靠表示越來越多的讚賞,而較少關心他們的服從(Alwin,1990;Remley,1988)。衣服和首飾越來越多樣化,個人自由增加,共同的價值觀在漸漸消退(Putnam,2000;Schlesinger,1991)。隨著個人主義的流行,到目前為止漸漸暴露出很多弊病,不僅僅是抑鬱情緒的增加,還有一些社會的退化——比如西方社會一直處於明顯上升的離婚率,青少年自殺,青少年暴力和單親家庭。
注意:這種趨勢有很多原因。個人主義的流行和社會的退化在時間上的相關性並不能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同樣,共產主義者也不贊成緬懷過去——比如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嚴格的不平等的性別角色的時代。相反,他們建議在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東方的集體主義之間尋找一箇中間地帶,在獨立的、男子氣的傳統男性描述和相依的、體貼人的傳統女性描述之間,在只關心個人利益和堅持集體利益之間,在自由和博愛之間,在“我想”和“我們想”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機場的行李檢查,飛機上的禁菸,高速公路上的酒精檢查和限速,這些都是社會為確保公共利益而對個人權利做出的一些調節。環境中的一些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汙染,不能捕鯨,不能砍伐森林)同樣也是以犧牲暫時的個人自由來換取長遠的共同利益。一些個人主義者警告說,這些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會把我們沿著光滑的繩索拖入一個陷阱當中,我們將失去更重要的自由。如果今天我們讓他們檢查行李,那麼明天他們就有可能敲開我們家的大門。如果今天我們讓他們檢查香菸廣告和電視上的色情節目,那麼明天他們可能就會從我們的書房把書拿走。如果今天我們禁止了手槍,那麼明天他們可能就會收繳我們打獵用的來複槍。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能冒著壓制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的風險嗎?集體主義者回答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在個人利益和社會穩定之間做一個平衡,我們會遭受更嚴重的社會弊病,那時可能又該呼籲需要一個專制性的鎮壓了。
毫無疑問,隨著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之間衝突的繼續,文化之間和性別之間的知識可以使我們看到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從而使我們對自己的價值觀看得更加清楚。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是否遇到過這樣的情形,你個人的權利被公共權利限制(比如說,一個約束法案禁止你的狗在公園自由跑動)?你能否指出這樣的情境,即別人行使他們的自由(比如把音樂開得很響)傷及了你和另一些人的利益?在個人和公共權利之間怎樣才能做到很好的平衡呢?
聯繫社會
本章介紹了埃里奧特·阿倫森(Elliot Aronson)的關於“拼圖技術”來進行合作學習的工作——一個有效學習和促進社會融合的技術。也許你已經在前文接觸到介紹阿倫森關於世俗的現實主義的工作(第1章),還有他關於“說服”的研究(第7章),以及關於“稱讚和吸引力”的研究(第11章)。
第四編
應用社會心理學
通觀全書,通過將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和研究成果同日常生活聯繫起來,我把實驗室的研究同生活聯結起來。現在,我們回憶一下這些原理,將其應用在三種實際情境中。第1章“社會心理學在臨床領域中的應用”,是將社會心理學用於評價和促進人們的身心健康。第15章“社會心理學在司法領域中的應用”是探索個體陪審員以及他們作為群體在進行判決時,社會思維和社會影響的作用。第16章“社會心理學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是探討在因人口增長、過度消費以及全球變暖引起的生態危機面前,社會心理學原理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第14章 社會心理學在臨床領域中的應用
什麼導致了臨床診斷的偏差
相關錯覺
事後聰明與過分自信
自我證實的診斷
臨床預測與統計預測
啟示
伴隨行為問題的認知過程是什麼
抑鬱
孤獨
焦慮
疾病
社會心理治療方法有哪些
通過外顯行為引發內在變化
打破惡性循環
通過對成功的內在歸因維持變化
通過社會影響來進行治療
社會關係如何促進健康與幸福感
親密關係與健康
親密關係與幸福感
個人後記:提升幸福感
生命的主要內容(甚或是大部分內容),並不是各種事實與場景,而是人們頭腦中永不停息地呼嘯著的思想的風暴。
——馬克·吐溫(1835~1910)
如 果你是一名典型的大學生,你可能會偶爾感到輕微的抑鬱。也許你有時感到對生活不滿意,對未來氣餒、悲傷,沒有胃口,缺乏精力,無法集中注意力,甚至還可能懷疑生命的價值。也許你認為令人喪氣的成績危及到你事業的目標。也許一段關係的破裂使你陷入絕望。在這些時候,關注於自我的焦慮只會令你的情緒更加惡劣。對於大約10%的男性和幾近20%的女性而言,生活中情緒低落的階段不僅僅是暫時的憂傷情緒,而是一段甚至更多的抑鬱事件,持續幾周而沒有明顯緣由。
在眾多繁榮的應用社會心理學研究領域中,有一個領域將社會心理學的概念與抑鬱,以及其他諸如孤獨、焦慮、生理疾病、快樂和健康之類的問題聯繫起來。這個聯結社會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的研究領域,探索四個重要問題的答案:
作為普通民眾或職業心理學家,我們應怎樣改進我們對於別人的診斷和預測?
我們對於自己以及他人的想法,是怎樣造成抑鬱、孤獨、焦慮和健康狀況不佳之類的問題的?
怎樣才可能轉變這些適應不良的思維模式?
親密的、支持性的關係,對健康和幸福感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在這一章裡,我們將探討這些問題的答案。
什麼導致了臨床診斷的偏差
我們在第2~4章中討論過的對人們的社會決策產生影響的因素,是否也會影響臨床心理學家對來訪者的臨床診斷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臨床心理學家(以及他們的來訪者)需要警惕哪些偏見呢?
一個假釋委員會正在與一名已定罪的強姦犯交談,並考慮是否要釋放他。一位臨床心理學家考慮她的病人是否有嚴重的自殺傾向。一位內科醫生注意到病人的症狀並推測其患癌症的可能性。一位學校的社會工作者思考著:無意中聽到的一名兒童的恐嚇是小男子漢的玩笑,是一時的衝動,還是一個潛在的校園謀殺案的信號?
所有這些專業人士都必須決定,是作出主觀的判斷還是客觀的判斷。他們應該相信自己的直覺嗎?他們應該聽從內心的本能反應?他們的第六感?他們內在智慧?抑或是,他們應該依賴於公式、統計分析和計算機處理得出的預測之類的知識?
在這場心與腦的較量中,大部分臨床專家都站到了心這邊。他們聆聽著自身經驗傳來的低語,一個靜悄悄的聲音在提示著他們。他們不願用冷冰冰的公式計算來決定活生生的人們的未來命運。正如圖14-1所示,與那些非臨床(更多的以研究為導向的)心理學家相比,臨床心理學家更歡迎這種非科學的“認識方式”。感覺勝過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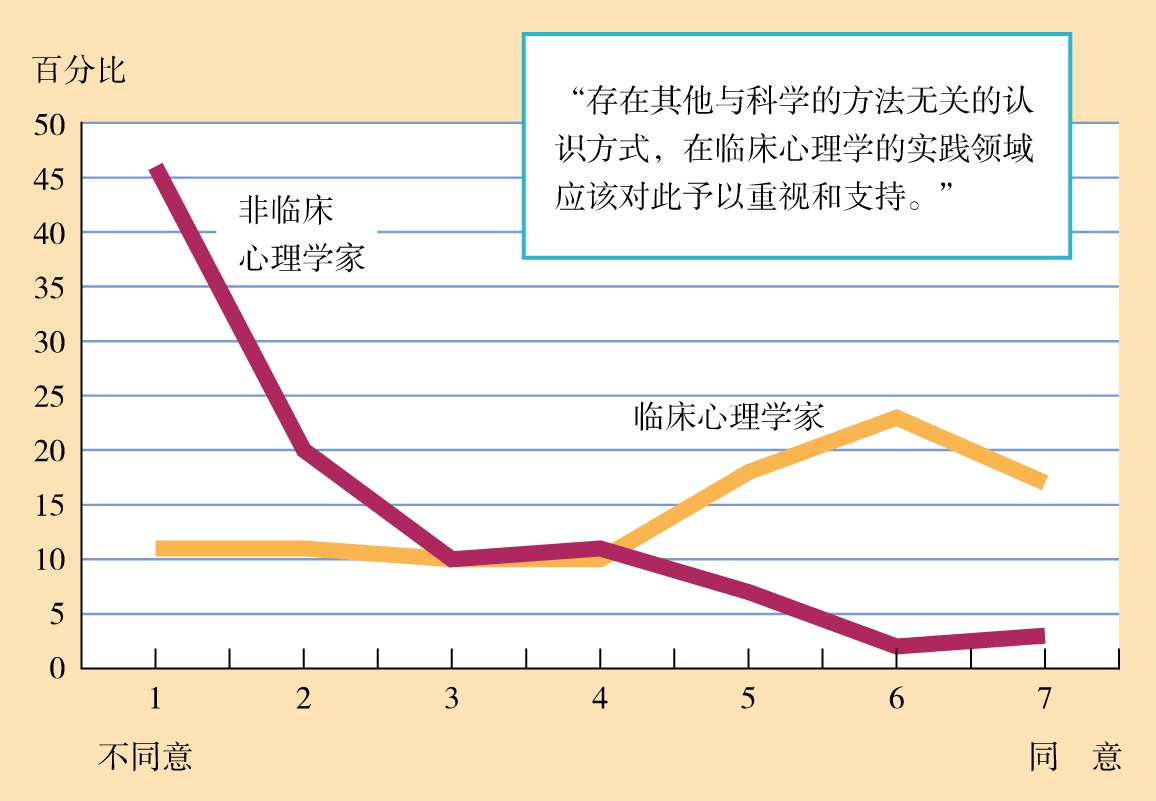
圖14-1 臨床判斷直覺
當努涅斯等人(Nunez,Poole,& others,Memon,待發表)對美國的臨床和非臨床心理學家做取樣調查時,他們發現了“兩種文化”——一類人對“其他認識方式”持懷疑態度,另一類人則幾乎完全接受。
資料來源:From Nunez,Poole,& Memon,inpress.
這些臨床診斷也同樣是社會 決策,因此也很容易受到相關錯覺、事後聰明造成的過分自信以及自我證實的診斷的影響(Maddux,1993)。讓我們來看看,為什麼提醒心理健康工作者人們是怎樣形成印象(和錯誤 印象)的,可以幫助他們避免嚴重的誤診(McFall,1991,2000)。
相關錯覺
讓我們來看下面的法庭記錄,其中描述了一位律師(律)詢問一位看起來很有自信的心理學家(心)的過程:
律:你要求被告畫一幅人像?
心:是的。
律:這是他畫出來的人像?這幅畫向你暗示了關於他人格的什麼信息?
心:你可以注意到這是一幅男性背面的畫像。從統計上來說,非常罕見。它暗示了一種隱藏的負疚情緒,或者是在逃避現實。
律:那麼這幅女人的畫像呢,是否向你暗示了什麼?如果有,那又是什麼?
心:這一部分暗示了對女性的敵意。這種姿勢,放在臀部上的手,堅毅的臉,嚴厲的表情。
律:還有別的嗎?
心:耳朵的大小暗示了一種偏執的觀念,或是幻覺。同時,腳的缺失暗示了一種不安全感。(Jeffery,1964)
像很多臨床診斷一樣,這裡的假設是:測驗的結果反映了某些重要的信息。真的是這樣嗎?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驗證。讓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來進行和解釋測驗。讓另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來評定這個被試的症狀。並對許多人重複這個過程。證據就在這個實驗中:測驗的結果是否真的反映了相應的症狀?一些測驗確實有很強的預測性。但另一些,如上面提到的畫人測驗,與實際症狀的聯繫就遠遠小於測驗使用者的假設(Lilienfeld & others,2000)。那麼,為什麼臨床心理學家還是對無所助益或是模稜兩可的測驗表現得這麼有信心呢?
由查普曼等人(1969,1971)進行的開創性實驗能幫助我們瞭解其中的原因。他們邀請了一些大學生和一些臨床心理學家一起研究測驗的表現和結果診斷。假如學生或心理學家期望 得到一種相關,那麼他們大多能得到 這種相關,無論數據是否支持這種結論。例如,有些臨床心理學家相信多疑的人會在畫人測驗中畫出奇異的眼睛,那麼他們就會覺察到這種聯繫——即使在呈現給他們的例子中,多疑的人比不多疑的人更少地畫出奇異的眼睛。相信兩種事物之間存在聯繫,使他們更可能注意到支持這種聯繫的證據。只要相信就能看見。
不僅是臨床心理學家,錯覺性的想法也同樣發生在政治分析者、歷史學家、體育解說員、人事主管、股票經理人和許多其他的職業中,包括指出這種現象的心理學家。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也時常忽略自己理論分析的缺點。我非常希望假定我關於真理的一個理念是真理,那 就是無論我多麼努力,我都不能看見自己的錯誤。任何一種學術刊物都需要編輯來審稿,就是對此的證明。在過去的30年裡,我看了許多關於我自己手稿和我對別人手稿的審稿意見。我的體會是:指出別人的漏洞,比發覺自己的錯誤要容易得多。
事後聰明與過分自信
假如我們認識的人自殺了,我們會有什麼反應?一個通常的反應是,我們或與這個人親近的人,應該能預料並阻止他自殺:“我們事先就應該知道。”在事後聰明的情況下,我們能看見自殺的信號和呼救的請求。一個實驗給了被試關於一個後來自殺了的抑鬱患者的描述。與沒有事先被告知這個人後來自殺的被試相比,那些事先知道他自殺的被試更傾向於說他們“已經預見到”他的自殺(Goggin & Range,1985)。而且,如果被試事先知道這個人自殺,他們對其家人的反應是更負面的。在一個悲劇之後,一種“我應該事先知道”的現象可以使家人、朋友和治療師陷入無限的負疚感之中。
羅森漢(Rosenhan,1973)和他的7位同事提供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來驗證事後解釋的潛在錯誤。為了測試心理健康工作者的臨床洞察力,他們每個人各自到一家精神病院的入院部,並抱怨說自己“聽見說話聲”。除了名字和職業是假的,他們如實報告了他們的生活史和情感狀況,並且沒有表現任何進一步的症狀。結果他們大多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在醫院住了兩到三週。接著醫院的治療師從這些假病人的生活事件和在院表現中找到了“確認”和“解釋”診斷結果的證據。羅森漢講述了一個假病人的經歷:這個病人告訴醫生他幼年時與母親關係很好但是和父親很疏遠。而在青春期和後來的日子裡,他和父親變成了好朋友,和母親的關係卻變得疏遠了。他現在和妻子的關係非常親密和融洽,除了偶爾會有互相生氣的時候,兩個人很少有矛盾。他也很少打孩子。
假病人的醫生,“知道”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便這樣解釋該病人的問題:
這個39歲的白人男性……從童年開始就對親密關係表現出相當矛盾的態度,並一直持續到現在。他與母親的融洽關係到青春期就結束了。而他和父親原來疏遠的關係後來被他自己描述為非常親密。他的感情缺乏穩定性。他努力想控制自己對孩子和妻子的情緒,但是這種努力被不時發生的爭吵和打孩子的情況所破壞。他也提到他有幾個好朋友,但可以感覺到在這些關係中他也是很矛盾的。
羅森漢後來告訴一些同行(這些人得知他的有爭議的實驗後認為這種錯誤不會在他們的醫院發生)在今後三個月中,將會有一個或更多的假病人會到他們醫院的入院部去。三個月後,羅森漢問這些同行,在這三個月裡入院的193名病人中有幾個是假病人。結果在這193名新入院的病人中,有41名被至少一個醫生認為是假病人。而事實上,沒有一個病人是真正的“假病人”。
自我證實的診斷
我們已經討論了心理健康工作者有時會因為相關錯覺和事後聰明的解釋而遭到質疑。第三個與臨床診斷有關的問題,就是人們往往會提供符合臨床醫生期望的信息。在明尼蘇達大學,斯奈德(Snyder,1984)與斯旺以及其他研究者合作的一系列巧妙的實驗中,他們要求面試者根據受訪者的不同特質對一些假設進行驗證。為了體驗他們的實驗情境,想像你自己與一個未曾謀面的人初次約會,而對方事先被告知你是一個放蕩不羈、生性開朗的人。為了看看這種說法是否正確,你的約會將充滿了類似下面的問題,“你曾經在別人面前做過很瘋狂的事情嗎?”當你在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你會不會表現得和你被問及一些試探你是否害羞和孤僻的問題時不一樣呢?
斯奈德和斯旺發現,人們總是通過尋找能夠驗證某一特質的信息來做測驗。例如人們想驗證某個人是否外向,他們就會問一些與外向有關的問題。(“當你想使一個聚會的氣氛活躍起來的時候,你會怎麼做?”)當想測驗一個人是否內向的時候,人們就更傾向於問,“是什麼原因令你不能真正與人坦誠相見?”這些問題使得被測驗是否外向的人表現得更加愛社交,而使被測驗是否內向的人表現得更加害羞保守。我們的假設把人們塑造成我們所期望的類型。
在印第安納大學,法齊奧和他的同事(Fazio & others,1981)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並發現被問及“外向問題”的被試後來真的覺得自己比那些被問及“內向問題”的被試更加開朗。而且,他們明顯地變得更加開朗。在做完測驗後,實驗者的同伴到休息室會見每個被試,結果有70%的概率能猜中之前被試參加的是內向還是外向的測驗。類似地,對假定的強姦案受害者所提的問題的結構——“你和彼得跳舞了嗎?”與“彼得和你跳舞了嗎?”——會對到底誰應該為這個案件負責任的判斷有微妙的影響(Semin & De Poot,1997)。
當面對一堆結構化的題目可以選擇時,即使是最有經驗的心理治療師,在測驗被試是否外向時,也會傾向於選擇那些更能引發被試的外向行為的問題(Copeland & Snyder,1995;Dallas & Baron,1985;Snyder & Thomsen,1988)。甚至在自己編制問題時,如果預先存在一個確定的假設,治療師的期望也可能會影響問題的編制(Devine & others,1990;Hodgins & Zuckerman,1993;Swann & Giuliano,1987)。不論在臨床診斷時還是在實驗室,強烈的信念都很容易產生自我證實的現象。
自我證實的偏見也同樣存在於人們評價他們自己的時候。設想這樣一種情境:你覺得你的社交生活快樂嗎?孔達和他的同事(Kunda & others,1993)在滑鐵盧大學和其他地方的學生中做了測驗。結果發現,與被問“你覺得你的社交生活不快樂嗎?”的被試相比,前者更多地搜索自己記憶中快樂的社交生活事件,因此他們在實驗結束時感到更為快樂。嘗試一下,你自己也可以發現這個現象。
在其他的實驗中,斯奈德和他的同事(1982)嘗試使被試搜索與他們被測試的特質相悖的行為。在其中一個實驗中,他們告訴負責訪談的人,“如果能找出受訪者那些與他們的刻板印象不符合的方面,那將是很有意義的。”在另一個實驗中,斯奈德(1981a)聲稱,誰編制的問題能發掘有關受訪者的信息最多,誰就能得到25美元。然而,自我證實的偏見依然存在:人們在做外向特質測驗時,仍然拒絕選擇使用那些“內向”問題。
通過斯奈德的實驗,你應該能瞭解,為什麼接受心理治療的人總是符合他們的治療師的理論假設了吧(Whitman & others,1963)。雷諾和埃斯蒂斯(Renaud & Estess,1961)就個人生活史訪談了100位健康、成功的成年男性,他們驚訝地發現這些受訪者的童年都充滿了“創傷性事件”,和某些人的緊張關係,父母糟糕的決定——這些因素通常會被用來解釋精神問題。當弗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學家試圖尋找早期童年經歷中的創傷性事件時,他們往往都會發現他們的直覺得到了驗證。所以,斯奈德(1981a)這樣推測:
一個治療師如果(錯誤地)相信男同性戀童年時代與母親的關係不好,那麼他就很可能會小心翼翼地刺探這個男同性戀者與母親的回憶中的(或者臆造的)緊張關係。但是在他的病人是異性戀者時,他就不會詢問關於他們與母親的關係問題。毫無疑問,任何人都會回憶起一些與母親產生摩擦的事件,儘管可能是很偶然發生的、細小的事情。
那麼治療師尋找能證實自己直覺的信息這個現象,是否能用來解釋“恢復的記憶”呢?比如在巴斯和戴維斯(1994)的《痊癒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 )一書中,他們指出童年遭到過性虐待的兒童成年後更可能體驗到抑鬱、羞愧、無價值和無助感。當病人出現這些症狀的時候(其實可能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一些治療師就會積極地搜索能驗證他們之前關於性虐待的假設的證據(Harris,1994;Loftus,2000;Loftus & Ketcham,1994;Poole & others,1995)。這些治療師會這樣解釋:“那些曾被性虐待的人經常會有你的這些症狀,所以你可能被虐待過。”假如病人不能回憶起任何被虐待的經歷,治療師可能會使用催眠,引導性的想像,或是釋夢等手段來試著發現那些肯定自己假設的信息。這種蒐集肯定信息的手段,使得一些病人虛構了從未存在過的經歷。
臨床預測與統計預測
考慮到事後聰明和自我證實的診斷,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臨床醫生和訪談者會對自己直覺的判斷更有信心而不怎麼相信統計的結果(例如用過去的成績和能力傾向測驗的結果,來預測學生在研究生院或職業學校的成績)。但當研究者將統計預測和直覺預測相比較時,統計預測的結果往往是正確的。統計預測確實不夠可靠,但是直覺——即使是專家的直覺——更不可靠(Faust & Ziskin,1988;Meehl,1954;Swets & others,2000)。
在人們證明統計預測比直覺預測更可靠的30年後,米爾(1986)找到了比以往更為有力的證據:
在社會科學中,關於這個有爭議的話題的眾多研究得到的結果是最一致的……當你進行了90項調查,預測從足球比賽的結果到肝病的診斷結果等一系列事件,而在這些預測中,只有6項的結果勉強能支持臨床心理學家的預測,是時候做出現實的結論了。
看看這一有爭議性的研究中的例子:
在《建築在神話之上的心理學與精神療法》(House of Card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ilt on Myth )一書中,道斯(1994)打擊了臨床心理學家對自己直覺的自信。例如,20世紀70年代,位於休斯敦的得克薩斯醫科大學每年錄取150名學生,錄取時由訪談者從800名合格的候選者中篩選出150人。而招生機構突然要求他們再多錄取50個人時,他們只能從還沒有被別的學校錄取的候選人裡面挑出50個人——這些人原來面試時得分普遍很低。那麼前150名和這50名今後的表現有什麼區別嗎?完全沒有。這兩個群體中各有82%的人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而且相同比例的人獲得優等學位。甚至在他們實習期結束一年後,兩個群體的表現也是不相上下。結論是毫無疑問的:某些人只是在面試方面沒有天賦。
加拿大律師協會(Canada's Ministry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的一個研究小組分析了64個樣本,其中包含25000餘個存在心理障礙的罪犯的資料。什麼因素能最好地預測未來的犯罪行為?和其他研究犯罪行為的研究一樣,答案是過去的犯罪行為。而什麼是最差的預測因素呢?是臨床心理學家的診斷(Bonta & others,1998)。
在明尼蘇達大學的一項元分析研究中,通過對134項預測人類行為或心理、醫藥診斷或預測的研究進行總結,研究小組得到了類似的結論(Grove & others,2000)。只有在8項研究中,其中大多是有關醫藥、心理健康或教育情境方面的,臨床預測的效果超越了“機械的”(統計的)預測。而在相當於這個數字的8倍(63個)的研究中,統計預測的效果更佳(其餘的則不分上下)。那麼當臨床心理學家有機會做面對面的訪談時,他們預測的效果是否會不一樣呢?確實不一樣,研究表明:在能進行訪談的條件下,臨床心理學家的預測要更為差勁。因此研究者總結道:“相對於統計預測而言,臨床心理學家的預測準確性存在很大的問題,因此臨床預測的支持者肩負重擔,他們必須證明臨床預測更準確或更為經濟有效才行。”
假如我們把統計預測和臨床心理學家的直覺預測結合起來,結果又會怎樣呢?如果我們把關於某個人未來的學業成就或釋放後再次違法或自殺機率的統計預測結果給專業的臨床心理學家,讓他們去修正和改進這個預測,又會怎樣呢?可惜的是,在僅有的幾個這樣的實驗中,沒有被心理學家改進的預測結果反而比較好(Dawes,1994)。
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臨床心理學家繼續使用羅夏墨跡測驗,繼續用直覺來預測假釋者是否會犯罪,人們是否會自殺,是否可能在童年受過虐待?除了純粹的無知,米爾認為,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關於道德的錯誤觀念”:
假如我試圖用低效而非有效的手段來預測一個學生、一個罪犯或一個抑鬱病人的重要事件,而收取的費用卻相當於我提高預測精確度所需的十倍,這就不是很道德了。這些不怎麼準確的預測指標感覺上卻更好,更有人情味,更樂於使用——而這只不過是個低劣的藉口罷了。
這些話聽起來令人震驚。米爾和其他研究者是否低估了我們的直覺呢?想知道他們的發現為什麼顯然是正確的,只要考慮一下之前提到的研究生錄取面試是怎樣評價人們的學習潛能就明白了。道斯(1976)解釋了為什麼在預測例如研究生學習成績之類的結果時,統計預測比單憑直覺的預測更準確: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花半小時面試,能比綜合所有諸如GPA、GRE成績和推薦信的評價之類的因素更好地選出合適的人?我認為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們高估了自己的認知能力。而這的確是我們自負的想法。比如,試想一下,GPA是怎麼得到的。因為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申請讀研時的GPA都是三年半大學成績的總結,它是至少28門課,如果是採用普遍的四學期制的學校則達到50門課成績的總結……而面試者只用半小時看檔案或面談,他們認為自己對候選人的評價能比三年半來20~40位教授的評價更準確……最後,如果我們一定要忽略GPA,那麼惟一可能的理由就是這個候選人特別優秀,即使他的成績沒有顯示出這一點。有什麼證據,能比精心設計的能力傾向測驗更能證明一個人的聰明程度呢?儘管教育考試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存在很多缺陷,但我們真的認為自己的判斷能比ETS的測驗更好地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嗎?
啟示
詹姆斯·馬德斯(Maddux,1993)總結道,專業的臨床心理學家“很可能受到各種陰險的錯誤和偏見的影響”。他們
經常是相關錯覺的受害者;
太容易對自己的事後聰明充滿自信;
經常因為自我證實的判斷而造成誤診;
經常對自己基於直覺的臨床判斷太有信心。
這些給臨床心理學家的啟示,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要注意病人口頭上對你的話表示贊同,但可能實際上並不意味著它是正確的。要避免因為自己的期望而建立實際上不存在的關聯,或是僅僅因為幾個容易想起的引人注意的事件支持這種相關,就錯誤地認為這種聯繫是普遍的。要信賴你的記錄而不是你的記憶。要認識到事後聰明是很具誘導性的:它能讓你感到過分的自信,並且因為沒有能預見到事情的發生而過分自責。要防止自己只問那些支持自己假設的問題,試著從相反的方向來考慮並嘗試著測試這種問題(Garb,1994)。
關於相關錯覺的研究,不僅對心理健康工作者有啟發性,同時也提醒了所有的心理學家。托馬斯(1978)關於生物學的一番話,也同樣適用於心理學:
我所知道的最確鑿的也是我最有信心的一個事實,就是我們在自然面前仍然是全然無知的。事實上,我把這一點作為過去100年裡生物學領域最重大的發現……正是因為我們發現自己的無知是多麼廣泛而深刻,才成就了20世紀人類知識的突飛猛進。最終,我們正在直面這種無知。而在此前的時代裡,我們或是假裝已經懂得了自然的規律,或是對問題視而不見,亦或是簡單地編造一些故事來填補知識的空白。
心理學僅僅跨出了探索人類狀況的一小步。一些心理學家無視於自己的無知,根據自己的理解建立了一些理論來填補知識的空白。直覺的觀察結果看起來支持這些理論,儘管有時這些理論本身是互相對立的。關於錯覺思維的研究再次使我們認識到必須保持謙卑:它提醒心理學家們,為何在指出自己的理論是真理之前,必須先對他們的預想進行檢驗。尋求事實真理是科學的最終目標,儘管有時它與一貫的錯覺相悖。
我並不是 說,科學方法能解決人類所有的疑問。有很多問題科學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有很多認識方法是科學無法記錄的。但是科學的確是 檢驗關於包括自然和人類本質的假設的一種手段。對可能得到的結果進行評價的最好方法,就是系統的觀察和實驗——這也是社會心理學最重要的根基。我們也需要有獨創性的思維,否則我們就永遠只能做做瑣碎的測試。但所有那些影響深遠的理論都是心理學家們從無數相互競爭的論斷中通過研究篩選出來的。科學永遠是直覺和嚴謹論證的結合,是創造性的直覺和懷疑批判精神的結合。
小結
當精神病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診斷和治療病人時,他們經常會出現相關錯覺。事後聰明使人們在事後解釋起當初的症狀來總是顯得很容易。事實上,事後的解釋會導致臨床判斷的過分自信。在與來訪者的交流中,錯誤的診斷往往會自我證實,因為治療師總是傾向於問那些能夠肯定他們假設的問題。
研究表明,依靠直覺的判斷頻頻出錯,因此必須用嚴格的檢驗來證明直覺的結論。科學方法不能解答所有疑問,而且很容易為偏見所左右。但值得慶幸的是,它能幫助我們明辨對錯。
伴隨行為問題的認知過程是什麼
心理學家最感興趣的前沿研究領域之一,就是與精神疾病相伴的認知過程。那些抑鬱、孤獨、害羞或是容易得病的人,他們記憶、歸因和期望是怎樣的呢?
抑鬱
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抑鬱患者都是消極思考的人。他們透過自己的黑色眼鏡來看這個世界。對於那些嚴重抑鬱的人——那些感到沒有價值,渾渾噩噩,對朋友和家庭都沒有興趣,不能正常飲食和作息的人——這種消極的思維往往會進一步惡化他們的處境。他們極度消極的觀點,使他們放大了痛苦的體驗而縮小快樂的體驗。一個抑鬱的年輕女性這樣說,“真實的那個我,是毫無價值而且無法照顧自己的。我無法進行我的工作,因為我被疑惑困住了。”(Burns,1980,p.29)。
聚焦 一個醫生眼中的社會心理學
作為一名癌症專家和需要管理大批員工的主任醫師,這本書幫助我理解了我所觀察到的種種人類行為。例如:
對病歷記錄的回顧證實了“我應該事先知道”的現象。那些對同事所寫的病歷記錄進行評價的醫生,經常因為有事後聰明而認為,像癌症或闌尾炎這種病應該很容易診斷並更為迅速地展開治療。一旦你知道了正確的診斷結果後,回過頭來看之前的症狀就很容易解釋了。
對於很多我認識的醫生來說,他們進入這個行業的內在動機——幫助別人,獻身科學——很快就被優厚的薪酬所淹沒。他們從事這個行業的快樂不久便消失了。外在的獎勵成了工作的理由,醫生失去了為他人服務的動機,只為了獲得“成功”而努力,而且把薪水高低作為評判的標準。
“自我服務偏見”一直存在。當事情進展順利時,醫生很樂意把功勞歸於自己。而當事情不順利——病人被誤診或沒有康復或是死了——我們就經常把責任推到別的方面。比如我們沒有得到足夠的信息,或者這件事註定是會發生的。
我還觀察到很多“信念固著”的例證。即使有科學事實告訴人們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人們還是不可思議地要堅持他們錯誤的信念,認為這是一種同性戀的疾病,或是自己必須避免蚊子的叮咬來防止受傳染。這讓我很想知道:我怎樣才能有效地告訴人們他們需要哪些知識,以及應該如何行動?
在觀察了醫生們的態度和診斷過程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就身處在一個大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室中。要了解周圍發生的事情,我覺得社會心理學有很高的價值,並且強烈建議醫學預科生學習該學科。
範德蘭(Burton F. VanderLaan)
芝加哥,伊利諾伊州
扭曲事實還是現實主義
是否所有抑鬱的人都是不現實地消極呢?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Alloy & Abramson,1979)以輕度抑鬱和不抑鬱的大學生為對象進行了研究。他們讓這些學生觀察他們按鍵的時候燈是否會亮。令人驚訝的是,那些抑鬱的學生在預測他們對燈的控制程度時準確性很高。反而那些不抑鬱學生的判斷是扭曲的,他們誇大了自己的控制程度。
這種令人驚訝的抑鬱現實主義 (depressive realism),又被稱為“悲觀而明智效應”(sadder-but-wiser effect),這種現象在多種對於控制或技能的判斷中都出現了(Ackermann & DeRubeis,1991;Alloy & others,1990)。泰勒(Shelley Taylor,1989,p.214)這樣解釋道:
普通人往往誇大自己的能力和受歡迎程度。抑鬱的人卻不這樣。普通人常會在回憶過去的時候加上玫瑰色的光環。抑鬱的人(除了嚴重抑鬱的)在回憶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時則更客觀。普通人大多對自己持正性的評價。抑鬱的人會既描述自己正性的品質又描述負性的品質。普通人一般把成功歸功於自己的能力,而推卸失敗的責任。抑鬱的人則無論成功和失敗,都認為是自己的責任。普通人誇大他們對於周圍發生的事情的控制能力。抑鬱的人就不太容易受到這種控制的錯覺的影響。普通人不現實地相信,未來會賜予很多美好的東西,而糟糕的事情會很少。抑鬱的人對未來有更現實的認識。事實上,幾乎在普通人表現出過分的利己、控制的錯覺和對未來的不現實預期的每一點上,抑鬱的人都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偏見。“悲觀而明智”確實很適用於抑鬱的人。
抑鬱者思維方式的基礎是他們對責任的歸因。試想一下:如果你因為考試沒有考好而責備自己,你可能將原因歸結為你自己不夠聰明或者太懶惰,因此會覺得很鬱悶。如果你將原因歸結為考試不公平或是其他不能由你控制的環境因素,那麼你更可能會覺得很氣憤。在包含了15000名被試的超過100個研究中,抑鬱者比正常人更多地表現出消極的解釋風格 (explanatory style)(Sweeney & others,1986;Peterson & Steen,2002,見圖14-2)。他們更傾向於將失敗和挫折的原因歸結為穩定的 (“它將會一直持續下去”)、普遍的 (“它會影響我做的每件事情”)和內在的 (“這全是我的錯”)。艾布拉姆森和她的同事(1989)認為,這種消極的、過度泛化的、自我責備的思維,是一種無助感的體現。

圖14-2 抑鬱的解釋風格
抑鬱是與一種消極的、悲觀的解釋失敗的方式相關聯的。
研究背後的故事:
泰勒對正性錯覺的研究
幾年前,為了研究對嚴重壓力事件的適應,我對一些得過癌症的病人進行了訪談。我驚奇地發現,對於一些病人來說,得癌症的經歷不僅帶來了痛苦,也同樣使他們獲益。很多病人告訴我,他們認為自己因為這個經歷而變得更好。他們覺得自己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適應癌症,他們相信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可以對癌症進行更好的控制,他們也相信自己將來不會再得癌症,儘管我們從他們的病歷中瞭解到他們的癌症很可能復發。
因此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人們能把最差的情形解釋為好事,於是從此我開始從事關於“正性錯覺”的研究。通過研究,我們很快發現,未必在經歷創傷事件後才表現出正性錯覺。大多數人,包括大部分的大學生,都認為他們自己要好於一般人,認為自己對周圍環境的控制程度高於真實水平,認為自己未來的生活比實際可能的更好。這種錯覺並非一種不適應環境的信號,而是恰恰相反。良好的心理健康狀況,正是建立在這種能把事情看得比實際好一些,並能在最為黯淡的情形裡看到光明的能力之上。
負性思維是抑鬱的原因還是結果
伴隨著抑鬱的這種特定認知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雞與蛋”的問題:究竟是抑鬱的心境導致了負性的思維還是負性的思維導致了抑鬱呢?
抑鬱心境導致負性思維 正如我們在第3章中所見,我們的心境毫無疑問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當我們感到 快樂時,我們的思維 也是快樂的。我們看見的和回憶起來的,都是一個美好的世界。當我們的情緒跌入低谷的時候,我們的思維就會進入另外一種模式。玫瑰色的眼鏡被摘去了,我們換上了黑色的眼鏡。現在,惡劣的心境主導著我們對負性事件的回憶(Bower,1987;Johnson & Magaro,1987)。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看起來很差,自我概念變得很糟糕,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變得黯淡,別人的行為看起來更加險惡(Taylor,1986;Mayer & Salovey,1987)。當抑鬱程度加深,記憶和期望都急速下降;當抑鬱消散時,思維也變得明快起來(Barnett & Gotlib,1988;Kuiper & Higgins,1985)。因此,當前 正處於抑鬱狀態的人回憶父母時,更多地認為自己受到拒絕和懲罰。但之前 出現抑鬱的人和從未抑鬱的人一樣正性地回憶父母(Lewinsohn & Rosenbaum,1987)。(當你聽到抑鬱的人貶低他們的父母時,記住:情緒改變了他們的記憶。)
赫特和他的同事(Hirt & others,1992)在對印第安納大學籃球迷的研究中證明,即使只是由於球隊失利造成的短暫的惡劣情緒,也可以使思維變得消極。在球迷看到自己球隊輸球而鬱鬱不樂或取勝而得意洋洋後,研究者讓他們預測球隊未來的表現以及他們自己的表現。在一次的失利之後,人們不僅對球隊的未來持消極的預期,他們對自己在投標槍、字謎遊戲和約會方面的表現也都持更消極的預期。當事情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式進行時,我們好像就會認為,它永遠也不會按照我們的意願進行了。
抑鬱的心境也會影響行為。一個退縮、陰鬱和哀怨的人不能給別人帶來歡樂和溫暖。斯特拉克和科因(Strack & Coyne,1983)發現,抑鬱者現實地認為,別人並不欣賞自己的行為。他們悲觀和惡劣的心境引起了社會拒斥(Carver & others,1994)。抑鬱的行為還會引起別人相應的抑鬱。有抑鬱的室友的大學生傾向於表現出一定的抑鬱症狀(Burchill & Stiles,1988;Joiner,1994;Sanislow & others,1989)。在約會的情侶中,抑鬱也經常是會傳染的(Katz & others,1999)。
因此,抑鬱的人更可能面臨離婚、被解僱、被迴避的風險,而這又加重了他們自己的抑鬱(Coyne & others,1991;Gotlib & Lee,1989;Sacco & Dunn,1990)。他們還會從那些不喜歡他們的人的觀點中,證明並進一步增強他們不良的自我概念(Lineham,1997;Swann & others,1991)。有這樣一個實驗,主試提供了兩份由不同大學生寫的關於被試的人格評價的報告,其中一份是讚許的,一份是批評的,被試可以從中選擇一份來看。25%的高自尊的人和82%的抑鬱者選擇看那份批評性的報告(Giesler & others,1996)。
抑鬱會對認知和行為產生影響。那麼抑鬱是否有認知方面的根源呢?
負性思維導致抑鬱心境 抑鬱在我們體驗到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是很自然的——失業、離婚或被排斥,生理上的嚴重創傷——任何一種打擊都會使我們懷疑自己是誰、自己的存在是否有價值(Hamilton & others,1993;Kendler & others,1993)。這種思考是有意義的;在抑鬱時期休止狀態中的洞察,可能會使得我們獲得在未來的生活中處理事件更好的策略。但有抑鬱傾向的人對不良事件的反應總是自我關注的反思和自責(Mor & Winquist,2002;Pyszczynski & others,1991)。他們的自尊隨著成功急劇攀升又隨著威脅急劇下降,波動得很厲害(Butler & others,1994)。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容易受到輕微 壓力的影響?證據表明,壓力導致的思慮受到消極歸因風格的過濾與選擇,導致最常見的結果就是抑鬱(Robinson & Alloy,2003)。薩克斯和巴吉特爾(Sacks & Bugental,1987)讓一些年輕的女性接觸一個有時候比較冷漠、不友好的陌生人,營造出一種難堪的社會情境。與樂觀的女性不同,那些有消極歸因風格的女性——把不好的事情歸因成穩定的、廣泛的、內在的原因的那些女性——因這種社交的失敗感到抑鬱。更重要的是,她們對之後遇見的人更多地表現出一種敵對行為。她們負性的思維導致了負性的情緒反應,進而導致了負性的行為。
在實驗室之外,對兒童、青少年和成人的研究都證實了,那些具有消極歸因風格的人更容易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時變得抑鬱。有一個為期兩年半的研究對一些大學生每6周進行一次觀察(Alloy & others,1999)。只有1%的樂觀思維風格的學生在大學生活開始時出現過抑鬱時期,而17%的悲觀思維風格的學生出現了這種抑鬱時期。塞利格曼(Seligman,1991,p.78)說過,“嚴重抑鬱,都是由早就存在的那種遇到失敗時的悲觀主義引起的。”更重要的是,那些經過治療不再覺得抑鬱的病人,如果繼續保持消極歸因風格,則很可能在遇到負性事件時再次崩潰(Seligman,1992)。如果那些擁有樂觀歸因風格的人受到打擊,他們通常能很快恢復過來(Metalsky & others,1993;Needles & Abramson,1990)。
萊文森和他的同事(Lewinsohn & others,1985)把這些發現整合為一個統一的關於抑鬱的心理學認識。在他們看來,抑鬱者的負性自我概念、歸因和期望是由負性體驗——也許是學術或事業的失敗,也許是家庭衝突或社會拒斥(圖14-3)——引發的一個惡性循環。對於那些容易抑鬱的人而言,這些壓力引發了陰鬱的、自我關注、自我責備的想法(Pyszczynski & others,1991;Wood & others,1990a,1990b)。這種思慮營造了一種能極大地改變人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抑鬱心境,而這種心境又進一步激發了之後的負性體驗、自我責備和抑鬱情緒。實驗表明,當輕微抑鬱者的注意被轉移到一些外部任務上時,他們的心境也變得明朗起來(Nix & others,1995)。(當人們不那麼關注自己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自身以外的事情上時,他們更容易得到快樂。)因此,抑鬱既是 負性認知的原因也是 它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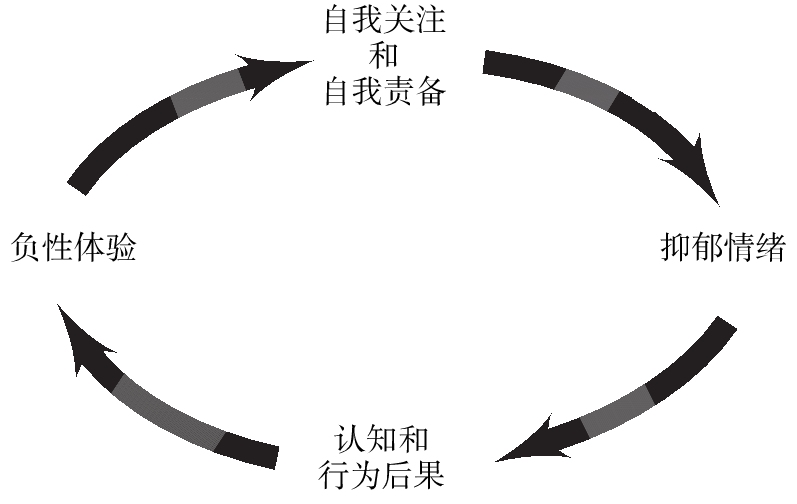
圖14-3 抑鬱的惡性循環
塞利格曼(1991,1998,2002)認為,自我關注和自我責備能為現在西方社會抑鬱的流行提供解釋。例如,在北美,現在的年輕人出現抑鬱的可能性是他們祖父輩的3倍——儘管他們的祖父輩們出現抑鬱的時間可能更長(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1992;Swindle & others,2000)。塞利格曼認為宗教信仰和家庭觀念的淡化,加上個人主義的滋長,導致了事情不順利時的無助感和自我責備。在我們孤獨而沒有任何東西、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時候,失敗的學業、事業和婚姻導致了絕望。假如,像《財富》上那個充滿陽剛之氣的廣告所說的那樣,你可以“自己獨立完成它”,憑藉“你的衝勁,你的勇氣,你的精力,你的野心”,那麼當你沒有 做到的時候,責任該由誰來負呢?在那些重視關係和睦與合作的非西方國家裡,嚴重的抑鬱沒有那麼普遍,人們也較少將個人失敗與負疚感和自責聯繫在一起。例如,在日本,抑鬱者更傾向於報告他們因為使家人或合作者失望而感到羞愧(Draguns,1990)。
這種探討思維風格與抑鬱關係的研究,促使心理學家們也試圖研究思維風格與其他心理問題的關係。那些被極度孤獨、害羞或嚴重虐待所折磨的人們,是怎樣看待他們自己的呢?他們如何回憶自己的成功和失敗?他們對自己的起起落落又是怎樣歸因的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什麼——是他們自己還是其他人?
孤獨
如果把抑鬱比作心理疾病中的感冒,那麼孤獨就可以算作頭疼。孤獨,無論長期還是暫時的,都是痛苦地發現社會關係不如想像當中那麼豐富多彩而有意義。吉爾維爾德(de Jong-Gierveld,1987)在她的研究中發現,荷蘭未結婚或訂婚的成年人更容易感覺到孤獨。這使她推測:現代社會強調個人實現和貶低婚姻、家庭生活的態度,可能是“孤獨的導火索”(同時也是抑鬱的導火索)。和工作相關的流動性也導致了長期的家庭和社會紐帶的減少,同時導致了孤獨的增加(Dill & Anderson,1999)。
感到孤獨和被排斥
但孤獨並不等同於孤單。一個人也可以在一個熱鬧的聚會中感到孤獨。“在美國,只有孤獨但沒有孤單,”皮弗(Pipher,2002)哀嘆道,“只有擁擠的人群卻沒有團體。”在洛杉磯,她的女兒觀察到,“有一千萬人圍著我,但卻沒有一個人認識我。”而一個人也可以完全孤單——就像我此刻在離家5000英里的英國大學隔離的塔樓辦公樓裡,獨自寫這些文字——卻並不感到孤獨。感到孤獨是感到被一個群體排斥、不被周圍的人喜歡、不能和人分享自己的個人感受,或是像個異類一樣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Beck & Young,1978;Davis & Franzoi,1986)。
青少年會比成人更多地體驗到孤獨。給被試每人配備一個尋呼機,在一週中多次地傳呼他們,詢問他們當時在做什麼、心情怎麼樣,結果發現青少年比成人更多地報告說,他們獨自一人的時候感到孤獨(Larsen & others,1982)。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情境下感到孤獨——男性是在被一個群體孤立時感到孤獨,而女性是在被剝奪了一段親密的一對一的關係時感到孤獨(Berg & McQuinn,1988;Stokes & Levin,1986)。據說,男性的關係常常是肩並肩的,而女性的關係則是面對面的。但對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喪偶不久的人而言,失去一個親密的人會造成無法避免的孤獨感(Stroebe & others,1996)。
消極地知覺他人
和抑鬱的人一樣,長期孤獨的人看起來也處於一個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的社會認知和社會行為的惡性循環中。他們也有一些像抑鬱者一樣消極的歸因風格;他們感到自己和別人的交往時給對方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因為不良的社會關係而責備自己,並且認為絕大多數事情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Anderson & others,1994;Christensen & Kashy,1998;Snodgrass,1987)。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一種消極的方式來知覺他人。當他們與一個同性的陌生人或是大學一年級的室友作搭檔時,孤獨的人更容易對另一個人形成負性的知覺(Jones & others,1981;Wittenberg & Reis,1986)。如圖14-4所示,孤獨、抑鬱和害羞有時候能相互加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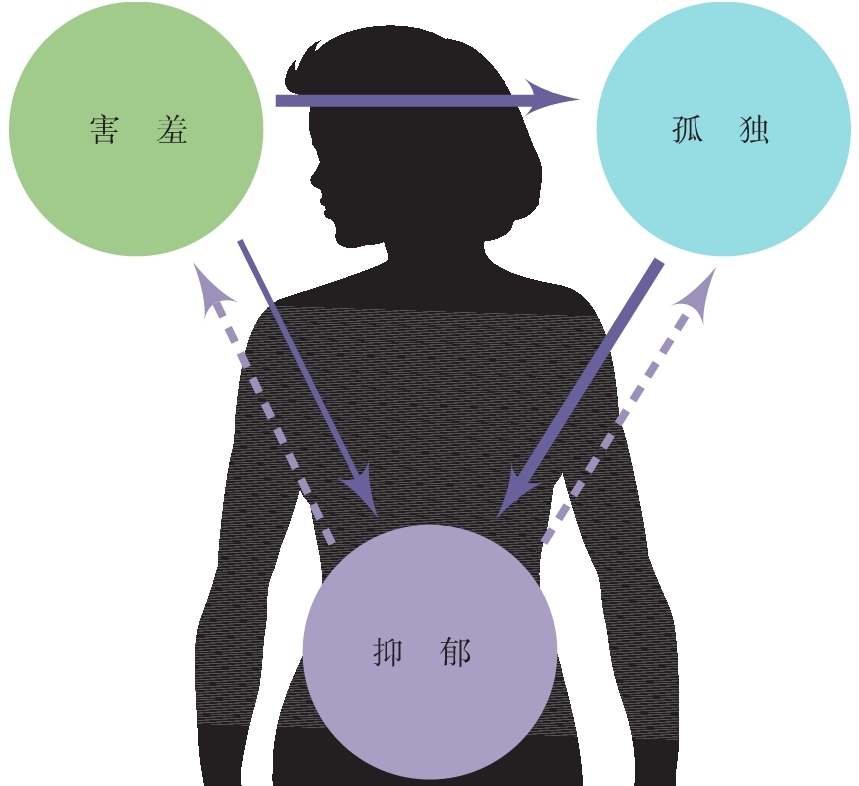
圖14-4 長期害羞、孤獨和抑鬱之間的相互作用
實線箭頭表示主要的因果關係,由迪爾和安德森(Dill & Anderson,1998)總結。
這種負性的觀念不僅反映,而且影響著孤獨者的體驗。認為自己沒有社會價值,以及對他人的消極看法,阻礙了孤獨的人採取行動減少他們的孤獨。孤獨的人經常發現他們在做自我介紹、打電話、參加團隊的時候都有很大的困難(Rook,1984;Spitzberg & Hurt,1987;Nurmi & others,1996,1997)。因為自我表露很困難,他們蔑視那些自我表露太快太多的人(Rotenberg,1997)。他們往往過度敏感,並且自尊很低(Check & Melchior,1990;Vaux,1988)。與不孤獨的人相比,他們在與陌生人聊天時,更多地談論自己的事情而很少關心談話對象的情況(Jones & others,1982)。在這種談話之後,這個新結識的人往往會帶著對這個孤獨者更為負面的印象離開(Jones & others,1983)。
焦慮
去應聘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第一次和某個人約會,闖入一屋子陌生人當中,在一個重要的聽眾面前表演,或是(最常見的恐懼)演講,這些事情差不多會讓每個人都感到焦慮。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害羞或很容易覺得尷尬的人,幾乎在任何自己會被評價的情境中都會感到焦慮。對這些人而言,焦慮更像是一種特質而不是一時的狀況。
懷疑我們在社會情境中的能力
什麼原因會讓我們在社會情境中感到焦慮?為什麼有些人被困在他們自己害羞的囚籠中?施倫克和利裡(Schlenker & Leary,1982b,1985;Leary & Kowalski,1995)用自我展示理論對這些問題作出瞭解答。正如你在第2、4章中看到的,自我展示理論假設:我們都渴望以一種留給別人美好印象的方式展示我們自己。社會焦慮的含義顯而易見:當我們想給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懷疑自己能否做到的時候,我們就會感到焦慮 。這個簡單的原理幫助我們解釋很多研究的發現,每個發現都和你自己的體驗息息相關。我們在以下的時候感到最為焦慮:
和有權勢、位居高位的人交往——他們對我們的印象如何對我們至關重要;
在一種評價情境中,例如第一次見未婚妻的父母;
過分敏感(就像害羞的人經常做的那樣)並將注意集中於自己和自己的行為上;
關注對我們的自我形象有重要意義的事物,例如一個大學教授在一個專業大會上在同行面前表述自己的觀點;
身處一種新奇的或沒有概念的情境中,例如第一次參加學校舞會或是第一次參加正式宴會,在這些場合我們對社交規則並不熟悉。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的傾向就是小心翼翼地自我保護:少說話;避開那些顯示自己無知的話題;言行謹慎;不要過分自信,和善並保持微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希望造成好印象的焦慮經常會造成一個不好的印象(Broome & Wegner,1994;Meleshko & Alden,1993)。然而,假以時日,害羞的人往往能被接受和喜歡。他們很少自我中心,而且謙虛、敏感、謹慎(Gough & Thorne,1986;Paulhus & Morgan,1997;Shepperd & others,1995)。
過分個人化的情境
害羞是一種以過度敏感和擔心別人的想法為特徵的社會焦慮(Anderson & Harvey,1988;Asendorpf,1987;Carver & Scheier,1986)。與不害羞的人相比,害羞的、過分敏感的人(包括很多青少年)或多或少地把一些偶然事件看做是與自己有關的(Fenigstein,1984;Feingstein & Vanable,1992)。當被告知有人正在現場訪談他們時(實際上是一個錄音帶中的訪談者),他們會感到這個訪談者對自己並不太感興趣、不願接受自己(Pozo & others,1991)。
害羞、焦慮的人還會將環境過分個人化,這種傾向導致了焦慮的產生,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會變成偏執狂。他們常常高估了其他人對自己的關注和評價程度。假如他們的頭髮沒有梳理好或是臉上有汙跡,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會注意到,並由此而對他們作出評價。更重要的是,害羞的人對自己的過分敏感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們希望自己不再擔心臉紅、別人的想法和接下來該說什麼。
為了減少這種社會焦慮,一些人開始求助於酒精。酒精能通過降低自我意識而達到減輕焦慮的效果(Hull & Young,1983)。因此,長期過於敏感的人特別容易在遭受挫敗的時候喝酒。而從酗酒中擺脫以後,他們會比那些自我意識弱的人更容易在再次體驗到壓力或失敗時復發。
焦慮和酒精濫用的多種多樣的症狀也可以具有自我保護的功能。給自己貼上焦慮、害羞或被酒精影響的標籤,就能為失敗提供藉口(Snyder & Smith,1986)。在這些症狀的保護欄後面,一個人的自我就能很安全地被保護起來。“為什麼我沒有約會?因為我是個害羞的人,所以人們不容易瞭解真實的我。”這類症狀是一種用來解釋負性結果的無意識的策略。
假如我們為害羞的人提供另外一種能更為方便地解釋他們的焦慮和可能由此帶來的失敗的說法,是否就可以使他們放棄使用這種策略呢?一個害羞的人可以因此而不再害羞嗎?這正是布羅特和津巴多(1981)在對女大學生的研究中發現的結論。他們把一些害羞的和不害羞的女生帶到實驗室,讓她們和一個英俊的男士談話,這個男士是作為另一名被試的身份出現的。在談話開始前,她們被集中在一間屋子裡並聽到很大的噪音。主試告訴其中一些害羞的女生,這個強烈的噪音將會使她們持續一段時間心跳加劇(另一些害羞的女生沒有被告知這條信息)。因此這些害羞的女生在後來和那個男士談話的時候,可以把自己心跳加劇和任何談話過程中出現的困難都歸咎於之前出現的噪音,而不是她們的害羞或是社交的適應不良。與那些沒有事先被提供噪音這個簡單理由的害羞女生相比,這些女生不再顯得那麼害羞。一旦談話開始,她們就能流利地交談下去並問那位男士一些問題。事實上,和另外那些害羞的女生相比(那些很容易就被那位男士指出是害羞的女生),他很難將她們與不害羞的女生區分開來。
疾病
在這個工業時代,至少一半的死亡是和行為聯繫在一起的——抽菸,喝酒,使用藥物,有害食品;對壓力的反應;缺乏鍛鍊和不聽從醫囑。研究致病的行為原因並試圖改變這種行為的努力促使了一個新的交叉學科的產生,這就是行為病理學 (behavioral medicine)。心理學在這個學科中的貢獻是它的一個分支,健康心理學 (health psychology)。它包括了約3900名在加拿大和美國的醫科學校工作的心理學家(Williams & Kohut,1999)。健康心理學家研究人們對於病症的反應,以及情緒和解釋怎樣影響健康。
對疾病的反應
人們如何確定他們是否病了?他們如何解釋自己的症狀?是什麼影響了他們求醫和堅持治療的意願?
察覺症狀 最近,你可能體驗到了下列生理不適的至少一項:頭疼,胃疼,鼻塞,肌肉痠痛,耳鳴,多汗,手涼,心跳加速,暈眩,關節僵硬,腹瀉或便祕(Pennebaker,1982)。這些症狀需要解釋。它們是否毫無意義?還是有什麼事情要發生?通常一週不到,我們就開始自己診斷這些症狀的重要性了。
察覺和解釋我們身體發出的信號,就像我們覺察和解釋車子的行駛狀況。除非信號很明顯且很清晰,否則我們往往會忽視它們。我們大多數人是不能僅憑聽引擎的聲音就能判斷車子是否應該換油的。同樣,我們大多不能準確地判斷自己的心率、血糖水平或血壓。人們憑藉自己的感覺猜測自己的血壓,但自我感覺與血壓往往是無關的(Baumann & Leventhal,1985)。更重要的是,很多疾病的早期信號(包括癌症和心臟疾病)都是很微弱的,極易被忽略。一半甚至更多的心臟病發作的患者在尋求和接受治療之前就死亡了(Friedman & DiMatteo,1989)。
解釋症狀 :我病了嗎? 對於那些嚴重的疼痛,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具體——而且更加關鍵。一個小囊腫是我們所認為的惡性腫瘤嗎?腹痛是否嚴重到是闌尾炎的程度?胸口的疼痛是否只是肌肉痙攣,就像很多心臟病發作的病人認為的那樣?哪些因素會影響我們對症狀的解釋呢?
一旦發現症狀,我們通常會用熟悉的疾病模式去解釋(Bishop,1991)。在醫科學校,這會導致很有趣的結果。作為訓練的一部分,醫科的學生學習了某種症狀與各種各樣的疾病的關係。因為他們也會體驗到很多的症狀,有時就會把這些症狀歸結為他們最近學習的疾病模式。(“可能我喘氣喘得厲害,是肺炎初始的症狀。”)正如你發現的一樣,心理學的學生在學習各種心理疾病時,也會發生類似的情況。
社會構造的疾病 輕微症狀的普遍性和模糊性,向社會暗示敞開了大門。1989年4月13日,接近2000名聽眾聚集在加州的聖莫尼卡(Santa Monica)禮堂,欣賞600名中學生的音樂表演。演出開始後不久,一些緊張的學生互相抱怨說頭疼、暈眩、肚子疼和噁心。最後有247人病了,聽眾被迫退席。消防隊在外面的草坪上整裝待發。後來的調查顯示,沒有任何問題——既沒有可診斷出的疾病,也沒有任何環境方面的問題。他們的症狀很快就消失了,也沒有影響到聽眾。看起來,這次短暫的流行病就是社會構造的(socially constructed)(Small & others,1991)。
人們是否也會社會性地構造出日常的小毛病呢?人們是否會認為他們的症狀符合某種聽說過的疾病,從而用這種病來解釋自己的症狀呢?卡託和朗爾(Kato & Runle,1992)的發現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女性在經期前兩三天,會更多地感到抑鬱、緊張和易怒。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一樣,在人們觀察並記住那些肯定他們信念的事件而不注意那些不符合這些信念的事件時,就會出現相關錯覺。因此,當女性在生理週期來臨的時候,她就更傾向於把這種緊張歸結為經前綜合症(PMS)。但如果女性在經期之後一週感覺到相同的緊張,或者在她下次生理週期臨近時沒有感到緊張,她就不太可能注意或記住這些相反的事實。
現在許多研究者認為,一些女性確實不僅經歷經期不適,還體驗到經前的緊張(Hurt & others,1992;Richardson,1990;Schmidt & others,1998)。因此,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DSM-Ⅳ中加入了經前綜合症的一種嚴重形式(經前焦慮症,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儘管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和精神病學會婦女委員會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堅持認為,女性的月經週期問題,不應該被視為一種精神疾病(DeAngelis,1993)。
一些研究讓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女性每天記心情日記(Hardie,1997;見圖14-5)。儘管許多女性回憶 她們上個月經週期之前情緒不佳,但是她們每天的自我報告卻表明,月經週期幾乎沒有帶來什麼情緒波動。而且,那些認為 自己患有PMS的女性與那些沒有的相比,在情緒波動上沒有差別。在一個研究中,那些報告有嚴重的月經前症狀的女性在她們整個月經週期的每日報告中與其他女性相比只有很小的差別(Gallant & others,1992)。與一些僱用者的推測相反,女性的身體和心理技能並不隨她們的月經週期發生顯著的變化。霍林沃斯(Leta Hollingworth)在她1914年的博士論文中發現了這一點(用婦女們的每日報告而不是回憶)。在這之後,其他許多研究者也證實了她的發現(Rosenberg,1984;Sommer,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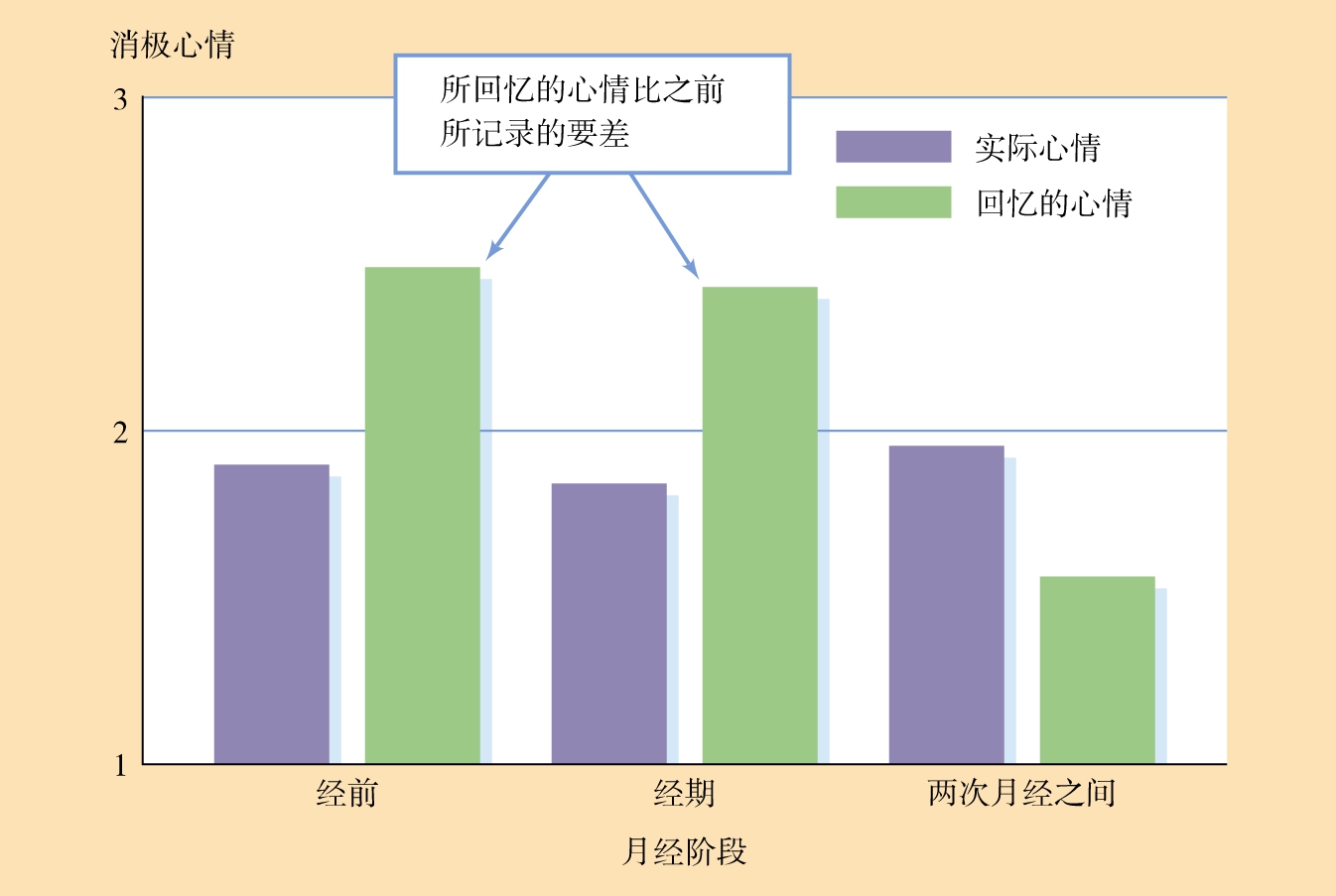
圖14-5 月經週期、真實心情與回憶的心情
麥克法蘭和她的同事(McFarland & others,1989)發現,安大略州的女性每天的心情報告,並不隨她們的月經週期而變化。而她們回憶自己的心情在月經前和月經中普遍較差,在週期的其他時候較好。
另外,對PMS的抱怨因文化而不同,但至今沒有發現與女性之間任何生理差異有關。批評者認為,這正是社會構造的疾病的特點(Richardson,1993;Rodin,1992;Usher,1992)。PMS有如此之多的日常症狀——無精打采,憂傷,易怒,頭痛,失眠(或嗜睡),性冷淡(或性亢奮)——“誰沒有得過PMS?”塔弗雷斯(Tavris,1992)提出了這樣的疑問。
我需要治療嗎? 一旦人們注意到自己的一個症狀,並認為可能很嚴重,一些因素會影響他們是否尋求醫院治療的決定。如果人們認為他們的症狀是由身體而不是心理原因引起的,他們通常更願意尋求治療(Bishop,1987)。但是,如果他們覺得尷尬,如果他們認為治療可能帶來的收益還抵不上他們的花費以及帶來的麻煩,或者如果他們不想證實一個令人震驚的診斷,那麼他們可能會拖延尋求醫療救助。
美國國家健康統計中心(The 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報告了在尋求治療上的性別差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報告症狀,使用更多的處方和非處方的藥物,在求助內科醫生的頻率上超過男性40%。在求助於心理治療頻率方面,女性超過男性50%(Olfson & Pincus,1994)。
女性更經常生病嗎?顯然不是。事實上,男性可能更容易生病。在其他一些問題中,男性患高血壓、潰瘍和癌症的機率更高,他們的預期壽命更短。那麼為什麼女性更可能去看醫生?可能是因為女性對她們的內在狀況更加關注。可能她們更願意承認自己是軟弱的,並尋求幫助(Bishop,1984)。或者只是因為女性感覺與醫生約時間更方便(Marcus & Siegel,1982)。
當病人與醫生關係融洽,當病人協助制定他們的治療計劃,而且可選方案擬定得較有吸引力時,他們通常更願意聽從治療指示。當人們聽到“有40%的存活機率”時,比聽到“有60%的不能存活的機率”時,更可能選擇接受一個手術(Rothman & Salovey,1997;Wilson & others,1987)。這類“獲得性設計”的信息同時也說服更多的人們去使用遮光劑(sunscreen)、拒絕香菸並接受HIV檢驗(Detweiler & others,1999;Schneider & others,2000;Salovey & others,2002)。告訴人們“遮光劑保持健康、年輕的皮膚”比告訴他們“不用遮光劑降低了你有健康、年輕的皮膚的機率”效果更好。
情緒與疾病
我們的情緒能預測到我們患心臟病、中風、癌症以及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嗎(圖14-6)?考慮以下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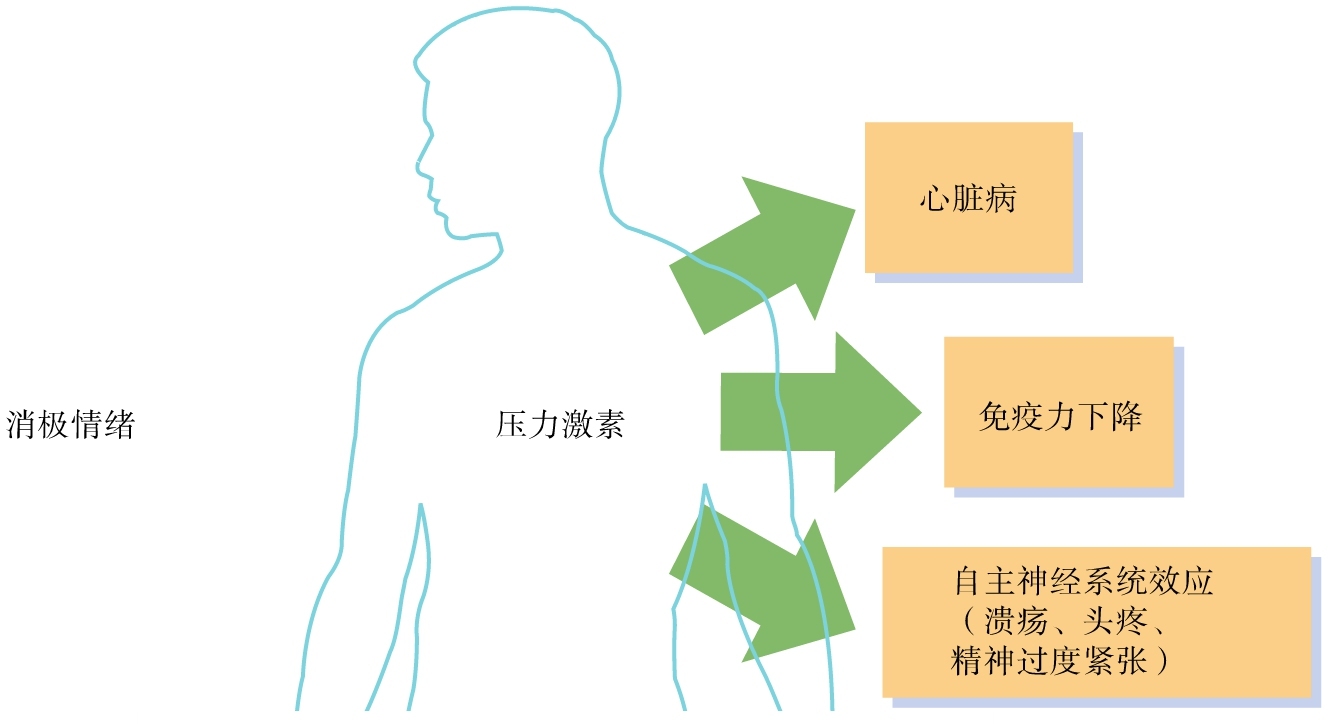
圖14-6
壓力引起的負性情緒可能對健康產生各種影響。對於抑鬱或易怒的人尤其如此。
業已證明,心臟病與一種好鬥的、缺乏耐心的以及易怒 的(很重要的一點)人格相聯繫(Smith & Ruiz,2002;Williams,1993)。處於壓力下,反應性強且易怒的“A型”性格的人會分泌更多的應激激素,這會加速生成心臟動脈壁上的斑塊。
抑鬱也增加了患各種疾病的危險。即使是在控制了吸菸和其他與疾病有關因素差異的情況下,也發現中度抑鬱的人更容易患心臟病(Anda & others,1993)。在心臟病發作後的一年裡,抑鬱的人進一步誘發心臟疾病的危險是正常人的兩倍(Frasure-Smith & others,1995)。消極情緒的危害,導致了在慢性病人中抑鬱和焦慮的高發率(Cohen & Rodriguez,1995)。
當瓦利恩特(Vaillant,1997)對一群哈佛男性校友進行從中年到老年跟蹤研究時,他證明了憂鬱和負性情緒的影響。他將52歲的人劃分為兩類:一類是“老古板”(從未酗酒、使用鎮靜劑或看精神科醫生),其中只有5%的人在75歲前去世;劃到“憂鬱”(酗酒、並使用鎮靜劑或去看過精神科醫生)的一類人當中,38%的人都在75歲前去世了。
樂觀與健康
當一件事情使人失去希望時情況急轉直下,希望復燃時又猛地好轉,這樣的故事非常多。九歲的傑夫患上肝癌時,他的醫生感覺很糟糕。但是傑夫還是很樂觀。他決心長大要當一名癌症研究專家。一天,傑夫興高采烈:一個對他的病例很有興趣的外地專家在一次跨國旅行的途中,計劃停下來看望他。傑夫有那麼多話想要跟這個醫生說,並要給醫生看他自患病以來記的日記。到了期待已久的那一天,濃霧籠罩了傑夫所在的城市。醫生的飛機改變航線飛向了另一座城市,從那裡醫生飛向了他的最終目的地。聽到這個消息後,傑夫無聲地哭了。第二天早上,他感染了肺炎且高燒不退,虛弱地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他進入了昏迷狀態。第二天下午,他離開了人世(Visintainer & Seligman,1983)。
要理解態度與疾病的聯繫,不僅僅需要生動的真實故事。癌症與絕望同時發生時,我們想要知道的是:是癌症導致了絕望,還是絕望降低了個體對癌症的抵抗力?為了解決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謎題,研究者開始:(1)在實驗中,通過讓有機體面對無法控制的壓力,來產生絕望感;(2)將絕望的歸因風格與將來的疾病相聯繫。
壓力與疾病 絕望感的效果最明顯的表現——第2章所講的習得性無助——來自於使動物處於中等但是不可控的電擊、噪音或擁擠環境的實驗中。這些經歷並沒有引起如癌症等疾病,但是它們的確降低了身體的抵抗力。注射了肝癌細胞的老鼠,如果它們接受了不可躲避的電擊,比接受可躲避的電擊或者沒有電擊,會更多地出現腫瘤並死亡。而且,與接受可控制電擊的幼鼠相比,那些接受不可控電擊的幼鼠在成年時期患腫瘤的可能性是其兩倍(Visintainer & Seligman,1985)。習得性無助的動物反應更消極,而且血液檢查表明其免疫反應更低。
誠然,老鼠和人有很大不同。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經受高度壓力體驗的人變得更易患病。持續的壓力從免疫系統中調用我們的精力,使我們更易受感染或患上惡性疾病(Cohen,2002)。配偶的死亡、航天飛行著陸的壓力,甚至一個考試周的緊張都與免疫能力下降相關(Jemmott & Locke,1984)。
看看下列事實:
在一個實驗中,一名志願者在知情同意後被注射感冒病毒,而一個暫時的壓力刺激增大了他體驗到的症狀的嚴重性(Dixon,1986)。
在另一個實驗中,討論問題時出現憤怒情緒的新婚夫婦,在第二天體驗了更多的免疫機能下降(Kiecolt-Glaser & others,1993)。
瑞士一個大型的研究發現,相比無壓力的工人,處在長期壓力情境下的工人患結腸癌的危險性是其5.5倍(Courtney & others,1993)。這個癌症的差異並不是由於年齡、吸菸、飲酒或生理特點的差異引起的。
相比不拖延的學生,逍遙自在的拖延者在學期初報告較少的壓力和疾病,但是在學期末有更多的壓力和疾病。總的來說,自我挫敗的拖延者也更易生病,且得到較低的分數(Tice & Baumeister,1997)。
歸因風格與疾病 如果不可控的壓力影響健康,降低免疫功能,並且產生被動而絕望的順從,那麼表現得悲觀的人會更容易患病嗎?一些研究已經證實,對不好的事情的悲觀的歸因風格(例如說,“這是我的責任,它將持續下去,它將破壞一切事情”)使發生疾病的可能性更大。彼得森和塞利格曼(1987)研究了棒球運動員名人堂的94個成員的新聞語錄,看他們有多頻繁地悲觀(穩定的、普遍的、內在的)解釋壞事情,例如輸掉重大比賽。那些經常這樣做的人,很多在相對年輕的年紀就去世。樂觀主義者——那些對好事情有穩定、普遍而內在的解釋的人——通常比悲觀主義者活得長。
謝爾和卡弗(1991,1992)同樣報告樂觀主義者(例如認為“我通常抱有最好的期望”)較少患各種疾病,且在冠狀手術後康復得更快。他們同樣更積極有效並快樂地面對身體的疾患(Affleck & others,2000;Aspinwall & Taylor,1997;Scheier & others,2000)。
其他的一些研究進行了長期追蹤。在一項研究中,彼得森和他的同事(1988)發現,那些對壞事情有樂觀解釋的普通心理學學生,一年後較少感冒、喉嚨痛或染上流感。另一個研究中,那些在1946年時表現非常樂觀的哈佛大學研究生,在34年後對其進行再次研究時發現他們是最健康的。還有一個研究,時跨半個世紀以上,那些在平均年齡為22歲時表達的正性情緒最多的天主教的修女,比那些表達負性情緒的同伴平均多活7年(Danner & others,2001)。健康行為——運動、良好的營養條件、不酗酒——都是促進樂觀主義者長壽的基本因素(Peterson & Bossio,2000)。
研究者坦南和阿弗萊克(Howard Tennen & Glenn Affleck,1987)從他們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致的結論,認為積極的、充滿希望的歸因風格通常是一劑良藥。從著名的安慰劑效應 (placebo effect)(即相信 自己正在接受有效的治療)的療效中,我們可以看到積極信念的強大療效。(如果你認為 一種治療將會起作用,那麼它就會有效,也許它實際上沒有任何用處。)但他們同時也提醒,每一線光芒前總有烏雲掩蓋。樂觀主義者可能把自己看成是無懈可擊的,因此不會有明智的警惕。[那些吸危險的高焦油含量的香菸的人,樂觀地低估了其中的危險性(Segerstrom & others,1993)]。而且當事情徹底變壞時——當樂觀主義者遭遇一種毀滅性的疾病——災難便無可避免。樂觀對健康的確 是有益的。但是請記住:即使是樂觀主義者,死亡率也是100%。
小結
社會心理學家正在積極地探索抑鬱、孤獨、社會性焦慮以及身體有疾病的人們的歸因和期望問題。抑鬱的人有一種消極的解釋風格。與不抑鬱的人們相比,他們更加自責,用一種更消極的看法去解釋和回憶事情,對於未來也不抱有太多的希望。儘管輕度抑鬱的人有較消極的看法,但是在實驗室測驗中他們表現出了出人意料的現實性。
抑鬱者抑鬱的思考方式對其行為產生了影響,反過來又使其持續了一種惡性循環。對於那些有長期孤獨以及處於社會性焦慮狀態(例如極度羞怯)的人,大都也是類似的情況。
健康心理學正處於迅速發展中,它探索的是人們怎樣判斷自己是否病了,怎樣解釋自己的症狀,以及何時他們會尋求和接受治療。同時它也在探索消極情緒的影響,以及疾病、壓力和消極解釋風格之間的聯繫。
社會心理治療方法有哪些
我們已經考慮了與生活中的問題——從嚴重抑鬱到極度羞怯,再到身體疾病——有關的思維模式。這些適應不良的思維方式需要給予治療嗎?
社會心理學的治療是不存在的。但是治療是一種社會交往的過程,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他們的原則可以整合到現有的治療技術當中去(Forsyth & Leary,1997;Strong & others,1992)。看看下列三個例子。
通過外顯行為引發內在變化
在第4章中,我們考察了一個簡單但卻強有力的原理的大量證據:我們的行為影響著我們的態度。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說和做的事情,以及我們做出的決定都對於“我們是誰”產生了影響。
與這個“態度取決於行為”的原則一致,一些心理治療技術使用了行為療法。行為治療師試圖塑造病人的行為,並假設內在性情會跟隨行為變化。自信訓練使用了登門檻(foot-in-the-door)程序。個體首先在一個支持情景中進行角色扮演練習自信,然後逐漸在日常生活中變得自信。理性情緒治療認為,是我們自己產生了自己的情緒;因此,治療師給病人佈置“家庭作業”,讓他們以一種會產生新情緒的新方式去說話、做事:挑戰那些支配他原來行為的相關行為方式。不再告訴自己“你是一個沒有吸引力的人”,並且開始邀請別人出去約會。自助小組巧妙地使參與者在團體面前表現新的行為方式——表達憤怒、哭泣、高自尊地行為、表達積極感受。所有這些技術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使我們不能通過掌控意志力來直接控制我們的感情,我們也能夠通過我們的行為來間接地影響它。
實驗證實,我們所說的有關自己的話,能夠影響我們的感覺。在一個實驗中,實驗者引導學生寫自我讚美的散文(Mirels & McPeek,1977)。之後,由另一個實驗者讓他們私下評定自己時,相對於其他寫了有關當前社會評論的學生,這些學生表現出更高的自尊。在另外幾個實驗中,瓊斯和他的同事(Jones & others,1981;Rhodewalt & Agustsdottir,1986)讓學生以自我美化或自我否定的方式來向一個面試者介紹自己。同樣,這個公眾表現——不管是樂觀還是悲觀的——繼續出現在接下來的實際的自尊測驗的個人反應中。口說為實,即使是當我們說自己的時候。當學生感覺要對他們怎樣表現自己而負責的時候,尤其如此。
在門敦卡和佈雷姆(Mendonca & Brehm,1983)的一個實驗中,對選擇的知覺顯然非常重要。他們邀請即將開始一個減肥計劃的一組超重兒童,選擇他們喜歡的治療方法。然後定時提醒他們,是他們自己選擇了治療方法。而對其他同時參加這個相同的八週計劃的兒童,則沒有給予選擇權。那些感覺要對他們的治療負有責任的兒童,在八週之後以及三個月之後減了更多體重。
阿克瑟姆和庫珀(Axsom & Cooper,1985;Axsom,1989)報告,當選擇與個人責任感和較高的努力程度結合起來時,影響會更大。他們讓一些想要減肥的婦女參加一些假想的(而不是真實的)治療任務,例如做知覺判斷。那些對任務做出了最大努力的婦女減了最多的體重。當婦女是自願選擇參與該任務時,結果尤其明顯。因此,大多數治療的承諾是:自願參與,並付出努力。
打破惡性循環
如果抑鬱、孤獨和社會性焦慮是通過消極體驗、消極的思維模式以及自我挫敗的行為構成的惡性循環得以維持,那麼應該可以通過破壞任何一個環節來打破循環——通過改變環境,訓練個體更加積極的行為方式,轉變消極思維。這的確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治療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從抑鬱的惡性循環中解脫出來。
社會技能訓練
抑鬱、孤獨和害羞不僅僅是一個人心理上的問題。在一個抑鬱者的身邊待一段時間,都會令人感到不愉快和壓抑。正像孤獨和害羞的人懷疑的那樣,他們確實會在社會情境中表現不佳。在這些情況下,社會技能訓練可能會有幫助。通過觀察並在安全情境中練習新的行為,個體可能在其他情境的行為中更有效地顯示出自信。
隨著個體開始享受應對自如的好處,一個更加積極的自我知覺逐漸形成了。黑默利和蒙哥馬利(Haemmerlie & Montgomery,1982,1984,1986)在一些鼓舞人心的研究中,用一些害羞、焦慮的大學生證明了這一點。那些面對異性沒有經驗且緊張的人可能會對自己說:“我沒有約會過,所以我肯定不行,所以我不應該試圖去追求任何人。”為了改變這種消極的結果,黑默利和蒙哥馬利引導這些學生與異性進行愉快交流。
在其中一個實驗中,大學男生填寫了社會焦慮問卷之後,並在接下來的兩天內來到實驗室。每一天他們都與六位年輕女性中的每一位進行12分鐘的交談。男生以為這些女性也是被試。事實上,這些女性是實驗者的合作者,被要求以一種自然、積極、友好的方式與每個男生談話。
這兩個半小時談話的效果是顯著的。正像一個被試事後寫的那樣,“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多能夠愉快交談的女孩子。在與幾個女孩聊了以後,我的自信心提高了,不再有曾經的那種緊張。”這些評價被各種測量所支持。與控制組的男生不同,那些經歷過交談實驗的男生在一個星期以及6個月之後的重測中,表現出與女性有關的焦慮明顯地較低。當他們被安排在一間房中,獨自與一個有吸引力的女性陌生人在一起時,他們同樣變得更加容易開始與她交談。實際上,在實驗室以外,他們也開始有了不定期的約會。
黑默利和蒙哥馬利指出,這種變化都是發生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的。但其實正因為 沒有諮詢,它才可能會發生。正因為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了成功,這些男生現在才能夠把自己看成有社會能力的。儘管7個月後,研究者還是把實驗向被試作了解釋,但到那個時候為止,那些男生已經經歷了足夠多的社會成功,足以使他們將成功歸於其內在特質。“一事成,則事事成,”黑默利(1987)總結道,“只要你不再拿什麼外在因素為成功找藉口推脫!”
解釋風格療法
抑鬱、孤獨和羞怯的惡性循環,可以通過社會技能訓練,通過積極事件改變自我知覺,以及 通過改變消極的思維方式來打破。有的人擁有社會技能,但是他們吹毛求疵的朋友和家人使他們確信自己沒有。對於這些人,幫助他們轉變其對於自己和未來的消極信念可能就足夠了。在認知療法中,社會心理學家懷著這種目的提出了解釋風格療法 (explanatory style therapy)(Abramson,1988;Gillham & others,2000a,b;Greenberg & others,1992)。
有這樣一個計劃,它教抑鬱的大學生改變他們典型的歸因方式。萊登(Layden,1982)首先解釋了使歸因更類似那些典型的非抑鬱者的好處(通過接納成功帶來的信心,並看環境是怎樣使事情變壞的)。通過各種任務,她幫助學生看他們一般是怎樣解釋成功和失敗的。接下來是治療階段:萊登讓他們每一個人記錄下每天的成功與失敗,注意成功的原因有他們自己的因素,注意失敗有外在的因素。當這種歸因訓練結束一個月之後加以重測時,相比沒有治療的控制組,他們的自尊提高了,歸因風格也變得更加積極。而且歸因風格越積極,他們的抑鬱就消失得越多。通過改變歸因,他們已經改變了自己的情緒。
通過對成功的內在歸因維持變化
目前為止考慮的兩個原則——行為改變可以導致內在的變化,以及自我知覺和自我歸因的改變能打破惡性循環——得出了一個推論性的原則:一旦有了提高,當人們將其歸因於受自己控制的因素而不是治療計劃時,效果將是最為持久的。
通常,強制性的手段會引發最為強烈和迅速的行為改變(Brehm & Smith,1986)。通過使想要消除的行為損失非常慘重或令人尷尬,並且使健康的行為帶來極大的回報,一個治療師的治療可能得到迅速而顯著的效果。問題是,正如社會心理學家30年來的研究提醒我們的那樣,強制性的行為改變很快就會消失。
為了探究其原因,我們來看看瑪莎的經歷。她很在意自己輕微的肥胖,併為對此無能為力而感到受挫。她正在考慮一些商業廣告中的體重控制計劃。每一個都聲稱它能達到最好的效果。瑪莎選擇了其中一個,要求實行一個嚴格的每天1200卡路里的節食計劃。而且,她還被要求記錄和報告她每天所攝入的卡路里,並每週來稱一次體重,以保證她和她的指導者能準確地瞭解她的實施情況。因為對這個計劃的價值很有信心,且不想令自己感到尷尬,瑪莎堅持參加了這個計劃,並且高興地發現多餘的體重正逐漸消失。“這個獨特的計劃真的有效!”當瑪莎達到她的目標體重時,她高興地告訴自己。
然而悲哀的是,在結束這個計劃之後,瑪莎重演了大多數體重控制結業者的經歷(Jeffery & others,2000):她的體重回升了。在街上,她看到她的指導者走近。她非常尷尬地跑向了人行道的另一邊,把臉轉了過去。唉,她還是被指導者認出來了,並被熱情地邀請重新參與“計劃”。因為這個計劃的確在第一次時幫助她達到了好的效果,瑪莎承認她很需要該計劃,並答應回去,開始她又一輪起伏不定的節食。
瑪莎的經歷代表了一些體重控制實驗參與者的經歷,包括由索恩和雅諾弗(Sonne & Janoff,1979)所做的一個實驗。像瑪莎一樣,一半的被試被要求將他們發生改變的飲食行為歸因於這個計劃。另一半則被要求歸功於他們自己的努力。兩組人在這個計劃中都減了肥。但是在11周之後再稱重時,那些自我控制條件下的人最好地保持了他們的減肥效果。這些人,正像前面介紹過的害羞男生遇到女性的研究中的被試一樣,證明了自我效能的作用。學會了成功地應對,並相信他們做到了 ,他們會感覺更有信心,且更有效。
在強調了行為和思維方式的改變能產生積極影響之後,我們應該提醒自己:它們也有侷限性。社會技能訓練和積極的思維方式,不可能將我們轉變成人人喜愛和欽佩的常勝將軍。而且,暫時的抑鬱、孤獨和羞怯是對嚴重的憂傷事件非常適當的反應。只是當這樣的情緒長期存在且沒有任何明確的原因時,就有理由去關注它,並有必要去改變這些惡性循環式的思維和行為。
通過社會影響來進行治療
心理學家越來越接受這樣一個觀點:社會影響——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是治療的核心。斯特朗(Strong,1991)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一個30多歲的婦女在一個治療師面前抱怨她的抑鬱。治療師細心地觀察了她的情緒、瞭解了她的處境。她解釋了她的無助感和她丈夫的需要。儘管欽佩她的奉獻精神,治療師還是幫助她看清,她應該對丈夫的問題負責。她提出反對。但是治療師堅持。最後,她終於承認,她的丈夫可能並不像她認為的那麼脆弱。她開始看清她應該如何既尊重她丈夫又尊重她自己。在治療師的幫助下,她為每一個星期制定計劃。在治療師和病人的長期互動接近尾聲時,她表現得不再抑鬱,並開始了新的行為方式。
對心理療法的影響的早期分析,集中於治療師怎樣建立可靠的專門技能和信任度,以及他們的可信度怎樣提升他們的影響(Strong,1968)。更多的近期分析更關注於治療師與病人之間互動關係如何影響病人的思維,而不僅僅是關注治療師(Cacioppo & others,1991;McNeill & Stoltenberg,1988;Neimeyer & others,1991)。非本質的因素,例如治療師的可信度,可能會讓人產生這樣的想法:治療師的想法引導著病人的想法。但是考慮周到的中心說服的途徑能提供最持久的態度和行為的改變。因此治療師的目的,不是要引出一個病人對他們專家判斷表面上的同意,而是要改變病人自己的思維。
幸運的是,參加治療的大部分病人都想要採取這個中心途徑,在治療師的指導下深入地思考他們的問題。治療師的任務只是提供意見,並提出適當的問題來引導積極有利的想法。治療師的洞見並沒有他們使病人產生的想法來得重要。治療師需要將事物以病人能聽懂的方式,能得到其同意而不是引起爭辯的方式來說明,並允許病人有時間有餘地做出反應。例如,“你對我剛才所說的怎麼看?”這樣的問題才能夠引起病人的思考。
希薩克(Heesacker,1989)用一名35歲的男研究生戴夫的例子來說明。戴夫否認他存在一個潛在的藥物濫用問題。諮詢師瞭解戴夫是個喜歡有力證據的聰明人,於是試圖說服他接受診斷,參加一個治療支持團體。諮詢師說:“好,如果我的診斷是錯誤的,我願意更改它。但是讓我們來看一個藥物濫用者的所有特徵,來檢驗我診斷的準確性。”諮詢師然後慢慢地檢查每一項標準,並給戴夫時間去思考每一點。當一切結束時,戴夫一下子靠到椅子上,喊道,“我不敢相信:我是一個該死的酒鬼。”
在一個實驗中,厄恩斯特和希薩克(Ernst & Heesacker,1993)證實了陪同被試參與一個使用說服的中心途徑的自信訓練小組的有效性。一些被試像通常的自信訓練小組那樣,學習和重複自信的觀念。其他人學習了相同的概念,但也自願地體驗了一次他們因為不自信而傷害自己的情境。然後讓他們聽到了厄恩斯特和希薩克認為有可能使他們會使他們產生積極想法的主張(例如,“由於你自己不夠自信,使得別人習慣不公正地對待你。”)當這個訓練小組活動接近結束時,厄恩斯特和希薩克讓參與者停下來思考,他們對所學習的東西感覺如何。相比那些在第一組中的人,那些經歷了引發思考小組的人以更有益的態度和自信的意願結束了這段經歷。而且,他們的室友發現,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他們表現出更大的自信。
在哲學家帕斯卡爾1620年的《思想錄》中,他就已經預見了這個原理:“人們通常對於他們自己發現的道理,比由別人發現的更加確信不疑。”這是一個值得銘記於心的原理。
小結
在社會心理學原理中,經常被應用於治療的是以下三個:(1)外在行為的改變能夠引起內在的改變。(2)通過對行為技能的訓練、積極體驗改變後的自我知覺、改變消極的思維模式,消極態度和行為所形成的惡性循環可以被打破。(3)如果人們將他們狀況的改善歸因於在他們持續控制下的內在因素而不是治療計劃本身,那麼改善的狀況能得到最好的維持。
心理健康工作者同時也認識到,要改變病人的態度和行為需要說服。治療師,由於其作為專家和令人信任的交流者的形象,可以試圖通過有說服力的論證和提出問題來促進更為健康的思維。
社會關係如何促進健康與幸福感
在有關身心幸福感領域的社會心理學中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題。支持性的親密關係——感到被親密的朋友和家人所喜歡、肯定以及鼓勵——能預測健康和幸福。
我們的人際關係是充滿壓力的。使徒保羅曾這樣諷刺道:“他人就是地獄。”當沃爾和佩恩(Warr & Payne,1982)問一群有代表性的英國成人:前一天,是什麼——如果有的話——在情緒上使他們緊張?“家人”是最常見的答案。而壓力,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會激化健康問題例如冠心病、高血壓,並抑制我們與疾病鬥爭的免疫系統。
儘管如此,總的來看,親密關係更多的是帶來健康與幸福,而不是疾病。對同一群英國人詢問前一天是什麼給他們帶來幸福時光,有更多的人回答是“家人”。親密關係給了我們最大的心痛,但同時也給了我們最大的歡樂。
親密關係與健康
八項大規模的調查,每一項都持續了好幾年並訪問了上千人次,已得出了一個共同的結論:親密關係能預測健康(Berkman,1995;Ryff & Singer,2000)。孤獨的人受到健康問題困擾的危險性更大,他們常常體驗到更大的壓力、睡眠質量較差、自殺行為更多(Cacioppo & others,2002a,b;2003)。與那些有較少社會關係的人相比,那些與朋友、親戚,或者宗教或社團組織的其他成員有親密關係的人較少早逝。開朗、摯愛、重視關係的人們不僅有更多的朋友,同時在實驗中,他們受到注射的感冒病毒影響的可能性也較小(見圖14-7,Cohen & others,1997,2003)。此外,一項對423對老年夫婦歷時5年的研究中,即便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原有的健康狀況和社會經濟條件之後,仍發現那些給予 最多社會支持(從讓朋友、鄰居搭車,為他們跑腿辦事,到給自己的伴侶提供情感支持)的人壽命更長(Brown & others,2003)。這樣看來,付出比僅僅是索取對自己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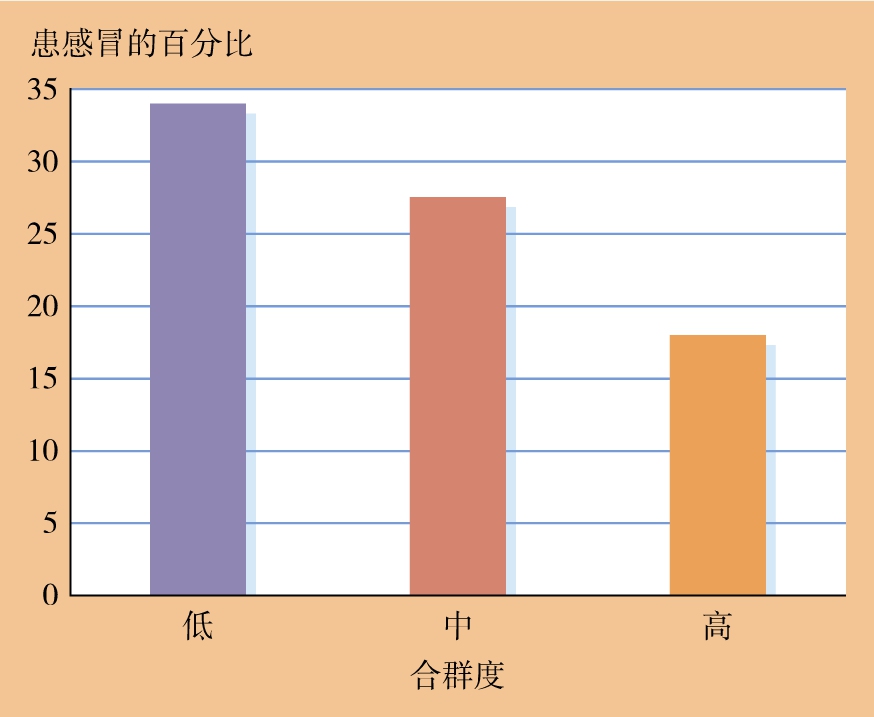
圖14-7 不同合群程度者的感冒比率
被注射感冒病毒之後,高度合群的人較不易於患上感冒。
資料來源:From Cohen & others,2003.
而失去人際紐帶則加大了患病的危險性。
芬蘭一個對96000個喪偶者的研究發現,在配偶去世後的一週之內,他們死亡的危險性加倍了(Kaprio & others,1987)。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研究顯示,那些新近喪偶的人變得更易患病和死亡(Dohrenwend & others,1982)。
一項對30000名男子的研究顯示,當一段婚姻破裂時,男性會更多喝酒、吸菸,蔬菜的攝入量減少而油炸食品的攝入量增加(Eng & others,2001)。
傾訴與健康
這麼看來,社會支持和健康之間有聯繫。為什麼?也許那些享受親密人際關係的人吃得更好,運動更多,而吸菸和喝酒較少。也許朋友和家人幫助我們提升自尊。也許一個支持性的人際網絡能夠幫助我們評估和戰勝壓力事件(Taylor & others,1997)。在超過80個的研究中,心血管及免疫系統的良好運行與社會支持成正相關(Uchino & others,1996)。因此,當我們因某人的不喜歡或失去工作而受傷害的時候,朋友的建議、幫助和安慰,的確是一劑良藥(Cutrona,1986;Rook,1987)。即使問題沒有被提及,朋友也可以使我們分心,並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會被接受、被喜歡、被尊重。
我們可能會向我們認為是親密朋友的人傾訴傷心事。在一項研究中,彭尼貝克和奧希倫(Pennebaker & O'Heeron,1984)接觸了一些自殺者或交通事故遇難者的配偶。那些獨自承擔悲痛的人,比起那些坦然表達出來的人,有更多的健康問題。彭尼貝克(1990)調查了超過700名女大學生,他發現有1/12的人在兒童期有創傷性的性經歷。相比那些經歷了與性侵犯無關的創傷的女生,例如父母死亡或離婚,經歷性創傷的女性報告了更多的頭痛、胃病和其他健康問題,尤其當她們對自己的祕密守口如瓶時。
為了分離出親密關係中傾訴、懺悔方面的作用,彭尼貝克讓喪偶的人敘述一直折磨著他們心靈的傷心事。最初,被要求描述一些小事的人在生理上很緊張。他們一直保持這種緊張的狀態,直到傾訴完他們的問題。然後他們變得輕鬆了。將個人創傷在日記中寫下來,似乎也是有用的。當另一個實驗的參與者這樣做了的時候,他們在接下來的6個月中較少出現健康問題。一個參與者解釋道:“儘管我沒有向任何人說我寫了什麼,但我終於能夠處理它,解決它,而不是逃避它。再想到它也不會使我受傷害。”即使只是“與日記對話”,甚至只是寫下自己未來的夢想和人生的目標,傾訴也都是大有裨益的(King,2001)。
其他一些實驗也證實了積極應對的好處,而不是抑制充滿痛苦的體驗。在一個實驗中,勒普爾和他的同事(Lepore & others,2000)讓學生們看一個有關大屠殺的充滿痛苦的幻燈片和錄像,看完後或者立即談論,或者不談論。兩天後,那些談論過的人感到的痛苦較小,突然闖入腦海的想法也較少。即便是在頭腦中再次思考那些令人壓抑的場景——生動地重現事件以及相關的感覺——也可以增進主動的應對,並改善心情(Rivkin & Taylor,1999)。
貧困、不平等與健康
我們已經看到了健康與一種伴隨積極歸因風格的控制感之間的聯繫。我們也看到了健康和社會支持之間的關係。控制感、社會支持以及衛生保健和營養因素,能夠解釋為什麼經濟地位與壽命有關。回憶第1章中對古老的蘇格蘭格拉斯哥墓穴的研究:那些擁有最昂貴、最高大墓碑(標誌著富裕)的人壽命最長(Carroll & others,1994)。即便是今天,在蘇格蘭、美國和加拿大,較貧困的人早逝的機率仍然較高。貧困意味著致命。貧困意味著面臨壓力、負性情緒和有害環境的危險性增加了(Adler & Snibbe,2003;Gallo & Matthews,2003)。即使在靈長類動物中,當感染類似的感冒病毒時,那些控制能力最低的——在社會等級中最底層的——更易受感染(Cohen & others,1997)。
收入嚴重不均的地區,人們的壽命也相對更短(Kawachi & others,1999;Lynch & others,1998;Marmot & Wilkinson,1999)。與日本人和瑞士人相比,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收入差異更大,預期壽命也更低。在過去十年中,貧富差距增大的地區,像東歐和俄國,預期壽命已經下降到蹺蹺板的盡頭了。
不平等僅僅是貧困的一個指標嗎?多項證據表明,貧困的確是重要因素,但不平等同樣也是。林奇和他的同事(Lynch & others,1998,2000)發現,人們若是住在一個有巨大收入差異的地區,那麼處於每個收入水平的人早逝的危險都比較大。
親密關係與幸福感
傾訴痛苦感受不僅對身體有好處,對精神狀態同樣也有好處。許多研究表明,擁有朋友和家人支持的人更幸福。
在第2章中總結過的一些研究,將競爭性的、個人主義的文化中的人們(例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人),與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們(例如日本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進行了比較。個人主義文化提供了獨立性、隱私和個人成就中的自豪感。而集體主義文化中,更為緊密的社會聯繫則保障人們避免遭受孤獨、疏遠、離婚和與壓力有關的疾病。即使在個人主義的國家,那些相對而言對生活持群體中心取向的人,比起個人主義者報告了更高的生活滿意度(Bettencourt & Dorr,1997)。
友誼與幸福
還有一些研究比較了那些幾乎沒有親密人際關係和有很多親密人際關係的個體。十七世紀的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認為,和可以與之分享祕密的朋友交流有兩個作用:“它將歡樂變成兩倍,將不幸分成兩半。”因此這看起來像民意調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對美國人所提的一個問題的答案(Burt,1986):“回頭看過去的6個月,誰是你與之討論重要問題的人?”相比那些寫不出這樣知心朋友的名字的人,那些寫了5個或6個這樣的朋友的人感到“非常幸福”的要多出60%。
其他一些研究證實了社會網絡的重要性。在人的一生中,友誼培養了自尊,促進了幸福感(Hartup & Stevens,1997)。舉例來說:
最幸福的大學生是那些對他們的愛情生活感到滿意的人(Emmons & others,1983)。
那些享受親密人際關係的人能更好地應對各種壓力,包括親人去世、遭遇強暴、失去工作和患上疾病(Abbey & Andrews,1985;Perlman & Rook,1987)。
由珀金斯(Wesley Perkins)調查的800名霍巴特和史密斯學院的畢業生中,那些有“雅皮士價值觀”——也就是寧願選擇高收入、事業成功和聲望,而不是擁有親密的朋友和幸福婚姻生活的人——描述自己為“相當”或“非常”不幸福的人數是他們原來同學的兩倍(Perkins,1991)。
當被問及“什麼東西對你的幸福是必要的?”或者“是什麼東西使得你的生活有意義?”,大部分人提到——比起任何其他東西更重要的——是與家人、朋友或愛人的令人滿意的親密關係(Berscheid,1985;Berscheid & Peplau,1983)。幸福與家庭緊密聯繫在一起。
婚姻與幸福
世界上每10個人當中,有超過9個人的親密人際關係最終的一種結果是婚姻。婚姻與幸福感呈正相關嗎?或者說追求快樂的單身生活比婚姻的“束縛”、“枷鎖”和“桎梏”有更多的幸福嗎?
堆積如山的數據揭示,大部分有依戀關係的人比起沒有的人更為幸福。針對成千上萬的歐洲人和美國人的一次次調查研究,得出了一個一致的結果:相比那些單身或喪偶的人,尤其是與那些離婚或者分居的人相比,已婚者報告感到更幸福,對生活的滿意度也更高(Gove & others,1990;Inglehart,1990)。一項自1972年起對42000名美國人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調查中,22%的從未結婚的成年人報告“非常幸福”,而在已婚的成年人中此類報告的比例是40%(NORC,2003)。這種婚姻與幸福的關係,是普遍存在於不同種族當中的(Parker & others,1995)。另外,對婚姻的滿意度比起對工作、收入或社區的滿意度,能更好地預測整體的幸福感(Lane,1998)。而在未婚的人當中,自殺率和抑鬱比例更高(Stack,1992;見圖14-8)。確實,與最好的朋友之間親近、關心、平等、親密、相伴一生的友誼,幾乎沒有什麼比這個能更好地預測幸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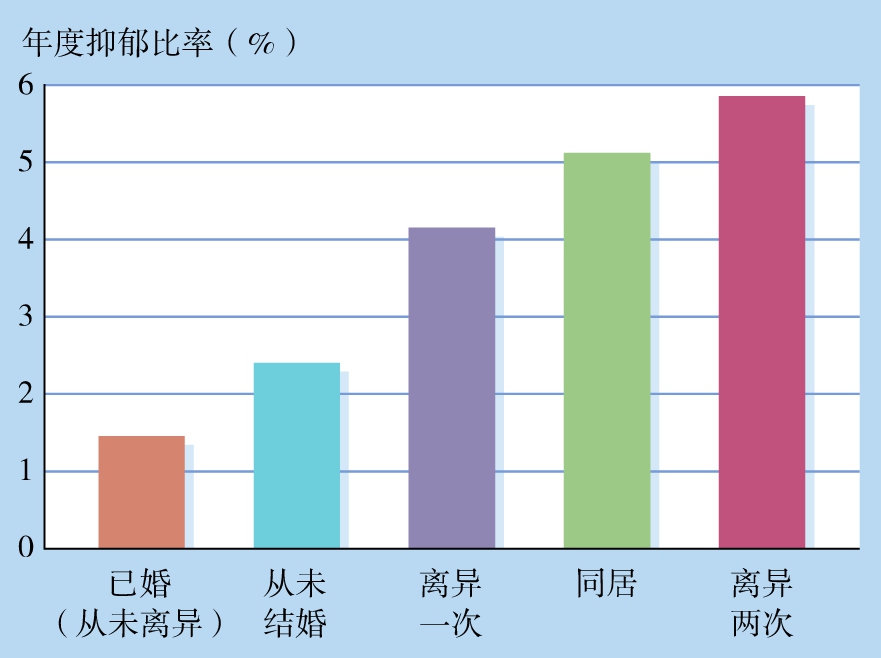
圖14-8 婚姻狀況和抑鬱
國家心理健康協會對於心理障礙的一個調查發現,未婚成年人的抑鬱狀態要嚴重2~4倍。
資料來源:Data from Robins & Regier,1991,p.72.
婚姻是否如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與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幸福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考慮到女性在家務活和養育上付出更多,我們預期可能是這樣。然而,對比已婚和未婚者幸福的差異,在男性當中這種差異僅僅比女性稍微大一點。而且,一項歐洲的調查以及對93個其他研究的統計總結髮現,這種婚姻幸福的差異對於男性和女性事實上是相等的(Inglehart,1990;Wood & others,1989)。儘管一個不幸的婚姻比起對男性的影響,更令女性抑鬱,然而單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幸福的傳言是不可信的。在整個西方世界,已婚的兩性比起未婚、離婚或分居的人,都報告了更大的幸福。
與是否結婚相比,更重要的是婚姻的質量。說他們的婚姻令人滿意的人——那些發現自己仍然與他們的伴侶相愛的人——很少報告自己不幸福,對生活不滿意,或者抑鬱。幸運的是,大部分已婚者的婚姻確實 是幸福的。在美國,近2/3的人說他們的婚姻“非常幸福”。3/4的人說他們的配偶是他們最好的朋友。4/5的人說他們願意再次與同一個人結婚。因而,大部分這樣的人感覺,生活總體來說非常幸福。
為什麼已婚的人普遍更加幸福?是婚姻促進了幸福,還是相反的——是幸福促成了婚姻?是否幸福的人有作為婚姻伴侶的更大的吸引力?是否不滿的或者抑鬱的人更常保持單身或者經歷離異呢?的確,與幸福快樂的人相處更有意思。他們也對人更加友好,令人信賴,富於同情心,以及更加關注於他人(Myers,1993)。不快樂的人,正像我們已說過的那樣,更容易被社會拒斥。抑鬱通常引發婚姻壓力,而婚姻壓力又加深了抑鬱(Davila & others,1997)。因此,積極的、快樂的人更容易形成幸福的人際關係。
但是奧斯陸大學社會學家馬斯特卡薩(Mastekaasa,1995)報告,“研究者中盛行的觀點”是婚姻-幸福關係“主要源於”婚姻的有益作用。試想一下,如果最幸福快樂的人更快且更易於進入婚姻生活,那麼隨著人們年齡的增長(而且逐漸地,較不幸福的人越來越多地走入婚姻),已婚和未婚者當中的平均幸福感都將下降。(年齡較大、較少幸福感的新婚夫婦會降低已婚者的平均幸福感,而且未婚群體將越來越多地由不幸福的人組成。)但是數據並不支持這個預測。這說明夫妻直接的親密關係確實——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能帶來積極的情緒體驗。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一項超過15年的針對1380名新澤西州成年人的追蹤研究,證明了相同的觀點(Horwitz & others,1997)。即使是在控制了結婚前的個人幸福感之後,研究也發現了已婚者抑鬱變少的趨勢。
婚姻促進幸福感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已婚者更可能享受一種持久的、支持性的、親密的人際關係,且更少地感到孤獨。難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庫姆斯(Coombs,1991)做的一個研究中,男性醫科學生如果已婚的話,則他們從醫學院畢業時會感到較少的壓力和焦慮。一個良好的婚姻給予伴侶一個可依賴的同伴、情人和朋友。
為什麼婚姻促進了幸福感,或者至少減輕了我們的痛苦,還有另一個更實際的原因。婚姻提供了配偶和伴侶的角色,這可以提供自尊的額外來源(Crosby,1987)。的確,多重角色會帶來多重壓力。我們的“線路”可能而且確實超載了。但是每個角色同時也提供了回報、地位,使人生更為豐富,使我們從人生中其他部分的壓力中解脫出來。一個有許多身份的自我,就像一個有著許多房間的大廈。當大火襲擊了溫莎城堡的一棟側樓時,城堡的大部分仍然可以供王室成員和旅遊者觀賞。當我們的個人身份依靠許多基石來支持,那麼在失去其中任何一個時,它也仍然可以繼續挺立。如果我在工作當中陷入困境,那麼我可以告訴自己,我仍然是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而且歸根結底,我的這些部分才是最要緊的。
小結
健康和幸福不僅受社會認知影響,而且還為社會關係所影響。那些享受親密的、支持性的人際關係的人,有較低的患病和早逝的危險性。這類人際關係幫助人們應對壓力,尤其是使人們能傾訴他們內心的情緒。
親密的人際關係還提升了幸福感。那些與朋友和家庭成員有親密的、長期的依戀關係的人能更好地應對失敗,並報告了更大的幸福感。舉例來說,相比未婚的成年人,那些已婚者報告“非常快樂”的可能性更大,且經歷抑鬱的可能性更小。這不僅由於快樂幸福的人有更大的社會成功,也由於一個支持性的生活伴侶帶來了幸福舒適。
個人後記:提升幸福感
幾年前我寫了一本叫作《追求幸福》的書,囊括了一些對於幸福的最新研究的主要成果。當編輯想要給書起一個副標題為“什麼給人們帶來幸福 ?”時,我提醒他們:這不是這本書或者任何一本書能夠回答的問題。我們所學到的僅僅只是什麼與幸福相關——即什麼能預測幸福。因此,這本書的副標題改為:“誰是幸福的——為什麼 ?”
然而,在隨後300個有關幸福的媒體採訪中,最常問的問題是:“要獲得幸福,人們能做什麼呢?”對於健康和幸福並不存在任何簡單的公式,這裡我僅列舉以研究為基礎的十點考慮:
認識到持久的幸福並不來自“製造它 ”。人們適應變化的環境——甚至適應財富或殘障。因此財富就像健康:沒有它會使人痛苦,但是擁有它(或者任何我們渴望的環境)也並不一定保證幸福。
控制你的時間 。幸福的人感覺到他們能控制自己的生命,這通常得益於他們對時間的掌控——設立目標,將它們分解為每天的小目標。儘管我們經常高估在任何給定的一天中我們能完成多少任務(帶來的結果是感到挫敗),但是我們通常低估在一年內我們能完成的工作量,考慮到每天只能有那麼一點點進展。
表現出幸福 。我們至少可以使自己假裝一個暫時的心情。做出一個微笑的表情,人們感覺會好一些;當他們皺著眉頭板著臉,整個世界似乎也在怒視自己。因此給自己一個快樂的笑容吧。說話時也好像你感覺到積極的自尊、樂觀和友好。體驗這些情緒,便可以引發這樣的情緒。
尋找合適的工作和休閒方式,使得你的技能得以發揮 。幸福的人通常處於一個叫“全神貫注(flow)”的圈裡——專心於一個挑戰自我而不會壓倒他們的任務。最奢侈的休閒形式(坐遊艇)比起從事園藝、交際或手工製作,通常提供的潮流體驗要少得多。
參加運動 。大量的研究揭示,有氧運動不僅促進了健康和精力,也是消除輕度抑鬱和焦慮的一劑良藥。健全的心靈存在於一個健康的身體中。不要使自己成為一個笨拙的、終日懶散、無所事事的人。
保證足夠的睡眠 。幸福的人們過著一種積極的、精力旺盛的生活,同時也預留了時間來補充睡眠和恢復獨處的寧靜。許多人都受到睡眠債,及隨之產生的疲乏、敏感性下降以及抑鬱的心境等的影響。
優先考慮親密的人際關係 。與那些非常關心你的人建立的親密友誼,能夠幫助你度過困難的時期。傾訴對於心理和身體都是很好的。要決心去精心培育你最為親密的關係:不要認為他們對你好是理所當然,要像對其他人那樣對他們顯示出你的友善,肯定你的伴侶,一起玩耍一起分享。如果要找回你的愛情,就要用這種深情表現的方法來達到。
關注自我之外的事物 。向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幸福能促進人們的助人行為(那些感覺很好的人會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同樣也使人感覺很好。
記錄感恩日記 。那些每天停下來思考他們生活當中的一些積極方面(他們的健康、朋友、家庭、自由、教育、感受、自然環境等)的人體驗了更多的幸福。
照顧你的精神自我 。對於許多人,信念提供了一個支持性的群體,一個超出自我關注的理由,一種生活目的和希望的意識。許多研究都發現,虔誠的宗教信奉者報告自己更加快樂,而且他們能更好地應對危機。
你的觀點是什麼
為你自己的幸福沉思一分鐘。你快樂嗎?是哪些人際關係讓你感到幸福?解釋這些關係是如何支撐你的幸福感的。上述列表中的十項建議,哪些已經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你將如何使其他幾項也應用到你的生活中?
聯繫社會
本章介紹了消極的思維方式,探討了它究竟是抑鬱的原因還是抑鬱的結果。我們同時也在第3章:社會信念與判斷,“情緒與判斷”部分討論了情緒問題。那麼,導致抑鬱的原因有哪些?
第15章 社會心理學在司法領域中的應用
目擊者的證詞可靠嗎
目擊者證詞的說服力
當眼見不為實時
誤導信息效應
重述
對目擊者的反饋
減少錯誤
影響陪審團判斷的其他因素
被告的特徵
法官的指示
其他因素
什麼影響了個體陪審員
陪審員的理解
陪審團的選擇
“死刑認定”陪審員
群體因素對陪審員的影響
少數派的影響
群體極化
寬大
十二個人會比一個人要好嗎
六個人會和十二個人一樣好嗎
從實驗室到生活:模擬陪審團和真實陪審團
個人後記:讓心理科學使我們更聰明地思考
“法庭是個戰場,律師們在那裡爭奪陪審團支持。”
——詹姆斯·蘭迪(James Randi,1999)
人 類歷史上最廣為人知的犯罪案件:橄欖球明星、演員兼體育評論員辛普森(O. J. Simpson)被指控殘忍地謀殺了與他不合的妻子和一個男性熟人。起訴者認為證據昭然:辛普森的行為屬於長期虐待配偶和暴力恐嚇。血液檢驗證實他的血液出現在犯罪現場,而受害者的血液出現在他的手套、汽車甚至臥室的襪子上。在謀殺案發生的當天晚上,他開車離開以及當要逮捕他時他的逃跑,都恰好說明他很符合罪犯的特徵。
辛普森的辯護律師認為,種族偏見可能會干擾那些聲稱在辛普森的家裡發現了帶血手套的警官;他們還認為,辛普森不可能接受公正的審判。這些審判員——其中有十位女性——會友善地對待這個涉嫌虐待婦女和謀殺婦女的人嗎?這些陪審員有多大可能去注意法官的指示,而忽略審判前那些易於導致偏見的公開報道呢?
這個案例向我們揭示了社會心理學實驗中研究過的其他問題:
案件裡沒有目擊者。目擊者證詞的影響力有多大?目擊者回憶的可信度有多高?怎樣才算是一個可信的目擊者?
辛普森是一個英俊、受歡迎、富有而出名的男子。陪審員們真的能夠像他們應該做到的那樣,忽視被告的吸引力和社會地位嗎?
陪審員們對那些重要信息(比如DNA測試中的統計概率)的理解是否充分?
該案例中的陪審團成員大部分由女性和黑人組成,當然也包括兩名男性,還有一個西班牙人和兩個非西班牙裔白人。在接下來的對辛普森索賠案的民事審判陪審團中有9個白人。陪審員的這些特徵會使他們的判決產生偏差嗎?如果會,律師們能否利用挑選陪審員的程序,組成一個符合自己意願的陪審團呢?
像這類案例,12個陪審員做出判決前要慎重討論。討論期間,陪審員之間會怎樣相互影響呢?少數派會贏過多數嗎?12個陪審員最終得出的結論,會和6個陪審員最終的結論一樣嗎?
這樣的問題讓眾多的律師、法官和被告們著迷。正如大部分法學院認識到要聘用“法律和社會科學”教授一樣,也正如出庭辯護律師認識到要僱用心理學顧問一樣,這些問題都可在社會心理學中找到一些答案。
我們可以把法庭看做是一個微型社會,它根據所涉及事件的主要結果,把日常的社會過程加以放大。在犯罪案件中,心理因素會影響包括拘留、審問、起訴、認罪求情協議、判決和假釋在內的一系列決定。美國地方法庭受理的刑事案件中,有五分之四的案件都沒有進入到審判階段(美國司法部,1980)。因此大部分審判律師的工作“不是在法庭上進行說服,而是在會議室裡談判(Saks & Hastie,1978,pp.119~120)。即便在會議室裡,決定也是根據對陪審員或者法官可能怎麼做的推測而得來的。
一個案件最終能否達成判決,與法庭的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有關。因此我們來討論一下目前正被深入研究的兩大類影響因素:(1)目擊者證詞及其對被告判決的影響;(2)作為個體和群體的陪審團成員的特點。
目擊者的證詞可靠嗎
當法庭審判拉開序幕時,陪審員聽取證詞並形成對被告的印象,同時聽從法官的指示並最終達成判決。讓我們從目擊者的證詞開始,一步步來看這些過程。
目擊者證詞的說服力
在第3章裡我們注意到,生動的軼事和個人的證詞往往比強有力的、抽象的信息更有說服力。一段論述最好的結束語莫過於說:“這是我親眼見到的!”畢竟眼見為實。
在華盛頓大學,伊麗莎白·洛夫特斯(Loftus,1974,1979)發現人們十分相信那些自稱“親眼目睹”的人,甚至當他們的證詞沒什麼用時也是這樣。研究者給學生們放映一段假設的搶劫—謀殺案件的錄像,當僅有情境證據而沒有目擊者證詞時,僅有18%的學生贊成定罪;另一部分被試接受同樣的信息,除了還有一個人證外其他的要素均相同,現在,知道有個人作證說,“就是這個人!”結果有72%的學生贊成定罪。第三組被試聽到,被告的律師駁斥了這個目擊者的證詞,因為該目擊者的視力僅有20/400,而且當時並沒有戴眼鏡。這種駁斥是否就降低了證詞的效應呢?這個案例中,並沒有下降多少:仍然有68%的被試贊成給被告定罪。
後來的實驗表明,對證詞可信度的質疑,也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同意給被告定罪的人數(Whitley,1987)。但是,除非當該目擊者的證詞與另一個目擊者的證詞相矛盾,否則該目擊者的生動解釋很難從陪審員的腦中抹去(Leippe,1985)。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相對於那些缺少目擊者證詞的刑事案件(如辛普森案)來說,有目擊者作證的案件更有可能將被告定罪(Visher,1987)。
難道陪審員不能發現錯誤的證詞嗎?為了找出答案,加里·韋爾斯,林賽(Wells,Lindsay,& others)及其同事導演了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計算器商店的數百個有目擊者的偷竊事件。然後,他們讓每一個目擊者從一系列的照片中辨認出嫌犯,讓模擬陪審員觀察正在被詢問的目擊者並做出評價。與相信不正確的目擊者相比,人們更容易相信那些正確的目擊者嗎?研究發現,被試相信正確的和不正確的目擊者的比例都是80%(Wells & others,1979)。這使研究者認為,“觀察者完全沒有能力分辨出,那些將無辜的人錯認為罪犯的目擊者”(Wells & others,1980)。
在一個後續實驗中,林賽,韋爾斯和卡羅琳·朗培爾(Lindsay,Wells,& Rumpel,1981)導演了偷竊案件,不過這些案件裡有時可以允許目擊者長時間地處於良好觀察條件下看偷竊事件,有時不能。當處於良好觀察條件時,陪審員們更相信目擊者。但是即使當觀察條件差到有三分之二的目擊者實際上認錯了人時,也有62%的陪審員仍然相信目擊者。
韋爾斯和邁克爾·利珀(Wells & Leippe,1981)也發現,陪審員對那些細節記憶很差的目擊者更為懷疑——儘管這些人往往是最準確 的目擊者。陪審員認為,一個能夠記住屋內懸掛著三張畫的目擊者“確實在注意”(Bell & Loftus,1988,1989)。而事實上,那些注意細節的人更不容易注意到嫌犯的面部。
三個目擊者的有力指證,把以前從未被捕過的芝加哥人詹姆斯·紐瑟姆(James Newsome)送入監獄,被判終身監禁。他被指控槍殺了便利店老闆。15年以後,他被釋放,指紋技術顯示真正的罪犯是丹尼斯·埃默森(Dennis Emerson),一位職業殺手,比前者高出3英寸,有更長的頭髮(《芝加哥論壇報》,2002)。
當眼見不為實時
目擊者的證詞總是不準確嗎?無辜的人由於目擊者錯誤的證詞而在監獄裡煎熬歲月,這樣的故事並不罕見(Brandon & Davies,1973)。70年前,耶魯法律教授埃德溫·博查德(Borchard,1932)考察了後來被證實無罪的65個人的判罪記錄。大部分案件是錯誤辨認所致,有一些在即將執行的千鈞一髮的時刻被解救了出來。在這個千年即將到來時,DNA檢測已經解救了100多個被判刑但事實上無罪的人,其中有75%是目擊者錯誤辨認的犧牲品(Wells & Olson,2003)。有一個分析估計,美國每年150萬的犯罪判決中有0.5%是錯判,這7500個案件中又有將近4500個是由於錯誤辨認造成的(Cutler & Penrod,1995)(參見聚焦:目擊者證詞)。
為了判斷目擊者回憶的準確性,我們需要了解他們總體的“命中率”和“漏報率”。蒐集這些信息的辦法之一,是模擬那些與日常生活的案件有可比性的犯罪事件,並請目擊者作證。
這樣的研究目前已經做過多次,有時結果很令人不安。例如,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所在的海沃德(Hayward),141個學生目擊了一起“騷擾”教授的案件。7周後,羅伯特·巴克霍特(Buckhout,1974)讓他們從6張照片中辨認出那個攻擊者,有60%的人選出了一個與案件無關的人。毫無疑問,目擊者指證的人有時並不是他們看到的那個人。後來的研究同樣證實,目擊者常因過於自信而有失準確。例如,布賴恩·伯恩斯坦和道格拉斯·齊克福斯(Bornstein & Zickafoose,1999)發現,讓學生回憶曾經來過教室的參觀者,確信自己的回憶正確的人達到74%,但實際上正確的只有55%。
聚焦 目擊者證詞
1984年,我是一個學業優秀、有著光明前途的22歲大學生。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有人破門而入,把刀架在我脖子上,強姦了我。
在這段痛苦的時間裡,我下定決心,我必須活下去。藉上帝的慈悲,我相信強姦犯一定會被抓住,並受到懲罰。我的思想迅速擺脫肉體的不適,開始記牢攻擊者的每個細節。我仔細審視他的臉龐,注意他的頭髮、額頭、下頷,我仔細聽他的嗓音、話語。我尋找他身上的傷疤、剌青和任何有助於辨認他的東西。在時間看來無窮無盡之際,強姦犯短暫地放鬆了警惕,我飛快地披了一條毯子,在清晨逃出了寓所,我逃脫了。
以後的日子裡,我開始了努力把攻擊者繩之以法的痛苦過程。一連幾個小時,我和警察畫師坐在一起,竭力查看著畫滿無數鼻子、眼睛、眉毛、髮際、鼻孔和嘴脣的像冊。一次一次地重溫那次攻擊,一個一個細節地拼成他的面部輪廓。次日,強姦犯的形象出現在報紙的頭版。蒼天有眼,案件很快有了第一個嫌疑犯。幾天後,我坐在一系列照片面前,指認那個攻擊者。我找到他了!我知道就是這個人。我很肯定。我確信。
6個月以後,案子進入了審判。我作為證人出場,把手放在《聖經》上,發出誓言,“我說的都是事實,除了真相別無其他。”根據我的目擊證詞,羅納德·科頓被判終身監禁。羅納德·科頓不能重見天日了。羅納德·科頓再也不能傷害其他婦女了。
1987年的再審中,被告方提到另一個同獄犯人,博比·普爾,他曾吹牛說強姦了我。在法庭上他又矢口否認。當問我是否以前見過他時,我斷然回答說,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另一個受害者也是這樣。羅納德·科頓被判兩次終生監禁,不得假釋。
1995年,在我第一次指控羅納德·科頓是強姦我的罪犯後11年,我被詢問,是否可留個血液樣本,這樣DNA檢測就可作為強姦的證據。我同意了,因為我知道羅納德·科頓強姦了我,DNA檢測只會確認這一點。檢測將會把任何將來對羅納德·科頓的上訴確認下來。
我決不會忘記知道DNA檢測結果的那一天。我站在廚房裡,偵探和地方檢察官告訴我:“羅納德·科頓沒有強姦你,真正強姦你的是博比·普爾。”他們的話像晴天霹靂。那個我堅信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的男人,就是那個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打我,強姦我,粉碎我的精神世界,撕碎我的靈魂的男人。而那個我認為對之所做的事都是正義的,他的臉常常在深夜浮現在我眼前的男人,竟然是無辜的。
服刑11年後,羅納德·科頓從獄中釋放,這是北卡羅來納通過DNA檢測第一個無罪釋放的重罪犯。博比·普爾判為終身監禁,死於癌症,他承認了強姦,無一絲悔改之意。由於這一使我們彼此對立數年的殘忍的罪行,我和羅納德·科頓現在還共同承擔著重荷——我們都是受害者。對於他的判刑,我深感有罪和悔恨。我們年齡相同,所以我知道,在監獄的11年裡他失去了什麼。我有機會搬家,開始治癒傷口,大學畢業,找到了信任和婚姻愛情,也在工作中找回了自信。在我漂亮的孩子身上,我看到了光明燦爛的未來。相反,羅納德·科頓在鐵窗下度日如年,保衛自己免受暴力,而暴力是監獄生活的標記。
羅納德·科頓釋放後,我通過我們的律師要求會見他,這樣我可以說,我很對不起,請求他的寬恕。結果,羅納德·科頓和我通過寬恕,終於找回了徹底的自由。現在我會永遠記得這幾乎不大可能建立起來的友誼,慶幸在錯誤指認羅納德·科頓的案子中,我沒有一錯到底。
詹妮弗·湯普遜,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當然,一些目擊者比另一些目擊者表現得更自信。韋爾斯和他的同事(2002)發現,正是這種自信的目擊者才使得陪審員們覺得更可靠。被DNA證據所推翻的定罪案件說明,由於目擊者在辨認犯罪者時高度但又錯誤的自信,使得他們變得更有說服力。所以,除非條件非常合適,罪犯的外貌特徵非常顯著,否則目擊者的確信程度與證詞的準確性只有中等程度的相關,這一點令人頗為不安。來自直覺的信心確實與準確性相關,但同時,隨見證時間的長短,會產生很大的差異——觀察時間較長的人,表現得既準確又自信(Lindsay & others,1998;Wells & others,2002)。然而,有一些人,無論對與錯,都習慣過於自信地表達自己。因此,邁克爾·利珀(1994)認為,這點就解釋了為什麼犯錯的目擊者也常常能說服人們。[目擊者對細節的回憶有時是很深刻的。約翰·尤伊爾和朱迪思·卡特歇爾 (Yuille & Cutshall,1986)研究了位於英屬哥倫比亞繁忙的伯納比 (Burnaby)街上發生的一樁午後謀殺案,發現目擊者對細節的回憶有80%是準確的 。]
這一發現對於1972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成員來說,無疑是個意外。基於目擊者指證做出的審判奠定了美國司法系統的地位,而現在我們認識到,法庭實際上很糟糕。因為它宣稱,決定準確性的眾多因素之一是“目擊者作證的確信水平”(Wells & Murray,1983)。
因為人的大腦不是錄像機,所以知覺和記憶才會發生錯誤。當給人們呈現一張新面孔和一張先前呈現過的面孔,人們認出舊照片的能力相當好。然而,斯特林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面孔識別研究者維基·布魯斯(Bruce,1998)很吃驚地發現,人類的視覺很難鑑別出視角、表情抑或光線上的細微差別。我們的記憶一部分是根據我們當時知覺到的,一部分是基於我們的預期、看法和當前的知識(見圖15-1,15-2)。

圖15-1 有時候所信即為所見
文化期待會影響知覺、記憶和報告。1947年“流言傳播”的實驗中,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奧·波斯特曼(Leo Postman)給人們呈現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一個拿著刀片的白人。實驗者讓被試把照片上的故事轉述給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再接著轉述給第三個人,依次下去。到轉述給第六個人時,拿在白人手裡的刀片被說成是在黑人手裡了。
資料來源:Allport,G.W.and L. Postman(1947,1975). Figure from The Psychology of Rumor by Gordon W. Allport and Leo Postman. Copyright © 1947 and renewed 1975 by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Illustration by Graphic Presentation Serv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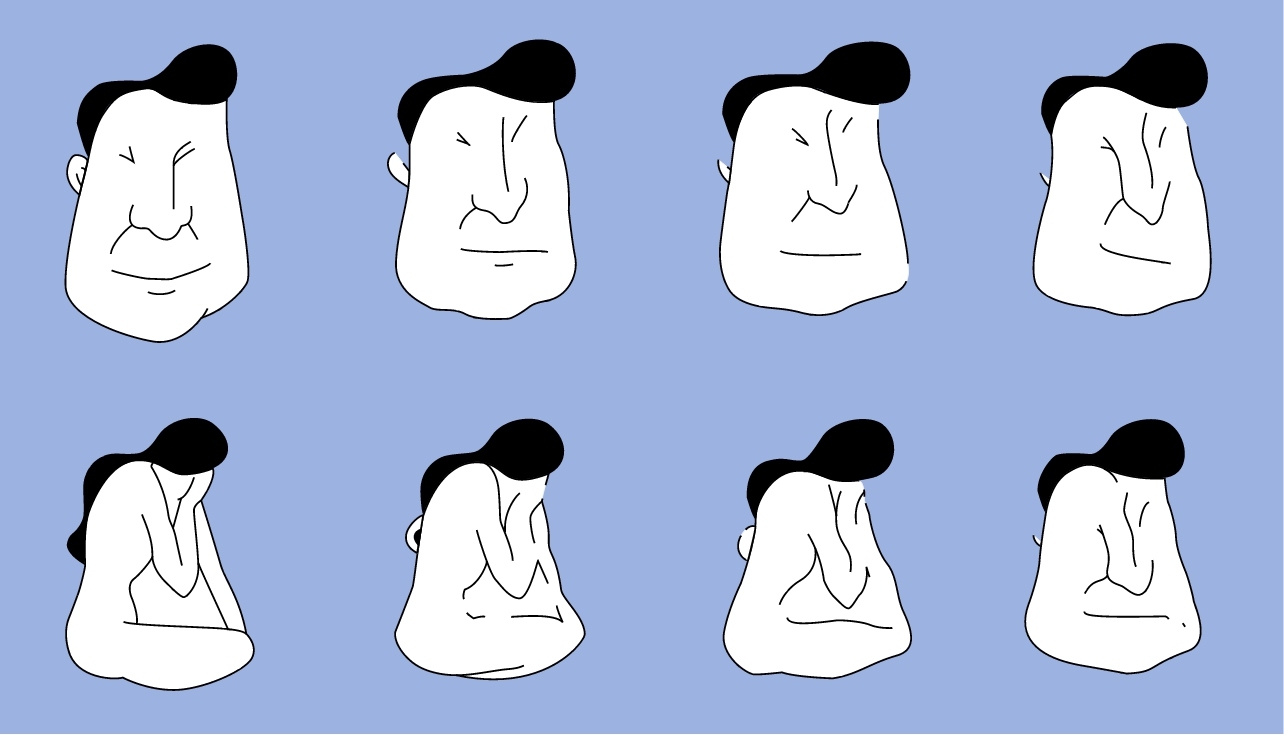
圖15-2 期望影響知覺
左邊的圖形是一張臉還是一個人的輪廓呢?
資料來源:From Fisher,1968. adapted by Loftus,1979. Drawing by Anne Canevari Green.
誤導信息效應
伊麗莎白·洛夫特斯(1978)和助手們為記憶構建提供了戲劇性的證明。他們給華盛頓大學的學生呈現了30張幻燈片,放映的是機動車和行人相撞的全過程。其中一張關鍵幻燈片顯示,一輛紅色的達特桑車(Datsun)在“停止”路標或“避讓”標誌前停住。然後他們問一半的學生一些問題,問題之一是:“當紅色達桑車停在‘停止’交通牌前時,另一輛汽車有沒有超過它?”他們問另一半的學生同樣的問題,但是把那個問題中的“停止”路標換成了“避讓”路標。後來,所有的學生都去看圖15-3中的幻燈片,然後回憶哪一張是他們先前看過的。問題中提到的與實際看到的一致的條件下,有75%的學生回答正確,而那些先前被問到誤導問題的學生正確率只有41%;並且,他們不僅否定了實際看到的,而且認為“記住了”那張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圖片。

圖15-3 誤導信息效應
當給證人呈現兩張照片中的一張,並問他一個問題,其中暗含著來自另一張照片裡的道路標誌,大多數人後來都“記得”看到過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看到的那個標誌。
資料來源:From Loftus,Miller,& Burns,1978. Photos courtesy of Elizabeth Loftus.
在對誤導信息效應 (misinformation effect)(記住錯誤導向的信息)的其他研究中,洛夫特斯(1979a,1979b,2001)發現,在暗示性的問題之後,目擊者可能相信當時看到的紅燈其實是綠燈,或者搶劫犯本來沒有鬍鬚卻變成了有鬍鬚。當詢問目擊者時,警察和律師通常從他們自己對事件理解的角度提問題。所以目擊者把誤導的信息混入他們的記憶非常容易,特別是當他們相信提問題的人很有學問而且暗示性問題一再被重複時,這一點是很棘手的(Smith & Ellsworth,1987;Zaragoza & Mitchell,1996)。
錯誤記憶感覺起來甚至看起來都像真實的記憶,這一點同樣很糟糕。這些錯誤記憶就像真實記憶一樣有說服力——一種讓人相信的真實,但卻是真實的錯誤。這種情況對於成人和兒童都一樣(兒童尤其容易受到誤導信息的影響)。斯蒂芬·切奇和瑪吉·布魯克(Ceci & Bruck,1993a,b,1995)證實了孩子的這種易受暗示性。每個星期他們都給孩子講一遍同樣的內容,一連講十週,然後問孩子“努力地想一想,然後告訴我,這件事有沒有發生在你身上。”例如,告訴孩子這樣的內容“你能記得曾經因為手指被捕鼠器夾過而去醫院嗎?”十週以後,另一個成年人問這些孩子同樣的問題,發現有58%的學前兒童講述了這個錯誤的假想的事情,而且講得很詳細。有一個男孩還解釋道,他的哥哥把他推到地下室裡的木頭堆裡,他的手指被夾進捕鼠器裡了。“然後我們就去醫院了,是我的媽媽、爸爸和科林開車把我送去的,開我們的貨車去的,因為那兒很遠。然後醫生給我的手指貼上了繃帶。”
面對如此生動的故事,就算是專業心理學家也會被愚弄。他們無法區分真實的記憶和錯誤的記憶,就像這些孩子一樣。當告訴他們,這件事實際上從未發生過時,許多孩子表示反對。“但是它確實發生了。我記得的!”對於布魯克和切奇(1999)來說,這些研究結果指出了極有可能產生錯誤控告的問題,就像兒童性虐待案中,兒童的記憶很可能被重複的暗示性問題所汙染,而事實上並沒有確鑿的證據。
重述
無論正確與否,重述事件使人們更容易相信回憶起來的東西。一個準確的重述會使得人們此後能更好地抵制誤導的信息(Bregman & McAllister,1982)。而其他情況下,我們重述的次數越多,我們自己就越容易相信謬誤是真實的。韋爾斯等人(Wells,Ferguson,& Lindsay,1981)證實了這一點。他們讓一個模擬偷竊案的目擊者在出庭作證前,重述他們對問題的回答。這樣做,增強了他們對自己錯誤證詞的自信心,而聽到他們錯誤證詞的陪審員們更可能給那個無辜的人判罪。
在第4章裡我們提到,我們時常調整自己所說的話來愉悅我們的聽者,這樣一來,我們就逐漸相信調整過了的信息。假想一下,你目擊了一場爭論突然爆發成一場毆鬥,在這場毆鬥裡一個人傷害了另一個人。然後,受傷的一方上訴了。在審判前,支持其中一方的一位溫和的律師採訪你。你可能稍微調整你的證詞,並講述一個有利於該律師當事人的事發經過嗎?如果你這樣做了,你後來在法庭上的回憶會有相同的傾向性嗎?
布萊爾·謝潑德和尼爾·維德馬(Sheppard & Vidmar,1980)證實,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西安大略大學,他們讓一些學生模擬目擊者,另一些人模擬律師和法官。當接受了被告律師的採訪後,這些目擊者給法官的證詞更加偏向被告。在後續實驗裡,維德馬和南希·萊爾德(Vidmar & Laird,1983)注意到,目擊者並沒有從他們的證詞中省略重要事實;他們只是改變了說話的語調和用詞,而這些都是根據他們自認為自己是被告還是原告的目擊者而定。但這已經足以歪曲那些聽到這些證詞的人的印象。所以,不僅僅是暗示性問題能夠歪曲目擊者的記憶,就連他們自己的重述也可能因為去迎合他們的聽眾而受到調整。
對目擊者的反饋
案件的目擊者在一列嫌犯中進行指認:“啊,我的天哪!……我不知道……他是那兩個中的一個……可是我不知道……啊,天……那個傢伙比2號稍微高一點……就是這兩個中的一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幾個月後在法庭上,當詢問:“你肯定是二號嗎?而不是一種懷疑?”
目擊者回答:“就是這樣的……我確信。”(Missouri v. Hutching ,1994,reported by Wells & Bradfield,1998)
怎樣解釋目擊者改變他們最初的不確定呢?加里·韋爾斯和埃米·布拉德菲爾德(Wells & Bradfield,1998,1999)對此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當知道另一個目擊者指認了同一個嫌疑犯時,當被重複提問相同的問題時,當為交叉檢驗(cross-examination)做準備時,這個目擊者的信心就增加了(Lüüs & Wells,1994;Shaw,1996;Wells & others,1981)。列隊指認時,面詢者的反饋是否不僅影響了目擊者的信心,而且影響了他們對最初信心的回憶(“我一直都知道”)?
為了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韋爾斯和布拉德菲爾德做了兩個實驗。352個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學生通過微型攝像頭觀看一個男人走入商店的錄像。過後,在攝像範圍之外,他謀殺了一個保安。然後給這些學生看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從實際的犯罪照片裡剪出來的罪犯的照片。然後讓這些學生去確認罪犯。352個學生都做出了錯誤的指認,接著主試給出肯定的反饋(“很好。你的懷疑是對的”),否定的反饋(“實際上,嫌疑犯是X號”),或者沒有反饋。最後,所有的人都被問:“在你指認照片上的那個人時,你有多大把握你在照片上認出的人,就是那個你在錄像裡看到的那個罪犯?”(7點量表,1表示一點也不確定,7表示完全肯定。)
這個實驗最後得出了兩個非常令人震驚的結果:首先,主試給予反饋的效應是巨大的。在肯定反饋條件下,58%的目擊者評價他們做最初的判斷時確定程度為6或7,是那些在沒有反饋條件下確定程度相同的人數(14%)的4倍,是那些在否定反饋條件下確定程度相同的人數(5%)的11倍。目擊者的信心被肯定的反饋所加強,對於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感到吃驚;然而真正使我們驚訝的是,這裡所提高的是他們對反饋前信心的評價。
被試們的判斷受到影響這一點,被試自己的感覺卻並不明顯——另一個讓人相當吃驚的發現便是,當問及被試反饋是否影響了他們的回答時,58%的被試否認了。而且,那些感到沒有受影響的人,所受到的影響並不比那些承認自己受影響的人少(圖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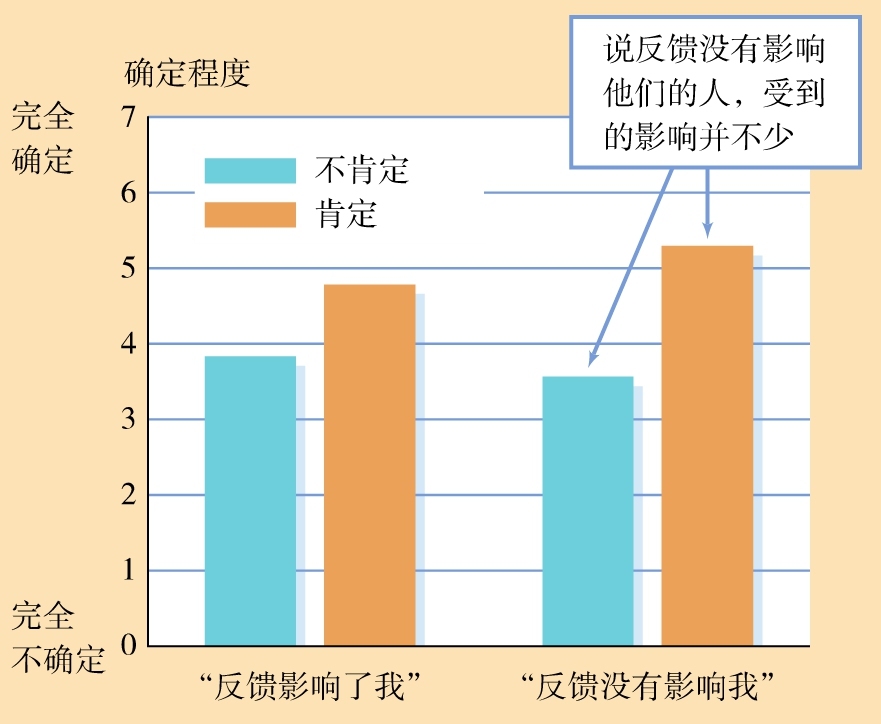
圖15-4 接受到肯定或否定反饋後,目擊者對錯誤辨認的確信度(實驗2)
注意:那些說反饋沒有影響他們的被試,實際受影響並不少。
資料來源:Data from Wells & Bradfield,1998.
這個教訓比對陪審團的研究更深刻。我們又一次看到了社會心理學的用武之處。當社會心理學家如此頻繁地發現——請回憶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只是簡單地問人們會如何反應,或者用什麼解釋他們的行為時,有時卻會得到錯誤的答案。本傑明·富蘭克林是正確的:“有三樣東西是極端堅硬的(困難,hard),那就是鋼鐵、鑽石以及認識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僅需要做調查、詢問人們如何解釋他們自己,同時還要做實驗看看他們實際上做了什麼。
減少錯誤
由於存在易於犯錯的傾向,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措施,才能提高目擊者和陪審員的準確率呢?前美國總檢察官珍尼特·雷諾(Janet Reno)以及十年前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員會都曾向加里·韋爾斯尋求建議。後來,司法部集合了一群研究者、律師和法律執行部門的官員,最終制定了一本法律執行指導手冊(Technical Group,1999;Wells & others,2000)。這本手冊提供的建議,與最近加拿大對目擊者辨認程序的回顧所提供的許多建議相類似(Yarmey,2003a),其中包括訓練警察面詢者和管理嫌犯列隊指認的方法。
訓練警察面詢者
當羅納德·費希爾和他的合作者(Fisher & others,1987)調查了有經驗的佛羅里達警探對目擊者的面詢錄音記錄。他們發現一種典型的模式:以一個開放式的問題(“告訴我你記得什麼?”)開頭,之後警探會不時以提問打斷對方,包括一些答案很簡單的問題(如“他有多高?”)。而費希爾和蓋澤爾曼(Fisher & Geiselman,1996)以及這本新指導手冊認為,面詢一開始就應該允許目擊者進行未經提示的回憶。
如果面詢官一開始引導目擊者慢慢地回憶並重建當時的情景,那麼回憶將是最完整的。使他們回想當時看到了什麼,在想什麼,感覺怎樣,甚至可以顯現出當時的情景——比如,商店出納臺的一個營業員站在她當時被搶的位置——都可以提高回憶的準確率(Cutler & Penrod,1988)。給目擊者充足的、不受打斷的時間報告出腦子裡出現的一切後,面試官用啟發性問題引導目擊者回憶(如“聲音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那個人的長相或者服飾有什麼不尋常嗎?”)。費希爾和他的同事(1989,1994)訓練警探們以這種方式問話,這時他們從目擊者那裡得到的信息增加了50%,而回憶錯誤率卻沒有增加。後來對42個研究的統計結果證實,這種認知面詢大量增加了回憶出的細節,並且無損於正確率(Kohnken & others,1999)。作為對此結果的反應,北美的大部分警官以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所有警官都採用了這種“認知面詢”的程序(Geiselman,1996;Kebbell & others,1999)。FBI如今也在他們的訓練項目裡增添了這個程序(Bower,1997)。(這個程序同樣有望促進在口述歷史和醫學調查裡的信息蒐集。)
負責測查記憶任務的面詢官必須小心地使他們的問題不包含事先假定。洛夫特斯和吉多·贊尼(Loftus & Guido Zanni,1975)發現,像“你看到那個破的前燈了嗎?”之類的問題引起對不存在事件的回憶量,是沒有這種隱藏假定的問題“你看到過破的前燈嗎?”時的兩倍。
讓目擊者看大量的嫌犯照片,同樣會降低他們後來辨認罪犯的準確率(Brigham & Cairns,1988)。當目擊者不得不停下來思考、分析比較面孔時,錯誤尤其容易發生。用言語描述一個搶劫犯的臉,破壞了從一系列照片中對它的再認。某些研究者認為,這種“言語掩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人們調整了對面孔的記憶,使之適應言語的描述;另一些研究者認為,以詞語為基礎的描述,代替了無意識的知覺,或者使得難以接近無意識的知覺(Fallshore & Schooler,1995;Merissner & others,2001;Schooler,2002)。
準確辨認總是自動的,不需要太費力的。那張正確的臉是僅僅一下子就湧上來的(Dunning & Stern,1994)。戴維·鄧寧和斯科特·佩雷塔(Dunning & Perretta,2002)的最近研究表明,在少於10~12秒內作出辨認的目擊者,其準確率接近90%;需要更長一點時間辨認的目擊者,其準確率大體上只有50%。
減少錯誤的列隊指認
羅恩·沙特福德(Ron Shatford)案件表明,警察局裡列隊指認的組成可能導致錯誤的辨認(Doob & Kirshenbaum,1973)。在多倫多郊外的百貨商店搶劫案之後,當時的收銀員只能回憶出罪犯沒有帶領帶,“穿得很考究,長得也相當好看。”當警察把英俊的沙特福德排在11個相貌平平的人裡面,並且那11個人都打著領帶,這個收銀員很快就把他確認為罪犯。他服刑15個月後另一個人承認了罪行,這樣沙特福德才被重新審判並無罪釋放。
加里·韋爾斯(1984,1993)以及他的《目擊者證詞》指導手冊認為,能夠減少錯誤辨認的一個方法,就是提醒目擊者:他們看到的那個人可能在,也可能不在這個隊列裡。換句話說,給目擊者一組沒有包含嫌疑犯的“空的”隊列,從而篩選出那些做錯誤辨認的人。那些沒有認錯的目擊者,後來面對真實的隊列辨認時,也表現得更加準確。
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南非的數十個研究顯示,當要求目擊者對一組 人逐個地做出簡單的“是”或“不是”的判斷時,錯誤率下降了(Lindsay & Wells,1985;Steblay & others,2001)。同時出現隊列,會誘使目擊者在這些人中選出更像罪犯的那個。讓目擊者一次只看一個嫌疑者,就更可能做出準確的辨認,較少犯錯誤。如果目擊者同時看到了一組照片或一組人,他們就更可能選擇那個最像罪犯的人。
這些無需花費的程序,使得警方的列隊指認更像一個設計精妙的實驗。這裡有一個控制組 (由非嫌疑犯組成的隊列,或者模擬目擊者僅僅根據一般的描述試著猜測哪個是犯人的隊列)。實驗者對假設是無所知的 (是一個不知道誰是嫌疑犯的官員)。問題是按腳本 安排的,並且是不偏不倚 的。所以它們不會引起特定的反應偏差(程序也不會暗示罪犯在哪個隊列中)。在目擊者作證前,它們也阻止列隊指認之後的評論(“你找對人了”)所造成的信心膨脹。這樣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人類天性的證實偏見(有了一個觀點後,尋求能夠證實該觀點的證據)。
雖然這些雙盲檢測程序在心理科學中已習以為常,但在罪行審判中卻不多見(Wells & Olson,2003)。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為時不遠。新澤西州的總檢察官命令全州進行雙盲檢測,避免操縱目擊者指認嫌犯;進行逐個列隊指認,儘量減少在人群中進行簡單比較並從中選出最像罪犯的人加以定罪(Kolata & Peterson,2001;Wells & others,2002)。警察也可以用由肖恩·普賴克,羅德·林賽及其同事們(Pryke,Lindsay & others,2004)檢測過的新程序。他們請學生辨認曾訪問過教室的一個人,這種辨認是根據多種隊列進行的,即分開呈現的面孔、身體和聲音樣本的隊列。他們發現,能一致辨認同一個嫌犯——通過面孔、身體、聲音——的目擊者,幾乎都是十分精確的目擊者。
訓練陪審團
陪審員們能夠理性地評價目擊者的證詞嗎?他們瞭解列隊檢視的環境怎樣影響證詞的可靠性嗎?他們知不知道把目擊者的自信心考慮在內?他們能否認識到記憶如何被早先的誤導性問題、事件發生時的緊張、事件發生和提問之間的時間間隔、與嫌犯是否屬於相同種族以及其他細節的回憶是否模糊等等所影響呢?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的研究顯示,陪審員不能完全理解上述大部分因素,而我們現在知道,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目擊者的證詞(Culter & others,1988;Devenport & others,2002;Noon & Hollin,1987;Wells & Turtle,1987;Yarmey,2003a,b)。
為了培訓陪審員,現在專家們被頻繁地要求驗證目擊者的證詞(通常由被告的律師提出要求)。他們的目的是給陪審員一些你們剛才讀到的信息,幫助他們評價起訴方和被告目擊者雙方的證詞。表15-1列出了普遍公認的現象,它來自64個研究者對目擊者證詞的調查。
表15-1 目擊者證詞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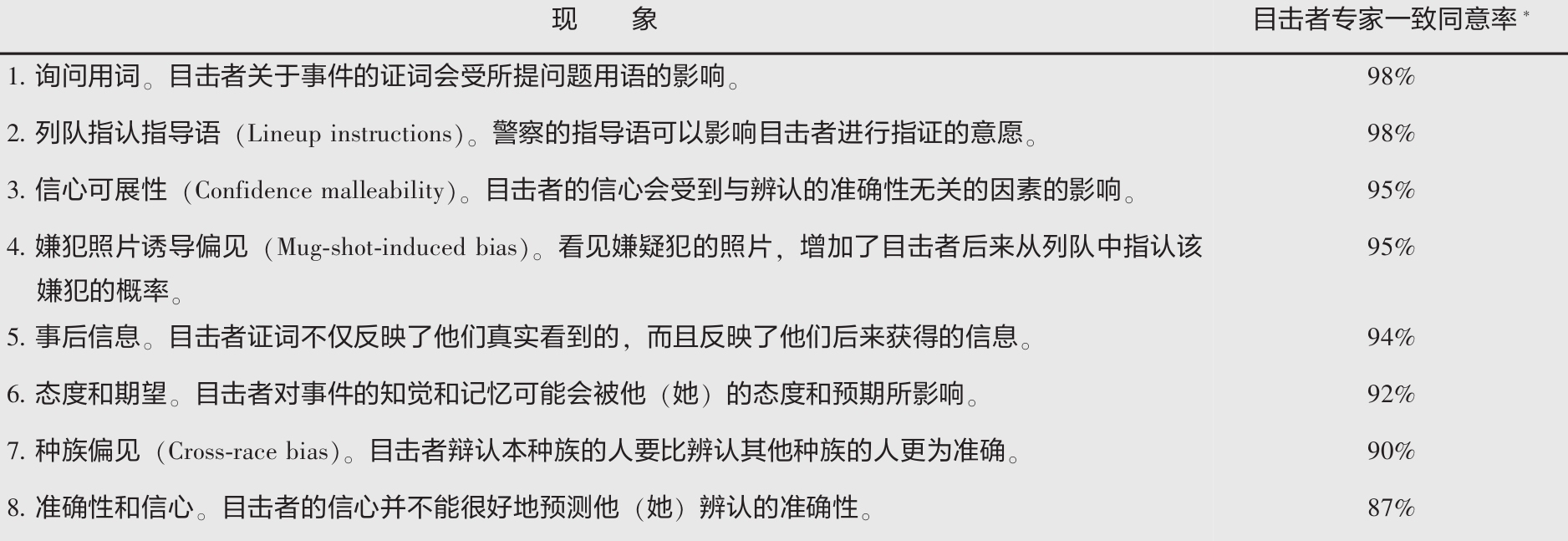
*這些現象足夠可靠,可以讓心理學家在法庭作證時呈現。
資料來源:From S. M. Kassin,V. A. Tubb,H. M. Hosch,& A. Memon(2001).
通過教給陪審員們在何種條件下目擊者的敘述是可以相信的,他們變得更具有辨別能力了(Culter & others,1989;Devenport & others,2002;Wells,1986)。另外,律師和法官也認識到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這有助於他們決定何時可以要求或者排除列隊指認所得證據(Stinson & others,1996,1997)。
小結
近期數百個實驗上演了法庭的程序,因為社會心理學家們相信,法庭提供了最自然的場景,便於研究人們如何做出判斷;同時他們也相信,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和方法,可以為重要的審判問題提供新的洞見。
實驗揭示,目擊者和陪審員都很容易形成一種錯覺,認為目擊者擁有的“心理記錄儀”是不會犯大錯的。但是當目擊者從記憶中構建和複述他所觀察到的事情時,錯誤就悄悄潛入了。研究提供了一些方法,能夠既減少目擊者報告中的錯誤,又減少陪審團運用該報告時的錯誤。
影響陪審團判斷的其他因素
被告的吸引力以及其與陪審團的相似性會使其判斷產生偏差嗎?陪審員能夠對法官的指示忠誠到何種程度呢?
被告的特徵
根據著名的審判律師克拉倫斯·達羅(Darrow,1933)所說,陪審員很少會給他們有好感的人判刑,或者宣告他們不喜歡的人無罪。他認為,審判律師的主要任務是組成一個對被告有好感的陪審團。這樣說正確嗎?另外,是否真的像達羅所說的那樣,“犯罪事實相對來說並不重要”嗎?
達羅言過其實了。有一個研究調查了3500多個刑事案件和4000多個民事案件,發現五分之四的案件裡法官同意了陪審團的決定(Kalven & Zeisel,1966)。儘管可能兩者都犯了錯誤,但有足夠明確的證據表明:陪審團能夠撇開他們的偏見,以事實為根據,達成一致的判決(Saks & Hastie,1978;Visher,1987)。事實起決定性作用。
不過,當讓陪審員做出社會決策時——這個被告是有意犯罪嗎?——就不光是事實起作用了。正如我們在第7章裡提到的,如果說話的人看起來很自信,也很有吸引力,那麼他的話也將更有說服力。陪審員不可能不對被告形成一定印象。他們能夠撇開這些印象,僅僅根據事實做出判斷嗎?
地位較高的被告常得到更為寬大的處理(McGillis,1979),由此看來的確存在一些起作用的文化偏差。但是現實中的案件是如此複雜多樣——犯罪的類型,被告的社會地位、年齡、性別以及種族——以至於很難區分出影響陪審團的那些因素。所以實驗者通常給模擬陪審員呈現相同的案件基本事實,只是變化一下被告的吸引力或者與陪審員的相似性,從而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
外表吸引力
在第11章裡,我們提到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漂亮的人們看起來更像好人。邁克爾·埃弗蘭(Efran,1974)考察了這種刻板印象是否會影響學生對一起詐騙案的判斷。他問多倫多大學的一些學生,外表的吸引力是否會影響他們對犯罪的判斷,他們的回答說,“不,應該不會的。”到底會不會呢?事實證明是會的。埃弗蘭給其他一些學生呈現被告的照片,一個長得有吸引力,另一個則沒有什麼吸引力。結果發現,他們認為更有吸引力的被告更可能無罪,並建議給他最輕的懲罰。
其他實驗者也證實了,當證據不足或者很模糊時,審判通常會受到被告外表的影響(Mazzella & Feingold,1994)。戴安娜·貝里和萊斯利·澤布羅維茨-麥克阿瑟(Berry & Zebrowitz-McArthur,1988)讓人們判斷有著娃娃臉的被告和有著成熟面孔的被告是否有罪。結果發現,有著娃娃臉長相的成人(有著大大的圓眼睛,小下巴)看起來似乎更加天真無辜,並且通常更容易被判為過失犯罪,判為有意犯罪的案件較少。如果被定罪,沒有吸引力的人使人們覺得更危險,特別是那些性侵犯案件(Esses & Webster,1988)。而像辛普森那樣的人,正如一個有遠見的陪審員所說,“是一個英俊的傢伙”很可能成為不傷害他的理由。
在一個由BBC電視臺完成的大型實驗中,理查德·懷斯曼(Wiseman,1998)給觀眾看一個有關盜竊案的證據,其中只有一個變量。一些觀眾看到的模擬被告,正好符合100個人心目中罪犯的那種刻板印象——沒有吸引力、鷹鉤鼻子、小眼睛。共有64000個人打電話進來,其中41%的人判定他是有罪的。而在英國其他地區的觀眾看到的是長得很有吸引力,有著娃娃臉和大大的藍眼睛的人,結果只有31%的觀眾認為他有罪。
為了檢驗這些發現是否能夠推廣到現實生活中,克里斯·唐斯和菲力浦·萊昂斯(Downs & Lyons,1991)讓警衛隊員在40個德克薩斯法官審判輕罪之前評價1742個被告的外表吸引力。無論案件的類型是嚴重(如偽造罪),中度(如騷擾罪)還是輕度(如公眾酗酒),法官們對外表不好的被告都判了更高的保釋金和更嚴厲的懲罰(見圖15-5)。怎樣才能解釋這種戲劇性的效應呢?是因為外表沒有吸引力的人地位更低嗎?或者他們就像法官們認為的那樣,更容易逃跑或者犯罪嗎?或者,法官們只是忽略了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建議:“一個明智的人最優之處和最高職責,在於抵制外表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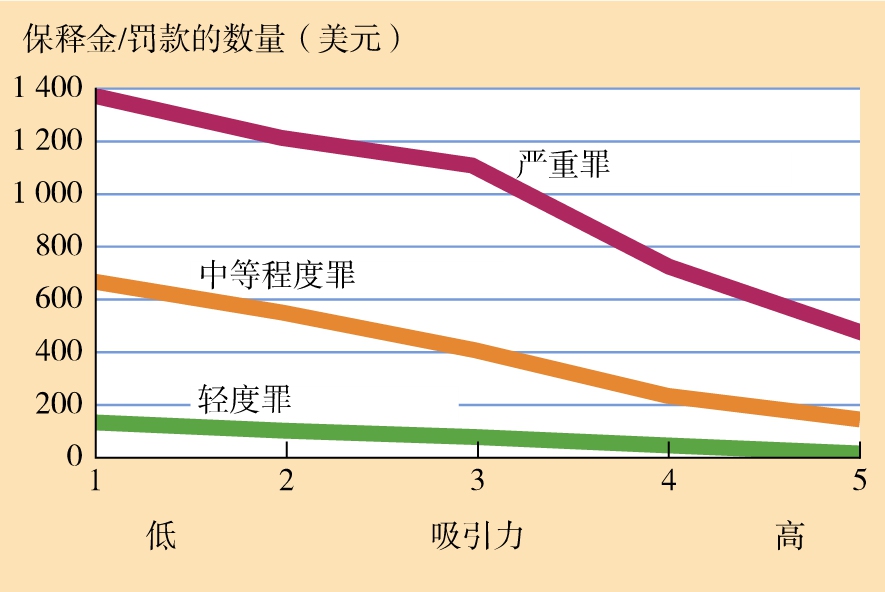
圖15-5 吸引力和審判
得克薩斯海灣法庭的法官對沒有吸引力的被告判了更高的保釋金和罰款。
資料來源:Data from Downs & Lyons,1991.
與陪審員的相似性
如果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所言“對被告是否有好感,會使判決帶上偏見”至少是部分正確的話,那麼其他可能影響好感的因素也應該起作用。在這些影響中有一個原理,在第11章裡也提到過,即相像(類似)會導致好感。當人們模擬陪審員時,他們對於與自己有著相同觀點、種族或性別(特別是在性騷擾案中)的被告更加有同情心(Selby & others,1977;Towson & Zanna,1983;Ugwuegbu,1979)。
這裡有一些例子:
保羅·阿馬託(Amato,1979)讓澳大利亞學生們讀一個出於政治原因的偷竊案,被告是左翼或右翼分子,發現如果被告的政治觀點與學生自己的觀點相似,他們更容易將被告判為輕罪。
庫基·斯蒂芬和沃爾特·斯蒂芬(Stephan & Stephan,1986)讓母語為英語的人們對一個被指控犯有襲擊罪的被告作判決,結果發現如果被告的證詞用的是英語而不是西班牙語或泰國語,人們就更可能認為這個被告沒有罪。
當被告的種族符合罪犯的刻板印象時——如白人犯貪汙罪,而黑人犯汽車盜竊罪——模擬陪審團會作出更為嚴厲的裁決和懲處(Jones & Kaplan,2003;Mazzella & Feingold,1994)。在種族問題不那麼顯眼時,贊成無種族偏見觀點的白人,更可能在審判中表現出種族觀點(Sommers & Ellsworth,2000,2001)。
根據克雷格·黑尼(Haney,1991)的報告,實際的重大案件中,數據顯示黑人被告通常被過分懲罰,或者作為受害者受害的程度被低估,或者兩者都存在。對1992年和1993年的8萬個判決案件的分析發現,在具有同樣的犯罪嚴重性和犯案歷史時,美國聯邦法官(其中只有5%為黑人)對黑人判的刑期要比白人判的刑期長10%(Associated Press,1995)。同樣,謀殺白人的黑人被判為死刑的概率,要大於謀殺黑人的白人(Butterfield,2001)。
[對辛普森是否有罪的判斷,在種族內部也有分歧。那些關注於性別特徵的白人婦女,特別可能認為辛普森有罪。以種族為其核心特徵的非洲裔美國人,特別可能認為辛普森無罪(Fairchild & Cowan,1997;Newman & others,1997)。]
似乎我們對一個我們認同的被告更有同情心。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不可能犯罪,那麼就很可能認為那些像我們的人也不會犯罪。這就幫我們解釋了在熟人強姦案中,為什麼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判被告無罪(Fischer,1997)。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在辛普森審判之前的一次全國性調查表明,有77%的白人將這個案子看成是至少“相當強烈地”不利於他的,相同的看法只存在於45%的黑人身上(Smolowe,1994)。這同樣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全是白人的陪審團宣判,暴力虐待了非洲裔美國人羅德尼·金的白人警察被無罪釋放時,會爆發大規模的騷亂。人們都爭論:如果一個沒有武器的白人被四個黑人警官追趕並逮捕,而且被暴打了一頓後,相同的陪審團還會無罪釋放他們嗎?
理想情況下,陪審團在法庭上可以拋棄他們的偏見,用開放的心態進行審判。正如美國憲法的第六修正案所說:“被控告者應該有權得到公正陪審團迅速而公開的審判。”當考慮到客觀性時,法律系統更類似於科學。因為科學家和陪審團要求證據。法庭和科學都有講證據的規則,兩者都要有翔實的記錄,並且都認為如果有相同證據,其他人都會作出同樣的決定。
當證據清晰而陪審團又集中注意在上面時(同樣當他們重讀證詞並爭論其意義時),他們的偏差實際上是最小的(Kaplan & Schersching,1980)。證據的質量,要比個別陪審員的偏見更為重要。
法官的指示
在法庭上,法官指示陪審團忽略帶有偏見的信息。我們每個人都能回憶起這樣的法庭劇鏡頭——一名律師大聲說,“尊敬的閣下,我反對!”於是,法官認可他的反對,並命令陪審團忽略對方律師暗示性的提問,或是目擊者的陳詞。
現在,幾乎美國所有的州都有“強姦案保護”法令,以禁止或限制提供關於受害者先前性行為的證詞。這種證詞雖然和當前的案子沒有關係,但往往會引起陪審團對被指控的強姦犯關於該女子同意發生性關係的辯護產生同情(Borgida,1981;Cann & others,1979)。然而,如果這種可信的、非法的或帶有偏見的證詞從被告嘴裡不經意地漏出,或經目擊者不假思索地說出,陪審團真的會按法官的指示去忽略它嗎?而法官提醒陪審團成員“問題的關鍵不是你喜歡被告與否,而是他有沒有犯罪”就夠了嗎?
極有可能不是這樣。一些實驗者報告說陪審團會關注既定程序(Fleming & others,1999),但是有時讓他們忽略一些不被允許的證據則是困難的,比如被告的前科。在一項研究中,斯坦利·休、羅納德·史密斯、凱茜·考德威爾(Sue,Smith,& Caldwell,1973)向華盛頓大學的學生提供了一場雜貨店搶劫凶殺案的描述,及原告和被告的陳詞概要。當原告的陳詞空白無力時,沒有人會判斷被告是有罪的。當加上了一盤和案件有牽連的被告的電話錄音帶時,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認為這個人是有罪的。法官關於錄音帶不是合法證據而應該被忽略的指示,無法消除這一破壞性證詞的影響。
實際上,莎倫·沃爾夫和戴維·蒙哥馬利(Wolf & Montgomery,1977)發現法官關於忽略證詞的命令——“這在你們對案件的思考中不應起任何作用。你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忽視它”——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助長證詞的影響力。或許這種聲明造成了陪審員的逆反 (reactance);或許它們使得陪審員對不被允許的證詞變得敏感起來,就像我提醒你看完這句話時不要看你的鼻子一樣。法官可以輕易地把不被允許的證詞從法庭記錄上抹掉,卻不能把它們輕易地從陪審員的思想裡抹掉。就像審判律師有時說的那樣,“你不能讓鐘不鳴。”對於帶有情感色彩的信息,就更是如此(Edwards & Bryan,1997)。與這種不被允許的信息不那麼情感化(“用致命武器攻擊”)相比,當陪審團為對被告行為活靈活現的描述(“砍死一名婦女”)所吸引時,法官命令忽略的指示就更容易適得其反。即使後來陪審團聲稱,他們已經忽略了不被允許的信息,這些信息也可能已經改變了他們對其他信息的分析。
審訊前的公開報道也很難被忽略,特別是在真實的陪審團和性質嚴重案件的研究中(Steblay & others,1999)。在一項大規模實驗中,傑弗裡·克雷默和他的同事(Kramer & others,1990)讓大約800名模擬陪審團成員(大部分抽自真實的陪審團名單)接觸到有關一名有前科男子的新聞報道,這名男子現在被指控搶劫超市。在陪審員看過重現當時場景的審訊錄像帶後,他們要麼聽到、要麼沒有聽到法官關於忽視審訊前公開報道的指示。但是法官勸誡的效果卻為零。更有甚者,那些被公眾影響而帶有偏見的人們通常否認受到了影響,並且,這種否認使得要減少有偏見的陪審員數目變得困難(Moran & Cutler,1991)。在實驗中,甚至讓模擬陪審員發誓保證公正性、願意忽視前期信息,都不能削減審訊前公開報道的影響(Dexter & others,1992)。這樣看來,辛普森的律師就有理由為審訊前鋪天蓋地的公開報道而擔心;而法官也有理由命令陪審團成員不要觀看相關的媒體公開報道,並在審訊過程中把他們與外界隔離起來。
法官可能希望,並且現有研究也有某些證據認為,在審議時,那些使用不被允許的信息的陪審員會被阻止這樣做,陪審團的裁決因此不會受到這些證據的太多影響(London & Nunez,2000)。為了把不被允許的證詞的影響力降到最低,法官通常事先提醒陪審團注意某些特定類型的證據是無關的,如強姦案受害者的性經歷。一旦陪審員根據這些證據形成了印象,法官勸誡的效果就要小得多(Borgida & White,1980;Kassin & Wrightsman,1979)。這樣看來,據維基·史密斯(Smith,1991)報告,一個審訊前的開庭訓練是有效的。對陪審團成員進行法律程序和辯護標準的指導,有助於提高他們對審訊程序的理解,增強他們直到聽完所有審訊信息再做判斷的意願。
更有效的是,法官可以在陪審團聽到不被允許的證詞之前就切斷它們,比如用錄製證詞的錄像帶,刪除未經許可的部分。現場證詞和錄製證詞,與現場和錄像帶裡的列隊指認一樣,都具有影響力(Cutler & others,1989;Miller & Fontes,1979)。也許,以後的法庭應該裝有和實物一樣大小的電視監視器。持反對意見的批評者認為,這種程序使陪審團無法觀察到被告和其他人對證據做出的反應。贊成者則認為,錄像的方式不僅可以使法官剪輯不被允許的證詞,還可以加速審訊進程,同時使目擊者在記憶消退前講述關鍵事件。
其他因素
我們已經討論了三個法庭上的要素——目擊者證詞,被告的特徵和法官的指示。研究者也考察了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在密歇根州立大學,諾伯特·克爾和他的同事們(Kerr & others,1978,1981,1982)研究過這些問題:一個可能的嚴厲懲罰(如死刑)會使陪審團不願做出判決嗎——洛杉磯的檢察官們是因此不要求給辛普森判死刑嗎?有經驗的陪審員做出的判決與那些新手們的判決有所不同嗎?當受害者較有吸引力或受害嚴重時,被告會被處以更重的刑罰嗎?克爾的研究結果表明,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是的”。
馬克·阿利克、特雷莎·戴維斯(Alicke & Davis,1989)和邁克爾·恩佐、溫迪·霍金斯(Enzle & Hawkins,1992)所做的實驗表明,受害者的特點會影響到陪審團對過失和刑罰的判斷,即使是連被告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時候。以1984年“地鐵警衛”案中的伯納德·戈茨為例。當四個青年在紐約的一個地鐵車站走近他並向其索要五美元時,受到驚嚇的戈茨拔出裝有子彈的手槍向他們開槍,射死了其中三個,剩下一個局部癱瘓。戈茨被指控為蓄意謀殺,這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抗議,並對戈茨表示支持。公眾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基於那幾個青年普遍有犯罪記錄,而且當時他們中的三個帶有藏匿的尖利螺絲刀。雖然戈茨並不知道這些,但他開脫了被指控的蓄意殺人罪,而僅被判以非法擁有武器罪。
小結
案件的事實通常有足夠的說服力,使陪審團放下偏見給出一個公正的判決。然而,當證據模糊時,陪審團往往傾向於用他們先入為主的偏見來解釋案件,並對有吸引力或者與自己相似的被告表示同情。
當陪審團接觸到破壞性的審訊前公開報道或不被允許的證據時,他們會聽從法官的指示將其忽略嗎?在模擬審訊中,法官的命令有時候是被遵守的,但是通常,特別是當法官的勸誡出現在印象形成以後,則沒有被遵守。研究者還研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受害者的特徵。
什麼影響了個體陪審員
判決取決於法庭上所發生的事情——目擊者的證詞,被告的特徵,法官的指示。同時,判決也取決於作為個體的陪審員怎樣處理信息。
法庭對於“普通陪審員”的影響值得思考。但是,沒有一個陪審員是所謂的普通陪審員,每一個人都把他的態度和個性帶進了審訊室。並且當他們商議時,陪審員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兩個關鍵的問題是:(1)判決是怎樣被作為個體的陪審員的心理傾向所影響的?(2)判決又是怎樣被群體商議所影響的?
陪審員的理解
為了對陪審團的理解作出探討,南希·彭寧頓和裡德·黑斯蒂(Pennington & Hastie,1993)抽取法院陪審團人員作為模擬陪審員,觀看真實的審訊過程。在做出決策的過程中,這些陪審員首先編造了一個令所有證據都能說得通的故事。例如,在觀察一場謀殺案審訊時,一些陪審員得出結論認為,被告由於爭吵而被激怒,他拿起刀,找到受害者並將其捅死。另一些人則推測,受到驚嚇的被告拿起一把他用來自衛的刀,卻碰到了死者。當陪審團成員開始商議時,通常會為發現其他人編造的故事與己不同而感到吃驚。這就意味著——研究也同時證明——當律師以敘事也就是故事的形式提出證據時,陪審員最容易被說服。在重罪案(全國判罪率達80%)中,原告陳詞比被告陳詞更多地採取敘事的形式。
理解指示
接下來,陪審團成員必須領會法官做出的關於有效判決範疇的指示。為了使這些指示行之有效,陪審員必須首先理解它們。一個又一個的研究卻發現:許多人並不理解法官用以指示的標準法律術語。根據案件的類型,陪審團會被告知辯護的標準應該是“佔優勢”的證據,“清楚又可信”的證據,或是“沒有理由懷疑”的證據。這些陳述在法律界中其含義都是確定惟一的,但在陪審員的腦子裡卻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Kagehiro,1990)。在一項內華達州的犯罪指示研究中,觀看指示錄像的人僅能對向他們提出的89個問題中的15%做出回答(Elwork & others,1982)。
法官也會提醒陪審團,在他們權衡每一項新證據時,要避免過早地下結論。但是,不只對大學生,就是對從未來的陪審團成員中選出來的模擬的陪審團成員的研究都表明了,易受感動的人類確實有過早的判斷,而這種過早的判斷確實影響了他們如何解釋新的信息(Carlson & Russo,2001)。
在觀察了真實案例和採訪了那些陪審員之後,斯蒂文·阿德勒(Stephen Adler,1994)發現“很多真誠又嚴肅的人們——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遺漏了要點,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不相關的問題上,屈從於難以識別的偏見,看不透最廉價的對同情或憎惡的訴求,因而通常搞砸了自己的工作。”
伊梅爾達·馬科斯(Imelda Marcos)因轉移價值數億美元的菲律賓貨幣到美國銀行以供己用而受到指控。在對她的審訊中,律師排除了任何知道她在其丈夫專制統治中扮演何種角色的人。由於不甚瞭解複雜的貨幣交易,這些坐在陪審團席位上的不知情的人們,反而開始表達對伊梅爾達的同情——她不過是一個身著黑衣,手持念珠,抹著眼淚的女人(Adler,1994)。
如果隨著程序從決定有罪還是無罪的審訊階段進入到定罪階段,判斷標準要發生變化的話,那麼,陪審團成員就更要糊塗了(Luginbuhl,1992)。例如,在北卡羅來納,陪審團只有當存在“無理由懷疑的證據”時才可以進行定罪。但是,當判斷是否存在減輕罪責的情況(如童年時曾受虐待),以致可避免死刑判決時,一個“佔優勢的證據”就足夠了。
最後,陪審團還得在自己的解釋與判決的範疇之間作一比較。例如,當用到法官關於法律上正當防衛的定義時,陪審員必須決定“按在牆上”是否和他們理解的“不能逃跑”的情況相一致。通常情況下,法官那抽象的、滿是術語的判決範疇的定義,敵不過陪審員自己腦海裡想像的犯罪場面。維基·史密斯(1991)認為,不管法官的定義怎樣,如果被告的行為與陪審員關於“暴力行為”、“攻擊”或“搶劫”的形象一致,他們就會認為這個人有罪。
理解統計信息
對在辛普森的前妻和她的同時受害者被謀殺現場發現的血液進行的測試顯示,血斑符合辛普森的血蛋白組合,而不符合被害者的。根據每二百個人中只有一個有這樣的血型,控方推斷有99.5%的可能辛普森就是凶手。但是辯方認為,二百比一意味著,凶手可能是洛杉磯至少四萬人中的任何一個。面對這樣的理由,威廉·湯普森和愛德華·舒曼(Thompson & Schumann,1987)報告說,五個人中會有三個人不大相信血型證據的重要性。事實上,雙方的律師都錯了。這一證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那其餘四萬人中幾乎很少有人可能被合理地認為是嫌疑犯。但是,99.5%的說法又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被告被起訴,只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的血型相符。[艾倫·德肖威茨(Alan Dershowitz),辛普森的一位辯護律師,向媒體宣稱在一千個虐待妻子的男人中只有一個後來會殺了她。而批評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一個丈夫若是虐待妻子並且她的妻子被謀殺了,他可能有罪的概率。根據現有的數據,喬恩·默茨和喬納森·考爾金斯(Merz & Caulkins,1995)計算出其概率為81%。 ]
當更精確的DNA測試發現與辛普森的血型相符後,原告就爭辯說這種匹配的機會僅有一億七千萬分之一,同時,被告的辯護律師則表示專家懷疑DNA測試的可信性。但是,加里·韋爾斯(Wells,1992)及基思·尼德邁耶和他的同事們(Niedermeier & others,1999)報告說,即使人們(包括有經驗的審判法官們)理解純粹的統計概率,他們仍可能不被說服。例如,藍色公交公司有80%的輪胎符合軋死一隻狗的公交車軌跡,而灰色公交公司的只有20%,但是他們很少因此給藍色公交公司定罪。原始數據允許可能的其他選擇出現——這場事故是由灰色公交公司的那20%的輪胎製造的。但是若有目擊者目擊該公車是藍色的,人們通常就會給它定罪,即使這個目擊者被證實只有80%做出正確判斷的可能性。在第一個案例中,這種似乎可行的其他場景產生了一個心理差異,這種差異存在於說一件事情有80%的可能性是真實的,與說一件事情在80%的置信概率水平上是真實的之間。
這樣看來,純粹的數字必須有可信的情節來支持。於是,韋爾斯說,在多倫多一樁母親為孩子尋求父親監護敗訴的案子中,血液測試已經說明有99.8%的可能性那名男子就是孩子的父親。但是,在該男子堅持了自己的立場,有力地否決了這項斷言後,她敗訴了。
增強陪審團的理解
理解陪審團成員是怎樣誤解法官指示和統計信息,是邁向更好決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讓陪審員們可以接觸到法院文本,而並非強制他們僅憑記憶來處理複雜的信息(Bourgeois & others,1993)。再下一步是,設計並檢驗更清晰、更有效的方式來提供信息——這是一些社會心理學家目前正在從事的工作。例如,當法官在量上規定了證據必需的標準時(如51%,71%或91%的確定性),陪審員就會理解和恰當地做出反應(Kagehiro,1990)。
當然了,就像《伊利諾伊州死刑判決法案》要求的,必須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告訴陪審員,不要在可辯護的情形下對謀殺案件做出死刑判決:“如果你們從對證據的考慮中不是一致地發現,沒有任何可以減緩的因素足以避免死刑判決,那麼你們應該簽署一份要求法庭做出其他判決的決議”(Diamond,1993)。當給予陪審員用簡單語言重寫的指示時,他們不大會受法官偏見的影響(Halverson & others,1997)。
菲比·埃爾斯沃思和羅伯特·莫羅(Ellsworth & Mauro,1998)根據陪審團研究得出令人沮喪的結論:“法律指示通常以這樣一種方式給出,即挫傷最認真地去理解的意願……它的語言技術性太強,並且……既沒有任何嘗試去評估陪審員對法律的錯誤預見,也沒有提供任何有益的教育。”
陪審團的選擇
既然在陪審員之間存在各種個體差異,審訊律師會不會利用陪審團選擇程序,使組成的陪審團有利於自己呢?法律人士認為有時候這是可能的。美國審訊律師協會的一位主席大膽地宣稱:“審訊律師善於協調人類行為中細微的差異,從而發現最微小的偏見的跡象,或難以達成合適決議的可能性”(Bigam,1997)。
如果留意的話會發現人們對他人的判斷易於出錯,可社會心理學家懷疑律師頭腦中裝備了調節良好的社會輻射計數器。在美國一年大約6000場審訊中,顧問們——其中有些是美國審訊顧問協會的社會科學家——幫助律師挑選陪審員和設計策略(Gavzer,1997;Miller,2001)。在一些著名的案件中,調查研究者利用“科學的陪審團選擇法”幫助律師除去那些不易引起共鳴的人。一樁著名的案子捲入了兩名尼克松總統的前內閣成員,即保守派人士約翰·米切爾和斯坦斯(John Mitchell & Maurice Stans)。調查表明,從被告方的觀點出發,最糟糕的陪審員可能是“一個自由派的猶太民主黨員,這個人讀《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聽瓦爾特·克朗卡特(Walter Cronkite),對政治事件很感興趣,又對水門事件知之甚多”(Zeisel & Diamond,1976)。在最初九場審訊中,依靠“科學的”選擇方法,被告方贏了七場(Hans & Vidmar,1981;Wrightsman,1978)。(然而,我們無法知道,如果不用科學的選擇陪審團的方法,九場中到底可贏幾場。)
現在,許多審訊律師利用科學的陪審團選擇法,找出一些問題並用它們排除對自己委託人有偏見的陪審員,並且大部分人報告結果是令人滿意的(Gayoso & others,1991;Moran & others,1994)。當法官問,“如果您讀過一些會對這個案子產生偏見的內容,請舉手”,大部分陪審員不會直接承認他們的先入之見。這需要進一步提問使其暴露。比如,如果法官允許律師試探預期的陪審員對毒品的態度,這名律師就可以據此猜測他們在一樁毒品交易案件中會做什麼樣的判決(Moran & others,1990)。同樣,一個承認“不太相信精神病醫師的證詞”的人,較不易接受對精神病患者的辯護(Cutler & others,1992)。
對一個案例具體特點的反應是有個體差異的。種族偏見與種族問題案件相關;性別觀念似乎只與強姦或襲擊婦女案件的判決有關;個人責任信念與集體責任信念之間的權衡,與起訴公司的工傷賠償案件有關(Ellsworth & Mauro,1998)。
儘管科學地選擇陪審團是刺激的,也是關乎道義的,實驗仍然表明:態度和個人特徵並不總是能預測判決。“沒有神奇的問題可以用來詢問未來的陪審員,甚至也沒有一項保證可以說,一項特殊調查就能探知有用的態度—行為之間的關係或個性—行為之間的關係,”斯蒂芬·彭羅德和布賴恩·卡爾特(Penrod & Culter,1987)警告。研究者米切爾·薩克斯和裡德·黑斯蒂(Saks & Hastie,1978)也表示同意:“研究一致表明,實質上,與陪審團成員個性特點相比,證據對於陪審員的判斷是一個更為有力的決定因素”(p. 68)。最佳的結論是,對一些案子來說,顧問選擇陪審團確實能造成一些差別,但這類案子是稀少的,而且相互之間相去甚遠”,尼爾·克雷塞爾和多利特·克雷塞爾(Kressel & Kressel,2002)補充道。在法庭上,陪審員公開作公正誓言和法官促使其“公正”的指示,都強有力地讓絕大部分陪審員遵循公正準則。
實驗表明,只有當證據模糊時,陪審員的個性和總體態度才產生影響。而且,加里·莫蘭(Gary Moran)及其同事認為,如果科學選擇陪審團的做法比依靠律師對陪審員傾向的預感更勝一籌,那麼在一樁重要的案子裡,你又何樂而不為呢?
話雖如此,不同案例的差異,尤其是證據方面的差異,才是最關鍵的。薩克斯和黑斯蒂總結道,“不論和陪審團相關與否,這在人類行為方面都意味著,雖然我們是不同的個體,但我們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的相似點所掩蓋。並且,我們可能遇到的情形要比遇到這些情形的人要複雜得多”(p.69)。
“死刑認定”陪審員
一個封閉的 案件可以由那些入選陪審團的人來決定。在刑事案件中,那些不反對死刑判決的人——也就是那些在允許死刑的情況下易於做出決策的人——更傾向於贊成起訴,認為法庭縱容了罪犯,並反對保護被告的憲法權利(Bersoff,1987)。簡單地說,那些支持死刑判決的人更關心控制犯罪率,而非法律的應有程序。當法庭遣散可能對死刑判決心存猶疑的陪審員時——這是辛普森案的原告方未做的——將形成一個更可能做出定罪表決的陪審團。
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科學家“在偏見對死刑認定的影響上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克雷格·黑尼(1993)報告說。研究記錄是“統一”的,菲比·埃爾斯沃思(Ellsworth,1985,p.46)說:“死刑案件中的被告,面對那些傾向於給他定罪的陪審員,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不僅如此,傾向於定罪的陪審員往往更加專斷——他們更加嚴厲和具有懲罰性,無視可以減輕罪責的情況,對社會底層的人也更加傲慢(Gerbasi & others,1977;Luginbuhl & Middendorf,1988;Moran & Comfort,1982,1986;Werner & others,1982)。
由於法律體系是依據傳統和先例運行的,這些研究成果也只能緩慢地改變實際司法工作。198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一項有爭議的決定中推翻了一個低層法院的裁決,認為其“死刑認定”陪審員確實有偏見。埃爾斯沃思(1989)認為,在這個案例中,最高法院對有說服力的和前後一致的證據不予理睬,部分是因為本案“死刑認定上有主觀性”,部分是因為擔心,判決上千人死刑的話會導致社會秩序混亂,而不得不重新考慮。最高法院希望把這種解決方法應用到以後的案例中去,也就是說,召集不同的陪審團(a)確定當處以死刑的凶殺案的罪行,並量刑判決;(b)並且在給出罪行後,能夠聽取關於罪犯動機因素的更多證據,從而在死刑和監禁之間做出選擇。
但是,這裡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深層問題:是否死刑本身,就是在美國憲法關於“殘忍的和罕見的刑罰”的禁令之下呢?其他一些國家是這樣認為的。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西歐和大部分南美國家的讀者所知道的那樣,他們的國家是禁止做出死刑判決的。在美國,公眾態度是傾向於支持任何盛行的做法的(Costanzo,1997)。但是美國民眾贊成死刑判決的態度似乎正在軟化。在1994年達到了80%,2002年就降為70%了(Jones,2003)。在伊利諾伊州13名男子由於新證據被免除死刑判決後,州長喬治·瑞安(George Ryan)宣佈了緩期執行(Johnson,2000)。
每100000人中的平均殺人案發率
全美:9
有死刑的州:9.3
資料來源:《科學美國人》,2001年2月
在與量刑的博弈中,美國的法院在考慮法庭量刑時是否過於專斷,量刑時是否帶有種族偏見,是否這種合法的殺人會減少非法殺人的情況。社會心理學家馬克·科斯坦佐(Costanzo,1997),克雷格·黑尼和迪恩·洛根(Haney & Logan,1994)認為,社會科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清楚的。就制止犯罪問題來說,有死刑的州的刑事殺人案發率並沒有因此更低。刑事殺人案發率沒有因為某些州採取死刑判決而降低,也沒有因為廢止這項刑罰而升高。當因一時衝動而觸犯刑律時,人們不會因為計算後果(無假釋的終身監禁也是一個有力的制止因素)而止步。此外,死刑量刑輕重也是不一致的(田納西州是紐約的四十倍),並且在貧窮的被告那裡,辯護常常是很虛弱無力的(Economist ,2000),因此他們也更多地被處以極刑。然而,最高法院還是認為,認可死刑案件陪審團,其本身就是同樣地位的陪審團的代表,並且“死刑無疑是一個有意義的威懾因素。”
大驚失色的社會科學家說,撇開人道主義不談,面對矛盾的證據時,我們依據什麼,堅持我們懷有的假定與直覺?為什麼不將文化因素加入測試當中?如果它們找得到支持,豈不是更好。如果由於矛盾的證據而陷入僵局,這對他們當然更糟。這種批判性思維的理想,正是心理科學與公民民主的推動力。
小結
事關重要的不僅僅是法庭上所發生的,陪審員的內心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同樣重要。
在判斷的形成中,作為個體的陪審員:(1)構思出一個可以解釋證據的故事;(2)考慮法官的指示;(3)在他們的理解與可能的裁決之間作出比較。在一個封閉案件中,陪審員個人的特徵會影響他們的判斷。支持死刑或者非常專斷的陪審員更易於給特定類型的被告定罪。然而,最重要的不是陪審員的個性和總體態度,而是他們必須對之做出反應的情境。
群體因素對陪審員的影響
哪些因素影響到個體的陪審員把他們的預先判斷聯合成一個群體決定這一過程?
設想一下,陪審團剛剛結束一場審訊,走進陪審團房間開始商議。研究者哈里·卡爾文和漢斯·蔡塞爾(Kalven & Zeisel,1966)報告認為,約有2/3的陪審團最初不會就一項判斷達成一致的裁決。但是,經過討論95%會產生一致意見。很明顯,群體影響起了作用。
僅僅在美國,一年就有30萬次要從300萬人中抽選出小群體承擔陪審團責任,集合起來做出一個集體決定(Kagehiro,1990)。他們和其他地方的陪審員一樣,會受到塑造其他決策群體的社會影響因素的制約嗎,比如多數派或少數派模式,群體極化或是小集團意識?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如果我們知道陪審員最初的傾向,我們能夠預測他們的判斷嗎?
法律禁止觀看真實的審議過程。因此研究者模仿這一過程。他們向模擬陪審員提供一個案例,並讓他們像真實陪審團那樣進行審議。在伊利諾伊大學進行的一系列這類研究中,詹姆斯·戴維斯等人(Davis,Holt,Kerr,& Stasser)測試了各種數學模型來預測群體決定,包括模擬陪審團的決定(Davis & others,1975,1977,1989;Kerr & others,1976)。陪審員們的最初判斷的某種數學組合能夠預測最終的群體決定嗎?戴維斯和他的同事發現,最佳預測模型會隨案件的性質而變化。但是許多實驗表明,“2/3多數”是最好的:群體裁決通常是那個最初被至少2/3的陪審員支持的選擇。沒有達到這個多數,陪審團往往會懸置不決。
同樣地,卡爾文和蔡塞爾對陪審員的調查也發現,陪審團中有90%的人可能達成在第一輪投票中被多數支持的決定。雖然你我也會幻想,某天一個勇敢的陪審員獨自一人改變多數決定,可事實上這種情況極少發生。
少數派的影響
很少發生,但有時也是可能的,就是最初的少數派意見後來佔了上風。一個典型的12人陪審團就像一個典型的小型的大學課堂:三個最沉寂的人幾乎什麼也不說,三個最有發言欲的人貢獻了一半以上的談話(Hastie & others,1983)。在米切爾-斯坦斯(Mitchell-Stans)審判中,四個陪審員堅持要無罪釋放,並且不斷發表意見,最後他們贏了。對少數派影響的研究顯示,如果佔少數的陪審員能夠保持一致、堅持不懈、信心十足,他們將最有說服力,特別是當他們能夠引起某些人倒戈時(Gordijn & others,2002;Kerr,198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米切爾-斯坦斯審訊中最有影響力的少數派陪審員安德魯·喬(Andrew Choa)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紐約時報》的讀者——一個並不符合調查結果所概括的、對被告有同情傾向的陪審員。但是,喬也是尼克松政府忠誠的支持者,同時他還是一家銀行的副總裁,經常以向其他陪審員提供各種好處而受到歡迎,如帶他們在銀行私有的禮堂看電影(Zeisel & Diamond,1976)。喬的例子也說明了陪審團實驗中一個普遍的發現:社會地位高的男性陪審員往往是最有影響力的(Gerbasi & others,1977)。
群體極化
陪審團的審議過程還以其他一些有趣的方式轉變了人們的看法。在實驗中,審議通常加強了最初的意見。例如,羅伯特·佈雷和奧德麗·諾貝爾(Robert Bray & Audrey Nobel,1978)讓肯塔基州立大學的學生聽取30分鐘的謀殺案審訊錄音帶。然後,在設想被告有罪的條件下,他們提出予以監禁。高專斷性的小組起初建議嚴厲懲罰(56年),在商議後則變得更加嚴厲(68年)。低專斷性的小組起初較為寬大(38年),商議後更加寬大(29年)。
陪審員中會發生群體極化的證明,來自裡德·黑斯蒂、斯蒂文·彭羅德、南希·彭寧頓(Hastie,Penrod,& Pennington,1983)所做的一個宏大的研究。他們把選自馬薩諸塞州的69個十二人陪審團集合在一起,分別向每一個陪審團再現了一個真實謀殺案例,裡面的角色由一位有經驗的法官和真實的律師扮演。然後,讓這些人在陪審團房間裡商議這個案件,時間不限。由圖15-6可見,證據是說明有罪的:4/5的陪審團在商討前認為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不夠確定“過失殺人罪”這個較輕的定罪是否是他們最願做的選擇。經過討論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原告是有罪的,而且大部分的人現在選擇一個較重的定罪——二級謀殺。可見,通過商議,他們最初的傾向被加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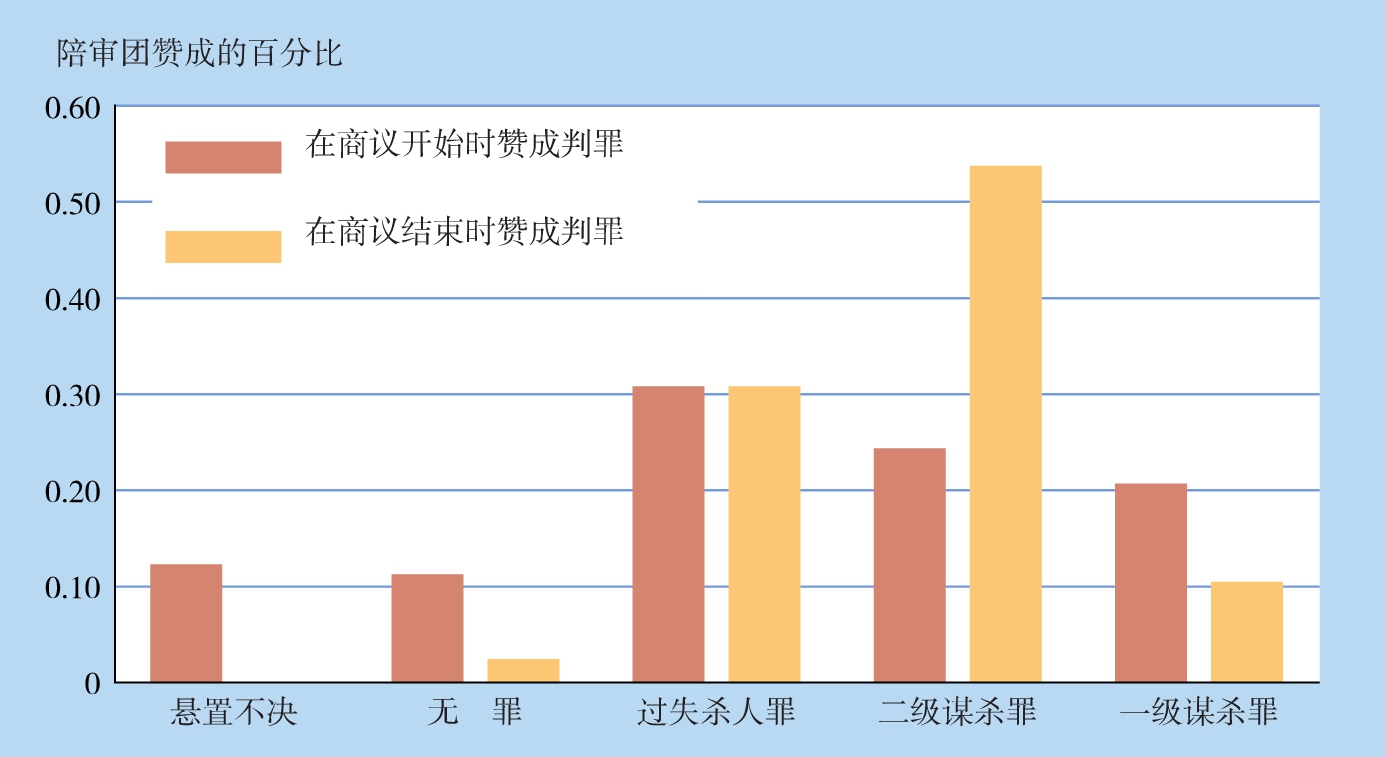
圖15-6 陪審團中的群體極化
在一場高度仿真的模擬謀殺案審訊中,828個馬薩諸塞州的陪審員陳述了他們最初的裁決選擇,然後就這個案子商議了不同的刑期,從三小時到五天不等。商議加強了最初的傾向,也就是支持原告。
寬大
在許多實驗中,商議的另一個奇特的效果浮出水面:特別是當證據並未充分說明有罪時,參與商討的陪審員通常變得更加寬容(MacCoun & Kerr,1988)。這修正了“2/3多數原則”,因為即使只有一個勉強的多數支持無罪判決 ,它通常也會勝出(Stasser & others,1981)。此外,支持無罪的少數派會比支持定罪的少數派擁有更多成功的機會(Tindale & others,1990)。
又一次,對真實陪審團的調查證實了實驗室的結果。卡爾文和蔡塞爾(Kalven & Zeisel,1996)報告說,在那些多數派沒有成功的案例中,審判結果通常轉為無罪(例如米切爾-斯坦斯案的審判)。當法官和陪審團意見不一致時,也通常是因為陪審團認為法官想定罪的那個人是無罪的。
可能是“信息性影響力”(來源於其他人有說服力的論證)增加了寬大處理嗎?“無罪推定”和“沒有理由懷疑的證據”原則,給那些支持定罪的人增加了證明方面的困難。也許是“規範性影響力”造成了寬大的效果,這種情形通常發生在自認為公正的陪審員,遇到了那些比他更關心對可能無辜的被告予以保護的陪審員時。
12個人會比1個人要好嗎
在第8章,我們已經知道,在“客觀準確的答案存在於何處”這一思辯問題上,群體判斷優於大多數個人的判斷。陪審團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嗎?在商議時,陪審員通過強調自己的觀點來試圖改變他人的判斷,從而施加規範性壓力。但是,他們也共享信息,從而擴大彼此對案件的瞭解。那麼,信息性影響力會產生更好的集體判斷嗎?
證據雖然不夠充分,但是令人鼓舞。群體比個體成員能更好地回憶審訊中的信息(Vollrath & others,1989)。有時,群體商議不僅去除了一些偏見,而且也把陪審員的注意力從他們自己的預先判斷吸引到事實證據上來。看起來,十二個人確實比一個人要好。
6個人會和12個人一樣好嗎
為了保持他們的英國傳統,美國和加拿大的陪審團習慣上都是由12人組成的,他們的任務是達成共同意見——一個全體一致的判決。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提起公訴的幾件案子中,美國最高法院宣佈,對於民事案件或不可能涉及死刑的州內刑事案件,法庭可以使用6人組成的陪審團。不僅如此,高等法院還肯定了各州有權利允許並非一致意見的判決,甚至支持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基於9:3選票的判決(Tanke & Tanke,1979)。最高法院聲稱,沒有理由認為較小的陪審團,或沒有達成完全一致意見的陪審團,就會和傳統陪審團在商議和決策上有什麼不同。
最高法院的設想,既引發了來自法律學者的大量批評,也遭受了社會心理學家雪崩般的指責(Saks,1974,1996)。一些批評僅是簡單的統計問題。例如,若一個社區總陪審團候選人的10%是黑人,那麼,只有72%的12人陪審團,或只有47%的6人陪審團可以期望有至少一個黑人。可見,小規模的陪審團較難反映出社區的多樣性。並且,如果在一個給定案例中,最初有1/6的陪審員支持無罪判決,這在6人陪審團中只是一個人,在12人中就有兩個人。最高法院認為,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這兩種情況沒有什麼區別。但是從我們對從眾效應所做的討論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少數派抗拒群體壓力,要比兩個人的少數派難得多。從心理學上來說,一個分裂為10:2的陪審團並不等於一個分裂為5:1的陪審團。毫不奇怪,12個人的陪審團面臨一個懸而不決的判決的可能性,是6人陪審團的兩倍(Ellsworth & Mauro,1998,Saks & Marti,1997)。[擱置未決情況不成其問題,因為在最近13年間的59511件刑事審判案中,只有2.5%是擱置未決的,67992件聯邦民事審判案中只有0.6%擱置未決(Saks,1998)。 ]
其他的批評建立在詹姆斯·戴維斯等人(1975),以及查倫·內梅斯(Nemeth,1997)和米切爾·薩克斯(1977,1996)所做實驗的基礎上。在這些模擬陪審團實驗中,來自小陪審團或不一致意見的陪審團的判決的整體分佈,與意見一致的12人陪審團的並無明顯不同(雖然較小規模陪審團的判決相對較難預測——例如,在裁定損害賠償額上有更多的差異)。但是,在這裡,對商議的影響就更大了。在使每一個陪審員更多更平衡地參與上,一個較小的陪審團擁有優勢。尼古拉斯·費伊等人(Fay,Garrod,& Carletta,2000)注意到,根據他們對格拉斯哥大學生的研究,與大於10人的陪審團的商議相比較,在較小群體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個體較少會擁有不成比例地大的影響力;更多對話,更少獨白,所以更常達成共識。
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較大的陪審團確實也具有重要的優勢。研究陪審團的米切爾·薩克斯(1998)總結說:“與較小的陪審團相比,較大的陪審團更可能包含少數民族群體成員,能更準確地回憶起審判證詞,有更多時間商議,會更經常地擱置未決,看起來更可能作出‘正確’的判決。”
1978年,在這些報告中的一些公佈之後,最高法院拒絕通過佐治亞州的5人陪審團(儘管該州仍保留有六人陪審團)。在宣佈這項決定時,法官哈里·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引用邏輯和實驗數據辯論說,5人陪審團代表性較弱,較難取信也不那麼精確(Grofman,1980)。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援引的許多數據都包含對6人陪審和12人陪審的比較,因此其自身也就否定了6人陪審團制度。但是,由於業已作出和維持對六人陪審團的承諾,最高法院沒有證實這個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此種情況(Tanke & Tanke,1979)。
從實驗室到生活:模擬陪審團和真實陪審團
也許在讀這一章時,你會考慮一些批評者(Tapp,1980;Vidmar,1979)也考慮過的問題:在大學生討論假設案例和真實陪審員討論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命運之間,是否有巨大的鴻溝?這種情況確實存在。在信息最少的條件下,權衡一個模擬的決議是一件事,為一個真實案例的複雜和意義深遠的後果而苦惱則是另一件事。因此,裡德·黑斯蒂等人(Hastie,Kaplan,Davis,& Borgida)曾要求那些有時選自真實陪審員候選人的參與者,觀看對真實審訊過程的場景重現。這種場景重現如此真實,以至於參與者有時都忘了電視裡的審訊場面僅僅是表演而已(Thompson & others,1981)。
由學生模仿的陪審員也很投入。“當我偷聽模仿的陪審團時,”研究者諾伯特·克爾(Kerr,1999)回憶道,“我確實被迷住了。陪審員們頗具洞察力的辯論、他們令人驚奇的回想和記憶結構織就的混合、他們的偏見、他們力圖說服和控制的嘗試,還有他們有時一個人站出來的勇氣,都令我極為吃驚。在這裡,我曾經研究過的許多心理過程都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了我的眼前!雖然我們的學生知道,他們只是在模擬一場真實的審訊,但他們卻真的很認真作出一個公正的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1986)爭論過有關在死刑案件應使用“死刑認定”陪審團的決定中,陪審團研究的適用性問題。憲法賦予被告“得到公正審訊和一個在組成上不偏向於原告的公正的陪審團”的權利。持反對意見的法官認為,當陪審團中只包括那些接受死刑的陪審員時,這種權利受到了侵犯。他們說,他們的論據主要基於“研究者使用多種被試和多種方法得出的基本一致的結論。”然而,大多數的法官表示,他們“對這些研究在預測實際的陪審員行為方面的價值,抱有強烈的質疑。”對此持異議的法官迴應說,這是由於法庭自己拒絕用真實的陪審團進行實驗;因此,“那些聲稱死刑判決中帶有偏見的被告,應該被允許訴諸於這種能證明他們案例的惟一可行的方式。”
研究員也為實驗室模擬辯護。他們認為,實驗室實驗為在控制條件下研究重要問題提供了一個實際而廉價的方法(Bray & Kerr,1982;Dillehay & Nietzel,1980;Kerr & others,1979)。不僅如此,研究者通過在真實情境中進行檢驗,發現實驗室研究結果通常都得到了很好的證明。沒有人爭辯說,陪審團實驗中簡化的世界可以反映紛繁複雜世界裡真實的法庭;但是,實驗可以幫助我們構建用以解釋複雜世界的理論。
讓我們思考一下,陪審團模擬和社會心理學其他實驗有什麼不同嗎?它們都創造了現實生活的縮簡版本。在模擬現實中,通過每次改變一個或兩個因素,實驗可以準確描述出這一兩個方面的變化將怎樣影響我們。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實驗方法的精髓所在。
小結
陪審團是群體,影響其他類型群體的那些力量也會使它們搖擺——說服性論證,多數派和少數派影響的模式,群體極化,信息交換等。研究者也對美國最高法院近來允許小型陪審團和非一致意見決定的陪審團的設想做了檢驗,並提出了質疑。
模擬陪審團畢竟不是真實的陪審團,因此,我們在把研究結果推廣到現實法庭上時必須要多加註意。但是,就像社會心理學的所有實驗一樣,有關陪審團的實驗室實驗,有助於我們構建用來解釋更加複雜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論和原則。
個人後記:讓心理科學使我們更聰明地思考
“後現代主義”,在知識界是一個很時髦的話題,它認為真理是在社會中構建的;知識總是反映了形成它的文化環境。確實,就像我們經常在這本書裡看到的,我們的確常常被自己的直覺、偏見和文化傾向所控制。社會科學家們同樣受到證實傾向、信念固著、過分自信和先入之見的偏見力量所影響。我們先入為主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指導著我們理論的發展、我們對事物的解釋、我們對主題的選擇和我們的語言。
注意到心理科學中隱藏的價值觀,應該促使我們擦拭乾淨用以觀察世界的眼鏡;注意到我們易於產生偏見和錯誤,我們就可以在兩個極端中自由遊走——一個極端是,認為心理學假裝價值中立、實質受價值操縱,顯得很幼稚;另一極端是,認為證據只不過是一堆偏見,滑向過度的主觀主義。在謙遜的精神下,我們可以把可檢驗的思想應用到實驗中。如果我們覺得死刑確實(或者確實不)比其他可用的刑罰能更好地防止犯罪發生,我們可以隨口說出我們個人的意見,就像美國最高法院所做的那樣。或者我們可以探詢一下:是否存在死刑的州就有較低的殺人案發率,是否當實行死刑之後殺人案發率有所下降,而當禁止死刑後殺人案發率是否又有所上升。
如我們所知,美國最高法院在拒絕五人陪審團和終止學校的種族隔離制度時,考慮到了相關的社會科學證據。但是在向其他一些問題提供意見時,高院則沒有考慮到研究成果。這些問題包括死刑是否減少犯罪,社會是否把死刑執行看成是美國憲法所禁止的(“殘忍和罕見的刑罰”),法庭是否專斷地施加刑罰,他們應用刑罰時是否帶有種族偏見,以及根據認可死刑這一點來挑選的未來的陪審員是否偏向於做出有罪的判決。
就像最高法院決定2000年總統競選結果時所做的——由保守的法官構成了五比四的多數,站在更加保守的喬治·布什一邊——信念和價值觀不僅影響了科學家和老百姓的知覺,也確實影響了法官的知覺。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思考得更聰明一點——從而依靠可獲得的證據來測試我們的預想和偏見,並加以控制。如果我們的信念找到了支持,這當然更好;如果找不到支持,這當然更糟糕。這是構成心理科學和日常批判性思考基礎的最質樸的精神。
你的觀點是什麼
如果選中你作為謀殺案中的陪審員,你會帶什麼樣的偏見到法庭去?(你認可死刑嗎?如果認可的話,那麼你像其他人一樣更傾向於定罪嗎?比起女性來,你更容易對男性定罪嗎?對於與你不同的人要比模樣和思考方式像你的人,你更可能將其定罪嗎?)你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更聰明地思考,從而依據可靠的證據來檢驗你的偏見進而消除它們?
聯繫社會
本章討論了記憶的準確性,特別是對犯罪情景的目擊者的記憶。第3章“社會信念和判斷”描述了我們如何構建記憶。我們的記憶是否會欺騙我們?想一下,我們記憶的精確性如何與社會心理學的其他主題相聯繫。
第16章 社會心理學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1]
什麼是全球危機及如何應對
地球超負荷
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眼中的物質主義和財富
日漸盛行的物質主義
財富與幸福感
為什麼物質主義未能讓我們滿意
社會心理學如何有助於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調整適應與社會比較
後物質主義的態度與行為
個人後記:個體如何在現代世界承擔自己的責任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狄更斯《雙城記》
隨 著世界步入新千年,好消息無所不在,撞踵而來:
儘管世界人口自1960年以來增加了一倍,但是糧食產量卻是以前的三倍,同時糧食價格也下降了。
通貨膨脹——“最殘酷的稅收”——保持30年來的較低水平,利率急劇下調,而證券市場,儘管剛剛經歷蕭條期,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汽車、機票、汽油和漢堡的價格都保持在通貨膨脹物價調整記錄上的最低水平。1919年生產半加侖牛奶平均起來需要每名美國工人花費39分鐘,而現在僅僅需要7分鐘。
酗酒率、酒精飲料的消費,以及酒後駕車所引發的事故都有所降低。
新藥物縮小了我們的腫瘤,增強了我們性愛的力量。
將今天和一個世紀以前的“美好舊日”相比
沒有室內抽水馬桶;
兒童在礦井中賣苦力,家庭常常因為死亡而破裂,窮人沒有社會安全保障;
大多數人教育程度有限,婦女擁有的機會有限,少數民族遭受歧視和排斥;
每年的發電量還不夠我們現在一天的消費;
輕微的傳染病有時也能奪走一條生命,那時人們害怕兩種主要致命的疾病——肺結核和肺炎。
1999年,喬伊絲和保羅——一對對過去生活方式懷有濃厚興趣的夫婦——從450名參加英國第四網絡頻道的申請人中脫穎而出,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一起花三個月的時間體驗1900年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乍看起來這是一種下午茶生活與上班族生活的對比)。他們每天早上5:30起床;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樣準備食物;穿緊身胸衣;用雞蛋、檸檬、硼砂和樟腦的混合物洗頭;晚上,他們在煤油燈的照耀下,在起居室裡玩遊戲,但僅僅過了一個星期後,他們“幾乎要放棄”。不過這一家還是堅持下來了。由於缺乏其他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社區背景,真實的1900時期的生活並不能反映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電影所展示的那種浪漫和吸引力。
令人有些吃驚的是,經濟學家克魯格曼(Krugman,2000)談到“從純粹物質基礎的角度來說,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一個人寧可當今天的窮人,也不願成為一個世紀前的上層中產階級。”今天的工薪階層享受的豪華和奢侈——電、熱水浴、抽水馬桶、電視機及便捷的交通工具——都是幾個世紀前的皇室所難以想像的。的確,這是最美好的時代。即使是在不太發達的國家,人們也意識到了這種優越的生活,並渴望能共享。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最好的時代正讓我們面臨全球經濟危機。在瞭解了今天的消費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後,我們將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思考物質和財富,以及邁向可持續性未來所採取的步驟。
什麼是全球危機及如何應對
隨著不斷增長的人口和能源消費,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長期的承載能力。因此,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需要控制人口,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以及適度消費。
但是,好消息僅僅是一半事實。在由聯合國、英國皇家協會和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舉辦的會議上,全世界的科學領袖們注意到,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的負荷能力。我們現在正在消耗我們環境的“資本”,而不是僅僅依靠“利息”來生活(Heap & Kent,2000;Oskamp,2000)。由於人口註定會繼續成倍增長,而且人類的消費也在日益遞增,我們正朝著生態毀滅的方向飛速前進。
地球超負荷
在200多年以前,馬爾薩斯預言洶湧的人口會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多虧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和農業發展,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糧食供應的預言還未兌現。只是暫時還沒有。但是請思考以下的一些問題:
世界人口繼續增長
好消息是:出生率正在不斷地下降。在40多個國家中,人口出生率已經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平均一個婦女2.1個孩子),甚至更低。壞消息是:在發展中國家,出生率的下降甚微,並不能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長。而且,儘管出生率達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但因為存在一大批達到生育年齡的人口,所以總人口仍然會繼續增加。如圖16-1所示,1830年後,在100年的時間內全世界人口才增長到20億,然後接下來的30年時間內人口增長到30億,接著是在15年的時間內世界人口增長到40億,再接著只用了12年時間就猛增到50和60億。如果這個世界,特別是比較貧窮的國家例如巴基斯坦和印度,現在看起來十分擁擠的話,請當心:人口學家預測,世界人口將會在大部分讀者的有生之年增加到70、80甚至90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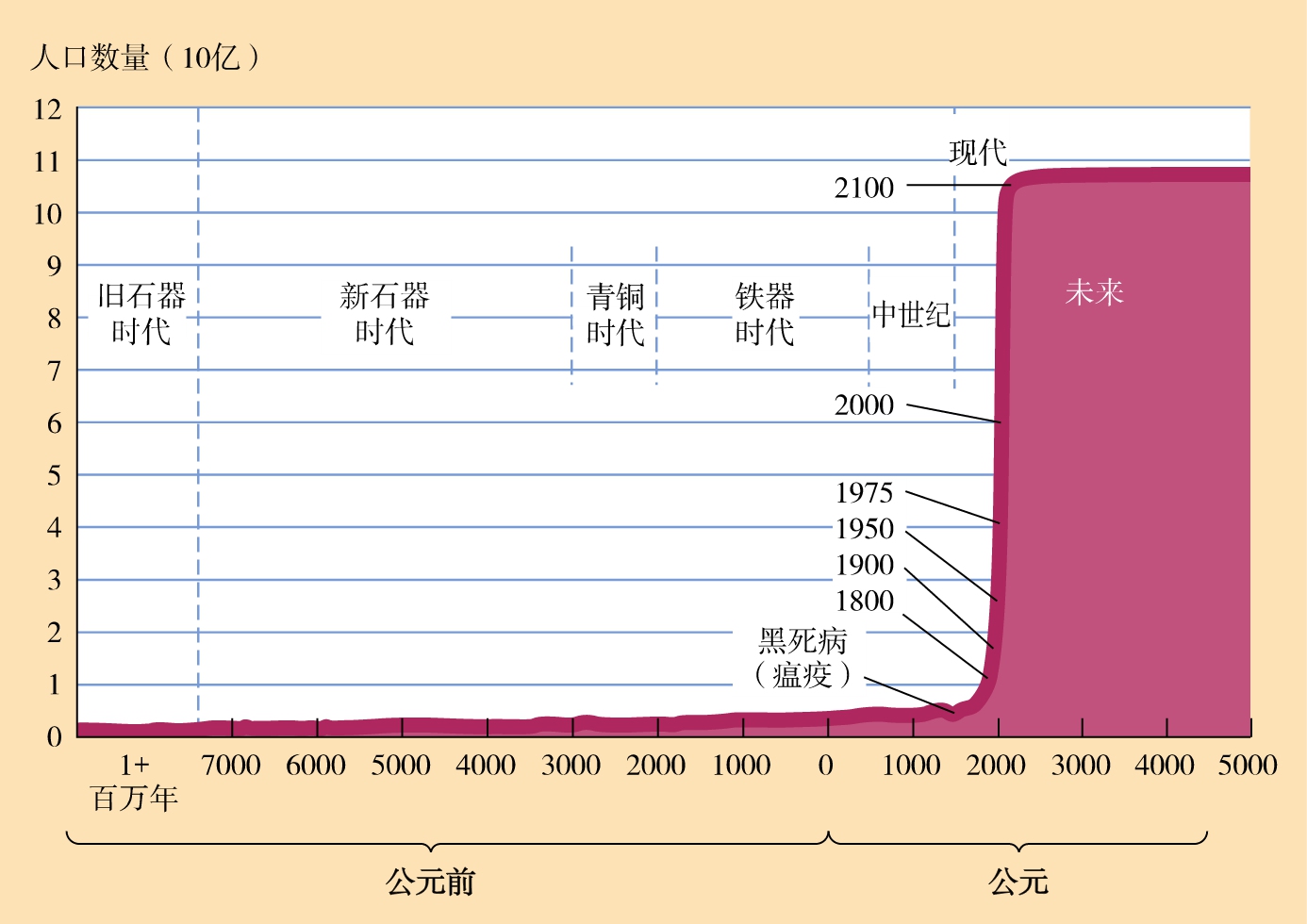
圖16-1 世界人口增長的歷史進程
資料來源: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and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2100(1998).
這樣的增長很明顯不可能無休止地持續下去。奧斯坎普(Oskamp,2003)指出,人口爆炸對世界的一半人口來說已經意味著貧窮、營養不良和疾病。“如果我們不能自發地控制人口增長,那麼最終可能需要用強力控制它。死亡率終將 趕上出生率——通過饑荒和飢餓,疾病(例如已經在非洲蔓延的艾滋病),或者通過戰爭和屠殺。”
經濟的增長刺激了消費的增加
地球正在遭受雙重的打擊——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消耗越來越多的地球資源。1950年,地球支撐了25億人口和5千萬輛小汽車。而今天地球上有超過60億的人口和以往10倍之多的汽車。如果經濟發展使得所有的國家都可以達到美國現在的汽車數量的話,那麼全球汽車的數量會再增加13倍多(N. Myers,2000)。儘管這一假設並不成立,但發展中國家的汽車量的確正在迅速增加。現在亞洲人購買的新車數量已經超過了西歐和北美的總和(Heap & Kent,2000)。
這些汽車,再加上利用煤炭和石油來發電和送暖氣的機器,產生了大量會導致溫室效應的氣體,最終導致全球變暖(Hileman,1999)。看看這些有關全球變暖的殘酷數據吧:
世界氣象協會報告,歷史上最熱的10個年份(從1861年開始記載)中有9個出現在1990年之後。而其中最炎熱的三年出現在1998~2003年之間。
在北極,氣溫正在上升,永凍層正在融化,樹木和灌木正在向苔原地帶入侵,冰蓋正消融,冰川正變小,海水開始危及村莊(Sturm & others,2003)。
其他地區,鳥類在春天的繁殖期提前了,花草樹木開始在阿爾卑斯山上生長,蝴蝶開始遷徙到更北部的地區(Kennedy,2002)。
隨著氣候的變化,極端異常的天氣必然會增加。降水更多的是以雨水的形式而不是降雪的形式降落地面。雨季可能出現更多洪澇災害,而旱季則沒有足夠多的積雪和冰川可以融化,河流乾涸。據世界氣象組織報道,2003年,西歐正經歷著它有史以來最炎熱的天氣,僅僅法國就有14802人的死亡與氣候炎熱有關。2003年5月(世界歷史上最炎熱的一個五月),美國遭受了562次龍捲風襲擊,遠遠超過了之前的399次。
如果全球變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如果它是可能帶來重大破壞的潛在武器,如果正如大多數科學家所推斷的那樣,它主要是由於溫室氣體所造成的,那麼為什麼全球變暖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關注呢?環境保護主義者質問道,為什麼美國願意花費超過一千億美金來抵制伊拉克可能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威脅,卻不願意來解決這個更有可能危及全球的問題?
此外,為什麼僅有28%的美國人對全球變暖問題表示“非常擔心”?難道真的像蓋洛普公司的調查員薩德(Saad,2003)認為的那樣,“對於一個寒冷的冬日,全球變暖聽起來挺不錯的”?或許,換種說法“全球加熱”,可能會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從前面幾章來看,不同的說法的確很重要。我們稱那些反對他國干涉自己內政的國家為“恐怖主義者”,或“非法武裝反抗者”,還是“為自由而抗爭的戰士”,會影響到我們的態度。我們描述某人對他人的反應是“順從”或“敏感”還是“直率”的,會影響到我們的知覺。語言塑造了思維。
世界上大部分的原始森林都已被人類砍伐殆盡,剩下的部分在熱帶地區也正為農業、畜牧業、伐木和住房所侵佔。可是,砍伐森林已經帶來了一系列惡果:對溫室氣體的吸收量降低,出現洪澇災害,土壤受腐蝕,降雨量和氣溫變化無常,以及大量動物物種滅絕。按現在對動物棲息地的破壞速度,生物學家雷文(Raven,2002)預測,地球上三分之二的物種都會在本世紀末消失。
人類對魚類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再加上生態系統的破壞,導致15個主要的海洋漁場中有11個漁場年捕獲量遞減,另有10個主要魚種中的7個魚種的捕獲量也逐年遞減(McGinn,1998;Karavellas,2000)。部分原因在於過度捕撈,致使野生的大馬哈魚、大西洋鱈魚、黑線鱈、鯡魚以及其他一些種群瀕臨滅絕。
誰應該為全球變暖和資源枯竭負主要責任呢?不幸的是,正是最有可能讀到這本書的我們。儘管不同的工業化國家存在差異——在荷蘭,30%的城市旅行是通過自行車完成的,而在美國卻只有1%——任何地方的工業化對生態系統都是有害的。最近聯合國的一項聲明(和英國皇家協會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完成)提供了以下證據(Herap & Kent,2000;N. Myers,2000):
孟加拉國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40萬,英國大約是每年增長10萬。但是如果考慮人均釋放的二氧化碳,那英國人的人均釋放量是孟加拉人的50倍。因此10萬個英國新生兒每年的排氣量將會是240萬個孟加拉新生兒的2倍。
自從1950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15個國家,肉和木材的人均消費量增加了一倍,而最窮的15個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消費量幾乎沒有變化。
最富有的15個國家擁有世界上87%的汽車,消費了85%的紙張,而最窮的15個國家在這些方面的消費只佔1%。
要點:如果有20億人口像今天的西歐和北美地區那樣消耗資源,那麼地球根本無力永遠滿足人們的需要(Pimental & others,1999;Willey,1999)。使用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人們評估了所謂的“生態覆蓋區”——不同國家的人們各需要多少生態空間來生產他們所需的消費品並分解掉他們產生的垃圾(Wackernagel,2000)。加拿大人均需要10個足球場多一點的空間。美國人均所需的空間比加拿大人多30%;英國、瑞士和德國的人均需要空間比加拿大少30%。如果每個人的消費量都像今天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一樣,那得需要三個地球那麼大的空間才能滿足人類的需求。然而,由於那些發展中國家的消耗量要小得多,所以,地球僅僅從1980年才開始出現“超載”的現象(圖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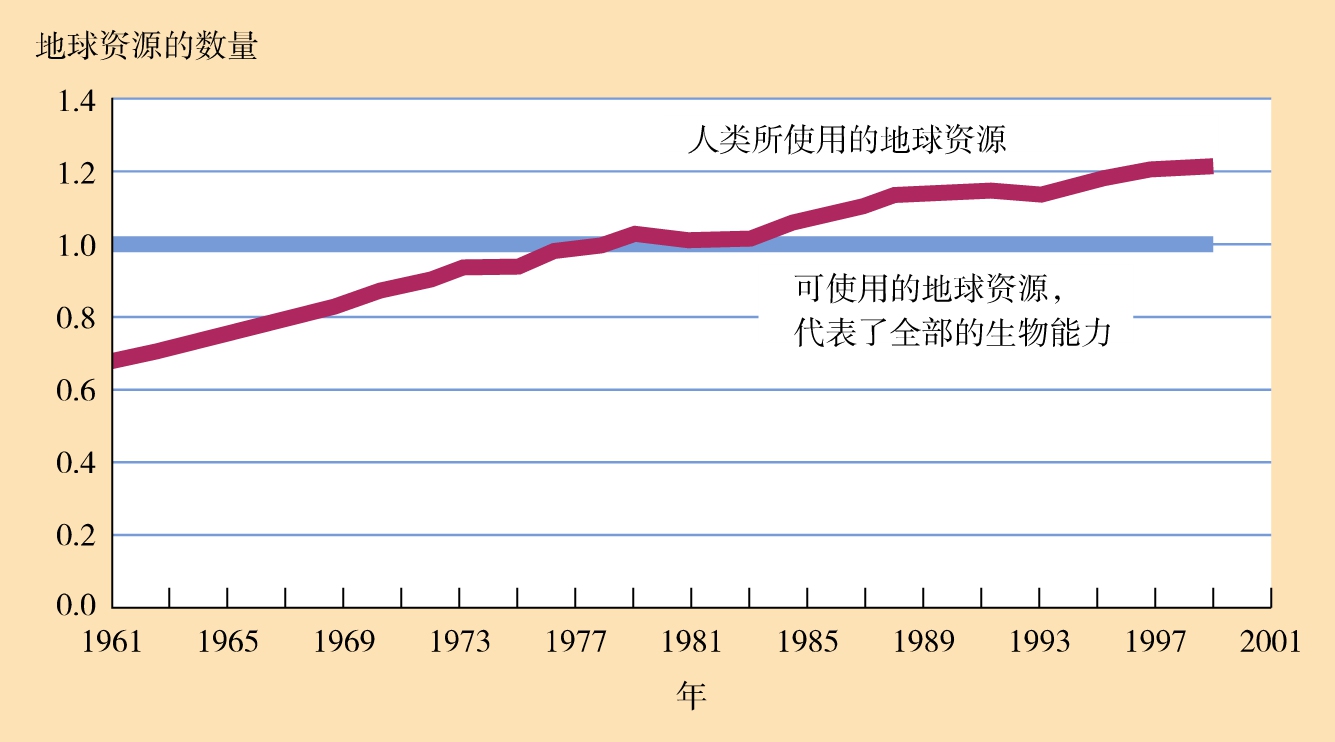
圖16-2 生態超載
人類對諸如土地、木材、魚類及能源的需求已經越來越超出地球的可再生能力。如果考慮到其他生物的需求,那麼使用量的曲線還會更高。
資料來源: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ckernagel & others,2002).
隨著全球人口突破60億,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富裕的迫切追求,人類對可持續消費的需求呈現出“緊迫性和全球意義”(Heap & Kent,2000)。邁爾斯(Myers,2000)指出,現在並不是說發達國家的消費水平應該 降低,而是他們必須 降低,因為地球不可能無限制地支撐目前的消耗量,更不用說要維持未來持續增長的消耗量(p.13)。生態學家說,按照現在的態勢發展下去,我們會步入第13章中提到的“公有地困境”。
為了不再向子孫後代索取資源,我們應該為可持續發展和消費的目標做些什麼呢?承認這些問題是由人類行為造成的——正是我們駕駛著那些耗油量極大的運動型跑車,也正是我們在食用需要大量穀物餵養而成的牛肉,使用著那些砍伐森林的機器——那社會心理學能夠做些什麼呢?我們來看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法。
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
那麼,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吃吃喝喝,然後愉快地等待世界末日的來臨?還是像許多參加囚徒困境遊戲的人一樣,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結果造成對整個集體的傷害?(“在全球範圍內,我的消耗量是無窮小的;這樣的消費給我帶來了快樂,但對於世界來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或者舉起我們的手,然後發誓永遠不會將我們的後代帶入到一個充滿傷痛的世界?生育與富裕相結合只能導致悲劇嗎?
那些對未來比較樂觀的人提出兩種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1)提高科技效率和農業生產率;(2)控制消費量和減少人口數量。
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促進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之一是發展生態科技。現在我們已經用散熱的熒光燈替代了許多白熾燈,用電子郵件和電子商務替代了需要打印和寄送的信件和目錄,而且還發明瞭環保型汽車。今天的中年人所開的汽車與他們的第一輛汽車相比,行駛的路程增加了一倍,而產生的汙染量僅為以前的1/20。
未來可能出現的科技包括:二極管,它不需要燈泡就可以發光20年;超聲波洗滌器,它不需要水、熱量和肥皂;可循環使用的塑料,同時還可以當肥料;汽車使用由氫和氧製成的燃料,而它們燃燒時只會排出水汽;一種極輕的材料,但其硬度卻可以和鋼鐵相媲美;屋頂和路面可以當成太陽能吸收器來使用(N. Myers,2000)。此外,科技革命正在加速發展。在美國,電被四分之一的人認同和接受了46年,電話35年,電視機26年,個人電腦16年,網絡7年(United Nations,1998)。
農業也正在經歷一場革命。不管是倍受爭議的轉基因技術,還是已達成共識的植物雜交技術都已經提高了產量。此外,人們還生產出了抗枯萎的土豆、營養成分更高的大米,同時農產品對乾旱和鹽度的耐受性,對昆蟲、病毒和細菌的抵抗力都提高了。
儘管我們還需要時間來評估這些科技和農業革新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但效率和生產力的提高必將是一條通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如果科技以現在的速度發展——誰能在一個世紀前想像出今天世界的面貌呢——未來一定能提出我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解決方案。所以,樂觀地講,未來一定會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物質和福利,同時卻只需要很少的原材料,帶來較少的汙染。
減少消費
第二條通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要通過減少消費來實現。美好的未來不是越來越多的人消耗得越來越多,汙染得越來越多,而是一個穩定的人口,而消耗和汙染都越來越少。
多虧家庭計劃的努力,今天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大減緩,特別是發達國家。在生活有保障、婦女可以接受教育並有較多權利的地方,出生率已經下降了。但是,就算世界各地的出生率立即降到生育更替水平,考慮到人口結構中的青年人部分,所以人口增長勢頭還會持續幾年。
假設我們已經超出了地球的承載能力,現在要求個人必須節制消費。隨著我們對物質生活質量的需求越來越高——人們追求更多的CD,更多的空調,更多的假期旅行——我們應該如何節制消費量呢?
一種方法是通過公共政策來限制強烈的購買慾望。按一般規則來講,如果對一件事情要納稅,我們就會少做一點;而對一件事情有獎勵,我們就會多做一些。如果高速公路堵塞,空氣遭到汙染,我們可以用快車道來鼓勵合夥駕駛汽車,同時懲罰單獨開車的人。我們可以設立自行車通道,資助公共交通工具,從而鼓勵人們使用汽車的替代物。我們可以像歐洲那樣對汽油收取重稅,對飲料罐頭和瓶子以可償還押金的形式來鼓勵重複利用(見“聚焦:為環保而創新機制”)。
弗蘭克(Frank,1999),一位非常精通社會心理學的經濟學家,提出一種為人類社會負責任的市場經濟不僅能夠獎勵成功,還應該可以促進更多可持續性的消費。他提出一種累進制的消費稅,這種方法是通過提高對非必需的奢侈品(例如,一種叫漫遊者的兒童玩具車的價格是18500美元)的價格來鼓勵儲蓄和投資。他的建議很簡單:並非對人們的收入,而是對人們的支出進行稅收——也就是說對收入減去存款和慈善投資的那一部分進行徵稅。累進制是這樣發揮作用的:完全免除對受贍養者徵稅,同時加大對揮霍者的稅收比率。弗蘭克認為累進制的消費稅(如果一個四口之家每年消費超過30000美元,則稅率為20%,而消費超過50000美元的家庭,稅率則增長到70%)能有效地調節消費。本來打算購買價值30000美元的寶馬汽車者,現在可能會作出調整,同樣高興地去購買23000美元的馬自達汽車。
這樣的政策可以將個人利益的驅動力導向對地球更有利的方向,不過這種法律的制定需要得到公眾的支持。如果皇家協會、國家科學院和聯合國的科學專家嚴正聲明我們已經超過了地球的承載水平,那麼公眾和政府的態度最終都將因為氣候變暖和激烈的資源競爭而改變。我們是否有理由希望公眾的態度也有可能在短期內改變——20世紀末的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是否可能在21世紀初被公共利益的價值觀所取代?
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20世紀70年代的婦女運動,大眾觀念得到了迅速改變,這些都證明公眾意識確實能在歷史的瞬間發生改變。在美國,20世紀60~90年代的社會環境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離婚率翻倍,自殺率則是3倍,青少年犯罪率是4倍,監獄人口5倍,非婚生子女數量呈6倍增加。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生活的變化是以不斷上升的個人主義和不斷下降的公共參與為標誌的。與那個年代相比,就像帕特南(Putnam,2000)證實的那樣,今天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更習慣於“獨自打保齡球 ”(而相應地更少參加選舉、旅行、娛樂、共用汽車等活動,更少相互信任、參加公共活動、會面、到鄰居家串門、參加志願活動以及付出)。作為對這些現實的迴應,在這個世紀之交,人們發起了一個社會生態運動,倡導公共的思維方式,鼓勵學校的個性化教育,促進婚姻的復甦以及共同養育孩子——同時振奮人心的是青少年的自殺、暴力和未婚懷孕行為都有所減少,而且志願活動的數量正在增加。瞧,不管是朝好的還是壞的方向,文化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物質主義的風潮將會很快萎縮呢?
聚焦 為環保而創新機制
2000年8月,有一封寫給蘇格蘭人的信——這封信是來自歐洲的某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要為10加侖的燃料多付出30英鎊(摺合45美元)的稅收,稅率達到了四分之三。來信者對此十分稱讚,認為稅收的運用和獎勵政策刺激了汽油的可持續消費:
儘管如果一年內每行駛12000英里,就意味著每年收入減少18000英鎊,我還是對提高私人駕車成本表示贊同。首先,事情看起來很可能這樣,在汽油上徵稅少的話,在其他地方的稅收同樣會增加,所以任何省錢的想法都是一種幻想。
對燃料徵稅簡單易行,按比例收稅,而且不容易作弊。幾乎所有的駕車者都清楚全球變暖部分是因為化石燃料的使用。幾乎沒有一個駕車者會自私到一點也不關心他(她)的行為可能會導致的自然界的失衡,主要表現為目前全球範圍的異常季節、天氣和不斷上升的海平面。
如果人們選擇住在遠離自己工作的地方,選擇開快車,選擇駕駛高能耗的汽車,選擇去更遠的商店購物或者允許縮減公共交通,那麼他們必須承受這些代價。
弗林(Tim Flinn )
聖安德魯斯(St. Andrews)
小結
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我們從沒像今天這樣生活得健康而長壽,擁有更多的繁榮景象,更多的人權和更多的先進科技。但是,全世界的科學領袖都指出,我們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災難。迅速增長的人口和不斷上升的消費量都使得地球嚴重“超載”。今天地球上的汽車數量是半個世紀前的10倍,我們燃燒更多的石油和煤炭來產生電和熱,溫室氣體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星球也變得越來越熱。要點:今天地球已經不能支撐那些發達國家的消費量,更不用說進一步增長的消費量。因此持關注態度的科學家和公民們都在考慮我們人類怎樣才能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如果我們提高科技的效率和農業生產力結果會如何?如果我們通過引發刺激,以及改變行為和態度來控制人口節制消費結果又會怎樣?在過去40年中,文化發生了快速地變化,作為對全球危機的迴應它還會再次發生。
什麼是社會心理學眼中的物質主義和財富
要改變我們對物質主義的理解,社會心理學能給我們哪些幫助?在多大程度上金錢和消費可以買來快樂?為什麼物質主義和經濟的增長不能給人類帶來持久而強烈的滿足感?
金錢可以買來快樂嗎?我們幾乎沒有人會同意。但是如果是另一個問題——“再多一點 錢會讓你更快樂一點 嗎?”——這時大部分人都會微笑和點頭。這就是,我們認為在財富和幸福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聯繫。這種信念符合肖爾(Juliet Schor,1998)所說的“工作和消費的循環”理念——工作量越多買得就越多。
日漸盛行的物質主義
心理學家卡塞(Tim Kasser)認為,當人們感到不確定、不安全和貧困時,物質主義,即崇尚金錢和財富的觀念,會比較流行。當缺乏安全感時,人們在得到一些新的佔有物時常常能獲得暫時的情緒提升。但是,這種滿足是很短暫的。
物質主義在現代西方文化中同樣很流行。儘管地球要求我們在它上面生活得更“輕”一點,但物質主義似乎勢頭強勁,這在美國體現得最為明顯。根據一份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二分之一的女性、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五分之四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人們都希望自己越來越富有。這正是所謂的“美國夢”:生活、自由和購買快樂。
這樣的物質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最為盛行。最富有戲劇性的證據來自於美國加州大學洛山磯分校、美國教育委員會對將近25萬剛入學的大學生所做的年度調查。同意走進大學的最重要原因是“掙更多的錢”的人,從1971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2003年的接近四分之三(如圖16-3所示)。實際上,伴隨著這一比例變化的卻是,認為“形成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人數卻在急劇減少。也就是說,物質主義膨脹,精神信仰卻在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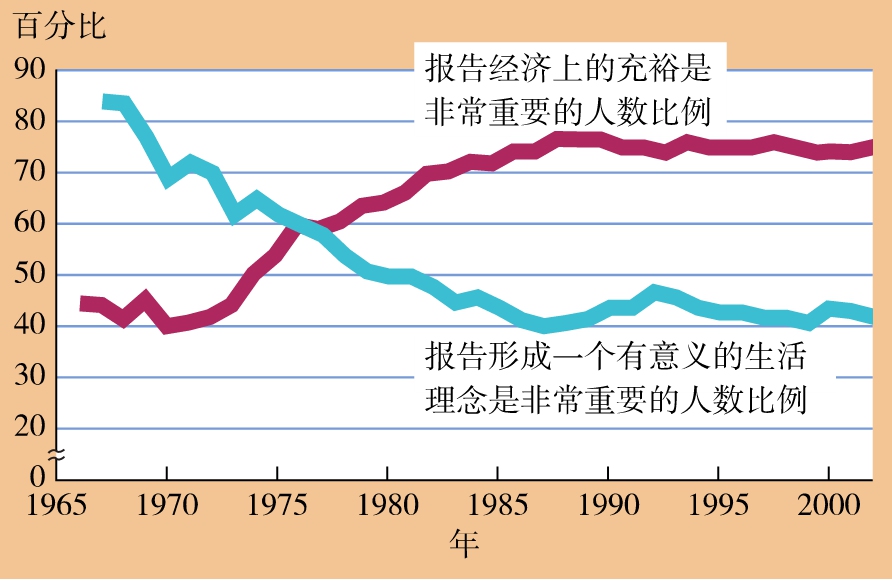
圖16-3
物質主義的變化歷程,來自於對超過200000人的剛入學的美國大學生的年度調查(全部的樣本量接近700000名學生)。
資料來源:Data from Dey,Astin,& Korn,1991,and subsequent annual reports.
價值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列出的19個目標中,現在新入學的美國大學生將“經濟上非常充裕”列為第一位。這不僅高於“發展一套生活的哲學體系”,還位居“成為我自己領域內的權威”、“幫助困難中的他人”和“供給家庭”等目標之上。
並不只有大學生崇尚物質主義。弗蘭克報告,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們擁有更多的金錢去消費,奢靡之風正在蔓延。20世紀90年代末期,在奢侈品上的花銷增長速度是全部消費品增長的四倍。棕櫚海灘的四季飯店中每晚一千美金的套房早在一個月前就被預訂用於舉辦婚禮,白楊飯店每晚5000美元的套房也是如此。美國500萬英尺的遊艇數量在過去十年中翻了一番,而且可能每小時的租金超過10000美元。價值超過30000美元(1996)的小汽車在過去十年中數量暴漲,在售出的交通工具中所佔的比例從7%增長到12%。
財富與幸福感
地球無法維持的巨大消費量真的能給人類帶來“美好的生活”嗎?富裕是否會產生(至少是與之相關)心理上的幸福感呢?如果人們可以用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取代另外一種奢華的生活——包圍在富麗堂皇的環境之中,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度假,總裁級別的旅行——那麼人們是否會更快樂呢?如果人們中了頭等大獎,並且可以選擇任何一種放縱的生活:一艘40英尺的遊艇,考究的家庭電器,由設計師專門設計的全套服裝,豪華汽車以及私人管家,那麼他們是否會更快樂呢?一些社會心理學理論和證據為此提供了答案。
富裕國家的人們更快樂嗎
就像迪納(Diener,2000)所報告的那樣,存在著這樣一種趨勢:發達國家中有更多感到滿意的人們。例如,瑞士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通常都是富裕和滿意的。在貧窮的國家,人們經常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保障。而且,將他們和發達國家的有錢人相比,可能會更強調他們的貧窮感。但是,在人均GNP超過8000美元的國家中,國家的財富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就不存在了(圖16-4)。愛爾蘭人比保加利亞人活得更好(包括快樂和生活滿意度)。但是,其收入是否是愛爾蘭人、挪威人或美國人的一般水平並不重要。在20世紀80年代,愛爾蘭人所報告的持續增長的生活滿意度超過了富裕程度是其兩倍但滿意程度更低的聯邦德國人(Inglehart,1990)。不論如何,迪納和他的同事(1995)注意到國家的財富與公民權利、文化程度,以及民主制持續的時間相關。為了更好地瞭解金錢與快樂之間的關係,研究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排除了個人和時間的因素之後,人們的幸福感是否會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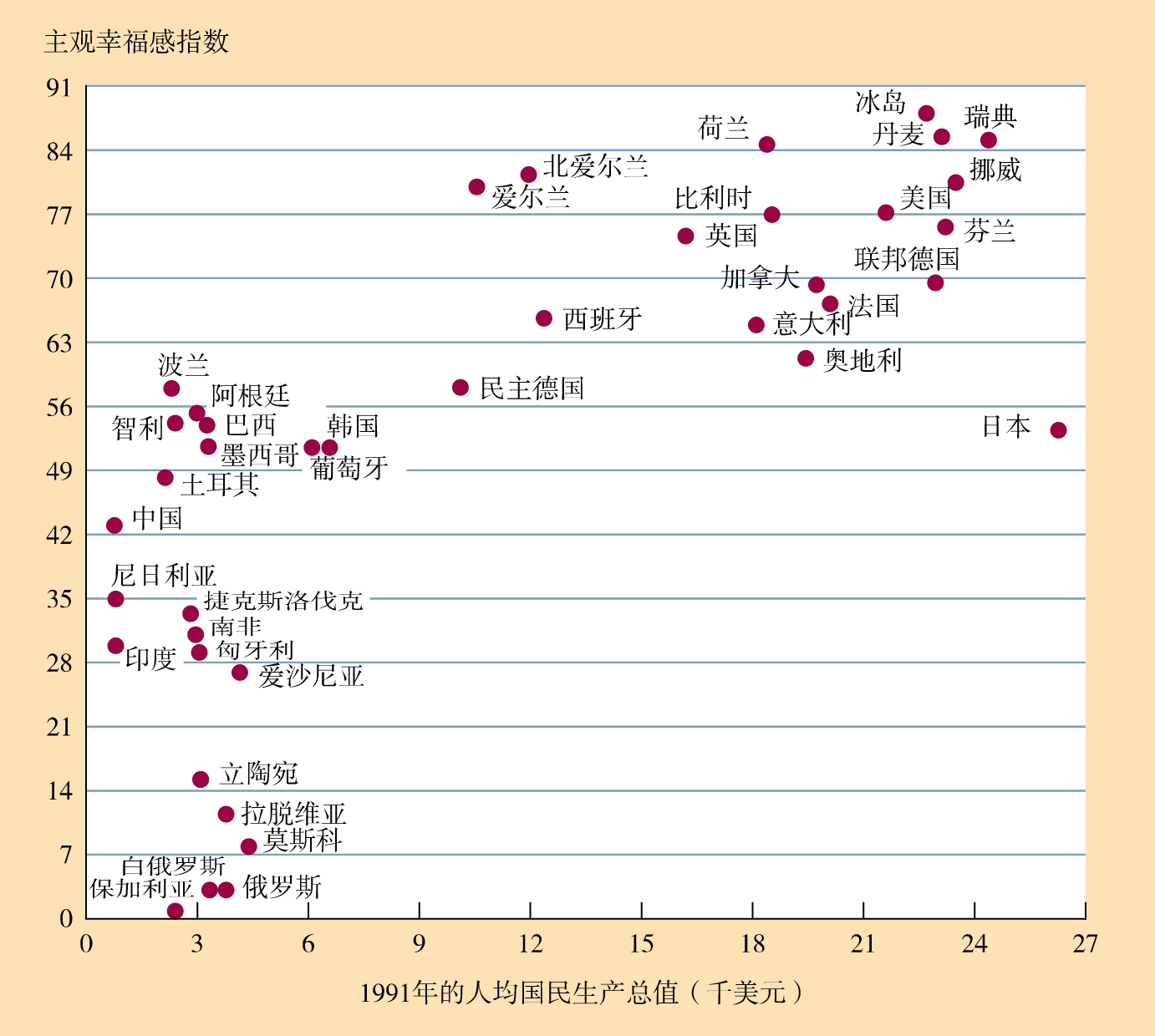
圖16-4 國家的財富和幸福感,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和1990~1991年世界價值觀的調查
主觀幸福感指數是快樂和生活滿意度的結合物(將他們自己描述為(a)“非常快樂”或者“快樂”的百分比的平均值減去“不是很快樂”和“不快樂”的百分比,(b)在生活滿意度的10點量表上,7或者以上,減去4或者以下)。
資料來源:From Ronald Inglehart,1997,p.62.
富有的人們更快樂嗎
在貧窮的國家裡,例如印度,低收入往往意味著基本生活需要會受到威脅,所以相對富有確實可以預測更強的幸福感(Argyle,1999)。不論是在心理層面還是物質層面,位於高等級總是好於低等級。但是在富有的國家,大部分人都可以負擔日常生活需要,但其富裕的重要性卻低的令人驚奇。英格爾哈特(Inglehart,1990,p.242)注意到,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收入和個人的幸福快樂之間的關係“弱得讓人吃驚(實際上是可以忽略的)”。非常窮困的人們的快樂感往往比較低。但是一旦生活變得充裕了,再增加同樣多的錢時,它所能帶來的回報卻變得越來越小。萊肯(Lykken,1999,p.17)通過總結他自己對快樂的研究發現,“一般而言,那些穿著工作裝,乘公車上班的人和穿著西服駕駛自己的奔馳去上班的人一樣快樂”。
甚至是非常有錢的人們——例如《福布斯》雜誌上最富有的100個美國人,根據迪納,霍維茨和埃蒙斯(Horwitz & Emmons,1985)的調查——其幸福感僅僅比平均水平高一點。儘管他們擁有足夠多的金錢可以買很多自己既不需要也不在意的東西,但49個接受調查的超級富翁中的五分之四同意以下觀點:金錢既能增加快樂也能減少快樂,這主要取決於它的使用方法。而且其中的一些富人確實並不快樂。一個擁有驚人財富的富翁根本想不起自己任何快樂的回憶。一位女性報告說,她認為金錢無法化解由孩子的問題所帶來的痛苦。當在泰坦尼克號航行的時候,就算住在頭等艙也不能將你帶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經濟的增長是否可以提高民眾的信心
隨著時間的流逝,快樂是否隨著富裕而增強呢?弗蘭克和卡帕西(Shirley Mae Capaci)在1998年贏得價值1.95億美金的勁球彩票後能否一直感到幸福快樂呢?可能不像他們最初設想地那樣快樂。贏得彩票、獲得一筆遺產,或者經濟增長帶來的意外之財的確能夠提升幸福感(Diener & Oishi,2000;Gardner & Oswald,2001)。彩票贏家的通常表現是隻能從他們的成功中獲得一種短暫而強烈的愉悅感(Brickman & others,1978;Argyle,1986)。儘管為成功感到異常高興,但這種歡樂最終很快消退了。同樣,那些收入比前十年有所增加的人們並不比那些收入沒有增加的人們更快樂(Diener & others,1993)。就像瑞安(Ryan,1999)所解釋的那樣,這種滿意感有一個“非常短暫的生命期”。[後來的一些報告表明,弗蘭克的一些老朋友不再與他談話,他買了一部粉碎機來處理自己不想看到的信件,有一段時間他還躲藏了起來(Annin,1999)。 ]
如果個人的持久幸福感並不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而增強,那麼集體幸福感是否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得到提升呢?今天的美國人是否比1940年的人們更快樂呢,那時五分之二的家庭還沒有淋浴設備或浴缸,而暖氣常常是意味著生一個木頭的或炭的爐子,而且35%的家庭沒有洗手間(人口普查局,1994)?還是讓我們來看看1957年,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John Galbraith)在這一年將美國描述為富裕的社會 。那時美國人的人均收入,換算為今天的金額是大約9000美元。而今天,人均收入超過了20000美元。與1957年相比,美國應該算是“兩倍富裕的社會”——金錢所能購買的東西是以前的兩倍。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經歷了這種迅速的財富增長——潮水對遊艇和小舟的推動效果是不同的,遊艇提升得更高——而且巨大的貧富差距是不健康社會的標誌。不過,幾乎所有的船都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今天的美國人人均汽車擁有量是以前的兩倍,去飯店的頻率是以前的兩倍,而且一般都擁有微波爐、大屏幕的彩色電視機、家庭電腦和空調。生活在其他工業化國家的人們也經歷了類似的變化。
所以,人們認為在經濟上非常充裕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40年中他們的財富正在一點一點地增加,呈現出了一種不可逆轉的上升趨勢,美國人現在真的更快樂嗎?
他們沒有。如圖16-5所示,那些報告自己是“非常快樂”的人們的比例,如果存在變化的話,就是在1957年和2002年之間有減少的趨勢,具體地說,比例從35%下降到了33%。富有程度是以前的兩倍,但人們並沒有感到更快樂。同時,抑鬱的比率劇增,特別是在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中(Seligman,1989;Klerman & Wiessman,1989;Cross-National Collaborative Group,1992)。與他們的祖父母相比,今天的年輕人在更加富裕的環境中成長,但其幸福感卻稍低,患抑鬱和各類社會病的風險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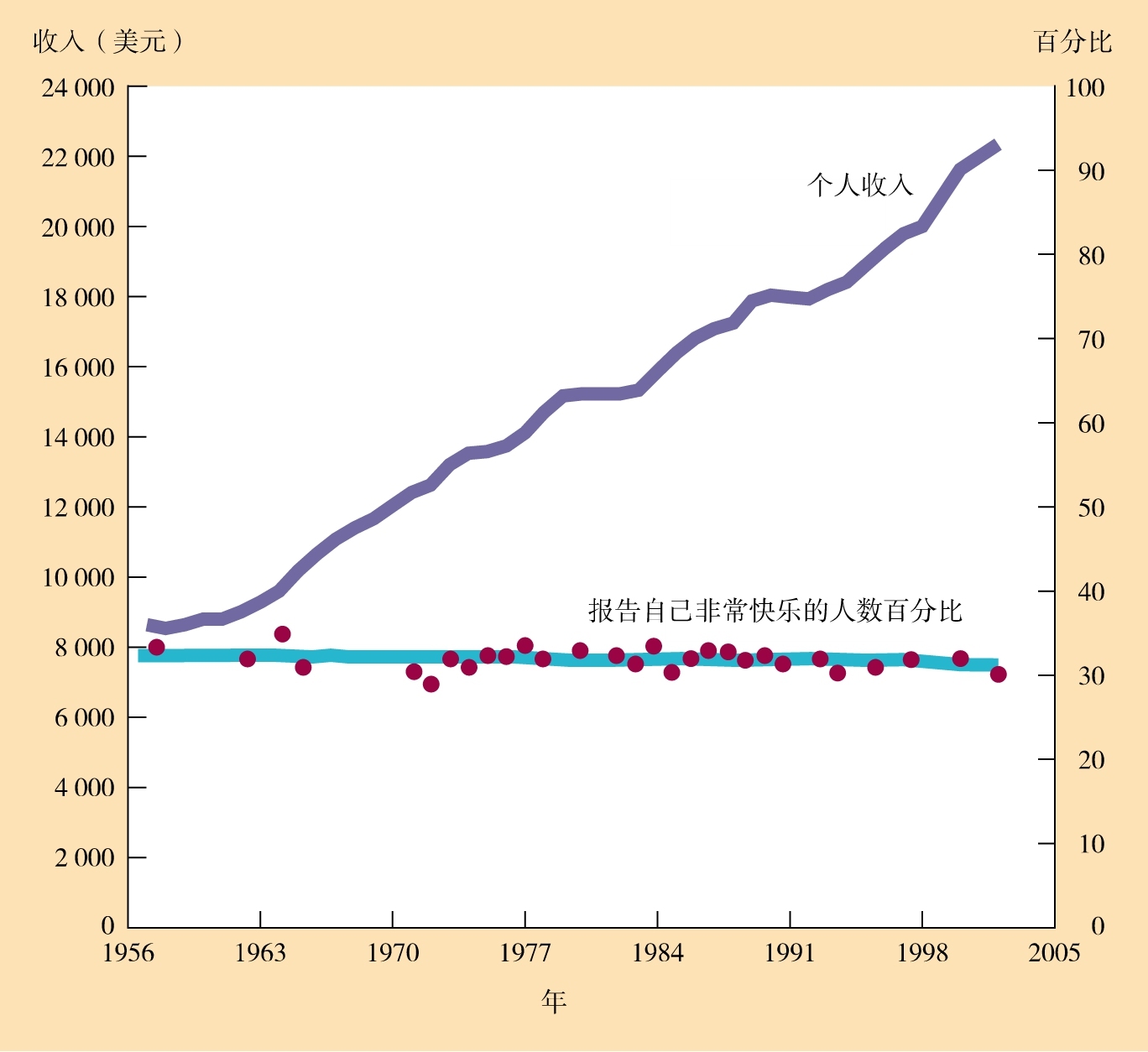
圖16-5
經濟增長是否提高了民眾的士氣呢?雖然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後,收入確實有所增加,但是個體自我報告的幸福感卻沒有增強。
資料來源:Happiness data from General Social Surveys,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 Income data from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and Economic Indicators .
這樣就得出了一個震驚的結論:在過去40年中我們快速增加的財富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哪怕極小的主觀幸福感的增強。埃斯特林(Easterlin,1995)報告,歐洲一些國家和日本也是如此。例如,在英國,擁有汽車、中央供暖系統和電話的家庭百分比急劇增長,但這並未伴隨著幸福感的增強。結論之所以令人吃驚是因為它對現在的物質主義提出了挑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明顯的民眾信心的提高。
為什麼物質主義未能讓我們滿意
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居然不能讓人們滿意!更令人驚訝的是越是為財富努力奮鬥的個體的幸福感可能越低,這是瑞安“在他所關注的每一個文化中都強烈地感受到”中發現的。他的合作者卡塞(Tim Kasser,2000),從他們的研究中總結出以下結論:那些轉而追求親密感,個人成長,和為社會事業而奮鬥的人會體驗到更高質量的生活。卡塞和瑞安(1993,1996)的研究(還有德國的施繆克)重複了早期珀金斯(H. W. Perkins)的發現:對800個學院的男畢業生的調查中,那些擁有“雅皮士價值觀”——喜歡高收入和追求事業上的成功,以及很高的聲望,勝於希望有親密的朋友和穩固的婚姻關係——的人在描述他們自己“相當”或者“非常”不 快樂方面比他們以前的同學多一倍。另一個研究訪問了13000個大學校友。那些中等收入者——而在20年前將“擁有極大財富”評價為非常重要或者非常必需的人,往往比那些之前並不是非常崇尚物質主義但現在也屬於中等收入的人顯得更不快樂(Nickerson & others,2003)。
暫停一下同時思考:在上個月中,哪件事是你所體驗到的最滿意的一件?謝爾登(Sheldon,2001)及其同事向大學生群體提出了這個問題(還有類似的關於上個星期和上個學期的問題)。接著他要求這些學生評價令人滿意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十種不同的需求。學生認為自尊、親近感(感覺和他人聯繫在一起)和自主(控制的感覺)是伴隨著滿意的事件而體驗到的最強烈的幾種情感需求。排在所有可以預測滿意度的因素項目中最底層的是金錢和奢侈品。
索爾伯格(Emily Solberg),迪納和羅賓遜(Robinson,2003)報告,那些認為自己擁有極大財富的人往往體驗到更少的積極情緒。這類物質主義者常常報告在他們所渴望和所擁有的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同時,享受到的親密而滿意的人際關係更少。特別是那些為了消除自我疑惑而趕超他人者,他們不是為了提升家庭的安全感、享受自由和慷慨救助他人而追求財富,這類人顯得尤為不快樂(Srivastava & others,2001)。迪納和塞利格曼(Seligman,2002)同時報告說,那些非常 快樂的大學生往往具有“豐富而令人滿意的親密關係”而不是有較多金錢。因而,對於一個健康國家的挑戰在於,我們要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遏制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風潮,因為它們會與人類歸屬的深層需要發生錯位。
我們已經清楚地瞭解到物質主義可能會給生態環境和個人帶來什麼樣的危害。在一個全國性且具代表性的調查中,普林斯頓的社會學家沃斯諾(Wuthnow,1994)發現2000多美國被試中有89%的人認為“我們的社會過於物質化了。”換句話說就是,其他 人太過於物質至上了。不過還是有84%的人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錢,78%的人說擁有“一棟漂亮的房子,一輛新車和其他美好的東西”是“非常或相當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得到漂亮的房子和嶄新的汽車後沒有變得更快樂呢?為什麼41%的美國人——與1973年的13%相比有所上升——現在將汽車、空調看成是日常必需品呢(Schor,1998)?而且昨天的奢侈品——CD播放器,彩色電視機,寬帶上網——是如何迅速地變成今天的必需品和明天的紀念品的呢?(我們家中的第一臺將信息儲存在盒式磁帶中的臺式電腦,起初看起來十分不凡,直到我們擁有了處理速度更快的硬盤驅動的機器,但是一旦擁有了奔騰處理器的芯片後,它就變得簡陋起來,不過芯片似乎也很快就看起來有點軟弱無力了。)
兩個原則驅動了這種消費心理。第一是我們人類的適應能力。第二是我們的社會比較傾向。
適應水平現象
適應水平現象 (adaptation-level phenomenon)意味著成功與失敗、滿意與不滿的情感都是相對於先前的狀態而言的。如果我們目前的成就降到我們先前所達到的水平之下,我們就會產生不滿和挫敗感;如果成績超過了先前的水平,我們就會體驗到成功和滿意感。
如果我們不斷地取得成功,那麼,我們將會很快適應成功。從前讓我們感覺良好的事件現在卻變成了中性事件,以前讓我們感覺中性的事件現在很可能體驗到一種失落感。這能夠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人類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實際收入雖然持續快速地增長而多數人並沒有更幸福的感覺。
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經體驗過適應水平現象。更多的生活消費品,更好的學業成就或者更高的社會聲望,最初能給我們帶來強烈的愉悅感。但是,這一切都讓我們感覺消逝得太快。接著我們會需要更高的水平來讓我們體驗另一個快樂的高潮。布里克曼和坎貝爾(Brickman & Campbell,1971)指出,“正當我們沉浸在某種成就所帶來的滿足感時,它會迅速地消退,最終取代它的是一種冷漠和更高的努力程度。”[帕金森的第二定律:支出增長以適應收入的增加 。]
也許你會回想起第2章中我們提到,人們總是低估自己的適應能力。人們在預測他們未來的情感強度和持久性方面存在困難,這種現象被稱為“持久性偏見”(durability bias,Wilson & Gilbert,2003)。達到我們所渴望的目標——財富、測驗最高得分、芝加哥隊贏了全美職業棒球冠軍賽——所體驗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我們有時會產生“錯誤的渴望”。當大一新生在搬進大學宿舍之前,對種種住宿條件的滿意程度進行預測時,他們都將注意力集中於外在物質條件。“能住在一個漂亮而出入方便的寢室我將感到最開心。”很多學生都是這麼想的。但是他們錯了。當一年之後對其進行重新調查時,鄧恩及其同事(Dunn & others,2003)發現,反而是社會性因素,如團體歸屬感等能很好地預測個體的幸福感。如果我們集中關注於短期效果而忽略我們適應速度的話,那麼也許我們會認為物質生活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我們帶來幸福。事實上,博文和吉洛維奇(Boven & Gilovich,2003)經過調查和實驗發現,積極的體驗 (常常是與社交有關的體驗)能使我們感到更幸福。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並不是物質。
社會比較
我們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會比較為中心的,正如那個有關兩個徒步旅行者遭遇狗熊的笑話所說的那樣。一個徒步旅行者從他的揹包中拿出一雙運動鞋。另一個問:“為什麼要穿上運動鞋?你不可能比一隻熊跑得還快!”“我不需要比那隻熊跑得還快,”第一個人回答說,“我只需要跑得比你快就夠了。”
快樂同樣也是如此,不僅取決於我們與自己過去的體驗相比較,而且還取決於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Lyubomirsky,2001)。我們感覺到好或者不好依賴於我們和誰相比較。只有當別人思維敏捷、靈活時,我們才是思維遲緩的或者笨拙的人。當一個棒球選手以年薪1千萬美元簽約時,那麼他年薪7百萬美元的隊友可能會感覺不滿。比較研究者馬斯魏勒(Mussweiler,2003)指出:“人類的判斷是由比較得出的。”[進化論心理學家推斷,男性追求積累和展示比他人更多資源的原因與雄孔雀爭相展示自己的羽毛是一樣的:為了贏得女性的注意力 。]
日漸盛行的奢靡之風可以歸因於人們具有向上比較的傾向:我們在攀登成功和財富的階梯時,我們通常將自己與和我們水平相當或者之上的同輩相比較。那些住在同一個社區收入不同的人們,當他們與非常富有的階層進行向上比較時,他們的認知就扭曲了,很容易體驗到不滿。哈格蒂(Hagerty,2000)觀察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富裕程度的增加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一般來說,當收入更均等而且很少有人明顯超過自己時,人們會覺得自己更幸福。
常見的向上社會比較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的結果就是第10章中所謂的相對剝奪 。例如,觀看電視可以引起相對剝奪的感覺,讓我們意識到其他人擁有而自己沒有的東西。人們觀看的電視劇越多,越會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相對富裕的人們做比較,那麼他們的物質慾望就會不斷地上升而自己卻越來越不滿意(Schor,1998)。
社會心理學如何有助於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我們人類是不是總會適應新的歡樂,是不是在與其他人的比較中會促使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持續盛行?是否物質主義有可能會讓位於一種更簡樸的“後物質主義”?是否光有知識並不意味著具有說服力,就像瞭解吸菸危害的人並不能擺脫煙癮一樣?又或者讓人們意識到財富和幸福之間的關係會有利於其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嗎?
調整適應與社會比較
適應水平現象和社會比較可以深深地啟迪我們:通過物質成就來追求滿足感要求財富不斷地擴展,但這卻僅僅只能維持 這種滿足感。柏拉圖說,“貧困並不是因為一個人的財產減少了,而是因為他的貪婪增加了。”
幸運的是,適應同樣可以使我們向下調整自己,我們需要或者應該選擇去簡化自己的生活嗎?如果我們的購買能力縮減,最初我們會感到有些痛苦。但是,我們最終會適應這一新的現實。20世紀70年代汽油價格飛速增長的結果是,北美洲的人們成功地降低了對耗油量大的汽車的需求。弗蘭克(Robert Frank,1996)就有一段適應節儉生活的經歷:
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作為和平團的志願者,我來到尼泊爾的鄉村。我所居住的一居室的房子,沒有電,沒有暖氣,沒有配套的廁所,也沒有自來水。當地的飲食一成不變,幾乎沒有肉……儘管起初我對自己在尼泊爾的生活條件感到相當吃驚,但是這份經歷中最突出的特點是,那一切如此迅速地就變得正常起來。僅僅在幾周之內,我就不再有任何貧困的感覺。事實上,我每個月有四十美金的補助,而這已經超過了我所在的村莊中大多數人的收入。我體驗到一種富裕的感覺,而這種感覺直到近年來才又再次體驗到。
就像新西蘭心理學家坎曼(Richard Kammann,1983)20年前所認識的那樣,“在快樂原理中,客觀生活的經濟狀況所發揮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住在人人都生活在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中的人們很可能並不比大家都住在2000平方英尺房子中的人們更快樂。
甚至是遭遇致人癱瘓事故的受害者,盲人和其他患有嚴重殘疾的人們通常也能鼓起勇氣,用樂觀的態度來面對不幸。他們適應了自己的殘疾,取得了正常或者接近正常水平的生活滿意度(Brickman & others,1978;Chwalisz & others,1988;Schulz & Decker,1985)。災難性事故的受害者無疑希望自己是健健康康的,同時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羨慕那些贏得彩票大獎的人們。但是,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我們發現了一個令人驚奇的事實:這三組中,任何一組在與他人相比時都不存在明顯的區別。人類擁有巨大的適應能力。
心理學對於可持續發展的貢獻,部分是通過對適應和社會比較的認識理解來實現的。那些低於我們比較標準的體驗能夠冷卻我們對奢靡的狂熱追求,並恢復滿足的狀態。要感覺更好一些,就跟那些處境更差的人——那些受病痛折磨、處於更差的人際關係之中的人,那些擁有更少財富的人相比吧(Affleck & others,2000;Buunk & others,2001;Locke,2003)。德默及其同事(Dermer & others,1979)所做的一個實驗揭示了向下社會比較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s)的積極效應。他們將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的女生置於一個假想的剝奪情景中。看完了對1900年密爾沃基市人民悲慘生活的描繪之後,或者是想像並寫下有關自己被焚燒、被毀容的情景之後,那些女生報告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更為滿意。在另一個實驗中,克羅克和加洛(Crocker & Gallo,1985)發現,與那些在實驗中完成以“我希望我是……”開頭的句子的被試相比,那些完成五句“我很高興我不是……”的句子被試在之後的測驗中,表達出更少的抑鬱跡象而表示對自己的生活更滿意。
人們似乎天生就懂得向下比較的優勢。那些在困境中的人們總是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線光明,通過與那些更不幸的人相比較來提升自尊(Gibbons & others,2002;Reis & others,1993;Taylor,1989)。意識到他人的境遇更糟糕能使得我們更看重自己的幸福,並意識到自己也許並不需要那些“東西”。一則波斯諺語是這樣說的:“我因為沒有鞋穿而感到沮喪,直到我發現還有人沒有腳。”
後物質主義的態度與行為
在第4章我們注意到行為受態度的影響,但是同時也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而且態度經常依從行為。因此更多對地球有利的行為將會從多種來源中產生——來自於鼓勵環保的公眾政策,來自於對個體承諾行為強有力的呼籲,以及來自於從對“我”的思考到對“我們”的思考和從對目前問題的思考到對未來問題思考的轉變(Stern,2000;McKenzie-Mohr,2000;Winter,2000)。教育——本章的目標——同樣也佔有一席之地,例如霍華德(George Howard,2000)提出所謂的“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請看“聚焦: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末期是以不斷增長的物質主義和消費量為標誌的,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羅珀(Roper)的民意調查要求人們選擇哪些事物能帶來“美好生活”,1975年時38%的美國人和1996年時63%的美國人選擇“許多許多的錢”(Putnam,2000)。39%年收入在75000~100000美元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無力負擔起所有我真正需要的東西”(Schor,1998)。
但是,有跡象表明一種向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轉移的趨勢已經出現,因為人們:
面臨著人口增長,氣候變化,動植物的棲息地和物種毀滅的現實;
認識到對財富的追求和奮鬥可能意味著更不快樂的生活;
意識到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並不能帶來滿足感。
對財富的追求通常體現在一大堆沒有聽過的CD,滿滿一衣櫃很少穿的衣服,擺放在車庫裡的豪華汽車,所有這些都不能賦予我們美好的生活。我們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破裂的家庭,我們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問題少年,我們有更多心理健康的專業人士和更多需要他們服務的人們。既然顯著的消費量是20世紀社會地位的標誌,那麼在這個新的世紀它會發生偏轉嗎?
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英格爾哈特(1990)追蹤調查了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他是第一批覺察到物質主義價值觀開始減弱的人中的一個。在歐洲和北美,他看到一些跡象,表明新一代開始成熟起來,他們對經濟增長和堅固國防關注在減少,同時對人際關係、保護自然完整性以及生活的意義性等問題的關注在增加。
民意測驗專家蓋洛普(George Gallup,Jr.,1998)認為,期望與比自己更重要的東西相聯繫的願望正在增長:“今天社會生活中的兩大主流趨勢之一是[另一個趨勢是對更深入、更有意義關係的追求]尋找精神的港灣。”蓋洛普報告(1998),從1994年到1998年的後期,感到自己需要“體驗精神上的成長”的美國人的百分比從58%增長到82%。伴隨當代精神性追求而來的是一種人們對“服務”地球的關注。
聚焦 對於有限世界的致命觀念
消費會帶來幸福 。“當我得到那棟度假別墅時我就會很幸福。”
忽視未來 。“未來的世界自然而然會好的。我的生活就是現在當前。”
增長是好的 。“越多越好。”
貪婪是好的 。“我們都應該盡我們所能地去索取。”
支付得越少越好 。“不應該通過對汽油徵稅來促進資源保護——我想要便宜的汽油。”
如果它還沒有出故障,就不要去修理它 。“全球變暖的預測可能是個錯誤。”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George S. Howard(2000),“Adapting Human Lifestyles for the 21st Century,”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09~515.
關於提高生活質量的研究
社會心理學還通過它對美好生活的研究來對可持續的未來有所貢獻。如果物質主義不能提高生活質量,那麼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
親密、支持性的關係 。正如我們在第11章所看到的那樣,我們最深層次的需求只有通過親密的支持性的關係才能獲得滿足。那些被親密的友情和忠貞的婚姻所支持的個體非常有可能宣佈他們自己是“非常快樂”的人。
團體信仰 經常是這些聯繫的來源,同時還包含其意義和希望。這有利於我們解釋自從1972年以來全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對42000個美國人的調查發現:那些很少或從未參加過宗教禮拜的人當中有26%宣佈自己非常快樂,但是那些多次參加禮拜的人們中有47%宣稱自己非常快樂。
積極的特質 。樂觀、自尊、知覺到的控制感和外向性也是幸福體驗和幸福生活的標誌。
全神貫注 。表現個人技能的工作和休閒經歷也是幸福生活的標誌。塞克斯密哈里(Csikszentmihalyi,1990,1999)指出,在絕對性的緊張焦慮與興趣全無的無聊冷漠之間還存在著一個區域,在這裡人們可以體驗到全神貫注 的感覺,這是一種最佳狀態,即沉浸在一種活動中,我們失去了對自己和時間的知覺。當使用電子尋呼機來抽樣調查人們的體驗時,人們所報告的最快樂的享受並不是在無意識安靜的時候,而是在全身心地投入一種忘我的精神挑戰的時候。實際上,一種休閒活動越不昂貴(而捲入程度越深),人們在這項活動中會感覺自己越快樂 。很多人在從事園藝活動時,會比玩汽艇更快樂,和朋友談話會比觀看電視更高興。低消費的娛樂活動通常被證實是令人滿意的。
這的確是個好消息。那些有助於真正美好生活的東西——親密牢固的友誼,一個充滿希望的信仰,積極的特質,全身心投入的活動——是經久不衰的。而這種觀點與不丹國王萬查克(Jigme Singye Wangchuk)的核心思想不謀而合。他認為“國民的總體幸福感要比國民生產總值更重要。”不丹研究中心的泰德曼(Tideman,2003)這樣解釋:“國民幸福值,旨在促進真正的發展和可持續性,是通過測量生活質量獲得的,而不僅僅是產品和消費的總和。”
小結
物質主義和消費能否帶來積極的情緒體驗呢?從大學生所表達的價值觀和20世紀末美國奢靡的生活方式中推斷,美國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們,程度相對較低——生活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
財富真的能增進幸福感嗎?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們與生活在貧困國家的人們相比,確實報告了更強烈的幸福感和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儘管一個人從中等發達的國家搬到到非常發達的國家時提高的幅度有所下降)。在某一個國家內,是否有錢人就比工薪階層更幸福呢?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這樣,雖然越來越多的錢所帶來的滿意度的提高幅度越來越小(對富豪和彩票贏家的研究可以作為證據)。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濟的增長是否能讓人們更幸福呢?不,根本不是這樣,在1960年以後的幾十年裡,儘管財富在不斷增長,但是個體自我報告的幸福感甚至有所降低,同時抑鬱的比率上升了。
兩個原理有助於我們解釋為什麼物質主義不能使我們滿意:適應水平現象和社會比較。當收入和消費量增加的時候,我們很快就會適應。而且同其他人相比我們可能發現自己的相對狀況並沒有發生變化。
個人後記:個體如何在現代世界承擔自己的責任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共同生活在地球這個社區裡,同呼吸共命運。我們必須聯合起來,為打造一個以尊重自然、普及人權、經濟公平與和平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而努力。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地球上的人類,都必須對彼此、對更廣大的生命群體、對未來的後代宣告我們的責任。
——前言,《地球憲章》,www.earthcharter.org
閱讀和寫作有關人口增長、全球變暖、物質主義、消費、適應、社會比較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引發了我的眾多思考:我是這些問題的一部分還是答案的一部分?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些大道理。但是,我自己都做到了嗎?
坦率地說,我的行為有時是互相矛盾的。
我全年都騎車上下班,但去年我仍然乘坐耗油量極大的飛機飛行了8萬英里。
我們對有105年曆史的老房子進行了隔熱處理,安裝了一個高效的暖氣爐,並在冬日將自動調溫器調整到華氏67度。但隨著夏日溫度的升高,我很難想像如果不使用空調該如何度過炎炎夏日。
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當我離開辦公室時,我習慣性地關上電燈和電腦顯示器,並在房子周圍栽種了樹木。但是,我又食用進口牛肉、飲用紅酒,這間接援助了南美的森林砍伐行為。
當1973年美國在全國範圍內設定55英里的時速限制以節省能源消耗時,我大加贊同,而當這一法令在1995年被廢除時,我感到失望。但是,既然周圍的高速公路允許時速達到70英里,我也駕駛著時速70英里的汽車——即使視野範圍內沒有其他車輛(羞愧)。
我家的所有紙張、罐頭容器和瓶子都是重複利用的。但是,每星期我們都會收到眾多的書信、報紙和雜誌,足以裝滿一個3立方英尺的回收箱了。
不錯了,我這樣告訴自己。但是,對於迫在眉睫的危機,這樣的反應,力度是不夠大的。如果今天的60多億的人口都企圖在生態環境中留下類似的痕跡,我們的曾曾曾子孫將無法在地球上生存,更不用說未來某一天人口將達到90億。
那麼,我們如何能在現代生活中,既享受著所有的美好與便利,同時對我們的環境遺產保持警覺呢?即使是一位倡導節儉生活方式的領導者——他也會乘坐耗油量大的飛機到華麗的會場去參加各種會議——也在掙扎著過一種對現代世界負責任的生活。
除了我們的個人選擇,我們還面臨著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市場經濟如何能夠兼容兩種不同的動機,既要促進繁榮又要有所控制以便維持一個適宜人類居住的地球?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賴諸如替代性的能源等技術創新,來降低我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作用?同時,我們追求為我們的子孫後代維護一個適宜生存的地球的崇高目標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激發我們限制自己的放縱行為——我們隨心所欲地開車、焚燒和傾倒垃圾的自由?
你的觀點是什麼
你贊同哪些規則,又反對哪些規則?你贊成為汽車和卡車設立更高的燃料效率標準嗎?對汽車排汙量限制呢?為減少煙霧汙染而設立的焚燒樹葉禁令呢?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為刺激人們駕駛低能耗的汽車而對燃料課以重稅的國家,你會希望燃料的賦稅更低一點、汽油的價格更便宜一些,以便美國人能駕駛大型汽車嗎?如果你是一名美國公民,為了保護環境資源並控制全球升溫,你會同意提高對汽油和石油的賦稅嗎?
人們控制全球溫室效應和資源告罄的可能性有多大?生物學家威爾遜(E. O. Wilson,2002)認為進化的結果使人們只對很小地域範圍內的、相同膚色、同一時代的人承擔責任,如果他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麼我們還能期望人類會因為考慮到我們遙遠的子孫後代而表現出“擴大化的利他主義”嗎?今天的某些物件,比如10英里/加侖的蜂鳴器,會不會成為明天羞恥的遺蹟呢?今天令人羨慕的“富裕和體面的生活方式”會不會在可持續發展成為必需的明天而變成一種粗魯的行為方式?或者,人們對自己和對成功的關切程度總是要勝過他們對不在眼前的子孫後代的關注呢?
聯繫社會
本章中提到,即便在比他們的祖輩富裕得多的環境中成長,青少年的抑鬱比率仍然有大幅度提高。在14章中,我們討論了消極的思維方式與抑鬱之間的關係。
在第2章中有關自我和第8章中有關團體影響的論述中,我們提出了社會比較的概念——通過將自己與他人進行比較來評價自己。這一概念在討論本章的什麼因素會令我們感到幸福的問題時再次提到。通常,將自己與他人作比並不能增強我們的幸福感(鄰居的車比我的好)。
事實上,還有一個聯繫在於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與社會心理學之間。本章中提到向上社會比較通常的結果是相對剝奪,這一概念在第10章中也提到過。
結語
如果你讀完了這整本書,那麼你的社會心理學的入門課程就結束了。在前言中我提出了我的希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既具有堅實的科學性,同時也是溫暖而人性化的,既是客觀真實的又是啟迪智慧的。”是你,而不是我,是判斷這個目標是否達到的評判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作為作者,傳播這門學科的知識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如果我的禮物給你帶來了任何的愉悅、激勵和充實感的話,那麼我的快樂就會倍增。
我堅信,社會心理學的知識能夠借批判性思維來限制直覺思維,用理解來揭穿幻覺,以同情避免不客觀的審判。在這16個章節中,我們集合了社會心理學關於信仰和說服,愛與恨,順從和獨立的見解。我們探討了那些有趣問題的部分答案:我們的態度與行為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為什麼有時候人們會傷害別人,有時候又會彼此幫助?是什麼引發了社會衝突,以及我們如何能將緊握的拳頭轉換成願意互相幫助的雙手?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擴展了我們的思維視野。而且,溫德爾(Oliver Wendell)注意到“一旦思維得到擴展”,思想“就再也不會回到原本狹小的領域了”。我的經歷就是如此,也許你也會有相同的經歷,因為你應該通過學習本課程和其他的課程,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
你的觀點是什麼
花幾分鐘時間來思考一下本書和你所上的社會心理學課程。寫下三到四個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觀點。是什麼令你驚訝不已?如果有的話,哪些觀點已經影響到你或者你渴望的生活方式?
邁爾斯
Davidmyers.org
[1] 本章的一部分內容改編自《美國悖論:物質豐富時代中的精神飢餓》(邁爾斯著,耶魯大學出版社,2000),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關於物質主義、財富、不平等和幸福感的更多資料。
專業術語表
A
接納
acceptance conformity that involves both acting and believing in accord with social pressure.
適應水平現象
adaptation-level phenomenon the tendency to adapt to a given level of stimulation and thus to notice and react to changes from that level.
攻擊性
aggression physical or verbal behavior intended to hurt someone. I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this might mean delivering electric shocks or saying something likely to hurt another's feelings. By this social psychological definition, one can be socially assertive without being aggressive.
利他主義
altruism a motive to increase another's welfare without conscious regard for one's self-interests.
仲裁
arbitration resolution of a conflict by a neutral third party who studies both sides and imposes a settlement.
態度
attitude a favorable or unfavorable evaluative reaction toward something or someone, exhibited in one's beliefs, feelings, or intended behavior.
態度免疫
attitude inoculation exposing people to weak attacks upon their attitudes so that when stronger attacks come, they will have refutations available.
吸引力
attractiveness having qualities that appeal to an audience. An appealing communicator (often someone similar to the audience) is most persuasive on matters of subjective preference.
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how people explain others' behavior; for example, by attributing it either to internal dispositions (enduring traits, motives, and attitudes) or to external situations.
似動現象
autokinetic phenomenon self (auto ) motion (kinetic ). The apparent movement of a stationary point of light in the dark. Perhaps you have experienced this when thinking you have spotted a moving satellite in the sky, only to realize later that it was merely an isolated star.
自動加工
automatic processing “implicit”or intuitive thinking that is effortless, habitual, and without awareness.
易得性直覺
availability heuristic an efficient but fallible rule-of-thumb that judges the likelihood of things in terms of their availability in memory. If instances of something come readily to mind, we presume it to be commonplace.
迴避型依戀
avoida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style marked by dismissive detachment.
B
談判
bargaining seeking an agreement through direct negotiation between parties to a conflict.
行為確證
behavioral confirmation a type of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whereby people's social expectations lead them to act in ways that cause others to confirm their expectations.
行為病理學
behavioral medicine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ntegrates and applies behavioral and medical knowledge about health and disease.
信念固著
belief perserverance persistence of one's initial conceptions, as when the basis for one's belief is discredited but an explanation of why the belief might be true survives.
偽途徑
bogus pipeline a procedure that fools people into disclosing their attitudes. Participants are first convinced that a machine can use their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measure their private attitudes. Then they are asked to predict the machine's reading, thus revealing their attitudes.
旁觀者效應
bystander effect the finding that a person is less likely to provide help when there are other bystanders.
C
宣洩
catharsis emotional release. The catharsis view of aggression is that aggressive drive is reduced when one“releases”aggressive energy, either by acting aggressively or by fantasizing aggression.
說服的中心途徑
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 persuasion that occurs when interested people focus on the arguments and respond with favorable thoughts.
溝通渠道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the way the message is delivered—whether face to face, in writing, on film, or in some other way.
臨床心理學
clinical psychology the study,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people with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共事者
co-actors co-participants working individually on a noncompetitive activity.
認知不協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tension that arises when one is simultaneously aware of two inconsistent cognitions. For example, dissonance may occur when we realize that we have, with little justification, acted contrary to our attitudes or made a decision favoring one alternative despite reasons favoring another.
凝聚力
cohesiveness a“we feeling”; the extent to which members of a group are bound together, such as by attraction for one another.
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 giving priority to the goals of one's groups (often one's extended family or work group) and defining one's identity accordingly.
伴侶之愛
companionate love the affection we feel for those with whom our live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 the popularly supposed tendency, in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ople, for each to complete what is missing in the other. The questionable 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people attract those whose needs are different, in ways that complement their own.
順從
compliance conformity that involves publicly acting in accord with social pressure while privately disagreeing. Obedience is acting in accord with a direct order.
同謀者
confederate an accomplice of the experimenter.
驗證性偏見
confirmation bias a tendency to search for information that confirms one's preconceptions.
衝突
conflict a perceived incompatibility of actions or goals.
從眾
conformity a change in behavior or belief as a result of real or imagined group pressure.
控制加工
controlled processing “explicit”thinking that is deliberate, reflective, and conscious.
相關研究
correlational research the study of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反事實思維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magining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but didn't.
信度
credibility believability. A credible communicator is perceived as both expert and trustworthy.
邪教組織
cult (also called a new religious movement) a group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1) distinctive ritual and beliefs related to its devotion to a god or a person, (2) isolation from the surrounding“evil”culture, and (3) a charismatic leader. (A sect, by contrast, is a spinoff from a major religion.)
文化
culture the enduring behaviors, ideas, attitudes, and traditions shared by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and transmitted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D
事後解說
debrief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post experimental explanation of a study to its participants. Debriefing usually discloses any deception and often queries participants regarding their understandings and feelings.
欺騙
deception occurs in research when participants are misinformed or misled about the study's methods and purposes.
去個體化
deindividuation loss of self-awareness and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occurs in group situations that foster responsiveness to group norms, good or bad.
需要特徵
demand characteristics cues in an experiment that tell the participant what behavior is expected.
因變量
dependent variable the variable being measured, so-called because it may depend on manipula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抑鬱現實主義
depressive realism the tendency of mildly depressed people to make accurate rather than self-serving judgments, attributions, and predictions.
性格歸因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attributing behavior to the person's disposition and traits.
表露互惠效應
disclosure reciprocity the tendency for one person's intimacy of self-disclosure to match that of a conversational partner.
歧視
discrimination unjustifiable negative behavior toward a group or its members.
轉移
displacement the redirection of aggression to a target other than the source of the frustration. Generally, the new target is a safer or more socially acceptable target.
留面子技術
door-in-the-face technique a strategy for gaining a concession. After someone first turns down a large request (the door-in-the-face), the same requester counteroffers with a more reasonable request.
向下社會比較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 comparing with others who are worse, or worse off, may trigger improved feelings about oneself.
雙重態度
dual attitudes differing implicit (automatic) and explicit (consciously controlled) attitudes toward the same object. Verbalized explicit attitudes may change with education and persuasion; implicit attitudes change slowly, with practice that forms new habits.
E
利己主義
egoism a motive (supposedly underlying all behavior) to increase one's own welfare. The opposite of altruism, which aims to increase another's welfare.
共情
empathy the vicarious experience of another's feelings; putting oneself in another's shoes.
地位平等的接觸
equal-status contact contact on an equal basis. Just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of unequal status breeds attitudes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lationship, so do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of equal status. Thus, to reduce prejudice, interracial contact should be between persons equal in status.
公平
equity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outcomes people receive from a relationship are proportional to what they contribute to it. Note: Equitable outcomes needn't always be equal outcomes.
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a belief in the superiority of one's own ethnic and cultural group, and a corresponding disdain for all other groups.
評價顧忌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concern for how others are evaluating us.
進化心理學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behavior using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
實驗現實主義
e8perimental realism degree to which an experiment absorbs and involves its participants.
實驗研究
e8perimental research studies that seek clues to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by manipulating one or more factor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hile controlling others (holding them constant).
解釋風格
explanatory style one's habitual way of explaining life events. A negative, pessimistic, depressive explanatory style attributes failures to stable, global, and internal causes.
F
虛假普遍性效應
false consensus effect the tendency to overestimate the commonality of one's opinions and one's undesirable or unsuccessful behaviors.
虛假獨特性效應
false uniqueness effect the tendency to underestimate the commonality of one's abilities and one's desirable or successful behaviors.
現場研究
field research research done in natural, real-life settings outside the laboratory.
登門檻現象
foot-in-the-door phenomenon the tendency for people who have first agreed to a small request to comply later with a larger request.
搭集體便車
free riders people who benefit from the group but give little in return.
挫折
frustration the blocking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挫折攻擊理論
frustration aggression theory the theory that frustration triggers a readiness to aggress.
基本歸因錯誤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the tendency for observers to underestimate situational influences and overestimate dispositional influences upon others' behavior. (Also called correspondence bias , because we so often see behavior as corresponding to a disposition.)
G
性別
gender in psych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whether biological or socially influenced, by which people define male and female. Because“sex”is a biological category, social psychologists sometimes refer to biologically based gender differences as“sex differences.”
性別角色
gender role a set of behavior expectations (norms) for males and females.
逐步、互惠、互動地減少緊張
GRIT acronym for“graduated and reciprocated initiatives in tension reduction”—a strategy designed to de-escalate international tensions.
群體
group two or more people who, for longer than a few moments, interact with and influence one another and perceive one another as“us.”
群體極化
group polarization group-produced enhancement of members' preexisting tendencies; a strengthening of the members' average tendency, not a split within the group.
群體服務偏見
group-serving bias explaining away outgroup members' positive behaviors; also attributing negative behaviors to their dispositions (while excusing such behavior by one's own group).
群體思維
groupthink “The mode of thinking that persons engage in when concurrence-seeking becomes so dominant in a cohesive in-group that it tends to override realistic appraisal of alternative courses of action.”—Irving Janis (1971).
H
健康心理學
health psychology a subfield of psychology that provides psychology's contribution to behavioral medicine.
直覺
heuristic a rule-of-thumb strategy that enables quick, efficient judgments.
事後聰明式偏見
hindsight bias the tendency to exaggerate, after learning an outcome, one's ability to have foreseen how something turned out. Also known as the I-knew-it-all-along phenomenon .
敵意性攻擊行為
hostile aggression aggression driven by anger and performed as an end in itself (also called affective aggression).
假設
hypothesis a testable proposition that describes a relationship that may exist between events.
I
控制錯覺
illusion of control perception of uncontrollable events as subject to one's control or as more controllable than they are.
透明度錯覺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the illusion that our concealed emotions leak out and can be easily read by others.
錯覺相關
illusory correlation (1) perception of a relationship where none exists, or perception of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than actually exists. (2) A false impression that two variables correlate.
自變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experimental factor that a researcher manipulates.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giving priority to one's own goals over group goals and defining one's identity in terms of personal attributes rather than group identifications.
信息影響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conformity occurring when people accept evidence about reality provided by other people.
知會同意
informed consent an ethical principle requiring that research participants be told enough to enable them to choose whether they wish to participate.
討好
ingratiation the use of strategies, such as flattery, by which people seek to gain another's favor.
內群體
ingroup “us”—a group of people who share a sense of belonging, a feeling of common identity.
內群體偏見
ingroup bias the tendency to favor one's own group.
不安全型依戀
insecure attachment attachments marked by anxiety, ambivalence, and possessiveness.
本能行為
instinctive behavior an innate, unlearned behavior pattern exhibited by all members of a species.
工具性攻擊行為
instrumental aggression aggression that is a means to some other end.
理由不足效應
in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effect reduction of dissonance by internally justifying one's behavior when external justification is“insufficient.”
整合性協議
integrative agreements win-win agreements that reconcile both parties' interests to their mutual benefit.
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the effect of one factor (such as biology) depends on another factor (such as environment).
J
公正世界現象
just-world phenomenon the tendency of people to believe the world is just and that people therefore get what they deserve and deserve what they get.
K
親緣選擇
kin selection the idea that evolution has selected altruism toward one's close relatives to enhance the survival of mutually shared genes.
L
領導
leadership the process by which certain group members motivate and guide the group.
習得性無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 hopelessness and resignation learned when a human or animal perceives no control over repeated bad events.
控制點
locus of control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 perceive outcomes as internally controllable by their own efforts and actions or as externally controlled by chance or outside forces.
低價法策略
low-ball technique a tactic for getting people to agree to something. People who agree to an initial request will often still comply when the requester ups the ante. People who receive only the costly request are less likely to comply with it.
M
匹配現象
matching phenomenon the tendency for men and women to choose as partners those who are a“good match”in attractiveness and other traits.
調解
mediation an attempt by a neutral third party to resolve a conflict by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and offering suggestions.
曝光效應
mere-exposure effect the tendency for novel stimuli to be liked more or rated more positively after the rater has been repeatedly exposed to them.
鏡像知覺
mirror-image perceptions reciprocal views of one another often held by parties in conflict; for example, each may view itself as moral and peace-loving and the other as evil and aggressive.
誤導信息效應
misinformation effect (1) incorporating“misinformation”into one's memory of the event, after witnessing an event and receiv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it. (2) Witnessing an event, receiving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it, and then incorporating the“misinformation”into one's memory of the event.
道德排除
moral exclusion the perception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r groups as outside the boundary within which one applies moral values and rules of fairness. Moral inclusion is regarding others as within one's circle of moral concern.
現世實在論
mundane realism degree to which an experiment is superficially similar to everyday situations.
N
自然選擇
natural selectio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by which nature selects traits that best enable organisms to survive and reproduce in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niches.
自然主義的謬論
naturalist fallacy the error of defining what is good in terms of what is observable. For example: What's typical is normal; what's normal is good.
認知需求
need for cognition the motivation to think and analyze. Assessed by agreement with items such as“the notion of thinking abstractly is displeasing to me”and disagreement with items such as“I only think as hard as I have to”.
歸屬需求
need to belong a motivation to bond with others in relationships that provide ongoing, positive interactions.
非零和博弈
non-zero-sum games games in which outcomes need not sum to zero. With cooperation, both can win; with competition, both can lose. (Also called mixed-motive situations .)
規範性影響
normative influence conformity based on a person's desire to fulfill others' expectations, often to gain acceptance.
規範
norms rules for accepted and expected behavior. Norms prescribe“proper”behavior. (In a different sense of the word, norms also describe what most others do—what is normal .)
O
服從
obedience acting in accord with a direct order.
外群體
outgroup “them”—a group that people perceive as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or apart from their ingroup.
外群體同質效應
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 perception of outgroup members as more similar to one another than are ingroup members. Thus“they are alike; we are diverse.”
過度自信現象
overconfidence phenomenon the tendency to be more confident than correct—to overestimate the accuracy of one's beliefs.
過度辯護效應
overjustification effect the result of bribing people to do what they already like doing; they may then see their action as externally controlled rather than intrinsically appealing.
同種偏差
own-race bias the tendency for people to more accurately recognize faces of their own race.
P
激情之愛
passionate love a state of intense longing for union with another. Passionate lovers are absorbed in one another, feel ecstatic at attaining their partner's love, and are disconsolate on losing it.
說服的外周途徑
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 persuasion that occurs when people are influenced by incidental cues, such as a speaker's attractiveness.
個人空間
personal space the buffer zone we like to maintain around our bodies. Its size depends on our familiarity with whoever is near us.
說服
persuasion the process by which a message induces change in beliefs, attitudes, or behaviors.
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
physical-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 the presumption that physically attractive people possess other socially desirable traits as well: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人眾無知
pluralistic ignorance a false impression of how other people are thinking, feeling, or responding.
可能的自我
possible selves images of what we dream of or dread becoming in the future.
偏見
prejudice a negative prejudgment of a group and its individual members.
首因效應
primacy effect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information presented first usually has the most influence.
啟動
priming activating particular associations in memory.
親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 positive, constructive, helpful social behavior; the opposite of antisocial behavior.
接近性
proximity geographical nearness. Proximity (more precisely,“functional distance”) powerfully predicts liking.
R
種族歧視
racism (1) an individual's prejudicial attitudes an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toward people of a given race, or (2)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even if not motivated by prejudice) that subordinate people of a given race.
隨機分配
random assignment the process of assigning participants to the conditions of an experiment such that all persons have the same chance of being in a given condition. (Not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andom assignment in experiments and random sampling in surveys. Random assignment helps us infer cause and effect. Random sampling helps us generalize to a population.)
隨機取樣
random sample survey procedure in which every person in the population being studied has an equal chance of inclusion.
逆反
reactance (1) a motive to protect or restore one's sense of freedom. Reactance arises when someone threatens our freedom of action. (2) The desire to assert one's sense of freedom.
現實群體衝突理論
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 the theory that prejudice arises from competition between groups for scarce resources.
近因效應
recency effect information presented last sometimes has the most influence. Recency effects are less common than primacy effects.
互惠規範
reciprocity norm an expectation that people will help, not hurt, those who have helped them.
趨均數迴歸
regression toward the average the statistical tendency for extreme scores or extreme behavior to return toward one's average.
相對剝奪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perception that one is less well off than others to whom one compares oneself.
代表性直覺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the tendency to presume, sometimes despite contrary odds, that someone or something belongs to a particular group if resembling (representing) a typical member.
吸引的回報理論
reward theory of attraction the theory that we like those whose behavior is rewarding to us or whom we associate with rewarding events.
角色
role a set of norms that defines how people in a given social position ought to behave.
S
安全型依戀
secure attachment attachments rooted in trust and marked by intimacy.
自我肯定理論
self-affirmation theory a theory that (a) people often experience a self-image threat after engaging in an undesirable behavior; and that (b) they can compensate by affirming another aspect of the self. Threaten people's self-concept in one domain and they will compensate by either refocusing or by doing good deeds in some other domain.
自我覺知
self-awareness a self-conscious state in which attention focuses on oneself. It makes people more sensitive to their own attitudes and dispositions.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a person's answers to the question“Who am I?”
自我表露
self-disclosure revealing intimate aspects of one-self to others.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a sense that one is competent and effective, distinguished from self-esteem, one's sense of self-worth. A bombardier might feel high self-efficacy and low self-esteem.
自尊
self-esteem a person's overall self-evaluation or sense of self-worth.
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 belief that leads to its own fulfillment.
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being attuned to the way one presents oneself in social situations and adjusting one's performance to create the desired impression.
自我知覺理論
self-perception theory the theory that when we are unsure of our attitudes, we infer them much as would someone observing us, by looking at our behavior and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it occurs.
自我展示
self-presentation the act of expressing oneself and behaving in ways designed to create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r an impression that corresponds to one's ideals.
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 the tendency to process efficiently and remember well information related to oneself.
自我圖式
self-schema beliefs about self that organize and guide the processing of self-relevant information.
自我服務偏見
self-serving bias the tendency to perceive oneself favorably.
性別歧視
sexism (1) an individual's prejudicial attitudes and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toward people of a given sex, or (2)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even if not motivated by prejudice) that subordinate people of a given sex.
情境歸因
situational attribution attributing behavior to the environment.
睡眠者效應
sleeper effect a delayed impact of a message. Occurs when an initially discounted message becomes effective, as we remember the message but forget the reason for discounting it.
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 evaluating one's abilities and opinions by comparing oneself to others.
社會支配性取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 motivation to have one's group be dominant over other social groups.
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exchange theory the theory that human interactions are transactions that aim to maximize one's rewards and minimize one's costs.
社會助長作用
social facilitation (1) original meaning—the tendency of people to perform simple or well-learned tasks better when others are present; (2) current meaning—strengthening of dominant (prevalent, likely) responses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others.
社會同一性
social identity the“we”aspect of our self-concept. The part of our answer to“Who am I?”that comes from our group memberships. Examples:“I am Australian.”“I am Catholic.”
社會型領導
social leadership leadership that builds teamwork, mediates conflict, and offers support.
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the theory that we learn social behavior by observing and imitating and by being rewarded and punished.
社會懈怠
social loafing the tendency for people to exert less effort when they pool their efforts toward a common goal than when they are individually accountable.
社會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how people think about, influence, and relate to one another.
社會表徵
social representations socially shared beliefs, and widely held ideas and values, including our assumptions and cultural ideologies. Our social representations help us make sense of our world.
焦點效應
spotlight effect the belief that other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one's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than they really are.
刻板印象
stereotype a belief about the personal attributes of a group of people. Stereotypes are sometimes overgeneralized, inaccurate, and resistant to new information.
刻板印象威脅
stereotype threat a disruptive concern, when facing a negative stereotype, that one will be evaluated based on a negative stereotype. Unlike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that hammer one's reputation into one's self-concept, stereotype threat situations have immediate effects.
再分群法
subgrouping accommodating groups of individu-als who deviate from one's stereotype by forming a new stereotype about this subset of the group.
再分類法
subtyping accommodating individuals who deviate from one's stereotype by splitting off a subgroup stereotype (such as“middle-class Blacks”or“feminist women”). Subtyping protects stereotypes.
超級目標
superordinate goal a shared goal that necessitates cooperative effort; a goal that overrides people's differences from one another.
T
任務型領導
task leadership leadership that organizes work, sets standards, and focuses on goals.
理論
theory an integrated set of principles that explains and predicts observed events.
公共地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e“commons”is any shared resource, including air, water, energy sources, and food supplies. The tragedy occurs when individuals consume more than their share, with the cost of their doing so dispersed among all, causing the ultimate collapse—the tragedy—of the commons.
情緒的兩因素理論
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arousal × label = emotion.
溝通的兩個流程
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 the process by which media influence often occurs through opinion leaders, who in turn influence others.
U
向上社會比較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comparing with others who are better, or better off, may trigger feeling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參考文獻
Abbey, A. (1987). Misperceptions of friendly behavior as sexual interest: A survey of naturally occurring inci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 11 , 173-194. (p. 85)
Abbey, A. (1991). Misperception as an antecedent of acquaintance rape: A consequence of ambiguity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A. Parrot (Ed.), Acquaintance rape . New York: John Wiley. (p. 85)
Abbey, A., & Andrews, F. M. (1985). Modeling the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life quali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16 , 1-34. (p. 600)
Abbey, A., McAuslan, P., & Ross, L. T . (1998). Sexual assault perpetration by college men: The role of alcohol, misperception of sexual intent, and sexual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17, 167-195. (p. 85)
Abelson, R. (1972). Are attitudes necessary? In B. T. King & E. McGinnies (Eds.), Attitudes,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135)
Abelson, R. P., Kinder, D. R., Peters, M. D., & Fiske, S. T. (1982). Affective and semantic components in political 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42, 619-630. (p. 256)
Abrams, D. (1991). AIDS: What young people believe and what they d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conference. (p. 71)
Abrams, D., Wetherell, M., Cochrane, S., Hogg, M. A., & Turner, J. C. (1990). Knowing what to think by knowing who you are: Self-categorization and the nature of norm formation, conformity and group polariz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29, 97-119. (p. 309)
Abramson, L. Y. (Ed.). (1988). Social cognition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A synthesis . New York: Guilford. (p. 594)
Abramson, L. Y., Metalsky, G. I., & Alloy, L. B. (1989).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 theory-based subtype. Psychological Review , 96, 358-372. (p. 577)
Acitelli, L. K., & Antonucci, T. C. (1994).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support and satisfaction in older coup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67, 688-698. (p. 183)
Ackermann, R., & DeRubeis, R. J. (1991). Is depressive realism rea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 11, 565-584. (p. 577)
Adair, J. G., Dushenko, T. W., & Lindsay, R. C. L. (1985). Ethical regu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research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 40, 59-72. (p. 28)
Adams, D. (Ed.) (1991). 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the constructing of peace . UNESCO. (p. 386)
Adams, J. M., & Jones, W. H. (1997).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arital commitment: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72, 1177-1196. (p. 467)
Addis, M. E., & Mahalik, J. R. (2003). Men, masculinity, and the contexts of help seek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 58, 5-14. (p. 182)
Aderman, D., & Berkowitz, L. (1970). Observational set, empathy, and hel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4, 141-148. (p. 480)
Aderman, D., & Berkowitz, L. (1983). Self-concern and the unwillingness to be helpful.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 46, 293-301. (p. 481)
Adler, N. E., Boyce, T., Chesney, M. A., Cohen, S., Folkman, S., Kahn, R. L., & Syme, S. L. (1993).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ealth: No easy solu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 269, 3140-3145. (p. 23)
Adler, N. E., & Snibbe, A. C. (2003). The role of psychosocial processes in explaining the gradient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12, 119-123. (p. 599)
Adler, R. P., Lesser, G. S., Meringoff, L. K., Robertson, T. S., & Ward, S. (1980).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advertising on children .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 281)
Adler, S. J. (1994). The jury . New York: Times Books. (p. 626)
Adorno, T., Frenkel-Brunswik, E., Levinson, D., & Sanford, R. N.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p. 345)
Affleck, G., Tennen, H., & Apter, A. (2000). Optimism, pessimism, and daily life with chronic illness. In E. C. Chang (Ed.), Optimism and pessimism . Washington, DC: APA Books. (pp. 590, 657)
Agostinelli, G., Sherman, S. J., Presson, C. C., & Chassin, L. (1992). Self-protec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biases in estimates of population preval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18, 631-642. (pp. 63)
Agres, S. J. (1987). Rational, emotional and mixed appeals in advertising: Impact on recall and persua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Available from Lowe Marschalk, Inc., 1345 Avenue of the Americas, New York, NY, 10105.) (p. 256)
Aiello, J. R., & Douthitt, E. Z. (2001). Social facilitation from Triplett to electronic performance monitoring.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 5, 163-180. (p. 290)
Aiello, J. R., Thompson, D. E., & Brodzinsky, D. M. (1983). How funny is crowding anyway? Effects of room size, group siz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humor.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 4, 193-207. (p. 289)
Ainsworth, M. D. S.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In B. Caldwell &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59)
Ainsworth, M. D. S. (1979).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 34, 932-937. (p. 459)
Ajzen, I. (1982). On behaving in accordance with one's attitudes. In M.P. Zanna, E. T. Higgins, & C. P. Herman (Eds.). Consistency in social behavior: The Ontario Symposium , vol. 2. Hillside, NJ: Erlbaum. (p. 138)
Ajzen, I. (2002).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 32, 665-683. (p. 138)
Ajzen, I., & Fishbein, M. (1977).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84, 888-918. (pp. 138)
Albarracin, D., Johnson, B. T., Fishbein, M., & Muellerleile, P. A. (2001). 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lanned behavior as models of condom us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27, 142-161. (p.138)
Albee, G. (1979, June 19). Politics, power, prevention, and social change. Keynote address to Vermont Conference on Primary Prevention of Psychopathology. (p. 204)
Alicke, M. D., & Davis, T. L. (1989). The role of a posteriori victim information in judgments of blame and san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25, 362-377. (p. 624)
Allee, W. C., & Masure, R. M. (1936). A comparison of maze behavior in paired and isolated shell-parakeets (Melopsittacus undulatus Shaw ) in a two-alley problem box.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 22, 131-155. (p.287)
Allen, V. L., & Levine, J. M. (1969). Consensus and conform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5, 389-399. (p. 229)
Allen, V. L., & Wilder, D. A. (1980). Impact of group consensus and social support on stimulus meaning: Mediation of conformity by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39, 1116-1124. (p.235)
Allison, S. T., Beggan, J. K., McDonald, R. A., & Rettew, M. L. (1995). The belief in majority determination of group decision outcom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 16, 367-382. (p. 359)
Allison, S. T., Jordan, M. R., & Yeatts, C. E. (1992). A cluster-analytic approach toward identify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human decision making. Human Relations , 45, 49-72. (p. 359)
Allison, S. T., Mackie, D. M., & Messick, D. M. (1996). Outcome biases in social perception: Implications for dispositional inference, attitude change, stereotyping, and social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28, 53-93. (p. 359)
Allison, S. T., Mackie, D. M., Muller, M. M., & Worth, L. T. (1993). Sequential correspondence biases and perceptions of change: The Castro studies revisit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19, 151-157. (pp. 88, 359)
Allison, S. T., McQueen, L. R., & Schaerfl, L. M. (1992). Soci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and the equal partitionment of shared resour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8, 23-42. (pp. 114, 359, 526)
Allison, S. T., & Messick, D. M. (1985). The group attribution err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563-579. (p. 359)
Allison, S. T., & Messick, D. M. (1987). From individual inputs to group outputs, and back again: Group processes and inferences about members. In C. Hendrick (Ed.), Group processes: 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8. Newbury Park, CA: Sage. (p. 359)
Allison, S. T., Messick, D. M., & Goethals, G. R. (1989). On being better but not smarter than others: The Muhammad Ali effect. Social Cognition, 7, 275-296. (pp. 69, 359)
Allison, S. T., Worth, L. T., & King, M. W. C. (1990). Group decisions as social inference heuristic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801-811. (p. 359)
Alloy, L. B., & Abramson, L. Y. (1979). Judgment of contingency in depressed and nondepressed students: Sadder but wis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8, 441-485. (p.577)
Alloy, L. B., Abramson, L. Y., Whitehouse, W. G., Hogan, M. E., Tashman, N. A., Steinberg, D. L., Rose, D. T., & Donovan, P. (1999). Depressogenic cognitive styles: Predictive validit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origin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 37, 503-531. (p. 580)
Alloy, L. B., Albright, J. S., Abramson, L. Y., & Dykman, B. M. (1990). Depressive realism and nondepressive optimistic illusions: The role of the self. In R. E. Ingram (Ed.),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depression: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 New York: Plenum. (p. 577)
Allport, F. H. (1920). The influence of the group upon association and though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59-182. (p. 287)
Allport, G.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 Cambridge, MA: Addison-Wesley. (pp. 332-333, 369, 550)
Allport, G. W. (1958).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abridged).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pp. 343-344, 347, 350, 370, 371)
Allport, G. W., & Ross, J. M. (1967). Personal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5, 432-443. (p. 346)
Altemeyer, B. (1988). Enemies of freedom: Understanding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345-346)
Altemeyer, B. (1992). Six studies of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mong American state legislator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p. 345-346)
Altemeyer, B., & Hunsberger, B. (1992). Authoritarianism,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quest, and prejud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 113-133. (p. 346)
Altemeyer, R. (in press). Highly dominating, highly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i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p. 346)
Altman, I., & Vinsel, A. M. (1978). Personal space: An analysis of E. T. Hall's proxemics framework. In I. Altman & J. Wohlwill (Eds.), Human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 New York: Plenum Press. (p. 175)
Alwin, D. F. (1990). Historical changes in parental orientations to children. In N. Mandell (Ed.),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 development, Vol. 3.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 561)
Alwin, D. F., Cohen, R. L., & Newcomb, T. M. (1991). Political attitudes over the life span: The Bennington women after fifty years .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 268)
Amabile, T. M., & Glazebrook, A. H. (1982). A negativity bias in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8, 1-22. (p. 355)
Amato, P. R. (1979). Juror-defendant similarity and the assessment of guilt in politically motivated crim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1, 79-88. (p. 620)
Amato, P. R. (1986). Emotional arousal and helping behavior in a real-life emergenc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6, 633-641. (pp. 490-491)
Ambady, N., & Rosenthal, R. (1992). Thin slices of expressive behavior as predictors of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1, 256-274. (p.123)
Ambady, N., & Rosenthal, R. (1993). Half a minute: Predicting teacher evaluations from thin slices of nonverbal behavior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431-441. (p. 123)
American Enterprise (1992, January/February). Women, men, marriages & ministers. P. 106. (p. 46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3). Violence and youth: Psychology's response. Vol I: Summary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ation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nd Youth . Washington, DC: Public Interest Directorat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p. 384-385)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2).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2002 . Washington, DC: APA(www.apa.org/ethics/code2002.html ). (p. 32)
Amir, Y. (1969). Contact hypothesis in ethnic rel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1, 319-342. (p. 539)
Anda, R., Williamson, D., Jones, D., Macera, C., Eaker, E., Glassman, A., & Marks, J. (1993). Depressed affect, hopelessness, and the risk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in a cohort of U.S. adults. Epidemiology, 4, 285-294. (p. 588)
Andersen, S. M. (1998). Service Learning: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Youth Development. A Position Paper issued by the Task Force on Education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Communitarian Policy Studie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p.478, 516)
Andersen, S. M., & Chen, S. (2002). The relational self: An interpersonal social-cognitive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 619-645. (p. 41)
Anderson, C. A. (1982). Inoculation and counter-explanation: Debiasing techniques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 Social Cognition, 1, 126-139. (p. 102)
Anderson, C. A. (1999). Attributional style,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482-499. (p. 80)
Anderson, C. A. (2003). Video game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D. Ravitch and J. P. Viteritti (Eds.), Kids stuff: Marking violence and vulgarity in the popular culture .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411, 412)
Anderson, C. A. (2004). An update on the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113-122. (p.410)
Anderson, C. A., & Anderson, D. C. (1984).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violent crime: Tests of the linear and curvilinear hypothe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91-97. (p. 395)
Anderson, C. A., & Anderson, K. B. (1998). Temperature and aggression: Paradox, controversy, and a (fairly) clear picture. In R. G. Geen & E. Donnerstein (Eds.), Human aggression: Theories,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 395)
Anderson, C. A., Anderson, K. B., Dorr, N., DeNeve, K. M., & Flanagan, M. (2000). Temperature and aggression.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 395)
Anderson, C. A., Benjamin, A. J., Jr., & Bartholow, B. D. (1998). Does the gun pull the trigger? Automatic priming effects of weapon pictures and weapon nam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9, 308-314. (pp. 396-397)
Anderson, C. A., Berkowitz, L., Donnerstein, E., Huesmann, R. L., Johnson, J., Linz, D., Malamuth, N., & Wartella, E. (in press). The influence of media violence on youth.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p. 407)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1997). External validity of“trivial”experiments: The case of laboratory aggress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 19-41. (p. 414)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1).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aggressive cognition, aggressive affect, physiological arous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353-359. (p. 412)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Media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revisited.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 448-450. (p. 406)
Anderson, C. A., Carnagey, N. L., & Eubanks, J. (2003). Exposure to violent media: The effects of songs with violent lyrics on aggressive thoughts and feel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960-971. (p. 411)
Anderson, C. A., Carnagey, N. L., Flanagan, M., Benjamin, A. J., Eubanks, J., & Valentine, J. C. (in press). Violent video games: Specific effects of violent content on aggressive thoughts and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 411)
Anderson, C. A., Deuser, W. E., & DeNeve, K. M. (1995). Hot temperatures, hostile affect, hostile cognition, and arousal: Tests of a general model of affective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434-448. (pp. 397, 509)
Anderson, C. A., & Harvey, R. J. (1988). Discriminating between problems in living: An examination of measures of depression, loneliness, shyness, and social anxie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 482-491. (p. 584)
Anderson, C. A., Horowitz, L. M., & French, R. D. (1983). Attributional style of lonely and depressed peo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27-136. (p. 75)
Anderson, C. A., Lepper, M. R., & Ross, L. (1980). Perseverance of social theories: The role of explanation in the persistence of discredit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1037-1049. (p. 102)
Anderson, C. A., Lindsay, J. J., & Bushman, B. J. (1999). Research in the psychological laboratory: Truth or trivial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3-9. (pp. 33, 395)
Anderson, C. A., Miller, R. S., Riger, A.L., Dill, J. C., & Sedikides, C. (1994). Behavioral and characterological attributional styles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Review, refinement, and 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549-558. (p. 582)
Anderson, C. A., & Morrow, M. (1995). Competitive aggression without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mpetitive versus cooperative instructions on aggressive behavior in video ga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1020-1031. (p. 529)
Anderson, C. A., & Sechler, E. S. (1986). Effects of explanation and counter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ocial the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24-34. (p. 102)
Anderson, C., Keltner, D., & John, O. P. (2003). Emotional convergence between people over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054-1068. (p. 444)
Anderson, K. J., & Leaper, C. (1998). Meta-analyses of gender effects on conversational interruption: Who, what, when, where, and how. Sex Roles, 39, 225-252. (p. 186)
Angier, N. (2003, November 11). Is war our biological destiny?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 ). (p. 419)
Annin, P. (1999, April 19). Big money, big trouble. Newsweek, p. 59. (p. 652)
Antill, J. K. (1983). Sex role complementarity versus similarity in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45-155. (p.185)
AP (1993, June 10). Walking past a dying man. New York Times (via Associated Press). (p. 498)
Apsler, R. (1975). Effects of embarrassment on behavior toward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 145-153. (p. 480)
Archer, D., & Gartner, R. (1976). Violent acts and violent tim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postwar homicide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 937-963. (p. 416)
Archer, D., Iritani, B., Kimes, D. B., & Barrios, M. (1983). Face-ism: Five studies of sex differences in facial promin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725-735. (p. 348)
Archer, J. (1991). The influence of testosterone on human aggre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82, 1-28. (p. 385)
Archer, J. (2000). Sex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between heterosexual partne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651-680. (pp. 187-188)
Archer, J. (2002).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ly aggressive acts between heterosexual partners: A meta-analytic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7, 313-351. (pp. 187-188)
Archer, R. L., & Cook, C. E. (1986). Personalistic self-disclosure and attraction: Basis for relationship or scarce resour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9, 268-272. (p. 462)
Arendt, 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p. 226)
Argyle, M. (1986).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 London: Methuen. (p. 652)
Argyle, M. (1999). Causes 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In D. Kahneman, E. Diener, and N. Schwartz (Eds.),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on enjoyment and suffering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651-652)
Argyle, M., & Henderson M. (1985). The anatomy of relationships . London: Heinemann. (p. 175)
Argyle, M., Shimoda, K., & Little, B. (1978). Variance due to persons and situations in England and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7, 335-337. (p. 203)
Arkes, H. R. (1990). Some practical judgment/decision making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p. 264)
Arkin, R. M., Appleman, A., & Burger, J. M. (1980). Social anxiety, self-presentation, and the self-serving bias in causal attribu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23-35. (p. 79)
Arkin, R. M., & Baumgardner, A. H. (1985). Self-handicapping. In J. H. Harvey & C. Weary (Eds.), Attribution: Basic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79)
Arkin, R. M., & Burger, J. M. (1980). Effects of unit relation tendencies on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3, 380-391. (p.426)
Arkin, R. M., Cooper, H., & Kolditz, T. (1980). A statis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self-serving attribution bias i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sit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8, 435-448. (p. 69)
Arkin, R. M., Lake, E. A., & Baumgardner, A. H. (1986). Shyness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W. H. Jones, J. M. Cheek, & S. R. Briggs (Eds.), Shyness: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 New York: Plenum. (p. 78)
Arkin, R. M., & Maruyama, G. M. (1979). Attribution, affect, and college ex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 85-93. (p.68)
Armitage, C. J., & Conner, M. (2001).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A meta-analy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 471-499. (p. 138)
Armor, D. A., & Taylor, S. E. (1996). Situated optimism: Specific outcome expectancies and self-regulation.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0.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 71)
Arms, R. L., Russell, G. W., & Sandilands, M. L. (1979). Effects on the hostility of spectators of viewing aggressive spor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2, 275-279. (p. 416)
Aron, A., & Aron, E. (1989). The heart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p. 213, 529)
Aron, A., & Aron, E. N. (1994). Love. In A. L. Weber & J. H. Harvey (Eds.), Perspective on close relationships . Boston: Allyn & Bacon. (p. 464)
Aron, A., Dutton, D. G., Aron, E. N., & Iverson, A. (1989). Experiences of falling in lov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6, 243-257. (p. 446)
Aron, A., Melinat, E., Aron, E. N., Vallone, R. D., & Bator, R. J. (1997). The experimental generation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A procedure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363-377. (p. 464)
Aron, A., Norman, C. C., Aron, E. N., McKenna, C., & Heyman, R. E. (2000). Couples' shared participation in novel and arousing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273-284. (p. 455)
Aronson, E. (1988). The social animal . New York: Freeman. (p. 449)
Aronson, E. (1997). Bring the family address to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nnual convention, reported in APS Observer, July/August, pp. 17, 34, 35. (p. 258)
Aronson, E. (2000). Nobody left to hate: Teaching compassion after Columbine . New York: Freeman/Worth. (p. 549)
Aronson, E. (2002). Building empathy, compassion, and achievement in the jigsaw classroom. In J. Aronson (Ed.), Improv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education .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 549)
Aronson, E., Blaney, N., Stephan, C., Sikes, J., & Snapp, M. (1978). The jigsaw classroom .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 549)
Aronson, E., Brewer, M., & Carlsmith, J. M. (1985). Experiment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G. Lindzey & E.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 Hillsdale, NJ: Erlbaum. (p. 31)
Aronson, E., & Gonzalez, A. (1988). Desegregation, jigsaw, and the Mexican-American experience. In P. A. Katz & D. Taylor (Eds.), Towards the elimination of racism: Profiles in controversy . New York: Plenum. (p.549)
Aronson, E., & Linder, D. (1965). Gain and loss of esteem as determinant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ve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 156-171. (p. 449)
Aronson, E., & Mettee, D. R. (1974). Affective reactions to appraisal from others. 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 449)
Aronson, E., & Mills, J. (1959).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 177-181. (p. 273)
Aronson, E., Turner, J. A., & Carlsmith, J. M. (1963). Communicator credibility and communicator discrepancy as determinants of opinion chang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1-36. (pp. 259, 260)
Arriaga, X. B. (2001). The ups and downs of dating: Fluctuations in satisfaction in newly forme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754-765. (p. 468)
Arriaga, X. B., & Agnew, C. R. (2001). Being committed: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conative components of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1190-1203. (p. 468)
ASAPS (2003). Statistics 2002.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 (www.surgery.org ). (pp. 432-433, 439)
Asch, S. E. (1946). Forming impres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 258-290. (p. 262)
Asch, S. E. (1955, November).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pp. 31-35. (pp. 213-214, 229, 230)
Asendorpf, J. B. (1987). Videotape re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and cognitions related to shy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541-549. (p. 584)
Ash, R. (1999). The top 10 of everything 2000 . New York: DK Publishing. (p. 382)
Asher, J. (1987, April). Born to be shy? Psychology Today , pp. 56-64. (p. 382)
Aspinwall, L. G., & Taylor, S. E. (1997). A stitch in time: Self-regulation and proactive cop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417-436. (p. 590)
Associated Press (1995, September 25). Blacks are given tougher sentences, analysis shows. Grand Rapids Press, p. A3. (p. 621)
Astin, A. W. (1972). Four critical years .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 265)
Astin, A. W., Green, K. C., Korn, W. S., & Schalit, M. (1987). The American freshman: National norms for Fall 1987 .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CLA. (b )(pp. 197, 341)
Augoustinos, M., & Innes, J. M. (1990). Towards an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social schema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29, 213-231. (p. 14)
Averill, J. R. (1983). Studies on anger and aggress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1145-1160. (p. 387)
Axelrod, R., & Dion, D. (1988). 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242, 1385-1390. (p. 559)
Axsom, D. (1989).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behavior change in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234-252. (p. 592)
Axsom, D., & Cooper, J. (1985).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psychotherapy: The role of effort justification in inducing weight lo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149-160. (p. 592)
Axsom, D., Yates, S., & Chaiken, S. (1987). Audience response as a heuristic cue in persua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 30-40. (p. 269)
Ayres, I. (1991). Fair driving: Gender and race discrimination in retail car negotiations. Harvard Law Review, 104, 817-872. (p. 337)
Ayres, I., & Nalebuff, B. (2003, April 15). Charity begins at Schedule A.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 ). (p. 513)
Azrin, N. H. (1967, May). Pain and aggression. Psychology Today, pp. 27-33. (p. 393)
Babad, E., Bernieri, F., & Rosenthal, R. (1991). Students as judges of teachers'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8, 211-234. (p. 123)
Babad, E., Hills, M., & O'Driscoll, M. (1992). Factors influencing wishful thinking and predictions of election outcom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3, 461-476. (p. 72)
Bachman, J. G., Johnston, L. D., O'Malley, P. M., & Humphrey, R. N. (1988). Explaining the recent decline in marijuana use: Differentiating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risks, disapproval, and general lifestyle factor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9, 92-112. (p. 252)
Bachman, J. G., & O'Malley, P. M. (1977). Self-esteem in young me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365-380. (p. 24)
Bailey, J. M., Gaulin, S., Agyei, Y., & Gladue, B. A. (1994). Effects of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on evolutionary relevant aspects of human mat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1081-1093. (p. 188)
Bailey, J. M., Kirk, K. M., Zhu, G., Dunne, M. P., & Martin, N. G. (2000). D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osexuality represent genetic or environmentally contingent strategies? Evidence from the Australian Twin Regist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8, 537-545. (p. 188)
Baize, H. R., Jr., & Schroeder, J. E. (1995). Personality and mate selection in personal ads: Evolutionary preferences in a public mate selection process.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0, 517-536. (p. 434)
Baker, L. A., & Emery, R. E. (1993). When every relationship is above average: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divorce at the time of marriage.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7, 439-450. (p. 71)
Baldwin, M. W., Keelan, J. P. R., Fehr, B., Enns, V., Koh-Rangarajoo, E. (1996). Social-cogni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Availa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eff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94-109. (p. 459)
Banaji, M. R. & Bhaskar, R. (2000). Implicit stereotypes and memory: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of social beliefs. In D. L. Schacter & E. Scarry (Eds.), Memory, brain, and belief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37)
Bandura, A. (1979). The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Mechanisms of aggression. In H. Toch (Ed.), Psychology of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p. 391, 392)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 New York: Freeman. (pp. 57, 390, 392)
Bandura, A. (2000).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52, 1-26. (p. 57)
Bandura, A., Pastorelli, C., Barbaranelli, C., & Caprara, G. V. (1999). Self-efficacy pathways to childhood de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258-269. (p. 57)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75-582. (p. 390)
Bandura, A., & Walters, R. H. (1959). Adolescent aggression . New York: Ronald Press. (p. 391)
Bandura, A., & Walters, R. H. (1963). Social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 406)
Banfield, S. & McCabe, M. P. (2001). Extra relationship involvement among women: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men?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0, 119-142. (p. 398)
Banks, S. M., Salovey, P., Greener, S., Rothman, A. J., Moyer, A., Beauvais, J., & Epel, E. (1995).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ing on mammography utilization. Health Psychology, 14, 178-184. (p. 258)
Barash, D. (1979). The whisperings within .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382, 487)
Barash, D. P. (2003, November 7). Unreason's seductive charm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www.chronicle.com/free/v50/i11/11b00601.htm ). (p. 171)
Barber, B. M., & Odean, T. (2001). The Internet and the invest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 41-54. (p. 117)
Barber, N. (200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sex ratios and teen pregnancy rates: A replicat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4, 327-333. (pp. 188-189)
Bargh, J. A. (1994). The four horsemen of automaticity: Awareness, intention, efficiency, and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 In R. S. Wyer & T.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2nd ed. (Vol. 1). Hillsdale, NJ: Erlbaum. (p. 107)
Bargh, J. A. (1997). The automaticity of everyday life. In R. S. Wyer, Jr. (Ed.), Advances in Social Cognition, Vol. 10. Mahwah, NJ: Erlbaum. (pp. 107, 108)
Bargh, J. A., & Chartrand, T. L. (1999). The unbearable automaticity of 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462-479. (pp. 105, 106-107, 337)
Bargh, J. A., McKenna, K. Y. A., & Fitzsimons, G. M. (2002). Can you see the real me? Activation and expression of the“true self”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33-48. (p. 466)
Bargh, J. A., & Raymond, P. (1995). The naive misuse of power: Nonconscious sources of sexual harassmen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1, 85-96. (p. 85)
Barnes, R. D., Ickes, W., & Kidd, R. F. (1979). Effects of the perceived intentionality and stability of another's dependency on helping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5, 367-372. (p. 485)
Barnett, M. A., King, L. M., Howard, J. A., & Melton, E. M. (1980). Experiencing negative affect about self or other: Effects on helping behavior in children and adul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 (p. 482)
Barnett, P. A., & Gotlib, I. H. (1988).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depression: Distinguishing among antecedents, concomitants, and consequ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4 , 97-126. (p. 579)
Baron, J., & Hershey, J. C. (1988). Outcome bias in decision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569-579. (p. 368)
Baron, J., & Miller, J. G. (2000). Limiting the scope of moral obligations to help: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1, 703-725. (p. 485)
Baron, L., & Straus, M. A. (1984). Sexual stratification, pornography, and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N. M. Malamuth & E. Donnerstein (Eds.), Pornography and sexual aggression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399-400)
Baron, R. A. (1977). Human aggression . New York: Plenum Press. (p. 417)
Baron, R. S. (1986). Distraction-conflict theory: Progress and problems.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p. 291)
Baron, R. S. (2000). Arousal, capacity, and intense indoctrin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238-254. (pp. 275-276)
Baron, R. S., David, J. P., Inman, M., & Brunsman, B. M. (1997). Why listeners hear less than they are told: Attentional load and the teller-listener extremity e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826-838. (p. 94)
Baron, R. S., Hoppe, S. I., Kao, C. F., Brunsman, B., Linneweh, B., & Rogers, D. (1996). Social corroboration and opinion extrem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2, 537-560. (p. 309)
Baron, R. S., Kerr, N. L., & Miller, N. (1992). Group process, group decision, group action .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p. 389)
Barongan, C., & Hall, G. C. N. (1995). The influence of misogynous rap music on sexual aggression against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 195-207. (p. 407)
Barrett, L. F., Lane, R. D., Sechrest, L., Schwartz, G. E. (2000).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awarenes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 1027-1035. (p. 185)
Barry, D. (1995, January). Bored Stiff. Funny Times, p. 5. (p. 189)
Barry, D. (1998). Dave Barry Turns 50. New York: Crown. (p. 70)
Bar-Tal, D. (1982).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helping behavior: A cognitive-learning approach. Development Review, 2 (2), 101-124. (p. 481)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226-244. (p. 460)
Bartholomew, R. E., & Goode, E. (2000, May/June). Mass delusions and hysterias: Highlights from the past millennium. Skeptical Inquirer, pp. 20-28. (p. 212)
Barzun, J. (1975). Simple and direct.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173-174. (p. 164)
Bass, E., & Davis, L. (1994). The courage to heal . New York: Harper & Row. (p. 572)
Bassili, J. N. (2003). The minority slowness effect: Subtle inhibitions in the expression of views not shared by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261-276. (p. 322)
Batson, C. D. (1983). Sociobiology and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An alternative 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1380-1385. (p. 513)
Batson, C. D. (1999a). Behind the scenes. In D. G. Myers, Social psychology,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 492)
Batson, C. D. (1999b). Addressing the altruism question experimentally. Paper presented at a Templeton Foundation/Fetzer Institute Symposium on Empathy, Altruism, and Agape, Cambridge, MA. (p. 492)
Batson, C. D. (2001). Addressing the altruism question experimentally. In S. G. Post, L. B. Underwood, J. P. Schloss, & W. B. Hurlbut (Eds.), Altruism and altruistic lov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dialogu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90, 492)
Batson, C. D., Ahmad, N., & Stocks, E. L. (2004). Benefits and liabilities of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In A. G. Miller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ood and evil.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p. 493)
Batson, C. D., Ahmad, N., Yin, J., Bedell, S. J., Johnson, J. W., Templin, C. M., & Whiteside, A. (1999). Two threats to the common good: Self-interested egoism and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3-16. (p. 493)
Batson, C. D., Bolen, M. H., Cross, J. A., & Neuringer-Benefiel, H. E. (1986). Where is the altruism in the altruistic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212-220. (p. 490)
Batson, C. D., Cochran, P. J., Biederman, M. F., Blosser, J. L., 8yan, M. J., & Vogt, B. (1978). Failure to help when in a hurry: Callousness or confli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 97-101. (p. 504)
Batson, C. D., Coke, J. S., Jasnoski, M. L., & Hanson, M. (1978). Buying kindness: Effect of an extrinsic incentive for helping on perceived altru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 86-91. (pp. 514-515)
Batson, C. D., Duncan, B. D., Ackerman, P., Buckley, T., & Birch, K. (1981). Is empathic emotion a source of altruist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 290-302. (p. 491)
Batson, C. D., Fultz, J., & Schoenrade, P. A. (1987). Distress and empathy: Two qualitatively distinct vicarious emotions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5, 19-40. (p. 491)
Batson, C. D., Harris, A. C., McCaul, K. D., Davis, M., & Schmidt, T. (1979). Compassion or compliance: Alternative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s for one's helping behavior.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 42, 405-409. (pp. 514-515)
Batson, C. D., Klein, T. R., Highberger, L., & Shaw, L. L. (1997). Immorality from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When compassion and justice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1042-1058. (p. 491)
Batson, C. D., Kobrynowicz, D., Dinnerstein, J. L., Kampf, H. C., & Wilson, A. D. (1997). In a very different voice: Unmasking moral hypocris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335-1348. (p. 135)
Batson, C. D., Lishner, D. A., Carpenter, A., Dulin, L., Harjusola-Webb, S., Stocks, E. L., Gale, S., Hassan, O., & Sampat, B. (2003).“. . .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Does imagining yourself in the other's place stimulate mor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1190-1201. (p. 513)
Batson, C. D., & Moran, T. (1999).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in a prisoner's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 909-924. (p. 557)
Batson, C. D., Sager, K., Garst, E., Kang, M., Rubchinsky, K., & Dawson, K. (1997). Is empathy-induced helping due to self-other merg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495-509. (p. 493)
Batson, C. D., Schoenrade, P., & Ventis, W. L. (1993).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46)
Batson, C. D., Sympson, S. C., Hindman, J. L., Decruz, P., Todd, R. M., Jennings, G., & Burris, C. T. (1996).“I'be been there, too”: Effect on empathy of prior experience with a ne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 474-482. (p. 184)
Batson, C. D., & Thompson, E. R. (2001). Why don't moral people act morally? Motivational consider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54-57. (p. 135)
Batson, C. D., Thompson, E. R., & Chen, H. (2002). Moral hypocrisy: Addressing some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330-339. (p. 135)
Batson, C. D., Thompson, E. R., Seuferling, G., Whitney, H., & Strongman, J. A. (1999). Moral hypocrisy: Appearing moral to oneself without being s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525-537. (p. 139)
Batson, C. D., & Ventis, W. L. (1982).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46)
Batson, C. D., & Weeks, J. L. (1996). Mood effects of unsuccessful helping: Another test of the 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 148-157. (p. 492)
Baumann, D. J., Cialdini, R. B., & Kenrick, D. T. (1981). Altruism as hedonism: Helping and self-gratification as equivalent respon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0, 1039-1046. (p. 481)
Baumann, L. J., & Leventhal, H. (1985).“I can tell when my blood pressure is up, can't I?”Health Psychology, 4, 203-218. (p. 585)
Baumeister, R. F. (1991). Meanings of life . New York: Guilford. (p. 469)
Baumeister, R. F., & Bratslavsky, E. (1999). Passion, intimacy, and time: Passionate love as a function of change in intimac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 49-67. (p. 463)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Finkenauer, C., & Vohs, D. K. (2001). Bad is stronger than good.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5, 323-370. (pp. 446, 447)
Baumeister, R. F., Bratslavsky, E., Muraven, M., & Tice, D. M.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1252-1265. (p. 57)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 (1), 1-44. (pp. 23, 62, 64, 65)
Baumeister, R. F., Catanese, K. R., & Vohs, K. D. (2001). Is there a gender difference in strength of sex drive? Theoretical views,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and a review of relevant evid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5, 242-273. (pp. 188, 446)
Baumeister, R. F., Catanese, K. R., & Wallace, H. M. (2002). Conquest by force: A narcissistic reactance theory of rape and sexual coerc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6, 92-135. (p. 239)
Baumeister, R. F., Chesner, S. P., Senders, P. S., & Tice, D. M. (1988). Who's in charge here? Group leaders do lend help in emergenc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4, 17-22. (p. 89)
Baumeister, R. F., & Exline, J. J. (2000). Self-control, morality, and human strengt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 29-42. (p. 57)
Baumeister, R. F., & Ilko, S. A. (1995). Shallow gratitude: Public and private acknowledgement of external help in accounts of succes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6, 191-209. (p. 78)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 497-529. (p. 423)
Baumeister, R. F., Muraven, M., & Tice, D. M. (2000). Ego depletion: A resource model of volition, self-regulation, and controlled processing. Social Cognition, 18, 130-150. (p. 57)
Baumeister, R. F., & Scher, S. J. (1988). Self-defeating behavior patterns among normal individuals: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ommon self-destructive tend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4, 3-22. (p. 78)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1996).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 (p. 65)
Baumeister, R. F., Twenge, J. M., & Nuss, C. K. (2002).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cognitive processes: Anticipated aloneness reduces intelligent though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817-827. (p. 424)
Baumeister, R. F., & Vohs, K. (in press). Sexual economics: Sex as female resource for social exchange in heterosexual interac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pp. 188-189)
Baumeister, R. F., & Wotman, S. R. (1992). Breaking hearts: The two sides of unrequited love . New York: Guilford. (p. 469)
Baumgardner, A. H., & Brownlee, E. A. (1987). Strategic failure in social interaction: Evidence for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25-535. (p. 79)
Baumgardner, A. H., Kaufman, C. M., & Levy, P. E. (1989). Regulating affect interpersonally: When low esteem leads to greater enhanc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907-921. (p. 66)
Baumhart, R. (1968). An honest profit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 70)
Baxter, T. L., & Goldberg, L. R. (1987).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sistency underlying trait attributions to oneself and another: An extension of the actor-observer effec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3, 437-447. (p. 94)
Bayer, E. (1929). Beitrage zur zeikomponenten theorie des hungers. Zeitschrift fur Psychologie, 112, 1-54. (p. 287)
Bazerman, M. H. (1986, June). Why negotiations go wrong. Psychology Today, pp. 54-58. (p. 558)
Bazerman, M. H. (1990). 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 2nd ed. New York: Wiley. (p. 558)
Beaman, A. L., Barnes, P. J., Klentz, B., & McQuirk, B. (1978). Increasing helping rate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aching pay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 406-411. (p. 516)
Beaman, A. L., & Klentz, B. (1983). The suppose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bias against supporter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A meta-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9, 544-550. (p. 441)
Beaman, A. L., Klentz, B., Diener, E., & Svanum, S. (1979). Self-awareness and transgression in children: Two field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 1835-1846. (p. 302)
Bearman, P. S., & Brueckner, H. (2001). Promising the future: Virginity pledges and first intercour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859-912. (p. 233)
Beauregard, K. S., & Dunning, D. (1998). Turning up the contrast: Self-enhancement motives prompt egocentric contrast effects in social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606-621. (p. 74)
Beauvois, J. L., & Dubois, N. (1988). The norm of internality in the explanation of psychological ev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299-316. (p. 96)
Beck, A. J., Kline, S. A., & Greenfeld, L. A. (1988). Survey of youth in custody, 1987.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p. 391)
Beck, A. T., & Young, J. E. (1978, September). College blues. Psychology Today, pp. 80-92. (p. 582)
Bell, B. E., & Loftus, E. F. (1988). Degree of detail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mock juror judg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 1171-1192. (p. 608)
Bell, B. E., & Loftus, E. F. (1989). Trivial persuasion in the courtroom: The power of (a few) minor detai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669-679. (p. 608)
Bell, P. A. (1980). Effects of heat, noise, and provocation on retaliatory evaluative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0, 97-100. (p. 394)
Bellah, R. N. (1995/1996, Winter). Community properly understood: A defense of‘democratic communitarianism.’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pp. 49-54. (p. 242)
Belson, W. A. (1978). Television violence and the adolescent boy . Westmead, England: Saxon House, Teakfield Ltd. (pp. 404-405)
Bem, D. J. (1972). Self-perception theory.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Vol. 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56, 161)
Bem, D. J., & McConnell, H. K. (1970). Testing the self-perception explanation of dissonance phenomena: On the salience of premanipulation attitu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 23-31. (p. 103)
Bennett, R. (1991, February). Pornography and extrafamilial child sexual abuse: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Sexually Exploited Child Unit. (p. 400)
Bennis, W. (1984). Transformative power and leadership. In T. J. Sergiovani & J. E. Corbally (Eds.),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 325)
Benson, P. L., Dehority, J., Garman, L., Hanson, E., Hochschwender, M., Lebold, C., Rohr, R., & Sullivan, J. (1980). Intrapersonal correlates of nonspontaneous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0, 87-95. (p. 508)
Benson, P. L., Karabenick, S. A., & Lerner, R. M. (1976). Pretty pleases: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race, and sex on receiving hel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2, 409-415. (p. 505)
Benvenisti, M. (1988, October 16). Growing up in Jerusalem.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pp. 34-37. (pp. 352-353)
Ben-Zeev, T., Fein, S., & Inzlicht, M. (2004). Arousal and stereotype threa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 (p. 373)
Berenbaum, S. A., & Hines, M. (1992). Early androgens are related to childhood sex-typed toy preferenc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203-206. (p. 192)
Berg, J. H. (1984). Development of friendship between roomm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346-356. (pp. 452, 460)
Berg, J. H. (1987). Responsiveness and self-disclosure. In V. J. Derlega & J. H. Berg (Eds.), Self-disclosure: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 New York: Plenum. (p. 462)
Berg, J. H., & McQuinn, R. D. (1986). Attraction and exchange in continuing and noncontinuing dating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 942-952. (pp. 452, 464)
Berg, J. H., & McQuinn, R. D. (1988). Loneliness and aspects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 582)
Berg, J. H., & Peplau, L. A. (1982). Loneliness: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disclosure and androgyn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8, 624-630. (p. 462)
Berglas, S., & Jones, E. E. (1978). Drug choice as a self-handicapping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noncontingent suc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405-417. (p. 78)
Berkman, L. F. (1995). The role of social relations in health promo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7, 245-254. (p. 597)
Berkowitz, L. (1954). Group standards, cohesiveness, and productivity. Human Relations, 7, 509-519. (p. 231)
Berkowitz, L. (1968, September). Impulse, aggression and the gun. Psychology Today , pp. 18-22. (p. 396)
Berkowitz, L. (1972). Frustrations, comparisons, and other sources of emotional arousal as contributors to social unres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8, 77-91. (a ) (p. 388)
Berkowitz, L. (1972). Social norms, feelings,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helping and altruism.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 ) (p. 485)
Berkowitz, L. (1978).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21, 691-708. (p. 387)
Berkowitz, L. (1981, June). How guns control us. Psychology Today, pp. 11-12. (p. 396)
Berkowitz, L. (1983). Aversively stimulated aggression: Some parallels and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with animals and huma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1135-1144. (p. 394)
Berkowitz, L. (1984). Some effects of thoughts on anti- and prosocial influences of media events: A cognitive-neoassociat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410-427. (p. 407)
Berkowitz, L. (1987). Mood, self-awareness, and willingness to hel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721-729. (p. 483)
Berkowitz, L. (1989).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 59-73. (pp. 387, 394)
Berkowitz, L. (1995). A career on aggression. In G. G. Brannigan & M. R. Merrens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ists: Research adventures . New York: McGraw-Hill. (p. 396)
Berkowitz, L. (1998). Affective aggression: The role of stress, pain, and negative affect. In R. G. Geen & E. Donnerstein (Eds.), Human aggression: Theories,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 394)
Berkowitz, L., & Geen, R. G. (1966). Film violence and the cue properties of available targe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 525-530. (p. 406)
Berkowitz, L., & LePage, A. (1967). Weapons as aggression-eliciting stimuli.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 202-207. (p. 396)
Bernard, J. (1976). Sex differences: An overview . New York: MSS Modular Publications. (p. 182)
Bernard, M. M., Maio, G. R., & Olson, J. M. (2003). The vulnerability of values to attack: Inoculation of values and value-relevant 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63-75. (p. 279)
Berndsen, M., Spears, R., & van der Plight, J. (1996). Illusory correlation and attitude-based vested interes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247-264. (p. 117)
Berndsen, M., Spears, R., van der Plight, J., & McGarty, C. (2002). Illusory correlation and stereotype formation: Making sense of group differences and cognitive biases. In C. McGarty, V. Y. Yzerbyt, & R. Spears (Eds.), Stereotypes as explanations: The formation of meaningful beliefs about social group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64)
Bernhardt, P. C. (1997). Influences of serotonin and testosterone in aggression and dominance: Convergence with social psycholog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y, 6, 44-48. (p. 385)
Bernhardt, P. C., Dabbs, J. M., Jr., Fielden, J. A., & Lutter, C. D. (1998). Testosterone changes during vicarious experiences of winning and losing among fans at sporting events.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65, 59-62. (p. 385)
Bernieri, F. J., Davis, J. M., Rosenthal, R., & others. (1994, June). Interactional synchrony and rapport: Measuring synchrony in displays devoid of sound and facial affect.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 303-311. (p. 158)
Berry, D. S., & Zebrowitz-McArthur, L. (1988). What's in a face: Facial maturity and the attribution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4, 23-33. (p. 619)
Berry, J. W., & Kalin, R. (1995). Multicultural and ethnic attitudes in Canada: An overview of the 1991 national survey.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27, 301-320. (pp. 334-335)
Berscheid, E. (1981). An over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some comments upon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knowledge of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W. Lucker, K. Ribbens, & J. A. McNamera (Eds.), Logical aspects of facial form (craniofacial growth series)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435-436)
Berscheid, E. (1985).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In G. Lindzey & E.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600)
Berscheid, E. (1999). The greening of relationship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 260-266. (p. 93)
Berscheid, E., Boye, D., & Walster (Hatfield), E. (1968). Retaliation as a means of restoring equ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 370-376. (p. 146)
Berscheid, E., Dion, K., Walster (Hatfield), E., & Walster, G. W. (1971).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dating choice: A test of the matching hypothe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 173-189. (pp. 432, 433)
Berscheid, E., Graziano, W., Monson, T., & Dermer, M. (1976). Outcome dependency: Attention, attribution, and att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 978-989. (p. 427)
Berscheid, E., & Peplau, L. A. (1983).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relationships. In Kelley, H. H., Berscheid, E., Christensen, A., Harvey, J. H., Huston, T. L., Levinger, G., McClintock, E., Peplau, L. A. & Peterson, D. R. (Eds.),……
如需更多參考文獻,請登陸本公司網站www.ncc-pub.com下載。